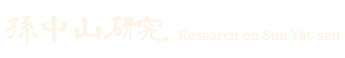中山公園簡介
引言
2004年,陳守仁博士透過聯泰國際團際集團有限公司捐款港幣一百萬元支持香港浸會大學發展。2009年,浸會大學與聯泰國際達成協議,以2004年之捐款設立“孫中山研究基金”,基金每年衍生之利息收入,將用作推動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題之學術活動、研究計劃及出版項目。其後陳博士亦透過陳守仁基金會及孫中山文教福利會於2012及2014年再額外注資超過一百萬元,加上政府配對補助金額,“孫中山研究基金”已擁有相當可觀的款項,長期支持大學有關研究。因此,身為是項研究主辦單位的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從事對孫中山先生的研究,其成果亦推動了本地對孫中山的興趣和認識。12016年,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全球各地亦將舉行大型的紀念活動,浸會大學歷史系亦藉此機會,開展對全球中山公園之研究,希望為孫中山研究開展新的路徑。中山公園與各地華人歷史息息相關,希望這個資料庫的開放,能引發大眾的興趣。公園是休憩文化的載體,為廣大市民提供公共活動的空間,但其構建、規劃往往反映種種人文關懷以至政治意涵。是故中山公園矗立於世界不同華人地區,確實體現到了孫中山先生作為一位民族英雄在海內外華人社群中的精神感召力量。休憩場所如何糅合家國情懷,以及對英雄人物致敬背後的種種社會和政治考慮,往往耐人尋味,值得一探。
顧名思義,中山公園是以孫中山先生(1866-1925)命名的公園,具有紀念孫中山先生的目的與意義。根據目前能掌握的資料,全球中山公園現有106個,分佈兩岸四地(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雖然不能說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山公園,但設立中山公園的確是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其中一種重要途徑。這個資料庫以中山公園為主題,目的是讓參瀏覽者瞭解各地中山公園的歷史、設施及特色。資料庫以圖片資料為主,配以文字解說,盡可能介紹位於世界不同角落的中山公園。
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1925年以後不少已建及新建的公園,相繼以“中山”命名,據估計民國時期共有超過300個。2中山公園不但是全球最多以相同名稱命名的公園,亦承載了海內外華人對孫中山先生的情感與敬仰。中山公園能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意識形態下存在,不單發揮提供休憩的功能,亦同時展現民眾對孫中山先生的紀念,很值得進一步研究。可惜,正如李恭忠所指,關於孫中山先生的研究是“重身前而輕死後”,3現時學界對於各種紀念孫中山先生的設施與活動的注意不多,中山公園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場所亦未有太充分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目的是將中山公園放於1925年至今的歷史脈絡中,審視中山公園把紀念與休閒結合的政治功能。
關於民國時期中山公園的研究
誠如李恭忠所指,現時學界對孫中山先生的研究是“重身前而輕死後”,關於中山公園的研究並不多,且以介紹性的著作為主。廈門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山公園博覽》是唯一對中山公園作全面研究的著作,其著者孫吉龍、李建載親身考察了86個中山公園,4並收集了不少關於這些公園的資料,是目前中山公園研究的資料較齊備的專書。《中山公園博覽》所收錄的資料具有兩個特質,一為在地性,二為全面性。前者是歸功於作者實地的考察,大部份中山公園沒有太多已出版的文字資料,這些公園的歷史與發展大多紀載在公園的碑文和簡介冊子中。因此在地的考察能收集到豐富的資料,同時亦可以更清楚瞭解公園的設施與設計。此外,《中山公園博覽》所記錄的資料十分全面,截止於2010年,收集了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澳門、加拿大、美國、新加坡及日本八地的中山公園,雖然當中不少有誤,卻是非常全面的研究。5
孫吉龍、林建載指出中山公園是中國現代歷史的“特定產物”,是始於民國期間的一場民間廣泛參與的建設中山公園運動下的發展。二氏又言各個公園的歷史淵源、特色、園林佈局、建築特色皆具有研究意義,並指出許多中山公園是“當年革命活動和集會的重要場所”及“還搭建了與海外華僑、台灣同胞的聯繫橋樑”。6與此同時,中國公園協會曾以《中山公園﹕昨天、今天、明天》為題作網上展覽,其前言亦指中山公園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命名的紀念性公園,是近代特定的“歷史產物”。7
中山公園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特定產物有三種的條件,一在於中國出現公園,二在於以公園作為公共空間及紀念地,三在於孫中山先生成為“紀念對象”。公園在中國是新的概念,安懷起於其《中國園林史》中指出古典園林具有“明顯的私人佔有性”,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公園的出現標誌了中國園林由古典發展至現代園林。8可是以“公私”來界定中國對公園的定義有一定的局限,因為1860年代出現在不同租界的公園並不向華人開放,卻被視之為公園。相反,唐學山、酈芯若認為中國園林種類中風景名勝園林和寺廟園林具有公共遊覽性質,9卻沒有被視為公園。不論如何,在1868年上海出現的首個公園即黃浦公園之前,中國並沒有“公園”或“私園”的概念,只有“園林”。奇怪的是,在清末時期清政府並沒有對公園加以注意,反而在民國時期卻出現大量公園。湖北省建設廳所編的《湖北建設志》指“民國時期,由於城市性質的變化,城市居民多階層的產生,生活情趣及遊樂動向亦有所變化。在私家宅園、府署庭園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市民公園相繼誕生”。10 以“城市性質的變化”解釋公園的出現忽視了民國以前中國城市的發展,斯波義信考察中國的都市發展時指雖然傳統中國是未普遍工業化,人口大多是以農業為生,但不能說中國社會沒有城市。11 同樣地,即使民國時期的城市性質真的出現變化,其產生的階層、生活情趣及遊樂動向是否能出現與晚清截然不同的變化也是疑問。單看大型城市的變化或會較明顯,可是在民國時期即使是經濟發展較慢而其城市階層變化較輕微的鄉鎮都活躍於建設公園。由此可以進一步說,當中國出現“公園”的概念後,並沒有立即湧現公園,反而在民國時期不少的城市都建設公園,而推動這個變化的力量並不在於經濟或城市的變化。
為了解釋為何民國出現大量的公園,我們必須把目光放在建設公園背後的政治力量。興建公園並不是簡單的事,政府批准與否、從收地至興建背後的資金都涉及政治力量。若只視公園為遊樂休閒之空間,城市不一定需要公園,賭場、煙館、妓院等場所都能提供遊樂休閒的功能,何況這些場所早已存在。站在政府而言,公園提供的空間若沒有適當的控制,有可能成為反政府者集會、宣傳訊息的場所,對政權之不利甚至大於賭場、煙館、妓院。然而,我們應該如何解釋清廷沒有積極地建設公園,反而民國政府卻建設公園?關鍵在於政治文化的改變。
公園是一種公共空間,卻不是唯一一種公共空間。因此城市需要公共空間,卻不一定需要公園。若因沒有公園便指該城市沒有或不需要公共空間,又或者因公園的出現便指該城市出現公共空間或對公共空間的需要,是不真實的。民國以前,對公園的需要不大是因為已經存在其他的公共空間,而且這些空間是符合清廷的統治。舉例而言,廟是傳統中國的公共空間,甘滿堂考察福建的村落,指出村廟是宗教活動中心的同時,也是日常交住的活動中心,是社區的標誌性建築。12 趙世瑜指出鄉村與城市廟會的形式有不同,可是不論城市還是鄉村,社區都需要透過對神的崇拜來加強其身份及組織。13 他同時亦指出民眾的廟會及其他祭神儀式活動具有商業貿易、休閒娛樂以及社區整合的功能,神誕、廟會成為民眾的節日,信仰成為民眾休閒娛樂的合理合法的借口。14 廟宇是提供合法娛樂休閒的公共空間,因為是國家被容許及規範的,蔡志祥考察明清有關祭祀及宗教信仰的法律下國家的規範在城隍和厲鬼祭祀中表現,並認為城隍是國家對地方的支配、對人民的教化工具的同時,鄉民可以在國家認可下有效地結合儀式及日常生活。15民眾對休閒娛樂以至公共空間的需求透過宗教活動被滿足,政府亦樂於利用對信仰的規範來限制民眾的公共空間。因此,公園的出現並不代表民眾利用宗教滿足公共空間及休閒娛樂的情況立即消失,而是政治文化的改變,使民國政府對於控制公共空間的規範亦出現改變。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為我們對民國時期政治文化的改變提供了啟發,她提出何為中國人的問題,又徵引華琛(James L. Watson)的研究,認為中國人的身份是通過參與不同儀式建立的,可是在民國時期的政治文化改變,民國的正統性是建立在民國是一現代國家上,新的中國人身份來自於參與現代的國家儀式而不是傳統儀式。16 在這觀點上,公園的出現能代表了“西方”、“現代化”的城市發展,有利於建構民國政府的正統性。民國的現代國家儀式亦不能透過廟宇等的傳統公共空間執行,而需要公園等新式的公共空間執行國家儀式及政府容許的休閒娛樂。是以公園作為政府容許的公共空間出現在城市建設中,而公園的功能和作用亦隨之變得重要。實際來說,民國政府建立後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不適合民國作為現代國家的公共空間,例如代表了皇權的宮殿、官衙以至作為“迷信”的廟宇。James A. Leith分析法國革命者如何利用紀念物、廣場、公共建築建立新秩序,並指出革命後需要經過去除舊秩序的合法性及神聖性,以及建立新秩序的合法性、神聖性的過程。Leith認為革命者透過拆除現有的紀念物以除去舊政權的象徵、符號,讓公眾體驗對舊秩序的拒絕,同時轉化舊建築物、興建新建築物以展示革命及新政權的卓越。17 借用Leith的看法,民國利用轉化舊宮殿、園林為公園、興建公園以建立新秩序的合法性、神聖性,因為公園符合民國的“新秩序”,而公園有助政府宣傳民國的合法統治,亦合適舉行民國的國家儀式。
公園作為公共空間對政府並不一定有利,雖然民眾可以使用公園作休閒娛樂之用,可是公園作為向公眾開放的空間,同樣可以成為對社會、甚至國家不利的溫床。公園亦依賴政權的規範,除了透過守則、管理把對政權不利的人和活動排除外,把公園設計成紀念地是最有效的方法。在公園建立“紀念物”,Hazel Conway與David Lambert認為可以展示民眾驕傲(Civic Pride)、愛國主義等,同時可以宣傳極權主義(Authoritarism),運用權力創造單一話語、壓制反社會行為的空間。18 透過紀念對國家有貢獻之人及事件,民眾感受到國家的存在。而作為紀念物,按Leith關於大型建築如何傳遞訊息的看法,不但浮雕、雕像、文字可以向公眾傳遞訊息,其風格、大小、位置亦可。因此公園中每一個部分只要經過設計,都可以用作感染民眾。民眾進入公園至少可以感受到國家的偉大,特別是樹立對國家有貢獻之人及事件的紀念碑文,一方面使公眾對國家認可的歷史觀有更多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激發他們學習這些人與事件的精神,亦即國家希望民眾服從的品格。透過這些人與事,不論是國家光輝的歷史還是屈辱的歲月,都傳播了一種團結的力量,在同一個空間中的人都是國民,有同樣的歷史,有同樣的未來。在紀念物以外,政府也可以透過公園舉行的活動發揮類近作用,如弗‧阿•戈羅霍夫(В. А. РOPOXВ)與勒•布•倫茨合(Л. В. Л У Н Ц)所指,紀念公園是“主要用以開展政治思想教育,舉行大規模的紀念宣傳、組織集會”。19
公園作為紀念地能消除公園對政權統治的不利因素,而紀念的人與事必須符合國家的意識形態,使公園能成為教育民眾的空間,以宣傳符合國家利益的歷史敘述。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後,孫中山立即成為中國的國家英雄,更成為整個國家紀念的對象。孫中山先生生前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他雖然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但其對民初政局的影響力不大,唯他去世後的影響卻超越了其統治的廣東,成為全國認同的象徵符號。沈艾娣重視不同的儀式與符號如何建構新的中國人身份,孫中山先生在1925年成為國家的象徵符號,對孫中山先生的紀念有助整合國家不同的份子,推廣愛國主義,成為中國人認同的象徵。20 中山公園是紀念孫中山先生的空間,亦同時可以視為承載了孫中山的符號,宣傳官方意識形態、舉行符合國家規範的現代國家儀式的場所。
南京大學陳蘊茜對中山公園的研究最為重要,陳蘊茜對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有深入的見解,她分析了各種建構孫中山崇拜的途徑,包括不同的儀式、禮儀、空間,探討國民黨如何利用孫中山符號,向民眾宣傳其意識形態並建立正統性。陳蘊茜將目光放在中山公園上,她提出中山公園是國民黨把孫中山符號空間化的重要途徑,並透過對空間的研究了解中山公園的結構與紋理,從而探討建設中山公園背後的意義。陳氏的研究指出國民黨透過公園這公共空間向民眾傳輸孫中山符號,將孫中山崇拜空間化。21 她界定中山公園是“中山紀念空間”,歸納陳蘊茜對中山公園作為紀念空間的特色,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部份﹕
- 以“中山”命名
- 中山公園的空間定位
- 中山公園的空間象徵建構
- 中山公園作為民族主義象徵空間
就命名而言,陳蘊茜指“國民黨透過公園等公共空間的更名與命名,取得對孫中山符號的詮釋權,由此彰顯該黨具有繼承孫中山政治遺產的正當性與合法性”,22 而將原有公園名稱改為中山公園,是對原有空間意義的重構。在空間定位上,陳蘊茜注意到中山公園大多位於城市的中心,而新建的公園“多與縣政府、縣黨部相毗鄰,或距文廟、學宮不遠,並距中山路較近,在整個城市空間中占據突出的位置”,是以她認為中山公園並不是一般休閒性公園,而是在城市空間上有象徵意”,是“孫中山具有至高至尊領袖政治地位的物化體現”。23 至於空間象徵建構,是指公園的佈局、設計如何營造出孫中山崇拜的情景。例如改名的中山公園一般以增加建築來分割、重組空間,而加建的建築一般為“孫中山像、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紀念亭”。新建的中山公園,有具民族特色的正門、孫中山像與中山堂建成“中山公園象徵系統”,而三民主義語彙形成空間“三民主義化”。24民族主義象徵空間是針對公園內的活動,中山符號強化了民族主義情緒,公園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空間,如不少抗日集會都會在中山公園舉行。25
雖然陳蘊茜強調紀念空間以及國民黨背後的政治意圖,但她並沒有忽視民眾在紀念中的角色,作為接收者的民眾會被不同的因素影響,使國民黨的宣傳作用產生偏差,包括原有公園的建築及對公園的記憶使中山公園對孫中山先生的紀念性大減,而公園的管理及商業元素會阻礙了民眾對公園的使用及使公園的主題改變。她的研究另一方面亦對國民黨建設公園的過程有很大的貢獻,她發現《中央日報》並沒有關於國民黨中央倡建中山公園的文件和命令,反映地方在建設中山公園時的角色並不被動。此外,她指出很多情況下地方雖然財力有限,但仍然透過動員社會力量支持建設。在建設的過程中,民間的捐款發揮一定的作用,可是在大部分地區仍是由當地政府及駐軍承擔建設工作及費用。陳蘊茜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但指出了中山公園在孫中山崇拜中的重要角色,亦在考察建設過程及公園空間設計時,提出政府與民間的角色,以及國民黨利用中山公園的空間把其意識形態傳播到民眾,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26 相似的研究還有李恭忠對中山陵作為政治符號的考察,他指出孫中山符號在近代中國的建構上的重要性,特別是建立在想像共同體上的近代國家,利用公共空間營造共同的歷史回憶和國民身份十分重要。他指孫中山先生的葬禮把孫中山先生塑造成新的民族偶像,於是孫中山先生成為“國”的象徵。而興建中山陵時,早期地方與中央之間的角力亦反映出參與各方不同的考慮,亦不見得參與者是真心敬仰孫中山先生。27 李恭忠的研究雖然是以中山陵為對象,而不是中山公園,可是作為政治符號空間化的例子,他對建設中山陵及在背後推動的政治力量的研究是很值得參考的。
此外,也有一些對於建設中山公園的政治力量以及個別中山公園作為紀念空間的研究。陳海忠指出雖然汕頭中山公園是由市民大會決定由中央公園改名中山公園,可是“關鍵是什麼政治勢力主持召開的市民大會,市民大會反映的往往是主持者的理念”28 ,相當明顯,陳海忠是從建園資金中觀察政府與商人的權力與意圖。他同時指出中山公園承載了某種符號的意義,公共空間是“黨化”的空間,市民在公園中賞景、遊樂、增長知識、擴大社交,甚至在公園集會,參與政治活動,“成為一個貌似西方意義上公平、平等的公共空間”的同時,官方實際上是利用中山公園表達其政治意圖。29 另一方面,胡俊修、李勇軍考察武漢中山公園的建園過程,指出中山公園的出現是“民眾生活所需與政府意願雙重動力推動的結果”。國民黨希望以公園作為“政治控制和生活教化的陣地”,以命名中山公園宣傳孫中山思想、國家思想,而公園的設計“將人們對孫中山先生的懷念敬仰之情而轉接到與之有延續關係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身上”,而民眾相反則視中山公園為“社會生活與展示自我的舞臺”。30 《中華民國專題史》則指出,民國所建設的公園中以中山公園之設置最為值得注意,同時認為中山公園帶有政治性色彩,在“塑造民族主義形象之外,帶給民眾的卻是另外一種戲謔及嘲諷的觀感”。31 劉媛、姜秉辰、楊宇辰指出北京中山公園是民國時期中國的“人才聚集地”,文人在公園集會使中山公園成為“重要教育空間”。32 胡俊修、黃琁指漢口中山公園是一城市空間讓市民增加公共生活經驗而培養市民的公共認同。33 馬樹華探討日治時期日本人在青島中山公園大量種植櫻花,展現日本的殖民地符號而如何內化成為青島人的一種城市習慣,進而變成了青島的文化空間。34 此外,部份中山公園由傳統園林轉化而成近化城市公園,私園與公共空間的轉化過程及社會意義,亦是研究中山公園的一大方向,張天潔與李澤指出漢口中山公園由私園的“自然意趣”轉化具有“公眾”與“健身”概念的現代公園。35 以上的研究令我們深思民眾在官方運用中山公園進行崇拜中的角色,官方在中山公園的建設、設計、管理上形成霸權,把不符合官方容許的意識形態者排除在外,但民眾總有他們自身的理解。
沒有爭議的是,中山公園是政治符號空間化的產物,當孫中山先生成為被紀念的對象時,便需要設計空間、場所作紀念地。能把對孫中山先生的紀念化成符號,進而設計並利用空間宣傳對該符號的崇拜,只有政權才有足夠的能力處理。陳恆明在《中華民國政治符號之研究》一書出,認為政治符號是一種政治力量的工具,他認為中華民國政治符號的內涵包括其繼承了歷代正統;立國正名象徵如國名、國旗、國歌、國花;立國基礎象徵即三民主義。陳恆明未有以孫中山先生作為獨立的政治符號作分析,但他在分析正名象徵和立國基礎的同時,卻不斷的使之與孫中山先生連繫,他這書本身便是孫中山崇拜的延續,特別是在1986年出版時仍然存在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其目標在於利用分析政治符號以加強中華民國的正統性。36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看孫中山崇拜,他生前並不是中國唯一的英雄或政治人物,但他逝世後民眾卻展示極其強烈的尊重,當中國民黨以孫中山先生繼承者的身份鞏固了其統治的正統性,並把孫中山符號注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中山公園不可能是沒有任何政治力量的介入而由民間自發而建,故中山公園的出現是國民黨,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運用孫中山符號鞏固統治,並把崇拜空間化的途徑。
關於1949年後國內中山公園的研究
蘇艷萍指“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不僅成為孫中山思想和政策的執行者,並對孫中山的革命遺跡與紀念場所進行保護與建設”。37 這個說法只說對了一半,絕大部份在民國時期建立起來的中山公園都在新中國時期遭到破壞或遭廢棄而消失,特別在文革時期,這樣的事實令我們難以相信在新中國成立早期中山公園得到了保護與建設。只有在特定地點的中山公園,如北京、武漢、上海等,得到較好的保護而保存下來。改革開放以後,各地中山公園的保護與建設得到重視,不少中山公園亦得以重建、發展。再者。踏入二十一世紀後,亦有不少新的中山公園得以建立,最新的一個還在興建當中。
關於中國大陸中山公園的發展,不少研究注意到個別中山公園的發展,中山公園被視為該城市重要的歷史回憶。園內的歷史建築物往往備受關注,因此北京中山公園的音樂堂、保衛和平牌坊,漢口中山公園的張公亭都已進入學者的視角。38 賀琳整理了漢口中山公園免費開放的過程,指出免費開放為公園帶來“崇高榮譽、美好遠景”。39 在這些研究中,中山公園的價值在於該公園在城市的歷史中佔有重要的意義,研究公園有助瞭解城市的歷史,記載其發展的脈絡及如何影響市民的生活,如免費開放的中山公園豐富了武漢市民的休閒活動。這些研究並沒有上述“空間”的概念,而是實在地描述公園的發展,關心的是個別城市的歷史如何從中山公園中被記憶起。王婧、陳志宏認為廈門中山公園可以“喚起觀者對老中山公園的記憶與情感”,從而重塑歷史記憶。40 以這樣的出發點,中山公園並不視為蘊含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元素,而是記載城市回憶的符號。誠如劉思佳指武漢中山公園的門樓“承載著城市的許多回憶”,而“明天的中山公園會如明天的武漢一樣,更加美好”,41 中山公園就是城市的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及回憶。
對於中山公園的紀念性,如雍東格所指出“(有些中山公園)內總體佈局不合理,文化品位較低,景觀性較差,基礎設施陳舊,游樂設施過多,這概不利於孫中山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傳承,也不能適應現代人生活的要求”。42 的確,大部份現存於中國大陸的中山公園都屬於上述的情況,公園的紀念性顯然不足。楊立新、劉堯、高陽、劉飛鴻對瀋陽中山公園的紀念性景觀進行評估,雖然指出紀念性景觀“體驗了人們對於精神情感表達的渴望與訴求”,卻沒有指出是對孫中山先生的紀念,更建議發掘地域文化而沒有建議增強中山元素。43 金海湘認為汕頭中山公園“現有紀念主軸在體量強度上與整個公園相比分量較輕”。44 這反映現存的中山公園普遍紀念性不足,當然不可忽視個別中山公園的情況,如武漢等中山公園的中山元素仍然是很強的。
國內中山公園的研究沒有往孫中山崇拜的意義進發,引起學者興趣的是,何以中國共產黨曾一度更易部份中山公園之名,又曾一度任由部份中山公園荒廢,但在文革以後中山公園又重新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對於上述的問題,Deborah S. Davis與王紹光為我們提供了一點的啟發,Davis認為在1949年以後城市的土地使用及空間分配需改變以符合新的經濟及政治的優先次序,對於宗教或儀式空間,或改變其用途及使之不再為公共空間,而當1980年代當局又放寬對公共空間的使用,包括公園。王紹光認為在1949年後私人時間被官方界定為工餘時間的休息,為的是回復體力而非個人娛樂,但在1980年代後私人時間、休閒娛樂又重新被鼓勵。45 洪長泰在《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中提出政治公園的研究,其對象是勞動人民文化宮。他認為勞動人民文化宮是重要的政治地標,而作為黨園,公園“主要是為共產黨服務”。46 天安門左右兩邊是勞動人民文化宮與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公園事實上亦可以引申為一政治公園,值得進一步研究。此外,華若璧(Rubie S. Watson)認為天安門廣場是由中國政府創造的國家空間,而在1949年以後天安門廣場發展了一段獨特的歷史,創造了不同群體對天安門廣場“持有非常不同的態度和形象意義”。47因此中山公園亦可視為國家空間,在官方以外,不同群體對中山公園的態度和形象意義亦非常重要。
關於台灣、港澳與國外中山公園的研究
現時位於台灣的中山公園有18個之多,全為1945年後才出現。儘管在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時,台灣民眾確曾舉行追悼會和有關紀念活動,但中山公園卻未有出現。趙勳達比較台灣官方《台灣日日新報》與民間《台灣民報》對孫中山逝世及台灣相應紀念活動的報導,指出台灣人很迅速地接收到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可是他們的處境非常尷尬,並不可以光明正大的進行悼念。48 進一步而言,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建立中山公園以資紀念是不可能的。
到了1945年後,台灣亦陸續出現了不少中山公園,陳蘊茜指出在台灣光復後,市政“中山化”,日據時期的公園改名為中山公園,“公園成為恢復主權及傳輸黨化意識形態的重要空間形式”。49 一方面中山公園代表了國民黨孫中山崇拜的持續,另一方面代表將台灣中華民國化的政策。陳毅嘉的碩士論文〈台灣地區中山公園研究〉從空間設計分析八個中山公園,並定意為四種不同的空間型態,分別是紀念性質、都市景觀性質、自然森林型態性質和歷史古蹟性質。50 參考陳蘊茜對中山公園作為紀念空間的定義,以“中山”命名便給予公園紀念性。陳毅嘉卻以空間的設計出發,認為不同中山公園有不同的性質,並不是劃一的具有強烈的紀念性。陳毅嘉的講法雖然忽視了中山公園在國民黨政治宣傳中的角色,卻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若只以公園設計而言,中山公園並不一定具有紀念性質。同時,陳毅嘉分析了八個中山公園,其中台中中山公園、台南中山公園、旗山中山公園已易名,這亦帶出近年來台灣的中山公園相繼易名的現象,但易名的情況相對少討論。普遍而言,對於台灣中山公園的研究一般著重於公園的管理及使用,也有以個別中山公園為對象的研究。51
關於港澳中山公園的研究討論成果相對較少。港澳兩地共有三個中山公園,其中兩個較新亦較偏遠而不佔重要的位置,因此研究確實不多,極其量是一些簡介性的書籍與文章,如《孫中山史蹟徑》中有〈中山紀念公園簡介〉一文,《香港中西區風物志》亦有對中山紀念公園的介紹。52 然而,位於屯門的中山公園,因為革命遺蹟紅樓在其旁邊的關係而得到較多注意,諸如羅香林的《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53 當然並不是針對中山公園的研究,但已是對中山公園早期的發展有重要的瞭解。至於殖民地政府對於孫中山崇拜的態度,民間與政府就建立中山公園的爭議,回歸前後政府對中山公園的態度等,似未有具體研究成果。
至於有關國外中山公園的研究,以溫哥華的中山公園為最多。Dongyang Liu的博士論文從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角度對作出研究。54 他指出中山公園代表了中國的存在,表示其在華人社群中的獨特意義。 這篇論文深入分析國外中山公園對華人的重要性,令中山公園的研究伸展到海外。可是溫哥華中山公園雖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卻不可能代表海外多個中山公園的整體價值,更遑論中山公園在國外所營造的紀念空間。此外,Maggie Keswick與Judy Oberlander亦出版了In a Chinese Garde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Dr. Sun Yat-Se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一書討論到溫哥華中山公園的建築特色。55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海外中山公園能否代表當地華人意識形態的問題,處理要非常小心。借用王維對日本中華街的研究,中華街應為以華人為主體,是華人進行經濟活動及生活的空間,可是日本的中華街卻變成以日本人進行經濟活動居多,遊客亦以日本人為主,是當地華僑按照日本人的想像而有意識地選擇中國文化符號而設計及打造的。56 因此,中山公園是為誰而設計及打造成為關鍵問題,對華裔或非華裔人士來說,孫中山先生似乎是大家都接受的人選。從此引伸,海外中山公園涉及的不但是海外華人對中國、孫中山先生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華人如何利用海外環境來締建身份認同。
同樣是海外中山公園,新加坡中山公園的情況較為特別,一方面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另一方面新加坡是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組成的國家,因此如何處理對孫中山先生的紀念是一重要的問題。張碧君對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出發點,張氏指出新加坡政府如何利用晚晴園建構國族、凝聚認同,利用孫中山先生與新加坡的關係展示新加坡與辛亥革命的連結,並把辛亥革命提昇為影響東南亞的重大事件,最終藉革命的情感及價值落戶新加坡而建構國族。新加坡中山公園作為晚晴園的延伸,我們是否可以利用建構國族的概念分析中山公園的建立及設計,值得深思。此外,張碧君指出晚晴園一直不被視為國家文物,然而在1990年代開始受到重視,原因在於新加坡定位的改變。57 張氏的研究對我們理解新加坡中山公園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中山公園對新加坡國族建構的作用、以及新加坡政府對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態度改變,皆成為值得深思的課題。
蘇艷萍指出全球孫中山紀念地是“全世界華人共同享用的紀念和休閒空間” 。58 因此既然我們視中山公園為中國現代歷史的產物,就不應忽視台灣、港澳、國外的中山公園的存在。孫中山先生是海內外華人共同敬仰的人物,各處的中山公園具有凝聚華人身份的功能,因此具有研究的意義。
中山公園研究的課題與路向
由以上可見,過往對於中山公園的研究集中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點較多。王冬青指出,“中山公園有它特殊的歷史背景、演變過程與內涵特質,不同階段的中山公園發展被賦予不同時代價值和意義,反映着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同時又說﹕“中山公園的地位在城市中是其他公園無法替代的”。59 誠然,日後中山公園尚有豐富的切入空間,期待將來有更多的發崛和探索,並對下列問題進行討論﹕
- 中山公園的發展情況
- 各地中山公園興建的年份﹕1920-30年代、1945年、1949年、1990年代
- 各地中山公園的沿革﹕新建、改建、易名
- 各地中山公園興建的資金問題
- 部分中山公園的破壞與重建
- 遭受易名、廢棄的中山公園
- 中山公園的結構
- 所處位置(市中心、邊緣)
- 空間設計及建築特色
- 銅像及紀念碑
- 中山公園的作用
- 孫中山崇拜建構
- 各地中山公園中的國家符號
- 中山公園在不同時代的歷史意義
- 政府與民眾對中山公園功能的理解與討論
本資料庫以整體視角為出發點,意在遂一臚列現存中山公園,藉以展示中山公園如何在提供休閒娛樂功能的同時,成為紀念或傳遞孫中山崇拜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