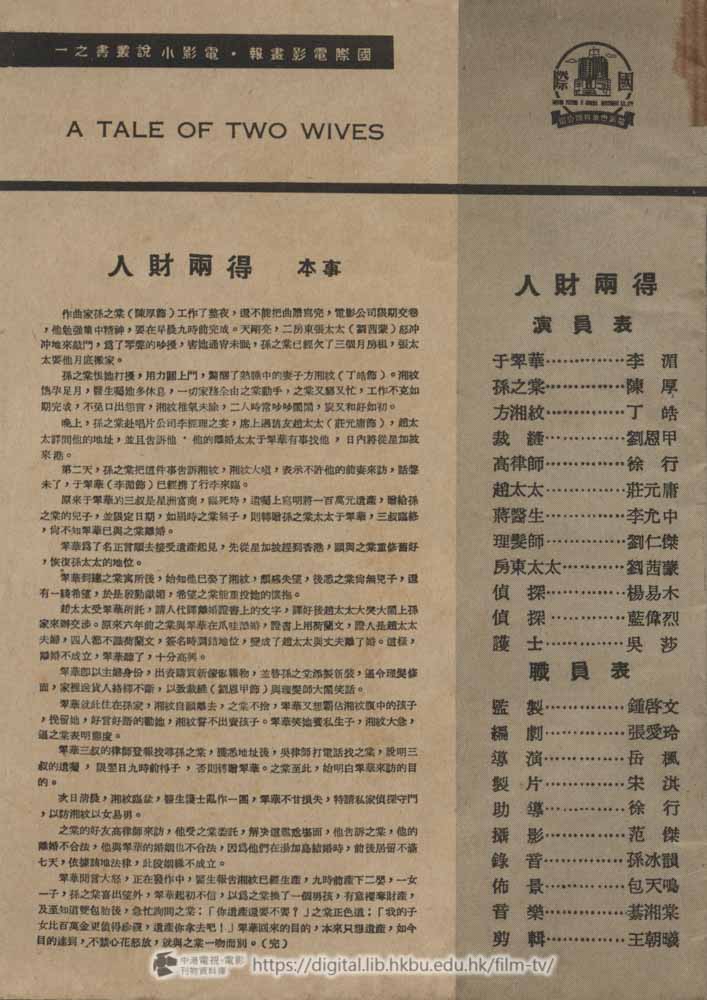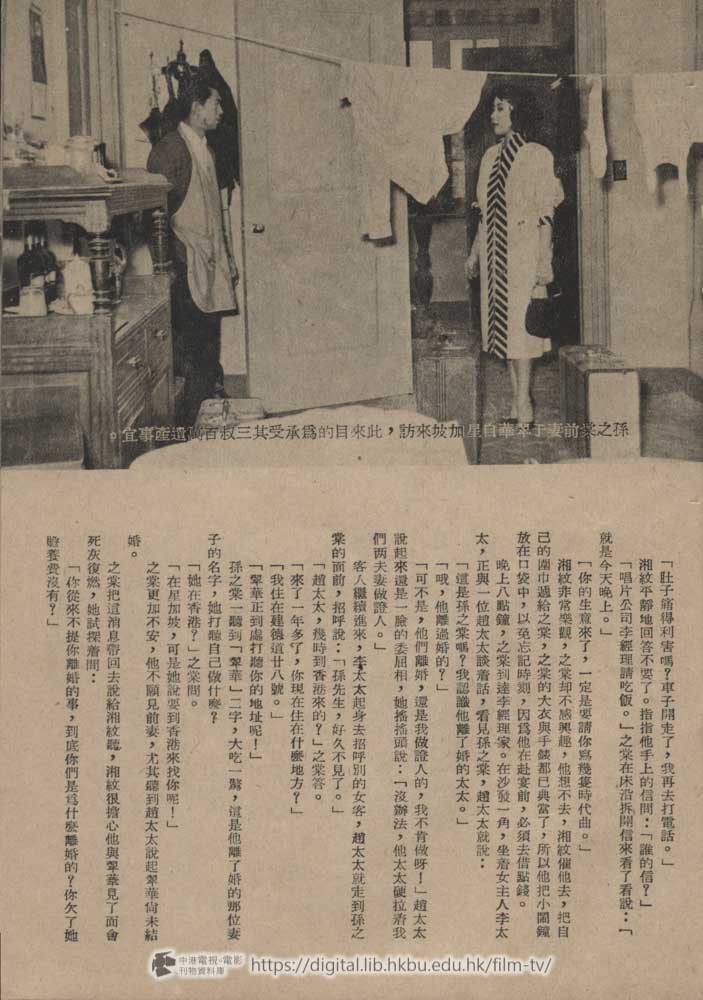人財兩得
TALE OF TWO WIVES
國際電影畫報・電影小說叢書之一
A TALE OF TWO WIVES
人財兩得 本事
作曲家孫之棠(陳厚飾)工作了整夜,還不能把曲譜寫完,電影公司限期交卷,他勉强集中精神,要在早晨九時前完成。天剛亮,二房東張太太(劉茜蒙)怒冲冲地來敲門,爲了琴聲的吵擾,害她通宵未眠,孫之棠已經欠了三個月房租,張太太耍他月底搬家。
孫之棠恨她打擾,用力關上門,驚醒了熟睡中的妻子方湘紋(丁皓飾)。湘紋懷孕足月,醫生囑她多休息,一切家務全由之棠動手,之棠又窮又忙,工作不克如期完成,不免口出怨言,湘紋稚氣夫除,二人時常吵吵鬧鬧,旋又和好如初。
晚上,孫之棠赴唱片公司李經理之宴,席上遇舊友趙太太(莊元庸飾)趙太太詳問他的地址,並且吿訴他,他的離婚太太于翠華有事找他,日內將從星加坡來港。
第二天,孫之棠把這件事吿訴湘紋,湘紋大嗔,表示不許他的前妻來訪,話聲未了,于翠華(李湄飾)已經携了行李來臨。
原來于翠華的三叔是星洲富商,臨死時,遺囑上寫明將一百萬元遺產,贈給孫之棠的兒子,並限定日期,如屆時之棠無子,則轉贈孫之棠太太于翠華,三叔臨終,尚不知翠華已與之棠離婚。
翠華爲了名正言順去接受遺產起見,先從星加坡趕到香港,願與之案重修舊好,恢復孫太太的地位。
翠華到達之棠寓所後,始知他已娶了湘校,頗感失望,後悉之棠尚無兒子,還有一綫希望,於是殷勤獻媚,希望之棠能重投她的懷抱。
趙太太受翠華所託,請人代譯離婚證書上的文字,譯好後趙太太大哭大鬧上孫家來辦交涉。原來六年前之棠與翠華在爪哇離婚,證書上用荷蘭文,證人是趙太太夫婦,四人都不識荷蘭文,簽名時調錯地位,變成了趙太太與丈夫離了婚。這樣,離婚不成立,翠華聽了,十分高興。
翠華即以主婦身份,出資購買新傢俬雜物,並替孫之棠添製新裝,通令理髮修面,家裡送貨人絡繹不斷,以致裁縫(劉恩甲飾)與理髮師大鬧笑話。
翠華就此住在孫家,湘紋自願離去,之棠不捨,翠華又想霸佔湘紋腹中的孩子,挽留她,好言好語的勸她,湘紋誓不出賣孩子。翠華笑她養私生子,湘紋大急,逼之棠表明態度。
翠華三叔的律師登報找尋孫之棠,獲悉地址後,吳律師打電話找之棠,說明三叔的遺囑,限翌日九時前得子,否則轉贈翠華。之棠至此,始明白翠華來訪的目的。
次日清晨,湘紋臨盆,醫生護士亂作一側,翠華不甘損失,特請私家偵探守門,以防湘紋以女易男。
之棠的好友高律師來訪,他受之棠委託,解決這尷尬塲面,他告訴之棠,他的離婚不合法,他與翠華的婚姻也不合法,因爲他們在湯加島結婚時,前後居留不滿七天,依據該地法律,此段姻緣不成立。
翠華聞言大怒,正在發作中,醫生報吿湘紋已經生產,九時前產下二嬰,一女一子,孫之棠喜出望外,翠華起初不信,以爲之棠換了一個男孩,有意攫奪財產,及至知道雙包胎後,急忙詢問之棠:「你遺產還要不要?」之棠正色道:「我的子女比百萬金更値得珍視,遺產你拿去吧!」翠華回來的目的,本來只想遺產,如今目的達到,不禁心花怒放,就與之棠一吻而別。(完)
離婚太太重投懷抱
「人財两得」是一部上乘喜劇,張愛玲繼「情塲如戰塲」後的新傑作。里面有兒戲般的婚姻,與眞摯的愛。有了上乘的劇本,也需要良好的演員,導演岳楓精揀細挑,選中了陳厚與李湄,還有劉恩甲,丁皓和莊元庸。劉恩甲與莊元庸,在外貌上是喜劇型的人物,丁皓的演技雖不能說無懈可擊,但小丁皓學什麼像什麼是內外人一致公認的,至於李湄與陳厚,他們在「人財兩得」中,發展了新的戲路,而且是成功的戲路。當然,好的演員配上好的劇本,他們的演技就有了發揮餘地,陳厚與李湄,大家各出小噱頭,增加小動作來强化喜劇性,而且眞眞實實地讓它成功一部喜劇,不是鬧劇。他們飾演一對已經離了婚的夫妻,爲了一筆遺產,女的去尋男的,希望覆水重收;李湄對這角色把握得很緊,她初時的百般獻殷勤,及知陳厚再婚後的一驚,一怒,又爲了遺產着想而强作笑容,情緖一陣陣推出,表情一次次變化,會使你對她的演技驚嘆佩服。同時與她做對手戲的陳厚也不錯,他處於錯綜複雜的環境中,應付二個太太,他把男人們的心理,通過其餘演技,刻劃得淋漓盡致,將使「人財兩得」的觀衆爲他不斷喝采。(夏帆)
陳厚返老還童
丁皓要生孩子了,李湄買了一架嬰孩車送給她,丁皓因爲李湄與陳厚的離婚手續不淸楚,堅决拒絶收受禮物,並且不准陳厚同睡,陳厚無奈,到客廳去睡沙發,却給李湄搶去氈毯,天寒地凍,無法可想,陳厚祇好睡到未來兒子的床上去——嬰孩車上,暫避風寒。結果,丁皓越想越氣,李湄哈哈大笑,而陳厚却被推翻在地上。
這是「人財两得」中的揷曲,亦反映世上有两個妻子的人的痛苦,觀衆中看到這些塲面,或許有人在嘻嘻哈哈聲中會作會心的微笑。尤其看到了陳厚那付尷尬相。
在拍攝這一場戲時,陳厚遵照導演岳楓指揮,爬入嬰兒車中,逗得全場工作人員笑聲不停,丁皓應該是一付生氣的表情,但是她老是板不起臉來,她笑彎了腰,陳厚見她樂,再把手指放入口中說:「來,照一張返老還童的相。」這一下,連李湄也拍不成戲丁,笑到肚疼。(紅棉)
風雲色變
這是「人財两得」中的打鬥塲面。
丁皓要生孩子了,李湄怕她以假換眞,生女換個兒子,一定要親自去監督生產,陳厚怕丁皓在生產時受剌激,下死動地拉住李湄不肯放。李湄越發起了疑心,先是偸偸地乘陳厚不備,去開房門,陳厚眼快一把拉住,正在此時,房內傳出啼聲,李湄着了急,掙扎不得,順手抓起身畔的酒瓶,向陳厚來一個迎頭痛擊,立刻把陳厚擊昏在地。這一塲打得落花流水的塲面,費了不少拍攝時候,因爲陳厚預知要挨打,總是先閉上眼,這樣當然與劇情不合,李湄機警,手指另一面,聲東擊西,手起瓶落,陳厚不知是計,無聲倒地,這樣才拍得了一個精采鏡頭。(飛花)
丁皓的醋勁
丁皓年紀輕輕,已經學會了吃醋,她在「人財两得」中,為了陳厚,與李湄大吃其醋。她有一套吃醋的手法,第一,她先以微笑作攻勢,要陳厚防不勝防。第二,她向床上一賴,任陳厚千呼萬喚,她不動聲色,第三,陳厚不認錯,在那里作强辯詞,丁皓先白他一眼,然後作勢要哭。第四,陳厚不認移情別愛,她把背向他,放聲大哭。第五,陳厚被她一哭,六神無主,祗好苦苦哀求,丁皓就漸漸收住哭聲,變成抽噎。第六,陳厚以為她回心轉意,想上去表示親熱,誰知她使勁一推,陳厚變作倒地葫蘆,丁皓又哭着說他欺侮她。叫陳厚愛又不是,恨又不是。
在讀劇本時,丁皓表示她沒有「吃醋」經驗,心里怎樣也酸不起來,岳楓對她附耳輕言,敎導她一套吃醋必勝。拍完戲後,李湄在旁看得大叫「好嘢」!陳厚却說,千萬別敎他的太太,不然,他無法招架。
有人問丁皓有什麼感想?丁皓說:吃醋是人的本能,從前沒有經過,現在雖然是假的,多少心里是有一點感觸後才能發揮出來。她感觸些什麼?丁皓笑而不答。
兩婦之間難為夫!愁眉不展的音樂家
在香港的作曲家大都是非常吃香,出入有汽車,請求作曲的人更紛至沓來。惟有陳厚改行做「作曲家」以來,老是愁眉不展,房租欠了三個月。
有人問陳厚,好好的演員不做,幹嗎要改行?他嘆一口氣說:第一是羨慕作曲家的進益比演員好;第二,導演岳楓說我大有音樂天才,不如改行。誰知近來靈感始終不降臨,人家請我作曲,我無法繳卷,妻子又要養孩子,眞是懊悔改了行。
「人財兩得」中的陳厚,飾一個潦倒的窮音樂家,半夜作曲,早晨煮飯,下午洗衣,内外兼顧,苦不堪言,所以心焦異常,曲譜一點也寫不出。他在拍「人財两得」前去請敎幾位有名的作曲家,他們對他笑着說:寫不出東西時的心焦情形我們都有這種經驗,但是煮飯洗衣一齊來的經驗,恐怕沒有人說得出。(小玉)
二哥怕剃頭
在古時候,皇帝怕人暗算,在理髪剃鬚的時候,左右有人持鎗保衞,以免皇帝在剃刀下喪生,所以有句俗語形容事情的險惡,說是「險過剃頭」,由此可見有許多人認剃頭爲險事,倒是大有來歷。試想,在刀光「剪」影下,至少要坐一個鐘頭,一不小心,可能有流血事件發生,難怪二哥劉恩甲耍怕剃頭了。一個熟練的理髮師尙且不免失手,「人財兩得」中,岳老爺還要叫一個演員飾理髮師,替二哥剃頭,二哥自然要憂容滿面,愁眉不展了。在試演的時候,「理髮師」劉仁傑拿起肥皂刷,先要和他剃鬚,二哥舉手叫道:「慢來」!岳楓問他做什麼?他說:有些心驚肉跳,這把剃刀太亮。引得哄堂大笑。其實,二哥如果眞的蓄了「奇勒基寶」式的鬍鬚,非常漂亮,可是他因爲有了一女朋友,所以不願蓄鬚。「人財兩得」中,他有了鬍鬚,理髪師看他穿了漂亮的西裝誤會了他是主人,强迫他剃頭,他越是推避,越被追逐,鬧出了一塲笑話。
人物介紹
于翠華——李湄飾
于翠華是孫之棠的前妻,因爲捱不慣貧苦生活,和孫之棠離了婚,但是不敢吿訴她的三叔聽。三叔逝世時,還沒有知道她的離婚事件,所以把遺產指定傳給孫之棠的兒子,也就是姪女的骨肉,豈知這一來急壞了于翠華,眼看百萬遺產要落別人家口袋,於是自星加坡趕往香港,希望把遣產弄到手里。李湄飾于翠華一角,施展混身解數,使陳厚乖乖的就範,從欺騙、懷舊、直至眞情流露,她的演技爐火純靑,眞叫人看了過癮。
孫之棠——陳厚飾
孫之棠是一個窮音樂家,窮到妻子懐了孕,沒有辦法請僕人,一切家事親自操作,忙上加忙,再加上一個飛來的前妻,和他捉迷藏地爭奪遺產,眞使他焦頭爛額。前妻的離婚不合法,現在太太的身份成問題,二妻之間難爲夫,孫之棠說什麼誰也不聽,結果得友人髙律師帮忙,解决了婚姻問題,他旣得子女,又獲愛妻,情願放棄遺產。陳厚對喜劇頗有心得,一舉一動惹笑而不過火,非有精湛演技與眞摯情感所不能達到的境界。
裁縫——劉恩甲飾
一個西裝裁縫,自然懂得一套奉承顧客的本領,同時,自己的服裝也整齊挺括,他到孫之棠家去爲孫之棠度身做西裝,却被理髮師誤會他是孫之棠,追着要剃去他最心愛的鬍鬚,鬧得天翻地覆。劉恩甲飾裁縫,不用說他對喜劇是拿手,一舉手,一瞪眼,都是笑料,他做什麼像什麼,絕對沒有身份外的表情與舉動,雖說劇中人物是一個裁縫,但他的一場戲,增加了不少喜劇氣氛,他是觀衆的開心菓,他的喜劇决不會使人失望。
方湘紋——丁皓飾
方湘紋是一個稚氣未除的小婦人,她愛家,愛丈夫,愛未來的子女,在她懐孕待產的時節,來了一個她認為情敵的于翠華。孫之棠對她百般解釋,都不能消除她心里疑團,接着而來的身份不成立,于翠華要謀取她的孩子,簡直把她氣暈了,她發脾氣,拒絕丈夫進房,消極的抵抗。方湘紋不是于翠華的對手,却是孫之棠所深愛的妻子,終於二人和好。丁皓的演技大有進步,加上有稚氣的臉,頗適合劇中人身份,演出極為稱職。
高律師——徐行飾
高律師是孫之棠的朋友,他為了孫之棠的兩妻問題,下了很多硏究功夫,到最後遺產限期前一小時,始把事情攪妥當。他對于翠華開了個大玩笑,先向她說她與孫之棠的離婚不成立,引得于翠華大樂,接着說,離婚雖不成立,但結婚也不成立,他說出當時的結婚地點與結婚手續,條理分明,激得于翠華大怒,却安了孫之棠的心,徐行飾髙律師,短短的一場戲中,精采紛呈,他有條不紊的談話,配合李湄一喜一怒,妙不可言。
趙太太——莊元庸飾
趙太太是于翠華的閨中好友,一個富家太太,她愛饒舌,愛管閒事,當年于翠華與孫之棠的離婚證書上,是她和她的丈夫做証明人。時隔六年,于翠華為了爭遺產,請她把荷蘭文的離婚証明書叫人譯出,不譯還好,一譯出來原來簽名簽錯了地位,變成趙太太與趙先生離婚。害得她一路哭一路找上于翠華的門,因離婚書上寫明無條件的,趙先生堅持不給分文。莊元庸有良好的喜劇外型,有流利國語與銀幕經驗,有凸出的成績。
人財兩得 電影小說
斷斷續續的鋼琴聲,從客廳里傳入臥室,湘紋甜甜地睡着,響了一夜的琴聲並沒有打擾她的睡眠,因爲她習慣了,彈琴的是她的丈夫孫之棠,一個作曲家。
室外的陽光普照大地,射入室内,孫之棠琴畔的燈還亮着,整夜的工作使他困倦不堪,他伸一下懶腰,望望客廳中的一切,凌亂不堪地堆在一起,精神越發不振,但是他必須在中午前完成這些曲子,人家等着要。
「篤、篤、篤」,有人敲門,孫之棠揉着眼睛,打着呵欠站起來開門,門一開,他的精神一振,因爲門外站着是二房東張太太。
孫先生,你怎麽叮叮咚咚鬧了一夜也沒停,你不睡覺,別人還睡不睡?」
房東太太一付失眠的神情,使孫之棠感到非常抱歉,他連聲道歉。張太太哼一聲說:
「你們找到了房子沒有?」
「張太太,我不是跟你解釋過了?我暫時不能搬家,要過了這兩天,等我太太養了孩子再搬。」
「等你太太養孩子?」張太太不耐煩地答:「一個多月前就說耍養了!」
孫之棠點點頭,指指客廳中並排着的三個箱子說:
「她不養有什麼辦法呢?你看,什麼都預備好了,就等上醫院,大概就在這两天了。」
「反正你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孫先生,不是我趕你搬家,你自己想想,房租三個月沒付了,要不是看在老房客面上,我眞跟你不客氣。」
張太太大聲地喊,之棠不能忍受,關上房門,由她在門外叫喊,他走回鋼琴邊。
「之棠!」
湘紋醒了。之棠推門進臥室,温柔地說:
「把你吵醒了,是二房東。」
湘紋憐惜地問:「你又是一夜沒睡?這樣白天黑夜地趕,趕出病來怎麼辦呢?」
「沒辦法,還是夜里比較淸靜,沒有人打攪我。」
湘紋疑心他說自己打攪他,負氣地睡下,之棠皺皺眉,回到客廳繼續工作,寫不上一行樂譜,臥室中又傳來了湘紋的聲氣。
「之棠,我餓了!」
醫生吿訴湘紋,在產前必須多多休息,之棠更細心照料,所有家務自己動手,連燒飯洗衣都不耍湘紋做。
湘紋餓了,孫之棠放下筆去厨房做早餐,圍上圍裙,把粥與菜放入托盤,捧入臥室去。
「你自己吃呢!」湘紋說。
之棠搖搖頭說不餓,趕着出去寫曲,他才坐下鋼琴邊,湘紋又在叫他,拿藥,拿絨線,拿圍巾,差遣得團團亂轉,把預備帶到醫院去的箱子翻得紊亂,藥瓶、圍巾、都耍在箱底找出來。找到後捧進臥室去,咀裡埋怨說:
「哪,你把東西全拿出來,等到上醫院的時候,手忙脚亂,又得理箱子。」
「我沒有把東西全那出來。」湘紋說。
「對了,你沒有拿,是我拿的。」
之棠說完,轉身走出臥室,想蓋上箱子,無論如何關不上,想不關,湘紋不依,逼不得巳,逐樣淸理,才把箱子關上,滿頭大汗去趕寫曲譜。
「之棠……之棠!」
湘紋又在聲聲喚叫。她是個年靑帶些稚氣的少婦,又是初次懐孕,所以把麻煩丈夫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她不管他理不理,催他打電話去醫院,問上次留下的房間。
她再三地打斷之棠工作,激得他憤怒異常,跳起來對着臥室大嚷:
「湘紋,我今天非得把曲子寫完不可,你讓我這段寫完行不行?」
湘紋萬分委屈,泣然欲涕說:
「你這神氣就像你的工作比孩子還要緊。」
「當然孩子耍緊。」之棠鐵靑了臉說:「可是不工作孩子就得餓死。」
湘紋不服氣,反駁他說:
「孩子吃奶有我餵他,不用你操心。」
「孩子吃奶,可是你要吃飯!」
這句話可讓湘紋傷了心,哀哀痛哭,之棠心不忍,臉色緩和下來,摟了湘紋哄著說:
「別哭,別哭,這两天不應當這樣緊張。」
好容易哄得湘紋止住哭聲,客廳中的電話鈴聲大响,之棠急忙走出去,從沙發下找出一條電綫,拉出來,哎,是熨斗,再找,總算找到電話。
是製片公司中打來的,催之棠的曲譜配音。之棠無法回答,推到明天,公司中人不肯,電話里說來說去為配音,湘紋在臥室插咀說:
「之棠,你不能讓人家為難,你不是答應今天交給人家的嗎?」
之棠不聽猶可,聽了心中直冒火,他忘記自己在聽電話忿忿然說:
「不錯,是我答應的,可是一天到晚打攪我,叫我怎麼工作呢?」
對方在聽電話的人,以為之棠罵他,也大光其火,和孫之棠對吵起來,湘紋却在臥室哇哇大叫肚痛。
孫之棠嚇得扔下電話,跑進臥室去,湘紋催他叫「的土」,汽車來了,她的肚子不痛了,車子開走後,她又痛起來,急得之棠又跑門去追汽車,汽車早已遠去,房東張太太聽聲出來,大罵之棠不顧門口,之棠無暇理她,跑進房去,張太太遞給他的一封信沒空看,奔向床前。
「肚子備得利害嗎?車子開走了,我再去打電話。」
湘紋平靜地回答不要了。指指他手上的信問:「誰的信?」
「唱片公司李經理請吃飯。」之棠在床沿拆開信來看了看說:「就是今天晚上。」
「你的生意來了,一定是耍請你寫幾隻時代曲。」
湘紋非常樂觀,之棠却不感興趣,他想不去,湘紋催他去,把自己的圍巾遞給之棠,之棠的大衣與手錶都已典當了,所以他把小鬧鐘放在口袋中,以免忘記時刻,因爲他在赴宴前,必須去借點錢。
晚上八點鐘,之棠到達李經理家。在沙發一角,坐着女主人李太太,正與一位趙太太談着話,看見孫之棠,趙太太就說:
「這是孫之棠嗎?我認識他離了婚的太太。」
「哦,他離過婚的?」
「可不是,他們離婚,還是我做證人的,我不肯做呀!」趙太太說起來還是一臉的委屈相,她搖搖頭說:「沒辦法,他太太硬拉着我們两夫妻做證人。」
客人繼續進來,李太太起身去招呼別的女客,趙太太就走到孫之棠的面前,招呼說:「孫先生,好久不見了。」
「趙太太,幾時到香港來的?」之棠答。
「來了一年多了,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住在建德道廿八號。」
「翠華正到處打聽你的地址呢!」
孫之棠一聽到「翠華」二字,大吃一驚,這是他離了婚的那位妻子的名字,她打聽自己做什麼?
「她在香港?」之棠問。
「在星加坡,可是她說要到香港來找你呢!」
之棠更加不安,他不願見前妻,尤其聽到趙太太說起翠華尙未結婚。
之棠把這消息帶回去說給湘紋聽,湘紋很擔心他與翠華見了面會死灰復燃,她試探着問:
「你從來不提你離婚的事,到底你們是爲什麼離婚的?你欠了她瞻養費沒有?」
「根本沒有贍養費,我那時候跟現在一樣窮,爲了窮,她吃不了苦過不慣。」之棠坦白地說。
「哦,她嫌你窮。」湘紋想了一想說:「也許她現在又懊悔跟你離了婚。」
「懊悔有什麼用?我已經結了婚了。」
「人家老遠從星加坡跑來看你,你一定很感動。」
「別胡說,我不歡迎她來。」
之棠這句話,就是湘紋等待着的回答,她急忙說:「那你何不叫她不要來」」
湘紋咀里說着話,又不想棠之看見她的不樂意,假裝着翻報紙,却看見了一段找孫之棠的廣吿。
「咦!你瞧!」湘紋詫異地說:「有個律師登報紙找你呢!」
孫之棠瞧着她手指處看。
「孫之棠君鑒 見報務請立卽駕臨皇后大厦吳仰安律師事務所,有要事接洽。」
之棠讀了又讀,自慰說:「同姓同名的人很多,不見得是我。」
但是湘紋並不這樣想,她說:
「這個人也找你,那個人也找你,這事情奇怪,一定跟那個女人有關係。」
夫妻兩人在討論的時候,于翠華已從星加坡到達香港,去接她的是趙太太。
「現在這個年頭不好,不怪你們年靑人,就是我們老頭子,也一天到晚鬧着要雖婚。」趙太太說。
「眞的?」于翠華放下粉鏡,微笑着說:「快別理他,這麼大年紀,讓人家笑話。」
說完,拿起鏡子塗口紅,趙太太打趣說:
「得了,別打扮了,還不够漂亮嗎?我看你眞是愛孫之棠。」
「那倒也不一定,這麼些年沒見面,怎知道他變成什麽樣子了?「翠華淡淡地回答。
「噯,這麼着好不好?如果一見面你很滿意,你就對我做個暗號,我馬上一個人就走,要是不滿意,你也做個暗號,我就說這地方出門不大方便,還是住在我家里好,我們就一同走。」
趙太太異想天開,于翠華很樂意照她的辦法做,於是决定以手帕放在鋼琴上爲暗號。
她們一路上孫之棠家去,孫之棠還在對湘紋保證,不讓于翠華去看他,但是,的士司機拿了箱子上來了,箱子上面掛的紙片上,赫然于翠華三宇。
箱子擲地聲,驚動在臥室中的湘紋,起初,她以爲之棠做家務闖了禍,之棠有氣無力地吿訴她,有客來了,隨手關上了臥室門。
隨着箱子進來的是翠華和趙太太,翠華要之棠帮她付車錢,之棠無奈出去付,進來時,翠華已經把手帕放在鋼琴上,可是趙太太沒注意,因爲她看見了客廳中晾着的乳罩與女衫。
「孫先生,你們這里住幾家了?」趙太太問。
「樓下就是我們一家。」之棠答。
「你這些女人衣裳那兒來的?」翠華也發現了乳罩,追問孫之棠。
趙太太很天眞地勸翠華不耍鬧,祇耍之棠以後好好地就算了,翠華順水推舟,先打發趙太太走,孫之棠要她一起走,翠華不肯,之棠說:
「翠華,你住在這兒實在不大方便。」
翠華不理他。臥室里傳了聲音出來,湘紋大叫:
「之棠!你在跟誰說話?」
「翠華來了!」之棠低低地回答。
「誰呀?」湘紋沒有聽明白,再問。
翠華的神情也緊張了,問:
「那是誰?」
「是我太太。」
翠華大吃一驚,走前一步說:
「你結了婚了?」
「當然結了婚了。」之棠坦然說。
「你有了小孩沒有?」
「沒有。」
翠華鬆了一口氣,弄得之棠莫明其妙,湘紋在臥室中連連追問,之棠打開臥室門說:
「翠華來了!」
「翠華?」湘紋的聲調中充滿怒意。
「噯,是我,你好?」翠華却意外的和悅,她回頭問之棠說:「她叫什麼名字?」
之棠不情不願地吿訴她,翠華得意地說:
「湘紋,我進來看看你好嗎?」
「噯,不行,不行,之棠你不能讓她進來。」
之棠立刻把門關上,翠華毫不在乎地說:
「我總想知道她長的是什麼樣子。」
孫之棠指着牆上的照片給翠華看,翠華讚一聲:
「呦,眞漂亮!」
之棠不理會她說什麼,進了臥室去。翠華見她進去,立刻打電話,鬼鬼崇崇說:
「吳律師,是我啦,我找到他啦,他沒有小孩。」
她瞧見孫之棠又出來,趕快掛上,孫之棠有點懐疑,但又不便問她,祗說:
「你變了,從前不是這樣。」
「是嗎?」翠華攏攏頭髪,飄了他一眼說:「這兩年我經過許多事情,也難怪我變了。」
「是什麼事?」
「去年我三叔死了,你不記得了,在星加坡開飯店的那個三叔。留吓一百萬塊錢給我。」
翠華得意洋洋地說著,孫之棠有些心動,繼而一想,兩人根本離了婚,還有什麼可說。翠華再吿訴他,她先得了一萬元,其餘的耍等一週年後,法律上手續完成才可以到手。
两人談著話,時間已是下午两時,湘紋在臥室中說家里沒菜,不預備招待客人,翠華自吿奮勇入㕑,先把菜讓之棠端進房給湘紋吃,隨後二人對面坐下吃飯,有一搭,沒一搭地談着。翠華批評湘紋不會管家,之棠就吿訴她,湘紋懷了孕,沒法做家務。話剛出口,翠華放下筷子,神色又趨緊張地問:「馬上就耍養了?什麼時候養?」
「這很難說,我也不知道。醫生也算不出。」
翠華鬆口氣,站起來走到之棠背後,扶着椅背說:
「咳,都是你,不然你想,我們二人加上一百萬塊錢,我們可以到世界各國去遊歷,你也不用爲生活發愁,可以到歐洲去學音樂,儘量的發展,寫出最偉大的交响曲,你不是一直這樣想嗎?」
之棠給她說得沉醉了,簡直要軟化。但是湘紋的呼喚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急急擺脫翠華摟着他的手,翠華帶誘惑性地笑着說:
「瞧你,眞怕太太,從前可一點都不怕我。」
說着,把臉貼上去,之棠掙扎着說:
「不是,這两天不能讓她受剌激,她就要養了。」
翠華馬上鬆了手,口里直嚷糟糕。但是她還得保持對自己的希望,不敢立刻發作,她下厨房去沏了二杯茶,哄着之棠彈鋼琴,務求能勾起他的回憶,使他懐念舊時的情感,她這樣舉動,弄得孫之棠手足無措,他說:「翠華,我老記住我們六年前在爪哇離了婚。」
「對了,在爪哇用的是荷蘭文,誰知道它說些什麼,怎麽能認眞?」
翠華一派輕鬆,之棠着急萬分。
「你想賴,我們一人有一張離婚證書。」
「也是荷蘭文。」翠華抱定不認賬的態度說:「我一句都不懂,怎知道我們是真離了婚了?」
「雙方同意,怎麼會是假的呢?」
之棠跳起來了。門外有人敲門,之棠立卽不敢大聲,他知道來的是誰。翠華去開門,是二房東催租,翠華不徵求之棠同意,很爽快把房租付淸,另外給了水電費,樂得張太太連連道謝而去。
翠華關上門,之棠從門後轉出說:「我不能讓你出這個錢。」
「呵,你別這樣。」翠華用雙手握着之棠的手,表情十足地說:「你不明白麼?我能够帮你一點忙,我心里眞痛快。」
之棠鬱鬱地掙脫她的手。門外又起了一陣猛然的打鬥聲,趙太太像一陣颶風似地冲進來,大哭大喊:
「孫之棠、于翠華,你們害死人了,我來跟你們拼命!」
「趙太太,有什麼事?」二人異口同聲問。
趙太太一時泣不成聲,把手中的文件交給翠華,原來是他們的一張離婚證書,翠華請趙太太找人翻譯的,翠華驚喜地問:
「不合法是不是?我知道我們離婚不成立。」
「合法,合法!」趙太太哭着說:「可是你們簽名簽錯了地方,你們成了離婚證人,而我們夫妻倆成了離婚人,老頭子和我離了婚,一個錢瞻養費也拿不到,你這害人精,害苦了我!」
趙太太繼續大哭,于翠華樂得大笑,這些話湘紋都聽見的,她也哭了,把之棠叫進臥室去,二人爭論起來,湘紋耍他决定誰去誰留,之棠左右為難,等趙太太走後,他和翠華開談判。
翠華一派主婦作風,開始整理房間,咀里嘰咕說:
「之棠,你這屋子不但亂七八糟,傢俱也不够用,一會兒,我出去看看,買套新傢俱。」
「不,不,翠華,我有話跟你說,你坐下。」
之棠先坐下,翠華一扭身坐在他膝上,他用力推,翠華含笑地說:
「跟自己丈夫親熱親熱有什麼關係?」
之棠痛苦萬分,推開翠華,對她説:
「翠華,我得吿訴你,老實說,我是絕對不會離開湘紋的。」
「當然,尤其在這時候,她正要生孩子,你得照應她,我們二個都得陪她,女人比男人細心,有些地方我比你想得週到,錢你不用擔心,有的是。」
「這不是錢能够解决的事,她說的,你不走她走。」
「她眞要走,誰也不能攔她,我是看她可憐,沒結婚就做了母親,她那孩子生下來可以過繼給我。」
翠華一味自說自話,之棠却束手無策。翠華就離去購買東西,臨走還鄭重地問湘紋愛吃什麼。
她出外沒有多久,送東西的人絡繹不絕,送砂鍋鷄,送沙發,送地毡,送無綫電,送嬰孩用品等等,把湘紋氣得淚流滿面。
「就憑她幾個臭錢,丈夫讓她買了去了,我的孩子可不賣,無論如何不賣。」
她又哭又鬧,孫之棠急得搓手,空言安慰她:
「湘紋,你安靜點,你不能發脾氣,自己傷身體,對于孩子也沒有好處。」
「孩子還沒有出世,倒已經是別人的了。」
湘紋索性起身,把東西亂擲一頓。之棠說:
「她並不是一定要孩子呀,她願意把孩子過繼給她,也是她的好意。」
事實是事實,翠華與之棠的離婚不成立,湘紋的地位是不能維持下去,這給未來的小母親很大的剌激,她使勁地罵之棠,罵翠華,但都是沒有用的。她恨之棠沉醉在發財夢中,她决定要離開他。
晚上,翠華回來睡覺,她打算睡長沙發上,從箱子取出一襲華麗的睡袍,給之棠看,之棠怕她泥住他,連忙入臥室,誰知湘紋不要他同睡,她板起臉說:
「從今天起,我叫你孫先生,你叫我方小姐,是你自己說的,我們根本不是夫妻,男女有別,請你自己放尊重些,我的房間你不能隨便進來。」
之棠素知湘紋有些孩子氣,他怔了一會,仍舊坐在床沿解開領帶,準備上床,湘紋不依,亂打亂推,又把枕頭與毡子擲出房門外,之棠無奈拾起到客廳,客廳中迎接他的是翠華的幸災樂禍的笑容。
這一夜,方湘紋睡在床上,于翠華睡在長沙發中,孫之棠靠着椅背,縮作一團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翠華入厨做早餐,之棠先把早餐送入湘紋室中,出來時打了噴嚏。
「你傷風得很利害?」翠華問。
「昨天晚上着了凉了。」之棠滿面寒意地說。
「我已經打了電話給醫生,又叫了栽縫和你做大衣,冬天的西裝也該添兩套了。還有理髪師。」
翠華坐在沙發挫指甲,又打電話,指揮若定,打完電話,在手袋里取出鈔票,要之棠到對面去買雙新鞋,不由他分說,一把推出門去。
孫之棠岀去後,理髪師來了,翠華叮囑他說:
「孫先生一會兒就來,他一進來,你就給他理髮刮鬍子,他耍是不願意,你別理他,他有怪牌氣。」
她把他領到厨房去等,在客廳,怕弄髒了新地氈。
接着裁縫來了,她又叫他上厨房等候,那里知道理髮師誤會裁縫是孫先生,二人在厨房一追一逃直鬧到客廳來,翠華給他們的纏夾攪到又氣又笑。
孫之棠回來時,醫生也來了,先診病,再量衣,又理髪修面,消費了整個上午,于翠華在厨房弄妥午餐,端上桌子,正安排碗筷,房東張太太端了一碗菜進來。
「我給孫太太燉了隻鷄送來。」
「謝謝,謝謝。」翠華客氣地說:「你幹麼破費?」
「孫太太這兩天好嗎?」
「我很好!」
「不。」張太太詫異地望她一眼說:「我不是說你,我是說孫太太。」
「噢!」翠華故意做成弄錯的樣子,指指臥室說:「那個孫太太,她也很好。」
翠華的外貌是妖艶的,舉止輕浮,引起房東太太的疑心,她本來好管閒事,於是不客氣地問:
「你是不是他嫂子?」
翠華搖搖頭。張太太轉問孫之棠,之棠含糊地說:
「她是來帮着照應湘紋的。」
「是什麼親戚?」張太太打爛砂鍋問到底。
翠華不耐煩,碍着之棠不好直接說,她轉灣抹角說:
「我是她丈夫的太太,你說該叫什麼?」
「那末,她是你丈夫什麼人?」
「這個……」翠華特意頓一頓說:「名稱倒是有的,不過不大客氣。」
「姨太太,是不是?」
張太太口沒遮攔,孫之棠又窘又氣,湘紋在房里聽得淸清楚楚,氣得混身發抖,她不顧一切走了出來,對孫之棠斥道:
「之棠,你就眼看着她侮辱我?你沒長着咀,你不會解釋?」
張太太不等他們解釋,就說:「孫先生,對不起,月底還是要請你們搬家。」
一轉身出去,把一碗鷄也帶走。
孫之棠指責翠華說:「你看,這算什麼呢?」
「這有什麼要緊?」翠華輕描淡寫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搬家的,這屋子根本不够住。」
湘紋逼着之棠去解釋,翠華勸她不耍生氣,湘紋不理她,但翠華攔住房門說:
「今天覺得怎麼樣?可以起來吃飯嗎?一塊兒吃,我們談談。」
她在碗廚中取出一付碗筷,放在桌上,又載飯拉椅,殷勤萬分。
湘紋打量客廳四周,喃喃自語:
「自個兒家里,這間屋子我都不認識了。」
她帶着諷剌的眼光,使之棠苦笑,三人圍桌坐下,翠華故意做作,夾菜勸食,口里說來說去,無非想霸佔湘紋的孩子,湘紋旣是食不下咽又滿腔怒氣,一言不發,跑回臥室,重重地把門關上。之棠想勸又不敢,獨個兒上庭院踱方步。留下翠華暗暗好笑。
電話鈴響。是吳律師打來找孫之棠,翠華怕他洩漏天機,想不給之棠聽,之棠已經聽見,搶了來聽。
「我們登廣吿找你,看見了沒有?」吳律師說。
「我看見了。」
之棠一邊回答,一邊拉住翠華想按斷電話的手。
「孫先生,你有兒子沒有?」
「沒有,我沒有兒子。」
「你明天早上九點鐘以前會不會有兒子?」
翠華開响了無綫電想搞亂,之棠扭停它。
「明天早晨九點鐘以前?定做也沒那麽快,爲什麼耍九點鐘之前?」之棠問。
翠華在一邊急得團團轉。
「你的兒子耍在九點以前生下來,他可以拿到一筆很大的遺產,一百萬塊錢!」
「一百萬,噯!」之棠想了一想說:「可以辦得到,我太太正要生孩子!」
「你太太?」
「我太太——孫太太。」
翠華恨極了,揭開琴蓋一陣亂擊。
王醫生仍然叫之棠出去,翠華也給推出來,翠華又驚又怒,問:
「哦,你是說跟你同居的那個女人。」吳律師說。
「照法律上也許只好這麼說,可是我們的確是正式結婚的。」
於是,吳律師要孫之棠到事務所去走一趙。之棠掛上電話,他明白了翠華對他的一切,他說穿她的謊言,他直斥她的陰謀。翠華哭了,她說:
「真是不公平,是我的三叔,銀倒要傳給她的兒子,三叔沒見過她,根本不知有她,他打算傳給我的兒子。」
「你沒有兒子?」
「沒有。沒有的話就歸我,他以為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他最不贊成離婚,所以我一直瞞着他,沒敢吿訴他。」
「你反正一天到晚撒謊。」
翠華還想挽回局面,抹乾眼淚,假作歡容說:
「可是我對你是眞心,之棠。」
孫之棠甩脫她伸過來的手,走向臥室。
緊張的一刻終于來臨,第二天湘紋臨盆了,在家里,醫生與護土,在門口,有翠華請來的二個私家偵探。
孫之棠發現私家偵探後,為之一怔,問翠華:
「這两人是誰?」
「私家偵探。」翠華精神頹喪,坐在無綫電旁。
「偵探?要偵探幹什麼?」
「我不能不防備呀,到時候,她孩子沒養下來,你們倒抱了一個孩子來,說不定養了女的,換了男的。」
翠華理直氣壯地回答他,把孫之棠氣得發抖,他憤然作色說:
「你想得眞週到,我們不是那種人,我就是養了兒子也不會要你的錢。」
時鐘指着八點四十分。之棠緊張萬分,翠華欣然而笑,距離得遺產時間僅廿分鐘。
孫之棠的朋友高律師來了,翠華問他爲什麼請律師來,之棠正經地說:
「你一定耍問,我就吿訴你,我把我的離婚與結婚證書都拿去給他看,請他硏究硏究,有沒有辦法跟你離婚。」
翠華不以爲然,撇撇咀說:
「你趁早死了這條心,我怎麼也不跟你離婚」
高律師在皮包里取出文件,對之棠說:
「你明白不明白?你犯了重婚罪。」
高律師這句話叫翠華樂了,她高興地參加他們談話,批評之棠喜新忘舊。高律師接下去說:
「你到過澳洲旅行。」
「我們上那兒去渡蜜月。」翠華搶著說:「咳,那兒想得到他心變得那麼快。」
「你們在湯加島結婚的。」
「是呀。」翠華不容之棠開口,把高律師當作親人般向他訴說:「嫁了他不到二年,就讓他扔了,現在我三叔寄了幾個錢給我,他倒又來打我的主意。」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號到湯加島,四月二十三日離開,那麽你們在那里沒有住滿七天,要是住滿七天,你們的婚姻才有效!」
高律師說來不慌不忙,于翠華頓時像被澆桶雪水,孫之棠可高興了,指着翠華說:
「照這麼說,我跟她根本不算結婚了?」
「在法律上,你們的婚姻是不成立的。」
之棠不能解决的事,終于獲得解决,他跳到臥室門口,請護士轉言給湘紋,翠華泫然欲涕,情急地罵:
「孫之棠!你別胡說八道,你騙不了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吿你重婚!」
她一跳跳到高律師面前,手指到他臉上,罵:
「你也不是好人,你們串通了的,都是一黨。」
高律師完成任務,無意捲入吵鬧漩渦,他吿辭走了。于翠華跳來跳去罵,孫之棠不睬不理。漸漸地,她消失了怒氣,眼眶中充滿眼淚,情感衝動地說:
「你現在有了別的女人,你的心,你的感情,什麼都給了她,連我三叔的錢,都成了她的了。」
之棠知道最使翠華痛心的事是一百萬元遺產,他說:
「你別難受,我拿到了,我不會要一個錢的。」
「哼,你倒眞大方,肯把錢給我。你明知道沒希望,樂得慷慨!」
時鐘指着八點五十分。
門外又來一個護士,原來的護士一見就說:
「你來得正好,快了,快了!」
之棠與翠華的神經緊張起來。翠華怕里面出花様,耍進去看,之棠怕她搶孩子,擱住不放,二人扭作一團,翠華情急智生,隨手拿起一樣東西,把之棠擊昏,她飛也似的趕去臥室,手還在門把上,里面傳出一陣陣嬰孩哭聲。
時鐘指在八點五十五分,翠華進了室又出來,歡歡喜喜地叫醒之棠,吿訴他得了個女兒,還說:
「那小東西長得眞可愛。」
「翠華,我得了個女兒,我眞髙興極了!」
「我比你髙興,你添千金,我有一百萬。」
但是孫之棠不是這様想,他興奮而驕傲地說:
「我的運氣比你更好,我有湘紋,又有孩子,還有我的音樂!」
他忘記一切地坐上琴椅,快樂地彈奏。
王醫生從臥室中仲出頭來說:
「孫先生,快來!快來!」
孫之棠急忙迎上去,只見二個看護,各人手里抱一個嬰孩,向他道喜說:
「這是個男孩子,他的姐姐比他大幾分鐘!」之棠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他轉向床邊叫:
「湘紋!」
湘紋安靜地入睡,她在極度疲乏中。
「那男孩子是那兒來的?」
「雙胞胎!」之棠樂得裂開咀儘笑:「生了雙胞胎。」
「我不能相信,簡直太奇怪!」
時鐘正指着九點。
孫之棠不管于翠華信不信,他覺得他的生命一下子充實了,飽滿了,他愛湘紋,湘紋不再會離開他,他愛孩子,一下子來了二個,二個美妙的小傢伙。
他坐在琴畔,順手彈起琴來,他發現自己有新的創作,新的風格,他對翠華的絕望神情視若無覩,他跟着琴聲喃喃地說:
「湘紋,我們太好了!」
翠華爲他的興奮感動,他明白他與湘紋之間的愛,之棠不會要她的一百萬,她輕輕地說:
「之棠,她給你雙胞胎,我給你五十萬。」
「我不要,我只耍我的兒女。」
翠華凄然地說:
「我不是給你,是給我們的兒女的。」
孫之棠的運氣眞不錯,「人財兩得」。
(完)
國際電影畫報・電影小說叢書之一
A TALE OF TWO WIVES
人財兩得 本事
作曲家孫之棠(陳厚飾)工作了整夜,還不能把曲譜寫完,電影公司限期交卷,他勉强集中精神,要在早晨九時前完成。天剛亮,二房東張太太(劉茜蒙)怒冲冲地來敲門,爲了琴聲的吵擾,害她通宵未眠,孫之棠已經欠了三個月房租,張太太耍他月底搬家。
孫之棠恨她打擾,用力關上門,驚醒了熟睡中的妻子方湘紋(丁皓飾)。湘紋懷孕足月,醫生囑她多休息,一切家務全由之棠動手,之棠又窮又忙,工作不克如期完成,不免口出怨言,湘紋稚氣夫除,二人時常吵吵鬧鬧,旋又和好如初。
晚上,孫之棠赴唱片公司李經理之宴,席上遇舊友趙太太(莊元庸飾)趙太太詳問他的地址,並且吿訴他,他的離婚太太于翠華有事找他,日內將從星加坡來港。
第二天,孫之棠把這件事吿訴湘紋,湘紋大嗔,表示不許他的前妻來訪,話聲未了,于翠華(李湄飾)已經携了行李來臨。
原來于翠華的三叔是星洲富商,臨死時,遺囑上寫明將一百萬元遺產,贈給孫之棠的兒子,並限定日期,如屆時之棠無子,則轉贈孫之棠太太于翠華,三叔臨終,尚不知翠華已與之棠離婚。
翠華爲了名正言順去接受遺產起見,先從星加坡趕到香港,願與之案重修舊好,恢復孫太太的地位。
翠華到達之棠寓所後,始知他已娶了湘校,頗感失望,後悉之棠尚無兒子,還有一綫希望,於是殷勤獻媚,希望之棠能重投她的懷抱。
趙太太受翠華所託,請人代譯離婚證書上的文字,譯好後趙太太大哭大鬧上孫家來辦交涉。原來六年前之棠與翠華在爪哇離婚,證書上用荷蘭文,證人是趙太太夫婦,四人都不識荷蘭文,簽名時調錯地位,變成了趙太太與丈夫離了婚。這樣,離婚不成立,翠華聽了,十分高興。
翠華即以主婦身份,出資購買新傢俬雜物,並替孫之棠添製新裝,通令理髮修面,家裡送貨人絡繹不斷,以致裁縫(劉恩甲飾)與理髮師大鬧笑話。
翠華就此住在孫家,湘紋自願離去,之棠不捨,翠華又想霸佔湘紋腹中的孩子,挽留她,好言好語的勸她,湘紋誓不出賣孩子。翠華笑她養私生子,湘紋大急,逼之棠表明態度。
翠華三叔的律師登報找尋孫之棠,獲悉地址後,吳律師打電話找之棠,說明三叔的遺囑,限翌日九時前得子,否則轉贈翠華。之棠至此,始明白翠華來訪的目的。
次日清晨,湘紋臨盆,醫生護士亂作一側,翠華不甘損失,特請私家偵探守門,以防湘紋以女易男。
之棠的好友高律師來訪,他受之棠委託,解決這尷尬塲面,他告訴之棠,他的離婚不合法,他與翠華的婚姻也不合法,因爲他們在湯加島結婚時,前後居留不滿七天,依據該地法律,此段姻緣不成立。
翠華聞言大怒,正在發作中,醫生報吿湘紋已經生產,九時前產下二嬰,一女一子,孫之棠喜出望外,翠華起初不信,以爲之棠換了一個男孩,有意攫奪財產,及至知道雙包胎後,急忙詢問之棠:「你遺產還要不要?」之棠正色道:「我的子女比百萬金更値得珍視,遺產你拿去吧!」翠華回來的目的,本來只想遺產,如今目的達到,不禁心花怒放,就與之棠一吻而別。(完)
離婚太太重投懷抱
「人財两得」是一部上乘喜劇,張愛玲繼「情塲如戰塲」後的新傑作。里面有兒戲般的婚姻,與眞摯的愛。有了上乘的劇本,也需要良好的演員,導演岳楓精揀細挑,選中了陳厚與李湄,還有劉恩甲,丁皓和莊元庸。劉恩甲與莊元庸,在外貌上是喜劇型的人物,丁皓的演技雖不能說無懈可擊,但小丁皓學什麼像什麼是內外人一致公認的,至於李湄與陳厚,他們在「人財兩得」中,發展了新的戲路,而且是成功的戲路。當然,好的演員配上好的劇本,他們的演技就有了發揮餘地,陳厚與李湄,大家各出小噱頭,增加小動作來强化喜劇性,而且眞眞實實地讓它成功一部喜劇,不是鬧劇。他們飾演一對已經離了婚的夫妻,爲了一筆遺產,女的去尋男的,希望覆水重收;李湄對這角色把握得很緊,她初時的百般獻殷勤,及知陳厚再婚後的一驚,一怒,又爲了遺產着想而强作笑容,情緖一陣陣推出,表情一次次變化,會使你對她的演技驚嘆佩服。同時與她做對手戲的陳厚也不錯,他處於錯綜複雜的環境中,應付二個太太,他把男人們的心理,通過其餘演技,刻劃得淋漓盡致,將使「人財兩得」的觀衆爲他不斷喝采。(夏帆)
陳厚返老還童
丁皓要生孩子了,李湄買了一架嬰孩車送給她,丁皓因爲李湄與陳厚的離婚手續不淸楚,堅决拒絶收受禮物,並且不准陳厚同睡,陳厚無奈,到客廳去睡沙發,却給李湄搶去氈毯,天寒地凍,無法可想,陳厚祇好睡到未來兒子的床上去——嬰孩車上,暫避風寒。結果,丁皓越想越氣,李湄哈哈大笑,而陳厚却被推翻在地上。
這是「人財两得」中的揷曲,亦反映世上有两個妻子的人的痛苦,觀衆中看到這些塲面,或許有人在嘻嘻哈哈聲中會作會心的微笑。尤其看到了陳厚那付尷尬相。
在拍攝這一場戲時,陳厚遵照導演岳楓指揮,爬入嬰兒車中,逗得全場工作人員笑聲不停,丁皓應該是一付生氣的表情,但是她老是板不起臉來,她笑彎了腰,陳厚見她樂,再把手指放入口中說:「來,照一張返老還童的相。」這一下,連李湄也拍不成戲丁,笑到肚疼。(紅棉)
丁皓的醋勁
丁皓年紀輕輕,已經學會了吃醋,她在「人財两得」中,為了陳厚,與李湄大吃其醋。她有一套吃醋的手法,第一,她先以微笑作攻勢,要陳厚防不勝防。第二,她向床上一賴,任陳厚千呼萬喚,她不動聲色,第三,陳厚不認錯,在那里作强辯詞,丁皓先白他一眼,然後作勢要哭。第四,陳厚不認移情別愛,她把背向他,放聲大哭。第五,陳厚被她一哭,六神無主,祗好苦苦哀求,丁皓就漸漸收住哭聲,變成抽噎。第六,陳厚以為她回心轉意,想上去表示親熱,誰知她使勁一推,陳厚變作倒地葫蘆,丁皓又哭着說他欺侮她。叫陳厚愛又不是,恨又不是。
在讀劇本時,丁皓表示她沒有「吃醋」經驗,心里怎樣也酸不起來,岳楓對她附耳輕言,敎導她一套吃醋必勝。拍完戲後,李湄在旁看得大叫「好嘢」!陳厚却說,千萬別敎他的太太,不然,他無法招架。
有人問丁皓有什麼感想?丁皓說:吃醋是人的本能,從前沒有經過,現在雖然是假的,多少心里是有一點感觸後才能發揮出來。她感觸些什麼?丁皓笑而不答。
兩婦之間難為夫!愁眉不展的音樂家
在香港的作曲家大都是非常吃香,出入有汽車,請求作曲的人更紛至沓來。惟有陳厚改行做「作曲家」以來,老是愁眉不展,房租欠了三個月。
有人問陳厚,好好的演員不做,幹嗎要改行?他嘆一口氣說:第一是羨慕作曲家的進益比演員好;第二,導演岳楓說我大有音樂天才,不如改行。誰知近來靈感始終不降臨,人家請我作曲,我無法繳卷,妻子又要養孩子,眞是懊悔改了行。
「人財兩得」中的陳厚,飾一個潦倒的窮音樂家,半夜作曲,早晨煮飯,下午洗衣,内外兼顧,苦不堪言,所以心焦異常,曲譜一點也寫不出。他在拍「人財两得」前去請敎幾位有名的作曲家,他們對他笑着說:寫不出東西時的心焦情形我們都有這種經驗,但是煮飯洗衣一齊來的經驗,恐怕沒有人說得出。(小玉)
二哥怕剃頭
在古時候,皇帝怕人暗算,在理髪剃鬚的時候,左右有人持鎗保衞,以免皇帝在剃刀下喪生,所以有句俗語形容事情的險惡,說是「險過剃頭」,由此可見有許多人認剃頭爲險事,倒是大有來歷。試想,在刀光「剪」影下,至少要坐一個鐘頭,一不小心,可能有流血事件發生,難怪二哥劉恩甲耍怕剃頭了。一個熟練的理髮師尙且不免失手,「人財兩得」中,岳老爺還要叫一個演員飾理髮師,替二哥剃頭,二哥自然要憂容滿面,愁眉不展了。在試演的時候,「理髮師」劉仁傑拿起肥皂刷,先要和他剃鬚,二哥舉手叫道:「慢來」!岳楓問他做什麼?他說:有些心驚肉跳,這把剃刀太亮。引得哄堂大笑。其實,二哥如果眞的蓄了「奇勒基寶」式的鬍鬚,非常漂亮,可是他因爲有了一女朋友,所以不願蓄鬚。「人財兩得」中,他有了鬍鬚,理髪師看他穿了漂亮的西裝誤會了他是主人,强迫他剃頭,他越是推避,越被追逐,鬧出了一塲笑話。
人物介紹
于翠華——李湄飾
于翠華是孫之棠的前妻,因爲捱不慣貧苦生活,和孫之棠離了婚,但是不敢吿訴她的三叔聽。三叔逝世時,還沒有知道她的離婚事件,所以把遺產指定傳給孫之棠的兒子,也就是姪女的骨肉,豈知這一來急壞了于翠華,眼看百萬遺產要落別人家口袋,於是自星加坡趕往香港,希望把遣產弄到手里。李湄飾于翠華一角,施展混身解數,使陳厚乖乖的就範,從欺騙、懷舊、直至眞情流露,她的演技爐火純靑,眞叫人看了過癮。
孫之棠——陳厚飾
孫之棠是一個窮音樂家,窮到妻子懐了孕,沒有辦法請僕人,一切家事親自操作,忙上加忙,再加上一個飛來的前妻,和他捉迷藏地爭奪遺產,眞使他焦頭爛額。前妻的離婚不合法,現在太太的身份成問題,二妻之間難爲夫,孫之棠說什麼誰也不聽,結果得友人髙律師帮忙,解决了婚姻問題,他旣得子女,又獲愛妻,情願放棄遺產。陳厚對喜劇頗有心得,一舉一動惹笑而不過火,非有精湛演技與眞摯情感所不能達到的境界。
裁縫——劉恩甲飾
一個西裝裁縫,自然懂得一套奉承顧客的本領,同時,自己的服裝也整齊挺括,他到孫之棠家去爲孫之棠度身做西裝,却被理髮師誤會他是孫之棠,追着要剃去他最心愛的鬍鬚,鬧得天翻地覆。劉恩甲飾裁縫,不用說他對喜劇是拿手,一舉手,一瞪眼,都是笑料,他做什麼像什麼,絕對沒有身份外的表情與舉動,雖說劇中人物是一個裁縫,但他的一場戲,增加了不少喜劇氣氛,他是觀衆的開心菓,他的喜劇决不會使人失望。
方湘紋——丁皓飾
方湘紋是一個稚氣未除的小婦人,她愛家,愛丈夫,愛未來的子女,在她懐孕待產的時節,來了一個她認為情敵的于翠華。孫之棠對她百般解釋,都不能消除她心里疑團,接着而來的身份不成立,于翠華要謀取她的孩子,簡直把她氣暈了,她發脾氣,拒絕丈夫進房,消極的抵抗。方湘紋不是于翠華的對手,却是孫之棠所深愛的妻子,終於二人和好。丁皓的演技大有進步,加上有稚氣的臉,頗適合劇中人身份,演出極為稱職。
高律師——徐行飾
高律師是孫之棠的朋友,他為了孫之棠的兩妻問題,下了很多硏究功夫,到最後遺產限期前一小時,始把事情攪妥當。他對于翠華開了個大玩笑,先向她說她與孫之棠的離婚不成立,引得于翠華大樂,接着說,離婚雖不成立,但結婚也不成立,他說出當時的結婚地點與結婚手續,條理分明,激得于翠華大怒,却安了孫之棠的心,徐行飾髙律師,短短的一場戲中,精采紛呈,他有條不紊的談話,配合李湄一喜一怒,妙不可言。
趙太太——莊元庸飾
趙太太是于翠華的閨中好友,一個富家太太,她愛饒舌,愛管閒事,當年于翠華與孫之棠的離婚證書上,是她和她的丈夫做証明人。時隔六年,于翠華為了爭遺產,請她把荷蘭文的離婚証明書叫人譯出,不譯還好,一譯出來原來簽名簽錯了地位,變成趙太太與趙先生離婚。害得她一路哭一路找上于翠華的門,因離婚書上寫明無條件的,趙先生堅持不給分文。莊元庸有良好的喜劇外型,有流利國語與銀幕經驗,有凸出的成績。
人財兩得 電影小說
斷斷續續的鋼琴聲,從客廳里傳入臥室,湘紋甜甜地睡着,響了一夜的琴聲並沒有打擾她的睡眠,因爲她習慣了,彈琴的是她的丈夫孫之棠,一個作曲家。
室外的陽光普照大地,射入室内,孫之棠琴畔的燈還亮着,整夜的工作使他困倦不堪,他伸一下懶腰,望望客廳中的一切,凌亂不堪地堆在一起,精神越發不振,但是他必須在中午前完成這些曲子,人家等着要。
「篤、篤、篤」,有人敲門,孫之棠揉着眼睛,打着呵欠站起來開門,門一開,他的精神一振,因爲門外站着是二房東張太太。
孫先生,你怎麽叮叮咚咚鬧了一夜也沒停,你不睡覺,別人還睡不睡?」
房東太太一付失眠的神情,使孫之棠感到非常抱歉,他連聲道歉。張太太哼一聲說:
「你們找到了房子沒有?」
「張太太,我不是跟你解釋過了?我暫時不能搬家,要過了這兩天,等我太太養了孩子再搬。」
「等你太太養孩子?」張太太不耐煩地答:「一個多月前就說耍養了!」
孫之棠點點頭,指指客廳中並排着的三個箱子說:
「她不養有什麼辦法呢?你看,什麼都預備好了,就等上醫院,大概就在這两天了。」
「反正你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孫先生,不是我趕你搬家,你自己想想,房租三個月沒付了,要不是看在老房客面上,我眞跟你不客氣。」
張太太大聲地喊,之棠不能忍受,關上房門,由她在門外叫喊,他走回鋼琴邊。
「之棠!」
湘紋醒了。之棠推門進臥室,温柔地說:
「把你吵醒了,是二房東。」
湘紋憐惜地問:「你又是一夜沒睡?這樣白天黑夜地趕,趕出病來怎麼辦呢?」
「沒辦法,還是夜里比較淸靜,沒有人打攪我。」
湘紋疑心他說自己打攪他,負氣地睡下,之棠皺皺眉,回到客廳繼續工作,寫不上一行樂譜,臥室中又傳來了湘紋的聲氣。
「之棠,我餓了!」
醫生吿訴湘紋,在產前必須多多休息,之棠更細心照料,所有家務自己動手,連燒飯洗衣都不耍湘紋做。
湘紋餓了,孫之棠放下筆去厨房做早餐,圍上圍裙,把粥與菜放入托盤,捧入臥室去。
「你自己吃呢!」湘紋說。
之棠搖搖頭說不餓,趕着出去寫曲,他才坐下鋼琴邊,湘紋又在叫他,拿藥,拿絨線,拿圍巾,差遣得團團亂轉,把預備帶到醫院去的箱子翻得紊亂,藥瓶、圍巾、都耍在箱底找出來。找到後捧進臥室去,咀裡埋怨說:
「哪,你把東西全拿出來,等到上醫院的時候,手忙脚亂,又得理箱子。」
「我沒有把東西全那出來。」湘紋說。
「對了,你沒有拿,是我拿的。」
之棠說完,轉身走出臥室,想蓋上箱子,無論如何關不上,想不關,湘紋不依,逼不得巳,逐樣淸理,才把箱子關上,滿頭大汗去趕寫曲譜。
「之棠……之棠!」
湘紋又在聲聲喚叫。她是個年靑帶些稚氣的少婦,又是初次懐孕,所以把麻煩丈夫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她不管他理不理,催他打電話去醫院,問上次留下的房間。
她再三地打斷之棠工作,激得他憤怒異常,跳起來對着臥室大嚷:
「湘紋,我今天非得把曲子寫完不可,你讓我這段寫完行不行?」
湘紋萬分委屈,泣然欲涕說:
「你這神氣就像你的工作比孩子還要緊。」
「當然孩子耍緊。」之棠鐵靑了臉說:「可是不工作孩子就得餓死。」
湘紋不服氣,反駁他說:
「孩子吃奶有我餵他,不用你操心。」
「孩子吃奶,可是你要吃飯!」
這句話可讓湘紋傷了心,哀哀痛哭,之棠心不忍,臉色緩和下來,摟了湘紋哄著說:
「別哭,別哭,這两天不應當這樣緊張。」
好容易哄得湘紋止住哭聲,客廳中的電話鈴聲大响,之棠急忙走出去,從沙發下找出一條電綫,拉出來,哎,是熨斗,再找,總算找到電話。
是製片公司中打來的,催之棠的曲譜配音。之棠無法回答,推到明天,公司中人不肯,電話里說來說去為配音,湘紋在臥室插咀說:
「之棠,你不能讓人家為難,你不是答應今天交給人家的嗎?」
之棠不聽猶可,聽了心中直冒火,他忘記自己在聽電話忿忿然說:
「不錯,是我答應的,可是一天到晚打攪我,叫我怎麼工作呢?」
對方在聽電話的人,以為之棠罵他,也大光其火,和孫之棠對吵起來,湘紋却在臥室哇哇大叫肚痛。
孫之棠嚇得扔下電話,跑進臥室去,湘紋催他叫「的土」,汽車來了,她的肚子不痛了,車子開走後,她又痛起來,急得之棠又跑門去追汽車,汽車早已遠去,房東張太太聽聲出來,大罵之棠不顧門口,之棠無暇理她,跑進房去,張太太遞給他的一封信沒空看,奔向床前。
「肚子備得利害嗎?車子開走了,我再去打電話。」
湘紋平靜地回答不要了。指指他手上的信問:「誰的信?」
「唱片公司李經理請吃飯。」之棠在床沿拆開信來看了看說:「就是今天晚上。」
「你的生意來了,一定是耍請你寫幾隻時代曲。」
湘紋非常樂觀,之棠却不感興趣,他想不去,湘紋催他去,把自己的圍巾遞給之棠,之棠的大衣與手錶都已典當了,所以他把小鬧鐘放在口袋中,以免忘記時刻,因爲他在赴宴前,必須去借點錢。
晚上八點鐘,之棠到達李經理家。在沙發一角,坐着女主人李太太,正與一位趙太太談着話,看見孫之棠,趙太太就說:
「這是孫之棠嗎?我認識他離了婚的太太。」
「哦,他離過婚的?」
「可不是,他們離婚,還是我做證人的,我不肯做呀!」趙太太說起來還是一臉的委屈相,她搖搖頭說:「沒辦法,他太太硬拉着我們两夫妻做證人。」
客人繼續進來,李太太起身去招呼別的女客,趙太太就走到孫之棠的面前,招呼說:「孫先生,好久不見了。」
「趙太太,幾時到香港來的?」之棠答。
「來了一年多了,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住在建德道廿八號。」
「翠華正到處打聽你的地址呢!」
孫之棠一聽到「翠華」二字,大吃一驚,這是他離了婚的那位妻子的名字,她打聽自己做什麼?
「她在香港?」之棠問。
「在星加坡,可是她說要到香港來找你呢!」
之棠更加不安,他不願見前妻,尤其聽到趙太太說起翠華尙未結婚。
之棠把這消息帶回去說給湘紋聽,湘紋很擔心他與翠華見了面會死灰復燃,她試探着問:
「你從來不提你離婚的事,到底你們是爲什麼離婚的?你欠了她瞻養費沒有?」
「根本沒有贍養費,我那時候跟現在一樣窮,爲了窮,她吃不了苦過不慣。」之棠坦白地說。
「哦,她嫌你窮。」湘紋想了一想說:「也許她現在又懊悔跟你離了婚。」
「懊悔有什麼用?我已經結了婚了。」
「人家老遠從星加坡跑來看你,你一定很感動。」
「別胡說,我不歡迎她來。」
之棠這句話,就是湘紋等待着的回答,她急忙說:「那你何不叫她不要來」」
湘紋咀里說着話,又不想棠之看見她的不樂意,假裝着翻報紙,却看見了一段找孫之棠的廣吿。
「咦!你瞧!」湘紋詫異地說:「有個律師登報紙找你呢!」
孫之棠瞧着她手指處看。
「孫之棠君鑒 見報務請立卽駕臨皇后大厦吳仰安律師事務所,有要事接洽。」
之棠讀了又讀,自慰說:「同姓同名的人很多,不見得是我。」
但是湘紋並不這樣想,她說:
「這個人也找你,那個人也找你,這事情奇怪,一定跟那個女人有關係。」
夫妻兩人在討論的時候,于翠華已從星加坡到達香港,去接她的是趙太太。
「現在這個年頭不好,不怪你們年靑人,就是我們老頭子,也一天到晚鬧着要雖婚。」趙太太說。
「眞的?」于翠華放下粉鏡,微笑着說:「快別理他,這麼大年紀,讓人家笑話。」
說完,拿起鏡子塗口紅,趙太太打趣說:
「得了,別打扮了,還不够漂亮嗎?我看你眞是愛孫之棠。」
「那倒也不一定,這麼些年沒見面,怎知道他變成什麽樣子了?「翠華淡淡地回答。
「噯,這麼着好不好?如果一見面你很滿意,你就對我做個暗號,我馬上一個人就走,要是不滿意,你也做個暗號,我就說這地方出門不大方便,還是住在我家里好,我們就一同走。」
趙太太異想天開,于翠華很樂意照她的辦法做,於是决定以手帕放在鋼琴上爲暗號。
她們一路上孫之棠家去,孫之棠還在對湘紋保證,不讓于翠華去看他,但是,的士司機拿了箱子上來了,箱子上面掛的紙片上,赫然于翠華三宇。
箱子擲地聲,驚動在臥室中的湘紋,起初,她以爲之棠做家務闖了禍,之棠有氣無力地吿訴她,有客來了,隨手關上了臥室門。
隨着箱子進來的是翠華和趙太太,翠華要之棠帮她付車錢,之棠無奈出去付,進來時,翠華已經把手帕放在鋼琴上,可是趙太太沒注意,因爲她看見了客廳中晾着的乳罩與女衫。
「孫先生,你們這里住幾家了?」趙太太問。
「樓下就是我們一家。」之棠答。
「你這些女人衣裳那兒來的?」翠華也發現了乳罩,追問孫之棠。
趙太太很天眞地勸翠華不耍鬧,祇耍之棠以後好好地就算了,翠華順水推舟,先打發趙太太走,孫之棠要她一起走,翠華不肯,之棠說:
「翠華,你住在這兒實在不大方便。」
翠華不理他。臥室里傳了聲音出來,湘紋大叫:
「之棠!你在跟誰說話?」
「翠華來了!」之棠低低地回答。
「誰呀?」湘紋沒有聽明白,再問。
翠華的神情也緊張了,問:
「那是誰?」
「是我太太。」
翠華大吃一驚,走前一步說:
「你結了婚了?」
「當然結了婚了。」之棠坦然說。
「你有了小孩沒有?」
「沒有。」
翠華鬆了一口氣,弄得之棠莫明其妙,湘紋在臥室中連連追問,之棠打開臥室門說:
「翠華來了!」
「翠華?」湘紋的聲調中充滿怒意。
「噯,是我,你好?」翠華却意外的和悅,她回頭問之棠說:「她叫什麼名字?」
之棠不情不願地吿訴她,翠華得意地說:
「湘紋,我進來看看你好嗎?」
「噯,不行,不行,之棠你不能讓她進來。」
之棠立刻把門關上,翠華毫不在乎地說:
「我總想知道她長的是什麼樣子。」
孫之棠指着牆上的照片給翠華看,翠華讚一聲:
「呦,眞漂亮!」
之棠不理會她說什麼,進了臥室去。翠華見她進去,立刻打電話,鬼鬼崇崇說:
「吳律師,是我啦,我找到他啦,他沒有小孩。」
她瞧見孫之棠又出來,趕快掛上,孫之棠有點懐疑,但又不便問她,祗說:
「你變了,從前不是這樣。」
「是嗎?」翠華攏攏頭髪,飄了他一眼說:「這兩年我經過許多事情,也難怪我變了。」
「是什麼事?」
「去年我三叔死了,你不記得了,在星加坡開飯店的那個三叔。留吓一百萬塊錢給我。」
翠華得意洋洋地說著,孫之棠有些心動,繼而一想,兩人根本離了婚,還有什麼可說。翠華再吿訴他,她先得了一萬元,其餘的耍等一週年後,法律上手續完成才可以到手。
两人談著話,時間已是下午两時,湘紋在臥室中說家里沒菜,不預備招待客人,翠華自吿奮勇入㕑,先把菜讓之棠端進房給湘紋吃,隨後二人對面坐下吃飯,有一搭,沒一搭地談着。翠華批評湘紋不會管家,之棠就吿訴她,湘紋懷了孕,沒法做家務。話剛出口,翠華放下筷子,神色又趨緊張地問:「馬上就耍養了?什麼時候養?」
「這很難說,我也不知道。醫生也算不出。」
翠華鬆口氣,站起來走到之棠背後,扶着椅背說:
「咳,都是你,不然你想,我們二人加上一百萬塊錢,我們可以到世界各國去遊歷,你也不用爲生活發愁,可以到歐洲去學音樂,儘量的發展,寫出最偉大的交响曲,你不是一直這樣想嗎?」
之棠給她說得沉醉了,簡直要軟化。但是湘紋的呼喚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急急擺脫翠華摟着他的手,翠華帶誘惑性地笑着說:
「瞧你,眞怕太太,從前可一點都不怕我。」
說着,把臉貼上去,之棠掙扎着說:
「不是,這两天不能讓她受剌激,她就要養了。」
翠華馬上鬆了手,口里直嚷糟糕。但是她還得保持對自己的希望,不敢立刻發作,她下厨房去沏了二杯茶,哄着之棠彈鋼琴,務求能勾起他的回憶,使他懐念舊時的情感,她這樣舉動,弄得孫之棠手足無措,他說:「翠華,我老記住我們六年前在爪哇離了婚。」
「對了,在爪哇用的是荷蘭文,誰知道它說些什麼,怎麽能認眞?」
翠華一派輕鬆,之棠着急萬分。
「你想賴,我們一人有一張離婚證書。」
「也是荷蘭文。」翠華抱定不認賬的態度說:「我一句都不懂,怎知道我們是真離了婚了?」
「雙方同意,怎麼會是假的呢?」
之棠跳起來了。門外有人敲門,之棠立卽不敢大聲,他知道來的是誰。翠華去開門,是二房東催租,翠華不徵求之棠同意,很爽快把房租付淸,另外給了水電費,樂得張太太連連道謝而去。
翠華關上門,之棠從門後轉出說:「我不能讓你出這個錢。」
「呵,你別這樣。」翠華用雙手握着之棠的手,表情十足地說:「你不明白麼?我能够帮你一點忙,我心里眞痛快。」
之棠鬱鬱地掙脫她的手。門外又起了一陣猛然的打鬥聲,趙太太像一陣颶風似地冲進來,大哭大喊:
「孫之棠、于翠華,你們害死人了,我來跟你們拼命!」
「趙太太,有什麼事?」二人異口同聲問。
趙太太一時泣不成聲,把手中的文件交給翠華,原來是他們的一張離婚證書,翠華請趙太太找人翻譯的,翠華驚喜地問:
「不合法是不是?我知道我們離婚不成立。」
「合法,合法!」趙太太哭着說:「可是你們簽名簽錯了地方,你們成了離婚證人,而我們夫妻倆成了離婚人,老頭子和我離了婚,一個錢瞻養費也拿不到,你這害人精,害苦了我!」
趙太太繼續大哭,于翠華樂得大笑,這些話湘紋都聽見的,她也哭了,把之棠叫進臥室去,二人爭論起來,湘紋耍他决定誰去誰留,之棠左右為難,等趙太太走後,他和翠華開談判。
翠華一派主婦作風,開始整理房間,咀里嘰咕說:
「之棠,你這屋子不但亂七八糟,傢俱也不够用,一會兒,我出去看看,買套新傢俱。」
「不,不,翠華,我有話跟你說,你坐下。」
之棠先坐下,翠華一扭身坐在他膝上,他用力推,翠華含笑地說:
「跟自己丈夫親熱親熱有什麼關係?」
之棠痛苦萬分,推開翠華,對她説:
「翠華,我得吿訴你,老實說,我是絕對不會離開湘紋的。」
「當然,尤其在這時候,她正要生孩子,你得照應她,我們二個都得陪她,女人比男人細心,有些地方我比你想得週到,錢你不用擔心,有的是。」
「這不是錢能够解决的事,她說的,你不走她走。」
「她眞要走,誰也不能攔她,我是看她可憐,沒結婚就做了母親,她那孩子生下來可以過繼給我。」
翠華一味自說自話,之棠却束手無策。翠華就離去購買東西,臨走還鄭重地問湘紋愛吃什麼。
她出外沒有多久,送東西的人絡繹不絕,送砂鍋鷄,送沙發,送地毡,送無綫電,送嬰孩用品等等,把湘紋氣得淚流滿面。
「就憑她幾個臭錢,丈夫讓她買了去了,我的孩子可不賣,無論如何不賣。」
她又哭又鬧,孫之棠急得搓手,空言安慰她:
「湘紋,你安靜點,你不能發脾氣,自己傷身體,對于孩子也沒有好處。」
「孩子還沒有出世,倒已經是別人的了。」
湘紋索性起身,把東西亂擲一頓。之棠說:
「她並不是一定要孩子呀,她願意把孩子過繼給她,也是她的好意。」
事實是事實,翠華與之棠的離婚不成立,湘紋的地位是不能維持下去,這給未來的小母親很大的剌激,她使勁地罵之棠,罵翠華,但都是沒有用的。她恨之棠沉醉在發財夢中,她决定要離開他。
晚上,翠華回來睡覺,她打算睡長沙發上,從箱子取出一襲華麗的睡袍,給之棠看,之棠怕她泥住他,連忙入臥室,誰知湘紋不要他同睡,她板起臉說:
「從今天起,我叫你孫先生,你叫我方小姐,是你自己說的,我們根本不是夫妻,男女有別,請你自己放尊重些,我的房間你不能隨便進來。」
之棠素知湘紋有些孩子氣,他怔了一會,仍舊坐在床沿解開領帶,準備上床,湘紋不依,亂打亂推,又把枕頭與毡子擲出房門外,之棠無奈拾起到客廳,客廳中迎接他的是翠華的幸災樂禍的笑容。
這一夜,方湘紋睡在床上,于翠華睡在長沙發中,孫之棠靠着椅背,縮作一團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翠華入厨做早餐,之棠先把早餐送入湘紋室中,出來時打了噴嚏。
「你傷風得很利害?」翠華問。
「昨天晚上着了凉了。」之棠滿面寒意地說。
「我已經打了電話給醫生,又叫了栽縫和你做大衣,冬天的西裝也該添兩套了。還有理髪師。」
翠華坐在沙發挫指甲,又打電話,指揮若定,打完電話,在手袋里取出鈔票,要之棠到對面去買雙新鞋,不由他分說,一把推出門去。
孫之棠岀去後,理髪師來了,翠華叮囑他說:
「孫先生一會兒就來,他一進來,你就給他理髮刮鬍子,他耍是不願意,你別理他,他有怪牌氣。」
她把他領到厨房去等,在客廳,怕弄髒了新地氈。
接着裁縫來了,她又叫他上厨房等候,那里知道理髮師誤會裁縫是孫先生,二人在厨房一追一逃直鬧到客廳來,翠華給他們的纏夾攪到又氣又笑。
孫之棠回來時,醫生也來了,先診病,再量衣,又理髪修面,消費了整個上午,于翠華在厨房弄妥午餐,端上桌子,正安排碗筷,房東張太太端了一碗菜進來。
「我給孫太太燉了隻鷄送來。」
「謝謝,謝謝。」翠華客氣地說:「你幹麼破費?」
「孫太太這兩天好嗎?」
「我很好!」
「不。」張太太詫異地望她一眼說:「我不是說你,我是說孫太太。」
「噢!」翠華故意做成弄錯的樣子,指指臥室說:「那個孫太太,她也很好。」
翠華的外貌是妖艶的,舉止輕浮,引起房東太太的疑心,她本來好管閒事,於是不客氣地問:
「你是不是他嫂子?」
翠華搖搖頭。張太太轉問孫之棠,之棠含糊地說:
「她是來帮着照應湘紋的。」
「是什麼親戚?」張太太打爛砂鍋問到底。
翠華不耐煩,碍着之棠不好直接說,她轉灣抹角說:
「我是她丈夫的太太,你說該叫什麼?」
「那末,她是你丈夫什麼人?」
「這個……」翠華特意頓一頓說:「名稱倒是有的,不過不大客氣。」
「姨太太,是不是?」
張太太口沒遮攔,孫之棠又窘又氣,湘紋在房里聽得淸清楚楚,氣得混身發抖,她不顧一切走了出來,對孫之棠斥道:
「之棠,你就眼看着她侮辱我?你沒長着咀,你不會解釋?」
張太太不等他們解釋,就說:「孫先生,對不起,月底還是要請你們搬家。」
一轉身出去,把一碗鷄也帶走。
孫之棠指責翠華說:「你看,這算什麼呢?」
「這有什麼要緊?」翠華輕描淡寫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搬家的,這屋子根本不够住。」
湘紋逼着之棠去解釋,翠華勸她不耍生氣,湘紋不理她,但翠華攔住房門說:
「今天覺得怎麼樣?可以起來吃飯嗎?一塊兒吃,我們談談。」
她在碗廚中取出一付碗筷,放在桌上,又載飯拉椅,殷勤萬分。
湘紋打量客廳四周,喃喃自語:
「自個兒家里,這間屋子我都不認識了。」
她帶着諷剌的眼光,使之棠苦笑,三人圍桌坐下,翠華故意做作,夾菜勸食,口里說來說去,無非想霸佔湘紋的孩子,湘紋旣是食不下咽又滿腔怒氣,一言不發,跑回臥室,重重地把門關上。之棠想勸又不敢,獨個兒上庭院踱方步。留下翠華暗暗好笑。
電話鈴響。是吳律師打來找孫之棠,翠華怕他洩漏天機,想不給之棠聽,之棠已經聽見,搶了來聽。
「我們登廣吿找你,看見了沒有?」吳律師說。
「我看見了。」
之棠一邊回答,一邊拉住翠華想按斷電話的手。
「孫先生,你有兒子沒有?」
「沒有,我沒有兒子。」
「你明天早上九點鐘以前會不會有兒子?」
翠華開响了無綫電想搞亂,之棠扭停它。
「明天早晨九點鐘以前?定做也沒那麽快,爲什麼耍九點鐘之前?」之棠問。
翠華在一邊急得團團轉。
「你的兒子耍在九點以前生下來,他可以拿到一筆很大的遺產,一百萬塊錢!」
「一百萬,噯!」之棠想了一想說:「可以辦得到,我太太正要生孩子!」
「你太太?」
「我太太——孫太太。」
翠華恨極了,揭開琴蓋一陣亂擊。
王醫生仍然叫之棠出去,翠華也給推出來,翠華又驚又怒,問:
「哦,你是說跟你同居的那個女人。」吳律師說。
「照法律上也許只好這麼說,可是我們的確是正式結婚的。」
於是,吳律師要孫之棠到事務所去走一趙。之棠掛上電話,他明白了翠華對他的一切,他說穿她的謊言,他直斥她的陰謀。翠華哭了,她說:
「真是不公平,是我的三叔,銀倒要傳給她的兒子,三叔沒見過她,根本不知有她,他打算傳給我的兒子。」
「你沒有兒子?」
「沒有。沒有的話就歸我,他以為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他最不贊成離婚,所以我一直瞞着他,沒敢吿訴他。」
「你反正一天到晚撒謊。」
翠華還想挽回局面,抹乾眼淚,假作歡容說:
「可是我對你是眞心,之棠。」
孫之棠甩脫她伸過來的手,走向臥室。
緊張的一刻終于來臨,第二天湘紋臨盆了,在家里,醫生與護土,在門口,有翠華請來的二個私家偵探。
孫之棠發現私家偵探後,為之一怔,問翠華:
「這两人是誰?」
「私家偵探。」翠華精神頹喪,坐在無綫電旁。
「偵探?要偵探幹什麼?」
「我不能不防備呀,到時候,她孩子沒養下來,你們倒抱了一個孩子來,說不定養了女的,換了男的。」
翠華理直氣壯地回答他,把孫之棠氣得發抖,他憤然作色說:
「你想得眞週到,我們不是那種人,我就是養了兒子也不會要你的錢。」
時鐘指着八點四十分。之棠緊張萬分,翠華欣然而笑,距離得遺產時間僅廿分鐘。
孫之棠的朋友高律師來了,翠華問他爲什麼請律師來,之棠正經地說:
「你一定耍問,我就吿訴你,我把我的離婚與結婚證書都拿去給他看,請他硏究硏究,有沒有辦法跟你離婚。」
翠華不以爲然,撇撇咀說:
「你趁早死了這條心,我怎麼也不跟你離婚」
高律師在皮包里取出文件,對之棠說:
「你明白不明白?你犯了重婚罪。」
高律師這句話叫翠華樂了,她高興地參加他們談話,批評之棠喜新忘舊。高律師接下去說:
「你到過澳洲旅行。」
「我們上那兒去渡蜜月。」翠華搶著說:「咳,那兒想得到他心變得那麼快。」
「你們在湯加島結婚的。」
「是呀。」翠華不容之棠開口,把高律師當作親人般向他訴說:「嫁了他不到二年,就讓他扔了,現在我三叔寄了幾個錢給我,他倒又來打我的主意。」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號到湯加島,四月二十三日離開,那麽你們在那里沒有住滿七天,要是住滿七天,你們的婚姻才有效!」
高律師說來不慌不忙,于翠華頓時像被澆桶雪水,孫之棠可高興了,指着翠華說:
「照這麼說,我跟她根本不算結婚了?」
「在法律上,你們的婚姻是不成立的。」
之棠不能解决的事,終于獲得解决,他跳到臥室門口,請護士轉言給湘紋,翠華泫然欲涕,情急地罵:
「孫之棠!你別胡說八道,你騙不了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吿你重婚!」
她一跳跳到高律師面前,手指到他臉上,罵:
「你也不是好人,你們串通了的,都是一黨。」
高律師完成任務,無意捲入吵鬧漩渦,他吿辭走了。于翠華跳來跳去罵,孫之棠不睬不理。漸漸地,她消失了怒氣,眼眶中充滿眼淚,情感衝動地說:
「你現在有了別的女人,你的心,你的感情,什麼都給了她,連我三叔的錢,都成了她的了。」
之棠知道最使翠華痛心的事是一百萬元遺產,他說:
「你別難受,我拿到了,我不會要一個錢的。」
「哼,你倒眞大方,肯把錢給我。你明知道沒希望,樂得慷慨!」
時鐘指着八點五十分。
門外又來一個護士,原來的護士一見就說:
「你來得正好,快了,快了!」
之棠與翠華的神經緊張起來。翠華怕里面出花様,耍進去看,之棠怕她搶孩子,擱住不放,二人扭作一團,翠華情急智生,隨手拿起一樣東西,把之棠擊昏,她飛也似的趕去臥室,手還在門把上,里面傳出一陣陣嬰孩哭聲。
時鐘指在八點五十五分,翠華進了室又出來,歡歡喜喜地叫醒之棠,吿訴他得了個女兒,還說:
「那小東西長得眞可愛。」
「翠華,我得了個女兒,我眞髙興極了!」
「我比你髙興,你添千金,我有一百萬。」
但是孫之棠不是這様想,他興奮而驕傲地說:
「我的運氣比你更好,我有湘紋,又有孩子,還有我的音樂!」
他忘記一切地坐上琴椅,快樂地彈奏。
王醫生從臥室中仲出頭來說:
「孫先生,快來!快來!」
孫之棠急忙迎上去,只見二個看護,各人手里抱一個嬰孩,向他道喜說:
「這是個男孩子,他的姐姐比他大幾分鐘!」之棠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他轉向床邊叫:
「湘紋!」
湘紋安靜地入睡,她在極度疲乏中。
「那男孩子是那兒來的?」
「雙胞胎!」之棠樂得裂開咀儘笑:「生了雙胞胎。」
「我不能相信,簡直太奇怪!」
時鐘正指着九點。
孫之棠不管于翠華信不信,他覺得他的生命一下子充實了,飽滿了,他愛湘紋,湘紋不再會離開他,他愛孩子,一下子來了二個,二個美妙的小傢伙。
他坐在琴畔,順手彈起琴來,他發現自己有新的創作,新的風格,他對翠華的絕望神情視若無覩,他跟着琴聲喃喃地說:
「湘紋,我們太好了!」
翠華爲他的興奮感動,他明白他與湘紋之間的愛,之棠不會要她的一百萬,她輕輕地說:
「之棠,她給你雙胞胎,我給你五十萬。」
「我不要,我只耍我的兒女。」
翠華凄然地說:
「我不是給你,是給我們的兒女的。」
孫之棠的運氣眞不錯,「人財兩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