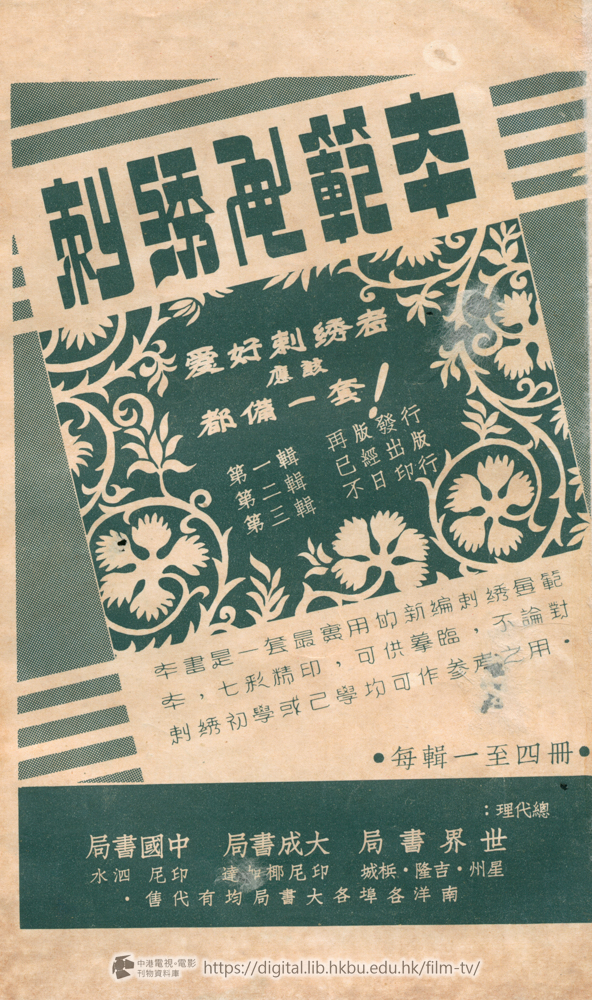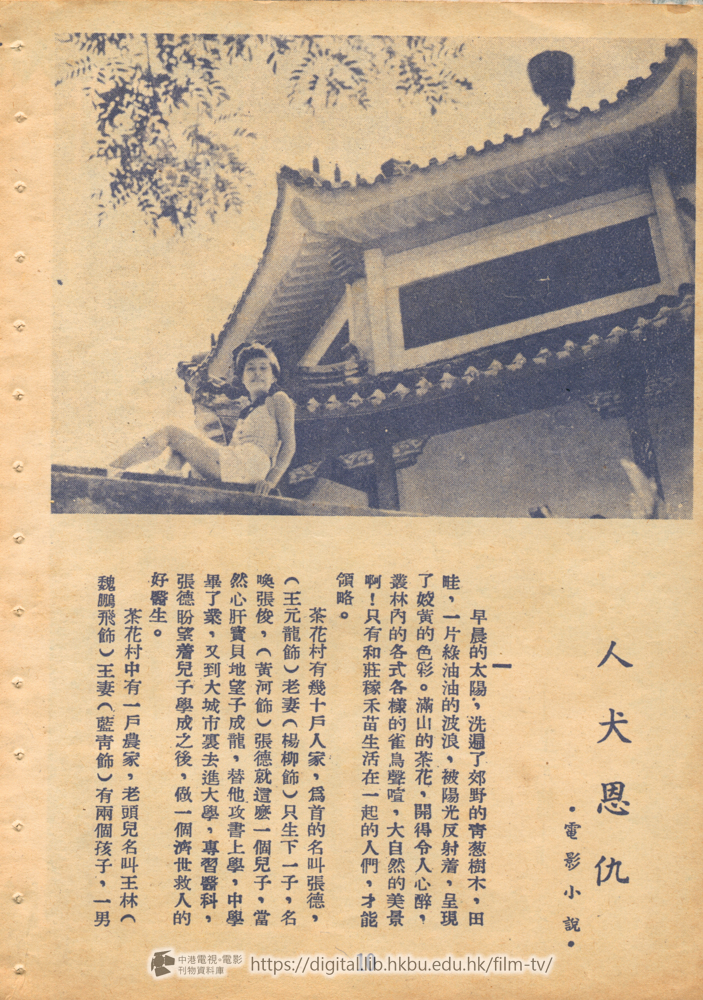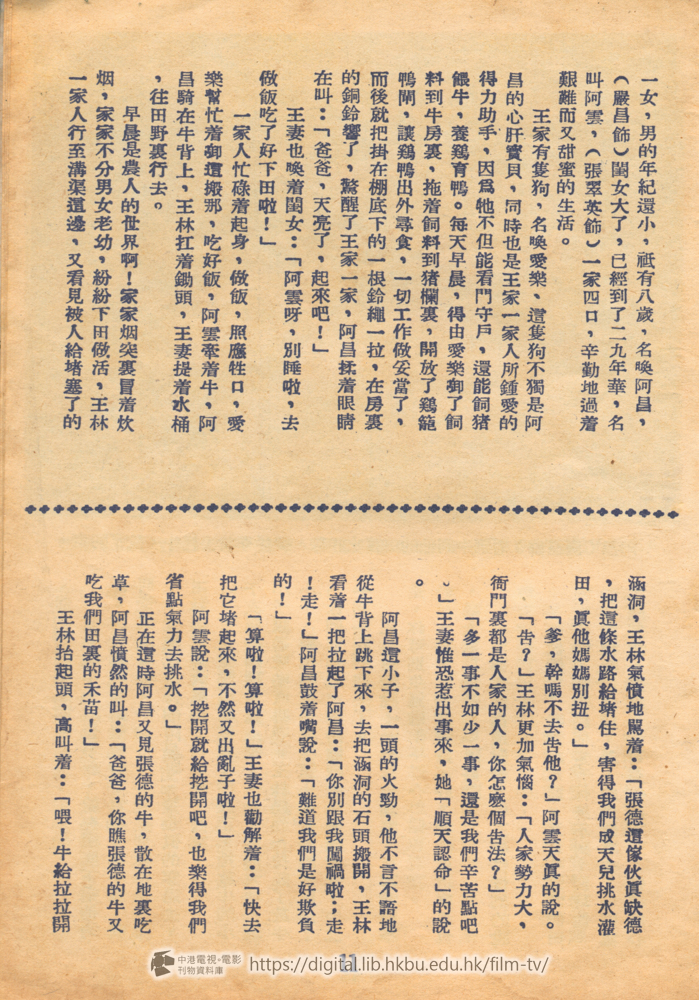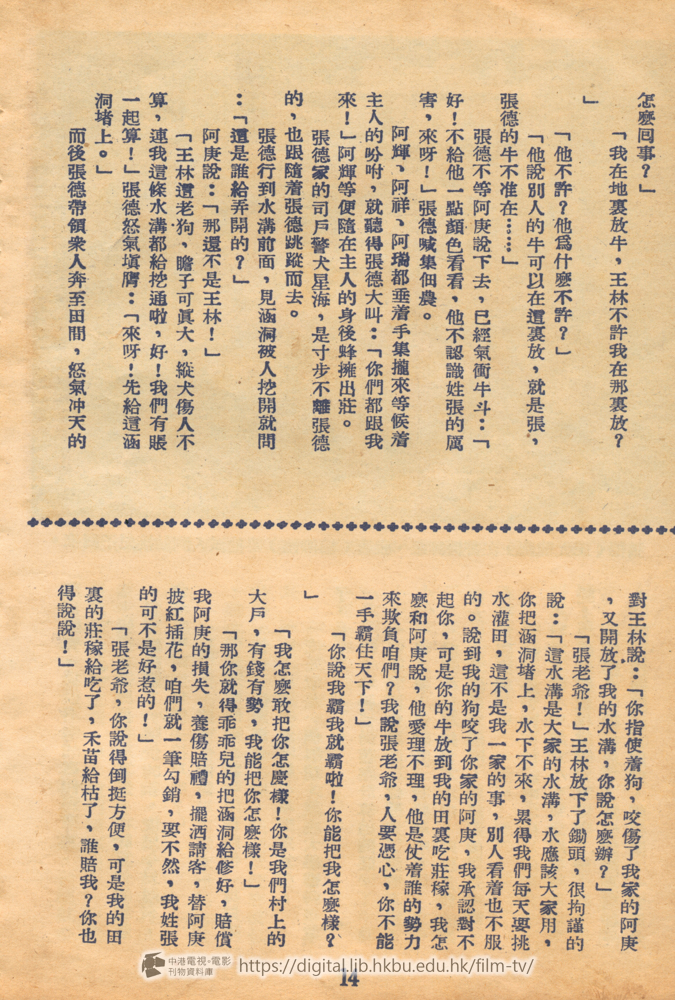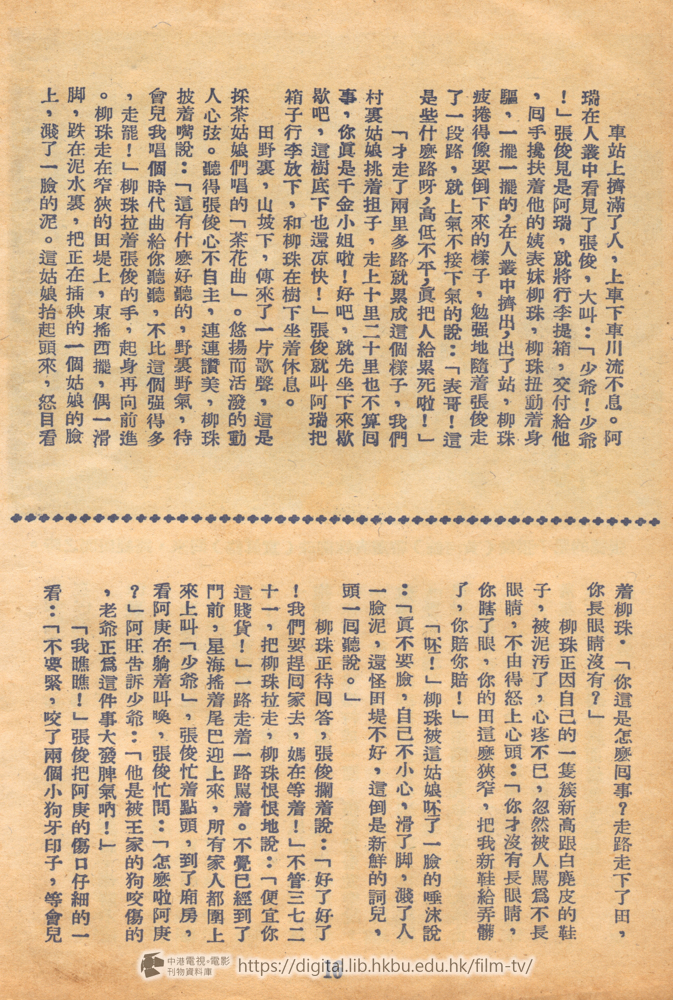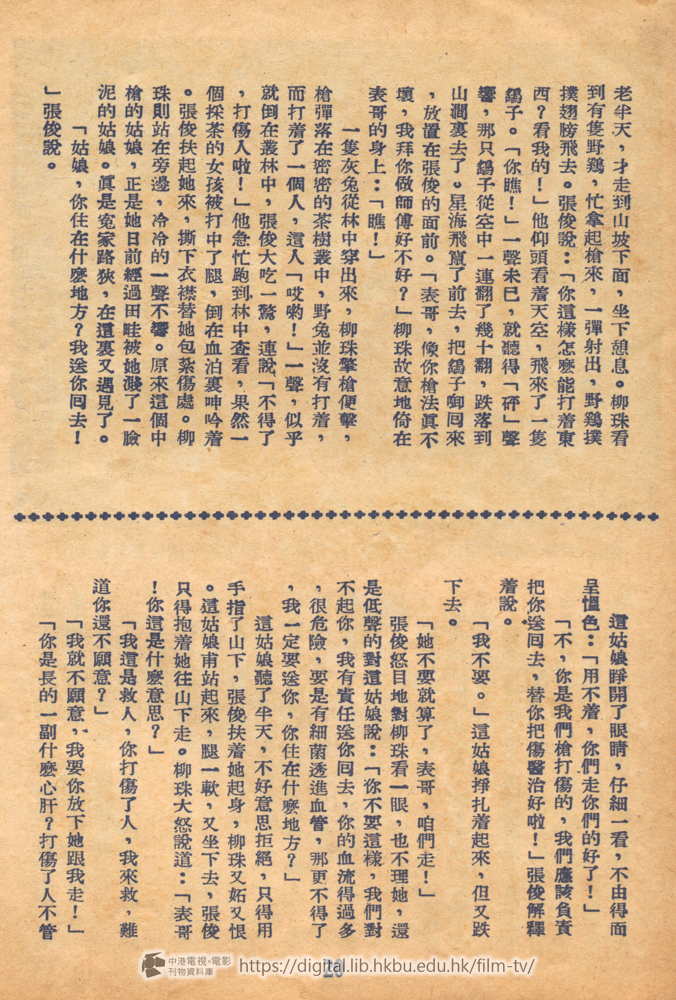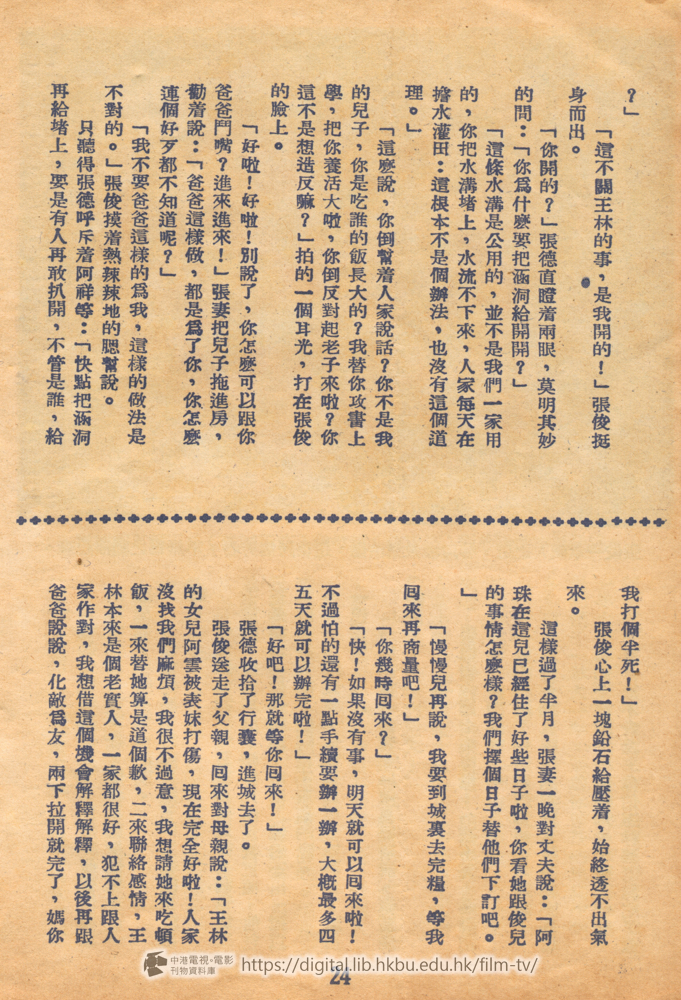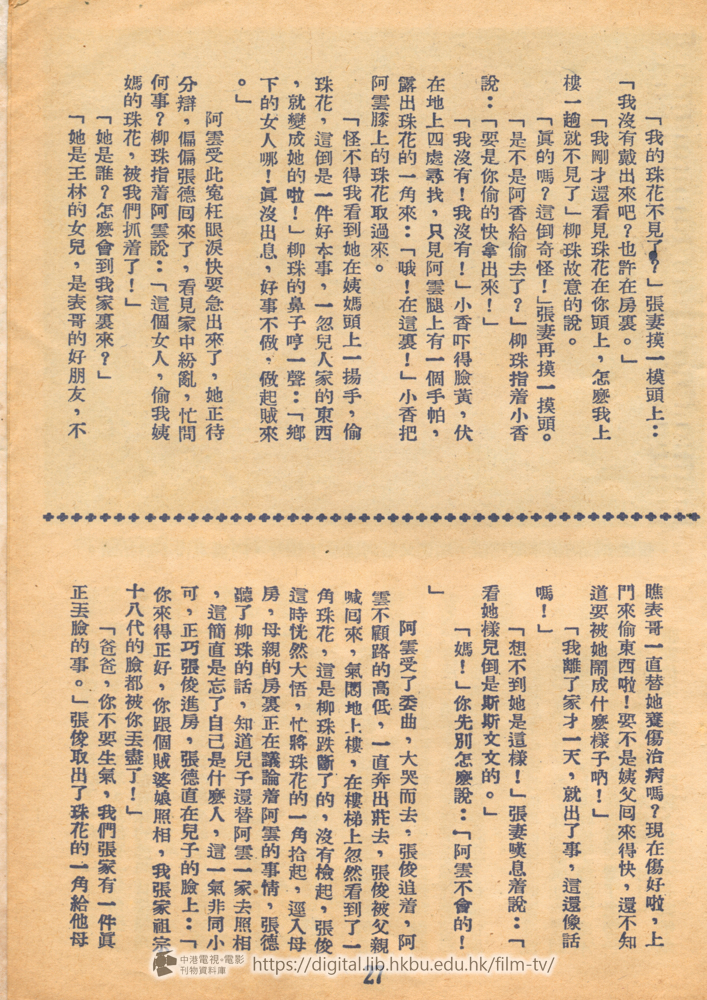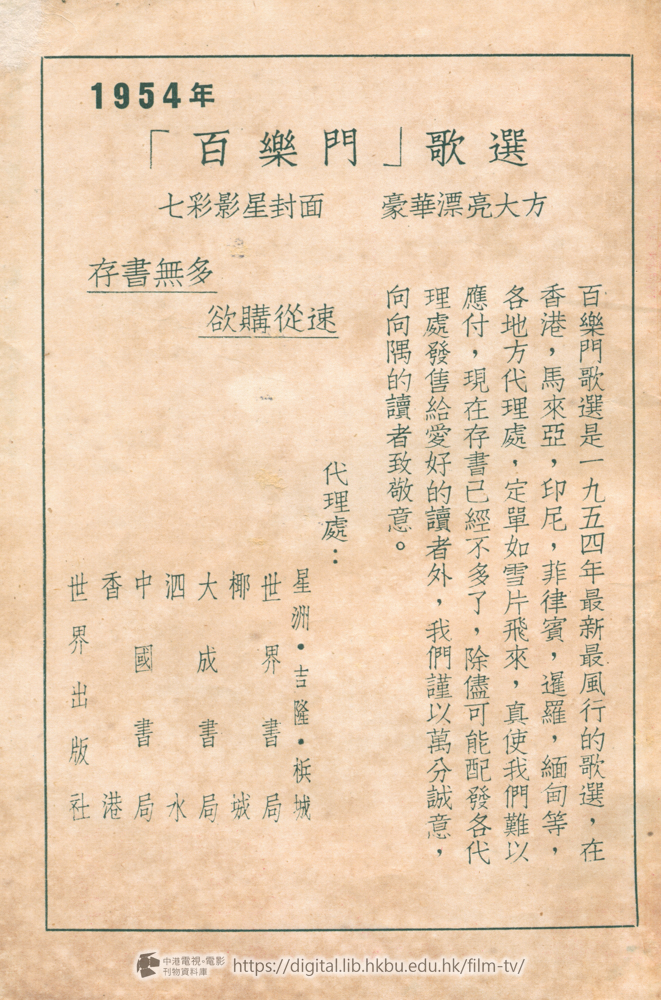黃河的素描
黃河這些年來演了不少的戲,「人犬恩仇」中的黃河,是演一個鄉村中富有的農家的兒子,雖然他已 由中學而大學,得來了不少社會知識,可是他也得來了不少人生經驗,他感到他的父親所行所爲,並不滿 意,所以他就力勸他的父親改弦易轍,從新做人。最後,他果然得到了成功;雖說這個成功是由於偶然的 外力所致。
黃河原來是學醫的,他父親希望他成爲一個能够醫世救人的良醫 ,但他偏偏喜歡電影戲劇,當十八年 前,那時他才十六七歲,他就逃出了醫科學校,走上舞台。他不專門去學習醫科了,他要學習什麽都可以 扮演的演員。誰知在這「人犬恩仇」裏,凑巧他是扮演醫科大學的學生,可說是,「璞玉返眞」了。(陳泰)
「風流花旦」的童眞
說起童眞這個人來,她的來歷倒相當的「藝術」,雖然她現在是以「風流花旦」的招牌出名的,但她最初確想走上一本正經的道路 。
顧而已,高占非等在港開設大光明公司,很想發掘新人,而已在上海認識童眞,便電邀來港,誰知童真到港後,大光明已遷囘上海,於是未能走入「正旦」之途,便「流落」成爲「花旦」了。然而童眞却因禍得福,她演這一路戲倒非常吃香,成為藥中甘草,幾乎差不多的片中都少不了她,她嬴得了一個「風流花旦」的雅號。(黃山)
張翠英結婚花絮
張翠英和李翰祥的閃結電婚, 震驚了港九電影圏內。他們相識了僅僅一個禮拜,便宣吿在九龍樂宮樓結婚。中間戀愛的過程,一共祗有七天,所以當這消息初初傳出時,許多人都不相信,直到接着大紅喜帖,這鐵的事實放在面前,也不容你不相信了。
結婚的那天,賓客如雲,整個樂宮樓都被李張兩府包了下來,嚴俊和嚴幼祥爲男女兩家的主婚人,姜南,蔣光超爲介紹人,由永華公司的總經理李祖永證婚。當時銀光閃灼,最惹人注目的有林黛,曾鷺紅,韋偉,李湄,而胖子劉恩甲担任司賬,忙得一頭大汗,頻頻叫苦不已。(力羣)
王元龍的塑像
王元龍以「銀壇霸王」號稱於世,爲的是在十八年前,他和金素琴一部電影「楚霸王」,由他飾演項羽而得名,誰知竟留傳到現在,幾乎無人不知這「霸王」王元龍了。
誰知他在十八年後的今日,又演了一部「霸王」戲,這個霸王,是「人犬恩仇」中他所演的角色,也稱王道霸,可說是無獨有偶。(司馬長靑)
人犬恩仇
・電影小說・
一
早晨的太陽,洗遍了郊野的靑葱樹木,田畦,一片綠油油的波浪,被陽光反射着,呈現了姣黃的色彩。滿山的茶花,開得令人心醉,叢林內的各式各樣的雀鳥聲喧,大自然的美景啊!只有和莊稼禾苗生活在一起的人們,才能領略。
茶花村有幾十戶人家,爲首的名叫張德,(王元龍飾)老妻(楊柳飾)只生下一子,名喚張俊,(黃河飾)張德就這麽一個兒子,當然心肝寳貝地望子成龍,替他攻書上學,中學畢了業,又到大城市裏去進大學,專習醫科,張德盼望着兒子學成之後,做一個濟世救人的好醫生。
茶花村中有一戶農家,老頭兒名叫王林(魏鵬飛飾)王妻(藍靑飾)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年紀還小,祗有八歲,名喚阿昌,(嚴昌飾)閨女大了,已經到了二九年華,名叫阿雲,(張翠英飾)一家四口,辛勤地過着艱難而又甜蜜的生活。
王家有隻狗,名喚愛樂,這隻狗不獨是阿昌的心肝寶貝,同時也是王家一家人所鍾愛的得力助手,因爲牠不但能看門守戶,還能飼猪餵牛,養鷄育鴨。每天早晨,得由愛樂啣了飼料到牛房裏,拖着飼料到猪欄裏,開放了鷄籠鴨閘,讓鷄鴨出外尋食,一切工作做妥當了,而後就把掛在棚底下的一根鈴繩一拉,在房裏的銅鈴響了,驚醒了王家一家,阿昌揉着眼睛在叫:「爸爸,天亮了,起來吧!」
王妻也喚着閨女:「阿雲呀,別睡啦,去做飯吃了好下田啦!」
一家人忙碌着起身,做飯,照應牲口,愛樂幫忙着啣這搬那,吃好飯,阿雲牽着牛,阿昌騎在牛背上,王林扛着鋤頭,王妻提着水桶,往田野裏行去。
早晨是農人的世界啊!家家烟突裏冒着炊烟,家家不分男女老幼,紛紛下田做活,王林一家人行至溝渠這邊,又看見被人給堵塞了的涵洞,王林氣憤地駡着:「張德這傢伙眞缺德,把這條水路給堵住,害得我們成天兒挑水灌田,眞他媽媽別扭。」
「爹,幹嗎不去吿他?」阿雲天眞的說。
「吿?」王林更加氣惱:「人家勢力大,衙門裏都是人家的人,你怎麼個吿法?」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我們辛苦點吧 。」王妻惟恐惹出事來,她「順天認命」的說 。
阿昌這小子,一頭的火勁,他不言不語地從牛背上跳下來,去把涵洞的石頭搬開,王林看着一把拉起了阿昌:「你別跟我闖禍啦;走!走!」阿昌鼓着嘴說:「難道我們是好欺負的!」
「算啦!算啦!」王妻也勸解着:「快去把它堵起來,不然又出亂子啦!」
阿雲說:「挖開就給挖開吧,也樂得我們省點氣力去挑水。」
正在這時阿昌又見張德的牛,散在地裏吃草,阿昌憤然的叫:「爸爸,你瞧張德的牛又吃我們田裏的禾苗!」
王林抬起頭,高叫着:「喂!牛給拉拉開,別吃我們的莊稼呀!」
放牛的小子理也不理,躺在樹底下乘他的涼。這可把阿昌給氣壞啦:「爹!他不理,我叫愛樂去咬他。」
愛樂巴不得的阿昌叫,飛也似的穿過去,王林,王妻大喊着:「愛樂!囘來!」
可是愛樂已經撲到了樹底下,把放牛的小子衣服給撕破,腿上咬了一口,血淋大地,這小子哎喲哎喲直叫喚,王林趕到,扶起了放牛小子,替他擦乾了血,這小子瞪着眼睛駡道:「你們別神氣,等着瞧吧!」站起身牽了牛就一拐一拐的回去了。
王林追着說:「請你包涵點,有事我賠不是,你可別生氣啦!」
「爹,你別這樣好不好?我們就這麼濃包,聽人家欺負呀?」阿昌說。
「闖下大禍你還强嘴?」王妻悻悻然的說。
「他們堵了我們的水路,又放牛到我們田家吃莊稼,我們趕他走有什麽不對?別理他,看他能把我們怎樣,爹,咱們鋤草去!」阿雲拉囘父親,王林也無可奈何的下來,他總躭心着可能有一場很不幸的事件到來。
二
張德在書房裏打着算盤,在計算他的租賬,張妻進來說:「阿俊的爹,俊兒今兒囘來,你沒吩咐阿庚也們去接車嗎?」
「早得很,要下午兩點車才到。」
「俊兒這囘囘來,我叫阿珠跟他一塊兒來住住,住完了假期再走!」
「唔!」張德漫不經心地撥着算盤。
「俊兒還差一個學期,就在大學醫科畢業了,是嗎?」
「唔!」張德仍舊在計算他的賬。
「喂!我跟你說話,你聽見了沒有?」
「噢!噢!你說呀,我聽着吶!」
「我想俊兒年紀也不小啦!阿珠是我的姨姪女,人又能幹又漂亮,正好跟俊兒是一對,你覺她怎麼樣?」
「好!好!再,再説吧!」
「老,老!」婢女小香氣急敗壞地跑進來説:「阿庚給王林家的狗咬傷啦!」
「什麼?」張德放下了算盤站起身來往外走,阿庚拐着腿站在廳前,張德問:「到底是怎麼囘事?」
「我在地裏放牛,王林不許我在那裏放?」
「他不許?他爲什麽不許?」
「他說別人的牛可以在這裏放,就是張,張德的牛不准在……」
張德不等阿庚說下去,已經氣衝牛斗:「好!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他不認識姓張的厲害,來呀!」張德喊集佃農。
阿輝、阿祥、阿瑞都垂着手集攏來等候着主人的吩咐,就聽得張德大叫:「你們都跟我來!」阿輝等便隨在主人的身後蜂擁出莊。
張德家的司戶警犬星海,是寸步不離張德的,也跟隨着張德跳蹤而去。
張德行到水溝前面,見涵洞被人挖開就問:「這是誰給弄開的?」
阿庚說:「那還不是王林!」
「王林這老狗,瞻子可眞大,縱犬傷人不算,連我這條水溝都給挖通啦,好!我們有賬一起算!」張德怒氣塡膺:「來呀,先給這涵洞堵上。」
而後張德帶領衆人奔至田間,怒氣冲天的對王林說:「你指使着狗,咬傷了我家的阿庚,又開放了我的水溝,你說怎麼辦?」
「張老爺!」王林放下了鋤頭,很拘謹的說:「這水溝是大家的水溝,水應該大家用,你把涵洞堵上,水下不來,累得我們每天要挑水灌田,這不是我一家的事,別人看着也不服的。說到我的狗咬了你家的阿庚,我承認對不起你,可是你的牛放到我的田裏吃莊稼,我怎麽和阿庚說,他愛理不理,他是仗着誰的勢力來欺負咱們?我說張老爺,人要憑心,你不能一手霸住天下!」
「你說我霸我就霸啦!你能把我怎麼樣?」
「我怎麼敢把你怎慶樣!你是我們村上的大戶,有錢有勢,我能把你怎麼樣!」
「那你就得乖乖兒的把涵洞給修好,賠償我阿庚的損失,養傷賠禮,擺洒請客,替阿庚披紅插花,咱們就一筆勾銷,要不然,我姓張的可不是好惹的!」
「張老爺,你說得倒挺方便,可是我的田裏的莊稼給吃了,禾苗給枯了,誰賠我?你也得說說!」
「那是你活該,我管不着!」
「你到底講理不講理?」
「沒有這麼多功夫跟你說廢話,你賠不賠?乾脆說一句!」
「我賠不起,張老爺,你的心擺在正當中,別祗看見自己,看不見別人,別人的莊稼也是辛辛苦苦從一根苗慢慢的長大的!」
「少囉嗦,你不賠我就請你吃個現的,來呀!」張德囘顧左右,「替我打!」
阿輝、阿祥、阿瑞等一窩風的上前把王林拖翻在地,星海也竄上待要咬人,這裏愛樂也不示弱,和星海打成一團。張德指着愛樂說:「把這隻狗拉囘去宰了,用骨頭燒灰,給阿庚敷傷口。」阿祥逕奔愛樂撲來,阿昌挺身廻護,愛樂乘機竄去,直奔山林逃逸。張德見王林已被打翻在地,也怕鬧出人命,喝令衆人停止,指着躺在地上的王林說:「慢慢兒的再跟你算賬!」說罷卽命阿祥率領星海務將愛樂捉住,又叫阿瑞到車站去接少爺囘家。阿祥奉命領着星海一路追去,愛樂穿山跳澗,一去無踪,星海和阿祥只得怏怏而返。
三
車站上擠滿了人,上車下車川流不息。阿瑞在人叢中看見了張俊,大叫:「少爺!少爺!」張俊見是阿瑞,就將行李提箱,交付給他,囘手攙扶着他的姨表妹柳珠,柳珠扭動着身驅,一擺一擺的,在人叢中擠出,出了站,柳珠疲捲得像要倒下來的樣子,勉强地隨着張俊走了一段路,就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表哥!這是些什麽路呀,高低不平,眞把人給累死啦!」
「才走了兩里多路就累成這個樣子,我們村裏姑娘挑着担子,走上十里二十里也不算囘事,你眞是千金小姐啦!好吧,就先坐下來歇歇吧,這樹底下也還凉快!」張俊就叫阿瑞把箱子行李放下,和柳珠在樹下坐着休息。
田野裏,山坡下,傳來了一片歌聲,這是採茶姑娘們唱的「茶花曲」。悠揚而活潑的動人心弦。聽得張俊心不自主,連連讚美,柳珠披着嘴說:「這有什麽好聽的,野裏野氣,待會兒我唱個時代曲給你聽聽,不比這個强得多,走罷!」柳珠拉着張俊的手,起身再向前進。柳珠走在窄狹的田堤上,東搖西擺,偶一滑脚,跌在泥水裏,把正在插秧的一個姑娘的臉上,濺了一臉的泥。這姑娘抬起頭來,怒目看着柳珠。「你這是怎麽囘事?走路走下了田,你長眼睛沒有?」
柳珠正因自己的一隻簇新高跟白麂皮的鞋子,被泥汚了,心疼不已,忽然被人駡爲不長眼睛,不由得怒上心頭:「你才沒有長眼睛,你瞎了眼,你的田這麽狹窄,把我新鞋給弄髒了,你賠你賠!」
「呸!」柳珠被這姑娘呸了一臉的唾沫說:「眞不要臉,自己不小心,滑了脚,濺了人一臉泥,還怪田堤不好,這倒是新鮮的詞兒,頭一囘聽說。」
柳珠正待囘答,張俊攔着說:「好了好了!我們要趕囘家去,媽在等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柳珠拉走,柳珠恨恨地說:「便宜你這賤貨!」一路走着一路駡着。不覺已經到了門前,星海搖着尾巴迎上來,所有家人都圍上來上叫「少爺」,張俊忙着點頭,到了廂房,看阿庚在躺着叫喚,張俊忙問:「怎麼啦阿庚?」阿旺吿訴少爺:「他是被王家的狗咬傷的,老爺正爲這件事大發脾氣吶!」
「我瞧瞧!」張俊把阿庚的傷口仔細的一看:「不要緊,咬了兩個小狗牙印子,等會兒我來替他洗一洗,消消毒,打一針,吃兩片藥就會好的。」
張俊帶着柳珠進入大廳,見着媽,上前叫了一聲,張妻滿面春風的笑着:「阿俊,阿珠,你們囘來啦!趕快洗臉做飯吃。」
柳珠撒嬌撒痴的說:「姨媽,你看我這只脚。」她把一隻玉腿伸到了姨媽的面前。
「哎呀,是怎麽弄的,弄成這樣?」
「就是那個臭丫頭的田堤弄的,我眞想給她一巴掌,要不是表哥拉着,我……」
「表妹!」張俊攔着說:「你怎麽可以怪人家吶!田堤窄關人家什麽事?鄕下的路都是這樣,不比你城裏柏油馬路又光又滑,這兒走路要自己當心。你把人家臉上濺了一臉泥,人家不來找你麻煩,已經算好的啦!」
「表哥,你爲什麽這樣護着外人?」
「不管裏頭入外頭人,總得講理呀!」
「俊兒!」張德從書房裏出來:「你在說些什麼?」
「爸爸!沒有什麽,我剛囘到家,還沒到書房去跟爸爸請安吶!」張俊指着柳珠說:「表妹也來了!」
「好!」張德說:「你們先歇着去吧,吃完飯我們再談。」
「爸爸,我得先替阿庚把傷口洗一洗,給他打一針消消炎,免得腫起來。」
「被狗咬了一口,有什麼要緊,何必這麼大驚小怪的,打針,消炎,好像害了大病似的。」
「不是這麽說,爸爸,小病不治,就可能成爲大病,他的傷不重,打一針,吃兩片藥就可以好的,不是省事得多了嗎?」
「好好好!」張德擺着手:「你喜歡你就去,我不管你,我不管你!」
張俊提了藥箱去為阿庚療治。
柳珠則隨姨媽到了房裏,換了衣服,塗上脂粉。姨媽對柳珠說:「姨父是個老古板,看不慣你們年靑的城裏人的時髦派頭,他講究禮貌,你等會兒見他,要規規矩矩的,站有個站相,坐有個坐相……」
「我不會,姨媽,那這麼辦呢?」
「我敎你!」姨媽把禮節完全吿訴了柳珠,柳珠果然照樣兒販賣給姨父,張德奇怪的說:「想不到城裏的女孩子,還這樣板板六十四的,跟我們鄕下人一樣,說站着不敢坐着,柳珠,聽說城裏的女孩子天天唱歌,晚晚跳舞,你怎麽還學不會這些時髦的頑意兒?」
「我!」柳珠厥着嘴:「我,我樣樣都會,可是姨媽說……」
姨媽立卽對她使了個眼色!意思是教她不要說出來,但柳珠誤解了這個眼色的用意,她跳起身來對姨父說:「姨父不信,我跳給你看!」柳珠一面跳着夏威夷的草裙舞,挺着胸,扭着臀,一面唱着火奴魯魯的熱情歌,這下子給姨媽可急壞了,欲止無從,張德大搖其頭,頗有世風日下之感。而柳珠還自鳴得意,以爲姨父正賞識其藝術的天才呢!
四
柳珠在鄉下住得十分乏味,如果她不是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好消息,終身大事的吉期宣佈,她早就囘到城裏去了。
張妻見姨姪女兒呆在家裏悶氣,就叫兒子帶着她打獵去。張俊,柳珠換了獵裝,帶着獵槍,獵犬,出了莊門,逕奔叢山峻嶺而去。可是柳珠走得慢,一會兒要表哥攙着,一會兒要表哥扶着,把張俊麻煩得不知怎樣才好。走了老半天,才走到山坡下面,坐下憩息。柳珠看到有隻野鷄,忙拿起槍來,一彈射出,野鷄撲撲翅膀飛去。張俊說:「你這樣怎麼能打着東西?看我的!」他仰頭看着天空,飛來了一隻鷂子。「你瞧!」一聲未已,就聽得「砰」聲響,那只鷂子從空中一連翻了幾十翻,跌落到山澗裏去了。星海飛竄了前去,把鷂子啣囘來,放置在張俊的面前。「表哥,像你槍法眞不壞,我拜你做師傅好不好?」柳珠故意地倚在表哥的身上:「瞧!」
一隻灰兔從林中穿出來,柳珠擎槍便擊,槍彈落在密密的茶樹叢中,野兔並沒有打着,而打着了一個人,這人「哎喲!」一聲,似乎就倒在叢林中,張俊大吃一驚,連說「不得了,打傷人啦!」他急忙跑到林中査看,果然一個採茶的女孩被打中了腿,倒在血泊裏呻吟着。張俊扶起她來,撕下衣襟替她包紮傷處。柳珠則站在旁邊,冷冷的一聲不響。原來這個中槍的姑娘,正是她日前經過田畦被她濺了一瞼泥的姑娘。真是寃家路狹,在這裏又遇見了。
「姑娘,你住在什麽地方?我送你囘去!」張俊說。
這姑娘睜開了眼睛,仔細一看,不由得面呈慍色:「用不着,你們走你們的好了!」
「不,你是我們槍打傷的,我們應該負責把你送囘去,替你把傷醫治好啦!」張俊解釋着說。
「我不要。」這姑娘掙扎着起來,但又跌下去。
「她不要就算了,表哥,咱們走!」
張俊怒目地對柳珠看一眼,也不理她,還是低聲的對這姑娘說:「你不要這樣,我們對不起你,我有責任送你囘去,你的血流得過多,很危險,要是有細菌透進血管,那更不得了,我一定要送你,你住在什麽地方?」
這姑娘聽了半天,不好意思拒絕,只得用手指了山下,張俊扶着她起身,柳珠又妬又恨。這姑娘甫站起來,腿一軟,又坐下去,張俊只得抱着她往山下走。柳珠大怒說道:「表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這是救人,你打傷了人,我來救,難道你還不願意?」
「我就不願意,我要你放下她跟我走!」
「你是長的一副什麽心肝?打傷了人不管,還要我跟你走,哼!」張俊逕自抱着這姑娘下山。
「好!」柳珠的眼涙都急出來:「星海,我們囘去!」然而星海不回去,牠搖着尾巴跟在張俊的後面走,柳珠只得拾起槍,一個人,獨自的跑囘家去。
張俊抱着這姑娘走下山來,原來這姑娘也是住在茶花村,走近她的家門時,只見一個老者驚訝的叫着:「你怎麼啦阿雲?」
阿雲從張俊的懷裏下來,坐在地上,流着淚,張俊抱歉地對老者說:「老伯伯,她是你的女兒嗎?我是張德的兒子叫張俊,因爲打獵誤傷了你的女兒,眞對不起,所以我送她囘來,替她醫治。」
這時愛樂看到了星海,兩狗相對,唁唁的狂吠,張俊連忙止住了星海,王林也止住了愛樂:「張少爺,我叫王林,你不認識我,我是認識你的,你在七八歲的時候,還不是常到我們家來頑嗎?那時候阿雲才四五歲,你們還在一起捉迷藏,唱山歌吶!後來你大啦,你爸爸不准你跟我們窮孩子在一塊頑,怕低辱你的身份,又把你送進城念書,這話一說十幾年嘍,阿雲都快二十啦,你出來進去我們都看着,你一年大一年,看着你從小長到大,也看着你爸爸的屋子一年大一年,看着你爸爸的地從少到多,現在這村上的富戶漸漸變成了窮戶,田地也一家一家的併到了你家,你家成了這個村上的第一大戶,我們剩下的十畝八畝地,也快要完啦!你家富啦!家家窮啦!錢給你爸爸一個人拿去啦!就連這條水溝的水都不給用,涵洞給堵上啦,讓我們乾死!」
「張老伯,我眞是這些年祗顧在外面念書,家裏的事,我一點兒也不淸楚,爸爸這個人,就是這點兒不好,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我想,我總要想法子勸他不能這様下去的。現在我得要先替雲姑娘治傷,我囘去拿藥箱,馬上就來!」
張俊拿了藥箱來,替阿雲洗淨,敷藥,打針,又留下了一包藥,叫王林每天給阿雲吃三次,每次三片。然後再替阿雲量一量溫度,這才提着藥箱囘去。
阿雲的傷漸漸的好了,張俊過一兩天,總要來看阿雲一次。王妻對丈夫說;「張德那樣的壞,可是他的兒子還不錯,懂得人情世故的。」
「他爸爸壞事做多了,自然要他假情假意的對我們窮人賣賣好,這樣不就少恨他爸爸一點兒嗎?」阿昌氣憤的說。
「你懂什麼,胡說八道!」王妻阻止阿昌說。
「你以爲我還是三歲小孩兒呀?我也快二十歲啦,還看不出?張俊比他爸爸更壞,他爸爸是明壞,他是暗壞,暗壞人家看不出,還以爲他是好人吶!」阿昌不服氣的說。
「少說幾句,你懂個屁」!王林拍了阿昌一巴掌。
「我不懂,你懂!」阿昌鼓着嘴,牽着愛樂出去了。
五
張德在大廳上咆哮着:「査!査!是誰把水溝的涵洞給開開的?」
「我不知道!」阿祥阿輝等低着頭說。
「你們是死人哪!涵洞被人扒開都不知道。」
「我們不敢說!」阿瑞抽冷子來上一句。
「有什麽不敢說,你怕王林那老狗吃了你?」
「這不關王林的事,是我開的!」張俊挺身而出。
「你開的?」張德直瞪着兩眼,莫明其妙的間:「你爲什麼要把涵洞給開開?」
「這條水溝是公用的,並不是我們一家用的,你把水溝堵上,水流不下來,人家毎天在擔水灌田:這根本不是個辦法,也沒有這個道理。」
「這麼說,你倒幫着人家說話?你不是我的兒子,你是吃誰的飯長大的?我替你攻書上學,把你養活大啦,你倒反對起老子來啦?你這不是想造反嘛?」拍的一個耳光,打在張俊的臉上。
「好啦!好啦!別說了,你怎麼可以跟你爸爸鬥嘴?進來進來!」張妻把兒子拖進房,勸着說:「爸爸這樣做,都是爲了你,你怎麽連個好歹都不知道呢?」
「我不要爸爸這樣的爲我,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張俊摸着熱辣辣地的腮幫說。
只聽得張德呼斥着阿祥等:「快點把涵洞再給堵上,要是有人再敢扒開,不管是誰,給我打個半死!」
張俊心上一塊鉛石給壓着,始終透不出氣來。
這樣過了半月,張妻一晚對丈夫說:「阿珠在這兒已經住了好些日子啦,你看她跟俊兒的事情怎麼樣?我們擇個日子替他們下訂吧。」
「慢慢兒再說,我要到城裏去完糧,等我囘來再商量吧!」
「你幾時囘來?」
「快!如果沒有事,明天就可以囘來啦!不過怕的還有一點手續要辦一辦,大槪最多四五天就可以辦完啦!」
「好吧!那就等你囘來!」
張德收拾了行囊,進城去了。
張俊送走了父親,囘來對母親說:「王林的女兒阿雲被表妹打傷,現在完全好啦!人家沒找我們麻煩,我很不過意,我想請她來吃頓飯,一來替她算是道個歉,二來聯絡感情,王林本來是個老實人,一家都很好,犯不上跟人家作對,我想借這個機會解釋解釋,以後再跟爸爸說說,化敵爲友,兩下拉開就完了,媽你說可是?」
「好是好,可是你爹的脾氣,怕不會答應。」
「只要你先答應了就行啦,爹到城裏,總得幾天才能囘來,我們明天就請她來吃飯,你說好不好?」
「好好好!媽疼你,你愛怎麼辦就怎麽辦吧!」
張俊高興地去請阿雲,可是柳珠看在眼裏,十分氣惱。只見表哥拿着照相機,一溜烟的出去了。
張俊到了王家,見沒人,又趕到田裏,阿雲一家正在鋤地,張俊叫着:「王老伯,我媽請雲姑娘明天到我家吃飯,我先來吿訴一聲。」
「你媽請阿雲吃飯?」王妻抬起腰來問。
「是的,伯母,因爲雲姑娘傷好了,我媽說眞對不起她,請她吃頓飯,賠個不是!」
「算啦!還賠什麼不是,只要大家知道就完啦!」王林說。
「老伯,一定一定,我媽的意思,一定要請雲姑娘去。」張俊又問阿雲:「你願意去嗎?」
阿雲低下頭,笑着不說話。
「好吧,旣然你誠心誠意的,去就去吧!」王林笑嘻嘻地看看張俊,也看着阿雲。
「來!我替你們照相。」張俊替阿雲照了又替阿昌照,再替王林夫婦照,把一捲膠片照光了才放手。張俊歡歡喜喜的囘家裏。第二天忙着叫廚房裏做菜,宰鷄,天傍晚,阿雲穿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張妻看阿雲眉清目秀,怪可人的,心中也自歡喜。只有柳珠不快,她認爲這是她的恥辱,一個男人,敢於在她面前和另外一個女人接近,這不是明明白白在諷剌她嗎?這事怎麼辦呢?思來想去,她想到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在她認爲是非常得意的傑作,於是她安排着逐步進行的計劃,假意地奉迎着阿雲,在吃飯的時候,柳珠手裏揑着一件東西,輕輕地從桌下伸手,準備放在阿雲的膝上,不料婢女小香捧着菜盤,柳珠的手一拐托盤跌落地上,碗碎湯潑,濺了柳珠一身,柳珠只得縮囘手,到樓上去換衣,誰知走得匆忙,手帕裏的東西掉了下來,柳珠連忙檢起包好,等衣服換畢,再入席間,又俟機把這手帕輕輕的從桌下送到阿雲的膝上。這時柳珠忽然的叫道:「哎呀!姨媽頭上的花怎麼不見了?」
「我的珠花不見了?」張妻摸一模頭上:「我沒有戴出來吧?也許在房裏。」
「我剛才還看見珠花在你頭上,怎麼我上樓一趟就不見了」柳珠故意的說。
「眞的嗎?這倒奇怪!」張妻再摸一摸頭。
「是不是阿香給偷去了?」柳珠指着小香說:「要是你偷的快拿出來!」
「我沒有!我沒有!」小香吓得臉黃,伏在地上四處尋找,只見阿雲腿上有一個手帕,露出珠花的一角來:「哦!在這裏!」小香把阿雲膝上的珠花取過來。
「怪不得我看到她在姨媽頭上一揚手,偷珠花,這倒是一件好本事,一忽兒人家的東西,就變成她的啦!」柳珠的鼻子哼一聲:「郷下的女人哪!眞沒出息,好事不做,做起賊來。」
阿雲受此寃枉眼淚快要急出來了,她正待分辯,偏偏張德囘來了,看見家中紛亂,忙問何事?柳珠指着阿雲說:「這個女人,偷我姨媽的珠花,被我們抓着了!」
「她是誰?怎麼會到我家裏來?」
「她是王林的女兒,是表哥的好朋友,不瞧表哥一直替她養傷治病嗎?現在傷好啦,上門來偷東西啦!要不是姨父囘來得快,還不知道要被她鬧成什麼樣子吶!」
「我離了家才一天,就出了事,這還像話嗎!」
「想不到她是這樣!」張妻嘆息着說:「看她樣兒倒是斯斯文文的。」
「媽!」你先別怎麼說:「阿雲不會的!」
阿雲受了委曲,大哭而去,張俊追着,阿雲不顧路的高低,一直奔出莊去,張俊被父親喊囘來,氣悶地上樓,在樓梯上忽然看到了一角珠花,這是柳珠跌斷了的,沒有檢起,張俊這時恍然大悟,忙將珠花的一角拾起,逕入母房,母親的房裏正在議論着阿雲的事情,張德聽了柳珠的話,知道兒子還替阿雲一家去照相,這簡直是忘了自己是什麼人,這一氣非同小可,正巧張俊進房,張德直在兒子的臉上:「你來得正好,你跟個賊婆娘照相,我張家祖宗十八代的臉都被你丟盡了!」
「爸爸,你不要生氣,我們張家有一件眞正丟臉的事。」張俊取出了珠花的一角給他母親,「你的珠花是不是缺了一角?」
張妻取下珠花看了看,果然有一隻角丟了,張俊說:「這隻角是在表妹的房門口樓梯角上檢來的?」
「珠花怎會到阿珠的房裏的?」張妻詫異地說。
「這就得問表妹了,她做的事,她自己知道。」
「阿珠,你說,怎會到你房裏的?」張妻問。
「我,我,我不知道……」柳珠一時倒急得說不上話來。
「我知道!」張俊冷笑着:「你這種贓栽害人的方法,瞞不了我,表妹,你爲什麽這樣幹!人家淸淸白白的給你這麼誣賴,你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柳珠柳眉倒豎,兩淚交流:「我要殺了她!你,你!你去愛那個臭丫頭去吧,我走啦!」柳珠上樓收拾了提箱,毫不留戀的走了,張徳目選柳珠去後,看了老婆一眼:「你的好姪女,還會來這麽一手!」
張妻伏案大哭:「阿珠,你太不替我爭氣了。」
六
阿雲哭囘家中,王林夫婦忙問何事?阿珠把珠花的事情說了一遍,王林氣得直搖頭:「到底張家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把我女兒騙去,做成圈套來害人,好!我去和那個小子算賬,拼了命也替我女兒弄個淸白。」
「我早就說過,張俊是什麼好人?假的!不瞧把姐姐騙去……」阿昌正得意揚揚的在說忽地被他母親打斷:「你少開口!」阿昌只有閉上嘴,不說了。凑巧張俊來到,解釋誤會,王林一家那裏肯聽,連阿雲也把張俊恨得牙癢癢地了。張俊不得要領,悻悻而去。門前的愛樂跟着張俊,直搖尾巴,張俊說:「難道你能同情我嗎?」愛樂點點狗頭。張俊大喜,從懷中取出紙筆,就地借着月光寫了一信,交給愛樂,愛樂啣了信,跳進阿雲的窗內,把信放在床上,阿雲見信,這才知道是柳珠因為妬忌撚酸,做出來的事情,心就軟了下來,她見愛樂蹲在地上不走,似乎等待囘信,她就寫了幾個字,交與愛樂。愛樂躍窗而去,不見了張俊,就循着張俊的足跡氣味,直到張家,星海迎來,愛樂把信交與星海,星海啣了進宅,不一會出來,又啣囘一信,交與愛樂,愛樂再啣囘家,由於這兩隻狗紅娘從中撮合,阿雲和張俊之間誤會,就完全冰釋了。
不料這晚愛樂正啣信來的時候,忽見人影幢幢在張德書房閃爍,愛樂狂吠,驚起了衆人,星海則竄入書房,見老主人正被盜匪綁在椅上,堵塞了嘴,在房中翻箱倒籠,搜羅財物,立卽向一盜猛力撲去,愛樂也加入戰團,向另一盜猛噬,羣盜見雙犬撲來,不敢久留,恐被人攔刼,就便推倒油燈,放起火來,把張德架走。張妻和張俊及所有的佣人一齊驚起,追盜的追盜,救火的救火。阿祥敲起一面銅鑼,連王林一家也驚起了,都來救火,只聽得張妻大叫:「俊兒!你爸爸還在火裏,快點救他出來呀!」
「爸爸已經被賊帶走了,我去追爸爸!」張俊說着就帶同阿祥阿輝阿瑞以及鄰舍人等!連同愛樂,星海,舉着火把直奔莊外,在橋口見有張德遺落的一隻鞋,張俊送在愛樂鼻上聞一聞,愛樂飛奔而去。大家在後力追,兩狗一路嗅着一路追,終於追到了盜匪,愛樂不顧生死的跳躍狂噬,咬翻了一匪,人犬糾纏,生死搏鬥,其餘人等已見目標,分路包圍上來,羣匪以衆寡不敵,只得丟下了張德,和刼來的財物,鼠竄而去。可是愛樂由於死纏盜匪不放,而被另一盜匪抽刀剌入腹中,倒地而死,但愛樂也還値得,被牠咬翻在地的一個盜匪,傷重氣絕,陪着愛樂一同死了。
刼後餘生的張德,見愛樂爲救他而死,立存「獸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想,嘆了口氣,撫摸着血糊零落的愛樂說:「你爲了救你主人的仇人,犧牲了性命,我,我……」老涙不禁由張德的眼中落下來。
囘到了莊前,見自己的家門 , 殘煙飄繞,張妻已被阿雲一家攙扶到了王家,躺在繩床上休息。
王林迎上來,默然無語,張德半天說不上話來,還是王林先說:「張老爺,你也別難過,房子雖然燒了,還可以再蓋,只要人在,還怕沒有屋子嗎!」
不自持的張德上前,執着王林的手,流着淚說:「王大哥,我眞對不住你,對不住大家,今天我家出了事,大家這樣的幫忙,連狗都不計前仇,爲了我送命,我張德是個人哪,難道我連個畜生都不如嗎?我要改囘我從前的過錯,我們都是種地的,應該大家幫助,可是從前我不這樣想,我要一個人發財,這財都是大家的血汗哪!我憑什麼一個人來享用,使大家吃苦吶?我錯了!請你原諒我,請大家原諒我,從今天起,我要從新做人。燒了的房子我也不蓋了,我要和大家一起做活,下地,耕田,水溝是大家的,當然大家都能用水,我的地多,我自己種不過來,應該分給沒有地的人種,俊兒!」張德含着兩泡淚水叫喚着兒子:「你說是不是!」
「爸爸,你這才是我的爸爸!」張俊也熱涙盈眶地拉着張德的手:「早該這樣啦!」
王林夫婦,阿雲阿昌,以及莊上的農戶們都爲感動,交頭接耳的談論着,變啦!變啦!連張德這個老頑固都變啦!
兩天後,張德簡單的土屋搭起來了,而愛樂的墳墓也建築起來了,墳前豎立着一塊碑,上寫「義犬愛樂之墓」六個大字,墓前圍着一圈人,都爲這隻義犬而哀悼,尤其是張德。
茶花村的情形變了,生氣也有了,滿山遍野的唱着「茶花曲」,水溝裏的水,通過了涵洞,向東西南北的田畦裏,四處奔流,王林夫婦在田裏插着秧,阿雲在山上採着茶,張俊在旁幫着搬簍子,携繩索,阿昌在山坡下放着牛,最奇怪的是阿祥、阿輝、阿瑞等一羣在田野鋤草的人們,中間夾着張德夫婦,老夫妻戴着斗笠,彎着腰,一鋤頭一鋤頭的在地上鋤着,汗水打到脚面,這是茶花村變了之後的新場面。
——完——
黃河的素描
黃河這些年來演了不少的戲,「人犬恩仇」中的黃河,是演一個鄉村中富有的農家的兒子,雖然他已 由中學而大學,得來了不少社會知識,可是他也得來了不少人生經驗,他感到他的父親所行所爲,並不滿 意,所以他就力勸他的父親改弦易轍,從新做人。最後,他果然得到了成功;雖說這個成功是由於偶然的 外力所致。
黃河原來是學醫的,他父親希望他成爲一個能够醫世救人的良醫 ,但他偏偏喜歡電影戲劇,當十八年 前,那時他才十六七歲,他就逃出了醫科學校,走上舞台。他不專門去學習醫科了,他要學習什麽都可以 扮演的演員。誰知在這「人犬恩仇」裏,凑巧他是扮演醫科大學的學生,可說是,「璞玉返眞」了。(陳泰)
人犬恩仇
・電影小說・
一
早晨的太陽,洗遍了郊野的靑葱樹木,田畦,一片綠油油的波浪,被陽光反射着,呈現了姣黃的色彩。滿山的茶花,開得令人心醉,叢林內的各式各樣的雀鳥聲喧,大自然的美景啊!只有和莊稼禾苗生活在一起的人們,才能領略。
茶花村有幾十戶人家,爲首的名叫張德,(王元龍飾)老妻(楊柳飾)只生下一子,名喚張俊,(黃河飾)張德就這麽一個兒子,當然心肝寳貝地望子成龍,替他攻書上學,中學畢了業,又到大城市裏去進大學,專習醫科,張德盼望着兒子學成之後,做一個濟世救人的好醫生。
茶花村中有一戶農家,老頭兒名叫王林(魏鵬飛飾)王妻(藍靑飾)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年紀還小,祗有八歲,名喚阿昌,(嚴昌飾)閨女大了,已經到了二九年華,名叫阿雲,(張翠英飾)一家四口,辛勤地過着艱難而又甜蜜的生活。
王家有隻狗,名喚愛樂,這隻狗不獨是阿昌的心肝寶貝,同時也是王家一家人所鍾愛的得力助手,因爲牠不但能看門守戶,還能飼猪餵牛,養鷄育鴨。每天早晨,得由愛樂啣了飼料到牛房裏,拖着飼料到猪欄裏,開放了鷄籠鴨閘,讓鷄鴨出外尋食,一切工作做妥當了,而後就把掛在棚底下的一根鈴繩一拉,在房裏的銅鈴響了,驚醒了王家一家,阿昌揉着眼睛在叫:「爸爸,天亮了,起來吧!」
王妻也喚着閨女:「阿雲呀,別睡啦,去做飯吃了好下田啦!」
一家人忙碌着起身,做飯,照應牲口,愛樂幫忙着啣這搬那,吃好飯,阿雲牽着牛,阿昌騎在牛背上,王林扛着鋤頭,王妻提着水桶,往田野裏行去。
早晨是農人的世界啊!家家烟突裏冒着炊烟,家家不分男女老幼,紛紛下田做活,王林一家人行至溝渠這邊,又看見被人給堵塞了的涵洞,王林氣憤地駡着:「張德這傢伙眞缺德,把這條水路給堵住,害得我們成天兒挑水灌田,眞他媽媽別扭。」
「爹,幹嗎不去吿他?」阿雲天眞的說。
「吿?」王林更加氣惱:「人家勢力大,衙門裏都是人家的人,你怎麼個吿法?」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我們辛苦點吧 。」王妻惟恐惹出事來,她「順天認命」的說 。
阿昌這小子,一頭的火勁,他不言不語地從牛背上跳下來,去把涵洞的石頭搬開,王林看着一把拉起了阿昌:「你別跟我闖禍啦;走!走!」阿昌鼓着嘴說:「難道我們是好欺負的!」
「算啦!算啦!」王妻也勸解着:「快去把它堵起來,不然又出亂子啦!」
阿雲說:「挖開就給挖開吧,也樂得我們省點氣力去挑水。」
正在這時阿昌又見張德的牛,散在地裏吃草,阿昌憤然的叫:「爸爸,你瞧張德的牛又吃我們田裏的禾苗!」
王林抬起頭,高叫着:「喂!牛給拉拉開,別吃我們的莊稼呀!」
放牛的小子理也不理,躺在樹底下乘他的涼。這可把阿昌給氣壞啦:「爹!他不理,我叫愛樂去咬他。」
愛樂巴不得的阿昌叫,飛也似的穿過去,王林,王妻大喊着:「愛樂!囘來!」
可是愛樂已經撲到了樹底下,把放牛的小子衣服給撕破,腿上咬了一口,血淋大地,這小子哎喲哎喲直叫喚,王林趕到,扶起了放牛小子,替他擦乾了血,這小子瞪着眼睛駡道:「你們別神氣,等着瞧吧!」站起身牽了牛就一拐一拐的回去了。
王林追着說:「請你包涵點,有事我賠不是,你可別生氣啦!」
「爹,你別這樣好不好?我們就這麼濃包,聽人家欺負呀?」阿昌說。
「闖下大禍你還强嘴?」王妻悻悻然的說。
「他們堵了我們的水路,又放牛到我們田家吃莊稼,我們趕他走有什麽不對?別理他,看他能把我們怎樣,爹,咱們鋤草去!」阿雲拉囘父親,王林也無可奈何的下來,他總躭心着可能有一場很不幸的事件到來。
二
張德在書房裏打着算盤,在計算他的租賬,張妻進來說:「阿俊的爹,俊兒今兒囘來,你沒吩咐阿庚也們去接車嗎?」
「早得很,要下午兩點車才到。」
「俊兒這囘囘來,我叫阿珠跟他一塊兒來住住,住完了假期再走!」
「唔!」張德漫不經心地撥着算盤。
「俊兒還差一個學期,就在大學醫科畢業了,是嗎?」
「唔!」張德仍舊在計算他的賬。
「喂!我跟你說話,你聽見了沒有?」
「噢!噢!你說呀,我聽着吶!」
「我想俊兒年紀也不小啦!阿珠是我的姨姪女,人又能幹又漂亮,正好跟俊兒是一對,你覺她怎麼樣?」
「好!好!再,再説吧!」
「老,老!」婢女小香氣急敗壞地跑進來説:「阿庚給王林家的狗咬傷啦!」
「什麼?」張德放下了算盤站起身來往外走,阿庚拐着腿站在廳前,張德問:「到底是怎麼囘事?」
「我在地裏放牛,王林不許我在那裏放?」
「他不許?他爲什麽不許?」
「他說別人的牛可以在這裏放,就是張,張德的牛不准在……」
張德不等阿庚說下去,已經氣衝牛斗:「好!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他不認識姓張的厲害,來呀!」張德喊集佃農。
阿輝、阿祥、阿瑞都垂着手集攏來等候着主人的吩咐,就聽得張德大叫:「你們都跟我來!」阿輝等便隨在主人的身後蜂擁出莊。
張德家的司戶警犬星海,是寸步不離張德的,也跟隨着張德跳蹤而去。
張德行到水溝前面,見涵洞被人挖開就問:「這是誰給弄開的?」
阿庚說:「那還不是王林!」
「王林這老狗,瞻子可眞大,縱犬傷人不算,連我這條水溝都給挖通啦,好!我們有賬一起算!」張德怒氣塡膺:「來呀,先給這涵洞堵上。」
而後張德帶領衆人奔至田間,怒氣冲天的對王林說:「你指使着狗,咬傷了我家的阿庚,又開放了我的水溝,你說怎麼辦?」
「張老爺!」王林放下了鋤頭,很拘謹的說:「這水溝是大家的水溝,水應該大家用,你把涵洞堵上,水下不來,累得我們每天要挑水灌田,這不是我一家的事,別人看着也不服的。說到我的狗咬了你家的阿庚,我承認對不起你,可是你的牛放到我的田裏吃莊稼,我怎麽和阿庚說,他愛理不理,他是仗着誰的勢力來欺負咱們?我說張老爺,人要憑心,你不能一手霸住天下!」
「你說我霸我就霸啦!你能把我怎麼樣?」
「我怎麼敢把你怎慶樣!你是我們村上的大戶,有錢有勢,我能把你怎麼樣!」
「那你就得乖乖兒的把涵洞給修好,賠償我阿庚的損失,養傷賠禮,擺洒請客,替阿庚披紅插花,咱們就一筆勾銷,要不然,我姓張的可不是好惹的!」
「張老爺,你說得倒挺方便,可是我的田裏的莊稼給吃了,禾苗給枯了,誰賠我?你也得說說!」
「那是你活該,我管不着!」
「你到底講理不講理?」
「沒有這麼多功夫跟你說廢話,你賠不賠?乾脆說一句!」
「我賠不起,張老爺,你的心擺在正當中,別祗看見自己,看不見別人,別人的莊稼也是辛辛苦苦從一根苗慢慢的長大的!」
「少囉嗦,你不賠我就請你吃個現的,來呀!」張德囘顧左右,「替我打!」
阿輝、阿祥、阿瑞等一窩風的上前把王林拖翻在地,星海也竄上待要咬人,這裏愛樂也不示弱,和星海打成一團。張德指着愛樂說:「把這隻狗拉囘去宰了,用骨頭燒灰,給阿庚敷傷口。」阿祥逕奔愛樂撲來,阿昌挺身廻護,愛樂乘機竄去,直奔山林逃逸。張德見王林已被打翻在地,也怕鬧出人命,喝令衆人停止,指着躺在地上的王林說:「慢慢兒的再跟你算賬!」說罷卽命阿祥率領星海務將愛樂捉住,又叫阿瑞到車站去接少爺囘家。阿祥奉命領着星海一路追去,愛樂穿山跳澗,一去無踪,星海和阿祥只得怏怏而返。
三
車站上擠滿了人,上車下車川流不息。阿瑞在人叢中看見了張俊,大叫:「少爺!少爺!」張俊見是阿瑞,就將行李提箱,交付給他,囘手攙扶着他的姨表妹柳珠,柳珠扭動着身驅,一擺一擺的,在人叢中擠出,出了站,柳珠疲捲得像要倒下來的樣子,勉强地隨着張俊走了一段路,就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表哥!這是些什麽路呀,高低不平,眞把人給累死啦!」
「才走了兩里多路就累成這個樣子,我們村裏姑娘挑着担子,走上十里二十里也不算囘事,你眞是千金小姐啦!好吧,就先坐下來歇歇吧,這樹底下也還凉快!」張俊就叫阿瑞把箱子行李放下,和柳珠在樹下坐着休息。
田野裏,山坡下,傳來了一片歌聲,這是採茶姑娘們唱的「茶花曲」。悠揚而活潑的動人心弦。聽得張俊心不自主,連連讚美,柳珠披着嘴說:「這有什麽好聽的,野裏野氣,待會兒我唱個時代曲給你聽聽,不比這個强得多,走罷!」柳珠拉着張俊的手,起身再向前進。柳珠走在窄狹的田堤上,東搖西擺,偶一滑脚,跌在泥水裏,把正在插秧的一個姑娘的臉上,濺了一臉的泥。這姑娘抬起頭來,怒目看着柳珠。「你這是怎麽囘事?走路走下了田,你長眼睛沒有?」
柳珠正因自己的一隻簇新高跟白麂皮的鞋子,被泥汚了,心疼不已,忽然被人駡爲不長眼睛,不由得怒上心頭:「你才沒有長眼睛,你瞎了眼,你的田這麽狹窄,把我新鞋給弄髒了,你賠你賠!」
「呸!」柳珠被這姑娘呸了一臉的唾沫說:「眞不要臉,自己不小心,滑了脚,濺了人一臉泥,還怪田堤不好,這倒是新鮮的詞兒,頭一囘聽說。」
柳珠正待囘答,張俊攔着說:「好了好了!我們要趕囘家去,媽在等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柳珠拉走,柳珠恨恨地說:「便宜你這賤貨!」一路走着一路駡着。不覺已經到了門前,星海搖着尾巴迎上來,所有家人都圍上來上叫「少爺」,張俊忙着點頭,到了廂房,看阿庚在躺着叫喚,張俊忙問:「怎麼啦阿庚?」阿旺吿訴少爺:「他是被王家的狗咬傷的,老爺正爲這件事大發脾氣吶!」
「我瞧瞧!」張俊把阿庚的傷口仔細的一看:「不要緊,咬了兩個小狗牙印子,等會兒我來替他洗一洗,消消毒,打一針,吃兩片藥就會好的。」
張俊帶着柳珠進入大廳,見着媽,上前叫了一聲,張妻滿面春風的笑着:「阿俊,阿珠,你們囘來啦!趕快洗臉做飯吃。」
柳珠撒嬌撒痴的說:「姨媽,你看我這只脚。」她把一隻玉腿伸到了姨媽的面前。
「哎呀,是怎麽弄的,弄成這樣?」
「就是那個臭丫頭的田堤弄的,我眞想給她一巴掌,要不是表哥拉着,我……」
「表妹!」張俊攔着說:「你怎麽可以怪人家吶!田堤窄關人家什麽事?鄕下的路都是這樣,不比你城裏柏油馬路又光又滑,這兒走路要自己當心。你把人家臉上濺了一臉泥,人家不來找你麻煩,已經算好的啦!」
「表哥,你爲什麽這樣護着外人?」
「不管裏頭入外頭人,總得講理呀!」
「俊兒!」張德從書房裏出來:「你在說些什麼?」
「爸爸!沒有什麽,我剛囘到家,還沒到書房去跟爸爸請安吶!」張俊指着柳珠說:「表妹也來了!」
「好!」張德說:「你們先歇着去吧,吃完飯我們再談。」
「爸爸,我得先替阿庚把傷口洗一洗,給他打一針消消炎,免得腫起來。」
「被狗咬了一口,有什麼要緊,何必這麼大驚小怪的,打針,消炎,好像害了大病似的。」
「不是這麽說,爸爸,小病不治,就可能成爲大病,他的傷不重,打一針,吃兩片藥就可以好的,不是省事得多了嗎?」
「好好好!」張德擺着手:「你喜歡你就去,我不管你,我不管你!」
張俊提了藥箱去為阿庚療治。
柳珠則隨姨媽到了房裏,換了衣服,塗上脂粉。姨媽對柳珠說:「姨父是個老古板,看不慣你們年靑的城裏人的時髦派頭,他講究禮貌,你等會兒見他,要規規矩矩的,站有個站相,坐有個坐相……」
「我不會,姨媽,那這麼辦呢?」
「我敎你!」姨媽把禮節完全吿訴了柳珠,柳珠果然照樣兒販賣給姨父,張德奇怪的說:「想不到城裏的女孩子,還這樣板板六十四的,跟我們鄕下人一樣,說站着不敢坐着,柳珠,聽說城裏的女孩子天天唱歌,晚晚跳舞,你怎麽還學不會這些時髦的頑意兒?」
「我!」柳珠厥着嘴:「我,我樣樣都會,可是姨媽說……」
姨媽立卽對她使了個眼色!意思是教她不要說出來,但柳珠誤解了這個眼色的用意,她跳起身來對姨父說:「姨父不信,我跳給你看!」柳珠一面跳着夏威夷的草裙舞,挺着胸,扭着臀,一面唱着火奴魯魯的熱情歌,這下子給姨媽可急壞了,欲止無從,張德大搖其頭,頗有世風日下之感。而柳珠還自鳴得意,以爲姨父正賞識其藝術的天才呢!
四
柳珠在鄉下住得十分乏味,如果她不是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好消息,終身大事的吉期宣佈,她早就囘到城裏去了。
張妻見姨姪女兒呆在家裏悶氣,就叫兒子帶着她打獵去。張俊,柳珠換了獵裝,帶着獵槍,獵犬,出了莊門,逕奔叢山峻嶺而去。可是柳珠走得慢,一會兒要表哥攙着,一會兒要表哥扶着,把張俊麻煩得不知怎樣才好。走了老半天,才走到山坡下面,坐下憩息。柳珠看到有隻野鷄,忙拿起槍來,一彈射出,野鷄撲撲翅膀飛去。張俊說:「你這樣怎麼能打着東西?看我的!」他仰頭看着天空,飛來了一隻鷂子。「你瞧!」一聲未已,就聽得「砰」聲響,那只鷂子從空中一連翻了幾十翻,跌落到山澗裏去了。星海飛竄了前去,把鷂子啣囘來,放置在張俊的面前。「表哥,像你槍法眞不壞,我拜你做師傅好不好?」柳珠故意地倚在表哥的身上:「瞧!」
一隻灰兔從林中穿出來,柳珠擎槍便擊,槍彈落在密密的茶樹叢中,野兔並沒有打着,而打着了一個人,這人「哎喲!」一聲,似乎就倒在叢林中,張俊大吃一驚,連說「不得了,打傷人啦!」他急忙跑到林中査看,果然一個採茶的女孩被打中了腿,倒在血泊裏呻吟着。張俊扶起她來,撕下衣襟替她包紮傷處。柳珠則站在旁邊,冷冷的一聲不響。原來這個中槍的姑娘,正是她日前經過田畦被她濺了一瞼泥的姑娘。真是寃家路狹,在這裏又遇見了。
「姑娘,你住在什麽地方?我送你囘去!」張俊說。
這姑娘睜開了眼睛,仔細一看,不由得面呈慍色:「用不着,你們走你們的好了!」
「不,你是我們槍打傷的,我們應該負責把你送囘去,替你把傷醫治好啦!」張俊解釋着說。
「我不要。」這姑娘掙扎着起來,但又跌下去。
「她不要就算了,表哥,咱們走!」
張俊怒目地對柳珠看一眼,也不理她,還是低聲的對這姑娘說:「你不要這樣,我們對不起你,我有責任送你囘去,你的血流得過多,很危險,要是有細菌透進血管,那更不得了,我一定要送你,你住在什麽地方?」
這姑娘聽了半天,不好意思拒絕,只得用手指了山下,張俊扶着她起身,柳珠又妬又恨。這姑娘甫站起來,腿一軟,又坐下去,張俊只得抱着她往山下走。柳珠大怒說道:「表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這是救人,你打傷了人,我來救,難道你還不願意?」
「我就不願意,我要你放下她跟我走!」
「你是長的一副什麽心肝?打傷了人不管,還要我跟你走,哼!」張俊逕自抱着這姑娘下山。
「好!」柳珠的眼涙都急出來:「星海,我們囘去!」然而星海不回去,牠搖着尾巴跟在張俊的後面走,柳珠只得拾起槍,一個人,獨自的跑囘家去。
張俊抱着這姑娘走下山來,原來這姑娘也是住在茶花村,走近她的家門時,只見一個老者驚訝的叫着:「你怎麼啦阿雲?」
阿雲從張俊的懷裏下來,坐在地上,流着淚,張俊抱歉地對老者說:「老伯伯,她是你的女兒嗎?我是張德的兒子叫張俊,因爲打獵誤傷了你的女兒,眞對不起,所以我送她囘來,替她醫治。」
這時愛樂看到了星海,兩狗相對,唁唁的狂吠,張俊連忙止住了星海,王林也止住了愛樂:「張少爺,我叫王林,你不認識我,我是認識你的,你在七八歲的時候,還不是常到我們家來頑嗎?那時候阿雲才四五歲,你們還在一起捉迷藏,唱山歌吶!後來你大啦,你爸爸不准你跟我們窮孩子在一塊頑,怕低辱你的身份,又把你送進城念書,這話一說十幾年嘍,阿雲都快二十啦,你出來進去我們都看着,你一年大一年,看着你從小長到大,也看着你爸爸的屋子一年大一年,看着你爸爸的地從少到多,現在這村上的富戶漸漸變成了窮戶,田地也一家一家的併到了你家,你家成了這個村上的第一大戶,我們剩下的十畝八畝地,也快要完啦!你家富啦!家家窮啦!錢給你爸爸一個人拿去啦!就連這條水溝的水都不給用,涵洞給堵上啦,讓我們乾死!」
「張老伯,我眞是這些年祗顧在外面念書,家裏的事,我一點兒也不淸楚,爸爸這個人,就是這點兒不好,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我想,我總要想法子勸他不能這様下去的。現在我得要先替雲姑娘治傷,我囘去拿藥箱,馬上就來!」
張俊拿了藥箱來,替阿雲洗淨,敷藥,打針,又留下了一包藥,叫王林每天給阿雲吃三次,每次三片。然後再替阿雲量一量溫度,這才提着藥箱囘去。
阿雲的傷漸漸的好了,張俊過一兩天,總要來看阿雲一次。王妻對丈夫說;「張德那樣的壞,可是他的兒子還不錯,懂得人情世故的。」
「他爸爸壞事做多了,自然要他假情假意的對我們窮人賣賣好,這樣不就少恨他爸爸一點兒嗎?」阿昌氣憤的說。
「你懂什麼,胡說八道!」王妻阻止阿昌說。
「你以爲我還是三歲小孩兒呀?我也快二十歲啦,還看不出?張俊比他爸爸更壞,他爸爸是明壞,他是暗壞,暗壞人家看不出,還以爲他是好人吶!」阿昌不服氣的說。
「少說幾句,你懂個屁」!王林拍了阿昌一巴掌。
「我不懂,你懂!」阿昌鼓着嘴,牽着愛樂出去了。
五
張德在大廳上咆哮着:「査!査!是誰把水溝的涵洞給開開的?」
「我不知道!」阿祥阿輝等低着頭說。
「你們是死人哪!涵洞被人扒開都不知道。」
「我們不敢說!」阿瑞抽冷子來上一句。
「有什麽不敢說,你怕王林那老狗吃了你?」
「這不關王林的事,是我開的!」張俊挺身而出。
「你開的?」張德直瞪着兩眼,莫明其妙的間:「你爲什麼要把涵洞給開開?」
「這條水溝是公用的,並不是我們一家用的,你把水溝堵上,水流不下來,人家毎天在擔水灌田:這根本不是個辦法,也沒有這個道理。」
「這麼說,你倒幫着人家說話?你不是我的兒子,你是吃誰的飯長大的?我替你攻書上學,把你養活大啦,你倒反對起老子來啦?你這不是想造反嘛?」拍的一個耳光,打在張俊的臉上。
「好啦!好啦!別說了,你怎麼可以跟你爸爸鬥嘴?進來進來!」張妻把兒子拖進房,勸着說:「爸爸這樣做,都是爲了你,你怎麽連個好歹都不知道呢?」
「我不要爸爸這樣的爲我,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張俊摸着熱辣辣地的腮幫說。
只聽得張德呼斥着阿祥等:「快點把涵洞再給堵上,要是有人再敢扒開,不管是誰,給我打個半死!」
張俊心上一塊鉛石給壓着,始終透不出氣來。
這樣過了半月,張妻一晚對丈夫說:「阿珠在這兒已經住了好些日子啦,你看她跟俊兒的事情怎麼樣?我們擇個日子替他們下訂吧。」
「慢慢兒再說,我要到城裏去完糧,等我囘來再商量吧!」
「你幾時囘來?」
「快!如果沒有事,明天就可以囘來啦!不過怕的還有一點手續要辦一辦,大槪最多四五天就可以辦完啦!」
「好吧!那就等你囘來!」
張德收拾了行囊,進城去了。
張俊送走了父親,囘來對母親說:「王林的女兒阿雲被表妹打傷,現在完全好啦!人家沒找我們麻煩,我很不過意,我想請她來吃頓飯,一來替她算是道個歉,二來聯絡感情,王林本來是個老實人,一家都很好,犯不上跟人家作對,我想借這個機會解釋解釋,以後再跟爸爸說說,化敵爲友,兩下拉開就完了,媽你說可是?」
「好是好,可是你爹的脾氣,怕不會答應。」
「只要你先答應了就行啦,爹到城裏,總得幾天才能囘來,我們明天就請她來吃飯,你說好不好?」
「好好好!媽疼你,你愛怎麼辦就怎麽辦吧!」
張俊高興地去請阿雲,可是柳珠看在眼裏,十分氣惱。只見表哥拿着照相機,一溜烟的出去了。
張俊到了王家,見沒人,又趕到田裏,阿雲一家正在鋤地,張俊叫着:「王老伯,我媽請雲姑娘明天到我家吃飯,我先來吿訴一聲。」
「你媽請阿雲吃飯?」王妻抬起腰來問。
「是的,伯母,因爲雲姑娘傷好了,我媽說眞對不起她,請她吃頓飯,賠個不是!」
「算啦!還賠什麼不是,只要大家知道就完啦!」王林說。
「老伯,一定一定,我媽的意思,一定要請雲姑娘去。」張俊又問阿雲:「你願意去嗎?」
阿雲低下頭,笑着不說話。
「好吧,旣然你誠心誠意的,去就去吧!」王林笑嘻嘻地看看張俊,也看着阿雲。
「來!我替你們照相。」張俊替阿雲照了又替阿昌照,再替王林夫婦照,把一捲膠片照光了才放手。張俊歡歡喜喜的囘家裏。第二天忙着叫廚房裏做菜,宰鷄,天傍晚,阿雲穿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張妻看阿雲眉清目秀,怪可人的,心中也自歡喜。只有柳珠不快,她認爲這是她的恥辱,一個男人,敢於在她面前和另外一個女人接近,這不是明明白白在諷剌她嗎?這事怎麼辦呢?思來想去,她想到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在她認爲是非常得意的傑作,於是她安排着逐步進行的計劃,假意地奉迎着阿雲,在吃飯的時候,柳珠手裏揑着一件東西,輕輕地從桌下伸手,準備放在阿雲的膝上,不料婢女小香捧着菜盤,柳珠的手一拐托盤跌落地上,碗碎湯潑,濺了柳珠一身,柳珠只得縮囘手,到樓上去換衣,誰知走得匆忙,手帕裏的東西掉了下來,柳珠連忙檢起包好,等衣服換畢,再入席間,又俟機把這手帕輕輕的從桌下送到阿雲的膝上。這時柳珠忽然的叫道:「哎呀!姨媽頭上的花怎麼不見了?」
「我的珠花不見了?」張妻摸一模頭上:「我沒有戴出來吧?也許在房裏。」
「我剛才還看見珠花在你頭上,怎麼我上樓一趟就不見了」柳珠故意的說。
「眞的嗎?這倒奇怪!」張妻再摸一摸頭。
「是不是阿香給偷去了?」柳珠指着小香說:「要是你偷的快拿出來!」
「我沒有!我沒有!」小香吓得臉黃,伏在地上四處尋找,只見阿雲腿上有一個手帕,露出珠花的一角來:「哦!在這裏!」小香把阿雲膝上的珠花取過來。
「怪不得我看到她在姨媽頭上一揚手,偷珠花,這倒是一件好本事,一忽兒人家的東西,就變成她的啦!」柳珠的鼻子哼一聲:「郷下的女人哪!眞沒出息,好事不做,做起賊來。」
阿雲受此寃枉眼淚快要急出來了,她正待分辯,偏偏張德囘來了,看見家中紛亂,忙問何事?柳珠指着阿雲說:「這個女人,偷我姨媽的珠花,被我們抓着了!」
「她是誰?怎麼會到我家裏來?」
「她是王林的女兒,是表哥的好朋友,不瞧表哥一直替她養傷治病嗎?現在傷好啦,上門來偷東西啦!要不是姨父囘來得快,還不知道要被她鬧成什麼樣子吶!」
「我離了家才一天,就出了事,這還像話嗎!」
「想不到她是這樣!」張妻嘆息着說:「看她樣兒倒是斯斯文文的。」
「媽!」你先別怎麼說:「阿雲不會的!」
阿雲受了委曲,大哭而去,張俊追着,阿雲不顧路的高低,一直奔出莊去,張俊被父親喊囘來,氣悶地上樓,在樓梯上忽然看到了一角珠花,這是柳珠跌斷了的,沒有檢起,張俊這時恍然大悟,忙將珠花的一角拾起,逕入母房,母親的房裏正在議論着阿雲的事情,張德聽了柳珠的話,知道兒子還替阿雲一家去照相,這簡直是忘了自己是什麼人,這一氣非同小可,正巧張俊進房,張德直在兒子的臉上:「你來得正好,你跟個賊婆娘照相,我張家祖宗十八代的臉都被你丟盡了!」
「爸爸,你不要生氣,我們張家有一件眞正丟臉的事。」張俊取出了珠花的一角給他母親,「你的珠花是不是缺了一角?」
張妻取下珠花看了看,果然有一隻角丟了,張俊說:「這隻角是在表妹的房門口樓梯角上檢來的?」
「珠花怎會到阿珠的房裏的?」張妻詫異地說。
「這就得問表妹了,她做的事,她自己知道。」
「阿珠,你說,怎會到你房裏的?」張妻問。
「我,我,我不知道……」柳珠一時倒急得說不上話來。
「我知道!」張俊冷笑着:「你這種贓栽害人的方法,瞞不了我,表妹,你爲什麽這樣幹!人家淸淸白白的給你這麼誣賴,你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柳珠柳眉倒豎,兩淚交流:「我要殺了她!你,你!你去愛那個臭丫頭去吧,我走啦!」柳珠上樓收拾了提箱,毫不留戀的走了,張徳目選柳珠去後,看了老婆一眼:「你的好姪女,還會來這麽一手!」
張妻伏案大哭:「阿珠,你太不替我爭氣了。」
六
阿雲哭囘家中,王林夫婦忙問何事?阿珠把珠花的事情說了一遍,王林氣得直搖頭:「到底張家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把我女兒騙去,做成圈套來害人,好!我去和那個小子算賬,拼了命也替我女兒弄個淸白。」
「我早就說過,張俊是什麼好人?假的!不瞧把姐姐騙去……」阿昌正得意揚揚的在說忽地被他母親打斷:「你少開口!」阿昌只有閉上嘴,不說了。凑巧張俊來到,解釋誤會,王林一家那裏肯聽,連阿雲也把張俊恨得牙癢癢地了。張俊不得要領,悻悻而去。門前的愛樂跟着張俊,直搖尾巴,張俊說:「難道你能同情我嗎?」愛樂點點狗頭。張俊大喜,從懷中取出紙筆,就地借着月光寫了一信,交給愛樂,愛樂啣了信,跳進阿雲的窗內,把信放在床上,阿雲見信,這才知道是柳珠因為妬忌撚酸,做出來的事情,心就軟了下來,她見愛樂蹲在地上不走,似乎等待囘信,她就寫了幾個字,交與愛樂。愛樂躍窗而去,不見了張俊,就循着張俊的足跡氣味,直到張家,星海迎來,愛樂把信交與星海,星海啣了進宅,不一會出來,又啣囘一信,交與愛樂,愛樂再啣囘家,由於這兩隻狗紅娘從中撮合,阿雲和張俊之間誤會,就完全冰釋了。
不料這晚愛樂正啣信來的時候,忽見人影幢幢在張德書房閃爍,愛樂狂吠,驚起了衆人,星海則竄入書房,見老主人正被盜匪綁在椅上,堵塞了嘴,在房中翻箱倒籠,搜羅財物,立卽向一盜猛力撲去,愛樂也加入戰團,向另一盜猛噬,羣盜見雙犬撲來,不敢久留,恐被人攔刼,就便推倒油燈,放起火來,把張德架走。張妻和張俊及所有的佣人一齊驚起,追盜的追盜,救火的救火。阿祥敲起一面銅鑼,連王林一家也驚起了,都來救火,只聽得張妻大叫:「俊兒!你爸爸還在火裏,快點救他出來呀!」
「爸爸已經被賊帶走了,我去追爸爸!」張俊說着就帶同阿祥阿輝阿瑞以及鄰舍人等!連同愛樂,星海,舉着火把直奔莊外,在橋口見有張德遺落的一隻鞋,張俊送在愛樂鼻上聞一聞,愛樂飛奔而去。大家在後力追,兩狗一路嗅着一路追,終於追到了盜匪,愛樂不顧生死的跳躍狂噬,咬翻了一匪,人犬糾纏,生死搏鬥,其餘人等已見目標,分路包圍上來,羣匪以衆寡不敵,只得丟下了張德,和刼來的財物,鼠竄而去。可是愛樂由於死纏盜匪不放,而被另一盜匪抽刀剌入腹中,倒地而死,但愛樂也還値得,被牠咬翻在地的一個盜匪,傷重氣絕,陪着愛樂一同死了。
刼後餘生的張德,見愛樂爲救他而死,立存「獸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想,嘆了口氣,撫摸着血糊零落的愛樂說:「你爲了救你主人的仇人,犧牲了性命,我,我……」老涙不禁由張德的眼中落下來。
囘到了莊前,見自己的家門 , 殘煙飄繞,張妻已被阿雲一家攙扶到了王家,躺在繩床上休息。
王林迎上來,默然無語,張德半天說不上話來,還是王林先說:「張老爺,你也別難過,房子雖然燒了,還可以再蓋,只要人在,還怕沒有屋子嗎!」
不自持的張德上前,執着王林的手,流着淚說:「王大哥,我眞對不住你,對不住大家,今天我家出了事,大家這樣的幫忙,連狗都不計前仇,爲了我送命,我張德是個人哪,難道我連個畜生都不如嗎?我要改囘我從前的過錯,我們都是種地的,應該大家幫助,可是從前我不這樣想,我要一個人發財,這財都是大家的血汗哪!我憑什麼一個人來享用,使大家吃苦吶?我錯了!請你原諒我,請大家原諒我,從今天起,我要從新做人。燒了的房子我也不蓋了,我要和大家一起做活,下地,耕田,水溝是大家的,當然大家都能用水,我的地多,我自己種不過來,應該分給沒有地的人種,俊兒!」張德含着兩泡淚水叫喚着兒子:「你說是不是!」
「爸爸,你這才是我的爸爸!」張俊也熱涙盈眶地拉着張德的手:「早該這樣啦!」
王林夫婦,阿雲阿昌,以及莊上的農戶們都爲感動,交頭接耳的談論着,變啦!變啦!連張德這個老頑固都變啦!
兩天後,張德簡單的土屋搭起來了,而愛樂的墳墓也建築起來了,墳前豎立着一塊碑,上寫「義犬愛樂之墓」六個大字,墓前圍着一圈人,都爲這隻義犬而哀悼,尤其是張德。
茶花村的情形變了,生氣也有了,滿山遍野的唱着「茶花曲」,水溝裏的水,通過了涵洞,向東西南北的田畦裏,四處奔流,王林夫婦在田裏插着秧,阿雲在山上採着茶,張俊在旁幫着搬簍子,携繩索,阿昌在山坡下放着牛,最奇怪的是阿祥、阿輝、阿瑞等一羣在田野鋤草的人們,中間夾着張德夫婦,老夫妻戴着斗笠,彎着腰,一鋤頭一鋤頭的在地上鋤着,汗水打到脚面,這是茶花村變了之後的新場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