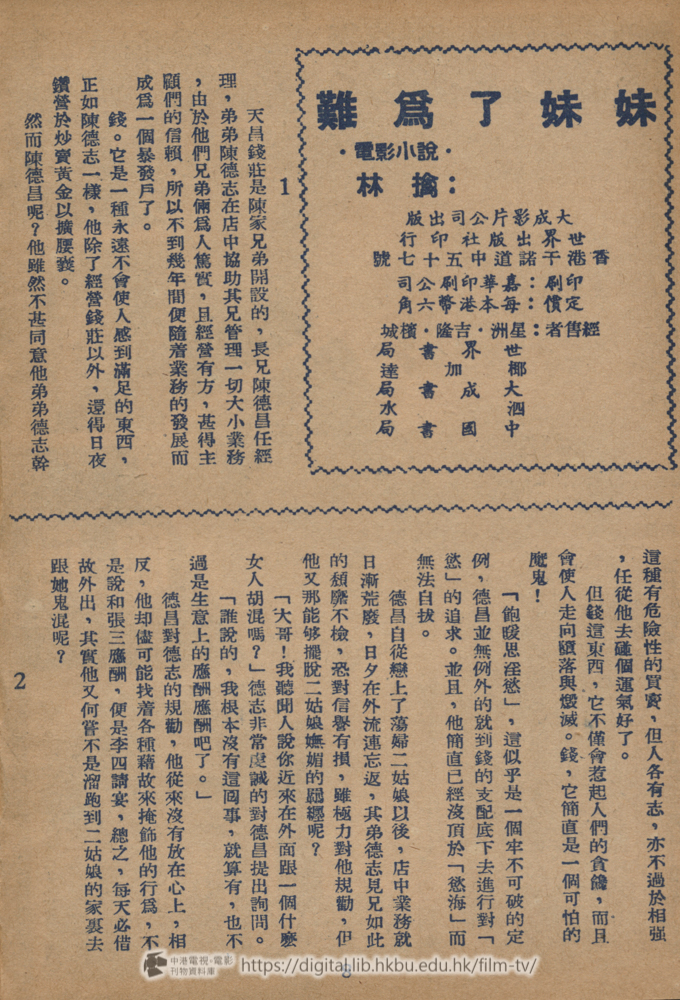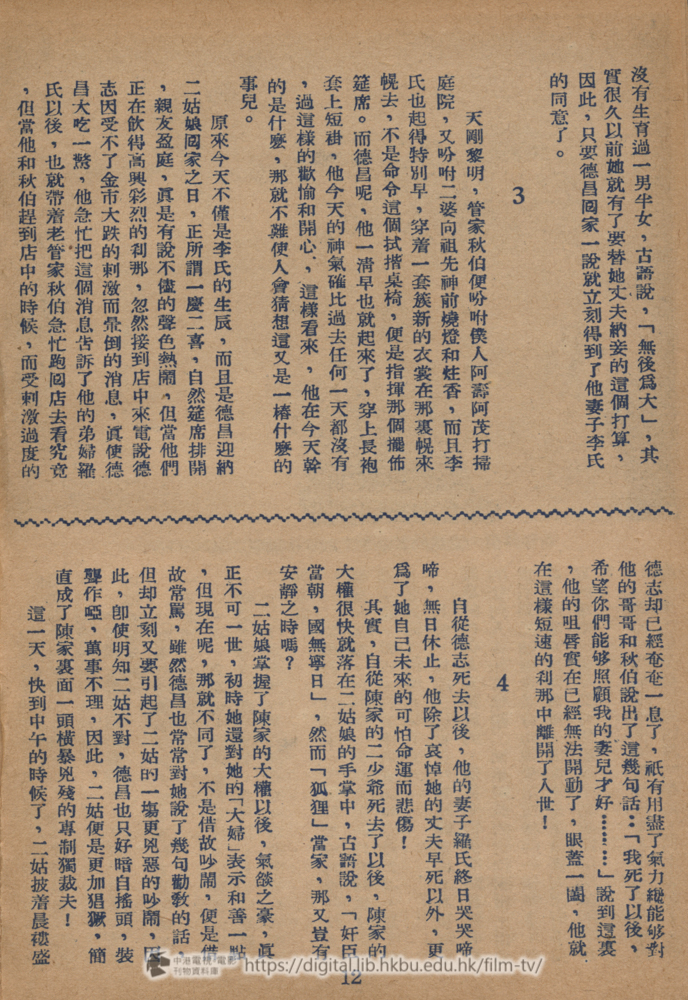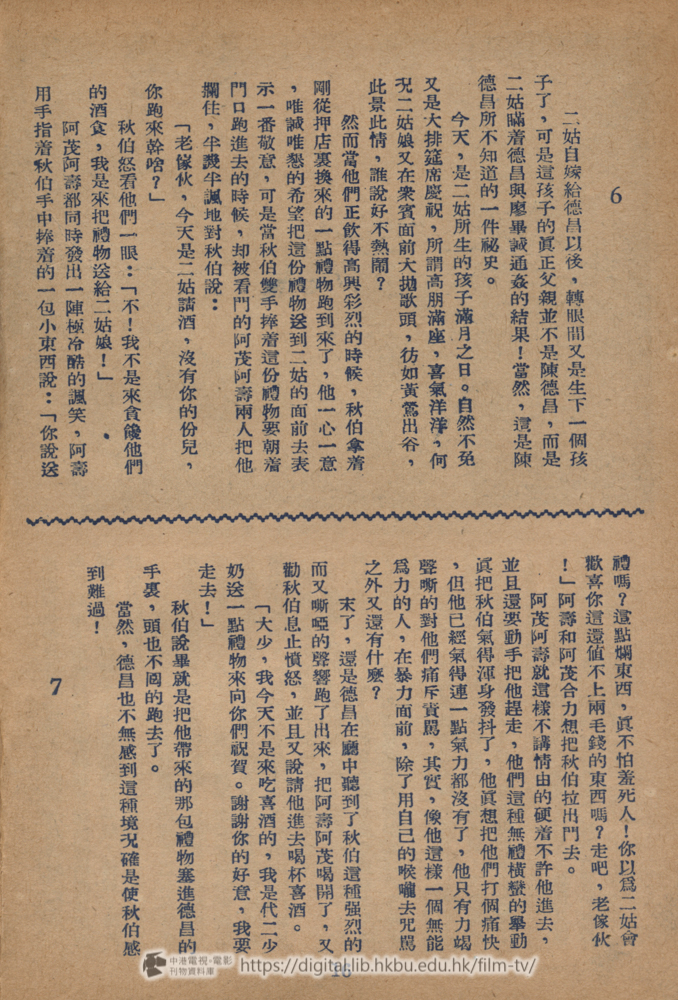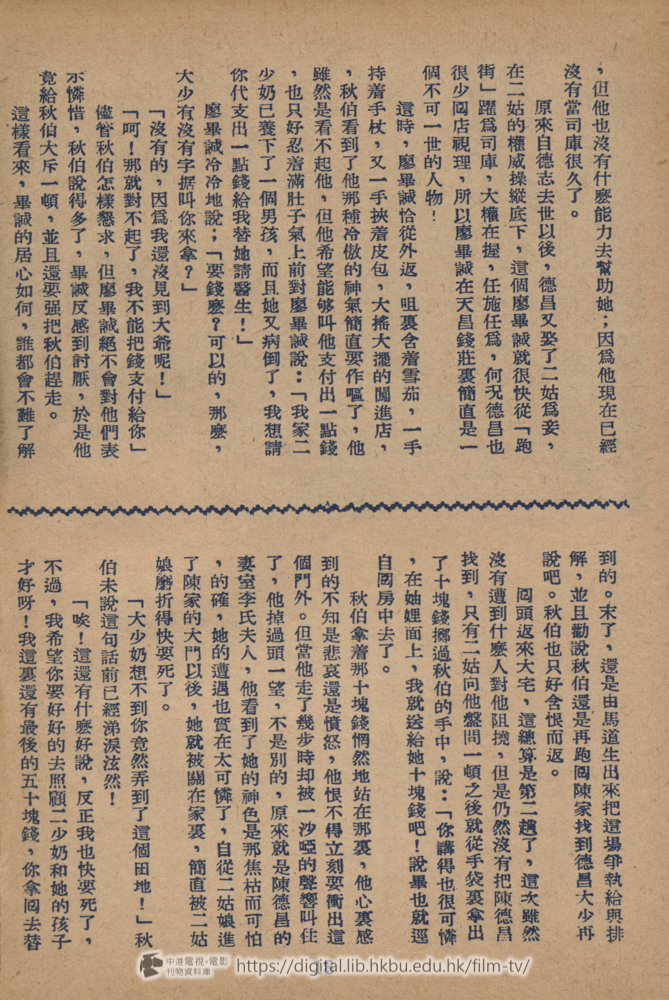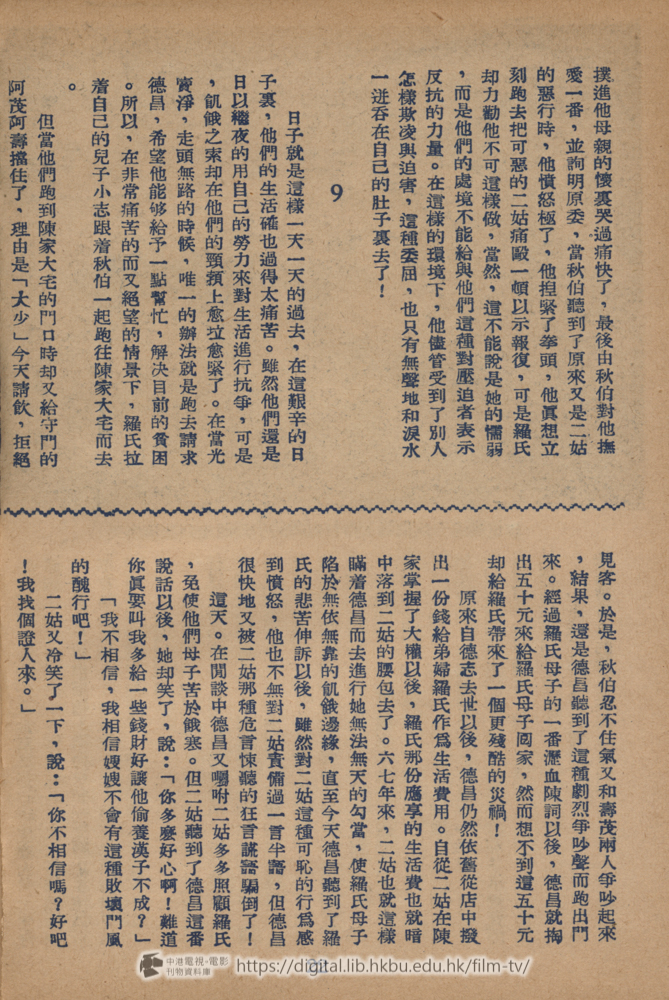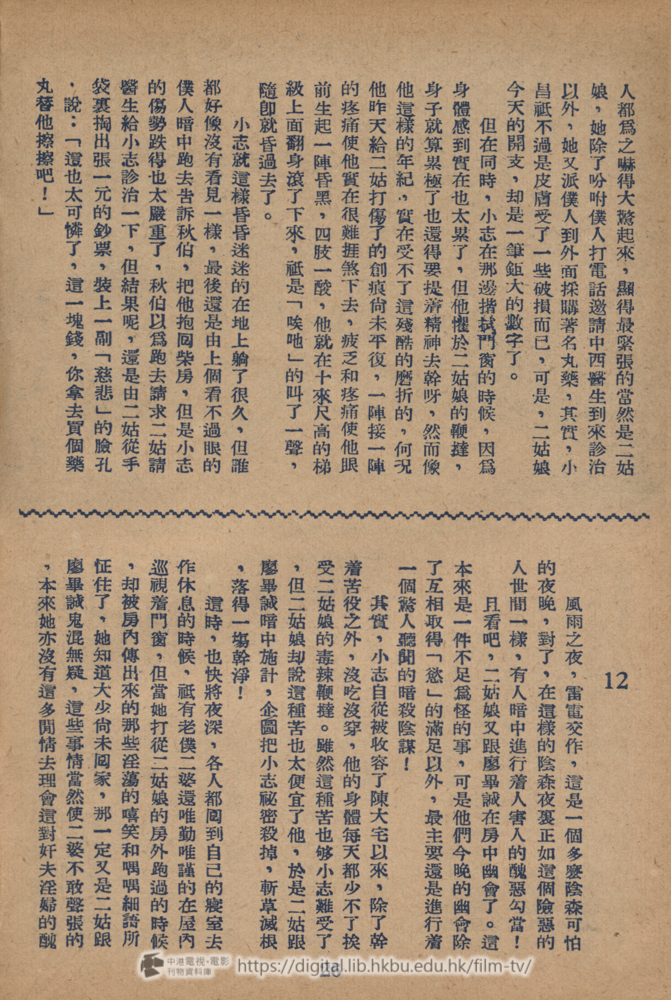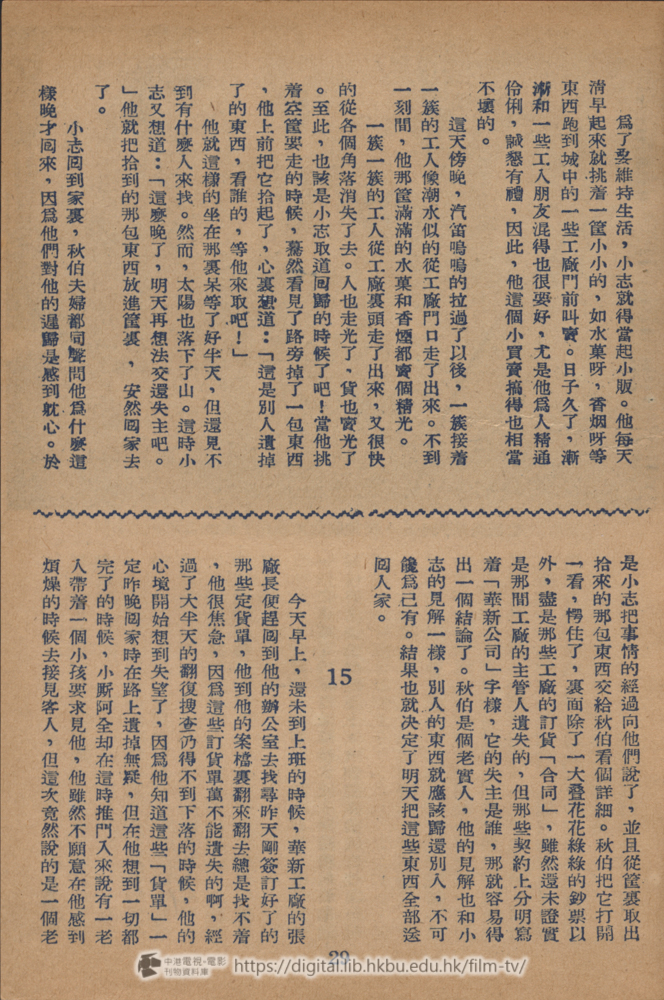難為了妹妹
吴楚㠶
帆大都以中年人的姿態管是在銀幕出現,但儘中年人吧,我們還是一樣感到一股泅湧澎湃的年靑人的氣息。就爲了這原因吧,你便可明白爲何電影界不能一天缺少吳楚帆。那麽讓我們爲他的永遠年靑而舉杯!
紫羅蓮
片塲中,正在休息的紫羅蓮眞是疲倦得可以,她躺在靠椅上,閉着眼睛,人家以爲她已經熟睡了。但這當中,有人突然叫:「蓮姐,到你!」那意思是要她到封影機前來。這一下,我們便看到紫羅蓮伸了伸腰站起來,神態是那樣的興奮,認眞,一點也看不出有何倦容。——對此,你能不驚異,能不嘆服。(林)
梅綺
要我對梅綺推崇,我眞是百分之百的情願。我主觀的看法,粵影界中,有優秀的演技的人不多,而梅綺是其中的一人。從來,人家以爲她只宜于演悲劇,誰知,她現在却以「反派」的姿態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有才能的演員决不受拘束于某幾種「型」,她要表現的是「社會的人」而不是編導者劃定的「人」。(林)
陳露華
這一年來,年靑女星能像陳露華似的躍進者除她以外無幾人。有人覺得這是她的幸運,我不同意。
陳露華有今天的地位聲譽決非幸運得來,那是憑了她不怠不倦的苦練有以致之。
里志誠
黄・楚・山
其實,對周和黄你比我更熟悉,他們在電影界已勤懇地工作了二十年,單這一點,就應對他們表示尊敬了。
鄭君綿
鄭君綿說他已放棄了當「小生」的企圖而願以丑角姿態出現,但我以爲為這是不必的,旣然有才能,何必限定自己于某一「範疇」,生活是多種多樣的,只要表現生活就够了。
姜中平
姜中平和鄭君綿都同是影界中年靑的鬥士,而且又是很相得的朋友,把兩人編在同一頁,意思就是說:希望他們能互相守望的向前邁進!
檸檬
「難爲了妹妹」是李因旗下的影片,導演是影壇宿將錢大叔,助導是周志誠。他們三人都是很有見地製片家,工作者,合作上固然順利,其成績也自使人可喜。
甘露
陶三姑
李兆芬
難為了妹妹
・電影小說・
林擒︰
天昌錢莊是陳家兄弟開設的,長兄陳德昌任經理,弟弟陳德志在店中協助其兄管理一切大小業務,由於他們兄弟倆爲人篤實,且經營有方,甚得主顧們的信賴,所以不到幾年間便隨着業務的發展而成爲一個暴發戶了。
錢。它是一種永遠不會使人感到滿足的東西,正如陳德志一樣,他除了經營錢莊以外,還得日夜鑽營於炒賣黄金以擴腰囊。
然而陳德昌呢?他雖然不甚同意他弟弟德志幹這種有危險性的買賣,但人各有志,亦不過於相强,任從他去碰個運氣好了。
但錢這東西,它不僅會惹起人們的貪饞,而且會使人走向墮落與燬滅。錢,它簡直是一個可怕的魔鬼!
「飽暖思淫慾」,這似乎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定例,德昌並無例外的就到錢的支配底下去進行對「慾」的追求。並且,他簡直已經沒頂於「慾海」而無法自拔。
德昌自從戀上了蕩婦二姑娘以後,店中業務就日漸荒廢,日夕在外流連忘返,其弟德志見兄如此的頹靡不檢,恐對信譽有損,雖極力對他規勸,但他又那能够擺脫二姑娘嫵媚的羈纒呢?
「大哥!我聽聞人說你近來在外面跟一個什麽女人胡混嗎?」德志非常虔誠的對德昌提出詢問。
「誰說的,我根本沒有這囘事,就算有,也不過是生意上的應酬應酬吧了。」
德昌對德志的規勸,他從來沒有放在心上,相反,他却儘可能找着各種藉故來掩飾他的行爲,不是說和張三應酬,便是李四請宴,總之,每天必借故外出,其實他又何嘗不是溜跑到二姑娘的家裏去跟她鬼混呢?
二姑娘原來就是店中那個「跑街」廖畢誠的姘婦,是一個又妖冶而又非常潑辣的女人,其實,廖畢誠就一個詭譎陰險的傢伙,與其說他們是一對妍頭,無寧說是一雙「老千」,他們倆現在又在商考着如何對陳德昌進行下手的計劃。
二姑娘穿着袒胸的褸衣躺在床上,廖畢誠俯下身去吻她的咀唇,輕輕的對她說:「那麽,你就照我們的計劃去幹吧。」看看手錶已經是四點三刻了。「時間快到五點了,我得要走了,不然,他來了那才是糟糕。」
廖畢誠接二連三的在她的咀唇,在她的胸脯吻吮過了以後就急忙跑出門外走了。
在廖畢誠剛跑出去不久,陳德昌的汽車已經在門前停了下來,二姑娘的「心腹之僕」心姐便急忙走過接下幾盒東西之後,陳德昌口咬雪茄,便大搖大擺的向二姑娘的臥房中闖進去了。他看見二姑娘還沒有起床,便輕輕的跑過去把她搖動了幾下,但二姑娘瞪了他一眼之後又不作聲了,
「您起來吧,我有很多東西要送給您呢!」他用非常撩人憐憫的口氣向她懇求。
但二姑娘並沒有瞧他一眼,似怨似艾的道:「你這沒有心肝的傢伙。你這種鬼東西我不要,我不要⋯⋯」
這樣看來,二姑娘顯然在生他的氣了,這出乎意料的突擊,眞是使他有點慌張起來,但爲了什麽緣故?這才是一椿使他感到惶惑的事。於是他忐忑不安的對二姑娘說;
「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事情,請你饒恕我吧,但對於我愛你,難道你還沒相信這是我的眞心嗎?」
二姑娘從床上翻過身來,又是冷冷漠漠的說:「哼!你說眞心愛我,爲什麽又要過了這多的時候才來,」指一指放在檯上的時鐘:「難過又不怕人家爲你等得心焦麽?」
聽了二姑娘的這句言說以後,他才敢鬆下了一口氣,因爲他已經明白她口中說的是什麽,心中想的又是什麽了,他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只亮晶晶的鑽戒在她的面前幌幌了幾下,說:「你別生氣了,我送一只鑽戒給你,讓你高興高興。」說罷把鑽戒套進了二姑娘的指頭,然後輕輕的又向她的面額吮吻了幾下。
果然,二姑娘剛纔那種刁潑的神態竟豁然消失了,臉上一雙媚眼,挑着咀唇對德昌打個嬌嗔,便像孩子似的撲過德昌的胸懷裏,又嬌又嬉的把身子讓他擁抱,雖然這不過是二姑娘的一種假意做作,但在德昌來說,他以爲這是二姑娘對他的一種柔情,他眞有點樂得飄然若仙了。然而,他又何曾曉得這「柔情」的裏面就是一個陷阱,是一個由廖畢誠擺佈下的,陰毒得令人可怕的陷阱。
「這個鑽戒我當然是高興的,不過,你有一件事情是使我感到不高興。」二姑娘當德昌感到樂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這樣說。
「什麽,你可以吿訴我呀!」德昌猶恐不及似的對她搶着說。
二姑娘用手擠擠眼睛。裝着不好意思的模樣:「我說出了,恐怕你會不答應。」
「不,你說吧,什麽事兒我都可以答應你的呀,難道你還會對我不相信,我可以⋯⋯」他舉起了一只拳頭好像一個牧師在神聖面前宣誓那樣不苟與莊嚴。
二姑娘再不裝嬌了,非常莊重地對德昌說:「那麽,那麽,我問你,你到底要到什麽時候才帶我囘家呀,難道你打算讓我就這樣在外面過一輩子嗎?况且我已經懷了孩子了。」
其實他跟二姑娘在外面的關係從來未曾對他家裏的任何人宣說過的,他從來也很不願意使家裏的任何人去知道他跟二姑娘厮混的這個祕密,但他想不到二姑娘竟然會向他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那眞是如晴天打個霹震,這儘管是德昌感到如何不願意的事吧,但他又可能敢對二姑娘說出半個不字麽?
然而,事情却出乎於德昌想像之外,原來他的妻子李氏却是個三從四德的婦人,三十多歲了,還沒有生育過一男半女,古語說,「無後爲大」,其實很久以前她就有了要替她丈夫納妾的這個打算,因此,只要德昌囘家一說就立刻得到了他妻子李氏的同意了。
天剛黎明,管家秋伯便吩咐撲人阿壽阿茂打掃庭院,又吩咐二婆向祖先神前燒燈和炷香,而且李氏也起得特別早,穿着一套簇新的衣裳在那裏幌來幌去,不是命令這個拭揩桌椅,便是指揮那個擺佈筵席。而德昌呢,他一淸早也就起來了,穿上長袍套上短褂,他今天的神氣確比過去任何一天都沒有,過這樣的歡愉和開心,這樣看來他在今天幹的是什麽,那就不難使人會猜想這又是一椿什麽的事兒。
原來今天不僅是李氏的生辰,而且是德昌迎納二姑娘囘家之日,正所謂一慶二喜,自然筵席排開,親友盈庭,眞是有說不儘的聲色熱鬧,但當他們正在飮得高興彩烈的刹那,忽然接到店中來電說德志因受不了金市大跌的剌激而暈倒的消息,眞使德昌大吃一驚,他急忙把這個消息吿訴了他的弟婦羅氏以後,也就帶着老管家秋伯急忙跑囘店去看究竟,但當他和秋伯趕到店中的時候,而受剌激過度的德志却已經奄奄一息了,祇有用盡了氣力纔能够對他的哥哥和秋伯說出了這幾句話:「我死了以後,希望你們能够照顧我的妻兒才好⋯⋯」說到這裏,他的咀唇實在已經無法開動了,眼蓋一闔,他就。在這樣短速的剎那中離開了人世!
自從德志死去以後,他的妻子羅氏終日哭哭啼啼,無日休止,他除了哀悼她的丈夫早死以外,更爲了她自己未來的可怕命運而悲傷!
其實,自從陳家的二少爺死去了以後,陳家的大權很快就落在二姑娘的手掌中,古語說,「奸臣當朝,國無寧日」,然而「狐狸」當家,那又豈有安靜之時嗎?
二姑娘掌握了陳家的大權以後,氣燄之豪,眞正不可一世,初時她還對她的「大婦」表示和善一點,但現在呢,那就不同了,不是借故吵鬧,便是借故常罵,雖然德昌也常常對她說了幾句勸敎的話,但却立刻又要引起了二姑旳一塲更兇惡的吵鬧,因此,卽使明知二姑不對,德昌也只好暗自搖頭,裝聾作啞,萬事不理,因此,二姑便是更加猖獗,簡直成了陳家裏面一頭橫暴兇殘的專制獨裁夫!
這一天,快到中午的時候了,二姑披着晨褸盛氣冲冲的從睡房裏面跑了出來,她一邊用手指擦着惺忪的眼睛,却又一邊張口大駡:
「這些過街叫賣東西的鬼小販,眞討厭,這麽早就給他們的鬼叫聲擾醒了!」她一股腦兒的坐在沙化椅上,順手拿着放在矮儿上的香煙盂就朝着羅氏的跟前那邊擲過去;「你這鬼東西,死吧!」
其實,只要聽到二姑那種呼喝叱駡的聲音就够使大家害怕了,何况還要看見她這麽兇狠狠的把烟孟一擲,那眞要是大家不給他嚇壞了才算奇怪,誰還敢開口?但畢竟還是德昌陪著笑臉上前對她這:
「我的好太太,別鬧吧!太陽也在半天了,這還不是應該起床的時候麽?」
德昌這句話却要引起了二姑一番更大的怒惱,還等待他說完時二姑便順手朝着德昌的臉上狠狠一指;像一頭老虎似的咆哮:「你這沒心肝的傢伙,難道連我多睡一點兒的權利也沒有?我老實吿訴你吧,要是我早知道你給我睡的房子是這樣糟,眞是連鬼也不會給你騙囘來呢!」
在德昌來說,他眞想不到二姑竟然兇蠻成這樣地步,但受到她這突然而來的一吵,他立刻光火了:
「喂,你說話要淸楚些!誰騙你囘來?要是我早知道你是這樣的,肯帶你囘來的才是鬼!」
當然,二姑也不會就這樣把口舌停止下來的,相反,她的嘴張得更闊,聲音更大,在那裏跳來跳去,簡直越駡越兇,也就越駡得爆火了。
最後還是羅氏跑上去對二姑勸說;「好了,你們別吵吧!你旣然不高興樓下這個房間,那麽就把我樓上的房間讓給你。」
到此爲止,一塲爭吵的結果,二姑娘總算已經獲得了一份「美滿」的勝利!
從此,羅氏就從樓上搬至地下。然而,誰也不會想到,羅氏不過纔在樓下住上了幾天也就被二姑又借某種緣故而把她硬着趕出陳家門外去了。
羅氏自從被二姑趕出陳家以後,也只好和秋伯搬到別一所破舊的房子去居住,起初的生活倒還可以說得過去一個時期,但後來也就一天比一天槽了,雖然秋伯也不計勞苦的去養雞畜鴨來撑持家中的用度,而羅氏呢,她也在家替人家幹上一些縫紉衣裳的活來供補家用,但這又眞能够解决他們處境上的困難嗎?沒有!他們的生活委實已走到了窮困竭極的時候了,何况在這樣困苦的日子裏,羅氏腹中之遺孤也快將分娩之期,目前生活旣已無法解决,而將來孩子出世以後又怎樣辦?這些問題終日在她腦子裏上下打轉,不由使她感到恐駭,徬徨,終於使她哀痛而哭!
「你又在哭什麽呢?就算眼淚流乾也又有什麽用?日子雖然是過得那麽難煞,只要你好好地把孩子生養下來,長大了,那時孩子不是就會替你報仇出氣了嗎?忍耐一點吧,何况哭得多了對胎兒的影響是不好的。」秋伯雖然是這樣的對羅氏進行勸慰,但她心裏的悲憤却又使她不禁酸淚橫流。
經過了秋伯一番勸解之後,她再沒有哭了,也只好正如秋伯所說,把將來的希望就寄放在未來孩子的身上吧!她反而看見秋伯的眼淚感到非常難過,說:
「秋伯,你別要難過吧,我不哭了⋯⋯今天的大爺的兒子滿月呢,我們雖然是那麽窮,但不能不要送給他們一點禮呀,不然,又說我們看不起他了!受不了這大罪!」
但是,他們又從那裏去拿錢?結果,羅氏又還不是翻開箱筐拿出最後一件比較像樣的衣服給秋伯去押店換上一些錢麽?
二姑自嫁給德昌以後,轉眼間又是生下一個孩子了,可是這孩子的正父親並不是陳德昌,而是二姑瞞着德昌與廖畢誠通姦的結果!當然,這是陳德昌所不知道的一件祕史。
今天,是二姑所生的孩子滿月之日。自然不免又是大排筵席慶祝,所謂高朋滿座,喜氣洋洋,何况二姑娘又在衆賓面前大拋歌頭,彷如黄鶯出谷,此景此情,誰說好不熱鬧?
然而當他們正飮得高興彩烈的時候,秋伯拿着剛從押店裏換來的一點禮物跑到來了,他一心一意,唯誠唯懇的希望把這份禮物送到二姑的面前去表示一番敬意,可是當秋伯雙手捧着這份禮物要朝着門口跑進去的時候,却被看門的阿茂阿壽兩人把他攔住,半譏半諷地對秋伯說:
「老傢伙,今天是二姑請酒,沒有你的份兒,你跑來幹啥?」
秋伯怒看他們一眼:「不!我不是來貪饞他們的酒食,我是來把禮物送給二姑娘!」
阿茂阿壽都同時發出一陣極冷酷的諷笑,阿壽用手指着秋伯手中捧着的一包小東西說:「你說送禮嗎?這點爛東西,眞不怕羞死人!你以爲二姑會歡喜你這還値不上兩毛錢的東西嗎?走吧,老傢伙!」阿壽和阿茂合力想把秋伯拉出門去。
阿茂阿壽就這樣不講情由的硬着不許他進去,並且還要動手把他趕走,他們這種無禮橫蠻的舉動眞把秋伯氣得渾身發抖了,他眞想把他們打個痛快,但他已經氣得連一點氣力都沒有了,他只有力竭聲嘶的對他們痛斥責駡,其實,像他這樣一個無能爲力的人,在暴力面前,除了用自己的喉嚨去咒駡之外又還有什麽?
末了,還是德昌在廳中聽到了秋伯這種强烈的而又嘶啞的聲響跑了出來,把阿壽阿茂喝開了,又勸秋伯息止憤怒,並且又說請他進去喝杯喜酒。
「大少我今天不是來吃喜酒的,我是代二少奶送一點禮物來向你們祝賀。謝謝你的好意,我要走去!」
秋伯說畢就是把他帶來的那包禮物塞進德昌的手裏,頭也不囘的跑去了。
當然,德昌也不無感到這種境况確是使秋伯感到難過!
過了不久,羅氏的腹中遺孤也吿誕生下來了。孩子的誕生,當然是羅氏感到慶幸而愉快的一件喜事。但那時候,他們的生活環境確實已經走到了極點,窮,雖然是他們捱熬慣的生活,但今天羅氏因爲養下了一個孩子而病倒了,這却是秋伯感到萬分焦急的事,於是,在這樣無法可想的情景,唯一的辦法除了向陳德昌請求週濟以外就別無其他了。
但當秋伯跑到了陳家的大門時却又被二姑娘的心腹女僕攔住了不許他進去:
「你找大少爺麽?他不在家!」心姐說了這兩句冷剌剌的話就砰然一聲把笨重的大門關鎖得緊緊了。
這個情景,雖然使秋伯的心頭感到有一種無比的槪憤,但環境如斯,也唯有呑聲忍氣的走了。
秋伯離去了陳家,又匆匆急急的跑到天昌錢莊,一進門口便扯住那個當會計的少泉就說:「大少在這嗎?」
秋伯那種愴忙萬急的神態與語氣倒使少泉爲之吃了一驚,待秋伯說明來意以後,少泉就把秋伯帶到馬道生那邊,請求馬道生替他們想想辦法。
馬道生本來就在天昌錢莊幹「司庫」的,爲人非常純樸而忠實,他雖然對二少奶的處境感到可憐,但他也沒有什麽能力去幫助她;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當司庫很久了。
原來自德志去世以後,德昌又娶了二姑爲妾,在二姑的權威操縱底下,這個廖畢誠就很快從「跑街」躍爲司庫,大權在握,任施任爲,何况德昌也很少囘店視理,所以廖畢誠在天昌錢莊裏簡直是一個不可一世的人物!
這時,廖畢誠恰從外返,咀裏含着雪茄,一手持着手杖,又一手挾着皮包,大搖大擺的闖進店,,秋伯看到了他那種冷傲的脾氣簡直要作嘔了,他雖然是看不起他,但他希望能够叫他支付出一點錢,也只好忍着滿肚子氣上前對廖畢誠說:「我家二少奶已養下了一個男孩,而且她又病倒了,我想請你代支出一點錢給我替她請醫生!」
廖畢誠冷冷地說;「要錢麽?可以的,那麽,大少有沒有字据叫你來拿?」
「沒有的,因爲我還沒見到大爺呢!」
「呵!那就對不起了,我不能把錢支付給你」
儘管秋伯怎樣懇求,但廖畢誠絕不會對他們表示憐惜,秋伯說得多了,畢誠反感到討厭,於是他竟給秋伯大斥一頓,並且還要强把秋伯趕走。
這樣看來,畢誠的居心如何,誰都會不難了解到的。末了,還是由馬道生出來把這場爭執給與排解,並且勸說秋伯還是再跑囘陳家找到德昌大少再說吧。秋伯也只好含恨而返。
囘頭返來大宅,這總算是第二趟了,這次雖然沒有遭到什麽人對他阻撓,但是仍然沒有把陳德昌找到,只有二姑向他盤問一頓之後就從手袋裏拿出了十塊錢擲過秋伯的手中,說:「你講得也很可憐,在妯娌面上,我就送給她十塊錢吧!說畢也就逕自囘房中去了。
秋伯拿着那十塊錢惘然地站在那裏,他心裏感到的不知是悲哀還是憤怒,他恨不得立刻要衝出這個門外。但當他走了幾步時却被一沙啞的聲響叫住了,他掉過頭一望,不是別的,原來就是陳德昌的妻室李氏夫人,他看到了她的神色是那焦枯而可怕,的確,她的遭遇也實在太可憐了,自從二姑娘進了陳家的大門以後,她就被關在家裏,簡直被二姑娘磨折得快要死了。
「大少奶想不到你竟然弄到了這個田地!」秋伯未說這句話前已經涕淚泫然!
「唉!這還有什麽好說,反正我也快要死了,不過,我希望你要好好的去照顧二少奶和她的孩子才好呀!我這裏還有最後的五十塊錢,你拿囘去替二少奶請醫生吧!」她把五張十元的鈔票緊緊地塞進了他的手裏。
秋伯拿着她那五十塊錢,心裏感到的不知是喜悅還是悲哀,他感動得要哭了。
「你囘去吧,請醫生要緊!」李氏還是這樣的對他催促着。
「謝謝你!」秋伯對李氏吿辭了也匆匆跑出門口去了。
然而,在這以後不久,李氏因受不了二姑的磨折也就悄然地死去了。
韶光易逝,轉眼又是過了六七個寒暑。
六七年以前的二姑的孩子小昌和羅氏的孩子小志都長大了,可是他們由於家庭教育不同,所以,這兩個小孩子有着兩種不同的性格。
小昌生長於一個富有的家庭裏,自然要給二姑當寶貝一樣的看待,縱驕成性,終日只曉吃吃玩玩打打鬧鬧,雖然年紀小小,但神氣十足,竟然一個十足美國電影中的小阿飛了!
然而小志呢?他雖然長養在一個這樣貧苦的家庭裏面,但他在他賢良的母親的循循敎導底下,成爲一個聰明伶俐的而又有優良品格的小孩,要是與小昌比較,那就簡直是無可比擬的!
有一天,小志獨個兒在門前看書,却給小昌走來硬給他牽走,本來小志很不高興跟他在一起玩的,但在小昌的苦苦的强迫底下他才肯跟他去逛一下。但當他們走到了一間小學校的門前,校塲上有一羣小孩子在那裏打球,他們倆站在籬笆外呆呆的望着,好不美羨,但小昌呢,他除了羨煞以外,他還有一個念頭,就是把別人的球搶到自己的手裏。
在他們看得出神的時候,却看見那個皮球自內跳過籬笆而跌進他們的面前,在小志正想把球拾起送囘人家的時候却被小昌把皮球搶走了。
小昌搶走了皮球便拔足狂奔,但却給那羣小孩子像窩蜂似的向小昌追逐,結果小昌被一羣孩子包圍着,這當然不免要受了這羣孩子的一番毆打,末了,還是小志人急生智,高叫「警察來了」才把這羣毆打小昌的孩子騙走。小志急忙扶着小昌奔跑囘家。
剛跑到小昌的家裏,恰巧德昌和二姑駕着汽車囘來,並且買了一大批玩具和幾大包糖菓給小昌。小昌一邊大叫「媽咪」又一邊把糖果塞進咀裏,同時又叫心姐把各種玩具搬來讓他玩過開心。
當然,陳家的僕人對這個「小少爺」是一呼百應的,這個遞糖果,那個捧玩具,大家都爲這個小「少爺」忙得團團轉。然而站在一旁的小志却從來不會給人當他是人的看他一眼,他在他們的眼中只不過是一條窮家狗罷了,甚至那個心姐還說小志「身臭」而加以驅逐。
然而更不幸的事來了。當小志站在一旁看小昌玩得高興的時候,他不禁忘形地拍手叫好起來,但立刻被心姐禁止了,而且要受一頓狼毒的斥駡,這也只不過還是一件小事罷了,更糟的還在後面呢!
小志站在一旁,不敢說,也不敢笑,只有像木雞似的站着,在那時却不提防小昌會把一架小車子推到小志跟前,小志給車子一碰,驚嚇得渾身一跳,雙脚一滑,也就跌倒地上去了,這一跌不打緊,最糟的是因爲小志跌倒而把小昌的車子踏壞了。
二姑看見小昌的車子被小志踏壞,這一怒是非同小可的,她氣勢汹汹的上前揪着小志的衣襟就舉掌朝着他的臉上一拍,說:「你這有爺生沒娘養的鬼東西,有意搗蛋,滾,給我滾!」拍了幾巴之後就把他推出門外去了。
小志被二姑一番無理毆打之後,也只好用手撫按着被打疼的臉兒哭哭啼啼的奔跑囘家。一進門便撲進他母親的懷裏哭過痛快了,最後由秋伯對他撫愛一番,並詢明原委,當秋伯聽到了原來又是二姑的惡行時,他憤怒極了,他揑緊了拳頭,他眞想立刻跑去把可惡的二姑痛毆一頓以示報復,可是羅氏却力勸他不可這樣做,當然,這不能說是她的懦弱,而是他們的處境不能給與他們這種對壓迫者表示反抗的力量。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儘管受到了別人怎樣欺凌與迫害,這種委屈,也只有無聲地和淚水一迸吞在自己的肚子裏去了!
日子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在這艱辛的日子裏,他們的生活確也過得太痛苦。雖然他們還是日以繼夜的用自己的勞力來對生活進行抗爭,可是,飢餓之索却在他們的頸𩓐上愈垃愈緊了。在當光賣淨,走頭無路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跑去請求德昌,希望他能够給予一點幫忙,解决目前的貧困。所以,在非常痛苦的而又絕望的情景下,羅氏拉着自己的兒子小志跟着秋伯一起跑往陳家大宅而去。
但當他們跑到陳家大宅的門口時却又給守門的阿茂阿壽擋住了,理由是「大少」今天請飮,拒絕見客。於是,秋伯忍不住氣又和壽茂兩人爭吵起來,結果,還是德昌聽到了這種劇烈爭吵聲而跑出門來。經過羅氏母子的一番瀝血陳詞以後,德昌就掏出五十元來給羅氏母子囘家,然而想不到這五十元却給羅氏帶來了一個更殘酷的災禍!
原來自德志去世以後,德昌仍然依舊從店中撥出一份錢給弟婦羅氏作爲生活費用。自從二姑在陳家掌握了大權以後,羅氏那份應享的生活費也就暗中落到二姑的腰包去了。六七年來,二姑也就這樣瞞着德昌而去進行她無法無天的勾當,使羅氏母子陷於無依無靠的飢餓邊緣,直至今天德昌聽到了羅氏的悲苦伸訴以後,雖然對二姑這種可恥的行爲感到憤怒,他也不無對二姑責備過一言半語,但德昌很快地又被二姑那種危言悚聽的狂言謊語騙倒了!
這天。在閒談中德昌又囑咐二姑多多照顧羅氏,免使他們母子苦於餓寒。但二姑聽到了德昌這番說話以後,她却笑了,說:「你多麽好心啊!難道你眞要叫我多給一些錢財好讓他偷養漢子不成?」
「我不相信,我相信嫂嫂不會有這種敗壞門風的醜行吧!」
二姑又冷笑了一下,說:「你不相信嗎?好吧!我找個證人來。」
所謂證人的人,當然又是心姐這個人了,其實心姐就是二姑的心腹,是二姑的同謀,她說的當然是跟二姑的一樣。所以,儘管起初還替羅氏辯護也好,但經心姐一說,也就不能不使他眞的對羅氏懷疑起來。
是夜,德昌果然看見一個男子從羅氏的園牆越過,又看見了一雙男女的影子在黑暗處擁抱,並且又聽到了那種不堪入耳猥褻細語和笑聲⋯⋯
至此,他相信了羅氏果然會幹出了這種下賤的醜行。他决意要把羅氏永遠逐出陳家。其實德昌已經被二姑愚弄了,原來他先頭看到的並不是眞的事實,而是二姑和廖畢誠預先佈置下來的一個醜惡計劃呢!
從此,羅氏便蒙受了這不白之寃而被德昌把她逐出陳家!
10
羅氏被趕走了之後,這個苦命的孤兒小志就被德昌拉囘他的家裏「育養」。照理伯父養育一個侄兒是應該的。何况他還是個陳家的眞正小主人。然而,事實却並不這樣,他在陳家只不過是一個小什役罷了:他每天總是跟着秋伯一起幹着澆花除草,打水,砍柴等粗重工作;他喝的吃的是一些冷飯殘羹,夜裏也就睡在柴房的稻桿堆上。他雖然是被磨折到這個令人不忍卒視的境地,但他每天還要受到的就是二姑的斥駡與鞭打。
其實,小志和小昌也同是陳家的少主人,但他們的生活是極端相反的;小志終日勞苦,除了兩頓冷飯殘羹以外也就什麽都沒有得進嘴:而小昌呢?終日閒逛,則時而「燕窩」,時而「參湯」,現在他又在那裏叫吃「山渣露」了,只要小昌一說,二姑便立刻吩咐心姐到廚房去拿。可是,當心姐捧着那碗熱騰騰的「山渣露」從廚裏要跑出來的時候,一不留神,就把坐在廚裏正在劈柴的小志一撞,碗打破了,那熱騰騰的「山渣露」立時把小志的腰背燙得又紅又腫,眞是使小志痛得在那裏直跳直叫,然而心姐還瞪大了眼,用力在小志臉就記一巴,氣凶凶地指住他駡:「你這小鬼頭,弄壞了別人的東西還要哭。燙死了你不要緊,小昌少爺沒有『山渣露』吃你才算倒霉!」
小志被燙傷了,痛楚難煞,受了心姐的一頓痛駡和一個耳光還不算,最後心姐還要把負了創的小志拖到二姑面前,使他得到一個更厲害的「懲罰」!
這次的「懲罰」,已經不是像心姐那樣祇給他一頓斥駡和記個耳光,而是一條相當粗糙的藤鞭拿在二姑手裏朝着他整個身軀像雨點般的鞭撻,打得皮開肉裂,鮮血直流,他抵不上二姑的幾鞭抽撻就昏倒過去。幸虧還是一個好心腸的老僕二婆因可憐小志的遭遇而暗中跑去報吿秋伯,然後由秋伯跑去向二姑哀求而把他寬恕。二姑又眞的會因秋伯的哀求而把他寬恕嗎?不!祗有聽從二姑認爲這種抽撻「遊戲」也感到相當滿足了的時候才會讓秋伯背負着重創的小志去。
小志的年紀雖然還是那末幼稚,但他却是人世間一個最不幸的人,他感到這人間也實在太殘酷而醜惡了,這人間醜惡就這様無情地把他潔白的心靈刻劃下了一道永難泯滅的創痕!
11
不待說,小昌在二姑的縱容底下是越來越壞了,然而,他正是二姑的掌上之珠,儘管他怎樣壞,但她對他的溺愛總是無微不至的。
一天,小志照例在那裏拭揩窗門。小昌又叫一羣僕人陪他在花園中踏車爲樂。不料被石頭一滑,小昌的小踏車翻倒了,這一跌,小昌自然要拚命地在那裏咆哮大哭,好像發生了件什麽似的,把全家人都爲之嚇得大驚起來,顯得最緊張的當然是二姑娘,她除了吩咐僕人打電話邀請中西醫生到來診治以外,她又派僕人到外面採購著名丸藥,其實,小昌祗不過是皮膚受了一些破損而已,可是,二姑娘今天的開支,却是一筆鉅大的數字了。
但在同時,小志在那邊揩拭門窗的時候,因爲身體感到實在也太累了,但他懼於二姑娘的鞭撻,身子就算累極了也還得要提着精神去幹呀,然而像他這樣的年紀,實在受不了這殘酷的磨折的,何况他昨天給二姑打傷了的創痕尙未平復,一陣接一陣的疼痛使他實在很難捱煞下去,疲乏和疼痛使他眼前生起一陣昏黑,四肢一酸,他就在十來尺高的梯級上面翻身滾了下來,祗是「唉地」的叫了一聲,隨卽就昏過去了。
小志就這樣昏昏迷迷的在地上躺了很久,但誰都好像沒有看見一様,最後還是由上個看不過眼的僕人暗中跑去吿訴秋伯,把他抱囘柴房,但是小志的傷勢跌得也太嚴重了,秋伯以爲跑去請求二姑請醫生給小志診治一下,但結果呢,還是由二姑從手袋裏掏出張一元的鈔票,裝上一副「慈悲」的臉孔,說:「這也太可憐了,這一塊錢,你拿去買個藥丸替他擦擦吧!」
12
風雨之夜,雷電交作,這是一個多麽陰森可怕的夜晚,對了,在這樣的陰森夜裏正如這個險惡的人世間一樣,有人暗中進行着人害人的醜惡勾當!
且看吧,二姑娘又跟廖畢誠在房中幽會了。這本來是一件不足爲怪的事,可是他們今晚的幽會除了互相取得「慾」的滿足以外,最主要還是進行着一個驚人聽聞的暗殺陰謀!
其實,小志自從被收容了陳大宅以來,除了幹着苦役之外,沒吃沒穿,他的身體每天都少不了挨受二姑娘的毒辣鞭撻。雖然這種苦也够小志難受了,但二姑娘却說這種苦也太便宜了他,於是二姑跟廖畢誠暗中施計,企圖把小志祕密殺掉,斬草滅根,落得一塲幹淨!
這時,也快將夜深,各人都囘到自己的寢室去作休息的時候,祗有老僕二婆還唯勤唯謹的在屋內巡視着門窗,但當她打從二姑娘的房外跑過的時候,却被房內傳出來的那些淫蕩的嘻笑和喁喁細語所怔住了,她知道大少尙未囘家,那一定又是二姑跟廖畢誠鬼混無疑,這些事情當然使二婆不敢聲張的,本來她亦沒有這多閒情去理會這對奸夫淫婦的醜行,可是當她正要掉身就跑的剎那,却有一句比刀尖還利的說話刺進她的耳朵;她淸楚地聽到廖畢誠這傢伙狼狼地說:「我已買到兇手了,準今晚可把小志殺掉!」
這句話眞像刀子一様剌進二婆的耳裏,使她驚得渾身打顫,她雖然是屬於「不管閒事」的一類人物,但她畢竟還是個有正義,有良心的老者,她不忍眼看着一個善良的孩子無辜被人殺害,她決定要救他,於是她絲毫不敢怠慢的躡足下樓,立刻跑去柴房把這事情報知秋伯,並決意勸吿和催促秋伯立卽携帶小志夤夜逃走。這個生死交關的危急關頭中,事實已不容許禍難臨頭的人有稍作思慮的要求了,在二婆的如星似火的催促底下,秋伯也顧不了這麽多,把正在發着高熱的小志駄在背上,冒着狂風猛雨,悄然地打從後園的小徑朝著野外拔足就跑。
果然,秋伯駄着小志剛跑出門去不久,幾個兇手拿利刃的大漢已潛進柴房,可是,秋伯駄着小志已經遠走他去了!
13
春去冬來,轉眼又是六七年了。一切事情都在變化着。
在這六七年來,小志一直跟着秋伯住在鄉間。依靠着秋伯夫婦的勤勞來把他養活,現在小志長大了,已經長成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伙子。由於他的天資聰穎,加上秋伯夫婦對他循循善導,他已經成爲一個很純良的而又精靈的孩子;尤其是他的身子長得也相當結實,能耐勤勞,幹起活來比誰都好,因此,秋伯夫婦對他的鍾愛簡直是自己的骨肉一樣。其實,在這六七年的艱辛日子裏,他們夫婦亦祗有從小志的身上來找獲一點安慰!
日子就這樣從不停留地走過,小志雖然隨着日子的流逝而長大,但相反的一面,秋伯夫婦却隨着日子的走去而衰老了,因此環境就大大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生活。旣已到了這個田地,秋伯那就不能不要叫小志挑些東西上城上去賣來維持生涯了!
然而,另一面呢?
同樣是六七年以後,自然小昌也長大到十四五歲的時候了,可是在他母親二姑娘的放縱下面也就越來越壞,不管還是那小小的年紀,但對于打牌抽烟等惡習却無不通曉。陳德昌眼看着自己兒子墮落行爲,雖然感到痛心,但他又有什麽說話可說呢?
14
爲了要維持生活,小志就得當起小販。他每天淸早起來就標着一筐小小的,如水菓呀,香烟呀等東西跑到城中的一些工廠門前叫賣。日子久了,漸漸和一些工人朋友混得也很要好,尤是他爲人精通伶俐,誠懇有禮,因此,他這個小買賣搞得也相當不壞的。
這天傍晚,汽笛嗚嗚的拉過了以後,一簇接着一簇的工人像潮水似的從工廠門口走了出來。不到一刻間,他那筐滿滿的水菓和香煙都賣個精光。
一簇一簇的工人從工廠裏頭走了出來,又很快的從各個角落消失了去。人也走光了,貨也賣光了。至此,也該是小志取道囘歸的時候了吧!當他挑着空筐要走的時候,驀然看見了路旁掉了一包東西,他上前把它拾起了,心裏想道:「這是別人遺掉了的東西,看誰的,等他來取吧!」
他就這樣的坐在那裏呆等了好半天,但還見不到有什麽人來找。然而,太陽也落下了山。這時小志又想道:「這麽晚了,明天再想法交還失主吧。」他就把拾到的那包東西放進筐裏,安然囘家去了。
小志囘到家裏,秋伯夫婦都同聲問他爲什麽這樣晚才囘來,因爲他們對他的遲歸是感到躭心。於是小志把事情的經過向他們說了,並且從筐裏取出拾來的那包東西交給秋伯看個詳細。秋伯把它打開一看,愕住了,裏面除了一大叠花花綠綠的鈔票以外,盡是那些工廠的訂貨「合同」,雖然還未證實是那間工廠的主管人遺失的,但那些契約上分明寫着「華新公司」字樣,它的失主是誰,那就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了。秋伯是個老實人,他的見解也和小志的見解一樣,別人的東西就應該歸還別人,不可饞爲己有。結果也就决定了明天把這些東西全部送囘人家。
15
今天早上,還未到上班的時候,華新工廠的張廠長便趕囘到他的辦公室去找尋昨天剛簽訂好了的那些定貨單,他到他的案檔裏翻來翻去總是找不着,他很焦急,因爲這些訂貨單萬不能遺失的啊,經過了大半天的翻復搜查仍得不到下落的時候,他的心境開始想到失望了,因爲他知道這些「貨單」一定昨晚囘家時在路上遺掉無疑,但在他想到一切都完了的時候,小厮阿全却在這時推門入來說有一老人帶着一個小孩要求見他,他雖然不願意在他感到煩燥的時候去接見客人,但這次竟然說的是一個老人與小孩求見,這却又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沉吟了一會,揮一揮手對小厮說:「好吧,你卽管帶他們進來!」
片刻,小厮帶着秋伯和小志進入張廠長的辦公室。秋伯手拿着一包東西便跑到張廠長的面前笑嘻嘻地說:「先生,你是華新工廠的廠長麽?」
張廠長看見秋伯是一個那麽善良的人,也就非常客氣的招待他,說:「是的,老伯,你有什麽事要跟我說麽?」
「不,我沒有什麽要向你說的事情,而是想把一包你遺掉了的東西送囘給你呀!」說着秋伯就把那包東西放進他的桌上:「你把裏頭的東西檢點一遍吧。」
秋伯這此言說眞使他感到驚異,要不是眞眞實實的見到就是自己遺掉了的那包東西放在眼前,他一定不會相世界上竟然會有這樣的一個奇蹟。他把紙包打開了,裏面的「貨單」不僅一張沒有失,而且那大叠鈔票也和原來的數目一毛都沒有錯。這個「奇蹟」給他的感動是太大了;因爲他最後已經知道這拾金不昧的人原來就是天天拿着東西在他工廠門前叫賣的那個從不被他注意的小孩!
張廠長很感動地擦摩着小志的面額說:「好孩子,我很感謝你,那麽,我給一點錢你作大一點的買賣好嗎?」
小志很堅决地瞪着一雙大眼睛說:「不,我們不希望別人給我們便宜的酧報,錢,並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東西呢!」
張廠長笑一笑,更受感動了,說:「好孩子,那麽你需要什麽呢,吿訴我吧?」
「你何以答應我在你工廠裏學習機器工作嗎?」
「當然是可以,不過像你這樣的年紀,你的媽媽是喜歡你這樣做嗎?」
小志聽到了張廠長說到他的媽的時候,不則聲了,垂下了頭,淚珠從暈紅了的眼眶裏一滴一滴的淌到地上。
「幹嗎,你哭了?」張廠長捧起了小志沾滿淚水的臉兒:「你吿訴我,你爲什麽哭呀?」可是,小堅並沒有囘答他的詢問,反而嗚嗚咽咽的伏在他的懷中哭了起來。於是,他不能不轉問秋伯去解釋了。
然而秋伯的心情也顯得非常沉重,打着那雙毫無光彩的眼睛,吁嘆了一聲,然後感慨地,一字一淚的把小志的身世吿訴了他。小志的身世確也太可憐了,從秋伯口中的復述:自從他的父親死了以後,他媽就含寃莫白的給趕出陳家,現在生死存亡未卜。而小志呢,要不是及時帶他逃走,恐怕早已被廖畢誠和二姑暗中謀害了。這一連串的有血有淚的事實,確實令人感到同情和槪感!
張廠長聽到了秋伯這番言說以後,不僅對小志的身世表示同情,除了收容小志在他的工廠中見習機器工作以外,還願意幫助學金給小志暇間上學讀書以求進步,並且還說需助秋伯解决生活困難,直至替小志報仇洩恨爲止。
16
一天,張廠長特地約請陳德昌到一間僻靜的酒店闢室談心,因爲他想藉着他們多年的友誼來對德昌進行勸諫,揭發廖畢誠跟二姑娘的醜穢行爲,希望德昌及時覺悟,免至日後身敗名裂。
儘管德昌被二姑娘迷惑太深了,可是事實到底還是事實,這多年來,廖畢誠跟二姑行爲如何,他當然亦不無知曉尤其是廖畢誠當了司庫以後,由於他的揮霍無度,行爲不檢,致影響店中的生意日落千丈。因此,德昌對廖畢誠早已失去了信任,因之常常跟二姑發生齟齬,弄得家無寧日。然而經過張廠長這次勸諫之後,他眞的開始覺悟了。他决意囘去馬上跟二姑提出離婚,並準備向官控吿廖畢誠虧空公款和跟別人妻子通姦罪。然而,當他囘到家裏的時候,二姑已經跟廖畢誠帶着孩子捲蓆私逃了。陳德昌立刻報警請求追緝。
其實,廖畢誠和二姑原來就是一對拼頭,並且是一雙「老千」,他們的目的本來就是爲了在陳德昌的身上搾騙一筆,現在旣然目的已達,也該是要走的時候了。
然而,當他們準備提款夜渡出走的時候,警局已根據情報及時趕至酒店把這對逃犯圍捕。廖畢誠自知罪惡難免,當場跳樓自殺,而二姑也罪惡滿盈,瑯璫入獄!
17
一個月前,小志不愼被機器軋傷而送入廣濟醫院留醫,今天正是張廠長,秋伯和德昌前來接他出院囘家休養的日子。但是秋伯他們扶掖着小志正離院房的時候,却看到一個中年女看護從樓上下來,這個看護是誰?原來就是七年前被德昌趕走了的小志的母親。
七年後的今日,他們母子雖然又吿重逢,但囘首前塵,恍如隔世,這又難怪他們不抱頭痛哭麽⋯⋯(完)
吴楚㠶
帆大都以中年人的姿態管是在銀幕出現,但儘中年人吧,我們還是一樣感到一股泅湧澎湃的年靑人的氣息。就爲了這原因吧,你便可明白爲何電影界不能一天缺少吳楚帆。那麽讓我們爲他的永遠年靑而舉杯!
紫羅蓮
片塲中,正在休息的紫羅蓮眞是疲倦得可以,她躺在靠椅上,閉着眼睛,人家以爲她已經熟睡了。但這當中,有人突然叫:「蓮姐,到你!」那意思是要她到封影機前來。這一下,我們便看到紫羅蓮伸了伸腰站起來,神態是那樣的興奮,認眞,一點也看不出有何倦容。——對此,你能不驚異,能不嘆服。(林)
梅綺
要我對梅綺推崇,我眞是百分之百的情願。我主觀的看法,粵影界中,有優秀的演技的人不多,而梅綺是其中的一人。從來,人家以爲她只宜于演悲劇,誰知,她現在却以「反派」的姿態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有才能的演員决不受拘束于某幾種「型」,她要表現的是「社會的人」而不是編導者劃定的「人」。(林)
陳露華
這一年來,年靑女星能像陳露華似的躍進者除她以外無幾人。有人覺得這是她的幸運,我不同意。
陳露華有今天的地位聲譽決非幸運得來,那是憑了她不怠不倦的苦練有以致之。
里志誠
黄・楚・山
其實,對周和黄你比我更熟悉,他們在電影界已勤懇地工作了二十年,單這一點,就應對他們表示尊敬了。
鄭君綿
鄭君綿說他已放棄了當「小生」的企圖而願以丑角姿態出現,但我以爲為這是不必的,旣然有才能,何必限定自己于某一「範疇」,生活是多種多樣的,只要表現生活就够了。
姜中平
姜中平和鄭君綿都同是影界中年靑的鬥士,而且又是很相得的朋友,把兩人編在同一頁,意思就是說:希望他們能互相守望的向前邁進!
檸檬
「難爲了妹妹」是李因旗下的影片,導演是影壇宿將錢大叔,助導是周志誠。他們三人都是很有見地製片家,工作者,合作上固然順利,其成績也自使人可喜。
甘露
陶三姑
李兆芬
難為了妹妹
・電影小說・
林擒︰
天昌錢莊是陳家兄弟開設的,長兄陳德昌任經理,弟弟陳德志在店中協助其兄管理一切大小業務,由於他們兄弟倆爲人篤實,且經營有方,甚得主顧們的信賴,所以不到幾年間便隨着業務的發展而成爲一個暴發戶了。
錢。它是一種永遠不會使人感到滿足的東西,正如陳德志一樣,他除了經營錢莊以外,還得日夜鑽營於炒賣黄金以擴腰囊。
然而陳德昌呢?他雖然不甚同意他弟弟德志幹這種有危險性的買賣,但人各有志,亦不過於相强,任從他去碰個運氣好了。
但錢這東西,它不僅會惹起人們的貪饞,而且會使人走向墮落與燬滅。錢,它簡直是一個可怕的魔鬼!
「飽暖思淫慾」,這似乎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定例,德昌並無例外的就到錢的支配底下去進行對「慾」的追求。並且,他簡直已經沒頂於「慾海」而無法自拔。
德昌自從戀上了蕩婦二姑娘以後,店中業務就日漸荒廢,日夕在外流連忘返,其弟德志見兄如此的頹靡不檢,恐對信譽有損,雖極力對他規勸,但他又那能够擺脫二姑娘嫵媚的羈纒呢?
「大哥!我聽聞人說你近來在外面跟一個什麽女人胡混嗎?」德志非常虔誠的對德昌提出詢問。
「誰說的,我根本沒有這囘事,就算有,也不過是生意上的應酬應酬吧了。」
德昌對德志的規勸,他從來沒有放在心上,相反,他却儘可能找着各種藉故來掩飾他的行爲,不是說和張三應酬,便是李四請宴,總之,每天必借故外出,其實他又何嘗不是溜跑到二姑娘的家裏去跟她鬼混呢?
二姑娘原來就是店中那個「跑街」廖畢誠的姘婦,是一個又妖冶而又非常潑辣的女人,其實,廖畢誠就一個詭譎陰險的傢伙,與其說他們是一對妍頭,無寧說是一雙「老千」,他們倆現在又在商考着如何對陳德昌進行下手的計劃。
二姑娘穿着袒胸的褸衣躺在床上,廖畢誠俯下身去吻她的咀唇,輕輕的對她說:「那麽,你就照我們的計劃去幹吧。」看看手錶已經是四點三刻了。「時間快到五點了,我得要走了,不然,他來了那才是糟糕。」
廖畢誠接二連三的在她的咀唇,在她的胸脯吻吮過了以後就急忙跑出門外走了。
在廖畢誠剛跑出去不久,陳德昌的汽車已經在門前停了下來,二姑娘的「心腹之僕」心姐便急忙走過接下幾盒東西之後,陳德昌口咬雪茄,便大搖大擺的向二姑娘的臥房中闖進去了。他看見二姑娘還沒有起床,便輕輕的跑過去把她搖動了幾下,但二姑娘瞪了他一眼之後又不作聲了,
「您起來吧,我有很多東西要送給您呢!」他用非常撩人憐憫的口氣向她懇求。
但二姑娘並沒有瞧他一眼,似怨似艾的道:「你這沒有心肝的傢伙。你這種鬼東西我不要,我不要⋯⋯」
這樣看來,二姑娘顯然在生他的氣了,這出乎意料的突擊,眞是使他有點慌張起來,但爲了什麽緣故?這才是一椿使他感到惶惑的事。於是他忐忑不安的對二姑娘說;
「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事情,請你饒恕我吧,但對於我愛你,難道你還沒相信這是我的眞心嗎?」
二姑娘從床上翻過身來,又是冷冷漠漠的說:「哼!你說眞心愛我,爲什麽又要過了這多的時候才來,」指一指放在檯上的時鐘:「難過又不怕人家爲你等得心焦麽?」
聽了二姑娘的這句言說以後,他才敢鬆下了一口氣,因爲他已經明白她口中說的是什麽,心中想的又是什麽了,他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只亮晶晶的鑽戒在她的面前幌幌了幾下,說:「你別生氣了,我送一只鑽戒給你,讓你高興高興。」說罷把鑽戒套進了二姑娘的指頭,然後輕輕的又向她的面額吮吻了幾下。
果然,二姑娘剛纔那種刁潑的神態竟豁然消失了,臉上一雙媚眼,挑着咀唇對德昌打個嬌嗔,便像孩子似的撲過德昌的胸懷裏,又嬌又嬉的把身子讓他擁抱,雖然這不過是二姑娘的一種假意做作,但在德昌來說,他以爲這是二姑娘對他的一種柔情,他眞有點樂得飄然若仙了。然而,他又何曾曉得這「柔情」的裏面就是一個陷阱,是一個由廖畢誠擺佈下的,陰毒得令人可怕的陷阱。
「這個鑽戒我當然是高興的,不過,你有一件事情是使我感到不高興。」二姑娘當德昌感到樂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這樣說。
「什麽,你可以吿訴我呀!」德昌猶恐不及似的對她搶着說。
二姑娘用手擠擠眼睛。裝着不好意思的模樣:「我說出了,恐怕你會不答應。」
「不,你說吧,什麽事兒我都可以答應你的呀,難道你還會對我不相信,我可以⋯⋯」他舉起了一只拳頭好像一個牧師在神聖面前宣誓那樣不苟與莊嚴。
二姑娘再不裝嬌了,非常莊重地對德昌說:「那麽,那麽,我問你,你到底要到什麽時候才帶我囘家呀,難道你打算讓我就這樣在外面過一輩子嗎?况且我已經懷了孩子了。」
其實他跟二姑娘在外面的關係從來未曾對他家裏的任何人宣說過的,他從來也很不願意使家裏的任何人去知道他跟二姑娘厮混的這個祕密,但他想不到二姑娘竟然會向他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那眞是如晴天打個霹震,這儘管是德昌感到如何不願意的事吧,但他又可能敢對二姑娘說出半個不字麽?
然而,事情却出乎於德昌想像之外,原來他的妻子李氏却是個三從四德的婦人,三十多歲了,還沒有生育過一男半女,古語說,「無後爲大」,其實很久以前她就有了要替她丈夫納妾的這個打算,因此,只要德昌囘家一說就立刻得到了他妻子李氏的同意了。
天剛黎明,管家秋伯便吩咐撲人阿壽阿茂打掃庭院,又吩咐二婆向祖先神前燒燈和炷香,而且李氏也起得特別早,穿着一套簇新的衣裳在那裏幌來幌去,不是命令這個拭揩桌椅,便是指揮那個擺佈筵席。而德昌呢,他一淸早也就起來了,穿上長袍套上短褂,他今天的神氣確比過去任何一天都沒有,過這樣的歡愉和開心,這樣看來他在今天幹的是什麽,那就不難使人會猜想這又是一椿什麽的事兒。
原來今天不僅是李氏的生辰,而且是德昌迎納二姑娘囘家之日,正所謂一慶二喜,自然筵席排開,親友盈庭,眞是有說不儘的聲色熱鬧,但當他們正在飮得高興彩烈的刹那,忽然接到店中來電說德志因受不了金市大跌的剌激而暈倒的消息,眞使德昌大吃一驚,他急忙把這個消息吿訴了他的弟婦羅氏以後,也就帶着老管家秋伯急忙跑囘店去看究竟,但當他和秋伯趕到店中的時候,而受剌激過度的德志却已經奄奄一息了,祇有用盡了氣力纔能够對他的哥哥和秋伯說出了這幾句話:「我死了以後,希望你們能够照顧我的妻兒才好⋯⋯」說到這裏,他的咀唇實在已經無法開動了,眼蓋一闔,他就。在這樣短速的剎那中離開了人世!
自從德志死去以後,他的妻子羅氏終日哭哭啼啼,無日休止,他除了哀悼她的丈夫早死以外,更爲了她自己未來的可怕命運而悲傷!
其實,自從陳家的二少爺死去了以後,陳家的大權很快就落在二姑娘的手掌中,古語說,「奸臣當朝,國無寧日」,然而「狐狸」當家,那又豈有安靜之時嗎?
二姑娘掌握了陳家的大權以後,氣燄之豪,眞正不可一世,初時她還對她的「大婦」表示和善一點,但現在呢,那就不同了,不是借故吵鬧,便是借故常罵,雖然德昌也常常對她說了幾句勸敎的話,但却立刻又要引起了二姑旳一塲更兇惡的吵鬧,因此,卽使明知二姑不對,德昌也只好暗自搖頭,裝聾作啞,萬事不理,因此,二姑便是更加猖獗,簡直成了陳家裏面一頭橫暴兇殘的專制獨裁夫!
這一天,快到中午的時候了,二姑披着晨褸盛氣冲冲的從睡房裏面跑了出來,她一邊用手指擦着惺忪的眼睛,却又一邊張口大駡:
「這些過街叫賣東西的鬼小販,眞討厭,這麽早就給他們的鬼叫聲擾醒了!」她一股腦兒的坐在沙化椅上,順手拿着放在矮儿上的香煙盂就朝着羅氏的跟前那邊擲過去;「你這鬼東西,死吧!」
其實,只要聽到二姑那種呼喝叱駡的聲音就够使大家害怕了,何况還要看見她這麽兇狠狠的把烟孟一擲,那眞要是大家不給他嚇壞了才算奇怪,誰還敢開口?但畢竟還是德昌陪著笑臉上前對她這:
「我的好太太,別鬧吧!太陽也在半天了,這還不是應該起床的時候麽?」
德昌這句話却要引起了二姑一番更大的怒惱,還等待他說完時二姑便順手朝着德昌的臉上狠狠一指;像一頭老虎似的咆哮:「你這沒心肝的傢伙,難道連我多睡一點兒的權利也沒有?我老實吿訴你吧,要是我早知道你給我睡的房子是這樣糟,眞是連鬼也不會給你騙囘來呢!」
在德昌來說,他眞想不到二姑竟然兇蠻成這樣地步,但受到她這突然而來的一吵,他立刻光火了:
「喂,你說話要淸楚些!誰騙你囘來?要是我早知道你是這樣的,肯帶你囘來的才是鬼!」
當然,二姑也不會就這樣把口舌停止下來的,相反,她的嘴張得更闊,聲音更大,在那裏跳來跳去,簡直越駡越兇,也就越駡得爆火了。
最後還是羅氏跑上去對二姑勸說;「好了,你們別吵吧!你旣然不高興樓下這個房間,那麽就把我樓上的房間讓給你。」
到此爲止,一塲爭吵的結果,二姑娘總算已經獲得了一份「美滿」的勝利!
從此,羅氏就從樓上搬至地下。然而,誰也不會想到,羅氏不過纔在樓下住上了幾天也就被二姑又借某種緣故而把她硬着趕出陳家門外去了。
羅氏自從被二姑趕出陳家以後,也只好和秋伯搬到別一所破舊的房子去居住,起初的生活倒還可以說得過去一個時期,但後來也就一天比一天槽了,雖然秋伯也不計勞苦的去養雞畜鴨來撑持家中的用度,而羅氏呢,她也在家替人家幹上一些縫紉衣裳的活來供補家用,但這又眞能够解决他們處境上的困難嗎?沒有!他們的生活委實已走到了窮困竭極的時候了,何况在這樣困苦的日子裏,羅氏腹中之遺孤也快將分娩之期,目前生活旣已無法解决,而將來孩子出世以後又怎樣辦?這些問題終日在她腦子裏上下打轉,不由使她感到恐駭,徬徨,終於使她哀痛而哭!
「你又在哭什麽呢?就算眼淚流乾也又有什麽用?日子雖然是過得那麽難煞,只要你好好地把孩子生養下來,長大了,那時孩子不是就會替你報仇出氣了嗎?忍耐一點吧,何况哭得多了對胎兒的影響是不好的。」秋伯雖然是這樣的對羅氏進行勸慰,但她心裏的悲憤却又使她不禁酸淚橫流。
經過了秋伯一番勸解之後,她再沒有哭了,也只好正如秋伯所說,把將來的希望就寄放在未來孩子的身上吧!她反而看見秋伯的眼淚感到非常難過,說:
「秋伯,你別要難過吧,我不哭了⋯⋯今天的大爺的兒子滿月呢,我們雖然是那麽窮,但不能不要送給他們一點禮呀,不然,又說我們看不起他了!受不了這大罪!」
但是,他們又從那裏去拿錢?結果,羅氏又還不是翻開箱筐拿出最後一件比較像樣的衣服給秋伯去押店換上一些錢麽?
二姑自嫁給德昌以後,轉眼間又是生下一個孩子了,可是這孩子的正父親並不是陳德昌,而是二姑瞞着德昌與廖畢誠通姦的結果!當然,這是陳德昌所不知道的一件祕史。
今天,是二姑所生的孩子滿月之日。自然不免又是大排筵席慶祝,所謂高朋滿座,喜氣洋洋,何况二姑娘又在衆賓面前大拋歌頭,彷如黄鶯出谷,此景此情,誰說好不熱鬧?
然而當他們正飮得高興彩烈的時候,秋伯拿着剛從押店裏換來的一點禮物跑到來了,他一心一意,唯誠唯懇的希望把這份禮物送到二姑的面前去表示一番敬意,可是當秋伯雙手捧着這份禮物要朝着門口跑進去的時候,却被看門的阿茂阿壽兩人把他攔住,半譏半諷地對秋伯說:
「老傢伙,今天是二姑請酒,沒有你的份兒,你跑來幹啥?」
秋伯怒看他們一眼:「不!我不是來貪饞他們的酒食,我是來把禮物送給二姑娘!」
阿茂阿壽都同時發出一陣極冷酷的諷笑,阿壽用手指着秋伯手中捧着的一包小東西說:「你說送禮嗎?這點爛東西,眞不怕羞死人!你以爲二姑會歡喜你這還値不上兩毛錢的東西嗎?走吧,老傢伙!」阿壽和阿茂合力想把秋伯拉出門去。
阿茂阿壽就這樣不講情由的硬着不許他進去,並且還要動手把他趕走,他們這種無禮橫蠻的舉動眞把秋伯氣得渾身發抖了,他眞想把他們打個痛快,但他已經氣得連一點氣力都沒有了,他只有力竭聲嘶的對他們痛斥責駡,其實,像他這樣一個無能爲力的人,在暴力面前,除了用自己的喉嚨去咒駡之外又還有什麽?
末了,還是德昌在廳中聽到了秋伯這種强烈的而又嘶啞的聲響跑了出來,把阿壽阿茂喝開了,又勸秋伯息止憤怒,並且又說請他進去喝杯喜酒。
「大少我今天不是來吃喜酒的,我是代二少奶送一點禮物來向你們祝賀。謝謝你的好意,我要走去!」
秋伯說畢就是把他帶來的那包禮物塞進德昌的手裏,頭也不囘的跑去了。
當然,德昌也不無感到這種境况確是使秋伯感到難過!
過了不久,羅氏的腹中遺孤也吿誕生下來了。孩子的誕生,當然是羅氏感到慶幸而愉快的一件喜事。但那時候,他們的生活環境確實已經走到了極點,窮,雖然是他們捱熬慣的生活,但今天羅氏因爲養下了一個孩子而病倒了,這却是秋伯感到萬分焦急的事,於是,在這樣無法可想的情景,唯一的辦法除了向陳德昌請求週濟以外就別無其他了。
但當秋伯跑到了陳家的大門時却又被二姑娘的心腹女僕攔住了不許他進去:
「你找大少爺麽?他不在家!」心姐說了這兩句冷剌剌的話就砰然一聲把笨重的大門關鎖得緊緊了。
這個情景,雖然使秋伯的心頭感到有一種無比的槪憤,但環境如斯,也唯有呑聲忍氣的走了。
秋伯離去了陳家,又匆匆急急的跑到天昌錢莊,一進門口便扯住那個當會計的少泉就說:「大少在這嗎?」
秋伯那種愴忙萬急的神態與語氣倒使少泉爲之吃了一驚,待秋伯說明來意以後,少泉就把秋伯帶到馬道生那邊,請求馬道生替他們想想辦法。
馬道生本來就在天昌錢莊幹「司庫」的,爲人非常純樸而忠實,他雖然對二少奶的處境感到可憐,但他也沒有什麽能力去幫助她;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當司庫很久了。
原來自德志去世以後,德昌又娶了二姑爲妾,在二姑的權威操縱底下,這個廖畢誠就很快從「跑街」躍爲司庫,大權在握,任施任爲,何况德昌也很少囘店視理,所以廖畢誠在天昌錢莊裏簡直是一個不可一世的人物!
這時,廖畢誠恰從外返,咀裏含着雪茄,一手持着手杖,又一手挾着皮包,大搖大擺的闖進店,,秋伯看到了他那種冷傲的脾氣簡直要作嘔了,他雖然是看不起他,但他希望能够叫他支付出一點錢,也只好忍着滿肚子氣上前對廖畢誠說:「我家二少奶已養下了一個男孩,而且她又病倒了,我想請你代支出一點錢給我替她請醫生!」
廖畢誠冷冷地說;「要錢麽?可以的,那麽,大少有沒有字据叫你來拿?」
「沒有的,因爲我還沒見到大爺呢!」
「呵!那就對不起了,我不能把錢支付給你」
儘管秋伯怎樣懇求,但廖畢誠絕不會對他們表示憐惜,秋伯說得多了,畢誠反感到討厭,於是他竟給秋伯大斥一頓,並且還要强把秋伯趕走。
這樣看來,畢誠的居心如何,誰都會不難了解到的。末了,還是由馬道生出來把這場爭執給與排解,並且勸說秋伯還是再跑囘陳家找到德昌大少再說吧。秋伯也只好含恨而返。
囘頭返來大宅,這總算是第二趟了,這次雖然沒有遭到什麽人對他阻撓,但是仍然沒有把陳德昌找到,只有二姑向他盤問一頓之後就從手袋裏拿出了十塊錢擲過秋伯的手中,說:「你講得也很可憐,在妯娌面上,我就送給她十塊錢吧!說畢也就逕自囘房中去了。
秋伯拿着那十塊錢惘然地站在那裏,他心裏感到的不知是悲哀還是憤怒,他恨不得立刻要衝出這個門外。但當他走了幾步時却被一沙啞的聲響叫住了,他掉過頭一望,不是別的,原來就是陳德昌的妻室李氏夫人,他看到了她的神色是那焦枯而可怕,的確,她的遭遇也實在太可憐了,自從二姑娘進了陳家的大門以後,她就被關在家裏,簡直被二姑娘磨折得快要死了。
「大少奶想不到你竟然弄到了這個田地!」秋伯未說這句話前已經涕淚泫然!
「唉!這還有什麽好說,反正我也快要死了,不過,我希望你要好好的去照顧二少奶和她的孩子才好呀!我這裏還有最後的五十塊錢,你拿囘去替二少奶請醫生吧!」她把五張十元的鈔票緊緊地塞進了他的手裏。
秋伯拿着她那五十塊錢,心裏感到的不知是喜悅還是悲哀,他感動得要哭了。
「你囘去吧,請醫生要緊!」李氏還是這樣的對他催促着。
「謝謝你!」秋伯對李氏吿辭了也匆匆跑出門口去了。
然而,在這以後不久,李氏因受不了二姑的磨折也就悄然地死去了。
韶光易逝,轉眼又是過了六七個寒暑。
六七年以前的二姑的孩子小昌和羅氏的孩子小志都長大了,可是他們由於家庭教育不同,所以,這兩個小孩子有着兩種不同的性格。
小昌生長於一個富有的家庭裏,自然要給二姑當寶貝一樣的看待,縱驕成性,終日只曉吃吃玩玩打打鬧鬧,雖然年紀小小,但神氣十足,竟然一個十足美國電影中的小阿飛了!
然而小志呢?他雖然長養在一個這樣貧苦的家庭裏面,但他在他賢良的母親的循循敎導底下,成爲一個聰明伶俐的而又有優良品格的小孩,要是與小昌比較,那就簡直是無可比擬的!
有一天,小志獨個兒在門前看書,却給小昌走來硬給他牽走,本來小志很不高興跟他在一起玩的,但在小昌的苦苦的强迫底下他才肯跟他去逛一下。但當他們走到了一間小學校的門前,校塲上有一羣小孩子在那裏打球,他們倆站在籬笆外呆呆的望着,好不美羨,但小昌呢,他除了羨煞以外,他還有一個念頭,就是把別人的球搶到自己的手裏。
在他們看得出神的時候,却看見那個皮球自內跳過籬笆而跌進他們的面前,在小志正想把球拾起送囘人家的時候却被小昌把皮球搶走了。
小昌搶走了皮球便拔足狂奔,但却給那羣小孩子像窩蜂似的向小昌追逐,結果小昌被一羣孩子包圍着,這當然不免要受了這羣孩子的一番毆打,末了,還是小志人急生智,高叫「警察來了」才把這羣毆打小昌的孩子騙走。小志急忙扶着小昌奔跑囘家。
剛跑到小昌的家裏,恰巧德昌和二姑駕着汽車囘來,並且買了一大批玩具和幾大包糖菓給小昌。小昌一邊大叫「媽咪」又一邊把糖果塞進咀裏,同時又叫心姐把各種玩具搬來讓他玩過開心。
當然,陳家的僕人對這個「小少爺」是一呼百應的,這個遞糖果,那個捧玩具,大家都爲這個小「少爺」忙得團團轉。然而站在一旁的小志却從來不會給人當他是人的看他一眼,他在他們的眼中只不過是一條窮家狗罷了,甚至那個心姐還說小志「身臭」而加以驅逐。
然而更不幸的事來了。當小志站在一旁看小昌玩得高興的時候,他不禁忘形地拍手叫好起來,但立刻被心姐禁止了,而且要受一頓狼毒的斥駡,這也只不過還是一件小事罷了,更糟的還在後面呢!
小志站在一旁,不敢說,也不敢笑,只有像木雞似的站着,在那時却不提防小昌會把一架小車子推到小志跟前,小志給車子一碰,驚嚇得渾身一跳,雙脚一滑,也就跌倒地上去了,這一跌不打緊,最糟的是因爲小志跌倒而把小昌的車子踏壞了。
二姑看見小昌的車子被小志踏壞,這一怒是非同小可的,她氣勢汹汹的上前揪着小志的衣襟就舉掌朝着他的臉上一拍,說:「你這有爺生沒娘養的鬼東西,有意搗蛋,滾,給我滾!」拍了幾巴之後就把他推出門外去了。
小志被二姑一番無理毆打之後,也只好用手撫按着被打疼的臉兒哭哭啼啼的奔跑囘家。一進門便撲進他母親的懷裏哭過痛快了,最後由秋伯對他撫愛一番,並詢明原委,當秋伯聽到了原來又是二姑的惡行時,他憤怒極了,他揑緊了拳頭,他眞想立刻跑去把可惡的二姑痛毆一頓以示報復,可是羅氏却力勸他不可這樣做,當然,這不能說是她的懦弱,而是他們的處境不能給與他們這種對壓迫者表示反抗的力量。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儘管受到了別人怎樣欺凌與迫害,這種委屈,也只有無聲地和淚水一迸吞在自己的肚子裏去了!
日子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在這艱辛的日子裏,他們的生活確也過得太痛苦。雖然他們還是日以繼夜的用自己的勞力來對生活進行抗爭,可是,飢餓之索却在他們的頸𩓐上愈垃愈緊了。在當光賣淨,走頭無路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跑去請求德昌,希望他能够給予一點幫忙,解决目前的貧困。所以,在非常痛苦的而又絕望的情景下,羅氏拉着自己的兒子小志跟着秋伯一起跑往陳家大宅而去。
但當他們跑到陳家大宅的門口時却又給守門的阿茂阿壽擋住了,理由是「大少」今天請飮,拒絕見客。於是,秋伯忍不住氣又和壽茂兩人爭吵起來,結果,還是德昌聽到了這種劇烈爭吵聲而跑出門來。經過羅氏母子的一番瀝血陳詞以後,德昌就掏出五十元來給羅氏母子囘家,然而想不到這五十元却給羅氏帶來了一個更殘酷的災禍!
原來自德志去世以後,德昌仍然依舊從店中撥出一份錢給弟婦羅氏作爲生活費用。自從二姑在陳家掌握了大權以後,羅氏那份應享的生活費也就暗中落到二姑的腰包去了。六七年來,二姑也就這樣瞞着德昌而去進行她無法無天的勾當,使羅氏母子陷於無依無靠的飢餓邊緣,直至今天德昌聽到了羅氏的悲苦伸訴以後,雖然對二姑這種可恥的行爲感到憤怒,他也不無對二姑責備過一言半語,但德昌很快地又被二姑那種危言悚聽的狂言謊語騙倒了!
這天。在閒談中德昌又囑咐二姑多多照顧羅氏,免使他們母子苦於餓寒。但二姑聽到了德昌這番說話以後,她却笑了,說:「你多麽好心啊!難道你眞要叫我多給一些錢財好讓他偷養漢子不成?」
「我不相信,我相信嫂嫂不會有這種敗壞門風的醜行吧!」
二姑又冷笑了一下,說:「你不相信嗎?好吧!我找個證人來。」
所謂證人的人,當然又是心姐這個人了,其實心姐就是二姑的心腹,是二姑的同謀,她說的當然是跟二姑的一樣。所以,儘管起初還替羅氏辯護也好,但經心姐一說,也就不能不使他眞的對羅氏懷疑起來。
是夜,德昌果然看見一個男子從羅氏的園牆越過,又看見了一雙男女的影子在黑暗處擁抱,並且又聽到了那種不堪入耳猥褻細語和笑聲⋯⋯
至此,他相信了羅氏果然會幹出了這種下賤的醜行。他决意要把羅氏永遠逐出陳家。其實德昌已經被二姑愚弄了,原來他先頭看到的並不是眞的事實,而是二姑和廖畢誠預先佈置下來的一個醜惡計劃呢!
從此,羅氏便蒙受了這不白之寃而被德昌把她逐出陳家!
10
羅氏被趕走了之後,這個苦命的孤兒小志就被德昌拉囘他的家裏「育養」。照理伯父養育一個侄兒是應該的。何况他還是個陳家的眞正小主人。然而,事實却並不這樣,他在陳家只不過是一個小什役罷了:他每天總是跟着秋伯一起幹着澆花除草,打水,砍柴等粗重工作;他喝的吃的是一些冷飯殘羹,夜裏也就睡在柴房的稻桿堆上。他雖然是被磨折到這個令人不忍卒視的境地,但他每天還要受到的就是二姑的斥駡與鞭打。
其實,小志和小昌也同是陳家的少主人,但他們的生活是極端相反的;小志終日勞苦,除了兩頓冷飯殘羹以外也就什麽都沒有得進嘴:而小昌呢?終日閒逛,則時而「燕窩」,時而「參湯」,現在他又在那裏叫吃「山渣露」了,只要小昌一說,二姑便立刻吩咐心姐到廚房去拿。可是,當心姐捧着那碗熱騰騰的「山渣露」從廚裏要跑出來的時候,一不留神,就把坐在廚裏正在劈柴的小志一撞,碗打破了,那熱騰騰的「山渣露」立時把小志的腰背燙得又紅又腫,眞是使小志痛得在那裏直跳直叫,然而心姐還瞪大了眼,用力在小志臉就記一巴,氣凶凶地指住他駡:「你這小鬼頭,弄壞了別人的東西還要哭。燙死了你不要緊,小昌少爺沒有『山渣露』吃你才算倒霉!」
小志被燙傷了,痛楚難煞,受了心姐的一頓痛駡和一個耳光還不算,最後心姐還要把負了創的小志拖到二姑面前,使他得到一個更厲害的「懲罰」!
這次的「懲罰」,已經不是像心姐那樣祇給他一頓斥駡和記個耳光,而是一條相當粗糙的藤鞭拿在二姑手裏朝着他整個身軀像雨點般的鞭撻,打得皮開肉裂,鮮血直流,他抵不上二姑的幾鞭抽撻就昏倒過去。幸虧還是一個好心腸的老僕二婆因可憐小志的遭遇而暗中跑去報吿秋伯,然後由秋伯跑去向二姑哀求而把他寬恕。二姑又眞的會因秋伯的哀求而把他寬恕嗎?不!祗有聽從二姑認爲這種抽撻「遊戲」也感到相當滿足了的時候才會讓秋伯背負着重創的小志去。
小志的年紀雖然還是那末幼稚,但他却是人世間一個最不幸的人,他感到這人間也實在太殘酷而醜惡了,這人間醜惡就這様無情地把他潔白的心靈刻劃下了一道永難泯滅的創痕!
11
不待說,小昌在二姑的縱容底下是越來越壞了,然而,他正是二姑的掌上之珠,儘管他怎樣壞,但她對他的溺愛總是無微不至的。
一天,小志照例在那裏拭揩窗門。小昌又叫一羣僕人陪他在花園中踏車爲樂。不料被石頭一滑,小昌的小踏車翻倒了,這一跌,小昌自然要拚命地在那裏咆哮大哭,好像發生了件什麽似的,把全家人都爲之嚇得大驚起來,顯得最緊張的當然是二姑娘,她除了吩咐僕人打電話邀請中西醫生到來診治以外,她又派僕人到外面採購著名丸藥,其實,小昌祗不過是皮膚受了一些破損而已,可是,二姑娘今天的開支,却是一筆鉅大的數字了。
但在同時,小志在那邊揩拭門窗的時候,因爲身體感到實在也太累了,但他懼於二姑娘的鞭撻,身子就算累極了也還得要提着精神去幹呀,然而像他這樣的年紀,實在受不了這殘酷的磨折的,何况他昨天給二姑打傷了的創痕尙未平復,一陣接一陣的疼痛使他實在很難捱煞下去,疲乏和疼痛使他眼前生起一陣昏黑,四肢一酸,他就在十來尺高的梯級上面翻身滾了下來,祗是「唉地」的叫了一聲,隨卽就昏過去了。
小志就這樣昏昏迷迷的在地上躺了很久,但誰都好像沒有看見一様,最後還是由上個看不過眼的僕人暗中跑去吿訴秋伯,把他抱囘柴房,但是小志的傷勢跌得也太嚴重了,秋伯以爲跑去請求二姑請醫生給小志診治一下,但結果呢,還是由二姑從手袋裏掏出張一元的鈔票,裝上一副「慈悲」的臉孔,說:「這也太可憐了,這一塊錢,你拿去買個藥丸替他擦擦吧!」
12
風雨之夜,雷電交作,這是一個多麽陰森可怕的夜晚,對了,在這樣的陰森夜裏正如這個險惡的人世間一樣,有人暗中進行着人害人的醜惡勾當!
且看吧,二姑娘又跟廖畢誠在房中幽會了。這本來是一件不足爲怪的事,可是他們今晚的幽會除了互相取得「慾」的滿足以外,最主要還是進行着一個驚人聽聞的暗殺陰謀!
其實,小志自從被收容了陳大宅以來,除了幹着苦役之外,沒吃沒穿,他的身體每天都少不了挨受二姑娘的毒辣鞭撻。雖然這種苦也够小志難受了,但二姑娘却說這種苦也太便宜了他,於是二姑跟廖畢誠暗中施計,企圖把小志祕密殺掉,斬草滅根,落得一塲幹淨!
這時,也快將夜深,各人都囘到自己的寢室去作休息的時候,祗有老僕二婆還唯勤唯謹的在屋內巡視着門窗,但當她打從二姑娘的房外跑過的時候,却被房內傳出來的那些淫蕩的嘻笑和喁喁細語所怔住了,她知道大少尙未囘家,那一定又是二姑跟廖畢誠鬼混無疑,這些事情當然使二婆不敢聲張的,本來她亦沒有這多閒情去理會這對奸夫淫婦的醜行,可是當她正要掉身就跑的剎那,却有一句比刀尖還利的說話刺進她的耳朵;她淸楚地聽到廖畢誠這傢伙狼狼地說:「我已買到兇手了,準今晚可把小志殺掉!」
這句話眞像刀子一様剌進二婆的耳裏,使她驚得渾身打顫,她雖然是屬於「不管閒事」的一類人物,但她畢竟還是個有正義,有良心的老者,她不忍眼看着一個善良的孩子無辜被人殺害,她決定要救他,於是她絲毫不敢怠慢的躡足下樓,立刻跑去柴房把這事情報知秋伯,並決意勸吿和催促秋伯立卽携帶小志夤夜逃走。這個生死交關的危急關頭中,事實已不容許禍難臨頭的人有稍作思慮的要求了,在二婆的如星似火的催促底下,秋伯也顧不了這麽多,把正在發着高熱的小志駄在背上,冒着狂風猛雨,悄然地打從後園的小徑朝著野外拔足就跑。
果然,秋伯駄着小志剛跑出門去不久,幾個兇手拿利刃的大漢已潛進柴房,可是,秋伯駄着小志已經遠走他去了!
13
春去冬來,轉眼又是六七年了。一切事情都在變化着。
在這六七年來,小志一直跟着秋伯住在鄉間。依靠着秋伯夫婦的勤勞來把他養活,現在小志長大了,已經長成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伙子。由於他的天資聰穎,加上秋伯夫婦對他循循善導,他已經成爲一個很純良的而又精靈的孩子;尤其是他的身子長得也相當結實,能耐勤勞,幹起活來比誰都好,因此,秋伯夫婦對他的鍾愛簡直是自己的骨肉一樣。其實,在這六七年的艱辛日子裏,他們夫婦亦祗有從小志的身上來找獲一點安慰!
日子就這樣從不停留地走過,小志雖然隨着日子的流逝而長大,但相反的一面,秋伯夫婦却隨着日子的走去而衰老了,因此環境就大大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生活。旣已到了這個田地,秋伯那就不能不要叫小志挑些東西上城上去賣來維持生涯了!
然而,另一面呢?
同樣是六七年以後,自然小昌也長大到十四五歲的時候了,可是在他母親二姑娘的放縱下面也就越來越壞,不管還是那小小的年紀,但對于打牌抽烟等惡習却無不通曉。陳德昌眼看着自己兒子墮落行爲,雖然感到痛心,但他又有什麽說話可說呢?
14
爲了要維持生活,小志就得當起小販。他每天淸早起來就標着一筐小小的,如水菓呀,香烟呀等東西跑到城中的一些工廠門前叫賣。日子久了,漸漸和一些工人朋友混得也很要好,尤是他爲人精通伶俐,誠懇有禮,因此,他這個小買賣搞得也相當不壞的。
這天傍晚,汽笛嗚嗚的拉過了以後,一簇接着一簇的工人像潮水似的從工廠門口走了出來。不到一刻間,他那筐滿滿的水菓和香煙都賣個精光。
一簇一簇的工人從工廠裏頭走了出來,又很快的從各個角落消失了去。人也走光了,貨也賣光了。至此,也該是小志取道囘歸的時候了吧!當他挑着空筐要走的時候,驀然看見了路旁掉了一包東西,他上前把它拾起了,心裏想道:「這是別人遺掉了的東西,看誰的,等他來取吧!」
他就這樣的坐在那裏呆等了好半天,但還見不到有什麽人來找。然而,太陽也落下了山。這時小志又想道:「這麽晚了,明天再想法交還失主吧。」他就把拾到的那包東西放進筐裏,安然囘家去了。
小志囘到家裏,秋伯夫婦都同聲問他爲什麽這樣晚才囘來,因爲他們對他的遲歸是感到躭心。於是小志把事情的經過向他們說了,並且從筐裏取出拾來的那包東西交給秋伯看個詳細。秋伯把它打開一看,愕住了,裏面除了一大叠花花綠綠的鈔票以外,盡是那些工廠的訂貨「合同」,雖然還未證實是那間工廠的主管人遺失的,但那些契約上分明寫着「華新公司」字樣,它的失主是誰,那就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了。秋伯是個老實人,他的見解也和小志的見解一樣,別人的東西就應該歸還別人,不可饞爲己有。結果也就决定了明天把這些東西全部送囘人家。
15
今天早上,還未到上班的時候,華新工廠的張廠長便趕囘到他的辦公室去找尋昨天剛簽訂好了的那些定貨單,他到他的案檔裏翻來翻去總是找不着,他很焦急,因爲這些訂貨單萬不能遺失的啊,經過了大半天的翻復搜查仍得不到下落的時候,他的心境開始想到失望了,因爲他知道這些「貨單」一定昨晚囘家時在路上遺掉無疑,但在他想到一切都完了的時候,小厮阿全却在這時推門入來說有一老人帶着一個小孩要求見他,他雖然不願意在他感到煩燥的時候去接見客人,但這次竟然說的是一個老人與小孩求見,這却又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沉吟了一會,揮一揮手對小厮說:「好吧,你卽管帶他們進來!」
片刻,小厮帶着秋伯和小志進入張廠長的辦公室。秋伯手拿着一包東西便跑到張廠長的面前笑嘻嘻地說:「先生,你是華新工廠的廠長麽?」
張廠長看見秋伯是一個那麽善良的人,也就非常客氣的招待他,說:「是的,老伯,你有什麽事要跟我說麽?」
「不,我沒有什麽要向你說的事情,而是想把一包你遺掉了的東西送囘給你呀!」說着秋伯就把那包東西放進他的桌上:「你把裏頭的東西檢點一遍吧。」
秋伯這此言說眞使他感到驚異,要不是眞眞實實的見到就是自己遺掉了的那包東西放在眼前,他一定不會相世界上竟然會有這樣的一個奇蹟。他把紙包打開了,裏面的「貨單」不僅一張沒有失,而且那大叠鈔票也和原來的數目一毛都沒有錯。這個「奇蹟」給他的感動是太大了;因爲他最後已經知道這拾金不昧的人原來就是天天拿着東西在他工廠門前叫賣的那個從不被他注意的小孩!
張廠長很感動地擦摩着小志的面額說:「好孩子,我很感謝你,那麽,我給一點錢你作大一點的買賣好嗎?」
小志很堅决地瞪着一雙大眼睛說:「不,我們不希望別人給我們便宜的酧報,錢,並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東西呢!」
張廠長笑一笑,更受感動了,說:「好孩子,那麽你需要什麽呢,吿訴我吧?」
「你何以答應我在你工廠裏學習機器工作嗎?」
「當然是可以,不過像你這樣的年紀,你的媽媽是喜歡你這樣做嗎?」
小志聽到了張廠長說到他的媽的時候,不則聲了,垂下了頭,淚珠從暈紅了的眼眶裏一滴一滴的淌到地上。
「幹嗎,你哭了?」張廠長捧起了小志沾滿淚水的臉兒:「你吿訴我,你爲什麽哭呀?」可是,小堅並沒有囘答他的詢問,反而嗚嗚咽咽的伏在他的懷中哭了起來。於是,他不能不轉問秋伯去解釋了。
然而秋伯的心情也顯得非常沉重,打着那雙毫無光彩的眼睛,吁嘆了一聲,然後感慨地,一字一淚的把小志的身世吿訴了他。小志的身世確也太可憐了,從秋伯口中的復述:自從他的父親死了以後,他媽就含寃莫白的給趕出陳家,現在生死存亡未卜。而小志呢,要不是及時帶他逃走,恐怕早已被廖畢誠和二姑暗中謀害了。這一連串的有血有淚的事實,確實令人感到同情和槪感!
張廠長聽到了秋伯這番言說以後,不僅對小志的身世表示同情,除了收容小志在他的工廠中見習機器工作以外,還願意幫助學金給小志暇間上學讀書以求進步,並且還說需助秋伯解决生活困難,直至替小志報仇洩恨爲止。
16
一天,張廠長特地約請陳德昌到一間僻靜的酒店闢室談心,因爲他想藉着他們多年的友誼來對德昌進行勸諫,揭發廖畢誠跟二姑娘的醜穢行爲,希望德昌及時覺悟,免至日後身敗名裂。
儘管德昌被二姑娘迷惑太深了,可是事實到底還是事實,這多年來,廖畢誠跟二姑行爲如何,他當然亦不無知曉尤其是廖畢誠當了司庫以後,由於他的揮霍無度,行爲不檢,致影響店中的生意日落千丈。因此,德昌對廖畢誠早已失去了信任,因之常常跟二姑發生齟齬,弄得家無寧日。然而經過張廠長這次勸諫之後,他眞的開始覺悟了。他决意囘去馬上跟二姑提出離婚,並準備向官控吿廖畢誠虧空公款和跟別人妻子通姦罪。然而,當他囘到家裏的時候,二姑已經跟廖畢誠帶着孩子捲蓆私逃了。陳德昌立刻報警請求追緝。
其實,廖畢誠和二姑原來就是一對拼頭,並且是一雙「老千」,他們的目的本來就是爲了在陳德昌的身上搾騙一筆,現在旣然目的已達,也該是要走的時候了。
然而,當他們準備提款夜渡出走的時候,警局已根據情報及時趕至酒店把這對逃犯圍捕。廖畢誠自知罪惡難免,當場跳樓自殺,而二姑也罪惡滿盈,瑯璫入獄!
17
一個月前,小志不愼被機器軋傷而送入廣濟醫院留醫,今天正是張廠長,秋伯和德昌前來接他出院囘家休養的日子。但是秋伯他們扶掖着小志正離院房的時候,却看到一個中年女看護從樓上下來,這個看護是誰?原來就是七年前被德昌趕走了的小志的母親。
七年後的今日,他們母子雖然又吿重逢,但囘首前塵,恍如隔世,這又難怪他們不抱頭痛哭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