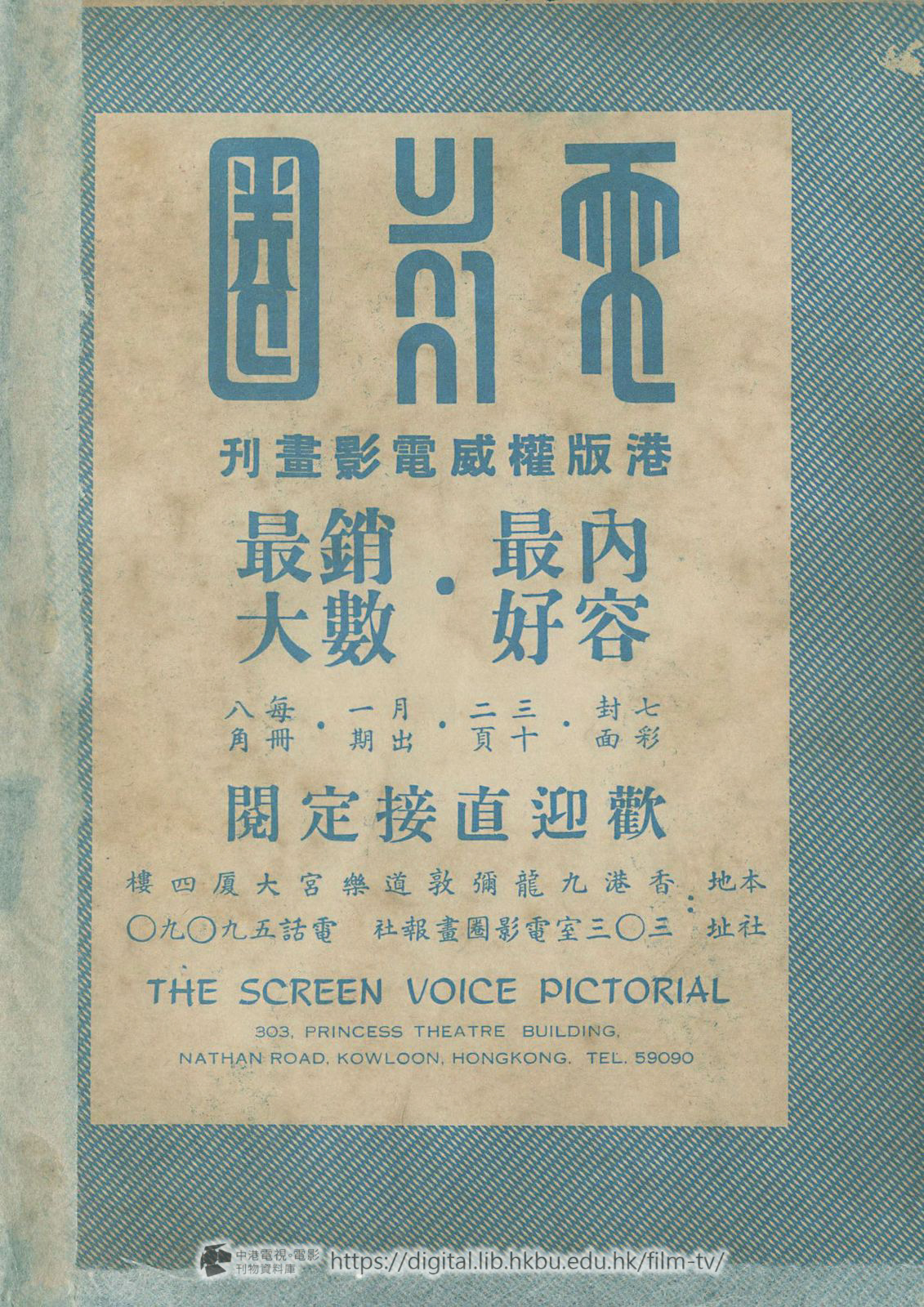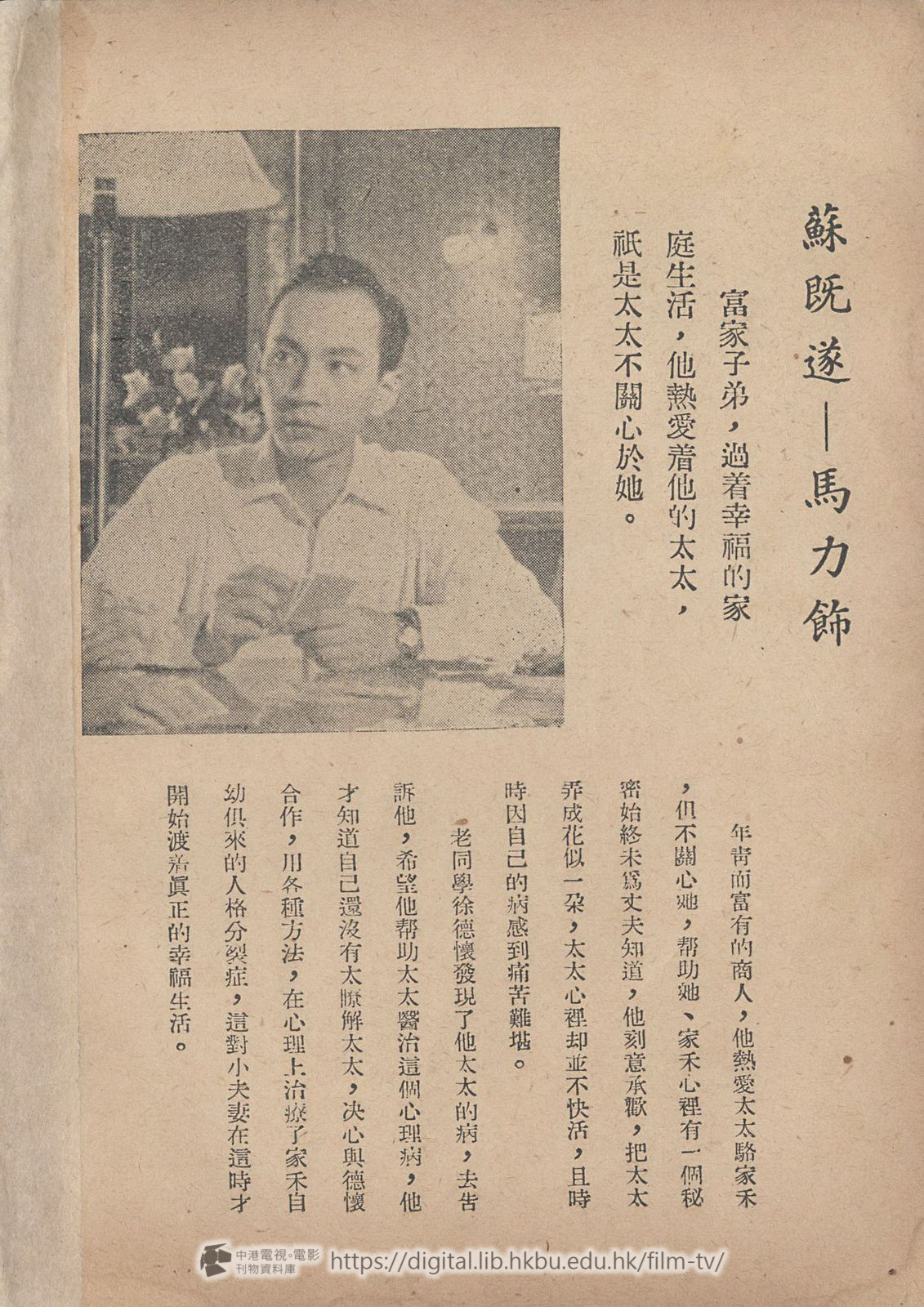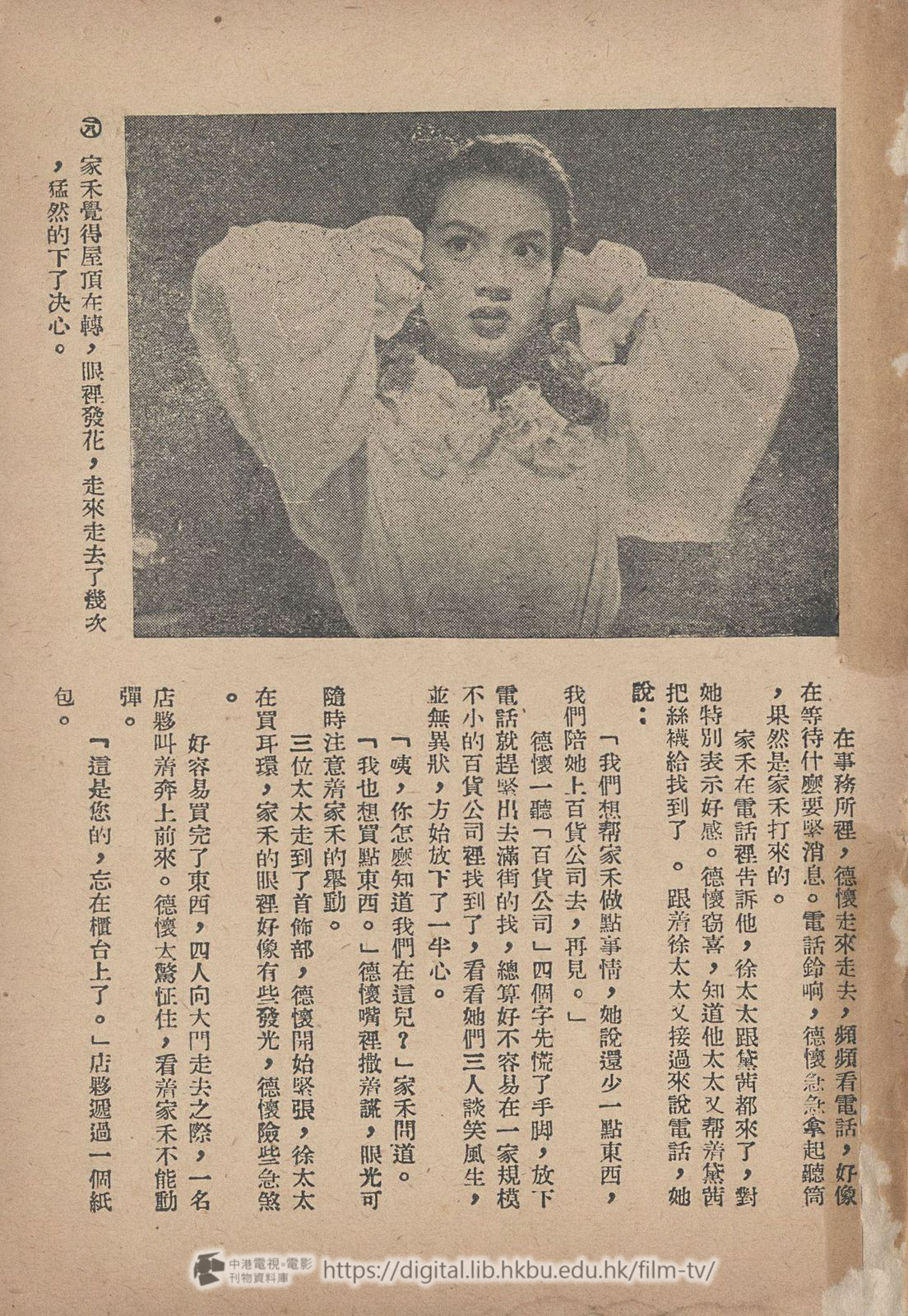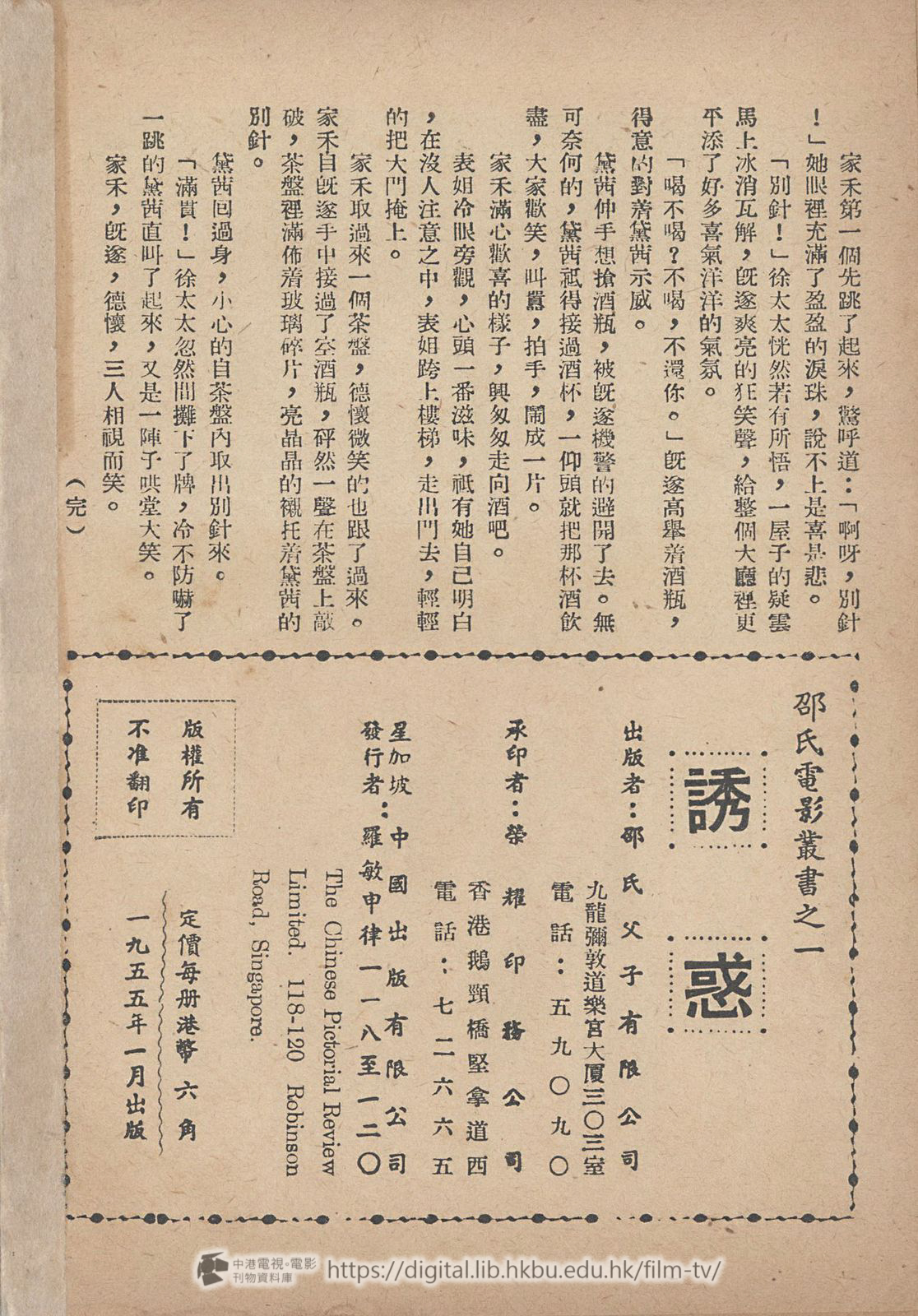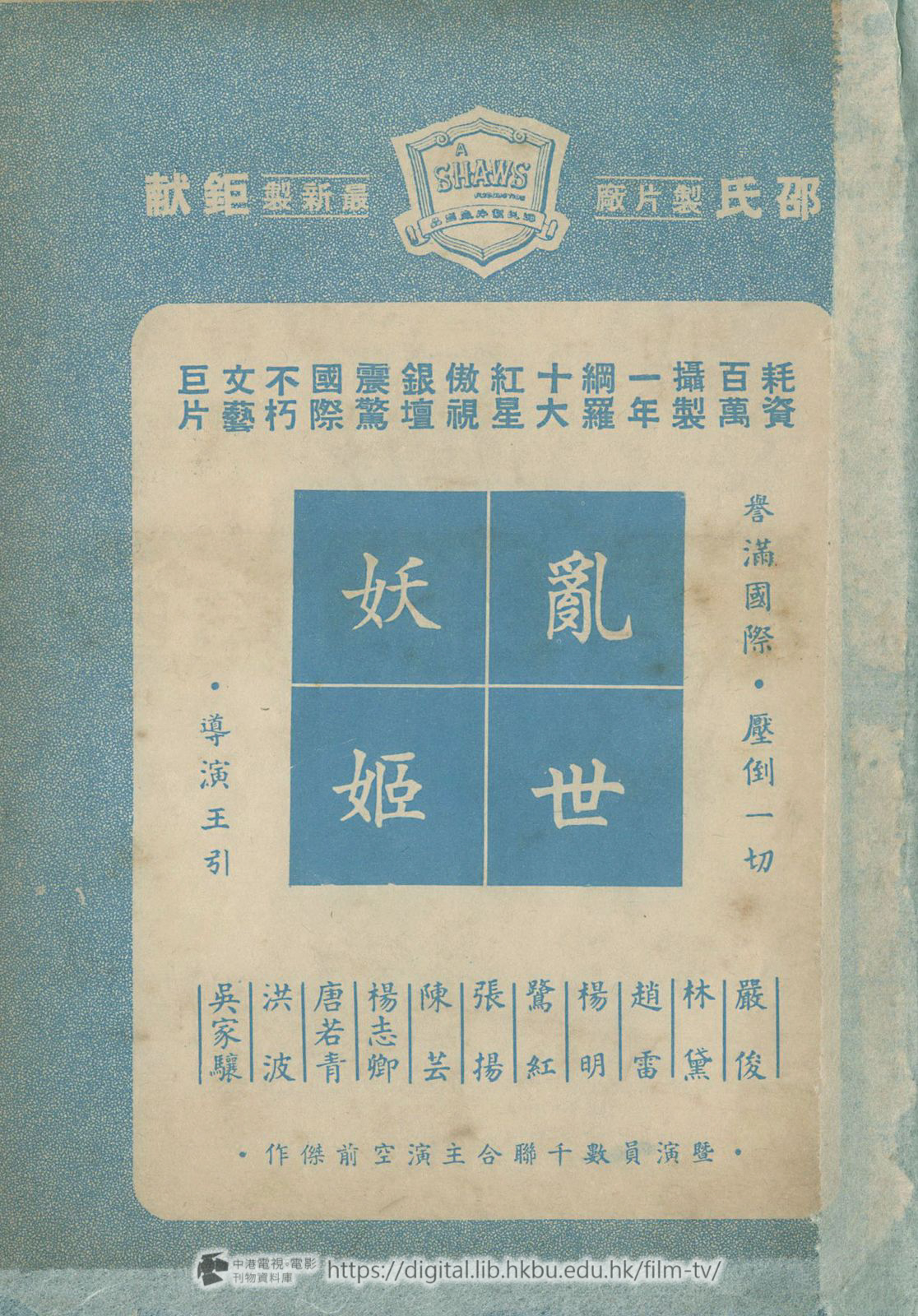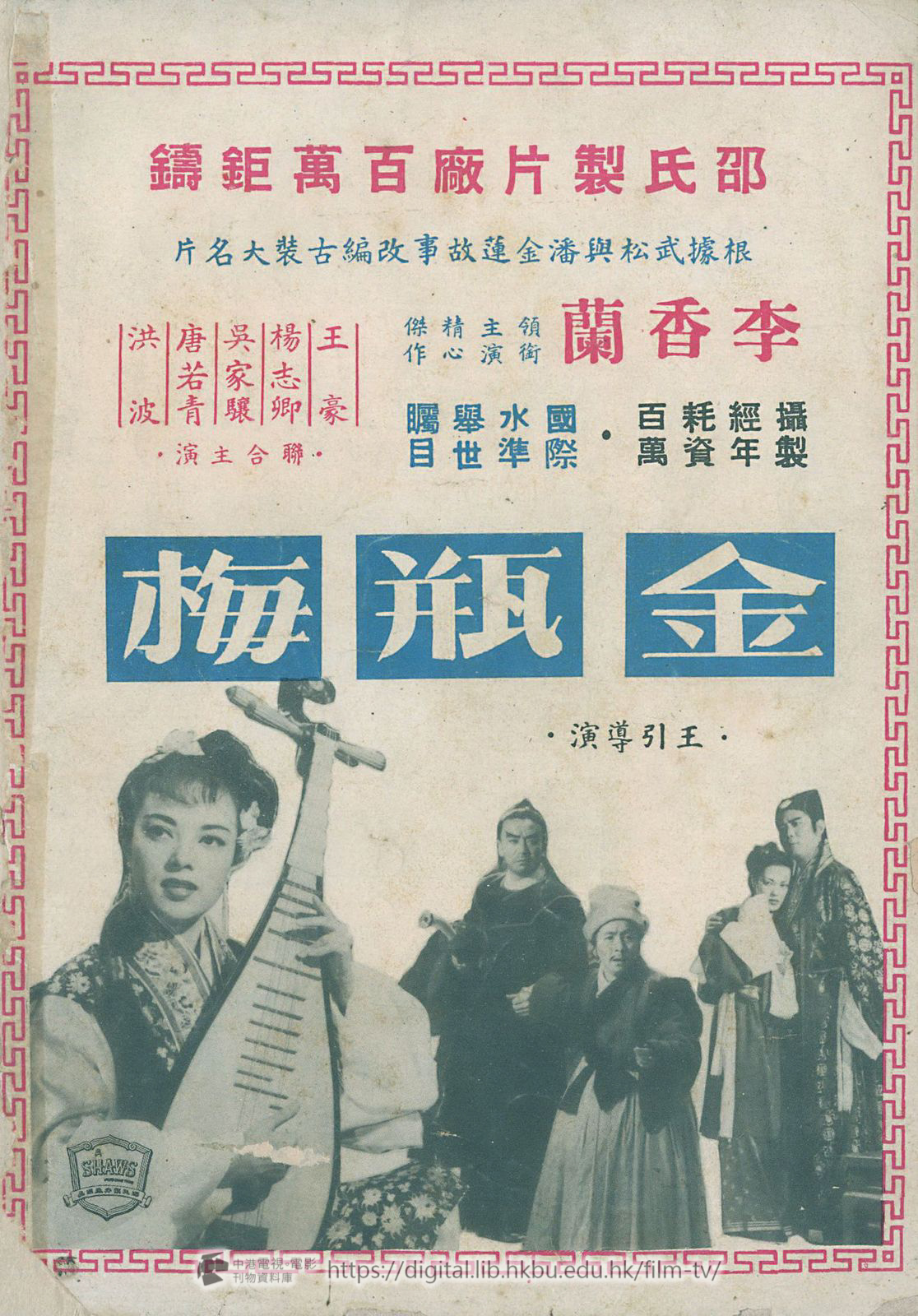駱家禾——尤敏飾
幼年時家庭環境造成,患了人格分裂症的弱女子,這裡是一篇她的奮鬥史。
富家小姐出身,受過良好敎育,學成後嫁年靑的地產商蘇旣遂,是一位有地位的體面人,這個秀外慧中生活得像一朶花似的家禾,誰也料不到她有一個「偷窃病」,這病是幼年家庭環境造成的,父親另納新寵,母親鬱鬱少歡,她穉弱心靈中以爲母親之所以寡歡,乃因父親把好的東西買給姨母關係,於是她就去偷姨母的東西博母親一笑,母親未予敎育,漸漸她的偷窃成爲一種下意 識的動作,人格分裂。
她的幼年同窗徐德懷,得悉了那秘密,以心理治療法糾正了她的變態心理,使她眞正地得到了幸福。
徐德懷——趙雷飾
熱心腸的年靑工程師,爲了朋友的名譽起見,不惜千方百計的設法糾正她。
年靑而有爲的建築師 ,當在學時他也是追求駱家禾的一員,但家禾卒被好友蘇旣遂追求成功而結婚,他就把感情昇華起來,他自己也結了婚,兩家時相往來,交誼典厚,有一天,太太忽然疑心到家禾偷了東西,他半信半疑,冷眼偵查之下,發覺家禾眞有這種行爲,他極力向家禾探問明白, 家禾把一生唯一的秘密吿知,德懷知道這是屬于心理上的一種病症,勸她吿訴丈夫,合力由心理上使她正常,結果雖有人阻撓,被德懐冷靜地指出眞象,使家禾的「病」,霍然而癒。
蘇既遂——馬力飾
富家子弟,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他熱愛着他的太太 ,祇是太太不關心於她。
年青而富有的商人,他熱愛太太駱家禾,仍不關心她,帮助她、家禾心裡有一個秘密始終未為丈夫知道,他刻意承歡,把太太弄成花似一朶,太太心裡却並不快活,且時時因自己的病感到痛苦難堪。
老同學徐德懷發现了他太太的 病,去吿訴他,希望他帮助太太醫治這個心理病,他才知道自己還沒有太瞭解太太,决心與德懷合作,用各種方法,在心理上治療了家禾自幼俱來的人格分裂症,這對小夫妻在這時才開始渡着眞正的幸幅生活。
徐太太——翁木蘭飾
本性忠厚,思想單純的 一位太太,純都市型的淺雜婦女,但有着善良的心。
徐德懷太太是個本性忠厚,思想單純,因環境關係,造成她成天打牌、吃喝的生活,她愛好新奇,有一位表弟同她在千里外的河内帶來了一支法國新式唇膏,她喜歡得了不得,以之示家禾,轉瞬間唇膏就不見了,加以另一位太太也失窃絲襪,根據推斷,她們認爲是蘇旣遂太太駱家禾所爲,任性地不再與家禾往來,但是徐德懷是個頭腦洽靜的人,他知道了家禾「病因」,使唇膏「復返原防」,徐太太看到唇膏,以爲自己錯怪了家禾,慚疚得很,一定要向家禾道歉,並大哭了一 塲,這是一位善良而淺撖的都市太太。
黛茜——陳芸飾
漂亮而喜歡熱鬧的少奶奶,沒有心眼光,祇愛的是打牌,單純得非常可愛。
是徐德懷太太家中的常客,開「派對」的熱心贊助人之一,長得漂亮,又懂得時髦玩意兒,是標準的都市小姐。
她與家禾很好,但最後在一塲舞會中,因蘇旣遂的表姊之故佈疑陣,黛茜的一支名貴胸針不見了,許多人都懷疑是家禾幹的事,連她也無例外。
徐德懷是明白其中秘密的,他用巧妙的手法,當埸証明了這是表姊所做的事,胸針在酒瓶中發現,黛茜這時高興萬 狀。
愛好新奇,物質慾强,但,不是壞人。
表姊——裘萍飾
老處女,私戀着她所不應該愛戀的人,頗工心機,但是命運並不使她如意。
一個心理變態的老處女,她是旣遂的表姊,也寄居旣遂家,自幼,她對旣遂很愛好,又不敢說明心事, 後來旣遂結了婚,她却不再想嫁人,但對旣遂的美麗太太駱家禾起了恨心,處處她挑撥離間二人的感情,但常常失效,這様使她因嫉妬而心理變態。
她從徳懷與家禾的談話中,偷聽得家禾的「秘密」,爲了洩憤,她故意在舞會中製造一個失竊案件,讓家禾的病可以復發,然而他逃不過冷靜的徐德懷,她的「秘密」被戳穿,旣愧且羞的走了。
「誘惑」故事
傍晚,徐家客廳裡一片歡笑,很是熱閙。
主人徐德懷,一位年青而又頗有聲望的建築設計師,明天要到星加坡去公幹,此刻正忙着接洽機票等事並不在家,家裡是徐太太舉行的宴會,客人都是平時最熟的朋友親戚們,這就算是給徐德懐餞行的。
四位太太小姐正在打牌,徐太太的舊時同學黛茜的手氣最好,興高采烈的大呼小叫,黛茜的丈夫陛經理正在那精緻的小酒吧前與徐太太談話,也被牌桌上的熱鬧給吸引了過來。
「這様的手風可把我嚇壤 了。」徐太太看着攤在黛茜而前的一副牌,嘴裡說。
桌上的一位張太太直抱怨自己打錯了牌,其餘的笑嘻嘻的數着籌碼,付給黛茜。
「黛茜祗有跟家禾打牌,纔會輸。」徐太太帶着嘲笑的口吻說。
「誰呀?」一位陳太太發問。
「蘇旣遂太 太。」站在一旁的陳先生接着答道。
大家繼續的討論着關於家禾的事情,看様子這位蘇太太好像很引人注意似的。
家禾姓駱,是徐德懐的女同學,聽說他倆在學校時曾經相戀過,不過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他們夫婦兩對彼此都成了極親密而知己的朋 友。家禾年輕漂亮,丈夫富有,是一位地產富商的兒子,夫婦二人在社交上的地位自然是極髙的。
說話時,徐太太的弟弟大森,一個幹着飛機師的活潑靑年,跨了進來,大家一陣亂招呼,黛茜一面打牌一面說:
「這回我要託你帶點東西。」
「大森連連答應,接着也問道:「蘇太太呢?」
可見家禾在這個小圈子裡是如何主要的一名人物了。一句話提醍了徐太太走到沙發上打個電話去催請。
徐太太剛拿起聽筒,徐德懷也回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回米晚了。」德懷手裡拿着行李照貼紙之類,顯然是從航空公司趕回來的,他招呼完了每一個客人之後,嘴裡咳的一聲問道:「家禾還沒來。」
徐太太笑道:「你們看,又是一個問她的人。」回過頭來向着徐德懐,半嗔半笑。「你快去洗個澡吧!我來打電話給我們的大衆情人。」
蘇家電話鈴響, 家禾急急忙忙的奔過去接聽,說話時笑得格格的。「喂………啊,就來了,旣遂他剛………。」
蘇旣遂一面打着領帶,一面走了出去,他是一個高個子的漂亮小伙子,俊秀的臉龐上的掩不住那種大孩子的天眞氣,一眼就看得出來是個忠實可靠的有爲靑年。旣遂的背後喝跟着的是他的表姐,一個外型美麗而內心竪强的老處女,她是蘇家的管家婦。
「快走,快走。」旣遂飛步往外跑,連領帶掉在地下也顧不得,家禾放下電話筒就走,表姐叫道:
「急什麽呀,家禾!他的領帶。」
家禾旣遂同時返身來拿,拔脚又走了,表姐搖搖頭,嘆口氣。
徐德懷那時在他的浴室裡也很緊張,洗澡、整容、換衣服。徐太太在臥室裡,正把黛茜託買東西的一張淸單交給大森,大森接過來看了幾眼,說道:
「嘖噴………口紅,這兒連口紅都沒得買?」
「不,她要你送給我的那一種,這兒買不到的。」
徐太太說着,在梳粧台旁取出一支精緻的口紅管來。
「糟糕!那兒買的我都忘了,我去問她去。」大森拿着口紅出去,徐太太追着吩咐道:
「別給我丢了。」
大森一直走到客廳裡牌桌旁,說道:
「黛茜,東西我可照准給你帶,別的沒問題,這支口紅恐怕不行………」
大森手中高舉的那支小口紅,引起了全堂女客們的讚羡聲。
「對不起,對不起,主人呢?」蘇旣遂夫婦那時恰巧來到,忙不迭的向大家打招呼,大森一本正經的說道:
「姐姐去接你去了。」
「眞的?你看都是你不好。」家禾回頭抱怨着旣遂。
黛茜坐在牌桌上,接嘴說道:「別聽那東西的話,在裡邊呢,我託他帶一點東西,他也不肯,你看這支口紅多漂亮。」說着把口扛遞了過去,家禾看着時不禁發了一呆。
黛茜順手把口紅交給了大森,此時徐太太笑駡着走了出來。「小鬼,你怎麽這會兒纔來?」
「對不起,對不起。」家禾連連抱歉。
大森走近,把口紅還給徐太太,她隨便接過,陪着蘇家夫婦到酒吧上去飮酒,在爲客人們倒酒時,口紅被放在桌上。德懷換好了衣服出來, 與旣遂討論着蘇家新建而尙未落成的別墅,太太們計劃着如何去佈置它,徐太太很是熱心,家禾倒反而好像有些心不在焉的神氣,從客廳另一角上又放出了黛茜的笑聲。
「黛茜的手風好極了,我們去看看。」徐太太一把拉着家禾就走,留下德懷與蘇旣遂在酒吧裡談生意經。
夜阑客散,華燈盡落,徐太太在黯淡的客廳裡四下尋找,德懷自臥室内走出,問道:
「你在找什麽呀?」
「口紅,我那支口紅。」
「睡了,快兩點了。」
「不,我那支口紅不是普通的口紅。」徐太太負氣的說道。
德懷畧施小計,把太太給哄進房锂,問道:「你明天晚上,會不會像丢了那支口紅一樣的找我?」
徐太太不答應的,耍槌丈夫,反被德懷一把抱住。臥室的燈也暗了。
一個月以後,徐太太又忙着佈置一個小小的宴會,因為德懷今天將要回來了。
大森在陽台上張望,看到接得丈夫的徐太太,喜吟吟的跨下汽車,連忙關照大家躱起來。
「客人來了沒有?」徐太太一進門就問。
「沒有呀!姐夫。」大森忙着跟德懷握手。
「讓我先打個電話給黛茜,我非駡她幾句不可。」徐太太走向電話那處。
猛然一陣哄笑起自簾内,黛西首先跳了出來,後面是陸經理、王小姐、陳先生、陳太太、張先生、張太太………原來客人早到齊了。笑聲駡聲中,大家向德懷道辛苦。
一陣忙亂過去,德懷四下捜望,嘴裡說:「咦,家禾呢?」安慰着說道。表姐離開窗下 。
德懷忽然想起,說道:「你知道你曾經拿過我太太的口紅,跟黛西的絲祙嗎?」
「口紅?」家禾說着立起身來走向內室,回頭又招呼德懷。「你來。」
德懷跟入,恰巧表姐跨進門來,看着德懷的背影發怔,忽然驚覺,匆匆又跑開了去。
家禾在臥室梳粧台抽屜裡找出來口紅及絲祙,德懷拿住,點點頭。
「她……她們知道了沒有?」家禾焦急的問道。
「知道了,而且她們知道是你。」德懷沮喪的答道。
「那………」
「你交給我,我想辦法去還給她們,讓她們以爲這些束西 並沒有遺失,錯怪了你。」德懷說着把口紅放入袋裡,又把絲祙小心的放入内袋。「讓她們再像以前一樣的跟你親密,不讓你再有一點空的時間去犯這種病,也許你就這様好了。」
「也許我就這末好了。」家禾破涕爲笑,頰上仍掛着亮晶晶的淚珠。
旣遂 回到家,晚飯桌上,與德懷談到卽將成功的一件生意,高起興來,跟德懷不住的碰杯。
表姐看在眼裡,也擧起了酒杯,說道:「家禾,我們也來喝一杯。」
家禾縐眉說:「我不想喝。」
「那末徐先生跟她喝。」表姐的話裡好像有剌。
德懷 陪笑說道:「表姐今天的興緻很好。」
「是呀,我發現了一個秘密。」
德懐筷中食物掉下落在身上,家禾對他看着。
「什麽秘密?」旣遂很感興趣,問道。
「你們不喝酒,我不說。」表姐故作神秘,微笑着說。
旣遂一飲而盡,德懷勉强追隨,家禾看看德懷,慢慢的喝完。大家放下酒杯,空氣緊張。
「我是說着玩的,騙你們喝酒是眞的。」表姐輕俏的說道。
大家都笑了,笑得最不自然的是德懷。
德懷回到家裡,客廳上一桌牌局還沒有散。徐太太今天手氣好,很是高興。
德懐搭訕着跟陸經理、黛茜等開了幾句玩笑,抽空子溜進了臥室,像做賊似的把袋裡的口紅放在梳粧台的背後。
第二天,陸經理在辦公室裡接到德懷打來的電話。
「德懷兄……早……什麽事?」
聽简裡傳來德懷的聲音。「昨天晚上你們走了以 後,我跟太太打起來了……」
「你怎麽啦,夫妻吵架不可以動手的呀!」陸經理是老實人,果然信以為眞。
「是她先動手的,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說過話。」徳懷越裝越像了。
「那不行,那不行………那當然難怪她的。」
「我現在想想,這 當然是我不好,我想請你打個電話給黛茜,可是千萬叫她裝作不知道這件事,你知道我太太是個很要面子的人,叫黛茜約她出來玩玩。」
「我知道……好了,你別管了!」陸經理義不容辭的說道:「你今天晚上到我家來吃飯,包你和好如初……」
「你有 把握嗎?」德懷說着電話,忍不住想笑。
「包在我身上,我這就打電話給黛茜。」陸經理放下電話,接着又撥號碼。
陸經理吿訴了黛茜,黛茜打電話邀徐太太,徐太太又用電話通知了德懷,一切總算按照德懐的預定計劃順利進行。
晚上在陸家,徐太太打着牌,徳懷偷進浴室,把那雙絲襪給塞在浴缸之下,裝着沒事的又走出去看牌。
翌日晨起,徐太太走出臥室去,徳懷對着鏡子打領帶,斜眼看看梳粧台下,心生一計,把手中的別针朝梳粧台下一扔,高聲又把徐太太叫了進來。
「什麽事?」徐太太 問。
「帮帮忙,我的別针掉下去了。」德懷指着梳粧台下說。
二人合力把梳粧台扛開,德懷用電筒往裡照探,祗聽得徐太太「啊呀」一聲的立起身來,手裡拿着別针,還有一支精緻的口紅管。
「我那支丟了的口紅!」徐太太看着手裡說道。
「怎麽會在那裡面?」德懷故作不解狀。
徐太太怔了個半天,坐下,忽的又站了起來,說道:
「我怎麽對得起人?」
「誰?」
「家禾,我不是吿訴過你,她偷……呀!那怎麽辧呢?」徐太太顯然受着良心上的責備,回過頭來急問:「你沒有跟家禾說起我寃枉她偷口紅的事吧?」
「你當我是瘋子呀!我早說這是謠言,你又不相信。」
徐太太立起身來,堅决的說道:「我馬上找她去,我要對她懺悔,我………」
德懷連忙阻止,笑道:「這樣反而叫人奇怪,你旣然知道不是她了,往後的日子長着呢,你急什麽呀?」
徐太太一言不發,坐下就哭,德懷得意的喑笑。
在事務所裡,德懷走來走去,頻頻看電話,好像在等待什麽要緊消息。電話鈴响,德懷急急拿起聽筒,果然是家禾打來的。
家禾在電話裡告訴他,太太跟黛茜都來了,對她特別表示好感。德懷窃喜,知道他太太又帮着黛茜把絲襪給找到了。跟着徐太太又接過來說電話,她說:
「我們想帮家禾做點事情,她說還少一點束西,我們陪她上百貨公司去,再見。」
德懐一聽「百貨公司」四個字先慌了手脚,放下電話就趕緊出 去滿街的找,總算好不容易在一家規模不小的百貨公司裡找到了,看看她們三人談笑風生,並無異狀,方始放下了一半心。
「咦,你怎麽知道我們在這兒?」家禾問道。
「我也想買點東西。」德懷嘴裡撒着謊,眼光可隨時注意着家禾的舉動。
三位太太走到了首飾部,德懐開始緊張,徐太太在買耳環,家禾的眼裡好像有些發光,德懷險些急煞。
好容易買完了東西,四人向大門走去之際,一名店夥叫着奔上前。德懷大驚怔住,看着家禾不能動彈。
「這是您的,忘在櫃台上了。」店夥遞過一個紙包。
「謝謝你。」徐太太笑着接過。
德懷鬆下一口氣,很高興的往外走。
大家一起回到了蘇家,飮酒、談天,挺熱鬧的局面。家禾走出窗外去透空氣,德懷跟着。
「家禾,我還沒有恭喜你。」德懷笑着說。
「什麽事?」
「我看這個秘密可以不必再吿訴第三個人了,你看,你祗對我說過一遍,就這麽好了,這是一種存在腦子下層的意識…………」
像幽靈一般出現的表姐,把德懷的話頭打斷。她對德懷跟家禾笑了笑,又飄然的走了過去。
家禾目送着表姐的背影,說道:「她是不是 有點知道我的秘密?」
德懷點頭說:「她也挺注意我的,明天再談吧」
裡面,黛茜鬧着要打牌,架不住大家反對,因爲家禾明天一早要到別墅去,黛茜也祗可嘆氣作罷。
家禾正式去佈置新居,這一夥又全部到了蘇家別墅,大森也帶着未婚妻愛茜前來凑熱鬧,一直鬧到了傍晚,德懷特別高興,自吿奮勇,請客吃飯及跳舞,一衆人擁進了舞廳。
樂台上奏请輕快的調子,舞池裡燈光暗淡。
愛茜遇到了一位女朋友,匆匆的說了幾句話,回到桌上,打開皮包取出一枝精緻的自來水筆在抄寫地址。愛茜把自 來水筆放在桌上,大家嘖嘖稱贊的拿來起傳觀,傅到家禾手中時,德懷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
音樂又起,大家下池跳舞,旣遂在要求家禾跳一隻,家禾推說頭痛。
「老蘇,你跟我太太去跳一個,我反正不跳舞。」德懷慫恿着說。
桌上祇剩下家禾與德懷二人,家禾忽然坐到愛茜的位置上去,德懷又開始緊張。閒談幾句之後,家禾起身到洗手間去,,德懷鬆動了不少。
家禾很快的就回來了。德懷問道:
「你是不是眞的有點頭痛?」
「有一點。」家禾對着德懷很不自然的笑了笑,打開皮包,取出手帕來擦手。
突然間,德懷的眼睛張得老大,那裡面充滿了恐怖與驚惶,他發現了一件怪事,家禾自洗手間裡帶回來的不是她自己的皮包,那是愛茜的!
不容他再思索,德懷一手按住了家禾的皮包,家禾起先愕然對他看着,但是很快的又低下頭去, 雙手掩面。
音樂已經停止,情勢是千鈞一髮,刻不容緩,德懷迅速的自家禾的皮包中取出那枝筆,把皮包交還給家禾,輕聲喝道:「去,快去!」
家禾猶豫一下,立起身來走去。德懷急轉身看桌上愛茜的皮包,大家已經回到位上坐下。
男客們談笑,女客們打開皮包重新化粧,愛茜也伸手拿起她的皮包,德懷可眞急了,假意不留心,手指帶着皮帶祇一拉,皮包掉在地下,裡而的零碎東西撒了一地,德懷連聲道歉,乘人們不注意,把手中暗藏的鋼筆混了進去。
德懷在擦汗,家禾回到桌上,她的神色很不好看。
自從那次舞會之後,家禾把自己給禁閉在屋裡,不出大門一步,終日睡在床上發呆,旣遂雖然着急,可是他怎能明瞭個中的內情呢?
祇有一個人最明白。德懷一再打電話給家禾,勸解她、鼓勵她,與她分析那個病源的發生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把秘密 向旣遂公開,可是家禾抵死不肯。
德懷在電話裡緊急的說道:「家禾,你難道不想好嗎?………我現在就到你那裡來,我來帮你對旣遂說!」
「我不要!我不要…」家禾大聲抗議,但是對方早已掛斷了線。家禾覺得屋頂在轉,眼裡發花,走來走去了幾次 ,猛的下了决心,像疯了似的往外就跑。
這一切,表姊都躱在一邊看在眼裡。
別墅内臥室的家具還是沒有送來,空洞洞的倍覺凄凉。家禾把窗子打開,海風吹亂了她的頭髮,往下看,危浪激石,怒潮澎湃,家禾閉上了服晴,她有着一個奇怪的想頭……
「家禾!」
德懷的聲音起自身後,家禾好似大夢初醒的睜開了眼睛,她回頭,呆立,突然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量,把她給撞了過去,直投到德懷的懷中。
家禾想說什麼,但是說不出。德懷低聲勸慰:「不要說話,來,我們到下面去。」
樓下,德懷在勸家禾向丈夫坦白,不知道表姐正在窗外偷聽。德懷問道:「你是不是怕他知道了以後,駡你、看不起你、不再愛你、給更多的人知道?」
家禾點頭,德懷繼續往下說:
「那麽,你可以跟他兩個人到這兒來住上幾天,這兒祇有你們兩個人,你可以靜 靜的一步一步吿訴他,別讓他受刺激。好呢,他可以原諒你,不好的話,大不了跟他離婚。」
表姐帶着笑容退出,坐上車子,急速離去。
很快的到了蘇家搬家的日子。
別墅裡空前的熱鬧,祇看見大森跑來跑去找人跳舞,旣遂和家禾托着洒菜盤子招待,黛茜徐太太等則是老規矩—打牌。
大家喝得髙了興,陸經理提議請女主人唱個歌,家禾很大方的答應了。一曲紅豆詞吸住了全體來賓,屛息凝神,注意在聽,尾聲已畢,大家熱烈鼓掌,在掌聲之中,忽然聽到黛茜「咦」的一聲。
「什麽事?」旁邊的 徐太太問道。
「我的別針不見了。」黛茜說着遍地在尋找。她的那件珍貴飾物曾經引起許多女賓的讚賞。
「剛纔不是……」徐太太的話猶未完,家禾也走了過來。
聽說黛茜丢了別針,家禾的神色有些異樣。德懷覩狀亦來,對家禾看了幾眼,爲解圍計,他說道:「我來替你們找,你們打牌。」
家禾好似失了主意一般,回身朝樓上飛奔,德懷想跟上,被一位小姐纏着了跳舞,沒法脫身。
在臥室裏,家禾匆匆的在抽屜内尋找,抬頭看鏡子,背後站定的表姐,面色很嚴肅。
家禾失神的看着她,表姐開口說:「你的秘密,家禾,我早知道了,可是我沒有跟你說,我想你自己會跟旣遂說的。」
家禾呆住了,不知說什麽好。表姐逼近一步,厲聲說道:
「我一直等着你自己跟旣遂說,你爲什麽不說?難道你一定要我代你說,要不要我現在下去對這許多 人說?」
家禾哀求着說道:「我已經沒有做這種事情了,我已經改過了,表姐!你一直待我很好,你………」
「不,家禾,你錯了!」表姐冷然說:「我一直沒有喜歡過你,旣途本來是我的,你給我搶了去,現在你的秘密落在我的手裏,我是不會放過的 。」
「家禾!」德懷叫着衝了進來。「把黛茜的別針交給我。」
「我沒有拿過。」
「記淸楚了,你一定沒有拿過?」
「我記得很淸楚。」
「那末這是你吿訴旣遂的時候了!」德懷興奮的說:「是是一種病,不是一種罪,他沒有理由不原諒你的。」
家禾欣喜的點着頭,德懷笑嘻嘻的帶了她出去,表姐的面部表情,先是愕然,繼而恍然,自言自語的:「原來這是你的秘密。」
家禾走下樓梯,看見旣遂在餐室裏找東西吃。
「旣遂,我有話跟你說。」家禾走進了餐室。
表 姐先到,德懷跟來,二人向餐室裏看,旣遂拉着家禾的手,他說:
「你爲什麽不早吿訴我,你以爲我是這樣一個沒有人性的丈夫嗎?」
家禾輕快的笑了起來,德懷在門外滿意的也笑了,表姐回身悄然離去。
旣遂滿臉笑容,拿着酒瓶直到黛茜身旁。
「黛茜,敬你一杯酒,喝不喝?」旣遂髙擧着酒瓶說道。
「我不喝。」黛茜乾脆回絕。
「好。」旣遂擧瓶倒酒,酒盡,別針在瓶底。
家禾第一個先跳了起來,驚呼道:「啊呀,別針!」她眼裡充滿了盈盈的淚珠,說不上是喜是悲。
「別針!」徐太太恍然若有所悟,一屋子的疑雲馬上冰消瓦解,旣遂爽亮的狂笑聲,給整個大廳更平添了好多喜氣洋洋的氣氛。
「喝不喝?不喝,不還你。」旣遂高肇酒瓶,得意的對着黛茜示威。
黛茜仲伸手想搶酒瓶,被旣遂機警的避開了去。無可奈何 的,黛茜祇得接過酒杯,一仰頭就把那杯酒飲盡,大家歡笑,叫囂,拍手,鬧成一片。
家禾滿心歡喜的樣子,興匆匆走向洒吧。
表姐冷眼旁觀,心頭一番滋味,祇有她自己明白,在沒人注意之中,表姐跨上樓梯,走出門去,輕輕的把大門掩上。
家禾取過來一個茶盤,德懷微笑的也跟了過來。家禾自旣遂手中接過了空酒瓶,砰然一聲在茶盤上敲破,茶盤裡滿佈着玻璃碎片,亮品晶的襯托着黛茜的8別针。
黛茜回過身,小心的自茶盤內取出別針來。
「滿貫!」徐太太忽然間攤下了牌,冷不防嚇了一跳的黛茜直叫了起來,又是一陣子哄堂大笑。
家禾,旣遂,德懷,三人相視而笑。
(完)
駱家禾——尤敏飾
幼年時家庭環境造成,患了人格分裂症的弱女子,這裡是一篇她的奮鬥史。
富家小姐出身,受過良好敎育,學成後嫁年靑的地產商蘇旣遂,是一位有地位的體面人,這個秀外慧中生活得像一朶花似的家禾,誰也料不到她有一個「偷窃病」,這病是幼年家庭環境造成的,父親另納新寵,母親鬱鬱少歡,她穉弱心靈中以爲母親之所以寡歡,乃因父親把好的東西買給姨母關係,於是她就去偷姨母的東西博母親一笑,母親未予敎育,漸漸她的偷窃成爲一種下意 識的動作,人格分裂。
她的幼年同窗徐德懷,得悉了那秘密,以心理治療法糾正了她的變態心理,使她眞正地得到了幸福。
徐德懷——趙雷飾
熱心腸的年靑工程師,爲了朋友的名譽起見,不惜千方百計的設法糾正她。
年靑而有爲的建築師 ,當在學時他也是追求駱家禾的一員,但家禾卒被好友蘇旣遂追求成功而結婚,他就把感情昇華起來,他自己也結了婚,兩家時相往來,交誼典厚,有一天,太太忽然疑心到家禾偷了東西,他半信半疑,冷眼偵查之下,發覺家禾眞有這種行爲,他極力向家禾探問明白, 家禾把一生唯一的秘密吿知,德懷知道這是屬于心理上的一種病症,勸她吿訴丈夫,合力由心理上使她正常,結果雖有人阻撓,被德懐冷靜地指出眞象,使家禾的「病」,霍然而癒。
蘇既遂——馬力飾
富家子弟,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他熱愛着他的太太 ,祇是太太不關心於她。
年青而富有的商人,他熱愛太太駱家禾,仍不關心她,帮助她、家禾心裡有一個秘密始終未為丈夫知道,他刻意承歡,把太太弄成花似一朶,太太心裡却並不快活,且時時因自己的病感到痛苦難堪。
老同學徐德懷發现了他太太的 病,去吿訴他,希望他帮助太太醫治這個心理病,他才知道自己還沒有太瞭解太太,决心與德懷合作,用各種方法,在心理上治療了家禾自幼俱來的人格分裂症,這對小夫妻在這時才開始渡着眞正的幸幅生活。
徐太太——翁木蘭飾
本性忠厚,思想單純的 一位太太,純都市型的淺雜婦女,但有着善良的心。
徐德懷太太是個本性忠厚,思想單純,因環境關係,造成她成天打牌、吃喝的生活,她愛好新奇,有一位表弟同她在千里外的河内帶來了一支法國新式唇膏,她喜歡得了不得,以之示家禾,轉瞬間唇膏就不見了,加以另一位太太也失窃絲襪,根據推斷,她們認爲是蘇旣遂太太駱家禾所爲,任性地不再與家禾往來,但是徐德懷是個頭腦洽靜的人,他知道了家禾「病因」,使唇膏「復返原防」,徐太太看到唇膏,以爲自己錯怪了家禾,慚疚得很,一定要向家禾道歉,並大哭了一 塲,這是一位善良而淺撖的都市太太。
黛茜——陳芸飾
漂亮而喜歡熱鬧的少奶奶,沒有心眼光,祇愛的是打牌,單純得非常可愛。
是徐德懷太太家中的常客,開「派對」的熱心贊助人之一,長得漂亮,又懂得時髦玩意兒,是標準的都市小姐。
她與家禾很好,但最後在一塲舞會中,因蘇旣遂的表姊之故佈疑陣,黛茜的一支名貴胸針不見了,許多人都懷疑是家禾幹的事,連她也無例外。
徐德懷是明白其中秘密的,他用巧妙的手法,當埸証明了這是表姊所做的事,胸針在酒瓶中發現,黛茜這時高興萬 狀。
愛好新奇,物質慾强,但,不是壞人。
表姊——裘萍飾
老處女,私戀着她所不應該愛戀的人,頗工心機,但是命運並不使她如意。
一個心理變態的老處女,她是旣遂的表姊,也寄居旣遂家,自幼,她對旣遂很愛好,又不敢說明心事, 後來旣遂結了婚,她却不再想嫁人,但對旣遂的美麗太太駱家禾起了恨心,處處她挑撥離間二人的感情,但常常失效,這様使她因嫉妬而心理變態。
她從徳懷與家禾的談話中,偷聽得家禾的「秘密」,爲了洩憤,她故意在舞會中製造一個失竊案件,讓家禾的病可以復發,然而他逃不過冷靜的徐德懷,她的「秘密」被戳穿,旣愧且羞的走了。
「誘惑」故事
傍晚,徐家客廳裡一片歡笑,很是熱閙。
主人徐德懷,一位年青而又頗有聲望的建築設計師,明天要到星加坡去公幹,此刻正忙着接洽機票等事並不在家,家裡是徐太太舉行的宴會,客人都是平時最熟的朋友親戚們,這就算是給徐德懐餞行的。
四位太太小姐正在打牌,徐太太的舊時同學黛茜的手氣最好,興高采烈的大呼小叫,黛茜的丈夫陛經理正在那精緻的小酒吧前與徐太太談話,也被牌桌上的熱鬧給吸引了過來。
「這様的手風可把我嚇壤 了。」徐太太看着攤在黛茜而前的一副牌,嘴裡說。
桌上的一位張太太直抱怨自己打錯了牌,其餘的笑嘻嘻的數着籌碼,付給黛茜。
「黛茜祗有跟家禾打牌,纔會輸。」徐太太帶着嘲笑的口吻說。
「誰呀?」一位陳太太發問。
「蘇旣遂太 太。」站在一旁的陳先生接着答道。
大家繼續的討論着關於家禾的事情,看様子這位蘇太太好像很引人注意似的。
家禾姓駱,是徐德懐的女同學,聽說他倆在學校時曾經相戀過,不過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他們夫婦兩對彼此都成了極親密而知己的朋 友。家禾年輕漂亮,丈夫富有,是一位地產富商的兒子,夫婦二人在社交上的地位自然是極髙的。
說話時,徐太太的弟弟大森,一個幹着飛機師的活潑靑年,跨了進來,大家一陣亂招呼,黛茜一面打牌一面說:
「這回我要託你帶點東西。」
「大森連連答應,接着也問道:「蘇太太呢?」
可見家禾在這個小圈子裡是如何主要的一名人物了。一句話提醍了徐太太走到沙發上打個電話去催請。
徐太太剛拿起聽筒,徐德懷也回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回米晚了。」德懷手裡拿着行李照貼紙之類,顯然是從航空公司趕回來的,他招呼完了每一個客人之後,嘴裡咳的一聲問道:「家禾還沒來。」
徐太太笑道:「你們看,又是一個問她的人。」回過頭來向着徐德懐,半嗔半笑。「你快去洗個澡吧!我來打電話給我們的大衆情人。」
蘇家電話鈴響, 家禾急急忙忙的奔過去接聽,說話時笑得格格的。「喂………啊,就來了,旣遂他剛………。」
蘇旣遂一面打着領帶,一面走了出去,他是一個高個子的漂亮小伙子,俊秀的臉龐上的掩不住那種大孩子的天眞氣,一眼就看得出來是個忠實可靠的有爲靑年。旣遂的背後喝跟着的是他的表姐,一個外型美麗而內心竪强的老處女,她是蘇家的管家婦。
「快走,快走。」旣遂飛步往外跑,連領帶掉在地下也顧不得,家禾放下電話筒就走,表姐叫道:
「急什麽呀,家禾!他的領帶。」
家禾旣遂同時返身來拿,拔脚又走了,表姐搖搖頭,嘆口氣。
徐德懷那時在他的浴室裡也很緊張,洗澡、整容、換衣服。徐太太在臥室裡,正把黛茜託買東西的一張淸單交給大森,大森接過來看了幾眼,說道:
「嘖噴………口紅,這兒連口紅都沒得買?」
「不,她要你送給我的那一種,這兒買不到的。」
徐太太說着,在梳粧台旁取出一支精緻的口紅管來。
「糟糕!那兒買的我都忘了,我去問她去。」大森拿着口紅出去,徐太太追着吩咐道:
「別給我丢了。」
大森一直走到客廳裡牌桌旁,說道:
「黛茜,東西我可照准給你帶,別的沒問題,這支口紅恐怕不行………」
大森手中高舉的那支小口紅,引起了全堂女客們的讚羡聲。
「對不起,對不起,主人呢?」蘇旣遂夫婦那時恰巧來到,忙不迭的向大家打招呼,大森一本正經的說道:
「姐姐去接你去了。」
「眞的?你看都是你不好。」家禾回頭抱怨着旣遂。
黛茜坐在牌桌上,接嘴說道:「別聽那東西的話,在裡邊呢,我託他帶一點東西,他也不肯,你看這支口紅多漂亮。」說着把口扛遞了過去,家禾看着時不禁發了一呆。
黛茜順手把口紅交給了大森,此時徐太太笑駡着走了出來。「小鬼,你怎麽這會兒纔來?」
「對不起,對不起。」家禾連連抱歉。
大森走近,把口紅還給徐太太,她隨便接過,陪着蘇家夫婦到酒吧上去飮酒,在爲客人們倒酒時,口紅被放在桌上。德懷換好了衣服出來, 與旣遂討論着蘇家新建而尙未落成的別墅,太太們計劃着如何去佈置它,徐太太很是熱心,家禾倒反而好像有些心不在焉的神氣,從客廳另一角上又放出了黛茜的笑聲。
「黛茜的手風好極了,我們去看看。」徐太太一把拉着家禾就走,留下德懷與蘇旣遂在酒吧裡談生意經。
夜阑客散,華燈盡落,徐太太在黯淡的客廳裡四下尋找,德懷自臥室内走出,問道:
「你在找什麽呀?」
「口紅,我那支口紅。」
「睡了,快兩點了。」
「不,我那支口紅不是普通的口紅。」徐太太負氣的說道。
德懷畧施小計,把太太給哄進房锂,問道:「你明天晚上,會不會像丢了那支口紅一樣的找我?」
徐太太不答應的,耍槌丈夫,反被德懷一把抱住。臥室的燈也暗了。
一個月以後,徐太太又忙着佈置一個小小的宴會,因為德懷今天將要回來了。
大森在陽台上張望,看到接得丈夫的徐太太,喜吟吟的跨下汽車,連忙關照大家躱起來。
「客人來了沒有?」徐太太一進門就問。
「沒有呀!姐夫。」大森忙着跟德懷握手。
「讓我先打個電話給黛茜,我非駡她幾句不可。」徐太太走向電話那處。
猛然一陣哄笑起自簾内,黛西首先跳了出來,後面是陸經理、王小姐、陳先生、陳太太、張先生、張太太………原來客人早到齊了。笑聲駡聲中,大家向德懷道辛苦。
一陣忙亂過去,德懷四下捜望,嘴裡說:「咦,家禾呢?」安慰着說道。表姐離開窗下 。
德懷忽然想起,說道:「你知道你曾經拿過我太太的口紅,跟黛西的絲祙嗎?」
「口紅?」家禾說着立起身來走向內室,回頭又招呼德懷。「你來。」
德懷跟入,恰巧表姐跨進門來,看着德懷的背影發怔,忽然驚覺,匆匆又跑開了去。
家禾在臥室梳粧台抽屜裡找出來口紅及絲祙,德懷拿住,點點頭。
「她……她們知道了沒有?」家禾焦急的問道。
「知道了,而且她們知道是你。」德懷沮喪的答道。
「那………」
「你交給我,我想辦法去還給她們,讓她們以爲這些束西 並沒有遺失,錯怪了你。」德懷說着把口紅放入袋裡,又把絲祙小心的放入内袋。「讓她們再像以前一樣的跟你親密,不讓你再有一點空的時間去犯這種病,也許你就這様好了。」
「也許我就這末好了。」家禾破涕爲笑,頰上仍掛着亮晶晶的淚珠。
旣遂 回到家,晚飯桌上,與德懷談到卽將成功的一件生意,高起興來,跟德懷不住的碰杯。
表姐看在眼裡,也擧起了酒杯,說道:「家禾,我們也來喝一杯。」
家禾縐眉說:「我不想喝。」
「那末徐先生跟她喝。」表姐的話裡好像有剌。
德懷 陪笑說道:「表姐今天的興緻很好。」
「是呀,我發現了一個秘密。」
德懐筷中食物掉下落在身上,家禾對他看着。
「什麽秘密?」旣遂很感興趣,問道。
「你們不喝酒,我不說。」表姐故作神秘,微笑着說。
旣遂一飲而盡,德懷勉强追隨,家禾看看德懷,慢慢的喝完。大家放下酒杯,空氣緊張。
「我是說着玩的,騙你們喝酒是眞的。」表姐輕俏的說道。
大家都笑了,笑得最不自然的是德懷。
德懷回到家裡,客廳上一桌牌局還沒有散。徐太太今天手氣好,很是高興。
德懐搭訕着跟陸經理、黛茜等開了幾句玩笑,抽空子溜進了臥室,像做賊似的把袋裡的口紅放在梳粧台的背後。
第二天,陸經理在辦公室裡接到德懷打來的電話。
「德懷兄……早……什麽事?」
聽简裡傳來德懷的聲音。「昨天晚上你們走了以 後,我跟太太打起來了……」
「你怎麽啦,夫妻吵架不可以動手的呀!」陸經理是老實人,果然信以為眞。
「是她先動手的,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說過話。」徳懷越裝越像了。
「那不行,那不行………那當然難怪她的。」
「我現在想想,這 當然是我不好,我想請你打個電話給黛茜,可是千萬叫她裝作不知道這件事,你知道我太太是個很要面子的人,叫黛茜約她出來玩玩。」
「我知道……好了,你別管了!」陸經理義不容辭的說道:「你今天晚上到我家來吃飯,包你和好如初……」
「你有 把握嗎?」德懷說着電話,忍不住想笑。
「包在我身上,我這就打電話給黛茜。」陸經理放下電話,接着又撥號碼。
陸經理吿訴了黛茜,黛茜打電話邀徐太太,徐太太又用電話通知了德懷,一切總算按照德懐的預定計劃順利進行。
晚上在陸家,徐太太打着牌,徳懷偷進浴室,把那雙絲襪給塞在浴缸之下,裝着沒事的又走出去看牌。
翌日晨起,徐太太走出臥室去,徳懷對着鏡子打領帶,斜眼看看梳粧台下,心生一計,把手中的別针朝梳粧台下一扔,高聲又把徐太太叫了進來。
「什麽事?」徐太太 問。
「帮帮忙,我的別针掉下去了。」德懷指着梳粧台下說。
二人合力把梳粧台扛開,德懷用電筒往裡照探,祗聽得徐太太「啊呀」一聲的立起身來,手裡拿着別针,還有一支精緻的口紅管。
「我那支丟了的口紅!」徐太太看着手裡說道。
「怎麽會在那裡面?」德懷故作不解狀。
徐太太怔了個半天,坐下,忽的又站了起來,說道:
「我怎麽對得起人?」
「誰?」
「家禾,我不是吿訴過你,她偷……呀!那怎麽辧呢?」徐太太顯然受着良心上的責備,回過頭來急問:「你沒有跟家禾說起我寃枉她偷口紅的事吧?」
「你當我是瘋子呀!我早說這是謠言,你又不相信。」
徐太太立起身來,堅决的說道:「我馬上找她去,我要對她懺悔,我………」
德懷連忙阻止,笑道:「這樣反而叫人奇怪,你旣然知道不是她了,往後的日子長着呢,你急什麽呀?」
徐太太一言不發,坐下就哭,德懷得意的喑笑。
在事務所裡,德懷走來走去,頻頻看電話,好像在等待什麽要緊消息。電話鈴响,德懷急急拿起聽筒,果然是家禾打來的。
家禾在電話裡告訴他,太太跟黛茜都來了,對她特別表示好感。德懷窃喜,知道他太太又帮着黛茜把絲襪給找到了。跟着徐太太又接過來說電話,她說:
「我們想帮家禾做點事情,她說還少一點束西,我們陪她上百貨公司去,再見。」
德懐一聽「百貨公司」四個字先慌了手脚,放下電話就趕緊出 去滿街的找,總算好不容易在一家規模不小的百貨公司裡找到了,看看她們三人談笑風生,並無異狀,方始放下了一半心。
「咦,你怎麽知道我們在這兒?」家禾問道。
「我也想買點東西。」德懷嘴裡撒着謊,眼光可隨時注意着家禾的舉動。
三位太太走到了首飾部,德懐開始緊張,徐太太在買耳環,家禾的眼裡好像有些發光,德懷險些急煞。
好容易買完了東西,四人向大門走去之際,一名店夥叫着奔上前。德懷大驚怔住,看着家禾不能動彈。
「這是您的,忘在櫃台上了。」店夥遞過一個紙包。
「謝謝你。」徐太太笑着接過。
德懷鬆下一口氣,很高興的往外走。
大家一起回到了蘇家,飮酒、談天,挺熱鬧的局面。家禾走出窗外去透空氣,德懷跟着。
「家禾,我還沒有恭喜你。」德懷笑着說。
「什麽事?」
「我看這個秘密可以不必再吿訴第三個人了,你看,你祗對我說過一遍,就這麽好了,這是一種存在腦子下層的意識…………」
像幽靈一般出現的表姐,把德懷的話頭打斷。她對德懷跟家禾笑了笑,又飄然的走了過去。
家禾目送着表姐的背影,說道:「她是不是 有點知道我的秘密?」
德懷點頭說:「她也挺注意我的,明天再談吧」
裡面,黛茜鬧着要打牌,架不住大家反對,因爲家禾明天一早要到別墅去,黛茜也祗可嘆氣作罷。
家禾正式去佈置新居,這一夥又全部到了蘇家別墅,大森也帶着未婚妻愛茜前來凑熱鬧,一直鬧到了傍晚,德懷特別高興,自吿奮勇,請客吃飯及跳舞,一衆人擁進了舞廳。
樂台上奏请輕快的調子,舞池裡燈光暗淡。
愛茜遇到了一位女朋友,匆匆的說了幾句話,回到桌上,打開皮包取出一枝精緻的自來水筆在抄寫地址。愛茜把自 來水筆放在桌上,大家嘖嘖稱贊的拿來起傳觀,傅到家禾手中時,德懷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
音樂又起,大家下池跳舞,旣遂在要求家禾跳一隻,家禾推說頭痛。
「老蘇,你跟我太太去跳一個,我反正不跳舞。」德懷慫恿着說。
桌上祇剩下家禾與德懷二人,家禾忽然坐到愛茜的位置上去,德懷又開始緊張。閒談幾句之後,家禾起身到洗手間去,,德懷鬆動了不少。
家禾很快的就回來了。德懷問道:
「你是不是眞的有點頭痛?」
「有一點。」家禾對着德懷很不自然的笑了笑,打開皮包,取出手帕來擦手。
突然間,德懷的眼睛張得老大,那裡面充滿了恐怖與驚惶,他發現了一件怪事,家禾自洗手間裡帶回來的不是她自己的皮包,那是愛茜的!
不容他再思索,德懷一手按住了家禾的皮包,家禾起先愕然對他看着,但是很快的又低下頭去, 雙手掩面。
音樂已經停止,情勢是千鈞一髮,刻不容緩,德懷迅速的自家禾的皮包中取出那枝筆,把皮包交還給家禾,輕聲喝道:「去,快去!」
家禾猶豫一下,立起身來走去。德懷急轉身看桌上愛茜的皮包,大家已經回到位上坐下。
男客們談笑,女客們打開皮包重新化粧,愛茜也伸手拿起她的皮包,德懷可眞急了,假意不留心,手指帶着皮帶祇一拉,皮包掉在地下,裡而的零碎東西撒了一地,德懷連聲道歉,乘人們不注意,把手中暗藏的鋼筆混了進去。
德懷在擦汗,家禾回到桌上,她的神色很不好看。
自從那次舞會之後,家禾把自己給禁閉在屋裡,不出大門一步,終日睡在床上發呆,旣遂雖然着急,可是他怎能明瞭個中的內情呢?
祇有一個人最明白。德懷一再打電話給家禾,勸解她、鼓勵她,與她分析那個病源的發生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把秘密 向旣遂公開,可是家禾抵死不肯。
德懷在電話裡緊急的說道:「家禾,你難道不想好嗎?………我現在就到你那裡來,我來帮你對旣遂說!」
「我不要!我不要…」家禾大聲抗議,但是對方早已掛斷了線。家禾覺得屋頂在轉,眼裡發花,走來走去了幾次 ,猛的下了决心,像疯了似的往外就跑。
這一切,表姊都躱在一邊看在眼裡。
別墅内臥室的家具還是沒有送來,空洞洞的倍覺凄凉。家禾把窗子打開,海風吹亂了她的頭髮,往下看,危浪激石,怒潮澎湃,家禾閉上了服晴,她有着一個奇怪的想頭……
「家禾!」
德懷的聲音起自身後,家禾好似大夢初醒的睜開了眼睛,她回頭,呆立,突然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量,把她給撞了過去,直投到德懷的懷中。
家禾想說什麼,但是說不出。德懷低聲勸慰:「不要說話,來,我們到下面去。」
樓下,德懷在勸家禾向丈夫坦白,不知道表姐正在窗外偷聽。德懷問道:「你是不是怕他知道了以後,駡你、看不起你、不再愛你、給更多的人知道?」
家禾點頭,德懷繼續往下說:
「那麽,你可以跟他兩個人到這兒來住上幾天,這兒祇有你們兩個人,你可以靜 靜的一步一步吿訴他,別讓他受刺激。好呢,他可以原諒你,不好的話,大不了跟他離婚。」
表姐帶着笑容退出,坐上車子,急速離去。
很快的到了蘇家搬家的日子。
別墅裡空前的熱鬧,祇看見大森跑來跑去找人跳舞,旣遂和家禾托着洒菜盤子招待,黛茜徐太太等則是老規矩—打牌。
大家喝得髙了興,陸經理提議請女主人唱個歌,家禾很大方的答應了。一曲紅豆詞吸住了全體來賓,屛息凝神,注意在聽,尾聲已畢,大家熱烈鼓掌,在掌聲之中,忽然聽到黛茜「咦」的一聲。
「什麽事?」旁邊的 徐太太問道。
「我的別針不見了。」黛茜說着遍地在尋找。她的那件珍貴飾物曾經引起許多女賓的讚賞。
「剛纔不是……」徐太太的話猶未完,家禾也走了過來。
聽說黛茜丢了別針,家禾的神色有些異樣。德懷覩狀亦來,對家禾看了幾眼,爲解圍計,他說道:「我來替你們找,你們打牌。」
家禾好似失了主意一般,回身朝樓上飛奔,德懷想跟上,被一位小姐纏着了跳舞,沒法脫身。
在臥室裏,家禾匆匆的在抽屜内尋找,抬頭看鏡子,背後站定的表姐,面色很嚴肅。
家禾失神的看着她,表姐開口說:「你的秘密,家禾,我早知道了,可是我沒有跟你說,我想你自己會跟旣遂說的。」
家禾呆住了,不知說什麽好。表姐逼近一步,厲聲說道:
「我一直等着你自己跟旣遂說,你爲什麽不說?難道你一定要我代你說,要不要我現在下去對這許多 人說?」
家禾哀求着說道:「我已經沒有做這種事情了,我已經改過了,表姐!你一直待我很好,你………」
「不,家禾,你錯了!」表姐冷然說:「我一直沒有喜歡過你,旣途本來是我的,你給我搶了去,現在你的秘密落在我的手裏,我是不會放過的 。」
「家禾!」德懷叫着衝了進來。「把黛茜的別針交給我。」
「我沒有拿過。」
「記淸楚了,你一定沒有拿過?」
「我記得很淸楚。」
「那末這是你吿訴旣遂的時候了!」德懷興奮的說:「是是一種病,不是一種罪,他沒有理由不原諒你的。」
家禾欣喜的點着頭,德懷笑嘻嘻的帶了她出去,表姐的面部表情,先是愕然,繼而恍然,自言自語的:「原來這是你的秘密。」
家禾走下樓梯,看見旣遂在餐室裏找東西吃。
「旣遂,我有話跟你說。」家禾走進了餐室。
表 姐先到,德懷跟來,二人向餐室裏看,旣遂拉着家禾的手,他說:
「你爲什麽不早吿訴我,你以爲我是這樣一個沒有人性的丈夫嗎?」
家禾輕快的笑了起來,德懷在門外滿意的也笑了,表姐回身悄然離去。
旣遂滿臉笑容,拿着酒瓶直到黛茜身旁。
「黛茜,敬你一杯酒,喝不喝?」旣遂髙擧着酒瓶說道。
「我不喝。」黛茜乾脆回絕。
「好。」旣遂擧瓶倒酒,酒盡,別針在瓶底。
家禾第一個先跳了起來,驚呼道:「啊呀,別針!」她眼裡充滿了盈盈的淚珠,說不上是喜是悲。
「別針!」徐太太恍然若有所悟,一屋子的疑雲馬上冰消瓦解,旣遂爽亮的狂笑聲,給整個大廳更平添了好多喜氣洋洋的氣氛。
「喝不喝?不喝,不還你。」旣遂高肇酒瓶,得意的對着黛茜示威。
黛茜仲伸手想搶酒瓶,被旣遂機警的避開了去。無可奈何 的,黛茜祇得接過酒杯,一仰頭就把那杯酒飲盡,大家歡笑,叫囂,拍手,鬧成一片。
家禾滿心歡喜的樣子,興匆匆走向洒吧。
表姐冷眼旁觀,心頭一番滋味,祇有她自己明白,在沒人注意之中,表姐跨上樓梯,走出門去,輕輕的把大門掩上。
家禾取過來一個茶盤,德懷微笑的也跟了過來。家禾自旣遂手中接過了空酒瓶,砰然一聲在茶盤上敲破,茶盤裡滿佈着玻璃碎片,亮品晶的襯托着黛茜的8別针。
黛茜回過身,小心的自茶盤內取出別針來。
「滿貫!」徐太太忽然間攤下了牌,冷不防嚇了一跳的黛茜直叫了起來,又是一陣子哄堂大笑。
家禾,旣遂,德懷,三人相視而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