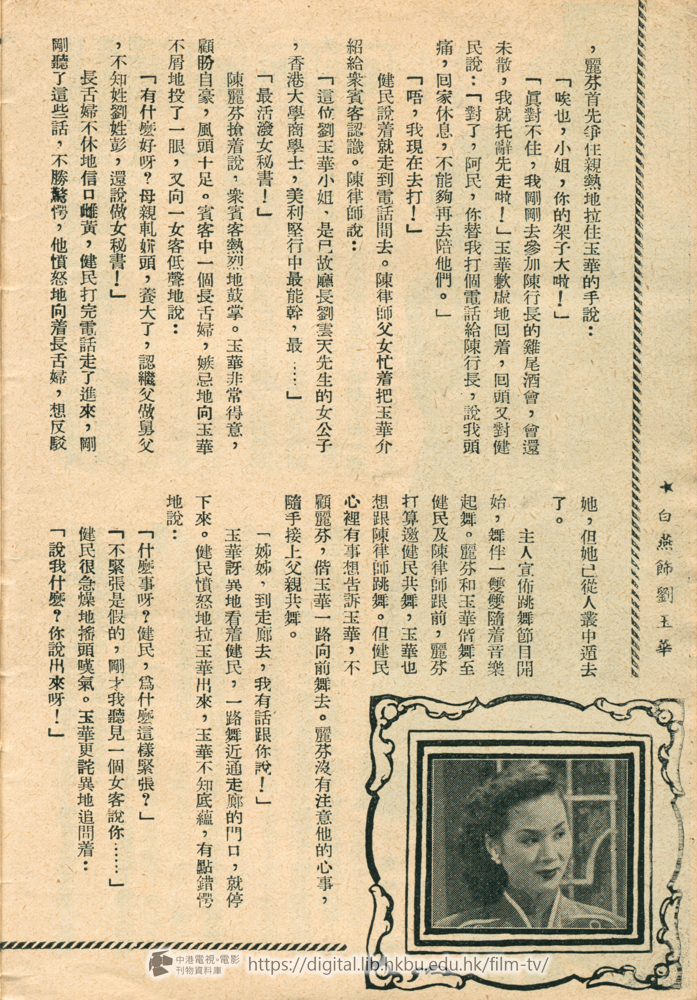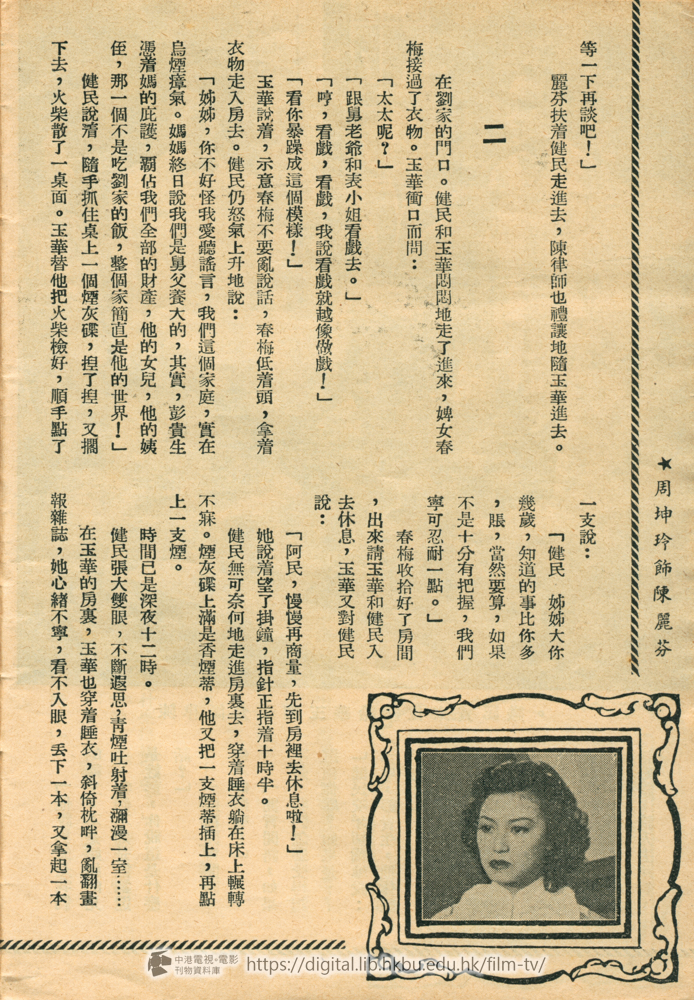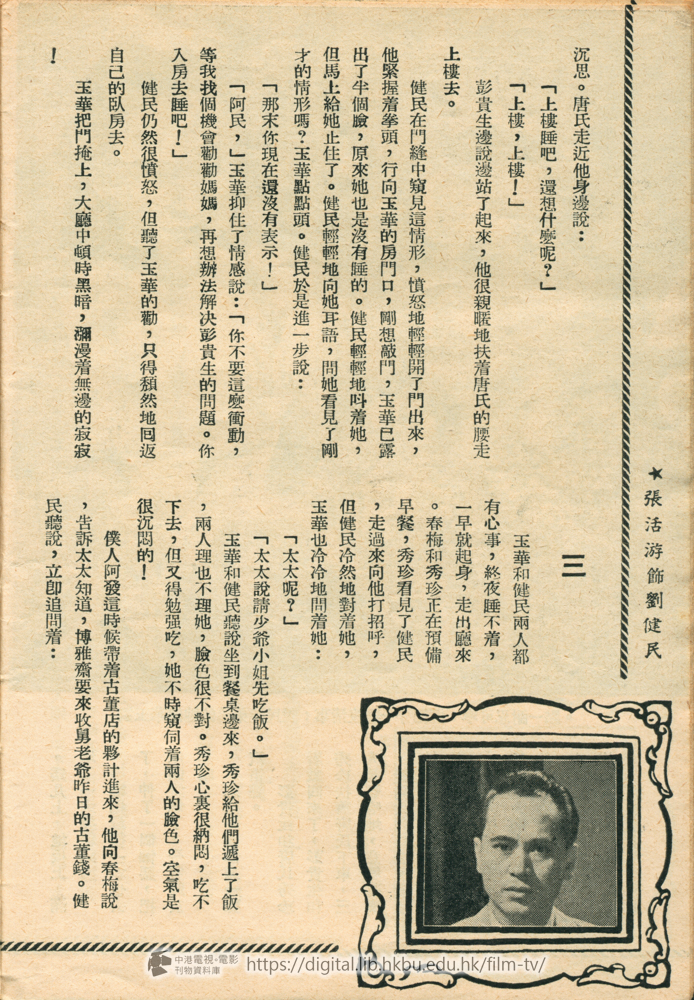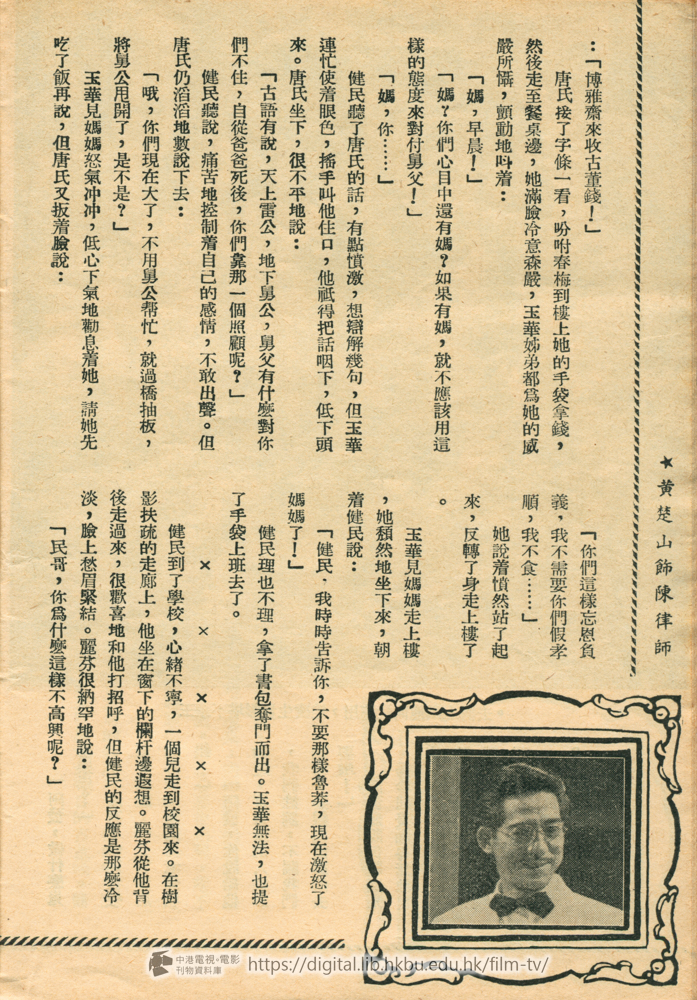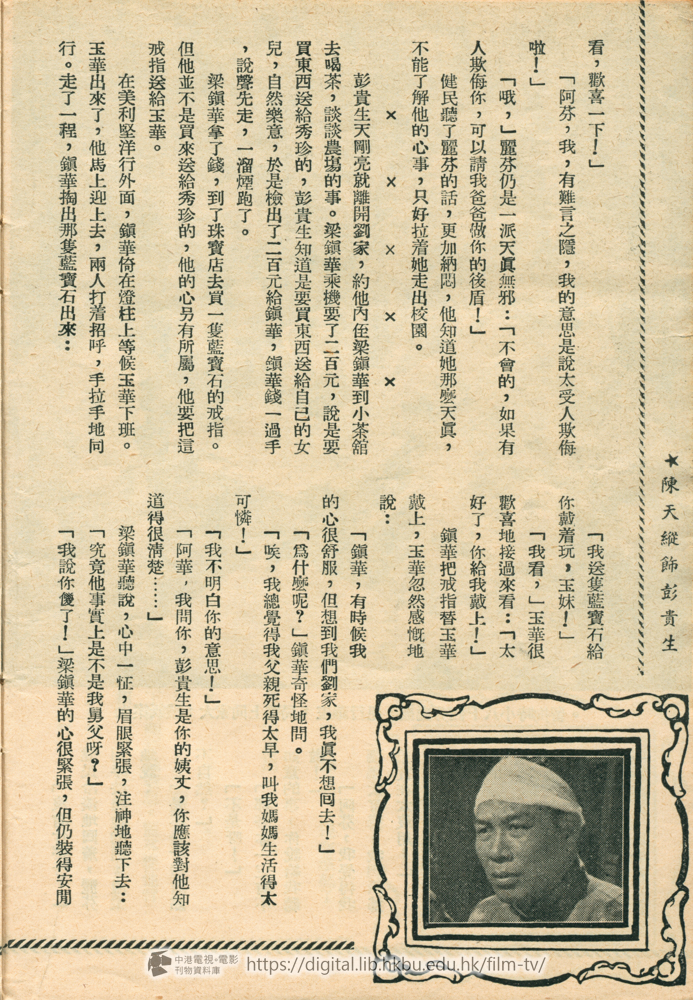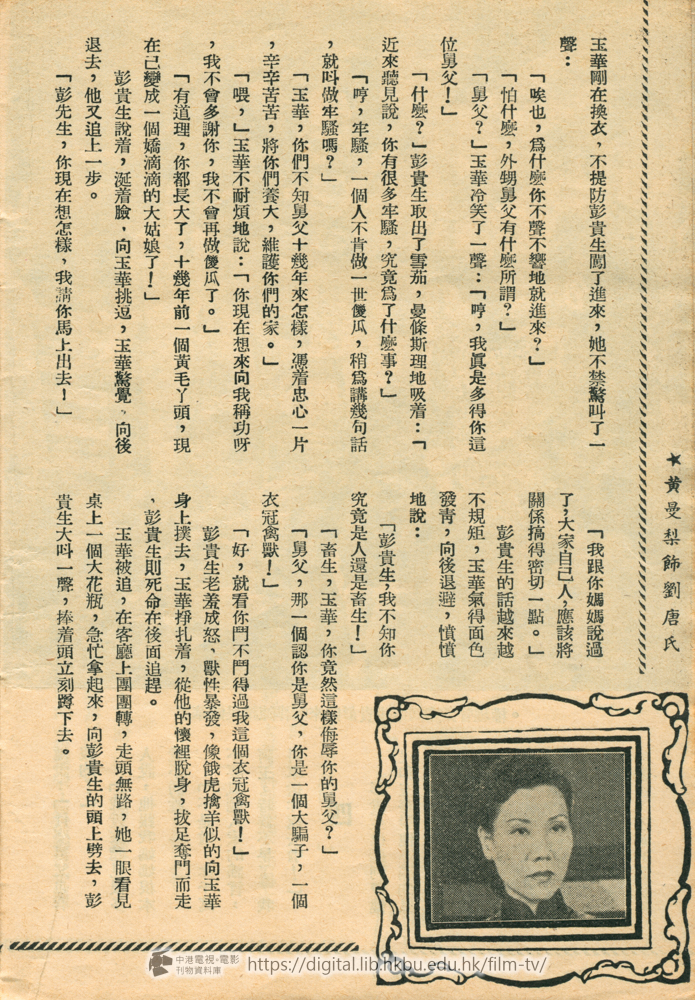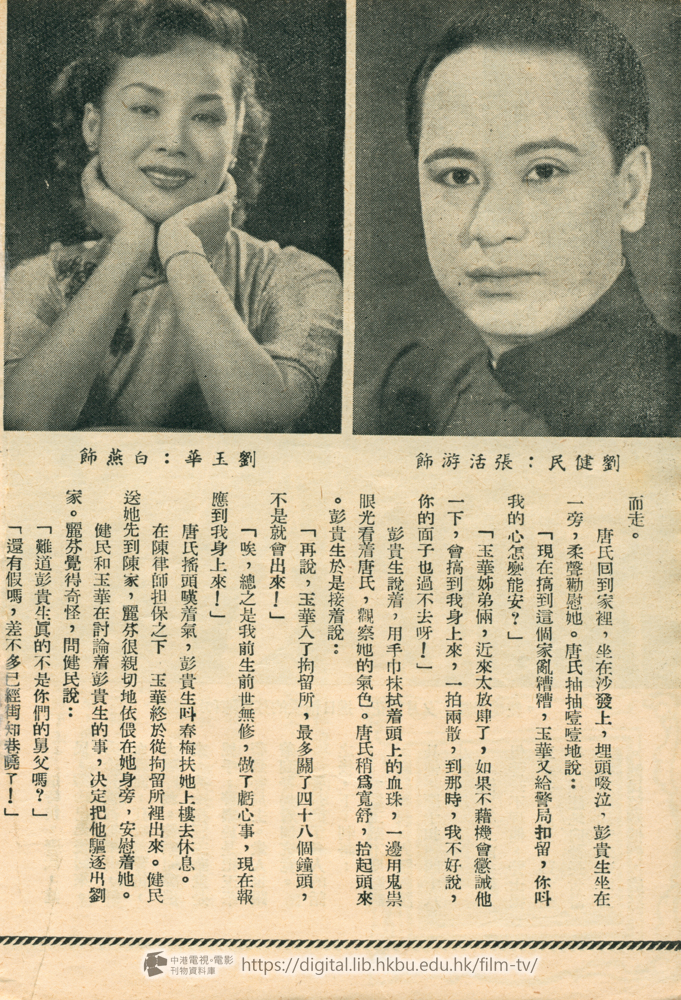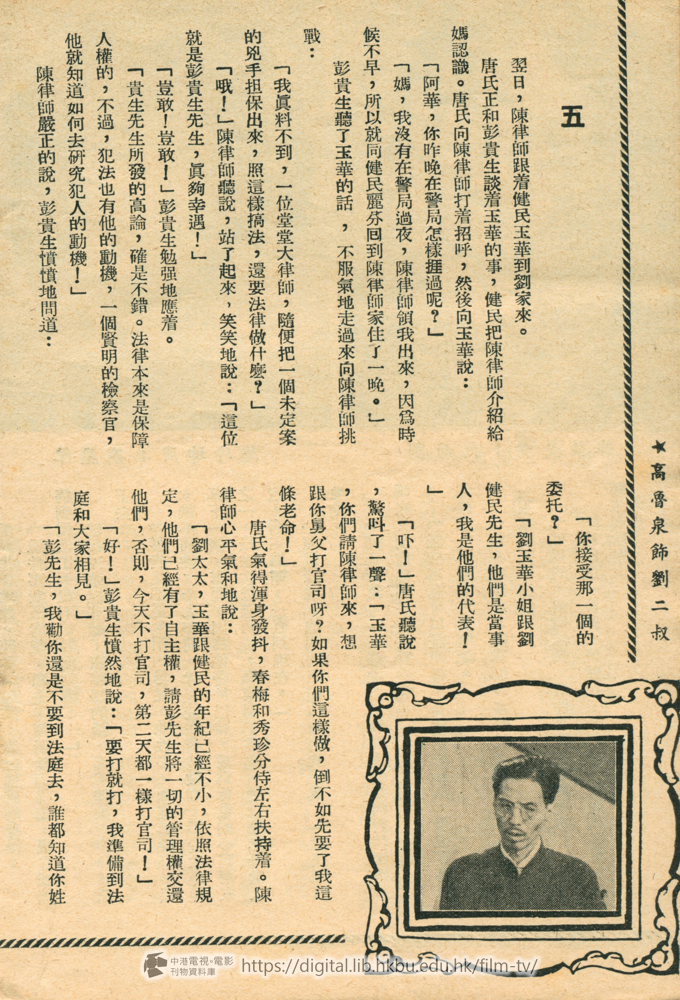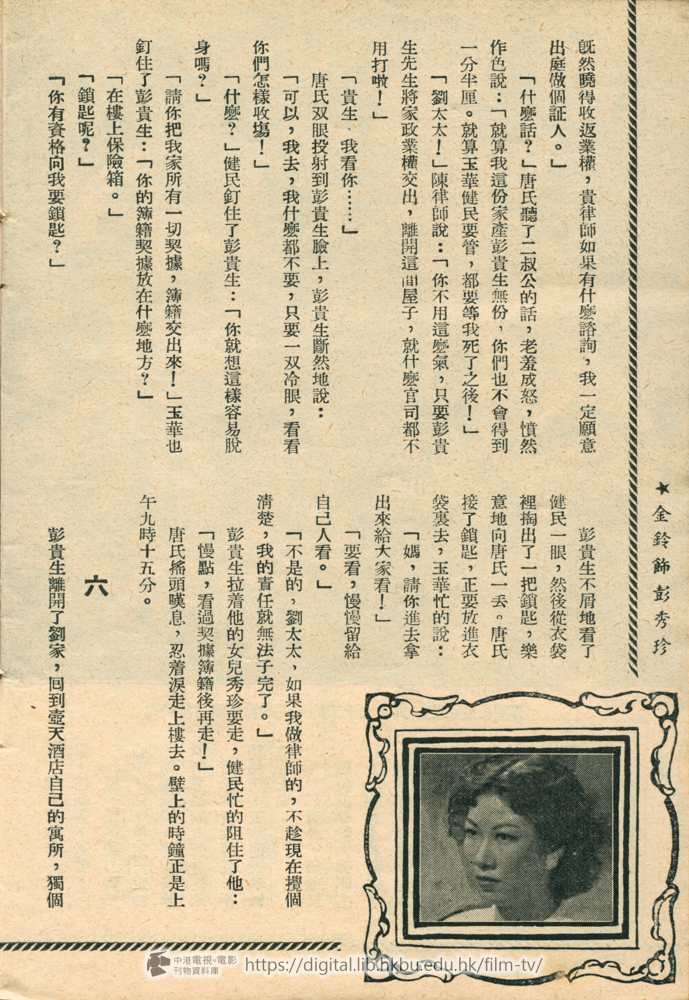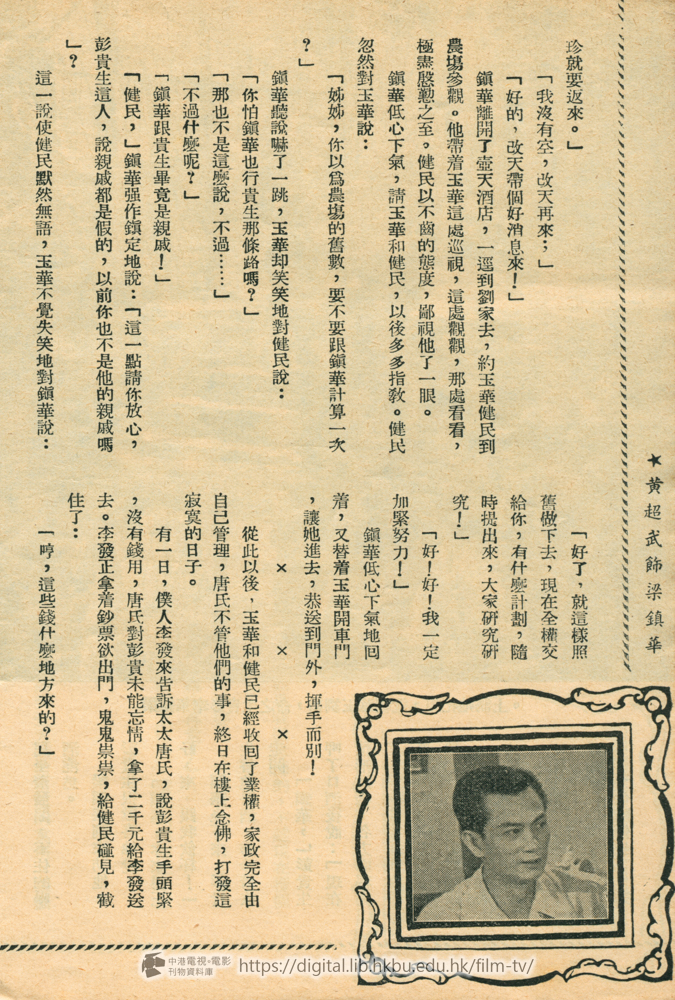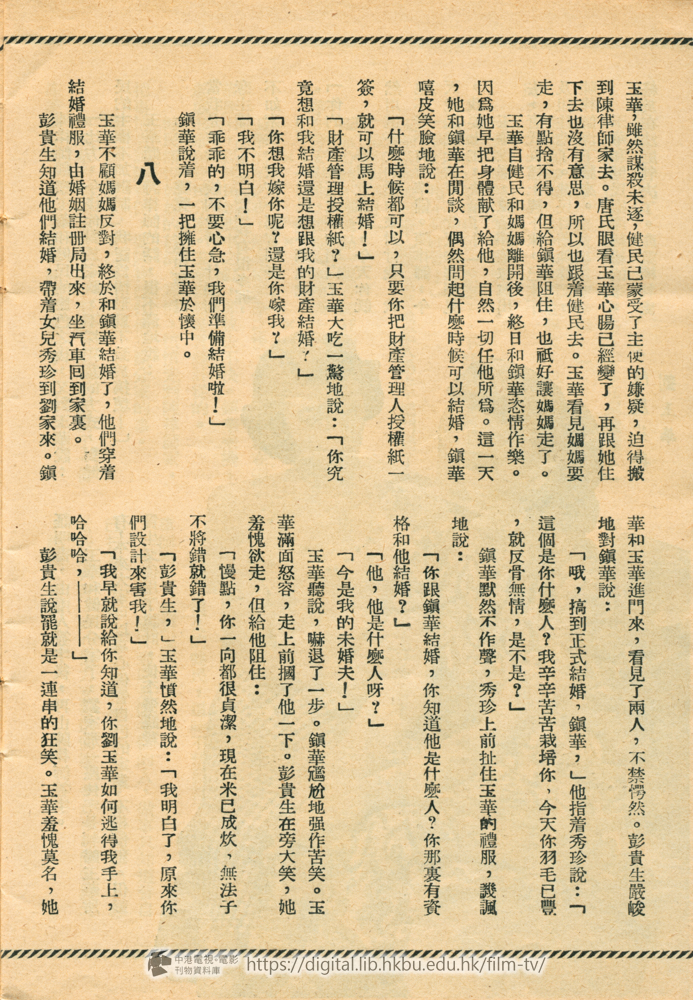綠窗紅淚
電影小說
海黛
這故事的開端,要追溯到十九年前。在廣州有一個舊官僚叫劉雲天的,做了很多年的廳長,刮了不少的錢,算是一個鉅富之家。他的太太唐氏,生得很漂亮,膝下有一雙男女,家庭生活是很美滿的。但當他正想退休,息影家園的那年,忽然得了急病死了。
太太唐氏正當盛年,一旦死了丈夫,自然感到很悲痛。雖然丈夫遺下了一筆很大的產業,生活可以無憂,而且膝下有了女兒玉華和兒子健民,可以慰她的寂寞。但是,她正當花信年華,日子一久,難免感到枕冷衾寒,苦悶難耐。
劉廳長有一個幕僚叫彭貴生,人很狡獪,他看淸廳長太太唐氏的心事,早已存了野心。機會到了,他乘虛而入,對唐氏大獻慇懃。唐氏的心,果然給他挑動,不自禁地做了他的情俘,和他一同移居到香港來。他們爲了遮掩人們的耳目,唐氏明裡說是彭貴生的胞妹,暗裡則做他的姘婦。彭貴生就這樣以舅老爺的身份,掌握了劉家的家政,又把他的姨侄黃鎭華帶領進來,管轄着一家大農塲。
時日飛快,倏忽過了十九年唐氏一直信任着彭貴生。彭貴生也一直對唐氏鞠躬盡瘁。但時光舐去了唐氏的艶色,她由少女變成了半老徐娘。她怕彭貴生會厭棄她,所以凡彭貴生所愛的,她都順從他,無論起居飮食,古董玩物,她都盡力羅置,務必使他稱心滿意。
現在玉華和健民都長大了,玉華畢業了大學之後,在美利堅洋行當高級秘書。健民則還在肄業中,而且和女同學陳麗芬在談戀愛。姊弟倆都有一個美麗的遠景,但都不知道母親有一個不可吿人的秘密。
一
劉健民終日沉醉在他的綺夢中。
今天是陳麗芬小姐的生日,健民一早就到陳家來向她祝賀。陳律師擁着愛女麗芬在衆賓客中間,麗芬倚着健民作媚笑,幸福的熱流在她倆的心裡交流。
陳麗芬走到了圓桌邊,在大蛋糕上吹滅了蠟燭,用一柄小刀切餅。許多賓客請求她唱一支歌,她看見健民首先鼓掌,立卽微笑地答應,展着珠喉漫歌。
陳律師向外面張望,看一看手錶,然後靠近了健民的耳旁說:
「令姊怎麽還沒有來?」
「她這兩日美國總行的經理來了,應酬多,大槪差不多要來了。」
健民低聲的囘答着陳律師。
麗芬一曲唱完,賓客狂熱地鼓掌,歡聲充滿了大客廳。劉玉華盛裝匆匆從外面走進來。陳律師父女和健民爭迎上去,麗芬首先爭住親熱地拉住玉華的手說:
「唉也,小姐,你的架子大啦!」
「眞對不住,我剛剛去參加陳行長的雞尾酒會,會還未散,我就托辭先走啦!」玉華歉虛地囘着,囘頭又對健民說:「對了,阿民,你替我打個電話給陳行長,說我頭痛,囘家休息,不能夠再去陪他們。」
「唔,我現在去打!」
健民說着就走到電話間去。陳律師父女忙着把玉華介紹給衆賓客認識。陳律師說:
「這位劉玉華小姐,是已故廳長劉雲天先生的女公子。香港大學商學士,美利堅行中最能幹,最……」
「最活潑女秘書!」
陳麗芬搶着說,衆賓客熱烈地鼓掌。玉華非常得意,顧盼自豪,風頭十足。賓客中一個長舌婦,嫉忌地向玉華不屑地投了一眼,又向一女客低聲地說:
「有什麽好呀?母親軋姘頭,養大了,認繼父做舅父,不知姓劉姓彭,還說做女秘書!」
長舌婦不休地信口雌黃,健民打完電話走了進來,剛剛聽了這些話,不勝驚愕,他憤怒地向着長舌婦,想反駁她,但她已從人叢中遁去了。
主人宣佈跳舞節目開始,舞伴一雙雙隨着音樂起舞。麗芬和玉華偕舞至健民及陳律師跟前,麗芬打算邀健民共舞,玉華也想跟陳律師跳舞。但健民心裡有事想吿訴玉華,不顧麗芬,偕玉華一路向前舞去。麗芬沒有注意他的心事。隨手接上父親共舞。
「姊姊,到走廊去,我有話跟你說!」
玉華訝異地看着健民,一路舞近通走廊的門口,就停下來。健民憤怒地拉玉華出來,玉華不知底蘊,有點錯愕地說:
「什麽事呀?健民,爲什麽這樣緊張?」
「不緊張是假的,剛才我聽見一個女客說你……」
健民很急燥地搖頭嘆氣。玉華更詫異地追問着:
「說我什麽?你說出來呀!」
「他說舅父是我們的繼父,不是媽媽的兄弟,我們不知是姓劉還是姓彭,你說這是什麽話?」
「這種閒言閒語,你不好聽啦!」
「閒言閒語,如果不是,我們怎麽受得起這種侮辱?如果是……」健民咬牙切齒地說:「哼,彭貴生,他休想活命!」
「阿民,你無謂胡思亂想,快的進去跳舞啦!」
健民還要說下去,陳麗芬和陳律師已走出來:
「你們姊弟有什麽話好談,請入去跳舞,等一下再談吧!」
麗芬扶着健民走進去,陳律師也禮讓地隨玉華進去。
二
在劉家的門口。健民和玉華悶悶地走了進來,婢女春梅接過了衣物。玉華衝口而問:
「太太呢?」
「跟舅老爺和表小姐看戲去。」
「哼,看戲,看戲,我說看戲就越像做戲!」
「看你暴躁成這個模樣!」
玉華說着,示意春梅不要亂說話,春梅低着頭,拿着衣物走入房去。健民仍怒氣上升地說:
「姊姊,你不好怪我愛聽謠言,我們這個家庭,實在烏煙瘴氣。媽媽終日說我們是舅父養大的,其實,彭貴生憑着媽的庇護,覇佔我們全部的財產,他的女兒,他的姨侄,那一個不是吃劉家的飯,整個家簡直是他的世界!」
健民說着,隨手抓住桌上一個煙灰碟,揑了揑,又擱下去,火柴散了一桌面。玉華替他把火柴檢好,順手點了一支說:
「健民,姊姊大你幾歲,知道的事比你多,賬,當然要算,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我們寧可忍耐一點。」
春梅收拾好了房間,出來請玉華和健民入去休息,玉華又對健民說:
「阿民,慢慢再商量,先到房裡去休息啦!」
她說着望了掛鐘,指針正指着十時半。
健民無可奈何地走進房裏去,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輾轉不寐。煙灰標上滿是香煙蒂,他又把一支煙蒂插上,再點上一支煙。
時間已是深夜十二時。
健民張大雙眼,不斷遐思,靑煙吐射着,瀰漫一室……
在玉華的房裏,玉華也穿着睡衣,斜倚枕畔,亂翻畫報雜誌,她心緖不寧,看不入眼,丟下一本,又拿起一本。矮几上,地板上,滿堆了一大叠雜誌。
她把最後一本也丢了,伸了一個懶腰,把床一頭燈熄了,全室歸於黑暗……
忽然外面傳來一聲汽笛聲。
彭貴生和唐氏秀珍看戲囘來了,彭貴生和秀珍扶着唐氏下車,三人笑哈哈地,意興甚樂,走向大門口去,貴生按了門鈴,屋裏的電燈亮了,春梅出來開門。
三人依然嘻笑不禁地走進大廳來。唐氏問春梅,知道玉華和健民去睡覺了,吩咐秀珍春梅也去睡。
彭貴生坐在沙發上沉思。唐氏走近他身邊說:
「上樓睡吧,還想什麽呢?」
「上樓,上樓!」
彭貴生邊說邊站了起來,他很親暱地扶着唐氏的腰走上樓去。
健民在門縫中窺見這情形,憤怒地輕輕開了門出來,他緊握着拳頭,行向玉華的房門口,剛想敲門,玉華已露出了半個臉,原來她也是沒有睡的。健民輕輕地呌着她,但馬上給她止住了。健民輕輕地向她耳語,問她看見了剛才的情形嗎?玉華點點頭。健民於是進一步說:
「那末你現在還沒有表示!」
「阿民,」玉華抑住了情感說:「你不要這麽衝動,等我找個機會勸勸媽媽,再想辦法解决彭貴生的問題。你入房去睡吧!」
健民仍然很憤怒,但聽了玉華的勸,只得頹然地囘返自己的臥房去。
玉華把門掩上,大廳中頓時黑暗,瀰漫着無邊的寂寂!
三
玉華和健民兩人都有心事,終夜睡不着,一早就起身,走出廳來。春梅和秀珍正在預備早餐,秀珍看見了健民,走過來向他打招呼,但健民冷然地對着她,玉華也冷冷地問着她:
「太太呢?」
「太太說請少爺小姐先吃飯。」
玉華和健民聽說坐到餐桌邊來,秀珍給他們遞上了飯,兩人理也不理她,臉色很不對。秀珍心裏很納悶,吃不下去,但又得勉强吃,她不時窺伺着兩人的臉色。空氣是很沉悶的!
僕人阿發這時候帶着古董店的夥計進來,他向春梅說,吿訴太太知道,博雅齋要來收舅老爺昨日的古董錢。健民聽說,立卽追問着:
「阿發,做什麼鬼鬼祟祟?」
「沒有!」阿發裝着笑臉說:「是古董店的夥計,來向舅老爺收銀!」
「阿發,你說給他知道,買古董的人姓彭,我們姓劉,不關我們的事,要銀向姓彭的去要啦!」
阿發聽說仍疇躇着,秀珍則羞慟得無地自容,幾乎哭出聲來。這時候,唐氏剛下樓來,聽了健民的話,不悅地問道:
「什麽事這樣嘈呀?」
「哦!太太!」李發忙把字條遞給唐氏說:「博雅齋來收古董錢!」
唐氏接了字條一看,吩咐春梅到樓上她的手袋拿錢,然後走至餐桌邊,她滿臉冷意森嚴,玉華姊弟都爲她的威嚴所懾,顫動地呌着:
「媽,早晨!」
「媽?你們心目中還有媽?如果有媽,就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來對付舅父!」
「媽,你……」
健民聽了唐氏的話有點憤激,想辯解幾句,但玉華連忙使着眼色,搖手叫他住口,他祗得把話咽下,低下頭來。唐氏坐下,很不平地說:
「古語有說,天上雷公,地下舅公,舅父有什麽對你們不住,自從爸爸死後,你們靠那一個照顧呢?」
健民聽說,痛苦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敢出聲。但唐氏仍滔滔地數說下去:
「哦,你們現在大了,不用舅公帮忙,就過橋抽板,將舅公甩開了,是不是?」
玉華見媽媽怒氣冲冲,低心下氣地勸息着她,請她先吃了飯再說,但唐氏又扳着臉說:
「你們這樣忘恩負義,我不需要你們假孝順,我不食……」
她說着憤然站了起來,反轉了身走上樓了。
玉華見媽媽走上樓,她頹然地坐下來,朝着健民說:
「健民,我時時吿訴你,不要那樣魯莽,現在激怒了媽媽了!」
健民理也不理,拿了書包奪門而出。玉華無法,也提了手袋上班去了。
X X X X X
健民到了學校,心緖不寧,一個兒走到校園來。在樹影扶疏的走廊上,他坐在窗下的欄杆邊遐想。麗芬從他背後走過來,很歡喜地和他打招呼,但健民的反應是那麼冷淡,臉上愁眉緊結。麗芬很納罕地說:
「民哥,你爲什麽這樣不高興呢?」
「沒有什麽呀!」健民冷淡地囘着,麗芬用手按撫他的頭,溫柔地說:
「是不是身體有點不自然?」
「不是呀!」
「那麽你一定有不如意的事,你說給我聽啦!」
「阿芬,我覺得我媽媽太可憐,我們倆姊弟實在太沒用!」
「原來你是爲了這件事,」麗芬誤會了健民的意思,她不禁失笑地說:「你眞是個孝子賢孫,何必這樣躁急呢?你就快大學畢業了,將來總可以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給老人家看看,歡喜一下!」
「阿芬,我,有難言之隱,我的意思是說太受人欺侮啦!」
「哦,」麗芬仍是一派天眞無邪:「不會的,如果有人欺侮你,可以請我爸爸做你的後盾!」
健民聽了麗芬的話,更加納悶,他知道她那麼天眞,不能了解他的心事,只好拉着她走出校園。
X X X X X
彭貴生天剛亮就離開劉家,約他內侄梁鎭華到小茶舘去喝茶,談談農塲的事。梁鎭華乘機要了二百元,說是要買東西送給秀珍的,彭貴生知道是要買東西送給自己的女兒,自然樂意,於是檢出了二百元給鎭華,鎭華錢一過手,說聲先走,一溜煙跑了。
梁鎭華拿了錢,到了珠寶店去買一隻藍寶石的戒指。但他並不是買來送給秀珍的,他的心另有所屬,他要把這戒指送給玉華。
在美利堅洋行外面,鎭華倚在燈柱上等候玉華下班。玉華出來了,他馬上迎上去,兩人打着招呼,手拉手地同行。走了一程,鎭華掏出那隻藍寶石出來:
「我送隻藍寶石給你戴着玩,玉妹!」
「我看,」玉華很歡喜地接過來看:「太好了,你給我戴上!」
鎭華把戒指替玉華戴上,玉華忽然感慨地說:
「鎭華,有時候我的心很舒服,但想到我們劉家,我眞不想囘去!」
「爲什麼呢?」鎭華奇怪地問。
「唉,我總覺得我父親死得太早,叫我媽媽生活得太可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華,我問你彭貴生是你的姨丈,你應該對他知道得很淸楚……」
梁鎭華聽說,心中一怔,眉眼緊張,注神地聽下去:
「究竟他事實上是不是我舅父呀?」
「我說你傻了!」梁鎭華的心很緊張,但仍裝得安閒地說:「什麽舅父也有假的!」
「我近來聽見很多人說,他跟我媽媽根本就不同姓。」
「不是啦,你千萬不要亂聽人家的謠言,阿玉,時候不早了,我叫車送你返去啦!」
四
彭貴生已聽到了健民和玉華對他不滿的風聲,他滿懷鬼計,想把玉華也吊上,以遂他霸產的陰謀。他一面買囑李發爲心腹,暗通消息,一面藉機去親近玉華。
這一日,他乘唐氏和健民外出未囘,偷偷地潛進了玉華的臥房。玉華剛在換衣,不提防彭貴生闖了進來,她不禁驚叫了一聲:
「唉也,爲什麼你不聲不響地就進來?」
「怕什麼,外甥舅父有什麽所謂?」
「舅父?」玉華冷笑了 一聲:「哼,我眞是多得你這位舅父!」
「什麼?」彭貴生取出了雪茄,曼條斯理地吸着:「近來聽見說,你有很多牢騷,究竟爲了什麼事?」
「哼,牢騷,一個人不肯做一世傻瓜,稍爲講幾句話,就呌做牢騷嗎?」
「玉華,你們不知舅父十幾年來怎樣,憑着忠心一片,辛辛苦苦,將你們養大,維護你們的家。」
「喂,」玉華不耐煩地說:「你現在想來向我稱功呀,我不會多謝你,我不會再做傻瓜了。」
「有道理,你都長大了,十幾年前一個黃毛丫頭,現在已變成一個嬌滴滴的大姑娘了!」
彭貴生說着,涎着臉,向玉華挑逗,玉華驚覺,向後退去,他又追上一步。
「彭先生,你現在想怎樣,我請你馬上出去!」
「我跟你媽媽說過了,大家自己人,應該將關係搞得密切一點。」
彭貴生的話越來越不規矩,玉華氣得面色發靑,向後退避,憤憤地說:
「彭貴生,我不知你究竟是人還是畜生!」
「畜生,玉華,你竟然這樣侮辱你的舅父?」
「舅父,那一個認你是舅父,你是一個大騙子,一個衣冠禽獸!」
「好,就看你鬥不鬥得過我這個衣冠禽獸!」
彭貴生老羞成怒,獸性暴發,像餓虎擒羊似的向玉華身上撲去,玉華掙扎着,從他的懷裡脫身,拔足奪門而走,彭貴生則死命在後面追趕。
玉華被追,在客廳上團團轉,走頭無路,她一眼看見桌上一個大花瓶,急忙拿起來,向彭貴生的頭上劈去,彭貴生大呌一聲,捧着頭立刻蹲下去。
這時候,唐氏,健民,秀珍巳先後囘來。秀珍見爸爸被擊傷,鮮血滿面,狂吹着警笛,大聲呼救。警察聞聲進來,秀珍指証玉華就是兇手,警察於是把玉華帶到警局去。衆人也跟着到警局看個究竟。
警長問了各人的話之後,下了判語:
「劉玉華不服敎訓,毆辱尊長,人証物証具備,應予扣押四十八小時,以示懲誡。」
健民欲上前抗辯,但警長不理他,警士把玉華拉了出去。彭貴生卑躬屈膝地向警長告辭,扶着唐氏和秀珍囘去。健民望着他們,盛怒而走。
唐氏囘到家裡坐在沙發上,埋頭啜泣,彭貴生坐在一旁,柔聲勸慰她。唐氏抽抽噎噎地說:
「現在稿到這個家亂糟糟,玉華又給警局扣留,你呌我的心怎麼能安?」
「玉華姊弟倆,近來太放肆了,如果不藉機會懲誡他一下,會搞到我身上來,一拍兩散,到那時,我不好說,你的面子也過不去呀!」
彭貴生說着,用手巾抹拭着頭上的血珠,一邊用鬼祟眼光看着唐氏,觀察她的氣色。唐氏稍爲寬舒抬起頭來。彭貴生於是接着說:
「再說,玉華入了拘留所,最多關了四十八個鐘頭,不是就會出來!」
「唉,總之是我前生前世無修,做了虧心事,現在報應到我身上來!」
唐氏搖頭嘆着氣,彭貴生呌春梅扶她上樓去休息。
在陳律師担保之下,玉華終於從拘留所裡出來。健民送她先到陳家,麗芬很親切地依偎在她身旁,安慰着她。
健民和玉華在討論着彭貴生的事,决定把他驅逐出劉家。麗芬覺得奇怪,問健民說:
「難道彭貴生眞的不是你們的舅父嗎?」
「還有假嗎,差不多已經街知巷曉了!」
健民憤憤地說。陳律師起來,走近他們的身邊:
「這件事我很淸楚,過去不便對你們提起,現在旣然搞到這樣子,我不妨對你們講……」
健民玉華麗芬聽了陳律師的話,都不禁集中精神傾聽下去:
「彭貴生不是你們的舅父,他姓彭,你媽媽姓唐,根本就不同姓,十九年前,你爸爸在省城做官,彭貴生是他幕下一個小幫閒,因爲他善於巴結,成爲你爸的心腹朋友之一,後來你爸爸死了,舉家到了香港,他就公然升堂入室,稱王稱霸,一直到現在。」
「照這樣說,他明明想覇佔我們的產業。」健民恍然地說。
「何止產業,」玉華說:「你知道他如何對待媽媽,現在又預備什麼手段來對待我。」
「旣然事實可以証明他不是你們的舅父,就很容易把他趕走。」麗芬天眞地說。
「現在我想請求陳律師多多幫忙,把這件事搞淸楚。」玉華向陳律師說。
「可以的,要這樣做,這件事我是應該做的!」
陳律師這一答應,使健民玉華和麗芬都面露喜氣,相顧共表欣慰!
五
翌日,陳律師跟着健民玉華到劉家來。
唐氏正和彭貴生談着玉華的事,健民把陳律師介紹給媽認識。唐氏向陳律師打着招呼,然後向玉華說:
「阿華,你昨晚在警局怎樣捱過呢?」
「媽我沒有在警局過夜,陳律師領我出來,因爲時候不早,所以就同健民麗芬囘到陳律師家住了一晚。」
彭貴生聽了玉華的話,不服氣地走過來向陳律師挑戰:
「我眞料不到,一位堂堂大律師,隨便把一個未定案的兇手担保出來,照這樣搞法,還要法律做什麽?」
「哦!」陳律師聽說,站了起來,笑笑地說:「這位就是彭貴生先生,眞夠幸遇!」
「豈敢!豈敢!」彭貴生勉强地應着。
「貴生先生所發的高論,確是不錯。法律本來是保障人權的,不過,犯法也有他的動機,一個賢明的檢察官,他就知道如何去硏究犯人的動機!」
陳律師嚴正的說,彭貴生憤憤地問道:
「你接受那一個的委托?」
「劉玉華小姐跟劉健民先生,他們是當事人,我是他們的代表!」
「吓!」唐氏聽說,驚叫了一聲:「玉華,你們請陳律師來,想跟你舅父打官司呀?如果你們這樣做,倒不如先要了我這條老命!」
唐氏氣得渾身發抖,春梅和秀珍分侍左右扶持着。陳律師心平氣和地說:
「劉太太,玉華跟健民的年紀已經不小,依照法律規定,他們已經有了自主權,請彭先生將一切的管理權交還他們,否則,今天不打官司,第二天都一樣打官司!」
「好!」彭貴生憤然地說:「要打就打,我準備到法庭和大家相見。」
「彭先生,我勸你還是不要到法庭去,誰都知道你姓彭,劉太太姓唐,這一點,已經落下風啦!」
這一說,使彭貴生心中一怔,他定一定神,仍想狡辯,劉家長輩叔卿惠德兩人忽忽進來,唐氏和貴生看見,不禁愕然,玉華則很歡喜地迎上去:
「二叔公,三伯父,這位就是陳大律師。」
「兩位來得正好,」陳律師向兩位長輩說:「關於這件事,兩位必定知道淸楚?」
「不錯,玉華他們姊弟倆,是我親眼看大的,他父親死後,家權落在外手之手,坊里閒言,我們一向不便過問。現在他姊弟長大了,旣然曉得收返業權,貴律師如果有什麽諮詢,我一定願意出庭做個証人。」
「什麽話?」唐氏聽了二叔公的話,老羞成怒,憤然作色說:「就算我這份家產彭貴生無份,你們也不會得到一分半厘。就算玉華健民要管,都要等我死了之後!」
「劉太太!」陳律師說:「你不用這麼氣,只要彭貴生先生將家政業權交出,離開這間屋子,就什麽官司都不用打啦!」
「貴生,我看你……」
唐氏双眼投射到彭貴生臉上,彭貴生斷然地說:
「可以,我去,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一双冷眼,看看你們怎樣收塲!」
「什麽?」健民釘住了彭貴生:「你就想這樣容易脫身嗎?」
「請你把我家所有一切契據,簿籍交出來!」玉華也釘住了彭貴生:「你的簿籍契據放在什麽地方?」
「在樓上保險箱。」
「鎖匙呢?」
「你有資格向我要鎖匙?」
彭貴生不屑地看了健民一眼,然後從衣袋裡掏出了一把鎖匙,樂意地向唐氏一丢。唐氏接了鎖匙,正要放進衣袋裏去,玉華忙的說:
「媽,請你進去拿出來給大家看!」
「要看,慢慢留給自己人看。」
「不是的,劉太太,如果我做律師的,不趁現在攪個淸楚,我的責任就無法子完了。」
彭貴生拉着他的女兒秀珍要走,健民忙的阻住了他:
「慢點,看過契據簿籍後再走!」
唐氏搖頭嘆息,忍着淚走上樓去。壁上的時鐘正是上午九時十五分。
六
彭貴生離開了劉家,囘到壺天酒店自己的寓所,獨個兒坐着發悶,不住的喝酒澆愁。
梁鎭華到來訪他,彭貴生很歡喜地說:
「鎭華,你來得正好,來,跟我飮杯!」
鎭華坐下來,彭貴生替他斟酒,秀珍借故走開。
「鎭華,」彭貴生呷了口酒後說:「現在情形這樣,各方面都完了,只有農塲還在你手裏,你可以一方面離間他們姊弟,一方面刮錢,否則我站不住,你將來做女婿的也沒有意思。」
「知道的!」鎭華唯命是從的說。
「你隨便坐下,秀珍就要返來。」
「我沒有空,改天再來;」
「好的,改天帶個好消息來!」
鎭華離開了壺天酒店,一逕到劉家去,約玉華健民到農塲參觀。他帶着玉華這處巡視,這處觀觀,那處看看,極盡慇懃之至。健民以不齒的態度,鄙視他了一眼。
鎭華低心下氣,請玉華和健民,以後多多指敎。健民忽然對玉華說:
「姊姊,你以爲農塲的舊數,要不要跟鎭華計算一次?」
鎭華聽說嚇了一跳,玉華却笑笑地對健民說:
「你怕鎭華也行貴生那條路嗎?」
「那也不是這麽說,不過……」
「不過什麼呢?」
「鎭華跟貴生畢竟是親戚!」
「健民,」鎭華强作鎭定地說:「這一點請你放心,彭貴生這人,說親戚都是假的,以前你也不是他的親戚嗎」?
這一說使健民默然無語,玉華不覺失笑地對鎭華說:
「好了,就這樣照舊做下去,現在全權交給你,有什麽計劃,隨時提出來,大家硏究硏究!」
「好!好!我一定加緊努力!」
鎭華低心下氣地囘着,又替着玉華開車門,讓她進去,恭送到門外,揮手而別!
X X X
從此以後,玉華和健民已經收囘了業權,家政完全由自己管理,唐氏不管他們的事,終日在樓上念佛,打發這寂寞的日子。
有一日,僕人李發來吿訴太太唐氏,說彭貴生手頭緊,沒有錢用,唐氏對彭貴未能忘情,拿了二千元給李發送去。李發正拿着鈔票欲出門,鬼鬼祟祟,給健民碰見,截住了:
「哼,這些錢什麽地方來的?」
「唏,少爺,你不要吵,這兩千元是太太叫我送給舅老爺的!」
「哦,你交給我就可以。」
「少爺,你想留這錢我不反對,不過你要想個辦法,給我交差才對!」
健民聽說,走至桌前,抽筆寫了張假收條給李發,然後警吿他,不能夠洩漏秘密。
李發接了收條,茫然不知所措。
健民高興萬分,向門外飛奔而去。
鎭華和玉華双双地囘來,剛踏入門,看見李發鬼鬼祟祟的態度,不禁生疑。鎭華問李發究竟爲了什麽事,李發把剛才太太送二千元給彭貴生,半路給健民截脏的事吿訴他。
他們的話說得太小聲,玉華聽不淸楚,緊問着鎭華說:
「什麽事?半路截脏呀?鎭華,不要吞呑吐吐,有話說出來大家知道!」
「沒有,今天你媽送二千元叫李發拿去給我姨丈,健民知道,把那筆錢扣留了,他應該說給你知道!」
「哦,」玉華驚訝地說:「有這件事,他說一聲都沒有,豈有此理?」
鎭華看見玉華生氣,認爲是一個好機會,馬上火上添油地說:
「二千元還是小事,最怕搞到連大事都瞞你就糟!」
玉華心裏有點懷疑,沉思間,樓上有唐氏的咳嗽聲,快要下樓了。鎭華乘機引退,他握着玉華的手說:
「我有事先走,你不好難爲健民,或者有其他的事,不便給你知道的苦衷,你原諒他啦!」
鎭華離開玉華,馬上到壺天酒店去找彭貴生,把唐氏送給他二千元被健民截去吿訴貴生的事。彭貴生聽說,幾乎氣破了肺,他憤然地說:
「想不到這衰仔猖狂到這個地步!眞把我氣煞了!」
「我以爲仍舊在玉華身上弄好法子,等我看風色敎唆玉華,把他的家產接收過來,如果
大權落在玉華手上,我運用兩度散手,等他兩姊弟不和,那時候我們就得從心所欲了!」
鎭華這一妙計,說得彭貴生轉怒爲喜,他不禁拍手的說:
「唔,這個好辦法!」
鎭華辭別了彭貴生,看看錶,知道玉華下班的時候到了,他熟習地走那個馬路角站着等她,不提防有人在後面叫了他一聲:
「阿鎭,等我很久嗎?」
「哦,」鎭華發覺是玉華叫他,笑笑地說:「不很久!」
說着挽了玉華的臂,行出馬路中心。玉華只放着慢步,眉黛深鎖,好像有滿懷心事。鎭華假慇懃地問道:
「爲什麽你終日悶悶不樂呢?」
「不悶就是假啦!」
「你是不是爲了健民那件事,你傻了,你是大姊,有權當家,旣然健民這樣,你可以自己打算,向母親接管財權。如果不這樣做,辛辛苦苦爭奪囘來的產業,不久又會化爲烏有,你說是不是呢?」
「好啦,我們現在囘去再說!」
玉華囘到家裏來,走到健民的房裏去,健民正在几上玩撲克,她故作試探的口吻說:
「健民,我問你,媽媽昨日靜靜地叫李發拿二千元去給彭貴生,你知道嗎?」
「不知道,」健民故作鎭定地說:「眞不眞呀?」
「我相信沒有假的,你知道這件事要怎麽辨?」
「如果是眞的,我覺得媽太不應該了!」
「你以爲我們是否應該把財產管理權爭取過來?」
玉華故作進一步的試探。健民聽說,放下撲克,沉思一會反問說:
「你以爲這件事,是不是我們能夠做得到呢?」
「譬如爭得到,你要不要反對?」
「由你一個人去爭,爭到,由你一個人保管好嗎?」
「你沒有後悔?」
「一言爲定!」
健民斬釘截鐵的說,這正中了玉華的下懷。她馬上到媽媽的房裏去,把情形向媽媽透露,試探媽媽的口氣。唐氏自從家庭鬧了事之後,她的心都冷了,一心念佛,看財產看得很淡。旣然玉華提出要掌管財產,她一口答應了,落得做一個閒人。
玉華掌管了財產之後,大權在握,一切獨斷獨行,隨便花錢,一輛一萬三千元的新型汽車,也毫不吝嗇的買了。健民看她這種派頭,雖然不窩心,但有言在先,怎麽能夠向她多說一句話呢?
玉華買了新汽車,心裏很高興,馬上和梁鎭華通電話,把一天的消遣節目都編定了:下午淺水灣游泳,晚上麗都晚飯,然後試新車遊車河。
健民看她這麽得意忘形,忍耐不住,走近了電話邊說:
「姊姊,你不能一朝大權在手,就這樣揮霍無度怕一下子會傾家蕩產呀!而且你同鎭華在外面攪三攪四,人家會說你閒話的!」
「哼!」玉華鼻子裏嗤了一聲:「健民,你放心啦,你還沒有敎訓姊姊的資格,請冷靜點,找你的麗芬拍拖去吧!」
玉華說着,睬也不睬地拿着手袋走了。健民望着她的背影、感到憤恨,想不到姊姊變得這樣子了!
七
玉華和鎭華坐着新汽車,在山道上馳行。她倆一會兒双双浮沉在綠波上,競逐於沙灘上,一會兒盛裝出現在大餐廳上,酒杯互碰,杯中現出歡笑的幻影……
夜深了,鎭華扶着玉華囘來,玉華已經醉了,一顚一顚的,整身子東搖西幌,口裏說着醉話。鎮華勸她入房去睡,她乘機投入他懷裏,鎭華摟着她的腰肢,正欲乘時吻她,廳上的電燈忽然一亮,鎭華一驚鬆開,把玉華投到沙發上去。
健民己經出現在他倆的面前。
「梁鎭華,現在什麼時候,這裏是什麼塲合?我說你應該尊重你自己的人格!」
「我什麽地方不尊重人格,」鎭華老羞成怒地頂着健民:「你憑什麽資格管我?」
「我憑着這個家庭的主人資格,要你立刻就滾!」
「健民,你不要做得這樣無禮!」
鎭華圓睜着眼說,玉華看在眼裏,也不滿地責備健民:
「你這種態度算什麼呀?」
「我想爲劉家保留一點面子,不好丟得太淸!」
「我的事用不到你管!」
玉華嚴峻地囘着,健民憤然地走入房去,把門扃了。
「豈有此理!」
玉華心緖不寧地點一根香煙狂抽,煙霧瀰漫了滿室。華在旁安慰她,把她抱進房裏去…………
X X X
玉華酒醉之夜,献身給鎭華之後,一心一意都在鎭華身上,視健民如眼中之釘,非拔去不快。鎭華乘機慫恿玉華和健民分家。玉華自然是言聽計從的。
健民痛恨姊姊的放浪,專權,憤憤走到陳律師家,把事情吿訴陳律師,要陳律師代他主斷分家的事。
陳律師沉默了一會說:
「玉華的舉動確是不對,不過兩姊弟就爲了一份產業來反面,是不是要再詳細考慮一下?」
「陳伯伯!」健民說:「我的意志已堅决,我一定要這樣做,無論如何請求伯伯鼎力幫忙!」
陳律師聽了健民的話,終於答應下來,偕同健民到劉家來遇玉華。
玉華剛好整裝,要跟鎮華出去,健民叫她慢點出去。玉華看見陳律師,恍然地說:
「哦,原來是請了陳律師來,這樣,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預先對我先禮後兵啦!」
「玉華,你不好誤會!」陳律師說:「我雖然是受委托而來,但我的本意,是想勸你們和解,並非要對你用兵。」
「陳律師,我的姊弟之間,並沒有外人滲雜□財權家務,掌握在自己手裏,跟從前落在彭貴生手裏情形不同,旣無不和,何須行什麽和解呢?」
「你就以爲沒有什麼不和,始終獨行其是!」
沉默了很久的健民這時不禁發言了。但馬上給陳律師指住,他對玉華說:
「玉華,健民到底是個年輕的人,做事只知道替自己打算,不錯,這是他的弱點。不過。你做大姊的,應當共艱共苦,齊心協力支撑這個家,千萬不可同室操戈,讓漁人得利!」
陳律師觀察玉華和健民的瞼色之後,又對玉華說:
「比方,今後你對於家政,不採獨裁的方式,對健民的主權不加限制,我認爲情形就不致於搞壞!」 玉華聽了詩律師的話,很不滿地說:
「你口口聲聲,說要和解,但當我是被吿一般的看待,什麼剝奪主權,如果你認爲我有很多罪,不如索性大家打一塲官司呀!」
「哼!」健民也不滿地說:「你的用意難道還不夠明白?」
「什麼用意都好,今天你旣然用這麽大的壓力來對付我,我也不能不有所準備。陳律師,今天說話就此結束,改天法庭相見,我要上工,失陪了!」
玉華說罷,拉着鎭華匆匆出去,唐氏從樓上趕下來,已來不及阻住她了。健民目着陳律師,陳律師沉下臉來。
玉華和健民家產糾紛的事,終於在法庭判决了。產業權判處証明書,由兩人簽字後,再由陳律師簽字。
玉華和健民分家了,劉家那一座住宅是判歸玉華所有,本來大家可以專心保管自已的家業,不相侵犯。但彭貴生又使用了詭計,使李發謀殺玉華,雖然謀殺未逐,健民已蒙受了主使的嫌疑,迫得搬到陳律師家去。唐氏眼看玉華心腸已經變了,再跟她住下去也沒有意思,所以也跟着健民去。玉華看見媽媽要走有點捨不得,但給鎭華阻住,也祗好讓媽媽走了。
玉華自健民和媽媽離開後,終日和鎮華恣情作樂。因爲她早把身體献了給他,自然一切任他所爲。這一天,她和鎭華在閒談,偶然問起什麽時候可以結婚,鎭華嘻皮笑臉地說:
「什麽時候都可以?只要你把財產管理人授權紙一簽,就可以馬上結婚!」
「財產管理授權紙?」玉華大吃一驚地說:「你究竟想和我結婚還是想跟我的財產結婚?」
「你想我嫁你呢?還是你嫁我?」
「我不明白!」
「乖乖的,不要心急,我們準備結婚啦!」
鎭華說着,一把擁住玉華於懷中。
八
玉華不顧媽媽反對,終於和鎭華結婚了,他們穿着結婚禮服,由婚姻註册局出來,坐汽車囘到家裏。
彭貴生知道他們結婚,帶着女兒秀珍到劉家來。鎭華和玉華進門來,看見了兩人,不禁愕然。彭貴生嚴峻地對鎭華說:
「哦,搞到正式結婚,鎭華,」他指着秀珍說:「這個是你什麽人?我辛辛苦苦栽培你,今天你羽毛已豐,就反骨無情,是不是?」
鎭華默然不作聲,秀珍上前扯住玉華的禮服,譏諷地說:
「你跟鎭華結婚,你知道他是什麽人?你那裏有資格和他結婚?」
「他,他是什麽人呀?」
「今是我的未婚夫!」
玉華聽說,嚇退了一步。鎭華尷尬地强作苦笑。玉華滿面怒容,走上前摑了他一下。彭貴生在旁大笑,她羞愧欲走,但給他阻住:
「慢點,你一向都很貞潔,現在米巳成炊,無法子不將錯就錯了!」
「彭貴生,」玉華憤然地說:「我明白了,原來你們設計來害我!」
「我早就說給你知道,你劉玉華如何逃得我手上,哈哈哈————」
彭貴生說罷就是一連串的狂笑。玉華羞愧莫名,她掙脫了貴生的手,瘋狂的把這一羣衣冠禽獸趕走。 她在房裏伏枕嗚咽,腦際思潮起伏,母親的責備,健民的抗議,秀珍的羞辱,鎭華的淫汚,貴生的狂笑,一切向她猛襲,她抓住頭髮,緊握拳頭,爬起床來,滿室奔突,終於又倒在床上,狂抽香煙,煙霧流溢房中,她臉上雙淚長流…………
黑暗的客廳中,給深夜的寂寞佔領着,除了時鐘滴答以外,沒有別的聲响。玉華披着晨褸,亂髮長垂,雙眼無神,面目狰獰。她輕輕開了房門,房裏的光線照射在廳上成了一度白光。她從室中慢步走了出來,到了案旁坐下,低頭沉思,淚如潮湧,終於藉着那道白光,抽紙匆匆地寫着遺書:——
「母親:我錯了,除了一死,沒有足以補償我的罪過。我的死是彭貴生梁鎭華迫成的。他們購兇謀殺我,他們設局陷我,毀我的貞操,預備進而搶奪我的財產。我死了,此仇必報。我希望健民能原諒我,替我報仇!女 玉華絕筆」
她看了一遍,忍淚緘封,放置桌上,然後拿出一把剪刀,看了一看,猛向頸上一戮…………
春梅在暗中見狀大驚,馬上給搶住,大呼救命。
玉華獲救不死,但頸上已傷了一剪,被送到醫院去。她包着繃帶,躺在病床上,護士在跟她敷葯打針。
唐氏,健民,麗芬,和陳律師聞訊,趕到醫院來看她,大家在床前慇切地望着她。唐氏詢問護士情勢怎麽樣,護士吿訴她:「現在沒有危險,醫生說過一個星期就可以出院。」
「大姊,你不好憂心,靜靜地調養呀!」
玉華聽了健民的話,伸出手來緊握着他說:
「健民,過去是我的錯,不應該看財產與個人的享受那麽重要,弄得骨肉分離,復遭奸人暗算。」
「姊姊,現在大家都明白了,等你出了院,我們把多餘的財產,捐助學校,我們大家憑雙手去勞動生產,過着合理的生活,你說好不好呢?」
「你待我太好了!」
玉華衷心的對着健民說。麗芬走過來向她說,彭貴生和梁鎮華己經給警察捕去。陳律師也說這兩個敗類□包管受到應得的裁判。
坐了一會,大家向玉華吿別,玉華望着他們,感動得流下涙來!
X X X
一個星期後,玉華的健康已恢復了。
劉家又恢復了一團和氣的氣象。
陣律師伴同唐氏到農塲去觀參。
廣塲的田野,農夫們正忙於操作。
玉華健民麗芬等也胼手胝足,荷鋤把鐮,開始嘗試勞動的生活。秀珍因爲覺悟過去的錯誤,也參加到他們這一羣中來。
豐富的田產,快樂的歌聲,每個美麗的笑臉在陽光下浮現,顯示出一片嚴肅而輕快的生活氣氛! (完)
綠窗紅淚
電影小說
海黛
這故事的開端,要追溯到十九年前。在廣州有一個舊官僚叫劉雲天的,做了很多年的廳長,刮了不少的錢,算是一個鉅富之家。他的太太唐氏,生得很漂亮,膝下有一雙男女,家庭生活是很美滿的。但當他正想退休,息影家園的那年,忽然得了急病死了。
太太唐氏正當盛年,一旦死了丈夫,自然感到很悲痛。雖然丈夫遺下了一筆很大的產業,生活可以無憂,而且膝下有了女兒玉華和兒子健民,可以慰她的寂寞。但是,她正當花信年華,日子一久,難免感到枕冷衾寒,苦悶難耐。
劉廳長有一個幕僚叫彭貴生,人很狡獪,他看淸廳長太太唐氏的心事,早已存了野心。機會到了,他乘虛而入,對唐氏大獻慇懃。唐氏的心,果然給他挑動,不自禁地做了他的情俘,和他一同移居到香港來。他們爲了遮掩人們的耳目,唐氏明裡說是彭貴生的胞妹,暗裡則做他的姘婦。彭貴生就這樣以舅老爺的身份,掌握了劉家的家政,又把他的姨侄黃鎭華帶領進來,管轄着一家大農塲。
時日飛快,倏忽過了十九年唐氏一直信任着彭貴生。彭貴生也一直對唐氏鞠躬盡瘁。但時光舐去了唐氏的艶色,她由少女變成了半老徐娘。她怕彭貴生會厭棄她,所以凡彭貴生所愛的,她都順從他,無論起居飮食,古董玩物,她都盡力羅置,務必使他稱心滿意。
現在玉華和健民都長大了,玉華畢業了大學之後,在美利堅洋行當高級秘書。健民則還在肄業中,而且和女同學陳麗芬在談戀愛。姊弟倆都有一個美麗的遠景,但都不知道母親有一個不可吿人的秘密。
一
劉健民終日沉醉在他的綺夢中。
今天是陳麗芬小姐的生日,健民一早就到陳家來向她祝賀。陳律師擁着愛女麗芬在衆賓客中間,麗芬倚着健民作媚笑,幸福的熱流在她倆的心裡交流。
陳麗芬走到了圓桌邊,在大蛋糕上吹滅了蠟燭,用一柄小刀切餅。許多賓客請求她唱一支歌,她看見健民首先鼓掌,立卽微笑地答應,展着珠喉漫歌。
陳律師向外面張望,看一看手錶,然後靠近了健民的耳旁說:
「令姊怎麽還沒有來?」
「她這兩日美國總行的經理來了,應酬多,大槪差不多要來了。」
健民低聲的囘答着陳律師。
麗芬一曲唱完,賓客狂熱地鼓掌,歡聲充滿了大客廳。劉玉華盛裝匆匆從外面走進來。陳律師父女和健民爭迎上去,麗芬首先爭住親熱地拉住玉華的手說:
「唉也,小姐,你的架子大啦!」
「眞對不住,我剛剛去參加陳行長的雞尾酒會,會還未散,我就托辭先走啦!」玉華歉虛地囘着,囘頭又對健民說:「對了,阿民,你替我打個電話給陳行長,說我頭痛,囘家休息,不能夠再去陪他們。」
「唔,我現在去打!」
健民說着就走到電話間去。陳律師父女忙着把玉華介紹給衆賓客認識。陳律師說:
「這位劉玉華小姐,是已故廳長劉雲天先生的女公子。香港大學商學士,美利堅行中最能幹,最……」
「最活潑女秘書!」
陳麗芬搶着說,衆賓客熱烈地鼓掌。玉華非常得意,顧盼自豪,風頭十足。賓客中一個長舌婦,嫉忌地向玉華不屑地投了一眼,又向一女客低聲地說:
「有什麽好呀?母親軋姘頭,養大了,認繼父做舅父,不知姓劉姓彭,還說做女秘書!」
長舌婦不休地信口雌黃,健民打完電話走了進來,剛剛聽了這些話,不勝驚愕,他憤怒地向着長舌婦,想反駁她,但她已從人叢中遁去了。
主人宣佈跳舞節目開始,舞伴一雙雙隨着音樂起舞。麗芬和玉華偕舞至健民及陳律師跟前,麗芬打算邀健民共舞,玉華也想跟陳律師跳舞。但健民心裡有事想吿訴玉華,不顧麗芬,偕玉華一路向前舞去。麗芬沒有注意他的心事。隨手接上父親共舞。
「姊姊,到走廊去,我有話跟你說!」
玉華訝異地看着健民,一路舞近通走廊的門口,就停下來。健民憤怒地拉玉華出來,玉華不知底蘊,有點錯愕地說:
「什麽事呀?健民,爲什麽這樣緊張?」
「不緊張是假的,剛才我聽見一個女客說你……」
健民很急燥地搖頭嘆氣。玉華更詫異地追問着:
「說我什麽?你說出來呀!」
「他說舅父是我們的繼父,不是媽媽的兄弟,我們不知是姓劉還是姓彭,你說這是什麽話?」
「這種閒言閒語,你不好聽啦!」
「閒言閒語,如果不是,我們怎麽受得起這種侮辱?如果是……」健民咬牙切齒地說:「哼,彭貴生,他休想活命!」
「阿民,你無謂胡思亂想,快的進去跳舞啦!」
健民還要說下去,陳麗芬和陳律師已走出來:
「你們姊弟有什麽話好談,請入去跳舞,等一下再談吧!」
麗芬扶着健民走進去,陳律師也禮讓地隨玉華進去。
二
在劉家的門口。健民和玉華悶悶地走了進來,婢女春梅接過了衣物。玉華衝口而問:
「太太呢?」
「跟舅老爺和表小姐看戲去。」
「哼,看戲,看戲,我說看戲就越像做戲!」
「看你暴躁成這個模樣!」
玉華說着,示意春梅不要亂說話,春梅低着頭,拿着衣物走入房去。健民仍怒氣上升地說:
「姊姊,你不好怪我愛聽謠言,我們這個家庭,實在烏煙瘴氣。媽媽終日說我們是舅父養大的,其實,彭貴生憑着媽的庇護,覇佔我們全部的財產,他的女兒,他的姨侄,那一個不是吃劉家的飯,整個家簡直是他的世界!」
健民說着,隨手抓住桌上一個煙灰碟,揑了揑,又擱下去,火柴散了一桌面。玉華替他把火柴檢好,順手點了一支說:
「健民,姊姊大你幾歲,知道的事比你多,賬,當然要算,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我們寧可忍耐一點。」
春梅收拾好了房間,出來請玉華和健民入去休息,玉華又對健民說:
「阿民,慢慢再商量,先到房裡去休息啦!」
她說着望了掛鐘,指針正指着十時半。
健民無可奈何地走進房裏去,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輾轉不寐。煙灰標上滿是香煙蒂,他又把一支煙蒂插上,再點上一支煙。
時間已是深夜十二時。
健民張大雙眼,不斷遐思,靑煙吐射着,瀰漫一室……
在玉華的房裏,玉華也穿着睡衣,斜倚枕畔,亂翻畫報雜誌,她心緖不寧,看不入眼,丟下一本,又拿起一本。矮几上,地板上,滿堆了一大叠雜誌。
她把最後一本也丢了,伸了一個懶腰,把床一頭燈熄了,全室歸於黑暗……
忽然外面傳來一聲汽笛聲。
彭貴生和唐氏秀珍看戲囘來了,彭貴生和秀珍扶着唐氏下車,三人笑哈哈地,意興甚樂,走向大門口去,貴生按了門鈴,屋裏的電燈亮了,春梅出來開門。
三人依然嘻笑不禁地走進大廳來。唐氏問春梅,知道玉華和健民去睡覺了,吩咐秀珍春梅也去睡。
彭貴生坐在沙發上沉思。唐氏走近他身邊說:
「上樓睡吧,還想什麽呢?」
「上樓,上樓!」
彭貴生邊說邊站了起來,他很親暱地扶着唐氏的腰走上樓去。
健民在門縫中窺見這情形,憤怒地輕輕開了門出來,他緊握着拳頭,行向玉華的房門口,剛想敲門,玉華已露出了半個臉,原來她也是沒有睡的。健民輕輕地呌着她,但馬上給她止住了。健民輕輕地向她耳語,問她看見了剛才的情形嗎?玉華點點頭。健民於是進一步說:
「那末你現在還沒有表示!」
「阿民,」玉華抑住了情感說:「你不要這麽衝動,等我找個機會勸勸媽媽,再想辦法解决彭貴生的問題。你入房去睡吧!」
健民仍然很憤怒,但聽了玉華的勸,只得頹然地囘返自己的臥房去。
玉華把門掩上,大廳中頓時黑暗,瀰漫着無邊的寂寂!
三
玉華和健民兩人都有心事,終夜睡不着,一早就起身,走出廳來。春梅和秀珍正在預備早餐,秀珍看見了健民,走過來向他打招呼,但健民冷然地對着她,玉華也冷冷地問着她:
「太太呢?」
「太太說請少爺小姐先吃飯。」
玉華和健民聽說坐到餐桌邊來,秀珍給他們遞上了飯,兩人理也不理她,臉色很不對。秀珍心裏很納悶,吃不下去,但又得勉强吃,她不時窺伺着兩人的臉色。空氣是很沉悶的!
僕人阿發這時候帶着古董店的夥計進來,他向春梅說,吿訴太太知道,博雅齋要來收舅老爺昨日的古董錢。健民聽說,立卽追問着:
「阿發,做什麼鬼鬼祟祟?」
「沒有!」阿發裝着笑臉說:「是古董店的夥計,來向舅老爺收銀!」
「阿發,你說給他知道,買古董的人姓彭,我們姓劉,不關我們的事,要銀向姓彭的去要啦!」
阿發聽說仍疇躇着,秀珍則羞慟得無地自容,幾乎哭出聲來。這時候,唐氏剛下樓來,聽了健民的話,不悅地問道:
「什麽事這樣嘈呀?」
「哦!太太!」李發忙把字條遞給唐氏說:「博雅齋來收古董錢!」
唐氏接了字條一看,吩咐春梅到樓上她的手袋拿錢,然後走至餐桌邊,她滿臉冷意森嚴,玉華姊弟都爲她的威嚴所懾,顫動地呌着:
「媽,早晨!」
「媽?你們心目中還有媽?如果有媽,就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來對付舅父!」
「媽,你……」
健民聽了唐氏的話有點憤激,想辯解幾句,但玉華連忙使着眼色,搖手叫他住口,他祗得把話咽下,低下頭來。唐氏坐下,很不平地說:
「古語有說,天上雷公,地下舅公,舅父有什麽對你們不住,自從爸爸死後,你們靠那一個照顧呢?」
健民聽說,痛苦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敢出聲。但唐氏仍滔滔地數說下去:
「哦,你們現在大了,不用舅公帮忙,就過橋抽板,將舅公甩開了,是不是?」
玉華見媽媽怒氣冲冲,低心下氣地勸息着她,請她先吃了飯再說,但唐氏又扳着臉說:
「你們這樣忘恩負義,我不需要你們假孝順,我不食……」
她說着憤然站了起來,反轉了身走上樓了。
玉華見媽媽走上樓,她頹然地坐下來,朝着健民說:
「健民,我時時吿訴你,不要那樣魯莽,現在激怒了媽媽了!」
健民理也不理,拿了書包奪門而出。玉華無法,也提了手袋上班去了。
X X X X X
健民到了學校,心緖不寧,一個兒走到校園來。在樹影扶疏的走廊上,他坐在窗下的欄杆邊遐想。麗芬從他背後走過來,很歡喜地和他打招呼,但健民的反應是那麼冷淡,臉上愁眉緊結。麗芬很納罕地說:
「民哥,你爲什麽這樣不高興呢?」
「沒有什麽呀!」健民冷淡地囘着,麗芬用手按撫他的頭,溫柔地說:
「是不是身體有點不自然?」
「不是呀!」
「那麽你一定有不如意的事,你說給我聽啦!」
「阿芬,我覺得我媽媽太可憐,我們倆姊弟實在太沒用!」
「原來你是爲了這件事,」麗芬誤會了健民的意思,她不禁失笑地說:「你眞是個孝子賢孫,何必這樣躁急呢?你就快大學畢業了,將來總可以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給老人家看看,歡喜一下!」
「阿芬,我,有難言之隱,我的意思是說太受人欺侮啦!」
「哦,」麗芬仍是一派天眞無邪:「不會的,如果有人欺侮你,可以請我爸爸做你的後盾!」
健民聽了麗芬的話,更加納悶,他知道她那麼天眞,不能了解他的心事,只好拉着她走出校園。
X X X X X
彭貴生天剛亮就離開劉家,約他內侄梁鎭華到小茶舘去喝茶,談談農塲的事。梁鎭華乘機要了二百元,說是要買東西送給秀珍的,彭貴生知道是要買東西送給自己的女兒,自然樂意,於是檢出了二百元給鎭華,鎭華錢一過手,說聲先走,一溜煙跑了。
梁鎭華拿了錢,到了珠寶店去買一隻藍寶石的戒指。但他並不是買來送給秀珍的,他的心另有所屬,他要把這戒指送給玉華。
在美利堅洋行外面,鎭華倚在燈柱上等候玉華下班。玉華出來了,他馬上迎上去,兩人打着招呼,手拉手地同行。走了一程,鎭華掏出那隻藍寶石出來:
「我送隻藍寶石給你戴着玩,玉妹!」
「我看,」玉華很歡喜地接過來看:「太好了,你給我戴上!」
鎭華把戒指替玉華戴上,玉華忽然感慨地說:
「鎭華,有時候我的心很舒服,但想到我們劉家,我眞不想囘去!」
「爲什麼呢?」鎭華奇怪地問。
「唉,我總覺得我父親死得太早,叫我媽媽生活得太可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華,我問你彭貴生是你的姨丈,你應該對他知道得很淸楚……」
梁鎭華聽說,心中一怔,眉眼緊張,注神地聽下去:
「究竟他事實上是不是我舅父呀?」
「我說你傻了!」梁鎭華的心很緊張,但仍裝得安閒地說:「什麽舅父也有假的!」
「我近來聽見很多人說,他跟我媽媽根本就不同姓。」
「不是啦,你千萬不要亂聽人家的謠言,阿玉,時候不早了,我叫車送你返去啦!」
四
彭貴生已聽到了健民和玉華對他不滿的風聲,他滿懷鬼計,想把玉華也吊上,以遂他霸產的陰謀。他一面買囑李發爲心腹,暗通消息,一面藉機去親近玉華。
這一日,他乘唐氏和健民外出未囘,偷偷地潛進了玉華的臥房。玉華剛在換衣,不提防彭貴生闖了進來,她不禁驚叫了一聲:
「唉也,爲什麼你不聲不響地就進來?」
「怕什麼,外甥舅父有什麽所謂?」
「舅父?」玉華冷笑了 一聲:「哼,我眞是多得你這位舅父!」
「什麼?」彭貴生取出了雪茄,曼條斯理地吸着:「近來聽見說,你有很多牢騷,究竟爲了什麼事?」
「哼,牢騷,一個人不肯做一世傻瓜,稍爲講幾句話,就呌做牢騷嗎?」
「玉華,你們不知舅父十幾年來怎樣,憑着忠心一片,辛辛苦苦,將你們養大,維護你們的家。」
「喂,」玉華不耐煩地說:「你現在想來向我稱功呀,我不會多謝你,我不會再做傻瓜了。」
「有道理,你都長大了,十幾年前一個黃毛丫頭,現在已變成一個嬌滴滴的大姑娘了!」
彭貴生說着,涎着臉,向玉華挑逗,玉華驚覺,向後退去,他又追上一步。
「彭先生,你現在想怎樣,我請你馬上出去!」
「我跟你媽媽說過了,大家自己人,應該將關係搞得密切一點。」
彭貴生的話越來越不規矩,玉華氣得面色發靑,向後退避,憤憤地說:
「彭貴生,我不知你究竟是人還是畜生!」
「畜生,玉華,你竟然這樣侮辱你的舅父?」
「舅父,那一個認你是舅父,你是一個大騙子,一個衣冠禽獸!」
「好,就看你鬥不鬥得過我這個衣冠禽獸!」
彭貴生老羞成怒,獸性暴發,像餓虎擒羊似的向玉華身上撲去,玉華掙扎着,從他的懷裡脫身,拔足奪門而走,彭貴生則死命在後面追趕。
玉華被追,在客廳上團團轉,走頭無路,她一眼看見桌上一個大花瓶,急忙拿起來,向彭貴生的頭上劈去,彭貴生大呌一聲,捧着頭立刻蹲下去。
這時候,唐氏,健民,秀珍巳先後囘來。秀珍見爸爸被擊傷,鮮血滿面,狂吹着警笛,大聲呼救。警察聞聲進來,秀珍指証玉華就是兇手,警察於是把玉華帶到警局去。衆人也跟着到警局看個究竟。
警長問了各人的話之後,下了判語:
「劉玉華不服敎訓,毆辱尊長,人証物証具備,應予扣押四十八小時,以示懲誡。」
健民欲上前抗辯,但警長不理他,警士把玉華拉了出去。彭貴生卑躬屈膝地向警長告辭,扶着唐氏和秀珍囘去。健民望着他們,盛怒而走。
唐氏囘到家裡坐在沙發上,埋頭啜泣,彭貴生坐在一旁,柔聲勸慰她。唐氏抽抽噎噎地說:
「現在稿到這個家亂糟糟,玉華又給警局扣留,你呌我的心怎麼能安?」
「玉華姊弟倆,近來太放肆了,如果不藉機會懲誡他一下,會搞到我身上來,一拍兩散,到那時,我不好說,你的面子也過不去呀!」
彭貴生說着,用手巾抹拭着頭上的血珠,一邊用鬼祟眼光看着唐氏,觀察她的氣色。唐氏稍爲寬舒抬起頭來。彭貴生於是接着說:
「再說,玉華入了拘留所,最多關了四十八個鐘頭,不是就會出來!」
「唉,總之是我前生前世無修,做了虧心事,現在報應到我身上來!」
唐氏搖頭嘆着氣,彭貴生呌春梅扶她上樓去休息。
在陳律師担保之下,玉華終於從拘留所裡出來。健民送她先到陳家,麗芬很親切地依偎在她身旁,安慰着她。
健民和玉華在討論着彭貴生的事,决定把他驅逐出劉家。麗芬覺得奇怪,問健民說:
「難道彭貴生眞的不是你們的舅父嗎?」
「還有假嗎,差不多已經街知巷曉了!」
健民憤憤地說。陳律師起來,走近他們的身邊:
「這件事我很淸楚,過去不便對你們提起,現在旣然搞到這樣子,我不妨對你們講……」
健民玉華麗芬聽了陳律師的話,都不禁集中精神傾聽下去:
「彭貴生不是你們的舅父,他姓彭,你媽媽姓唐,根本就不同姓,十九年前,你爸爸在省城做官,彭貴生是他幕下一個小幫閒,因爲他善於巴結,成爲你爸的心腹朋友之一,後來你爸爸死了,舉家到了香港,他就公然升堂入室,稱王稱霸,一直到現在。」
「照這樣說,他明明想覇佔我們的產業。」健民恍然地說。
「何止產業,」玉華說:「你知道他如何對待媽媽,現在又預備什麼手段來對待我。」
「旣然事實可以証明他不是你們的舅父,就很容易把他趕走。」麗芬天眞地說。
「現在我想請求陳律師多多幫忙,把這件事搞淸楚。」玉華向陳律師說。
「可以的,要這樣做,這件事我是應該做的!」
陳律師這一答應,使健民玉華和麗芬都面露喜氣,相顧共表欣慰!
五
翌日,陳律師跟着健民玉華到劉家來。
唐氏正和彭貴生談着玉華的事,健民把陳律師介紹給媽認識。唐氏向陳律師打着招呼,然後向玉華說:
「阿華,你昨晚在警局怎樣捱過呢?」
「媽我沒有在警局過夜,陳律師領我出來,因爲時候不早,所以就同健民麗芬囘到陳律師家住了一晚。」
彭貴生聽了玉華的話,不服氣地走過來向陳律師挑戰:
「我眞料不到,一位堂堂大律師,隨便把一個未定案的兇手担保出來,照這樣搞法,還要法律做什麽?」
「哦!」陳律師聽說,站了起來,笑笑地說:「這位就是彭貴生先生,眞夠幸遇!」
「豈敢!豈敢!」彭貴生勉强地應着。
「貴生先生所發的高論,確是不錯。法律本來是保障人權的,不過,犯法也有他的動機,一個賢明的檢察官,他就知道如何去硏究犯人的動機!」
陳律師嚴正的說,彭貴生憤憤地問道:
「你接受那一個的委托?」
「劉玉華小姐跟劉健民先生,他們是當事人,我是他們的代表!」
「吓!」唐氏聽說,驚叫了一聲:「玉華,你們請陳律師來,想跟你舅父打官司呀?如果你們這樣做,倒不如先要了我這條老命!」
唐氏氣得渾身發抖,春梅和秀珍分侍左右扶持着。陳律師心平氣和地說:
「劉太太,玉華跟健民的年紀已經不小,依照法律規定,他們已經有了自主權,請彭先生將一切的管理權交還他們,否則,今天不打官司,第二天都一樣打官司!」
「好!」彭貴生憤然地說:「要打就打,我準備到法庭和大家相見。」
「彭先生,我勸你還是不要到法庭去,誰都知道你姓彭,劉太太姓唐,這一點,已經落下風啦!」
這一說,使彭貴生心中一怔,他定一定神,仍想狡辯,劉家長輩叔卿惠德兩人忽忽進來,唐氏和貴生看見,不禁愕然,玉華則很歡喜地迎上去:
「二叔公,三伯父,這位就是陳大律師。」
「兩位來得正好,」陳律師向兩位長輩說:「關於這件事,兩位必定知道淸楚?」
「不錯,玉華他們姊弟倆,是我親眼看大的,他父親死後,家權落在外手之手,坊里閒言,我們一向不便過問。現在他姊弟長大了,旣然曉得收返業權,貴律師如果有什麽諮詢,我一定願意出庭做個証人。」
「什麽話?」唐氏聽了二叔公的話,老羞成怒,憤然作色說:「就算我這份家產彭貴生無份,你們也不會得到一分半厘。就算玉華健民要管,都要等我死了之後!」
「劉太太!」陳律師說:「你不用這麼氣,只要彭貴生先生將家政業權交出,離開這間屋子,就什麽官司都不用打啦!」
「貴生,我看你……」
唐氏双眼投射到彭貴生臉上,彭貴生斷然地說:
「可以,我去,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一双冷眼,看看你們怎樣收塲!」
「什麽?」健民釘住了彭貴生:「你就想這樣容易脫身嗎?」
「請你把我家所有一切契據,簿籍交出來!」玉華也釘住了彭貴生:「你的簿籍契據放在什麽地方?」
「在樓上保險箱。」
「鎖匙呢?」
「你有資格向我要鎖匙?」
彭貴生不屑地看了健民一眼,然後從衣袋裡掏出了一把鎖匙,樂意地向唐氏一丢。唐氏接了鎖匙,正要放進衣袋裏去,玉華忙的說:
「媽,請你進去拿出來給大家看!」
「要看,慢慢留給自己人看。」
「不是的,劉太太,如果我做律師的,不趁現在攪個淸楚,我的責任就無法子完了。」
彭貴生拉着他的女兒秀珍要走,健民忙的阻住了他:
「慢點,看過契據簿籍後再走!」
唐氏搖頭嘆息,忍着淚走上樓去。壁上的時鐘正是上午九時十五分。
六
彭貴生離開了劉家,囘到壺天酒店自己的寓所,獨個兒坐着發悶,不住的喝酒澆愁。
梁鎭華到來訪他,彭貴生很歡喜地說:
「鎭華,你來得正好,來,跟我飮杯!」
鎭華坐下來,彭貴生替他斟酒,秀珍借故走開。
「鎭華,」彭貴生呷了口酒後說:「現在情形這樣,各方面都完了,只有農塲還在你手裏,你可以一方面離間他們姊弟,一方面刮錢,否則我站不住,你將來做女婿的也沒有意思。」
「知道的!」鎭華唯命是從的說。
「你隨便坐下,秀珍就要返來。」
「我沒有空,改天再來;」
「好的,改天帶個好消息來!」
鎭華離開了壺天酒店,一逕到劉家去,約玉華健民到農塲參觀。他帶着玉華這處巡視,這處觀觀,那處看看,極盡慇懃之至。健民以不齒的態度,鄙視他了一眼。
鎭華低心下氣,請玉華和健民,以後多多指敎。健民忽然對玉華說:
「姊姊,你以爲農塲的舊數,要不要跟鎭華計算一次?」
鎭華聽說嚇了一跳,玉華却笑笑地對健民說:
「你怕鎭華也行貴生那條路嗎?」
「那也不是這麽說,不過……」
「不過什麼呢?」
「鎭華跟貴生畢竟是親戚!」
「健民,」鎭華强作鎭定地說:「這一點請你放心,彭貴生這人,說親戚都是假的,以前你也不是他的親戚嗎」?
這一說使健民默然無語,玉華不覺失笑地對鎭華說:
「好了,就這樣照舊做下去,現在全權交給你,有什麽計劃,隨時提出來,大家硏究硏究!」
「好!好!我一定加緊努力!」
鎭華低心下氣地囘着,又替着玉華開車門,讓她進去,恭送到門外,揮手而別!
X X X
從此以後,玉華和健民已經收囘了業權,家政完全由自己管理,唐氏不管他們的事,終日在樓上念佛,打發這寂寞的日子。
有一日,僕人李發來吿訴太太唐氏,說彭貴生手頭緊,沒有錢用,唐氏對彭貴未能忘情,拿了二千元給李發送去。李發正拿着鈔票欲出門,鬼鬼祟祟,給健民碰見,截住了:
「哼,這些錢什麽地方來的?」
「唏,少爺,你不要吵,這兩千元是太太叫我送給舅老爺的!」
「哦,你交給我就可以。」
「少爺,你想留這錢我不反對,不過你要想個辦法,給我交差才對!」
健民聽說,走至桌前,抽筆寫了張假收條給李發,然後警吿他,不能夠洩漏秘密。
李發接了收條,茫然不知所措。
健民高興萬分,向門外飛奔而去。
鎭華和玉華双双地囘來,剛踏入門,看見李發鬼鬼祟祟的態度,不禁生疑。鎭華問李發究竟爲了什麽事,李發把剛才太太送二千元給彭貴生,半路給健民截脏的事吿訴他。
他們的話說得太小聲,玉華聽不淸楚,緊問着鎭華說:
「什麽事?半路截脏呀?鎭華,不要吞呑吐吐,有話說出來大家知道!」
「沒有,今天你媽送二千元叫李發拿去給我姨丈,健民知道,把那筆錢扣留了,他應該說給你知道!」
「哦,」玉華驚訝地說:「有這件事,他說一聲都沒有,豈有此理?」
鎭華看見玉華生氣,認爲是一個好機會,馬上火上添油地說:
「二千元還是小事,最怕搞到連大事都瞞你就糟!」
玉華心裏有點懷疑,沉思間,樓上有唐氏的咳嗽聲,快要下樓了。鎭華乘機引退,他握着玉華的手說:
「我有事先走,你不好難爲健民,或者有其他的事,不便給你知道的苦衷,你原諒他啦!」
鎭華離開玉華,馬上到壺天酒店去找彭貴生,把唐氏送給他二千元被健民截去吿訴貴生的事。彭貴生聽說,幾乎氣破了肺,他憤然地說:
「想不到這衰仔猖狂到這個地步!眞把我氣煞了!」
「我以爲仍舊在玉華身上弄好法子,等我看風色敎唆玉華,把他的家產接收過來,如果
大權落在玉華手上,我運用兩度散手,等他兩姊弟不和,那時候我們就得從心所欲了!」
鎭華這一妙計,說得彭貴生轉怒爲喜,他不禁拍手的說:
「唔,這個好辦法!」
鎭華辭別了彭貴生,看看錶,知道玉華下班的時候到了,他熟習地走那個馬路角站着等她,不提防有人在後面叫了他一聲:
「阿鎭,等我很久嗎?」
「哦,」鎭華發覺是玉華叫他,笑笑地說:「不很久!」
說着挽了玉華的臂,行出馬路中心。玉華只放着慢步,眉黛深鎖,好像有滿懷心事。鎭華假慇懃地問道:
「爲什麽你終日悶悶不樂呢?」
「不悶就是假啦!」
「你是不是爲了健民那件事,你傻了,你是大姊,有權當家,旣然健民這樣,你可以自己打算,向母親接管財權。如果不這樣做,辛辛苦苦爭奪囘來的產業,不久又會化爲烏有,你說是不是呢?」
「好啦,我們現在囘去再說!」
玉華囘到家裏來,走到健民的房裏去,健民正在几上玩撲克,她故作試探的口吻說:
「健民,我問你,媽媽昨日靜靜地叫李發拿二千元去給彭貴生,你知道嗎?」
「不知道,」健民故作鎭定地說:「眞不眞呀?」
「我相信沒有假的,你知道這件事要怎麽辨?」
「如果是眞的,我覺得媽太不應該了!」
「你以爲我們是否應該把財產管理權爭取過來?」
玉華故作進一步的試探。健民聽說,放下撲克,沉思一會反問說:
「你以爲這件事,是不是我們能夠做得到呢?」
「譬如爭得到,你要不要反對?」
「由你一個人去爭,爭到,由你一個人保管好嗎?」
「你沒有後悔?」
「一言爲定!」
健民斬釘截鐵的說,這正中了玉華的下懷。她馬上到媽媽的房裏去,把情形向媽媽透露,試探媽媽的口氣。唐氏自從家庭鬧了事之後,她的心都冷了,一心念佛,看財產看得很淡。旣然玉華提出要掌管財產,她一口答應了,落得做一個閒人。
玉華掌管了財產之後,大權在握,一切獨斷獨行,隨便花錢,一輛一萬三千元的新型汽車,也毫不吝嗇的買了。健民看她這種派頭,雖然不窩心,但有言在先,怎麽能夠向她多說一句話呢?
玉華買了新汽車,心裏很高興,馬上和梁鎭華通電話,把一天的消遣節目都編定了:下午淺水灣游泳,晚上麗都晚飯,然後試新車遊車河。
健民看她這麽得意忘形,忍耐不住,走近了電話邊說:
「姊姊,你不能一朝大權在手,就這樣揮霍無度怕一下子會傾家蕩產呀!而且你同鎭華在外面攪三攪四,人家會說你閒話的!」
「哼!」玉華鼻子裏嗤了一聲:「健民,你放心啦,你還沒有敎訓姊姊的資格,請冷靜點,找你的麗芬拍拖去吧!」
玉華說着,睬也不睬地拿着手袋走了。健民望着她的背影、感到憤恨,想不到姊姊變得這樣子了!
七
玉華和鎭華坐着新汽車,在山道上馳行。她倆一會兒双双浮沉在綠波上,競逐於沙灘上,一會兒盛裝出現在大餐廳上,酒杯互碰,杯中現出歡笑的幻影……
夜深了,鎭華扶着玉華囘來,玉華已經醉了,一顚一顚的,整身子東搖西幌,口裏說着醉話。鎮華勸她入房去睡,她乘機投入他懷裏,鎭華摟着她的腰肢,正欲乘時吻她,廳上的電燈忽然一亮,鎭華一驚鬆開,把玉華投到沙發上去。
健民己經出現在他倆的面前。
「梁鎭華,現在什麼時候,這裏是什麼塲合?我說你應該尊重你自己的人格!」
「我什麽地方不尊重人格,」鎭華老羞成怒地頂着健民:「你憑什麽資格管我?」
「我憑着這個家庭的主人資格,要你立刻就滾!」
「健民,你不要做得這樣無禮!」
鎭華圓睜着眼說,玉華看在眼裏,也不滿地責備健民:
「你這種態度算什麼呀?」
「我想爲劉家保留一點面子,不好丟得太淸!」
「我的事用不到你管!」
玉華嚴峻地囘着,健民憤然地走入房去,把門扃了。
「豈有此理!」
玉華心緖不寧地點一根香煙狂抽,煙霧瀰漫了滿室。華在旁安慰她,把她抱進房裏去…………
X X X
玉華酒醉之夜,献身給鎭華之後,一心一意都在鎭華身上,視健民如眼中之釘,非拔去不快。鎭華乘機慫恿玉華和健民分家。玉華自然是言聽計從的。
健民痛恨姊姊的放浪,專權,憤憤走到陳律師家,把事情吿訴陳律師,要陳律師代他主斷分家的事。
陳律師沉默了一會說:
「玉華的舉動確是不對,不過兩姊弟就爲了一份產業來反面,是不是要再詳細考慮一下?」
「陳伯伯!」健民說:「我的意志已堅决,我一定要這樣做,無論如何請求伯伯鼎力幫忙!」
陳律師聽了健民的話,終於答應下來,偕同健民到劉家來遇玉華。
玉華剛好整裝,要跟鎮華出去,健民叫她慢點出去。玉華看見陳律師,恍然地說:
「哦,原來是請了陳律師來,這樣,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預先對我先禮後兵啦!」
「玉華,你不好誤會!」陳律師說:「我雖然是受委托而來,但我的本意,是想勸你們和解,並非要對你用兵。」
「陳律師,我的姊弟之間,並沒有外人滲雜□財權家務,掌握在自己手裏,跟從前落在彭貴生手裏情形不同,旣無不和,何須行什麽和解呢?」
「你就以爲沒有什麼不和,始終獨行其是!」
沉默了很久的健民這時不禁發言了。但馬上給陳律師指住,他對玉華說:
「玉華,健民到底是個年輕的人,做事只知道替自己打算,不錯,這是他的弱點。不過。你做大姊的,應當共艱共苦,齊心協力支撑這個家,千萬不可同室操戈,讓漁人得利!」
陳律師觀察玉華和健民的瞼色之後,又對玉華說:
「比方,今後你對於家政,不採獨裁的方式,對健民的主權不加限制,我認爲情形就不致於搞壞!」 玉華聽了詩律師的話,很不滿地說:
「你口口聲聲,說要和解,但當我是被吿一般的看待,什麼剝奪主權,如果你認爲我有很多罪,不如索性大家打一塲官司呀!」
「哼!」健民也不滿地說:「你的用意難道還不夠明白?」
「什麼用意都好,今天你旣然用這麽大的壓力來對付我,我也不能不有所準備。陳律師,今天說話就此結束,改天法庭相見,我要上工,失陪了!」
玉華說罷,拉着鎭華匆匆出去,唐氏從樓上趕下來,已來不及阻住她了。健民目着陳律師,陳律師沉下臉來。
玉華和健民家產糾紛的事,終於在法庭判决了。產業權判處証明書,由兩人簽字後,再由陳律師簽字。
玉華和健民分家了,劉家那一座住宅是判歸玉華所有,本來大家可以專心保管自已的家業,不相侵犯。但彭貴生又使用了詭計,使李發謀殺玉華,雖然謀殺未逐,健民已蒙受了主使的嫌疑,迫得搬到陳律師家去。唐氏眼看玉華心腸已經變了,再跟她住下去也沒有意思,所以也跟着健民去。玉華看見媽媽要走有點捨不得,但給鎭華阻住,也祗好讓媽媽走了。
玉華自健民和媽媽離開後,終日和鎮華恣情作樂。因爲她早把身體献了給他,自然一切任他所爲。這一天,她和鎭華在閒談,偶然問起什麽時候可以結婚,鎭華嘻皮笑臉地說:
「什麽時候都可以?只要你把財產管理人授權紙一簽,就可以馬上結婚!」
「財產管理授權紙?」玉華大吃一驚地說:「你究竟想和我結婚還是想跟我的財產結婚?」
「你想我嫁你呢?還是你嫁我?」
「我不明白!」
「乖乖的,不要心急,我們準備結婚啦!」
鎭華說着,一把擁住玉華於懷中。
八
玉華不顧媽媽反對,終於和鎭華結婚了,他們穿着結婚禮服,由婚姻註册局出來,坐汽車囘到家裏。
彭貴生知道他們結婚,帶着女兒秀珍到劉家來。鎭華和玉華進門來,看見了兩人,不禁愕然。彭貴生嚴峻地對鎭華說:
「哦,搞到正式結婚,鎭華,」他指着秀珍說:「這個是你什麽人?我辛辛苦苦栽培你,今天你羽毛已豐,就反骨無情,是不是?」
鎭華默然不作聲,秀珍上前扯住玉華的禮服,譏諷地說:
「你跟鎭華結婚,你知道他是什麽人?你那裏有資格和他結婚?」
「他,他是什麽人呀?」
「今是我的未婚夫!」
玉華聽說,嚇退了一步。鎭華尷尬地强作苦笑。玉華滿面怒容,走上前摑了他一下。彭貴生在旁大笑,她羞愧欲走,但給他阻住:
「慢點,你一向都很貞潔,現在米巳成炊,無法子不將錯就錯了!」
「彭貴生,」玉華憤然地說:「我明白了,原來你們設計來害我!」
「我早就說給你知道,你劉玉華如何逃得我手上,哈哈哈————」
彭貴生說罷就是一連串的狂笑。玉華羞愧莫名,她掙脫了貴生的手,瘋狂的把這一羣衣冠禽獸趕走。 她在房裏伏枕嗚咽,腦際思潮起伏,母親的責備,健民的抗議,秀珍的羞辱,鎭華的淫汚,貴生的狂笑,一切向她猛襲,她抓住頭髮,緊握拳頭,爬起床來,滿室奔突,終於又倒在床上,狂抽香煙,煙霧流溢房中,她臉上雙淚長流…………
黑暗的客廳中,給深夜的寂寞佔領着,除了時鐘滴答以外,沒有別的聲响。玉華披着晨褸,亂髮長垂,雙眼無神,面目狰獰。她輕輕開了房門,房裏的光線照射在廳上成了一度白光。她從室中慢步走了出來,到了案旁坐下,低頭沉思,淚如潮湧,終於藉着那道白光,抽紙匆匆地寫着遺書:——
「母親:我錯了,除了一死,沒有足以補償我的罪過。我的死是彭貴生梁鎭華迫成的。他們購兇謀殺我,他們設局陷我,毀我的貞操,預備進而搶奪我的財產。我死了,此仇必報。我希望健民能原諒我,替我報仇!女 玉華絕筆」
她看了一遍,忍淚緘封,放置桌上,然後拿出一把剪刀,看了一看,猛向頸上一戮…………
春梅在暗中見狀大驚,馬上給搶住,大呼救命。
玉華獲救不死,但頸上已傷了一剪,被送到醫院去。她包着繃帶,躺在病床上,護士在跟她敷葯打針。
唐氏,健民,麗芬,和陳律師聞訊,趕到醫院來看她,大家在床前慇切地望着她。唐氏詢問護士情勢怎麽樣,護士吿訴她:「現在沒有危險,醫生說過一個星期就可以出院。」
「大姊,你不好憂心,靜靜地調養呀!」
玉華聽了健民的話,伸出手來緊握着他說:
「健民,過去是我的錯,不應該看財產與個人的享受那麽重要,弄得骨肉分離,復遭奸人暗算。」
「姊姊,現在大家都明白了,等你出了院,我們把多餘的財產,捐助學校,我們大家憑雙手去勞動生產,過着合理的生活,你說好不好呢?」
「你待我太好了!」
玉華衷心的對着健民說。麗芬走過來向她說,彭貴生和梁鎮華己經給警察捕去。陳律師也說這兩個敗類□包管受到應得的裁判。
坐了一會,大家向玉華吿別,玉華望着他們,感動得流下涙來!
X X X
一個星期後,玉華的健康已恢復了。
劉家又恢復了一團和氣的氣象。
陣律師伴同唐氏到農塲去觀參。
廣塲的田野,農夫們正忙於操作。
玉華健民麗芬等也胼手胝足,荷鋤把鐮,開始嘗試勞動的生活。秀珍因爲覺悟過去的錯誤,也參加到他們這一羣中來。
豐富的田產,快樂的歌聲,每個美麗的笑臉在陽光下浮現,顯示出一片嚴肅而輕快的生活氣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