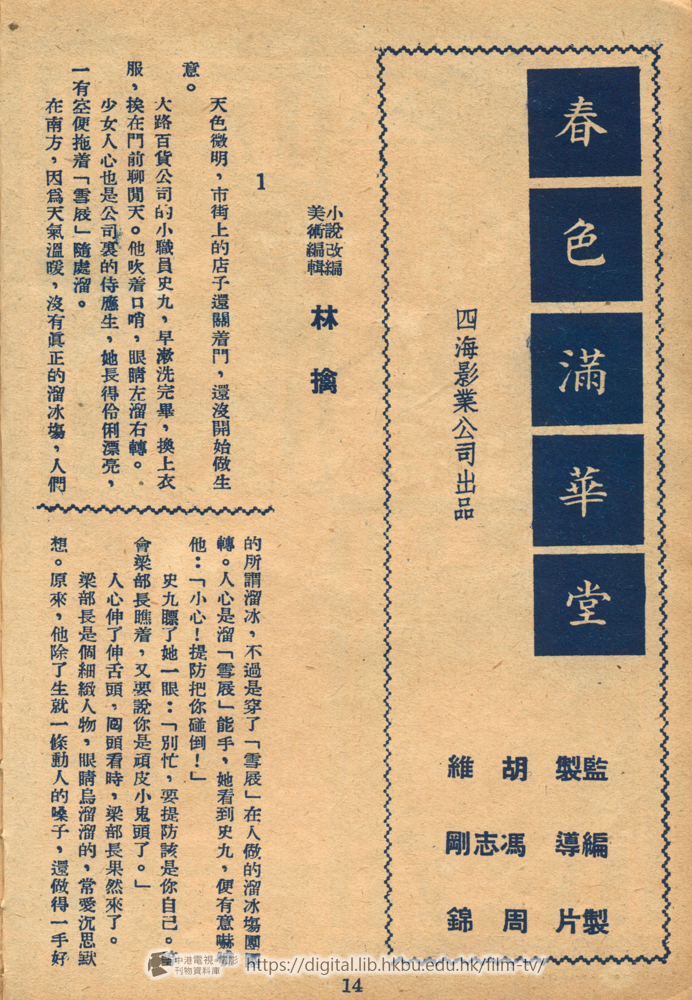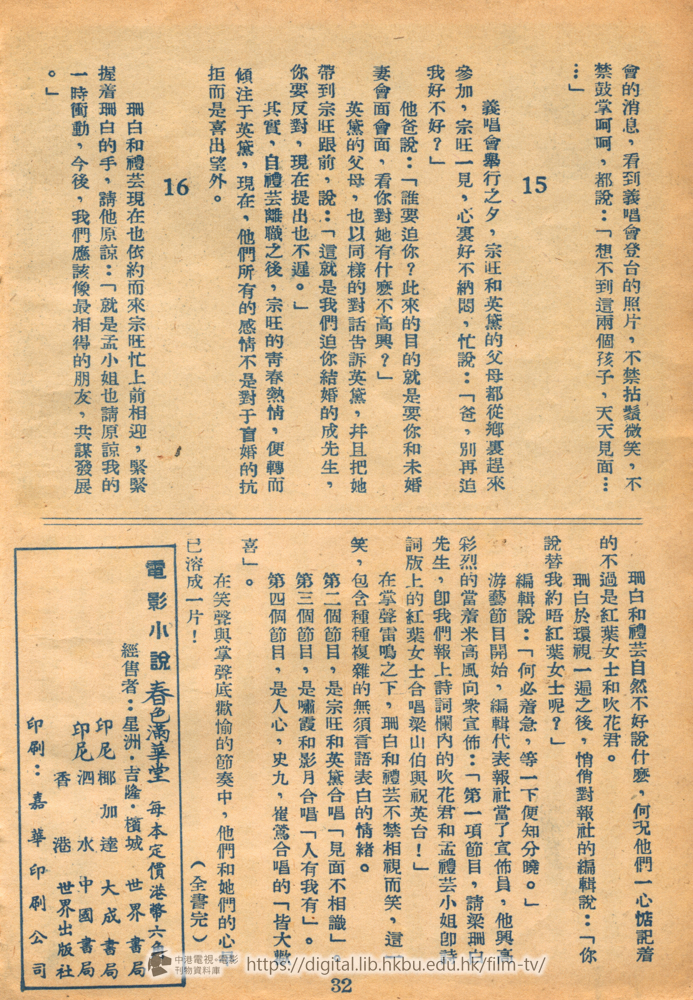人物介紹
何非凢
因爲是一個在唱工方面很有成就的舞台紅伶,所以,卽使在銀幕上,他的名字也同樣的刮刮叫。尤其自一九五一年以來,他在銀幕的出現不但有駕乎紅星之勢,并且,演技也一天比一天更純煉。爲了這原因,「春色滿華堂」裏,他便有了從所未有的輝煌的表現。(林)
人物介紹
鄭惠森
朝氣蓬勃,有如生龍活虎!這是鄭惠森的寫照。就憑了這股剛勁之氣,一年來,電影廣吿上,幾乎天天都有鄭惠森的名字。可是,他却并不因此傲人,說實話,他比前越發謙虛,越發勤於學習。有人說,一九五二是鄭惠森雄霸影壇的一年。(林)
黃金愛
黃金愛給人的印象,使人越發覺得她比黃金還可愛。可能,黄金愛這名字之來,本義在此。我們看她在片塲裏跑跑跳跳,忽而像六七歲的小丫頭,忽而像將屆成熟之年的姑娘,總之她變幻多端,無一而不使人可愛。(林)
梅珍
愛哭便哭,愛笑便笑,愛罵便駡,愛打便打,這是梅珍的可愛處,這是梅珍的所以使人覺得她純眞謹厚,沒有矯飾也沒有虛僞。但是這樣的性格在這樣的社會裏終究要吃虧的。所以,論者以爲,梅珍應該把感情放到工作上。(林)
人物介紹
芳雪芬
芳雪芬是名伶芳艶芬的妹妹,雖然她初登銀幕,但爲了姊姊給她的薰陶給她的影響,她的表現也使人感到她是大有前途的。
林家声
讓我們把希望寄託在林家聲這年靑的一輩身上吧。因爲,粤語影壇實在太需要有一顆熱熾的心,有一份力求上進的不苟且的工作態度底年靑朋友了,而林家聲,正好是我們所希冀的一人。
對于李鵬飛,相信觀衆决不會陌生,雖然他目前已成爲許多影片的製片人,可是却不放過任何的表現機會。他在這裏演一個報紙編輯,戲不多,却可見他豐富的經驗。
賽秋霜是名旦賽珍珠的姊姊,陳醒章是舞台名角,在表演上,都有可取之處。
人物介紹
馮志剛
馮志剛是電影壇裏導演羣中的知名之士,因爲在開麥拉前活動了二十多年,所以,無論什麽題材的劇本,經他導演,都成爲有票房價値的好影片,譬如「春色滿華堂」,情節是如此簡單,名角又如此濟濟一堂,要不是富于經驗肯動腦筋的導演,必有顧此失彼之虞。(林)
胡維
不久之前,胡維曾經監製了」嫡庶之間難爲母」。爲了他的手段活靈,慷慨好義,所以,演員們都高興和他合作。這一囘,他監製「春色滿華堂」,我們只要看演員名單,都是第一流的紅伶紅星,便可見胡維在這些朋友心裏的地位了。(林)
春色滿華堂
四海影業公司出品
監製 胡維
編導 馮志剛
製片 周錦
小說改編
美術編輯
林擒
天色微明,市街上的店子還關着門,還沒開始做生意。
大路百貨公司的小職員史九,早漱洗完畢,換上衣服,挨在門前聊閒天。他吹着口哨,眼睛左溜右轉。
少女人心也是公司裏的侍應生,她長得伶俐漂亮,一有空便拖着「雪屐」隨處溜。
在南方,因爲天氣溫暖,沒有眞正的溜冰塲,人們的所謂溜冰,不過是穿了「雪屐」在人做的溜冰塲團團轉。人心是溜「雪屐」能手,她看到史九,便有意嚇唬他:「小心!提防把你碰倒!」
史九瞟了她一眼:「別忙,要提防該是你自己。等會梁部長瞧着,又要說你是頑皮小鬼頭了。」
人心伸了伸舌頭,囘頭看時,梁部長果然來了。
梁部長是個細緻人物,眼睛烏溜溜的,常愛沉思默想。原來,他除了生就一條動人的嗓子,還做得一手好詩詞。照理,他該是一個藝術家才對。
這幾天來,他正在聚精會神於一家報紙的讀者欄上詩詞酬答。因爲有一個署名吹花和署名紅葉女士的讀者每天的詩詞唱和引起了他大大的興趣。
人心和史九見了他忙點頭道早,可是他咀裏答應,眼睛還是傾注于手上的報紙。
瞧着那模樣,兩個小鬼頭都覺得好笑,人心說:「西藥部的孟禮芸姐姐也是一個模樣,總愛讀什麽詩詞歌賦。」
「所以呀,我說梁部長和芸姐姐眞是志同道合。」史九隨和着。
「再說一遍,是誰?」梁珊白眼睛一轉。
「還有誰?還不是孟禮芸。」史九把咀呶,大家囘頭看時,孟禮芸也正全神貫注的拿着報紙從那邊來了。
「孟禮芸?志同道合?我才不高興跟她一道呢。除了事事頂撞,她從沒和我說一句好話。」
話雖然這麽說,對於孟禮芸的天天注意讀報上的詩詞,珊白也不能不感到詫異,也不能不伸着脖子偷瞧一下。
而這一下,却也證明珊白不說的錯,至少,孟禮芸看他伸着脖子,立刻便開口啐他:「什麽値得偷偷摸摸的!要看,不好說一聲嗎?」
珊白把手上的報紙一揚:「別意得!報販有的是...…。」
要不是祝英黛從外進來,移轉了禮芸的目標,兩人又要大耍唇鎗舌劍了。
禮芸挽着英黛的臂灣:「你眞早,爲什麽不多休息一下?」
英黛嫣然一笑,這一笑,是表示她對禮芸的感謝。
忽然,人心像想到了什麽:「哎喲,我想着了,黛姐姐叫祝英黛,梁部長叫梁珊白,我叫人心,九哥是史九,都和「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裏的名字相同,要是我們演一齣這故事的戲,人家瞧着演員表,不是很有趣麽。」
然而孟禮芸却另有見解,她看英黛跑囘樂器部,便說:「其實,我就覺得祝英台不該配梁山伯。」
史九側着脖子:「爲了什麼?」
「祝英台連多等四天都不能,便改嫁馬家郞了。」
「那麼誰該配梁山伯?」人心說。
「我說孟麗君倒還不錯!」
禮芸這様一說,兩個小鬼頭却咭咭的樂開了:「那卽是說,孟禮芸該配梁珊白呵!」
禮芸暗裏高興咀裏硬,偏說:「誰說我自己?誰高興配……」
珊白自然曉得她要說什麼:「你們這些「華麗緣」,只配和蘇影月,皇甫嘯霞做一路吧了。」
蘇影月也恰在這時上班:「唷唷,梁部長偏高興把人家拖在一起。」
「正是,他專挑我們的不是!」是禮芸的還擊。
英黛無意參戰,只說:「都吃得太飽了,專愛尋是惹非。」
珊白眼睛一眨:「人心和史九的一張咀就够把他們說倒啦,用得着我?」
在這唇鎗舌劍的緊張局勢下,如果不是經理成宗旺乘時而至,還不知要纏到什麼時候。
皇甫嘯霞和梁珊白同樣,也是個對唱曲頂有興緻的風流人物,他是公司裏的高級職員,對招徠之術,頗有心得。這一天,他决定以人心和史九在門前高唱「無任歡迎」一曲以引顧客。憑了人心和史九的伶俐機智,憑了兩人都有一張嘹喨的嗓子和惹笑的動作,顧客們必會大感興趣,聞聲而至。
但成宗旺却不表贊同,他說:「財不入唱家!」
「經理,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唱戲的給人瞧不起,這觀念早成過去。至於唱曲能否吸引顧客,等會便知分曉。」嘯霞朗朗伸辯。
畢竟皇甫嘯霞的說法沒有錯,人心和史九在門前引吭高歌,原來要進公司的固然如蟻赴羶,就是順道而過的,也毫不考慮讓脚步停住。
成經理瞧着顧客像流水似的湧進來,心裏實在高興,實在佩服嘯霞有先見之明,但有錢人總以爲自己是對的,因此,咀裏也不便說什麼了。
偏偏,皇甫嘯霞却只管盯着宗旺笑一下,又囘頭看一下那些潮湧而來的顧客。自然,這種動作一方面證明宗旺的意見是錯的,另一個目的是有意氣他一下。
小心眼的宗旺,不禁兩眼一瞪,掉頭跑進經理室。
嘯霞和別的幾人都爲之樂開了。
一會,人心興高彩烈的連跑帶跳的進來,一手拖着珊白:「梁部長,我們唱得還不錯吧?」
珊白想了一想:「也差不多了。」
史九不服氣:「梁部長,該給我們指點指點呵?」
珊白說:「唱粤曲也和别的歌唱道理一様,首先,應該清清楚楚地把毎一個字唱出,不能含糊,要達到這樣的境地眞也不容易。譬如演粤劇的新馬師曾,便是最懂得這竅兒的。不少曲兒因爲「咬字」清楚,「腔」調常能和內容配合,所以很動人,成爲家傳戶誦的曲子。」
珊白說了,驀地聽得嗤嗤的笑聲,囘頭看時,禮芸正朝着他說:「咬字!看那些字都給你咬爛了!」 珊白怒目而視:「別嘵舌,你憑什麼資格批評?」
影月從旁插咀說:「梁部長,你也感認真,雖說不是誰也懂得歌唱,難道連聽衆要表示一點點感想也要什麼資格不成?譬如我說,你梁部長也不算唱的頂好,你好意思駡我?」
珊白不好發作,訕訕的道:「那麼你說,誰唱得頂好?」
影月說:「祝英黛唱得眞不錯!」
「剛好,她唱了。」禮芸瞇着眼,那意思,是要向珊白示威。
原來英黛正斜靠着身子,向顧客以幽怨悲凉的聲調唱一曲「英台祭奠」。
果然,珊白、禮芸、人心、史九、影月都默然傾聽。
一曲旣終,大家都噓了口氣。
英黛從貨櫥裏拿出一張唱片,以誠懇的口吻對顧客說:「就是這一張,「英台祭奠」,先生總高興吧?」
那人搖搖頭:「不!那太凄慘了,聽了多難過。」
英黛看那人移動脚步,有點着急:「我們還有別種貨式,隨便選擇。」
可是那顧客比她更着急,三步兩步跑出,咀裏只說:「改天買改天買!」
英黛像洩了氣的皮球,軟攤攤的向椅上一躺。
珊白跑到英黛與另一售貨員崔鶯跟前,以一種非常關切的神態道:「你們這種着急的態度,如果我是顧客,也要給你們唬跑。而且,要是他不高興悲涼凄怨的曲子的,便該馬上換給他輕鬆愉快的歌調。」 「但是「英台祭奠」從來是熱門貨呀。」英黛有點不服氣。
「所以,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永遠都是那一套!」珊白强調說。
崔鶯也提出抗議:「部長,你說你有本領,那邊顧客來了,試試你的手段呀。」
珊白昂頭挺胸的:「等着瞧!」
于是,珊白先讓顧客坐下,然後引吭高歌「多情梁山泊」一曲。一點不錯,「運腔」,「咬字」的確不讓當今名伶新馬師曾。
只可惜那顧客幷非知音者,不過是一個小什貨販,所以,纔坐下不久,便呼呼的睡着了。
影月見不對勁,悄悄的通知珊白。可是珊白正在聚精會神,全不曉得。
禮芸偏說:「他不過凝神欣賞吧了。」
一曲旣終,崔鶯推了那顧客幾把:「哎唷!眞的睡着了。」
珊白有點難爲情:「這不是很動聽的曲子嗎?」
顧客勉强的站起來,搖搖欲墮:「對不起,我有點暈眩。」
禮芸和影月只覺好笑,也隨着顧客裝腔作態的嚷頭疼。
珊白禁不住禮芸幾入的訕笑,紅了臉的說:「啐!那傢伙根本不懂。你們何必隨和着!」
人心看珊白和姐姐們劍拔弓張,就要大開「殺戒」,忙跑進經理室,揪着成宗旺:「經理,要不替他們排解,眞要大打出手了。經理,快去快去!」
宗旺趕來時,珊白和禮芸正瞪着眼互相詬駡。
宗旺氣得搖頭頓脚:「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英黛也要排難解紛:「芸姐姐,算了吧,何必爲了我唱得不好大傷和氣哩。」
宗旺還是氣噓噓的說:「罷了罷了!以後工作時間,誰也不許唱曲。英黛一唱,顧客給唱跑了,珊白却弄得顧客昏昏欲睡。何况,我這裏也不是什麽戲園娛樂塲!」
大家瞧經理眞的有氣,都噤不作聲。
宗旺邊跑進經理室,邊通知人心:「請孟小姐進來!」
人心伸了伸舌頭。影月說:「糟了!」
大家儘以爲禮芸要受責駡,其實,禮芸不但沒有被責,相反,成宗旺還嘻着咀請她坐下,裝得很親切的問長問短。
禮芸呢,却以一種愛理不理的神態對付他。
宗旺只好靦覥的說:「唔,就替我寫一通短信吧。是:明天清明節,放假一天,我請你,請你…請你…請你…」
禮芸很不耐煩:「究竟要寫幾個「請你」?」
宗旺給她說得好沒意思:「嘻嘻,是…二個,一個吧了。」
外面,另有一番心事的影月却希望能進經理室一看究竟。
恰巧史九拿了一張「八折單」要經理簽字,影月乘勢道:「我替你拿給經理。」
影月之突然闖進,正如好夢之被驚破,使宗旺大感狼狽,他恨影月,却又沒有可資責駡的把柄,何況影月的進來是爲了本位工作。
相反,影月的進來禮芸却如獲救星,她立刻拖着影月:「好姐姐,你的文字工夫比我好,你替經理寫信經理一定高興。」
成宗旺本要藉此親近禮芸,偏給影月進來破壞了。影月呢,却是巴不得留下來,和宗旺多接近一下,因此,她把禮芸寫好的信塡上上款成宗旺先生,下暑蘇影月謹約。
原來,宗旺有意要禮芸寫信,不過暗示約他明天到公園相見。現在給影月加上名字,變了蘇影月約宗旺了。這一下,宗旺反而不知如何脫身?
再說,皇甫嘯霞從來就有意於影月,如今看影月進了經理室,便借故進去看看究竟。
宗旺巴不得他進來,忙說:「很好很好,我跟你一道去!」也不和影月打話,便匆匆跑出。
這裏,倒恨得影月牙癢癢的。
女宿舍裏,影月問禮芸:「經理約你明天到公園玩耍談心麼?」
禮芸把咀一呶:「別吃乾醋啦,我不會把你的宗旺搶去的,難道你不曉得我有個「報紙情人」嗎?」
影月訕訕的跑開:「我也得向崔鶯解釋。」
人心躡手躡脚跑到禮芸身後,悄悄的看她寫信,但見她寫着:「吹花先生:今日請在公園池畔見面,我穿白外衣爲號。紅葉謹約。」
禮芸囘頭,不禁啐了人心一口:「你這小鬼,偷偷摸摸的幹嗎?」
人心涎着臉:「我以爲你畫畫兒。」
「好極了,替我把信送到報社去。」
可是人心這小鬼頭却把信公開在宗旺面前。宗旺這纔明白,紅葉女士竟是孟禮芸,吹花先生正是梁珊白,因爲珊白也在此時寫信給紅葉女士。而彼此却幷不淸楚對方就是終日舌劍唇鎗的同事哩。
但是宗旺偏要把這底蘊瞞着珊白,他瞧珊白也在那裏聚精會神寫信給紅葉女士,便說:「珊白,假如紅葉女士就是孟禮芸,你會不會愛她?」
「別開玩笑,她一天到晚跟我嘔氣,那怎麽就會是紅葉女士?」珊白拿着信稿匆匆跑出。
宗旺曉得珊白送到報紙的信稿,是通知紅葉女士,淸明放假,擱筆一天。所以,他决定將計就計,李化桃僵,準備明天到花園會晤孟禮芸。
幷且,當珊白寫給紅葉女士的通訊稿送到報社時編輯早下班囘去,小廝不敢直接送往排字房,只隨便放下算了。
可是禮芸約晤吹花先生的通訊稿却給送到排字房去了。
這樣的誤會,正好給宗旺以難得的機會。
于是宗旺大清早便穿着停當跑到公園去。——他的對像自然是孟禮芸。
蘇影月大淸早也跑到公園來。——她的對像是成宗旺。
皇甫嘯霞大清早也摸到公園來。——對像却是蘇影月。
孟禮芸自然也在公園裏等。——這個紅葉女士,她要等的不過是吹花先生而幷非梁部長珊白。
這時間,成宗旺便發現了孟禮芸,他連忙上前爲禮,裝得斯斯文文的樣子:「呵!紅葉女士,小生就是吹花先生。」
禮芸不勝驚愕:「你是……?」
宗旺情不自禁,便要來拖禮芸,禮芸連忙掙脫:「唷唷,編輯說吹花先生一表斯文,如何就像你這般魯莽!」
宗旺只好耐着性子坐下。
禮芸說:「吹花先生的詩寫得如此雅典的,對詩詞儘是很有硏究?儘是讀了不少古詩啦?」
宗旺不能不裝腔,點頭稱是。
禮芸說:「那麽你高興誰家的詩作?」
「呵,自然是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我是說我國詩人,而他,却是外國貨!」
「哎!我想起來了,是……是那吃醉酒,便吟唐詩的那一位,後來……後來……」
禮芸把笑聲悶在肚裏:「那麼,那詩人的詩你最高興的一篇麼?」
這可把宗旺弄得手足無措,開口不得。
禮芸站起來:「你慢慢想慢慢唸呵……」說着一直的跑開去。迎面却來了報社裏的編輯,原來他早上囘到報舘,得悉原因,覺得非馬上到公園來通知紅葉女士不可。
禮芸聽說,自是笑不可仰。
禮芸和編輯跑開,影月也找到來了,她看宗旺呆坐那裏沉沉吟吟的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便說:「成經理眞够風雅,大淸早便獨坐公園唸詩了。」
宗旺愕然囘視:「唔,是你…?孟小姐呢?」
「孟小姐和她的男朋友去了。成經理,難得有今天的空閒,我們坐下暢談暢談。」影月担着一雙充滿希望的眼睛。
宗旺幷沒有滿足影月的願望,他隨便應了兩句囘頭便跑。
影月又恨又惱,要趕上宗旺時,嘯霞却從後趕來,呼喚着她的名字。影月一心一意只惦念着宗旺,對嘯霞的邀請自然無心理會。
眞是無巧不成話,嘯霞給影月冷落在一邊,正惱恨影月的無情,那曉得,崔鶯却從後趕來,一手拖着嘯霞:「嘯霞哥,難得有這樣好天氣,我們何不趁此談個暢快。」
崔鶯是「神女有心」嘯霞則「襄王無夢」,在如此情形之下,崔鶯不過留得一片痴心的失望。
10
第二天,珊白掃墓囘來,從報紙副刊上看到紅葉女士的通訊約晤,而自己的通訊却沒有刊出,不禁又是着急又是激動,連忙搖了個電話給編輯,請他代約紅葉女士,再在公園相晤。
禮芸接到編輯的電話,疑假疑眞,便要和影月商量,影月說:「我怕是成宗旺假冒吹花君。」
「所以,我想請你替我去一看究竟。」禮芸說。
11
當然影月巴不得能在公園看到宗旺,可是,說來奇怪,她在公園看到的不是成宗旺,也不是什麼吹花君,而是梁珊白部長。
珊白見影月在那裏來東張西望,說:「你看到紅葉女士沒有?」
影月搖搖頭:「我不認識。請問你,成經理曾到這裏來?」
兩人都無所獲,怏怏而囘。
影月囘到宿舍,把經過吿訴禮芸,禮芸自翩聰明,認爲宗旺儘以珊白做說客,要珊白說服自己,和宗旺結婚。
影月亦以爲然,兩人越想越覺好笑,笑聲把宿舍裏的人都愕住了。
至于珊白,因爲始終未曾一晤紅葉女士,就像害了單相思一樣,弄得寢食不安。末了,還是再電吿編輯,請再約紅葉女士於第二天下午八時,到「六香酒家」相晤,他說:「麻煩編輯先生轉吿紅葉女士,她襟上最好飾以紅玫瑰。」
12
這一天,成宗旺不知爲了什麽原因,突然到唱片部檢査營業狀况,當他發覺職員們自撰的樂曲唱片銷路不佳,便肆意批評,珊白按捺不住,悻悻的說:「那麽,要怎樣的樂曲才收暢銷之效?」
宗旺舉出自己最近撰作的「風流皇帝」爲例,幷且引吭高歌,說必可招徠顧客,誰知歌還未了,顧客早紛紛皺眉退出,弄得局面非常尷尬。就是痴心一片的影月,也不好意思糊亂鼓掌。
要不是史九這時遞了一封信給宗旺,替他解圍,宗旺倒不知如何「下台」?至少,他現在可以借拆信這幌子,去掩飾他心裏的煩惱與慌亂,幷且,他還馬上把內容吿訴衆人,以分散衆人的注意,他說:「XX日報就要舉行義唱籌款,請我們公司全體人員義務演唱,相信大家總不會提出反對吧?那麽,等一會下了班,大家都到我那裏計劃計劃。」
大家都因爲有表演機會而感到興奮,但「梁山伯派」的珊白和英黛與演出「粱山伯與祝英台」一劇。「華麗緣派」的孟禮芸和皇甫嘯霞則要演出「孟麗君」,因爲相持不下,結果,大家决定不演劇而只登台唱曲。
13
黃昏時分,珊白因爲約了紅葉女士,禮芸也因爲吹花君約了她,所以兩人都穿着得整齊大方,同赴「六香酒家」之約。
自然,彼此都不曉得對方就是所約的「報紙情人」。
這底細,宗旺是知道的,所以,他有意要使珊白難過,覷準珊白去了,立刻貼了一紙通吿在宿舍門前,寫的是:「各職員注意,下午九時以後,不得進入宿舍,如違面斥。」下暑經理成宗旺。
再說禮芸到了「六香酒家」,正要把玫瑰花別在襟頭,誰知斜剌裏來了兩條醉漢,追追逐逐嚇得她把花也失掉。
禮芸旣然失掉攻瑰花,所以,「六香酒家」裏,雖和珊白碰頭,也不曉得對方便是所約的「報紙情人」。
幷且,他們不但錯過了這難得的機會。甚至,珊白因爲看到宿舍門前的吿示,認爲宗旺有意向他爲難,憤而留下了一封信辭職離去。禮芸呢,也爲了第二天宗旺的査根究底,問長問短,認爲宗旺存心侮蔑,一氣之下,憤而辭職不幹。
這一下,可把英黛和嘯霞着急死了,英黛說:「義唱會過兩天便要舉行,沒有了他們兩人,如何是好?」
嘯霞說:「我看不妨搖電話給編輯先生,他不會不知道踪跡的。」
果然,那編輯剛和嘯霞通過話,珊白的電話便來了:「六香酒家始終看不到襟上有玫瑰花的女士,我想,最好由編輯當面給我們介紹了。」
編輯說:「也吧,我們就在義唱會之夕見面吧。」
14
這裏,不妨補叙一筆,原來英黛和宗旺從小在鄕便給父母作主,定了婚嫁,宗旺和英黛都是年靑人,因爲雙方不但未經戀愛,甚至連對方是什麽樣人也不曉得。這一來,英黛在無可奈何之下,悄悄逃出鄉下,跑到城市來自食其力。
同樣,成宗旺也因爲不滿盲婚,匆匆離鄕,得友人的助力,開了這一爿百貨公司。
誰知無巧不成話,英黛正投在宗旺的公司裏當職。
所以,當宗旺和英黛雙方的父母從報紙上讀到義唱會的消息,看到義唱會登台的照片,不禁拈鬚微笑,不禁鼓掌呵呵,都說:「想不到這兩個孩子,天天見面……」
15
義唱會舉行之夕,宗旺和英黛的父母都從鄉裏趕來參加,宗旺一見,心裏好不納悶,忙說:「爸,別再迫我好不好?」
他爸說:「誰要迫你?此來的目的就是要你和未婚妻會面會面,看你對她有什麽不高興?」
英黛的父母,也以同樣的對話吿訴英黛,幷且把她帶到宗旺跟前,說:「這就是我們迫你結婚的成先生,你要反對,現在提出也不遲。」
其實,自禮芸離職之後,宗旺的靑春熱情,便轉而傾注于英黛,現在,他們所有的感情不是對于盲婚的抗拒而是喜出望外。
16
珊白和禮芸現在也依約而來宗旺忙上前相迎,緊緊握着珊白的手,請他原諒:「就是孟小姐也請原諒我的一時衝動,今後,我們應該像最相得的朋友,共謀發展。」
珊白和禮芸自然不好說什麽,何况他們一心惦記着的不過是紅葉女士和吹花君。
珊白於環視一遍之後,悄俏對報社的編輯說:「你說替我約晤紅葉女士呢?」
編輯說:「何必着急,等一下便知分曉。」
游藝節目開始,編輯代表報社當了宣佈員,他興高彩烈的當着米高風向衆宣佈:「第一項節目,請梁珊白先生,卽我們報上詩詞欄內的吹花君和孟禮芸小姐卽詩詞版上的紅葉女士合唱梁山伯與祝英台!」
在掌聲雷鳴之下,珊白和禮芸不禁相視而笑,這一笑,包含種種複雜的無須言語表白的情緖。
第二個節目,是宗旺和英黛合唱「見面不相識」。
第三個節目,是嘯霞和影月合唱「人有我有」。
第四個節目,是人心,史九,崔鶯合唱的「皆大歡喜」。
在笑聲與掌聲底歡愉的節奏中,他們和她們的心早已溶成一片!(全書完)
人物介紹
鄭惠森
朝氣蓬勃,有如生龍活虎!這是鄭惠森的寫照。就憑了這股剛勁之氣,一年來,電影廣吿上,幾乎天天都有鄭惠森的名字。可是,他却并不因此傲人,說實話,他比前越發謙虛,越發勤於學習。有人說,一九五二是鄭惠森雄霸影壇的一年。(林)
黃金愛
黃金愛給人的印象,使人越發覺得她比黃金還可愛。可能,黄金愛這名字之來,本義在此。我們看她在片塲裏跑跑跳跳,忽而像六七歲的小丫頭,忽而像將屆成熟之年的姑娘,總之她變幻多端,無一而不使人可愛。(林)
梅珍
愛哭便哭,愛笑便笑,愛罵便駡,愛打便打,這是梅珍的可愛處,這是梅珍的所以使人覺得她純眞謹厚,沒有矯飾也沒有虛僞。但是這樣的性格在這樣的社會裏終究要吃虧的。所以,論者以爲,梅珍應該把感情放到工作上。(林)
春色滿華堂
四海影業公司出品
監製 胡維
編導 馮志剛
製片 周錦
小說改編
美術編輯
林擒
天色微明,市街上的店子還關着門,還沒開始做生意。
大路百貨公司的小職員史九,早漱洗完畢,換上衣服,挨在門前聊閒天。他吹着口哨,眼睛左溜右轉。
少女人心也是公司裏的侍應生,她長得伶俐漂亮,一有空便拖着「雪屐」隨處溜。
在南方,因爲天氣溫暖,沒有眞正的溜冰塲,人們的所謂溜冰,不過是穿了「雪屐」在人做的溜冰塲團團轉。人心是溜「雪屐」能手,她看到史九,便有意嚇唬他:「小心!提防把你碰倒!」
史九瞟了她一眼:「別忙,要提防該是你自己。等會梁部長瞧着,又要說你是頑皮小鬼頭了。」
人心伸了伸舌頭,囘頭看時,梁部長果然來了。
梁部長是個細緻人物,眼睛烏溜溜的,常愛沉思默想。原來,他除了生就一條動人的嗓子,還做得一手好詩詞。照理,他該是一個藝術家才對。
這幾天來,他正在聚精會神於一家報紙的讀者欄上詩詞酬答。因爲有一個署名吹花和署名紅葉女士的讀者每天的詩詞唱和引起了他大大的興趣。
人心和史九見了他忙點頭道早,可是他咀裏答應,眼睛還是傾注于手上的報紙。
瞧着那模樣,兩個小鬼頭都覺得好笑,人心說:「西藥部的孟禮芸姐姐也是一個模樣,總愛讀什麽詩詞歌賦。」
「所以呀,我說梁部長和芸姐姐眞是志同道合。」史九隨和着。
「再說一遍,是誰?」梁珊白眼睛一轉。
「還有誰?還不是孟禮芸。」史九把咀呶,大家囘頭看時,孟禮芸也正全神貫注的拿着報紙從那邊來了。
「孟禮芸?志同道合?我才不高興跟她一道呢。除了事事頂撞,她從沒和我說一句好話。」
話雖然這麽說,對於孟禮芸的天天注意讀報上的詩詞,珊白也不能不感到詫異,也不能不伸着脖子偷瞧一下。
而這一下,却也證明珊白不說的錯,至少,孟禮芸看他伸着脖子,立刻便開口啐他:「什麽値得偷偷摸摸的!要看,不好說一聲嗎?」
珊白把手上的報紙一揚:「別意得!報販有的是...…。」
要不是祝英黛從外進來,移轉了禮芸的目標,兩人又要大耍唇鎗舌劍了。
禮芸挽着英黛的臂灣:「你眞早,爲什麽不多休息一下?」
英黛嫣然一笑,這一笑,是表示她對禮芸的感謝。
忽然,人心像想到了什麽:「哎喲,我想着了,黛姐姐叫祝英黛,梁部長叫梁珊白,我叫人心,九哥是史九,都和「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裏的名字相同,要是我們演一齣這故事的戲,人家瞧着演員表,不是很有趣麽。」
然而孟禮芸却另有見解,她看英黛跑囘樂器部,便說:「其實,我就覺得祝英台不該配梁山伯。」
史九側着脖子:「爲了什麼?」
「祝英台連多等四天都不能,便改嫁馬家郞了。」
「那麼誰該配梁山伯?」人心說。
「我說孟麗君倒還不錯!」
禮芸這様一說,兩個小鬼頭却咭咭的樂開了:「那卽是說,孟禮芸該配梁珊白呵!」
禮芸暗裏高興咀裏硬,偏說:「誰說我自己?誰高興配……」
珊白自然曉得她要說什麼:「你們這些「華麗緣」,只配和蘇影月,皇甫嘯霞做一路吧了。」
蘇影月也恰在這時上班:「唷唷,梁部長偏高興把人家拖在一起。」
「正是,他專挑我們的不是!」是禮芸的還擊。
英黛無意參戰,只說:「都吃得太飽了,專愛尋是惹非。」
珊白眼睛一眨:「人心和史九的一張咀就够把他們說倒啦,用得着我?」
在這唇鎗舌劍的緊張局勢下,如果不是經理成宗旺乘時而至,還不知要纏到什麼時候。
皇甫嘯霞和梁珊白同樣,也是個對唱曲頂有興緻的風流人物,他是公司裏的高級職員,對招徠之術,頗有心得。這一天,他决定以人心和史九在門前高唱「無任歡迎」一曲以引顧客。憑了人心和史九的伶俐機智,憑了兩人都有一張嘹喨的嗓子和惹笑的動作,顧客們必會大感興趣,聞聲而至。
但成宗旺却不表贊同,他說:「財不入唱家!」
「經理,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唱戲的給人瞧不起,這觀念早成過去。至於唱曲能否吸引顧客,等會便知分曉。」嘯霞朗朗伸辯。
畢竟皇甫嘯霞的說法沒有錯,人心和史九在門前引吭高歌,原來要進公司的固然如蟻赴羶,就是順道而過的,也毫不考慮讓脚步停住。
成經理瞧着顧客像流水似的湧進來,心裏實在高興,實在佩服嘯霞有先見之明,但有錢人總以爲自己是對的,因此,咀裏也不便說什麼了。
偏偏,皇甫嘯霞却只管盯着宗旺笑一下,又囘頭看一下那些潮湧而來的顧客。自然,這種動作一方面證明宗旺的意見是錯的,另一個目的是有意氣他一下。
小心眼的宗旺,不禁兩眼一瞪,掉頭跑進經理室。
嘯霞和別的幾人都爲之樂開了。
一會,人心興高彩烈的連跑帶跳的進來,一手拖着珊白:「梁部長,我們唱得還不錯吧?」
珊白想了一想:「也差不多了。」
史九不服氣:「梁部長,該給我們指點指點呵?」
珊白說:「唱粤曲也和别的歌唱道理一様,首先,應該清清楚楚地把毎一個字唱出,不能含糊,要達到這樣的境地眞也不容易。譬如演粤劇的新馬師曾,便是最懂得這竅兒的。不少曲兒因爲「咬字」清楚,「腔」調常能和內容配合,所以很動人,成爲家傳戶誦的曲子。」
珊白說了,驀地聽得嗤嗤的笑聲,囘頭看時,禮芸正朝着他說:「咬字!看那些字都給你咬爛了!」 珊白怒目而視:「別嘵舌,你憑什麼資格批評?」
影月從旁插咀說:「梁部長,你也感認真,雖說不是誰也懂得歌唱,難道連聽衆要表示一點點感想也要什麼資格不成?譬如我說,你梁部長也不算唱的頂好,你好意思駡我?」
珊白不好發作,訕訕的道:「那麼你說,誰唱得頂好?」
影月說:「祝英黛唱得眞不錯!」
「剛好,她唱了。」禮芸瞇着眼,那意思,是要向珊白示威。
原來英黛正斜靠着身子,向顧客以幽怨悲凉的聲調唱一曲「英台祭奠」。
果然,珊白、禮芸、人心、史九、影月都默然傾聽。
一曲旣終,大家都噓了口氣。
英黛從貨櫥裏拿出一張唱片,以誠懇的口吻對顧客說:「就是這一張,「英台祭奠」,先生總高興吧?」
那人搖搖頭:「不!那太凄慘了,聽了多難過。」
英黛看那人移動脚步,有點着急:「我們還有別種貨式,隨便選擇。」
可是那顧客比她更着急,三步兩步跑出,咀裏只說:「改天買改天買!」
英黛像洩了氣的皮球,軟攤攤的向椅上一躺。
珊白跑到英黛與另一售貨員崔鶯跟前,以一種非常關切的神態道:「你們這種着急的態度,如果我是顧客,也要給你們唬跑。而且,要是他不高興悲涼凄怨的曲子的,便該馬上換給他輕鬆愉快的歌調。」 「但是「英台祭奠」從來是熱門貨呀。」英黛有點不服氣。
「所以,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永遠都是那一套!」珊白强調說。
崔鶯也提出抗議:「部長,你說你有本領,那邊顧客來了,試試你的手段呀。」
珊白昂頭挺胸的:「等着瞧!」
于是,珊白先讓顧客坐下,然後引吭高歌「多情梁山泊」一曲。一點不錯,「運腔」,「咬字」的確不讓當今名伶新馬師曾。
只可惜那顧客幷非知音者,不過是一個小什貨販,所以,纔坐下不久,便呼呼的睡着了。
影月見不對勁,悄悄的通知珊白。可是珊白正在聚精會神,全不曉得。
禮芸偏說:「他不過凝神欣賞吧了。」
一曲旣終,崔鶯推了那顧客幾把:「哎唷!眞的睡着了。」
珊白有點難爲情:「這不是很動聽的曲子嗎?」
顧客勉强的站起來,搖搖欲墮:「對不起,我有點暈眩。」
禮芸和影月只覺好笑,也隨着顧客裝腔作態的嚷頭疼。
珊白禁不住禮芸幾入的訕笑,紅了臉的說:「啐!那傢伙根本不懂。你們何必隨和着!」
人心看珊白和姐姐們劍拔弓張,就要大開「殺戒」,忙跑進經理室,揪着成宗旺:「經理,要不替他們排解,眞要大打出手了。經理,快去快去!」
宗旺趕來時,珊白和禮芸正瞪着眼互相詬駡。
宗旺氣得搖頭頓脚:「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英黛也要排難解紛:「芸姐姐,算了吧,何必爲了我唱得不好大傷和氣哩。」
宗旺還是氣噓噓的說:「罷了罷了!以後工作時間,誰也不許唱曲。英黛一唱,顧客給唱跑了,珊白却弄得顧客昏昏欲睡。何况,我這裏也不是什麽戲園娛樂塲!」
大家瞧經理眞的有氣,都噤不作聲。
宗旺邊跑進經理室,邊通知人心:「請孟小姐進來!」
人心伸了伸舌頭。影月說:「糟了!」
大家儘以爲禮芸要受責駡,其實,禮芸不但沒有被責,相反,成宗旺還嘻着咀請她坐下,裝得很親切的問長問短。
禮芸呢,却以一種愛理不理的神態對付他。
宗旺只好靦覥的說:「唔,就替我寫一通短信吧。是:明天清明節,放假一天,我請你,請你…請你…請你…」
禮芸很不耐煩:「究竟要寫幾個「請你」?」
宗旺給她說得好沒意思:「嘻嘻,是…二個,一個吧了。」
外面,另有一番心事的影月却希望能進經理室一看究竟。
恰巧史九拿了一張「八折單」要經理簽字,影月乘勢道:「我替你拿給經理。」
影月之突然闖進,正如好夢之被驚破,使宗旺大感狼狽,他恨影月,却又沒有可資責駡的把柄,何況影月的進來是爲了本位工作。
相反,影月的進來禮芸却如獲救星,她立刻拖着影月:「好姐姐,你的文字工夫比我好,你替經理寫信經理一定高興。」
成宗旺本要藉此親近禮芸,偏給影月進來破壞了。影月呢,却是巴不得留下來,和宗旺多接近一下,因此,她把禮芸寫好的信塡上上款成宗旺先生,下暑蘇影月謹約。
原來,宗旺有意要禮芸寫信,不過暗示約他明天到公園相見。現在給影月加上名字,變了蘇影月約宗旺了。這一下,宗旺反而不知如何脫身?
再說,皇甫嘯霞從來就有意於影月,如今看影月進了經理室,便借故進去看看究竟。
宗旺巴不得他進來,忙說:「很好很好,我跟你一道去!」也不和影月打話,便匆匆跑出。
這裏,倒恨得影月牙癢癢的。
女宿舍裏,影月問禮芸:「經理約你明天到公園玩耍談心麼?」
禮芸把咀一呶:「別吃乾醋啦,我不會把你的宗旺搶去的,難道你不曉得我有個「報紙情人」嗎?」
影月訕訕的跑開:「我也得向崔鶯解釋。」
人心躡手躡脚跑到禮芸身後,悄悄的看她寫信,但見她寫着:「吹花先生:今日請在公園池畔見面,我穿白外衣爲號。紅葉謹約。」
禮芸囘頭,不禁啐了人心一口:「你這小鬼,偷偷摸摸的幹嗎?」
人心涎着臉:「我以爲你畫畫兒。」
「好極了,替我把信送到報社去。」
可是人心這小鬼頭却把信公開在宗旺面前。宗旺這纔明白,紅葉女士竟是孟禮芸,吹花先生正是梁珊白,因爲珊白也在此時寫信給紅葉女士。而彼此却幷不淸楚對方就是終日舌劍唇鎗的同事哩。
但是宗旺偏要把這底蘊瞞着珊白,他瞧珊白也在那裏聚精會神寫信給紅葉女士,便說:「珊白,假如紅葉女士就是孟禮芸,你會不會愛她?」
「別開玩笑,她一天到晚跟我嘔氣,那怎麽就會是紅葉女士?」珊白拿着信稿匆匆跑出。
宗旺曉得珊白送到報紙的信稿,是通知紅葉女士,淸明放假,擱筆一天。所以,他决定將計就計,李化桃僵,準備明天到花園會晤孟禮芸。
幷且,當珊白寫給紅葉女士的通訊稿送到報社時編輯早下班囘去,小廝不敢直接送往排字房,只隨便放下算了。
可是禮芸約晤吹花先生的通訊稿却給送到排字房去了。
這樣的誤會,正好給宗旺以難得的機會。
于是宗旺大清早便穿着停當跑到公園去。——他的對像自然是孟禮芸。
蘇影月大淸早也跑到公園來。——她的對像是成宗旺。
皇甫嘯霞大清早也摸到公園來。——對像却是蘇影月。
孟禮芸自然也在公園裏等。——這個紅葉女士,她要等的不過是吹花先生而幷非梁部長珊白。
這時間,成宗旺便發現了孟禮芸,他連忙上前爲禮,裝得斯斯文文的樣子:「呵!紅葉女士,小生就是吹花先生。」
禮芸不勝驚愕:「你是……?」
宗旺情不自禁,便要來拖禮芸,禮芸連忙掙脫:「唷唷,編輯說吹花先生一表斯文,如何就像你這般魯莽!」
宗旺只好耐着性子坐下。
禮芸說:「吹花先生的詩寫得如此雅典的,對詩詞儘是很有硏究?儘是讀了不少古詩啦?」
宗旺不能不裝腔,點頭稱是。
禮芸說:「那麽你高興誰家的詩作?」
「呵,自然是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我是說我國詩人,而他,却是外國貨!」
「哎!我想起來了,是……是那吃醉酒,便吟唐詩的那一位,後來……後來……」
禮芸把笑聲悶在肚裏:「那麼,那詩人的詩你最高興的一篇麼?」
這可把宗旺弄得手足無措,開口不得。
禮芸站起來:「你慢慢想慢慢唸呵……」說着一直的跑開去。迎面却來了報社裏的編輯,原來他早上囘到報舘,得悉原因,覺得非馬上到公園來通知紅葉女士不可。
禮芸聽說,自是笑不可仰。
禮芸和編輯跑開,影月也找到來了,她看宗旺呆坐那裏沉沉吟吟的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便說:「成經理眞够風雅,大淸早便獨坐公園唸詩了。」
宗旺愕然囘視:「唔,是你…?孟小姐呢?」
「孟小姐和她的男朋友去了。成經理,難得有今天的空閒,我們坐下暢談暢談。」影月担着一雙充滿希望的眼睛。
宗旺幷沒有滿足影月的願望,他隨便應了兩句囘頭便跑。
影月又恨又惱,要趕上宗旺時,嘯霞却從後趕來,呼喚着她的名字。影月一心一意只惦念着宗旺,對嘯霞的邀請自然無心理會。
眞是無巧不成話,嘯霞給影月冷落在一邊,正惱恨影月的無情,那曉得,崔鶯却從後趕來,一手拖着嘯霞:「嘯霞哥,難得有這樣好天氣,我們何不趁此談個暢快。」
崔鶯是「神女有心」嘯霞則「襄王無夢」,在如此情形之下,崔鶯不過留得一片痴心的失望。
10
第二天,珊白掃墓囘來,從報紙副刊上看到紅葉女士的通訊約晤,而自己的通訊却沒有刊出,不禁又是着急又是激動,連忙搖了個電話給編輯,請他代約紅葉女士,再在公園相晤。
禮芸接到編輯的電話,疑假疑眞,便要和影月商量,影月說:「我怕是成宗旺假冒吹花君。」
「所以,我想請你替我去一看究竟。」禮芸說。
11
當然影月巴不得能在公園看到宗旺,可是,說來奇怪,她在公園看到的不是成宗旺,也不是什麼吹花君,而是梁珊白部長。
珊白見影月在那裏來東張西望,說:「你看到紅葉女士沒有?」
影月搖搖頭:「我不認識。請問你,成經理曾到這裏來?」
兩人都無所獲,怏怏而囘。
影月囘到宿舍,把經過吿訴禮芸,禮芸自翩聰明,認爲宗旺儘以珊白做說客,要珊白說服自己,和宗旺結婚。
影月亦以爲然,兩人越想越覺好笑,笑聲把宿舍裏的人都愕住了。
至于珊白,因爲始終未曾一晤紅葉女士,就像害了單相思一樣,弄得寢食不安。末了,還是再電吿編輯,請再約紅葉女士於第二天下午八時,到「六香酒家」相晤,他說:「麻煩編輯先生轉吿紅葉女士,她襟上最好飾以紅玫瑰。」
12
這一天,成宗旺不知爲了什麽原因,突然到唱片部檢査營業狀况,當他發覺職員們自撰的樂曲唱片銷路不佳,便肆意批評,珊白按捺不住,悻悻的說:「那麽,要怎樣的樂曲才收暢銷之效?」
宗旺舉出自己最近撰作的「風流皇帝」爲例,幷且引吭高歌,說必可招徠顧客,誰知歌還未了,顧客早紛紛皺眉退出,弄得局面非常尷尬。就是痴心一片的影月,也不好意思糊亂鼓掌。
要不是史九這時遞了一封信給宗旺,替他解圍,宗旺倒不知如何「下台」?至少,他現在可以借拆信這幌子,去掩飾他心裏的煩惱與慌亂,幷且,他還馬上把內容吿訴衆人,以分散衆人的注意,他說:「XX日報就要舉行義唱籌款,請我們公司全體人員義務演唱,相信大家總不會提出反對吧?那麽,等一會下了班,大家都到我那裏計劃計劃。」
大家都因爲有表演機會而感到興奮,但「梁山伯派」的珊白和英黛與演出「粱山伯與祝英台」一劇。「華麗緣派」的孟禮芸和皇甫嘯霞則要演出「孟麗君」,因爲相持不下,結果,大家决定不演劇而只登台唱曲。
13
黃昏時分,珊白因爲約了紅葉女士,禮芸也因爲吹花君約了她,所以兩人都穿着得整齊大方,同赴「六香酒家」之約。
自然,彼此都不曉得對方就是所約的「報紙情人」。
這底細,宗旺是知道的,所以,他有意要使珊白難過,覷準珊白去了,立刻貼了一紙通吿在宿舍門前,寫的是:「各職員注意,下午九時以後,不得進入宿舍,如違面斥。」下暑經理成宗旺。
再說禮芸到了「六香酒家」,正要把玫瑰花別在襟頭,誰知斜剌裏來了兩條醉漢,追追逐逐嚇得她把花也失掉。
禮芸旣然失掉攻瑰花,所以,「六香酒家」裏,雖和珊白碰頭,也不曉得對方便是所約的「報紙情人」。
幷且,他們不但錯過了這難得的機會。甚至,珊白因爲看到宿舍門前的吿示,認爲宗旺有意向他爲難,憤而留下了一封信辭職離去。禮芸呢,也爲了第二天宗旺的査根究底,問長問短,認爲宗旺存心侮蔑,一氣之下,憤而辭職不幹。
這一下,可把英黛和嘯霞着急死了,英黛說:「義唱會過兩天便要舉行,沒有了他們兩人,如何是好?」
嘯霞說:「我看不妨搖電話給編輯先生,他不會不知道踪跡的。」
果然,那編輯剛和嘯霞通過話,珊白的電話便來了:「六香酒家始終看不到襟上有玫瑰花的女士,我想,最好由編輯當面給我們介紹了。」
編輯說:「也吧,我們就在義唱會之夕見面吧。」
14
這裏,不妨補叙一筆,原來英黛和宗旺從小在鄕便給父母作主,定了婚嫁,宗旺和英黛都是年靑人,因爲雙方不但未經戀愛,甚至連對方是什麽樣人也不曉得。這一來,英黛在無可奈何之下,悄悄逃出鄉下,跑到城市來自食其力。
同樣,成宗旺也因爲不滿盲婚,匆匆離鄕,得友人的助力,開了這一爿百貨公司。
誰知無巧不成話,英黛正投在宗旺的公司裏當職。
所以,當宗旺和英黛雙方的父母從報紙上讀到義唱會的消息,看到義唱會登台的照片,不禁拈鬚微笑,不禁鼓掌呵呵,都說:「想不到這兩個孩子,天天見面……」
15
義唱會舉行之夕,宗旺和英黛的父母都從鄉裏趕來參加,宗旺一見,心裏好不納悶,忙說:「爸,別再迫我好不好?」
他爸說:「誰要迫你?此來的目的就是要你和未婚妻會面會面,看你對她有什麽不高興?」
英黛的父母,也以同樣的對話吿訴英黛,幷且把她帶到宗旺跟前,說:「這就是我們迫你結婚的成先生,你要反對,現在提出也不遲。」
其實,自禮芸離職之後,宗旺的靑春熱情,便轉而傾注于英黛,現在,他們所有的感情不是對于盲婚的抗拒而是喜出望外。
16
珊白和禮芸現在也依約而來宗旺忙上前相迎,緊緊握着珊白的手,請他原諒:「就是孟小姐也請原諒我的一時衝動,今後,我們應該像最相得的朋友,共謀發展。」
珊白和禮芸自然不好說什麽,何况他們一心惦記着的不過是紅葉女士和吹花君。
珊白於環視一遍之後,悄俏對報社的編輯說:「你說替我約晤紅葉女士呢?」
編輯說:「何必着急,等一下便知分曉。」
游藝節目開始,編輯代表報社當了宣佈員,他興高彩烈的當着米高風向衆宣佈:「第一項節目,請梁珊白先生,卽我們報上詩詞欄內的吹花君和孟禮芸小姐卽詩詞版上的紅葉女士合唱梁山伯與祝英台!」
在掌聲雷鳴之下,珊白和禮芸不禁相視而笑,這一笑,包含種種複雜的無須言語表白的情緖。
第二個節目,是宗旺和英黛合唱「見面不相識」。
第三個節目,是嘯霞和影月合唱「人有我有」。
第四個節目,是人心,史九,崔鶯合唱的「皆大歡喜」。
在笑聲與掌聲底歡愉的節奏中,他們和她們的心早已溶成一片!(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