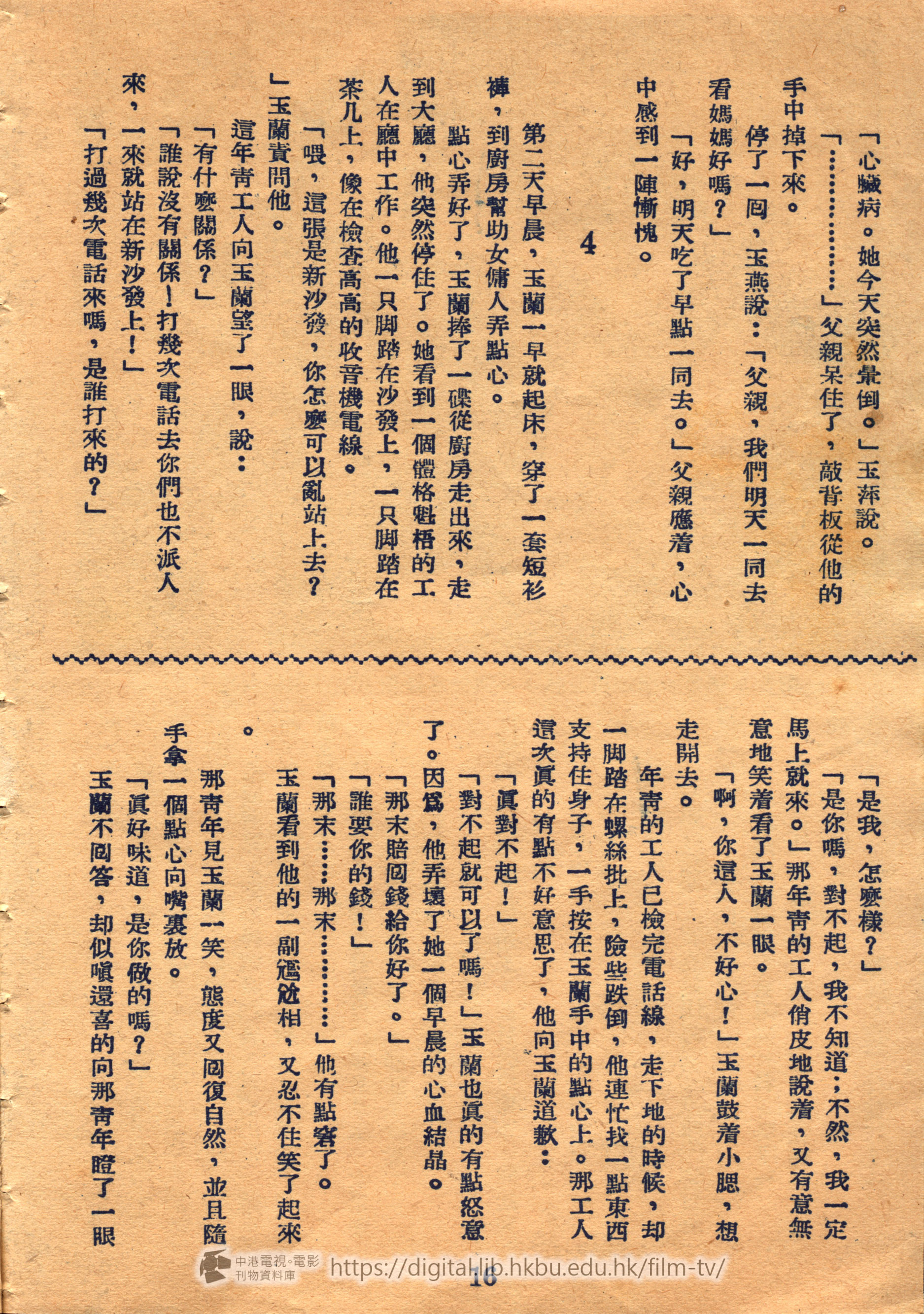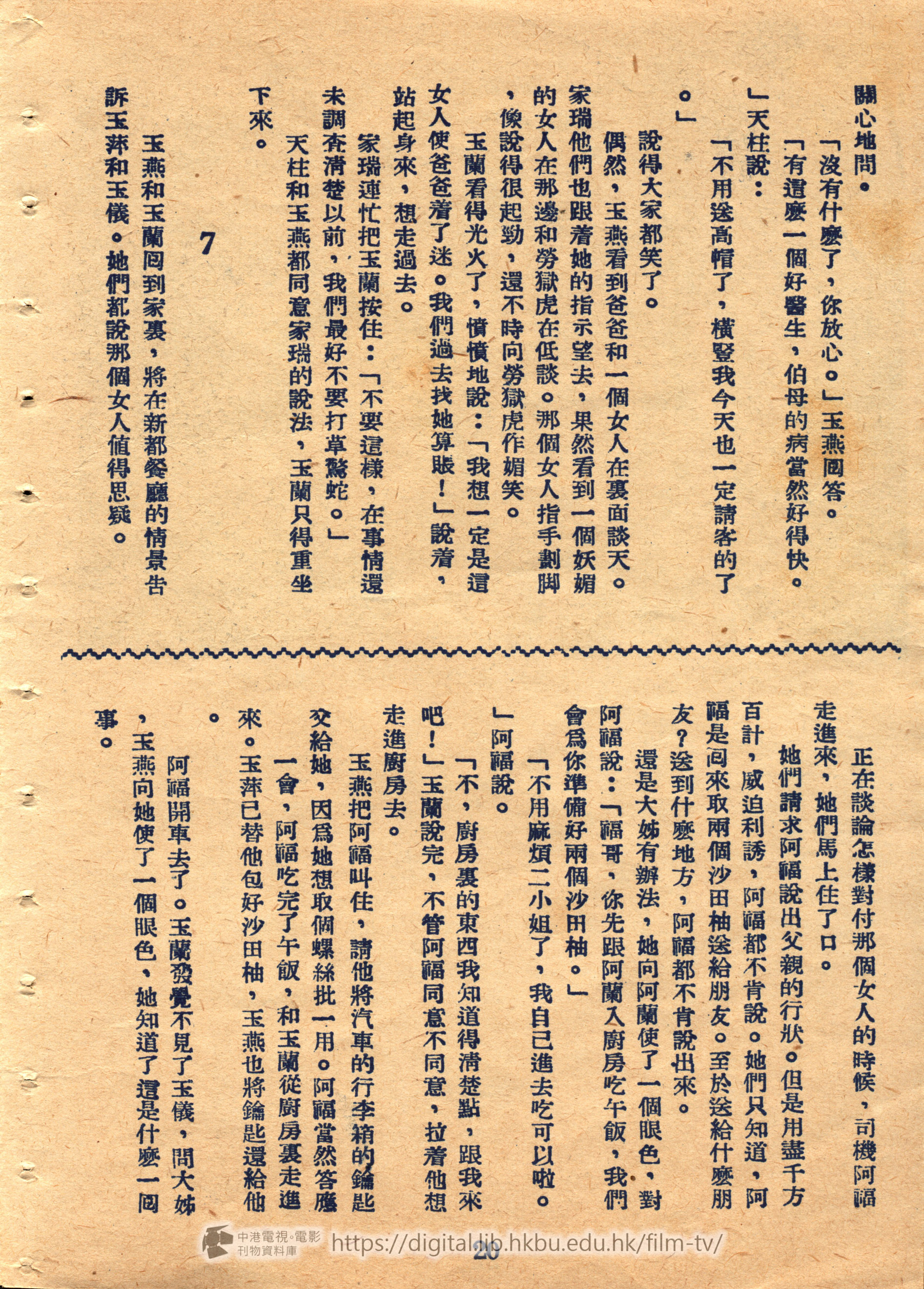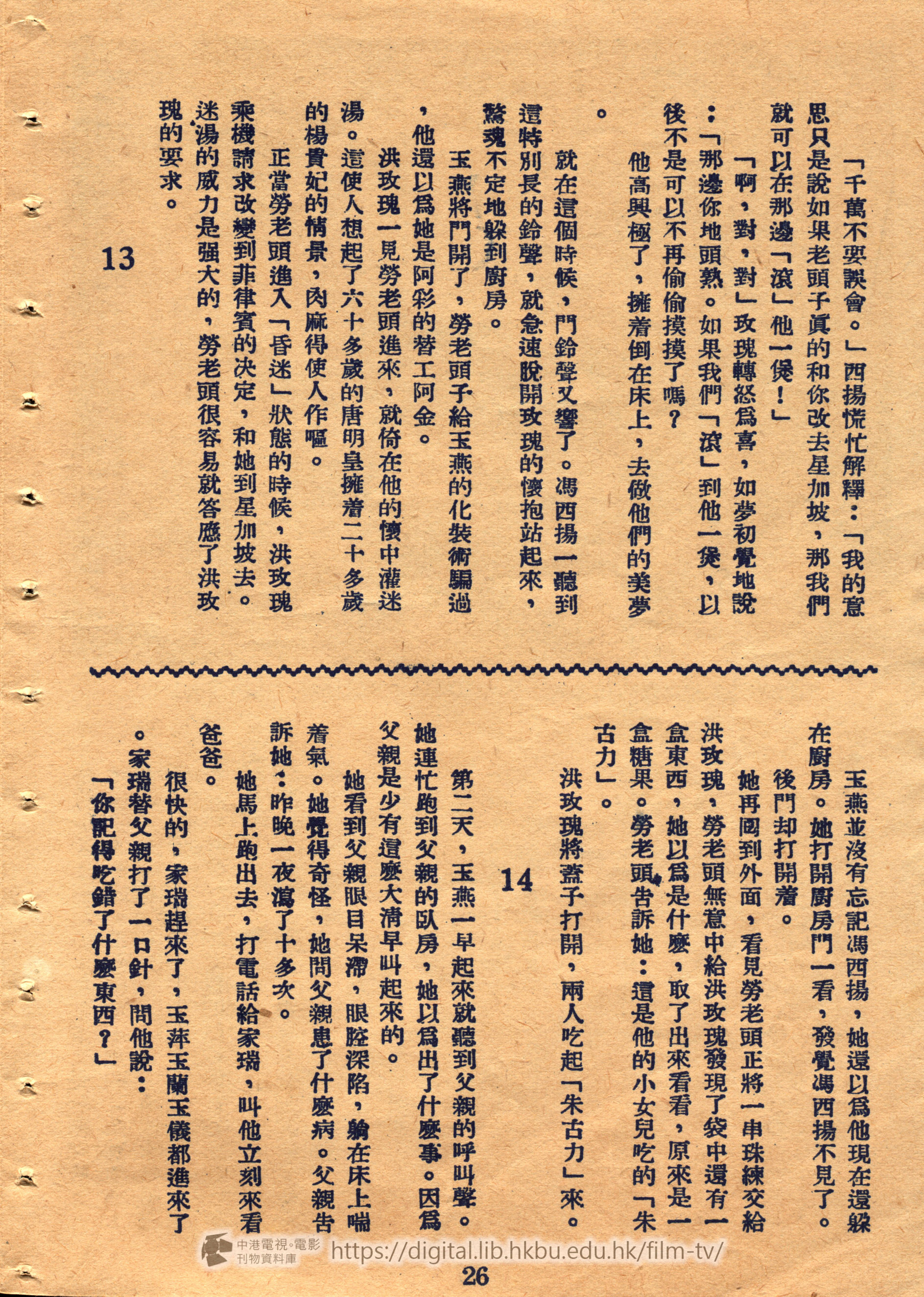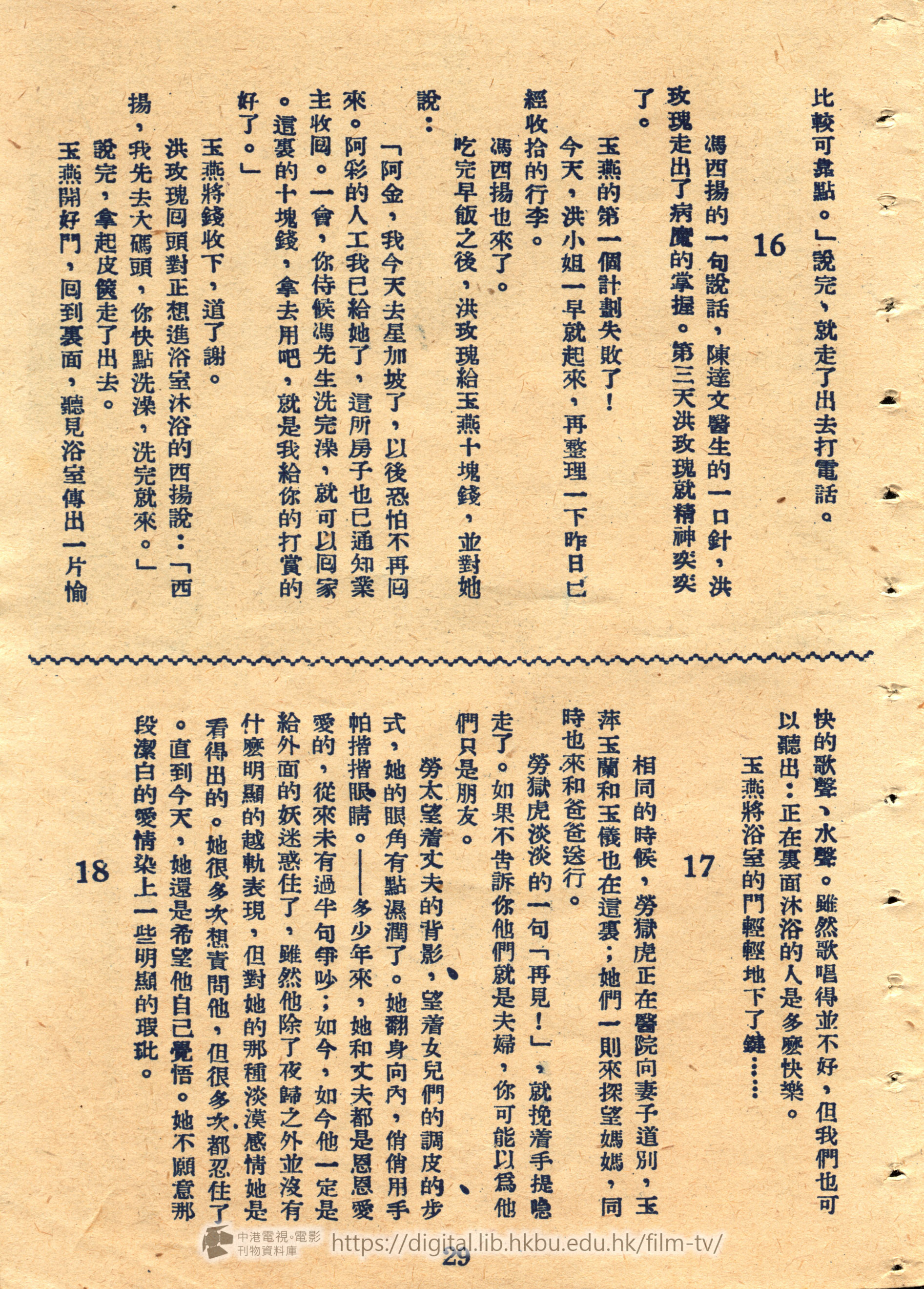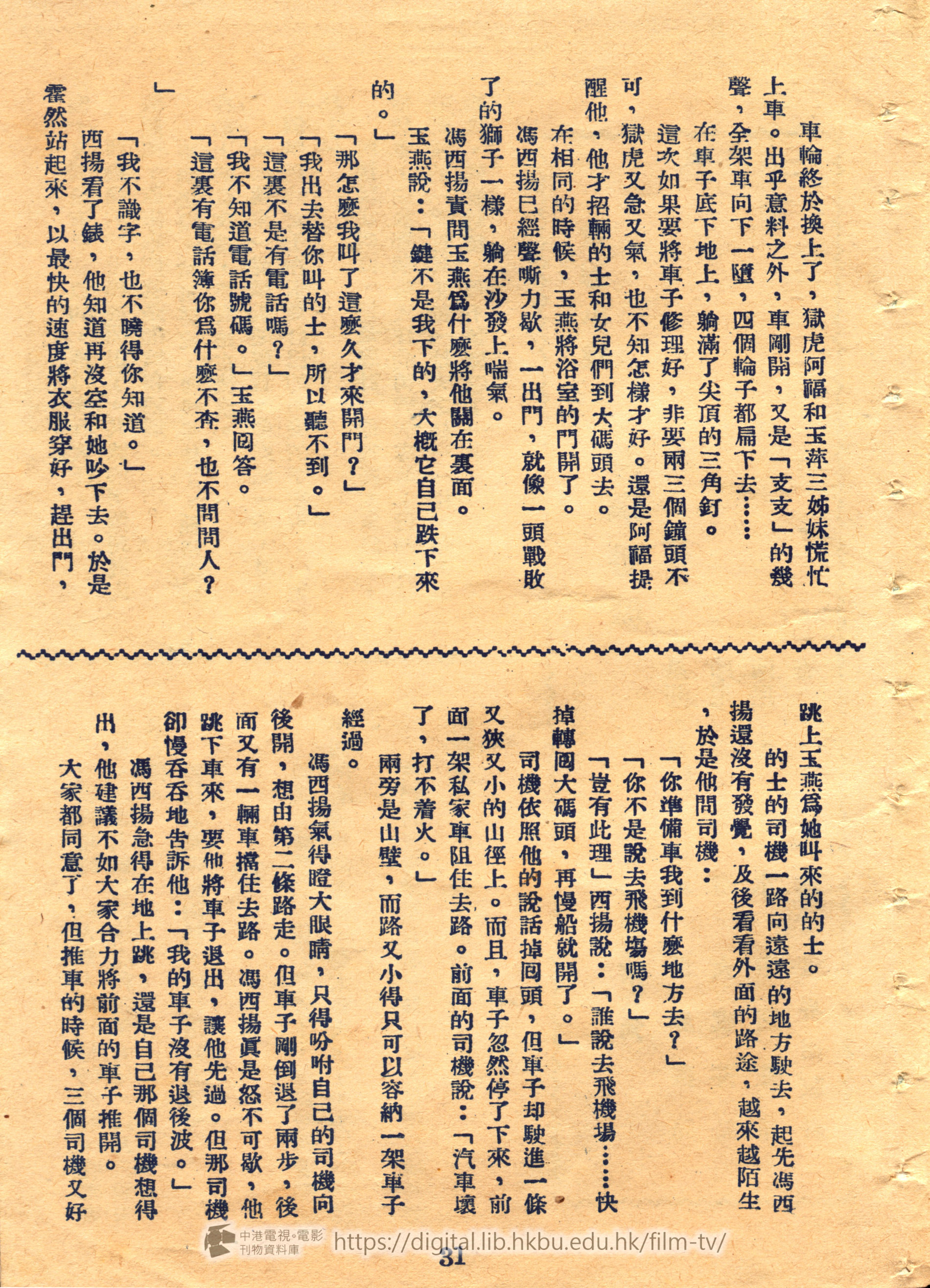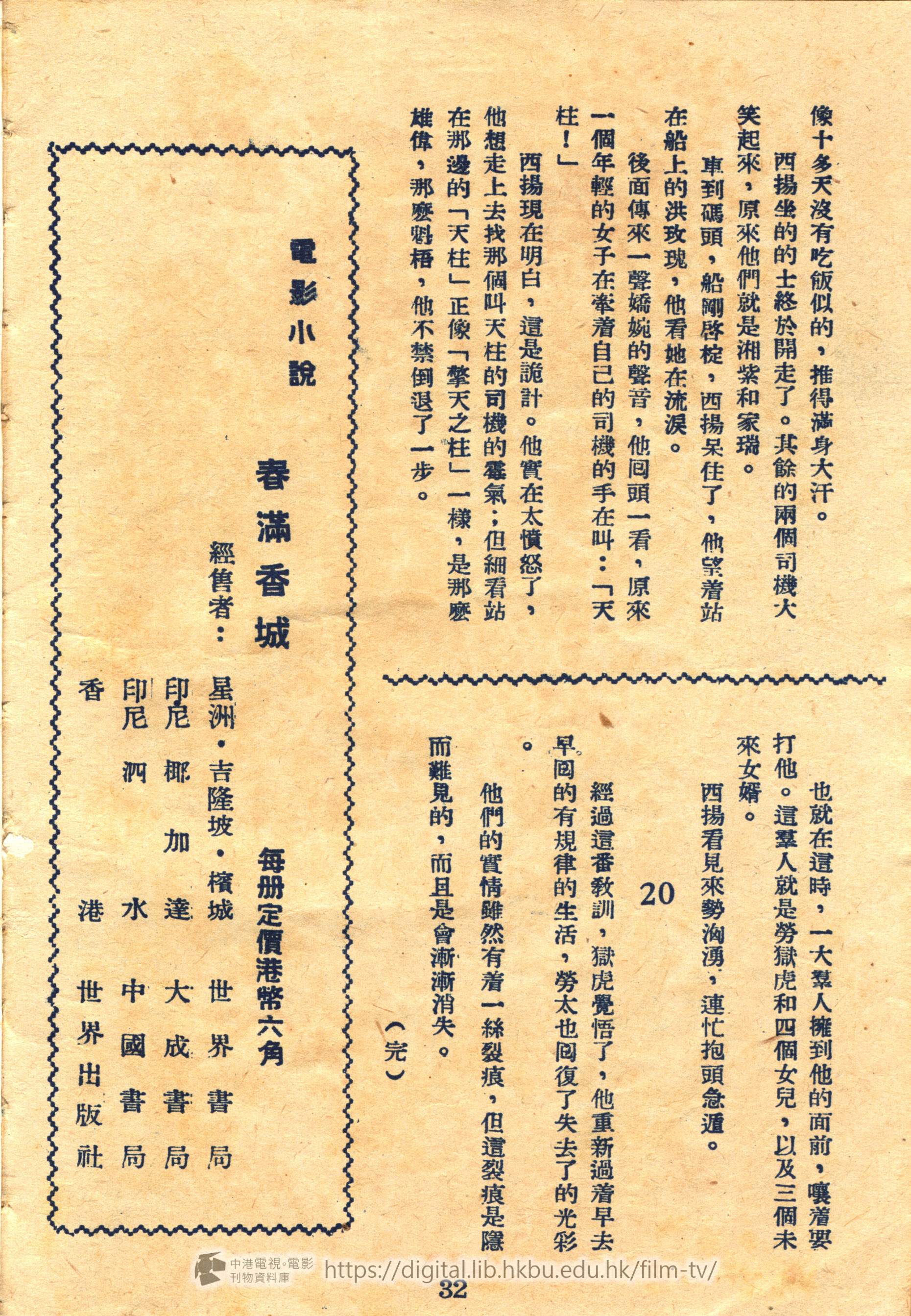人物介紹
二小姐•芳艳芬
芳艶芬在這裏演二小姐,她的角色不但和紫羅蓮、容小意有同樣的重要,並且顯出非常獨特的風格。當然,因爲她是一個以唱工著名的紅伶,這裏自免不了賣弄一下。只是,編導者認爲,她更應該賣弄的是已臻純煉的演技。(林)
吳楚帆
幾乎沒有一部粤語片能離開吳楚帆,為什麽呢?其實,單從吳楚帆面貌與身段那雄偉的線條去着眼,就覺得他眞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鄭惠森
一九五二年開始,鄭惠森以一種挑戰的姿態在影壇縱橫馳聘。他一方面使製片家和導演們感到興奮和喜悦,也使許多前輩不得不步步爲營。但鄭森惠很謙虛很坦白,他說他雖然經常在主演六七部影片,決不因此自滿,他認爲仍應向前輩學習。所以我要說,鄭惠森眞是個好傢伙!(林)
編導:莫康時
編導者莫康時是影界最得人望的君子。我們說他君子,固然因爲他的處世態度,又和平又忠實,但主要還是爲了他在工作上的沉着、不苟與從容。在粵語影界,要做到沉着,不苟與從容眞不容易,一切都是那樣的匆促,一切都是那樣的煩瑣,一切都是那樣的混噩,而莫康峰却不爲這種浪潮所淹沒,他還保持過去一樣的「臨危不亂」,非君子而何?(林擒)
春滿香城
小說改編 藍菲
美術編輯 林擒
1
戲台上,名伶鄧湘紫正在演戲。
他看到台下的玉萍,向她點頭微笑,玉萍也輕輕地向他瞟了一眼。
這場戲外戲給大姊玉燕和三妹玉蘭看到了,都取笑起她來。玉蘭說:
「今晚湘哥做得特別好!」
「當然啦,因爲今晚二姊來了。」玉蘭說。
「屁話,我又不是今晚才來的。」
「卽就是因爲你今晚的眼角拋得特別出色啦。」玉蘭說得臉也紅了起來。
剛巧這時幕下了,玉萍連忙站起來,想離開她們的圍攻:
「我不和你們說,我上後台去。」
玉蘭看見她想逃了,把她拉住:
「想去會情人嗎?可以,先拿十塊錢來!」
「給你好了,我的好妹妹。」玉萍從手袋裏取了十元給玉蘭,輕鬆地走向後台。
玉萍走了不多久,大堂閘口處起了一陣嘈雜聲。一個女孩子的聲音說:
「爲什麼不讓我進去,你以爲我想看霸王戲嗎?」
玉蘭她們聽出這就是四妹玉儀的聲音。
「玉儀爲什麼走出來呢?」玉燕說。
「我們出去看看!」
她倆走到閘口、看見果然是玉儀和守閘的在爭論。
玉儀看見大姊和三姊來了,就將來意一五一十的吿訴了她們。原來她們的媽剛才在家暈倒了,玉儀已立刻將她送進醫院,請玉燕的摯友張家瑞替她們診治。
這消息像霹靂一樣震驚了她們的神經。母親是很少有病的,何況一病竟然暈倒。她們連忙上後台找同玉萍去看媽媽。
2
她們乘了車子,趕到醫院,由玉儀領前,以最高的速率奔到母親的旁邊,圍着母親問長問短。
勞太看見女兒們這麼關心地慰問着,反而安慰起她們來:
「你們不用担心,過幾天就可以出院了。家瑞說這是輕微的心臟病。在這裏,家瑞會好好看護我的。」
「看護未來岳母當然格外留心!」小妹妹玉儀取笑起大姊姊來。
「玉儀,你說什麽?」大姊舉起手,要打玉儀。玉儀笑着,避開了。
「玉燕,」家瑞說:「我和你到配藥室去配點藥。配藥室的工作人員巳經下了班,我不好意思再麻煩他們。」
玉燕巴不得和他逃出去,免得在這裏給小妹妹取笑。
在配藥室裏,家瑞對玉燕說:
「你有沒有發覺你媽有什麼隱憂?」
「沒有,」玉燕囘答:「只是她近來不大喜笑。」
「你知到這是什麼原因?……譬如,你爸近來有什麼軌外行動?」
「也不覺得。」玉燕想了一想,又說:「只是爸爸近來好像晚晚都很夜才囘來。」
「唔……」家瑞說,「也許就因爲這點,你最好囘去多留意。」
3
夜深了,她們囘到家裏。
玉燕問女傭人,知到父親還未向來。她心中馬上浮起一種同情母親的感想:
近半年來,父親總是深夜才囘來,打破了以前「早出早囘」的慣例。母親近來也很少笑,沉默得多了。——這並不是偶然的,而且,這可能是有關聯的。剛才家瑞不是明明對我說過,母親除了心臟病,好像還有點隱憂嗎?母親是不喜歡將心事吿訴人的,說不定她的心中隱着什麽痛苦。
玉燕將自己的心事吿訴了三個妹妹,原來她們都有同樣的感覺。
他們都一致認爲,她們是應該負起保持家庭幸福的義務。經過一番商討,她們成立了一個協議:凡是破壞她們的家庭幸福的,她們都聯合起來,抗拒到底;並且選出大姊爲總司令,先由大姊領導大家起了誓,以後由大姊領導一切,指揮一切。
她們正說得起勁的時候,忽然門外傳來一陣汽車的煞止聲,打破了黑夜的沉寂。
她們連忙跑出露台,看見下面門口停了一架的士,車門看了,她們的父親勞嶽虎走下來,回身和一只從車廂裏伸出來的手緊握。她們從高處看下來,看不到車裏坐着一個怎麽樣的人但她們清楚地聽到,有一個嬌響的聲音自車內傳出來,向她們的爸爸說「拜拜!」
汽車開去了,接着聽到父親上樓的聲音,一步輕一步重的。
她們走下去,將父親摻扶着進了房,父親一進房就倒在椅上昏昏地睡着了。一陣陣的酒氣撲到她們的臉上,她們感到不好受。
玉儀看見父親醉得這麽利害,就走出取一枝水槍,吸了水,向着父親的面上射去。玉燕她們想來阻止也來不及。
父親醒來了,當他發覺自己滿身是水,女兒圍着自己大笑的時候,他大怒了,漲紅了臉說:
「你們想作反嗎!誰用水來射我?」
「爸爸,是我。」玉儀說着,將平日父親用來打她們屁股的敲背板送上,並且轉身俯下,聳起屁股,請父親打她。
「豈有此理!」父親舉起板手,想重重的打下去。
玉燕連忙拉住他的手,說:
「不要打她了,實在她因爲想立刻叫醒你吿訴你一件事情,可是你一進門就醉倒了,所以——」
「所以她就應該用水槍來對付我了嗎?」
「這只是她急昏了,她想立刻吿訴你媽進了醫院。」玉蘭說。
「什麼?媽媽進了醫院?患了什麼病?」
「心臓病。她今天突然暈倒。」玉萍說。
「………………」父親呆住了,敲背板從他的手中掉下來。
停了一囘,玉燕說:「父親,我們明天一同去看媽媽好嗎?」
「好,明天吃了早點一同去。」父親應着,心中感到一陣慚愧。
4
第二天早晨,玉蘭一早就起床,穿了一套短衫褲,到廚房幫助女傭人弄點心。
點心弄好了,玉蘭捧了一碟從廚房走出來,走到大廳,他突然停住了。她看到一個體格魁梧的工人在廳中工作。他一只脚踏在沙發上,一只脚踏在茶几上,像在檢查高高的收音機電線。
「喂,這張是新沙發,你怎麼可以亂站上去?」玉蘭責問他。
這年靑工人向玉蘭望了一眼,說:
「有什麼關係?」
「誰說沒有關係!打幾次電話去你們也不派人來,一來就站在新沙發上!」
「打過幾次電話來嗎,是誰打來的?」
「是我,怎麼樣?」
「是你嗎,對不起,我不知道;不然,我一定馬上就來。」那年靑的工人俏皮地說着,又有意無意地笑着看了玉蘭一眼。
「啊,你這人,不好心!」玉蘭鼓着小腮,想走開去。
年靑的工人已檢完電話線,走下地的時候,却一脚踏在螺絲批上,險些跌倒,他連忙找一點東西支持住身子,一手按在玉蘭手中的點心上。那工人這次眞的有點不好意思了,他向玉蘭道歉:
「眞對不起!」
「對不起就可以了嗎!」玉蘭也眞的有點怒意了。因為,他弄壞了她一個早晨的心血結晶。
「那末賠囘錢給你好了。」
「誰要你的錢!」
「那末….那末…」他有點窘了。
玉蘭看到他的一副尶尬相,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那靑年見玉蘭一笑,態度又囘復自然,並且隨手拿一個點心向嘴裏放。
「眞好味道,是你做的嗎?」
玉蘭不囘答,却似嗔還喜的向那靑年瞪了一眼。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女傭人去開了門,張家瑞走進來。
家瑞一看見那靑年人,就立刻走上前去,熱烈地和他握手。他們是老同學,不見面已經一年了。「天柱,」家瑞對那工人說:「眞想不到會在這兒見到你,你什麼時候囘來的?」
「已經半年了。」那青年工人囘答。
「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
「太平無線電行。」
「爲什麽今天要你親自動手來呀?」
「今天幾個助手都沒空,而這裏又催得緊,我只得自己來了。」
到現在,家瑞才知道玉蘭在旁邊聽着他們說話。
「只顧得說,到忘記爲你們介紹——這位就是勞玉蘭小姐,這位就是吳天柱先生,我的老同學。」
吳天柱望着玉蘭,玉蘭也望着天柱,他們都有點不好意思。
「家瑞,我忘記了問你」天柱說?「你大淸早就到這兒幹嗎?是看病入嗎?」
「不,是來看朋友——噢,她來了!」
家瑞指了指樓梯,天柱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子從樓上下來,對家瑞笑說早安。
家瑞替天柱介紹了,他知道,那女子就是玉蘭的大姊姊勞玉燕。
接着,勞獄虎和玉萍都下樓了。家瑞替天柱一一介紹。
天柱對勞獄虎說:「勞老伯,你眞好福氣!有三個這麼可愛的千金。」
「還說福氣」勞老伯說:「激氣才眞!」
玉蘭望了天柱一眼,說:「吳先生,我們不只三姊妹哩。」
話則說完,一個壘球從外飛進來,打在玻璃櫃上,玻璃被打得粉碎。
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持着球棒跑進來。她看見闖了禍,立刻取了敲背板遞給父親,自己伏在地上,請父親打她的屁股。
她這副天眞的行狀,把大家都引得笑了起來。父親也笑着說:
「今天人客多,就掛住一次帳吧。」
鄧湘紫也來了。令他們一齊吃了早點,就出門去。除了天柱,大家都去看勞太太。
勞太看見大家都來看她,而且帶來了大批禮物。她感到溫暖,這是她曾經以爲失去了的溫暖。
5
第二天,勞玉蘭走進太平無線電行找吳天柱。天柱剛巧修好一個鋼線錄音機,看見玉蘭進來,就說:
「巧了,巧了,我剛好修理好這副收音機,勞小姐請來說幾句話,待我收收看!」
玉蘭依着天柱的話說了,播出的聲音是:「吳先生,昨天你弄壞了我的點心,今天我要你請飮茶。」
吳天柱聽了笑着說:「去,去,你不說,今天我也要請飮茶的啦。」
「改天才請罷」玉蘭說:「今天由家瑞去請,他和大姊現在新都餐廳等我們。」最後說到的「我們」,聲音輕輕地,在天柱聽來,是怪溫柔的。
6
吳天柱和勞玉蘭來到了,家瑞和玉燕招呼他們坐下。
「勞伯母沒有什麽了嗎?」吳天柱一坐下,就關心地問。
「沒有什麼了,你放心。」玉燕囘答。
「有這麽一個好醫生,伯母的病當然好得快。」天柱說:
「不用送高帽了,横豎我今天也一定請客的了。」
說得大家都笑了。
偶然,玉燕看到爸爸和一個女人在裏面談天。家瑞他們也跟着她的指示望去,果然看到一個妖媚的女人在那邊和勞獄虎在低談。那個女人指手劃脚,像說得很起勁,還不時向勞獄虎作媚笑。
玉蘭看得光大了,憤憤地說:「我想一定是這女人使爸爸着了迷。我們過去找她算賬!」說着,站起身來,想走過去。
家瑞連忙把玉蘭按住:「不要這樣,在事情還未調查清楚以前,我們最好不要打草驚蛇。」
天柱和玉燕都同意家瑞的說法,玉蘭只得重坐下來。
7
玉燕和玉蘭囘到家裏,將在新都餐廳的情景吿訴玉萍和玉儀。她們都說那個女人値得思疑。
正在談論怎樣對付那個女人的時候,司機阿福走進來,她們馬上住了口。
她們請求阿福說出父親的行狀。但是用盡千方百計,威迫利誘,阿福都不肯說。她們只知道,阿福是囘來取兩個沙田柚送給朋友。至於送給什麽朋友?送到什麼地方,阿福都不肯說出來。
還是大姊有辦法,她向阿蘭使了一個眼色,對阿福說:「福哥,你先跟阿蘭入廚房吃午飯,我們會爲你準備好兩個沙田柚。」
「不用麻煩二小姐了,我自己進去吃可以啦。」阿福說。
「不,廚房裏的東西我知道得清楚點,跟我來吧!」玉蘭說完,不管阿福同意不同意,拉着他想走進廚房去。
玉燕把阿福叫住,請他將汽車的行李箱的鑰匙交給她,因爲她想取個螺絲批一用。阿福當然答應
一會,阿福吃完了午飯,和玉蘭從廚房裏走進來。玉萍已替他包好沙田柚,玉燕也將鑰匙還給他。
阿福開車去了。玉蘭發覺不見了玉儀,問大姊,玉燕向她使了一個眼色,她知道了這是什麼一囘事。
8
阿福駕駛的車子停在一所洋房的門口,阿福走前去按門鈴。一會,一個女傭人出來開了門,讓阿福進去。
行李箱鑽出一個頭,是玉儀的頭,她看見阿福進了去,立刻從行李箱走出來,將門牌記下,走了。
9
第二天,玉儀和玉燕化了裝,走到昨天抄下門牌那所洋房的後門,從矮窗看進去,看見一個女傭模樣的人在洗衣。她們拍門,那一個女傭走出來,愕然地問玉燕:
「你找誰?」
「你叫什麽名字?」玉燕以問作答。
「你問這個幹嗎?」
「因爲我有要緊的事。」玉燕說。
那個女傭想了一想,說:「我叫阿彩。」
「哦,彩姐,」玉燕說:「我想來替你幾天工,我不但不要工錢,而且還給你一百元。」
阿彩從未見過這樣的好人,她懷疑,她不肯答應。 玉燕看見她不肯答應,就抱着玉儀,在阿彩跟前哭了起來。她哭着對阿彩說:
「你們小姐的一位朋友,他就是我的丈夫,這就是他的女兒」她指着玉儀說,「他爲了你們的小姐,拋棄了我們母女兩個——」
「你說的就是勞先生嗎?」阿彩插嘴問。
「對了,就是他。所以,我想請你幫幫忙,讓我來做幾天工,我只想離婚,取一筆錢養活這個女兒。」
她說着哭着,阿彩起先不肯答應,但終於給她哭軟了,答應了玉燕。
玉燕千多萬謝,臨走的時候對阿彩說:「我過兩天就來工作。」
10
勞玉萍又到戲院後台找湘紫,一幕戲完了,湘紫囘後台補裝,玉萍在旁幫忙。偶然,玉萍發現湘紫的化裝桌上有一盒東西,樣子很精緻,她取了看看,原來是一盒瀉糖。她請湘紫送給她,她準備囘去當朱古力送給玉儀吃。玉儀是她的死對頭,她想瀉得玉儀半生半死。 這夜,湘紫送她囘家。剛進門,女傭就悄悄吿訴她:「老爺囘來了。」
她慌了,除了鞋,躡足上樓,走到半樓梯,她聽見父親的開門聲,她連忙蜷縮在樓梯的轉角處。她看見父親穿着睡衣從臥室走出來,站在樓梯頂端看了一會,看見沒有什麽動靜,又走到女兒們的房門口,將耳朵貼在門上,聽了一會,想推門進去,門剛推開,隆然一聲,一個乘滿了水的水桶從門楣上跌下來,剛好套在父親的脖子上。父親掙扎着,叫駡着,大姊,三妹和四妹都被這巨響驚醒了。
玉萍看見父親忙亂了手脚,脫來脫去也沒法將小桶取出,她忍不住,大着胆子上前替他除了下來。
父親瞪大眼睛,一道道的熱汗在面上流。他喝問這是誰弄的把戲,玉儀挺身承認了。因爲她知道今晚二姊去看湘哥,一定很夜才向來,所以她佈置了這個機關,想使二姊變成落湯鷄。
結果,父親將玉萍和玉儀都判罰坐牆刑,明天執行。罪名玉萍是夜歸,玉儀是存心害人。
11
第二天,在父親的房中,玉萍和玉儀在受刑。
玉萍突然想起了昨晚湘哥送她那盒瀉糖,她取了出來給玉儀,玉儀歡天喜地接了。偏巧父親走進來,將玉儀手中的「朱古力」取了。他說:「在受刑的時候,不準吃糖!」說完,他連打了兩個大噴嚏,他昨晚被水淋得傷風了。
12
「彭,彭,彭,」阿彩聽見是後門傳來一陣敲門聲,她走出開了門,看見一個陌生的女人站在門口,身上穿了白衫黑褲,頭上梳髻,口角上有一粒黑誌,全個工人模樣。阿彩認不得她,問道:
「你找誰?」
玉燕笑了,她吿訴阿彩,她就是姓勞的老婆。阿彩也笑了,她的笑是稱贊「勞太」化裝術的神奇。
房裏傳出小姐的呼叫聲,阿彩應着和玉燕進去,阿彩吿訴小姐,她的母親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要囘去看看媽,她請了「阿金」來替一天工。
小姐答應了,阿彩也出去了。阿彩臨走的時候吿訴玉燕,她的小姐姓洪,叫玫瑰。
玉燕現在才看得淸楚,那洪小姐正是那天在新都餐廳所見的那個女人。
一會,一個姓馮的來找洪小姐,一進來就跑到洪小姐的臥室,擁着洪小姐叫「大令」。洪小姐也將小嘴接上去,還叫了一聲「My dear 西揚」。他們像看不見「阿金」在旁邊似的做着肉麻的動作,玉燕看得臉也紅了。但我們應該知道,玉燕的臉紅不單只爲害臊,實在也有點氣憤。所以如果我們細心察看,就可以看到玉燕的額上還浮起了兩條靑筋。
跟着她聽到馮西揚和洪玫瑰說起老頭子來:
「老頭子近來的生意怎樣?」西揚問。
「還不錯,」玫瑰說了,「他還打算過幾天和我去菲律賓玩玩,也順便找點生意做。」
「去菲律賓?……」
「怎樣,吃酸醋嗎?」
西揚連忙否認:「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
「想什麽?」
「想——你們不如去星架坡。」
「爲什麽?」
「因爲我那邊朋友多;同時,星架坡我也可以去。你知道,菲律賓我是不能進境的。」
「朋友多又怎樣,你可以去又怎樣,難道還放心不過?」玫瑰說着,扁了扁嘴,擰過頭去。
「千萬不要誤會。」西揚慌忙解釋:「我的意思只是說如果老頭子眞的和你改去星加坡,那我們就可以在那邊「滾」他一煲!」
「啊,對,對」玫瑰轉怒爲喜,如夢初覺地說:「那邊你地頭熟。如果我們「滾」到他一煲,以後不是可以不再偷偷摸摸了嗎?
他高興極了,擁着倒在床上,去做他們的美夢。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聲又響了。馮西揚一聽到這特別長的鈴聲,就急速脫開玫瑰的懷抱站起來,驚魂不定地躱到廚房。
玉燕將門開了,勞老頭子給玉燕的化裝術騙過,他還以爲她是阿彩的替工阿金。
洪玫瑰一見勞老頭進來,就倚在他的懷中灌迷湯。這使人想起了六十多歲的唐明皇擁著二十多歲的楊貴妃的情景,肉麻得使人作嘔。
正當勞老頭進入「昏迷」狀熊的時候,洪玫瑰乘機請求改變到菲律賓的决定,和她到星加坡去。迷湯的威力是强大的,勞老頭很容易就答應了洪玫瑰的要求。
13
玉燕並沒有忘記馮西揚,她還以爲他現在還躱在廚房。她打開廚房門一看,發覺馮西揚不見了。
後門却打開着。
她再囘到外面,看見勞老頭正將一串珠練交給洪玫瑰,勞老頭無意中給洪玫瑰發現了袋中還有一盒東西,她以爲是什麽,取了出來看看,原來是一盒糖果。勞老頭告訴她:這是他的小女兒吃的「朱古力」。
洪玫瑰將蓋子打開,兩人吃起「朱古力」來。
14
第二天,玉燕一早起來就聽到父親的呼叫聲。她連忙跑到父親的臥房,她以爲出了什麼事。因爲父親是少有這麼大清早叫起來的。
她看到父親眼目呆滯,眼腔深陷,躺在床上喘着氣。她覺得奇怪,她問父親患了什麽病。父親吿訴她:昨晚一夜瀉了十多次。
她馬上跑出去,打電話給家瑞,叫他立刻來看爸爸。
很快的,家瑞趕來了,玉萍玉蘭玉儀都進來了。家瑞替父親打了一口針,問他說:
「你記得吃錯了什麼東西?」
勞獄虎說:「沒有。」接着又是一陣呻吟。
在房間的一邊,玉萍附着玉燕的耳朵說:「上爸一定是吃了湘哥送給我的瀉糖。」她連昨日早爸的一幕也吿訴了玉燕。
玉燕明白了,她忍不住笑了。但她立刻又緊張起來,她知道,昨晚洪玫瑰也一定瀉得很厲害。於是她急急離開這裏,走囘自己的房間,穿囘昨天那套衣服,化了一會裝,悄悄地由後門出去了。
15
她一走進門口,就聽到洪玫瑰的呻吟聲,她再走到房門口,看見洪玫瑰和她的父親一樣:一樣目光呆滯,一樣的眼腔深陷地躺在床上。洪玫瑰一看見是她,就說:
「怎麼,今天阿彩也囘了家去嗎?」
「是啊,她的媽今天病得更厲害,她又囘家看媽媽了。」
「好的。」玉燕應了,出去撥電話叫家瑞馬上來。
不多久,家瑞來了。他一進門就認得開門的是玉燕。對於一個女孩子的愛人對她的認識該是比父親深厚的。怪不得父親分辨不出來,而家瑞一看就認出來了。
玉燕將實際的情况完全吿訴了他;並且請他幫助,要他只給一些溫和慢性的藥給洪玫瑰吃,使她誤了行期。家瑞當然答應。
家瑞替攻瑰看完了病,玫瑰問她,她究竟患的是什麼病?
「沒關係,那是腸胃病。」
「要多久才復原?」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她差不多驚叫起來:「我後天就要去星加坡啦,那怎麼辦?」
「也沒有辦法,醫病是不可以心急的。」
家瑞說完,挽着藥箱走了。
洪玫瑰伏在床上飮泣;看情形,醫生的話比疾病更使她痛苦。
家瑞剛走後,馮西揚也就來了,他看見玫瑰伏在床上痛哭。他連忙坐在床沾,撫慰着玫瑰,他低聲地問玫瑰:「是什麼事使你這麽傷心?」
玫瑰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
他忽然像想起了什麽似的,對攻瑰說:
「近來痢疾很流行。我想張醫生未必靠得住,不如再找陳達文醫生看看,他是我們所認識的,總比較可靠點。」說完,就走了出去打電話。
16
馮西揚的一句說話,陳達文醫生的一口針,洪玫瑰走出了病魔的掌握。第三天洪玫瑰就精神奕奕了。
玉燕的第一個計劃失敗了!
今天,洪小姐一早就起來,再整理一下昨日已經收拾的行李。
馮西揚也來了。
吃完早飯之後,洪玫瑰給玉燕十塊錢,並對她說:
「阿金,我今天去星加坡了,以後恐怕不再囘來。阿彩的人工我巳給她了,這所房子也已通知業主收囘。一會,你侍候馮先生洗完澡,就可以囘家。這裏的十塊錢,拿去用吧,就是我給你的打賞的好了。」
玉燕將錢收下,道了謝。
洪玫瑰囘頭對正想進浴室沐浴的西揚說:「西揚,我先去大碼頭,你快點洗澡,洗完就來。」
說完,拿起皮篋走了出去。
玉燕開好門,囘到裏面,聽見浴室傳出一片愉快的歌聲、水聲。雖然歌唱得並不好,但我們也可以聽出:正在裏面沐浴的人是多麽快樂。
玉燕將浴室的門輕輕地下了鍵……
17
相同的時候,勞獄虎正在醫院向妻子道別,玉萍玉蘭和玉儀也在這裏;她們一則來探望媽媽,同時也來和爸爸送行。
勞獄虎淡淡的一句「再見!」,就挽着手提喼走了。如果不吿訴你他們就是夫婦,你可能以爲他們只是朋友。
勞太望着丈夫的背影,望着女兒們的調皮的步式,她的眼角有點濕潤了。她翻身向內,俏俏用手帕揩揩眼睛。——多少年來,她和丈夫都是恩恩愛愛的,從來未有過半句爭吵;如今,如今他一定是給外面的妖迷惑住了,雖然他除了夜歸之外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越軌表現,但對她的那種淡漠感情她是看得出的。她很多次想責問他,但很多次都忍住了。直到今天,她還是希望他自己覺悟。她不願意那段潔白的愛情染上一些明顯的瑕玭。
18
勞獄虎走出門口,阿福已在那裏侍候。他一看見是老爺出來,連忙拉開車門,請老爺進去。
忽然間,阿福聽到車子那邊發出「支支」的聲音,他慌了起來,立刻跑過去察看。他看見玉儀迅速從後輪旁邊站起來,嘻嘻哈哈地走開去。那邊的車胎漸漸變扁…………
相同的時候,洪攻瑰的家中,玉燕正在看報紙。
浴室中急促的打門聲代替了歌聲。
玉燕放下報紙,倒在床上,拖一張被子蓋着頭。不管浴室的敲門聲和叫聲越來越響…………
19
醫院門口,勞獄虎不時看着手錶,手錶的長短針正指着9字和1字。距離輪船開行的時間只有三十分鐘。
獄虎急得滿頭大汗,不時摧促正在換車輪的阿福。
阿福被他摧得昏了,反而手忙脚亂。獄虎更急,將阿福亂駡,阿福也就更亂,更加不知所措。
他們兩人的狼狽相,引到在旁邊的玉萍三人也笑起來。
車輪終於換上了,獄虎阿福和玉萍三姊妹慌忙上車。出乎意料之外,車剛開,又是「支支」的幾聲,全架車向下一墮,四個輪子都扁下去……
在車子底下地上,躺滿了尖頂的三角釘。
這次如果要將車子修理好,非要兩三個鐘頭不可,獄虎又急又氣,也不知怎樣才好。還是阿福提醒他,他才招輛的士和女兒們到大碼頭去。
在相同的時候玉燕將浴室的門開了。
馮西揚已經聲嘶力歇,一出門,就像一頭戰敗了的獅子一樣,躺在沙發上喘氣。
馮西揚責問玉燕爲什麼將他關在裏面。
玉燕說:「鍵不是我下的,大概它自己跌下來的。」
「那怎麼我叫了這麼久才來開門?」
「我出去替你叫的士,所以聽不到。」
「這裏不是有電話嗎?」
「我不知道電話號碼。」玉燕囘答。
「這裏有電話簿你爲什麼不査,也不問問人?」
「我不識字,也不曉得你知道。」
西揚看了錶,他知道再沒空和她吵下去。於是霍然站起來,以最快的速度將衣服穿好,趕出門,跳上玉燕爲她叫來的的士。
的士的司機一路向遠遠的地方駛去,起先馮西揚還沒有發覺,及後看看外面的路途,越來越陌生,於是他問司機:
「你準備車我到什麼地方去?」
「你不是說去飛機塲嗎?」
「豈有此理」西揚說:「誰說去飛機場……快掉轉囘大碼頭,再慢船就開了。」
司機依照他的說話掉囘頭,但車子却駛進一條又狹又小的山徑上。而且,車子忽然停了下來,前面一架私家車阻住去路。前面的司機說:「汽車壞了,打不着火。」
兩旁是山壁,而路又小得只可以容納一架車子經過。
馮西揚氣得瞪大眼睛,只得吩咐自己的司機向後開,想由第二條路走。但車子剛倒退了兩步,後面又有一輛車擋住去路。馮西揚眞是怒不可歇,他跳下車來,要他將車子退出,讓他先過。但那司機卻慢吞吞地吿訴他:「我的車子沒有退後波。」
馮西揚急得在地上跳,還是自己那個司機想得出,他建議不如大家合力將前面的車子推開。
大家都同意了,但推車的時候,三個司機又好像十多天沒有吃飯似的,推得滿身大汗。
西揚坐的的士終於開走了。其餘的兩個司機大笑起來,原來他們就是湘紫和家瑞。
車到碼頭,船剛啓椗,西揚呆住了,他望着站在船上的洪玫魂,他看她在流涙。
後面傳來一聲嬌婉的聲音,他囘頭一看,原來一個年輕的女子在牽着自己的司機的手在叫:「天柱!」
西揚現在明白,這是詭計。他實在太憤怒了,他想走上去找那個叫天柱的司機的霉氣;但細看站在那邊的「天柱」正像「擎天之柱」一樣,是那麽雄偉,那麼魁梧,他不禁倒退了一步。
也就在這時,一大羣人擁到他的面前,嚷着要打他。這羣人就是勞獄虎和四個女兒,以及三個未來女婿。
西揚看見來勢洶湧,連忙抱頭急遁。
20
經過這番敎訓,獄虎覺悟了,他重新過着早去早囘的有規律的生活,勞太也囘復了失去了的光彩。
他們的實情雖然有着一絲裂痕,但這裂痕是隱而難見的,而且是會漸漸消失。
(完)
春滿香城
小說改編 藍菲
美術編輯 林擒
1
戲台上,名伶鄧湘紫正在演戲。
他看到台下的玉萍,向她點頭微笑,玉萍也輕輕地向他瞟了一眼。
這場戲外戲給大姊玉燕和三妹玉蘭看到了,都取笑起她來。玉蘭說:
「今晚湘哥做得特別好!」
「當然啦,因爲今晚二姊來了。」玉蘭說。
「屁話,我又不是今晚才來的。」
「卽就是因爲你今晚的眼角拋得特別出色啦。」玉蘭說得臉也紅了起來。
剛巧這時幕下了,玉萍連忙站起來,想離開她們的圍攻:
「我不和你們說,我上後台去。」
玉蘭看見她想逃了,把她拉住:
「想去會情人嗎?可以,先拿十塊錢來!」
「給你好了,我的好妹妹。」玉萍從手袋裏取了十元給玉蘭,輕鬆地走向後台。
玉萍走了不多久,大堂閘口處起了一陣嘈雜聲。一個女孩子的聲音說:
「爲什麼不讓我進去,你以爲我想看霸王戲嗎?」
玉蘭她們聽出這就是四妹玉儀的聲音。
「玉儀爲什麼走出來呢?」玉燕說。
「我們出去看看!」
她倆走到閘口、看見果然是玉儀和守閘的在爭論。
玉儀看見大姊和三姊來了,就將來意一五一十的吿訴了她們。原來她們的媽剛才在家暈倒了,玉儀已立刻將她送進醫院,請玉燕的摯友張家瑞替她們診治。
這消息像霹靂一樣震驚了她們的神經。母親是很少有病的,何況一病竟然暈倒。她們連忙上後台找同玉萍去看媽媽。
2
她們乘了車子,趕到醫院,由玉儀領前,以最高的速率奔到母親的旁邊,圍着母親問長問短。
勞太看見女兒們這麼關心地慰問着,反而安慰起她們來:
「你們不用担心,過幾天就可以出院了。家瑞說這是輕微的心臟病。在這裏,家瑞會好好看護我的。」
「看護未來岳母當然格外留心!」小妹妹玉儀取笑起大姊姊來。
「玉儀,你說什麽?」大姊舉起手,要打玉儀。玉儀笑着,避開了。
「玉燕,」家瑞說:「我和你到配藥室去配點藥。配藥室的工作人員巳經下了班,我不好意思再麻煩他們。」
玉燕巴不得和他逃出去,免得在這裏給小妹妹取笑。
在配藥室裏,家瑞對玉燕說:
「你有沒有發覺你媽有什麼隱憂?」
「沒有,」玉燕囘答:「只是她近來不大喜笑。」
「你知到這是什麼原因?……譬如,你爸近來有什麼軌外行動?」
「也不覺得。」玉燕想了一想,又說:「只是爸爸近來好像晚晚都很夜才囘來。」
「唔……」家瑞說,「也許就因爲這點,你最好囘去多留意。」
3
夜深了,她們囘到家裏。
玉燕問女傭人,知到父親還未向來。她心中馬上浮起一種同情母親的感想:
近半年來,父親總是深夜才囘來,打破了以前「早出早囘」的慣例。母親近來也很少笑,沉默得多了。——這並不是偶然的,而且,這可能是有關聯的。剛才家瑞不是明明對我說過,母親除了心臟病,好像還有點隱憂嗎?母親是不喜歡將心事吿訴人的,說不定她的心中隱着什麽痛苦。
玉燕將自己的心事吿訴了三個妹妹,原來她們都有同樣的感覺。
他們都一致認爲,她們是應該負起保持家庭幸福的義務。經過一番商討,她們成立了一個協議:凡是破壞她們的家庭幸福的,她們都聯合起來,抗拒到底;並且選出大姊爲總司令,先由大姊領導大家起了誓,以後由大姊領導一切,指揮一切。
她們正說得起勁的時候,忽然門外傳來一陣汽車的煞止聲,打破了黑夜的沉寂。
她們連忙跑出露台,看見下面門口停了一架的士,車門看了,她們的父親勞嶽虎走下來,回身和一只從車廂裏伸出來的手緊握。她們從高處看下來,看不到車裏坐着一個怎麽樣的人但她們清楚地聽到,有一個嬌響的聲音自車內傳出來,向她們的爸爸說「拜拜!」
汽車開去了,接着聽到父親上樓的聲音,一步輕一步重的。
她們走下去,將父親摻扶着進了房,父親一進房就倒在椅上昏昏地睡着了。一陣陣的酒氣撲到她們的臉上,她們感到不好受。
玉儀看見父親醉得這麽利害,就走出取一枝水槍,吸了水,向着父親的面上射去。玉燕她們想來阻止也來不及。
父親醒來了,當他發覺自己滿身是水,女兒圍着自己大笑的時候,他大怒了,漲紅了臉說:
「你們想作反嗎!誰用水來射我?」
「爸爸,是我。」玉儀說着,將平日父親用來打她們屁股的敲背板送上,並且轉身俯下,聳起屁股,請父親打她。
「豈有此理!」父親舉起板手,想重重的打下去。
玉燕連忙拉住他的手,說:
「不要打她了,實在她因爲想立刻叫醒你吿訴你一件事情,可是你一進門就醉倒了,所以——」
「所以她就應該用水槍來對付我了嗎?」
「這只是她急昏了,她想立刻吿訴你媽進了醫院。」玉蘭說。
「什麼?媽媽進了醫院?患了什麼病?」
「心臓病。她今天突然暈倒。」玉萍說。
「………………」父親呆住了,敲背板從他的手中掉下來。
停了一囘,玉燕說:「父親,我們明天一同去看媽媽好嗎?」
「好,明天吃了早點一同去。」父親應着,心中感到一陣慚愧。
4
第二天早晨,玉蘭一早就起床,穿了一套短衫褲,到廚房幫助女傭人弄點心。
點心弄好了,玉蘭捧了一碟從廚房走出來,走到大廳,他突然停住了。她看到一個體格魁梧的工人在廳中工作。他一只脚踏在沙發上,一只脚踏在茶几上,像在檢查高高的收音機電線。
「喂,這張是新沙發,你怎麼可以亂站上去?」玉蘭責問他。
這年靑工人向玉蘭望了一眼,說:
「有什麼關係?」
「誰說沒有關係!打幾次電話去你們也不派人來,一來就站在新沙發上!」
「打過幾次電話來嗎,是誰打來的?」
「是我,怎麼樣?」
「是你嗎,對不起,我不知道;不然,我一定馬上就來。」那年靑的工人俏皮地說着,又有意無意地笑着看了玉蘭一眼。
「啊,你這人,不好心!」玉蘭鼓着小腮,想走開去。
年靑的工人已檢完電話線,走下地的時候,却一脚踏在螺絲批上,險些跌倒,他連忙找一點東西支持住身子,一手按在玉蘭手中的點心上。那工人這次眞的有點不好意思了,他向玉蘭道歉:
「眞對不起!」
「對不起就可以了嗎!」玉蘭也眞的有點怒意了。因為,他弄壞了她一個早晨的心血結晶。
「那末賠囘錢給你好了。」
「誰要你的錢!」
「那末….那末…」他有點窘了。
玉蘭看到他的一副尶尬相,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那靑年見玉蘭一笑,態度又囘復自然,並且隨手拿一個點心向嘴裏放。
「眞好味道,是你做的嗎?」
玉蘭不囘答,却似嗔還喜的向那靑年瞪了一眼。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女傭人去開了門,張家瑞走進來。
家瑞一看見那靑年人,就立刻走上前去,熱烈地和他握手。他們是老同學,不見面已經一年了。「天柱,」家瑞對那工人說:「眞想不到會在這兒見到你,你什麼時候囘來的?」
「已經半年了。」那青年工人囘答。
「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
「太平無線電行。」
「爲什麽今天要你親自動手來呀?」
「今天幾個助手都沒空,而這裏又催得緊,我只得自己來了。」
到現在,家瑞才知道玉蘭在旁邊聽着他們說話。
「只顧得說,到忘記爲你們介紹——這位就是勞玉蘭小姐,這位就是吳天柱先生,我的老同學。」
吳天柱望着玉蘭,玉蘭也望着天柱,他們都有點不好意思。
「家瑞,我忘記了問你」天柱說?「你大淸早就到這兒幹嗎?是看病入嗎?」
「不,是來看朋友——噢,她來了!」
家瑞指了指樓梯,天柱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子從樓上下來,對家瑞笑說早安。
家瑞替天柱介紹了,他知道,那女子就是玉蘭的大姊姊勞玉燕。
接着,勞獄虎和玉萍都下樓了。家瑞替天柱一一介紹。
天柱對勞獄虎說:「勞老伯,你眞好福氣!有三個這麼可愛的千金。」
「還說福氣」勞老伯說:「激氣才眞!」
玉蘭望了天柱一眼,說:「吳先生,我們不只三姊妹哩。」
話則說完,一個壘球從外飛進來,打在玻璃櫃上,玻璃被打得粉碎。
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持着球棒跑進來。她看見闖了禍,立刻取了敲背板遞給父親,自己伏在地上,請父親打她的屁股。
她這副天眞的行狀,把大家都引得笑了起來。父親也笑着說:
「今天人客多,就掛住一次帳吧。」
鄧湘紫也來了。令他們一齊吃了早點,就出門去。除了天柱,大家都去看勞太太。
勞太看見大家都來看她,而且帶來了大批禮物。她感到溫暖,這是她曾經以爲失去了的溫暖。
5
第二天,勞玉蘭走進太平無線電行找吳天柱。天柱剛巧修好一個鋼線錄音機,看見玉蘭進來,就說:
「巧了,巧了,我剛好修理好這副收音機,勞小姐請來說幾句話,待我收收看!」
玉蘭依着天柱的話說了,播出的聲音是:「吳先生,昨天你弄壞了我的點心,今天我要你請飮茶。」
吳天柱聽了笑着說:「去,去,你不說,今天我也要請飮茶的啦。」
「改天才請罷」玉蘭說:「今天由家瑞去請,他和大姊現在新都餐廳等我們。」最後說到的「我們」,聲音輕輕地,在天柱聽來,是怪溫柔的。
6
吳天柱和勞玉蘭來到了,家瑞和玉燕招呼他們坐下。
「勞伯母沒有什麽了嗎?」吳天柱一坐下,就關心地問。
「沒有什麼了,你放心。」玉燕囘答。
「有這麽一個好醫生,伯母的病當然好得快。」天柱說:
「不用送高帽了,横豎我今天也一定請客的了。」
說得大家都笑了。
偶然,玉燕看到爸爸和一個女人在裏面談天。家瑞他們也跟着她的指示望去,果然看到一個妖媚的女人在那邊和勞獄虎在低談。那個女人指手劃脚,像說得很起勁,還不時向勞獄虎作媚笑。
玉蘭看得光大了,憤憤地說:「我想一定是這女人使爸爸着了迷。我們過去找她算賬!」說着,站起身來,想走過去。
家瑞連忙把玉蘭按住:「不要這樣,在事情還未調查清楚以前,我們最好不要打草驚蛇。」
天柱和玉燕都同意家瑞的說法,玉蘭只得重坐下來。
7
玉燕和玉蘭囘到家裏,將在新都餐廳的情景吿訴玉萍和玉儀。她們都說那個女人値得思疑。
正在談論怎樣對付那個女人的時候,司機阿福走進來,她們馬上住了口。
她們請求阿福說出父親的行狀。但是用盡千方百計,威迫利誘,阿福都不肯說。她們只知道,阿福是囘來取兩個沙田柚送給朋友。至於送給什麽朋友?送到什麼地方,阿福都不肯說出來。
還是大姊有辦法,她向阿蘭使了一個眼色,對阿福說:「福哥,你先跟阿蘭入廚房吃午飯,我們會爲你準備好兩個沙田柚。」
「不用麻煩二小姐了,我自己進去吃可以啦。」阿福說。
「不,廚房裏的東西我知道得清楚點,跟我來吧!」玉蘭說完,不管阿福同意不同意,拉着他想走進廚房去。
玉燕把阿福叫住,請他將汽車的行李箱的鑰匙交給她,因爲她想取個螺絲批一用。阿福當然答應
一會,阿福吃完了午飯,和玉蘭從廚房裏走進來。玉萍已替他包好沙田柚,玉燕也將鑰匙還給他。
阿福開車去了。玉蘭發覺不見了玉儀,問大姊,玉燕向她使了一個眼色,她知道了這是什麼一囘事。
8
阿福駕駛的車子停在一所洋房的門口,阿福走前去按門鈴。一會,一個女傭人出來開了門,讓阿福進去。
行李箱鑽出一個頭,是玉儀的頭,她看見阿福進了去,立刻從行李箱走出來,將門牌記下,走了。
9
第二天,玉儀和玉燕化了裝,走到昨天抄下門牌那所洋房的後門,從矮窗看進去,看見一個女傭模樣的人在洗衣。她們拍門,那一個女傭走出來,愕然地問玉燕:
「你找誰?」
「你叫什麽名字?」玉燕以問作答。
「你問這個幹嗎?」
「因爲我有要緊的事。」玉燕說。
那個女傭想了一想,說:「我叫阿彩。」
「哦,彩姐,」玉燕說:「我想來替你幾天工,我不但不要工錢,而且還給你一百元。」
阿彩從未見過這樣的好人,她懷疑,她不肯答應。 玉燕看見她不肯答應,就抱着玉儀,在阿彩跟前哭了起來。她哭着對阿彩說:
「你們小姐的一位朋友,他就是我的丈夫,這就是他的女兒」她指着玉儀說,「他爲了你們的小姐,拋棄了我們母女兩個——」
「你說的就是勞先生嗎?」阿彩插嘴問。
「對了,就是他。所以,我想請你幫幫忙,讓我來做幾天工,我只想離婚,取一筆錢養活這個女兒。」
她說着哭着,阿彩起先不肯答應,但終於給她哭軟了,答應了玉燕。
玉燕千多萬謝,臨走的時候對阿彩說:「我過兩天就來工作。」
10
勞玉萍又到戲院後台找湘紫,一幕戲完了,湘紫囘後台補裝,玉萍在旁幫忙。偶然,玉萍發現湘紫的化裝桌上有一盒東西,樣子很精緻,她取了看看,原來是一盒瀉糖。她請湘紫送給她,她準備囘去當朱古力送給玉儀吃。玉儀是她的死對頭,她想瀉得玉儀半生半死。 這夜,湘紫送她囘家。剛進門,女傭就悄悄吿訴她:「老爺囘來了。」
她慌了,除了鞋,躡足上樓,走到半樓梯,她聽見父親的開門聲,她連忙蜷縮在樓梯的轉角處。她看見父親穿着睡衣從臥室走出來,站在樓梯頂端看了一會,看見沒有什麽動靜,又走到女兒們的房門口,將耳朵貼在門上,聽了一會,想推門進去,門剛推開,隆然一聲,一個乘滿了水的水桶從門楣上跌下來,剛好套在父親的脖子上。父親掙扎着,叫駡着,大姊,三妹和四妹都被這巨響驚醒了。
玉萍看見父親忙亂了手脚,脫來脫去也沒法將小桶取出,她忍不住,大着胆子上前替他除了下來。
父親瞪大眼睛,一道道的熱汗在面上流。他喝問這是誰弄的把戲,玉儀挺身承認了。因爲她知道今晚二姊去看湘哥,一定很夜才向來,所以她佈置了這個機關,想使二姊變成落湯鷄。
結果,父親將玉萍和玉儀都判罰坐牆刑,明天執行。罪名玉萍是夜歸,玉儀是存心害人。
11
第二天,在父親的房中,玉萍和玉儀在受刑。
玉萍突然想起了昨晚湘哥送她那盒瀉糖,她取了出來給玉儀,玉儀歡天喜地接了。偏巧父親走進來,將玉儀手中的「朱古力」取了。他說:「在受刑的時候,不準吃糖!」說完,他連打了兩個大噴嚏,他昨晚被水淋得傷風了。
12
「彭,彭,彭,」阿彩聽見是後門傳來一陣敲門聲,她走出開了門,看見一個陌生的女人站在門口,身上穿了白衫黑褲,頭上梳髻,口角上有一粒黑誌,全個工人模樣。阿彩認不得她,問道:
「你找誰?」
玉燕笑了,她吿訴阿彩,她就是姓勞的老婆。阿彩也笑了,她的笑是稱贊「勞太」化裝術的神奇。
房裏傳出小姐的呼叫聲,阿彩應着和玉燕進去,阿彩吿訴小姐,她的母親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要囘去看看媽,她請了「阿金」來替一天工。
小姐答應了,阿彩也出去了。阿彩臨走的時候吿訴玉燕,她的小姐姓洪,叫玫瑰。
玉燕現在才看得淸楚,那洪小姐正是那天在新都餐廳所見的那個女人。
一會,一個姓馮的來找洪小姐,一進來就跑到洪小姐的臥室,擁着洪小姐叫「大令」。洪小姐也將小嘴接上去,還叫了一聲「My dear 西揚」。他們像看不見「阿金」在旁邊似的做着肉麻的動作,玉燕看得臉也紅了。但我們應該知道,玉燕的臉紅不單只爲害臊,實在也有點氣憤。所以如果我們細心察看,就可以看到玉燕的額上還浮起了兩條靑筋。
跟着她聽到馮西揚和洪玫瑰說起老頭子來:
「老頭子近來的生意怎樣?」西揚問。
「還不錯,」玫瑰說了,「他還打算過幾天和我去菲律賓玩玩,也順便找點生意做。」
「去菲律賓?……」
「怎樣,吃酸醋嗎?」
西揚連忙否認:「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
「想什麽?」
「想——你們不如去星架坡。」
「爲什麽?」
「因爲我那邊朋友多;同時,星架坡我也可以去。你知道,菲律賓我是不能進境的。」
「朋友多又怎樣,你可以去又怎樣,難道還放心不過?」玫瑰說着,扁了扁嘴,擰過頭去。
「千萬不要誤會。」西揚慌忙解釋:「我的意思只是說如果老頭子眞的和你改去星加坡,那我們就可以在那邊「滾」他一煲!」
「啊,對,對」玫瑰轉怒爲喜,如夢初覺地說:「那邊你地頭熟。如果我們「滾」到他一煲,以後不是可以不再偷偷摸摸了嗎?
他高興極了,擁着倒在床上,去做他們的美夢。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聲又響了。馮西揚一聽到這特別長的鈴聲,就急速脫開玫瑰的懷抱站起來,驚魂不定地躱到廚房。
玉燕將門開了,勞老頭子給玉燕的化裝術騙過,他還以爲她是阿彩的替工阿金。
洪玫瑰一見勞老頭進來,就倚在他的懷中灌迷湯。這使人想起了六十多歲的唐明皇擁著二十多歲的楊貴妃的情景,肉麻得使人作嘔。
正當勞老頭進入「昏迷」狀熊的時候,洪玫瑰乘機請求改變到菲律賓的决定,和她到星加坡去。迷湯的威力是强大的,勞老頭很容易就答應了洪玫瑰的要求。
13
玉燕並沒有忘記馮西揚,她還以爲他現在還躱在廚房。她打開廚房門一看,發覺馮西揚不見了。
後門却打開着。
她再囘到外面,看見勞老頭正將一串珠練交給洪玫瑰,勞老頭無意中給洪玫瑰發現了袋中還有一盒東西,她以爲是什麽,取了出來看看,原來是一盒糖果。勞老頭告訴她:這是他的小女兒吃的「朱古力」。
洪玫瑰將蓋子打開,兩人吃起「朱古力」來。
14
第二天,玉燕一早起來就聽到父親的呼叫聲。她連忙跑到父親的臥房,她以爲出了什麼事。因爲父親是少有這麼大清早叫起來的。
她看到父親眼目呆滯,眼腔深陷,躺在床上喘着氣。她覺得奇怪,她問父親患了什麽病。父親吿訴她:昨晚一夜瀉了十多次。
她馬上跑出去,打電話給家瑞,叫他立刻來看爸爸。
很快的,家瑞趕來了,玉萍玉蘭玉儀都進來了。家瑞替父親打了一口針,問他說:
「你記得吃錯了什麼東西?」
勞獄虎說:「沒有。」接着又是一陣呻吟。
在房間的一邊,玉萍附着玉燕的耳朵說:「上爸一定是吃了湘哥送給我的瀉糖。」她連昨日早爸的一幕也吿訴了玉燕。
玉燕明白了,她忍不住笑了。但她立刻又緊張起來,她知道,昨晚洪玫瑰也一定瀉得很厲害。於是她急急離開這裏,走囘自己的房間,穿囘昨天那套衣服,化了一會裝,悄悄地由後門出去了。
15
她一走進門口,就聽到洪玫瑰的呻吟聲,她再走到房門口,看見洪玫瑰和她的父親一樣:一樣目光呆滯,一樣的眼腔深陷地躺在床上。洪玫瑰一看見是她,就說:
「怎麼,今天阿彩也囘了家去嗎?」
「是啊,她的媽今天病得更厲害,她又囘家看媽媽了。」
「好的。」玉燕應了,出去撥電話叫家瑞馬上來。
不多久,家瑞來了。他一進門就認得開門的是玉燕。對於一個女孩子的愛人對她的認識該是比父親深厚的。怪不得父親分辨不出來,而家瑞一看就認出來了。
玉燕將實際的情况完全吿訴了他;並且請他幫助,要他只給一些溫和慢性的藥給洪玫瑰吃,使她誤了行期。家瑞當然答應。
家瑞替攻瑰看完了病,玫瑰問她,她究竟患的是什麼病?
「沒關係,那是腸胃病。」
「要多久才復原?」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她差不多驚叫起來:「我後天就要去星加坡啦,那怎麼辦?」
「也沒有辦法,醫病是不可以心急的。」
家瑞說完,挽着藥箱走了。
洪玫瑰伏在床上飮泣;看情形,醫生的話比疾病更使她痛苦。
家瑞剛走後,馮西揚也就來了,他看見玫瑰伏在床上痛哭。他連忙坐在床沾,撫慰着玫瑰,他低聲地問玫瑰:「是什麼事使你這麽傷心?」
玫瑰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
他忽然像想起了什麽似的,對攻瑰說:
「近來痢疾很流行。我想張醫生未必靠得住,不如再找陳達文醫生看看,他是我們所認識的,總比較可靠點。」說完,就走了出去打電話。
16
馮西揚的一句說話,陳達文醫生的一口針,洪玫瑰走出了病魔的掌握。第三天洪玫瑰就精神奕奕了。
玉燕的第一個計劃失敗了!
今天,洪小姐一早就起來,再整理一下昨日已經收拾的行李。
馮西揚也來了。
吃完早飯之後,洪玫瑰給玉燕十塊錢,並對她說:
「阿金,我今天去星加坡了,以後恐怕不再囘來。阿彩的人工我巳給她了,這所房子也已通知業主收囘。一會,你侍候馮先生洗完澡,就可以囘家。這裏的十塊錢,拿去用吧,就是我給你的打賞的好了。」
玉燕將錢收下,道了謝。
洪玫瑰囘頭對正想進浴室沐浴的西揚說:「西揚,我先去大碼頭,你快點洗澡,洗完就來。」
說完,拿起皮篋走了出去。
玉燕開好門,囘到裏面,聽見浴室傳出一片愉快的歌聲、水聲。雖然歌唱得並不好,但我們也可以聽出:正在裏面沐浴的人是多麽快樂。
玉燕將浴室的門輕輕地下了鍵……
17
相同的時候,勞獄虎正在醫院向妻子道別,玉萍玉蘭和玉儀也在這裏;她們一則來探望媽媽,同時也來和爸爸送行。
勞獄虎淡淡的一句「再見!」,就挽着手提喼走了。如果不吿訴你他們就是夫婦,你可能以爲他們只是朋友。
勞太望着丈夫的背影,望着女兒們的調皮的步式,她的眼角有點濕潤了。她翻身向內,俏俏用手帕揩揩眼睛。——多少年來,她和丈夫都是恩恩愛愛的,從來未有過半句爭吵;如今,如今他一定是給外面的妖迷惑住了,雖然他除了夜歸之外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越軌表現,但對她的那種淡漠感情她是看得出的。她很多次想責問他,但很多次都忍住了。直到今天,她還是希望他自己覺悟。她不願意那段潔白的愛情染上一些明顯的瑕玭。
18
勞獄虎走出門口,阿福已在那裏侍候。他一看見是老爺出來,連忙拉開車門,請老爺進去。
忽然間,阿福聽到車子那邊發出「支支」的聲音,他慌了起來,立刻跑過去察看。他看見玉儀迅速從後輪旁邊站起來,嘻嘻哈哈地走開去。那邊的車胎漸漸變扁…………
相同的時候,洪攻瑰的家中,玉燕正在看報紙。
浴室中急促的打門聲代替了歌聲。
玉燕放下報紙,倒在床上,拖一張被子蓋着頭。不管浴室的敲門聲和叫聲越來越響…………
19
醫院門口,勞獄虎不時看着手錶,手錶的長短針正指着9字和1字。距離輪船開行的時間只有三十分鐘。
獄虎急得滿頭大汗,不時摧促正在換車輪的阿福。
阿福被他摧得昏了,反而手忙脚亂。獄虎更急,將阿福亂駡,阿福也就更亂,更加不知所措。
他們兩人的狼狽相,引到在旁邊的玉萍三人也笑起來。
車輪終於換上了,獄虎阿福和玉萍三姊妹慌忙上車。出乎意料之外,車剛開,又是「支支」的幾聲,全架車向下一墮,四個輪子都扁下去……
在車子底下地上,躺滿了尖頂的三角釘。
這次如果要將車子修理好,非要兩三個鐘頭不可,獄虎又急又氣,也不知怎樣才好。還是阿福提醒他,他才招輛的士和女兒們到大碼頭去。
在相同的時候玉燕將浴室的門開了。
馮西揚已經聲嘶力歇,一出門,就像一頭戰敗了的獅子一樣,躺在沙發上喘氣。
馮西揚責問玉燕爲什麼將他關在裏面。
玉燕說:「鍵不是我下的,大概它自己跌下來的。」
「那怎麼我叫了這麼久才來開門?」
「我出去替你叫的士,所以聽不到。」
「這裏不是有電話嗎?」
「我不知道電話號碼。」玉燕囘答。
「這裏有電話簿你爲什麼不査,也不問問人?」
「我不識字,也不曉得你知道。」
西揚看了錶,他知道再沒空和她吵下去。於是霍然站起來,以最快的速度將衣服穿好,趕出門,跳上玉燕爲她叫來的的士。
的士的司機一路向遠遠的地方駛去,起先馮西揚還沒有發覺,及後看看外面的路途,越來越陌生,於是他問司機:
「你準備車我到什麼地方去?」
「你不是說去飛機塲嗎?」
「豈有此理」西揚說:「誰說去飛機場……快掉轉囘大碼頭,再慢船就開了。」
司機依照他的說話掉囘頭,但車子却駛進一條又狹又小的山徑上。而且,車子忽然停了下來,前面一架私家車阻住去路。前面的司機說:「汽車壞了,打不着火。」
兩旁是山壁,而路又小得只可以容納一架車子經過。
馮西揚氣得瞪大眼睛,只得吩咐自己的司機向後開,想由第二條路走。但車子剛倒退了兩步,後面又有一輛車擋住去路。馮西揚眞是怒不可歇,他跳下車來,要他將車子退出,讓他先過。但那司機卻慢吞吞地吿訴他:「我的車子沒有退後波。」
馮西揚急得在地上跳,還是自己那個司機想得出,他建議不如大家合力將前面的車子推開。
大家都同意了,但推車的時候,三個司機又好像十多天沒有吃飯似的,推得滿身大汗。
西揚坐的的士終於開走了。其餘的兩個司機大笑起來,原來他們就是湘紫和家瑞。
車到碼頭,船剛啓椗,西揚呆住了,他望着站在船上的洪玫魂,他看她在流涙。
後面傳來一聲嬌婉的聲音,他囘頭一看,原來一個年輕的女子在牽着自己的司機的手在叫:「天柱!」
西揚現在明白,這是詭計。他實在太憤怒了,他想走上去找那個叫天柱的司機的霉氣;但細看站在那邊的「天柱」正像「擎天之柱」一樣,是那麽雄偉,那麼魁梧,他不禁倒退了一步。
也就在這時,一大羣人擁到他的面前,嚷着要打他。這羣人就是勞獄虎和四個女兒,以及三個未來女婿。
西揚看見來勢洶湧,連忙抱頭急遁。
20
經過這番敎訓,獄虎覺悟了,他重新過着早去早囘的有規律的生活,勞太也囘復了失去了的光彩。
他們的實情雖然有着一絲裂痕,但這裂痕是隱而難見的,而且是會漸漸消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