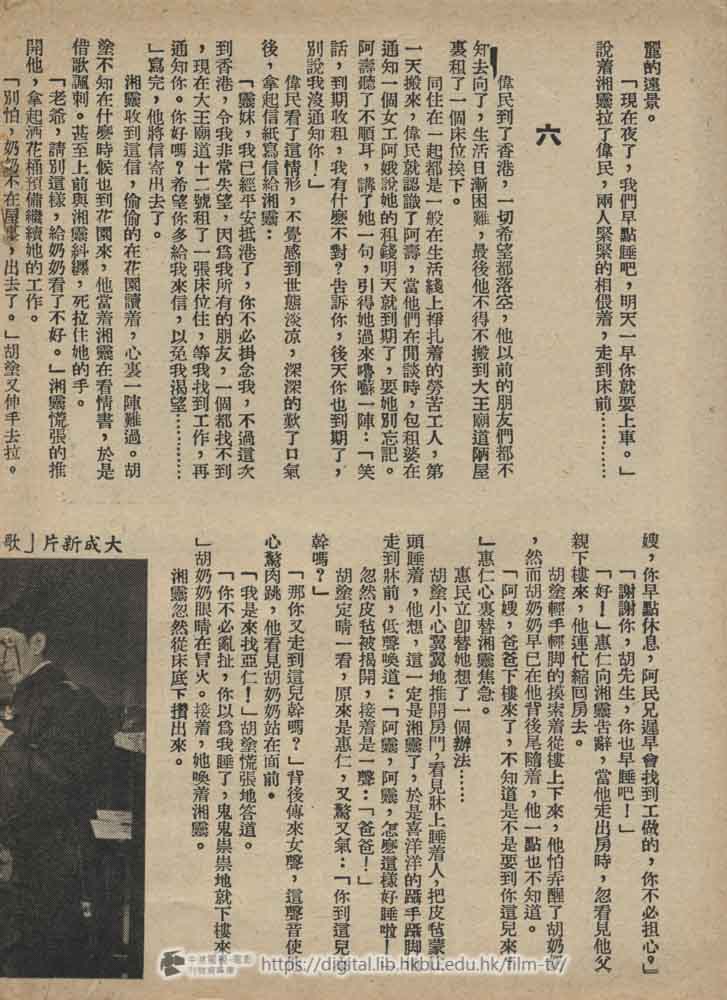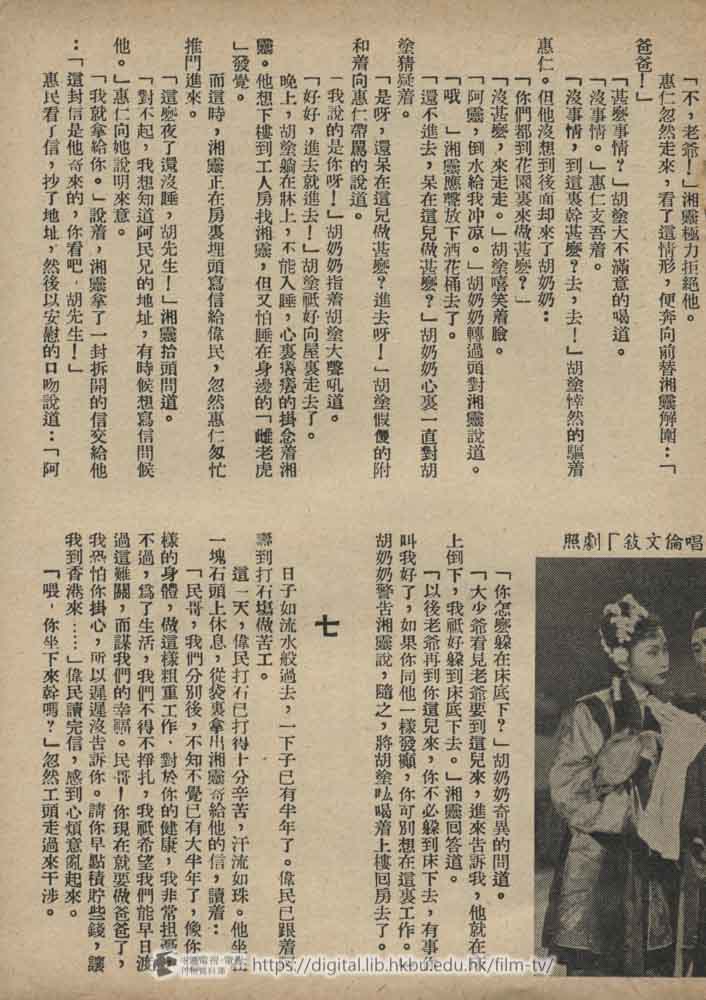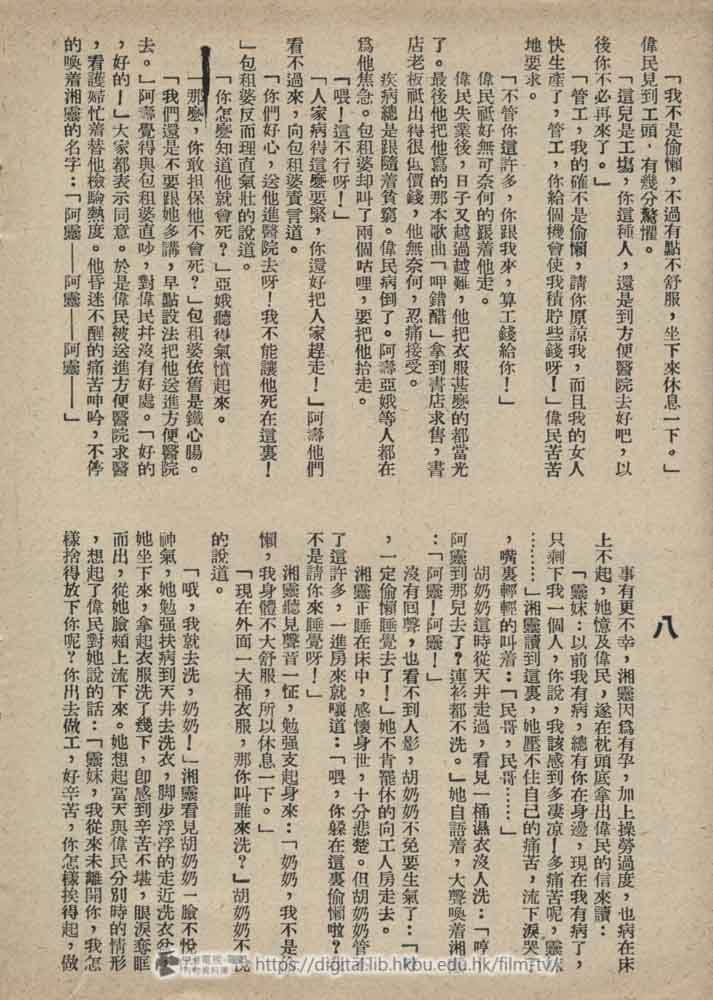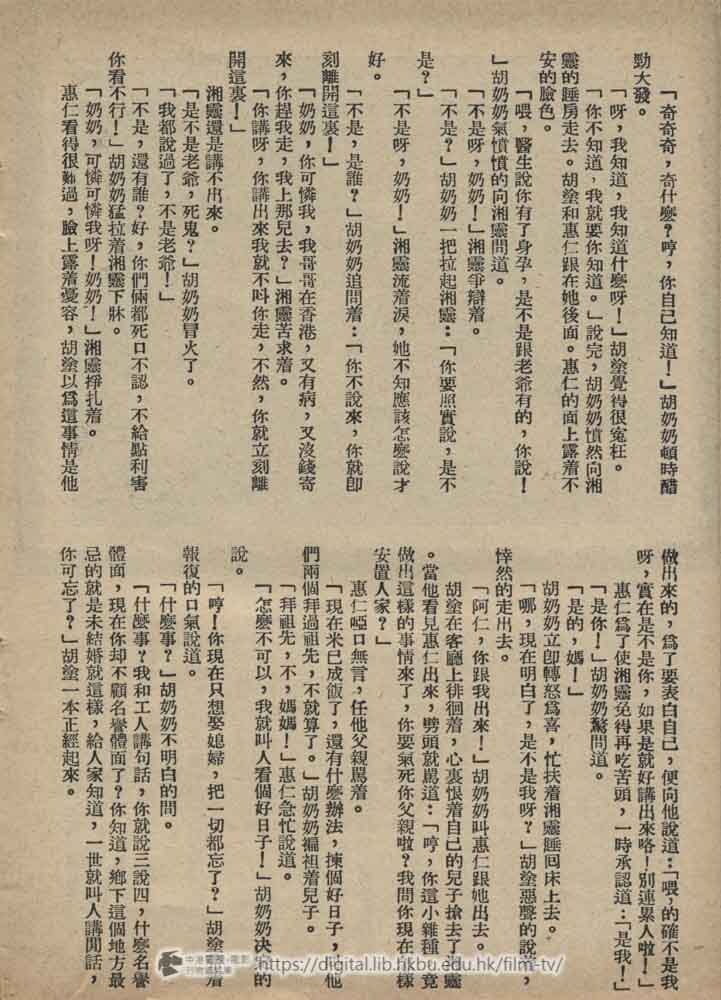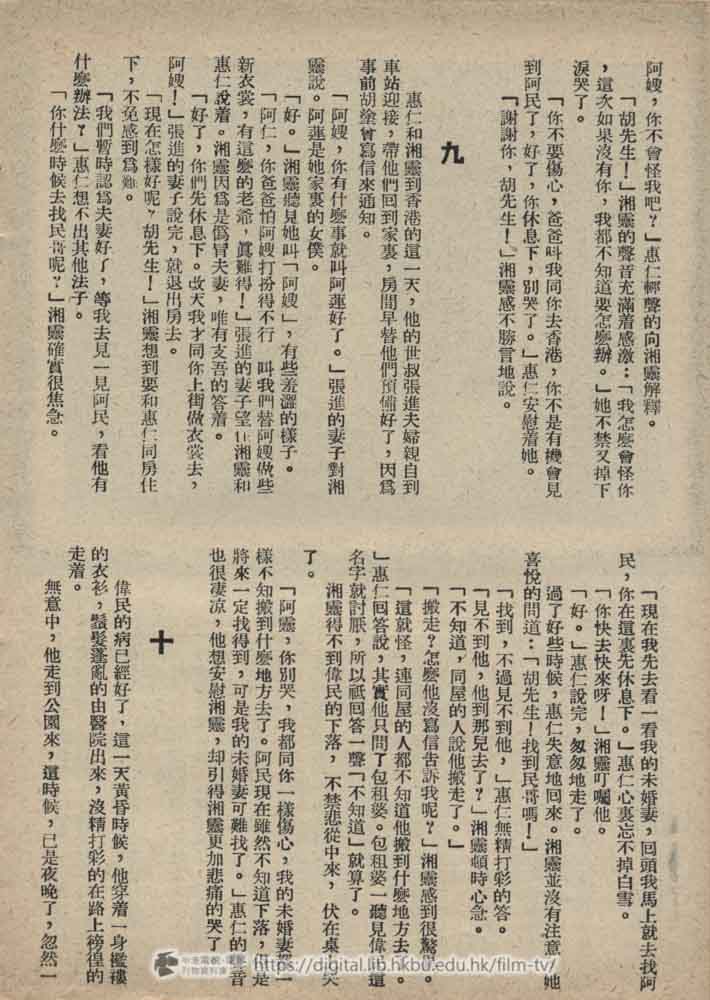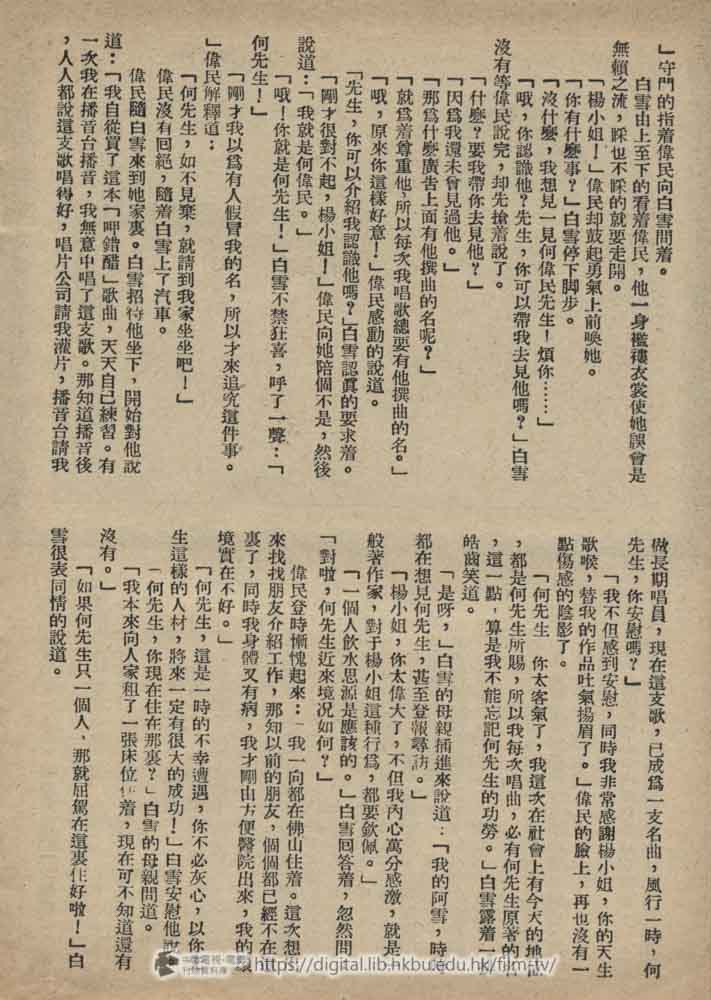呷錯醋
電影小說
金馬
一
鄕鎮郊外,一眼望去,阡陌相連。空中正盪漾着一陣悅耳的歌聲,這是從小巷一間舊屋傳出來的。
音樂家何偉民在拉着梵鈴,他的妻子趙湘靈則拿着曲譜隨着音樂高低抑揚的唱着,引得許多鄕民在門外圍着聚聽。
一曲終了,何偉民夫婦不知不覺中竟互相拍手叫好。
「民哥,你拍手做什麼呀?」湘靈笑着問道。
「贊你唱得好囉,那麼,你又拍手做什麼呀?」偉民囘答了,又問道。
「我也是贊你呀!」湘靈挨近他說:「玩梵玲玩得多好囉!」
他們快樂的互相擁抱起來,門外的鄕民看見他們這般親暱的樣子,感到好笑!
笑聲把湘靈從偉民的懷抱中驚醒,她推開了他,示意門外說道:「別這樣,你看門外這麼多人」。
偉民看看門外,他放開手笑着,不敢再動了。
而這時,收租人三叔却匆匆的走進人羣中,大聲的嚷道:「喂喂,走開走開,你們在這裏幹什麼,」有猪肉分嗎? 走走!」她一面揚手逐開衆人,一面走進屋子。
「看他這副怪相,眞叫人討厭!」不知誰在背後駡了一聲。
三叔耳尖,聽見有人罵她,囘頭厲聲責問道:「吓!誰說我叫人討厭?我怎樣叫人討厭?」
鄕民們看他這情形,大家一哄而散了。
屋裏偉民不知道三叔進來,拿着梵鈴對湘靈說道:「來,再唱一次⋯⋯」
「哦,這麽快活呀,又彈又唱!」三叔冷諷熱嘲的說。
「三叔!」湘靈向她打了招呼。
「三叔,怎末你來了,有什麽事呀?」偉民驚異的問他。
「你以爲我來聽你們唱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嗎?」三叔拉長着臉說:「來收租啦,欠了這麽久,怎末樣呀?」
「三叔,請你再寬限幾天。亞民哥還沒有事做,實在沒有錢。」湘靈向他要求。
「三叔,現在沒有錢,再寬限幾天吧!」偉民亦求着說。
「你們總說沒有錢,成日發癲發狂,拉琴唱歌,難道老天會掉下錢來給你們嗎?」三叔扳起面孔來。
「三叔,拉琴唱歌都是我們的職業啦!」偉民解釋道。
「職業,看你們這副窮相,幹這行的,你以爲還會發達嗎?古言說,財不入唱門,越拉越緊,把你們 窮死啦!」
「喂,三叔,我只不過欠你房租,你不能夠這樣亂詆毀我!」偉民有些憤怒。
「我要講,你掩得住我的口?哼!要爭氣,立卽交下租來呀!」三叔的口氣惡狠狠地。
「哼!⋯⋯」偉民憤怒極了,像要爆發的火山。
「民哥,你⋯⋯」湘靈急拉住他,制止他發火。
「怎樣?我吿訴你,最多這次賞你們臉,下次再不交租,我就請你們滾蛋!」三叔似乎有點怕偉民發 火,祗好剛中帶軟的,說完就走了。
「哼,一個人窮了就叫人看不去。」偉民拿起梵鈴,自言自語着:「說我越拉越緊,財不入唱門?」
「民哥,你別這樣,慢慢想個辦法。」湘靈安慰他。
「好,我以後再不玩這個梵鈴了!」偉民說着,發狂似的走近窗前。
「民哥——」湘靈急追上來。但她來不及了,偉民在極度悲憤中,將梵鈴擲出窗外。
偉民的朋友胡惠仁畢業囘來正要來找他,梵鈴恰巧掉在他面前,嚇了他一跳:「咦!這是搞什麼呀?」他俯下身拾起被摔壞了的梵鈴,表示很可惜:「幹嗎這樣浪費呀?」
湘靈一眼看見他:「哦,胡先生,你囘來了!請進來坐 。」
「好好。」惠仁拿着梵鈴走進去。
「請用茶,胡先生。」湘靈奉茶招待客人。
「哦,謝謝,」惠仁接着問道:「喂,你們幹嗎這樣浪費,將一個梵鈴丟了,耍花槍也不必這樣呀,而且這個梵鈴,你不是把它當着生命寶貝看嗎?」最後他向偉民說道。
「唉,你不知道,總之是受不了氣!」偉民煩燥的囘答。
「難道是同亞嫂鬥氣了?不會吧,你們素來是如膠似漆的這麽好。」
「不,民哥一時發了脾氣!」湘靈解釋道。
「什麽事呀?」
「哼,總是自己窮,不爭氣,連收租公都看不起。」偉民自艾自怨起來,接着說道:「惠仁兄,你知道的,我沒事做這麼久了,那裏有錢還他呢!」
「那麽就遲點還他好了。」惠仁寬慰着他。
「他跟你這麽講就好了。我沒錢還他,他亂詆毀我,又說什麼財不入唱門,我們幹這一行的,越扯越緊,一世都出不了頭。你說氣不氣?」
「哦,是這樣嗎,那你也不必氣了。」惠仁還是寬慰他 :「得啦 明天我替你想個辦法還他。」
「這怎末好意思。」
「沒問題,大家都是老朋友,有什麽計較。我現在囘家去看看父母先,明天再來跟你談。 」惠仁立起身來。
「那麽,明天請你一定來。」 偉民也跟着站起來。
「我一定來,你們不必担心。 」說着,惠仁向他們吿辭了。
送走客人後,湘靈對偉民說道:「哪,這一來可不必担心了,民哥。」
偉民沒有囘答她,靜靜地又坐在一張櫈子上去。
「民哥,胡先生都肯替我們交租了,你爲什麽又這樣發悶呢?」湘靈走過來,關切的問道。
「靈妹,我平生最喜歡的就是音樂和作曲,所以我用盡苦心去做,希望成爲一件事業,那兒知道一無發展,而且還要受人奚落!」偉民感到很失意。
「你不要灰心,民哥,今天雖然是受人奚落,但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我相信總有成功的一天,民哥,你放心啦,民哥,來,你敎我唱那支連環相思債吧!」湘靈鼓勵着他,把他從櫈子上拉起來,走到寫字台去拿曲譜。
二
胡惠仁囘家來,一進門正遇着女佣人亞三,她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拿着手巾揩眼淚。
「大少,你囘來了!」亞三招呼道。
「是的,你拿了包袱上哪兒去呀?」惠仁奇怪的問她。
「我走了,大少!」
「做得好好的,爲什麼要走?」
「奶奶把我辭掉了。」亞三很委曲的樣子。
「爲什麽奶奶要辭掉你?」惠仁不明白。
「我怎麽知道?大少,我走了!」亞三提着包袱 ,心裏難過的走了。
惠仁走進大廳,他父親胡塗在一邊抽烟,母親則負氣的坐在另一邊,惠仁走上去向他們個老人家招呼 道:「爸爸,媽媽。」
「亞仁,你囘來了。」胡奶奶臉上有了一些笑容。
「爸爸,爲什麽把亞三辭掉了?」恵仁向他父親問道。
「怎末知道你媽呀!」胡塗帶着不高興的口氣說道。
「哼,還說怎未知道我。」胡奶奶負氣地截斷道:「成天掛住同亞三拉拉扯扯,人家是有丈夫的,我就怕他搞出事情,才把她辭了。」
「你別聽她亂講,我幾十歲的人了,那有這麽糊塗呢,分明是她心地窄吃乾醋!」胡塗紅着臉爭辯。 「心地窄!你有條尾巴我都知道!」胡奶奶大聲吆喝。
「你把我當狗啦?有條尾!」
「媽,我們沒有人打理家庭,不是不方便嗎!」惠仁見父親和母親在鬥嘴,便改換話題問道。
「沒有人,再請一個。」胡奶奶覺得這事情很簡單。
「你請工人有這麽容易?疑三疑四的!」胡塗的話像支冷箭。
「我有分數,不嫁人的我就請,有了丈夫的我就不請, 你不愛名譽,我可愛呀!」胡奶奶很有把握的樣子。
「你怎末說都行,橫直口是你的。」
「你知道就好。」胡奶奶自覺勝利, 她轉向惠仁說道: 「亞仁,你囘來正好。」
「有什麼事嗎?」惠仁覺得母親說得很突然。
「我知道你這次畢業了,所以托人找個門當戶對的小姐配親,現在媒婆已有了囘音,祗等你囘來看看喜歡不喜歡。」
「那不用看了,媽!」
「爲什麽?」胡奶奶不禁很焦急。
「我已經有了⋯⋯」
「哪,你不必怕沒有媳婦服侍你!」胡塗的一肚子氣好像還未洩完。
「亞仁,娶老婆不同別的事情,你有沒有查明她的家世呀?」胡奶奶不放心。
「怎未還不知道, 以前是我的同學。」
「她肯囘來鄕下住嗎?」胡奶奶追問着。
「當然肯跟我囘來 。」
「肯囘來鄕下住就好。」胡奶奶放下心。接着向胡塗問道:「你贊成不贊成 ?」
「全由你主意,我沒有問題。 」胡塗愛理不理的樣子。
「不過,爸爸,她要我給她三千元,才肯與我結婚。」惠仁對這問題不免要覺得困難。
「要三千元?」胡塗驚訝問道:「喂,我們是娶媳婦,不要買媳婦的呀!」
「不錯,亞仁,爲什麽要三千元這麽多呢?」胡奶奶附和丈夫說道。
「還要問,我看這一定是不三不四的女子。」胡塗斬釘截鐵的斷定着。
「不呀,爸爸,她要錢是有理由的。」惠仁急說道。
「有理由,那就是刮錢的理由了。」
「不,爸爸,因爲她父親臨死的時候,欠了人家三千元,所以她母親要這筆欵還人家。」
「分明是借辭,那裏有嫁女還債的?你受人欺詐,我却不上當!」胡塗口氣很堅强。
「亞仁,還是好好地聽我替你找一個吧。」胡奶奶勸着說。
「媽,你叫我這樣盲婚,我實在做不到而且我又答應了她。」惠仁不贊同他母親的意見。
「你答應是你的事,要我給三千元,做不到!」 胡塗堅决地不答應兒子的要求。
惠仁聽了父親這番話,不再出聲的憤然囘到自己房中,焦急的踱着,忽然坐到寫字枱前,執起筆寫信 。寫後自己讀着:
「白雪妹:」他情不自禁的吻了一下信紙:「我離開你一分鐘,好似離開你一百年這樣難過。我覺得我的心永遠在你身邊一樣,關於我們結婚的事情,我爸爸已經答應,不過,那三千元,暫時不能給你,請你耐心等候,我一定設法,我的心都很急,你需要這筆錢卽是我需要一樣,雪妹,卽使海枯石爛,我永遠愛你! 」讀完信,寫好了地址,他又在皮挾內拿出白雪的照片,甜蜜的在它上面吻了一下。
三
白雪和女友從書檔買了幾本歌集囘家,幾個女友圍住她坐下,聽她唱歌,剛唱完一曲,她母親拿了一封信給她:
「亞雪,別唱啦,你的亞仁哥有信寄給你呀!」
白雪歡喜的接信:「仁哥有信來啦,給我。」
「哎呀,看你這樣心急。」她母親取笑她。
「情書來的呀!」
「公開!公開!」
大家擁上前圍住白雪,白雪把信舉得高高的,像一個快樂的天使一樣跳上櫈上,然後折信讀着,當她讀完信時,她的笑容盡歛了,心情沉重地從櫈上下來。
「什麽事呀?雪姐!」
「信說什麽,怎麽你看了不高興!」
女友們關心的問着。
白雪默不作聲。她母親上前問道:「亜雪,信究竟講什麽呀?」
「仁哥說他爸爸已經答應了,不過三千元一時不能給我們,叫我們等一個時候。」白雪悒不樂的囘答。
「是不是呢,我都說過他沒辦法,三千元,可不是容易找呀。」她母親帶着輕蔑的口氣說道。
「媽,我相信仁哥對我很好,一定不會失信的,我們就再等個時候吧。」白雪依然對惠仁懷着希望。
「你別這樣傻了,聽他的話等到什麽時候,等到來老了,還是讓我替你找個有錢的人結婚,還了這筆債。」
「不!媽!無論怎樣我都要等他!」白雪要求她母親。
「吓,笑話,那不必還錢給你世伯了?」她母親不以爲然的說。
「世伯的錢,我同他講,慢慢的還給他,我一定要等仁哥的消息!」白雪對惠仁還是一片痴心。
「就算不必還債,但是我們還要生活呀!」
「怕什麽,我不會去找工作做嗎?」白雪自有打算。
「不用怕,伯母!慢慢的想辦法好了!」女友們也幫助白雪向她母親勸道。
「唉!我不明白你怎麼會這樣死心亞仁?」白雪的母親對自己的女兒還是不很同情。
四
這一天,三叔帶了兩個挑伕來到偉民家裏,聲勢兇兇地:「喂,怎麽樣?今天的租錢給不給得出呀?」
「三叔,你別迫人太甚哦,你不用担憂我沒租錢給你。」偉民看到三叔那種兇狠的態度,心裏確實有 些憤恨。
「這麽說你又不給了?」
「急什麽呀,等一下我朋友來就給你!」
「我管不了這許多,要給就快點給,不給就快點搬!」
「請你等一等,三叔,別怕沒錢給你呀!」湘靈忍氣地說道:
然而三叔依然不肯罷休,她一定要偉民立卽交出租錢,因此大家喧鬧起來,就在這時候,惠仁來了。 「喂喂,什麽事呀,鬧成這樣?」惠仁向大家問道。
「又來趕搬啦。」湘靈第一個囘答。
「趕搬?怎麼一點人情都不講?」惠仁也覺得三叔太不講情了。
「不給租,我當然要趕!」三叔依舊沒有好聲的說。
「哦,爲了欠租嗎?那也不必趕得這麽緊!」
「笑話,不必趕得緊,那就錢來呀,不然,你替他們給呀!」三叔向惠仁伸出一隻手。
這簡直對惠仁是一種侮辱,他爭氣地要掏錢還他,可是袋子是空的,他感到很失意。
三叔看在眼裏:「怎樣?沒有錢就不要學人講大話啊!」
惠仁忍受不了,他毅然脫下手錶給他:「就用這隻錶作數,好嗎?」
三叔接着手錶審視一番:「手錶呀,也好,就算你的! 」說完,他得意的笑着,走出去了。
「亞仁,你怎麼給他手錶呢?你沒有錢嗎?」偉民奇異的問道。
「唉,因爲我愛上了一個女子,想同她結婚,但需要三千元,這樣我同我父親鬧了,他不但不答應,還要叫我和這個女子斷絕來往,現在他一分錢都不給我,禁止我再去香港,迫我離開這個女子。」惠仁有所痛苦的解釋着。
「亞仁,你這樣幫我忙,我太感激你了。」偉民不禁說道.
「是的,眞過意不去,胡先生!」湘靈也用感激的眼光望住惠仁。
惠仁並不計較這些,他反而替偉民日後生活躭心,最後他贊成偉民到香港去找點事情做,不過偉民却爲了旅費和湘靈的問題感到困難。
「民哥,你不必替我担心,如果你去找事情做,我也可以在這替人家做工,這樣你不是可以安心啦。」湘靈也贊同偉民到香港去。
「誰會請你呢?你又做不慣,而且這裏找工作也不是容易。」偉民仍覺得有難題。
「正好我家裏要請人,如果亞嫂不見嫌,就到我家裏去做先。」惠仁想起家裏沒用僕人,善意的說道。
「好呀,民哥,我到胡先生那裏做工,你不就可安心啦!」湘靈認爲這機會太好了。
「不過我母親說過,要請不出嫁的女子。」惠仁補充道。
「我就承認我不出嫁不就行嗎,你母親又不認得我。」
「如果這樣,我還可以同我父親商量, 先借旅費給你, 然後才在亞嫂的工錢中扣下,相信我父親會答應的。」
「能這樣更好。」偉民不再感到有困難了。
「好,我們現在到我家裏去,你們假認爲兄妹,我就有辦法向我父親借錢。」
於是惠仁帶了偉民夫婦到家裏來了。他先到書房裏找他父親:「爸爸,我有個朋友,想來借二百元, 爸爸,你借給他好嗎?」
「吓,枉你是我的兒子,你不知道你爸爸的脾氣 ,一向是賒借免問的!」胡塗最怕聽見借錢。
「我知道。」
「你知道還要問什麼?」
「不過他是我的朋友,想借點旅費到香港去找工作,所以才敢開口。」
「好朋友又怎樣?總之,借錢就不行。你知道嗎?借給人容易,叫人還就難。還算你這麽大了,眞是白吃了米。」
「不,爸爸,他還有條件向你借。」惠仁把「條件」兩字說得特別重。
「有什麽條件?」胡塗登時睜大了眼睛。
「他有個妹妹,我想叫她在這裏做工,以她的工錢來還債,這樣就不怕他欠了,而且我和他又是好朋 友,爸爸,你幫下他的忙吧。」惠仁誠懇的說道。
「他的妹妹嫁人了嗎?」胡塗似乎對這條件有了興趣。
「還沒有,今年最多十八九歲哩。」
「哦,她生得怎樣?」胡塗的興趣濃起來了。
「很漂亮,兩兄妹現在就在客廳裏,你出去看看。」惠仁覺得自己的計劃有了八九成了。
「好,我同你去見見她,如果合意的,就有得商量。」胡塗心裏另有一種希望。
惠仁帶了他父親來到客廳裏,替偉民和湘靈介紹,胡塗嘴裏「哦,哦,」的點着頭,兩隻眼晴却很貪婪的瞪住湘靈,使湘靈不免感到有些羞澀。
「你們倆是兄妹嗎?」胡塗的眼睛一刻也不離湘靈。
「是的,胡先生,」偉民囘答道。
「你還未嫁嗎?」胡塗望一眼偉民,囘過頭去就對湘靈問道。
「⋯⋯⋯⋯」湘靈畏羞的沒有作答。
「還沒有,我不是已經說給爸爸聽了。」還是惠仁替湘靈囘答道。
「我都要問個明白,你知道你媽媽,她是要沒有嫁人的 。」
「我是還沒有嫁人,胡老爺!」湘靈鼓着勇氣說了。
「好極了!」胡塗心裏一陣快樂:「你哥哥想出城去找工作嗎?」
「是的,老爺,請你幫忙幫忙!」湘靈帶着要求的口吻說。
「不成問題,不成問題!」胡塗連聲說道:「我一向都好商量。」他囘頭向偉民問道:「你是想借二百元嗎?」
「不錯,胡老先生,這筆錢等我找到工作就還你,明天我就要起程了。」偉民囘答說。
「不忙不忙,祗要你妹妹在這裏做一年工,還不還,都沒問題。」胡塗心裏當然有數:「現在就先給你錢。」他一面拿出錢,一面向湘靈說道:「最好你快來上工。」
「老爺,不過我妹妹不大會做工⋯⋯⋯⋯」偉民說道,他話還沒說完,胡塗却搶着說:
「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敎她的,不會慢慢學好了,你放心!」
接着偉民和湘靈向胡塗吿辭了,胡塗一直望住湘靈的背影,他忘形的涎着臉瞪住。惠仁看得在旁偷笑。
「你笑什麽?」胡塗見兒子在笑,有點羞愧。
「沒什麽。」惠仁收歛了笑容。
「等下你媽媽囘來,你就說這工人是你中意的,千萬別說我看合意,你知道你媽媽好像開醬園舖一樣,一埕埕的都是醋!」胡塗再三的叮囑兒子。
五
晚上,湘靈在家裹替偉民收拾一切,她將一本「呷錯醋 」的曲本裝到衣箱裏去。偉民看見這曲本,感慨萬端的說道:「枉費我幾年心血寫成這部曲,結果如此。」
「民哥,你別灰心,這裏沒有人賞識,或許到城市就一曲成名都說不定,本來萬事都是講機會。」湘 靈安慰他,叫他早點休息,以便明早動身。
「今晚怎睡得着。」偉民悒悒不樂地走到窗前。
「⋯⋯⋯⋯」湘靈一時找不到話再安慰他,因爲她自己也和偉民一樣爲了這次別離而難過,不禁掉下眼淚了。
「靈妹,你怎麽哭了?」偉民走過來,拉住她的手。
「不,我沒哭。」湘靈强笑着,她不想引起偉民更大的傷感。
「靈妹,你別騙我,我想我還是不去。」
「你不去?」
「嗯,因爲我們從來未曾離開過,這次離開不但你傷心,我實在也萬分捨不得你,靈妹!」
「民哥,我知道我們的心情一樣,不願離開,不過因爲環境,同時爲了你的前途,民哥,我們不能不 離開。」湘靈壓住心底的痛苦說:「我只希望你向前奮鬥,得囘離別痛苦的代價!」
「我當然會向前掙扎,不過留下你一個人在這裏 ,你又未曾出去做過工,怎樣受得人家的氣,所以我 實在不能安心。」
「你別這麼想,這不過是暫時的事。你出去一找到錢,我們不是可以從新組織新家庭了,你說那時我 們多快活呀!」湘靈勉强的安慰偉民。
偉民沒有做聲,他像是在痛苦的深淵裏看見了美麗的遠景。
「現在夜了,我們早點睡吧,明天一早你就要上車。」 說着湘靈拉了偉民,兩人緊緊的相偎着,走到床前⋯⋯⋯⋯
六
偉民到了香港,一切希望都落空,他以前的朋友們都不知去向了,生活日漸困難,最後他不得不搬到大王廟道陋屋裏租了一個床位挨下。
同住在一起都是一般在生活綫上掙扎着的勞苦工人,第一天搬來,偉民就認識了阿壽,當他們在閒談時,包租婆在通知一個女工阿娥說她的租錢明天就到期了,要她別忘記。 阿壽聽了不順耳,講了她一句,引得她過來嚕囌一陣:「 笑話,到期收租,我有什麼不對?吿訴你,後天你也到期了, 別說我沒通知你!」
偉民看了這情形,不覺感到世態淡凉,深深的歎了口氣後,拿起信紙寫信給湘靈:
「靈妹,我已經平安抵港了,你不必掛念我,不過這次到香港,令我非常失望,因爲我所有的朋友,一個都找不到,現在大王廟道十二號租了一張床位住,等我找到工作,再通知你。你好嗎?希望你多給我來信,以免我渴望⋯⋯⋯⋯ 」寫完,他將信寄出去了。
湘靈收到這信,偷偷的在花園讀着,心裏一陣難過。胡塗不知在什麽時候也到花園來,他當着湘靈在看情書,於是借歌諷剌。甚至上前與湘靈糾纏,死拉住她的手。
「老爺,請別這樣,給奶奶看了不好。」湖靈慌張的推開他,拿起洒花桶預備繼續她的工作。
「別怕,奶奶不在屋,出去了。」胡塗又伸手去拉。
「不,老爺!」湘靈極力拒絕他。
惠仁忽然走來,看了這情形,便奔向前替湘靈解圍:「爸爸!」
「甚麽事情?」胡塗大不滿意的喝道。
「沒事情。」惠仁支吾着。
「沒事情,到這裏幹甚麼?去,去!」胡塗悻然的驅着惠仁。但他沒想到後面却來了胡奶奶:
「你們都到花園裏來做甚麽?」
「沒甚麽,來走走。」胡塗嘻笑着臉。
「阿靈,倒水給我冲凉。」胡奶奶轉過頭對湘靈說道。
「哦 」湘靈應聲放下洒花桶去了。
「還不進去,呆在這兒做甚麼?」胡奶奶心裏一直對胡塗猜疑着。
「是呀,還呆在這兒做甚麽?進去呀!」胡塗假傻的附和着向惠仁帶罵的說道。
「我說的是你呀!」胡奶奶指着胡塗大聲吼道。
「好好,進去就進去!」胡塗祗好向屋裏走去了。
晚上,胡塗躺在牀上,不能入睡,心裏癢癢的掛念着湘靈。他想下樓到工人房找湘靈,但又怕睡在身邊的「雌老虎 」發覺。
而這時,湘靈正在房裏理頭寫信給偉民,忽然惠仁匆忙推門進來。
「這麽夜了還沒睡,胡先生!」湘靈抬頭問道。
「對不起,我想知道阿民兄的地址,有時候想寫信問候他。」惠仁向她說明來意。
「我就拿給你。」說着,湘靈拿了一封拆開的信交給他 :「這封信是他寄來的,你看吧,胡先生!」
惠民看了信,抄了地址,然後以安慰的口吻說道:「阿嫂,你早點休息,阿民兄遲早會找到工做的,你不必担心。」
「謝謝你,胡先生,你也早睡吧!」
「好!」惠仁向湘靈吿辭,當他走出房時,忽看見他父親下樓來,他連忙縮囘房去。
胡塗輕手轉脚的摸索着從樓上下來,他怕弄醒了胡奶奶 ,然而胡奶奶早已在他背後尾隨着,他一點也不知道。
「阿嫂,爸爸下樓來了,不知道是不是要到你這兒來? 」惠仁心裏替湘靈焦急。
惠民立卽替她想了一個辦法⋯⋯⋯⋯
胡塗小心翼翼地推開房門,看見牀上睡着人,把皮毡蒙住頭睡着,他想,這一定是湘靈了,於是喜洋洋的躡手躡脚地走到牀前,低聲喚道:「阿靈,阿靈,怎麽這樣好睡啦——」
忽然皮毡被揭開,接着是一聲:「爸爸!」
胡塗定晴一看,原來是惠仁,又驚又氣:「你到這兒來幹嗎?」
「那你又走到這兒幹嗎?」背後傳來女聲,這聲音使他心驚肉跳,他看見胡奶奶站在面前。
「我是來找亞仁!」胡塗慌張地答道。
「你不必亂扯,你以爲我睡了,鬼鬼祟祟地就下樓來! 」胡奶奶眼睛在冒火。接着,她喚着湘靈。
湘靈忽然從床底下攢出來。
「你怎麽躱在床底下?」胡奶奶奇異的問道。
「大少爺看見老爺要到這兒來,進來吿訴我,他就在床上倒下,我祗好躱到床底下去。」湘靈囘答道。
「以後老爺再到你這兒來,你不必躱到床下去,有事你叫我好了,如果你同他一樣發癲,你可別想在這裏工作。」 胡奶奶初警吿湘靈說,隨之,將胡塗吆喝着上樓囘房去了。
七
日子如流水般過去,一下子已有半年了。偉民已跟着阿壽到打石塲做苦工。
這一天,偉民打工已打得十分辛苦,汗流如珠。他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從袋裹拿出湘靈寄給他的信,讀着:
「民哥,我們分別後,不知不覺已有大半年了,像你這樣的身體,做這樣粗重工作,對於你的健康,我非常担憂, 不過,爲了生活,我們不得不掙扎,我祗希望我們能早日渡過這難關,而謀我們的幸福。民哥!你現在就要做爸爸了,我恐怕你掛心,所以遲遲沒吿訴你。請你早點積貯些錢,讓我到香港來⋯⋯」偉民讀完信,感到心煩意亂起來。
「喂,你坐下來幹嗎?」忽然工頭走過來干涉。
「我不是偷懶,不過有點不舒服,坐下來休息一下。」 偉民見到工頭,有幾分驚懼。
「這兒是工場,你這種人,還是到方便醫院去好吧,以後你不必再來了。」
「管工,我的確不是偷懶,請你原諒我,而且我的女人快生產了,管工,你給個機會使我積貯些錢呀!」偉民苦苦地要求。
「不管你這許多,你跟我來,算工錢給你!」
偉民祗好無可奈何的跟着他走。
偉民失業後,日子又越過越難,他把衣服甚麽的都當光了。最後他把他寫的那本歌曲「呷錯醋」拿到書店求售,書店老板祗出得很低價錢,他無奈何,忍痛接受。
疾病總是跟隨着貧窮。偉民病倒了。阿壽亞娥等人都在爲他焦急。包租婆却叫了兩個咕哩,要把他抬走。
「喂!這不行呀!」
「人家病得這麽要緊,你還好把人家趕走!」阿壽他們看不過來,向包租婆責言道。
「你們好心,送他進醫院去呀!我不能讓他死在這裏!」包租婆反而理直氣壯的說道。
「你怎麽知道他就會死?」亞娥聽得氣憤起來。
「那麼,你敢担保他不會死?」包租婆依舊是鐵心腸。
「我們還是不要跟她多講,早點設法把他送進方便醫院去。」阿壽覺得與包租婆直吵,對偉民幷沒有好處。「好的,好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於是偉民被送進方便醫院求醫,看護婦忙着替他檢驗熱度。他昏迷不醒的痛苦呻吟,不停的喚着湘靈的名字:「阿靈——阿靈——阿靈——」
八
事有更不幸,湘靈因爲有孕,加上操勞過度,也病在床上不起,她憶及偉民,遂在枕頭底拿出偉民的信來讀:
「靈妹:以前我有病,總有你在身邊,現在我有病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你說,我該感到多凄凉!多痛苦呢,靈妹⋯⋯⋯」湘靈讀到這裏,她壓不住自己的痛苦,流下淚哭了,嘴裏輕輕的叫着:「民哥,民哥⋯⋯」
胡奶奶這時從天井走過,看見一桶濕衣沒人洗:「哼!阿靈到那兒去了?連衫都不洗。」她自語着,大聲喚着湘靈 :「阿靈!阿靈!」
沒好囘聲,也看不到人影,胡奶奶不免要生氣了:「哼 ,一定偷懶睡覺去了!」她不肯罷休的向工人房走去。
湘靈正睡在床中,感懷身世,十分悲楚。但胡奶奶管不了這許多,一進房來就嚷道:「喂,你躱在這裏偷懶啦?我不是請你來睡覺呀!」
湘靈聽見聲音一怔,勉强支起身來:「奶奶,我不是偷懶,我身體不大舒服,所以休息一下。」
「現在外面一大桶衣服,那你叫誰來洗?」胡奶奶不悅的說道。
「哦,我就去洗,奶奶!」湘靈看見胡奶奶一臉不悅的神氣,她勉强扶病到天井去洗衣,脚步浮浮的走近洗衣盆, 她坐下來,拿起衣服洗了幾下,卽感到辛苦不堪,眼淚奪眶而出,從她臉頰上流下來。她想起當天與偉民分別時的情形,想起了偉民對她說的話:「靈妹,我從來未離開你,我怎樣捨得放下你呢?你出去做工,好辛苦,你怎樣挨得起,做工要受人家的氣⋯⋯」想到這裏,她愈覺辛苦,她再支持不住了,突然昏倒在地上。
幸而惠仁在外面進來,急忙過來把湘靈抱起:「 阿嫂!阿嫂!」湘靈還不醒過來,惠仁急得驚叫:「 救命呀!救命呀!你們快出來!」
胡塗和胡奶奶聞聲,慌慌張張地趕來:「什麼事 ,什麽事?」
「亞靈昏過去了!」
「哎呀!怎麼辦!」胡奶奶也有些焦急:「亞仁 ,你快點去請醫生來!快去!快去!」
惠仁請醫生的時候,湘靈已被抬囘睡在她牀上了 ,她已經醒了。
當醫生替她診視後,胡塗和胡奶奶先後問道:「 怎樣?要緊嗎?醫生!」
「沒有事情,等我出去開條藥方她吃。」醫生微笑着說。
「醫生,她究竟是什麽病呀?」胡奶奶等醫生開完藥方後,問道。
「她有喜了,不好讓她勞動太多,應該休息一下 。」醫生回答道。
大家聽了都顯得很詫異,胡塗不信的說道:「不是罷,她還是個女子!」
胡奶奶却裝得鎭定向醫生說了一句:「謝謝你, 醫生!」
「吓!這就奇怪了,亞靈沒嫁人,怎末會有喜呢 ?奇怪!」醫生走後,胡塗莫明其妙的說道。 「奇奇奇,奇什麼?哼,你自己知道!」胡奶奶頓時醋勁大發。
「呀,我知道,我知道什麽呀!」胡塗覺得很寃枉。
「你不知道,我就要你知道。」說完,胡奶奶憤然向湘靈的睡房走去。胡塗和惠仁跟在她後面。惠仁的面上露着不安的臉色。
「喂,醫生說你有了身孕,是不是跟老爺有的,你說! 」胡奶奶氣憤憤的向湘靈問道。
「不是呀,奶奶!」湘靈爭辯着。
「不是?」胡奶奶一把拉起湘靈:「你要照實說,是不是?」
「不是呀,奶奶!」湘靈流着淚,她不知應該怎麽說才好。
「不是,是誰?」胡奶奶追問着:「你不說來,你就即刻離開這裏!」
「奶奶,你可憐我,我哥哥在香港,又有病,又沒錢寄來,你趕我走,我上那兒去?」湘靈苦求着。
「你講呀,你講出來我就不呌你走,不然你就立刻離開這裏!」
湘靈還是講不出來。
「是不是老爺,死鬼?」胡奶奶冒火了。
「我都說過了,不是老爺!」
「不是,還有誰?好,你們倆都死口不認,不給點利害你看不行!」胡奶奶猛拉着湘靈下牀。
「奶奶可憐可憐我呀!奶奶!」湘靈掙扎着。
惠仁看得很難過,臉上露着憂容,胡塗以爲這事情是他做出來的,爲了要表白自己,便向他說道: 「喂,的確不是我呀,實在是不是你,如果是就好講出來咯!別連累人啦!」
惠仁為了使湘靈免得再吃苦頭,一時承認道:「是我!」
「是你!」胡奶奶驚問道。
「是的,媽!」
胡奶奶立卽轉怒爲喜,忙扶着湘靈睡囘床上去。
「哪,現在明白了,是不是我呀?」胡塗惡聲的說着,悻然的走出去。
「阿仁,你跟我出來!」胡奶奶叫惠仁跟她出去。
胡塗在客廳上徘徊着,心裏恨着自己的兒子搶去了湘靈 。當他看見惠仁出來,劈頭就罵道:「哼,你這小雜種竟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了,你要氣死你父親啦?我問你現在怎樣安置人家?」
惠仁啞口無言,任他父親罵着。
「現在米已成飯了,還有什麽辦法,揀個好日子,叫他們兩個拜過祖先,不就算了。」胡奶奶褊袒着兒子。
「拜祖先,不,媽媽!」惠仁急忙說道。
「怎麽不可以,我就叫人看個好日子!」胡奶奶决定的說。
「哼!你現在只想娶媳婦,把一切都忘了?」胡塗帶着報復的口氣說道。
「什麽事?」胡奶奶不明白的問。
「什麽事?我和工人講句話,你就說三說四,什麽名譽體面,現在你却不顧名譽體面了?你知道,鄕下這個地方最忌的就是未結婚就這樣,給人家知道,一世就叫人講閒話,你可忘了?」胡塗一本正經起來。
「是呀,這可怎麽辦?」胡奶奶也覺得很對:「 可是畢竟還是自己的骨肉,你還是想個辦法安置他們 。」
胡塗想了想:「叫他們兩人先到香港住住,等孩子生了才囘來拜祖先。」
「也好,可是叫他們住到什麼地方去!」
「到世叔那兒住好了。孩子生了,做滿月的時候,我就跟你出去,這樣你就笑了!」
胡奶奶的確眼開眉笑:「好好,阿仁,我同你進去對阿靈說。」
湘靈一直倒在床上流淚,想着偉民,想到自己的遭遇,心裏像給萬刀碎割一般難過痛苦。
「你不要哭,不然要哭壞身體,我現在决定娶你做媳婦了。」胡奶奶坐在床邊安慰她。
「不,不行,奶奶!」湘靈又感到多一層痛苦。
「就這樣吧,阿靈,爸爸叫我們到香港去,等你生產了才囘來拜祖先。」惠仁連忙插嘴說,他知道他 這些話會使湘靈放心。
「是呀!」胡奶奶高興的說:「等你病好了,就同亞仁到香港去,免得給人知道了恥笑。」
「喂,你也做過年靑人啦,老呆在這裏做什麽,出來吧!」胡塗站在房門口對胡奶奶叫道。胡奶奶覺 得他言之有理,應該讓兩個年靑人私下談談,於是就跟着胡塗走出房去。
「我知道阿民在香港環境不好,又生病,如果媽把你趕出去,不是使你太難過了,所以我冒認下來,阿嫂,你不會怪我吧?」惠仁輕聲的向湘靈解釋。
「胡先生!」湘靈的聲音充滿着感激:「我怎麽會怪你,這次如果沒有你,我都不知道要怎麽辦。」她不禁又掉下淚哭了。
「你不要傷心,爸爸叫我同你去香港,你不是有機會見到阿民了,好了,你休息下,別哭了。」惠仁安慰着她。
「謝謝你,胡先生!」湘靈感不勝言地說。
九
惠仁和湘靈到香港的這一天,他的世叔張進夫婦親自到車站迎接,帶他們囘到家裏,房間早替他們預備好了,因為事前胡塗曾寫信來通知。
「阿嫂,你有什麼事就叫阿蓮好了。」張進的妻子對湘靈說。阿蓮是她家裏的女僕。
「好。」湘靈聽見她叫「阿嫂」,有些羞澀的樣子。
「阿仁,你爸爸怕阿嫂打扮得不行 叫我們替阿嫂做些新衣裳,有這麽的老爺,眞難得!」張進的妻子望住湘靈和惠仁說着。湘廳因為是僞冒夫妻,唯有支吾的答着。
「好了,你們先休息下。改天我才同你上街做衣裳去, 阿嫂!」張進的妻子說完,就退出房去。
「現在怎樣好呢?胡先生!」湘靈想到要和惠仁同房住下,不免感到為難。
「我們暫時認為夫妻好了,等我去見一見阿民,看他有什麼辦法?」惠仁想不出其他法子。
「你什麽時候去找民哥呢?」湘靈確實很焦急。
「現在我先去看一看我的未婚妻,囘頭我馬上就去找阿民,你在這裏休息下。」惠仁心裏忘不掉白雪。
「你快去快來呀!」湘靈叮囑他。
「好。」惠仁說完,匆匆地走了。
過了好些時候,惠仁失意地囘來。湘靈並沒有注意她喜悅的問道:「胡先生!找到民哥嗎!」
「找到,不過見不到他,」惠仁無精打彩的答。
「見不到他,他到那兒去了?」湘靈頓時心急。
「不知道,同屋的人說他搬走了。」
「搬走?怎麼他沒寫信吿訴我呢?」湘靈感到很驚異。
「這就怪,連同屋的人都不知道他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惠仁囘答說,其實他只問了包租婆。包租婆一聽見偉民這名字就討厭,所以祗囘答一聲「不知道」就算了。
湘靈得不到偉民的下落,不禁悲從中來,伏在桌上哭了。
「阿靈,你別哭,我都同你一樣傷心,我的未婚妻都一樣不知搬到什麽地方去了。阿民現在雖然不知道下落,但是將來一定找得到,可是我的未婚妻可難找了。」惠仁的聲音也很凄凉,他想安慰湘靈,却引得湘靈更加悲痛的哭了。
十
偉民的病已經好了,這一天黃昏時候,他穿着一身襤褸的衣衫,鬚髮蓬亂的由醫院出來,沒精打彩的在路上徬徨的走着。
無意中,他走到公園來,這時候,已是夜晚了,忽然一片歌聲迎面送來,唱的正是他所作的「呷錯醋」主題曲,他奇怪着,一步一步的行前,最後他看到凉亭處圍着許多人在聽歌。
凉亭處便是「天堂花園舞廳」,音樂台上正站着一個女子在唱歌,她就是惠仁一刻也不能忘懷的白雪。
歌聲一陣陣的在空中旋轉着,飄進偉民的耳裡 ——傷感把他佔有了,他頹然的在一張石櫈上坐下。 他想起了當時在鄕下和湘靈和唱的情形⋯⋯不久,歌聲停止了,接着從播音筒傳出一片掌聲,把偉民從追憶中喚醒,他聽見播音筒在報吿:
「各位聽衆,這裏是天堂花園舞廳,鑽石音樂茶座,播音台每日都在這個時候轉播本舞廳的特別歌唱 節目,由歌星楊白雪小姐主唱「呷錯醋」主題曲,請各位留意,現在本節目已經完了,再會!」
偉民感到自己的作品已替人成名,但自己還是潦倒不堪,他無限感慨的從石櫈站起來,走到舞廳門口 ,一幅大廣吿遂進他的眼廉:
天堂花園舞廳鑽石音樂茶座,每日情商禮聘歌唱明星白楊小姐登台主唱名曲「呷錯醋」,撰曲者:何 偉民先生。
偉民看到最後自己的名字,以爲有人竊用他的名,有些憤然,預備進舞廳找楊白雪理論,但被守門所 阻。正在這時候,舞廳陳經理送白雪出來:
「明晚再見!」
「再見,陳經理!」白雪揮了一下手。
「哦,楊小姐!這個人說要找你,你認識他嗎?」守門的指着偉民向白雪問着。
白雪由上至下的看着偉民,他一身號褸衣裳使她誤會是無賴之流,睬也不睬的就要走開。
「楊小姐!」偉民却鼓起勇氣上前喚她。
「你有什麽事?」白雪停下脚步。
「沒什麽,我想見一見何偉民先生!煩你⋯⋯」
「哦,你認識他?先生,你可以帶我去見他嗎?」白雪沒有等偉民說完,却先搶着說了。
「什麼?要我帶你去見他?」
「因爲我還未曾見過他。」
「那爲什麼廣吿上面有他撰曲的名呢?」
「就爲着尊重他,所以每次我唱歌總要有他撰曲的名。」
「哦,原來你這樣好意!」偉民感動的說道。
「先生,你可以介紹我認識他嗎?」白雪認眞的要求着。
「剛才很對不起,楊小姐!」偉民向她陪個不是,然後說道:「我就是何偉民。」
「哦!你就是何先生!」白雪不禁狂喜,呼了一聲:「何先生!」
「剛才我以爲有人假冒我的名,所以才來追究這件事。」偉民解釋道:
「何先生,如不見棄,就請到我家坐坐吧!」
偉民沒有囘絶,隨着白雪上了汽車。
偉民隨白雪來到她家裏。白雪招待他坐下,開始對他說道:「我自從買了這本「呷錯醋」歌曲,天天自己練習。有一次我在播音台播音,我無意中唱了這支歌。那知道播音後 ,人人都說這支歌唱得好,唱片公司請我灌片,播音台請我做長期唱員,現在這支歌,已成爲一支名曲,風行一時,何先生,你安慰嗎?」
「我不但感到安慰,同時我非常感謝楊小姐,你的天生歌喉,替我的作品吐氣揚眉了。」偉民的臉上,再也沒有一點傷感的陰影了。
「何先生 你太客氣了,我這次在社會上有今天的地位 ,都是何先生所賜,所以我每次唱曲,必有何先生原著的名,這一點,算是我不能忘記何先生的功勞。」白雪露着一排皓齒笑道。
「是呀,」白雪的母親插進來說道:「我的阿雪,時時都在想見何先生,甚至登報尋訪。」
「楊小姐,你太偉大了,不但我內心萬分感激,就是一般著作家,對于楊小姐這種行爲,都要欽佩。」
「一個人飮水思源是應該的。」白雪囘答着,忽然問:「對啦,何先生近來境况如何?」
偉民登時慚愧起來:「我一向都在佛山住着。這次想出來找找朋友介紹工作,那知以前的朋友,個個都已經不在這裏了,同時我身體又有病,我才剛由方便醫院出來,我的環境實在不好。」
「何先生,這是一時的不幸遭遇,你不必灰心,以你先生這樣的人材,將來一定有很大的成功!」白雪安慰他說。
「何先生,你現在住在那裏?」白雪的母親問道。
「我本來向人家租了一張床位住着,現在可不知道還有沒有。」
「如果何先生只一個人,那就屈駕在這裏住好哦!」白雪很表同情的說道。
「這太不方便了。」偉民不好意思接受。
「不會的,這裏有空房。」白雪的母親亦挽留着偉民。
「何先生就住下來好了,得空又可以敎敎阿雪唱歌。」白雪的母親又說道,她的態度是十分誠意。 「對了,改天我可以介紹何先生相識各方娛樂界的人,今後不怕沒有機會發展,何先生你說是不是? 」白雪想幫忙偉民找出路。
「能得到楊小姐這樣幫忙,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酬謝才好!」偉民非常感動。
「你是我的恩人,而且又是我的老師,我做子弟的應該替老師効勞,還敢要什麼酬謝。」白雪自己先 認起學生來了,她不讓偉民說話,就向她母親說道: 「媽!何先生剛病好,你帶何先生到房裏去休息吧!」
白雪這一片誠意,偉民感動得不好意思再推辭而且,自己眼前的生活,實在也很成問題,於是就答應住下來。
十一
這一天,偉民約好白雪出去見見各方面娛樂界的人物。他換上了新西裝,打著漂亮的領帶,頭髮梳得 光光的,鬍子也刮得領淨淨。
「阿雪,何先生這件西裝做得眞合身,穿起來整個人不同了,又年靑,又漂亮!」百雪的母親取笑着。 她這些話說得白雪羞答答起來,不自然的對偉民說:
「何先生,我們現在去吧!」
偉民隨着白雪出來,他們先訪問了舞廳,播音台,唱片公司諸經理,大家都表示對偉民很敬仰,滿口請他多多幫忙。
從此,偉民在音樂界漸漸有盛譽,終於紅極一時了。他的新唱片一出來,大家都紛紛爭購。因此各唱片公司,播音台,都忙着拉他簽合同。
現在偉民有了很大的收入,生活也就轉好了,他想起了湘靈,預備囘鄕下帶她出來。
起程之日,白雪親自送他到車站,火車開行時,她熱情的說道:「何先生,早點帶你的太太一齊來呀!」
「好好!」偉民快樂而感激的與她握了握手。「再見! 」白雪看着他走上車⋯⋯⋯⋯
十二
偉民一下火車,就趕往胡家。他敲着胡家大門。他按不住心裏的快樂,臉上露着笑容。
出來開門的是胡塗。
「胡先生!」偉民招呼道。
可是胡塗見他衣冠楚楚,一時想不起是誰,兩道猜疑的眼光一直打量着他。
「胡先生!我是何偉民呀!」偉民提醒了他。
「哦,你是何偉民呀!」胡塗恍然笑道:「你這一身西裝,叫我認不得你了。請進來,請進來!」
偉民進客廳,胡塗客氣地招待:「隨便坐,阿民!」
「不用客氣,胡先生!」偉民囘答,忽然問道:「怎末沒看見阿靈呢?」
「她同阿仁去香港了!」
「去香港了?」偉民很爲詫異。
「是呀,去好久了,他們沒去見你嗎?」
「沒有。」偉民接着奇怪的問道:「怎麼阿靈會同阿仁去香港呢?」
「你的阿靈已嫁給我的阿仁了!」胡塗像在報喜訊似的說道。
偉民嚇然一驚:「吓?你說什麼?胡先生?」
「我說你的妹妹嫁了我的兒子了。」
「嫁了你的兒子?」偉民不相信的問。
「你還不信,你的妹妹就快做媽媽了,我怕在鄉下給人講閒話,所以叫他們兩人到香港去,等你妹妹生產了再囘來拜祖完婚。」
偉民聽胡塗這麽說,頓時憤怒起來。
「也許你妹妹不敢見你,所以到香港沒去找你!」胡塗繼續說道。
「他們住在香港什麽地方?」偉民忍住心頭的氣憤。
「住在九龍花園街一百三十六號。你去見她呀!你妹妹這樣大了,也應該嫁人,而且又嫁給我們阿仁,我相信你一定很滿意。」胡塗似乎還沒有發覺偉民在憤怒。
然而偉民聽着再也不能忍耐了,他突然站起來,一聲也不吿別的走了。
「阿民,阿民!」胡塗莫明其妙,在他背後叫!⋯⋯⋯
偉民懷着一種又悲痛又激憤的心情囘到香港,照着地址找到張進的家來。
「請問這位伯母,胡惠仁是不是住在這裏?」偉民向張進的妻子問道。
「不錯,他現在正送他的女人到醫院去了!」
「吓?正到醫院去?」偉民心更急,他覺得事情越眞了。
「是呀,他的女人就要生小孩了,你是哪位呀,請進來坐坐吧!」張進的妻子誠意的說道。
可是偉民却「哼」了一聲,憤極的走了。
「吓,這種人也有!」張進的妻子對偉民這種態度感到奇怪⋯⋯
夜晚,偉民失意的走進天堂花園舞廳,他向僕役要了酒。當他聽見台上白雪在唱他所撰的歌曲時痛苦 就像音樂的拍子,一下下的擊着他的心,他受不住這痛苦,便以酒澆愁,狂飮起來。
白雪唱完曲後,便到他身邊坐下:「何老師,你來了!」
「嗯!」偉民失意的沒精打彩地應着。
「怎麽沒同何師母來呢?」白雪還未發覺他內心的痛苦。
「師母?——她嫁人了!」偉民顫抖着聲音說,他壓不下心裏的悲痛。
「老師,你是不是喝醉了?」白雪笑着說。
「我沒醉!」
「怎麼你說師母嫁了人?」
「請你別再提她,阿雪!」偉民很覺痛苦,接着解釋道:「因爲我離開鄕下的時候,她就到人家家裏做工,那知我囘去,他已經跟那少爺有了私情!」
「不會吧,老師?」白雪疑信參半。
「不會!他們兩個人已到香港來渡蜜月。而且她已進了醫院就要做媽媽了。」偉民說着,將那大半杯酒一飮而盡。
十三
湘靈進了醫院還未生產,惠仁在房門外徘徊,他等得心裏有些焦急,也感到疲倦,便走至客廳,無意中拿起報紙來看,却給他看到一段廣吿:
「歌園明星楊白雪小姐每晚八時在天堂花園舞廳鑽石音樂茶座播唱名曲「呷錯醋」⋯⋯⋯」
惠仁看完,不禁高興起來,他忘了湘靈要生產,放下報紙就走出醫院,一直到天堂花園舞廳來了。
「這裏是不是有位楊白雪小姐?」惠仁向僕役問道。
「有呀!」僕役囘答。
「對不起,請你通知她一下,說有一位胡惠仁想見她。」
「好,請你等一等。」於是僕役來通知白雪:「楊小姐 ,有位胡惠仁先生想見你。」
「胡惠仁!」白雪聽見這名字非常高興:「你請他到這兒來。」
「怎麽,你認識胡惠仁?」偉民很驚訝的問道。
「是的,我認識他!」
「引誘我老婆就是胡惠仁,不過不知道是不是這個胡惠仁?」偉民不敢斷定。
「哦?」白雪有點疑惑。
這時,惠仁正跟着僕役走來,偉民一眼看見:「就是他!」
「怎麽,就是他?」白雪對惠仁的情感一時崩潰了。她感到一陣憤恨。
惠仁並不知道,一看見她,歡喜欲狂的喚道:「阿雪!」
白雪並不囘答,偉民坐在一邊也一聲不响。
惠仁囘頭突見偉民,他更加高興起來:「呀!阿民,你也在這裏?」
偉民聽見惠仁叫他,他發火了,一掌推開他,怒聲說道 :「不錯,我在這裏!」
惠仁給他一推,差點跌倒地上,但却把隔台的玻璃杯瓶碰摔在地上碎了,引得全塲衆客嘩然起來。
舞廳的陳經理連忙趕來,勸解說道:「有事慢慢講,你們有什麼事呀?」他向偉民問着。
「這個人本來是我同鄕,他騙我老婆到他家做工,乘機佔了我老婆,你說這種人該不該打!」偉民理直氣壯的說道。
「阿民,你怎麽這樣說呀?」惠仁感到寃枉。
「你父親親口對我說的,難道我會寃枉你?」
「這就該打啦!」
「該打!」
「該打!」
衆人聽了都替偉民抱不平,惠仁正要分辯,但他沒有機會,許多人已向他衝來,逼得他從枱底下竄走,但他的頭上已受傷流血了。
惠仁帶傷囘到醫院,看護婦迎頭向他說道:「恭喜,胡先生!」
「豈有此理,我給人打得頭破血流,你還說恭喜!」惠仁委曲的皺着眉頭。
「胡太太生個男孩子啦!」
「生男子關我什麽事!」
「添丁呀,胡先生!怎麽跟你沒有關係?」看護婦奇異的望着他。
「哦,是是,謝謝你!」惠仁敷衍着:「對不起,請你快點給我一點止血藥。」
「好!」看護婦走了,惠仁走進房來看湘靈。
「胡先生!怎麽你頭上受傷了?」湘靈疲倦的躺在上牀撫着剛生下的嬰孩。
「給你阿民打了!」惠仁頹喪的說道。看護婦這時拿了藥進來,替他止血敷藥。
「胡先生!你在什麽地方見到阿民?」湘靈很心急的想知道偉民的下落。
「在天堂舞廳,還同我的未婚妻在一齊喝酒!」 惠仁帶着幾分醋意的說。
「噢?阿民怎麽會在舞廳呢?」湘靈覺得很奇怪。
「你的丈夫可派頭了,一身西裝畢挺挺,係個公子哥兒,怕中了馬票也說不定哦!」惠仁帶幾分諷刺的口氣說道。他這幾句話使看護婦非常詫異,怎末湘靈還有丈夫?於是開口問道:
「胡先生你的精神沒有受到很大的刺激吧!」
「沒有呵!」惠仁覺得看護婦的話很突然。
「可是你對胡太太說的話有點不對呀!」看護婦說着,笑着出去了。
惠仁和湘靈這才想起來,剛才的談話的確使局外人感到驚異,不禁也互相笑了笑。
「胡先生,阿民又怎樣會打你呢?」湘靈繼續問道。
「他以爲我們兩人眞的做了夫妻!」
「你不是可以對他解釋嗎?」
「一見就打,那兒有機會,走遲一步恐怕連命都沒有了!」
「他一向都不會這樣鹵莽的!」
「最糟的,連我的未婚妻都誤會起來,眞是自找麻煩!」惠仁自歎了一口氣。
「別怕,我出了院去見她,向她解釋,就沒事了。胡先生別再傷心了,囘去休息。」湘靈最後安慰他說。
「你也該早點休息了!」惠仁這才想起了湘靈是一個產婦。
十四
湘靈出了醫院,和惠仁來找白雪,可是白雪已搬了新址,他們又照址找上門,然而更不幸的是白雪的母親一開門, 看見了惠仁就生了氣,一聲不响的又把門關上,惠仁和湘靈只好沒精打彩的囘家。
由於對惠仁的誤會,白雪和偉民都受到同樣的痛苦,於是兩人的感情,已由師生的關係,一躍而達到沸點,而成爲一對熱戀的情人了。
十五
這一天,是湘靈的孩子彌月,「恭喜」聲充滿了整個客堂,從鄕下特地趕來替孫兒做彌月的糊塗夫婦,滿臉笑容的招呼着客人,忙個不了!
忽然一個客人送來一張請帖,上面寫着:「胡惠仁先生,趙湘靈小姐台升」胡塗接過來,順平翻開看着:「我倆謹定于五月十八日假座天堂花園大禮堂盟行結婚典禮,敬迓光臨。何偉民,楊白雪敬約」
胡塗看了,連忙拿給湘靈:「你哥哥今天結婚了,怎末沒早點通知,沒送禮眞不好意思。」
湘靈和惠仁聽了,不禁大驚。湘靈忍住心裏的焦急,等到沒人注意的時候,抱着兒子趕到天堂花園。偉民和白雪正在舉行婚禮,湘靈進來時,聽見司儀叫道:
「現在請新郞公開戀愛經過情形。」
湘靈忍不住心頭的憤恨,她衝上去,向大家宣佈道:「各位,你們想知道這位新郞哥的艶史嗎?我可以講給各位知道。這位新郞哥原來在鄕下有了髮妻,抛離了她,而愛上了這位歌星皇后⋯⋯⋯⋯」
衆來賓聽了湘靈這番話,非常奇異,大家面面相看。
「這對所謂才子佳人,」湘靈繼續含淚說道:「當然是天生佳偶,我是一個鄕下婆,當然配不上一個已成名的音樂家。」說着,她走近偉民:「我很自量,不會追究你,不過,這是你的骨肉,應由你負責。」她將手裏的孩子送還偉民。
偉民沒有把孩子抱過來:他發愕地呆視着湘靈,不知如何作答。而這時,惠仁也追來了,他向偉民大罵道:「你還算對得住我?阿民,我千辛萬苦保護你太太安全,你就竟然同我愛人結婚,現在我同你拼命!」惠仁舉手要打。
司儀連忙勸解:「有事慢慢講。偉民,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呀?」
「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偉民有點覺悟的樣子。
「你當然不知道,現在你已發達,你沒良心,我千方百計將阿嫂假冒我的愛人,連自己的父親都騙了 ,目的就是想帶阿嫂出來香港,等你們夫妻重逢,你就以德報怨,反而奪了我的愛人 你怎樣對得住我?」
偉民顯得非常慚愧:「阿仁,我太辜負你一片苦心,靈妹,這次完全出於誤會,我才這樣做,我何嘗 沒有爲你相思!楊小姐也一樣,阿仁,她本來也一直在愛着你,這隻戒指應該是你戴的!」他除下自己手 上戴着的戒指,替惠仁戴上後,拉他到白雪身邊:「我祝你們兩人幸福無邊。」
忽然,胡塗急匆匆地來了:「亞仁,現在來賓到齊了,還不快點囘去?」
「爸爸你來得正好,我介紹你認識,這位就是我以前對你說的,楊白雪小姐,我今天同她結婚呀!」 惠仁把白雪拉得緊緊地。
「吓,你結婚!」胡塗睜大眼睛,轉過頭對湘靈說道:「你怎麼不阻止他,你別怕,有什麽事情,有我替你出頭。」
「我不是你的媳婦,老爺!」湘靈冷靜的囘答。
「胡老伯,她是我的老婆。」偉民插進來說道。
「你親口對我說,她是你的妹妹,怎麼現在又是你的老婆?你們可別把我當着三歲孩子!」
「爸爸,他們的確是兩夫妻來的,不過想在我們家裏做工,所以騙了你是兩兄妹。」惠仁向他父親解釋。
「那麽那孩子是不是你的?」
「不是,我騙了媽,是爲了使她不把阿靈趕走。」
「吓,你把老子氣死了,現在所有親戚朋友都知道我今天請抱孫滿月酒,你說我有什麽面目去見人?」胡塗氣咻咻的說道。
「胡老伯,這次阿仁這樣做全是爲了朋友的原故—— 就算親友知道也會原諒的。」偉民溫聲和氣說,接着他催着司儀:「陳經理,請你請主婚人入席簽名啦!」
司儀於是叫道:「新郞主婚人入席。」
來賓狂笑鼓掌,胡塗經不起別人催請,終於在証婚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胡塗」。
「先生,這張是證婚書,你怎麼好在上面寫下「胡塗」;請你簽好它,胡先生!」司儀以爲胡塗心裏不滿,在証婚書上亂寫。
「要怎末簽才對呢?」胡塗感到不明白。
「請簽閣下大名。」
「我的名就是胡塗!」
「先生,你就是胡塗嗎?」司儀很奇怪。
「你說我是不是胡塗呀?」
「那我可不知道。」司儀接着向偉民問道:「是不是呀,何先生?」
「不錯,他是胡塗。」
「我不是胡塗,怎麽又會這樣胡塗呢?」
胡塗這句話,引得全場的人都大笑起來。
(完)
「艶福齊天」定期開鏡
香港大成影片公司籌備進行拍攝之新片「艶福齊天」業經定期三月十日在南洋片場開鏡 ,「艶福齊天」爲名導演蔣偉光編導,全劇極富輕鬆情調,笑料新穎繁多,以播音台作背景,主角芳艶芬,周坤玲同飾名滿播音界之一雙姊妹花,張活游即爲追求芳姐之小職員,芳姐及周坤玲旣係播音歌星身份,故先後合唱歌曲甚多,中有賣吻歌爲最香艶者。
又該片陣容,原已充實,但大成主腦人,素以眞材實料爲旨,故最近復重金聘請諧劇大王鄧寄塵加盟演出,而配上諧角伊秋水,劉桂康,歐陽儉三位典型招笑人物,更覺錦上添花,倍加熱鬧,他日公映,必能哄動一時也
諧劇大王鄧寄塵加盟。
呷錯醋
電影小說
金馬
一
鄕鎮郊外,一眼望去,阡陌相連。空中正盪漾着一陣悅耳的歌聲,這是從小巷一間舊屋傳出來的。
音樂家何偉民在拉着梵鈴,他的妻子趙湘靈則拿着曲譜隨着音樂高低抑揚的唱着,引得許多鄕民在門外圍着聚聽。
一曲終了,何偉民夫婦不知不覺中竟互相拍手叫好。
「民哥,你拍手做什麼呀?」湘靈笑着問道。
「贊你唱得好囉,那麼,你又拍手做什麼呀?」偉民囘答了,又問道。
「我也是贊你呀!」湘靈挨近他說:「玩梵玲玩得多好囉!」
他們快樂的互相擁抱起來,門外的鄕民看見他們這般親暱的樣子,感到好笑!
笑聲把湘靈從偉民的懷抱中驚醒,她推開了他,示意門外說道:「別這樣,你看門外這麼多人」。
偉民看看門外,他放開手笑着,不敢再動了。
而這時,收租人三叔却匆匆的走進人羣中,大聲的嚷道:「喂喂,走開走開,你們在這裏幹什麼,」有猪肉分嗎? 走走!」她一面揚手逐開衆人,一面走進屋子。
「看他這副怪相,眞叫人討厭!」不知誰在背後駡了一聲。
三叔耳尖,聽見有人罵她,囘頭厲聲責問道:「吓!誰說我叫人討厭?我怎樣叫人討厭?」
鄕民們看他這情形,大家一哄而散了。
屋裏偉民不知道三叔進來,拿着梵鈴對湘靈說道:「來,再唱一次⋯⋯」
「哦,這麽快活呀,又彈又唱!」三叔冷諷熱嘲的說。
「三叔!」湘靈向她打了招呼。
「三叔,怎末你來了,有什麽事呀?」偉民驚異的問他。
「你以爲我來聽你們唱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嗎?」三叔拉長着臉說:「來收租啦,欠了這麽久,怎末樣呀?」
「三叔,請你再寬限幾天。亞民哥還沒有事做,實在沒有錢。」湘靈向他要求。
「三叔,現在沒有錢,再寬限幾天吧!」偉民亦求着說。
「你們總說沒有錢,成日發癲發狂,拉琴唱歌,難道老天會掉下錢來給你們嗎?」三叔扳起面孔來。
「三叔,拉琴唱歌都是我們的職業啦!」偉民解釋道。
「職業,看你們這副窮相,幹這行的,你以爲還會發達嗎?古言說,財不入唱門,越拉越緊,把你們 窮死啦!」
「喂,三叔,我只不過欠你房租,你不能夠這樣亂詆毀我!」偉民有些憤怒。
「我要講,你掩得住我的口?哼!要爭氣,立卽交下租來呀!」三叔的口氣惡狠狠地。
「哼!⋯⋯」偉民憤怒極了,像要爆發的火山。
「民哥,你⋯⋯」湘靈急拉住他,制止他發火。
「怎樣?我吿訴你,最多這次賞你們臉,下次再不交租,我就請你們滾蛋!」三叔似乎有點怕偉民發 火,祗好剛中帶軟的,說完就走了。
「哼,一個人窮了就叫人看不去。」偉民拿起梵鈴,自言自語着:「說我越拉越緊,財不入唱門?」
「民哥,你別這樣,慢慢想個辦法。」湘靈安慰他。
「好,我以後再不玩這個梵鈴了!」偉民說着,發狂似的走近窗前。
「民哥——」湘靈急追上來。但她來不及了,偉民在極度悲憤中,將梵鈴擲出窗外。
偉民的朋友胡惠仁畢業囘來正要來找他,梵鈴恰巧掉在他面前,嚇了他一跳:「咦!這是搞什麼呀?」他俯下身拾起被摔壞了的梵鈴,表示很可惜:「幹嗎這樣浪費呀?」
湘靈一眼看見他:「哦,胡先生,你囘來了!請進來坐 。」
「好好。」惠仁拿着梵鈴走進去。
「請用茶,胡先生。」湘靈奉茶招待客人。
「哦,謝謝,」惠仁接着問道:「喂,你們幹嗎這樣浪費,將一個梵鈴丟了,耍花槍也不必這樣呀,而且這個梵鈴,你不是把它當着生命寶貝看嗎?」最後他向偉民說道。
「唉,你不知道,總之是受不了氣!」偉民煩燥的囘答。
「難道是同亞嫂鬥氣了?不會吧,你們素來是如膠似漆的這麽好。」
「不,民哥一時發了脾氣!」湘靈解釋道。
「什麽事呀?」
「哼,總是自己窮,不爭氣,連收租公都看不起。」偉民自艾自怨起來,接着說道:「惠仁兄,你知道的,我沒事做這麼久了,那裏有錢還他呢!」
「那麽就遲點還他好了。」惠仁寬慰着他。
「他跟你這麽講就好了。我沒錢還他,他亂詆毀我,又說什麼財不入唱門,我們幹這一行的,越扯越緊,一世都出不了頭。你說氣不氣?」
「哦,是這樣嗎,那你也不必氣了。」惠仁還是寬慰他 :「得啦 明天我替你想個辦法還他。」
「這怎末好意思。」
「沒問題,大家都是老朋友,有什麽計較。我現在囘家去看看父母先,明天再來跟你談。 」惠仁立起身來。
「那麽,明天請你一定來。」 偉民也跟着站起來。
「我一定來,你們不必担心。 」說着,惠仁向他們吿辭了。
送走客人後,湘靈對偉民說道:「哪,這一來可不必担心了,民哥。」
偉民沒有囘答她,靜靜地又坐在一張櫈子上去。
「民哥,胡先生都肯替我們交租了,你爲什麽又這樣發悶呢?」湘靈走過來,關切的問道。
「靈妹,我平生最喜歡的就是音樂和作曲,所以我用盡苦心去做,希望成爲一件事業,那兒知道一無發展,而且還要受人奚落!」偉民感到很失意。
「你不要灰心,民哥,今天雖然是受人奚落,但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我相信總有成功的一天,民哥,你放心啦,民哥,來,你敎我唱那支連環相思債吧!」湘靈鼓勵着他,把他從櫈子上拉起來,走到寫字台去拿曲譜。
二
胡惠仁囘家來,一進門正遇着女佣人亞三,她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拿着手巾揩眼淚。
「大少,你囘來了!」亞三招呼道。
「是的,你拿了包袱上哪兒去呀?」惠仁奇怪的問她。
「我走了,大少!」
「做得好好的,爲什麼要走?」
「奶奶把我辭掉了。」亞三很委曲的樣子。
「爲什麽奶奶要辭掉你?」惠仁不明白。
「我怎麽知道?大少,我走了!」亞三提着包袱 ,心裏難過的走了。
惠仁走進大廳,他父親胡塗在一邊抽烟,母親則負氣的坐在另一邊,惠仁走上去向他們個老人家招呼 道:「爸爸,媽媽。」
「亞仁,你囘來了。」胡奶奶臉上有了一些笑容。
「爸爸,爲什麽把亞三辭掉了?」恵仁向他父親問道。
「怎末知道你媽呀!」胡塗帶着不高興的口氣說道。
「哼,還說怎未知道我。」胡奶奶負氣地截斷道:「成天掛住同亞三拉拉扯扯,人家是有丈夫的,我就怕他搞出事情,才把她辭了。」
「你別聽她亂講,我幾十歲的人了,那有這麽糊塗呢,分明是她心地窄吃乾醋!」胡塗紅着臉爭辯。 「心地窄!你有條尾巴我都知道!」胡奶奶大聲吆喝。
「你把我當狗啦?有條尾!」
「媽,我們沒有人打理家庭,不是不方便嗎!」惠仁見父親和母親在鬥嘴,便改換話題問道。
「沒有人,再請一個。」胡奶奶覺得這事情很簡單。
「你請工人有這麽容易?疑三疑四的!」胡塗的話像支冷箭。
「我有分數,不嫁人的我就請,有了丈夫的我就不請, 你不愛名譽,我可愛呀!」胡奶奶很有把握的樣子。
「你怎末說都行,橫直口是你的。」
「你知道就好。」胡奶奶自覺勝利, 她轉向惠仁說道: 「亞仁,你囘來正好。」
「有什麼事嗎?」惠仁覺得母親說得很突然。
「我知道你這次畢業了,所以托人找個門當戶對的小姐配親,現在媒婆已有了囘音,祗等你囘來看看喜歡不喜歡。」
「那不用看了,媽!」
「爲什麽?」胡奶奶不禁很焦急。
「我已經有了⋯⋯」
「哪,你不必怕沒有媳婦服侍你!」胡塗的一肚子氣好像還未洩完。
「亞仁,娶老婆不同別的事情,你有沒有查明她的家世呀?」胡奶奶不放心。
「怎未還不知道, 以前是我的同學。」
「她肯囘來鄕下住嗎?」胡奶奶追問着。
「當然肯跟我囘來 。」
「肯囘來鄕下住就好。」胡奶奶放下心。接着向胡塗問道:「你贊成不贊成 ?」
「全由你主意,我沒有問題。 」胡塗愛理不理的樣子。
「不過,爸爸,她要我給她三千元,才肯與我結婚。」惠仁對這問題不免要覺得困難。
「要三千元?」胡塗驚訝問道:「喂,我們是娶媳婦,不要買媳婦的呀!」
「不錯,亞仁,爲什麽要三千元這麽多呢?」胡奶奶附和丈夫說道。
「還要問,我看這一定是不三不四的女子。」胡塗斬釘截鐵的斷定着。
「不呀,爸爸,她要錢是有理由的。」惠仁急說道。
「有理由,那就是刮錢的理由了。」
「不,爸爸,因爲她父親臨死的時候,欠了人家三千元,所以她母親要這筆欵還人家。」
「分明是借辭,那裏有嫁女還債的?你受人欺詐,我却不上當!」胡塗口氣很堅强。
「亞仁,還是好好地聽我替你找一個吧。」胡奶奶勸着說。
「媽,你叫我這樣盲婚,我實在做不到而且我又答應了她。」惠仁不贊同他母親的意見。
「你答應是你的事,要我給三千元,做不到!」 胡塗堅决地不答應兒子的要求。
惠仁聽了父親這番話,不再出聲的憤然囘到自己房中,焦急的踱着,忽然坐到寫字枱前,執起筆寫信 。寫後自己讀着:
「白雪妹:」他情不自禁的吻了一下信紙:「我離開你一分鐘,好似離開你一百年這樣難過。我覺得我的心永遠在你身邊一樣,關於我們結婚的事情,我爸爸已經答應,不過,那三千元,暫時不能給你,請你耐心等候,我一定設法,我的心都很急,你需要這筆錢卽是我需要一樣,雪妹,卽使海枯石爛,我永遠愛你! 」讀完信,寫好了地址,他又在皮挾內拿出白雪的照片,甜蜜的在它上面吻了一下。
三
白雪和女友從書檔買了幾本歌集囘家,幾個女友圍住她坐下,聽她唱歌,剛唱完一曲,她母親拿了一封信給她:
「亞雪,別唱啦,你的亞仁哥有信寄給你呀!」
白雪歡喜的接信:「仁哥有信來啦,給我。」
「哎呀,看你這樣心急。」她母親取笑她。
「情書來的呀!」
「公開!公開!」
大家擁上前圍住白雪,白雪把信舉得高高的,像一個快樂的天使一樣跳上櫈上,然後折信讀着,當她讀完信時,她的笑容盡歛了,心情沉重地從櫈上下來。
「什麽事呀?雪姐!」
「信說什麽,怎麽你看了不高興!」
女友們關心的問着。
白雪默不作聲。她母親上前問道:「亜雪,信究竟講什麽呀?」
「仁哥說他爸爸已經答應了,不過三千元一時不能給我們,叫我們等一個時候。」白雪悒不樂的囘答。
「是不是呢,我都說過他沒辦法,三千元,可不是容易找呀。」她母親帶着輕蔑的口氣說道。
「媽,我相信仁哥對我很好,一定不會失信的,我們就再等個時候吧。」白雪依然對惠仁懷着希望。
「你別這樣傻了,聽他的話等到什麽時候,等到來老了,還是讓我替你找個有錢的人結婚,還了這筆債。」
「不!媽!無論怎樣我都要等他!」白雪要求她母親。
「吓,笑話,那不必還錢給你世伯了?」她母親不以爲然的說。
「世伯的錢,我同他講,慢慢的還給他,我一定要等仁哥的消息!」白雪對惠仁還是一片痴心。
「就算不必還債,但是我們還要生活呀!」
「怕什麽,我不會去找工作做嗎?」白雪自有打算。
「不用怕,伯母!慢慢的想辦法好了!」女友們也幫助白雪向她母親勸道。
「唉!我不明白你怎麼會這樣死心亞仁?」白雪的母親對自己的女兒還是不很同情。
四
這一天,三叔帶了兩個挑伕來到偉民家裏,聲勢兇兇地:「喂,怎麽樣?今天的租錢給不給得出呀?」
「三叔,你別迫人太甚哦,你不用担憂我沒租錢給你。」偉民看到三叔那種兇狠的態度,心裏確實有 些憤恨。
「這麽說你又不給了?」
「急什麽呀,等一下我朋友來就給你!」
「我管不了這許多,要給就快點給,不給就快點搬!」
「請你等一等,三叔,別怕沒錢給你呀!」湘靈忍氣地說道:
然而三叔依然不肯罷休,她一定要偉民立卽交出租錢,因此大家喧鬧起來,就在這時候,惠仁來了。 「喂喂,什麽事呀,鬧成這樣?」惠仁向大家問道。
「又來趕搬啦。」湘靈第一個囘答。
「趕搬?怎麼一點人情都不講?」惠仁也覺得三叔太不講情了。
「不給租,我當然要趕!」三叔依舊沒有好聲的說。
「哦,爲了欠租嗎?那也不必趕得這麽緊!」
「笑話,不必趕得緊,那就錢來呀,不然,你替他們給呀!」三叔向惠仁伸出一隻手。
這簡直對惠仁是一種侮辱,他爭氣地要掏錢還他,可是袋子是空的,他感到很失意。
三叔看在眼裏:「怎樣?沒有錢就不要學人講大話啊!」
惠仁忍受不了,他毅然脫下手錶給他:「就用這隻錶作數,好嗎?」
三叔接着手錶審視一番:「手錶呀,也好,就算你的! 」說完,他得意的笑着,走出去了。
「亞仁,你怎麼給他手錶呢?你沒有錢嗎?」偉民奇異的問道。
「唉,因爲我愛上了一個女子,想同她結婚,但需要三千元,這樣我同我父親鬧了,他不但不答應,還要叫我和這個女子斷絕來往,現在他一分錢都不給我,禁止我再去香港,迫我離開這個女子。」惠仁有所痛苦的解釋着。
「亞仁,你這樣幫我忙,我太感激你了。」偉民不禁說道.
「是的,眞過意不去,胡先生!」湘靈也用感激的眼光望住惠仁。
惠仁並不計較這些,他反而替偉民日後生活躭心,最後他贊成偉民到香港去找點事情做,不過偉民却爲了旅費和湘靈的問題感到困難。
「民哥,你不必替我担心,如果你去找事情做,我也可以在這替人家做工,這樣你不是可以安心啦。」湘靈也贊同偉民到香港去。
「誰會請你呢?你又做不慣,而且這裏找工作也不是容易。」偉民仍覺得有難題。
「正好我家裏要請人,如果亞嫂不見嫌,就到我家裏去做先。」惠仁想起家裏沒用僕人,善意的說道。
「好呀,民哥,我到胡先生那裏做工,你不就可安心啦!」湘靈認爲這機會太好了。
「不過我母親說過,要請不出嫁的女子。」惠仁補充道。
「我就承認我不出嫁不就行嗎,你母親又不認得我。」
「如果這樣,我還可以同我父親商量, 先借旅費給你, 然後才在亞嫂的工錢中扣下,相信我父親會答應的。」
「能這樣更好。」偉民不再感到有困難了。
「好,我們現在到我家裏去,你們假認爲兄妹,我就有辦法向我父親借錢。」
於是惠仁帶了偉民夫婦到家裏來了。他先到書房裏找他父親:「爸爸,我有個朋友,想來借二百元, 爸爸,你借給他好嗎?」
「吓,枉你是我的兒子,你不知道你爸爸的脾氣 ,一向是賒借免問的!」胡塗最怕聽見借錢。
「我知道。」
「你知道還要問什麼?」
「不過他是我的朋友,想借點旅費到香港去找工作,所以才敢開口。」
「好朋友又怎樣?總之,借錢就不行。你知道嗎?借給人容易,叫人還就難。還算你這麽大了,眞是白吃了米。」
「不,爸爸,他還有條件向你借。」惠仁把「條件」兩字說得特別重。
「有什麽條件?」胡塗登時睜大了眼睛。
「他有個妹妹,我想叫她在這裏做工,以她的工錢來還債,這樣就不怕他欠了,而且我和他又是好朋 友,爸爸,你幫下他的忙吧。」惠仁誠懇的說道。
「他的妹妹嫁人了嗎?」胡塗似乎對這條件有了興趣。
「還沒有,今年最多十八九歲哩。」
「哦,她生得怎樣?」胡塗的興趣濃起來了。
「很漂亮,兩兄妹現在就在客廳裏,你出去看看。」惠仁覺得自己的計劃有了八九成了。
「好,我同你去見見她,如果合意的,就有得商量。」胡塗心裏另有一種希望。
惠仁帶了他父親來到客廳裏,替偉民和湘靈介紹,胡塗嘴裏「哦,哦,」的點着頭,兩隻眼晴却很貪婪的瞪住湘靈,使湘靈不免感到有些羞澀。
「你們倆是兄妹嗎?」胡塗的眼睛一刻也不離湘靈。
「是的,胡先生,」偉民囘答道。
「你還未嫁嗎?」胡塗望一眼偉民,囘過頭去就對湘靈問道。
「⋯⋯⋯⋯」湘靈畏羞的沒有作答。
「還沒有,我不是已經說給爸爸聽了。」還是惠仁替湘靈囘答道。
「我都要問個明白,你知道你媽媽,她是要沒有嫁人的 。」
「我是還沒有嫁人,胡老爺!」湘靈鼓着勇氣說了。
「好極了!」胡塗心裏一陣快樂:「你哥哥想出城去找工作嗎?」
「是的,老爺,請你幫忙幫忙!」湘靈帶着要求的口吻說。
「不成問題,不成問題!」胡塗連聲說道:「我一向都好商量。」他囘頭向偉民問道:「你是想借二百元嗎?」
「不錯,胡老先生,這筆錢等我找到工作就還你,明天我就要起程了。」偉民囘答說。
「不忙不忙,祗要你妹妹在這裏做一年工,還不還,都沒問題。」胡塗心裏當然有數:「現在就先給你錢。」他一面拿出錢,一面向湘靈說道:「最好你快來上工。」
「老爺,不過我妹妹不大會做工⋯⋯⋯⋯」偉民說道,他話還沒說完,胡塗却搶着說:
「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敎她的,不會慢慢學好了,你放心!」
接着偉民和湘靈向胡塗吿辭了,胡塗一直望住湘靈的背影,他忘形的涎着臉瞪住。惠仁看得在旁偷笑。
「你笑什麽?」胡塗見兒子在笑,有點羞愧。
「沒什麽。」惠仁收歛了笑容。
「等下你媽媽囘來,你就說這工人是你中意的,千萬別說我看合意,你知道你媽媽好像開醬園舖一樣,一埕埕的都是醋!」胡塗再三的叮囑兒子。
五
晚上,湘靈在家裹替偉民收拾一切,她將一本「呷錯醋 」的曲本裝到衣箱裏去。偉民看見這曲本,感慨萬端的說道:「枉費我幾年心血寫成這部曲,結果如此。」
「民哥,你別灰心,這裏沒有人賞識,或許到城市就一曲成名都說不定,本來萬事都是講機會。」湘 靈安慰他,叫他早點休息,以便明早動身。
「今晚怎睡得着。」偉民悒悒不樂地走到窗前。
「⋯⋯⋯⋯」湘靈一時找不到話再安慰他,因爲她自己也和偉民一樣爲了這次別離而難過,不禁掉下眼淚了。
「靈妹,你怎麽哭了?」偉民走過來,拉住她的手。
「不,我沒哭。」湘靈强笑着,她不想引起偉民更大的傷感。
「靈妹,你別騙我,我想我還是不去。」
「你不去?」
「嗯,因爲我們從來未曾離開過,這次離開不但你傷心,我實在也萬分捨不得你,靈妹!」
「民哥,我知道我們的心情一樣,不願離開,不過因爲環境,同時爲了你的前途,民哥,我們不能不 離開。」湘靈壓住心底的痛苦說:「我只希望你向前奮鬥,得囘離別痛苦的代價!」
「我當然會向前掙扎,不過留下你一個人在這裏 ,你又未曾出去做過工,怎樣受得人家的氣,所以我 實在不能安心。」
「你別這麼想,這不過是暫時的事。你出去一找到錢,我們不是可以從新組織新家庭了,你說那時我 們多快活呀!」湘靈勉强的安慰偉民。
偉民沒有做聲,他像是在痛苦的深淵裏看見了美麗的遠景。
「現在夜了,我們早點睡吧,明天一早你就要上車。」 說着湘靈拉了偉民,兩人緊緊的相偎着,走到床前⋯⋯⋯⋯
六
偉民到了香港,一切希望都落空,他以前的朋友們都不知去向了,生活日漸困難,最後他不得不搬到大王廟道陋屋裏租了一個床位挨下。
同住在一起都是一般在生活綫上掙扎着的勞苦工人,第一天搬來,偉民就認識了阿壽,當他們在閒談時,包租婆在通知一個女工阿娥說她的租錢明天就到期了,要她別忘記。 阿壽聽了不順耳,講了她一句,引得她過來嚕囌一陣:「 笑話,到期收租,我有什麼不對?吿訴你,後天你也到期了, 別說我沒通知你!」
偉民看了這情形,不覺感到世態淡凉,深深的歎了口氣後,拿起信紙寫信給湘靈:
「靈妹,我已經平安抵港了,你不必掛念我,不過這次到香港,令我非常失望,因爲我所有的朋友,一個都找不到,現在大王廟道十二號租了一張床位住,等我找到工作,再通知你。你好嗎?希望你多給我來信,以免我渴望⋯⋯⋯⋯ 」寫完,他將信寄出去了。
湘靈收到這信,偷偷的在花園讀着,心裏一陣難過。胡塗不知在什麽時候也到花園來,他當着湘靈在看情書,於是借歌諷剌。甚至上前與湘靈糾纏,死拉住她的手。
「老爺,請別這樣,給奶奶看了不好。」湖靈慌張的推開他,拿起洒花桶預備繼續她的工作。
「別怕,奶奶不在屋,出去了。」胡塗又伸手去拉。
「不,老爺!」湘靈極力拒絕他。
惠仁忽然走來,看了這情形,便奔向前替湘靈解圍:「爸爸!」
「甚麽事情?」胡塗大不滿意的喝道。
「沒事情。」惠仁支吾着。
「沒事情,到這裏幹甚麼?去,去!」胡塗悻然的驅着惠仁。但他沒想到後面却來了胡奶奶:
「你們都到花園裏來做甚麽?」
「沒甚麽,來走走。」胡塗嘻笑着臉。
「阿靈,倒水給我冲凉。」胡奶奶轉過頭對湘靈說道。
「哦 」湘靈應聲放下洒花桶去了。
「還不進去,呆在這兒做甚麼?」胡奶奶心裏一直對胡塗猜疑着。
「是呀,還呆在這兒做甚麽?進去呀!」胡塗假傻的附和着向惠仁帶罵的說道。
「我說的是你呀!」胡奶奶指着胡塗大聲吼道。
「好好,進去就進去!」胡塗祗好向屋裏走去了。
晚上,胡塗躺在牀上,不能入睡,心裏癢癢的掛念着湘靈。他想下樓到工人房找湘靈,但又怕睡在身邊的「雌老虎 」發覺。
而這時,湘靈正在房裏理頭寫信給偉民,忽然惠仁匆忙推門進來。
「這麽夜了還沒睡,胡先生!」湘靈抬頭問道。
「對不起,我想知道阿民兄的地址,有時候想寫信問候他。」惠仁向她說明來意。
「我就拿給你。」說着,湘靈拿了一封拆開的信交給他 :「這封信是他寄來的,你看吧,胡先生!」
惠民看了信,抄了地址,然後以安慰的口吻說道:「阿嫂,你早點休息,阿民兄遲早會找到工做的,你不必担心。」
「謝謝你,胡先生,你也早睡吧!」
「好!」惠仁向湘靈吿辭,當他走出房時,忽看見他父親下樓來,他連忙縮囘房去。
胡塗輕手轉脚的摸索着從樓上下來,他怕弄醒了胡奶奶 ,然而胡奶奶早已在他背後尾隨着,他一點也不知道。
「阿嫂,爸爸下樓來了,不知道是不是要到你這兒來? 」惠仁心裏替湘靈焦急。
惠民立卽替她想了一個辦法⋯⋯⋯⋯
胡塗小心翼翼地推開房門,看見牀上睡着人,把皮毡蒙住頭睡着,他想,這一定是湘靈了,於是喜洋洋的躡手躡脚地走到牀前,低聲喚道:「阿靈,阿靈,怎麽這樣好睡啦——」
忽然皮毡被揭開,接着是一聲:「爸爸!」
胡塗定晴一看,原來是惠仁,又驚又氣:「你到這兒來幹嗎?」
「那你又走到這兒幹嗎?」背後傳來女聲,這聲音使他心驚肉跳,他看見胡奶奶站在面前。
「我是來找亞仁!」胡塗慌張地答道。
「你不必亂扯,你以爲我睡了,鬼鬼祟祟地就下樓來! 」胡奶奶眼睛在冒火。接着,她喚着湘靈。
湘靈忽然從床底下攢出來。
「你怎麽躱在床底下?」胡奶奶奇異的問道。
「大少爺看見老爺要到這兒來,進來吿訴我,他就在床上倒下,我祗好躱到床底下去。」湘靈囘答道。
「以後老爺再到你這兒來,你不必躱到床下去,有事你叫我好了,如果你同他一樣發癲,你可別想在這裏工作。」 胡奶奶初警吿湘靈說,隨之,將胡塗吆喝着上樓囘房去了。
七
日子如流水般過去,一下子已有半年了。偉民已跟着阿壽到打石塲做苦工。
這一天,偉民打工已打得十分辛苦,汗流如珠。他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從袋裹拿出湘靈寄給他的信,讀着:
「民哥,我們分別後,不知不覺已有大半年了,像你這樣的身體,做這樣粗重工作,對於你的健康,我非常担憂, 不過,爲了生活,我們不得不掙扎,我祗希望我們能早日渡過這難關,而謀我們的幸福。民哥!你現在就要做爸爸了,我恐怕你掛心,所以遲遲沒吿訴你。請你早點積貯些錢,讓我到香港來⋯⋯」偉民讀完信,感到心煩意亂起來。
「喂,你坐下來幹嗎?」忽然工頭走過來干涉。
「我不是偷懶,不過有點不舒服,坐下來休息一下。」 偉民見到工頭,有幾分驚懼。
「這兒是工場,你這種人,還是到方便醫院去好吧,以後你不必再來了。」
「管工,我的確不是偷懶,請你原諒我,而且我的女人快生產了,管工,你給個機會使我積貯些錢呀!」偉民苦苦地要求。
「不管你這許多,你跟我來,算工錢給你!」
偉民祗好無可奈何的跟着他走。
偉民失業後,日子又越過越難,他把衣服甚麽的都當光了。最後他把他寫的那本歌曲「呷錯醋」拿到書店求售,書店老板祗出得很低價錢,他無奈何,忍痛接受。
疾病總是跟隨着貧窮。偉民病倒了。阿壽亞娥等人都在爲他焦急。包租婆却叫了兩個咕哩,要把他抬走。
「喂!這不行呀!」
「人家病得這麽要緊,你還好把人家趕走!」阿壽他們看不過來,向包租婆責言道。
「你們好心,送他進醫院去呀!我不能讓他死在這裏!」包租婆反而理直氣壯的說道。
「你怎麽知道他就會死?」亞娥聽得氣憤起來。
「那麼,你敢担保他不會死?」包租婆依舊是鐵心腸。
「我們還是不要跟她多講,早點設法把他送進方便醫院去。」阿壽覺得與包租婆直吵,對偉民幷沒有好處。「好的,好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於是偉民被送進方便醫院求醫,看護婦忙着替他檢驗熱度。他昏迷不醒的痛苦呻吟,不停的喚着湘靈的名字:「阿靈——阿靈——阿靈——」
八
事有更不幸,湘靈因爲有孕,加上操勞過度,也病在床上不起,她憶及偉民,遂在枕頭底拿出偉民的信來讀:
「靈妹:以前我有病,總有你在身邊,現在我有病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你說,我該感到多凄凉!多痛苦呢,靈妹⋯⋯⋯」湘靈讀到這裏,她壓不住自己的痛苦,流下淚哭了,嘴裏輕輕的叫着:「民哥,民哥⋯⋯」
胡奶奶這時從天井走過,看見一桶濕衣沒人洗:「哼!阿靈到那兒去了?連衫都不洗。」她自語着,大聲喚着湘靈 :「阿靈!阿靈!」
沒好囘聲,也看不到人影,胡奶奶不免要生氣了:「哼 ,一定偷懶睡覺去了!」她不肯罷休的向工人房走去。
湘靈正睡在床中,感懷身世,十分悲楚。但胡奶奶管不了這許多,一進房來就嚷道:「喂,你躱在這裏偷懶啦?我不是請你來睡覺呀!」
湘靈聽見聲音一怔,勉强支起身來:「奶奶,我不是偷懶,我身體不大舒服,所以休息一下。」
「現在外面一大桶衣服,那你叫誰來洗?」胡奶奶不悅的說道。
「哦,我就去洗,奶奶!」湘靈看見胡奶奶一臉不悅的神氣,她勉强扶病到天井去洗衣,脚步浮浮的走近洗衣盆, 她坐下來,拿起衣服洗了幾下,卽感到辛苦不堪,眼淚奪眶而出,從她臉頰上流下來。她想起當天與偉民分別時的情形,想起了偉民對她說的話:「靈妹,我從來未離開你,我怎樣捨得放下你呢?你出去做工,好辛苦,你怎樣挨得起,做工要受人家的氣⋯⋯」想到這裏,她愈覺辛苦,她再支持不住了,突然昏倒在地上。
幸而惠仁在外面進來,急忙過來把湘靈抱起:「 阿嫂!阿嫂!」湘靈還不醒過來,惠仁急得驚叫:「 救命呀!救命呀!你們快出來!」
胡塗和胡奶奶聞聲,慌慌張張地趕來:「什麼事 ,什麽事?」
「亞靈昏過去了!」
「哎呀!怎麼辦!」胡奶奶也有些焦急:「亞仁 ,你快點去請醫生來!快去!快去!」
惠仁請醫生的時候,湘靈已被抬囘睡在她牀上了 ,她已經醒了。
當醫生替她診視後,胡塗和胡奶奶先後問道:「 怎樣?要緊嗎?醫生!」
「沒有事情,等我出去開條藥方她吃。」醫生微笑着說。
「醫生,她究竟是什麽病呀?」胡奶奶等醫生開完藥方後,問道。
「她有喜了,不好讓她勞動太多,應該休息一下 。」醫生回答道。
大家聽了都顯得很詫異,胡塗不信的說道:「不是罷,她還是個女子!」
胡奶奶却裝得鎭定向醫生說了一句:「謝謝你, 醫生!」
「吓!這就奇怪了,亞靈沒嫁人,怎末會有喜呢 ?奇怪!」醫生走後,胡塗莫明其妙的說道。 「奇奇奇,奇什麼?哼,你自己知道!」胡奶奶頓時醋勁大發。
「呀,我知道,我知道什麽呀!」胡塗覺得很寃枉。
「你不知道,我就要你知道。」說完,胡奶奶憤然向湘靈的睡房走去。胡塗和惠仁跟在她後面。惠仁的面上露着不安的臉色。
「喂,醫生說你有了身孕,是不是跟老爺有的,你說! 」胡奶奶氣憤憤的向湘靈問道。
「不是呀,奶奶!」湘靈爭辯着。
「不是?」胡奶奶一把拉起湘靈:「你要照實說,是不是?」
「不是呀,奶奶!」湘靈流着淚,她不知應該怎麽說才好。
「不是,是誰?」胡奶奶追問着:「你不說來,你就即刻離開這裏!」
「奶奶,你可憐我,我哥哥在香港,又有病,又沒錢寄來,你趕我走,我上那兒去?」湘靈苦求着。
「你講呀,你講出來我就不呌你走,不然你就立刻離開這裏!」
湘靈還是講不出來。
「是不是老爺,死鬼?」胡奶奶冒火了。
「我都說過了,不是老爺!」
「不是,還有誰?好,你們倆都死口不認,不給點利害你看不行!」胡奶奶猛拉着湘靈下牀。
「奶奶可憐可憐我呀!奶奶!」湘靈掙扎着。
惠仁看得很難過,臉上露着憂容,胡塗以爲這事情是他做出來的,爲了要表白自己,便向他說道: 「喂,的確不是我呀,實在是不是你,如果是就好講出來咯!別連累人啦!」
惠仁為了使湘靈免得再吃苦頭,一時承認道:「是我!」
「是你!」胡奶奶驚問道。
「是的,媽!」
胡奶奶立卽轉怒爲喜,忙扶着湘靈睡囘床上去。
「哪,現在明白了,是不是我呀?」胡塗惡聲的說着,悻然的走出去。
「阿仁,你跟我出來!」胡奶奶叫惠仁跟她出去。
胡塗在客廳上徘徊着,心裏恨着自己的兒子搶去了湘靈 。當他看見惠仁出來,劈頭就罵道:「哼,你這小雜種竟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了,你要氣死你父親啦?我問你現在怎樣安置人家?」
惠仁啞口無言,任他父親罵着。
「現在米已成飯了,還有什麽辦法,揀個好日子,叫他們兩個拜過祖先,不就算了。」胡奶奶褊袒着兒子。
「拜祖先,不,媽媽!」惠仁急忙說道。
「怎麽不可以,我就叫人看個好日子!」胡奶奶决定的說。
「哼!你現在只想娶媳婦,把一切都忘了?」胡塗帶着報復的口氣說道。
「什麽事?」胡奶奶不明白的問。
「什麽事?我和工人講句話,你就說三說四,什麽名譽體面,現在你却不顧名譽體面了?你知道,鄕下這個地方最忌的就是未結婚就這樣,給人家知道,一世就叫人講閒話,你可忘了?」胡塗一本正經起來。
「是呀,這可怎麽辦?」胡奶奶也覺得很對:「 可是畢竟還是自己的骨肉,你還是想個辦法安置他們 。」
胡塗想了想:「叫他們兩人先到香港住住,等孩子生了才囘來拜祖先。」
「也好,可是叫他們住到什麼地方去!」
「到世叔那兒住好了。孩子生了,做滿月的時候,我就跟你出去,這樣你就笑了!」
胡奶奶的確眼開眉笑:「好好,阿仁,我同你進去對阿靈說。」
湘靈一直倒在床上流淚,想着偉民,想到自己的遭遇,心裏像給萬刀碎割一般難過痛苦。
「你不要哭,不然要哭壞身體,我現在决定娶你做媳婦了。」胡奶奶坐在床邊安慰她。
「不,不行,奶奶!」湘靈又感到多一層痛苦。
「就這樣吧,阿靈,爸爸叫我們到香港去,等你生產了才囘來拜祖先。」惠仁連忙插嘴說,他知道他 這些話會使湘靈放心。
「是呀!」胡奶奶高興的說:「等你病好了,就同亞仁到香港去,免得給人知道了恥笑。」
「喂,你也做過年靑人啦,老呆在這裏做什麽,出來吧!」胡塗站在房門口對胡奶奶叫道。胡奶奶覺 得他言之有理,應該讓兩個年靑人私下談談,於是就跟着胡塗走出房去。
「我知道阿民在香港環境不好,又生病,如果媽把你趕出去,不是使你太難過了,所以我冒認下來,阿嫂,你不會怪我吧?」惠仁輕聲的向湘靈解釋。
「胡先生!」湘靈的聲音充滿着感激:「我怎麽會怪你,這次如果沒有你,我都不知道要怎麽辦。」她不禁又掉下淚哭了。
「你不要傷心,爸爸叫我同你去香港,你不是有機會見到阿民了,好了,你休息下,別哭了。」惠仁安慰着她。
「謝謝你,胡先生!」湘靈感不勝言地說。
九
惠仁和湘靈到香港的這一天,他的世叔張進夫婦親自到車站迎接,帶他們囘到家裏,房間早替他們預備好了,因為事前胡塗曾寫信來通知。
「阿嫂,你有什麼事就叫阿蓮好了。」張進的妻子對湘靈說。阿蓮是她家裏的女僕。
「好。」湘靈聽見她叫「阿嫂」,有些羞澀的樣子。
「阿仁,你爸爸怕阿嫂打扮得不行 叫我們替阿嫂做些新衣裳,有這麽的老爺,眞難得!」張進的妻子望住湘靈和惠仁說着。湘廳因為是僞冒夫妻,唯有支吾的答着。
「好了,你們先休息下。改天我才同你上街做衣裳去, 阿嫂!」張進的妻子說完,就退出房去。
「現在怎樣好呢?胡先生!」湘靈想到要和惠仁同房住下,不免感到為難。
「我們暫時認為夫妻好了,等我去見一見阿民,看他有什麼辦法?」惠仁想不出其他法子。
「你什麽時候去找民哥呢?」湘靈確實很焦急。
「現在我先去看一看我的未婚妻,囘頭我馬上就去找阿民,你在這裏休息下。」惠仁心裏忘不掉白雪。
「你快去快來呀!」湘靈叮囑他。
「好。」惠仁說完,匆匆地走了。
過了好些時候,惠仁失意地囘來。湘靈並沒有注意她喜悅的問道:「胡先生!找到民哥嗎!」
「找到,不過見不到他,」惠仁無精打彩的答。
「見不到他,他到那兒去了?」湘靈頓時心急。
「不知道,同屋的人說他搬走了。」
「搬走?怎麼他沒寫信吿訴我呢?」湘靈感到很驚異。
「這就怪,連同屋的人都不知道他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惠仁囘答說,其實他只問了包租婆。包租婆一聽見偉民這名字就討厭,所以祗囘答一聲「不知道」就算了。
湘靈得不到偉民的下落,不禁悲從中來,伏在桌上哭了。
「阿靈,你別哭,我都同你一樣傷心,我的未婚妻都一樣不知搬到什麽地方去了。阿民現在雖然不知道下落,但是將來一定找得到,可是我的未婚妻可難找了。」惠仁的聲音也很凄凉,他想安慰湘靈,却引得湘靈更加悲痛的哭了。
十
偉民的病已經好了,這一天黃昏時候,他穿着一身襤褸的衣衫,鬚髮蓬亂的由醫院出來,沒精打彩的在路上徬徨的走着。
無意中,他走到公園來,這時候,已是夜晚了,忽然一片歌聲迎面送來,唱的正是他所作的「呷錯醋」主題曲,他奇怪着,一步一步的行前,最後他看到凉亭處圍着許多人在聽歌。
凉亭處便是「天堂花園舞廳」,音樂台上正站着一個女子在唱歌,她就是惠仁一刻也不能忘懷的白雪。
歌聲一陣陣的在空中旋轉着,飄進偉民的耳裡 ——傷感把他佔有了,他頹然的在一張石櫈上坐下。 他想起了當時在鄕下和湘靈和唱的情形⋯⋯不久,歌聲停止了,接着從播音筒傳出一片掌聲,把偉民從追憶中喚醒,他聽見播音筒在報吿:
「各位聽衆,這裏是天堂花園舞廳,鑽石音樂茶座,播音台每日都在這個時候轉播本舞廳的特別歌唱 節目,由歌星楊白雪小姐主唱「呷錯醋」主題曲,請各位留意,現在本節目已經完了,再會!」
偉民感到自己的作品已替人成名,但自己還是潦倒不堪,他無限感慨的從石櫈站起來,走到舞廳門口 ,一幅大廣吿遂進他的眼廉:
天堂花園舞廳鑽石音樂茶座,每日情商禮聘歌唱明星白楊小姐登台主唱名曲「呷錯醋」,撰曲者:何 偉民先生。
偉民看到最後自己的名字,以爲有人竊用他的名,有些憤然,預備進舞廳找楊白雪理論,但被守門所 阻。正在這時候,舞廳陳經理送白雪出來:
「明晚再見!」
「再見,陳經理!」白雪揮了一下手。
「哦,楊小姐!這個人說要找你,你認識他嗎?」守門的指着偉民向白雪問着。
白雪由上至下的看着偉民,他一身號褸衣裳使她誤會是無賴之流,睬也不睬的就要走開。
「楊小姐!」偉民却鼓起勇氣上前喚她。
「你有什麽事?」白雪停下脚步。
「沒什麽,我想見一見何偉民先生!煩你⋯⋯」
「哦,你認識他?先生,你可以帶我去見他嗎?」白雪沒有等偉民說完,却先搶着說了。
「什麼?要我帶你去見他?」
「因爲我還未曾見過他。」
「那爲什麼廣吿上面有他撰曲的名呢?」
「就爲着尊重他,所以每次我唱歌總要有他撰曲的名。」
「哦,原來你這樣好意!」偉民感動的說道。
「先生,你可以介紹我認識他嗎?」白雪認眞的要求着。
「剛才很對不起,楊小姐!」偉民向她陪個不是,然後說道:「我就是何偉民。」
「哦!你就是何先生!」白雪不禁狂喜,呼了一聲:「何先生!」
「剛才我以爲有人假冒我的名,所以才來追究這件事。」偉民解釋道:
「何先生,如不見棄,就請到我家坐坐吧!」
偉民沒有囘絶,隨着白雪上了汽車。
偉民隨白雪來到她家裏。白雪招待他坐下,開始對他說道:「我自從買了這本「呷錯醋」歌曲,天天自己練習。有一次我在播音台播音,我無意中唱了這支歌。那知道播音後 ,人人都說這支歌唱得好,唱片公司請我灌片,播音台請我做長期唱員,現在這支歌,已成爲一支名曲,風行一時,何先生,你安慰嗎?」
「我不但感到安慰,同時我非常感謝楊小姐,你的天生歌喉,替我的作品吐氣揚眉了。」偉民的臉上,再也沒有一點傷感的陰影了。
「何先生 你太客氣了,我這次在社會上有今天的地位 ,都是何先生所賜,所以我每次唱曲,必有何先生原著的名,這一點,算是我不能忘記何先生的功勞。」白雪露着一排皓齒笑道。
「是呀,」白雪的母親插進來說道:「我的阿雪,時時都在想見何先生,甚至登報尋訪。」
「楊小姐,你太偉大了,不但我內心萬分感激,就是一般著作家,對于楊小姐這種行爲,都要欽佩。」
「一個人飮水思源是應該的。」白雪囘答着,忽然問:「對啦,何先生近來境况如何?」
偉民登時慚愧起來:「我一向都在佛山住着。這次想出來找找朋友介紹工作,那知以前的朋友,個個都已經不在這裏了,同時我身體又有病,我才剛由方便醫院出來,我的環境實在不好。」
「何先生,這是一時的不幸遭遇,你不必灰心,以你先生這樣的人材,將來一定有很大的成功!」白雪安慰他說。
「何先生,你現在住在那裏?」白雪的母親問道。
「我本來向人家租了一張床位住着,現在可不知道還有沒有。」
「如果何先生只一個人,那就屈駕在這裏住好哦!」白雪很表同情的說道。
「這太不方便了。」偉民不好意思接受。
「不會的,這裏有空房。」白雪的母親亦挽留着偉民。
「何先生就住下來好了,得空又可以敎敎阿雪唱歌。」白雪的母親又說道,她的態度是十分誠意。 「對了,改天我可以介紹何先生相識各方娛樂界的人,今後不怕沒有機會發展,何先生你說是不是? 」白雪想幫忙偉民找出路。
「能得到楊小姐這樣幫忙,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酬謝才好!」偉民非常感動。
「你是我的恩人,而且又是我的老師,我做子弟的應該替老師効勞,還敢要什麼酬謝。」白雪自己先 認起學生來了,她不讓偉民說話,就向她母親說道: 「媽!何先生剛病好,你帶何先生到房裏去休息吧!」
白雪這一片誠意,偉民感動得不好意思再推辭而且,自己眼前的生活,實在也很成問題,於是就答應住下來。
十一
這一天,偉民約好白雪出去見見各方面娛樂界的人物。他換上了新西裝,打著漂亮的領帶,頭髮梳得 光光的,鬍子也刮得領淨淨。
「阿雪,何先生這件西裝做得眞合身,穿起來整個人不同了,又年靑,又漂亮!」百雪的母親取笑着。 她這些話說得白雪羞答答起來,不自然的對偉民說:
「何先生,我們現在去吧!」
偉民隨着白雪出來,他們先訪問了舞廳,播音台,唱片公司諸經理,大家都表示對偉民很敬仰,滿口請他多多幫忙。
從此,偉民在音樂界漸漸有盛譽,終於紅極一時了。他的新唱片一出來,大家都紛紛爭購。因此各唱片公司,播音台,都忙着拉他簽合同。
現在偉民有了很大的收入,生活也就轉好了,他想起了湘靈,預備囘鄕下帶她出來。
起程之日,白雪親自送他到車站,火車開行時,她熱情的說道:「何先生,早點帶你的太太一齊來呀!」
「好好!」偉民快樂而感激的與她握了握手。「再見! 」白雪看着他走上車⋯⋯⋯⋯
十二
偉民一下火車,就趕往胡家。他敲着胡家大門。他按不住心裏的快樂,臉上露着笑容。
出來開門的是胡塗。
「胡先生!」偉民招呼道。
可是胡塗見他衣冠楚楚,一時想不起是誰,兩道猜疑的眼光一直打量着他。
「胡先生!我是何偉民呀!」偉民提醒了他。
「哦,你是何偉民呀!」胡塗恍然笑道:「你這一身西裝,叫我認不得你了。請進來,請進來!」
偉民進客廳,胡塗客氣地招待:「隨便坐,阿民!」
「不用客氣,胡先生!」偉民囘答,忽然問道:「怎末沒看見阿靈呢?」
「她同阿仁去香港了!」
「去香港了?」偉民很爲詫異。
「是呀,去好久了,他們沒去見你嗎?」
「沒有。」偉民接着奇怪的問道:「怎麼阿靈會同阿仁去香港呢?」
「你的阿靈已嫁給我的阿仁了!」胡塗像在報喜訊似的說道。
偉民嚇然一驚:「吓?你說什麼?胡先生?」
「我說你的妹妹嫁了我的兒子了。」
「嫁了你的兒子?」偉民不相信的問。
「你還不信,你的妹妹就快做媽媽了,我怕在鄉下給人講閒話,所以叫他們兩人到香港去,等你妹妹生產了再囘來拜祖完婚。」
偉民聽胡塗這麽說,頓時憤怒起來。
「也許你妹妹不敢見你,所以到香港沒去找你!」胡塗繼續說道。
「他們住在香港什麽地方?」偉民忍住心頭的氣憤。
「住在九龍花園街一百三十六號。你去見她呀!你妹妹這樣大了,也應該嫁人,而且又嫁給我們阿仁,我相信你一定很滿意。」胡塗似乎還沒有發覺偉民在憤怒。
然而偉民聽着再也不能忍耐了,他突然站起來,一聲也不吿別的走了。
「阿民,阿民!」胡塗莫明其妙,在他背後叫!⋯⋯⋯
偉民懷着一種又悲痛又激憤的心情囘到香港,照着地址找到張進的家來。
「請問這位伯母,胡惠仁是不是住在這裏?」偉民向張進的妻子問道。
「不錯,他現在正送他的女人到醫院去了!」
「吓?正到醫院去?」偉民心更急,他覺得事情越眞了。
「是呀,他的女人就要生小孩了,你是哪位呀,請進來坐坐吧!」張進的妻子誠意的說道。
可是偉民却「哼」了一聲,憤極的走了。
「吓,這種人也有!」張進的妻子對偉民這種態度感到奇怪⋯⋯
夜晚,偉民失意的走進天堂花園舞廳,他向僕役要了酒。當他聽見台上白雪在唱他所撰的歌曲時痛苦 就像音樂的拍子,一下下的擊着他的心,他受不住這痛苦,便以酒澆愁,狂飮起來。
白雪唱完曲後,便到他身邊坐下:「何老師,你來了!」
「嗯!」偉民失意的沒精打彩地應着。
「怎麽沒同何師母來呢?」白雪還未發覺他內心的痛苦。
「師母?——她嫁人了!」偉民顫抖着聲音說,他壓不下心裏的悲痛。
「老師,你是不是喝醉了?」白雪笑着說。
「我沒醉!」
「怎麼你說師母嫁了人?」
「請你別再提她,阿雪!」偉民很覺痛苦,接着解釋道:「因爲我離開鄕下的時候,她就到人家家裏做工,那知我囘去,他已經跟那少爺有了私情!」
「不會吧,老師?」白雪疑信參半。
「不會!他們兩個人已到香港來渡蜜月。而且她已進了醫院就要做媽媽了。」偉民說着,將那大半杯酒一飮而盡。
十三
湘靈進了醫院還未生產,惠仁在房門外徘徊,他等得心裏有些焦急,也感到疲倦,便走至客廳,無意中拿起報紙來看,却給他看到一段廣吿:
「歌園明星楊白雪小姐每晚八時在天堂花園舞廳鑽石音樂茶座播唱名曲「呷錯醋」⋯⋯⋯」
惠仁看完,不禁高興起來,他忘了湘靈要生產,放下報紙就走出醫院,一直到天堂花園舞廳來了。
「這裏是不是有位楊白雪小姐?」惠仁向僕役問道。
「有呀!」僕役囘答。
「對不起,請你通知她一下,說有一位胡惠仁想見她。」
「好,請你等一等。」於是僕役來通知白雪:「楊小姐 ,有位胡惠仁先生想見你。」
「胡惠仁!」白雪聽見這名字非常高興:「你請他到這兒來。」
「怎麽,你認識胡惠仁?」偉民很驚訝的問道。
「是的,我認識他!」
「引誘我老婆就是胡惠仁,不過不知道是不是這個胡惠仁?」偉民不敢斷定。
「哦?」白雪有點疑惑。
這時,惠仁正跟着僕役走來,偉民一眼看見:「就是他!」
「怎麽,就是他?」白雪對惠仁的情感一時崩潰了。她感到一陣憤恨。
惠仁並不知道,一看見她,歡喜欲狂的喚道:「阿雪!」
白雪並不囘答,偉民坐在一邊也一聲不响。
惠仁囘頭突見偉民,他更加高興起來:「呀!阿民,你也在這裏?」
偉民聽見惠仁叫他,他發火了,一掌推開他,怒聲說道 :「不錯,我在這裏!」
惠仁給他一推,差點跌倒地上,但却把隔台的玻璃杯瓶碰摔在地上碎了,引得全塲衆客嘩然起來。
舞廳的陳經理連忙趕來,勸解說道:「有事慢慢講,你們有什麼事呀?」他向偉民問着。
「這個人本來是我同鄕,他騙我老婆到他家做工,乘機佔了我老婆,你說這種人該不該打!」偉民理直氣壯的說道。
「阿民,你怎麽這樣說呀?」惠仁感到寃枉。
「你父親親口對我說的,難道我會寃枉你?」
「這就該打啦!」
「該打!」
「該打!」
衆人聽了都替偉民抱不平,惠仁正要分辯,但他沒有機會,許多人已向他衝來,逼得他從枱底下竄走,但他的頭上已受傷流血了。
惠仁帶傷囘到醫院,看護婦迎頭向他說道:「恭喜,胡先生!」
「豈有此理,我給人打得頭破血流,你還說恭喜!」惠仁委曲的皺着眉頭。
「胡太太生個男孩子啦!」
「生男子關我什麽事!」
「添丁呀,胡先生!怎麽跟你沒有關係?」看護婦奇異的望着他。
「哦,是是,謝謝你!」惠仁敷衍着:「對不起,請你快點給我一點止血藥。」
「好!」看護婦走了,惠仁走進房來看湘靈。
「胡先生!怎麽你頭上受傷了?」湘靈疲倦的躺在上牀撫着剛生下的嬰孩。
「給你阿民打了!」惠仁頹喪的說道。看護婦這時拿了藥進來,替他止血敷藥。
「胡先生!你在什麽地方見到阿民?」湘靈很心急的想知道偉民的下落。
「在天堂舞廳,還同我的未婚妻在一齊喝酒!」 惠仁帶着幾分醋意的說。
「噢?阿民怎麽會在舞廳呢?」湘靈覺得很奇怪。
「你的丈夫可派頭了,一身西裝畢挺挺,係個公子哥兒,怕中了馬票也說不定哦!」惠仁帶幾分諷刺的口氣說道。他這幾句話使看護婦非常詫異,怎末湘靈還有丈夫?於是開口問道:
「胡先生你的精神沒有受到很大的刺激吧!」
「沒有呵!」惠仁覺得看護婦的話很突然。
「可是你對胡太太說的話有點不對呀!」看護婦說着,笑着出去了。
惠仁和湘靈這才想起來,剛才的談話的確使局外人感到驚異,不禁也互相笑了笑。
「胡先生,阿民又怎樣會打你呢?」湘靈繼續問道。
「他以爲我們兩人眞的做了夫妻!」
「你不是可以對他解釋嗎?」
「一見就打,那兒有機會,走遲一步恐怕連命都沒有了!」
「他一向都不會這樣鹵莽的!」
「最糟的,連我的未婚妻都誤會起來,眞是自找麻煩!」惠仁自歎了一口氣。
「別怕,我出了院去見她,向她解釋,就沒事了。胡先生別再傷心了,囘去休息。」湘靈最後安慰他說。
「你也該早點休息了!」惠仁這才想起了湘靈是一個產婦。
十四
湘靈出了醫院,和惠仁來找白雪,可是白雪已搬了新址,他們又照址找上門,然而更不幸的是白雪的母親一開門, 看見了惠仁就生了氣,一聲不响的又把門關上,惠仁和湘靈只好沒精打彩的囘家。
由於對惠仁的誤會,白雪和偉民都受到同樣的痛苦,於是兩人的感情,已由師生的關係,一躍而達到沸點,而成爲一對熱戀的情人了。
十五
這一天,是湘靈的孩子彌月,「恭喜」聲充滿了整個客堂,從鄕下特地趕來替孫兒做彌月的糊塗夫婦,滿臉笑容的招呼着客人,忙個不了!
忽然一個客人送來一張請帖,上面寫着:「胡惠仁先生,趙湘靈小姐台升」胡塗接過來,順平翻開看着:「我倆謹定于五月十八日假座天堂花園大禮堂盟行結婚典禮,敬迓光臨。何偉民,楊白雪敬約」
胡塗看了,連忙拿給湘靈:「你哥哥今天結婚了,怎末沒早點通知,沒送禮眞不好意思。」
湘靈和惠仁聽了,不禁大驚。湘靈忍住心裏的焦急,等到沒人注意的時候,抱着兒子趕到天堂花園。偉民和白雪正在舉行婚禮,湘靈進來時,聽見司儀叫道:
「現在請新郞公開戀愛經過情形。」
湘靈忍不住心頭的憤恨,她衝上去,向大家宣佈道:「各位,你們想知道這位新郞哥的艶史嗎?我可以講給各位知道。這位新郞哥原來在鄕下有了髮妻,抛離了她,而愛上了這位歌星皇后⋯⋯⋯⋯」
衆來賓聽了湘靈這番話,非常奇異,大家面面相看。
「這對所謂才子佳人,」湘靈繼續含淚說道:「當然是天生佳偶,我是一個鄕下婆,當然配不上一個已成名的音樂家。」說着,她走近偉民:「我很自量,不會追究你,不過,這是你的骨肉,應由你負責。」她將手裏的孩子送還偉民。
偉民沒有把孩子抱過來:他發愕地呆視着湘靈,不知如何作答。而這時,惠仁也追來了,他向偉民大罵道:「你還算對得住我?阿民,我千辛萬苦保護你太太安全,你就竟然同我愛人結婚,現在我同你拼命!」惠仁舉手要打。
司儀連忙勸解:「有事慢慢講。偉民,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呀?」
「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偉民有點覺悟的樣子。
「你當然不知道,現在你已發達,你沒良心,我千方百計將阿嫂假冒我的愛人,連自己的父親都騙了 ,目的就是想帶阿嫂出來香港,等你們夫妻重逢,你就以德報怨,反而奪了我的愛人 你怎樣對得住我?」
偉民顯得非常慚愧:「阿仁,我太辜負你一片苦心,靈妹,這次完全出於誤會,我才這樣做,我何嘗 沒有爲你相思!楊小姐也一樣,阿仁,她本來也一直在愛着你,這隻戒指應該是你戴的!」他除下自己手 上戴着的戒指,替惠仁戴上後,拉他到白雪身邊:「我祝你們兩人幸福無邊。」
忽然,胡塗急匆匆地來了:「亞仁,現在來賓到齊了,還不快點囘去?」
「爸爸你來得正好,我介紹你認識,這位就是我以前對你說的,楊白雪小姐,我今天同她結婚呀!」 惠仁把白雪拉得緊緊地。
「吓,你結婚!」胡塗睜大眼睛,轉過頭對湘靈說道:「你怎麼不阻止他,你別怕,有什麽事情,有我替你出頭。」
「我不是你的媳婦,老爺!」湘靈冷靜的囘答。
「胡老伯,她是我的老婆。」偉民插進來說道。
「你親口對我說,她是你的妹妹,怎麼現在又是你的老婆?你們可別把我當着三歲孩子!」
「爸爸,他們的確是兩夫妻來的,不過想在我們家裏做工,所以騙了你是兩兄妹。」惠仁向他父親解釋。
「那麽那孩子是不是你的?」
「不是,我騙了媽,是爲了使她不把阿靈趕走。」
「吓,你把老子氣死了,現在所有親戚朋友都知道我今天請抱孫滿月酒,你說我有什麽面目去見人?」胡塗氣咻咻的說道。
「胡老伯,這次阿仁這樣做全是爲了朋友的原故—— 就算親友知道也會原諒的。」偉民溫聲和氣說,接着他催着司儀:「陳經理,請你請主婚人入席簽名啦!」
司儀於是叫道:「新郞主婚人入席。」
來賓狂笑鼓掌,胡塗經不起別人催請,終於在証婚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胡塗」。
「先生,這張是證婚書,你怎麼好在上面寫下「胡塗」;請你簽好它,胡先生!」司儀以爲胡塗心裏不滿,在証婚書上亂寫。
「要怎末簽才對呢?」胡塗感到不明白。
「請簽閣下大名。」
「我的名就是胡塗!」
「先生,你就是胡塗嗎?」司儀很奇怪。
「你說我是不是胡塗呀?」
「那我可不知道。」司儀接着向偉民問道:「是不是呀,何先生?」
「不錯,他是胡塗。」
「我不是胡塗,怎麽又會這樣胡塗呢?」
胡塗這句話,引得全場的人都大笑起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