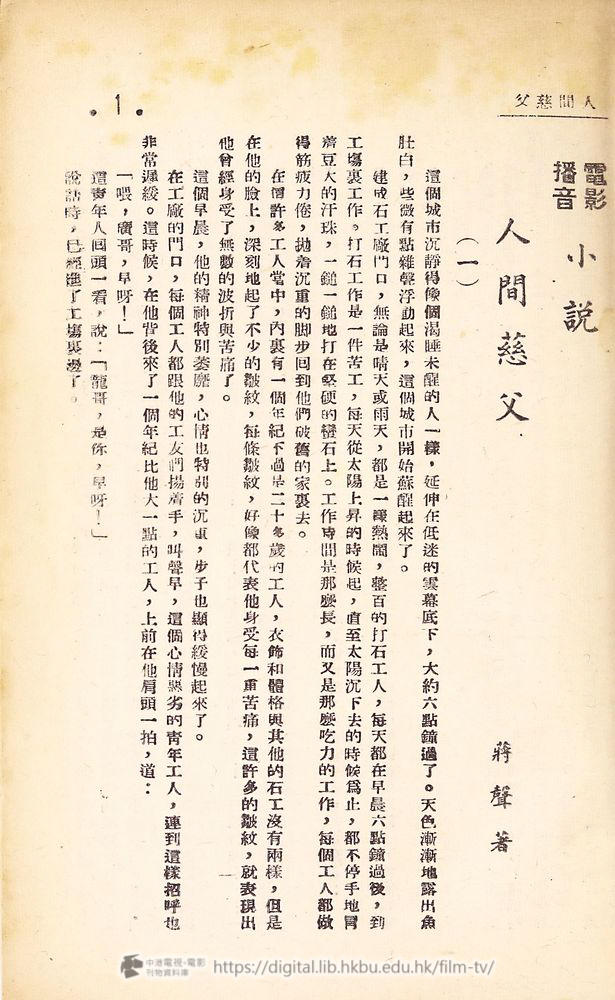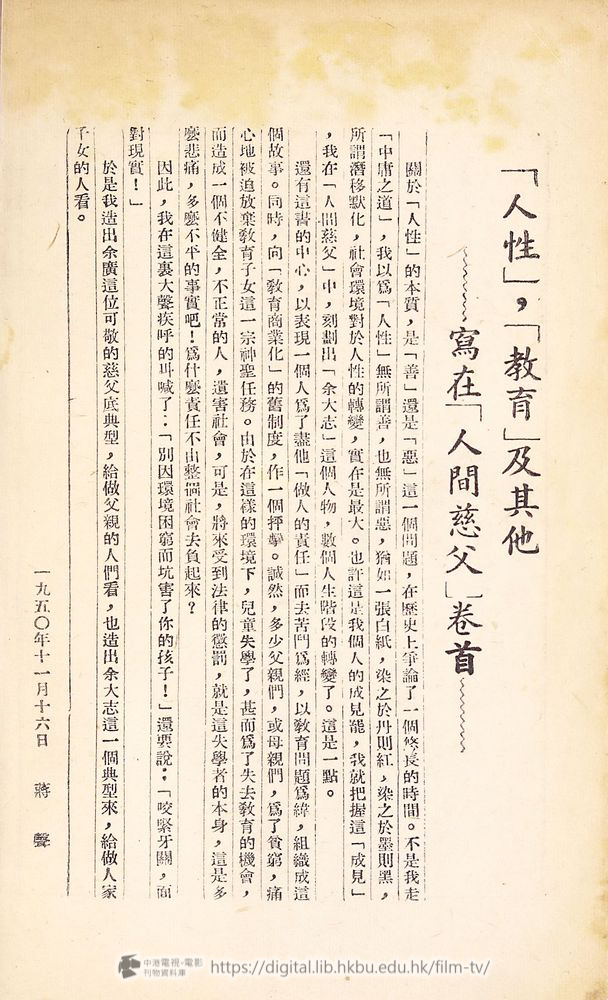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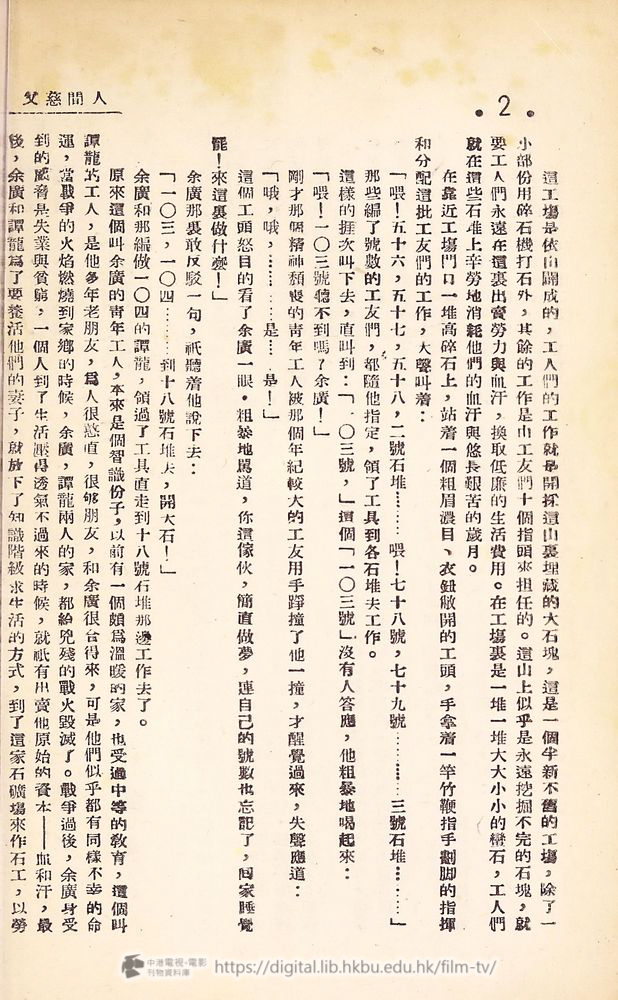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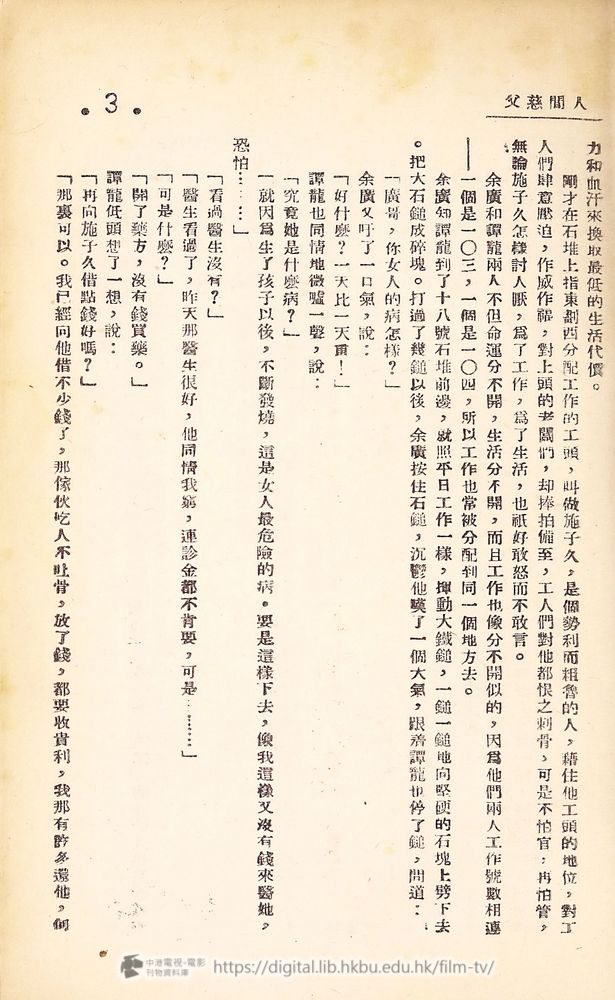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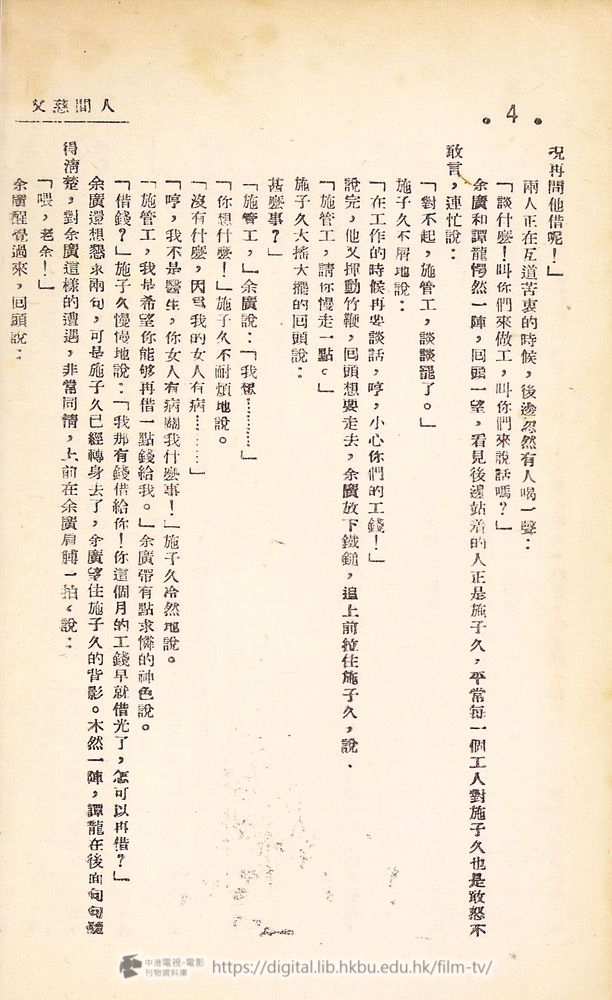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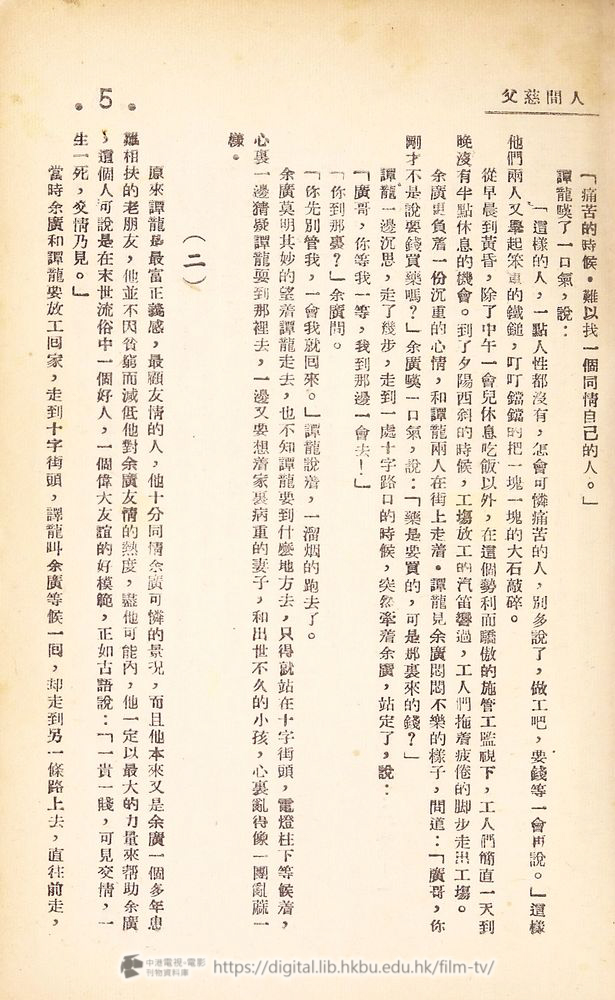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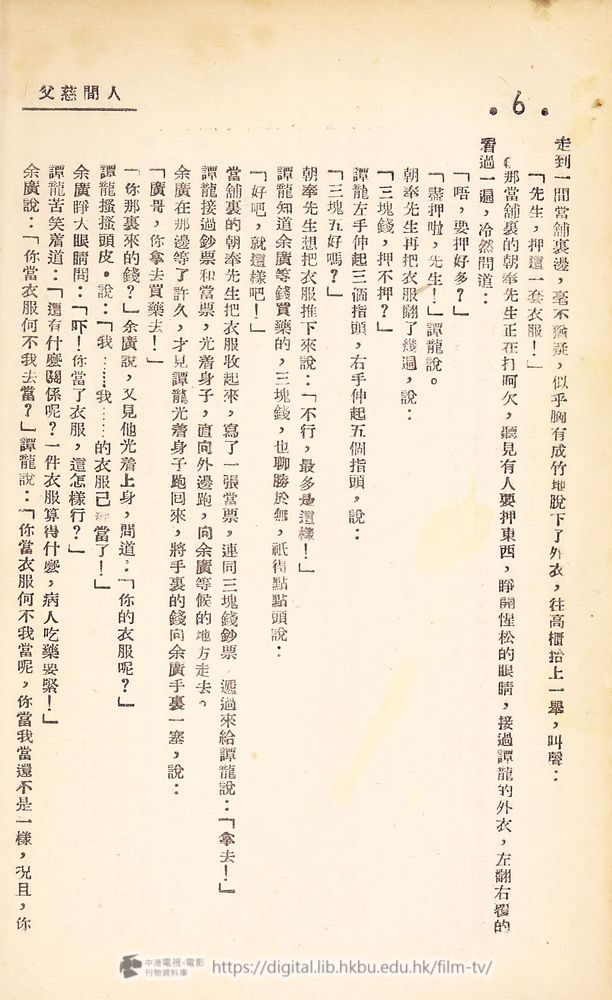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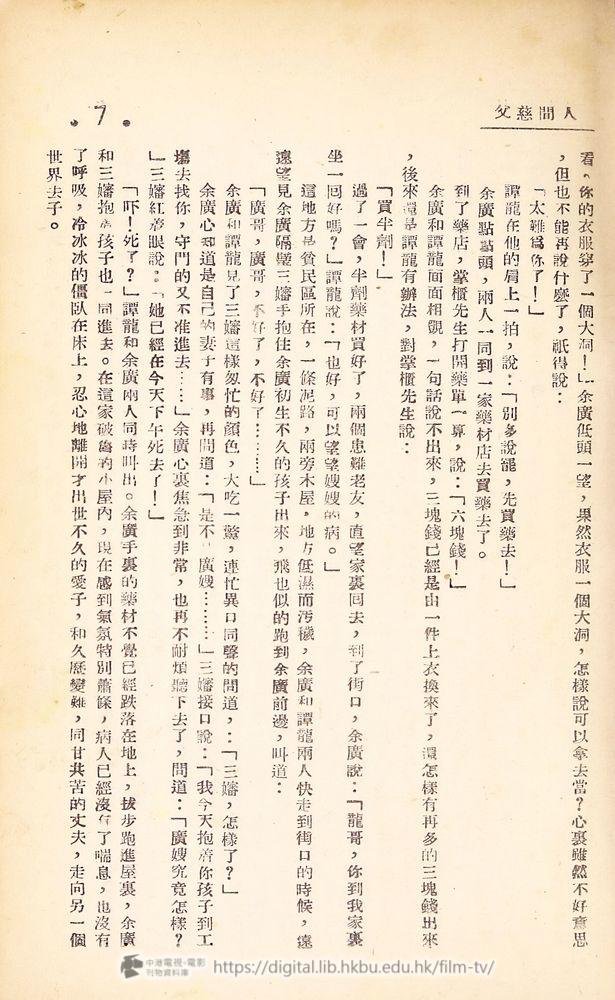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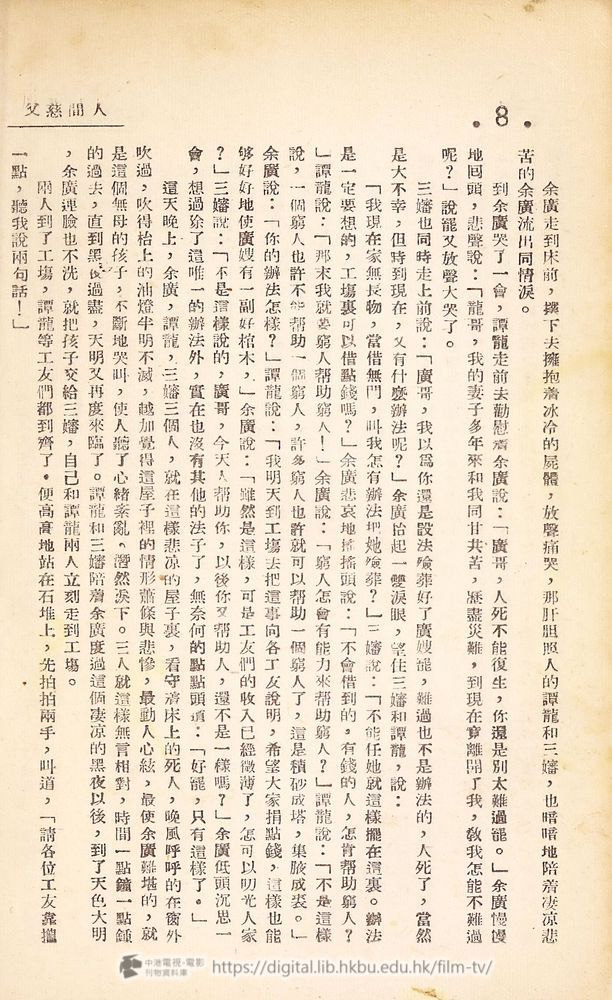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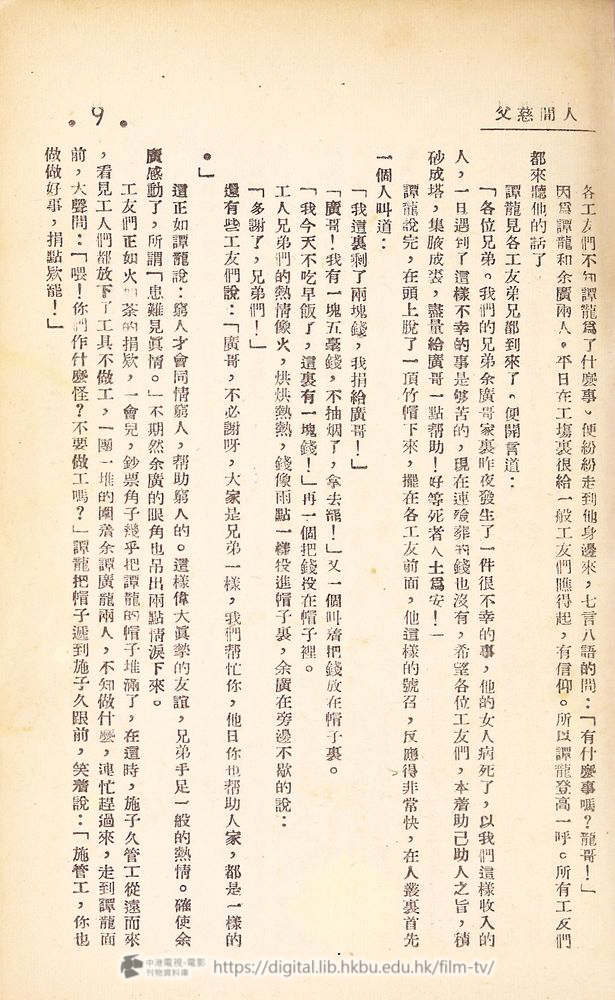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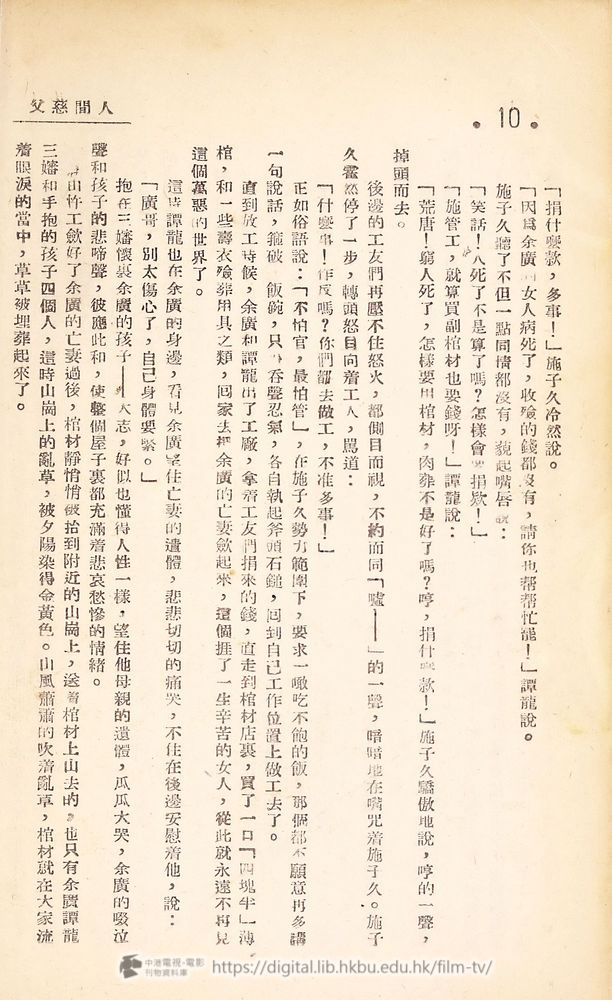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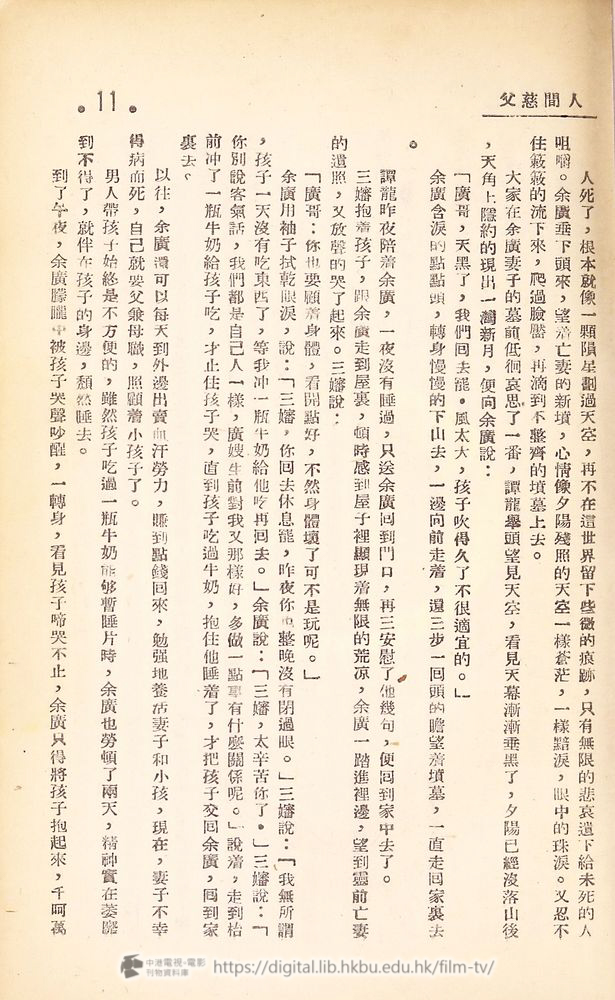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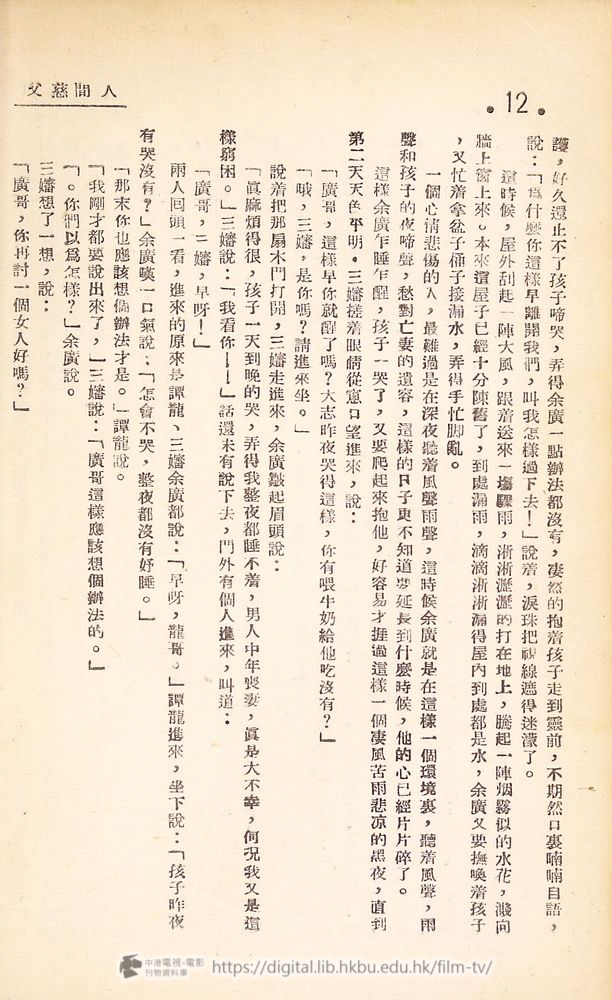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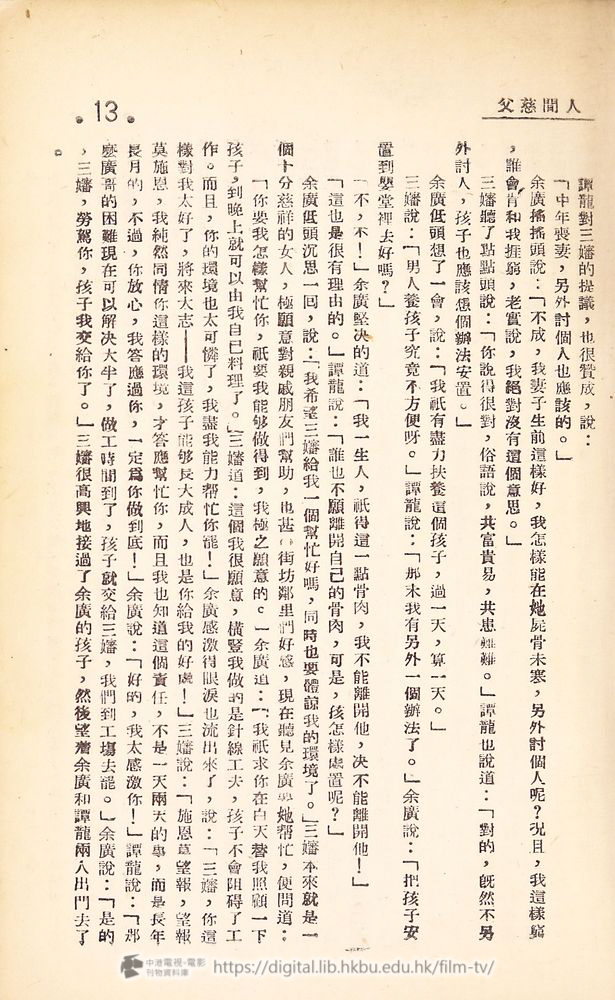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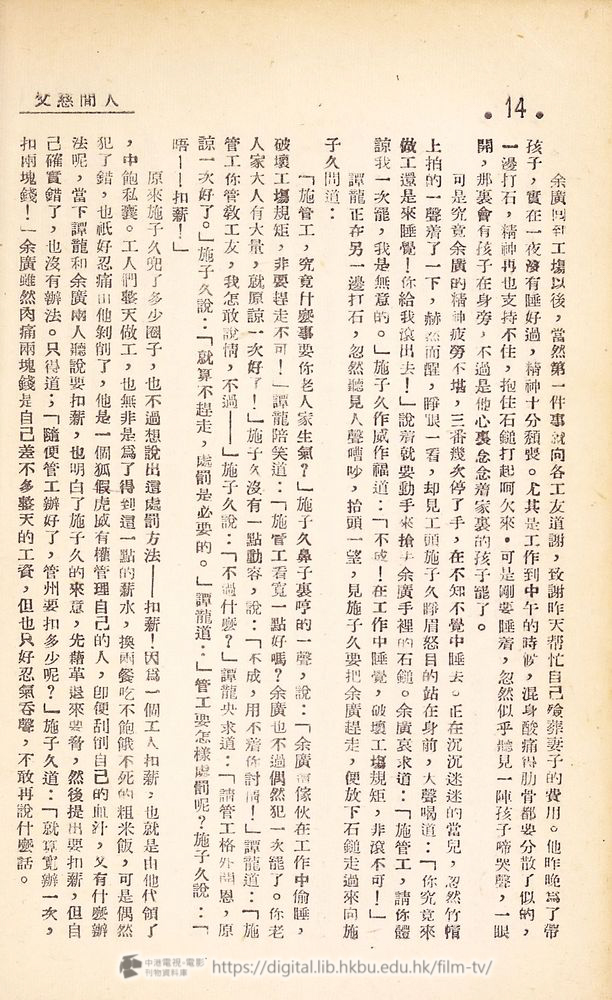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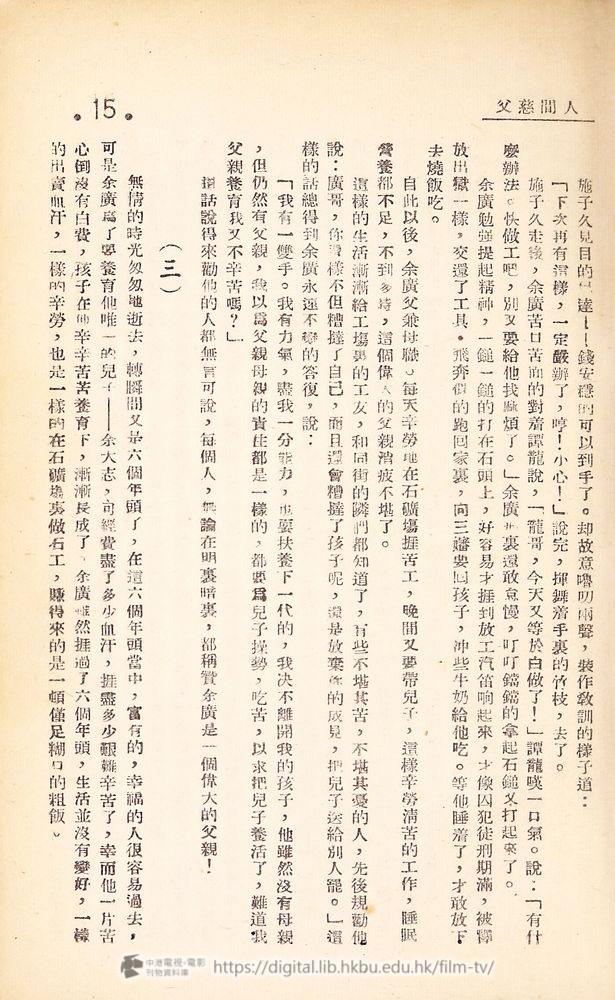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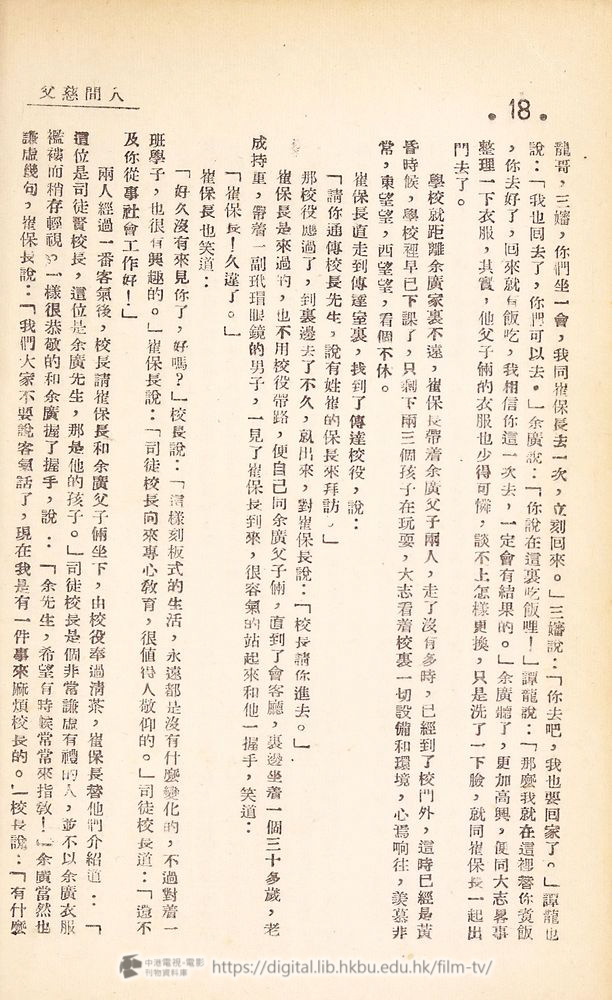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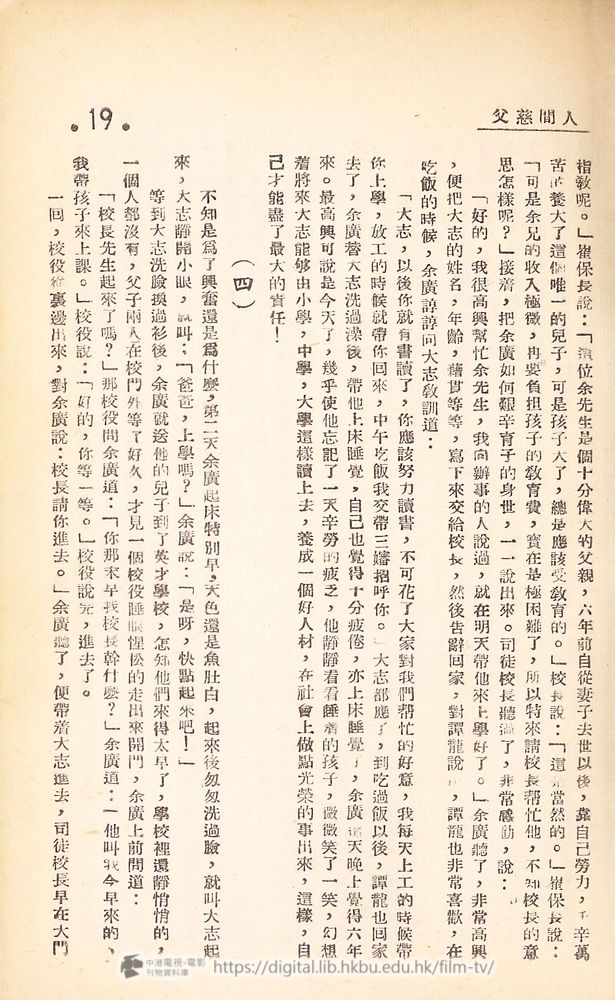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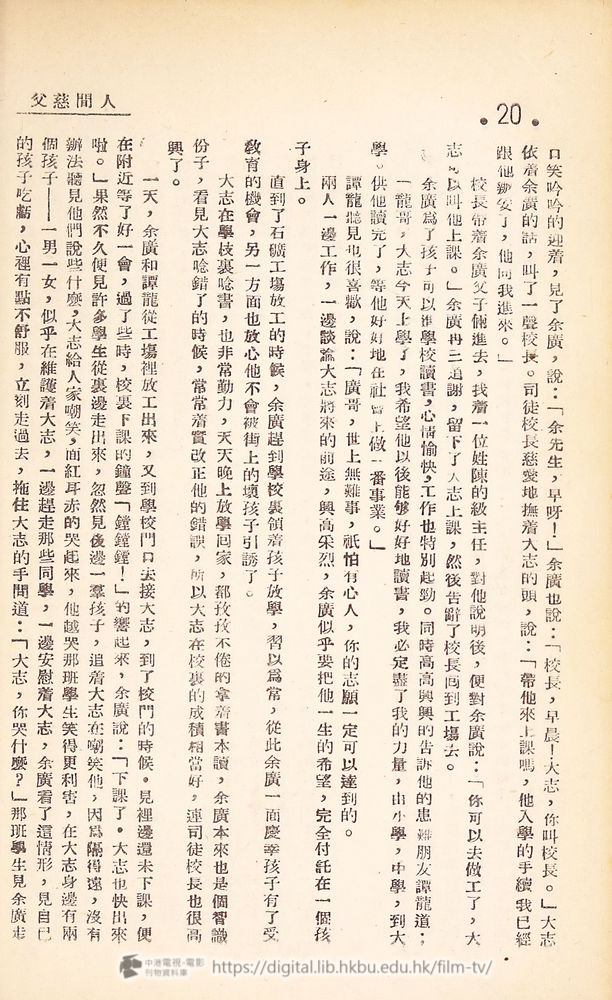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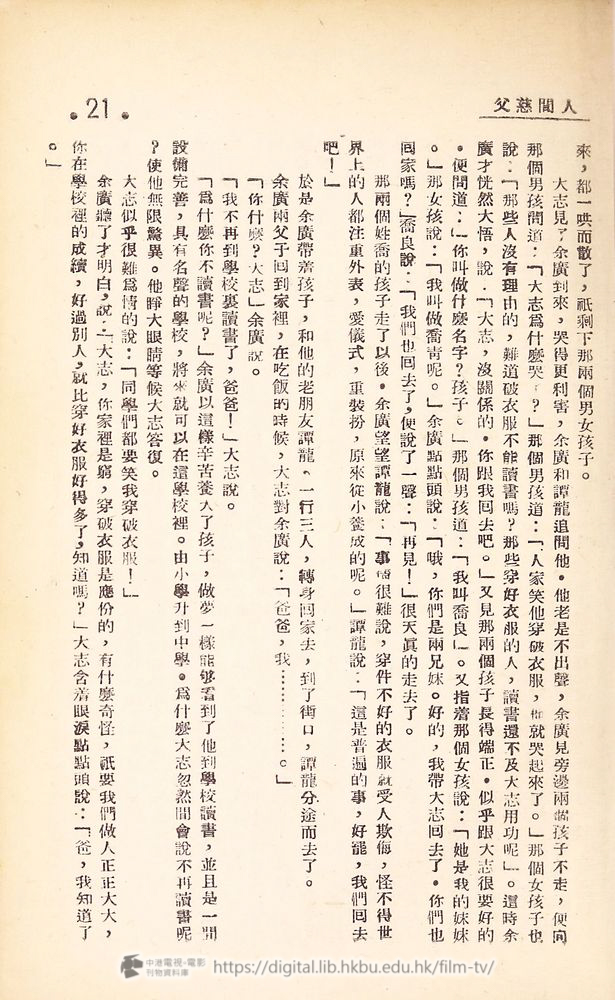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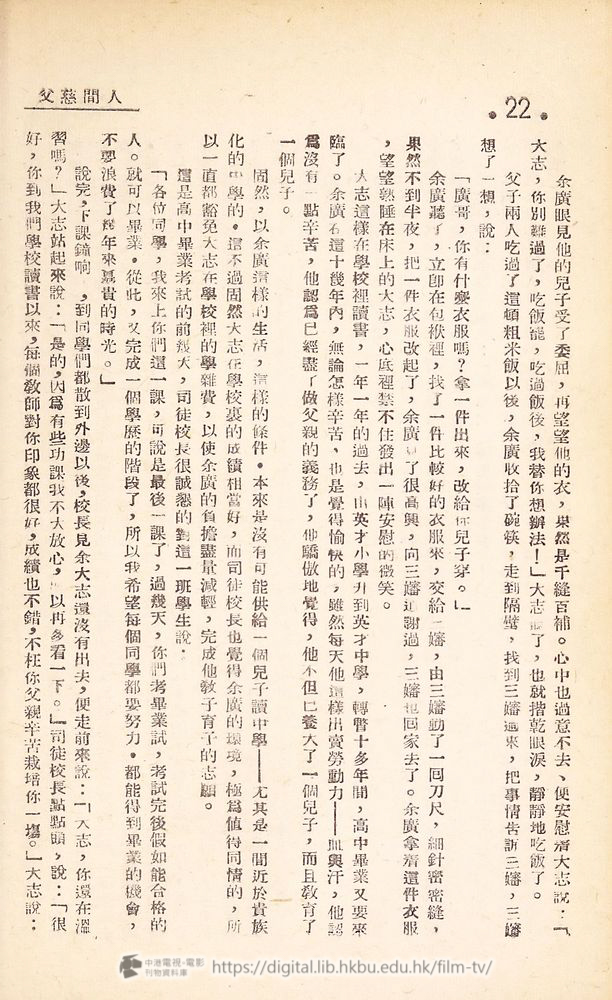













































































人間慈父
蔣聲著
電影文藝小說
人間慈父
蔣聲著述
1951
「人性」,「教育」及其他
﹏﹏寫在「人間慈父」卷首﹏﹏
關於「人性」的本質,是「善」還是「惡」這一個問題,在歷史上爭論了一個悠長的時間。不是我走「中庸之道」,我以為「人性」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猶如一張白紙,染之於丹則紅,染之於墨則黑,所謂潛移默化,社會環境對人性的轉變,實在是最大。也許這是我個人的成見罷,我就把握這「成見」,我在「人間慈父」中,刻劃出「余大志」這個人物,數個人生階段的轉變了。這是一點。
還有這書的中心,以表現一個人為了盡他「做人的責任」而去苦鬥為經,以教育問題為緯,組織成這個故事。同時,向「教育商業化」的舊制度,作一個抨擊。誠然,多少父親們,或母親們,為了貧窮,痛心地被迫放棄教育子女這一宗神聖任務。由於在這樣的環境下,兒童失學了,甚而為了失去教育的機會,而造成一個不健全,不正常的人,遺害社會,可是,將來受到法律的懲罰,就是這失學者的本身,這是多麼悲痛,多磨不平的事實吧!為什麼責任不由整個社會去負起來?
因此,我在這裹大聲疾呼地叫喊:「別因環境困窮而坑害了你的孩子!」還要說:「咬緊牙關,面對現實!」
於是我造出余廣這位可敬的慈父底典型,給做父親的人們看,也造出余大志這一個典型來,給做人家子女的人看。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蔣聲
電影播音
小說
人間慈父
蔣聲著
(一)
這個城市沉靜得像個渴睡未醒的人一樣,延伸在低迷的雲幕底下,大約六點鐘過了。天色漸漸地露出魚肚白,些微有點雜聲浮動起來,這個城市開始蘇醍起來了。
建成石工廠門口,無論是晴天或雨天,都是一樣熱鬧,整百的打石工人,毎天都在早晨六點鐘過後,到工場裏工作,打石工作是一件苦工,每天從太陽上昇的時候起,直至太陽沉下去的時候爲止,都不停手地冒着豆大的汗珠,一鎚一鎚地打在堅硬的蠻石上。工作時間是那麽長,而又是那麼吃力的工作,每個工人都做得筋疲力倦,拋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他們破舊的家裏去。
在這許多工人當中,內裏有一個年紀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工人,衣飾和體格與其他的石工沒有兩樣,但是在他的瞼上,深刻地起了不少的皺紋,毎條皺紋,好像都代表他身受每一重苦痛,這許多的皺紋,就表現出他曾經身受了無數的波折與苦痛了。
這個早晨,他的精神特別萎靡,心情也特別的沉重,步子也顯得緩慢起來了。
在工廠的門口,每個工人都跟他的工友們揚着手,叫聲早,這個心情惡劣的青年工人,連到這樣招呼也非常遲緩。這時候,在他背後來了一個年紀比他大一點的工人,上前在他肩頭一拍,道:
「喂,廣哥,早呀!」
這青年人回頭一看,說:「龍哥,是你,早呀!」
說話時,已經進了工場裏邊了。
這工場是依山闢成的,工人們的工作就是開採這山裏埋藏的大石塊,這是一個半新不舊的工場,除了一小部份用碎石機打石外,其餘的工作是由工友們十個指頭來担任的。這山上似乎是永遠挖掘不完的石塊,就要工人們永遠在這裏出賣勞力與血汗,換取低廉的生活費用。在工場裏是一堆一堆大大小小的蠻石,工人們就在這些石堆上辛勞地消耗他們的血汗與悠長艱苦的歲月。
在靠近工場門口一堆高碎石上,站着一個粗眉濃目、衣鈕敝開的工頭,手拿着一竿竹鞭指手劃脚的指揮和分配這批工友們的工作,大聲叫着:
「喂!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二號石堆……喂!七十八號,七十九號……三號石堆……」
那些編了號數的工友們,都隨他指定,領了工具到各石堆去工作。
這樣的捱次叫下去,直叫到:「一〇三號,」這個「一〇三號」沒有人答應,他粗暴地喝起來:
「喂!一〇三號聽不到嗎?余廣!」
剛才那個精神頹喪的青年工人被那個年紀較大的工友用手踭撞了他一撞,才醒覺過來,失聲應道:
「哦,哦,……是……是!」
這個工頭怒目的看了余廣一眼,粗暴地駡道,你這傢伙,簡直做夢,連自己的號數也忘記了,回家睡覺罷!來這裏做什麼!」
余廣那裏敢反駁一句,祇聽着他說下去:
「一〇三,一〇四……到十八號石堆去,開大石!」
余廣和那編做一〇四的譚龍,領過了工具直走到十八號石堆那邊工作去了。
原來這個叫余廣的青年工人,本來是個智識份子,以前有一個頗爲溫暖的家,也受過中等的敎育,這個叫譚龍的工人,是他多年老朋友,爲人很憨直,很够朋友,和余廣很合得來,可是他們似乎都有同樣不幸的命運,當戰爭的火焰燃燒到家鄕的時候,余廣,譚龍兩人的家,都給兇殘的戰火毀滅了。戰爭過後,余廣身受到的威脅是失業與貧窮,一個人到了生活壓得透氣不過來的時候,就祇有出賣他原始的資本——血和汗,最後,余廣和譚龍為了要養活他們的妻子,就放下了知識階級求生活的方式,到了這家石礦場來作石工,以勞力和血汗來換取最低的生活代價。
剛才在石堆上指東劃西分配工作的工頭,叫做施子久,是個勢利而粗魯的人,藉住他工頭的地位,對工人們肆意壓迫,作威作福,對上頭的老闆們,却捧拍備至,工人們對他都恨之剌骨,可是不怕官,再怕管,無論施子久怎樣討人厭,爲了工作,爲了生活,也祇好敢怒而不敢言。
余廣和譚龍兩人不但命運分不開,生活分不開,而且工作也像分不開似的,因為他們兩人工作號數相連——一個是一〇三,一個是一〇四,所以工作也常被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去。
余廣和譚龍到了十八號石堆前邊,就照平日工作一樣,揮動大鐵鎚,一鎚一鎚地向堅硬的石塊上劈下去。把大石鎚成碎塊。打過了幾鎚以後,余廣按住石鎚,沉鬱他嘆了一個大氣,跟着譚龍也停了鎚,問道:
「廣哥,你女人的病怎様?」
余廣又吁了一口氣,說:
「好什麼?一天比一天重!」
譚龍也同情地微噓一聲,說:
「究竟她是什麼病?」
「就因爲生了孩子以後,不斷發燒,這是女人最危險的病。要是這樣下去,像我這樣又沒有錢來醫她,恐怕……」
「看過醫生沒有?」
醫生看過了,昨天那醫生很好,他同情我窮,連診金都不肯要,可是……」
「可是什麽?」
「開了藥方,沒有錢買藥。」
譚龍低頭想了一想,說:
「再向施子久借點錢好嗎?」
「那裏可以。我已經向他借不少錢了,那傢伙吃人不吐骨,放了錢,都要收貴利,我那有許多還他,何况再問他借呢!」
兩人正在互道苦衷的時候,後邊忽然有人喝一聲:
「談什麽!叫你們來做工,叫你們來說話嗎?」
余廣和譚龍愕然一陣,回頭一望,看見後邊站着的人正是施子久,平常每一個工人對施子久也是敢怒不敢言,連忙說:
「對不起,施管工,談談罷了。」
施子久不屑地說:「在工作的時候再要談話,哼,小心你們的工錢!」
說完,他又揮動竹鞭,回頭想要走去,余廣放下鐵鎚,追上前拉住施子久,說:
「施管工,請你慢走一點。」
施子久大搖大擺的回頭說:
甚麼事?」
「施管工,」余廣說:「我想……」
「你想什麼!」施子久不耐煩地說。
「沒有什麼,因爲我的女人有病……」
「哼,我不是醫生,你女人有病關我什麼事!」施子久冷然地說。
「施管工,我是希望你能够再借一點錢給我。」余廣帶有點求憐的神色說。
「借錢?」施子久慢慢地說:「我那有錢借給你!你這個月的工錢早就借光了,怎可以再借?」
余廣還想懇求兩句,可是施子久已經轉身去了,余廣望住施子久的背影。木然一陣,譚龍在後面句句聽得清楚,對余廣這樣的遭遇,非常同情,上前在余廣肩膊一拍,說:
「喂,老余!」
余廣醒覺過來,回頭說:
「痛苦的時候,難以找一個同情自己的人。」
譚龍嘆了一口氣,說:
「這樣的人,一點人性都沒有,怎會可憐痛苦的人,別多說了,做工吧,要錢等一會再說。」這樣他們兩人又舉起笨重的鐵鎚,叮叮鐺鐺的把一塊一塊的大石敲碎。
從早晨到黃昏,除了中午一會兒休息吃飯以外,在這個勢利而驕傲的施管工監視下,工人們簡直一天到晚沒有半點休息的機會。到了夕陽西斜的時候,工場放工的汽笛響過,工人們拖着疲倦的脚步走出工場。
余廣更負着一份沉重的心情,和譚龍兩人在街上走着。譚龍見余廣悶悶不樂的樣子,問道:「廣哥,你剛才不是說要錢買藥嗎?」余廣嘆一口氣,說:「藥是要買的,可是那裏來的錢?」
譚龍一邊沉思,走了幾步,走到一處十字路口的時候,突然牽着余廣,站定了,說:
「廣哥,你等我一等,我到那邊一會去!」
「你到那裏?」余廣問。
「你先別管我,一會我就回來。」譚龍說着,一溜烟的跑去了。
余廣莫明其妙的望着譚龍走去,也不知譚龍要到什麽地方去,只得就站在十字街頭,電燈柱下等候着,心裏一邊猜疑譚龍要到那裡去,一邊又要想着家裏病重的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小孩,心裏亂得像一團亂蔴一樣。
(二)
原來譚龍是最富正義感,最顧友情的人,他十分同情余廣可憐的景况,而且他本來又是余廣一個多年患難相扶的老朋友,他並不因貧窮而減低他對余廣友情的熱度,盡他可能內,他一定以最大的力量來帮助余廣;這個人可說是在末世流俗中一個好人,一個偉大友誼的好模範,正如古語說:「一貴一賤,可見交情,一生一死,交情乃見。」
當時余廣和譚龍要放工回家,走到十字街頭,譚龍叫余廣等候一回,却走到另一條路上去,直往前走,走到一間當舖裏邊,毫不猶豫,似乎胸有成竹地脫下了外衣,往高櫃抬上一舉,叫聲:
「先生,押這一套衣服!」
那當鋪裏的朝奉先生正在打呵欠,聽見有人要押東西,睜開惺松的眼睛,接過譚龍的外衣,左翻右覆的看過一遍,冷然問道:
「唔,要押好多?」
「盡押啦,先生!」譚龍說。
朝奉先生再把衣服翻了幾遍,說:
「三塊錢,押不押?」
譚龍左手伸起三個指頭,右手伸起五個指頭,說:
「三塊五好嗎?」
朝奉先生想把衣服推下來說:「不行,最多是這樣!」
譚龍知道余廣等錢買藥的,三塊錢,也聊勝於無,祇得點點頭說:
「好吧,就這樣吧!」
當舖裏的朝奉先生把衣服收起來,寫了一張當票,連同三塊錢鈔票,遞過來給譚龍說:「拿去!」
譚龍接過鈔票和當票,光着身子,直向外邊跑,向余廣等候的地方走去。
余廣在那邊等了許久,才見譚龍光着身子跑回來,將手裏的錢向余廣手裏一塞,說:
「廣哥,你拿去買藥去!」
「你那裏來的錢?」余廣說,又見他光着上身,問道:「你的衣服呢?」
譚龍搔搔頭皮,說:「我……我……的衣服已經當了!」
余廣睜大眼睛問:「吓!你當了衣服,這怎樣行?」
譚龍苦笑着道:「還有什麼關係呢?一件衣服算得什麽,病人吃藥要緊!」
余廣說:「你當衣服何不我去當?」譚龍說:「你當衣服何不我當呢,你當我當還不是一樣,况且,你看,你的衣服穿了一個大洞!」余廣低頭一望,果然衣服一個大洞,怎樣說可以拿去當?心裏雖然不好意思,但也不能再說什麽了,祇得說:
「太難為你了!」
譚龍在他的肩上一拍,說:「別多說罷,先買藥去!」
余廣點點頭,兩人一同到一家藥材店去買藥去了。
到了藥店,掌櫃先生打開藥單一算,說:「六塊錢!」
余廣和譚龍面面相覷,一句話說不出來,三塊錢已經是由一件上衣換來了,還怎樣有再多的三塊錢出來,後來還是譚龍有辦法,對掌櫃先生說:
「買半劑!」
過了一會,半劑藥材買好了,兩個患難老友,直望家裏回去,到了街口,余廣說:「龍哥,你到我家裏坐一回好嗎?」譚龍說:「也好,可以望望嫂嫂的病。」
這地方是貧民區所在,一條泥路,兩旁木屋,地方低濕而汚穢,余廣和譚龍兩人快走到街口的時候,遠遠望見余廣隔壁三嬸手抱住余廣初生不久的孩子出來,飛也似的跑到余廣前邊,叫道:
「廣哥,廣哥,不好了,不好了……」
余廣和譚龍見了三嬸這樣匆忙的顏色,大吃一驚,連忙異口同聲的問道:「三嬸,怎樣了?」
余廣心知道是自己的妻子有事,再問道:「是不是廣嫂……」三嬸接口說:「我今天抱着你孩子到工場去找你,守門的又不准進去……」余廣心裏焦急到非常,也再不耐煩聽下去了,問道:「廣嫂究竟怎樣?」三嬸紅着眼說:「她已經在今天下午死去了!」
「吓!死了?」譚龍和余廣兩人同時叫出。余廣手裏的藥材不覺已經跌落在地上,拔步跑進屋裏,余廣和三嬸抱着孩子也一同進去。在這家破舊的小屋內,現在感到氣氛特別蕭條,病人已經沒有了喘息,也沒有了呼吸,冷冰冰的僵臥在床上,忍心地離開才出世不久的愛子,和久歷變難,同甘共苦的丈夫,走向另一個世界去了。
余廣走到床前,撲下去擁抱着冰冷的屍體,放聲痛哭,那肝胆照人的譚龍和三嬸,也暗喑地陪着凄凉悲苦的余廣流出同情淚。
到余廣哭了一會,譚龍走前去勸慰着余廣說:「廣哥,人死不能復生,你還是別太難過罷。」余廣幔幔地回頭,悲聲說:「龍哥,我的妻子多年來和我同甘共苦,歷盡災難,到現在竟離開了我,敎我怎能不難過呢?」說罷又放聲大哭了。
三嬸也同時走上前說:「廣哥,我以爲你還是設法殮葬好了廣嫂罷,難過也不是辦法的,人死了,當然是大不幸,但時到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余廣抬起一雙淚眼,望住三嬸和譚龍,說:
「我現在家無長物,當借無門,叫我怎有辦法把她殮葬?」三嬸說:「不能任她就這樣擺在這裏。辦法是一定要想的,工場裏可以借點錢嗎?」余廣悲哀地搖搖頭說:「不會借到的,有錢的人,怎肯帮助窮人?」譚龍說:「那末我就要窮人帮助窮人!」余廣說:「窮人怎會有能力來帮助窮人?」譚龍說:「不是這樣說,一個窮人也許不能帮助一個窮人,許多窮人也許就可以帮助一個窮人了,這是積砂成塔,集腋成裘。」余廣說:「你的辦法怎樣?」譚龍說:「我明天到工場去把這事向各工友說明,希望大家捐點錢,這樣也能够好好地使廣嫂有一副好棺木,」余廣說:「雖然是這様,可是工友們的收入已經微薄了,怎可以叨光人家?」三嬸說:「不是這樣說的,廣哥,今天人幚助你,以後你又帮助人,這不是一樣嗎?」余廣低頭沉思一會,想過除了這唯一的辦法外,實在也沒有其他的法子了,無奈何的點點頭道:「好罷,只有這樣了。」
這天晚上,余廣,譚龍,三嬸三個人,就在這樣悲凉的屋子裏,看守着床上的死人,晚風呼呼的在窗外吹過,吹得台上的油燈半明不滅,越加覺得這屋子裡的情形蕭條與悲慘,最動人心絃,最使余廣難堪的,就是這個無母的孩子,不斷地哭叫,使人聽了心緖紊亂,潛然淚下。三人就這様無言相對,時間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直到黑夜過盡,天明又再度來臨了。譚龍和三嬸陪着余廣度過這個凄凉的黑夜以後,到了天色大明,余廣連臉也不洗,就把孩子交給三嬸,自己和譚龍兩人立刻走到工場。
兩人到了工場,譚龍等工友們都到齊了,便高高地站在石堆上,先拍拍兩手,叫道,「請各位工友靠攏一點,聽我說兩句話!」
各工友們不知譚龍爲了什麼事,便紛紛走到他身邊來,七言八語的問:「有什麽事嗎?龍哥!」
因為譚龍和余廣兩人,平日在工場裏很給一般工友們瞧得起,有信仰。所以譚龍登高一呼,所有工友們都來聽他的話了。
譚龍見各工友弟兄都到來了,便開言道:
「各位兄弟。我們的兄弟余廣哥家裏昨夜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他的女人病死了,以我們這樣收入的人,一旦遇到了這樣不幸的事是够苦的,現在連殮葬的錢也沒有,希望各位工友們,本着助己助人之旨,積砂成塔,集腋成裘,盡量給廣哥一點帮助!好等死者入土爲安!」
譚龍說完,在頭上脫了一頂竹帽下來,擺在各工友前面,他這樣的號召,反應得非常快,在人叢裏首先一個人叫道:
「我這裏剩了兩塊錢,我捐給廣哥!」
「廣哥!我有一塊五毫錢,不抽烟了,拿去罷!」又一個叫着把錢放在帽子裏。
「我今天不吃早飯了,這裏有一塊錢!」再一個把錢投在帽子裡。
工人兄弟們的熱情像火,烘烘熱熱,錢像雨點一様投進帽子裏,余廣在旁邊不歇的說:
「多謝了,兄弟們!」
還有些工友們說:「廣哥,不必謝呀,大家是兄弟一樣,我們帮忙你,他日你也帮助人家,都是一樣的。」
這正如譚龍說:窮人才會同情窮人,帮助窮人的。這樣偉大真摯的友誼,兄弟手足一般的熱情。確使余廣感動了,所謂「患難見真情。」不期然余廣的眼角也吊出兩點情淚下來。
工友們正如火如荼的捐款,一會兒,鈔票角子幾乎把譚龍的帽子堆滿了,在這時,施子久管工從遠而來,看見工人們都放下工具不做工,一團一堆的圍着余譚廣龍兩人,不知做什麼,連忙趕過來,走到譚龍面前,大聲問:「喂!你們作什麼怪?不要做工嗎?」譚龍把帽子遞到施子久跟前,笑着說:「施管工,你也做做好事,捐點款罷!」
「捐什麼款,多事!」施子久冷然說。
「因為余廣的女人病死了,收殮的錢都沒有,請你也帮帮忙罷!」譚龍說。
施子久聽了不但一點同情都沒有,藐起嘴唇說:
「笑話!人死了不是算了嗎?怎樣會要捐款!」
「施管工,就算買副棺材也要錢呀!」譚龍說:
「荒唐!窮人死了,怎樣要用棺材,肉葬不是好了嗎?哼,捐什麼款!」施子久驕傲地說,哼的一聲,掉頭而去。
後邊的工友們再壓不住怒火,都側目而視,不約而同「噓——」的一聲,喑暗地在嘴咒着施子久。施子久霍然停了一步,轉頭怒目向着工人,罵道:
「什麼事!作反嗎?你們都去做工,不准多事!」
正如俗語說:「不怕官,最怕管」,在施子久勢力範圍下,要求一噉吃不飽的飯,那個都不願意再多講一句說話,箍破X飯碗,只X呑聲忍氣,各自執起斧頭石鎚,回到自己工作位置上做工去了。
直到放工時候,余廣和譚龍出了工廠,拿着工友們捐來的錢,直走到棺材店裏,買了一口「四塊半」薄棺,和一些壽衣殮葬用具之類,回家去把余廣的亡妻歛起來,這個捱了一生辛苦的女人,從此就永遠不再見這個萬惡的世界了。
這時譚龍也在余廣的身邊,看見余廣望住亡妻的遺體,悲悲切切的痛哭,不住在後邊安慰着他,說:
「廣哥,別太傷心了,自己身體要緊。」
抱在三嬸懷裏余廣的孩子——大志,好似也懂得人性一樣,望住他母親的遺體,瓜瓜大哭,余廣的啜泣聲和孩子的悲啼聲,彼應此和,使整個屋子裏都充滿着悲哀愁慘的情緖。
由忤工歛好了余廣的亡妻過後,棺材靜悄悄被抬到附近的山崗上,送着棺材上山去的,也只有余廣譚龍三嬸和手抱的孩子四個人,這時山崗上的亂草,被夕陽染得金黃色。山風蕭蕭的吹着亂草,棺材就在大家流着眼淚的當中,草草被埋葬起來了。
人死了,根本就像一顆隕星劃過天空,再不在這世界留下些微的痕跡,只有無限的悲哀遺下給未死的人咀嚼。余廣垂下頭來,望着亡妻的新墳,心情像夕陽殘照的天空一樣蒼茫,一樣黯淚,眼中的珠淚。又忍不住簌簌的流下來,爬過臉靨,再滴到不整齊的墳墓上去。
大家在余廣妻子的墓前低徊哀思了一番,譚龍舉頭望見天空,看見天幕漸漸垂黑了,夕陽已經沒落山後,天角上隱約的現出一彎新月,便向余廣說:
「廣哥,天黑了,我們回去罷。風太大,孩子吹得久了不很適宜的。」
余廣含淚的點點頭,轉身慢慢的下山去,一邊向前走着,還三步一回頭的瞻望着墳墓,一直走回家裏去。
譚龍昨夜陪着余廣,一夜沒有睡過,只送余廣回到門口,再三安慰了他幾句,便回到家中去了。
三嬸抱着孩子,跟余廣走到屋裏,頓時感到屋子裡顯現着無限的荒凉,余廣一踏進裡邊,望到靈前亡妻的遺照,又放聲的哭了起來。三嬸說:
「廣哥:你也要顧着身體,看開點好,不然身體壞了可不是玩呢。」
余廣用袖子拭乾眼淚,說:「三嬸,你回去休息罷,昨夜你也整晚沒有閉過眼。」三嬸說:「我無所謂,孩子一天沒有吃東西了,等我冲一瓶牛奶給他吃再回去。」余廣說:「三嬸,太辛苦你了。」三嬸說:「你別說客氣話,我們都是自己人一樣,廣嫂生前對我又那樣好,多做一點事有什麽關係呢。」說着,走到檯前冲了一瓶牛奶給孩子吃,才止住孩子哭,直到孩子吃過牛奶,抱住他睡着了,才把孩子交回余廣,回到家裏去。
以往,余廣還可以每天到外邊出賣血汗勞力,賺到點錢回來,勉强地養活妻子和小孩,現在,妻子不幸得病而死,自己就要父兼母職,照顧着小孩子了。
男人帶孩子始終是不方便的,雖然孩子吃過一瓶牛奶能够暫睡片時,余廣也勞頓了兩天,精神實在萎靡到不得了,就伴在孩子的身邊,頹然睡去。
到了午夜,余廣矇朧中被孩子哭聲吵醒,一轉身,看見孩子啼哭不止,余廣只得將孩子抱起來,千呵萬護,好久還止不了孩子啼哭,弄得余廣一點辦法都沒有,凄然的抱着孩子走到靈前,不期然口裏喃喃自語,說:「為什麼你這樣早離開我們,叫我怎樣過下去!」說着,淚珠把視線遮得迷濛了。
這時候,屋外刮起一陣大風,跟着送來一場驟雨,淅淅瀝瀝的打在地上,騰起一陣烟霧似的水花,濺向牆上窗上來。本來這屋子已經十分陳舊了,到處漏雨,滴滴淅淅漏得屋內到處都是水,余廣又要撫喚着孩子,又忙着拿盆子桶子接漏水,弄得手忙脚亂。
一個心情悲傷的人,最難過是在深夜聽着風聲雨聲,這時候余廣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裏,聽着風聲,雨聲和孩子的夜啼聲,愁對亡妻的遺容,這樣的日子更不知道要延長到什麼時候,他的心已經片片碎了。
這樣余廣乍睡乍醒,孩子一哭了,又要爬起來抱他,好容易才捱過這樣一個凄風苦雨悲凉的黑夜,直到第二天天色平明,三嬸搓着眼睛從窗口望進來,說:
「廣哥,這様早你就醒了嗎?大志昨夜哭得這樣,你有喂牛奶給他吃沒有?」
「哦,三嬸,是你嗎?請進來坐。」
說着把那扇木門打開,三嬸走進來,余廣皺起眉頭說:
「眞麻煩得很,孩子一天到晚的哭,弄得我整夜都睡不着,男人中年喪妻,眞是大不幸,何况我又是這樣窮困。」三嬸說:「我看你——」話還未有說下去,門外有個人進來,叫道:
「廣哥,三嬸,早呀!」
兩人回頭一看,進來的原來是譚龍,三嬸余廣都說:「早呀,龍哥。」譚龍進來,坐下說:「孩子昨夜有哭沒有?」余廣嘆一口氣說:「怎會不哭,整夜都沒有妤睡。」
「那末你也應該想個辦法才是。」譚龍說。
「我剛才都要說出來了,」三嬸說:「廣哥這樣應該想個辦法的。」
「你們以爲怎樣?」余廣說。
三嬸想了一想,說:
「廣哥,你再討一個女人好嗎?」
譚龍對三嬸的提議,也很贊成,說:
「中年喪妻,另外討個人也應該的。」
余廣搖搖頭說:「不成,我妻子生前這樣好,我怎樣能在她屍骨未寒,另外討個人呢?况且,我這樣窮,誰會肯和我捱窮,老實說,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三嬸聽了點點頭說:「你說得很對,俗語說,共富貴易,共患難難。」譚龍也說道:「對的,既然不另外討人,孩子也應該想個辦法安置。」
余廣低頭想了一會,說:「我祇有盡力扶養這個孩子,過一天,算一天。」
三嬸說:「男人養孩子究竟不方便呀。」譚龍說:「那末我有另外一個辦法了。」余廣說:「把孩子安置到嬰堂裡去好嗎?」
「不,不!」余廣堅决的道:「我一生人,祇得這一點骨肉,我不能離開他,决不能離開他!」
「這也是很有理由的。」譚龍說:「誰也不願離開自己的骨肉,可是,孩怎樣處置呢?」
余廣低頭沉思一回,說:「我希望三嬸給我一個幚忙好嗎,同時也要體諒我的環境了。」三嬸本來就是一個十分慈祥的女人,極願意對親戚朋友們幚助,也甚X街坊鄰里們好感,現在聽見余廣要她帮忙,便問道:
「你要我怎樣幚忙你,祇要我能够做得到,我極之願意的。」余廣道:「我祇求你在白天替我照顧一下孩子,到晚上就可以由我自己料理了。」三嬸道:這個我很願意,橫豎我做的是針線工夫,孩子不會阻碍了工作。而且,你的環境也太可憐了,我盡我能力帮忙你罷!」余廣感激得眼淚也流出來了,說:「三嬸,你這樣對我太好了,將來大志——我這孩子能够長大成人,也是你給我的好處!」三嬸說:「施恩莫望報,望報莫施恩,我純然同情你這樣的環境,才答應幚忙你,而且我也知道這個責任,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長年長月的,不過,你放心,我答應過你,一定爲你做到底!」余廣說:「好的,我太感激你!」譚龍說:「那麼廣哥的困難現在可以解决大半了,做工時間到了,孩子就交給三嬸,我們到工場去罷。」余廣說:「是的,三嬸,勞駕你,孩子我交給你了。」三嬸很高興地接過了余廣的孩子,然後望着余廣和譚龍兩人出門去了。
余廣回到工場以後,當然第一件事就向各工友道謝,致謝昨天帮忙自己殮葬妻子的費用。他昨晚爲了帶孩子,實在一夜沒有睡好過,精神十分頹喪。尤其是工作到中午的時候,混身酸痛得肋骨部要分散了似的,一邊打石,精神再也支持不住,抱住石鎚打起呵欠來,可是剛要睡着,忽然似乎聽見一陣孩子啼哭聲,一眼開,那裏會有孩子在身旁,不過是他心裏念念着家裏的孩子罷了。
可是究竟余廣的精神疲勞不堪,三番幾次停了手,在不知不覺中睡去。正在沉沉迷迷的當兒,忽然竹帽上拍的一聲着了一下,赫然而醒,睜眼一看,却見工頭施子久睜眉怒目的站在身前,大聲喝道:「你究竟來做工還是來睡覺!你給我滾出去!」說着就要動手来搶去余廣手裡的石鎚。余廣哀求道:「施管工,請你體諒我一次罷,我是無意的。」施子久作威作福道:「不成!在工作中睡覺,破壞工場規矩,非滾不可!」
譚龍正在另一邊打石,忽然聽見人聲嘈吵,抬頭一望,見施子久要把余廣趕走,便放下石鎚走過來向施子久問道:
「施管工,究竟什麼事要你老人家生氣?」施子久鼻子裏哼的一聲,說:「余廣這傢伙在工作中偷睡,破壞工場規矩,非要趕走不可!」譚龍陪笑道:「施管工看寬一點好嗎?余廣也不過偶然犯一次罷了。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就原諒一次好了!」施子久沒有一點動容,說:「不成,用不着你討情!」譚龍道:「施管工你管敎工友,我怎敢說情,不過——」施子久說:「不過什麼?」譚龍央求道:「請管工格外開恩,原諒一次好了。」施子久說:「就算不趕走,處罰是必要的。」譚龍道:「管工要怎樣處罰呢?施子久說:「唔——扣薪!」
原來施子久兜了多少圈子,也不過想說出這處罰方法——扣薪!因爲一個工人扣薪,也就是由他代領了,中飽私囊。工人們整天做工,也無非是爲了得到這一點的薪水,換兩餐吃不飽餓不死的粗米飯,可是偶然犯了錯,也祇好忍痛由他剝削了,他是一個狐假虎威有權管理自己的人,即便刮削自己的血汗,又有什麼辦法呢,當下譚龍和余廣兩人聽說要扣薪,也明白了施子久的來意,先藉革退來要脅,然後提出要扣薪,但自己確實錯了,也沒有辦法。只得道:「隨便管工辦好了,管州要扣多少呢?」施子久道:「就算寛辦一次,扣兩塊錢!」余廣雖然肉痛兩塊錢是自己差不多整天的工資,但也只好忍氣呑聲,不敢再說什麼話。
施子久見目的已達——錢安穏的可以到手了。却故意嚕叨兩聲,裝作敎訓的樣子道:
「下次再有這樣,一定嚴辦了,哼!小心!」說完,揮舞着手裏的竹枝,去了。
施子久走後,余廣苦口苦面的對着譚龍說,「龍哥,今天又等於白做了!」譚龍嘆一口氣。說:「有什麼辦法。快做工吧,別又要給他找麻煩了。」余廣那裏還敢怠慢,叮叮鐺鐺的拿起石鎚又打起来了。
余廣勉强提起精神,一鎚一鎚的打在石頭上,好容易才捱到放工汽笛响起來,才像囚犯徒刑期滿,被釋放出獄一樣,交還了工具,飛奔似的跑回家裏,向三嬸要回孩子,冲些牛奶給他吃。等他睡着了,才敢放下去燒飯吃。
自此以後,余廣父兼母職。每天辛勞地在石礦場捱苦工,晚間又要帶兒子,這樣辛勞清苦的工作,睡眠營養都不足,不到多時,這個偉大的父親消疲不堪了。
這樣的生活漸漸給工場裏的工友,和同街的隣們都知道了,有些不堪其苦,不堪其憂的人,先後規勸他說:廣哥,你這樣不但糟蹋了自己,而且還糟蹋了孩子呢,還是放棄你的成見,把兒子送給別人罷。」這樣的話總得到余廣永遠不變的答復,說:
「我有一雙手。我有力氣,盡我一分能力,也要扶養下一代的,我决不離開我的孩子,他雖然沒有母親,但仍然有父親,我以爲父親母親的責任都是一樣的,都要爲兒子操勢,吃苦,以求把兒子養活了,難道我父親養育我又不辛苦嗎?」
這話說得來勸他的人都無言可說,每個人,無論在明裏暗裏,都稱贊余廣是一個偉大的父親!
(三)
無情的時光匆匆地逝去,轉瞬間又是六個年頭了,在這六個年頭當中,富有的,幸福的人很容易過去,可是余廣爲了要養育他唯一的兒子——余大志,可經費盡了多少血汗,捱盡多少艱難辛苦了,幸而他一片苦心倒沒有白費?孩子在他辛辛苦苦養育下,漸漸長成了,余廣雖然捱過了六個年頭,生活並沒有變好,一樣的出賣血汗,一樣的辛勞,也是一様的在石礦場裏做石工,賺得來的是一頓僅足糊口的粗飯。
那天余廣放工以後,和譚龍兩人一起回家,因爲他們兩人的家相去不遠,都往在同一條街上,不過一個是街頭,一個是街尾罷了。
兩人一邊走一邊閒談,余廣是把整副精神放在他兒子的身上,當然談不上幾句又說到兒子身上來,說:「龍哥,我看大志也應該要入學校了。」
譚龍道:「要是有錢人家,早就送到學校裡去了,奈何我們窮呢。」余廣說:「所以我非常擔心,光是把孩子養大了,不好好地叫他受敎育是不對的,我想無論如何自己吃點苦,也要供給他讀書。」譚龍說:
「這是當然的,廣哥,自從大嫂死了以後,這六年來你也吃盡苦頭了。」余廣苦笑道:「即使再苦,我也無怨言的,養育孩子,是我應盡的責任,既然是自己的責任,怎可以不負責呢?」譚龍笑着拍拍余廣肩膊,說:
「你真是一個偉大的父親,怪不得每個認識你的人,都對你稱贊的。」
兩人談談說說間,不覺又到了街口了,余廣說:「今晚你在我家裡吃飯好嗎?」譚龍道:「好,一來我沒有見你的兒子多天了,也想見見他。」余廣說:「你對大志也很受護!這使我非常高興。」
當余廣和譚龍兩人走到余廣的家門口的時候,却見那裏一羣孩子蹲在地上攤着骰子,余廣的孩子余大志也蹲在旁邊看,那班孩子一見余廣回來,檢了骰子都走去了。余廣見了大志在玩骰子,心裏非常不高興,叫道:「大志,你過來!」大志見父親顏色不對,也吃了一驚,走過來叫聲「爸爸!」余廣問道:「爲什麼你在街邊玩骰子!」大志垂着頭不敢說一聲。余廣以敎訓的口吻道:「你總不知道你爸爸用多心血養大你,你就在街上學賭錢,你可知道,賭錢是最壞的,多少人爲了賭錢,命都送掉了,我非要給你一個敎訓不可。」說着,在地上執起一根小竹枝,就要打大志,嚇得大志呱呱哭起來。譚龍攔住說道:
「余大哥,何必動氣呢,敎訓過就算了。」余廣道:「不成,非要給他吃些苦不可!」可是竹枝給譚龍接住,說:「算了,下次再玩才打未遲。」但是余廣一定要打,正在爭持間,三嬸到了,問道:
「為什麼這様嘈吵?」
「大志越學越壞,竟然在街上賭錢!」余廣說。
「小孩子是要敎的,說起來也是我的過失,我每天顧着做工,有時會不大留意到大志,任便他到處玩,住在這裏的孩子又是壞的多,我也怕大志學壞了。」三嬸很着意地說。
三嬸這樣的話,打動了余廣的心,他覺得,他六年來辛勞養子的結果,也不過做到一個「養」字,並未做到「敎」字,所謂「養不敎,父之過!」自己有一種過失,大志在街頭學賭錢,實在是養而不敎的錯誤,這錯誤,應該由自己負起,大志是無知的,天眞的,玩,是每個兒童都愛好,怎能怪大志呢?想着,手上的竹枝不期落在地上。
這時在窗口外邊,忽然叫進來一種聲音:「廣哥!放工了嗎?」
大家轉頭一望,原來在外邊的人是這街上的崔保長,崔保長是個最熱心辦理街坊福利事業的人,一來是老街坊,二來辦街坊福利的時候,常常和各人接觸,所以在這街上,毎個坊衆都跟他很厮熟的。崔保長爲人十分和靄,愛帮助別人,附近的人對他都非常好感,非常擁戴。
當時余廣見在窗外的是崔保長,便請了他進來,倒了一杯冷茶,遞過去,說:
「茶冷了,對不起!」
崔保長笑吟吟的接過茶杯,說:「沒關係,不要客氣,今天人齊,三嬸龍哥都來了,可有什麽商量嗎?」
「剛才說起大志的事,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老在家裏玩,又沒有人看管,不到學校裏讀書,究竟不是辦法的。」
崔保長點點頭說:「你說得非常對,養孩子怎可以不敎育呢?那末你打算送他到那裏讀書?」余廣說:「現在就是有困難了。」崔保長說:「你不說明我也明白了,你的困難料也不過為了一個窮字。」余廣道:「當然是這樣啦!」崔保長道:「你幾年來的環境,不但我個人同情,就是附近的人也非常敬佩,你這樣千辛萬苦也爲了一個孩子,誰也感動的,你的困難,我會盡力帮忙你!」余廣喜道:「保長,你眞能够帮忙我嗎?」崔保長想了想,說:「大志這孩子是要讀書的,這裏街頭有一間英才中學,裏邊也附設有小學的,校長先生我和他有點交情,我可以帶你見他,或者他就會給你一次幚忙的。」余廣多時祈求的希望,到現在有了一線曙光了,非常高興的道:「如果校長先生能給我帮忙,那最好了,我們什麼時候去見他哩?」崔保長說:「現在學校已經下課,他是留在校裡的,我可以立即同你去見他。」余廣說:「好,好,我們立即去,龍哥,三嬸,你們坐一會,我同崔保長去一次,立刻回來。」三嬸說:「你去吧,我也要回家了。」譚龍也說:「我也回去了,你們可以去。」余廣說:「你說在這裏吃飯哩!」譚龍說:「那麽我就在這裡替你煮飯,你去好了,回來就有飯吃,我相信你這一次去,一定會有結果的。」余廣聽了,更加高興,便同大志略事整理一下衣服,其實他父子倆的衣服也少得可燐,談不上怎様更換,只是洗了一下臉,就同崔保長一起出門去了。
學校就距離余廣家裏不遠,崔保長帶着余廣父子兩人,走了沒有多時,已經到了校門外,這時已經是黃昏時候,學校裡早已下課了,只剩下兩三個孩子在玩耍,大志看着校裏一切設備和環境,心焉响往,羨慕非常,東望望,西望望,看個不休。
崔保長直走到傳達室裏,找到了傳達校役,說:
「請你通傳校長先生,說有姓崔的保長來拜訪。」
那校役應過了,到裏邊去了不久,就出來,對崔保長說:「校長請你進去。」
崔保長是來過的,也不用校役帶路,便自己同余廣父子倆,直到了會客廳,裏邊坐着一個三十多歲,老成持重,帶着一副玳瑁眼鏡的男子,一見了崔保長到來,很客氣的站起來和他握手,笑道:
「崔保長!久違了。」
崔保長也笑道:
「好久沒有來見你了,好嗎?」校長說:「這様刻板式的生活,永遠都是沒有什麼變化的,不過對着一班學子,也很有興趣的。」崔保長說:「司徒校長向來專心敎育,很値得人敬仰的。」司徒校長道:「還不及你從事社會工作好!」
兩人經過一番客氣後,校長請崔保長和余廣父子倆坐下,由校役奉過清茶,崔保長替他們介紹道:「這位是司徒賢校長,這位是余廣先生,那是他的孩子。」司徒校長是個非常謙虛有禮的人,並不以余廣衣服襤褸而稍存輕視。一樣很恭敬的和余廣握了握手,說:「余先生,希望有時候常常來指敎!」余廣當然也謙虛幾句。崔保長說:「我們大家不要說客氣話,現在我是有一件事來麻煩校長的。」校長說:「有什麼指敎呢。」崔保長說:「這位余先生是個十分偉大的父親,六年前自從妻子去世以後,靠自己勞力,千辛萬苦的養大了這個唯一的兒子,可是孩子大了,總是應該受敎育的。」校長說:「這是當然的。」崔保長說:「可是余兄的收入極微,再要負担孩子的敎育費,實在是極困難了,所以特來請校長帮忙他,不知校長的意思怎樣呢?」接着,把余廣如何艱辛育子的身世,一一說岀來。司徒校長聽過了,非常感動,說:
「好的,我很高興幚忙余先生,我向辦事的人說過,就在明天帶他來上學好了。」余廣聽了,非常高興,便把大志的姓名,年齡,藉貫等等,寫下來交給校長,然後告辭回家,對譚龍說X,譚龍也非常喜歡,在吃飯的時候,余廣諄諄向大志敎訓道:
「大志,以後你就有書讀了,你應該努力讀書,不可花了大家對我們帮忙的好意,我每天上工的時候帶你上學,放工的時候就帶你回來,中午吃飯我交帶三嬸招呼你。」大志都應了,到吃過飯以後,譚龍也回家去了,余廣替大志洗過澡後,帶他上床睡覺,自己也覺得十分疲倦,亦上床睡覺了,余廣這天晚上覺得六年來。最高興可說是今天了,幾乎使他忘記了一天辛勞的疲乏,他靜靜看看睡着的孩子,微微笑了一笑,幻想着將來大志能够由小學,中學,大學這樣讀上去,養成一個好人材,在社會上做點光榮的事出來,這樣,自己才能盡了最大的責任!
(四)
不知是爲了興奮還是爲什麼,第二天余廣起床特別早,天色還是魚肚白,起來後匆匆洗過瞼,就叫大志起來,大志睜開小眼,就叫:「爸爸,上學嗎?」余廣説:「是呀,快點起來吧!」
等到大志洗瞼換過衫後,余廣就送他的兒子到了英才學校,怎知他們來得太早了,學校裡還靜悄悄的,一個人都沒有,父子兩人在校門外等了好久,才見一個校役睡眼惺忪的走出來開門,余廣上前問道:
「校長先生起來了嗎?」那校役問余廣道:「你那末早找校長幹什麼?」余廣道:「他叫我今早來的,我帶孩子來上課。」校役說:「好的,你等一等。」校役說完,進去了。
一回,校役從裏邊出來,對余廣說:校長請你進去。」余廣聽了,便帶着大志進去,司徒校長早在大門口笑吟吟的迎着,見了余廣,說:「余先生,早呀!」余廣也說:「校長,早晨!大志,你叫校長。」大志依着余廣的話,叫了一聲校長。司徒校長慈愛地撫着大志的頭,說:「帶他來上課嗎,他入學的手續我已經跟他辦妥了,他同我進來。」
校長帶着余廣父子倆進去,找着一位姓陳的級主任,對他說明後,便對余廣說:「你可以去做工了,大志可以叫他上課。」余廣再三道謝,留下了大志上課,然後告辭了校長回到工場去。
余廣爲了孩子可以進學校讀書,心情愉快,工作也特別起勁。同時高高興興的告訴他的患難朋友譚龍道:「龍哥,大志今天上學了,我希望他以後能够好好地讀書,我必定盡了我的力量,由小學,中學,到大學,供他讀完了,等他好好地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
譚龍聽見也很喜歡,說:「廣哥,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你的志願一定可以達到的。
兩人一邊工作,一邊談論大志將來的前途,興高采烈,余廣似乎要把他一生的希望,完全付託在一個孩子身上。
直到了石礦工場放工的時候,余廣趕到學校裏領着孩子放學,習以爲常,從此余廣一面慶幸孩子有了受敎育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放心他不會被街上的壞孩子引誘了。
大志在學校裏唸書,也非常勤力,天天晚上放學回家,都孜孜不倦的拿着畫本讀,余廣本來也是個智識份子,看見大志唸錯了的時候,常常着實改正他的錯誤,听以大志在校裏的成積相當好,連司徒校長也很高興了。
一天,余廣和譚龍從工場裡放工出來,又到學校門口去接大志,到了校門的時候,見裡邊還未下課,便在附近等了好一會,過了些時,校裏下課的鐘聲「鐺鐺鐺!」的響起來,余廣說:「下課了,大志也快出來啦。」果然不久便見許多學生從裏邊走出來,忽然見後邊一羣孩子,追着大志在嘲笑他,因為隔得遠,沒有辦法聽見他們說些什麼,大志給人家嘲笑,面紅耳赤的哭起來,他越哭那班學生笑得更利害,在大志身邊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似乎在維護着大志,一邊趕走那些同學,一邊安慰着大志,余廣看了這情形,見自己的孩子吃虧,心裡有點不舒服,立刻走過去,拖住大志的手問道:「大志,你哭什麽?」那班學生見余廣走來,都一哄而散了,祇剩下那兩個男女孩子。
大志見了余廣到來,哭得更利害,余廣和譚龍追問他,他老是不出聲,余廣見旁邊兩個孩子不走,便向那個男孩問道:「大志爲什麽哭了?」那個男孩道:「人家笑他穿破衣服,他就哭起來了。」那個女孩子也說:「那些人沒有理由的,難道破衣服不能讀書嗎?那些穿好衣服的人,讀書還不及大志用功呢。」這時余廣才恍然大悟,說:「大志,沒關係的,你跟我回去吧。」又見那兩個孩子長得端正,似乎跟大志很要好的,便問道:「你叫做什麼名字?孩子。」那個男孩道:「我叫喬良。」又指着那個女孩說:「她是我的妹妹。」那女孩說:「我叫做喬青呢。」余廣點點頭說:「哦,你們是兩兄妹。好的,我帶大志回去了。你們也回家嗎?」喬良說:「我們也回去了,便說了一聲:「再見!」很天眞的走去了。
那兩個姓喬的孩子走了以後,余廣望望譚龍說:「事情很難說,穿件不好的衣服就受人欺侮,怪不得世界上的人都注重外表,愛儀式,重裝扮,原來從小養成的呢。」譚龍說:「這是普遍的事,好罷,我們回去吧!」
於是余廣帶着孩子,和他的老朋友譚龍,一行三人,轉身回家去,到了街口,譚龍分途而去了。
余廣兩父子回到家裡,在吃飯的時候,大志對余廣說:「爸爸,我……。」
「你什瘀?大志」余廣說。
「我不再到學校裏讀書了,爸爸!」大志說。
「爲什麼你不讀書呢?」余廣以這樣辛苦養大了孩子,做夢一樣能夠看到了他到學校讀書,並且是一間設備完善,具有名聲的學校,將來就可以在這學校裡。由小學升到中學。爲什麽大志忽然間會說不再讀書呢?使他無限驚異。他睜大眼睛等候大志答復。
大志似乎很難爲情的說:「同學們都耍笑我穿破衣服!」
余廣聽了才明白,說:「大志,你家裡是窮,穿破衣服是應份的,有什麽奇怪,祇要我們做人正正大大,你在學校裡的成績,好過別人,就比穿好衣服好得多了,知道嗎?」大志含着眼淚點點頭說:「爸,我知道了。」
余廣眼見他的兒子受了委屈,再望望他的衣,果然是千縫百補。心中也過意不去、便安慰着大志說:「大志,你別難過了,吃飯罷,吃過飯後,我替你想辦法!」大志X了,也就揩乾眼淚,靜靜地吃飯了。
父子兩人吃過了這頓粗米飯以後,余廣收拾了碗筷,走到隔壁,找到三嬸過來,把事情告訴三嬸,三嬸想了一想,說:
「廣哥,你有什麼衣服嗎?拿一件出來,改給你兒子穿。」
余廣聽了,立即在包袱裡,找了一件比較好的衣服來,交給三嬸,由三嬸動了一回刀尺,細針密密縫,果然不到半夜,把一件衣服改起了,余廣見了很高興,向三嬸道謝過,三嬸也回家去了。余廣拿着這件衣服,望望熟睡在床上的大志,心底裡禁不住發出一陣安慰的微笑。
大志這樣在學校裡讀書,一年一年的過去,由英才小學升到英才中學,轉瞥十多年間,高中畢業又要來臨了。余廣在這十幾年內,無論怎様辛苦,也是覺得愉快的,雖然每天他是這樣出賣勞動力——血與汗,他認為沒有一點辛苦,他認爲已經盡了做父親的義務了,他驕傲地覺得,他不但已養大了一個兒子,而且敎育了一個兒子。
固然,以余廣這様的生活,這样的條件,本來是沒有可能供給一個兒子讀中學——尤其是一間近於貴族化的中學的。這不過固然大志在學校裏的成績相當好,而司徒校長也覺得余廣的環境,極為値得同情的,所以一直都豁免大志在學校裡的學雜費,以使余廣的負擔盡量減輕,完成他敎子育子的志願。
這是高中畢業考試的前幾天,司徒校長很誠懇的對這一班學生說:
「各位同學,我來上你們這一課,可說是最後一課了,過幾天,你們考畢業試,考試完後假如能合格的人,就可以畢業,從比,又完成一個學歷的階段了,所以我希望每個同學都要努力,都能得到畢業的機會,不要浪費了幾年來寶貴的時光。」
說完,下課鐘响,到同學們都散到外邊以後,校長見余大志還沒有出去,便走前來說:「大志,你還在溫習嗎?」大志站起來說:「是的,因爲有些功課我不大放心,所以再多看一下。」司徒校長點點頭,說:「很好,你到我們學校讀書以來,每個敎師對你印象都很好,成績也不錯,不枉你父親辛苦栽培你一場。」大志說:「也是校長對我特別帮忙,不然也難以有讀書的機會的。」校長說:「還是你自己肯努力,否則誰願栽培一個不爭氣的人呢?大志,畢業以後你打算再讀大學不呢?」大志沉鬱的搖搖頭。校長說:「什麼?你不打算讀大學嗎?」大志帶有點痛苦說:「我家裏這様窮,怎樣有能力讀大學呢?當然,我X很希望能够讀上去的,實在一個中學畢業的人,能夠做得什麼呢?」司徒校長說:「這點你不必愁,我曾經替你想過,或者可以保送你讀免費學額。」大志聽了,很高興說:「假如能够,我太感謝校長了。」司徒校長說:「這點你不必客氣我多年從事敎育,也是以作育人材,百年樹人爲宗旨,我能够做得到的事,都應該帮忙你,不過也看你的努力如何,是否能够考得上呢。好罷,你看書好了。」說定,司徒校長轉身去了。
在司徒校長心裏也很高興,十多年來自己栽培的一個學生,果然不負自己所望,成為學校裏第一個高材生,也許將來在社會能够做出一番事業,這様,爲人師者,也不無安慰的。一邊想着,微微含笑的出了課室,怎知轉角的地方一個學生叫叫跳跳的走來,跟司徒校長撞個滿懷,幾乎把司徒校長撞倒了,司徒校長站定脚,抬頭一望,原來是鄭秋明——這個在學校裏有名跳皮,曾經記了兩個大過,兩個小過,幾乎要被學校革除的。
「秋明!你看你一點正經都沒有,冒冒失失的幹什麼。」司徒校長向鄭秋明責備說。
秋明知道自己做錯了,一聲不敢响,聳聳肩膊,伸伸舌頭,垂手站住了。
好在司徒校長是個仁慈寬大的師長,也並不以為甚,只薄責秋明兩句,說:「去吧!下次小心了,碰倒誰也是不好的!」秋明呑一口涎沫,應個「是」字,轉身走去,一直走進課室裡。
大志正在看書,準備考試,耳邊聽見脚步聲,抬頭看見鄭秋明躡手躡脚走進來,說:「秋明,鬼鬼祟祟的作什麼怪!」秋明笑了一下說:「危險得很——」大志說:「什麼事這様危險?」秋明縮一縮頸子,說:「剛才在外邊跟校長一撞,蓬!的一聲,幾乎把他撞倒呢,你說危險不危險?」大志說:「又給校長駡了一頓,是嗎?」秋明點點頭說:「還用說嗎?」大志說:「活該!走路一點不小心,老是叫叫跳跳的,不駡你還罵誰?」秋明說:「不說這個了,打球嗎?」大志搖搖頭說:「這個時候還要玩嗎?考試的時候快到了,快看看書罷!」秋明笑道:「考試也要看書嗎?管他的,到時候自然有辦法!」秋明說着,驕傲和有恃無恐的神色,揚溢在瞼上,似乎他應付考試十分有辦法似的。
「你別亂吹牛,秋明,到現在你也不看書,還說要打球,對付考試你有什麼辦法?」大志說。
秋明神秘的一笑道:「哼!先把重要的書本抄好,到時拿出來一抄了之,X其「了哥」,這不是好辦法嗎?」大志是個專心求學的人,絕不贊成秋明這様作僞的行動,搖頭道:「我不能學你這様做法,我也勸你別這樣做!」秋明反對說:「難道自在不好,要辛苦才舒服嗎?你這様死讀書,簡直是蠢人!」大志說:「我不跟你作辯了,總是我要讀我的書,求學時候當然要埋頭向學的!」秋明說:「你不去玩算了,我也怕聽你一套偉大讀書的理論!」他說着,又奔出去了。大志望着他的背影,搖頭嘆息,心裏暗道:「父親有點錢供你讀書,你却這様花去,有什麽意思呢?」想着,不禁欷噓。
一回,窗外有人向大志叫道:「大志哥,這樣勤力呀,讀熟了書沒有?」大志抬頭向外一望,原來是喬良喬青兄妹兩人,大志喊道:「你們進來。」喬良和喬青兩人,應着走進來了。
喬青和喬良兄妹倆走進來,喬青說:
「大志哥,功課全預備好了沒有?」
「還有一部份未完全妥當。」大志說:「你們呢?」
「未有呢,」喬青說:「還有許多功課要預備的。」
「快要考畢業試了,功課也應該早點預備。」大志說。
喬青似乎想起了一件事,向大志問道:「大志哥,你今晚有空嗎?」大志問:「有什麽事嗎?」喬青說「我想……」她說出「我想……」兩個字,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大志說:「你想什麽?說呀!喬良接着口說:「妹妹,你怕什麼呢?又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喬青說:「我怕大志哥不答應我!」大志說:「你們兄妹倆好像猜啞謎一樣,要我答應你做什麼?」喬良說:「等我說出來好了,我們想叫你今晚到家裏指導我們一點功課。」大志說:「哦,我以為什麼事!原來是這樣,說指導我可不敢當,要是大家硏究,臨時都是可以的。」喬青聽了很高興道:「那麽大志哥算是答應了?」大志說:「這是沒有關係的,只要你歡喜!」喬良說:「現在沒有課了,就到我家去好嗎?」大志說應:「好的,等我回家去告訴了父親以後,再一起去好嗎?」喬青說:「很好,我們也到大志哥家裏見見老伯,然後到我們家裏,大志哥在我們家裏吃晚飯好了,大志說:「吃晚飯太打攪了吧?」喬良說:「千萬別客氣!就當自己家一樣。」
於是大家檢好了書籍,出了校門,喬良喬青是個富家兒女,有汽車接送上學放學的,他們三人就坐上了汽車,先回到大志家裏。那時大志的父親余廣早已放工了,在家裏休息。大志帶着喬良喬青兩人進門以後,大志首先叫了一聲:「爸爸!」喬良喬青兄妹兩人也叫了一聲:「伯伯!」余廣说:「大志,你回來了嗎?這兩位是誰?」余大志說:「爸爸,你不認得他們嗎!你是見過的。」原來余廣在喬青兄妹兩人還是孩子的時候,曾經見過。時間過得久了,他們兩人也長大多了,尤其是喬青,長得亭亭玉立,玉琢粉雕,還怎會認得,余廣端詳了一會,說:「記不清楚了。是誰?」大志笑道:「是喬良喬青兩兄妹呀!」余廣哦的一聲,說:「怪不得這様面善呢。請坐請坐,你們兩位吃飯了沒有,就在這裡吃晚飯好嗎,恐怕沒有餸菜招待你們呢。」
喬青喬良兄妹兩人雖然是富家的兒女,可是沒有半點富家兒女驕奢的氣習,對余大志的家庭,不但不嫌他們寒微,反而覺得余廣這位老人家和藹可親,大志勤奮有爲,倒是一對好父子。聽見余廣留他們吃飯,謙遜道:「別客氣了,我們今晚還請大志哥到我們家裏吃晚飯,同時指導我們溫習功課。」大志說:「爸爸,我到他們家裏溫習功課,預備畢業試,好嗎?」余廣說:「好是好的,不過打攪你們府上了。」喬良說:「老伯,你別要客氣,你老人家肯答應給大志哥去,那末現在就去了。」余廣說:「好的,你們去吧。」
喬良和喬青向余廣說過「再見」以後,便同大志出門去了。余廣見自己的兒子,認識的朋友,謙虛而有禮,心裏也很高興。
大志和喬良喬青兄妹兩人告別了余廣,出下街口,到了馬路上,還是坐着原來的汽車,直到喬青他們的家裏去。
喬青他們的家,是位置在市裡高貴的住宅區裡,在這地方,完全是有錢人的住宅,每家房子都建築得美輪美奐。喬青的父親叫喬林,是一家農業機械公司的總經理,雖然是營商致富,可是爲人非常謙虛有禮,沒有什麽階級XX,並且對於貧窮的人非常同情,也是市裏一個有名的慈善家。
當汽車到了喬家門口的時候,三人下了汽車,喬良走前去按按電鈴,不久就有工人來開門,三人進去了,直到大廳裏面,大志一看,這裏裝飾得十分講究,無論一桌一几,一簾一幔,都精美絕俗,大志雖然是個窮家子弟,可是行動舉止却十分大方,沒有半點怯志。
當時在大廳裏,有個四五十歲模様的男子,坐在沙發上看報紙,喬良和喬青走前去,叫聲:「爸爸!」大志知道這人就是他們的父親,也走前去叫聲:「伯伯!」
喬林放下了報紙,說:「你們回來了嗎?」喬良說:「是的!」喬林看着大志,見這個青年眉清目秀,器宇軒昂,雖然衣飾樸素,也掩不住他爽颯英姿,問道:「這位是——」喬青連忙替他們介紹,說:「這位是余大志同學,這位是我的父親。爸,余同學在我們學校裡是唯一的高材生呢,我們的功課,也常常得余同學指導的。」
喬林聽見,非常高興地說:「很好,很好,大志——你是我的世姪,我也不客氣地叫你的名字了,你有時候常常到這裏來坐,不知怎様,我一見了你就對你非常喜歡,以你這様又英俊,又好學的青年人,前途是未可限量的。」大志謙虛地說:「世伯,你太過獎了。」喬林說:「我從來不說客氣話,你對我的兒女,也應該看作弟妹一様,對他們的功課也好,行動也好,多多加以管束,一點不要客氣。」大志說:「我們常常是對學问上互相硏究的。」
大志雖然是第一次見喬林,可是由於說話得體,態度謙虛,而又有好禮貌,給予喬林一個極好的印象,非常高興的和大志談了許多話,同時又問起大志的家世,大志毫不隱諱的將家裏的景况,一一說出來,喬林聽完了,寄予很大的同情,安慰着大志說:「古語說得好,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古往今來做大事業的人,許多是出自寒門的,像你這樣的人材,將來一定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希望你自愛,珍惜自己,努力一點吧!」
大志接受了喬林的勉勵,非常興奮,也非常感激,說道:「世伯金石良言,我一定記住的。」喬青和喬良兩人,見自己的父親和大志兩人,雖是第一次見面,却談得投機,所謂交淺言深,心裏也很安慰。
他們談過了一會,工人出來說開飯,喬林很客氣的讓大志到飯廳去吃飯,飯後,他們同學三人,就在書房裏溫習一回功課,大志指導了喬青和喬良許多不明白的功課,喬林在旁邊看見大志對書本上的一切,做得非常深造,對大志的印象更加好了。
這樣直到九點多鐘,大志見時間不早,要回家去了,喬林叫入預備汽車,送大志回去,大志說:「不用汽車了,走路也很容易到的。」喬林道:「開車回去也很方便的,就坐汽車回去罷。」大志見喬林一片誠意,也不好過份推却,便答應下來了。喬青要同着大志一起走,送大志回去,大志推辭不來,祇得任她去了。
汽車把大志送到街口,喬青和大志一同下了汽車,大志說:「到我家裏坐一會嗎?」喬青說:「不去了,時候不早了。」大志見喬青不肯去,X無爲勉强她,說:「那末再見!」喬青想起一件事,向大志問道:「大志哥,你打算升大學嗎?」大志嘆了一口氣,似乎有無限心事說:「大學是希望升的,不過,不知道環境是否許可呢。」喬青聽見大志這樣說,也有點黯然,只有向大志安慰道:「環境不能阻止志向的,你想想辦法吧!」大志說「校長答應過保送我去考免費學額,不知道能不能够考取呢?」喬青說:「以你這樣好的學問,考取是意中事的,努力一點吧!」大志說:「謝謝你,好,再見了。」喬青見大家站在街上,不能再多說話的,也祇有說聲,再見,望住大志回家去了。可是在她心裡却想,以大志這様好的人材,却生長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裏。受了多少磨折與苦難,太可惜了。
喬青直望到大志的背影在小街中消失了,才乘車回去,在她的心裡,對大志愛才心理,悠然而生了。
(五)
大志別過喬青,回到自己的家門口,舉手敲門。裡邊余廣應道:「誰呀?」大志答道:「爸爸,是我!」余廣認出是大志的聲音,便把門開了。大志進去,叫聲:「爸爸。」余廣說:回來了嗎?你一個人回來的?大志說:「喬青用汽車送我回來的。」余廣說:「我看你姓喬的兩位同學,雖然是富家子女,可是卻沒有驕奢習慣,謙和有禮,這樣的朋友很値得認識的。」大志說:「是的,他們兄妹兩人,從小就和我做同學,兩個都非常好的。」
余廣父子談了幾句話以後,各自回床睡覺了,大志在床上一時睡不着,想起今天喬青的父親喬林對自己勉厲的話,語重心長,非常安慰,更想起喬林喬青倆對自己深厚的友情,也值得告慰的,自己只有在學問上加倍努力,才不致失了友人們的厚望,這様想了一回,漸漸地睡着了。
再禍了幾天,考過畢業試以後,大志中學求學的階段又結束了,這天是行畢業禮,在典禮散會以後,大志手持着剛才頒發了的畢業文憑,喜氣洋洋的走到校園去,迎面看見喬青和喬良都來了,大家便在校園的石凳上坐下來,喬青說:「大志哥,我們辛苦幾年總算有結果了。」喬良也說:「大志哥,你這張畢業文憑拿利家裡給老伯看,一定非常歡喜了。」大志說:「這個當然的,就算你父親也是一様,那個父親都總希望他的子女們學業成功的呢。」喬青說:「大志哥的話說得很X!」
正在他們說話間,鄭秋明也拿着畢業文憑走過來,笑嘻的說:「我今天得到了一張支票!」大志說:「什麼支票?」秋明把自己的文憑揚了一揚,說:「這不是支票嗎?」喬良說:「畢業文憑怎様會是支票呢?」秋明說:「我拿這畢業文憑回去見我父親,他一定很高興,這様就會給我許多錢了,這様畢業文憑不就是支票了嗎?」大志才恍然大悟道:「哦!原來這樣呢。」秋明繼續興高彩烈的說道:「這個星期,又不要上課,錢到手了,還不玩個痛快嗎?」喬青露出一種輕視的樣子說:「你就是懂得玩!」秋明說:「那麽你們不是在這裡商量怎樣去玩是商量什麽?」大志說:「誰像你這樣快活,我們商量升學的問題!」秋明笑道:「升學何必要商屋,有錢你愁沒X讀書嗎?」大志和喬青兄妹三人,見再說也和秋明說不來的,祇好不說了。
大志拿了他的畢業文憑回家去以後,等到他的父親余廣回來,就把文憑交給他看,余廣拿起文憑來看,頓時想起自從亡妻死了以後,從手抱嬰孩把大志養大,現在又完成了一個階段的學業了,這様艱辛的十多年生活,就捱X這個結果,所謂似喜還悲,�>
電影播音
小說
人間慈父
蔣聲著
(一)
這個城市沉靜得像個渴睡未醒的人一樣,延伸在低迷的雲幕底下,大約六點鐘過了。天色漸漸地露出魚肚白,些微有點雜聲浮動起來,這個城市開始蘇醍起來了。
建成石工廠門口,無論是晴天或雨天,都是一樣熱鬧,整百的打石工人,毎天都在早晨六點鐘過後,到工場裏工作,打石工作是一件苦工,每天從太陽上昇的時候起,直至太陽沉下去的時候爲止,都不停手地冒着豆大的汗珠,一鎚一鎚地打在堅硬的蠻石上。工作時間是那麽長,而又是那麼吃力的工作,每個工人都做得筋疲力倦,拋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他們破舊的家裏去。
在這許多工人當中,內裏有一個年紀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工人,衣飾和體格與其他的石工沒有兩樣,但是在他的瞼上,深刻地起了不少的皺紋,毎條皺紋,好像都代表他身受每一重苦痛,這許多的皺紋,就表現出他曾經身受了無數的波折與苦痛了。
這個早晨,他的精神特別萎靡,心情也特別的沉重,步子也顯得緩慢起來了。
在工廠的門口,每個工人都跟他的工友們揚着手,叫聲早,這個心情惡劣的青年工人,連到這樣招呼也非常遲緩。這時候,在他背後來了一個年紀比他大一點的工人,上前在他肩頭一拍,道:
「喂,廣哥,早呀!」
這青年人回頭一看,說:「龍哥,是你,早呀!」
說話時,已經進了工場裏邊了。
這工場是依山闢成的,工人們的工作就是開採這山裏埋藏的大石塊,這是一個半新不舊的工場,除了一小部份用碎石機打石外,其餘的工作是由工友們十個指頭來担任的。這山上似乎是永遠挖掘不完的石塊,就要工人們永遠在這裏出賣勞力與血汗,換取低廉的生活費用。在工場裏是一堆一堆大大小小的蠻石,工人們就在這些石堆上辛勞地消耗他們的血汗與悠長艱苦的歲月。
在靠近工場門口一堆高碎石上,站着一個粗眉濃目、衣鈕敝開的工頭,手拿着一竿竹鞭指手劃脚的指揮和分配這批工友們的工作,大聲叫着:
「喂!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二號石堆……喂!七十八號,七十九號……三號石堆……」
那些編了號數的工友們,都隨他指定,領了工具到各石堆去工作。
這樣的捱次叫下去,直叫到:「一〇三號,」這個「一〇三號」沒有人答應,他粗暴地喝起來:
「喂!一〇三號聽不到嗎?余廣!」
剛才那個精神頹喪的青年工人被那個年紀較大的工友用手踭撞了他一撞,才醒覺過來,失聲應道:
「哦,哦,……是……是!」
這個工頭怒目的看了余廣一眼,粗暴地駡道,你這傢伙,簡直做夢,連自己的號數也忘記了,回家睡覺罷!來這裏做什麼!」
余廣那裏敢反駁一句,祇聽着他說下去:
「一〇三,一〇四……到十八號石堆去,開大石!」
余廣和那編做一〇四的譚龍,領過了工具直走到十八號石堆那邊工作去了。
原來這個叫余廣的青年工人,本來是個智識份子,以前有一個頗爲溫暖的家,也受過中等的敎育,這個叫譚龍的工人,是他多年老朋友,爲人很憨直,很够朋友,和余廣很合得來,可是他們似乎都有同樣不幸的命運,當戰爭的火焰燃燒到家鄕的時候,余廣,譚龍兩人的家,都給兇殘的戰火毀滅了。戰爭過後,余廣身受到的威脅是失業與貧窮,一個人到了生活壓得透氣不過來的時候,就祇有出賣他原始的資本——血和汗,最後,余廣和譚龍為了要養活他們的妻子,就放下了知識階級求生活的方式,到了這家石礦場來作石工,以勞力和血汗來換取最低的生活代價。
剛才在石堆上指東劃西分配工作的工頭,叫做施子久,是個勢利而粗魯的人,藉住他工頭的地位,對工人們肆意壓迫,作威作福,對上頭的老闆們,却捧拍備至,工人們對他都恨之剌骨,可是不怕官,再怕管,無論施子久怎樣討人厭,爲了工作,爲了生活,也祇好敢怒而不敢言。
余廣和譚龍兩人不但命運分不開,生活分不開,而且工作也像分不開似的,因為他們兩人工作號數相連——一個是一〇三,一個是一〇四,所以工作也常被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去。
余廣和譚龍到了十八號石堆前邊,就照平日工作一樣,揮動大鐵鎚,一鎚一鎚地向堅硬的石塊上劈下去。把大石鎚成碎塊。打過了幾鎚以後,余廣按住石鎚,沉鬱他嘆了一個大氣,跟着譚龍也停了鎚,問道:
「廣哥,你女人的病怎様?」
余廣又吁了一口氣,說:
「好什麼?一天比一天重!」
譚龍也同情地微噓一聲,說:
「究竟她是什麼病?」
「就因爲生了孩子以後,不斷發燒,這是女人最危險的病。要是這樣下去,像我這樣又沒有錢來醫她,恐怕……」
「看過醫生沒有?」
醫生看過了,昨天那醫生很好,他同情我窮,連診金都不肯要,可是……」
「可是什麽?」
「開了藥方,沒有錢買藥。」
譚龍低頭想了一想,說:
「再向施子久借點錢好嗎?」
「那裏可以。我已經向他借不少錢了,那傢伙吃人不吐骨,放了錢,都要收貴利,我那有許多還他,何况再問他借呢!」
兩人正在互道苦衷的時候,後邊忽然有人喝一聲:
「談什麽!叫你們來做工,叫你們來說話嗎?」
余廣和譚龍愕然一陣,回頭一望,看見後邊站着的人正是施子久,平常每一個工人對施子久也是敢怒不敢言,連忙說:
「對不起,施管工,談談罷了。」
施子久不屑地說:「在工作的時候再要談話,哼,小心你們的工錢!」
說完,他又揮動竹鞭,回頭想要走去,余廣放下鐵鎚,追上前拉住施子久,說:
「施管工,請你慢走一點。」
施子久大搖大擺的回頭說:
甚麼事?」
「施管工,」余廣說:「我想……」
「你想什麼!」施子久不耐煩地說。
「沒有什麼,因爲我的女人有病……」
「哼,我不是醫生,你女人有病關我什麼事!」施子久冷然地說。
「施管工,我是希望你能够再借一點錢給我。」余廣帶有點求憐的神色說。
「借錢?」施子久慢慢地說:「我那有錢借給你!你這個月的工錢早就借光了,怎可以再借?」
余廣還想懇求兩句,可是施子久已經轉身去了,余廣望住施子久的背影。木然一陣,譚龍在後面句句聽得清楚,對余廣這樣的遭遇,非常同情,上前在余廣肩膊一拍,說:
「喂,老余!」
余廣醒覺過來,回頭說:
「痛苦的時候,難以找一個同情自己的人。」
譚龍嘆了一口氣,說:
「這樣的人,一點人性都沒有,怎會可憐痛苦的人,別多說了,做工吧,要錢等一會再說。」這樣他們兩人又舉起笨重的鐵鎚,叮叮鐺鐺的把一塊一塊的大石敲碎。
從早晨到黃昏,除了中午一會兒休息吃飯以外,在這個勢利而驕傲的施管工監視下,工人們簡直一天到晚沒有半點休息的機會。到了夕陽西斜的時候,工場放工的汽笛響過,工人們拖着疲倦的脚步走出工場。
余廣更負着一份沉重的心情,和譚龍兩人在街上走着。譚龍見余廣悶悶不樂的樣子,問道:「廣哥,你剛才不是說要錢買藥嗎?」余廣嘆一口氣,說:「藥是要買的,可是那裏來的錢?」
譚龍一邊沉思,走了幾步,走到一處十字路口的時候,突然牽着余廣,站定了,說:
「廣哥,你等我一等,我到那邊一會去!」
「你到那裏?」余廣問。
「你先別管我,一會我就回來。」譚龍說着,一溜烟的跑去了。
余廣莫明其妙的望着譚龍走去,也不知譚龍要到什麽地方去,只得就站在十字街頭,電燈柱下等候着,心裏一邊猜疑譚龍要到那裡去,一邊又要想着家裏病重的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小孩,心裏亂得像一團亂蔴一樣。
(二)
原來譚龍是最富正義感,最顧友情的人,他十分同情余廣可憐的景况,而且他本來又是余廣一個多年患難相扶的老朋友,他並不因貧窮而減低他對余廣友情的熱度,盡他可能內,他一定以最大的力量來帮助余廣;這個人可說是在末世流俗中一個好人,一個偉大友誼的好模範,正如古語說:「一貴一賤,可見交情,一生一死,交情乃見。」
當時余廣和譚龍要放工回家,走到十字街頭,譚龍叫余廣等候一回,却走到另一條路上去,直往前走,走到一間當舖裏邊,毫不猶豫,似乎胸有成竹地脫下了外衣,往高櫃抬上一舉,叫聲:
「先生,押這一套衣服!」
那當鋪裏的朝奉先生正在打呵欠,聽見有人要押東西,睜開惺松的眼睛,接過譚龍的外衣,左翻右覆的看過一遍,冷然問道:
「唔,要押好多?」
「盡押啦,先生!」譚龍說。
朝奉先生再把衣服翻了幾遍,說:
「三塊錢,押不押?」
譚龍左手伸起三個指頭,右手伸起五個指頭,說:
「三塊五好嗎?」
朝奉先生想把衣服推下來說:「不行,最多是這樣!」
譚龍知道余廣等錢買藥的,三塊錢,也聊勝於無,祇得點點頭說:
「好吧,就這樣吧!」
當舖裏的朝奉先生把衣服收起來,寫了一張當票,連同三塊錢鈔票,遞過來給譚龍說:「拿去!」
譚龍接過鈔票和當票,光着身子,直向外邊跑,向余廣等候的地方走去。
余廣在那邊等了許久,才見譚龍光着身子跑回來,將手裏的錢向余廣手裏一塞,說:
「廣哥,你拿去買藥去!」
「你那裏來的錢?」余廣說,又見他光着上身,問道:「你的衣服呢?」
譚龍搔搔頭皮,說:「我……我……的衣服已經當了!」
余廣睜大眼睛問:「吓!你當了衣服,這怎樣行?」
譚龍苦笑着道:「還有什麼關係呢?一件衣服算得什麽,病人吃藥要緊!」
余廣說:「你當衣服何不我去當?」譚龍說:「你當衣服何不我當呢,你當我當還不是一樣,况且,你看,你的衣服穿了一個大洞!」余廣低頭一望,果然衣服一個大洞,怎樣說可以拿去當?心裏雖然不好意思,但也不能再說什麽了,祇得說:
「太難為你了!」
譚龍在他的肩上一拍,說:「別多說罷,先買藥去!」
余廣點點頭,兩人一同到一家藥材店去買藥去了。
到了藥店,掌櫃先生打開藥單一算,說:「六塊錢!」
余廣和譚龍面面相覷,一句話說不出來,三塊錢已經是由一件上衣換來了,還怎樣有再多的三塊錢出來,後來還是譚龍有辦法,對掌櫃先生說:
「買半劑!」
過了一會,半劑藥材買好了,兩個患難老友,直望家裏回去,到了街口,余廣說:「龍哥,你到我家裏坐一回好嗎?」譚龍說:「也好,可以望望嫂嫂的病。」
這地方是貧民區所在,一條泥路,兩旁木屋,地方低濕而汚穢,余廣和譚龍兩人快走到街口的時候,遠遠望見余廣隔壁三嬸手抱住余廣初生不久的孩子出來,飛也似的跑到余廣前邊,叫道:
「廣哥,廣哥,不好了,不好了……」
余廣和譚龍見了三嬸這樣匆忙的顏色,大吃一驚,連忙異口同聲的問道:「三嬸,怎樣了?」
余廣心知道是自己的妻子有事,再問道:「是不是廣嫂……」三嬸接口說:「我今天抱着你孩子到工場去找你,守門的又不准進去……」余廣心裏焦急到非常,也再不耐煩聽下去了,問道:「廣嫂究竟怎樣?」三嬸紅着眼說:「她已經在今天下午死去了!」
「吓!死了?」譚龍和余廣兩人同時叫出。余廣手裏的藥材不覺已經跌落在地上,拔步跑進屋裏,余廣和三嬸抱着孩子也一同進去。在這家破舊的小屋內,現在感到氣氛特別蕭條,病人已經沒有了喘息,也沒有了呼吸,冷冰冰的僵臥在床上,忍心地離開才出世不久的愛子,和久歷變難,同甘共苦的丈夫,走向另一個世界去了。
余廣走到床前,撲下去擁抱着冰冷的屍體,放聲痛哭,那肝胆照人的譚龍和三嬸,也暗喑地陪着凄凉悲苦的余廣流出同情淚。
到余廣哭了一會,譚龍走前去勸慰着余廣說:「廣哥,人死不能復生,你還是別太難過罷。」余廣幔幔地回頭,悲聲說:「龍哥,我的妻子多年來和我同甘共苦,歷盡災難,到現在竟離開了我,敎我怎能不難過呢?」說罷又放聲大哭了。
三嬸也同時走上前說:「廣哥,我以爲你還是設法殮葬好了廣嫂罷,難過也不是辦法的,人死了,當然是大不幸,但時到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余廣抬起一雙淚眼,望住三嬸和譚龍,說:
「我現在家無長物,當借無門,叫我怎有辦法把她殮葬?」三嬸說:「不能任她就這樣擺在這裏。辦法是一定要想的,工場裏可以借點錢嗎?」余廣悲哀地搖搖頭說:「不會借到的,有錢的人,怎肯帮助窮人?」譚龍說:「那末我就要窮人帮助窮人!」余廣說:「窮人怎會有能力來帮助窮人?」譚龍說:「不是這樣說,一個窮人也許不能帮助一個窮人,許多窮人也許就可以帮助一個窮人了,這是積砂成塔,集腋成裘。」余廣說:「你的辦法怎樣?」譚龍說:「我明天到工場去把這事向各工友說明,希望大家捐點錢,這樣也能够好好地使廣嫂有一副好棺木,」余廣說:「雖然是這様,可是工友們的收入已經微薄了,怎可以叨光人家?」三嬸說:「不是這樣說的,廣哥,今天人幚助你,以後你又帮助人,這不是一樣嗎?」余廣低頭沉思一會,想過除了這唯一的辦法外,實在也沒有其他的法子了,無奈何的點點頭道:「好罷,只有這樣了。」
這天晚上,余廣,譚龍,三嬸三個人,就在這樣悲凉的屋子裏,看守着床上的死人,晚風呼呼的在窗外吹過,吹得台上的油燈半明不滅,越加覺得這屋子裡的情形蕭條與悲慘,最動人心絃,最使余廣難堪的,就是這個無母的孩子,不斷地哭叫,使人聽了心緖紊亂,潛然淚下。三人就這様無言相對,時間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直到黑夜過盡,天明又再度來臨了。譚龍和三嬸陪着余廣度過這個凄凉的黑夜以後,到了天色大明,余廣連臉也不洗,就把孩子交給三嬸,自己和譚龍兩人立刻走到工場。
兩人到了工場,譚龍等工友們都到齊了,便高高地站在石堆上,先拍拍兩手,叫道,「請各位工友靠攏一點,聽我說兩句話!」
各工友們不知譚龍爲了什麼事,便紛紛走到他身邊來,七言八語的問:「有什麽事嗎?龍哥!」
因為譚龍和余廣兩人,平日在工場裏很給一般工友們瞧得起,有信仰。所以譚龍登高一呼,所有工友們都來聽他的話了。
譚龍見各工友弟兄都到來了,便開言道:
「各位兄弟。我們的兄弟余廣哥家裏昨夜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他的女人病死了,以我們這樣收入的人,一旦遇到了這樣不幸的事是够苦的,現在連殮葬的錢也沒有,希望各位工友們,本着助己助人之旨,積砂成塔,集腋成裘,盡量給廣哥一點帮助!好等死者入土爲安!」
譚龍說完,在頭上脫了一頂竹帽下來,擺在各工友前面,他這樣的號召,反應得非常快,在人叢裏首先一個人叫道:
「我這裏剩了兩塊錢,我捐給廣哥!」
「廣哥!我有一塊五毫錢,不抽烟了,拿去罷!」又一個叫着把錢放在帽子裏。
「我今天不吃早飯了,這裏有一塊錢!」再一個把錢投在帽子裡。
工人兄弟們的熱情像火,烘烘熱熱,錢像雨點一様投進帽子裏,余廣在旁邊不歇的說:
「多謝了,兄弟們!」
還有些工友們說:「廣哥,不必謝呀,大家是兄弟一樣,我們帮忙你,他日你也帮助人家,都是一樣的。」
這正如譚龍說:窮人才會同情窮人,帮助窮人的。這樣偉大真摯的友誼,兄弟手足一般的熱情。確使余廣感動了,所謂「患難見真情。」不期然余廣的眼角也吊出兩點情淚下來。
工友們正如火如荼的捐款,一會兒,鈔票角子幾乎把譚龍的帽子堆滿了,在這時,施子久管工從遠而來,看見工人們都放下工具不做工,一團一堆的圍着余譚廣龍兩人,不知做什麼,連忙趕過來,走到譚龍面前,大聲問:「喂!你們作什麼怪?不要做工嗎?」譚龍把帽子遞到施子久跟前,笑着說:「施管工,你也做做好事,捐點款罷!」
「捐什麼款,多事!」施子久冷然說。
「因為余廣的女人病死了,收殮的錢都沒有,請你也帮帮忙罷!」譚龍說。
施子久聽了不但一點同情都沒有,藐起嘴唇說:
「笑話!人死了不是算了嗎?怎樣會要捐款!」
「施管工,就算買副棺材也要錢呀!」譚龍說:
「荒唐!窮人死了,怎樣要用棺材,肉葬不是好了嗎?哼,捐什麼款!」施子久驕傲地說,哼的一聲,掉頭而去。
後邊的工友們再壓不住怒火,都側目而視,不約而同「噓——」的一聲,喑暗地在嘴咒着施子久。施子久霍然停了一步,轉頭怒目向着工人,罵道:
「什麼事!作反嗎?你們都去做工,不准多事!」
正如俗語說:「不怕官,最怕管」,在施子久勢力範圍下,要求一噉吃不飽的飯,那個都不願意再多講一句說話,箍破X飯碗,只X呑聲忍氣,各自執起斧頭石鎚,回到自己工作位置上做工去了。
直到放工時候,余廣和譚龍出了工廠,拿着工友們捐來的錢,直走到棺材店裏,買了一口「四塊半」薄棺,和一些壽衣殮葬用具之類,回家去把余廣的亡妻歛起來,這個捱了一生辛苦的女人,從此就永遠不再見這個萬惡的世界了。
這時譚龍也在余廣的身邊,看見余廣望住亡妻的遺體,悲悲切切的痛哭,不住在後邊安慰着他,說:
「廣哥,別太傷心了,自己身體要緊。」
抱在三嬸懷裏余廣的孩子——大志,好似也懂得人性一樣,望住他母親的遺體,瓜瓜大哭,余廣的啜泣聲和孩子的悲啼聲,彼應此和,使整個屋子裏都充滿着悲哀愁慘的情緖。
由忤工歛好了余廣的亡妻過後,棺材靜悄悄被抬到附近的山崗上,送着棺材上山去的,也只有余廣譚龍三嬸和手抱的孩子四個人,這時山崗上的亂草,被夕陽染得金黃色。山風蕭蕭的吹着亂草,棺材就在大家流着眼淚的當中,草草被埋葬起來了。
人死了,根本就像一顆隕星劃過天空,再不在這世界留下些微的痕跡,只有無限的悲哀遺下給未死的人咀嚼。余廣垂下頭來,望着亡妻的新墳,心情像夕陽殘照的天空一樣蒼茫,一樣黯淚,眼中的珠淚。又忍不住簌簌的流下來,爬過臉靨,再滴到不整齊的墳墓上去。
大家在余廣妻子的墓前低徊哀思了一番,譚龍舉頭望見天空,看見天幕漸漸垂黑了,夕陽已經沒落山後,天角上隱約的現出一彎新月,便向余廣說:
「廣哥,天黑了,我們回去罷。風太大,孩子吹得久了不很適宜的。」
余廣含淚的點點頭,轉身慢慢的下山去,一邊向前走着,還三步一回頭的瞻望着墳墓,一直走回家裏去。
譚龍昨夜陪着余廣,一夜沒有睡過,只送余廣回到門口,再三安慰了他幾句,便回到家中去了。
三嬸抱着孩子,跟余廣走到屋裏,頓時感到屋子裡顯現着無限的荒凉,余廣一踏進裡邊,望到靈前亡妻的遺照,又放聲的哭了起來。三嬸說:
「廣哥:你也要顧着身體,看開點好,不然身體壞了可不是玩呢。」
余廣用袖子拭乾眼淚,說:「三嬸,你回去休息罷,昨夜你也整晚沒有閉過眼。」三嬸說:「我無所謂,孩子一天沒有吃東西了,等我冲一瓶牛奶給他吃再回去。」余廣說:「三嬸,太辛苦你了。」三嬸說:「你別說客氣話,我們都是自己人一樣,廣嫂生前對我又那樣好,多做一點事有什麽關係呢。」說着,走到檯前冲了一瓶牛奶給孩子吃,才止住孩子哭,直到孩子吃過牛奶,抱住他睡着了,才把孩子交回余廣,回到家裏去。
以往,余廣還可以每天到外邊出賣血汗勞力,賺到點錢回來,勉强地養活妻子和小孩,現在,妻子不幸得病而死,自己就要父兼母職,照顧着小孩子了。
男人帶孩子始終是不方便的,雖然孩子吃過一瓶牛奶能够暫睡片時,余廣也勞頓了兩天,精神實在萎靡到不得了,就伴在孩子的身邊,頹然睡去。
到了午夜,余廣矇朧中被孩子哭聲吵醒,一轉身,看見孩子啼哭不止,余廣只得將孩子抱起來,千呵萬護,好久還止不了孩子啼哭,弄得余廣一點辦法都沒有,凄然的抱着孩子走到靈前,不期然口裏喃喃自語,說:「為什麼你這樣早離開我們,叫我怎樣過下去!」說着,淚珠把視線遮得迷濛了。
這時候,屋外刮起一陣大風,跟着送來一場驟雨,淅淅瀝瀝的打在地上,騰起一陣烟霧似的水花,濺向牆上窗上來。本來這屋子已經十分陳舊了,到處漏雨,滴滴淅淅漏得屋內到處都是水,余廣又要撫喚着孩子,又忙着拿盆子桶子接漏水,弄得手忙脚亂。
一個心情悲傷的人,最難過是在深夜聽着風聲雨聲,這時候余廣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裏,聽着風聲,雨聲和孩子的夜啼聲,愁對亡妻的遺容,這樣的日子更不知道要延長到什麼時候,他的心已經片片碎了。
這樣余廣乍睡乍醒,孩子一哭了,又要爬起來抱他,好容易才捱過這樣一個凄風苦雨悲凉的黑夜,直到第二天天色平明,三嬸搓着眼睛從窗口望進來,說:
「廣哥,這様早你就醒了嗎?大志昨夜哭得這樣,你有喂牛奶給他吃沒有?」
「哦,三嬸,是你嗎?請進來坐。」
說着把那扇木門打開,三嬸走進來,余廣皺起眉頭說:
「眞麻煩得很,孩子一天到晚的哭,弄得我整夜都睡不着,男人中年喪妻,眞是大不幸,何况我又是這樣窮困。」三嬸說:「我看你——」話還未有說下去,門外有個人進來,叫道:
「廣哥,三嬸,早呀!」
兩人回頭一看,進來的原來是譚龍,三嬸余廣都說:「早呀,龍哥。」譚龍進來,坐下說:「孩子昨夜有哭沒有?」余廣嘆一口氣說:「怎會不哭,整夜都沒有妤睡。」
「那末你也應該想個辦法才是。」譚龍說。
「我剛才都要說出來了,」三嬸說:「廣哥這樣應該想個辦法的。」
「你們以爲怎樣?」余廣說。
三嬸想了一想,說:
「廣哥,你再討一個女人好嗎?」
譚龍對三嬸的提議,也很贊成,說:
「中年喪妻,另外討個人也應該的。」
余廣搖搖頭說:「不成,我妻子生前這樣好,我怎樣能在她屍骨未寒,另外討個人呢?况且,我這樣窮,誰會肯和我捱窮,老實說,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三嬸聽了點點頭說:「你說得很對,俗語說,共富貴易,共患難難。」譚龍也說道:「對的,既然不另外討人,孩子也應該想個辦法安置。」
余廣低頭想了一會,說:「我祇有盡力扶養這個孩子,過一天,算一天。」
三嬸說:「男人養孩子究竟不方便呀。」譚龍說:「那末我有另外一個辦法了。」余廣說:「把孩子安置到嬰堂裡去好嗎?」
「不,不!」余廣堅决的道:「我一生人,祇得這一點骨肉,我不能離開他,决不能離開他!」
「這也是很有理由的。」譚龍說:「誰也不願離開自己的骨肉,可是,孩怎樣處置呢?」
余廣低頭沉思一回,說:「我希望三嬸給我一個幚忙好嗎,同時也要體諒我的環境了。」三嬸本來就是一個十分慈祥的女人,極願意對親戚朋友們幚助,也甚X街坊鄰里們好感,現在聽見余廣要她帮忙,便問道:
「你要我怎樣幚忙你,祇要我能够做得到,我極之願意的。」余廣道:「我祇求你在白天替我照顧一下孩子,到晚上就可以由我自己料理了。」三嬸道:這個我很願意,橫豎我做的是針線工夫,孩子不會阻碍了工作。而且,你的環境也太可憐了,我盡我能力帮忙你罷!」余廣感激得眼淚也流出來了,說:「三嬸,你這樣對我太好了,將來大志——我這孩子能够長大成人,也是你給我的好處!」三嬸說:「施恩莫望報,望報莫施恩,我純然同情你這樣的環境,才答應幚忙你,而且我也知道這個責任,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長年長月的,不過,你放心,我答應過你,一定爲你做到底!」余廣說:「好的,我太感激你!」譚龍說:「那麼廣哥的困難現在可以解决大半了,做工時間到了,孩子就交給三嬸,我們到工場去罷。」余廣說:「是的,三嬸,勞駕你,孩子我交給你了。」三嬸很高興地接過了余廣的孩子,然後望着余廣和譚龍兩人出門去了。
余廣回到工場以後,當然第一件事就向各工友道謝,致謝昨天帮忙自己殮葬妻子的費用。他昨晚爲了帶孩子,實在一夜沒有睡好過,精神十分頹喪。尤其是工作到中午的時候,混身酸痛得肋骨部要分散了似的,一邊打石,精神再也支持不住,抱住石鎚打起呵欠來,可是剛要睡着,忽然似乎聽見一陣孩子啼哭聲,一眼開,那裏會有孩子在身旁,不過是他心裏念念着家裏的孩子罷了。
可是究竟余廣的精神疲勞不堪,三番幾次停了手,在不知不覺中睡去。正在沉沉迷迷的當兒,忽然竹帽上拍的一聲着了一下,赫然而醒,睜眼一看,却見工頭施子久睜眉怒目的站在身前,大聲喝道:「你究竟來做工還是來睡覺!你給我滾出去!」說着就要動手来搶去余廣手裡的石鎚。余廣哀求道:「施管工,請你體諒我一次罷,我是無意的。」施子久作威作福道:「不成!在工作中睡覺,破壞工場規矩,非滾不可!」
譚龍正在另一邊打石,忽然聽見人聲嘈吵,抬頭一望,見施子久要把余廣趕走,便放下石鎚走過來向施子久問道:
「施管工,究竟什麼事要你老人家生氣?」施子久鼻子裏哼的一聲,說:「余廣這傢伙在工作中偷睡,破壞工場規矩,非要趕走不可!」譚龍陪笑道:「施管工看寬一點好嗎?余廣也不過偶然犯一次罷了。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就原諒一次好了!」施子久沒有一點動容,說:「不成,用不着你討情!」譚龍道:「施管工你管敎工友,我怎敢說情,不過——」施子久說:「不過什麼?」譚龍央求道:「請管工格外開恩,原諒一次好了。」施子久說:「就算不趕走,處罰是必要的。」譚龍道:「管工要怎樣處罰呢?施子久說:「唔——扣薪!」
原來施子久兜了多少圈子,也不過想說出這處罰方法——扣薪!因爲一個工人扣薪,也就是由他代領了,中飽私囊。工人們整天做工,也無非是爲了得到這一點的薪水,換兩餐吃不飽餓不死的粗米飯,可是偶然犯了錯,也祇好忍痛由他剝削了,他是一個狐假虎威有權管理自己的人,即便刮削自己的血汗,又有什麼辦法呢,當下譚龍和余廣兩人聽說要扣薪,也明白了施子久的來意,先藉革退來要脅,然後提出要扣薪,但自己確實錯了,也沒有辦法。只得道:「隨便管工辦好了,管州要扣多少呢?」施子久道:「就算寛辦一次,扣兩塊錢!」余廣雖然肉痛兩塊錢是自己差不多整天的工資,但也只好忍氣呑聲,不敢再說什麼話。
施子久見目的已達——錢安穏的可以到手了。却故意嚕叨兩聲,裝作敎訓的樣子道:
「下次再有這樣,一定嚴辦了,哼!小心!」說完,揮舞着手裏的竹枝,去了。
施子久走後,余廣苦口苦面的對着譚龍說,「龍哥,今天又等於白做了!」譚龍嘆一口氣。說:「有什麼辦法。快做工吧,別又要給他找麻煩了。」余廣那裏還敢怠慢,叮叮鐺鐺的拿起石鎚又打起来了。
余廣勉强提起精神,一鎚一鎚的打在石頭上,好容易才捱到放工汽笛响起來,才像囚犯徒刑期滿,被釋放出獄一樣,交還了工具,飛奔似的跑回家裏,向三嬸要回孩子,冲些牛奶給他吃。等他睡着了,才敢放下去燒飯吃。
自此以後,余廣父兼母職。每天辛勞地在石礦場捱苦工,晚間又要帶兒子,這樣辛勞清苦的工作,睡眠營養都不足,不到多時,這個偉大的父親消疲不堪了。
這樣的生活漸漸給工場裏的工友,和同街的隣們都知道了,有些不堪其苦,不堪其憂的人,先後規勸他說:廣哥,你這樣不但糟蹋了自己,而且還糟蹋了孩子呢,還是放棄你的成見,把兒子送給別人罷。」這樣的話總得到余廣永遠不變的答復,說:
「我有一雙手。我有力氣,盡我一分能力,也要扶養下一代的,我决不離開我的孩子,他雖然沒有母親,但仍然有父親,我以爲父親母親的責任都是一樣的,都要爲兒子操勢,吃苦,以求把兒子養活了,難道我父親養育我又不辛苦嗎?」
這話說得來勸他的人都無言可說,每個人,無論在明裏暗裏,都稱贊余廣是一個偉大的父親!
(三)
無情的時光匆匆地逝去,轉瞬間又是六個年頭了,在這六個年頭當中,富有的,幸福的人很容易過去,可是余廣爲了要養育他唯一的兒子——余大志,可經費盡了多少血汗,捱盡多少艱難辛苦了,幸而他一片苦心倒沒有白費?孩子在他辛辛苦苦養育下,漸漸長成了,余廣雖然捱過了六個年頭,生活並沒有變好,一樣的出賣血汗,一樣的辛勞,也是一様的在石礦場裏做石工,賺得來的是一頓僅足糊口的粗飯。
那天余廣放工以後,和譚龍兩人一起回家,因爲他們兩人的家相去不遠,都往在同一條街上,不過一個是街頭,一個是街尾罷了。
兩人一邊走一邊閒談,余廣是把整副精神放在他兒子的身上,當然談不上幾句又說到兒子身上來,說:「龍哥,我看大志也應該要入學校了。」
譚龍道:「要是有錢人家,早就送到學校裡去了,奈何我們窮呢。」余廣說:「所以我非常擔心,光是把孩子養大了,不好好地叫他受敎育是不對的,我想無論如何自己吃點苦,也要供給他讀書。」譚龍說:
「這是當然的,廣哥,自從大嫂死了以後,這六年來你也吃盡苦頭了。」余廣苦笑道:「即使再苦,我也無怨言的,養育孩子,是我應盡的責任,既然是自己的責任,怎可以不負責呢?」譚龍笑着拍拍余廣肩膊,說:
「你真是一個偉大的父親,怪不得每個認識你的人,都對你稱贊的。」
兩人談談說說間,不覺又到了街口了,余廣說:「今晚你在我家裡吃飯好嗎?」譚龍道:「好,一來我沒有見你的兒子多天了,也想見見他。」余廣說:「你對大志也很受護!這使我非常高興。」
當余廣和譚龍兩人走到余廣的家門口的時候,却見那裏一羣孩子蹲在地上攤着骰子,余廣的孩子余大志也蹲在旁邊看,那班孩子一見余廣回來,檢了骰子都走去了。余廣見了大志在玩骰子,心裏非常不高興,叫道:「大志,你過來!」大志見父親顏色不對,也吃了一驚,走過來叫聲「爸爸!」余廣問道:「爲什麼你在街邊玩骰子!」大志垂着頭不敢說一聲。余廣以敎訓的口吻道:「你總不知道你爸爸用多心血養大你,你就在街上學賭錢,你可知道,賭錢是最壞的,多少人爲了賭錢,命都送掉了,我非要給你一個敎訓不可。」說着,在地上執起一根小竹枝,就要打大志,嚇得大志呱呱哭起來。譚龍攔住說道:
「余大哥,何必動氣呢,敎訓過就算了。」余廣道:「不成,非要給他吃些苦不可!」可是竹枝給譚龍接住,說:「算了,下次再玩才打未遲。」但是余廣一定要打,正在爭持間,三嬸到了,問道:
「為什麼這様嘈吵?」
「大志越學越壞,竟然在街上賭錢!」余廣說。
「小孩子是要敎的,說起來也是我的過失,我每天顧着做工,有時會不大留意到大志,任便他到處玩,住在這裏的孩子又是壞的多,我也怕大志學壞了。」三嬸很着意地說。
三嬸這樣的話,打動了余廣的心,他覺得,他六年來辛勞養子的結果,也不過做到一個「養」字,並未做到「敎」字,所謂「養不敎,父之過!」自己有一種過失,大志在街頭學賭錢,實在是養而不敎的錯誤,這錯誤,應該由自己負起,大志是無知的,天眞的,玩,是每個兒童都愛好,怎能怪大志呢?想着,手上的竹枝不期落在地上。
這時在窗口外邊,忽然叫進來一種聲音:「廣哥!放工了嗎?」
大家轉頭一望,原來在外邊的人是這街上的崔保長,崔保長是個最熱心辦理街坊福利事業的人,一來是老街坊,二來辦街坊福利的時候,常常和各人接觸,所以在這街上,毎個坊衆都跟他很厮熟的。崔保長爲人十分和靄,愛帮助別人,附近的人對他都非常好感,非常擁戴。
當時余廣見在窗外的是崔保長,便請了他進來,倒了一杯冷茶,遞過去,說:
「茶冷了,對不起!」
崔保長笑吟吟的接過茶杯,說:「沒關係,不要客氣,今天人齊,三嬸龍哥都來了,可有什麽商量嗎?」
「剛才說起大志的事,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老在家裏玩,又沒有人看管,不到學校裏讀書,究竟不是辦法的。」
崔保長點點頭說:「你說得非常對,養孩子怎可以不敎育呢?那末你打算送他到那裏讀書?」余廣說:「現在就是有困難了。」崔保長說:「你不說明我也明白了,你的困難料也不過為了一個窮字。」余廣道:「當然是這樣啦!」崔保長道:「你幾年來的環境,不但我個人同情,就是附近的人也非常敬佩,你這樣千辛萬苦也爲了一個孩子,誰也感動的,你的困難,我會盡力帮忙你!」余廣喜道:「保長,你眞能够帮忙我嗎?」崔保長想了想,說:「大志這孩子是要讀書的,這裏街頭有一間英才中學,裏邊也附設有小學的,校長先生我和他有點交情,我可以帶你見他,或者他就會給你一次幚忙的。」余廣多時祈求的希望,到現在有了一線曙光了,非常高興的道:「如果校長先生能給我帮忙,那最好了,我們什麼時候去見他哩?」崔保長說:「現在學校已經下課,他是留在校裡的,我可以立即同你去見他。」余廣說:「好,好,我們立即去,龍哥,三嬸,你們坐一會,我同崔保長去一次,立刻回來。」三嬸說:「你去吧,我也要回家了。」譚龍也說:「我也回去了,你們可以去。」余廣說:「你說在這裏吃飯哩!」譚龍說:「那麽我就在這裡替你煮飯,你去好了,回來就有飯吃,我相信你這一次去,一定會有結果的。」余廣聽了,更加高興,便同大志略事整理一下衣服,其實他父子倆的衣服也少得可燐,談不上怎様更換,只是洗了一下臉,就同崔保長一起出門去了。
學校就距離余廣家裏不遠,崔保長帶着余廣父子兩人,走了沒有多時,已經到了校門外,這時已經是黃昏時候,學校裡早已下課了,只剩下兩三個孩子在玩耍,大志看着校裏一切設備和環境,心焉响往,羨慕非常,東望望,西望望,看個不休。
崔保長直走到傳達室裏,找到了傳達校役,說:
「請你通傳校長先生,說有姓崔的保長來拜訪。」
那校役應過了,到裏邊去了不久,就出來,對崔保長說:「校長請你進去。」
崔保長是來過的,也不用校役帶路,便自己同余廣父子倆,直到了會客廳,裏邊坐着一個三十多歲,老成持重,帶着一副玳瑁眼鏡的男子,一見了崔保長到來,很客氣的站起來和他握手,笑道:
「崔保長!久違了。」
崔保長也笑道:
「好久沒有來見你了,好嗎?」校長說:「這様刻板式的生活,永遠都是沒有什麼變化的,不過對着一班學子,也很有興趣的。」崔保長說:「司徒校長向來專心敎育,很値得人敬仰的。」司徒校長道:「還不及你從事社會工作好!」
兩人經過一番客氣後,校長請崔保長和余廣父子倆坐下,由校役奉過清茶,崔保長替他們介紹道:「這位是司徒賢校長,這位是余廣先生,那是他的孩子。」司徒校長是個非常謙虛有禮的人,並不以余廣衣服襤褸而稍存輕視。一樣很恭敬的和余廣握了握手,說:「余先生,希望有時候常常來指敎!」余廣當然也謙虛幾句。崔保長說:「我們大家不要說客氣話,現在我是有一件事來麻煩校長的。」校長說:「有什麼指敎呢。」崔保長說:「這位余先生是個十分偉大的父親,六年前自從妻子去世以後,靠自己勞力,千辛萬苦的養大了這個唯一的兒子,可是孩子大了,總是應該受敎育的。」校長說:「這是當然的。」崔保長說:「可是余兄的收入極微,再要負担孩子的敎育費,實在是極困難了,所以特來請校長帮忙他,不知校長的意思怎樣呢?」接着,把余廣如何艱辛育子的身世,一一說岀來。司徒校長聽過了,非常感動,說:
「好的,我很高興幚忙余先生,我向辦事的人說過,就在明天帶他來上學好了。」余廣聽了,非常高興,便把大志的姓名,年齡,藉貫等等,寫下來交給校長,然後告辭回家,對譚龍說X,譚龍也非常喜歡,在吃飯的時候,余廣諄諄向大志敎訓道:
「大志,以後你就有書讀了,你應該努力讀書,不可花了大家對我們帮忙的好意,我每天上工的時候帶你上學,放工的時候就帶你回來,中午吃飯我交帶三嬸招呼你。」大志都應了,到吃過飯以後,譚龍也回家去了,余廣替大志洗過澡後,帶他上床睡覺,自己也覺得十分疲倦,亦上床睡覺了,余廣這天晚上覺得六年來。最高興可說是今天了,幾乎使他忘記了一天辛勞的疲乏,他靜靜看看睡着的孩子,微微笑了一笑,幻想着將來大志能够由小學,中學,大學這樣讀上去,養成一個好人材,在社會上做點光榮的事出來,這樣,自己才能盡了最大的責任!
(四)
不知是爲了興奮還是爲什麼,第二天余廣起床特別早,天色還是魚肚白,起來後匆匆洗過瞼,就叫大志起來,大志睜開小眼,就叫:「爸爸,上學嗎?」余廣説:「是呀,快點起來吧!」
等到大志洗瞼換過衫後,余廣就送他的兒子到了英才學校,怎知他們來得太早了,學校裡還靜悄悄的,一個人都沒有,父子兩人在校門外等了好久,才見一個校役睡眼惺忪的走出來開門,余廣上前問道:
「校長先生起來了嗎?」那校役問余廣道:「你那末早找校長幹什麼?」余廣道:「他叫我今早來的,我帶孩子來上課。」校役說:「好的,你等一等。」校役說完,進去了。
一回,校役從裏邊出來,對余廣說:校長請你進去。」余廣聽了,便帶着大志進去,司徒校長早在大門口笑吟吟的迎着,見了余廣,說:「余先生,早呀!」余廣也說:「校長,早晨!大志,你叫校長。」大志依着余廣的話,叫了一聲校長。司徒校長慈愛地撫着大志的頭,說:「帶他來上課嗎,他入學的手續我已經跟他辦妥了,他同我進來。」
校長帶着余廣父子倆進去,找着一位姓陳的級主任,對他說明後,便對余廣說:「你可以去做工了,大志可以叫他上課。」余廣再三道謝,留下了大志上課,然後告辭了校長回到工場去。
余廣爲了孩子可以進學校讀書,心情愉快,工作也特別起勁。同時高高興興的告訴他的患難朋友譚龍道:「龍哥,大志今天上學了,我希望他以後能够好好地讀書,我必定盡了我的力量,由小學,中學,到大學,供他讀完了,等他好好地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
譚龍聽見也很喜歡,說:「廣哥,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你的志願一定可以達到的。
兩人一邊工作,一邊談論大志將來的前途,興高采烈,余廣似乎要把他一生的希望,完全付託在一個孩子身上。
直到了石礦工場放工的時候,余廣趕到學校裏領着孩子放學,習以爲常,從此余廣一面慶幸孩子有了受敎育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放心他不會被街上的壞孩子引誘了。
大志在學校裏唸書,也非常勤力,天天晚上放學回家,都孜孜不倦的拿着畫本讀,余廣本來也是個智識份子,看見大志唸錯了的時候,常常着實改正他的錯誤,听以大志在校裏的成積相當好,連司徒校長也很高興了。
一天,余廣和譚龍從工場裡放工出來,又到學校門口去接大志,到了校門的時候,見裡邊還未下課,便在附近等了好一會,過了些時,校裏下課的鐘聲「鐺鐺鐺!」的響起來,余廣說:「下課了,大志也快出來啦。」果然不久便見許多學生從裏邊走出來,忽然見後邊一羣孩子,追着大志在嘲笑他,因為隔得遠,沒有辦法聽見他們說些什麼,大志給人家嘲笑,面紅耳赤的哭起來,他越哭那班學生笑得更利害,在大志身邊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似乎在維護着大志,一邊趕走那些同學,一邊安慰着大志,余廣看了這情形,見自己的孩子吃虧,心裡有點不舒服,立刻走過去,拖住大志的手問道:「大志,你哭什麽?」那班學生見余廣走來,都一哄而散了,祇剩下那兩個男女孩子。
大志見了余廣到來,哭得更利害,余廣和譚龍追問他,他老是不出聲,余廣見旁邊兩個孩子不走,便向那個男孩問道:「大志爲什麽哭了?」那個男孩道:「人家笑他穿破衣服,他就哭起來了。」那個女孩子也說:「那些人沒有理由的,難道破衣服不能讀書嗎?那些穿好衣服的人,讀書還不及大志用功呢。」這時余廣才恍然大悟,說:「大志,沒關係的,你跟我回去吧。」又見那兩個孩子長得端正,似乎跟大志很要好的,便問道:「你叫做什麼名字?孩子。」那個男孩道:「我叫喬良。」又指着那個女孩說:「她是我的妹妹。」那女孩說:「我叫做喬青呢。」余廣點點頭說:「哦,你們是兩兄妹。好的,我帶大志回去了。你們也回家嗎?」喬良說:「我們也回去了,便說了一聲:「再見!」很天眞的走去了。
那兩個姓喬的孩子走了以後,余廣望望譚龍說:「事情很難說,穿件不好的衣服就受人欺侮,怪不得世界上的人都注重外表,愛儀式,重裝扮,原來從小養成的呢。」譚龍說:「這是普遍的事,好罷,我們回去吧!」
於是余廣帶着孩子,和他的老朋友譚龍,一行三人,轉身回家去,到了街口,譚龍分途而去了。
余廣兩父子回到家裡,在吃飯的時候,大志對余廣說:「爸爸,我……。」
「你什瘀?大志」余廣說。
「我不再到學校裏讀書了,爸爸!」大志說。
「爲什麼你不讀書呢?」余廣以這樣辛苦養大了孩子,做夢一樣能夠看到了他到學校讀書,並且是一間設備完善,具有名聲的學校,將來就可以在這學校裡。由小學升到中學。爲什麽大志忽然間會說不再讀書呢?使他無限驚異。他睜大眼睛等候大志答復。
大志似乎很難爲情的說:「同學們都耍笑我穿破衣服!」
余廣聽了才明白,說:「大志,你家裡是窮,穿破衣服是應份的,有什麽奇怪,祇要我們做人正正大大,你在學校裡的成績,好過別人,就比穿好衣服好得多了,知道嗎?」大志含着眼淚點點頭說:「爸,我知道了。」
余廣眼見他的兒子受了委屈,再望望他的衣,果然是千縫百補。心中也過意不去、便安慰着大志說:「大志,你別難過了,吃飯罷,吃過飯後,我替你想辦法!」大志X了,也就揩乾眼淚,靜靜地吃飯了。
父子兩人吃過了這頓粗米飯以後,余廣收拾了碗筷,走到隔壁,找到三嬸過來,把事情告訴三嬸,三嬸想了一想,說:
「廣哥,你有什麼衣服嗎?拿一件出來,改給你兒子穿。」
余廣聽了,立即在包袱裡,找了一件比較好的衣服來,交給三嬸,由三嬸動了一回刀尺,細針密密縫,果然不到半夜,把一件衣服改起了,余廣見了很高興,向三嬸道謝過,三嬸也回家去了。余廣拿着這件衣服,望望熟睡在床上的大志,心底裡禁不住發出一陣安慰的微笑。
大志這樣在學校裡讀書,一年一年的過去,由英才小學升到英才中學,轉瞥十多年間,高中畢業又要來臨了。余廣在這十幾年內,無論怎様辛苦,也是覺得愉快的,雖然每天他是這樣出賣勞動力——血與汗,他認為沒有一點辛苦,他認爲已經盡了做父親的義務了,他驕傲地覺得,他不但已養大了一個兒子,而且敎育了一個兒子。
固然,以余廣這様的生活,這样的條件,本來是沒有可能供給一個兒子讀中學——尤其是一間近於貴族化的中學的。這不過固然大志在學校裏的成績相當好,而司徒校長也覺得余廣的環境,極為値得同情的,所以一直都豁免大志在學校裡的學雜費,以使余廣的負擔盡量減輕,完成他敎子育子的志願。
這是高中畢業考試的前幾天,司徒校長很誠懇的對這一班學生說:
「各位同學,我來上你們這一課,可說是最後一課了,過幾天,你們考畢業試,考試完後假如能合格的人,就可以畢業,從比,又完成一個學歷的階段了,所以我希望每個同學都要努力,都能得到畢業的機會,不要浪費了幾年來寶貴的時光。」
說完,下課鐘响,到同學們都散到外邊以後,校長見余大志還沒有出去,便走前來說:「大志,你還在溫習嗎?」大志站起來說:「是的,因爲有些功課我不大放心,所以再多看一下。」司徒校長點點頭,說:「很好,你到我們學校讀書以來,每個敎師對你印象都很好,成績也不錯,不枉你父親辛苦栽培你一場。」大志說:「也是校長對我特別帮忙,不然也難以有讀書的機會的。」校長說:「還是你自己肯努力,否則誰願栽培一個不爭氣的人呢?大志,畢業以後你打算再讀大學不呢?」大志沉鬱的搖搖頭。校長說:「什麼?你不打算讀大學嗎?」大志帶有點痛苦說:「我家裏這様窮,怎樣有能力讀大學呢?當然,我X很希望能够讀上去的,實在一個中學畢業的人,能夠做得什麼呢?」司徒校長說:「這點你不必愁,我曾經替你想過,或者可以保送你讀免費學額。」大志聽了,很高興說:「假如能够,我太感謝校長了。」司徒校長說:「這點你不必客氣我多年從事敎育,也是以作育人材,百年樹人爲宗旨,我能够做得到的事,都應該帮忙你,不過也看你的努力如何,是否能够考得上呢。好罷,你看書好了。」說定,司徒校長轉身去了。
在司徒校長心裏也很高興,十多年來自己栽培的一個學生,果然不負自己所望,成為學校裏第一個高材生,也許將來在社會能够做出一番事業,這様,爲人師者,也不無安慰的。一邊想着,微微含笑的出了課室,怎知轉角的地方一個學生叫叫跳跳的走來,跟司徒校長撞個滿懷,幾乎把司徒校長撞倒了,司徒校長站定脚,抬頭一望,原來是鄭秋明——這個在學校裏有名跳皮,曾經記了兩個大過,兩個小過,幾乎要被學校革除的。
「秋明!你看你一點正經都沒有,冒冒失失的幹什麼。」司徒校長向鄭秋明責備說。
秋明知道自己做錯了,一聲不敢响,聳聳肩膊,伸伸舌頭,垂手站住了。
好在司徒校長是個仁慈寬大的師長,也並不以為甚,只薄責秋明兩句,說:「去吧!下次小心了,碰倒誰也是不好的!」秋明呑一口涎沫,應個「是」字,轉身走去,一直走進課室裡。
大志正在看書,準備考試,耳邊聽見脚步聲,抬頭看見鄭秋明躡手躡脚走進來,說:「秋明,鬼鬼祟祟的作什麼怪!」秋明笑了一下說:「危險得很——」大志說:「什麼事這様危險?」秋明縮一縮頸子,說:「剛才在外邊跟校長一撞,蓬!的一聲,幾乎把他撞倒呢,你說危險不危險?」大志說:「又給校長駡了一頓,是嗎?」秋明點點頭說:「還用說嗎?」大志說:「活該!走路一點不小心,老是叫叫跳跳的,不駡你還罵誰?」秋明說:「不說這個了,打球嗎?」大志搖搖頭說:「這個時候還要玩嗎?考試的時候快到了,快看看書罷!」秋明笑道:「考試也要看書嗎?管他的,到時候自然有辦法!」秋明說着,驕傲和有恃無恐的神色,揚溢在瞼上,似乎他應付考試十分有辦法似的。
「你別亂吹牛,秋明,到現在你也不看書,還說要打球,對付考試你有什麼辦法?」大志說。
秋明神秘的一笑道:「哼!先把重要的書本抄好,到時拿出來一抄了之,X其「了哥」,這不是好辦法嗎?」大志是個專心求學的人,絕不贊成秋明這様作僞的行動,搖頭道:「我不能學你這様做法,我也勸你別這樣做!」秋明反對說:「難道自在不好,要辛苦才舒服嗎?你這様死讀書,簡直是蠢人!」大志說:「我不跟你作辯了,總是我要讀我的書,求學時候當然要埋頭向學的!」秋明說:「你不去玩算了,我也怕聽你一套偉大讀書的理論!」他說着,又奔出去了。大志望着他的背影,搖頭嘆息,心裏暗道:「父親有點錢供你讀書,你却這様花去,有什麽意思呢?」想着,不禁欷噓。
一回,窗外有人向大志叫道:「大志哥,這樣勤力呀,讀熟了書沒有?」大志抬頭向外一望,原來是喬良喬青兄妹兩人,大志喊道:「你們進來。」喬良和喬青兩人,應着走進來了。
喬青和喬良兄妹倆走進來,喬青說:
「大志哥,功課全預備好了沒有?」
「還有一部份未完全妥當。」大志說:「你們呢?」
「未有呢,」喬青說:「還有許多功課要預備的。」
「快要考畢業試了,功課也應該早點預備。」大志說。
喬青似乎想起了一件事,向大志問道:「大志哥,你今晚有空嗎?」大志問:「有什麽事嗎?」喬青說「我想……」她說出「我想……」兩個字,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大志說:「你想什麽?說呀!喬良接着口說:「妹妹,你怕什麼呢?又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喬青說:「我怕大志哥不答應我!」大志說:「你們兄妹倆好像猜啞謎一樣,要我答應你做什麼?」喬良說:「等我說出來好了,我們想叫你今晚到家裏指導我們一點功課。」大志說:「哦,我以為什麼事!原來是這樣,說指導我可不敢當,要是大家硏究,臨時都是可以的。」喬青聽了很高興道:「那麽大志哥算是答應了?」大志說:「這是沒有關係的,只要你歡喜!」喬良說:「現在沒有課了,就到我家去好嗎?」大志說應:「好的,等我回家去告訴了父親以後,再一起去好嗎?」喬青說:「很好,我們也到大志哥家裏見見老伯,然後到我們家裏,大志哥在我們家裏吃晚飯好了,大志說:「吃晚飯太打攪了吧?」喬良說:「千萬別客氣!就當自己家一樣。」
於是大家檢好了書籍,出了校門,喬良喬青是個富家兒女,有汽車接送上學放學的,他們三人就坐上了汽車,先回到大志家裏。那時大志的父親余廣早已放工了,在家裏休息。大志帶着喬良喬青兩人進門以後,大志首先叫了一聲:「爸爸!」喬良喬青兄妹兩人也叫了一聲:「伯伯!」余廣说:「大志,你回來了嗎?這兩位是誰?」余大志說:「爸爸,你不認得他們嗎!你是見過的。」原來余廣在喬青兄妹兩人還是孩子的時候,曾經見過。時間過得久了,他們兩人也長大多了,尤其是喬青,長得亭亭玉立,玉琢粉雕,還怎會認得,余廣端詳了一會,說:「記不清楚了。是誰?」大志笑道:「是喬良喬青兩兄妹呀!」余廣哦的一聲,說:「怪不得這様面善呢。請坐請坐,你們兩位吃飯了沒有,就在這裡吃晚飯好嗎,恐怕沒有餸菜招待你們呢。」
喬青喬良兄妹兩人雖然是富家的兒女,可是沒有半點富家兒女驕奢的氣習,對余大志的家庭,不但不嫌他們寒微,反而覺得余廣這位老人家和藹可親,大志勤奮有爲,倒是一對好父子。聽見余廣留他們吃飯,謙遜道:「別客氣了,我們今晚還請大志哥到我們家裏吃晚飯,同時指導我們溫習功課。」大志說:「爸爸,我到他們家裏溫習功課,預備畢業試,好嗎?」余廣說:「好是好的,不過打攪你們府上了。」喬良說:「老伯,你別要客氣,你老人家肯答應給大志哥去,那末現在就去了。」余廣說:「好的,你們去吧。」
喬良和喬青向余廣說過「再見」以後,便同大志出門去了。余廣見自己的兒子,認識的朋友,謙虛而有禮,心裏也很高興。
大志和喬良喬青兄妹兩人告別了余廣,出下街口,到了馬路上,還是坐着原來的汽車,直到喬青他們的家裏去。
喬青他們的家,是位置在市裡高貴的住宅區裡,在這地方,完全是有錢人的住宅,每家房子都建築得美輪美奐。喬青的父親叫喬林,是一家農業機械公司的總經理,雖然是營商致富,可是爲人非常謙虛有禮,沒有什麽階級XX,並且對於貧窮的人非常同情,也是市裏一個有名的慈善家。
當汽車到了喬家門口的時候,三人下了汽車,喬良走前去按按電鈴,不久就有工人來開門,三人進去了,直到大廳裏面,大志一看,這裏裝飾得十分講究,無論一桌一几,一簾一幔,都精美絕俗,大志雖然是個窮家子弟,可是行動舉止却十分大方,沒有半點怯志。
當時在大廳裏,有個四五十歲模様的男子,坐在沙發上看報紙,喬良和喬青走前去,叫聲:「爸爸!」大志知道這人就是他們的父親,也走前去叫聲:「伯伯!」
喬林放下了報紙,說:「你們回來了嗎?」喬良說:「是的!」喬林看着大志,見這個青年眉清目秀,器宇軒昂,雖然衣飾樸素,也掩不住他爽颯英姿,問道:「這位是——」喬青連忙替他們介紹,說:「這位是余大志同學,這位是我的父親。爸,余同學在我們學校裡是唯一的高材生呢,我們的功課,也常常得余同學指導的。」
喬林聽見,非常高興地說:「很好,很好,大志——你是我的世姪,我也不客氣地叫你的名字了,你有時候常常到這裏來坐,不知怎様,我一見了你就對你非常喜歡,以你這様又英俊,又好學的青年人,前途是未可限量的。」大志謙虛地說:「世伯,你太過獎了。」喬林說:「我從來不說客氣話,你對我的兒女,也應該看作弟妹一様,對他們的功課也好,行動也好,多多加以管束,一點不要客氣。」大志說:「我們常常是對學问上互相硏究的。」
大志雖然是第一次見喬林,可是由於說話得體,態度謙虛,而又有好禮貌,給予喬林一個極好的印象,非常高興的和大志談了許多話,同時又問起大志的家世,大志毫不隱諱的將家裏的景况,一一說出來,喬林聽完了,寄予很大的同情,安慰着大志說:「古語說得好,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古往今來做大事業的人,許多是出自寒門的,像你這樣的人材,將來一定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希望你自愛,珍惜自己,努力一點吧!」
大志接受了喬林的勉勵,非常興奮,也非常感激,說道:「世伯金石良言,我一定記住的。」喬青和喬良兩人,見自己的父親和大志兩人,雖是第一次見面,却談得投機,所謂交淺言深,心裏也很安慰。
他們談過了一會,工人出來說開飯,喬林很客氣的讓大志到飯廳去吃飯,飯後,他們同學三人,就在書房裏溫習一回功課,大志指導了喬青和喬良許多不明白的功課,喬林在旁邊看見大志對書本上的一切,做得非常深造,對大志的印象更加好了。
這樣直到九點多鐘,大志見時間不早,要回家去了,喬林叫入預備汽車,送大志回去,大志說:「不用汽車了,走路也很容易到的。」喬林道:「開車回去也很方便的,就坐汽車回去罷。」大志見喬林一片誠意,也不好過份推却,便答應下來了。喬青要同着大志一起走,送大志回去,大志推辭不來,祇得任她去了。
汽車把大志送到街口,喬青和大志一同下了汽車,大志說:「到我家裏坐一會嗎?」喬青說:「不去了,時候不早了。」大志見喬青不肯去,X無爲勉强她,說:「那末再見!」喬青想起一件事,向大志問道:「大志哥,你打算升大學嗎?」大志嘆了一口氣,似乎有無限心事說:「大學是希望升的,不過,不知道環境是否許可呢。」喬青聽見大志這樣說,也有點黯然,只有向大志安慰道:「環境不能阻止志向的,你想想辦法吧!」大志說「校長答應過保送我去考免費學額,不知道能不能够考取呢?」喬青說:「以你這樣好的學問,考取是意中事的,努力一點吧!」大志說:「謝謝你,好,再見了。」喬青見大家站在街上,不能再多說話的,也祇有說聲,再見,望住大志回家去了。可是在她心裡却想,以大志這様好的人材,却生長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裏。受了多少磨折與苦難,太可惜了。
喬青直望到大志的背影在小街中消失了,才乘車回去,在她的心裡,對大志愛才心理,悠然而生了。
(五)
大志別過喬青,回到自己的家門口,舉手敲門。裡邊余廣應道:「誰呀?」大志答道:「爸爸,是我!」余廣認出是大志的聲音,便把門開了。大志進去,叫聲:「爸爸。」余廣說:回來了嗎?你一個人回來的?大志說:「喬青用汽車送我回來的。」余廣說:「我看你姓喬的兩位同學,雖然是富家子女,可是卻沒有驕奢習慣,謙和有禮,這樣的朋友很値得認識的。」大志說:「是的,他們兄妹兩人,從小就和我做同學,兩個都非常好的。」
余廣父子談了幾句話以後,各自回床睡覺了,大志在床上一時睡不着,想起今天喬青的父親喬林對自己勉厲的話,語重心長,非常安慰,更想起喬林喬青倆對自己深厚的友情,也值得告慰的,自己只有在學問上加倍努力,才不致失了友人們的厚望,這様想了一回,漸漸地睡着了。
再禍了幾天,考過畢業試以後,大志中學求學的階段又結束了,這天是行畢業禮,在典禮散會以後,大志手持着剛才頒發了的畢業文憑,喜氣洋洋的走到校園去,迎面看見喬青和喬良都來了,大家便在校園的石凳上坐下來,喬青說:「大志哥,我們辛苦幾年總算有結果了。」喬良也說:「大志哥,你這張畢業文憑拿利家裡給老伯看,一定非常歡喜了。」大志說:「這個當然的,就算你父親也是一様,那個父親都總希望他的子女們學業成功的呢。」喬青說:「大志哥的話說得很X!」
正在他們說話間,鄭秋明也拿着畢業文憑走過來,笑嘻的說:「我今天得到了一張支票!」大志說:「什麼支票?」秋明把自己的文憑揚了一揚,說:「這不是支票嗎?」喬良說:「畢業文憑怎様會是支票呢?」秋明說:「我拿這畢業文憑回去見我父親,他一定很高興,這様就會給我許多錢了,這様畢業文憑不就是支票了嗎?」大志才恍然大悟道:「哦!原來這樣呢。」秋明繼續興高彩烈的說道:「這個星期,又不要上課,錢到手了,還不玩個痛快嗎?」喬青露出一種輕視的樣子說:「你就是懂得玩!」秋明說:「那麽你們不是在這裡商量怎樣去玩是商量什麽?」大志說:「誰像你這樣快活,我們商量升學的問題!」秋明笑道:「升學何必要商屋,有錢你愁沒X讀書嗎?」大志和喬青兄妹三人,見再說也和秋明說不來的,祇好不說了。
大志拿了他的畢業文憑回家去以後,等到他的父親余廣回來,就把文憑交給他看,余廣拿起文憑來看,頓時想起自從亡妻死了以後,從手抱嬰孩把大志養大,現在又完成了一個階段的學業了,這様艱辛的十多年生活,就捱X這個結果,所謂似喜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