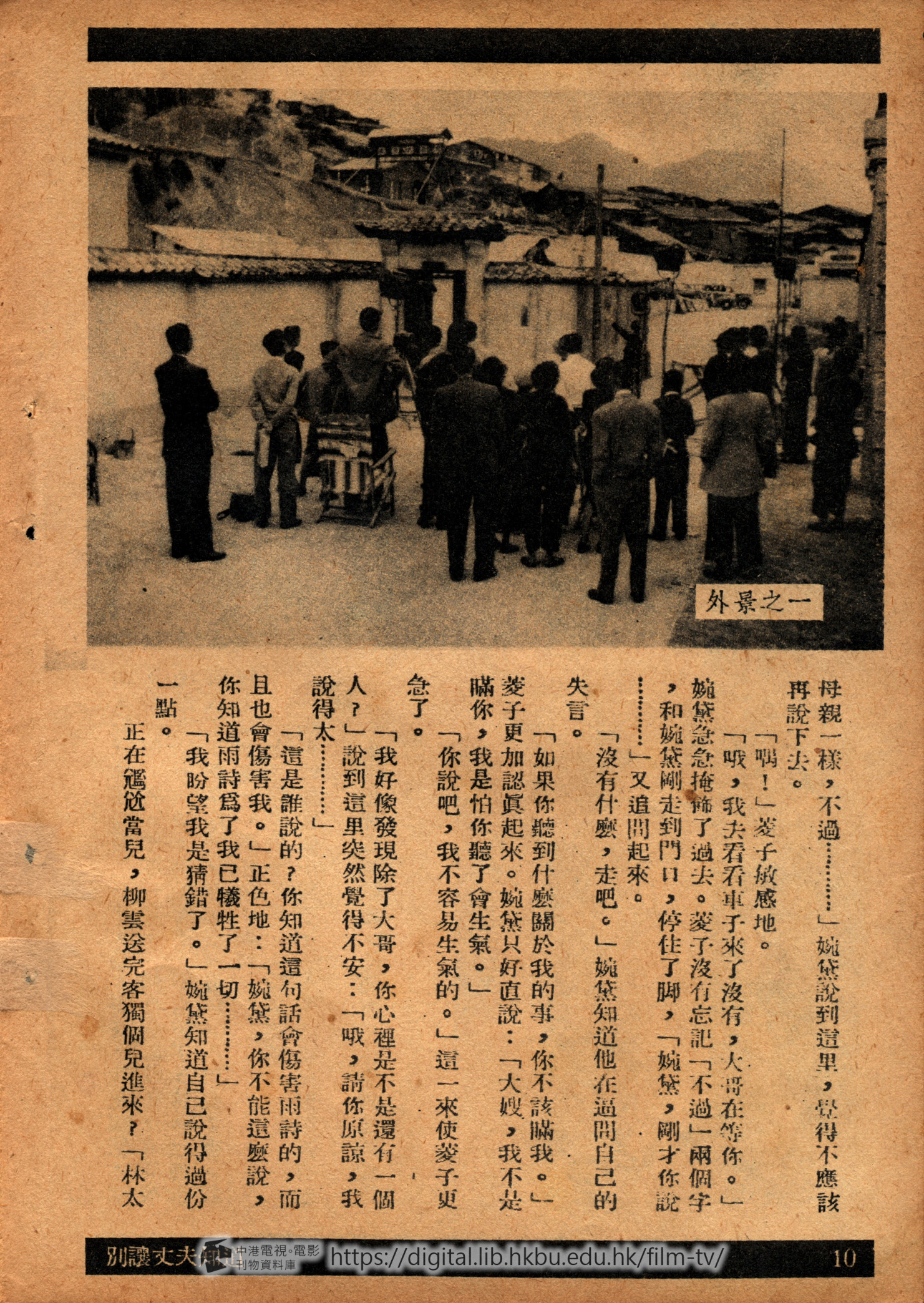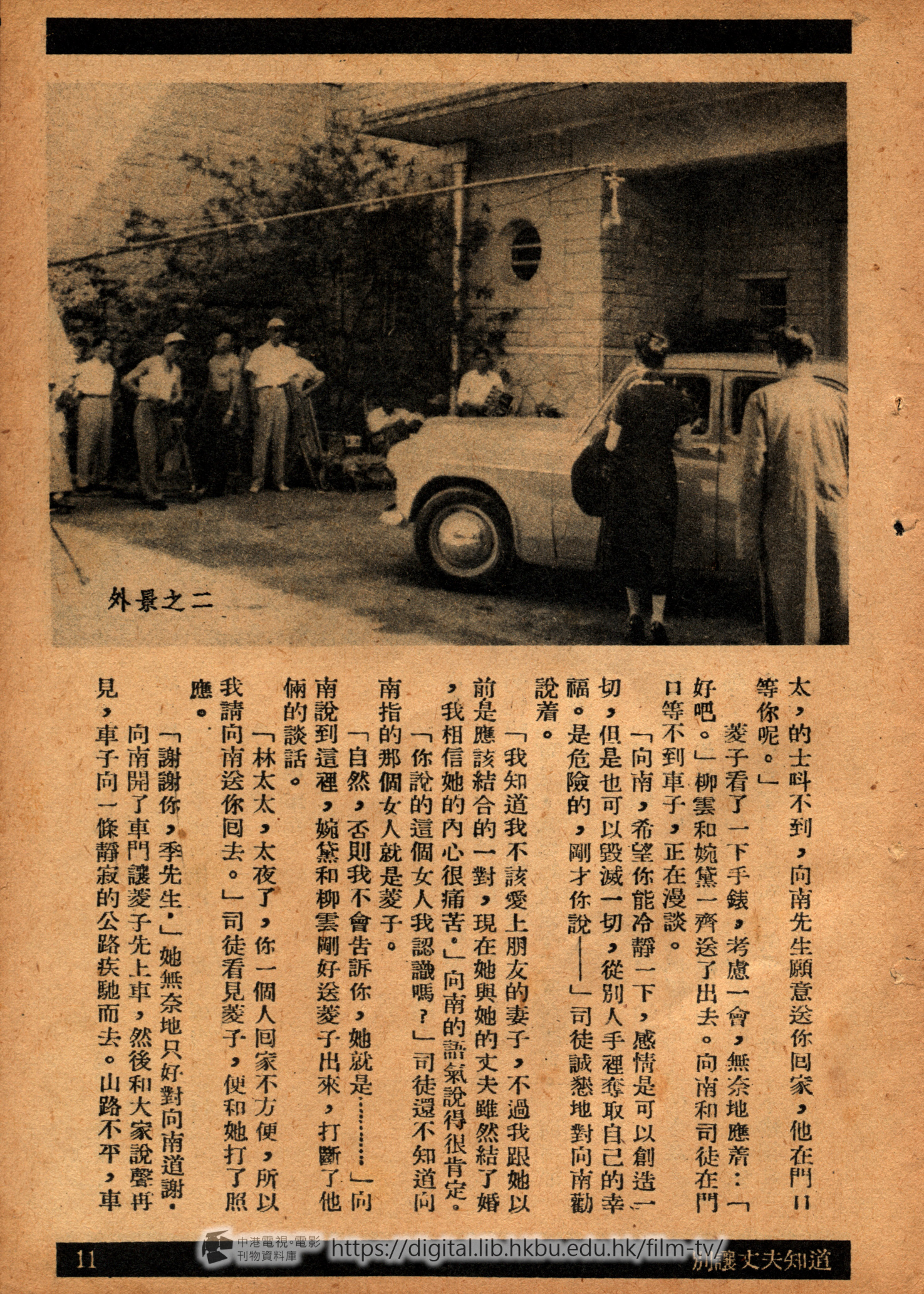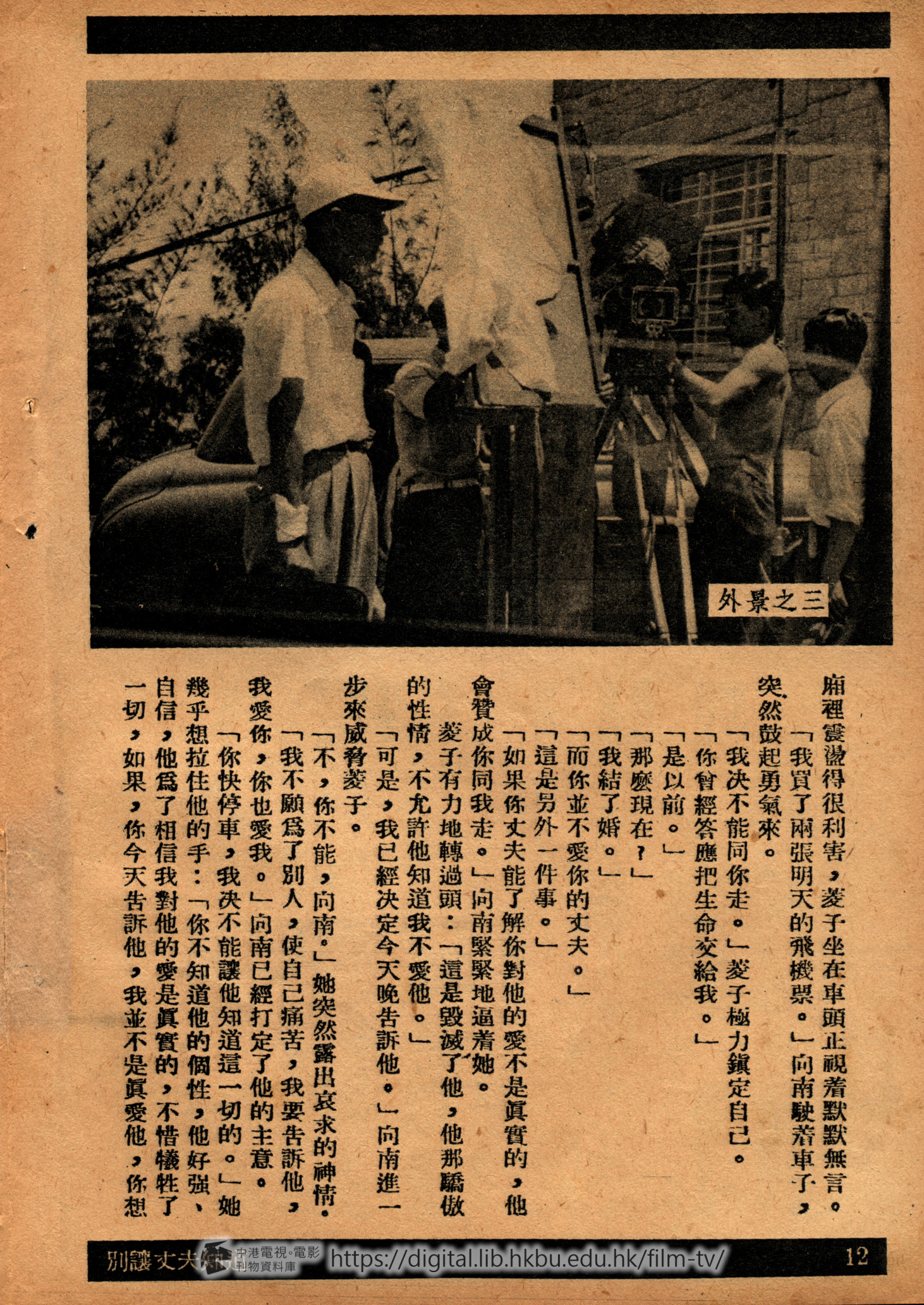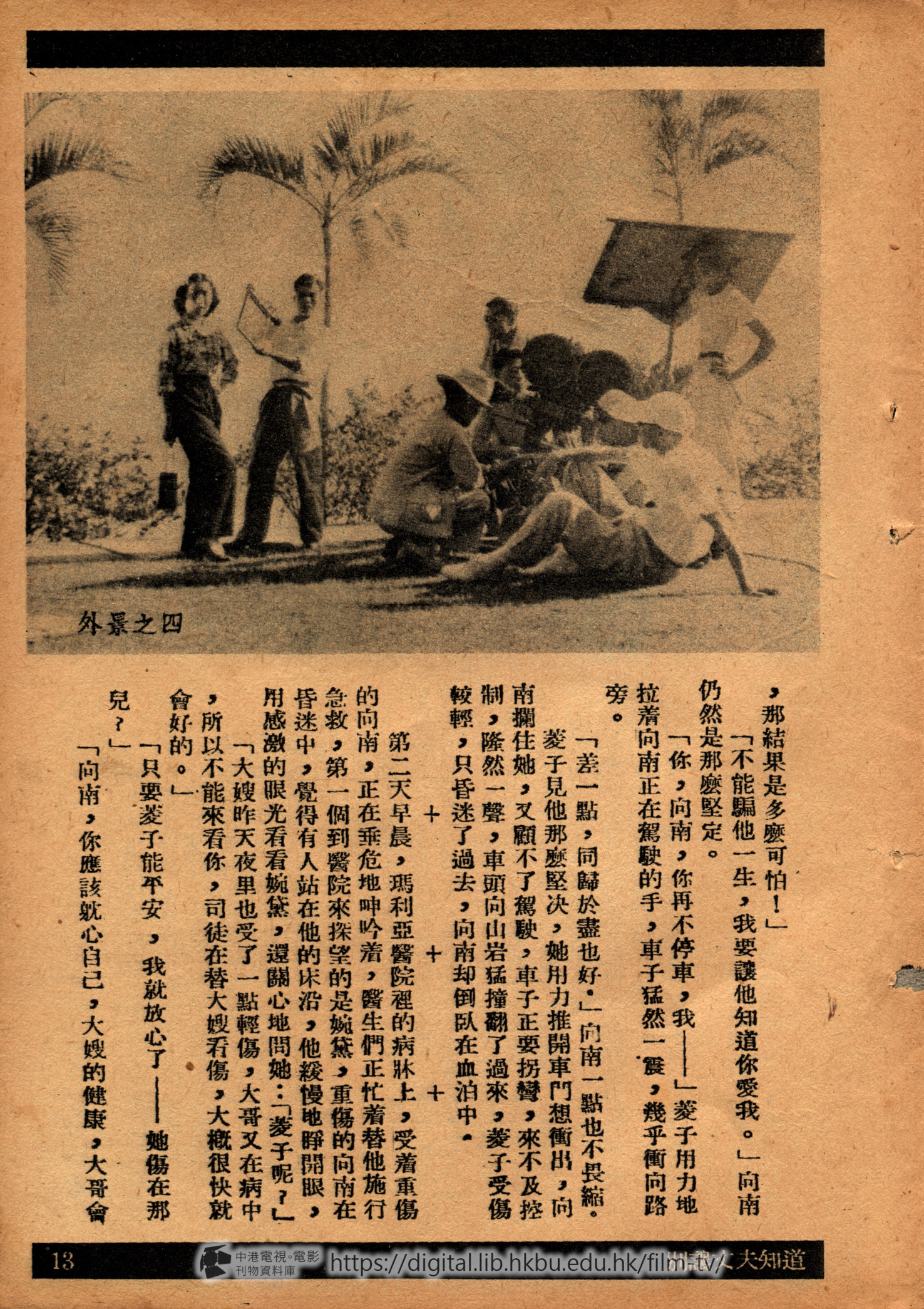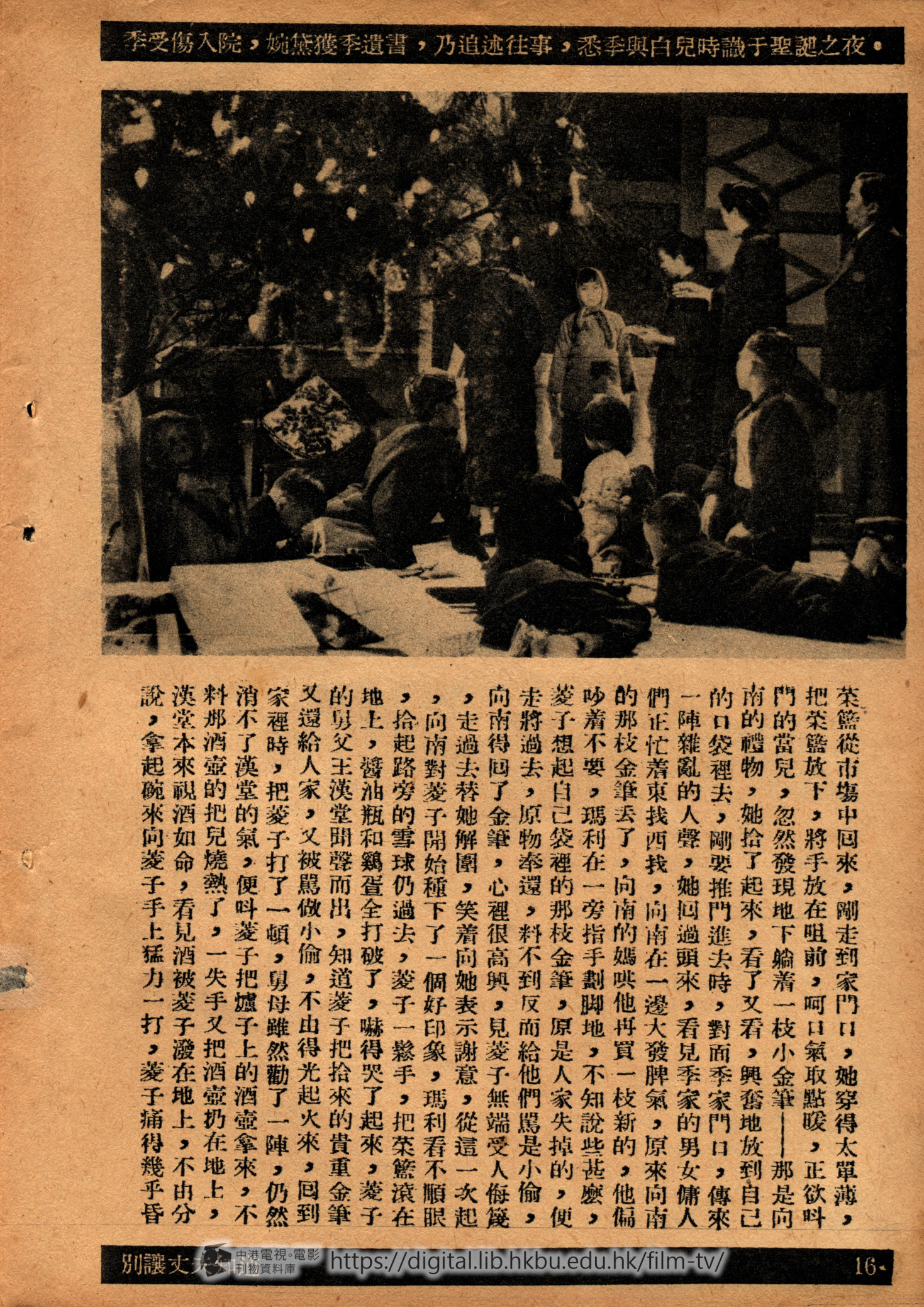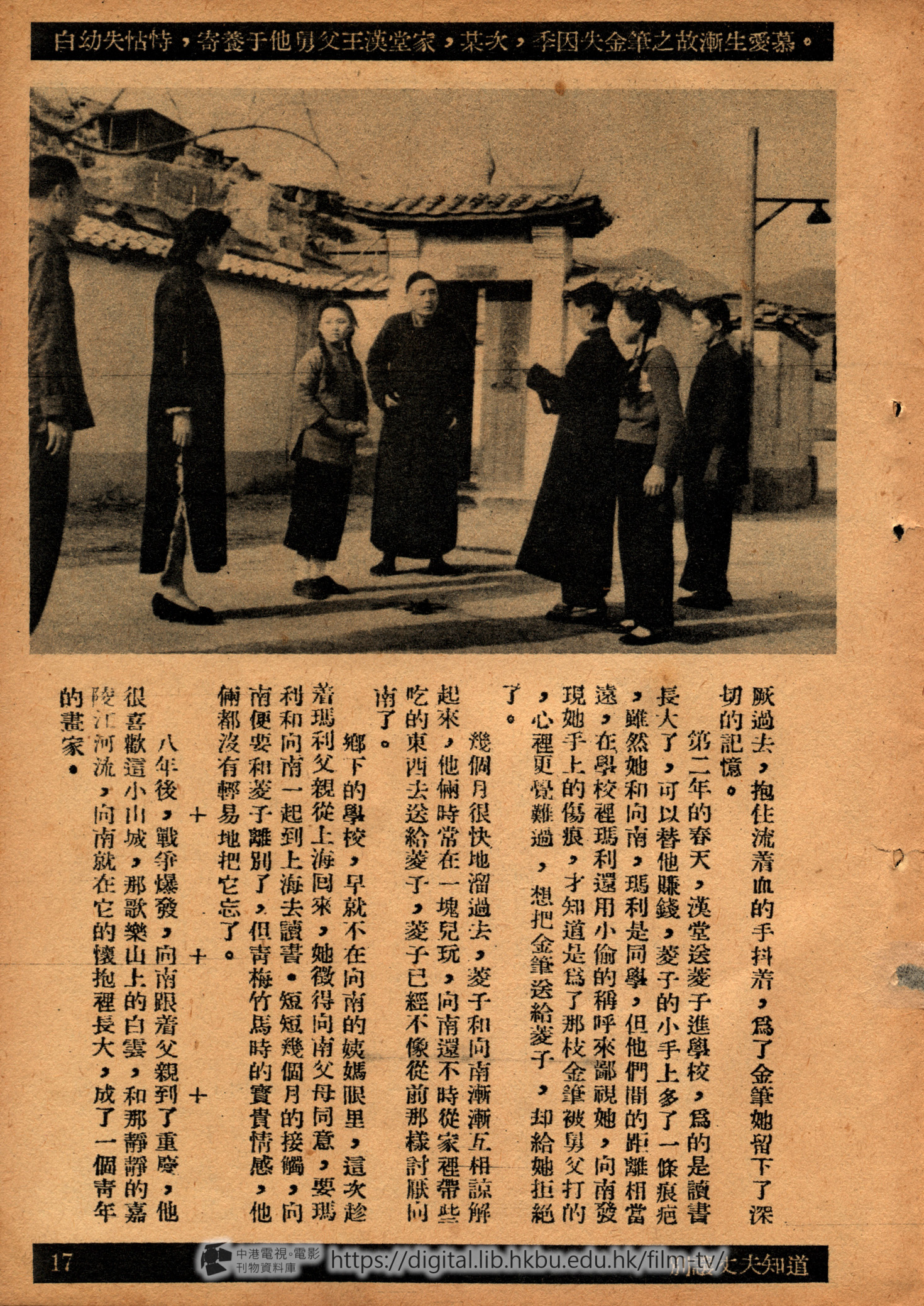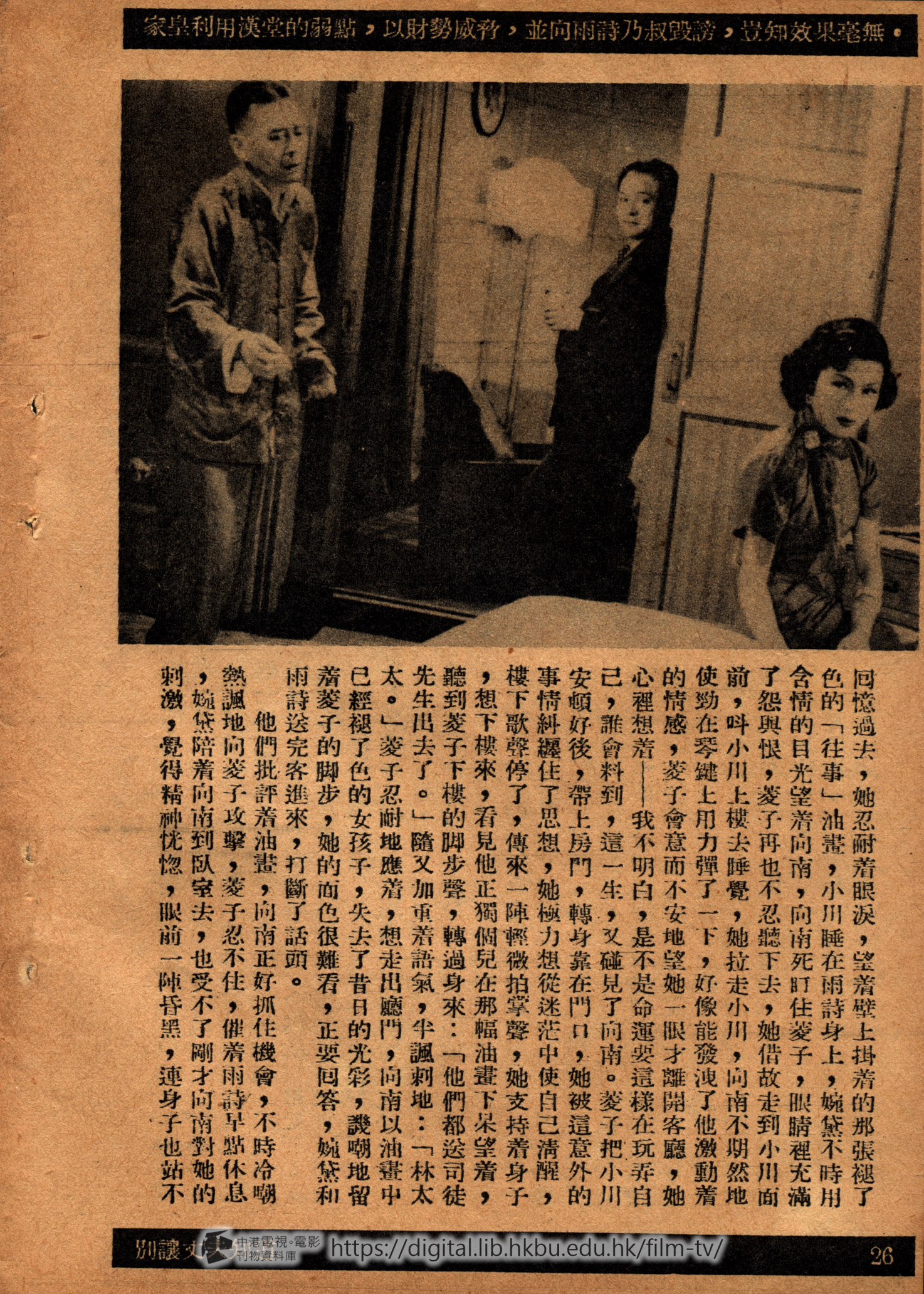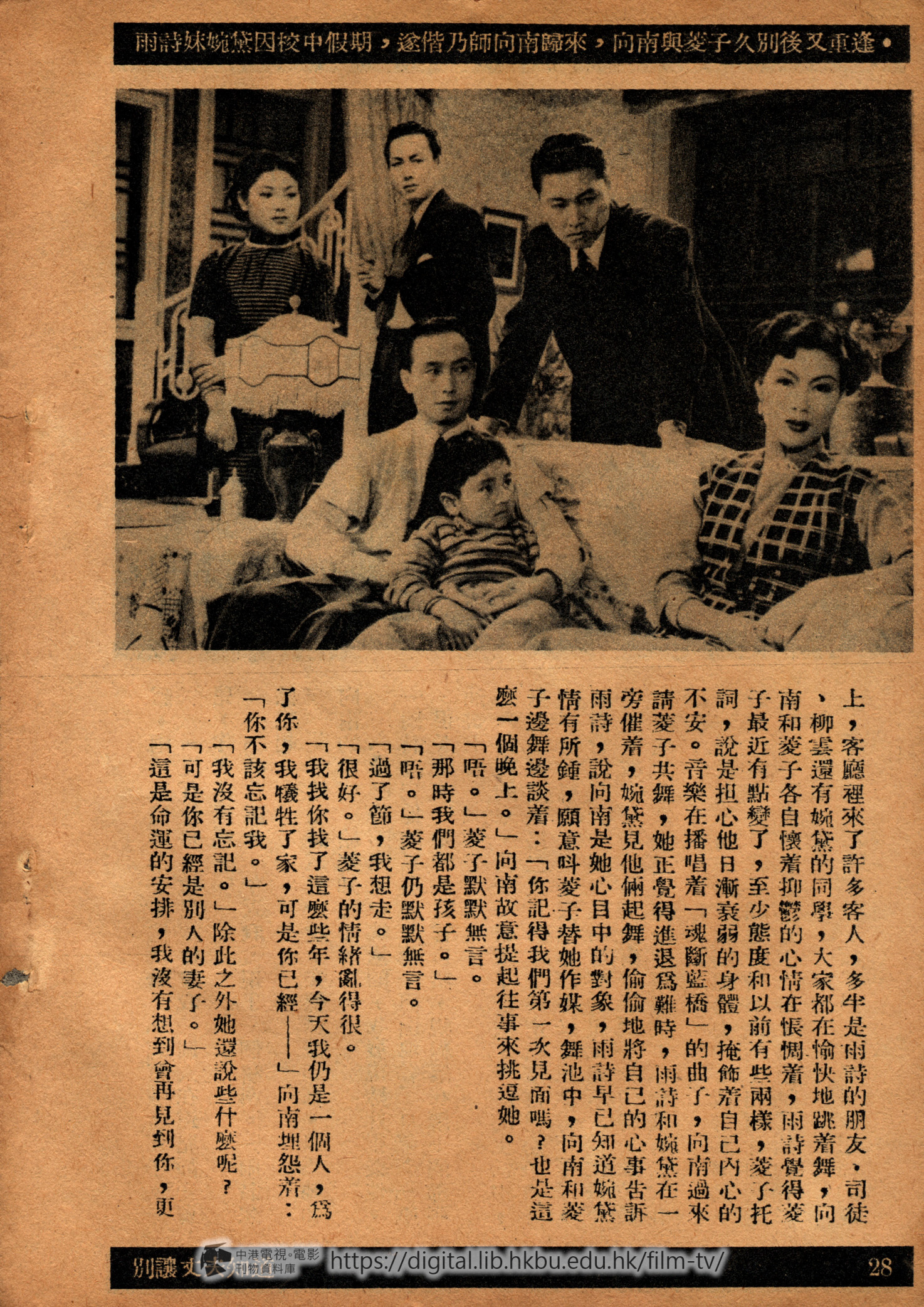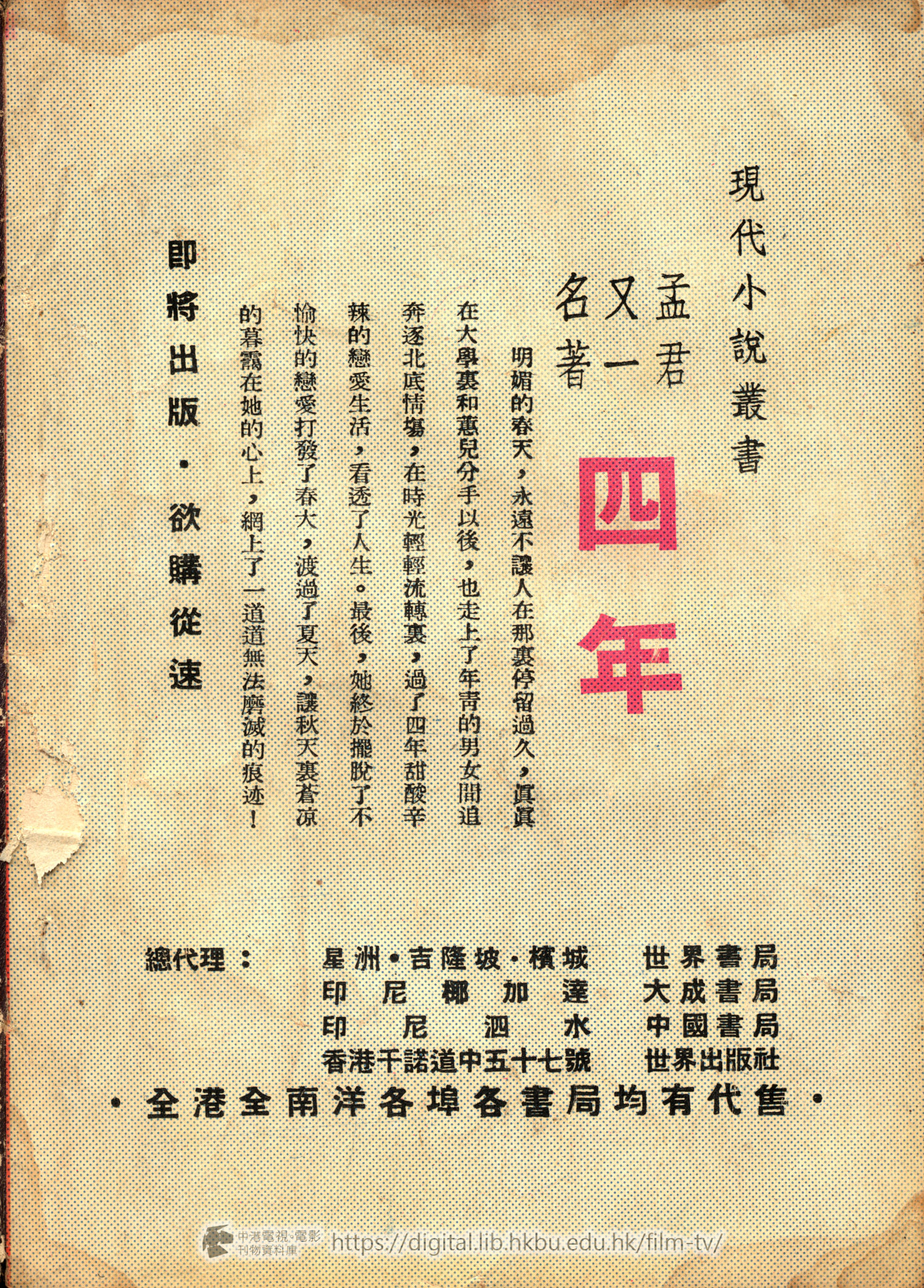歐陽莎菲的日常生活
有當東方美的歐陽莎菲,也有着如中國舊詩一般的日常生活和純粹國畫一樣的談吐舉止,換句話說,歐陽莎菲的待人接物,是那末的嫻雅,那末的和諧。
她現在的寓所,是靠近火車站和天星碼頭的尖沙咀,住宅的佈置相當樸素,有些微的古典美,在客廳的書架上排列着許多別緻小擺設,常常使人愛不釋手。
她每天的生活,除了忙着拍電影以外,很少見到她在公衆塲所應酬,總是在家裡看看書寫寫字!
悠閒哉!歐陽莎菲的日常生活。
別讓丈夫知道
電影小說
夜深更闌,寧靜的半山區,一條蜿蜓的公路上,一個蓬頭散髮的女人,蜷伏在路旁,娟秀的姿容,艷麗的服飾,和着遍身血跡斑斑的傷痕,距離她不遠地方,又有一個西裝畢挺的男人躺在血泊中,另外一架黑色轎車,四論朝天地翻倒在一邊,這情形使人一望而知,他們是遭遇到意外。這個女人的名字叫白菱子,她慢慢地從昏迷中醒過來,强力地睜大了失去光彩的眼睛,驚奇地去記憶剛才所發生的一切,她緊咬着牙根,掙扎起來,隨又感到大腿上有些痛楚,想用手絹揩去腿上傷痕的血水,就在她低下頭去預備揩血跡的當兒,發現了,她的脚下留下了一頂男人的呢帽,拾起帽子,她仍然有些昏迷,用手輕敲著自己的額頭,她又看到向南倒臥在血泊中,便搶前去恐慌地叫着他,但他已經失去了知覺,看看摔在地上的金手錶,玻璃売子已經被壓破了,長短時針剛巧指在一點鐘上面。
菱子的記憶力牽引到兩小時前,她正參加着一個結婚盛會,這盛會是屬於司徒賓和林婉黛的。司徒賓家里的小客廳裡,僅留着的客人,只有季向南、白菱子和三五個婉黛的同學,大家鬧烘烘地談笑着,時針正指在十一時,該是新婚夫婦疲勞一整天的休息時候了,婉黛、司徒賓和司徒的妹妹柳雲,正在忙着向客人們送行。
「再見,林小姐,祝你與司徒先生結婚以後是幸福的!」向南看看身旁的婉黛,態度有些不自然。
「謝謝你,希望你也過得幸福。」婉黛對向南似有訴不盡的苦衷,但囘顧身旁的司徒,只好欲言又止。她轉過頭來向菱子說:「大嫂,請你囘去替我謝謝大哥的禮物,明天我們走得很早,怕來不及囘家辭行了,問候大哥的病。」
「眞不巧,雨詩爲了病,不能趕來參加你與司徒的婚禮,希望你們去後,常寫信囘來,時候不早了,再見。」菱子替她的丈夫解釋着。
向南和司徒正在一旁低談,聽菱子說再見,便囘轉身來對菱子:「林太太,我有車在門口,可以送你囘家,半山區,夜深了,一個人囘去不方便。」
「不,我可以叫的士,不要緊的。」菱子面有難色。
向南不愉快地看了菱子一眼,在衆人面前只好:「那麼我先走了,再見!」
「我代表送一送,順便給大嫂叫車子,婉黛,你陪陪大嫂。」司徒說着,向南看看菱子,菱子更覺不安,婉黛看出大嫂和向南的舉措,心裡有着難言的反應。
柳雲送另外幾個客人出去,客廳裡只剩下了婉黛和菱子,熱鬧的氣氛突然沉寂下來。桌上的電話鈴响着,婉黛拿起聽筒:「喂,是大哥哥?我是婉黛,哦,謝謝你,啊,你等一等。」轉身吿訴菱子,大哥要她聽電話。「哦,我是菱子,不用猜了,妹妹已經吿訴我了,你是雨詩,你怎麼還沒睡,小川呢?哦,我馬上就囘來。」菱子放下聽筒。
「大哥簡直少不了你。」婉黛笑着。
「有時他像個小孩子。」菱子的語氣對雨詩有點機憫。
「小川也那樣喜歡你,他簡直把你當做他的親生母親一樣,不過……」婉黛說到這里,覺得不應該再說下次。
「喁!」菱子敏感地。
「哦,我去看看車子來了沒有,大哥在等你。」婉黛急急掩飾了過去。菱子沒有忘記「不過」兩個字,和婉黛剛走到門口,停住了脚,「婉黛,剛才你說……」又追問起來。
「沒有什麼,走吧!」婉黛知道他在逼問自己的失言。
「如果你聽到什麽關於我的事,你不該瞞我。」菱子更加認眞起來。婉黛只好直說:「大嫂,我不是瞞你,我是怕你聽了會生氣。」
「你說吧,我不容易生氣的。」這一來使菱子更急了。
「我好像發現除了大哥,你心裡是不是還有一個人?」說到這里突然覺得不安:「哦,請你原說,我說得太……」
「這是誰說的?你知道這句話會傷害雨詩的,而且也會傷害我。」正色地:「婉黛,你不能這麽說,你知道雨詩爲了我已犧牲了一切………」
「我盼望我是猜錯了。」婉黛知道自己說得過份一點。
正在贈尬當兒,柳雲送完客獨個兒進來?「林太太,的士叫不到,向南先生願意送你囘家,他在門口等你呢。」
菱子看了一下手錶,考慮一會,無奈地應着:「好吧。」柳雲和婉黛一齊送了出去。向南和司徒在門口等不到車子,正在漫談。
「向南,希望你能冷靜一下,感情是可以創造一切,但是也可以毀滅一切,從別人手裡奪取自己的幸福。是危險的,剛才你說——」司徒誠懇地對向南勸說着。
「我知道我不該愛上朋友的妻子,不過我跟她以前是應該結合的一對,現在她與她的丈夫雖然結了婚,我相信她的內心很痛苦・」向南的語氣說得很肯定。
「你說的這個女人我認識嗎?」司徒還不知道向南指的那個女人就是菱子。
「自然,否則我不會吿訴你,她就是.………」向南說到這裡,婉黛和柳雲剛好送菱子出來,打斷了他倆的談話。
「林太太,太夜了,你一個人囘家不方便,所以我請向南送你囘去。」司徒看見菱子,便和她打了照應。
「謝謝你,季先生,」她無奈地只好對向南道謝。
向南開了車門讓菱子先上車,然後和大家說聲再見,車子向一條靜寂的公路疾馳而去。山路不平,車廂裡震盪得很利害,菱子坐在車頭正視着默默無言。
「我買了兩張明天的飛機票。」向南駛著車子,突然鼓起勇氣來。
「我决不能同你走。」菱子極力鎭定自己。
「你曾經答應把生命交給我。」
「是以前。」
「那麽現在?」
「我結了婚。」
「而你並不愛你的丈夫。」
「這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丈夫能了解你對他的愛不是眞實的,他會贊成你同我走。」向南緊緊地逼着她。
菱子有力地轉過頭:「這是毀滅了他,他那驕傲的性情,不允許他知道我不愛他。」
「可是,我已經决定今天晚吿訴他。」向南進一步來威脅菱子。
「不,你不能,向南。」她突然露出哀求的神情。
「我不願爲了別人,使自己痛苦,我耍吿訴他,我愛你,你也愛我。」向南已經打定了他的主意。
「你快停車,我决不能讓他知道這一切的。」她幾乎想拉住他的手:「你不知道他的個性,他好强,自信,他爲了相信我對他的愛是眞實的,不惜犧牲了一切,如果,你今天吿訴他,我並不是眞愛他,你想,那結果是多麼可怕!」
「不能騙他一生,我要讓他知道你愛我。」向南仍然是那麽堅定。
「你,向南,你再不停車,我——」菱子用力地拉着向南正在駕駛的手,車子猛然一震,幾乎衝向路旁。
「差一點,同歸於盡也好。」向南一點也不畏縮。
菱子見他那麽堅决,她用力推開車門想衝出,向南攔住她,又顧不了駕駛,車子正要拐彎,來不及控制,隆然一聲,車頭向山岩猛撞翻了過來,菱子受傷較輕,只昏迷了過去,向南却倒臥在血泊中。
第二天早晨,瑪利亞醫院裡的病牀上,受着重傷的向南,正在垂危地呻吟着,醫生們正忙着替他施行急救,第一個到醫院來探望的是婉黛,重傷的向南在昏迷中,覺得有人站在他的床沿,他緩慢地睜開眼,用感激的眼光看看婉黛,還關心地問她:「菱子呢?」
「大嫂昨天夜里也受了一點輕傷,大哥又在病中,所以不能來看你,司徒在替大嫂看傷,大概很快就會好的。」
「只要菱子能平安,我就放心了——她傷在那兒?」
「向南,你應該耽心自己,大嫂的健康,大哥會替她照料的。」婉黛也有幾分了解,特別暗示了一下。
「婉黛,也許你不相信,你大哥只可以照料菱子的皮肉的健康,而無法醫治菱子內心的創痛!?」
「怎麽解釋?!」婉黛很不了解阿南所說的話。
「我以爲你會知道我與菱子——」
「哦,沒有想到我的懷疑,居然是事實,那麽你以前所說的你心裡的那個女孩子就是——」婉黛方才醒悟過來。
「你的嫂子——!」。
婉黛責備他不應去愛戀別人的妻子時,向南憤怒地欲掙孔起來,但因傷重又跌下去,婉黛想起他的傷勢,不忍過份刺激他,只要求向南別去破壞菱子的幸福,向南吿訴她,昨天他寫了一封信,預備送給雨詩,不料晚上出了事,說著他從枕邊拿出一封信,耍婉黛帶囘去給她的大哥,但給婉黛拒絕了,向南要求她先看完這封信,就會明白了一切。
婉黛拆開了這封漫長的信,裡面完全是叙述——向南和菱子十五年認識的經過。
於是,一連串的往事,就在這封信中翻展開來。
十五年前,向南生長在富貴而安樂的家庭裡,過着美麗的童年生活,他是惟一的獨生子,所以更被他的父母所寵愛着。
一個聖誕節的夜晚,大客廳裡,彩色繽紛燈光耀目,音樂悠揚地響着,一顆滿佈着雪景的聖誕樹竪立在中間,整個家庭裡充滿着溫暖和平的氣氣,向南的父親相嚴,正開着一個盛大的舞會,向南和他的表妹瑪利兩個小鬼也在旁邊模仿着大人跳舞,落地窗外而站着一個窮苦的女孩子,她不過十一二歲光景,這就是童年時的菱子,她帶着神秘莫測的眼神向裡面呆呆地望着,正巧一個女傭人捧酒推門進來,小菱子一不提防也隨着跌了進來,女傭人看她那一付野孩子的窮酸相,還以爲她是偷東西的,罵了一頓,向南的媽過來,叫她快囘家去過聖誕節,小菱子聽說過聖誕節,反弄得莫明其妙,她看見大廳裡許多小孩子們在歡樂地鼓舞着,吃着餅乾,並且還做着鬼臉在取笑她,她悄然地囘頭跑回去,一不小心被門檻絆倒在外面走廊上,她幾乎要哭,倔强地忍着眼涙狼狽不堪。向南的媽關上落地窗,囘過身來,把手上的一對小金筆給向南,說是姨媽送給他的聖誕禮物,向南高興地連聲讚美,拿着金筆向他的表妹瑪利孩子氣地炫耀一番。
季家的後門對面,就是菱子的家,一邊是高聳大厦,一邊是小戶人家,富與貧之間,在外表上就有着顯著的識別,一個星期後的淸晨,巷子裡靜悄悄地,外面的雪花已停,天氣冷得發抖,菱子凍紅的手挽着菜籃從市場中囘來,剛走到家門口,她穿得太單薄,把菜籃放下,將手放在咀前,呵口氣取點暖,正欲叫門的當兒,忽然發現地下躺着一枝小金筆——那是向南的禮物,她拾了起來,看了又看,興奮地放到自己的口袋裡去,剛要推門進去時,對面季家門口,傳來一陣雜亂的人聲,她回過頭來,看見季家的男女傭人們正忙著東找西找,向南在一邊大發脾氣,原來向南的那枝金筆丟了,向南的媽哄他再買一枝新的,他偏吵着不要,瑪利住一旁指手劃脚地,不知說些甚麼,菱子想起自己袋裡的那枝金筆,原是人家失掉的,便走將過去,原物奉還,料不到反而給他們駡是小偷,向南得回了金筆,心裡很高興,見菱子無端受人侮篾,走過去替她解圍,笑着向她表示謝意,從這一次起,向南對菱子開始種下了一個好印象,瑪利看不順眼,拾起路旁的雪球仍過去,菱子一鬆手,把菜籃滾在地上,醬油瓶和鷄蛋全打破了,嚇得哭了起來,菱子的男父王漢堂聞聲而出,知道菱子把拾來的貴重金筆又還給人家,又被駡做小偷,不由得光起火來,囘到家裡時,把菱子打了一頓,舅母雖然勸了一陣,仍然消不了漢堂的氣,便叫菱子把爐子上的酒壺拿來,不料那酒壺的把兒燒熱了,一失手又把酒壺扔在地上,漢堂本來視酒如命,看見酒被菱子潑在地上,不由分說,拿起碗來向菱子手上猛力一打,菱子痛得幾乎昏厥過去,抱住流着血的手料着,爲了金筆她留下了深切的記憶。
第二年的春天,漢堂送菱子進學校,爲的是讀書長大了,可以替他赚錢,菱子的小手上多了一條痕疤,雖然她和向南,瑪利是同學,但他們間的距離相當遠,在學校裡瑪利還用小偷的稱呼來鄙視她,向南發現她手上的傷痕,才知道是爲了那枝金筆被舅父打的,心裡更覺難過,想把金筆送給菱子,却給她拒絶了。
幾個月很快地溜過去,菱子和向南漸漸互相諒解起來,他倆時常在一塊兒玩,向南還不時從家裡帶些吃的東西去送給菱子,菱子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討厭向南了。
鄉下的學校,早就不在向南的姨媽眼里,這次趁着瑪利父親從上海囘來,她徴得向南父母同意,要瑪利和向南一起到上海去讀書。短短幾個月的接觸,向南便耍和菱子離別了,但靑梅竹馬時的寳貴情感,他倆都沒有輕易地把它忘了。
八年後,戰爭爆發,向南跟着父親到了重慶,他很喜歡這小山城,那歌樂山上的白雲,和那靜靜的嘉陵江河流,向南就在它的懷抱裡長大,成了一個靑年的畫家。
一塊靑年會主辦靑年畫家聯會的布條,正在迎風飄蕩,靑年會門口參觀畫展的人們川流不息地進出,世界上常發生偶然而使人不相信的事情,就在這一塲合裡引現。八年離亂後的向南和菱子的重逢,就是一個例子。青年會門口,一張來賓簽名的白布上居然有着「白菱子」的字跡,這是向南無論如何也夢想不到的,他發狂似的在畫展會的人羣中,四處找尋菱子,終於他發現一幅自己所畫的油畫下,站着一個少女的背影,那幅油畫是畫他和菱子童年時的事情,題名爲「往事」,白菱子正看得出神,向南想叫她,但又覺得冒眛,終又忍不住:「你是白——。」
菱子聞聲轉過頭來,眼睛裡尙掛着淚水,那是她對畫兒的感觸,她驚訝地:「你,你是——」一時也記不起來,兩人相視良久。
「我姓季,季向南,我們從小——」幾乎不相信地,「你是白菱子?」
「是的,眞沒想到。」菱子高興極了。向南興奮地握住菱子的手:太意外了,白小姐,這麼遠的地方,這麼久的時間,我們居然又會見面。」
「是的,怪不得這張畫對我是這麽親切,原來——」。
向南笑着:「你也沒有忘記以前?你好嗎,白小姐,我在藝專剛畢業。」
「哦,我在一家小學校敎書,敎音樂。」
「哦,做敎員。」向南握着她的手,見她手上的傷痕仍在,想起了:「你的舅父和舅母呢?」
「舅母前年去世了,舅父在此地,靠我敎書來維持生活。」言卜覺得感槪萬千
他們談到這裡,向南的表妹瑪利姗姗而來,華麗的服飾,撲鼻的脂香,十足摩登的氣派,妖艷得令人肉麻,她找到了向南,一開口便說:「重慶這鬼地方,眞沒意思,跑了十五家醫院,連一架X光都沒有。「說完才發現菱子:「咦!」向南替她介紹一番,瑪利裝腔作勢地:「哦,對了。」習慣性地諷剌著:「我記起來了,爲了表哥那枝金筆,我們還鬧過誤會呢?小孩子,眞無聊。」
「瑪利小姐剛從香港來。」向南忙替菱子解嘲。
「完全爲了參觀表哥的畫展而來,表哥,這次畫展也是義賣性質嗎?」瑪利特地在菱于面前表明她的來因。
「是的。」向南冷淡地答着。
瑪利便指着「往事」那張畫:「我賣這張,一萬塊。」
「不,這張是非賣品,我已經决定把這張畫送給白小姐了。」向南的話中,他對菱子仍然相當好感。
「啊!?」瑪利對向南的態度覺得詫異,同時也非常不滿。
第二天,向南把那幅油畫另外再買些禮物,去探望菱子,同時更把那枝金筆也送給她,菱子的舅父漢堂喜出望外,對菱子說:「喂,這是財神爺,要走………」他扮着一付鬼臉:「我贊成,」拿起向南送來的酒,嗅了嗅,露出狰獰的笑。
在重慶的幾個月,向南和菱子間的情感,很快便達到頂點,向南的父親爲了在商塲上的經濟關係,强迫他和瑪利訂婚,給向南堅决地拒絕了,他不顧家庭的反對,要求菱子答應他求婚,甚至他决定同菱子出走。
向南抗婚失敗,他的父親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包辦了一切,他的行動被瑪利監視着,寸步都失去了自由。菱子看到報上所登載着向南和瑪利的訂婚啓事,她傷心地悄然離開了重慶,希望從此不再見他。向南惦念菱子心切,覺得只有出走,才能獲得自由,行婚禮的那天晚上,他收拾着簡單行裝,急急潛出去找菱子,沒有想到,菱子竟先他一步走了,向南拖着失望的脚歩,像是做了一塲夢,他想着這麼偶然的重逢,而又如此意外的分手,他不由自主地走着,走着,走過了多少城池,多少山野,他只爲了找尋菱子。
菱子離開重慶後,受着舅父的唆使,上了他的圏套。勝利那年,她到了香港,被舅舅推下了火坑,做了歌女,那時,她改名叫白雪梅。幾個月的功夫,白雪梅的名字,紅遍了香港,傾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火山孝子,如蟻附蛆地捧紅了她,共中尤以大亨金家皇追求最力。每天,菱子從歡笑的瘋狂似的舞廳,囘到家裡時,她會感到了一陣莫名的寂寞與空虛,她時時沒有忘記向南,而家皇只不過是她的搖錢樹而已。
當菱子開始厭惡舞廳裡的燈紅酒綠生活時,她常在秋天的黃昏,獨自躑躅在靜靜的街道上,有一天,她漫步街頭,在一家照相舘門前,意外的事又發生了,她驚視着櫉窗裡一張女人的照片,非常像她自己,可是那張照片下面又明明寫着——亡妻劉娟慧遺像——幾個字。菱子正看得出神時,照相舘裡的夥計把這張照片收進去,菱子爲了好奇心驅使,便推門進去,看見一個男人——雨詩正付了錢拿着那張包紮好的照片正要出來,和菱子打個照面,雨詩驚望着菱子,覺得菱子長得和他的亡妻一模一樣,菱子也不約而同好奇地看着他,相顧中自已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急轉身而去,雨詩却緊緊地隨着她。
追至照相舘門外,雨詩失聲地叫著她「娟慧。」
「你認錯人了。」菱子對雨詩的誤會,表示同情。
雨詩仔細打量着她:「哦,對不起。」
菱子不安地走了,雨詩仍然戀戀不捨地跟着她,從此他知道了菱于的身份。
雨詩每天都到舞廳裡來,奇怪的是他從不跳舞,老是那麽呆坐着角落裡注著在麥克風前歌唱的菱子,起初菱子有點害怕,後來覺得雨詩的態度極和氣,舉行也很莊重,但是她仍然不明白雨詩每天晚上來舞廳的目的。有一天晚上,外面雨下得很大,舞廳快打烊時,菱子爲了想知道這位怪客的究竟,故意跟着雨詩步出舞廳,雨詩叫了一輛的士正要上車,菱子追上去「先生,雨下得很大,可以兩個人坐嗎?」
「哦,可以的。」雨詩的樣子很窘。
這情形給金家皇看見,憤恨交併,心裡非常不愉快。
正因爲菱子發現雨詩不是一個尋常的舞客,所以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她爲了想知道雨詩心裡所隱藏的是什麼,自從那天晚上認識後。經常都保持着聯絡。有一次,菱子請他到家裡吃宵夜,他倆談得很投機,她知道雨詩是一個作家,他的太太剛死去不久,第一次在照相舘碰見菱子時,覺得菱子不論相貌、聲音、態度,都使他相信是娟慧的再生,他天天到舞廳裡來,爲着多看菱子,也爲着想起死去的娟慧。
以後,菱子和雨詩時相往來,她了解雨詩對自己的感情在日漸加深,她感激雨詩對目前處境的諒解與同情,他倆彼此都希望能生活在一起,但她對向南的初戀,却仍然難以忘懷。
菱子想和雨詩結婚,並不是一樣容易的事,第一、菱子的債務問題耍先獲得解决。第二、金家皇的壓力也在重重地阻礙着。况且雨詩的經濟環境不見得好,他父母死後,一切產業都操縱在二叔耀祖手裡,同時耍和一個歌女結婚,也一定會遭受二叔的反對。家皇知道菱子和雨詩的秘密後,更進一步地向漢堂利誘威脅,又向雨詩的二叔極力破壞,逼着菱子和他結婚,否則他將用武力來解决雨詩。
菱子將家皇的毒辣手段吿訴雨詩,雨詩並不因當前惡勢力而低頭屈服,相反地,他不顧二叔的反對,盡了他的力量,犧牲一切,爲菱子淸償債務,他所需耍的是菱子的眞實的愛。他决定離開二叔的家,寫了信給在學校裡的妹妹婉黛,叫她送小川囘來,雖然,菱子感激雨詩的誠懇,敬慕他做事的勇氣,但,她心裡仍然是愛着向南。
婉黛帶著小川自廣州囘來的那一天,雨詩和菱子一齊到碼頭去迎接,小川見到菱子誤爲親娘,連婉黛也以爲大嫂沒有死,這情形使雨詩覺得快樂,也覺得辛酸,爲了小川,菱子對雨詩更加深深憐憫。
當菱子離開舞廳的第二天,不幸的事情傳來了,雨詩被人打傷進了醫院,菱子以爲這勾當是舅舅漢堂幹的,雨詩的二叔責他不該這樣任性不聽話,但雨詩爲了自己未來的幸福,却一點也不埋怨,菱子眼看着雨詩爲了自己,承受着双重災難,她小心地照應着小川,極力去安慰雨詩,而唆使流氓毆打雨詩的,正是無賴金家皇所幹的勾當。
菱子和雨詩結婚後,住在雨詩父親遺下的一幢半山別墅裡,雨詩對她非常好,菱子也不願使他失望,不過,所遺憾的是——菱子心裡始終還在愛着向南。
結婚後一個月的清晨,是小川的生日,菱子起得很早,她整理了一下頭髮,望望床上甜睡的雨詩,正耍下樓時,小川跑來吿訴她阿姑來了,她叫小川輕聲點,爸爸夜裡寫稿子,睡得遲別驚醒他,說着便和小川下樓來,不知怎的,因爲雨詩的前妻就死在她的睡房裡,因此她對這房子有時會感到一點不自在。她和小川下來時,婉黛帯着送給小川的禮物早已在客廳裡等着,爲了馬上耍趕囘廣州準備學校裡的大考,特地來和大哥大嫂辭行,菱子送婉黛出來時,花園裡正坐着王漢堂,看樣子他已等了很久,漢堂的來因,她早已猜着了,爲了雨詩的環境不好,她叫漢堂別時常來騷擾,只好給了一點錢打發他走,漢堂走後,家裡的老傭人老趙神秘地過來吿訴菱子,後門山岩上有一位太太要會她,菱子覺得奇怪,便到山岩上去,四處望了一下,突然背後有人叫聲:「林太太」,她囘過頭來,看見枯樹後立着一個女人,蒼白的瞼,形容很憔悴,登時把她嚇了一跳,這個女人吿訴菱子,她就是雨詩的前妻——劉娟慧,並沒有死,因爲她和雨詩婚後,又愛上了另一個男人而私奔。她知道雨詩是一個最驕傲最自信的人,妻子的失節讓他知道了會毀了他的一切,所以,她臨走的時候,吿訴老趙,替她造一座假墳,等雨詩從廣州囘來時,會眞的相信她死了,現在她被人遺棄了,雖然後悔,但又不敢囘來,因爲人家已經把她當做鬼了,而且,雨詩也已經結了婚,今天她要會見菱子,目的是耍見她親生的兒子小川一面,說到這裡,菱子聽見雨詩在喊她,娟慧爲了不能讓雨詩看見,自己又置身於沒有退路的懸岩中,下面是濤濤海水,雨詩叫着菱子的聲音愈來愈近,菱子跑過去找雨詩,娟慧情急從數丈懸崖跳下慘死,菱子一囘頭,見娟慧不在,懸岩上那塊石頭也落了下去,她明白了,驚叫一聲投入雨詩懷抱,弄得雨詩莫名其妙。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聖誕節的的幾天,婉黛從廣州假歸,和她一齊到香港來的除柳雲外,還有她學校裡的圖畫老師季向南,到車站去接的有雨詩、菱子、小川和柳雲哥哥司徒賓等,向南幾年來不斷在打聽着菱子的消息,想不到麥子嫁後,又一次偶然的重逢,他和菱子在車站相見時,大家都呆了半响,說不出話來,最使向南感傷的是——景物依舊而人面全非了。
晚飯後,大家都歡聚在雨詩的客廳裡,要婉黛唱一隻歌,向南担任鋼琴伴奏,婉黛的歌聲,激起菱子囘憶過去,她忍耐着眼淚,望着壁上掛著的那張褪了色的「往事」油畫,小川睡在雨詩身上,婉黛不時用含情的目光望着向南,向南死盯住菱子,眼睛裡充滿了怨與恨,菱子再也不忍聽下去,她借故走到小川面前,時小川上樓去睡覺,她拉走小川,向南不期然地使勁在琴鍵上用力彈了一下,好像能發洩了他激動着的情感,菱子會意而不安地望她一眼才離開客廳,她心裡想着——我不明白,是不是命運要這樣在玩弄自己,誰會料到,這一生,又碰見了向南。菱子把小川安頓好後,帶上房門,轉身靠在門口,她被這意外的事情糾纏住了思想,她極力想從迷茫中使自己清醒,樓下歌聲停了,傳來一陣輕微拍掌聲,她支持着身子,想下樓來,看見他正獨個兒在那幅油畫下呆望着,聽到菱子下樓的脚步聲,轉過身來:「他們都送司徒先生出去了。」隨又加重着語氣,半諷刺地:「林太太。」菱子忍耐地應着,想走出廳門,向南以油畫中已經褪了色的女孩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譏嘲地留着菱子的脚步,她的面色很難看,正要囘答,婉黛和雨詩送完客進來,打斷了話頭。
他們批評着油畫,向南正好抓住機會,不時冷嘲熱調地向菱子攻擊,菱子忍不住,催着雨詩早點休息,婉黛陪着向南到臥室去,也受不了剛才向南對她的刺激,覺得精神恍惚,眼前一陣昏黑,連身子也站不隱,雨詩以爲她累了,忙扶着:「怎麼啦?菱子。」
「沒有什麽,我想請你讓我一個人在這兒靜一會兒,你先去睡吧。」
「我告訴你,今天我發現了一個秘密。」雨詩忽然想起。
菱子給雨詩這麼一說,突然驚慌起來,以爲她和向南的秘密,給他知道了。
「是關於季先生和婉黛的,我發現妹妹很愛他。」雨詩說完他的新發現,菱子囹囹地鬆了口氣:「哦,很愛他。」她像在自言自語,視線落在牆上的那張油畫上面。
向南的來,給菱子帶來了苦惱,平靜的生活中,掀起了風波,第二天早晨——向南對着自已房子窗外的懸岩在寫生,但,因爲心情不好,正欲丟下了筆,忽然看見菱子一個人正向這座懸崖上走着,他忙丢下了筆,披上外衣追出,向南走近菱子身旁時,菱子發現着他,急欲走避,却給向南攔住:「你沒有話對我說嗎?」
「只有一句,耍求你別把過去的事情吿訴雨詩,過去已經死去,我不願意雨詩不快活,相信你也會這樣想。」說着菱子急步走下山岩,向南望着她的背影,內心怨恨交併。
矛盾的生活中,日子流了過去,那是聖誕節的晚上,客廳裡來了許多客人,多半是雨詩的朋友,司徒、柳雲還有婉黛的同學,大家都在愉快地跳着舞,向南和菱子各自懷着抑鬱的心情在悵惆着,雨詩覺得菱子最近有點變了,至少態度和以前有些兩樣,菱丁托詞,說是担心他日漸衰弱的身體,掩飾着自己内心的不安。音樂在播唱着「魂斷藍橋」的曲子,向南過來請菱子共舞,她正覺得進退爲難時,雨詩和婉黛在一旁催着,婉黛見他倆起舞,偷偷地將自己的心事吿訴雨詩,說向南是她心目中的對象,雨詩早已知道婉黛情有所鍾,願意叫菱子替她作媒,舞池中,向南和菱子邊舞邊談着:「你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嗎?也是這麽一個晚上。」向南故意提起往事來挑逗她。
「唔。」菱子默默無言。
「那時我們都是孩子。」
「唔。」菱子仍默默無言。
「過了節,我想走。」
「很好。」菱子的情緖亂得很。
「我找你找了這麼些年,今天我仍是一個人,爲了你,我犧牲了家,可是你已經——」向南埋怨箭:「你不該忘記我。」
「我沒有忘記。」除此之外她還說些什麼呢?
「可是你已經是別人的妻子。」
「這是命運的安排,我沒有想到會再見到你,更沒有想到——」菱子始終不敢吐露出自己的眞情。
舞罷,婉黛在大家面前宜佈請大嫂唱一支歌,由向南來伴奏,除賓客外連小川也在拍掌歡迎,向南從菱子身邊走過:「請唱『往事』一曲。」如泣如訴的歌聲中可以看出菱子的痛苦、悲哀、激動的心情。
老佣人過來吿訴雨詩,說二叔在外面要見他,二叔的來是通知雨詩別墅抵押期滿,出押人耍贖囘房子,過了年就得搬家,雨詩明知二叔的心計,要呑沒他父親留下來的遺產,但沒有証據只好答應。他以爲社會上什麼都是虛僞的,只有菱子對他的愛才是眞實的,雨詩的身體本來不好,受不了這打擊,終於肺病發作,進了醫院,一切費用,還是由雨詩的摯友司徒賓替他負責。
第二天晚上,外面雨下得很大,狂風呼嘯,電光閃閃,雷聲像擊鼓似的響着,菱子剛從醫院里囘來,看見婉黛氣冲冲地出去,菱子想問她,却見她乘一輛的士逕去,菱子不解,正欲進內,不料漢堂又出現在樹蔭下,菱子見他喝得醉醺醺的,無奈又給他幾個錢叫他快去。
菱子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情,正要上樓,見向南從樓上下來,向南沒有將剛才和婉黛吵架的吿訴她,只說已經决定明天一清早就走,請菱子向婉黛解釋,他沒有辦法接受婉黛的愛,向南的苦衷,當然也只有菱子能了解,菱子正欲上樓,給向南擋住:「別就走。」
「請別這樣,給人家看見了不像話。」
「今天這房子裡沒有人,連佣人都到醫院裏送東西去了。」
「小川在家——」菱子覺得向南的態度有點不對。
「他已經睡了。」向南盯住菱子不放。
「你要怎麼樣。」菱子恐佈地帶着誘感的眼情。
「我要你同我走!」向南拉住她的手。
外面狂風怒嘯,暴雨如注,巨響的雷聲,震盪着菱子的心靈。
「你忘了,我已經是林太太。」用力地掙脫了向南的手,發狂似地奔上樓去。
向南追上去,大聲地叫着:「菱子,菱子。」
菱子慌忙奔入房內,緊關上門,向南重敲着房門:菱子,菱子,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沒有你不行,只耍你能答應,過去的一切,我都會原諒你。」
菱子把頭靠在門上哭泣:「向南,我知道,我明白,吿訴你,我也一樣的愛你,可是,今天不是過去,我結了婚,我不能把痛苦加在雨詩身上,你應該原諒我。」
「可是,你是我的啊!」向南的血在沸騰着。
「向南,感情以外還有道德,我們走了,你料到雨詩的結果嗎?他爲我犧牲了一切,我不能在他病中再傷他的心。」菱子極力壓制住自己的情感,想以道德來約朿發狂中的向南。
「那你開開門,讓我見見你,見你最後一面。」向南的哀求,打動了菱子的同情心,她想開門,突然外面饗着一聲巨雷,她驚恐地縮囘戰悚的手,終于她倒在床上哭泣着。
電光閃得更可怕,雷聲響得更隆,向南在外面狂叫菱子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她昏迷地和衣睡在床上,等到醒來時,已經是深夜一點鐘了,她隱約地聽到樓下的電話鈴聲斷續地響着,便打開房門,見外面空無一人,先到小川臥室,小川已熟睡在一張小床上,婉黛的床仍然空着,她隨手關上門下樓去,客廳裡冷淸淸的,她拿起話筒,是婉黛打來的,說是外面雨大,今晚上在司徒處過夜,不想囘家來,菱子按完電話,正欲上樓,見向南的房門開着,房內空空的,只剩下收拾好的行李,她奇異地同身向外望,花園外風雨不停,也不見人影,她大聲地呌着向南,沒有囘音,心頭裡突然感到一陣陰森森的恐佈,四處張望了一下,見後門大開,狂風呼呼地吹進來,她走到後門口,猛抬起頭來,電光正閃了一下,懸岩上突現着一個人影,站在暴風雨中,菱子激動地衝上山岩,向南聽見菱子在叫他,兩人迎面而奔,電炬閃照着兩個人影,終於相抱在一起。
「向南這不怪我,你饒了我….」菱子緊抱着向南。
「菱子,我不怪你。」向南吻着她的秀髮。
閃電中菱子突見枯樹後有一婦人身影,娟慧蒼百的臉,突然現在她的面前,菱子彷彿聽見她說:「你忘了,我是從懸崖上跳下去的——」這完全是菱子自己的幻想,突然又响着一聲巨雷,震盪了大地,她想她不能這樣做,良心上的譴責,使她瘋狂地推開向南,急急奔囘。
第二天向南一個人走了,幾個月來,菱子一直躭心着這件事,怕讓雨詩知道,前天雨詩出了醫院,不料在司徒與婉黛的結婚宴會上,又遇見了向南,才鬧出了今天翻車的意外。
菱子的傷勢很快痊癒了,她關心着向南,又怕雨詩知道了她的秘密,料不到向南留給雨詩的信,竟成遺言,婉黛同情菱子的不幸遭遇,沒有把向南的信給雨詩,菱子感激而又悔恨地,献出她赤裸的心開始眞誠地去愛雨詩,所幸的她沒有步上娟慧的後塵。
——完——
別讓丈夫知道
電影小說
夜深更闌,寧靜的半山區,一條蜿蜓的公路上,一個蓬頭散髮的女人,蜷伏在路旁,娟秀的姿容,艷麗的服飾,和着遍身血跡斑斑的傷痕,距離她不遠地方,又有一個西裝畢挺的男人躺在血泊中,另外一架黑色轎車,四論朝天地翻倒在一邊,這情形使人一望而知,他們是遭遇到意外。這個女人的名字叫白菱子,她慢慢地從昏迷中醒過來,强力地睜大了失去光彩的眼睛,驚奇地去記憶剛才所發生的一切,她緊咬着牙根,掙扎起來,隨又感到大腿上有些痛楚,想用手絹揩去腿上傷痕的血水,就在她低下頭去預備揩血跡的當兒,發現了,她的脚下留下了一頂男人的呢帽,拾起帽子,她仍然有些昏迷,用手輕敲著自己的額頭,她又看到向南倒臥在血泊中,便搶前去恐慌地叫着他,但他已經失去了知覺,看看摔在地上的金手錶,玻璃売子已經被壓破了,長短時針剛巧指在一點鐘上面。
菱子的記憶力牽引到兩小時前,她正參加着一個結婚盛會,這盛會是屬於司徒賓和林婉黛的。司徒賓家里的小客廳裡,僅留着的客人,只有季向南、白菱子和三五個婉黛的同學,大家鬧烘烘地談笑着,時針正指在十一時,該是新婚夫婦疲勞一整天的休息時候了,婉黛、司徒賓和司徒的妹妹柳雲,正在忙着向客人們送行。
「再見,林小姐,祝你與司徒先生結婚以後是幸福的!」向南看看身旁的婉黛,態度有些不自然。
「謝謝你,希望你也過得幸福。」婉黛對向南似有訴不盡的苦衷,但囘顧身旁的司徒,只好欲言又止。她轉過頭來向菱子說:「大嫂,請你囘去替我謝謝大哥的禮物,明天我們走得很早,怕來不及囘家辭行了,問候大哥的病。」
「眞不巧,雨詩爲了病,不能趕來參加你與司徒的婚禮,希望你們去後,常寫信囘來,時候不早了,再見。」菱子替她的丈夫解釋着。
向南和司徒正在一旁低談,聽菱子說再見,便囘轉身來對菱子:「林太太,我有車在門口,可以送你囘家,半山區,夜深了,一個人囘去不方便。」
「不,我可以叫的士,不要緊的。」菱子面有難色。
向南不愉快地看了菱子一眼,在衆人面前只好:「那麼我先走了,再見!」
「我代表送一送,順便給大嫂叫車子,婉黛,你陪陪大嫂。」司徒說着,向南看看菱子,菱子更覺不安,婉黛看出大嫂和向南的舉措,心裡有着難言的反應。
柳雲送另外幾個客人出去,客廳裡只剩下了婉黛和菱子,熱鬧的氣氛突然沉寂下來。桌上的電話鈴响着,婉黛拿起聽筒:「喂,是大哥哥?我是婉黛,哦,謝謝你,啊,你等一等。」轉身吿訴菱子,大哥要她聽電話。「哦,我是菱子,不用猜了,妹妹已經吿訴我了,你是雨詩,你怎麼還沒睡,小川呢?哦,我馬上就囘來。」菱子放下聽筒。
「大哥簡直少不了你。」婉黛笑着。
「有時他像個小孩子。」菱子的語氣對雨詩有點機憫。
「小川也那樣喜歡你,他簡直把你當做他的親生母親一樣,不過……」婉黛說到這里,覺得不應該再說下次。
「喁!」菱子敏感地。
「哦,我去看看車子來了沒有,大哥在等你。」婉黛急急掩飾了過去。菱子沒有忘記「不過」兩個字,和婉黛剛走到門口,停住了脚,「婉黛,剛才你說……」又追問起來。
「沒有什麼,走吧!」婉黛知道他在逼問自己的失言。
「如果你聽到什麽關於我的事,你不該瞞我。」菱子更加認眞起來。婉黛只好直說:「大嫂,我不是瞞你,我是怕你聽了會生氣。」
「你說吧,我不容易生氣的。」這一來使菱子更急了。
「我好像發現除了大哥,你心裡是不是還有一個人?」說到這里突然覺得不安:「哦,請你原說,我說得太……」
「這是誰說的?你知道這句話會傷害雨詩的,而且也會傷害我。」正色地:「婉黛,你不能這麽說,你知道雨詩爲了我已犧牲了一切………」
「我盼望我是猜錯了。」婉黛知道自己說得過份一點。
正在贈尬當兒,柳雲送完客獨個兒進來?「林太太,的士叫不到,向南先生願意送你囘家,他在門口等你呢。」
菱子看了一下手錶,考慮一會,無奈地應着:「好吧。」柳雲和婉黛一齊送了出去。向南和司徒在門口等不到車子,正在漫談。
「向南,希望你能冷靜一下,感情是可以創造一切,但是也可以毀滅一切,從別人手裡奪取自己的幸福。是危險的,剛才你說——」司徒誠懇地對向南勸說着。
「我知道我不該愛上朋友的妻子,不過我跟她以前是應該結合的一對,現在她與她的丈夫雖然結了婚,我相信她的內心很痛苦・」向南的語氣說得很肯定。
「你說的這個女人我認識嗎?」司徒還不知道向南指的那個女人就是菱子。
「自然,否則我不會吿訴你,她就是.………」向南說到這裡,婉黛和柳雲剛好送菱子出來,打斷了他倆的談話。
「林太太,太夜了,你一個人囘家不方便,所以我請向南送你囘去。」司徒看見菱子,便和她打了照應。
「謝謝你,季先生,」她無奈地只好對向南道謝。
向南開了車門讓菱子先上車,然後和大家說聲再見,車子向一條靜寂的公路疾馳而去。山路不平,車廂裡震盪得很利害,菱子坐在車頭正視着默默無言。
「我買了兩張明天的飛機票。」向南駛著車子,突然鼓起勇氣來。
「我决不能同你走。」菱子極力鎭定自己。
「你曾經答應把生命交給我。」
「是以前。」
「那麽現在?」
「我結了婚。」
「而你並不愛你的丈夫。」
「這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丈夫能了解你對他的愛不是眞實的,他會贊成你同我走。」向南緊緊地逼着她。
菱子有力地轉過頭:「這是毀滅了他,他那驕傲的性情,不允許他知道我不愛他。」
「可是,我已經决定今天晚吿訴他。」向南進一步來威脅菱子。
「不,你不能,向南。」她突然露出哀求的神情。
「我不願爲了別人,使自己痛苦,我耍吿訴他,我愛你,你也愛我。」向南已經打定了他的主意。
「你快停車,我决不能讓他知道這一切的。」她幾乎想拉住他的手:「你不知道他的個性,他好强,自信,他爲了相信我對他的愛是眞實的,不惜犧牲了一切,如果,你今天吿訴他,我並不是眞愛他,你想,那結果是多麼可怕!」
「不能騙他一生,我要讓他知道你愛我。」向南仍然是那麽堅定。
「你,向南,你再不停車,我——」菱子用力地拉着向南正在駕駛的手,車子猛然一震,幾乎衝向路旁。
「差一點,同歸於盡也好。」向南一點也不畏縮。
菱子見他那麽堅决,她用力推開車門想衝出,向南攔住她,又顧不了駕駛,車子正要拐彎,來不及控制,隆然一聲,車頭向山岩猛撞翻了過來,菱子受傷較輕,只昏迷了過去,向南却倒臥在血泊中。
第二天早晨,瑪利亞醫院裡的病牀上,受着重傷的向南,正在垂危地呻吟着,醫生們正忙着替他施行急救,第一個到醫院來探望的是婉黛,重傷的向南在昏迷中,覺得有人站在他的床沿,他緩慢地睜開眼,用感激的眼光看看婉黛,還關心地問她:「菱子呢?」
「大嫂昨天夜里也受了一點輕傷,大哥又在病中,所以不能來看你,司徒在替大嫂看傷,大概很快就會好的。」
「只要菱子能平安,我就放心了——她傷在那兒?」
「向南,你應該耽心自己,大嫂的健康,大哥會替她照料的。」婉黛也有幾分了解,特別暗示了一下。
「婉黛,也許你不相信,你大哥只可以照料菱子的皮肉的健康,而無法醫治菱子內心的創痛!?」
「怎麽解釋?!」婉黛很不了解阿南所說的話。
「我以爲你會知道我與菱子——」
「哦,沒有想到我的懷疑,居然是事實,那麽你以前所說的你心裡的那個女孩子就是——」婉黛方才醒悟過來。
「你的嫂子——!」。
婉黛責備他不應去愛戀別人的妻子時,向南憤怒地欲掙孔起來,但因傷重又跌下去,婉黛想起他的傷勢,不忍過份刺激他,只要求向南別去破壞菱子的幸福,向南吿訴她,昨天他寫了一封信,預備送給雨詩,不料晚上出了事,說著他從枕邊拿出一封信,耍婉黛帶囘去給她的大哥,但給婉黛拒絕了,向南要求她先看完這封信,就會明白了一切。
婉黛拆開了這封漫長的信,裡面完全是叙述——向南和菱子十五年認識的經過。
於是,一連串的往事,就在這封信中翻展開來。
十五年前,向南生長在富貴而安樂的家庭裡,過着美麗的童年生活,他是惟一的獨生子,所以更被他的父母所寵愛着。
一個聖誕節的夜晚,大客廳裡,彩色繽紛燈光耀目,音樂悠揚地響着,一顆滿佈着雪景的聖誕樹竪立在中間,整個家庭裡充滿着溫暖和平的氣氣,向南的父親相嚴,正開着一個盛大的舞會,向南和他的表妹瑪利兩個小鬼也在旁邊模仿着大人跳舞,落地窗外而站着一個窮苦的女孩子,她不過十一二歲光景,這就是童年時的菱子,她帶着神秘莫測的眼神向裡面呆呆地望着,正巧一個女傭人捧酒推門進來,小菱子一不提防也隨着跌了進來,女傭人看她那一付野孩子的窮酸相,還以爲她是偷東西的,罵了一頓,向南的媽過來,叫她快囘家去過聖誕節,小菱子聽說過聖誕節,反弄得莫明其妙,她看見大廳裡許多小孩子們在歡樂地鼓舞着,吃着餅乾,並且還做着鬼臉在取笑她,她悄然地囘頭跑回去,一不小心被門檻絆倒在外面走廊上,她幾乎要哭,倔强地忍着眼涙狼狽不堪。向南的媽關上落地窗,囘過身來,把手上的一對小金筆給向南,說是姨媽送給他的聖誕禮物,向南高興地連聲讚美,拿着金筆向他的表妹瑪利孩子氣地炫耀一番。
季家的後門對面,就是菱子的家,一邊是高聳大厦,一邊是小戶人家,富與貧之間,在外表上就有着顯著的識別,一個星期後的淸晨,巷子裡靜悄悄地,外面的雪花已停,天氣冷得發抖,菱子凍紅的手挽着菜籃從市場中囘來,剛走到家門口,她穿得太單薄,把菜籃放下,將手放在咀前,呵口氣取點暖,正欲叫門的當兒,忽然發現地下躺着一枝小金筆——那是向南的禮物,她拾了起來,看了又看,興奮地放到自己的口袋裡去,剛要推門進去時,對面季家門口,傳來一陣雜亂的人聲,她回過頭來,看見季家的男女傭人們正忙著東找西找,向南在一邊大發脾氣,原來向南的那枝金筆丟了,向南的媽哄他再買一枝新的,他偏吵着不要,瑪利住一旁指手劃脚地,不知說些甚麼,菱子想起自己袋裡的那枝金筆,原是人家失掉的,便走將過去,原物奉還,料不到反而給他們駡是小偷,向南得回了金筆,心裡很高興,見菱子無端受人侮篾,走過去替她解圍,笑着向她表示謝意,從這一次起,向南對菱子開始種下了一個好印象,瑪利看不順眼,拾起路旁的雪球仍過去,菱子一鬆手,把菜籃滾在地上,醬油瓶和鷄蛋全打破了,嚇得哭了起來,菱子的男父王漢堂聞聲而出,知道菱子把拾來的貴重金筆又還給人家,又被駡做小偷,不由得光起火來,囘到家裡時,把菱子打了一頓,舅母雖然勸了一陣,仍然消不了漢堂的氣,便叫菱子把爐子上的酒壺拿來,不料那酒壺的把兒燒熱了,一失手又把酒壺扔在地上,漢堂本來視酒如命,看見酒被菱子潑在地上,不由分說,拿起碗來向菱子手上猛力一打,菱子痛得幾乎昏厥過去,抱住流着血的手料着,爲了金筆她留下了深切的記憶。
第二年的春天,漢堂送菱子進學校,爲的是讀書長大了,可以替他赚錢,菱子的小手上多了一條痕疤,雖然她和向南,瑪利是同學,但他們間的距離相當遠,在學校裡瑪利還用小偷的稱呼來鄙視她,向南發現她手上的傷痕,才知道是爲了那枝金筆被舅父打的,心裡更覺難過,想把金筆送給菱子,却給她拒絶了。
幾個月很快地溜過去,菱子和向南漸漸互相諒解起來,他倆時常在一塊兒玩,向南還不時從家裡帶些吃的東西去送給菱子,菱子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討厭向南了。
鄉下的學校,早就不在向南的姨媽眼里,這次趁着瑪利父親從上海囘來,她徴得向南父母同意,要瑪利和向南一起到上海去讀書。短短幾個月的接觸,向南便耍和菱子離別了,但靑梅竹馬時的寳貴情感,他倆都沒有輕易地把它忘了。
八年後,戰爭爆發,向南跟着父親到了重慶,他很喜歡這小山城,那歌樂山上的白雲,和那靜靜的嘉陵江河流,向南就在它的懷抱裡長大,成了一個靑年的畫家。
一塊靑年會主辦靑年畫家聯會的布條,正在迎風飄蕩,靑年會門口參觀畫展的人們川流不息地進出,世界上常發生偶然而使人不相信的事情,就在這一塲合裡引現。八年離亂後的向南和菱子的重逢,就是一個例子。青年會門口,一張來賓簽名的白布上居然有着「白菱子」的字跡,這是向南無論如何也夢想不到的,他發狂似的在畫展會的人羣中,四處找尋菱子,終於他發現一幅自己所畫的油畫下,站着一個少女的背影,那幅油畫是畫他和菱子童年時的事情,題名爲「往事」,白菱子正看得出神,向南想叫她,但又覺得冒眛,終又忍不住:「你是白——。」
菱子聞聲轉過頭來,眼睛裡尙掛着淚水,那是她對畫兒的感觸,她驚訝地:「你,你是——」一時也記不起來,兩人相視良久。
「我姓季,季向南,我們從小——」幾乎不相信地,「你是白菱子?」
「是的,眞沒想到。」菱子高興極了。向南興奮地握住菱子的手:太意外了,白小姐,這麼遠的地方,這麼久的時間,我們居然又會見面。」
「是的,怪不得這張畫對我是這麽親切,原來——」。
向南笑着:「你也沒有忘記以前?你好嗎,白小姐,我在藝專剛畢業。」
「哦,我在一家小學校敎書,敎音樂。」
「哦,做敎員。」向南握着她的手,見她手上的傷痕仍在,想起了:「你的舅父和舅母呢?」
「舅母前年去世了,舅父在此地,靠我敎書來維持生活。」言卜覺得感槪萬千
他們談到這裡,向南的表妹瑪利姗姗而來,華麗的服飾,撲鼻的脂香,十足摩登的氣派,妖艷得令人肉麻,她找到了向南,一開口便說:「重慶這鬼地方,眞沒意思,跑了十五家醫院,連一架X光都沒有。「說完才發現菱子:「咦!」向南替她介紹一番,瑪利裝腔作勢地:「哦,對了。」習慣性地諷剌著:「我記起來了,爲了表哥那枝金筆,我們還鬧過誤會呢?小孩子,眞無聊。」
「瑪利小姐剛從香港來。」向南忙替菱子解嘲。
「完全爲了參觀表哥的畫展而來,表哥,這次畫展也是義賣性質嗎?」瑪利特地在菱于面前表明她的來因。
「是的。」向南冷淡地答着。
瑪利便指着「往事」那張畫:「我賣這張,一萬塊。」
「不,這張是非賣品,我已經决定把這張畫送給白小姐了。」向南的話中,他對菱子仍然相當好感。
「啊!?」瑪利對向南的態度覺得詫異,同時也非常不滿。
第二天,向南把那幅油畫另外再買些禮物,去探望菱子,同時更把那枝金筆也送給她,菱子的舅父漢堂喜出望外,對菱子說:「喂,這是財神爺,要走………」他扮着一付鬼臉:「我贊成,」拿起向南送來的酒,嗅了嗅,露出狰獰的笑。
在重慶的幾個月,向南和菱子間的情感,很快便達到頂點,向南的父親爲了在商塲上的經濟關係,强迫他和瑪利訂婚,給向南堅决地拒絕了,他不顧家庭的反對,要求菱子答應他求婚,甚至他决定同菱子出走。
向南抗婚失敗,他的父親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包辦了一切,他的行動被瑪利監視着,寸步都失去了自由。菱子看到報上所登載着向南和瑪利的訂婚啓事,她傷心地悄然離開了重慶,希望從此不再見他。向南惦念菱子心切,覺得只有出走,才能獲得自由,行婚禮的那天晚上,他收拾着簡單行裝,急急潛出去找菱子,沒有想到,菱子竟先他一步走了,向南拖着失望的脚歩,像是做了一塲夢,他想着這麼偶然的重逢,而又如此意外的分手,他不由自主地走着,走着,走過了多少城池,多少山野,他只爲了找尋菱子。
菱子離開重慶後,受着舅父的唆使,上了他的圏套。勝利那年,她到了香港,被舅舅推下了火坑,做了歌女,那時,她改名叫白雪梅。幾個月的功夫,白雪梅的名字,紅遍了香港,傾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火山孝子,如蟻附蛆地捧紅了她,共中尤以大亨金家皇追求最力。每天,菱子從歡笑的瘋狂似的舞廳,囘到家裡時,她會感到了一陣莫名的寂寞與空虛,她時時沒有忘記向南,而家皇只不過是她的搖錢樹而已。
當菱子開始厭惡舞廳裡的燈紅酒綠生活時,她常在秋天的黃昏,獨自躑躅在靜靜的街道上,有一天,她漫步街頭,在一家照相舘門前,意外的事又發生了,她驚視着櫉窗裡一張女人的照片,非常像她自己,可是那張照片下面又明明寫着——亡妻劉娟慧遺像——幾個字。菱子正看得出神時,照相舘裡的夥計把這張照片收進去,菱子爲了好奇心驅使,便推門進去,看見一個男人——雨詩正付了錢拿着那張包紮好的照片正要出來,和菱子打個照面,雨詩驚望着菱子,覺得菱子長得和他的亡妻一模一樣,菱子也不約而同好奇地看着他,相顧中自已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急轉身而去,雨詩却緊緊地隨着她。
追至照相舘門外,雨詩失聲地叫著她「娟慧。」
「你認錯人了。」菱子對雨詩的誤會,表示同情。
雨詩仔細打量着她:「哦,對不起。」
菱子不安地走了,雨詩仍然戀戀不捨地跟着她,從此他知道了菱于的身份。
雨詩每天都到舞廳裡來,奇怪的是他從不跳舞,老是那麽呆坐着角落裡注著在麥克風前歌唱的菱子,起初菱子有點害怕,後來覺得雨詩的態度極和氣,舉行也很莊重,但是她仍然不明白雨詩每天晚上來舞廳的目的。有一天晚上,外面雨下得很大,舞廳快打烊時,菱子爲了想知道這位怪客的究竟,故意跟着雨詩步出舞廳,雨詩叫了一輛的士正要上車,菱子追上去「先生,雨下得很大,可以兩個人坐嗎?」
「哦,可以的。」雨詩的樣子很窘。
這情形給金家皇看見,憤恨交併,心裡非常不愉快。
正因爲菱子發現雨詩不是一個尋常的舞客,所以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她爲了想知道雨詩心裡所隱藏的是什麼,自從那天晚上認識後。經常都保持着聯絡。有一次,菱子請他到家裡吃宵夜,他倆談得很投機,她知道雨詩是一個作家,他的太太剛死去不久,第一次在照相舘碰見菱子時,覺得菱子不論相貌、聲音、態度,都使他相信是娟慧的再生,他天天到舞廳裡來,爲着多看菱子,也爲着想起死去的娟慧。
以後,菱子和雨詩時相往來,她了解雨詩對自己的感情在日漸加深,她感激雨詩對目前處境的諒解與同情,他倆彼此都希望能生活在一起,但她對向南的初戀,却仍然難以忘懷。
菱子想和雨詩結婚,並不是一樣容易的事,第一、菱子的債務問題耍先獲得解决。第二、金家皇的壓力也在重重地阻礙着。况且雨詩的經濟環境不見得好,他父母死後,一切產業都操縱在二叔耀祖手裡,同時耍和一個歌女結婚,也一定會遭受二叔的反對。家皇知道菱子和雨詩的秘密後,更進一步地向漢堂利誘威脅,又向雨詩的二叔極力破壞,逼着菱子和他結婚,否則他將用武力來解决雨詩。
菱子將家皇的毒辣手段吿訴雨詩,雨詩並不因當前惡勢力而低頭屈服,相反地,他不顧二叔的反對,盡了他的力量,犧牲一切,爲菱子淸償債務,他所需耍的是菱子的眞實的愛。他决定離開二叔的家,寫了信給在學校裡的妹妹婉黛,叫她送小川囘來,雖然,菱子感激雨詩的誠懇,敬慕他做事的勇氣,但,她心裡仍然是愛着向南。
婉黛帶著小川自廣州囘來的那一天,雨詩和菱子一齊到碼頭去迎接,小川見到菱子誤爲親娘,連婉黛也以爲大嫂沒有死,這情形使雨詩覺得快樂,也覺得辛酸,爲了小川,菱子對雨詩更加深深憐憫。
當菱子離開舞廳的第二天,不幸的事情傳來了,雨詩被人打傷進了醫院,菱子以爲這勾當是舅舅漢堂幹的,雨詩的二叔責他不該這樣任性不聽話,但雨詩爲了自己未來的幸福,却一點也不埋怨,菱子眼看着雨詩爲了自己,承受着双重災難,她小心地照應着小川,極力去安慰雨詩,而唆使流氓毆打雨詩的,正是無賴金家皇所幹的勾當。
菱子和雨詩結婚後,住在雨詩父親遺下的一幢半山別墅裡,雨詩對她非常好,菱子也不願使他失望,不過,所遺憾的是——菱子心裡始終還在愛着向南。
結婚後一個月的清晨,是小川的生日,菱子起得很早,她整理了一下頭髮,望望床上甜睡的雨詩,正耍下樓時,小川跑來吿訴她阿姑來了,她叫小川輕聲點,爸爸夜裡寫稿子,睡得遲別驚醒他,說着便和小川下樓來,不知怎的,因爲雨詩的前妻就死在她的睡房裡,因此她對這房子有時會感到一點不自在。她和小川下來時,婉黛帯着送給小川的禮物早已在客廳裡等着,爲了馬上耍趕囘廣州準備學校裡的大考,特地來和大哥大嫂辭行,菱子送婉黛出來時,花園裡正坐着王漢堂,看樣子他已等了很久,漢堂的來因,她早已猜着了,爲了雨詩的環境不好,她叫漢堂別時常來騷擾,只好給了一點錢打發他走,漢堂走後,家裡的老傭人老趙神秘地過來吿訴菱子,後門山岩上有一位太太要會她,菱子覺得奇怪,便到山岩上去,四處望了一下,突然背後有人叫聲:「林太太」,她囘過頭來,看見枯樹後立着一個女人,蒼白的瞼,形容很憔悴,登時把她嚇了一跳,這個女人吿訴菱子,她就是雨詩的前妻——劉娟慧,並沒有死,因爲她和雨詩婚後,又愛上了另一個男人而私奔。她知道雨詩是一個最驕傲最自信的人,妻子的失節讓他知道了會毀了他的一切,所以,她臨走的時候,吿訴老趙,替她造一座假墳,等雨詩從廣州囘來時,會眞的相信她死了,現在她被人遺棄了,雖然後悔,但又不敢囘來,因爲人家已經把她當做鬼了,而且,雨詩也已經結了婚,今天她要會見菱子,目的是耍見她親生的兒子小川一面,說到這裡,菱子聽見雨詩在喊她,娟慧爲了不能讓雨詩看見,自己又置身於沒有退路的懸岩中,下面是濤濤海水,雨詩叫着菱子的聲音愈來愈近,菱子跑過去找雨詩,娟慧情急從數丈懸崖跳下慘死,菱子一囘頭,見娟慧不在,懸岩上那塊石頭也落了下去,她明白了,驚叫一聲投入雨詩懷抱,弄得雨詩莫名其妙。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聖誕節的的幾天,婉黛從廣州假歸,和她一齊到香港來的除柳雲外,還有她學校裡的圖畫老師季向南,到車站去接的有雨詩、菱子、小川和柳雲哥哥司徒賓等,向南幾年來不斷在打聽着菱子的消息,想不到麥子嫁後,又一次偶然的重逢,他和菱子在車站相見時,大家都呆了半响,說不出話來,最使向南感傷的是——景物依舊而人面全非了。
晚飯後,大家都歡聚在雨詩的客廳裡,要婉黛唱一隻歌,向南担任鋼琴伴奏,婉黛的歌聲,激起菱子囘憶過去,她忍耐着眼淚,望着壁上掛著的那張褪了色的「往事」油畫,小川睡在雨詩身上,婉黛不時用含情的目光望着向南,向南死盯住菱子,眼睛裡充滿了怨與恨,菱子再也不忍聽下去,她借故走到小川面前,時小川上樓去睡覺,她拉走小川,向南不期然地使勁在琴鍵上用力彈了一下,好像能發洩了他激動着的情感,菱子會意而不安地望她一眼才離開客廳,她心裡想着——我不明白,是不是命運要這樣在玩弄自己,誰會料到,這一生,又碰見了向南。菱子把小川安頓好後,帶上房門,轉身靠在門口,她被這意外的事情糾纏住了思想,她極力想從迷茫中使自己清醒,樓下歌聲停了,傳來一陣輕微拍掌聲,她支持着身子,想下樓來,看見他正獨個兒在那幅油畫下呆望着,聽到菱子下樓的脚步聲,轉過身來:「他們都送司徒先生出去了。」隨又加重着語氣,半諷刺地:「林太太。」菱子忍耐地應着,想走出廳門,向南以油畫中已經褪了色的女孩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譏嘲地留着菱子的脚步,她的面色很難看,正要囘答,婉黛和雨詩送完客進來,打斷了話頭。
他們批評着油畫,向南正好抓住機會,不時冷嘲熱調地向菱子攻擊,菱子忍不住,催着雨詩早點休息,婉黛陪着向南到臥室去,也受不了剛才向南對她的刺激,覺得精神恍惚,眼前一陣昏黑,連身子也站不隱,雨詩以爲她累了,忙扶着:「怎麼啦?菱子。」
「沒有什麽,我想請你讓我一個人在這兒靜一會兒,你先去睡吧。」
「我告訴你,今天我發現了一個秘密。」雨詩忽然想起。
菱子給雨詩這麼一說,突然驚慌起來,以爲她和向南的秘密,給他知道了。
「是關於季先生和婉黛的,我發現妹妹很愛他。」雨詩說完他的新發現,菱子囹囹地鬆了口氣:「哦,很愛他。」她像在自言自語,視線落在牆上的那張油畫上面。
向南的來,給菱子帶來了苦惱,平靜的生活中,掀起了風波,第二天早晨——向南對着自已房子窗外的懸岩在寫生,但,因爲心情不好,正欲丟下了筆,忽然看見菱子一個人正向這座懸崖上走着,他忙丢下了筆,披上外衣追出,向南走近菱子身旁時,菱子發現着他,急欲走避,却給向南攔住:「你沒有話對我說嗎?」
「只有一句,耍求你別把過去的事情吿訴雨詩,過去已經死去,我不願意雨詩不快活,相信你也會這樣想。」說着菱子急步走下山岩,向南望着她的背影,內心怨恨交併。
矛盾的生活中,日子流了過去,那是聖誕節的晚上,客廳裡來了許多客人,多半是雨詩的朋友,司徒、柳雲還有婉黛的同學,大家都在愉快地跳着舞,向南和菱子各自懷着抑鬱的心情在悵惆着,雨詩覺得菱子最近有點變了,至少態度和以前有些兩樣,菱丁托詞,說是担心他日漸衰弱的身體,掩飾着自己内心的不安。音樂在播唱着「魂斷藍橋」的曲子,向南過來請菱子共舞,她正覺得進退爲難時,雨詩和婉黛在一旁催着,婉黛見他倆起舞,偷偷地將自己的心事吿訴雨詩,說向南是她心目中的對象,雨詩早已知道婉黛情有所鍾,願意叫菱子替她作媒,舞池中,向南和菱子邊舞邊談着:「你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嗎?也是這麽一個晚上。」向南故意提起往事來挑逗她。
「唔。」菱子默默無言。
「那時我們都是孩子。」
「唔。」菱子仍默默無言。
「過了節,我想走。」
「很好。」菱子的情緖亂得很。
「我找你找了這麼些年,今天我仍是一個人,爲了你,我犧牲了家,可是你已經——」向南埋怨箭:「你不該忘記我。」
「我沒有忘記。」除此之外她還說些什麼呢?
「可是你已經是別人的妻子。」
「這是命運的安排,我沒有想到會再見到你,更沒有想到——」菱子始終不敢吐露出自己的眞情。
舞罷,婉黛在大家面前宜佈請大嫂唱一支歌,由向南來伴奏,除賓客外連小川也在拍掌歡迎,向南從菱子身邊走過:「請唱『往事』一曲。」如泣如訴的歌聲中可以看出菱子的痛苦、悲哀、激動的心情。
老佣人過來吿訴雨詩,說二叔在外面要見他,二叔的來是通知雨詩別墅抵押期滿,出押人耍贖囘房子,過了年就得搬家,雨詩明知二叔的心計,要呑沒他父親留下來的遺產,但沒有証據只好答應。他以爲社會上什麼都是虛僞的,只有菱子對他的愛才是眞實的,雨詩的身體本來不好,受不了這打擊,終於肺病發作,進了醫院,一切費用,還是由雨詩的摯友司徒賓替他負責。
第二天晚上,外面雨下得很大,狂風呼嘯,電光閃閃,雷聲像擊鼓似的響着,菱子剛從醫院里囘來,看見婉黛氣冲冲地出去,菱子想問她,却見她乘一輛的士逕去,菱子不解,正欲進內,不料漢堂又出現在樹蔭下,菱子見他喝得醉醺醺的,無奈又給他幾個錢叫他快去。
菱子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情,正要上樓,見向南從樓上下來,向南沒有將剛才和婉黛吵架的吿訴她,只說已經决定明天一清早就走,請菱子向婉黛解釋,他沒有辦法接受婉黛的愛,向南的苦衷,當然也只有菱子能了解,菱子正欲上樓,給向南擋住:「別就走。」
「請別這樣,給人家看見了不像話。」
「今天這房子裡沒有人,連佣人都到醫院裏送東西去了。」
「小川在家——」菱子覺得向南的態度有點不對。
「他已經睡了。」向南盯住菱子不放。
「你要怎麼樣。」菱子恐佈地帶着誘感的眼情。
「我要你同我走!」向南拉住她的手。
外面狂風怒嘯,暴雨如注,巨響的雷聲,震盪着菱子的心靈。
「你忘了,我已經是林太太。」用力地掙脫了向南的手,發狂似地奔上樓去。
向南追上去,大聲地叫着:「菱子,菱子。」
菱子慌忙奔入房內,緊關上門,向南重敲着房門:菱子,菱子,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沒有你不行,只耍你能答應,過去的一切,我都會原諒你。」
菱子把頭靠在門上哭泣:「向南,我知道,我明白,吿訴你,我也一樣的愛你,可是,今天不是過去,我結了婚,我不能把痛苦加在雨詩身上,你應該原諒我。」
「可是,你是我的啊!」向南的血在沸騰着。
「向南,感情以外還有道德,我們走了,你料到雨詩的結果嗎?他爲我犧牲了一切,我不能在他病中再傷他的心。」菱子極力壓制住自己的情感,想以道德來約朿發狂中的向南。
「那你開開門,讓我見見你,見你最後一面。」向南的哀求,打動了菱子的同情心,她想開門,突然外面饗着一聲巨雷,她驚恐地縮囘戰悚的手,終于她倒在床上哭泣着。
電光閃得更可怕,雷聲響得更隆,向南在外面狂叫菱子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她昏迷地和衣睡在床上,等到醒來時,已經是深夜一點鐘了,她隱約地聽到樓下的電話鈴聲斷續地響着,便打開房門,見外面空無一人,先到小川臥室,小川已熟睡在一張小床上,婉黛的床仍然空着,她隨手關上門下樓去,客廳裡冷淸淸的,她拿起話筒,是婉黛打來的,說是外面雨大,今晚上在司徒處過夜,不想囘家來,菱子按完電話,正欲上樓,見向南的房門開着,房內空空的,只剩下收拾好的行李,她奇異地同身向外望,花園外風雨不停,也不見人影,她大聲地呌着向南,沒有囘音,心頭裡突然感到一陣陰森森的恐佈,四處張望了一下,見後門大開,狂風呼呼地吹進來,她走到後門口,猛抬起頭來,電光正閃了一下,懸岩上突現着一個人影,站在暴風雨中,菱子激動地衝上山岩,向南聽見菱子在叫他,兩人迎面而奔,電炬閃照着兩個人影,終於相抱在一起。
「向南這不怪我,你饒了我….」菱子緊抱着向南。
「菱子,我不怪你。」向南吻着她的秀髮。
閃電中菱子突見枯樹後有一婦人身影,娟慧蒼百的臉,突然現在她的面前,菱子彷彿聽見她說:「你忘了,我是從懸崖上跳下去的——」這完全是菱子自己的幻想,突然又响着一聲巨雷,震盪了大地,她想她不能這樣做,良心上的譴責,使她瘋狂地推開向南,急急奔囘。
第二天向南一個人走了,幾個月來,菱子一直躭心着這件事,怕讓雨詩知道,前天雨詩出了醫院,不料在司徒與婉黛的結婚宴會上,又遇見了向南,才鬧出了今天翻車的意外。
菱子的傷勢很快痊癒了,她關心着向南,又怕雨詩知道了她的秘密,料不到向南留給雨詩的信,竟成遺言,婉黛同情菱子的不幸遭遇,沒有把向南的信給雨詩,菱子感激而又悔恨地,献出她赤裸的心開始眞誠地去愛雨詩,所幸的她沒有步上娟慧的後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