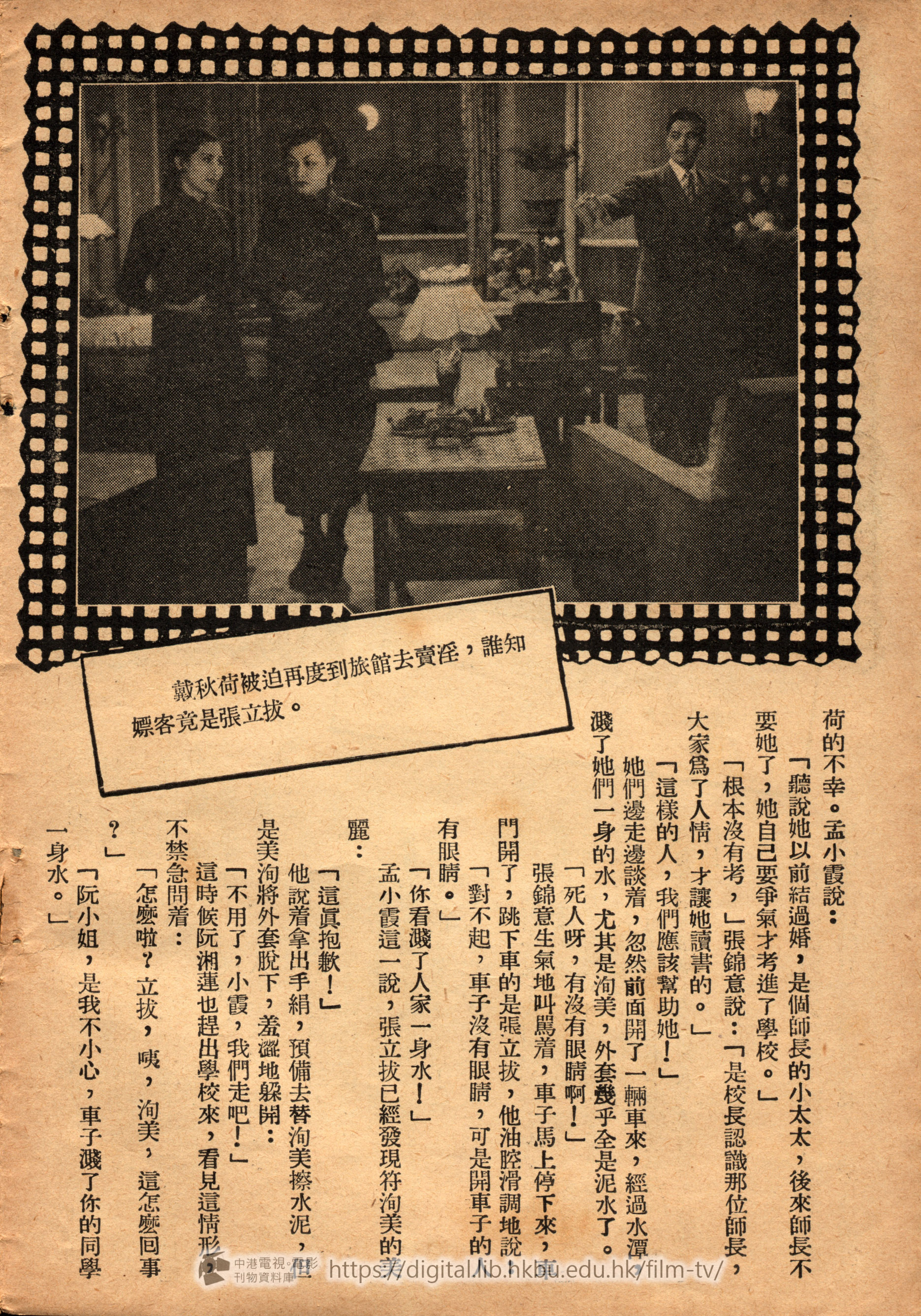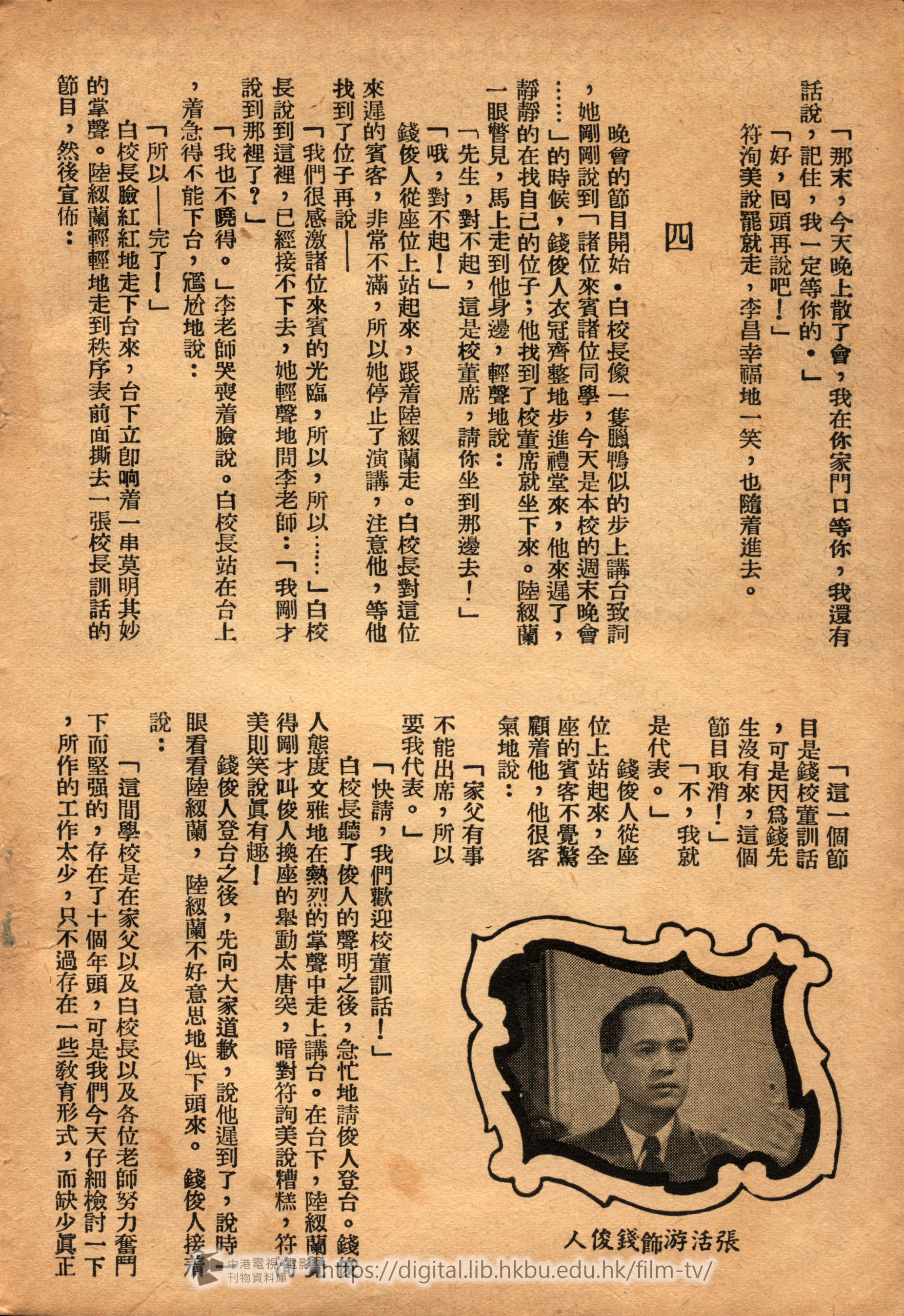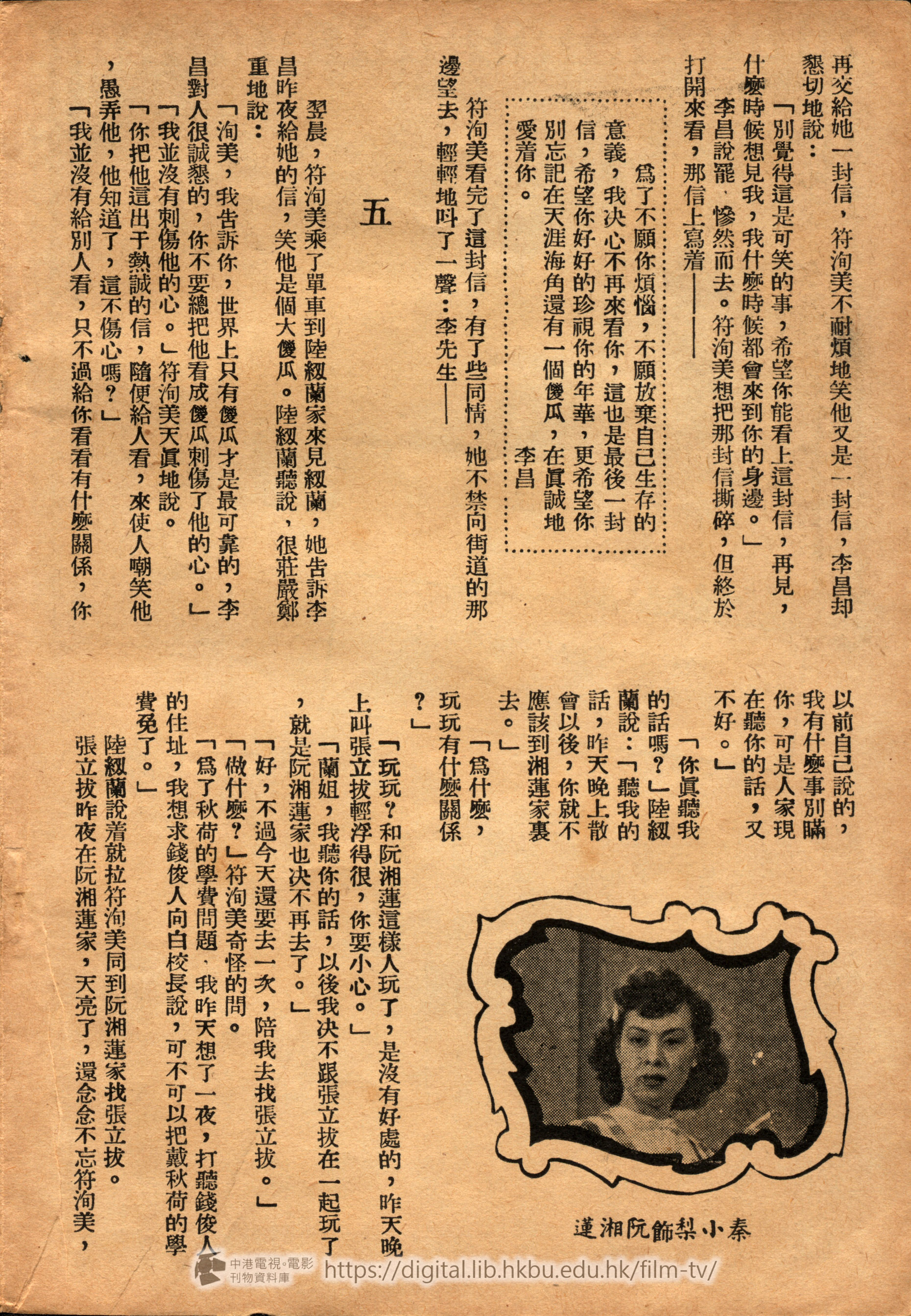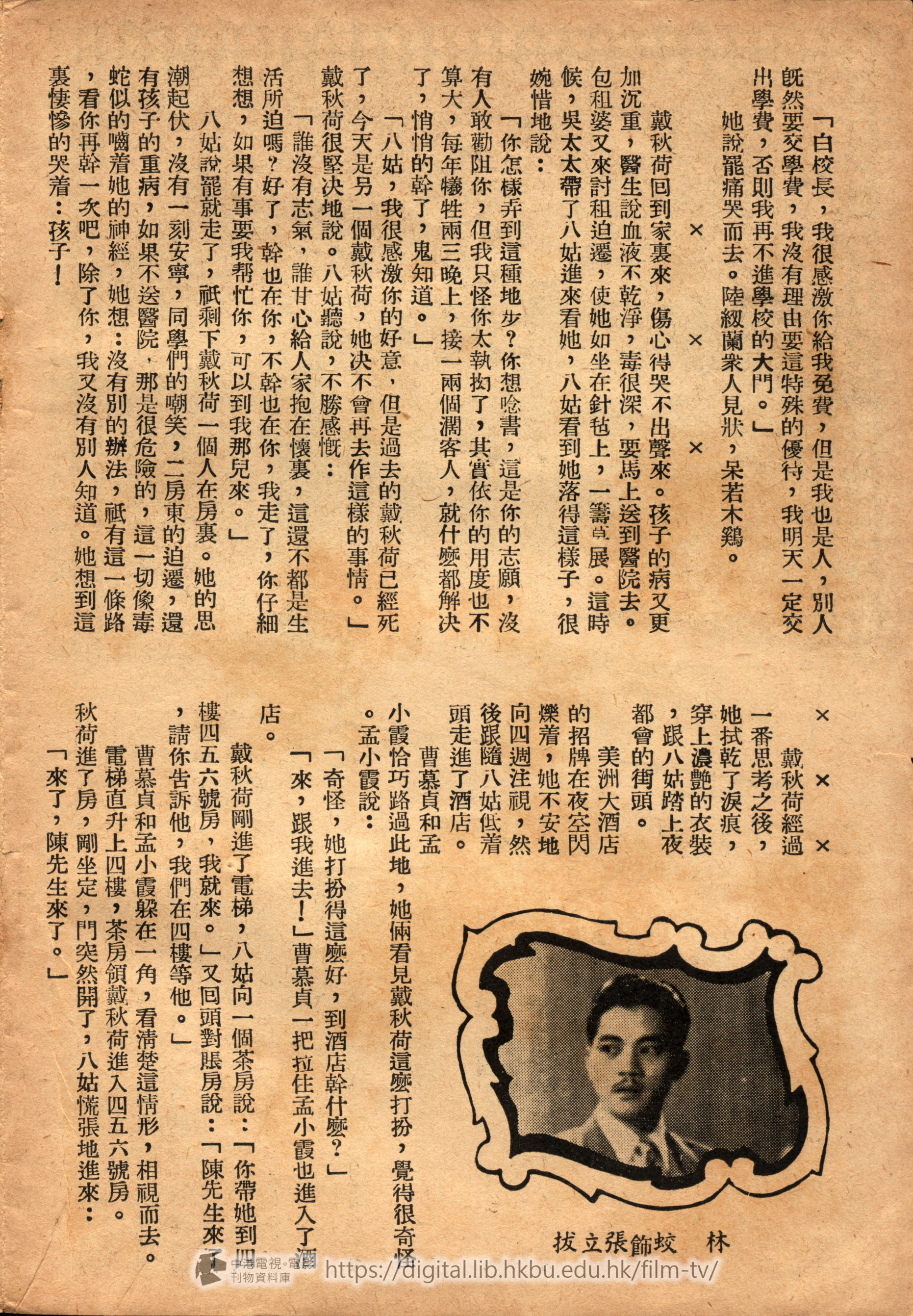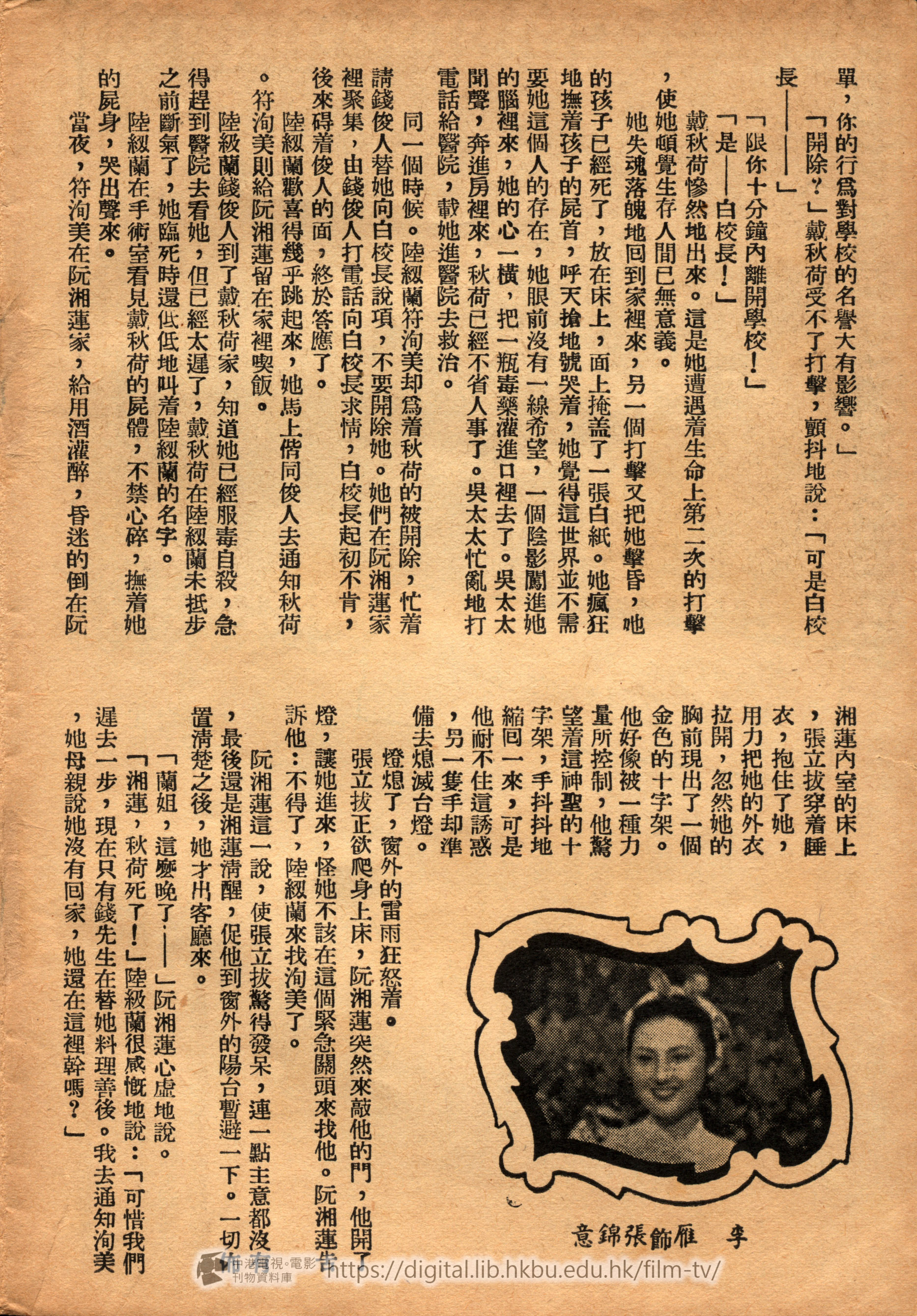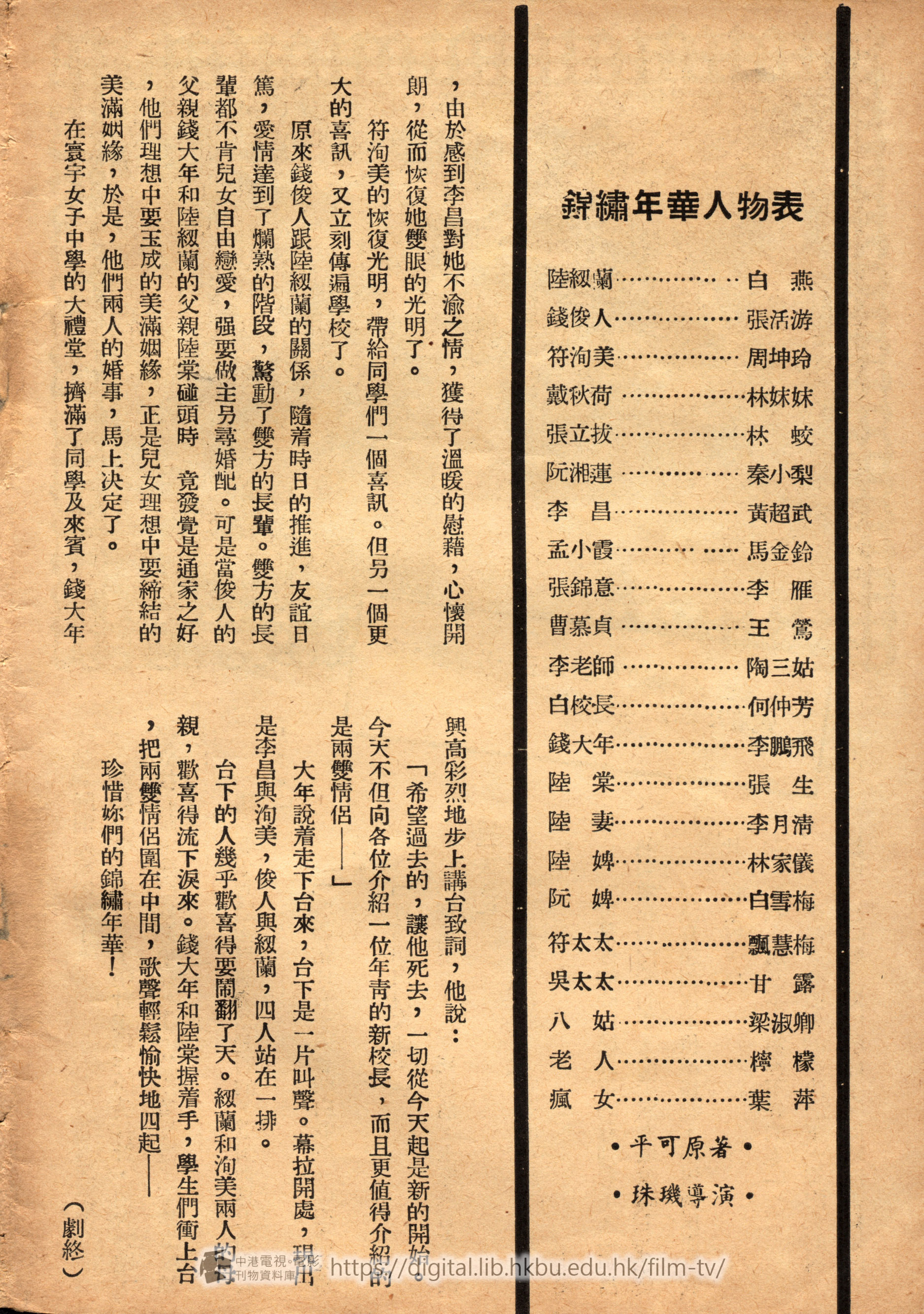一
春天的原野,柳浪聞鶯。
春江水暖,鴨兒優閒地在戲水;水中映出一羣女學生騎着脚車疾馳而過的倒影。她們是剛剛春遊歸來,一路快樂的歌唱着,歌醫着轉動的車輪飄送出來——
看哪,天邊的浮雲片片,
看哪,遍野的花兒迎風競艶,
我們投向春的懷抱,
把生命交付給大自然!
啊!歌唱吧,春天的兒女,
歌唱吧,幸福無邊!
莫等到春盡花殘,
辜負這錦繡年華!
她們的隊伍疾馳地轉彎,消失在叢林裏,一會兒囘到她們的學校——寰宇女子中學的門口。她們一個個跳下脚車來,那位肥婆李老師已站在門口迎着她們,要大家到校園去,有幾句話講,大家聽說,一哄地到校園去了。
在校園裏的操塲上,大家一字兒排列成行,李老師戴着近視眼鏡,手裏拿着一本簿子,一本正經地說:
「諸位同學,今天的週末遠足,大家一定都玩得非常開心,明天是星期,白天大家可以不用上課。可是晚上的晚會,大家一定都要出席,而且各人都要預備一點精彩的節目。」
李老師說着,幾個頑皮的同學,不禁竊竊在私議,有的竟哈哈大笑起來。李老師啼笑皆非地說:
「請大家靜些,怪不得人家說學校裏第二班的同學都是一羣猴子,你們比猴子還頑皮!哼!現在我把你們上個月的品行考驗成績報吿一下,品學兼優第一名——陸紉蘭。」
那個叫陸紉蘭的聽說,感到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
「第一名,好傢伙!」
李老師聞聲,囘過頭來,看見說這話的是曹慕貞,她瞪了她一眼:
「甚麽好傢伙,對同學有同情心,和氣而用功。——第二名符洵美。」
符洵美嬌羞答答地低着頭,孟小霞看了她一眼,推着她說:
「聽見沒有,第二名狀元。」
符洵美沒有做聲,李老師沉着臉說:
「其他的都及格,可是有三位同學要特別注意,一個是曹慕貞,成天只知道打球,踢球,其他功課都不好,要用功才行。第二個就是戴秋荷——」
戴秋荷聞聲,吃了一驚。李老師走到她跟前說:
「你這一期學費到今天還沒有交,知道嗎?要快點交來,如果每一個學生都像你,那學校不是要關門了嗎?」
「是,李老師!」
戴秋荷不好意思地應着。
「最後一個特別値得提出的是——」
李老師說着向同學巡視,她又習慣的把眼鏡向上一推,(每個人都有點不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走到阮湘蓮的面前突然停住了。阮湘蓮手上正拿着一面小鏡子在抹口紅,不想李老師已停在自己面前,她急忙把粉盒收起,故作立正狀。李老師大聲地叫着:
「阮湘蓮你手裏拿的是甚麽?拿來!」
「沒有甚麽?」阮湘蓮無可奈何的將粉盒鏡交給李老師。李老師一手接過來,打開一看,發現粉盒裏面,一面是鏡,另一面却貼着一個男人(張立拔)的照片,偏偏那張照片頑皮的對着她笑,她憤怒一的把紛盒盖上,兩眼瞪着湘蓮:
「阮湘蓮,你的私生活雖然有你的自由,但是你要小心,你是寰宇中學的學生,一切要爲着整個學校的名譽着想。」
「如果擦擦口紅就是破壞學校名譽,那我以後就不擦好了!」
「你在學校爲甚麼要擦口?」李老師話剛脫口,忽然想起了自己也擦口紅,轉口說:「你別以爲我也擦了口紅,我是老師,……而且你就是擦也不能夠在我給你說話的時候擦。」
「是!」阮湘蓮頑皮而誇張的說,引得衆人哈哈大笑起來。李老師氣得大半天講不出一句話。最後她突然命令解散。學生們有的對着她做鬼險,有的散去。她把近視眼鏡向上一推:
「簡直是一羣猴子!」
說着慢吞吞地走了。
陸紉蘭偕同符洵美,張錦意,孟小霞,戴秋荷,幾個人走進課室來取書,預備囘家。陸紉蘭對符洵美她們說:不應該以那種輕薄的態度對待李老師,她旣是我們的老師,不尊重她就等於不尊重自己。孟小霞聽說,故意地說:
「大姐怪不得考第一名,原來會尊重老師。」
「小鬼,你小心我打你的嘴。」陸紉蘭說。
「哎喲,不敢了,大姐。」
孟小霞裝腔作勢地說。阮湘蓮氣冲冲的跑進來,一路呌着:
「簡直不合時代,連擦口紅都不許,人家美國電影的女學生見到男學生都可以公開Kiss。」
陸紉蘭和符洵美這時候已檢好了書正欲囘去。阮湘蓮跑上來拉了拉符洵美:
「洵美,今天我有個朋友請我跳舞,你們去不去,多幾個熟人好玩些。」
「唔」符洵美聽說,不知道怎樣答覆,看看陸紉蘭,陸紉蘭說:
「你不是說要到我家裏溫習功課嗎?」
「對了!」符洵美恍然地說:「而且我也不會跳舞!」
「學啊!」阮湘蓮說:「我的小姐,二十世紀的女學生,不會跳舞,簡直是耻辱,一道去好不好?」
「改天吧,多謝了!」
符洵美說罷,偕着陸紉蘭張錦意等走了,在走廊上,陸紉蘭對符洵美說:
「洵美,希望你少與阮湘蓮多接近,她的行動思想,對你都不大有利的,尤其你又是這樣一個富於感情而意志薄弱的女孩子。」
「我根本不大跟她說話。」
「聽說她的錢都是一個男人供給的,名譽很不好聽。」
張錦意單刀直入地插進了這麽一句,符洵美瞟了她一眼:
「你老是愛背後說人家的是非,我覺得她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麼壞。」
她們一行,邊說邊走,到了校園,陸紉蘭突然停住了脚,奇怪地說:
「你們看那是誰?」
符洵美張錦意隨着陸敏蘭的手看去,……
暮色蒼茫中,校園裏是多麽荒涼的,戴秋荷一個人孤苦伶仃地低着頭坐在樹下,樹上鳥兒的歸巢,引起了她的感懷。樹葉被風片片吹落,打在她的身上,她隨口哼着:
「鳥花有家,樹兒有花,可憐我孤苦伶仃,漂泊天涯!」
她在地上隨便畫了幾個字:「我好苦啊!」
陸紉蘭符洵美張錦意靜靜地到她身邊來。陸紉蘭誠懇地撫慰着她:
「可有甚麼事情要我們幫忙你?」
「多謝!」戴秋荷的頭低得更利害:「沒有甚麽?」
「有甚麼不如意的事情可以吿訴我,是不是爲了學費?」
陸紉蘭溫純地說。戴秋荷半響才吐出一句話:
「不是這麼小的事,心裏的苦,說不出!」
她的話剛說出口,淚水就禁不住流下來。符洵美看見她哭,也跟着哭了:
「秋荷姐,你——別哭啊!」
「洵美,你這樣愈勸人家愈難過,你們先走吧,我送秋荷囘家。」
符洵美聽了陸紉蘭的話,戀戀不捨地偕同孟小霞張錦意走了。陸紉蘭拉着戴秋荷的手說:
「秋荷,雖然你沒有把你的身世吿訴我,但從你的眼神裏,我猜得出你的過去是隱藏着無限的傷心淚的,是嗎?秋荷!」
「你說的很對,我太羨慕你們!」戴秋荷很傷感的說。
「別這麽說,我們都是一樣的可憐虫,你別看我這麽高興,我的家庭也一樣的不幸福,不過ー切都要樂觀些,白校長的話你還記得嗎?這不合理的時代裏女人是最不幸的!」
「蘭姐,可是我是不幸中的最不幸的一個,沒有爸爸,媽媽,沒有親人,沒有家,甚麼也沒有!」
二
符洵美偕同張錦意孟小霞從校園裏走出來,慢慢走出校門口,她淚痕未乾,一路在談着戴秋荷的不幸。孟小霞說:
「聽說她以前結過婚,是個師長的小太太,後來師長不要她了,她自己要爭氣才考進了學校。」
「根本沒有考,」張錦意說:「是校長認識那位師長,大家爲了人情,才讓她讀書的。」
「這樣的人,我們應該幫助她!」
她們邊走邊談着,忽然前面開了一輛車來,經過水潭,濺了她們一身的水,尤其是洵美,外套幾乎全是泥水了。
「死人呀,有沒有眼睛啊!」
張錦意生氣地叫駡着,車子馬上停下來,車門開了,跳下車的是張立拔,他油腔滑調地說:
「對不起,車子沒有眼睛,可是開車子的人有眼睛。」
「你看濺了人家一身水!」
孟小霞這一說,張立拔已經發現符洵美的美麗:
「這眞抱歉!」
他說着拿出手絹,預備去替洵美擦水泥,但是美洵將外套脫下,羞澀地躱開:
「不用了,小霞,我們走吧!」
這時候阮湘蓮也趕出學校來,看見這情形不禁急問着:
「怎麼啦?立拔,咦,洵美,這怎麼囘事?」
「阮小姐,是我不小心,車子濺了你的同學一身水。」
「沒有關係,」符洵美說:「小霞,錦意,我們走吧!」
張立拔向阮湘蓮便了個眼色,阮湘蓮機警地說:
「這可不能饒了你。洵美,我來介紹,這是我的朋友張立拔先生,是留過洋鍍過金的,這位是符洵美小姐。這兩位都是我的同學。符洵美,我們今天罰他送你們囘去,好不好?」
「O.K,理當如此!」
張立拔如奉綸音的遵命。符洵美孟小霞張錦意同時說:
「不用了,我們走吧!」
阮湘蓮見狀,馬上提出主意來:
「那麼這樣,洵美,把外套交給他,罰他替你洗乾淨。」
「O.K,遵命辦理。」
張立拔仍是油腔滑調,符洵美欲待推辭,那身外套已給阮湘蓮强搶過去,她走上了車說:
「洵美,千萬別饒他,明天晚會上,我叫他送來給你。拜,拜!」
符洵美望着張立拔和阮湘蓮開車走了,感到了很討厭,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不禁哎喲了一聲:
「我,我,我外套口袋裏有東西!」
「有甚麽東西?」
張錦意孟小霞急問着,符洵美嗒然地一句話說不出來。
這一夜,張立拔在阮湘蓮家,他發現了符洵美外套有一封情書,他大聲地朗誦給阮湘蓮聽:
「——洵美,這是我寫給你的第廿九封信,如果你不再囘信給我,那我只有毀滅了我自己……李昌。」
「李昌,」阮湘蓮聽說笑出聲來搶了信過來說:「哦,原來是李老師的弟弟,這位寶貝,下面還有一排小字,說明天星期晚會他會來看她,瞧這裏還有張照片,也是寄給符小姐的!」
張立拔看着李昌土頭土腦的樣子,不禁哈哈大笑:
「簡直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不過,說實在的,我玩過的女人少說也有一打,我見了符小姐却有一點——」
「着迷,是不是?」阮湘蓮搶着說:「哼,你張開嘴我能看到你的肚腸子,你的意思我早明白,所以硬把外套拿囘來,給你下次見面的機會,懂不懂!」
「所以我這一生離不開你,不是別的,你眞了解我。要是你能給我把她弄上手,湘蓮,這一次不止給你學費,你以後的一切都由我負責!」
「你說話失信呢!」
「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中間有良心!」
「你的良心早黑了!」
「我是從美國囘來的,最講究的就是在女人面前守信用。」
「虧你好意思說,在外國甚麼沒有學會,只會玩女人——」
阮湘蓮話剛脫口,張立拔就走近來胡扯,電燈熄後,就是一串無恥的笑聲⋯⋯
三
星期日的晚上。
寰宇女子中學的禮堂,今晚佈置得特別講究,舞台上一塊方牌寫着「週末晚會」四個大字,幕帳下垂,有幾個學生在忙着招待來賓簽名,大槪是時間未到,所以好些人沒來。陸紉蘭在指揮一切,她是這晚會的總負責。白校長與李老師等出來,一羣老師都緊緊地跟隨尾後。白校長對陸紉蘭說:
「陸紉蘭,囘頭你們找四個同學招待董事長。」說着又面着李老師:「李老師今天這個晚會的意義,就是要錢董事長看看我們的成績,只要他滿意了,我們然後向他建議自蓋校舍的計劃。所以等一會你要選幾個特別會說話的同學招待吧!」
「好,好!我知道了,校長放心!」李老師說:「陸紉蘭,你囘頭通知符洵美阮湘蓮孟小霞張錦意,由你們四個招待校董,你總負責!」
「是,李老師!」陸紉蘭唯命是從的應了一聲。
白校長今晚走進走出,忙得滿頭大汗,她領導了一羣敎員,在校門口預備迎接董事長錢大年,等了好久,看見一輛車子開來,大家神經質地以爲是錢董事長來了,都鞠躬歡迎,誰知車門開了,下車的却是張立拔和阮湘蓮,弄得啼笑皆非。
張立拔和院湘蓮大模大樣地踏進禮堂來,阮湘蓮見了同學們就大呼小叫。白校長瞪了她一眼,呌她有禮貌些,別這樣輕浮。說罷就出去。阮湘蓮理都不理走近符洵美身邊說:
「洵美,今天張先生特地來向你陪罪的。」
「符小姐,昨天的事情眞對不起。」張立拔乘機附和着。符洵美不知如何是好地囘着:
「沒有甚麼關係,用不着這麽客氣!」
「可是他昨天晚上難過了一夜,覺得非買一件新衣服賠你不可,所以今天一大淸早,他就拉我上街,幫他挑選了這一件。」阮湘蓮說着把紙盒子打開給洵美看:「你看這顏色你喜歡嗎?」
「…………………………」
符洵美不知怎麼開口才好,那邊陸紉蘭她們已注意到了,覺得很奇怪。孟小霞吿訴紉蘭,這姓張的跟阮湘蓮走的,準不是好人。陸紉蘭納罕地說:「奇怪,洵美怎麽會認識這樣的人?」
張立拔仍在纏着符洵美,他說:
「如果符小姐不喜歡那一件,我明天再買一件!」
「不是,不是,哎喲,我眞不知道怎麼說!」
「洵美,張先生不是外人,你就收下吧!」
阮湘蓮强着符洵美接受那件外套,符洵美沒有主意,走過去徵求陸紉蘭的意見。陸紉蘭吿訴她,一個女孩子最好不要接受男孩子的東西。阮湘蓮怕陸紉蘭阻碍她的進行,和張立拔趕過來,她把張立拔介紹給陸紉蘭她們認識,張立拔和陸紉蘭一見如舊地油腔滑調牛皮一番,陸紉蘭好氣不好笑地敷衍着他。阮湘蓮乘機强把那件外套敎符洵美收下。
「來了,來了,來了!」
曹慕貞忽然呼叫着,陸紉蘭忙問是不是錢校董來了。
「不是的!」曹慕貞說:「你們看,是李老師的弟弟李昌,那個書呆子來了。」
衆人聽說都望過去,門口出現了李昌,他的外表的確不算好,但他的內在,的確存在着許多値得讚頌的地方。他進來動作有些侷促不安。符洵美看見李昌到來,覺得討厭,但陸紉蘭要她過去招待他,說不應該對付一個老實人這樣。符洵美無可奈何地走過去,李昌一見了她就說:
「符小姐,我給你的信收到嗎?」
「今天我是招待,李先生,這邊是來賓席。」
「多謝!」
李昌老實地說。符洵美於是帶他去找坐位。那邊張立拔偷偷地對阮湘蓮說:「原來是這麽一個傻小子!」阮湘蓮輕聲地說:「你的情敵!」
李昌在座位上坐下來。戴秋荷從門口無精打彩地進來,陸紉蘭看見,馬上迎上去:
「秋荷,你是不是不舒服?」
「不,沒有甚麽?」戴秋荷低低地說。
「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不,我早來了,我□我不敢進來。」
「爲甚麽?」
「我沒有交學費。」
「你放心,秋荷,我一定會幫忙你的。」
白校長和李老師等進來,因爲時間已經到了,董事長還沒有來,所以宣佈先行開會。符洵美出去打鐘,李昌也跟着她出來。她感到了很厭煩,請他快進去。這時候裏面的歌聲已響,莊嚴而又聖潔。李昌若有所感地對洵美說:
「你聽歌聲這麽莊嚴,正象徵着我對你的愛一樣純潔!」
「快進去吧,我都知道?改天再說吧!」
符洵美很焦急地說,李昌還不肯放鬆,他又說:
「我還有一句你聽我說完,等我大學畢業,我準備學醫,你贊成嗎?我沒有高的希望與夢想,我只想做點實際上的工作!」
「好,好,贊成,你快進去吧,囘頭校長看見了!」
「那末,今天晚上散了會,我在你家門口等你,我還有話說,記住,我一定等你的。」
「好,囘頭再說吧!」
符洵美說罷就走,李昌幸福地一笑,也隨着進去。
四
晚會的節目開始,白校長像一隻臘鴨似的步上講台致詞,她剛剛說到「諸位來賓諸位同學,今天是本校的週末晚會……」的時候,錢俊人衣冠齊整地步進禮堂來,他來遲了,靜靜的在找自己的位子;他找到了校董席就坐下來。陸紉蘭一眼瞥見馬上走到他身邊,輕聲地說:
「先生,對不起,這是校董席,請你坐到那邊去!」
「哦,對不起!」
錢俊人從座位上站起來,跟着陸紉蘭走。白校長對這位來遲的賓客,非常不滿,所以她停止了演講,注意他,等他找到了位子再說——
「我們很感激諸位來賓的光臨,所以,所以……」白校長說到這裡,已經接不下去,她輕聲地問李老師:「我剛才說到那裡了?」
「我也不曉得。」李老師哭喪着臉說。白校長站在台上,着急得不能下台,尷尬地說:
「所以——完了!」
白校長臉紅紅地走下台來,台下立卽响着一串莫明其妙的掌聲。陸紉蘭輕輕地走到秩序表前面撕去一張校長訓話的節目,然後宣佈:
「這一個節目是錢校董訓話,可是因爲錢先生沒有來,這個節目取消!」
「不,我就是代表。」
錢俊人從座位上站起來,全座的賓客不覺驚顧着他,他很客氣地說:
「家父有事不能出席,所以要我代表。」
「快請,我們歡迎校董訓話!」
白校長聽了俊人的聲明之後,急忙地請俊人登台。錢俊人態度文雅地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上講台。在台下,陸紉蘭覺得剛才叫俊人換座的舉動太唐突,暗對符詢美說槽糕,符洵美則笑說眞有趣!
錢俊人登台之後,先向大家道歉,說他遲到了,說時一眼看看陸紉蘭,陸紉蘭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錢俊人接着說:
「這間學校是在家父以及白校長以及各位老師努力奮鬥下而堅强的,存在了十個年頭,可是我們今天仔細檢討一下,所作的工作太少,只不過存在一些敎育形式,而缺少眞正的敎育內容。今天已不是孔夫子的時代,我們需耍新的敎育,新的智識,完了!」
錢俊人言簡意眩地說了幾句話就走下台來,台下立卽响着雷動的掌聲。陸紉蘭和符洵美相視,表示他說得很對。白校長忙地趨到俊人面前跟他握手:
「錢先生,剛才眞抱歉,大家不認識,而且我們也從沒有見過面。」
「這並沒有關係。」
錢俊人邊說邊走到座位來。陸紉蘭不好意思地請他到校董席上坐,但給俊人婉辭了。張立拔看見俊人坐下,跑過來和他打招呼,而且吿訴他自己的住址,原來俊人是張立拔從前的同學。
晚會照着程序進行。忽然有人來吿訴戴秋荷,外面有人找她,她輕輕應聲而去。陸紉蘭看見,不禁一怔,也偷偷地跟着去。
戴秋荷到了走廊,看見吳太太焦急地站在那兒,吳太太吿訴秋荷,她的孩子病了,熱度很高,要她馬上去,現在還讀什麼書?秋荷聽說,心很不安,答應馬上就去。但當她轉身的時候在柱曾碰見陸紉蘭,她不禁驚叫着:
「蘭姐!」
「剛才的話我都聽到了,」陸紉蘭說:「秋荷,爲什麽你有孩子不能吿訴我們,難道這就是恥辱!」
「輕聲一點,蘭姐,我怕人家知道我有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更看不起我。話長得很,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蘭姐我先囘去看看,等一會你有空請到我家裡來,我再跟你暢談。杏花巷五號,你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
「我曉得,你走吧!」
陸紉蘭目送着戴秋荷轉身而去。不勝感慨!
X X X
晚會散塲之後,阮湘蓮强邀符洵美到家裡去吃壽麵。陸紉蘭則到杏花巷探訪戴秋荷。
戴秋荷見陸紉蘭來看她,更加傷心地叫着蘭姐。陸紉蘭問她孩子怎麽樣?她很哀傷地說:
「我怕他是胎毒,我不瞞你說,我以前——」
「妳眞的出賣過自己,這是爲了……」
「爲了死去的媽媽不能入土,」戴秋荷說:「爲了替母親買棺材,我做了最下賤的職業。這不是人過的生活,我挨一年了,後來遇見了陳師長,算是他把我救出了火坑,我替他生下了毛毛,可是後來——」
「後來他又把你遺棄了?」
「不,我自己願意離開他,因爲後來我才知道他家裡已經有了太太。」
「這樣說,你離開他的理由□是値得同情的。」
「離開他,我無親無友,除了再去做妓女,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是我已經有了孩子,爲了這個小生命,我不能再去做。我决心重新做人,所以想讀書,想好好的過生活,但是——」
「但是這不合理的社會對你不能諒解,」陸紉蘭接着秋荷的話說:「你放心,你過去所做的,都不是你的錯,而錯在這個時代,你現在不能灰心,我們一定盡最大力量幫助你做好人,你現在還年靑,一切都不太遲。」
「我還年靑?」戴秋荷眼前突然現出一線光彩,陸紉蘭眞切地鼓勵着她:
「秋荷,現在正是向命運反抗的時候,你不用嘆息,大胆一點,緊强一點!」
「蘭姐,我一定記住你的話!」
戴秋荷說着,眼淚串串落下來。
陸紉蘭送她一點錢給孩子醫病,明天再幫她想辦法,然後辭別走了。其時已是深夜十一點鐘。
X X X
在阮湘蓮家裡。
阮湘蓮,符洵美,張立拔飯後正坐在沙發上閒談。壁上的報時鐘,噹噹地響着,符洵美聞聲,看着腕錶說:
「十一點了,我該囘去,太晚了媽媽不放心的。」
「忙什麽?」張立拔攔住着她「再玩一會,反正有我送你囘去。」
「洵美要囘去就讓她囘去吧,今天學校開了那麽久的會,也該早點囘去休息,以後玩的機會還多。」
阮湘蓮看穿張立拔猴急的心事,攔着忙住了他,張立拔無可奈何地說:
「好過幾天我們找多幾位朋友玩玩!」
「好!」
符洵美很高興地答應他。阮湘蓮乘機向她說:
「洵美,以後我們常在一起,希望你和立拔多多聯絡,你別看立拔年紀輕又有錢,可從不亂交女朋友。他留學囘來,有多少小姐追求他,他都不要。」
張立拔聽說,也大吹了他的法螺。符洵美不知說什麽好,看看張立拔,正低頭微笑,然後坐他的汽車囘家。
張立拔送符洵美到她家門口,戀戀不捨地和她道別。符洵美拿着張立拔送給她的外套,正準備按門鈴的時候,忽然聽見有人叫她,她轉過身來,看見李昌在黑暗的牆角立著,她嚇了一跳地說:
「原來是你站在這兒?」
「我已經這在兒站了三個小時了。」李昌沉重地說。
「在這兒站了三個小時?——你真傻!」
「是的,我現在承認我是個傻子,可是你別忘了,天底下只有傻子才是最眞誠的,希望你多相信傻子的話,而且不要上聰明人的當!」
「不早了,明天談吧!」符洵美很厭煩地說,但李昌不肯走,他要求她讓他的話說完。而且再交給她一封信,符洵美不耐煩地笑他又是一封信,李昌却懇切地說:
「別覺得這是可笑的事,希望你能看上這封信,再見,什麽時候想見我,我什麽時候都會來到你的身邊。」
李昌說罷,慘然而去。符洵美想把那封信撕碎,但終於打開來看,那信上寫着————
爲了不願你煩惱,不願放棄自己生存的意義,我决心不再來看你,這也是最後一封信,希望你好好的珍視你的年華,更希望你別忘記在天涯海角還有一個傻瓜,在眞誠地愛着你。 李昌
符洵美看完了這封信,有了些同情,她不禁向街道的那邊望去,輕輕地呌了一聲:李先生——
五
翌晨,符洵美乘了單車到陸紉蘭家來見紉蘭,她吿訴李昌昨夜給她的信,笑他是個大傻禺。陸紉蘭聽說,很莊嚴鄭重地說:
「洵美,我吿訴你,世界上只有傻瓜才是最可靠的,李昌對人很誠懇的,你不要總把他看成傻瓜刺傷了他的心。」
「我並沒有刺傷他的心。」符洵美天眞地說。
「你把他這出于熱誠的信,隨便給人看,來使人嘲笑他,愚弄他,他知道了,這不傷心嗎?」
「我並沒有給別人看,只不過給你看看有什麽關係,你以前自己說的,我有什麽事別瞞你,可是人家現在聽你的話,又不好。」
「你眞聽我的話嗎?」陸紉蘭說:「聽我的話,昨天晚上散會以後,你就不應該到湘蓮家裏去。」
「爲什麽,玩玩有什麽關係?」
「玩玩?和阮湘蓮這樣人玩了,是沒有好處的,昨天晚上叫張立拔輕浮得很,你要小心。」
「蘭姐,我聽你的話,以後我决不跟張立拔在一起玩了,就是阮湘蓮家也决不再去了。」
「好,不過今天還要去一次,陪我去找張立拔。」
「做什麼?」符洵美奇怪的問。
「爲了秋荷的學費問題,我昨天想了一夜,打聽錢俊人的住址,我想求錢俊人向白校長說,可不可以把戴秋荷的學費免了。」
陸紉蘭說着就拉符洵美同到阮湘蓮家找張立拔。
張立拔昨夜在阮湘蓮家,天亮了,還念念不忘符洵美,請湘蓮碰到她,代他問她好。忽然聽到陸紉蘭來訪他,急得團團轉,最後湘蓮只好叫暫時避到床底下去。
陸紉蘭偕符洵美進來,紉蘭見了阮湘蓮,問張立拔有沒有在這兒,要找他問錢俊人的住址。阮湘蓮推說沒有來,紉蘭正想走了,恰巧錢俊人進來,他也是來找張立拔的,說是老同學幾年沒見面,昨天晚上在晚會上見到,立拔給他兩個地址,所以隨便到這兒來看看。阮湘蓮說張立拔不住這兒,不過常來玩玩而已。接着,她又笑笑說:
「這太巧了,陸小姐正準備找你。」
「找我?」錢俊人一愕地看着陸紉蘭,陸紉蘭點着頭說:
「是的,有點事,想請錢先生帮忙!」
「是關於——」
「一個同學的學費問題,戴秋荷是個非常肯奮鬥的學生,但是爲了沒有錢交學費,將要失學了,錢先生這樣愛護同學,維護敎育,應該同情她的處境,向學校請求免費!」
錢俊人聽了陸紉蘭的話,很佩服她的愛護同學的熱心,馬上答應她,代打電話向白校長磋商。
錢俊人一個電話,白校長立卽答應載秋荷免費。但當佈吿揭示之後,曹慕貞,張錦意竟大肆冷嘲熱諷,阮湘蓮也從旁推波助瀾,使戴秋荷不能忍受,她排開了眾人,走到揭示牌前,把佈吿用力撕下,瘋狂地跑到校長室去。白校長見她來勢洶洶,不覺驚呆。戴秋荷臉色靑白地說:
「白校長,我很感激你給我免費,但是我也是人,別人旣然要交學費,我沒有理由要這特殊的優待,我明天一定交出學費,否則我再不進學校的大門。」
她說罷痛哭而去。陸紉蘭衆人見狀,呆若木鷄。
X X X
戴秋荷囘到家裏來,傷心得哭不出聲來。孩子的病又更加沉重,醫生說血液不乾淨,毒很深,要馬上送到醫院去。包租婆又來討租迫遷,使她如坐在針毡上,一籌莫展。這時候,吳太太帶了八姑進來看她,八姑看到她落得這樣子,很婉惜地說:
「你怎樣弄到這種地步?你想唸書,這是你的志願,沒有人敢勸阻你,但我只怪你太執抝了,其實依你的用度也不算大,每年犧牲兩三晚上,接一兩個濶客人,就什麽都解决了,悄悄的幹了,鬼知道。」
「八姑,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是過去的戴秋荷已經死了,今天是另一個戴秋荷,她决不會再去作這樣的事情。」戴秋荷很堅决地說。八姑聽說,不勝感慨:
「誰沒有志氣,誰甘心給人家抱在懷裏,這還不都是生活所迫嗎?好了,幹也在你,不幹也在你,我走了,你仔細想想,如果有事要我帮忙你,可以到我那兒來。」
八姑說罷就走了,祇剩下戴秋荷一個人在房裏。她的思潮起伏,沒有一刻安寧,同學們的嘲笑,二房東的迫遷,還有孩子的重病,如果不送醫院,那是很危險的,這一切像毒蛇似的嚙着她的神經,她想:沒有別的辦法,祗有這一條路,看你再幹一次吧,除了你,我又沒有別人知道。她想到這裏悽慘的哭着:孩子!
X X X
戴秋荷經過一番思考之後,她拭乾了淚痕,穿上濃艶的衣裝,跟八姑踏上夜都會的街頭。
美洲大酒店的招牌在夜空閃爍着,她不安地向四週注視,然後跟隨八姑低着頭走進了酒店。
曹慕貞和孟小霞恰巧路過此地,她倆看見戴秋荷這麼打扮,覺得很奇怪。孟小霞說:
「奇怪,她打扮得這麽好,到酒店幹什麽?」
「來,跟我進去!」曹慕貞一把拉住孟小霞也進入了酒店。
戴秋荷剛進了電梯,八姑向一個茶房說:「你帶她到四樓四五六號房,我就來。」又囘頭對賬房說:「陳先生來了,請你吿訴他,我們在四樓等他。」
曹慕貞和孟小霞躱在一角,看淸楚這情形,相視而去。
電梯直升上四樓,茶房領戴秋荷進入四五六號房。秋荷進了房,剛坐定,門突然開了,八姑慌張地進來:
「來了,陳先生來了。」
秋荷聽說,地緊張整整頭髮,彎下腰去拉拉衣服,當她把腰慢慢伸直起來,往門外一望,但她一定睛,不禁大吃一驚,在門外站着的却是張立拔。張立拔也在意料不到地注視着秋荷,兩人相視良久,張立拔一步一步地走向秋荷那邊,秋荷不知所措地呆立不動。張立拔笑嘻嘻地說:「啊!原來是戴小姐,今天幸會了,哈哈哈……」
「沒有想到是你!」戴秋荷羞憤滿面地說。
「這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哈哈哈……」
張立拔說着,用手去摸她的臉,戴秋荷一時火起,排脫了他的手,跑了出來。
六
戴秋荷再度賣淫的秘密,給孟小霞曹慕貞揭穿之後,立卽成爲校中同學談話的中心。許多同學都在竊竊私議,對戴秋荷投擲了鄙夷的眼光,曹慕貞甚至拒絕和她同位而坐。
學校當局旣知道了這件事,認爲有這樣一個學生是不名譽的,所以白校長立卽傳戴秋荷進校長室來。戴秋荷見了白校長,白校長面目狰獰地說:
「戴秋荷,我叫你來的意思,你一定很明白。」
「是的,學費我已帶來了,在這兒!」戴秋荷懦怯地說。
「不用了,學校已經把你開除了,理由很簡單,你的行爲對學校的名譽大有影響。」
「開除?」戴秋荷受不了打擊,顫抖地說:「可是白校長————」
「限你十分鐘內離開學校!」
「是——白校長!」
戴秋荷慘然地出來。這是她遭遇着生命上第二次的打擊,使她頓覺生存人間已無意義。
她失魂落魄地囘到家裡來,另一個打擊又把她擊昏,她的孩子巳經死了,放在床上,面上掩盖了一張白紙。她瘋狂地撫着孩子的屍首,呼天搶地號哭着,她覺得這世界並不需要她這個人的存在,她眼前沒有一線希望,一個陰影闖進她的腦裡來,她的心一橫,把一瓶毒藥灌進口裡去了。吳太太聞聲,奔進房裡來,秋荷已經不省人事了。吳太太忙亂地打電話給醫院,載她進醫院去救治。
同一個時候。陸紉蘭符洵美却爲着秋荷的被開除,忙着請錢俊人替她向白校長說項,不要開除她。她們在阮湘蓮家裡聚集,由錢俊人打電話向白校長求情,白校長起初不肯,後來碍着俊人的面,終於答應了。
陸紉蘭歡喜得幾乎跳起來,她馬上偕同俊人去通知秋荷。符洵美則給阮湘蓮留在家裡喫飯。
陸紉蘭錢俊人到了戴秋荷家,知道她已經服毒自殺,急得趕到醫院去看她,但已經太遲了,戴秋荷在陸紉蘭未抵步之前斷氣了,她臨死時還低低地叫着陸紉蘭的名字。
陸紉蘭在手術室看見戴秋荷的屍體,不禁心碎,撫着她的屍身,哭出聲來。
當夜,符洵美在阮湘蓮家,給用酒灌醉,昏迷的倒在阮湘蓮內室的床上,張立拔穿着睡衣,抱住了她,用力把她的外衣拉開,忽然她的胸前現出了一個金色的十字架。他好像被一種力量所控制,他驚望着這神聖的十字架,手抖抖地縮囘一來,可是他耐不住這誘惑,另一隻手却準備去熄滅台燈。
燈熄了,窗外的雷雨狂怒着。
張立拔正欲爬身上床,阮湘蓮突然來敲他的門,他開了燈,讓她進來怪她不該在這個緊急關頭來找他。阮湘蓮吿訴他:不得了,陸紉蘭來找洵美了。
阮湘蓮這一說,使張立拔驚得發呆,連一點主意都沒有,最後還是湘蓮清醒,促他到窗外的陽台暫避一下。一切佈置淸楚之後,她才出客廳來。
「蘭姐,這麽晚了——」阮湘蓮心虛地說。
「湘蓮,秋荷死了!」陸級蘭很感慨地說:「可惜我們遲去一步,現在只有錢先生在替她料理善後。我去通知洵美,她母親說她沒有囘家,她還在這裡幹嗎?」
「她剛才喝了兩杯酒,醉得不能動,所以我就叫她睡在我這兒了。」
「她喝了酒——」陸紉蘭驚駭地說:「現在人呢?」
「在我房裡。」
陸紉蘭聽說,立卽走入湘蓮內房、看見符洵美還沉睡着,她把洵美推醒,叫了輛街車送她囘家去,把她從那個色魔的手裡拯救了出來。
X X X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
夕陽西下,在郊外的墳地。陸紉蘭符洵美,錢俊人,張立拔,阮湘蓮,吳太太和曹慕貞,孟小霞,張錦意諸人,站在剛入土的秋荷的坆旁。同學們唱着追悼歌,聲音是那麽沉重而暗慘。這時候張錦意覺得從前尖嘴滑舌,太對不起了戴秋荷,禁不住大哭起來,符洵美也泣不成聲。
在歸途上,張立拔說這裡離開他的別墅不遠,耍錢俊人他們到那兒休息一下,然後再囘家。錢俊人本來不要去,但經不起張立拔的强邀和阮湘蓮的慫恿,終於跟着大夥兒去了。
張家古舊的別墅門口,因爲多年失修,有些垣毀與荒涼,紫籐盤滿了牆柱,彷彿使人感到一些陰霾,尤其是黃昏更使人感到了恐怖。
張立拔和錢俊人的汽車在門口停下來,立拔首先下車去按門鈴,衆人隨着下車。
「就是這兒,以前家父每年夏天都來住一些時候,他老人家去世以後,這些年我在外邊,這房子除了一個看門的簡直沒有人來,所以顯得有些荒涼!」
張立拔向錢俊人介紹他這間別墅,大家眼對這高大的舊屋,都帶着些恐怖的心情。驀然,沉重的大門慢慢的開了,呀的一聲,使人有些寒意,接着是一個年老的守門人,手擎着燭火出現在門口,他的臉上長滿了鬚,兩隻眼睛,瞪着前面,態度陰森奇異,動作慢緩而呆板,他低低地呌着一聲少爺。張立拔吿訴大家,他是他的看門的老頭。衆人注視這個老人,老人也用奇怪的眼睛注視着衆人。
大家緩慢而猶疑地進去,門呀的一聲已關上了。
老人執着燭火帶領衆人入客廳。
符洵美偷偷地對陸紉蘭說:
「蘭姐,這房子眞有點怕人!」
「唔,」陸紉蘭低聲說:「我看張立拔跟這房子一樣可怕,昨天晚上,你不該喝酒。下次不可以這樣大意,戴秋荷的死就是我們的敎訓,因爲她以前走錯了路,所以——」
「你別提戴秋荷好吧,怪怕人的!」
提到了戴秋荷,符洵美脆弱的心猶有餘怖,她依偎在陸紉蘭的身邊。
那邊張立拔正在向錢俊人介紹他這個別墅的歷史性,耍大家上樓參觀。
大家聽他的話跟着上樓,老人執着燭火帶路。
張立拔看見衆人上樓,他拉住阮湘蓮說:
「昨天晚上失去了好機會,我想今晚留洵美下來。」
「不行,今天她好像有點躱着我,而且這麽多人一齊來的,怎麽好留她一個人呢?」
「不得到洵美,我死也不甘心。」
張立拔舐着嘴唇說,阮湘蓮瞟了他一眼。
錢俊人衆人上樓,樓上陰森得可怕,他們正在一間房子瀏覽,忽然瞥見一個女子,披着髮,臉色蒼白,兩手呆板的下垂,立在黑暗處。錢俊人大叱一聲,問是誰?那女子呆立不動,衆人緊張地擠在一起。那女子突然向衆人撲來,而且發出瘋狂的笑聲,大家失魂落魄地向樓下跑,那女人也追着衆人下樓。張立拔看見馬上把她抓住,厲聲詰問着老頭:
「誰把她放出來的,把她拉上去鎖起來。」
老人把那女人扶送上樓去。張立拔吿訴錢俊人,說那女人是瘋子,請大家不耍理她。但大家經過這一嚇,也沒有心再在這兒逗下去,走了。
七
錢俊人因爲料理了戴秋荷的善後過於勞瘁,和在張立拔的別墅給那瘋女人一嚇,竟吿病倒了。
陸紉蘭好幾天沒有看見錢俊人,心裡好像失去了什麽似的。阮湘蓮從張立拔口裡探知錢俊人有病,而且念念不忘陸紉蘭。她把這些話吿訴符洵美張錦意她們,大家聽說,當着陸紉蘭的面,向她取笑,害得陸紉蘭不好意思。最後阮湘蓮提議去探病。大家一致贊成,而且推陸紉蘭爲代表,符洵美阮湘蓮作陪。衆意難却,陸級蘭祗得羞答答地應承了。
陸紉蘭符洵美阮湘蓮三人,拿着鮮花到錢俊人家來,見了錢俊人之後,符洵美和阮湘蓮借故走出房外,留陸紉蘭在房裡,陸級蘭要攔住她們已來不及,無可奈何,██地問着錢俊人:
「是那天你受了驚嗎?」
「本來我心臟就有點不健康。」錢俊人說。
「吃了藥嗎?」
「謝謝你,吃了藥了,今天早上我已經叫人送些錢給吳太太替戴姑娘淸了賬。」
「你的熱心很使人感動!」
「到是因爲你的熱心感動了我!」錢俊人溫純地一笑。
「別這麽說,同學們對你的爲人,都很欽佩,所以她們要我代表來看看你。」
「我知道你會來看我的!」
「爲什麽?」陸紉蘭微笑地問。
「說不出理由,只是這麽想,你覺得奇怪嗎?」
錢俊人說着,一雙溫柔的眼睛,注視着陸級蘭,陸紉蘭含情脈脈地低下頭來。俊人從抽斗裡取出一本包好了的書送給她,笑着說:
「你不知道,你眞的不知道?我送給你這本書,叫什麼名字,你把它帶囘去看看就會明白的。」
陸紉蘭接過了那本書之後,和錢俊人吿辭,跟着符洵美阮湘蓮出來。
X X X
陸紉蘭囘到了家裡,心裡有點異樣的感覺。她把錢俊人送給她那書的紙包打開來!——
初戀
巴金譯
這兩個字奪了她的視線,她迷惑的把這本書再包起,臉上一陣熱,有些紅雲。她的心跳得很利害,躺在床上,但天花板到處都是——
「初戀,初戀,初戀,初戀!」
她把書藏在枕頭下,閉着眼,做着處女的綺夢,緩慢地她走入了夢的天國了。
X X X
錢俊人和陸紉蘭已由初戀而進至熱戀的階段了,他們常常相約出遊,幸福的氣氛溫暖地圍住着他倆。
另一方面,張立拔除謀誘騙符洵美的計劃,也進行到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日,阮湘蓮張立拔又約符洵美到郊外野餐。阮湘蓮向符洵美說:
「洵美,你別那麼傻,什麼事都去問蘭姐,現在你該相信了吧,她自己還不是一樣。」
「不過,錢俊人的確値得人歡喜,那麼斯文,那麽熱心!」
符洵美低着頭說,阮湘蓮忙的問:「那末你覺得立拔呢?」
「人家都說他壞,可是我看他還好!」
「你千萬別信人家的話,這都是人家破壞他的。」
她們兩人正在閒談。張立拔在汽車那邊呌湘蓮過去,他輕聲對她說:
「今天可是最後的關頭,我决不能再放過她。」
「我明白,羊入虎口,不過你要小心!」
「囘頭我準備——」
張立拔在阮湘蓮耳邊吱咕一陣,湘蓮說他太毒,伸手向他要錢,他給了她,兩人一笑,携着點心走向洵美這邊來。
張立拔在草地開了留聲機,迷人的音樂嬝娜地飄蕩出來。符洵美不知道自己的惡運將吿降臨,她無邪地沉醉在美妙的音樂裏。
X X X
同一個時間,錢俊人和陸紉蘭也在郊外水邊談心。他們由友情到了事業,談到了將來。錢俊人說:
「我囘國的時候,下過决心把父親辦的這間學校辦好,可是總覺得少了一個帮手!」
「你可以去找一個帮手啊!」陸紉蘭說。
「現在不用找,我已經找到了。」
「找到了在那兒?」
「就在眼前!」錢俊人看看陸紉蘭,陸紉蘭嬌羞地說:
「你覺得我可以做你的帮手嗎?可是我父親今天要我結婚。」
「結婚?你答應了嗎?」
「我老早就决定,一天不能自立,一天不結婚。我不倚賴男人過一生。」
「沒有想到你有這麽偉大的意志,我的眼光沒有錯,希望你不要投降,决定——」
錢俊人說着熱切地拉着她的手。在歡愉的夕陽影裏,他係踏上歸途。
X X X
是夜,陸紉蘭剛睡去的時候,符洵美的母親忽來找她,說洵美還沒有囘去,什麽地方都找過了,都沒有她的踪影。陸紉蘭聽說大驚,馬上打電話去問阮湘蓮,阮湘蓮說老早已經和她分手了,就把電話放下。陸紉蘭和符老太急得什麽似的。
一點也不錯,阮湘蓮早就借故和符洵美分手了。符洵美已經給張立拔騙到那座恐怖的別墅去了。
到了別墅,符洵美看不見湘蓮,她驚懼地知道被騙。她失常的呌着湘蓮,可是沒有囘應。她眼淚簌簌地嚷着要囘去,她衝到門口,門口出現了那個僵屍般的瘋女人,她嚇得退囘了來。
張立拔叫看門的老人送她上樓,自己把客廳的門鎖了,得意的笑着。
老人帶着符洵美上樓,送她走入了那間陰森的房子裏去。老人吿訴她,當她睡了的時候,把門鎖起來,半夜裏有人推門,可不要怕。符洵美聽說,驚震地說:
「你說什麽?半夜有人推門?」
「唉,這也是你的造化,到了這間房子裏來的女子就別想好好出去!」老人搖着頭嘆息,符洵美發抖地說:
「爲什麽:你說這兒眞有鬼嗎?」
「有的,有鬼,是一個魔鬼,不瞞你說,小姐,那個瘋女人就是我的女兒,四年前被這個魔鬼騙到這兒來强姦了,他有勢力,我沒有辦法,只好忍氣帮他看房子,靠他一碗飯吃。」
「剛才那個瘋女兒就是你的女兒?」
「她被人姦汚了一時憤怒就氣瘋了!」
「這個魔鬼在那兒?」
「就在樓下——今天晚上輪到你了!」
符洵美聽說,驚得跪下地來,要求老人救她走,老人不勝傷心,他低低地嘆息,靜靜地領她走了出來。四週寂靜如死,只聽見門呀的一聲。在轉角處,張立拔站在那裏,叱了一聲,一個巴掌打在老人臉上,惡駡着他,然後,一步一步地迫着符洵美,他把符洵美迫進了原來那間房間,關上了門。
房裏立刻傳出了符洵美的掙扎聲,哀呼聲,接着是張立拔的一串獰笑聲……
那個女人瘋跑來,拚命的擊着門,她用頭向門上撞,原野傳來了幾聲狗吠聲。
符洵美憤怒而發狂地由室內跑出來,她衣衫不整,披散頭髪,狂奔下樓,她兩眼直直衝出門口。張立拔也由樓上追下來。
符洵美出了大門,迷茫地向前面奔,她奔向林中,沒有目的地向前奔,張立拔也跟着追,他在後面叫着:「洵美!洵美!」
四野無聲,囘答的只是森林的反音,他一邊呼喚,一邊走地跑到河邊,見無去路,四顧無人,忽然發現河灘洵美遺下的一隻鞋,他忙的拾起來,大吃一驚,意識到她已投河自殺了。
銀色的浪花翻滾,像代表千萬人的憤怒。張立拔一陣寒慄,慢慢地後退,急轉身發足狂奔忽然給什麽絆倒了,他急爬起來,看見一塊墓碑寫着——
「戴秋荷之墓」
他不禁胆寒神落,恐怖與痛苦交加,彷彿遠處有一個披髮女人的黑影出現……
他慌忙地向公路奔,到了他的汽車邊,他的心稍定,但發見前面火光燭天,憤怒的火燄,呑沒了整個別墅。
八
報紙登載著符洵美投河遇救的消息。
符洵美被救傷車載到中山醫院去,出人意料之外的負責醫治她的就是那個被目爲傻瓜的李昌。李昌在細心地檢驗着她的傷狀,她因爲受刺激過度,又加上在水裏的時間過長,所以她的眼睛巳經失明了。
陸紉蘭符老太及錢俊人等趕到醫院來,符老太看見女兒這形狀,不禁傷心地流下淚來,她拉着女兒的手,抽噎地說:
「孩子,媽在這兒,你怎麽啦?你到底爲了什麼?」
「媽,我看不見你,我對不起你!」
符洵美哭出聲來。陸紉蘭走近前來說:
「洵美,好妹妹,你說爲了什麽,你說啊!」
「是蘭姐嗎?」符洵美痛苦地說:「我不能說…」
陸紉蘭正待追問下去,已給醫生李昌制止,請她們不要限她多說話,勸大家暫且出去。陸紉蘭要求讓她一個人留住陪伴洵美,得到李昌的同意。她一待衆人出去後,很快地貼在洵美耳說:
「洵美,是不是昨天阮湘蓮與張立拔欺侮了你?你千萬別瞞我,洵美!」
「蘭姐,……別問我……」符洵美傷心的哭了:「我完了,我一生都完了,我現在只後悔不聽你的話。」
「洵美,你說是不是張立拔——」陸紉蘭緊急地追問,符洵美哀怨地說:
「如果我死了,蘭姐,你要替我伸寃,張立拔他强姦了我!」
符洵美說罷又是一陣痛哭,陸紉蘭意外地哦了一聲:
「什麽?我早就担心他對你,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居然這麼毒!」
「蘭姐,你千萬不能把這事吿訴別人!」
「不,這件事我不能不說,被人欺侮了,不能反抗,那太可憐了,洵美,我們一定要找他!」
陸紉蘭說着,不顧符洵美的勸阻,她和俊人及一班同學,分頭去報吿學校當局及警署,一面去找阮湘蓮及張立拔。但張立拔和阮湘蓮已聞風逃了。
公路上,張立拔駕着汽車瘋狂地奔馳,後面有警車疾馳地追着,到了山下,張立拔心慌,把汽車撞翻了,發火燃燒,他和阮湘蓮給燒死了。
在醫院中,李昌拿了藥針在爲符洵美打針,他吿訴她,張立拔和阮湘蓮已經翻車身死了。符洵美聽說,不禁慨嘆地說:
「現在我才知道你以前的話是對的,這個世界上聰明人太多。」
「我相信你有一天會明白我的。」李昌笑着說。
「可惜明白得太遲。」
「別這麽說,人在死以前,永遠沒有太遲的一天。」
「現在我了解了,可是我已經看不見你了。」
「可是你的心已經眞正的看到我了。」李昌熱切地拉着洵美的手,洵美感激地說說:
「沒有想到你不但不怪我,不恨我反而對我比以前更好。」
「我永遠都不會對你不好的!」
在李昌悉心盡力的醫治之下,符洵美的病,經過一些時間,慢慢的好了。同時洵美創傷的,由於感到李昌對她不渝之情,獲得了溫暖的慰藉,心懷開朗,從而恢復她雙眼的光明了。
符洵美的恢復光明,帶給同學們一個喜訊。但另一個更大的喜訊,又立刻傳遍學校了。
原來錢俊人跟陸紉蘭的關係,隨着時日的推進,友誼日篤,愛情達到了爛熟的階段,驚動了雙方的長輩。雙方的長輩都不肯兒女自由戀愛,强要做主另尋婚配。可是當俊人的父親錢大年和陸紉蘭的父親陸棠碰頭時□竟發覺是通家之好,他們理想中要玉成的美滿姻緣,正是兒女理想中要締結的美滿姻緣,於是,他們兩人的婚事,馬上决定了。
在寰宇女子中學的大禮堂,擠滿了同學及來賓,錢大年興高彩烈地步上講台致詞,他說:
「希望過去的,讓他死去,一切從今天起是新的開始。今天不但向各位介紹一位年靑的新校長,而且更値得介紹的是兩雙情侶——」
大年說着走下台來,台下是一片叫聲。幕拉開處,現出是李昌與洵美,俊人與紉蘭,四人站在一排。
台下的人幾乎歡喜得要鬧翻了天。紉蘭和洵美兩人的母親,歡喜得流下淚來。錢大年和陸棠握着手,學生們衝上台,把兩雙情侶圍在中間,歌聲輕鬆愉快地四起——
珍惜妳們的錦繡年華!
(劇終)
一
春天的原野,柳浪聞鶯。
春江水暖,鴨兒優閒地在戲水;水中映出一羣女學生騎着脚車疾馳而過的倒影。她們是剛剛春遊歸來,一路快樂的歌唱着,歌醫着轉動的車輪飄送出來——
看哪,天邊的浮雲片片,
看哪,遍野的花兒迎風競艶,
我們投向春的懷抱,
把生命交付給大自然!
啊!歌唱吧,春天的兒女,
歌唱吧,幸福無邊!
莫等到春盡花殘,
辜負這錦繡年華!
她們的隊伍疾馳地轉彎,消失在叢林裏,一會兒囘到她們的學校——寰宇女子中學的門口。她們一個個跳下脚車來,那位肥婆李老師已站在門口迎着她們,要大家到校園去,有幾句話講,大家聽說,一哄地到校園去了。
在校園裏的操塲上,大家一字兒排列成行,李老師戴着近視眼鏡,手裏拿着一本簿子,一本正經地說:
「諸位同學,今天的週末遠足,大家一定都玩得非常開心,明天是星期,白天大家可以不用上課。可是晚上的晚會,大家一定都要出席,而且各人都要預備一點精彩的節目。」
李老師說着,幾個頑皮的同學,不禁竊竊在私議,有的竟哈哈大笑起來。李老師啼笑皆非地說:
「請大家靜些,怪不得人家說學校裏第二班的同學都是一羣猴子,你們比猴子還頑皮!哼!現在我把你們上個月的品行考驗成績報吿一下,品學兼優第一名——陸紉蘭。」
那個叫陸紉蘭的聽說,感到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
「第一名,好傢伙!」
李老師聞聲,囘過頭來,看見說這話的是曹慕貞,她瞪了她一眼:
「甚麽好傢伙,對同學有同情心,和氣而用功。——第二名符洵美。」
符洵美嬌羞答答地低着頭,孟小霞看了她一眼,推着她說:
「聽見沒有,第二名狀元。」
符洵美沒有做聲,李老師沉着臉說:
「其他的都及格,可是有三位同學要特別注意,一個是曹慕貞,成天只知道打球,踢球,其他功課都不好,要用功才行。第二個就是戴秋荷——」
戴秋荷聞聲,吃了一驚。李老師走到她跟前說:
「你這一期學費到今天還沒有交,知道嗎?要快點交來,如果每一個學生都像你,那學校不是要關門了嗎?」
「是,李老師!」
戴秋荷不好意思地應着。
「最後一個特別値得提出的是——」
李老師說着向同學巡視,她又習慣的把眼鏡向上一推,(每個人都有點不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走到阮湘蓮的面前突然停住了。阮湘蓮手上正拿着一面小鏡子在抹口紅,不想李老師已停在自己面前,她急忙把粉盒收起,故作立正狀。李老師大聲地叫着:
「阮湘蓮你手裏拿的是甚麽?拿來!」
「沒有甚麽?」阮湘蓮無可奈何的將粉盒鏡交給李老師。李老師一手接過來,打開一看,發現粉盒裏面,一面是鏡,另一面却貼着一個男人(張立拔)的照片,偏偏那張照片頑皮的對着她笑,她憤怒一的把紛盒盖上,兩眼瞪着湘蓮:
「阮湘蓮,你的私生活雖然有你的自由,但是你要小心,你是寰宇中學的學生,一切要爲着整個學校的名譽着想。」
「如果擦擦口紅就是破壞學校名譽,那我以後就不擦好了!」
「你在學校爲甚麼要擦口?」李老師話剛脫口,忽然想起了自己也擦口紅,轉口說:「你別以爲我也擦了口紅,我是老師,……而且你就是擦也不能夠在我給你說話的時候擦。」
「是!」阮湘蓮頑皮而誇張的說,引得衆人哈哈大笑起來。李老師氣得大半天講不出一句話。最後她突然命令解散。學生們有的對着她做鬼險,有的散去。她把近視眼鏡向上一推:
「簡直是一羣猴子!」
說着慢吞吞地走了。
陸紉蘭偕同符洵美,張錦意,孟小霞,戴秋荷,幾個人走進課室來取書,預備囘家。陸紉蘭對符洵美她們說:不應該以那種輕薄的態度對待李老師,她旣是我們的老師,不尊重她就等於不尊重自己。孟小霞聽說,故意地說:
「大姐怪不得考第一名,原來會尊重老師。」
「小鬼,你小心我打你的嘴。」陸紉蘭說。
「哎喲,不敢了,大姐。」
孟小霞裝腔作勢地說。阮湘蓮氣冲冲的跑進來,一路呌着:
「簡直不合時代,連擦口紅都不許,人家美國電影的女學生見到男學生都可以公開Kiss。」
陸紉蘭和符洵美這時候已檢好了書正欲囘去。阮湘蓮跑上來拉了拉符洵美:
「洵美,今天我有個朋友請我跳舞,你們去不去,多幾個熟人好玩些。」
「唔」符洵美聽說,不知道怎樣答覆,看看陸紉蘭,陸紉蘭說:
「你不是說要到我家裏溫習功課嗎?」
「對了!」符洵美恍然地說:「而且我也不會跳舞!」
「學啊!」阮湘蓮說:「我的小姐,二十世紀的女學生,不會跳舞,簡直是耻辱,一道去好不好?」
「改天吧,多謝了!」
符洵美說罷,偕着陸紉蘭張錦意等走了,在走廊上,陸紉蘭對符洵美說:
「洵美,希望你少與阮湘蓮多接近,她的行動思想,對你都不大有利的,尤其你又是這樣一個富於感情而意志薄弱的女孩子。」
「我根本不大跟她說話。」
「聽說她的錢都是一個男人供給的,名譽很不好聽。」
張錦意單刀直入地插進了這麽一句,符洵美瞟了她一眼:
「你老是愛背後說人家的是非,我覺得她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麼壞。」
她們一行,邊說邊走,到了校園,陸紉蘭突然停住了脚,奇怪地說:
「你們看那是誰?」
符洵美張錦意隨着陸敏蘭的手看去,……
暮色蒼茫中,校園裏是多麽荒涼的,戴秋荷一個人孤苦伶仃地低着頭坐在樹下,樹上鳥兒的歸巢,引起了她的感懷。樹葉被風片片吹落,打在她的身上,她隨口哼着:
「鳥花有家,樹兒有花,可憐我孤苦伶仃,漂泊天涯!」
她在地上隨便畫了幾個字:「我好苦啊!」
陸紉蘭符洵美張錦意靜靜地到她身邊來。陸紉蘭誠懇地撫慰着她:
「可有甚麼事情要我們幫忙你?」
「多謝!」戴秋荷的頭低得更利害:「沒有甚麽?」
「有甚麼不如意的事情可以吿訴我,是不是爲了學費?」
陸紉蘭溫純地說。戴秋荷半響才吐出一句話:
「不是這麼小的事,心裏的苦,說不出!」
她的話剛說出口,淚水就禁不住流下來。符洵美看見她哭,也跟着哭了:
「秋荷姐,你——別哭啊!」
「洵美,你這樣愈勸人家愈難過,你們先走吧,我送秋荷囘家。」
符洵美聽了陸紉蘭的話,戀戀不捨地偕同孟小霞張錦意走了。陸紉蘭拉着戴秋荷的手說:
「秋荷,雖然你沒有把你的身世吿訴我,但從你的眼神裏,我猜得出你的過去是隱藏着無限的傷心淚的,是嗎?秋荷!」
「你說的很對,我太羨慕你們!」戴秋荷很傷感的說。
「別這麽說,我們都是一樣的可憐虫,你別看我這麽高興,我的家庭也一樣的不幸福,不過ー切都要樂觀些,白校長的話你還記得嗎?這不合理的時代裏女人是最不幸的!」
「蘭姐,可是我是不幸中的最不幸的一個,沒有爸爸,媽媽,沒有親人,沒有家,甚麼也沒有!」
二
符洵美偕同張錦意孟小霞從校園裏走出來,慢慢走出校門口,她淚痕未乾,一路在談着戴秋荷的不幸。孟小霞說:
「聽說她以前結過婚,是個師長的小太太,後來師長不要她了,她自己要爭氣才考進了學校。」
「根本沒有考,」張錦意說:「是校長認識那位師長,大家爲了人情,才讓她讀書的。」
「這樣的人,我們應該幫助她!」
她們邊走邊談着,忽然前面開了一輛車來,經過水潭,濺了她們一身的水,尤其是洵美,外套幾乎全是泥水了。
「死人呀,有沒有眼睛啊!」
張錦意生氣地叫駡着,車子馬上停下來,車門開了,跳下車的是張立拔,他油腔滑調地說:
「對不起,車子沒有眼睛,可是開車子的人有眼睛。」
「你看濺了人家一身水!」
孟小霞這一說,張立拔已經發現符洵美的美麗:
「這眞抱歉!」
他說着拿出手絹,預備去替洵美擦水泥,但是美洵將外套脫下,羞澀地躱開:
「不用了,小霞,我們走吧!」
這時候阮湘蓮也趕出學校來,看見這情形不禁急問着:
「怎麼啦?立拔,咦,洵美,這怎麼囘事?」
「阮小姐,是我不小心,車子濺了你的同學一身水。」
「沒有關係,」符洵美說:「小霞,錦意,我們走吧!」
張立拔向阮湘蓮便了個眼色,阮湘蓮機警地說:
「這可不能饒了你。洵美,我來介紹,這是我的朋友張立拔先生,是留過洋鍍過金的,這位是符洵美小姐。這兩位都是我的同學。符洵美,我們今天罰他送你們囘去,好不好?」
「O.K,理當如此!」
張立拔如奉綸音的遵命。符洵美孟小霞張錦意同時說:
「不用了,我們走吧!」
阮湘蓮見狀,馬上提出主意來:
「那麼這樣,洵美,把外套交給他,罰他替你洗乾淨。」
「O.K,遵命辦理。」
張立拔仍是油腔滑調,符洵美欲待推辭,那身外套已給阮湘蓮强搶過去,她走上了車說:
「洵美,千萬別饒他,明天晚會上,我叫他送來給你。拜,拜!」
符洵美望着張立拔和阮湘蓮開車走了,感到了很討厭,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不禁哎喲了一聲:
「我,我,我外套口袋裏有東西!」
「有甚麽東西?」
張錦意孟小霞急問着,符洵美嗒然地一句話說不出來。
這一夜,張立拔在阮湘蓮家,他發現了符洵美外套有一封情書,他大聲地朗誦給阮湘蓮聽:
「——洵美,這是我寫給你的第廿九封信,如果你不再囘信給我,那我只有毀滅了我自己……李昌。」
「李昌,」阮湘蓮聽說笑出聲來搶了信過來說:「哦,原來是李老師的弟弟,這位寶貝,下面還有一排小字,說明天星期晚會他會來看她,瞧這裏還有張照片,也是寄給符小姐的!」
張立拔看着李昌土頭土腦的樣子,不禁哈哈大笑:
「簡直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不過,說實在的,我玩過的女人少說也有一打,我見了符小姐却有一點——」
「着迷,是不是?」阮湘蓮搶着說:「哼,你張開嘴我能看到你的肚腸子,你的意思我早明白,所以硬把外套拿囘來,給你下次見面的機會,懂不懂!」
「所以我這一生離不開你,不是別的,你眞了解我。要是你能給我把她弄上手,湘蓮,這一次不止給你學費,你以後的一切都由我負責!」
「你說話失信呢!」
「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中間有良心!」
「你的良心早黑了!」
「我是從美國囘來的,最講究的就是在女人面前守信用。」
「虧你好意思說,在外國甚麼沒有學會,只會玩女人——」
阮湘蓮話剛脫口,張立拔就走近來胡扯,電燈熄後,就是一串無恥的笑聲⋯⋯
三
星期日的晚上。
寰宇女子中學的禮堂,今晚佈置得特別講究,舞台上一塊方牌寫着「週末晚會」四個大字,幕帳下垂,有幾個學生在忙着招待來賓簽名,大槪是時間未到,所以好些人沒來。陸紉蘭在指揮一切,她是這晚會的總負責。白校長與李老師等出來,一羣老師都緊緊地跟隨尾後。白校長對陸紉蘭說:
「陸紉蘭,囘頭你們找四個同學招待董事長。」說着又面着李老師:「李老師今天這個晚會的意義,就是要錢董事長看看我們的成績,只要他滿意了,我們然後向他建議自蓋校舍的計劃。所以等一會你要選幾個特別會說話的同學招待吧!」
「好,好!我知道了,校長放心!」李老師說:「陸紉蘭,你囘頭通知符洵美阮湘蓮孟小霞張錦意,由你們四個招待校董,你總負責!」
「是,李老師!」陸紉蘭唯命是從的應了一聲。
白校長今晚走進走出,忙得滿頭大汗,她領導了一羣敎員,在校門口預備迎接董事長錢大年,等了好久,看見一輛車子開來,大家神經質地以爲是錢董事長來了,都鞠躬歡迎,誰知車門開了,下車的却是張立拔和阮湘蓮,弄得啼笑皆非。
張立拔和院湘蓮大模大樣地踏進禮堂來,阮湘蓮見了同學們就大呼小叫。白校長瞪了她一眼,呌她有禮貌些,別這樣輕浮。說罷就出去。阮湘蓮理都不理走近符洵美身邊說:
「洵美,今天張先生特地來向你陪罪的。」
「符小姐,昨天的事情眞對不起。」張立拔乘機附和着。符洵美不知如何是好地囘着:
「沒有甚麼關係,用不着這麽客氣!」
「可是他昨天晚上難過了一夜,覺得非買一件新衣服賠你不可,所以今天一大淸早,他就拉我上街,幫他挑選了這一件。」阮湘蓮說着把紙盒子打開給洵美看:「你看這顏色你喜歡嗎?」
「…………………………」
符洵美不知怎麼開口才好,那邊陸紉蘭她們已注意到了,覺得很奇怪。孟小霞吿訴紉蘭,這姓張的跟阮湘蓮走的,準不是好人。陸紉蘭納罕地說:「奇怪,洵美怎麽會認識這樣的人?」
張立拔仍在纏着符洵美,他說:
「如果符小姐不喜歡那一件,我明天再買一件!」
「不是,不是,哎喲,我眞不知道怎麼說!」
「洵美,張先生不是外人,你就收下吧!」
阮湘蓮强着符洵美接受那件外套,符洵美沒有主意,走過去徵求陸紉蘭的意見。陸紉蘭吿訴她,一個女孩子最好不要接受男孩子的東西。阮湘蓮怕陸紉蘭阻碍她的進行,和張立拔趕過來,她把張立拔介紹給陸紉蘭她們認識,張立拔和陸紉蘭一見如舊地油腔滑調牛皮一番,陸紉蘭好氣不好笑地敷衍着他。阮湘蓮乘機强把那件外套敎符洵美收下。
「來了,來了,來了!」
曹慕貞忽然呼叫着,陸紉蘭忙問是不是錢校董來了。
「不是的!」曹慕貞說:「你們看,是李老師的弟弟李昌,那個書呆子來了。」
衆人聽說都望過去,門口出現了李昌,他的外表的確不算好,但他的內在,的確存在着許多値得讚頌的地方。他進來動作有些侷促不安。符洵美看見李昌到來,覺得討厭,但陸紉蘭要她過去招待他,說不應該對付一個老實人這樣。符洵美無可奈何地走過去,李昌一見了她就說:
「符小姐,我給你的信收到嗎?」
「今天我是招待,李先生,這邊是來賓席。」
「多謝!」
李昌老實地說。符洵美於是帶他去找坐位。那邊張立拔偷偷地對阮湘蓮說:「原來是這麽一個傻小子!」阮湘蓮輕聲地說:「你的情敵!」
李昌在座位上坐下來。戴秋荷從門口無精打彩地進來,陸紉蘭看見,馬上迎上去:
「秋荷,你是不是不舒服?」
「不,沒有甚麽?」戴秋荷低低地說。
「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不,我早來了,我□我不敢進來。」
「爲甚麽?」
「我沒有交學費。」
「你放心,秋荷,我一定會幫忙你的。」
白校長和李老師等進來,因爲時間已經到了,董事長還沒有來,所以宣佈先行開會。符洵美出去打鐘,李昌也跟着她出來。她感到了很厭煩,請他快進去。這時候裏面的歌聲已響,莊嚴而又聖潔。李昌若有所感地對洵美說:
「你聽歌聲這麽莊嚴,正象徵着我對你的愛一樣純潔!」
「快進去吧,我都知道?改天再說吧!」
符洵美很焦急地說,李昌還不肯放鬆,他又說:
「我還有一句你聽我說完,等我大學畢業,我準備學醫,你贊成嗎?我沒有高的希望與夢想,我只想做點實際上的工作!」
「好,好,贊成,你快進去吧,囘頭校長看見了!」
「那末,今天晚上散了會,我在你家門口等你,我還有話說,記住,我一定等你的。」
「好,囘頭再說吧!」
符洵美說罷就走,李昌幸福地一笑,也隨着進去。
四
晚會的節目開始,白校長像一隻臘鴨似的步上講台致詞,她剛剛說到「諸位來賓諸位同學,今天是本校的週末晚會……」的時候,錢俊人衣冠齊整地步進禮堂來,他來遲了,靜靜的在找自己的位子;他找到了校董席就坐下來。陸紉蘭一眼瞥見馬上走到他身邊,輕聲地說:
「先生,對不起,這是校董席,請你坐到那邊去!」
「哦,對不起!」
錢俊人從座位上站起來,跟着陸紉蘭走。白校長對這位來遲的賓客,非常不滿,所以她停止了演講,注意他,等他找到了位子再說——
「我們很感激諸位來賓的光臨,所以,所以……」白校長說到這裡,已經接不下去,她輕聲地問李老師:「我剛才說到那裡了?」
「我也不曉得。」李老師哭喪着臉說。白校長站在台上,着急得不能下台,尷尬地說:
「所以——完了!」
白校長臉紅紅地走下台來,台下立卽响着一串莫明其妙的掌聲。陸紉蘭輕輕地走到秩序表前面撕去一張校長訓話的節目,然後宣佈:
「這一個節目是錢校董訓話,可是因爲錢先生沒有來,這個節目取消!」
「不,我就是代表。」
錢俊人從座位上站起來,全座的賓客不覺驚顧着他,他很客氣地說:
「家父有事不能出席,所以要我代表。」
「快請,我們歡迎校董訓話!」
白校長聽了俊人的聲明之後,急忙地請俊人登台。錢俊人態度文雅地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上講台。在台下,陸紉蘭覺得剛才叫俊人換座的舉動太唐突,暗對符詢美說槽糕,符洵美則笑說眞有趣!
錢俊人登台之後,先向大家道歉,說他遲到了,說時一眼看看陸紉蘭,陸紉蘭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錢俊人接着說:
「這間學校是在家父以及白校長以及各位老師努力奮鬥下而堅强的,存在了十個年頭,可是我們今天仔細檢討一下,所作的工作太少,只不過存在一些敎育形式,而缺少眞正的敎育內容。今天已不是孔夫子的時代,我們需耍新的敎育,新的智識,完了!」
錢俊人言簡意眩地說了幾句話就走下台來,台下立卽响着雷動的掌聲。陸紉蘭和符洵美相視,表示他說得很對。白校長忙地趨到俊人面前跟他握手:
「錢先生,剛才眞抱歉,大家不認識,而且我們也從沒有見過面。」
「這並沒有關係。」
錢俊人邊說邊走到座位來。陸紉蘭不好意思地請他到校董席上坐,但給俊人婉辭了。張立拔看見俊人坐下,跑過來和他打招呼,而且吿訴他自己的住址,原來俊人是張立拔從前的同學。
晚會照着程序進行。忽然有人來吿訴戴秋荷,外面有人找她,她輕輕應聲而去。陸紉蘭看見,不禁一怔,也偷偷地跟着去。
戴秋荷到了走廊,看見吳太太焦急地站在那兒,吳太太吿訴秋荷,她的孩子病了,熱度很高,要她馬上去,現在還讀什麼書?秋荷聽說,心很不安,答應馬上就去。但當她轉身的時候在柱曾碰見陸紉蘭,她不禁驚叫着:
「蘭姐!」
「剛才的話我都聽到了,」陸紉蘭說:「秋荷,爲什麽你有孩子不能吿訴我們,難道這就是恥辱!」
「輕聲一點,蘭姐,我怕人家知道我有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更看不起我。話長得很,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蘭姐我先囘去看看,等一會你有空請到我家裡來,我再跟你暢談。杏花巷五號,你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
「我曉得,你走吧!」
陸紉蘭目送着戴秋荷轉身而去。不勝感慨!
X X X
晚會散塲之後,阮湘蓮强邀符洵美到家裡去吃壽麵。陸紉蘭則到杏花巷探訪戴秋荷。
戴秋荷見陸紉蘭來看她,更加傷心地叫着蘭姐。陸紉蘭問她孩子怎麽樣?她很哀傷地說:
「我怕他是胎毒,我不瞞你說,我以前——」
「妳眞的出賣過自己,這是爲了……」
「爲了死去的媽媽不能入土,」戴秋荷說:「爲了替母親買棺材,我做了最下賤的職業。這不是人過的生活,我挨一年了,後來遇見了陳師長,算是他把我救出了火坑,我替他生下了毛毛,可是後來——」
「後來他又把你遺棄了?」
「不,我自己願意離開他,因爲後來我才知道他家裡已經有了太太。」
「這樣說,你離開他的理由□是値得同情的。」
「離開他,我無親無友,除了再去做妓女,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是我已經有了孩子,爲了這個小生命,我不能再去做。我决心重新做人,所以想讀書,想好好的過生活,但是——」
「但是這不合理的社會對你不能諒解,」陸紉蘭接着秋荷的話說:「你放心,你過去所做的,都不是你的錯,而錯在這個時代,你現在不能灰心,我們一定盡最大力量幫助你做好人,你現在還年靑,一切都不太遲。」
「我還年靑?」戴秋荷眼前突然現出一線光彩,陸紉蘭眞切地鼓勵着她:
「秋荷,現在正是向命運反抗的時候,你不用嘆息,大胆一點,緊强一點!」
「蘭姐,我一定記住你的話!」
戴秋荷說着,眼淚串串落下來。
陸紉蘭送她一點錢給孩子醫病,明天再幫她想辦法,然後辭別走了。其時已是深夜十一點鐘。
X X X
在阮湘蓮家裡。
阮湘蓮,符洵美,張立拔飯後正坐在沙發上閒談。壁上的報時鐘,噹噹地響着,符洵美聞聲,看着腕錶說:
「十一點了,我該囘去,太晚了媽媽不放心的。」
「忙什麽?」張立拔攔住着她「再玩一會,反正有我送你囘去。」
「洵美要囘去就讓她囘去吧,今天學校開了那麽久的會,也該早點囘去休息,以後玩的機會還多。」
阮湘蓮看穿張立拔猴急的心事,攔着忙住了他,張立拔無可奈何地說:
「好過幾天我們找多幾位朋友玩玩!」
「好!」
符洵美很高興地答應他。阮湘蓮乘機向她說:
「洵美,以後我們常在一起,希望你和立拔多多聯絡,你別看立拔年紀輕又有錢,可從不亂交女朋友。他留學囘來,有多少小姐追求他,他都不要。」
張立拔聽說,也大吹了他的法螺。符洵美不知說什麽好,看看張立拔,正低頭微笑,然後坐他的汽車囘家。
張立拔送符洵美到她家門口,戀戀不捨地和她道別。符洵美拿着張立拔送給她的外套,正準備按門鈴的時候,忽然聽見有人叫她,她轉過身來,看見李昌在黑暗的牆角立著,她嚇了一跳地說:
「原來是你站在這兒?」
「我已經這在兒站了三個小時了。」李昌沉重地說。
「在這兒站了三個小時?——你真傻!」
「是的,我現在承認我是個傻子,可是你別忘了,天底下只有傻子才是最眞誠的,希望你多相信傻子的話,而且不要上聰明人的當!」
「不早了,明天談吧!」符洵美很厭煩地說,但李昌不肯走,他要求她讓他的話說完。而且再交給她一封信,符洵美不耐煩地笑他又是一封信,李昌却懇切地說:
「別覺得這是可笑的事,希望你能看上這封信,再見,什麽時候想見我,我什麽時候都會來到你的身邊。」
李昌說罷,慘然而去。符洵美想把那封信撕碎,但終於打開來看,那信上寫着————
爲了不願你煩惱,不願放棄自己生存的意義,我决心不再來看你,這也是最後一封信,希望你好好的珍視你的年華,更希望你別忘記在天涯海角還有一個傻瓜,在眞誠地愛着你。 李昌
符洵美看完了這封信,有了些同情,她不禁向街道的那邊望去,輕輕地呌了一聲:李先生——
五
翌晨,符洵美乘了單車到陸紉蘭家來見紉蘭,她吿訴李昌昨夜給她的信,笑他是個大傻禺。陸紉蘭聽說,很莊嚴鄭重地說:
「洵美,我吿訴你,世界上只有傻瓜才是最可靠的,李昌對人很誠懇的,你不要總把他看成傻瓜刺傷了他的心。」
「我並沒有刺傷他的心。」符洵美天眞地說。
「你把他這出于熱誠的信,隨便給人看,來使人嘲笑他,愚弄他,他知道了,這不傷心嗎?」
「我並沒有給別人看,只不過給你看看有什麽關係,你以前自己說的,我有什麽事別瞞你,可是人家現在聽你的話,又不好。」
「你眞聽我的話嗎?」陸紉蘭說:「聽我的話,昨天晚上散會以後,你就不應該到湘蓮家裏去。」
「爲什麽,玩玩有什麽關係?」
「玩玩?和阮湘蓮這樣人玩了,是沒有好處的,昨天晚上叫張立拔輕浮得很,你要小心。」
「蘭姐,我聽你的話,以後我决不跟張立拔在一起玩了,就是阮湘蓮家也决不再去了。」
「好,不過今天還要去一次,陪我去找張立拔。」
「做什麼?」符洵美奇怪的問。
「爲了秋荷的學費問題,我昨天想了一夜,打聽錢俊人的住址,我想求錢俊人向白校長說,可不可以把戴秋荷的學費免了。」
陸紉蘭說着就拉符洵美同到阮湘蓮家找張立拔。
張立拔昨夜在阮湘蓮家,天亮了,還念念不忘符洵美,請湘蓮碰到她,代他問她好。忽然聽到陸紉蘭來訪他,急得團團轉,最後湘蓮只好叫暫時避到床底下去。
陸紉蘭偕符洵美進來,紉蘭見了阮湘蓮,問張立拔有沒有在這兒,要找他問錢俊人的住址。阮湘蓮推說沒有來,紉蘭正想走了,恰巧錢俊人進來,他也是來找張立拔的,說是老同學幾年沒見面,昨天晚上在晚會上見到,立拔給他兩個地址,所以隨便到這兒來看看。阮湘蓮說張立拔不住這兒,不過常來玩玩而已。接着,她又笑笑說:
「這太巧了,陸小姐正準備找你。」
「找我?」錢俊人一愕地看着陸紉蘭,陸紉蘭點着頭說:
「是的,有點事,想請錢先生帮忙!」
「是關於——」
「一個同學的學費問題,戴秋荷是個非常肯奮鬥的學生,但是爲了沒有錢交學費,將要失學了,錢先生這樣愛護同學,維護敎育,應該同情她的處境,向學校請求免費!」
錢俊人聽了陸紉蘭的話,很佩服她的愛護同學的熱心,馬上答應她,代打電話向白校長磋商。
錢俊人一個電話,白校長立卽答應載秋荷免費。但當佈吿揭示之後,曹慕貞,張錦意竟大肆冷嘲熱諷,阮湘蓮也從旁推波助瀾,使戴秋荷不能忍受,她排開了眾人,走到揭示牌前,把佈吿用力撕下,瘋狂地跑到校長室去。白校長見她來勢洶洶,不覺驚呆。戴秋荷臉色靑白地說:
「白校長,我很感激你給我免費,但是我也是人,別人旣然要交學費,我沒有理由要這特殊的優待,我明天一定交出學費,否則我再不進學校的大門。」
她說罷痛哭而去。陸紉蘭衆人見狀,呆若木鷄。
X X X
戴秋荷囘到家裏來,傷心得哭不出聲來。孩子的病又更加沉重,醫生說血液不乾淨,毒很深,要馬上送到醫院去。包租婆又來討租迫遷,使她如坐在針毡上,一籌莫展。這時候,吳太太帶了八姑進來看她,八姑看到她落得這樣子,很婉惜地說:
「你怎樣弄到這種地步?你想唸書,這是你的志願,沒有人敢勸阻你,但我只怪你太執抝了,其實依你的用度也不算大,每年犧牲兩三晚上,接一兩個濶客人,就什麽都解决了,悄悄的幹了,鬼知道。」
「八姑,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是過去的戴秋荷已經死了,今天是另一個戴秋荷,她决不會再去作這樣的事情。」戴秋荷很堅决地說。八姑聽說,不勝感慨:
「誰沒有志氣,誰甘心給人家抱在懷裏,這還不都是生活所迫嗎?好了,幹也在你,不幹也在你,我走了,你仔細想想,如果有事要我帮忙你,可以到我那兒來。」
八姑說罷就走了,祇剩下戴秋荷一個人在房裏。她的思潮起伏,沒有一刻安寧,同學們的嘲笑,二房東的迫遷,還有孩子的重病,如果不送醫院,那是很危險的,這一切像毒蛇似的嚙着她的神經,她想:沒有別的辦法,祗有這一條路,看你再幹一次吧,除了你,我又沒有別人知道。她想到這裏悽慘的哭着:孩子!
X X X
戴秋荷經過一番思考之後,她拭乾了淚痕,穿上濃艶的衣裝,跟八姑踏上夜都會的街頭。
美洲大酒店的招牌在夜空閃爍着,她不安地向四週注視,然後跟隨八姑低着頭走進了酒店。
曹慕貞和孟小霞恰巧路過此地,她倆看見戴秋荷這麼打扮,覺得很奇怪。孟小霞說:
「奇怪,她打扮得這麽好,到酒店幹什麽?」
「來,跟我進去!」曹慕貞一把拉住孟小霞也進入了酒店。
戴秋荷剛進了電梯,八姑向一個茶房說:「你帶她到四樓四五六號房,我就來。」又囘頭對賬房說:「陳先生來了,請你吿訴他,我們在四樓等他。」
曹慕貞和孟小霞躱在一角,看淸楚這情形,相視而去。
電梯直升上四樓,茶房領戴秋荷進入四五六號房。秋荷進了房,剛坐定,門突然開了,八姑慌張地進來:
「來了,陳先生來了。」
秋荷聽說,地緊張整整頭髮,彎下腰去拉拉衣服,當她把腰慢慢伸直起來,往門外一望,但她一定睛,不禁大吃一驚,在門外站着的却是張立拔。張立拔也在意料不到地注視着秋荷,兩人相視良久,張立拔一步一步地走向秋荷那邊,秋荷不知所措地呆立不動。張立拔笑嘻嘻地說:「啊!原來是戴小姐,今天幸會了,哈哈哈……」
「沒有想到是你!」戴秋荷羞憤滿面地說。
「這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哈哈哈……」
張立拔說着,用手去摸她的臉,戴秋荷一時火起,排脫了他的手,跑了出來。
六
戴秋荷再度賣淫的秘密,給孟小霞曹慕貞揭穿之後,立卽成爲校中同學談話的中心。許多同學都在竊竊私議,對戴秋荷投擲了鄙夷的眼光,曹慕貞甚至拒絕和她同位而坐。
學校當局旣知道了這件事,認爲有這樣一個學生是不名譽的,所以白校長立卽傳戴秋荷進校長室來。戴秋荷見了白校長,白校長面目狰獰地說:
「戴秋荷,我叫你來的意思,你一定很明白。」
「是的,學費我已帶來了,在這兒!」戴秋荷懦怯地說。
「不用了,學校已經把你開除了,理由很簡單,你的行爲對學校的名譽大有影響。」
「開除?」戴秋荷受不了打擊,顫抖地說:「可是白校長————」
「限你十分鐘內離開學校!」
「是——白校長!」
戴秋荷慘然地出來。這是她遭遇着生命上第二次的打擊,使她頓覺生存人間已無意義。
她失魂落魄地囘到家裡來,另一個打擊又把她擊昏,她的孩子巳經死了,放在床上,面上掩盖了一張白紙。她瘋狂地撫着孩子的屍首,呼天搶地號哭着,她覺得這世界並不需要她這個人的存在,她眼前沒有一線希望,一個陰影闖進她的腦裡來,她的心一橫,把一瓶毒藥灌進口裡去了。吳太太聞聲,奔進房裡來,秋荷已經不省人事了。吳太太忙亂地打電話給醫院,載她進醫院去救治。
同一個時候。陸紉蘭符洵美却爲着秋荷的被開除,忙着請錢俊人替她向白校長說項,不要開除她。她們在阮湘蓮家裡聚集,由錢俊人打電話向白校長求情,白校長起初不肯,後來碍着俊人的面,終於答應了。
陸紉蘭歡喜得幾乎跳起來,她馬上偕同俊人去通知秋荷。符洵美則給阮湘蓮留在家裡喫飯。
陸紉蘭錢俊人到了戴秋荷家,知道她已經服毒自殺,急得趕到醫院去看她,但已經太遲了,戴秋荷在陸紉蘭未抵步之前斷氣了,她臨死時還低低地叫着陸紉蘭的名字。
陸紉蘭在手術室看見戴秋荷的屍體,不禁心碎,撫着她的屍身,哭出聲來。
當夜,符洵美在阮湘蓮家,給用酒灌醉,昏迷的倒在阮湘蓮內室的床上,張立拔穿着睡衣,抱住了她,用力把她的外衣拉開,忽然她的胸前現出了一個金色的十字架。他好像被一種力量所控制,他驚望着這神聖的十字架,手抖抖地縮囘一來,可是他耐不住這誘惑,另一隻手却準備去熄滅台燈。
燈熄了,窗外的雷雨狂怒着。
張立拔正欲爬身上床,阮湘蓮突然來敲他的門,他開了燈,讓她進來怪她不該在這個緊急關頭來找他。阮湘蓮吿訴他:不得了,陸紉蘭來找洵美了。
阮湘蓮這一說,使張立拔驚得發呆,連一點主意都沒有,最後還是湘蓮清醒,促他到窗外的陽台暫避一下。一切佈置淸楚之後,她才出客廳來。
「蘭姐,這麽晚了——」阮湘蓮心虛地說。
「湘蓮,秋荷死了!」陸級蘭很感慨地說:「可惜我們遲去一步,現在只有錢先生在替她料理善後。我去通知洵美,她母親說她沒有囘家,她還在這裡幹嗎?」
「她剛才喝了兩杯酒,醉得不能動,所以我就叫她睡在我這兒了。」
「她喝了酒——」陸紉蘭驚駭地說:「現在人呢?」
「在我房裡。」
陸紉蘭聽說,立卽走入湘蓮內房、看見符洵美還沉睡着,她把洵美推醒,叫了輛街車送她囘家去,把她從那個色魔的手裡拯救了出來。
X X X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
夕陽西下,在郊外的墳地。陸紉蘭符洵美,錢俊人,張立拔,阮湘蓮,吳太太和曹慕貞,孟小霞,張錦意諸人,站在剛入土的秋荷的坆旁。同學們唱着追悼歌,聲音是那麽沉重而暗慘。這時候張錦意覺得從前尖嘴滑舌,太對不起了戴秋荷,禁不住大哭起來,符洵美也泣不成聲。
在歸途上,張立拔說這裡離開他的別墅不遠,耍錢俊人他們到那兒休息一下,然後再囘家。錢俊人本來不要去,但經不起張立拔的强邀和阮湘蓮的慫恿,終於跟着大夥兒去了。
張家古舊的別墅門口,因爲多年失修,有些垣毀與荒涼,紫籐盤滿了牆柱,彷彿使人感到一些陰霾,尤其是黃昏更使人感到了恐怖。
張立拔和錢俊人的汽車在門口停下來,立拔首先下車去按門鈴,衆人隨着下車。
「就是這兒,以前家父每年夏天都來住一些時候,他老人家去世以後,這些年我在外邊,這房子除了一個看門的簡直沒有人來,所以顯得有些荒涼!」
張立拔向錢俊人介紹他這間別墅,大家眼對這高大的舊屋,都帶着些恐怖的心情。驀然,沉重的大門慢慢的開了,呀的一聲,使人有些寒意,接着是一個年老的守門人,手擎着燭火出現在門口,他的臉上長滿了鬚,兩隻眼睛,瞪着前面,態度陰森奇異,動作慢緩而呆板,他低低地呌着一聲少爺。張立拔吿訴大家,他是他的看門的老頭。衆人注視這個老人,老人也用奇怪的眼睛注視着衆人。
大家緩慢而猶疑地進去,門呀的一聲已關上了。
老人執着燭火帶領衆人入客廳。
符洵美偷偷地對陸紉蘭說:
「蘭姐,這房子眞有點怕人!」
「唔,」陸紉蘭低聲說:「我看張立拔跟這房子一樣可怕,昨天晚上,你不該喝酒。下次不可以這樣大意,戴秋荷的死就是我們的敎訓,因爲她以前走錯了路,所以——」
「你別提戴秋荷好吧,怪怕人的!」
提到了戴秋荷,符洵美脆弱的心猶有餘怖,她依偎在陸紉蘭的身邊。
那邊張立拔正在向錢俊人介紹他這個別墅的歷史性,耍大家上樓參觀。
大家聽他的話跟着上樓,老人執着燭火帶路。
張立拔看見衆人上樓,他拉住阮湘蓮說:
「昨天晚上失去了好機會,我想今晚留洵美下來。」
「不行,今天她好像有點躱着我,而且這麽多人一齊來的,怎麽好留她一個人呢?」
「不得到洵美,我死也不甘心。」
張立拔舐着嘴唇說,阮湘蓮瞟了他一眼。
錢俊人衆人上樓,樓上陰森得可怕,他們正在一間房子瀏覽,忽然瞥見一個女子,披着髮,臉色蒼白,兩手呆板的下垂,立在黑暗處。錢俊人大叱一聲,問是誰?那女子呆立不動,衆人緊張地擠在一起。那女子突然向衆人撲來,而且發出瘋狂的笑聲,大家失魂落魄地向樓下跑,那女人也追着衆人下樓。張立拔看見馬上把她抓住,厲聲詰問着老頭:
「誰把她放出來的,把她拉上去鎖起來。」
老人把那女人扶送上樓去。張立拔吿訴錢俊人,說那女人是瘋子,請大家不耍理她。但大家經過這一嚇,也沒有心再在這兒逗下去,走了。
七
錢俊人因爲料理了戴秋荷的善後過於勞瘁,和在張立拔的別墅給那瘋女人一嚇,竟吿病倒了。
陸紉蘭好幾天沒有看見錢俊人,心裡好像失去了什麽似的。阮湘蓮從張立拔口裡探知錢俊人有病,而且念念不忘陸紉蘭。她把這些話吿訴符洵美張錦意她們,大家聽說,當着陸紉蘭的面,向她取笑,害得陸紉蘭不好意思。最後阮湘蓮提議去探病。大家一致贊成,而且推陸紉蘭爲代表,符洵美阮湘蓮作陪。衆意難却,陸級蘭祗得羞答答地應承了。
陸紉蘭符洵美阮湘蓮三人,拿着鮮花到錢俊人家來,見了錢俊人之後,符洵美和阮湘蓮借故走出房外,留陸紉蘭在房裡,陸級蘭要攔住她們已來不及,無可奈何,██地問着錢俊人:
「是那天你受了驚嗎?」
「本來我心臟就有點不健康。」錢俊人說。
「吃了藥嗎?」
「謝謝你,吃了藥了,今天早上我已經叫人送些錢給吳太太替戴姑娘淸了賬。」
「你的熱心很使人感動!」
「到是因爲你的熱心感動了我!」錢俊人溫純地一笑。
「別這麽說,同學們對你的爲人,都很欽佩,所以她們要我代表來看看你。」
「我知道你會來看我的!」
「爲什麽?」陸紉蘭微笑地問。
「說不出理由,只是這麽想,你覺得奇怪嗎?」
錢俊人說着,一雙溫柔的眼睛,注視着陸級蘭,陸紉蘭含情脈脈地低下頭來。俊人從抽斗裡取出一本包好了的書送給她,笑着說:
「你不知道,你眞的不知道?我送給你這本書,叫什麼名字,你把它帶囘去看看就會明白的。」
陸紉蘭接過了那本書之後,和錢俊人吿辭,跟着符洵美阮湘蓮出來。
X X X
陸紉蘭囘到了家裡,心裡有點異樣的感覺。她把錢俊人送給她那書的紙包打開來!——
初戀
巴金譯
這兩個字奪了她的視線,她迷惑的把這本書再包起,臉上一陣熱,有些紅雲。她的心跳得很利害,躺在床上,但天花板到處都是——
「初戀,初戀,初戀,初戀!」
她把書藏在枕頭下,閉着眼,做着處女的綺夢,緩慢地她走入了夢的天國了。
X X X
錢俊人和陸紉蘭已由初戀而進至熱戀的階段了,他們常常相約出遊,幸福的氣氛溫暖地圍住着他倆。
另一方面,張立拔除謀誘騙符洵美的計劃,也進行到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日,阮湘蓮張立拔又約符洵美到郊外野餐。阮湘蓮向符洵美說:
「洵美,你別那麼傻,什麼事都去問蘭姐,現在你該相信了吧,她自己還不是一樣。」
「不過,錢俊人的確値得人歡喜,那麼斯文,那麽熱心!」
符洵美低着頭說,阮湘蓮忙的問:「那末你覺得立拔呢?」
「人家都說他壞,可是我看他還好!」
「你千萬別信人家的話,這都是人家破壞他的。」
她們兩人正在閒談。張立拔在汽車那邊呌湘蓮過去,他輕聲對她說:
「今天可是最後的關頭,我决不能再放過她。」
「我明白,羊入虎口,不過你要小心!」
「囘頭我準備——」
張立拔在阮湘蓮耳邊吱咕一陣,湘蓮說他太毒,伸手向他要錢,他給了她,兩人一笑,携着點心走向洵美這邊來。
張立拔在草地開了留聲機,迷人的音樂嬝娜地飄蕩出來。符洵美不知道自己的惡運將吿降臨,她無邪地沉醉在美妙的音樂裏。
X X X
同一個時間,錢俊人和陸紉蘭也在郊外水邊談心。他們由友情到了事業,談到了將來。錢俊人說:
「我囘國的時候,下過决心把父親辦的這間學校辦好,可是總覺得少了一個帮手!」
「你可以去找一個帮手啊!」陸紉蘭說。
「現在不用找,我已經找到了。」
「找到了在那兒?」
「就在眼前!」錢俊人看看陸紉蘭,陸紉蘭嬌羞地說:
「你覺得我可以做你的帮手嗎?可是我父親今天要我結婚。」
「結婚?你答應了嗎?」
「我老早就决定,一天不能自立,一天不結婚。我不倚賴男人過一生。」
「沒有想到你有這麽偉大的意志,我的眼光沒有錯,希望你不要投降,决定——」
錢俊人說着熱切地拉着她的手。在歡愉的夕陽影裏,他係踏上歸途。
X X X
是夜,陸紉蘭剛睡去的時候,符洵美的母親忽來找她,說洵美還沒有囘去,什麽地方都找過了,都沒有她的踪影。陸紉蘭聽說大驚,馬上打電話去問阮湘蓮,阮湘蓮說老早已經和她分手了,就把電話放下。陸紉蘭和符老太急得什麽似的。
一點也不錯,阮湘蓮早就借故和符洵美分手了。符洵美已經給張立拔騙到那座恐怖的別墅去了。
到了別墅,符洵美看不見湘蓮,她驚懼地知道被騙。她失常的呌着湘蓮,可是沒有囘應。她眼淚簌簌地嚷着要囘去,她衝到門口,門口出現了那個僵屍般的瘋女人,她嚇得退囘了來。
張立拔叫看門的老人送她上樓,自己把客廳的門鎖了,得意的笑着。
老人帶着符洵美上樓,送她走入了那間陰森的房子裏去。老人吿訴她,當她睡了的時候,把門鎖起來,半夜裏有人推門,可不要怕。符洵美聽說,驚震地說:
「你說什麽?半夜有人推門?」
「唉,這也是你的造化,到了這間房子裏來的女子就別想好好出去!」老人搖着頭嘆息,符洵美發抖地說:
「爲什麽:你說這兒眞有鬼嗎?」
「有的,有鬼,是一個魔鬼,不瞞你說,小姐,那個瘋女人就是我的女兒,四年前被這個魔鬼騙到這兒來强姦了,他有勢力,我沒有辦法,只好忍氣帮他看房子,靠他一碗飯吃。」
「剛才那個瘋女兒就是你的女兒?」
「她被人姦汚了一時憤怒就氣瘋了!」
「這個魔鬼在那兒?」
「就在樓下——今天晚上輪到你了!」
符洵美聽說,驚得跪下地來,要求老人救她走,老人不勝傷心,他低低地嘆息,靜靜地領她走了出來。四週寂靜如死,只聽見門呀的一聲。在轉角處,張立拔站在那裏,叱了一聲,一個巴掌打在老人臉上,惡駡着他,然後,一步一步地迫着符洵美,他把符洵美迫進了原來那間房間,關上了門。
房裏立刻傳出了符洵美的掙扎聲,哀呼聲,接着是張立拔的一串獰笑聲……
那個女人瘋跑來,拚命的擊着門,她用頭向門上撞,原野傳來了幾聲狗吠聲。
符洵美憤怒而發狂地由室內跑出來,她衣衫不整,披散頭髪,狂奔下樓,她兩眼直直衝出門口。張立拔也由樓上追下來。
符洵美出了大門,迷茫地向前面奔,她奔向林中,沒有目的地向前奔,張立拔也跟着追,他在後面叫着:「洵美!洵美!」
四野無聲,囘答的只是森林的反音,他一邊呼喚,一邊走地跑到河邊,見無去路,四顧無人,忽然發現河灘洵美遺下的一隻鞋,他忙的拾起來,大吃一驚,意識到她已投河自殺了。
銀色的浪花翻滾,像代表千萬人的憤怒。張立拔一陣寒慄,慢慢地後退,急轉身發足狂奔忽然給什麽絆倒了,他急爬起來,看見一塊墓碑寫着——
「戴秋荷之墓」
他不禁胆寒神落,恐怖與痛苦交加,彷彿遠處有一個披髮女人的黑影出現……
他慌忙地向公路奔,到了他的汽車邊,他的心稍定,但發見前面火光燭天,憤怒的火燄,呑沒了整個別墅。
八
報紙登載著符洵美投河遇救的消息。
符洵美被救傷車載到中山醫院去,出人意料之外的負責醫治她的就是那個被目爲傻瓜的李昌。李昌在細心地檢驗着她的傷狀,她因爲受刺激過度,又加上在水裏的時間過長,所以她的眼睛巳經失明了。
陸紉蘭符老太及錢俊人等趕到醫院來,符老太看見女兒這形狀,不禁傷心地流下淚來,她拉着女兒的手,抽噎地說:
「孩子,媽在這兒,你怎麽啦?你到底爲了什麼?」
「媽,我看不見你,我對不起你!」
符洵美哭出聲來。陸紉蘭走近前來說:
「洵美,好妹妹,你說爲了什麽,你說啊!」
「是蘭姐嗎?」符洵美痛苦地說:「我不能說…」
陸紉蘭正待追問下去,已給醫生李昌制止,請她們不要限她多說話,勸大家暫且出去。陸紉蘭要求讓她一個人留住陪伴洵美,得到李昌的同意。她一待衆人出去後,很快地貼在洵美耳說:
「洵美,是不是昨天阮湘蓮與張立拔欺侮了你?你千萬別瞞我,洵美!」
「蘭姐,……別問我……」符洵美傷心的哭了:「我完了,我一生都完了,我現在只後悔不聽你的話。」
「洵美,你說是不是張立拔——」陸紉蘭緊急地追問,符洵美哀怨地說:
「如果我死了,蘭姐,你要替我伸寃,張立拔他强姦了我!」
符洵美說罷又是一陣痛哭,陸紉蘭意外地哦了一聲:
「什麽?我早就担心他對你,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居然這麼毒!」
「蘭姐,你千萬不能把這事吿訴別人!」
「不,這件事我不能不說,被人欺侮了,不能反抗,那太可憐了,洵美,我們一定要找他!」
陸紉蘭說着,不顧符洵美的勸阻,她和俊人及一班同學,分頭去報吿學校當局及警署,一面去找阮湘蓮及張立拔。但張立拔和阮湘蓮已聞風逃了。
公路上,張立拔駕着汽車瘋狂地奔馳,後面有警車疾馳地追着,到了山下,張立拔心慌,把汽車撞翻了,發火燃燒,他和阮湘蓮給燒死了。
在醫院中,李昌拿了藥針在爲符洵美打針,他吿訴她,張立拔和阮湘蓮已經翻車身死了。符洵美聽說,不禁慨嘆地說:
「現在我才知道你以前的話是對的,這個世界上聰明人太多。」
「我相信你有一天會明白我的。」李昌笑着說。
「可惜明白得太遲。」
「別這麽說,人在死以前,永遠沒有太遲的一天。」
「現在我了解了,可是我已經看不見你了。」
「可是你的心已經眞正的看到我了。」李昌熱切地拉着洵美的手,洵美感激地說說:
「沒有想到你不但不怪我,不恨我反而對我比以前更好。」
「我永遠都不會對你不好的!」
在李昌悉心盡力的醫治之下,符洵美的病,經過一些時間,慢慢的好了。同時洵美創傷的,由於感到李昌對她不渝之情,獲得了溫暖的慰藉,心懷開朗,從而恢復她雙眼的光明了。
符洵美的恢復光明,帶給同學們一個喜訊。但另一個更大的喜訊,又立刻傳遍學校了。
原來錢俊人跟陸紉蘭的關係,隨着時日的推進,友誼日篤,愛情達到了爛熟的階段,驚動了雙方的長輩。雙方的長輩都不肯兒女自由戀愛,强要做主另尋婚配。可是當俊人的父親錢大年和陸紉蘭的父親陸棠碰頭時□竟發覺是通家之好,他們理想中要玉成的美滿姻緣,正是兒女理想中要締結的美滿姻緣,於是,他們兩人的婚事,馬上决定了。
在寰宇女子中學的大禮堂,擠滿了同學及來賓,錢大年興高彩烈地步上講台致詞,他說:
「希望過去的,讓他死去,一切從今天起是新的開始。今天不但向各位介紹一位年靑的新校長,而且更値得介紹的是兩雙情侶——」
大年說着走下台來,台下是一片叫聲。幕拉開處,現出是李昌與洵美,俊人與紉蘭,四人站在一排。
台下的人幾乎歡喜得要鬧翻了天。紉蘭和洵美兩人的母親,歡喜得流下淚來。錢大年和陸棠握着手,學生們衝上台,把兩雙情侶圍在中間,歌聲輕鬆愉快地四起——
珍惜妳們的錦繡年華!
(劇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