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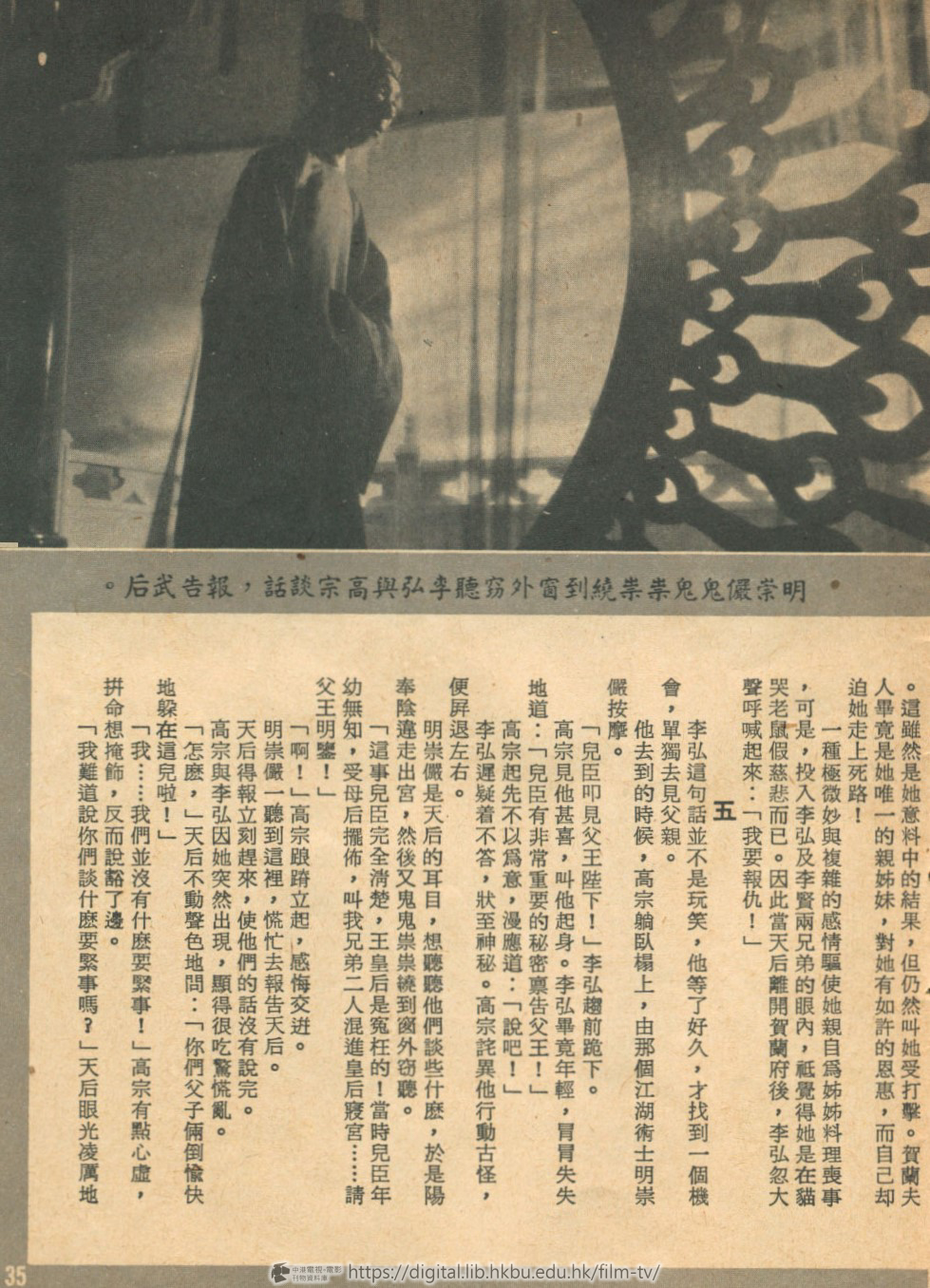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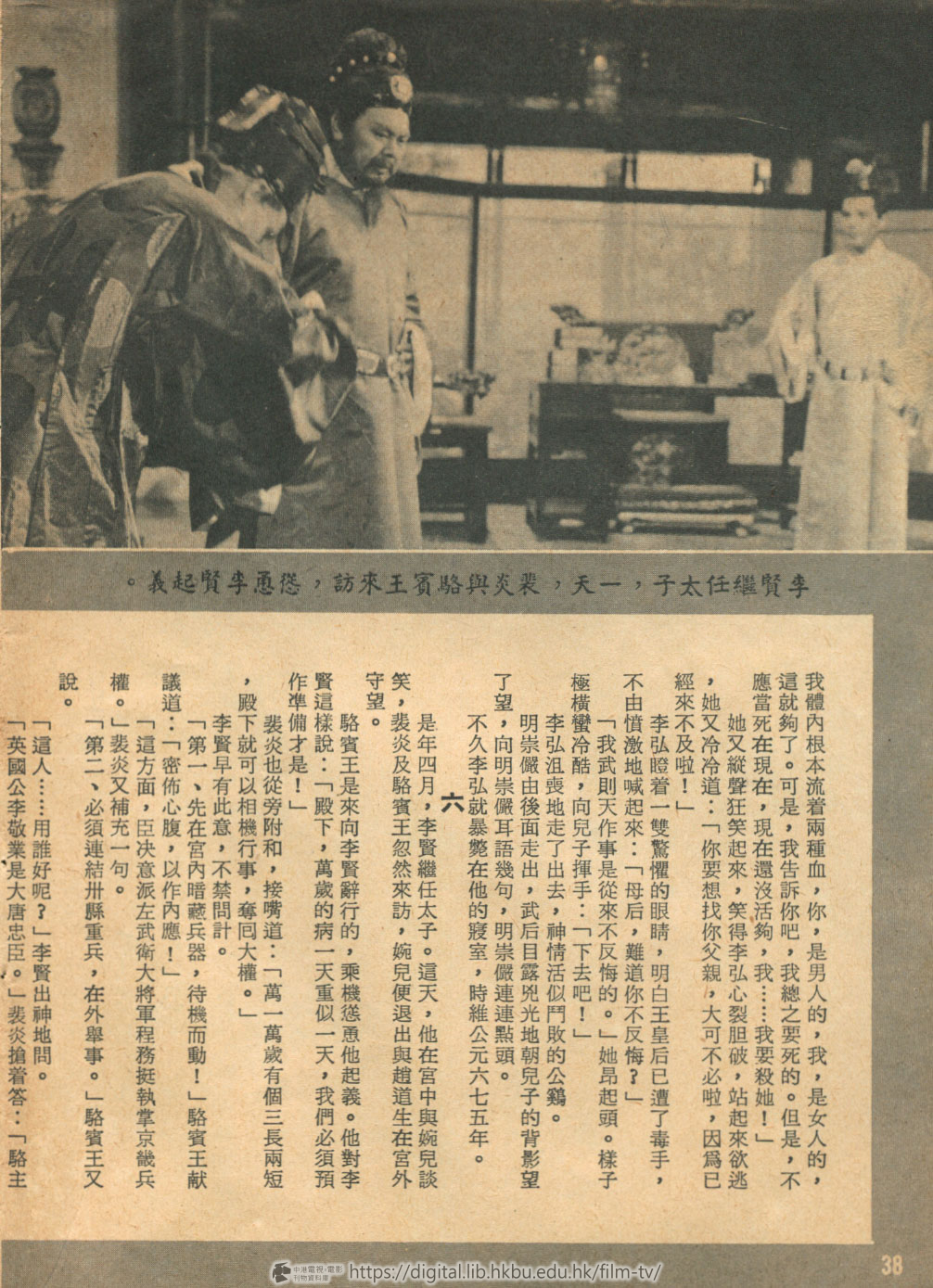









武則天 電影小説
一
感業寺鐘鼓聲大作,搖憾山岳,在風中顫慄。
顯然有件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在寺中潜修的尼姑們,聽到這一陣急激的鐘鼓聲,分由各殿房、經樓、禪院走出,向正殿集中。雖然她們走得很急,脚步聲却輕得幾乎聼不見,而且誰也沒有開口,祗默默地走着,以眼睛來探詢究竟。
主持該寺的老尼,肅穆地站在正殿,待衆尼齊集,然後率領她們匆匆走下石階,往山門而去。
這時山門大開,遠遠便見一列手執茅槍的御林軍,護着一座宮庭的鳳輿,後面跟着穿官服的女官、太監及宮女們,緩緩上山而來。
原來是當今正宮娘娘王皇后駕到!
御林軍禮儀隊在山門外一字排開,女官及宮女們擁簇上前侍候皇后下轎,老尼忙不迭率衆迎上,跑拜行禮。
老尼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知皇后的來意,直把她迎入殿內坐定,便合什道:「皇后駕臨,寒寺不勝榮幸!」
皇后似不欲多說廢話,立刻開門見山的問道:「聽說先王駕崩那年,有位才人貶在這兒削髮修行是嗎?」
老尼意外地一怔,訥訥地道:「是貧尼小徒,法號明空!」
「傳她進見!」皇后急不及待,馬上向太監發令。
太監應命,走到殿前大喊:「傳明空進見!」
老尼暗暗替明空揑一把汗,不知是禍是福。
當明空緩緩循着石階走上來的時候,皇后目不稍瞬地注視她,上下打量着。她感到驚奇,明空比她想像中還要美麗,尤其那一對眼睛好似能勾人魂魄,難怪皇上被她迷住了!
「叩見皇后!」明空恭恭敬敬走到皇后座前跪下。
「平身。」
「謝皇后。」
明空垂首站着,不敢仰視,直覺她有股迫人氣燄。
皇后屛退左右,單獨留下明空。
這舉動太離奇了,明空開始感到不安起來。
「你在這兒有多久啦?」王皇后等衆人全退去,便這樣問。
「五年!」
「噢!」
皇后突然離座,走前走後向她看,希望從她身上找出一點缺點。沒有,身材適度,骨肉勻停,無論從那一個角度去看都很美,縱然頭上光禿禿,也還是美,美得淸逸超凡!
「昨天皇上又來過了,是嗎?」
雖然這話說得很輕,聲音也顯得很温和,但仍然叫明空心跳,面熱起來。
「不用怕,你跟皇上的事情,我早就知道啦!而且,我還知道你替皇上生了兩個孩子,養在你姊姊賀蘭夫人家裡。」
明空感到羞慚,頭垂得更低了。
「你知道我今天到這兒來傳見你的意思嗎?」皇后邊說邊走囘座去,明空偸偸望她一眼,當她轉身坐下的時候,明空趕緊又把頭低下。
「皇上是萬乘之尊,常常偷偷摸摸地出入尼庵,到底不成體統!」皇后的語氣開始加重了。「你本是先王才人,跟皇上可以說是母子輩份,而且身入佛門,六根不净,外邊傳說得非常難聽!」
語含指責與威脅,令明空感到無地自容,身體微微抖索起來。
「不過,你巳經有兩個孩子,都是皇上的親生骨肉,養在民間,也不大好——」她故意把尾音拖得很長。
提到孩子,明空心一緊,不由抬頭注視皇后,覺得她的外貌雖然端莊也頗美,可是神情詭秘莫測。
「因此,」皇后提着說:「我現在打算命你蓄髪還俗,接你進宮。」
這話出乎明空意料以外,驚喜得眼中閃出涙光,抖動着嘴唇,囘道:「皇后恩德,我母子沒齒不忘!」
「不過,我有一句話,不能不跟你說在前頭。」
「請皇后吩咐。」明空誠惶誠恐。
皇后微微一笑,面色放和下來。「聽說你很有才學,想必深明大義,如今我成全了你,希望你進宮以後,能夠知恩報德,幫我做一件事!」
她故意停下來,眼光凌厲地望着明空,似想看穿她的心是否忠於自己。明空此時那敢怠慢,自己與兩個兒子的命脈操縱在她手裡,面上自然流露出關心與緊張之色。
皇后諒她不敢反抗,大胆說下去:「皇上在宮十分寵愛蕭氏淑妃,不理朝政,沉迷酒色,弄得身體很壞,我再三諫諍,巳經無能爲力,所以,我希望你……你是聰明人,想必會懂得我的意思!」
話雖說得冠冕堂皇,但弦外之音……明空玲瓏剔透,那有不明白的道理。「原來是想利用我,借刀殺人!」明空心裡這樣說,頗鄙視她爲人。不過面上却表現得很誠懇與恭順,朗朗囘道:「皇后對我恩重如山,我一定遵命!」
交易成功,皇后便擺駕囘宮,部署一切。
可是明空却陷入無比的煩亂中。這任務非常重大與艱難,皇后之心昭然欲揭,成與敗都不是好事,而且她旣敢謀害蕭淑妃,他日難保不以同樣的陰謀,加諸在自己的身上?
她無法安枕,伺衆尼睡熟,悄悄走到正殿,跑在佛前祈禱,求神靈庇祐她,並賜予力量。
殿外雷聲轟轟,閃電頻頻,照着明空的臉份外蒼白,她終於在神前許下了一個毒願!
明空多年的願望終於達到了!皇后也沒有爽約,待她頭髪蓄長,便接她進宮。從此明空恢復本姓,叫武媚娘。
二
在武媚娘進宮的那一天,風光不讓正宮娘娘,情形宛似出會一般,鑼聲喧天,唯恐天下不知的樣子,武媚娘盛裝艷服坐在輿上,由御林軍、禮儀隊、太監、宮女們的前導後随中,浩浩蕩蕩,經過一條街,又一條街。
老百姓聚集在路邊觀看,莫不露出驚愕的眼光,與詫異的神色。因此,一等行列走過,便交頭接耳議論起來。
「感業寺的明空尼姑還了俗啦?」
「而且封爲昭儀接進宮去哩!」
「這不是亂倫嗎?」
「朝廷裡許多元老大臣,難道就不聞不問?」
朝廷裡的大臣難道眞的不問不間嗎?可也不盡然,至少在群臣中還有三位忠義之士發出不平的聲音。
最先是吏部尙書褚遂良,憤慨地道:「我們怎麼可以不聞不問?」
接着太尉長孫無忌,說:「子幸父妃,眞是太不成話啦!」
西台侍郎上官儀也忍不住挿嘴,感喟地道:「據說這是王皇后出的主意,我看引狼入室,必將自食其果!」
儘管羣情激昂,武媚娘還是堂而皇之的走進宮來,打從乾元殿經過。羣臣敢怒不敢言,惟以憤怒的眼光相送。
倡議人王皇后的心情也並不見得比他們輕鬆。這時她正站在玉華宮外的廻廊上,瞧着護送武媚娘的行列經過,心裡有些患得患失。
她的心腹侍女,瞧見武媚娘的排場不弱於皇后,頗感不安,嘀咕道:「皇后,奴婢替你担憂!」
「担什麼憂?」皇后不解地問。
「只怕她奪了蕭淑妃的寵愛以後,對皇后忘恩負義,那時候……」
「這怕什麼!她是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先王才人,只要蕭淑妃一失寵,哼哼!」
王皇后似胸有成竹,陰森地冷笑起來。
侍女恍然大悟,失笑道:「噢,對了,這叫做一舉兩得!」
侍女的担心並非全無道理,誰要看到高宗與武媚娘在翠微宮的情形,難免沒有這樣的感覺。
這是他們第一次,光明正大的同在一起。
高宗欣然地注視着媚娘,覺得她越加美麗明艷。
的確,經過修飾後的媚娘,儀態萬千,她嫵媚笑着對高宗說道:
「臣妾多少年的期望,今天總算如願以償啦!」
「弘兒賢兒兩個孩子都好嚅?」高宗關切地問。「都很好,只是……」
「只是什麼?」
「他們一生下地,就托我姊姊扶養,現在已經懂事啦,都以爲我姊姊是他們親生的母親,對我,簡直沒有一點感情!」
「這個你放心,過幾天把他們接到宮裡,慢慢會轉變的!」高宗安慰她。
「但願這樣就好啦!」媚娘喃喃自語。
兩人談着,高宗突然眉頭攢緊,以手撫額,身微搖擺起來。媚娘大吃一驚,趕忙扶着他問:「陛下怎麼啦?」
「朕近來常常頭昏目眩,吃藥無效,今後有你長伴左右,我的病想必也會好!」
媚娘突想起王皇后所交給的使命,乘機婉言動道:「希望陛下少近女色,戒絕酒宴,而且,不可操勞過度,相信龍體一定會日漸康復的。」
話說得委婉動聽,令高宗十分感動,緊握媚娘的手,道:「我一定聽你的話!」
高宗確沒有辜負美人這一番情意,自從媚娘進宮以後,高宗的生活確實改變了,也確做到「少近女色,戒絶酒宴,不可操勞過度」。媚娘曲意奉承,漸把他生活從絢爛歸于平淡。兩情繾綣,如膠似漆。時見他倆手携手,在御花園散步,或栽花飼魚。晚上,媚娘在宮中作書,創造新字給高宗欣賞,或引經據典與皇上談天說地。
這是屬好的一方面,而在壞的一方面,他却從此冷落三宮六院,也從此君王不早朝。
羣臣在朝中等候,日過一日,仍不見駕臨,奏章堆積如山,高宗視若無睹,沉溺于媚娘的柔情蜜意中。
高宗對武媚娘日益寵信,言聽計從,羣臣祗敢怒不敢言。而最感刺激的莫過於王皇后,她借刀殺人之計雖已成功,但前門送狼,從門進虎;而且大有取其位而代之勢,怎不令她驚慌起來。日思夜想,不禁由妬生恨,與心腹侍女密議陷害媚娘,準備一不做二不休。
三
不久,事情發生了!
一晚,高宗躺在榻上,手裡拿着媚娘創造的新字賞玩。婚娘偶然瞥見案上奏章又高了幾寸,心頗不安,趨前對高宗說:「陛下近來身體好得多啦,那許多奏章,先挑重要的慢慢把它批閲了吧!」
高宗漫應道:「自你入宮以後,朕遠色戒酒,心境確是好得多啦,可是,頭還是有點昏昏的,你還是代朕批閱好啦!」
媚娘聽了喑喜,口中却謙遜道:「臣妾孤陋寡聞,怎麼行呢?」
「朕知道你懂的並不比我少,昨天你談的『唐律疏議』,就比我淸楚,而且你絕頂聰明,這二十個新字眞是別有見地!」高宗由衷讚美她。
媚娘正感洋洋得意之時,忽然神色大變,撫胸慘叫起來,彷彿有柄利劍刺進她的心房。
她好好地怎的忽然病起來呢?
這就是王皇后的陰謀。她無法離間高宗與媚娘的感情,甚至連進言的機會都沒有,却眼見媚娘的勢力一天比一天膨脹,恨得她咬牙切齒,思去之而後快。於是想出一條毒計,用重金延聘一個會使法術的道士來,欲以邪術制媚娘于死地。
當媚娘猝然發病的那一晚,也正是那邪道士在玉華宮作法的時候。他披髮仗劍,站在香案前,手舞足蹈,口中唸唸有詞。旁有個小道士,在一旁敲擊法器。在香案正中,供着一個小木人,上面寫着武媚娘及她的年庚八字,胸部釘着一隻釘。
王皇后及她的心腹侍女,專心一意注視道士做法,却不知窗外有人窺視,看破她的秘密以後,急忙走報媚娘。媚娘驚得從床上坐起,「有這樣的事?」
「奴婢親眼看到。」
「我想不會吧,皇后命我蓄髮入宮,待我這末好,而且我也依從了她,勸皇把蕭淑妃廢啦,她不會害我的!」
媚娘不相信這是眞的,可是說着,突然又感到一陣澈骨的疼痛,整個心房好似被人挖出來似的,痛得她又惨叫起來。
爲了證實這件事的眞僞,媚娘扶痛偕吿密的太監,到玉華宮窺望。果然發現道士在作法,王皇后一臉虔誠和侍女恭立一旁。太監指指小木人,提示媚娘注意;她不看猶可,一看不禁震怒,赫然發現小木的胸部又多了一只釘!
這就是她疼痛的來由。
媚娘沒有立刻發作,她是個工心計的人,不想打草驚蛇。於是先囘自己的寢宮,第二天召她的姊姊賀蘭夫人來商議。
終於給她想出一個嫁禍的辦法,决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她倣製一個小木人,上寫唐高宗李治及年庚八字,並在額上及兩眼釘着釘子。
小木人做好了,但怎樣放進玉華宮去呢?這倒使媚娘爲難了。皇后內宮,門禁森嚴,對閒人是不准進去的。
她苦思不出,最後還是賀蘭夫人偶然瞥見兩皇兒李弘及李賢在御花園玩彩球,靈機一觸,計上心來,拿着小木人匆匆出宮。
小孩子不知利害,便照着賀蘭夫人的囑咐,故意把球踢進玉華宮,然後兩人追逐進去,你奪我爭,直把彩球踢入寢宮皇后牀下。表面看來李弘是爲着拿球而吧入床下,殊不知他乘機將藏在懷裡的小木人暗置牀下,然後拿球返身爬出,兩人臨走還向皇后吐舌做怪臉而去。
王皇后做夢也沒想到,這兩個孩子給人利用,使她跌入陷阱,使她萬劫不復!
媚娘佈下天羅地網之後,便在皇帝面前做態了。
她不施脂粉,裝成很憔悴的樣子,躺在床上。賀蘭夫人及李弘、李賢兩兄弟,環立牀前。一見高宗進來,媚娘便嚶哭起來,哭得很哀切。
「現在好點了嗎?」高宗焦急地問。
賀蘭夫人向他搖搖頭。
高宗走近榻前,摸摸媚娘的額,安慰她道:「朕在前殿跟大夫們商議到現在,我要他們思想辦法找靈丹去啦!」
賀蘭夫人表情沉重,用嗚咽的聲音道:「不用找啦,她不會好的!」
「這是什麼話?」高宗詫異地問。
賀蘭夫人不答,縮縮鼻子,拚命擠出一點眼淚,向媚娘自說自話道:「早知道她會謀害你,當初就不該進宮來的。」
高宗聽了一怔,忙追問:「謀害她?是誰?」
「宮裡還有誰呢?」
「難道說……」
媚娘的心腹太監一聽話納入正題,便揷把嘴進來:「聽說有個邪術妖道,每天晚上在玉華宮……」
「怎麽?」高宗聲色俱厲地盯着太監。
太監裝成極害怕的樣子,抖聲道:「奴婢不敢說!」
高宗若有所悟,返身疾走,太監們急忙跟去。
媚娘馬上停止哭泣,以勝利的眼光,望着高宗的背影遠去。
一切果如所料,高宗怒氣冲冲闖進玉華宮,使王皇后措手不及,即命衆太監搜宮。
當然一搜,就搜出二個小木人來,當高宗看到那個寫着自己姓名,年庚八字的小木人,氣得暴跳如雷,也不問明査白就對皇后大嚷起來:「好哇,怪不得我頭昏目眩,經年累月的治不好,原來是你在搞鬼,你……你……還有什麽話說!」
「陛下……」王皇后驚至面無人色,百詞莫辯。
高宗在盛怒之下立刻升朝,待羣臣叩拜之後,向大家宣佈:
「皇后失德,勾結妖道、圖謀不軌、着即廢爲庶人、幽禁冷宮!」
這突如其來的發佈,令在朝諸臣無不大驚失色,面面相覷。
接着高宗又宣佈:「武昭儀端莊賢淑,才德並茂,茲册封爲皇后!」
此話一出,立刻響起一片嗡嗡之聲。長孫無忌挺身而出,趨前跪下,冒死動諫道:
「啓奏陛下,老臣以爲不可——」
「爲什麼?」高宗一愕。
「武氏是先王才人,封爲昭儀,接進宮來,已屬不當,如再册封爲皇后,難免貽笑天下!」
高宗怫然不悅,正沉吟着,褚遂良也跪下,高聲道:「臣受先王咐託,言猶在耳,陛下必欲廢立,亦希望另選名門令族,武氏千萬不可册封!」
接着上宮儀亦阻諫道:「天下望族淑女,到處皆是,陛下何必册封這種失德不貞婦人!而且……」
聲聲指責他心愛之人,高宗不能忍受,惱怒地喝叫起來:「不要再說啦!這是朕自己的家事,你們不必過問!」說到這裡,他想了想:於其留着這兩個倚老賣老的傢伙在這裡吐舌,不如去之,以示殺一儆百之意。於是毫不留情道:「太尉長孫無忌,吏部尙書褚遂良,年事之高,賜你們吿老還鄕,即日起程,勿稍延遲!」
說罷拂袖離座,擺駕囘宮。
長孫無忌本無意留戀,此時見他更倒行逆施,不禁仰天長嘆:「唉!看來大唐天下,要噺送在這婦人之手啦!」
四
武媚娘嚮往皇后之位多年,一旦得償大慾,氣燄愈張,瞧她御皇冠服,在肅儀門接受文武百姓膜拜朝賀的那一天,當時那種傲視羣臣的神氣與不可一世的態度,直令人不寒而慄!
這時武后的野心已呈端倪,偏巧高宗不爭氣,風眩病日甚一日,朝中大事皆委武后聽政,因此武后的手掌能從宮裡伸出宮外!
十年人次番新,轉眼巳到公元六七四年,即甲戍上元元年。當時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中外謂之二聖!
後來居上的中書令侍郎裴炎,爲了討好天后,遍防名醫術士來爲天皇治病。不久果然給他訪到一位名叫明崇儼的術士,據說此人善召鬼神,法力無邊。
這是個怎樣的人物呢?看來一臉邪氣,直非善類。
一天,他被迎接入宮,經過街道時給老百姓發現。瞧他那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模樣,還要裝得神氣活現,不由齒冷,紛紛議論起來:
「這洛州江湖術士怎麽這樣威風?」
「聽說官封正諫大夫,替皇上治病來的。」
「女人當權,江湖術士封宮,這世道可真變啦!」
「大唐忠臣褚遂良在安南國愛州自盡,長孫無忌在黔州被殺,還有忠心耿耿的西台侍郎上官儀父子兩人……唉!」
「上官大人父子被斬,一貶眼已經十四年啦!」
「可不是嗎?聽說上官夫人母女兩人到如今還在宮裡做奴婢呢!」
這些話並非傳聞,上官夫人的的確確在宮中做奴婢。這時候她正在太子書齋龍麟宮,抹桌掃地。
她的女兒婉兒,匆匆走了進來,吿訴她裴炎來了。上官夫人本能地整整衣服,理理頭髪,迎接裴炎。儘管她身穿素服,臉上不施脂粉,看來她的態度還是十分高雅與斯文,不愧出自名門。
「侍郎早。」她恭聲向斐炎請安。
「夫人早。」裴炎忙不迭還禮。
婉兒也跟着母親向他問安:「九叔早!」
裴炎瞧婉兒那一臉嬌憨之態,帶點撩逗地問:「最近有沒有得意的詩句啊?」
「還不是糊塗風抹,要請九叔多多指敎呢!」婉兒稚氣地一笑,樣子活潑可愛。
上官夫人請裴炎坐下,自己坐一側相陪,然後感喟地道:「唉,女孩子舞文弄墨有什麼用?她祖父爸爸學問再好,也都完啦!」
「提起老師上官儀,我做門生的也眞慚愧!」裴炎馬上收歛起笑容,黯然道:
「常年他老人家父子被害的時候,我曾經在靈前立誓要替他們報仇,可是……十四年啦!」
「嗯,十四年啦,婉兒也整整的十四歲啦!」夫人眼眶濕潤起來。
婉兒站在母親身邊,聼了忙打岔:「媽,你眞是的,想這些幹什麽呢?」
「這是不共戴天仇恨,怎麼能忘了呢!」
一想起慘痛的往事,夫人就忍不住激動起來,婉兒傷心地哭倒母懷。母女倆抱頭哭泣。
裴炎有點不安,可是他心裡有他自己的打算,沉默了一陣,然後暗示她們道:「聽說近來皇帝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我想天后專權的末日,也會一天近一天啦!」
夫人忍住眼淚,不以爲然地道:「可是,太子殿下很不成器,整天跟宮女們胡混,將來即了位,也不會有什麼作爲的。」
上官夫人的話眞是一針見血,太子李弘確實渾噩輕浮,所作所爲更令人不屑。這可從李弘的日常生活裡,畧見一斑。
有一天,他正在御花園追逐一個年輕的宮女,欲施以輕薄,宮女駭得四處逃避。李弘那肯放過,緊追不捨,沒想到天后恰巧經過,兩人遇個正着。李弘色迷心竅,一把將天后抱住,待他抬頭瞧淸楚,驚至面無人色,立即踉蹌退後跪下,抖巍巍地道:「啊…母后!」
天后氣極竟出不得聲,半响才逬出一句話來:「太不成器啦!」
「臣兒……」
「你不要以爲是太子,可以隨便胡來!」天后聲色俱厲地:「要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年紀輕輕,不好好的唸書,整天跟官女胡混,心不正,身不修,將來怎麼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
李弘心中旣愧且恨,俯首無言。
「下去!」天后怒喝一聲。
李弘如釋負重,立起轉身就走。
天后怒他不知禮法,又把他叫住:「就這麼走啦?」
李弘沒法,祇得重跪下,非常勉强地道:「謝母親敎訓!」說完,悻悻走開。
天后的話非但沒有令李弘折服,反引起他的反感,囘到龍麟宮,見裴炎及他兄弟李賢在那裡,便向他們發起牢騒來:「正心?她自己就心不正,想謀奪李氏的天下!修身?她自己就身不修,不但身事二主,而且,女嫁二夫!」
裴炎老奸巨滑,聽了親笑着道:「殿下,這話未免太重啦,她到底是你的親生母親啊!」
「親生母親?哼!你以爲我不知道?我們的母親是……」
李賢知他指的是賀蘭夫人,忍不住喝止他:「哥哥!你這樣明目張胆的大吵大嚷,讓她知道了怎麽得了?她的耳目衆多……」
說到這裡,他忽見窗外人影一閃,驚得立刻住口。李弘及裴炎不約而同順着他視線望過去,原來是個宮女,在窗外探頭探腦,向李弘招招手,眨眨眼,笑着跑了!'
李弘頓時怒氣全消,輕佻地向裴炎䀹䀹眼睛,追了出去。
裴炎與李賢互望一眼,裴炎意味深長地道:「唉!要整飭綱常,維護先王的基業,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所能做到的!」
李賢爲兄長的無行而感痛心,連連嗆咳起來。
可是,李弘巳經走遠了!
他追着那個撩撥他的俏宮女,把她拉到叢裡,狂放地抱着她,吻着。
賀蘭夫人正無聊的在御花園散步,聽見嬉笑聲,走來探視,大槪那個宫女不耐李弘的輕薄,又掙脱跑掉,李弘爬起狂奔過去,消失在賀蘭夫人的視野裡。她見李弘那付色迷迷的狂態,不勝感觸,茫然地走到荷池邊,俯望池內有對鴛鴦,怡然浮遊,同進同退,親密得令人羡幕。她沉思着,偶一抬頭,又發現枝頭有兩只小鳥依偎在一起,心內不由起一陣凄迷的感覺,自己好似無根的浮萍……
突然有雙手輕輕搭在她肩上。她猛吃一驚,囘頭來望,原來是高宗,不知什麼時候站在她身邊。
「噢,陛下!」她輕吁一口氣。
高宗笑着注視她,用充滿感情的聲音道:「孩子都長大啦,都懂事啦!」
賀蘭夫人稍稍退後一步:「天后怎麼不陪陛下一塊兒出來?」
「嘿,她呀!整天整晚的只知道批文卷看奏章,開口天下,閉口百姓,理都少理我啦!」
「她眞是太苦啦!」賀蘭夫人避重就輕地答。
「可是我……」
高宗熱烈地望着她,眼內閃出飢渴的光芒。賀蘭夫人陡覺面上一陣熱,心急促跳起來,不敢接觸他的現線,羞答答地低下頭。
「我……我……」高宗猛然抱住她,氣喘喘地:「我更苦啊!」
「陛下不好不好……」
賀蘭夫人怯怯的推開他,可是,高宗的手臂愈收愈緊,用乞求的眼光望着她,令她不知怎樣才好;旣不敢聲張又無法抗拒。異性的熱力融開她長期禁錮的心扉,挑撥起她的情燄,令她心猿意馬。
當他倆拉拉扯扯的時候,無意中給伏在翠微宮窗前的書案,批閱奏章的天后瞥見,不禁怒火中燒,立刻擱下手中的公文,追踪而出。
等她追到花園,他們已進了後殿。紗窗現出兩人的影子,賀蘭夫人還在半推半就,伊唔道:「陛下,不好,不好,我怕天后知道,不好,不好!」
「她不會知道,她不會知道的。」
高宗急喘喘地,看來他眞的忍不住了!
一個曠夫,一是怨婦,他們亟需要安慰,於是,屋內的燈光滅了,跟着傳出猥瑣的笑聲與呢喃的軟語……
天后痛心地閉上眼晴,內心憤怒到極黙。
她奔到宮門口,欲推門進去打破他們的好夢,但她轉念又停住,想了想,陰險地笑一笑,拔下髮間的釵簪揷在門上,轉身去了!
春宵苦短,第二天一早,高宗便悄悄溜了出來,匆匆走了。
賀蘭夫人也正在慶幸沒人發覺他們,怎知出來一囘身帶上門,便發現震落在地的釵簪!
她認得是天后的飾物,不禁呆住了!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誰知道一夕纏綿,她却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她的生命!
賀蘭夫人一囘到家裡,便服毒自盡。
天后似乎也不快樂,她終夜在宮中徘徊,心中又矛盾又痛苦。當惡耗傳來的時候,她禁不住流出了痛悔的眼淚。這雖然是她意料中的結果,但仍然叫她受打撃。賀蘭夫人畢竟是她唯一的親姊妹,對她有如許的恩惠,而自己却迫她走上死路!
一種極微妙與複雑的感情驅使她親自爲姊姊料理喪事,可是,投入李弘及李賢兩兄弟的眼內,祇覺得她是在猫哭老鼠假慈悲而巳。因此當天后離開賀蘭府後,李弘忽大聲呼喊起來:「我要報仇!」
五
李弘這句話並不是玩笑,他等了好久,才找到一個機會,單獨去見父親。
他去到的時候,高宗躺臥榻上,由那個江湖術士明崇儼按摩。
「兒臣叩見父王陛下!」李弘尊前跪下。
高宗見他甚喜,叫他起身。李弘畢竟年輕,冒冒失失地道:「兒臣有非常重要的秘密稟告父王!」
高宗起先不以爲意,漫應道:「說吧!」
李弘遲疑着不答,狀至神秘。高宗詫異他行動古怪,便屛退左右。
明崇儼是天后的耳目,想聽聽他們談些什麼,於是陽奉陰違走出宮,然後又鬼鬼崇祟繞到窗外窃睡。
「這事兒臣完全淸楚,王皇后是冤枉的!當時兒臣年幼無知,受母后擺佈,叫我兄弟二人混進皇后寢宮……請父王明鑒!」
「啊!」高宗踉蹐立起,感悔交进。
明崇儼一聽到這裡,慌忙去報吿天后。
天后得報立刻趕來,使他們的話沒有說完。
高宗與李弘因她突然出現,顯得很吃驚慌亂。
「怎麼,」天后不動聲色地問:「你們父子倆倒愉快地躱在這兒啦!」
「我……我們並沒有什麼要緊事!」高宗有點心虛,拼命想掩飾,反而說豁了邊。
「我難道說你們談什麼要緊事嗎?」天后眼光凌厲地朝着他倆臉上一掃。
高宗越發窘了:「我們什麼事也沒有。」
「我却有件要緊事要跟陛下商量。」
「是有關係的嗯?」
「很有關係。」高宗害怕起來,規避地囘道:「你知道,我近來頭昏目眩的病越來越厲害,什麽事你瞧着辦吧,不用跟我商量啦!」
「這對於陛下的病,並沒有什麽妨害。」
高宗無奈何,祇好聽着。原來天后擬好建言十二事,請他頒佈施行。
「一、動農桑,薄賦徭!」天后開始唸道。
「等一等,怎麼,百姓不給朝延納稅?」高宗奇怪地問。
天后解釋給他聽,說捐稅重,民不聊生。接着她又唸下去:「三、給復二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尙禁浮巧。五、有功費力役。六、廣言路……」
「慢點,」高宗又打斷她的話問:「你的意思是使得無論什麼人,都可以隨便亂講話嗎?」
「我以爲朝政得失,維繫着天下百姓性命,要想探知民間疾苦,只有廣開言路。」天后耐心地解釋,繼續唸下去:「七、杜讒口!陛下明白我的意思嗎?」她有意無意的望望李弘:「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爲母服齊喪三年!十、上元前,勛官巳經吿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
「夠啦!夠啦!」高宗頭痛更劇,不耐煩地喊起來。一「陛下肯用壐嗎?」
「你瞧着辦好啦……讓我休息休息!」高宗不支地躺下來。
天后立刻命人抬高宗囘寢宮休息,單獨留下李弘。
李弘不安到極點,不知是禍是福,自然流露出害怕之色。
天后瞧他這付神色,不禁氣餒,她一直想和兒子修好,但不知怎的却始終不能把感情建立起來。她想了一陣,温和地叫李弘走近來,對他說:「孩子,我知道這樣嚴厲地督促你,罵你,你會恨我。可是,你要明白,天下母親那一個不愛孩子,不想孩子好呀!」她忽然激動起來,停一停,又說:「可是,你並不理解你的母親,我們太疏遠了,你剛才反對我,那原因我是知道的。」
李弘痛苦地請求她別說下去,她不理,自管自說:「有許多人反對我,恨我,甚至想把我殺掉,這我都懂得。但是,我並不會被殺掉,我仍舊是站在這兒!」
她挺了挺腰幹,筆直地站着,宛似一尊天神,頑强,鋭不可當。
「我要吿訴他們說,我是一個人,別人做的事情,我都能做!別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你會覺得奇怪嗎?」
「兒臣只覺得難過!」李弘漠然答。
「不,這並不是你心裡的話,你心裡恐怕在那兒冷笑哩!」
「這未免太寃屈兒臣啦!」
「冤屈?」天后盯牢着他,忽然抓住他一只手臂,凌厲地問:「那麼吿訴我,方才我沒來以前,你們父子談了些什麼?」
「母后!」李弘似被她看穿心事,不由顫慄起來。
「你們不是在商議着怎樣損害我嗎?」
「……」
「你們不是準備和我作對嗎?」
「……」
「你們不是計劃着恩赦王皇后,然後廢我,殺我,害我嗎?」
她步步逼緊,逼得李弘透不過氣來,抖索着跪下:「母……后請想想,兒臣怎麽敢!」
天后歇斯底里地笑起來:「不必辯了,我很知道,在我體內根本流着兩種血,你,是男人的,我,是女人的,這就夠了。可是,我吿訴你吧,我總之要死的。但是,不應當死在現在,現在還沒活夠,我……我要殺她!」
她又縱聲狂笑起來,笑得李弘心裂胆破,站起來欲逃,她又冷冷道:「你要想找你父親,大可不必啦,因爲巳經來不及啦!」
李弘瞪着一雙驚懼的眼睛,明白王皇后巳遭了毒手,不由憤激地喊起來:「母后,難道你不反悔?」
「我武則天作事是從來不反悔的。」她昂起頭。樣子極横蠻冷酷,向兒子揮手:「下去吧!」
李弘沮喪地走了出去,神情活似鬥敗的公鷄。
明崇儼由後面走出,武后目露兇光地朝兒子的背影望了望,向明崇儼耳語幾句,明崇儼連連點頭。
不久李弘就暴斃在他的寢室,時維公元六七五年。
六
是年四月,李賢繼任太子。這天,他在宮中與婉兒談笑,裴炎及駱賓王忽然來訪,婉兒便退出與趙道生在宮外守望。
駱賓王是來向李賢辭行的,乘機慫恿他起義。他對李賢這樣說:「殿下,萬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我們必須預作準備才是!」
裴炎也從旁附和,接嘴道:「萬一萬歲有個三長兩短,殿下就可以相機行事,奪囘大權。」
李賢早有此意,不禁問計。
「第一、先在宮內喑議兵器,待機而動!」駱賓王献議道:「密佈心腹,以作內應!」
「這方面,臣决意派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執掌京畿兵橫。」裴炎又補充一句。
「第二、必須連結卅縣重兵,在外舉事。」駱賓王又說。
「這人……用誰好呢?」李賢出神地問。
「英國公李敬業是大唐忠臣。」裴炎搶着答:「駱主簿曾經跟他初步談過。聼說大有肅淸君側的决心,只要殿下派駱主簿再去連絡一下,想必沒有問題。」
顯然兩人早有計劃與預謀,李賢聼了大喜,請二人分頭去部署一切。
三人剛談到這裡,婉兒氣急敗壊地奔進來報訊,說天后帶着英王李哲,跟術士來到。三人駭得面面相覷,手足無措。倒是裴炎歷經險患,比较鎮靜,吩咐婉兒帶駱賓王廻避,又叫李賢取出孝經,装作在讀書的樣子。
天后多疑善猜,發現裴炎與李賢在一起,頗感詫異。幸二人掩飾得好,大談孝經諫諍那一章,說來頭頭是道,這樣才把天后瞞混過去。
天后來此目的,是要明崇儼爲李賢看相,而明崇儼却另有企圖,故言李賢福薄,非永壽之相。同時,又把英王大大捧了一番,說英王的面貌很像太宗皇帝,名符其實的帝王之相。
李賢知英王和明崇儼勾成一氣,圖奪其位,不禁把他恨之刺骨,但碍着天后之面,不敢發作。
果然天后信以爲眞,當即對李賢貴備起來,道:「像你這樣孱弱的身體,將來怎能日理萬機?」
李賢不敢作聲,心內却像滾油煎熱着一般。
天后對這個兒子一向另眼看待,此時見他一派惶恐不安,反不忍多說,走去書案,檢視他平日所讀的書典,無意中發現一首詩。詩這樣寫着:「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屛虚,欲奏江南調,貪封蓟北書,書中無別意,但悵久離居!」天后看罷,追問是誰所作。裴炎代李賢囘答,說是上官婉兒,又將上官婉兒及她母親怎樣發配在宮裡做奴隸的經過,畧約說工一些。
當天后知道婉兒祇十四歲大,不勝驚訝,惜才之念頓起,臨走時對裴炎道:「這詩我拿去,記得叫那孩子一會兒見我。」說着望了李賢一眼,又叮囑裴炎:「唉!裴侍郎,你該向殿下講些少陽正範,還要叫他學些武藝,練練身體!」
這最後一句話給藏匿在簾後的駱賓王不少啓示,一俟天后去遠,便走出對李賢建議道:
「天后不是說要殿下學練武藝嚅?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弄些兵器進宮,以圖大計!」
裴炎聼了大表贊同,心中却另有打算,望着婉兒道:「對!看來天后很喜歎你的詩,一會召見的時候,你要應對得好,討她歡喜,就可以接近她,做我們的耳目。」
婉兒一想起殺父之仇,就覺熱血沸騰,恨不能手刃這個專横殘酷的女皇后,但遇她一個弱女子有何作爲?這時聽裴炎一說,不覺高興起來。於是懐着復仇的情緒去見武則天了!
出乎她意料以外天后對她不止和靄可親,還當面試她的才學,以彩花爲題,要她寫一首五律詩。
婉兒果不負天后所望,畧一思索,一揮而就,令天后也不禁驚歎起來,執着詩箋,唸道:「春至由來發,秋還未肯疏,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爲?唔——」天后沉吟着,反覆唸後兩句,突然問:「你這兩句是什麼意思?」
婉兒心中駭然,想天后果眞聰明絕頂,看就看出詩中含譏諷之意。
幸而惡劣的環境已把婉兒磨練得非常堅强,當下她不慌不忙地囘道:「是說假的花,要以假亂眞!」
「你是否在含沙影射?」
「天后陛下,應說時是沒有一定的解釋的,要看解釋者的心境如何,陛下說我含沙影射,奴婢也不敢狡辯。」
天后想不到她小小年紀寛有這麼好的辯才,非但不生氣,反而欣賞她那倔强的性格。因爲婉兒,使她囘憶起自己的往事,同是十四歲那年,被太宗皇帝召進宮來,也因爲她倔强,所以太宗喜歡她。想不到如今在婉兒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她把自己的感想,說給婉兒聼,婉兒聼了突然對她發生了好感。不過,她們之間的仇恨,並不是三言兩絡就可以抹掉的。這點天后看得很清楚,因此特別對婉兒解釋,她爲什麼殺上官儀父子的理由,說他們祇顧個人的利益,不顧生靈塗炭,接着她又舉出事實來說。她說:
「太宗皇帝歸天的時候,天下只有三百多萬戶人家,我幫當今皇帝治理二十多年,百姓已經加到六萬戶啦!你祖父跟你父親,及諸老臣勾結在一起,反對我,仇視我,怨恨我,想廢我害我殺我,因爲我是女人,而且我把天下治理得很好,粉碎他們残民以逞的陰謀!」
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婉兒不信。她開始有點了解天后了!雖然覺得她的手段過於毒辣,排除異己不遺餘力,但她的出發點仍是爲國爲民,囘顧過去,誰有她這樣的成就呢?婉兒這樣一想,對她的觀感不由大變,因此,當天后徵表她留在自己身邊時,婉兒也不再拒絕了。
從此,婉兒與母親便搬進天后的宮內去了。
不久,宮內又發生一件驚人的事件。
原來李賢因懷恨明崇儼在天后面前進讒言,暗使心腹侍衛趙道生,剌死明崇儼。結果術士雖死,趙道生也失手就擒,連帶李賢也被捕。
事前婉兒曾力阻李賢,動他別魯莽行事,李賢不聽,以致全盤計劃粉碎!
爲了這件事,天后頗費躊躇,因李賢深獲帝愛。她想表示自己嚴明公正,有意當着高宗之面,審訊犯人。特恕趙道生不死,將她發配到奉先寺,削髪爲僧;婉兒因知情不報,處以黥刑,在她額前刺上一朶梅花,塗上硃砂,仍留在自己身邊,再予以機會改過自新。
最後輪到審訊李賢了!假如李賢肯眞心悔改,相信天后絕不會將他放逐。可是他對天后成見巳深,非但不肯乞饒,反口口聲聲指責天后,說她逼死賀蘭夫人,毒殺親兒,聽得高宗也不禁跳起,怒指他幾下耳光。但任高宗怎麼說,李賢也不信天后是自己的親母。
天后傷心之餘,即傳裴炎進宮,草擬詔書,曉諭天下,廢太子爲庶民,放逐巴州。
怎知李賢一出城外,即爲人暗殺,弄得壯志未酬身先死的下塲!
七
經過這一次變故後不久,高宗去世,中宗即位,但次年二月,又爲天后廢貶爲廬陵王,卒自僭位臨朝執政。
這是武則天全盛的時代。
接着她又頒行建言十二事。
新朝政實施後,非但沒有改善老百姓對她的觀感,反因她倒行逆施而更加不滿,以致怨聲四起,人心動盪。
裴炎苦心積慮,欲與徐敬業起義,討伐天后,但天后的權勢如日方中,令他無機可乘,唯有耐心等候。
也是合當有事,天后忽然遊興大發,到奉天縣去安葬高宗皇帝。裴炎以爲天賜機緣,機不可失,立刻召駱賓王商議,準備發難,不料事機不密,功敗垂成!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剃度後的趙道生在宮裡爲高宗皇帝做修荐大道塲。一晚,抽空去探訪上官夫人,適裴炎與駱賓王來到,商量叛國大事。駱賓王早知裴炎久懷大志,特偏造童謠,在外散播,訛稱裴炎天命所歸,當繼大位,以堅其謀反之意;並且爲他在揚州找到了一個面貌酷似太子賢的人,打算挾其號召天下。裴炎大喜,即派親信隨駱賓王同往徐敬業處,約時起義。
至此上官夫人及趙道生始知裴炎的野心,趙道生爲報天后不殺之恩,連夜趕往奉天縣報訊。
裴炎老謀深算,因駱賓王是徐敬業的心腹,恐爲他出賣,一面和駱實王週旋,一面又派人攔途把他截囘,囚入天牢,然後誘使徐敬業發兵長安,這一邊又叫黨羽程務挺按兵不動,實行一石二鳥的辦法,這樣自己便可坐享其成,奪取天下。
這計劃不可謂不毒辣,但他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天后先發制人,突然提早囘宮,把裴炎軟禁起來,一面密令大將李孝逸立斬程務挺,然後領兵三十萬兼程南下,一舉平定徐敬業。
捷報傳來時,天娟正與婉兒書內談論駱賓王所作之「討武曌檄」,內史騫味道帯李孝逸的奏章進來,因奏章內提及捉到一個假太子,因而勾起天后的傷感。遣走秦味道後,便對婉兒吐露心事,說她實在愛李賢,當時送他去巴蜀,實有別用意,想等高宗去世以後,就把他召囘,讓他即位。說到這裡,天后的表情黯淡下來,兩眼微紅。稍停,又歎息道:「我曾歷跟裴炎談過這件事,沒想到……賢兒就被人殺害!外面不明眞相的人,還以爲是我派人去殺的,我旣受失子之痛,又蒙殺子之名,怎不叫我傷心哩!」說着眼淚奪眶而出,神情鬱鬱不歓。
婉兒第一次看到這個頑强的女人落涙,也第一次在她臉上找到母性的情感。然而,她仍懷疑這番話的眞實性。究竟是誰害了太子賢?不是她,還有誰?
一連串的問號閃入婉兒的腦際,她想了想,突有所悟,立刻借意離開天后。
她爲了証實她的推想,於是着手去調査這事的眞象。
當晚,她到合碧宮去探防被软禁的裴炎。裴炎不知婉兒早巳變志,猶當她是自己的心腹,殷殷向她追問外邊的情形。婉兒據實以吿,所有參與此事的人,皆被天后殺的殺,捉的捉,無一人漏網。裴炎知道大勢巳去,向婉兒求助。兩人正談着,突然一陣風吹來,吹得燭光推曳不定,跟着又聽到啾啾的叫聲,門角落馬上出現一個披頭散髪的黑影!
裴炎定睛一看,駭得毛骨悚然,兩條腿簌簌抖起來,指着黑影,抖着喊:「啊!鬼!鬼!婉兒,那……那不是太子殿下嗎?」
婉兒見他駭得這樣,巳料到幾分,故意向四邊掃望,說:「什麼也沒有啊,你自己在疑神疑鬼!」
黑影又移動了幾步,使裴炎更清楚的看到,那面孔的確和李賢長得一模一樣,而且黑影身後還随着兩個鬼卒,更叫裴炎相信那是李賢的鬼魂無疑。
他們手指着裴炎,怒目瞪視,活似向他索命的模樣。
陰風一陣陣吹來,燭明忽光忽暗,空氣端的陰森恐怖,如同處身鬼域。
裴炎的胆子,爲這可怖的氣氛嚇破了!不由屈膝跪下,不打自招地哀求道:「太子殿下,你饒恕我吧,是我買通左金吾將軍邱神勣假傳聖旨把你殺害,原想等我做了皇帝封贈你的呀!如今我皇帝做不成了,但我會超度你,你饒了我吧!」他一面討饒,一面不停的磕頭。
婉兒感到滿意了,暗示鬼魂退下,然後假惺地去安慰裴炎,拉他坐起。
裴炎仍不知這是婉兒故弄的玄虛,喘定一口氣,又在轉懷念頭了,他對婉兒說:「我還有一着棋,看你是不是肯幫我忙?」
婉兒心裡可把他恨透了,臉上却裝出一派天眞,囘道:「你說吧!」
裴炎從懷掏出一小紙包,愼重地道:「你把這砒霜分爲兩半,一半偸偸的放在天后菜飯裡面,還有一半讓駱賓王吃吧!」
「駱賓王?」婉兒早以爲他死了,突然聽裴炎提及,不禁驚訝的喊起來。
「駱賓王沒有到楊州去,是我把他關在天牢裡的!」假如不是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婉兒眞不相信裴炎是這樣詐奸、陰險、狠毒!心想眞該把他萬刀剁成肉醬不可,這樣才能洩去她心頭之憤哩!
眞相大白後,裴炎終於自食其果,連同他的黨羽薛仲璋,於都亭驛斬首示衆。
天后素重駱實王的文才,復会他年老,不忍施以重刑,即發配到杭州靈隱寺剃度爲僧。
八
叛變平定之後,天后御則天樓,改國號曰「周」,自稱聖神皇帝。
當聖神皇帝八十一歲生辰那天,她戴皇冠,御龍袍,端坐在則天摟上,接受文武百官的頌揚歓呼,萬歲之聲不絕於耳,這時天后不免躊躇滿志,以她一個弱女子,竟然赤手空拳與這個惡劣的環境鬥爭,控制這個國家數十年,如今一切平定,羣臣懾服,個個伏在她的脚下,怎不叫她覺得自豪與驕傲?
然而,她想錯了!謀反的運動正方興未艾,祗是因爲時間沒有到而巳!
當晚,天后在萬象神宮歡宴羣臣,同時由武士們表演七德九功舞助興。
婉兒一直侍立在天后身旁,無意中發現她身子搖搖欲墜,一臉疲態,不禁關心地問:「皇帝陛下怎麽啦?」
天后聼了暗自一驚,强行振作起來,馬上又恢復她往常一樣,把嘴巴緊緊抿着,露出堅毅不拔,頑强不屈的神態。
當表演正熱鬧的時候,突然有個太監氣急敗壞地從宮外奔入,報吿薛懷義縱火燒明堂,散騎常侍張昌宗及司衛少卿張易之叛變,率兵殺進宮來。
彷彿晴天一聲霹靂,全朝震動,又彷彿一顆炸彈投擲進來,在天后面前爆炸,使她平地從皇座上跳起,身子微微幌了幌,但立刻又站定了!
這時候,一切都停頓下來。
宮內變得鴉雀無聲,而宮外却愈來愈嘈雜,火光照紅半邊天。看樣子那一天終於來到了!
天后環視羣臣,每一張面孔都顯出驚懼之色,呆若木鷄地愕着,彷彿末日來臨。她的心開始往下沉,沉!怎的無人敢挺身站出鎭壓?怎的無人敢說一句話?那怕是一句反對她的話,她也愛聽。然而,誰也沒有講話,像死去一般的兀立着。她感到心痛、悲憤,突然嘶叫起來:「你們還不給我出去救火!」
所有人都爭先恐後地走了,祇婉兒及忠心的徐有功留在她身邊。
偌大的一個宮殿,頓時變得異常的冷落,蕭索!
天后的信念崩潰了,但她仍在掙扎着,力圖振作,因此當婉兒勸她暫避一下時,她傲然說:「我不怕的,我要讓他們看看我是什麼人!」
徐有功力陳利害,勸她禪位休息,還政給廬陵王。天后聼了,歇斯底里的大笑起來:「怎麼?你已經想到我死了嗎?」
徐有功很想無情的說一句:「你已經到了風燭殘年了!」但他這句話尙未說出口,天后突然止笑,兩眼凌厲地望着前面,原來是張宗昌與張易之按劍而入,士卒們手抓火把兵器跟隨在後。
儘管怒火在天后心內燃燒,但她的意志却像頑鐵一樣剛强,態度也顯得出奇的冷靜。
她目不稍瞬地注視着這兩個叛徒,瞧着他們緩緩走上前來,對她祇作揖拜却但不跪下。
婉兒與徐有功暗暗在担心,深怕兩人對天后不利。但不知怎的,天后好似有種攝人的魔力,使人不由心怯起來;她的神氣高傲而頑强,叫人不敢迫近,兩只脚自然的停止不前了。
結果天后不費吹灰之力,就將叛黨征服下來,先是士卒們跪下,表示矢忠効皇,接着張宗昌及張易之也像被她奪去心魄,棄劍下跪,求她開恩。
天后鄙視這兩個懦弱無用的像伙,覺得他們不値得她砍,輕輕將他們發落走了。
這時候,天后感到不支了,一陣疲倦欲死的感覺,悄悄襲上心頭,死亡的陰影在她眼前出現了!她遣走婉兒及徐有功,遣走太監與宮女們;她不願讓人看到她那衰颯的老態,她要單獨與死神作戰。
所有的人都走開了,她軟弱無力的倒在皇座下,思索着,思索着……
無數的幻影在她眼前飛舞,一個一個,像走馬燈似的,指着她凌笑,笑得她頭痛欲裂,掙扎着站起來。
幻影消失了!她留戀地撫摸着竇座,然後又走去撫摸御案,她的生命就在這裡發出光輝,她的力量就在這裡得以延續。
於是,她昂起頭,傲視一切,有誰比她更偉大呢?
最後,她拿起駱賓王那份「討武曌檄文」來看,文中對她聲聲指責,大加撻伐,仿佛她是國家的罪人,老百姓的公敵。
她責問自己,究竟作錯了什麼?
但誰能囘答她呢?
她漠視空間,漸漸感到死神的脚步,愈走愈近。
她掙扎着,想囘到寶座上,終於因爲體力不支,倒在地下。
但她仍不想放棄這個願望。於是,她慢慢爬過去,當她的指尖剛預到寶座的邊緣,她吐出最後一口氣,含笑而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