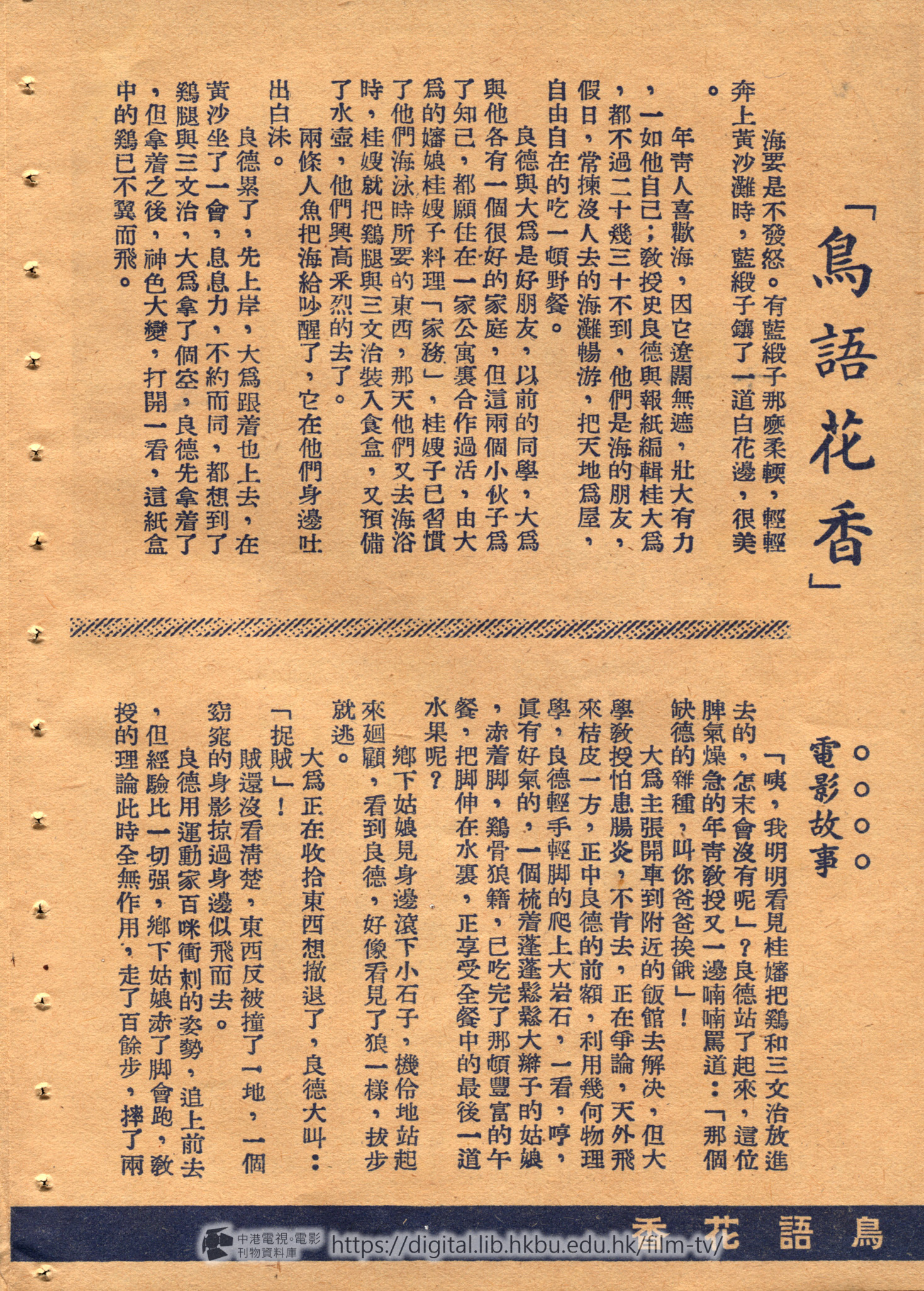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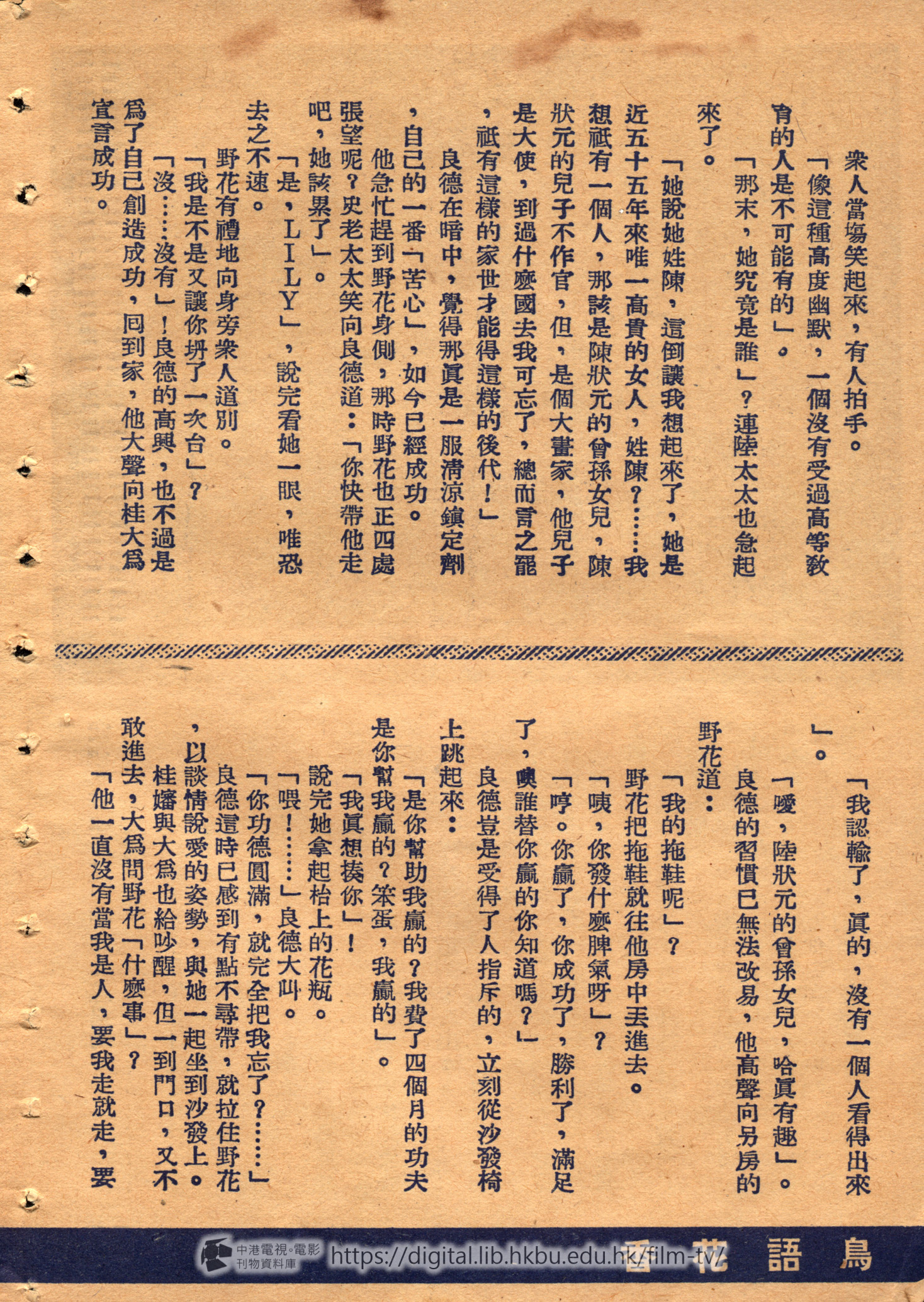


「鳥語花香」
電影故事
海要是不發怒。有藍緞子那麽柔輭,輕輕奔上黃沙灘時,藍緞子鑲了一道白花邊,很美。
年靑人喜歡海,因它遼闊無遮,壯大有力,一如他自己;敎授史良德與報紙編輯桂大爲,都不過二十幾三十不到,他們是海的朋友,假日,常揀沒人去的海灘暢游,把天地爲屋,自由自在的吃一頓野餐。
良德與大爲是好朋友,以前的同學,大爲與他各有一個很好的家庭,但這兩個小伙子爲了知己,都願住在一家公寓裏合作過活,由大爲的嬸娘桂嫂子料理「家務」,桂嫂子已習慣了他們海泳時所要的東西,那天他們又去海浴時,桂嫂就把鷄腿與三文治裝入食盒,又預備了水壺,他們興高釆烈的去了。
兩條人魚把海給吵醒了,它在他們身邊吐出白沬。
良德累了,先上岸,大爲跟着也上去,在黃沙坐了一會,息息力,不約而同,都想到了鷄腿與三文治,大爲拿了個空,良德先拿着了,但拿着之後,神色大變,打開一看,這紙盒中的鷄已不翼而飛。
「咦,我明明看見桂嬸把鷄和三文治放進去的,怎末會沒有呢」?良德站了起來,這位脾氣燥急的年靑教授又一邊喃喃罵道:「那個缺德的雜種,叫你爸爸挨餓」!
大爲主張開車到附近的飯館去解决但大學敎授怕患腸炎,不肯去,正在爭論,天外飛來桔皮一方,正中良德的前額,利用幾何物理學,良德輕手輕脚的爬上大岩石,一看,哼,眞有好氣的,一個梳着蓬蓬鬆鬆大瓣子的姑娘,赤着脚,鷄骨狼籍,已吃完了那頓豐富的午餐,把脚伸在水裏,正享受全餐中的最後一道水果呢?
鄕下姑娘見身邊滾下小石子,機伶地站起來廻顧,看到良德,好像看見了狼一樣,拔步就逃。
大爲正在收拾東西想撤退了,良德大叫:「捉賊」!
賊還沒看清楚,東西反被撞了一地,一個窈窕的身影掠過身邊似飛而去。
良德用運動家百咪衝刺的姿勢,追上前去,但經驗比一切强,鄕下姑娘赤了脚會跑,敎授的理論此時全無作用,走了百餘步,摔了兩三次。
穿過那條大馬路,又進竹林,人很少,祇有幾個鄕下人偶而佇立以驚奇目光看這個一女一男的長途賽。
小溪中鴨子因此振翼,過了小橋,有一幢木屋,背山向林,大樹蔭覆,小鳥輕唱,有一位肓了眼的老奶奶在樹蔭下編草帽。
「誰」?目盲耳聰,她聽得有人聲就注意發問。
「剛才有個女孩子你看見沒有」?
盲奶奶看他這末兇,不理,他再問,盲奶奶忍不住問了:
「這麼兇的,你是誰」?
良德自己也覺不太禮貌,正在尷尬,盲奶奶又開口了:
「走,走,這是我的家,走遠些」!
良德故意大步的走,其實繞向樹後看她們動靜,盲奶奶心裏很明白,這位淘氣的姪女兒又不知闖了什麽禍,聽着良德的脚步聲已遠,於是生氣地高叫「野花,野花,快過來!」
那位盲奶奶口中的「野花」出來了,就是良德心裏的「賊」。
她走出屋看看,一眼見了良德又廻身逃,良德拼力追去,口中大聲嚷嚷:「我看你逃那兒去」?
他追近屋,忽然眼前金星直冒,中了伏,野花端端正正用大竹竿在他頭上打了一下,良德呱呱叫痛,盲奶奶喝住了野花:
「不要頑皮,喂,你究竟爲什麽找她」?
「她偷吃我的東西」!
「唉,一會兒叔叔要是囘來,又得挨一頓打」。
「我不怕」!野花忿怒地看良德,盲奶奶叫野花把東西還他,但野花承認已吃下肚子去,並且又得意地吿訴盲奶奶道:「嬸嬸,我還給你留下一份呢?我們不是好幾天沒有吃過肉了」?
良德愈聽愈覺不忍,方才的火氣已經完全消除,他也不再聽下去了,帶着一身「傷痕」囘去,走了幾步,背後忽然有人叫:「喂,喂」!
囘頭一看,分外眼紅,就是那野姑娘野花。
「幹什麽」?
「喂,你爲什麽吿訴我嬸嬸」?
「野……我……我……」對着那雙天眞無邪的大眼珠,他一時倒反說不上話了,正在嚅嚅吶吶一杷泥像劍光般飛到,弄了一身,野花一邊逃,又高叫:「我,我,我,小氣鬼,多嘴鬼」!
良德在半途就看見大爲坐汽車來,對於這位忠勇捕賊受傷歸來的老朋友,大爲又氣又好笑。
囘到家裏,吃完飯,籐椅上靠靠,悠然抽了一支烟,看看晚報,良德把日間的事忘了,看到報上一段新聞,他的社會學又作怪了,他落入沉思,大爲叫他不應,推他才醒:
「你又看見什麼了?」
「一個失戀的人,爬上高樓想自殺,這眞是笑話,你看看!」
大爲看報,良德歎了口氣道:
「我眞不知道女人有什麽好……女人……」
桂嬸剛端茶進來,聽了微笑道:「你讓我走了再說好不好?啊,說是,差點兒忘了,有個女人打電話給你」!
「我?誰」?
「大槪是老太太,叫你明天囘去吃晚飯」!
良德聽了很窘,訕訕地把飮茶作爲掩飾,幸好,桂嬸走了。
臨走又吿訴大爲,某小姐來電話,某小姐約他……
大爲拍拍腦袋道:「該死,把約會忘記了」。
「那你也去跳樓吧!該死!把自己看得太不値價了,你嬸娘在我不不好意思說,其實呢?女人就是麻煩,麻煩就是女人」。
大爲笑道:「舉個例,史良德敎授沙灘遇美」。
「哈!……」史良德也笑了。
正笑,門鈴響了,桂嬸來報,有兩位小姐來訪,大爲一看自己與良德都袒裼裸裎,十分肉感,一急,跳起來往房裏就逃。
良德跟到房門口道:「女人等於麻煩,麻煩等於女人,再舉一例,桂大爲編輯赤身見美」!
小姐們看見良德赤身,作驚叫並憤怒又不屑之狀,良德火了,他推開大爲房門高聲像喊:
「你這兩位姑奶奶,怎一點兒禮貌也不懂的?這是單身漢住的地方,怎麽瞎撞?」
兩位小姐「是可忍孰不可忍」,轉身就走,大爲要攔也攔不得,門已經開了,
大爲氣得發抖,但也奈何這位良朋不得,良德勸大爲:
「像這種裝模作樣的女人,你去跟她們談戀愛,我史良德眞要與你絕交了」。
「唉,人家是高貴的小姐,十個有十個是這樣的」!
「我快吐了,高貴什麼?任何一個女人都可以做成這樣」!
「那話我反對,畢竟一個人的氣度上看得出她出身」!
「看得出?方才沙灘上那野女孩子祗要我肯敎她,不出三月,我可以改造成一位高貴小姐」。
大爲冷笑,良德知道是笑自己,他發揮宏論,他說:「在今天硏究社會學的人,應該否定遺傳,而且必須認識環境與敎育,據一九五三年,歐洲各國的統計……」
「得啦,反正放暑假,不妨來一個實驗,我們賭一下如何」?
「行,三個月……」
「我給你四個月,四個月以後她要變成一位高貴的小姐,沒有人看得出她的出身」。
他們兩位年靑人訂定了協約——四個月後成功,四月中改造費用槪由他(大爲)付,不然,良德雙倍歸還大爲的錢,還得在大爲所編的雜誌上,發表改造失敗的經過。
良德果然在第二天的一早就趕到野花家去,遇上野花的叔叔,他提出的要求是借野花四個月,毎月津貼他們夫婦二百元,保證,野花不會受一點損害。
由於史家是有地位的,野花的叔叔答應了,當然,一半還是錢在作怪。
千哄萬騙,才把野花說服,她以爲良德是來復仇的,叔叔解釋給她聽,人家是善意的,要她去作四個月事,不勞苦,祗要她聽他的話就是了。
野花答應與良德同去,可是心裏還是放不下,又捨不得她的朋友——那頭小鳥,良德替她拿了一起走。
野花第一次上汽車,鄕下人都以奇怪的目光看她,在汽車裏她一直不坐,直到汽車一停,她却又坐下了,被逼的。
良德開了車門,野花才下,大爲在陽台上看到,大吃一驚,嬸嬸是知道那件事的,趕緊去開門,門開了,祗見良德並無野花,良德這一急非同小可,囘頭看不見人,却聽得野花在電梯裏大叫,那架自動電梯,已直升上去,德趕快按住電鈕,才使電梯下來。
一進門,良德就跟野花來了個下馬威,他指着她說:
「從現在起,不得許可,不許走出這扇門」。
介紹完大爲及桂嬸,野花的眼睛貪婪地諦視着桌上一個盆子,盆裏是她曾禁吃過的美味食物——三文治。
良德把三文治給她吃,又與大爲訂定,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七點三十八分開始改造工作。
又爲野花拍了「工作照片」第一張。
良德叫嬸娘陪野花脫衣服洗澡,把她的舊衣服燒去,剪短頭髮,洗四次頭,用消毒劑……
野花不願意,她指了指一裸體石膏像說:「你要燒去我的衣服,你要把我變成她?先生,我們雖然窮,也是清白人家,我還念過書,我囘去了」。
「不不,你不要想錯,我不要你做那個,我要把你改成另外一個人,一個小姐」。
說完,良德把雜誌上的美女指給她看道:「不是光穿的漂亮,打扮得好,而且還要敎你坐的好看,站的好看,吃的好看,說話說得好聽,要是你不聽我的話,你叔叔叫我打你,你要是聽我的話,那末四個月以後,你就可以跟她一樣,像一個公主」。
「公豬」?野花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第一道難關已過,良德向大爲要錢,買野花的需要衣服,大爲叫他把發票帶囘來。
買來的衣服,不是十分合適,但已改觀了,又印下了第二張照片。
敎會她一件事是不容易的,譬如一個鐘上的時間,已够攪的了。
吃東西的禮節亦然,叫她喝酒,她就拼命的喝,漸漸的良德覺得有點棘手,但他還是一意要把她改造成功,大爲却認爲要把這樣一個傻頭傻腦的姑娘改成公主,眞是太累的事。
幾天之後,野花在良德裝修機器似的訓練下,漸有進步,但,她對過去生活還是念念不忘,常常會在半夜裏起身去看看她那頭小鳥。
大爲看看有點不忍了,他向良德道:「我們爲什麽要叫她這樣?剝削了人家自由,塗改了人家的未來面目,是爲了什麽」?
「哼,要證明我史良德的話」。
良德像一個馴獸師,一邊用鞭子,一邊用肉食。
野花在他的改造下,漸漸學會怎樣坐,不是雙足平開八字式,要坐得妙,脚遮脚,又穿了高跟鞋走路,經過七跌八跌大翻身,吃盡痛苦,終算能走幾步了,一直到完全自然,良德化了不少力氣。
野花得毎天在頭上頂着一本厚厚的書走路,求其姿態之美,又學習各種拿杯子方法,認清了各種酒的牌子,又訓練成功用刀乂劍戟十八般武器的西菜吃法。
每一次遭到良德的痛斥,野花忍不住哭,但是八百元錢使她無法擺脫良德的桎梏。
良德的壓力一天重一天,野花耐不得,一晚,她偷偷起身拿了鳥籠,逃囘了木屋——她的家,自由的世界。
盲眼的嬸嬸驚問:「是誰」,野花却祗知嗚咽,但聲音是盲嬸聽得出來的,她叫野花伏在她脚邊,盲嬸摸摸她頭髮,辮子不見,摸摸衣服也好像沒穿,其實呢?穿的衣服太時新款式,跟多長了一層皮一般。
野花盡情痛哭。
「你哭什麼呀」!
在房裏的叔父也聽到了,就走到門口問野花道:
「你怎麽變外國人了?他們欺負你」?
野花說她吃得飽,穿得好,睡得舒服,但是他們限止了她的一切。
叔父大惑不解:「待你這末好,說是欺負?還不快囘去」。
「我不囘」!野花哀鳴道。
「你……」叔父又要動手打,嬸子盲了眼亂拉叫道:
「你要是打,我跟你拼命」!
叔父咕嚷着,盲嬸却主張把錢還給人家,但叔父已化了六十元付了牌照費了。
野花爲了免叔父嬸子爲難起見,以絕望的神色,挽了鳥籠,再囘她的「鳥籠」中去。
二次歸來後的野花她好像已認了命,聽候良德擺佈,良德却高興了,由大爲敎會她打網球,游泳,歷盡艱辛,大爲與良德也覺得疲乏。
連跳舞都學會了,野花被良德改了個名字,叫做「LILY」改姓了陳,也就是密司陳。
最要緊的還有裝模作樣的七十二種表情,喜怒哀樂嬌嗔媚……經過一番敎育,七十二種也會了大半之多。
每天,良德劃定一張課程表,叫她學習功課,所謂功課,也就是七十二種表情啦,一百五十個外國電影明星的名字咧,這些跟那些……
在野花,不,LILY心中,對良德心中有了矛盾的感情,她偷偷問桂嬸:「桂太太,你說良德沒有女朋友」?
「誰喜歡他?那張嘴一天到晚的駡人」!
「他不是有個母親的」?
「跟他一樣,也是貧嘴。」
這母子兩張嘴這時也正在交談,良德吿訴他母觀:
「我想帶一個人來見見您」!
「是一位小姐」?
「唔……是的」。
「哈哈,現在你才曉得「男大當婚」的意思了吧」?
「不,你想錯了,我這跟男大當婚沒有關係」。
他接着就說出有這末一囘事,要他母親鑑賞批評他的得意雕刻品——野花,看她是否看得出她是一位野姑娘?
母親當然答應了,第二天,野花由大爲帶着去,結果,弄得一塲大笑話,把良德給氣得要死,不單此也,做母親的又打個電話給兒子,在電話裏又敎訓了他一塲,說什麽想到了一個比方囉,你們做這件事就好像古時女人纏小足,把天然的東西做成一件畸形怪物……
良德氣得發昏章第十七,他暴跳似雷道:「我非把她訓練成功不可。」
野花頭上頂着一册書出來,良德的怒火全升了起來,他指着野花高聲道:
「LILY,你聽好,今天你使我坍了一次台,可是我還一定要把你改成一個,一個高貴的小姐,你必須聽我的話,每天用用你的腦子,過去,每天工作是八小時,現在起,每天增加到十二小時,你要拼命的練,練,練」!
野花果然拼命的練,第一節目,先練坐的姿勢,坐遍了各式各樣的椅子沙發,二練走,走來走去,三練表情,擠眉弄眼,搔首弄姿,四練化粧,彎彎眉毛,鮮紅嘴唇,她練呀練的,學無止境,但越練越熟却是不言可知的,她漸有熟能生巧之感。
戶內的練妥了,就練戶外的,學開汽車,學打網球,學游泳。
良德又帶了她去跳舞,各式各樣的舞,由華爾滋到「格拉却」,又帶她吃飯,飮茶,形式上已經非常的完美了。
那晚,野花,良德,大爲,桂嬸,「工作」方畢,想要開飯擺筵的時候,門鈴忽響,原來是大爲的女朋友李小姐來訪,良德與大爲怕野花鬧笑話,一時無處安放,就把她按入桌子底下去,然後去開門。
李小姐打扮得花似一朵。
「哈,大爲」!
「哈囉!台莉斯」。
「吃飯嗎」?李小姐看了餐桌一眼,大爲立刻接口問:
「你還沒吃吧」?
桂嬸忙於按排各人就座,在桌子底下的野花,常見李小姐的手與大爲的手,時常相握,在桌子底下看得很淸楚,十分奇怪:「這算是什麽」?
野花將窒息的時候,李小姐才走。
這一天起,野花的心裏有點異樣感覺,他老想念着所看到的兩隻緊握着的手。
若干天來,良德對於野花漸有好感,由於她的確漸漸進步中。
野花依舊勤練「武功祕訣」似的「手,眼,身,法,步」,桂嬸拿了一封信進來,信是張家大少爺寫來的,張大少爺自從在史良德母親處見到野花,就一直單戀她,這封已經是第二十一封了,野花很奇怪,她問桂嬸:
「怎麽他老是寫信來」?
「這人對你癡心呀」?
「什麼叫癡心」?野花不能消化這個新名詞,桂嬸想了半天道:「癡心嗎……就是愛」。
「什麼是愛」?野花依舊茫然。
「愛嗎?……」桂嬸再也答不上來了,野花分析半天:
「也許就是喜歡的意思」!
「這不是歡喜,問題在……」
「桂嬸,你愛過沒有哇?好不好玩」?
桂嬸居然臉色發紅,她吶吶然說:
「這是男人跟女人之間一件奇怪的事,不是好玩不好玩的」
「怎麽樣的」?打碎沙煲問到底,桂嬸一知半解的道:
「我也說不出,總之,心理,舉止上都變得很奇怪,比如苔莉斯跟大爲他們的就是愛,你到那個時候就會知道了」
野花又想起了那一對緊握着的手。
到吃晚飯的時候,野花看着餐桌發呆,到晚飯時,她坐在良德身邊,見良德的手在桌面上,就一手把他的手拉到桌下,良德爲此突然而來的襲擊,大吃一驚,,急忙把手摔開,野花又吃一驚,她想:「我這不是很好嗎」?由此失望而哭泣起來。
雖然已過了幾天的事了,野花心中老橫梗着一個問題,乘着桂大爲在車上等良德去買東西時,就問起這個問題,大爲笑道:
「LILY」我吿訴你,這種是很難解釋的,一定要男的心理喜歡這樣,女的心理也喜歡這樣,那才行,單是女的或男的心理喜歡這樣是不行的」!
「那麼,怎樣才可以使男的喜歡這女的呢」?
「這……這樣,LILY,」他嚥了口唾沬道:
「比如那男人所喜歡的事,女的也要喜歡」。
「這我明白了」。
「你要聽好,男的要聽女的話,同時,女的也要聽男的話,這也行」。
「我還是不大懂,剛才還有點明白,讓你這一說,反而糊塗了」。
「不說它了,LILY,你究竟是不是喜歡良德」?
「我……我不知道」!
「你如果喜歡良德,就應該隨時注意良德所喜歡的東西,譬如說他喜歡唱歌……」
「他不喜歡唱歌」,野花截斷了他的話,大爲搖頭道:「我是譬喩着這末說」!
「嬸娘說,他喜歡駡人」!
「那你……」一眼望見良德出來,就趕快說完了,心裏暗笑。
良德剛想踩上「風門」開車,大爲却想起要打個電話,於是良德在無聊之餘問剛才與大爲說些什麽?
「我先問你,你是不是喜歡駡人」?
良德奇怪地看她:「誰說的」?
「那你喜歡什麽」?
「我啊!我希望把你改成一個公主」。
「我能成爲一個公主嗎」?
「當然,祗要你聽我的話」!
「好,我以後聽你的話」。
車子開走了,野花癡癡想着良德與大爲的話,微笑一陣,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覺。
良德這次歸來,顯得很緊張的樣子,他拿出兩張請柬來道:「野花,不,LILY,你聽好了,六號晚上,將是你在這裏的最後一個晚上,同時那天晚上將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慈善舞會,是你從來也沒見過的,這是請帖,大爲也去,我媽也去,我帶你去,這是個大塲面,是你從來沒有見過的,在這一禮拜中,一定要加緊練習,我一定要你變成那舞會裏的公主」。
野花靜聽着,聽完又神祕的一笑。
盛大的慈善舞會,跟着日子走近逼達而展開!
一個城裏最大的夜花園四週滿綴着燈彩,近海邊有一排在在風中挺着下肢而鞠躬甚頻的棕櫚樹,樹底下擺着一桌鷄尾酒,那些有錢有地位的人,男的燕尾服,黑白分明,女的珍飾一身,五光十色,加上燈彩及鷄尾酒的各種顏色,眞有令人目不暇擊之感。
那些人中,包括有張家大少爺與他兩個妹妹,史良德的母親,有名的陸敎授夫婦,紛紛取了酒,聚在一隅,間談家常,母親看兒子還不來,笑向陸敎授道:
「你看見我那寳貝兒子沒有」?
「沒有,我們先到那邊去吧」?
花園走盡,就是大廳,廳裏設有舞池,池中一對又一對的男女,正興高釆烈的跳着舞,音樂很好,奏的都是最新流行曲。
桂大爲與李小姐是一對舞侶,但人太多了,大爲顯得有點累,他請李小姐避入花園中去,剛到花園,遠遠就看見良德的車燈射過又斜向一邊,車門由BOY開了,良德禮貌地扶着LILY下車,LILY今天漂亮極了,華貴而不俗的白紗夜禮服,垂鬢短髮,掛着大方而甜的笑,正蓮步姗姗地走進來。
那邊的張少爺看得怔住了,心癢癢地,也別說是他,每一個在此作客的,當LILY經過時,雙脚雙目像頑鐵遇到了吸鐵石似不能轉動而飛向她身上去。
今天的野花是栽在水盆,彩瓶裏的牡丹一樣,良德心裏反覺得有點慌,野花發覺了,低聲說:
「你不用慌」。
「這不是你第一次上戲塲嗎」?
「我可不是第一次,最少也百次以上了,現在就像在作夢,你別叫醒我,要不然,我會把一切都忘記的」。
「是」!
正說時陸敎授在遠處來。
「喂,那就是陸敎授,這人的眼光很凶,你可當心」!
「我才不怕」。
大爲與李小姐過來,兩個男人與兩位小姐介紹了。
李小姐笑問LILY道:「眞熱鬧」!
「噯」!野花點點頭,落落大方。
良德的母親來了,大爲用警吿的口氣道:「你媽來了」!
史太太一路走過來,已聽不少人在談或問她:「史太太,那位跟少爺一起的小姐是誰呀?眞漂亮」!
做母親的心裏十分高興,良德爲LILY的禮貌起見,扶她迎上去,同時說:
「媽,陳小姐來看您」!
「伯母您請坐」!野花自然地。
良德見人多,怕露馬脚,起來拉了野花想去跳舞,不料竟是一個冷門,野花說:
「不,你不是有許多朋友要談談嗎?我在這裏跟老太太談談好了」,
良德祗好走,却看見陸敎授走近野花,他心裏眞着急,一邊又聽得許多人問大爲:
「這究竟是誰呀?大爲」!
「我也不知道,是良德的新朋友」!
又有女人問:「桂先生,這位小姐是外埠來的吧」?
另有一位却岔開問題道:「你看她的衣服多美呀」?
有一位仁兄忽然想到査日記本。
另有一位却笑這位仁兄道:「放心,你的日記本上不會有她」!
良德躱在暗隅,聽了心裏雖高興,但想起陸敎授,不由他心裏不緊張起來。
陸敎授過來了,良德的心直跳,敎授一到人羣處,高聲道:「給我一杯酒」!
酒來,他又哈哈大笑,良德心想「完」!這會準「砸」了。
陸敎授道:「據我硏究下來,這位小姐,旣不是富商女兒,也不是什麽大官之女,他的出身可不平凡,我故意用英文和她說話,你猜她怎麽說來着,她說你要和我說中國話,不要和我說日本話!你們聽,這話多幽默」?
衆人當塲笑起來,有人拍手。
「像這種高度幽默,一個沒有受過高等敎育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那末,她究竟是誰」?連陸太太也急起來了。
「她說她姓陳,這倒讓我想起來了,她是近五十五年來唯一高貴的女人,姓陳?……我想祗有一個人,那該是陳狀元的曾孫女兒,陳狀元的兒子不作官,但,是個大畫家,他兒子是大使,到過什麼國去我可忘了,總而言之罷,祗有這樣的家世才能得這樣的後代!」
良德在暗中,覺得那眞是一服清涼鎭定劑,自己的一番「苦心」,如今巳經成功。
他急忙趕到野花身側,那時野花也正四處張望呢?史老太太笑向良德道:「你快帶他走吧,她該累了」。
「是,LILY」,說完看她一眼,唯恐去之不速。
野花有禮地向身旁衆人道別。
「我是不是又讓你坍了一次台」?
「沒……沒有」!良德的高興,也不過是爲了自己創造成功,囘到家,他大聲向桂大爲宣言成功。
「我認輸了,眞的,沒有一個人看得出來」。
「噯,陸狀元的曾孫女兒,哈眞有趣」。
良德的習慣已無法改易,他高聲向另房的野花道:
「我的拖鞋呢」?
野花把拖鞋就往他房中丟進去。
「咦,你發什麽脾氣呀」?
「哼。你贏了,你成功了,勝利了,滿足了,噢誰替你贏的你知道嗎?」
良德豈是受得了人指斥的,立刻從沙發椅上跳起來:
「是你幫助我贏的?我費了四個月的功夫是你幫我贏的?笨蛋,我贏的」。
「我眞想撲你」!
說完她拿起枱上的花瓶。
「喂!……」良德大叫。
「你功德圓滿,就完全把我忘了?……」
良德這時已感到有點不尋帶,就拉住野花,以談情說愛的姿勢,與她一起坐到沙發上。
桂嬸與大爲也給吵醒,但一到門口,又不敢進去,大爲問野花「什麽事」?
「他一直沒有當我是人,要我走就走,要我坐,就坐,就跟個洋娃娃似的」。
良德又跳起來了:「本來。我就是這希望嗎」!
大爲按下他道:「你……」
「他謝了天,謝了地,却不謝我,明天我怎末樣,他也沒想過」。
「噢,原來你爲這個,明天你要囘去就囘去,我送你囘去,你要是願意在這裏多住幾天,我也沒有趕你」!
野花也不理他,轉問大爲道:「這衣服是我的還是你的」?
「當然是你的」!
「你們假如要再試另外一個野花呢」?
「眞厲害你倒學會了損人」!良德插嘴。
「不要你開口,我要知道,我身上有什麽東西是我的,我不能不穿衣服走出去,因爲你們把我衣服燒了。像你媽的畫像才好看哪」!
這話使他火更大了,他簡直想打野花,野花眼快,良德還沒「出手」早就挨她一頓踢。
野花把項鍊耳環一一拉下,擲給良德,同時,又除下鞋,把鞋往良德頭上去敲,大爲拉住了。
野花的激動的感情,奔發於一瞬間:r鳥生來是會唱的,你偏不讓牠唱,最好改變成像你這一樣的牛叫」!說完,她去拿了鳥籠:「花也一樣,花一生長就有香味,你要改變他的香味,這裏,祗有你,沒有我,出了這門,我就是我,我可以自由選擇我歡喜的聲音,我不作什麽狀元的曾孫女,我要自自在在的做一個人」!
說完野花頭也不囘的直着身子走了。
祗有桂嬸,處世經驗最豐,她指着良德,吿訴良德,野花已愛上了他。
良德由嬸母的話,及自身因野花之去,而心理頗有點惆悵,忽有所悟,他開了門直追出去。
野花有的是恨,良德去拉她,她拼死打。
良德也奔不動了,又加上野花一脚,他就跌倒在地上。
野花一味要囘家,走,走,走,但走到後來,脚底有了黏膠一樣,走不了啦,囘頭看看良德,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又起,她忍不住,依舊走囘去。
這對年靑人終於擁抱一起,天是藍的,樹在搖動,虫在唱歌,愛是自然的,一對燕子正在追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