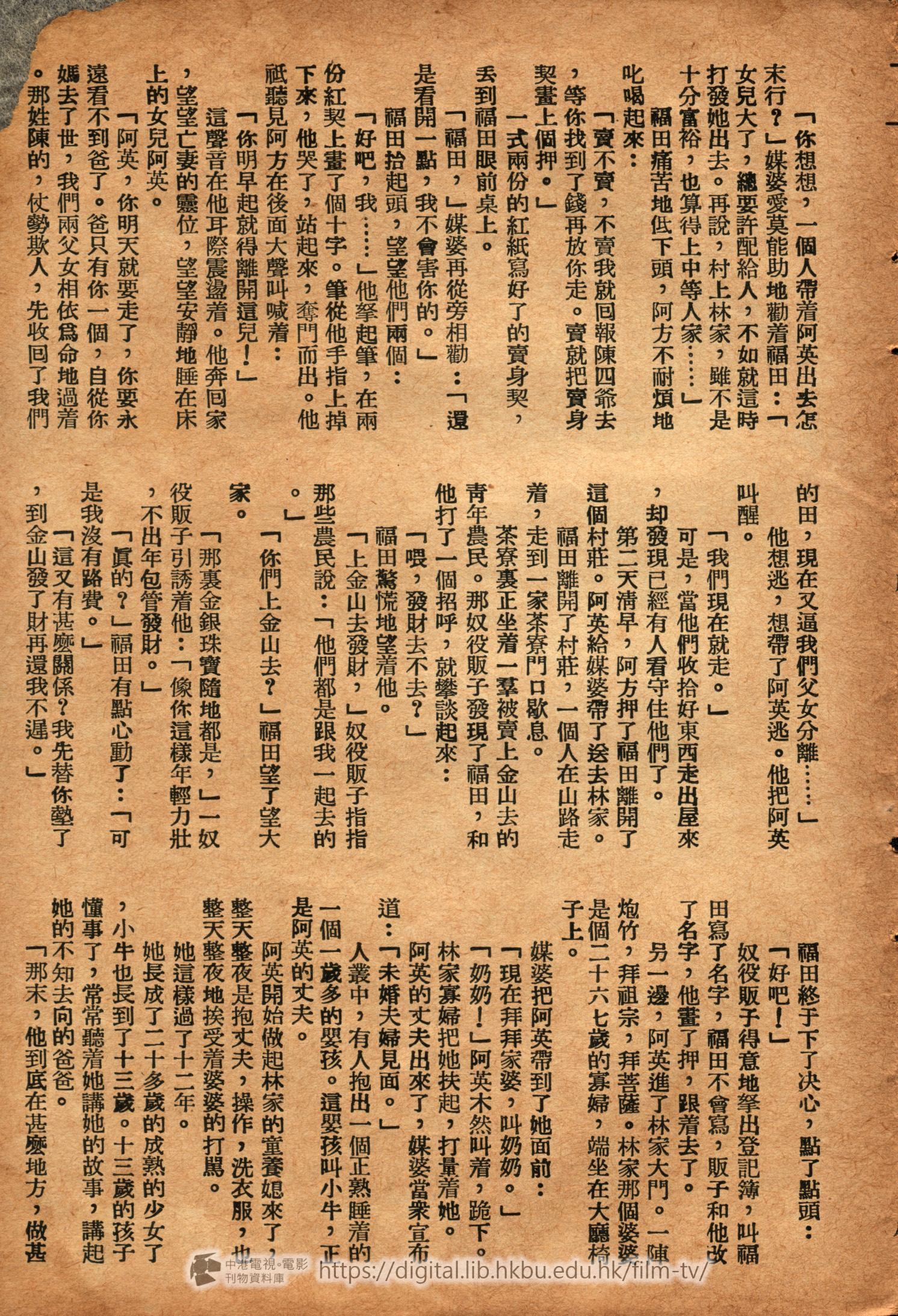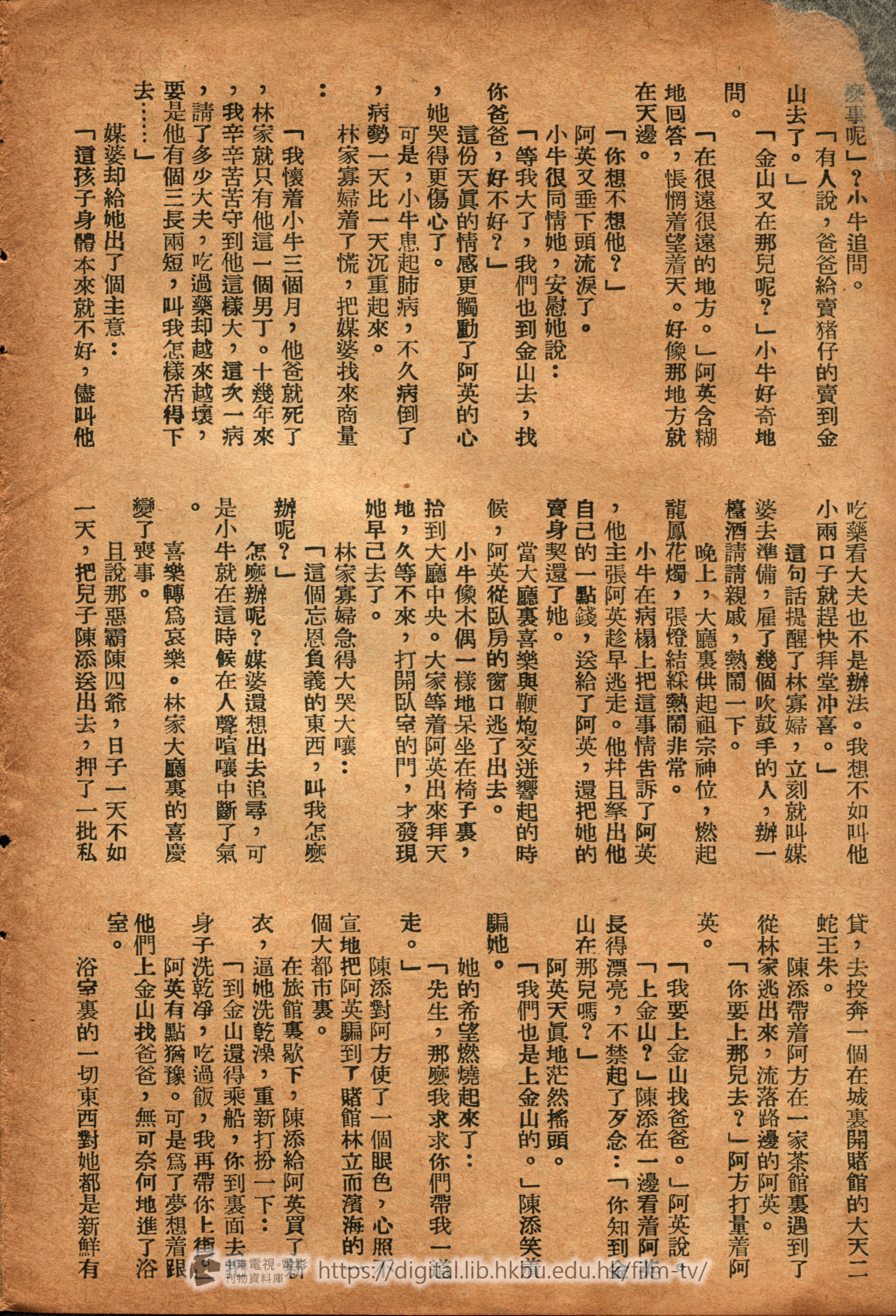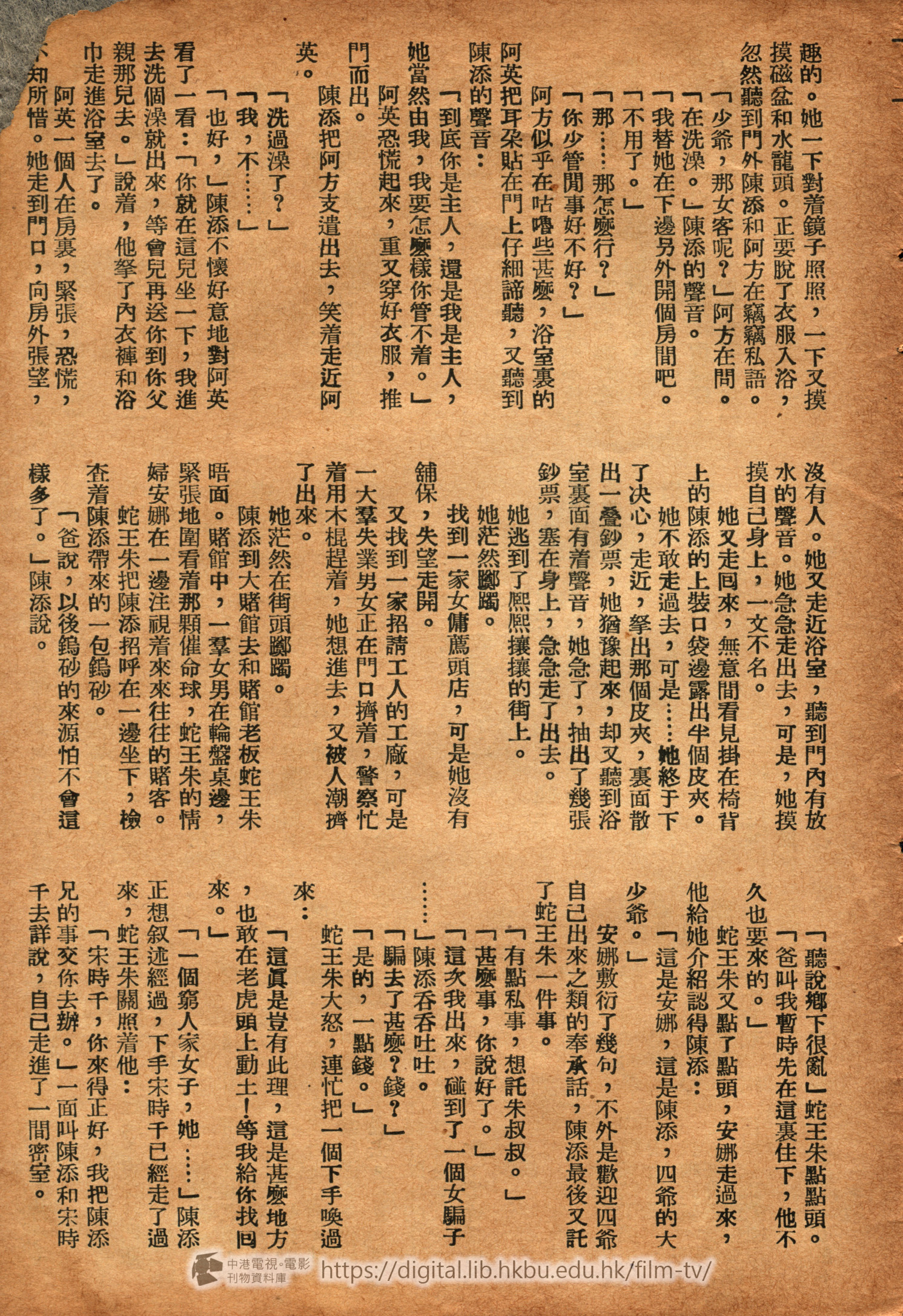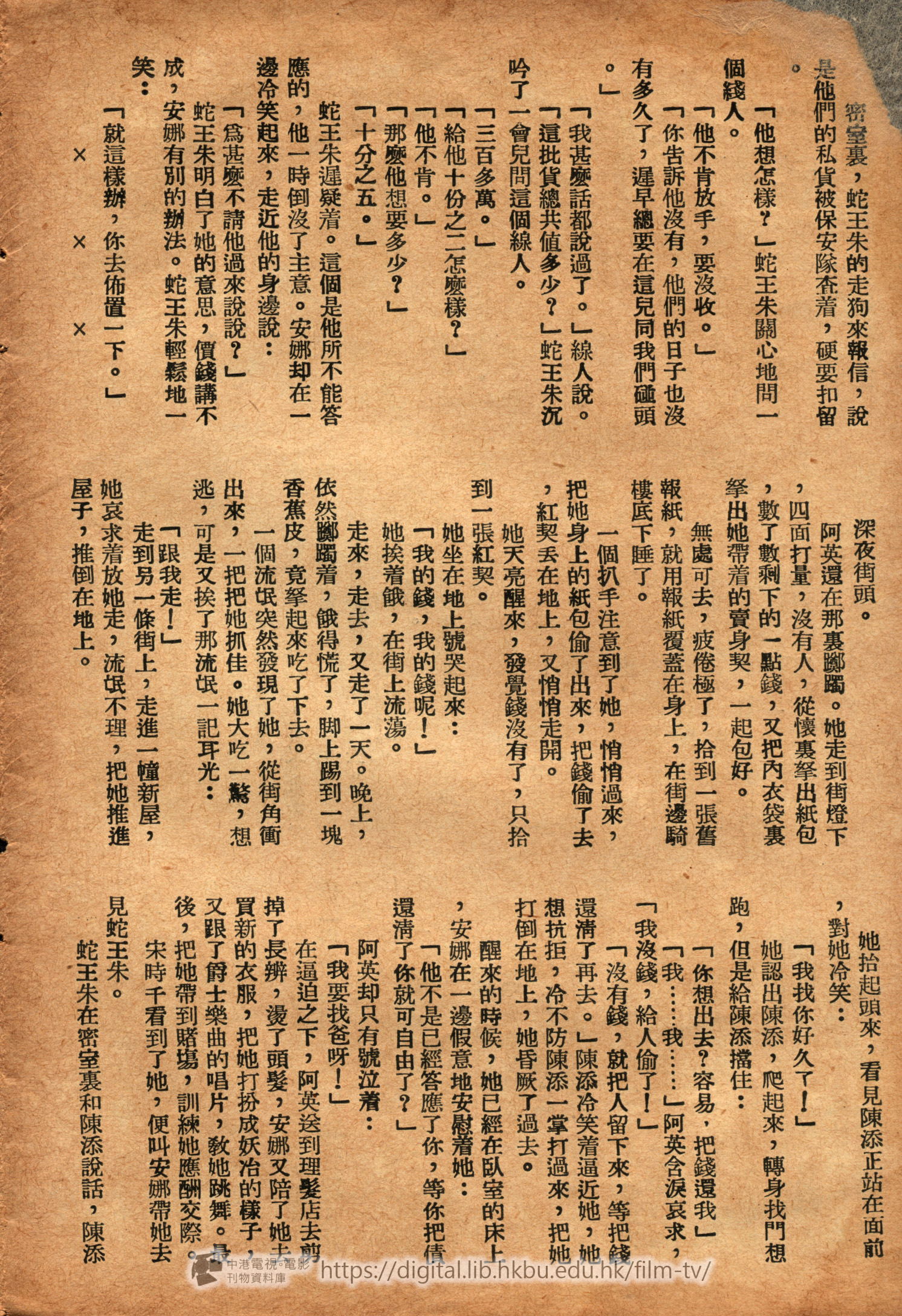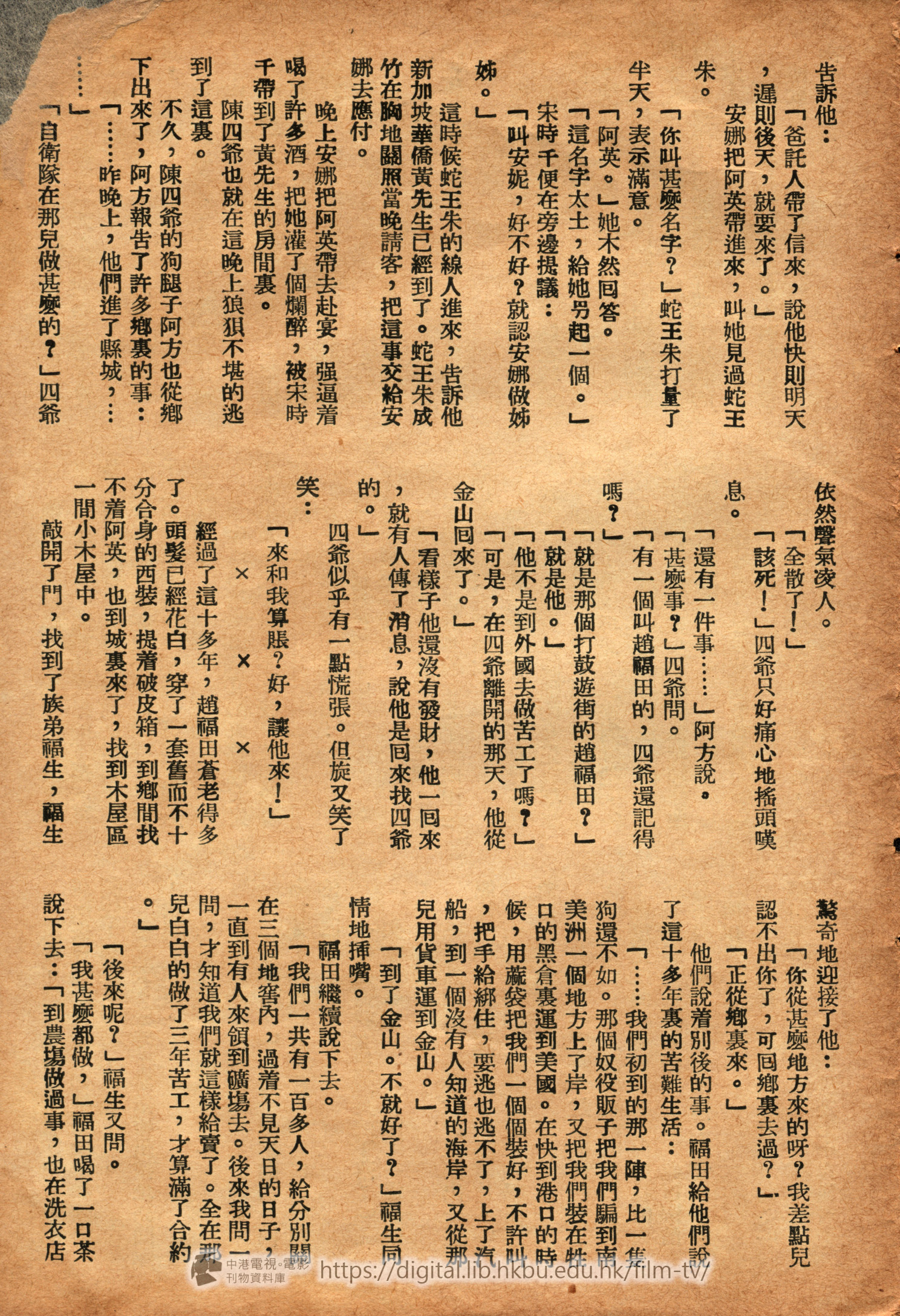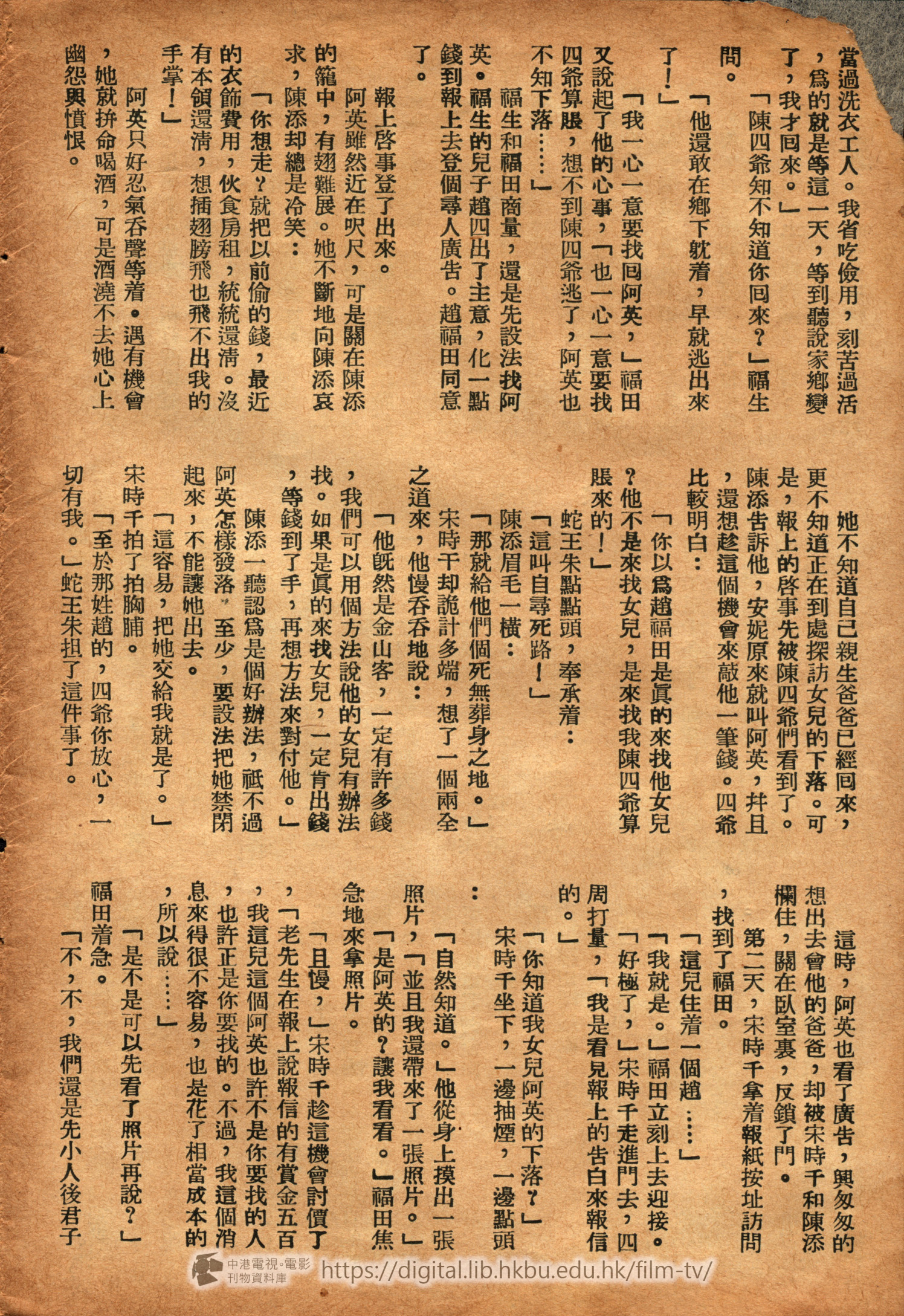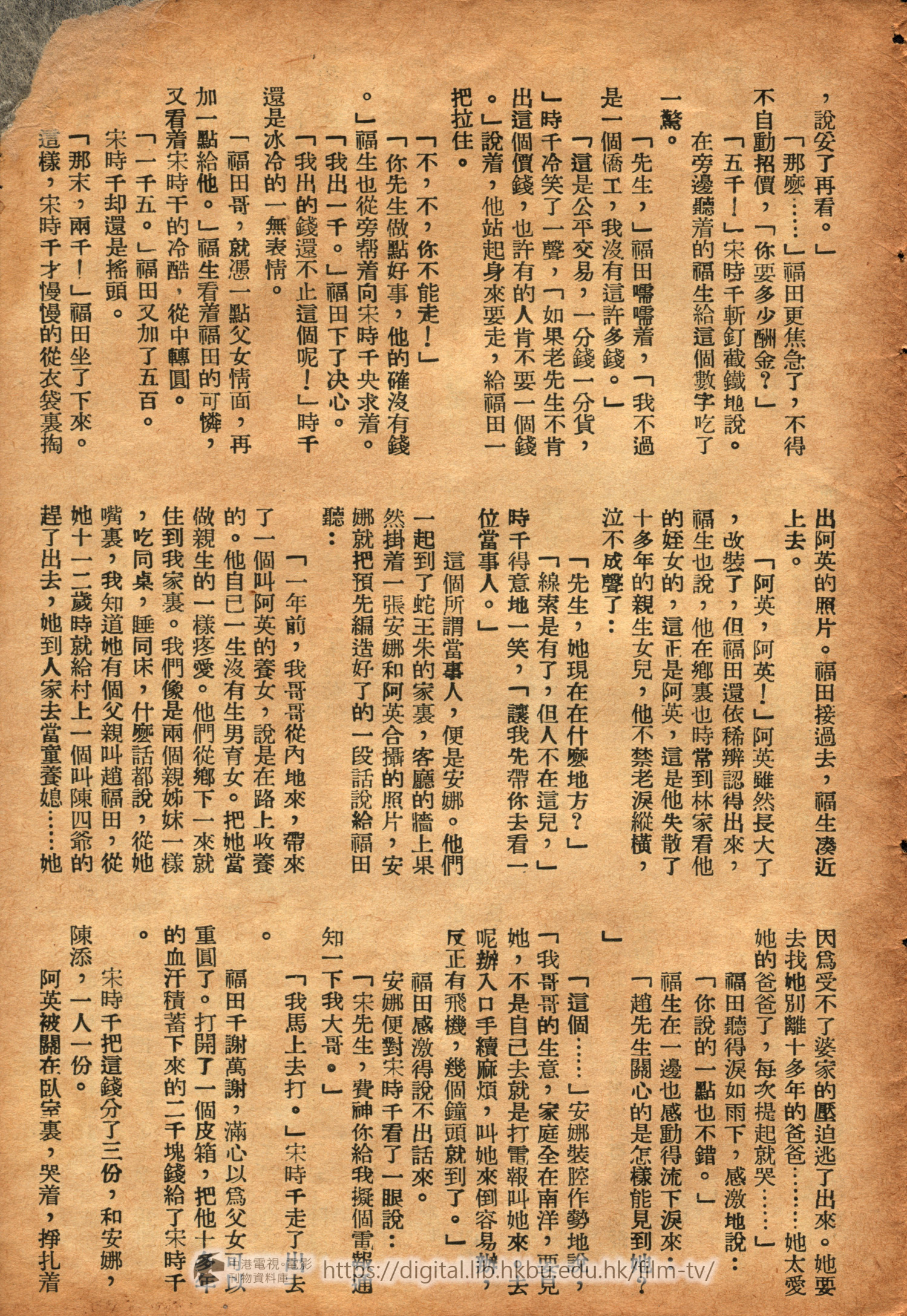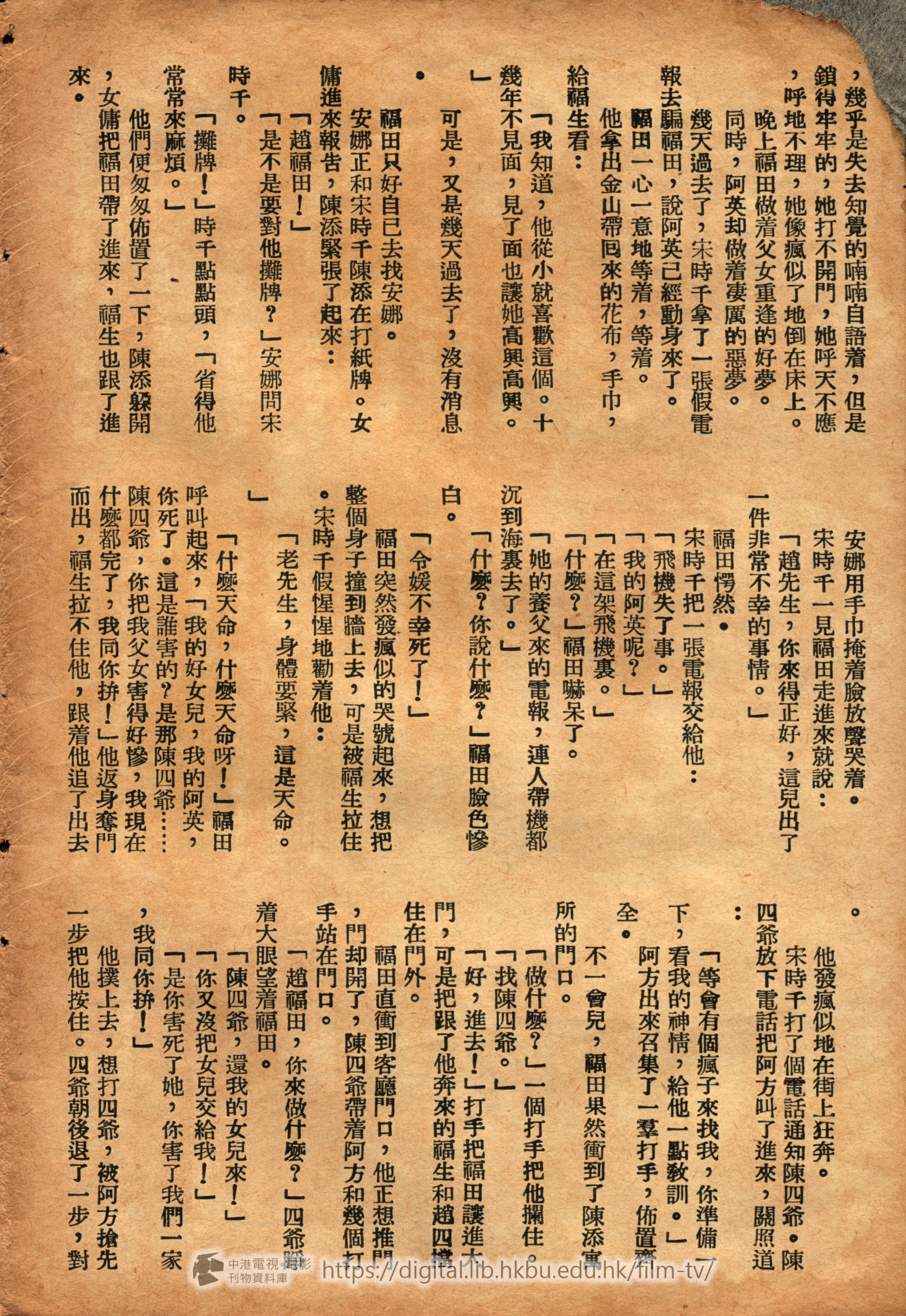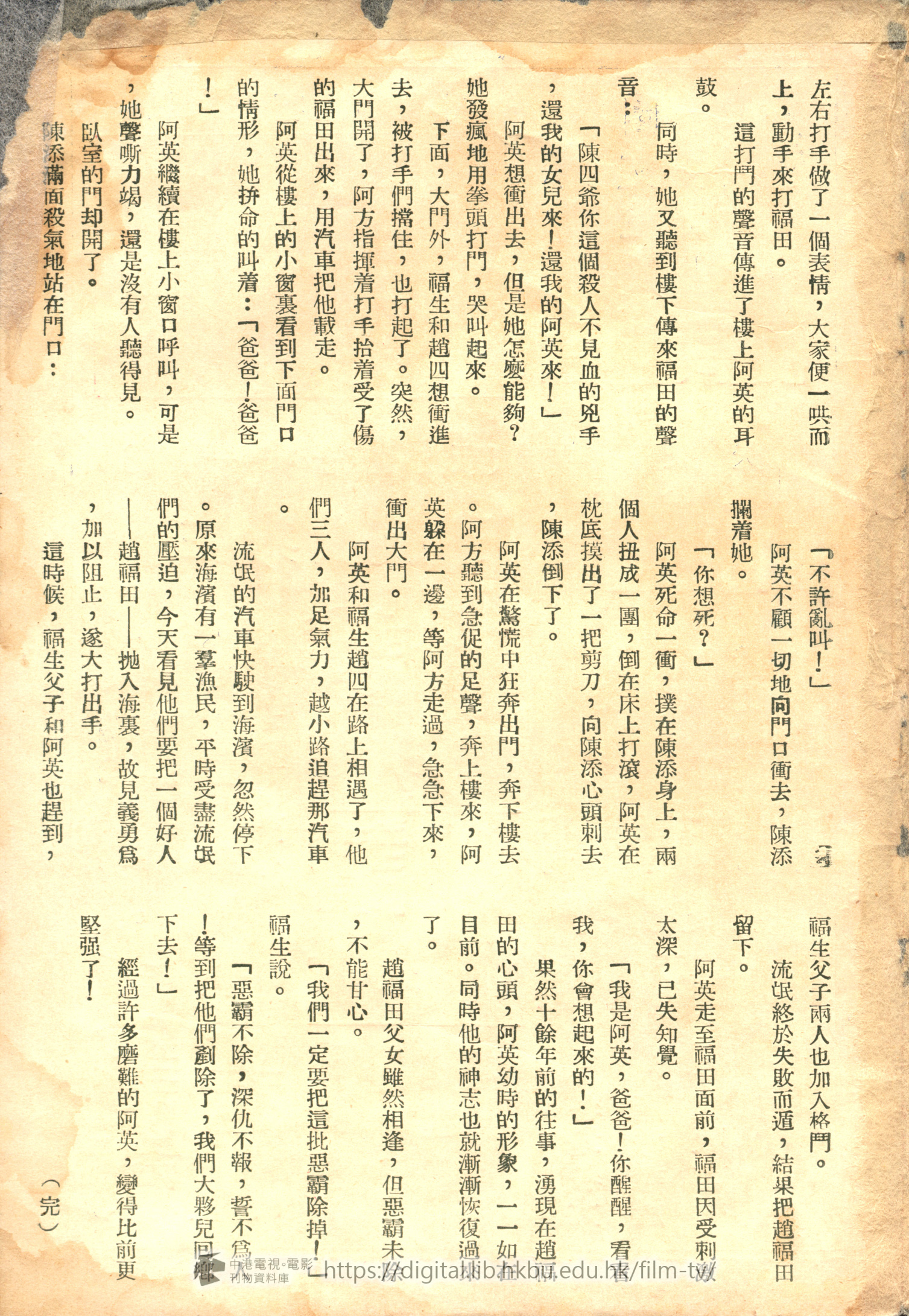珠海魂電影小說
趙福田是華南某地一個破落村莊上的佃農。妻子死了,和女兒阿英相依為命,過着凄苦的耕種生活。爲了他曾經要求減租,得罪了惡霸陳四爺。一次又一次起受着迫害。終于,被寃枉做賊,誣指偷了陳家田裏的蕃薯,讓陳四爺綑了起來,受了惡毒地鞭撻。
這晚上,村裏寂靜了,他負着傷,掙扎着一步步囘家,走到他茅屋門口,幾乎不能支持,阿英開門,驚慌地把他扶了進去。
在黯淡的燈火下,在他亡妻的靈位前,他倒在床上,望着阿英在床邊流淚。他囘想着這一天裏所遭受到的侮辱與毒害。他又看到陳四爺的狰獰的臉。
「四爺,四爺,我沒有偷!」他是這樣向四爺哀求的。
可是,在陳家大門口,旗桿下,四爺的狗腿子阿方,狠命地用鞭子抽打着他。他的族弟福生看不過去,站出來替他向陳四爺求情:
「四爺,饒過他這一次吧!」
四爺冷笑了一聲,搖搖頭:
「平時他和大家一起反對我,鬧減租反稅,這次又到我田裏偷東西,放過了這一次,我陳四爺以後怎末還能在這兒做人?」
又一個農民站出來:
「四爺,那末罰他打打鼓,擺擺酒,陪個不是!他實在可憐,高抬貴手………」
福生跟着又說:
「罰他打鼓算了,酒實在擺不起。」
四爺沉思了一下。
福生又補充了一句:
「他連餐飯都吃不起,叫他怎末擺得起酒?」
四爺又沉思了一下,冷冷對他望了一下,問他的狗腿子阿方:
「他家裏還有甚麼沒有?」
「囘四爺,」阿方囘道:「福田種的地已經收囘了,沒有別的。只有一間破屋子,和一個十歲大的女兒。」
四爺點了點頭:
「哦,還有房子女兒,不會賣了擺酒?」
他說着,冷冷看了福田一眼走開了。福生還想跟上去求情,可是,「今天打鼓,明天擺酒」,一點兒轉圜的餘地都沒有了。
沒有辦法,福田忍受着侮辱,當衆打鼓,被逼認罪,接着,當地的媒婆和陳四爺的狗腿子阿方又把他拉到了陳家
「你想想,一個人帶着阿英出去怎末行?」媒婆愛莫能助地勸着福田:「女兒大了,總要許配給人,不如就這時打發她出去。再說,村上林家,雖不是十分富裕,也算得上中等人家……」
福田痛苦地低下頭。阿方不耐煩地叱喝起來:
「賣不賣,不賣我就囘報陳四爺去,等你找到了錢再放你走。賣就把賣身契畫上個押。」
一式兩份的紅紙寫好了的賣身契,丢到福田眼前桌上。
「福田,」媒婆再從旁相勸:「還是看開一點,我不會害你的。」
福田抬起頭。望望他們兩個:
「好吧,我……」他拏起筆,在兩份紅契上畫了個十字。筆從他手指上掉下來,他哭了,站起來,奪門而出。他祗聽見阿方在後面大聲叫喊着:
「你明早起就得離開這兒!」
這聲音在他耳際震盪着。他奔囘家,望望亡妻的靈位,望望安靜地睡在床上的女兒阿英。
「阿英,你明天就要走了,你要永遠看不到爸了。爸只有你一個,自從你媽去了世,我們兩父女相依爲命地過着。那姓陳的,仗勢欺人:先收囘了我們的田,現在又逼我們父女分離……」
他想逃,想帶了阿英逃。他把阿英叫醒。
「我們現在就走。」
可是,當他們收拾好東西走出屋來,却發現已經有人看守住他們了。
第二天淸早,阿方押了福田離開了這個村莊。阿英給媒婆帶了送去林家。
福田離開了村莊,一個人在山路走着,走到一家茶寮門口歇息。
茶寮裏正坐着一羣被賣上金山去的靑年農民。那奴役販子發現了福田,和他打了一個招呼,就攀談起來:
「喂,發財去不去?」
福田驚慌地望着他。
「上金山去發財,」奴役販子指指那些農民說:「他們都是跟我一起去的。」
「你們上金山去?」福田望了望大家。
「那裏金銀珠寶隨地都是,」一奴役販子引誘着他:「像你這樣年輕力壯,不出年包管發財。」
「眞的?」福田有點心動了:「可是我沒有路費。」
「這又有甚麼關係?我先替你墊了,到金山發了財再還我不遲。」
福田終于下了决心,點了點頭:
「好吧!」
奴役販子得意地拏出登記簿,叫福田寫了名字,福田不會寫,販子和他改了名字,他畫了押,跟着去了。
另一邊,阿英進了林家大門。一陣炮竹,拜祖宗,拜菩薩。林家那個婆婆是個二十六匕歲的寡婦,端坐在大廳椅子上。
媒婆把阿英帶到了她面前:
「現在拜拜家婆,叫奶奶。」
「奶奶!」阿英木然叫着,跪下。
林家寡婦把她扶起,打量着她。
阿英的丈夫出來了,媒婆當衆宣布道:「未婚夫婦見面。」
人叢中,有人抱出一個正熟睡着的一個一歲多的嬰孩。這嬰孩叫小牛,正是阿英的丈夫。
阿英開始做起林家的童養媳來了,整天整夜是抱丈夫,操作,洗衣服,也整天整夜地挨受着婆婆的打駡。
她這樣過了十二年。
她長成了二十多歲的成熟的少女了,小牛也長到了十三歲。十三歲的孩子懂事了,常常聽着她講她的故事,講起她的不知去向的爸爸。
「那末,他到底在甚麼地方,做甚麼事呢?」?小牛追問。
「有人說,爸爸給賣猪仔的賣到金山去了。」
「金山又在那兒呢?」小牛好奇地問。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阿英含糊地囘答,悵惘着望着天。好像那地方就在天邊。
「你想不想他?」
阿英又垂下頭流淚了。
小牛很同情她,安慰她說:
「等我大了,我們也到金山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這份天眞的情感更觸動了阿英的心,她哭得更傷心了。
可是,小牛患起肺病,不久病倒了,病勢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
林家寡婦着了慌,把媒婆找來商量:
「我懷着小牛三個月,他爸就死了,林家就只有他這一個男丁。十幾年來,我辛辛苦苦守到他這樣大,這次一病,請了多少大夫,吃過藥却越來越壞,耍是他有個三長兩短,叫我怎樣活得下去……」
媒婆却給她出了個主意:
「這孩子身體本來就不好。儘叫他吃藥看大夫也不是辦法。我想不如叫他小兩口子就趕快拜堂冲喜。」
這句話提醒了林寡婦,立刻就叫媒婆去準備。雇了幾個吹鼓手的人,辦一檯酒請請親戚,熱鬧一下。
晚上,大廳裏供起祖宗神位,燃起龍鳳花燭,張燈結綵熱鬧非常。
小牛在病榻上把這事情吿訴了阿英,他主張阿英趁早逃走。他幷且拏出他自己的一點錢,送給了阿英,還把她的賣身契還了她。
當大廳裏喜樂與鞭炮交迸響起的時候,阿英從臥房的窗口逃了出去。
小牛像木偶一樣地呆坐在椅子裏,拾到大廳中央。大家等着阿英出來拜天地,久等不來,打開臥室的門,才發現她早己去了。
林家寡婦急得大哭大嚷:
「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叫我怎麽辦呢?」
怎麼辦呢?媒婆還想出去追尋,可是小牛就在這時候在人聲喧嚷中斷了氣。
喜樂轉爲哀樂。林家大廳裏的喜慶變了喪事。
且說那惡霸陳四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把兒子陳添送出去,押了一批私貸,去投奔一個在城裏開賭館的大天二蛇王朱。
陳添帶着阿方在一家茶館裏遇到了從林家逃出來,流落路邊的阿英。
「你要上那兒去?」阿方打量着阿英。
「我要上金山找爸爸。」阿英說。
「上金山?」陳添在一邊看着阿英長得漂亮,不禁起了歹念:「你知到金山在那兒嗎?」
阿英天眞地茫然搖頭。
「我們也是上金山的。」陳添笑着騙她。
她的希望燃燒起來了:
「先生,那麼我求求你們帶我一道走。」
陳添對阿方使了一個眼色,心照不宣地把阿英騙到了賭館林立而濱海的一個大都市裏。
在旅館裏歇下,陳添給阿英買了新衣,逼她洗乾澡,重新打扮一下:
「到金山還得乘船,你到裏面去把身子洗乾净,吃過飯,我再帶你上街。」
阿英有點猶豫。可是爲了夢想着跟他們上金山找爸爸,無可奈何地進了浴室。
浴室裏的一切東西對她都是新鮮有趣的。她一下對着鏡子照照,一下又摸摸磁盆和水龍頭。正要脫了衣服入浴,忽然聽到門外陳添和阿方在竊竊私語。
「少爺,那女客呢?」阿方在問。
「在洗澡。」陳添的聲音。
「我替她在下邊另外開個房間吧。
「不用了。」
「那⋯⋯那怎麼行?」
「你少管閒事好不好?」
阿方似乎在咕嚕些甚麼,浴室裏的阿英把耳朶貼在門上仔細諦聽,又聽到陳添的聲音:
「到底你是主人,還是我是主人,她當然由我,我耍怎麼樣你管不着。」
阿英恐慌起來,重又穿好衣服,推門而出。
陳添把阿方支遣出去,笑着走近阿英。
「洗過澡了?」
「我,不……」
「也好,」陳添不懷好意地對阿英看了一看:「你就在這兒坐一下,我進去洗個澡就出來,等會兒再送你到你父親那兒去。」說着,他拏了內衣褲和浴陰巾走進浴室去了。
阿英一個人在房裏,緊張,恐慌,不知所惜。她走到門口,向房外張望,沒有人。她又走近浴室,聽到門內有放水的聲音。她急急走出去,可是,她摸摸自己身上,一文不名。
她又走囘來,無意間看見掛在椅背上的陳添的上裝口袋邊露出半個皮夾。
她不敢走過去,可是……她終于下了决心,走近,拏出那個皮夾,裏面散出一叠鈔票,她猶豫起來,却又聽到浴室裏面有着聲音,她急了,抽出了幾張鈔票,塞在身上,急急走了出去。
她逃到了熙裡攘攘的街上。
她茫然躑躅。
找到一家女傭薦頭店,可是她沒有舖保,失望走開。
又找到一家招請工人的工廠,可是一大羣失業男女正在門口擠着,警察忙着用木棍趕着,她想進去,又被人潮擠了出來。
她茫然在街頭擲躅。
陳添到大賭館去和賭館老板蛇王朱晤面。賭館中,一羣女男在輪盤桌邊,緊張地圍看着那顆催命球,蛇王朱的情婦安娜在一邊注視着來來往往的賭客。
蛇王朱把陳添招呼在一邊坐下,檢查着陳添帶來的一包鎢砂。
「爸說,以後鎢砂的來源怕不會這樣多了。」陳添說。
「聽說鄕下很亂」蛇王朱點點頭。
「爸叫我暫時先在這裏住下,他不久也要來的。」
蛇王朱又點了點頭,安娜走過來,他給她介紹認得陳添:
「這是安娜,這是陳添,四爺的大少爺。」
安娜敷衍了幾句,不外是歡迎四爺自己出來之類的奉承說,陳添最後又託了蛇王朱一件事。
「有點私事,想託朱叔叔。」
「甚麽事,你說好了。」
「這次我出來,碰到了一個女騙子……」陳添呑呑吐吐。
「騙去了甚麽?錢?」
「是的,一點錢。」
蛇王朱大怒,連忙把一個下手喚過來:
「這眞是豈有此理,這是甚麼地方,也敢在老虎頭上動土!等我給你找囘來。」
「一個窮人家女子,她…」陳添正想叙述經過,下手宋時千已經走了過來,蛇王朱關照着他:
「宋時千,你來得正好,我把陳添兄的事交你去辨。」一面叫陳添和宋時千去詳說,自己走進了一間密室。
密室裏,蛇王朱的走狗來報信,說是他們的私貨被保安隊查着,硬要扣留。
「他想怎樣?」蛇王朱關心地問一個綫人。
「他不肯放手,要沒收。」
「你吿訴他沒有,他們的日子也沒有多久了,遲早總要在這兒同我們碰頭。」
「我甚麼話都說過了。」線人說。
「這批貨總共値多少?」蛇王朱沉吟了一會兒問這個線人。
「三百多萬。」
「給他十份之二怎麼樣?」
「他不肯。」
「那麽他想要多少?」
「十分之五。」
蛇王朱遲疑着。這個是他所不能答應的,他一時倒沒了主意。安娜却在一邊冷笑起來,走近他的身邊說:
「爲甚麽不請他過來說說?」
蛇王朱明白了她的意思,價錢講不成,安娜有別的辦法。蛇王朱輕鬆地一笑:
「就這樣辦,你去佈置一下。」
X X X
深夜街頭。
阿英還在那裏躑躅。她走到街燈下,四面打量,沒有人,從懷裏拏出紙包,數了數剩下的一點錢,又把內衣袋裏拏出她帶着的賣身契,一起包好。
無處可去,疲倦極了,拾到一張舊報紙,就用報紙覆蓋在身上,在街邊騎樓底下睡了。
一個扒手注意到了她,悄悄過來,把她身上的紙包偷了出來,把錢偷了去,紅契丟在地上,又悄悄走開。
她天亮醒來發覺錢沒有了,只拾到一張紅契。
她坐在地上號哭起來:
「我的錢,我的錢呢!」
她挨着餓,在街上流蕩。
走來,走去,又走了一天。晚上,依然躑躅着,餓得慌了,脚上踢到一塊香蕉皮,竟拏起來吃了下去。
一個流氓突然發現了她,從街角衝出來,一把把她抓佳。她大吃一驚,想逃,可是又挨了那流氓一記耳光:
「跟我走!」
走到另一條街上,走進一幢新屋,她哀求着放她走,流氓不理,把她推進屋子,推倒在地上。
她抬起頭來,看見陳添正站在面前,對她冷笑:
「我找你好久了」
她認出陳添,爬起來,轉身找門想跑,但是給陳添擋住:
「你想出去?容易,把錢還我」
「我……我……」阿英含淚哀求,「我沒錢,給人偷了!」
「沒有錢,就把人留下來,等把錢還淸了再去。」陳添冷笑着逼近她,她想抗拒,冷不防陳添一掌打過來,把她打倒在地上,她昏厥了過去。
醒來的時候,她已經在臥室的床上,安娜在一邊假意地安慰着她:
「他不是已經答應了你,等你把債還淸了你就可自由了?」
阿英却只有號泣着:
「我要找爸呀!」
在逼迫之下,阿英送到理髮店去剪掉了長辨,燙了頭髮,安娜又陪了她去買新的衣服,把她打扮成妖冶的樣子,又跟了爵士樂曲的唱片,敎她跳舞。最後把她帶到賭場,訓練她應酬交際。
宋時千看到了她,便叫安娜帶她去見蛇王朱。
蛇王朱在密室裏和陳添說話,陳添吿訴他:
「爸託人帶了信來,說他快則明天,遲則後天,就要來了。」
安娜把阿英帶進來,叫她見過蛇王朱。
「你叫甚麼名字?」蛇王朱打量了半天,表示滿意。
「阿英。」她木然囘答。
「這名字太土,給她另起一個。」
宋時千便在旁邊提議:
「叫安妮,好不好?就認安娜做姊姊。」
這時候蛇王朱的線人進來,吿訴他新加坡華僑黃先生已經到了。蛇王朱成竹在胸地關照當晚請客,把這事交給安娜去應付。
晚上安娜把阿英帶去赴宴,强逼着喝了許多酒,把她灌了個爛醉,被宋時千帶到了黃先生的房間裏。
陳四爺也就在這晚上狼狽不堪的逃到了這裏。
不久,陳四爺的狗腿子阿方也從鄕下出來了,阿方報吿了許多鄕裏的事:
「……昨晚上,他們進了縣城,……」
「自衛隊在那兒做甚麽的?」四爺依然聲氣凌人。
「全散了!」
「該死!」四爺只好痛心地搖頭嘆息。
「還有一件事……」阿方說。
「甚麽事?」四爺問。
「有一個叫趙福田的,四爺還記得嗎?」
「就是那個打鼓遊街的趙福田?」
「就是他。」
「他不是到外國去做苦工了嗎?」
「可是,在四爺離開的那天,他從金山囘來了。」
「看樣子他還沒有發財,他一囘來就有人傳了消息,說他是囘來找四爺的。」
四爺似乎有一點慌張。但旋又笑了笑:
「來和我算賬?好,讓他來!」
X X X
經過了這十多年,趙福田蒼老得多了。頭髮已經花白,穿了一套舊而不十分合身的西裝,提着破皮箱,到鄕間找不着阿英,也到城裏來了,找到木屋區一間小木屋中。
敲開了門,找到了族弟福生,福生驚奇地迎接了他:
「你從甚麼蝴方來的呀?我差點兒認不出你了,可囘鄕裏去過?」
「正從鄕裏來。」
他們說着別後的事。福田給他們說了這十多年裏的苦難生活:
「……我們初到的那一陣,比一隻狗還不如。那個奴役販子把我們騙到南美洲一個地方上了岸,又把我們裝在牲口的黑倉裏運到美國。在快到港口的時候,用蔴袋把我們一個裝好,不許叫,把手給綁住,要逃也逃不了,上了汽船,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海岸,又從那兒用貨車運到金山。」
「到了金山。不就好了?」福生同情地揷嘴。
福田繼續說下去。
「我們一共有一百多人,給分別關在三個地窖內,過着不見天日的日子,一直到有人來領到礦塲去。後來我問一問,才知道我們就這樣給賣了。全在那兒白白的做了三年苦工,才算滿了合約。」
「後來呢?」福生又問。
「我甚麽都做,」福田喝了一口茶說下去:「到農塲做過事,也在洗衣店當過洗衣工人。我省吃儉用,刻苦過活,爲的就是等這一天等到聽說家鄕變了,我才囘來。」
「陳四爺知不知道你囘來?」福生問。
「他還敢在鄕下就着,早就逃出來了!」
「我一心一意要找囘阿英,」福田又說起了他的心事,「也一心一意要找四爺算賬,想不到陳四爺逃了,阿英也不知下落……」
福生和福田商量,還是先設法找阿英。福生的兒子趙四出了主意,化一點錢到報上去登個尋人廣吿。趙福田同意了。
報上啓事登了出來。
阿英雖然近在呎尺,可是關在陳添的籠中,有翅難展。她不斷地向陳添哀求,陳添却總是冷笑:
「你想走?就把以前偷的錢,最近的衣飾費用,伙食房租,統統還淸。沒有本領還淸,想插翅膀飛也飛不出我的手掌!」
阿英只好忍氣吞聲等着。遇有機會,她就拚命喝酒,可是酒澆不去她心上幽怨與憤恨。
她不知道自己親生爸爸已經囘來,更不知道正在到處探訪女兒的下落。可是,報上的啓事先被陳四爺們看到了。陳添吿訴他,安妮原來就叫阿英,幷且,還想趁這個機會來敲他一筆錢。四爺比較明白:
「你以爲趙福田是眞的來找他女兒?他不是來找女兒,是來找我陳四爺算賬來的!」
蛇王朱點點頭,奉承着:
「這叫自尋死路!」
陳添眉毛一橫:
「那就給他們個死無葬身之地。」
宋時干却詭計多端,想了一個兩全之道來,他慢吞吞地說:
「他旣然是金山客,一定有許多錢,我們可以用個方法說他的女兒有辦法找。如果是眞的來找女兒,一定肯出錢,等錢到了手,再想方法來對付他。」
陳添一聽認爲是個好辨法,祗不過阿英怎樣發落,至少,耍設法把她禁閉起來,不能讓她出去。
「這容易,把她交給我就是了。」宋時千拍了拍胸脯。
「至於那姓趙的,四爺你放心,一切有我。」蛇王朱担了這件事了。
這時,阿英也看了廣吿,興匆匆的想出去會他的爸爸,却被宋時千和陳添欄住,關在臥室裏,反鎖了門。
第二天,宋時千拿着報紙按址訪問,找到了福田。
「這兒住着一個趙……」
「我就是。」福田立刻上去迎接。
「好極了,」宋時千走進門去,四周打量,「我是看見報上的吿白來報信的。」
「你知道我女兒阿英的下落?」
宋時千坐下,一邊抽煙,一邊點頭:
「自然知道。」他從後上摸出一張照片,「並且我還帶來了一張照片。」
「是阿英的?讓我看看。」福田焦急地來拿照片。
「且慢,」宋時千趁這機會討價了,「老先生在報上說報信的有賞金五百,我這兒這個阿英也許不是你要找的人,也許正是你要找的。不過,我這個消息來得很不容易,也是花了相當成本的,所以說……」
「是不是可以先看了照片再說?」福田着急。
「不,不,我們還是先小人後君子,說妥了再看。」
「那麽……」福田更焦急了,不得不自動招價,「你要多少酬金?」
「五千!」宋時千斬釘截鐵地說。
在旁邊聽着的福生給這個數字吃了一驚。
「先生,」福田嚅嚅着:「我不過是一個僑工,我沒有這許多錢。」
「這是公平交易,一分錢一分貨,」時千冷笑了一聲,「如果老先生不肯出這個價錢,也許有的人肯不要一個錢。」說着,他站起身來要走給福田一把拉住。
「不,不,你不能走!」
「你先生做點好事,他的確沒有錢。」福生也從旁帮着向宋時千央求着。
「我出一千。」福田下了决心。
「我出的錢還不止這個呢!」時千還是冰冷的一無表情。
「福田哥,就憑一點父女情面,再加一點給他。」福生看着福田的可憐,又看着宋時干的冷酷,從中轉圓。
「一千五。」福田又加了五百。
宋時千却還是搖頭。
「那末,兩千!」福田坐了下來。
這樣,宋時千才慢慢的從衣袋裏掏出阿英的照片。福田接過去,福生凑近上去。
「阿英,阿英!」阿英雖然長大了,改裝了,但福田還依稀辨認得出來。福生也說,他在鄕裏也時常到林家看他的姪女的,這正是阿英,這是他失散了十多年的親生女兒,他不禁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了:
「先生,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線索是有了,但人不在這兒,」時千得意地一笑,「讓我先帶你去看一位當事人。」
這個所謂當事人,便是安娜。他們一起到了蛇王朱的家裏,客廳的牆上果然掛着一張安娜和阿英合攝的照片,安娜就把預先編造好了的一段話說給福田聽:
「一年前,我哥哥從內地來,帶來了一個叫阿英的養女,說是在路上收養的。他自已一生沒有生男育女。把她當做親生的一樣疼愛。他們從鄕下一來就住到我家裏。我們像是兩個親姊妹一樣,吃同桌,睡同床,什麼話都說,從她嘴裏,我知道她有個父親叫趙福田,從她十一二歲時就給村上一個叫陳四爺的趕了出去,她到人家去當童養媳……她因爲受不了婆家的壓迫逃了出來。她要去找地別離十多年的爸爸她太愛她的爸爸了,每次提起就哭……」
福田聽得淚如雨下,感激地說: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福生在一邊也感動得流下淚來:
「趙先生關心的是怎樣能見到她?」
「這個……」安娜裝腔作勢地說,「我哥哥的生意,家庭全在南洋,要見她,不是自己去就是打電報叫她來。去呢辦入口手續麻煩,叫她來倒容易辦,反正有飛機,幾個鐘頭就到了。」
福田感激得說不出話來。
安娜便對宋時千看了一眼說:
「宋先生,費神你給我擬個電報通知一下我大哥。」
「我馬上去打。」宋時千走了出去。
福田千謝萬謝,滿心以爲父女可以重圓了。打開了一個皮箱,把他十多年的血汗積蓄下來的二千塊錢給了宋時千。
宋時千把這錢分了三份,和安娜,陳添,一人一份。
阿英被關在臥室裏,哭着,掙扎着,幾乎是失去知覺的喃喃自語着,但是鎖得牢牢的,她打不開門,她呼天不應,呼地不理,她像瘋似了地倒在床上。
晚上福田做着父女重逢的好夢。
同時,阿英却做着凄厲的惡夢。
幾天過去了,宋時千拿了一張假電報去騙福田,說阿英己經動身來了。
福田一心一意地等着,等着。
他拿出金山帶同來的花布,手巾,給福生看:
「我知道,他從小就喜歡這個。十幾年不見面,見了面也讓她高興高興。」
可是又是幾天過去了,沒有消息。
福田只好自已去找安娜。
安娜正和宋時千陳添在打紙牌。女傭進來報吿,陳添緊張了起來:
「趙福田!」
「是不是要對他攤牌?」安娜問宋時千。
「攤牌!」時千點點頭,「省得他常常來麻煩。」
他們便匆匆佈置了一下,陳添躱開,女傭把福田帶了進來,福生也跟了進來。
安娜用手巾掩着臉放聲哭着。
宋時千一見福田走進來就說:
「趙先生,你來得正好,這兒出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福田愕然。
宋時千把一張電報交給他:
「飛機失了事。」
「我的阿英呢?」
「在這架飛機裏。」
「什麼?」福田嚇呆了。
「她的養父來的電報,連人帶機都沉到海裏去了。」
「什麼?你說什麼?」福田臉色慘白。
「令媛不幸死了!」
福田突然發瘋似的哭號起來,想把整個身子撞到牆上去,可是被福生拉住。宋時千假惺惺地勸着他:
「老先生,身體要緊,這是天命。」
「什麼天命,什麼天命呀!」福田呼叫起來,「我的好女兒,我的阿英,你死了。這是誰害的?是那陳四爺……陳四爺,你把我父女害得好慘,我現在什麼都完了,我同你拼!」他返身奪門而出,福生拉不住他,跟着他追了出去。
他發瘋似地在街上狂奔。
宋時千打了個電話通知陳四爺。陳四爺放下電話把阿方叫了進來,關照道:
「等會有個瘋子來找我,你準備一下,看我的神情,給他一點敎訓。」
阿方出來召集了一羣打手,佈置齊全。
不一會兒,福田果然衝到了陳添寓所的門口。
「做什麼?」一個打手把他攔住。
「找陳四爺。」
「好,進去!」打手把福田讓進大門,可是把跟了他奔來的福生和趙四擋住在門外。
福田直衝到客廳門口,他正想推門,門却開了,陳四爺帶着阿方和幾個打手站在門口。
「趙福田,你來做什麽?」四爺睜着大眼望着福田。
「陳四爺,還我的女兒來!」
「你又沒把女兒交給我!」
「是你害死了她,你害了我們一家,我同你拼!」
他撲上去,想打四爺,被阿方搶先一步把他按住。四爺朝後退了一步,對左右打手做了一個表情,大家便一哄而上,動手來打福田。
這打鬥的聲音傳進了樓上阿英的耳鼓。
同時,她又聽到樓下傳來福田的聲音:
「陳四爺你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兇手,還我的女兒來!還我的阿英來!」
阿英想衝出去,但是她怎麼能夠?她發瘋地用拳頭打門,哭叫起來。
下面,大門外,福生和趙四想衝進去,被打手們擋住,也打起了。突然,大門開了,阿方指揮着打手抬着受了傷的福田出來,用汽車把他載走。
阿英從樓上的小窗裏看到下面門口的情形,她拚命的叫着:「爸爸!爸爸!」
阿英繼續在樓上小窗口呼叫,可是,她聲嘶力竭,還是沒有人聽得見。
臥室的門却開了。
陳添滿面殺氣地站在門口:
「不許亂叫!」阿英不顧一切地向門口衝去,陳添攔着她。
「你想死?」
阿英死命一衝,撲在陳添身上,兩個人扭成一團,倒在床上打滾,阿英在枕底摸出了一把剪刀,向陳添心頭刺去,陳添倒下了。
阿英在驚慌中狂奔出門,奔下樓去。阿方聽到急促的足聲,奔上樓來,阿英躱在一邊,等阿方走過,急急下來,衝出大門。
阿英和福生趙四在路上相遇了。他們三人,加足氣力,越小路追趕那汽車。
流氓的汽車快駛到海濱,忽然停下。原來海濱有一羣漁民,平時受盡流氓們的壓迫,今天看見他們要把一個好人——趙福田——抛入海裏,故見義勇爲,加以阻止,遂大打出手。
這時候,福生父子和阿英也趕到,福生父子兩人也加入格鬥。
流氓終於失敗而遁,結果把趙福田留下。
阿英走至福田面前,福田因受刺激太深,已失知覺。
「我是阿英,爸爸!你醒醒,看看我,你會想起來的!」
果然十餘年前的往事,湧現在趙福田的心頭,阿英幼時的形象,一一如在目前。同時他的神志也就漸漸恢復過來了。
趙福田父女雖然相逢,但惡霸未除,不能甘心。
「我們一定耍把這批惡霸除掉!」福生說。
「惡霸不除,深仇不報,誓不爲人!等到把他們剷除了,我們大夥兒囘鄕下去!」
經過許多磨難的阿英,變得比前更堅强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