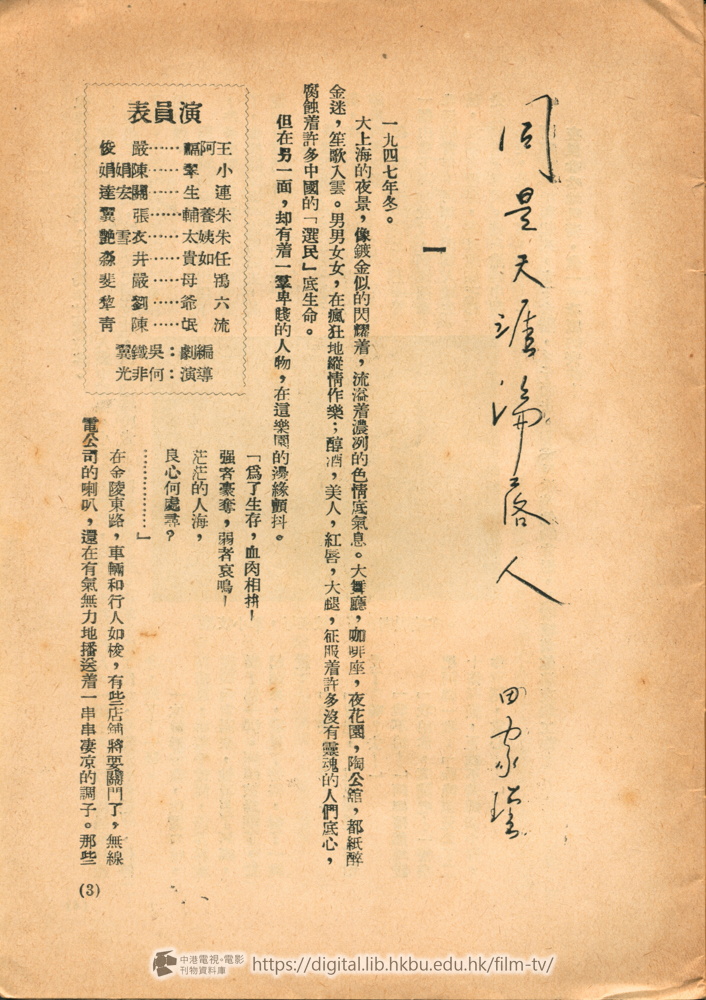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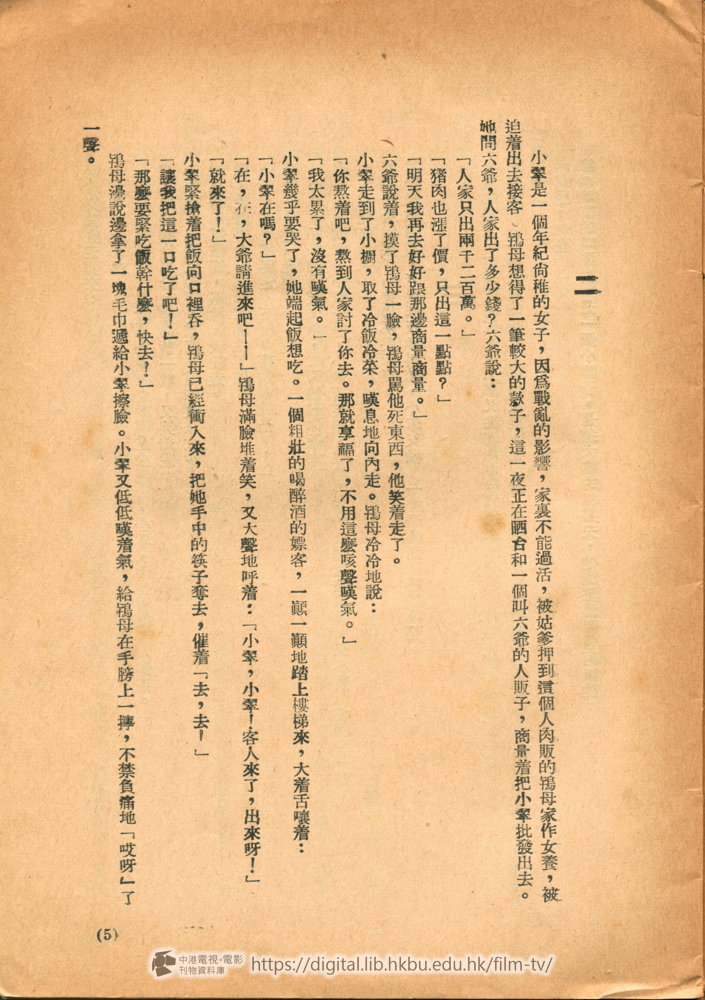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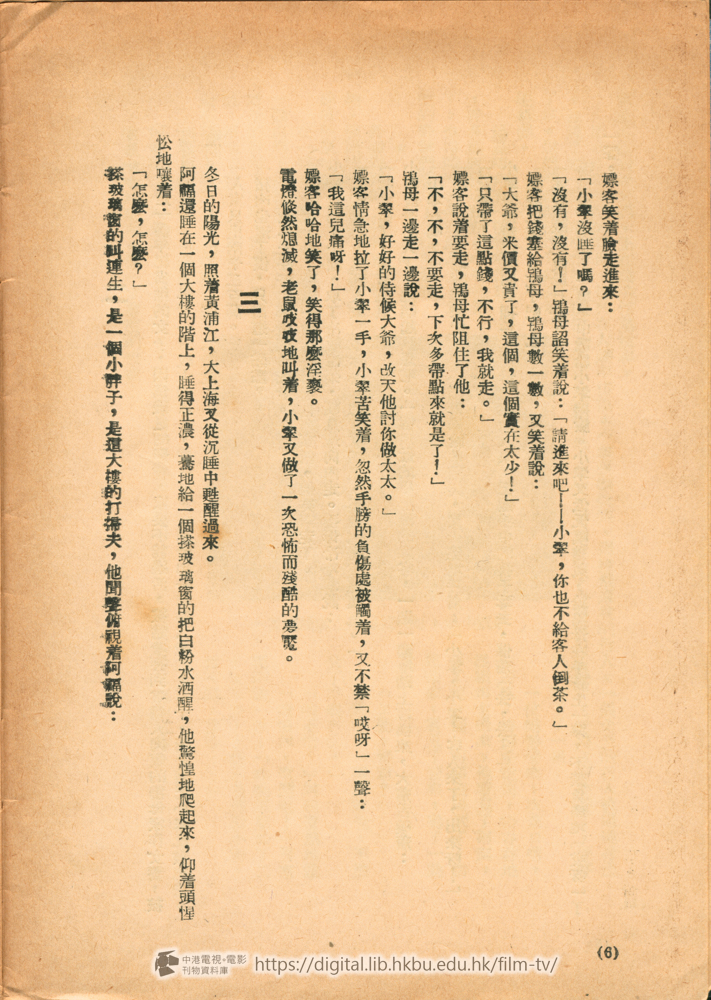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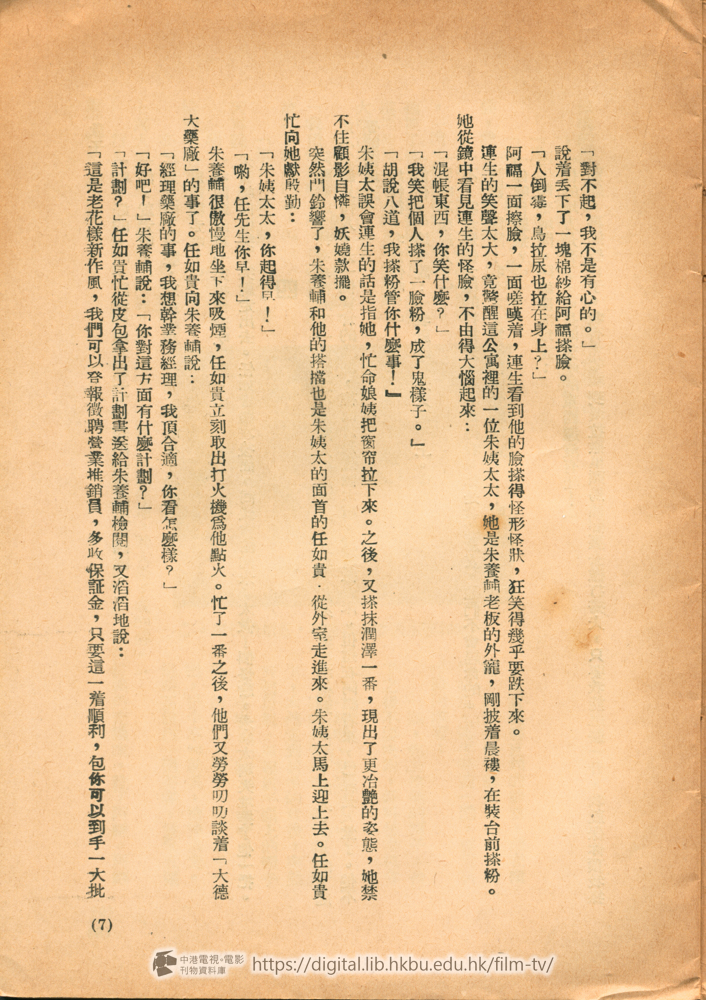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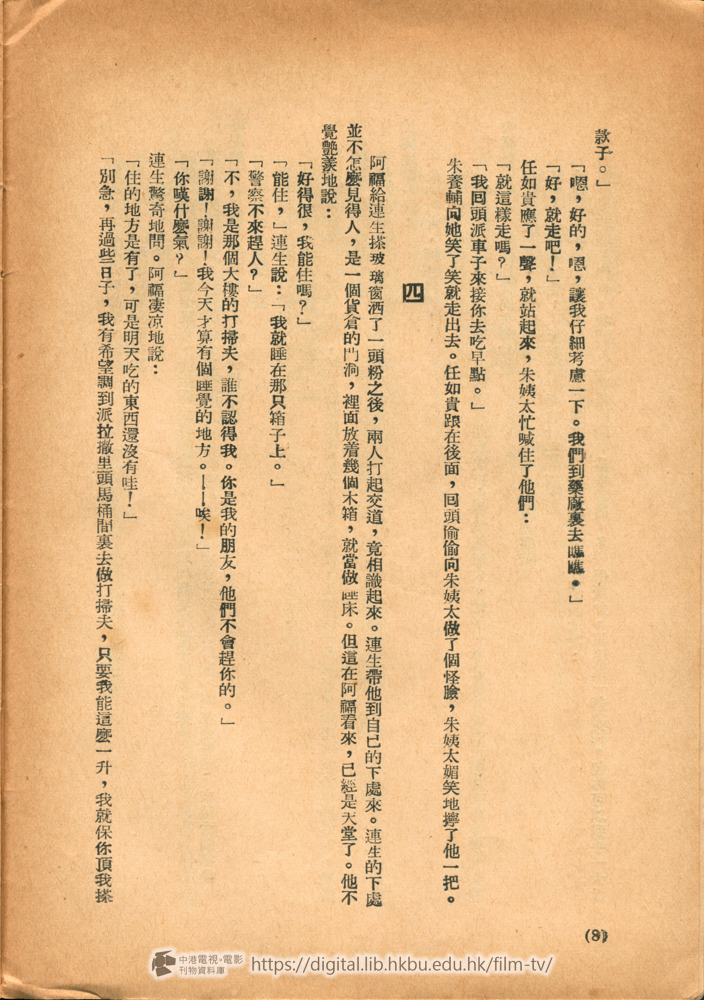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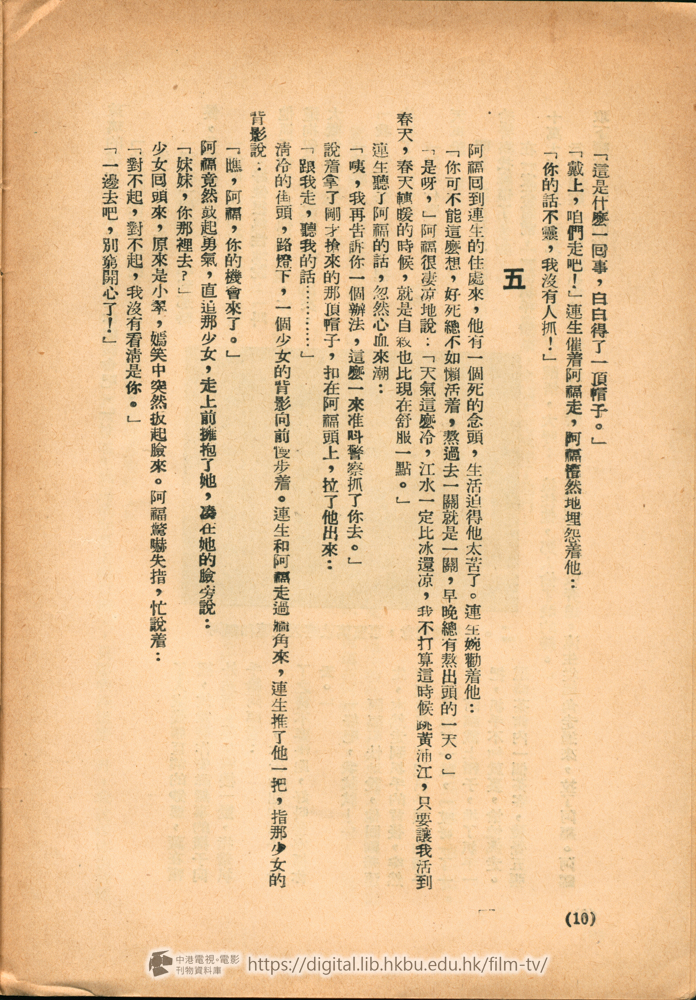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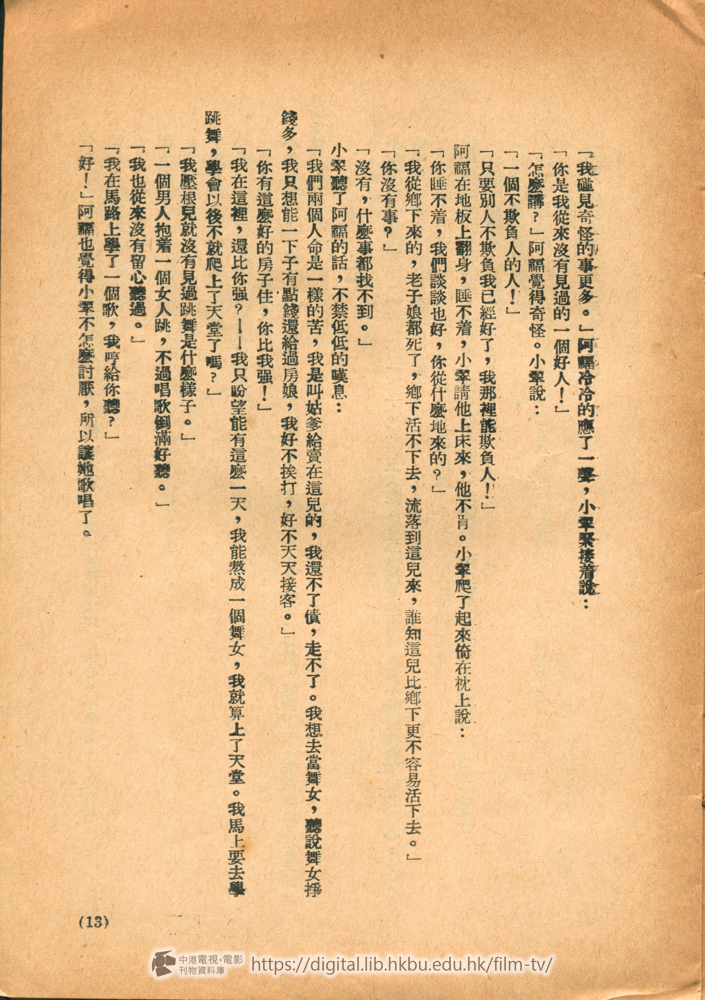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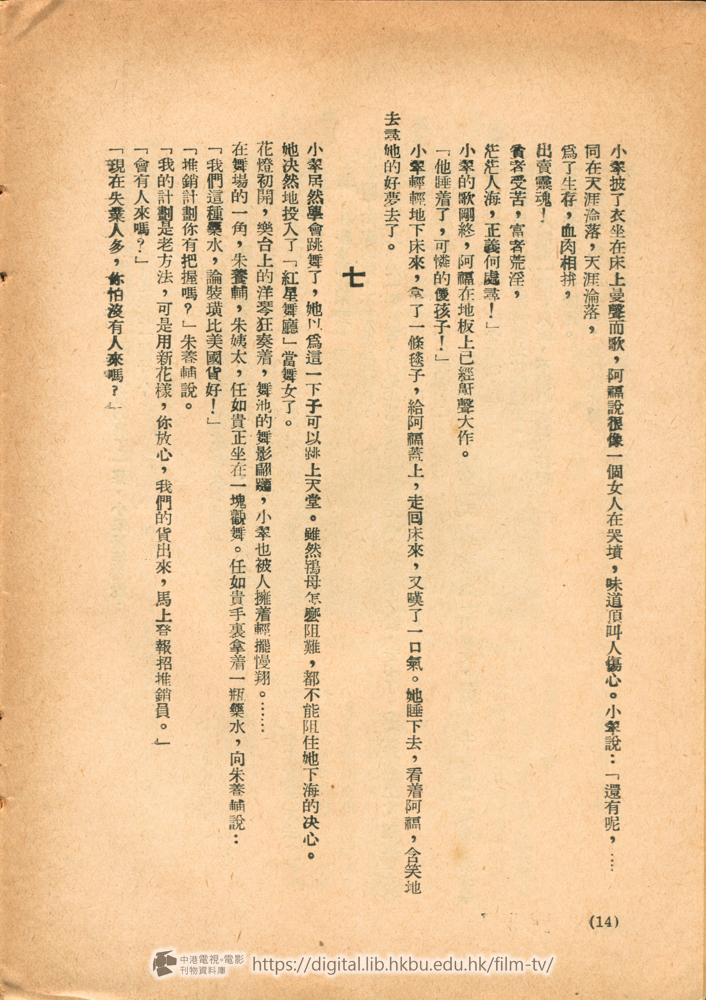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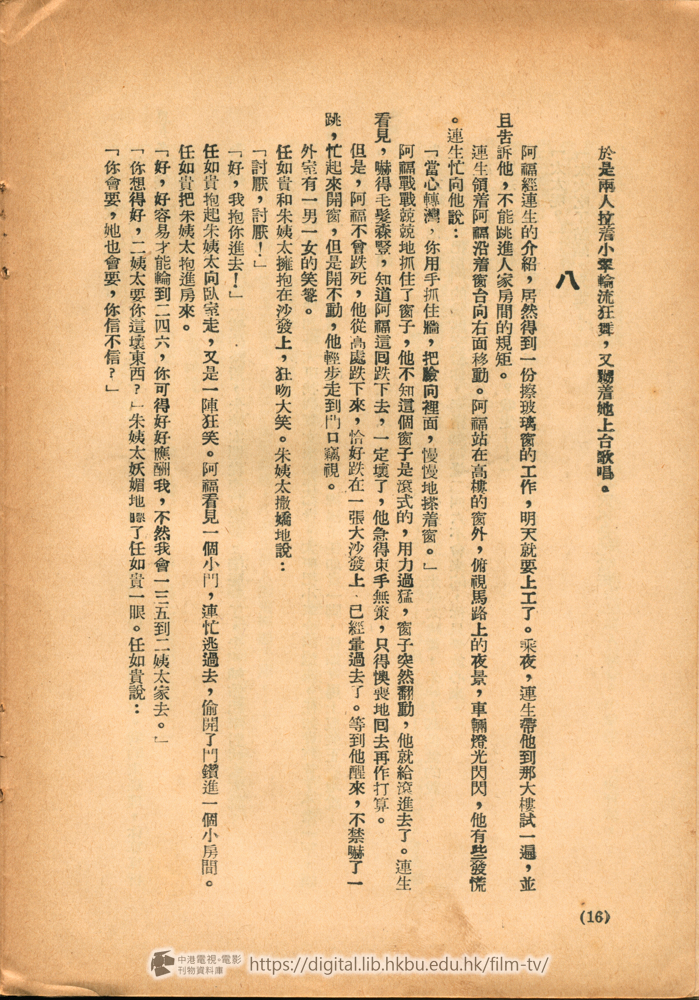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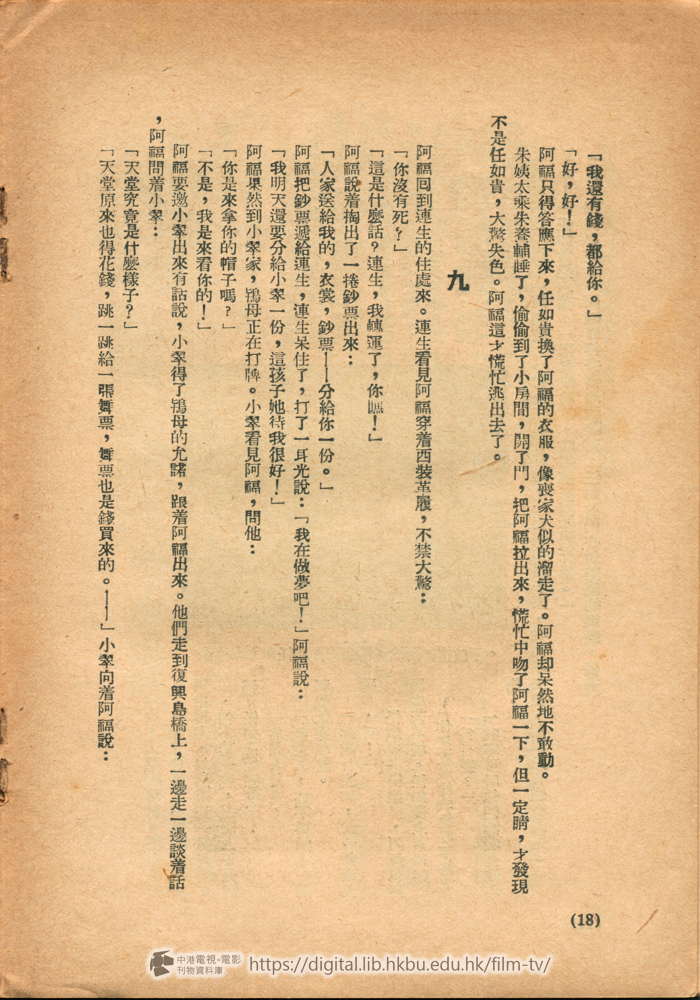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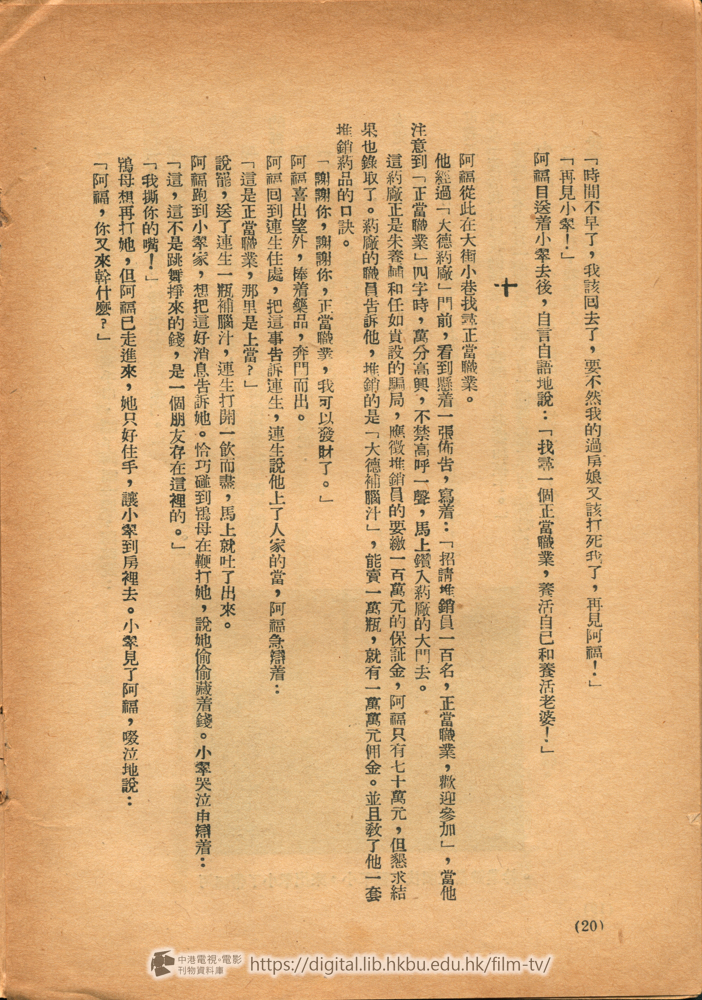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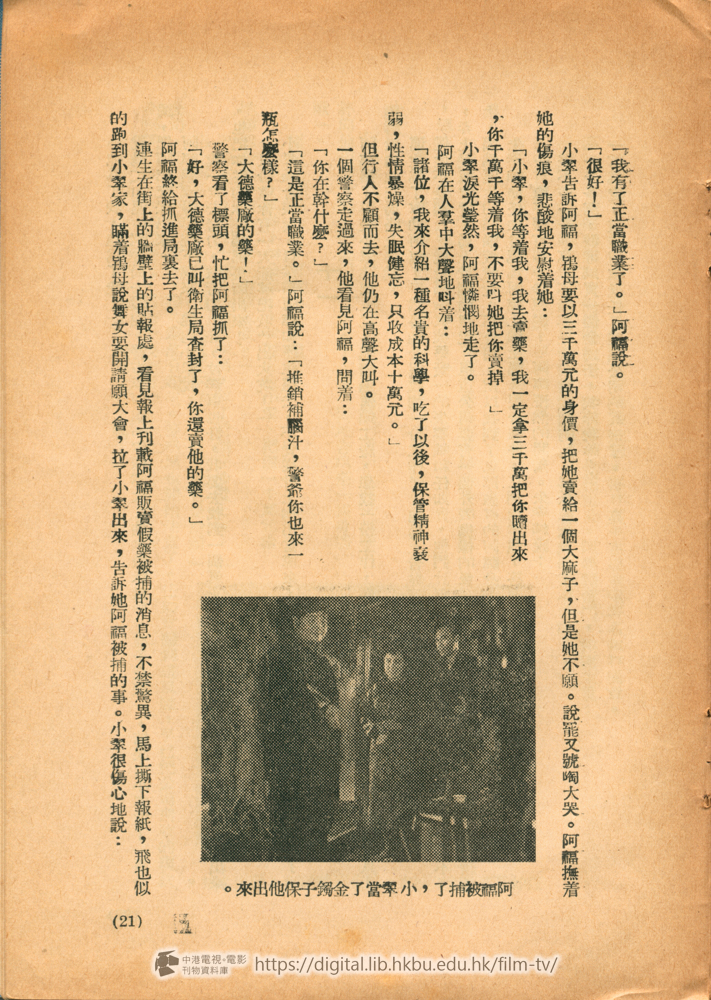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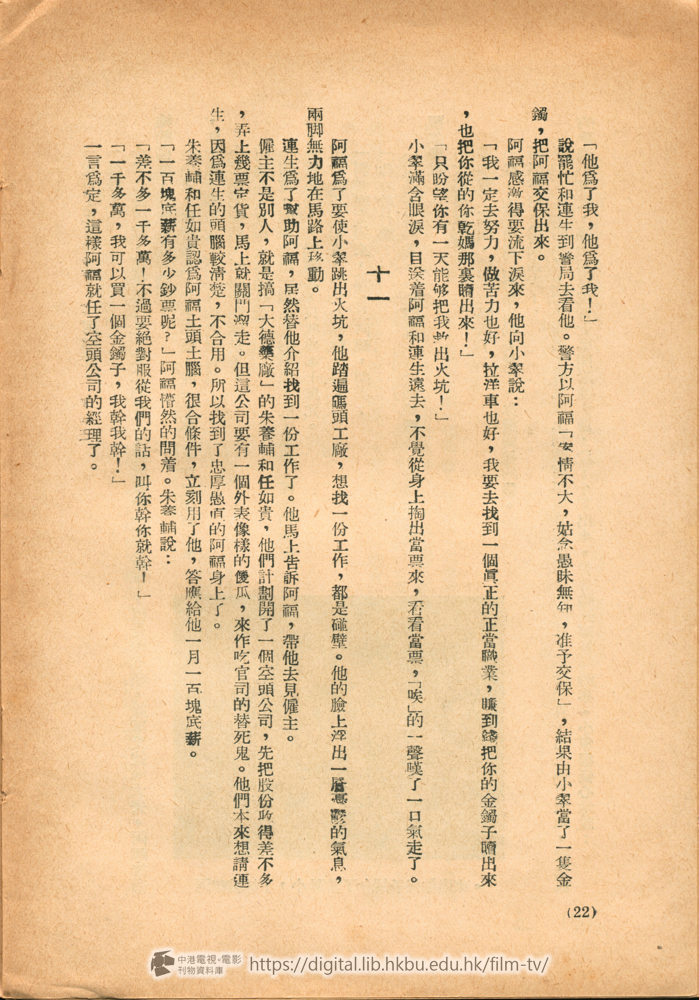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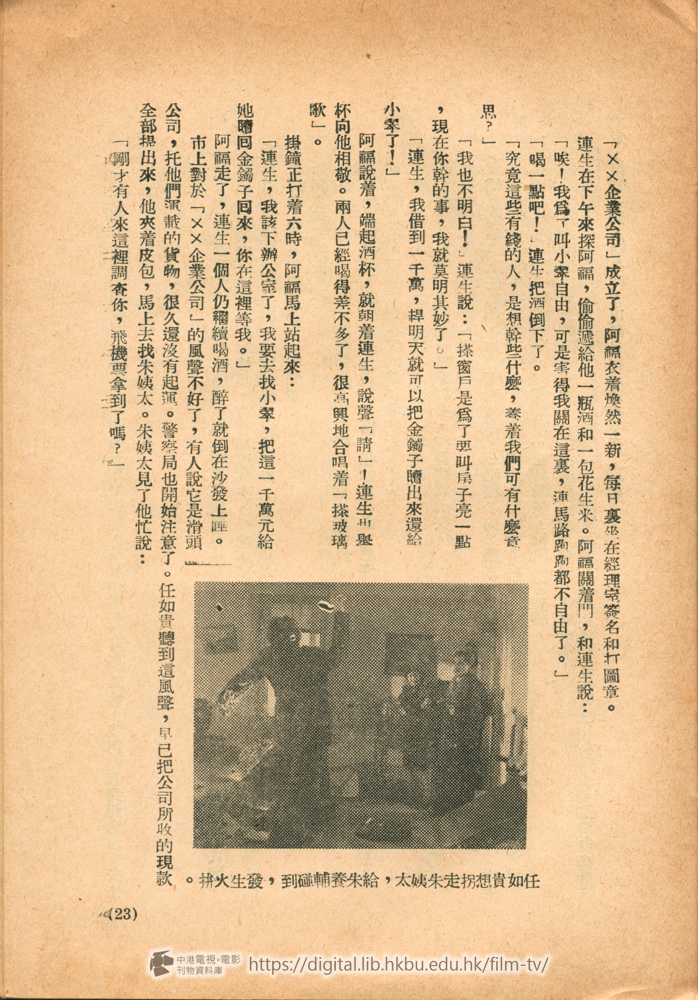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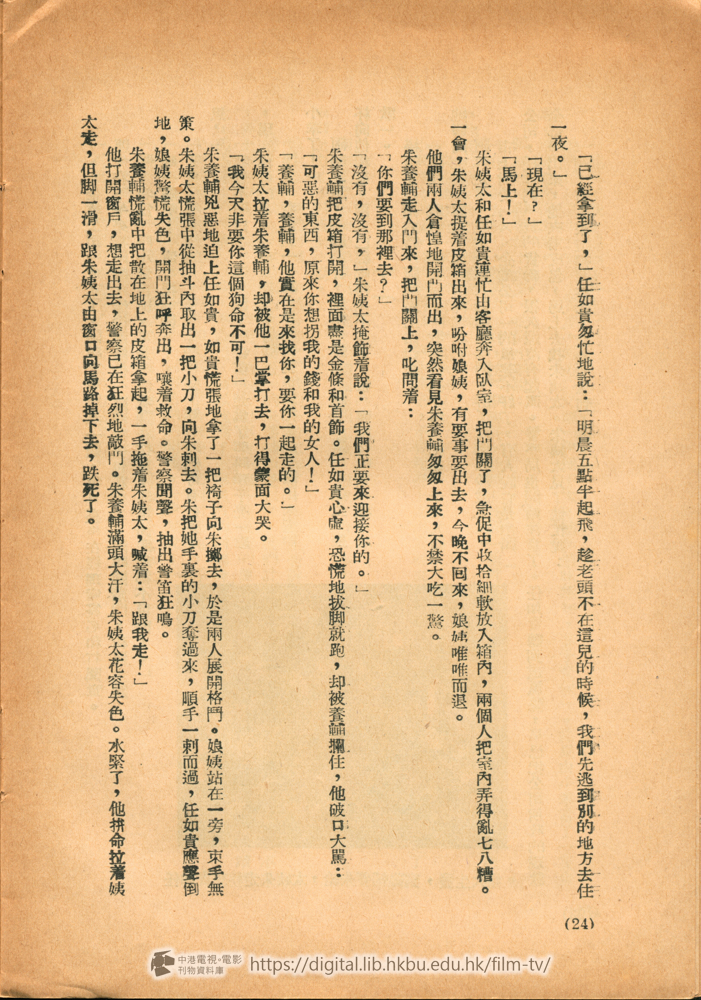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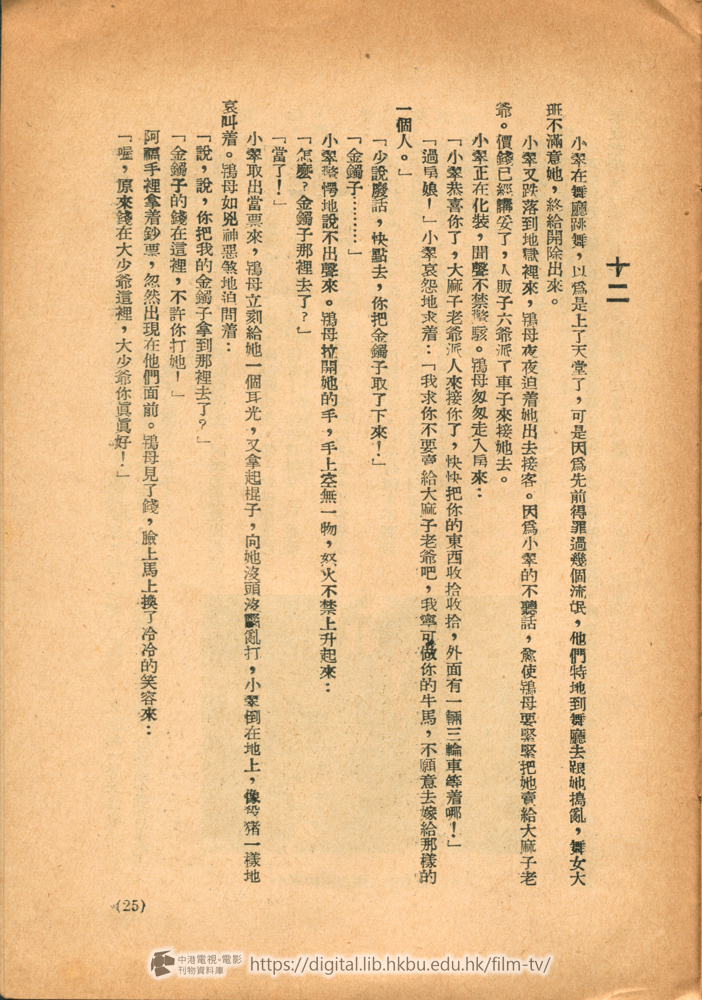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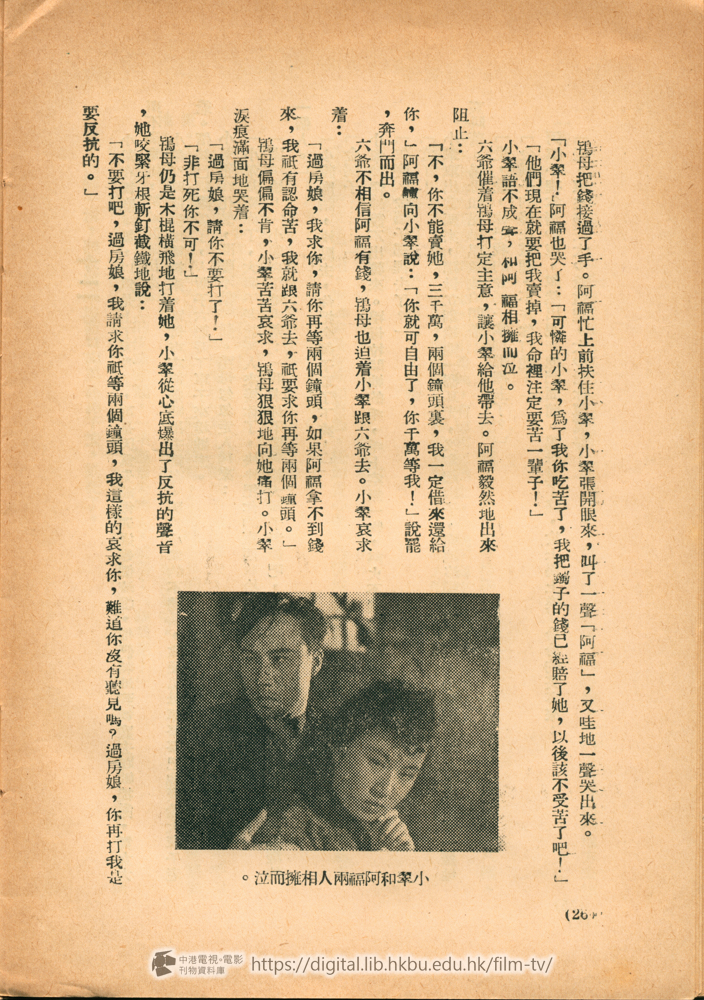

同是天涯淪落人
一
一九四七年冬。
大上海的夜景,像鍍金似的閃耀着,流溢着濃冽的色情底氣息。大舞廳,咖啡座,夜花園,陶公舘,都紙醉金迷,笙歌入雲。男男女女,在瘋狂地縱情作樂;醇酒,美人,紅唇,大腿,征服着許多沒有靈魂的人們底心,腐蝕着許多中國的「選民」底生命。
但在另一面,却有着一羣卑賤的人物,在這樂園的邊緣顫抖。
「爲了生存,血肉相拼!
强者豪奪,弱者哀鳴!
茫茫的人海,
良心何處尋?
…………」
在金陵東路,車輛和行人如梭,有些店鋪將要關門了,無線電公司的喇叭,還在有氣無力地播送着一串串凄凉的調子。那些像遊魂似的神女們,正在路旁忙着拉客。
雛妓小翠和她的養母,也夾在人叢中彷徨。小翠强做歡笑,迎拉着來往的行人。一個土老的行人經過她身邊,注視了她一眼,鴇母忙把他拉住,但給他掙脫走了。鴇母緊追上去。小翠也追了幾步,覺得沒有希望了,便停了步。忽然有幾個流氓走近來和她糾纏。
馬路轉角有一個警察出現了,許多攤販發足狂奔。小翠發覺了,也掙開流氓奔過馬路去,其他的野雞們看見了也四散狂飛。
★ ★
外灘海關的大鐘指在一時三刻。街頭的行人絕跡了,路旁的碎紙隨風吹動。
在一個高樓的階上,正睡着一個由鄕下逃抽壯丁,到這裡來尋活的靑年王阿福,因爲人地生疏,沒地方投奔,所以他每夜都是在騎樓下露宿。他在酣睡中翻身,跌下了一級。
一位彪形警察,吹着口哨,頂着風,持着手電筒,慢呑呑地從牆角走過來,他看見了阿福,踢了他一脚。阿福被踢醒了,抬起頭來,看見了警察,嚇了一跳說:
「怎麼,警爺?」
「請吧,在這兒睡覺,不怕受了涼嗎?去!」
「我不怕!」阿福懵然地說
「我怕你,滾開吧!」警察把阿福一推:「昨晚這兒丟了二十條麻袋,正找不着那個小偷。你滾開,當心……」
「是,是,我滾,我滾!」
阿福顫抖地爬起來,走下台階,彳亍而去。警察目送着他的背影,又繼續着他巡夜的工作。
夜風咻咻地吼着,像一支凄厲的喪曲!
二
小翠是一個年紀尙稚的女子,因爲戰亂的影響,家裏不能過活,被姑爹押到這個人肉販的鴇母家作女養,被迫着出去接客。鴇母想得了一筆較大的款子,這一夜正在晒台和一個叫六爺的人販子,商量着把小翠批發出去。她問六爺,人家出了多少錢?六爺說:
「人家只出兩干二百萬。」
「猪肉也漲了價,只出這一點點?」
「明天我再去好好跟那邊商量商量。」
六爺說着,摸了鴇母一臉,鴇母駡他死東西,他笑着走了。
小翠走到了小櫉,取了冷飯冷菜,嘆息地向內走。鴇母冷冷地說:
「你熬着吧,熬到人家討了你去。那就享福了,不用這麼咳聲嘆氣。」
「我太累了,沒有嘆氣。」
小翠幾乎要哭了,她端起飯想吃。一個粗壯的喝醉酒的嫖客,一顚一顚地踏上樓梯來,大着舌嚷着:
「小翠在嗎?」
「在,在,大爺請進來吧——」鴇母滿臉堆着笑,又大聲地呼着:「小翠,小翠!客人來了,出來呀!」
「就來了!」
小翠緊搶着把飯向口裡呑,鴇母已經衝入來,把她手中的筷子奪去,催着「去,去!」
「讓我把這一口吃了吧!」
「那麽要緊吃飯幹什麽,快去!」
鴇母邊說邊拿了一塊毛巾遞給小翠擦臉。小翠又低低嘆着氣,給鴇母在手膀上一擰,不禁負痛地「哎呀」了一聲。
嫖客笑着臉進來:
「小翠沒睡了嗎?」
「沒有,沒有!」鴇母諂笑着說:「請進來吧——小翠,你也不給客人倒茶。」
嫖客把錢塞給鴇母,鴇母數一數,又笑着說:
「大爺,米價又貴了,這個,這個實在太少!」
「只帶了這點錢,不行,我就走。」
嫖客說着要走,鴇母忙阻住了他:
「不,不,不要走,下次多帶點來就是了!」
鴇母一邊走一邊說:
「小翠,好好的侍候大爺,改天他討你做太太。」
嫖客情急地拉了小翠一手,小翠苦笑着,忽然手膀的負傷處被觸着,又不禁「咬呀」一聲:
「我這兒痛呀!」
嫖客哈哈地笑了,笑得那麽淫褻。
電燈倏然熄滅,老鼠吱吱地叫着,小翠又做了一次恐怖而殘酷的夢魘。
三
冬日的陽光,照着黃浦江,大上海又從沉睡中甦醒過來。
阿福還睡在一個大樓的階上,睡得正濃,驀地給一個搽玻璃窗的把白粉水洒醒,他驚惶地爬起來,仰着頭惺忪地嚷着:
「怎麼,怎麽?」
搽玻璃領的連生,是一個小胖子,是這大樓的打掃夫,他聞聲俯視着阿褔說:
「對不起,我不是有心的。」
說着丟下了一塊棉紗給阿福搽臉。
「人倒霉,鳥拉尿也拉在身上?」
阿福一面擦臉,一面嗟嘆着,連生看到他的臉搽得怪形怪狀,狂笑得幾乎要跌下來。
連生的笑聲太大,竟驚醒這公寓裡的一位朱姨太太,她是朱養輔老板的外寵,剛披着晨褸,在裝台前搽粉。她從鏡中看見連生的怪臉,不由得大惱起來:
「混帳東西,你笑什麼?」
「我笑把個人搽了一臉粉,成了鬼樣子。」
「胡說八道,我搽粉管你什麼事!」
朱姨太誤會連生的話是指她,忙命娘姨把窗帘拉下來。之後,又搽抹潤澤一番,現出了更冶艶的姿態,她禁不住顧影自憐,妖嬈款擺。
突然門鈴響了,朱養輔和他的搭擋也是朱姨太的面首的任如貴,從外室走進來。朱姨太馬上迎上去。任如貴忙向她獻殷勤:
「朱姨太太,你起得早!」
「喲,任先生你早!」
朱養輔很傲慢地坐下來吸煙,任如貴立刻取出打火機爲他點火。忙了一番之後,他們又勞勞叨叨談着「大德大藥廠」的事了。任如貴向朱養輔說:
「經理藥廠的事,我想幹業務經理,我頂合適,你看怎麽樣?」
「好吧!」朱養輔說:「你對這方面有什麼計劃?」
「計劃?」任如貴忙從皮包拿出了計劃書送給朱養輔檢閱,又滔滔地說:
「這是老花樣新作風,我們可以登報徵聘營業推銷員,多收保証金,只要這一着順利,包你可以到手一大批款子。」
「嗯,好的,嗯,讓我仔細考慮一下。我們到藥廠裏去瞧瞧。」
「好,就走吧!」
任如貴應了一聲,就站起來,朱姨太忙喊住了他們:
「就這樣走嗎?」
「我囘頭派車子來接你去吃早點。」
朱養輔向她笑了笑就走出去。任如貴跟在後面,囘頭偷偷向朱姨太做了個怪險,朱姨太媚笑地擰了他一把。
四
阿福給連生搽玻璃窗洒了一頭粉之後,兩人打起交道,竟相識起來。連生帶他到自己的下處來。連生的下處並不怎見得人,是一個貨倉的門洞,裡面放着幾個木箱,就當做睡床。但這在阿福看來,已經是天堂了。他不覺艶羨地說:
「好得很,我能住嗎?」
「能住,」連生說:「我就睡在那只箱子上。」
「警察不來趕人?」
「不,我是那個大樓的打掃夫,誰不認得我。你是我的朋友,他們不會趕你的。」
「謝謝!謝謝!我今天才算有個睡覺的地方。——唉!」
「你嘆什麼氣?」
連生驚奇地問。阿福凄凉地說:
「住的地方是有了,可是明天吃的東西還沒有哇!」
「別急,再過些日子,我有希望調到派拉撤里頭馬桶間裏去做打掃夫,只要我能這麼一升,我就保你頂我搽玻璃的這份差事,搽玻璃這事你總該會吧。」
「什麼時候你才升呢?」阿福緊問着。
「過了年準有希望吧。」
「還得一個來月,等到那時候,我不凍死也餓死了。」
「你可以給警察找點小麻煩。」連生好像很熟性地說:「叫他抓了你去,押他個把月,你知道拘留所是管飯的,等你出來,大槪你就可以搽玻璃了。」
「警察?」阿福驚駭地說:「我頂怕警察,昨天夜裡無緣無故打了我兩巴掌!」
「這有什麽要緊,睡吧,明天再說・」
明日,連生果然引阿福出去給警察找麻煩了。
在一家茶舘前,一個扒手竊了人家幾張巨額的鈔票,藏在帽裡,故意裝作安祥無事的樣子向外站着。連生靈機一動,指着扒手給阿福看:
「瞧,你去搶他的帽子,搶了之後不要快跑,好呌警察抓你去。」
「好吧,我試試!」
阿福胆怯地說,他囘顧着連生,木然走到扒手的背後,突然鼓起勇氣,抓起扒手頭上的帽子,扒手嚇了一跳,「哎呀」了一聲,阿福戴上帽子,推了扒手一把,扒手不知就裏,愴惶逃走。這時茶館內一個茶客,發覺五張十萬大票不見,看見扒手奔逃,方才醒悟,大呼:「追住他,那人偷了我的錢。」
行人聞聲,紛紛向扒手追趕。阿福戴着帽,果然望着那些人呼喊奔追。連生從牆角走過來,拉了阿幅。阿福取下帽來,奇怪的說:
「這是什麼一囘事,白白得了一頂帽子。」
「戴上,咱們走吧!」連生催着阿福走,阿福懵然地埋怨着他:
「你的話不靈,我沒有人抓!」
五
阿福囘到連生的住處來,他有一個死的念頭,生活迫得他太苦了。連生婉勸着他:
「你可不能這麽想,好死總不如懶活着,熬過去一關就是一關,早晚總有熬出頭的一天。」
「是呀,」阿福很凄凉地說:「天氣這麼冷,江水一定比冰還凉,我不打算這時候跳黃浦江,只要讓我活到春天,春天轉暖的時候,就是自殺也比現在舒服一點。」
連生聽了阿福的話,忽然心血來潮:
「咦,我再吿訴你一個辦法,這麽一來准呌警察抓了你去。」
說着拿了剛才搶來的那頂帽子,扣在阿福頭上,拉了他出來:
「跟我走,聽我的話…………」
淸冷的街頭,路燈下,一個少女的背影向前慢步着。連生和阿幅走過牆角來,連生推了他一把,指那少女的背影說:
「瞧,阿福,你的機會來了。」
阿幅竟然鼓起勇氣,直追那少女,走上前擁抱了她,凑在她的臉旁說:
「妹妹,你那裡去?」
少女囘頭來,原來是小翠,嫣笑中突然扳起臉來。阿福驚嚇失措,忙說着:
「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有看清是你。」
「一邊去吧,別窮開心了!」
小翠瞟了阿福一眼,阿福狼狽地想走,但迎面來了鴇母,竟一把拉住了他,駡着小翠說:
「怎麽,怎麽?小翠爲什麼不拉他?怪不得整天沒有生意。」
「不,不,我不能!」
阿福奇窘的說,鴇母狠狠地向小翠一盯:
「小翠,死東西!」
「他就在我們弄堂裡叫人打了一頓的那個人,他是我們的鄰居。」
小翠向鴇母解釋着,鴇母仍死拉住阿福不放。
「我沒有錢,不,不!」
掙扎中阿福跌落了帽子,皮邊中的鈔票跌漏了出來。
「這不是錢嗎?都是五千關金一張的。」
「這,這可不是我的。」
阿福終被拉着走,他死命地叫着:
「不,不,連生,你害了我!」
連生聞言,閉上眼睛,不忍再看,無可奈何的轉囘身就走。
六
阿福啼笑皆非的被拉到小翠的香巢來。鴇母把五十萬大票算做夜廂錢,叫小翠好好的侍候他,自己到張家去搓麻將了。
阿福嚇得面無人色,小翠斟了一杯茶送到他面前說:
「請喝茶!」
「謝謝!」阿福木然的不安地站着,小翠看得好笑:
「坐下來吧!」
「是,是!」阿福在房裡四下觀望,失魂落魄似的坐下來,忽然自語地說:「簡直像做夢一樣呀!」
「什麽?」小翠說:「看你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唔!」
「你貴姓?」
「我姓王!」阿福說:「你呢?」
「我叫小翠!」
小翠說罷,走入帳幔後脫衣。阿福忽然站起來,說聲「再見!」小翠忙走出來說:
「你花了這許多錢就走嗎?到那兒去?」
「我還不是囘到我老地方去睡。」
「這兒不好?」
「這兒太好!」
阿福說着要走,小翠惶恐地走過來拉住他:
「你不能走,走了我的那位過房娘會打死我的,我求你明天再走!」
「她這麼厲害?」
「眞的!」
「唉!」阿福不覺嘆了一口氣:「我原想到拘留所裏去過夜的,眞沒有想到來給你添麻煩!」說着又不禁埋怨着連生。小翠勸他睡了,他要睡在地板上。小翠奇怪地說:
「你睡在地上?」
「這樣很好!」阿福說:
「地上又冷又硬。」
「比水門汀好多了!你睡吧!」
阿福說着就自已向地板上躺下去,小翠勸阻他不得,只得熄了電燈,翻開被要睡,想一想又笑着說:
「你這個人眞有趣,也眞奇怪!」
「我碰見奇怪的事更多。」阿福冷冷的應了一聲,小翠緊接着說:
「你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個好人!」
「怎麽講?」阿福覺得奇怪。小翠說:
「一個不欺負人的人!」
「只要別人不欺負我已經好了,我那裡能欺負人!」
阿福在地板上翻身,睡不着,小翠請他上床來,他不肯。小翠爬了起來倚在枕上說:
「你睡不着,我們談談也好,你從什麽地來的?」
「我從鄕下來的,老子娘都死了,鄕下活不下去,流落到這兒來,誰知這兒比鄕下更不容易活下去。」
「你沒有事?」
「沒有,什麼事都找不到。」
小翠聽了阿福的話,不禁低低的嘆息:
「我們兩個人命是一樣的苦,我是叫姑爹給買在這兒的,我還不了債,走不了。我想去當舞女,聽說舞女掙錢多,我只想能一下子有點錢還給過房娘,我好不挨打,好不天天接客。」
「你有這麼好的房子住,你比我强!」
「我在這裡,還比你强?——我只盼望能有這麽一天,我能熬成一個舞女,我就算上了天堂。我馬上要去學跳舞,學會以後不就爬上了天堂了嗎?」
「我壓根兒就沒有見過跳舞是什麽樣子。」
「一個男人抱着一個女人跳,不過唱歌倒滿好聽。」
「我也從來沒有留心聽過。」
「我在馬路上學了一個歌,我哼給你聽?」
「好!」阿福也覺得小翠不怎麼討厭,所以讓她歌唱了。
小翠披了衣坐在床上曼聲而歌,阿福說很像一個女人在哭墳,味道頂叫人傷心。小翠說:「還有呢,…
同在天涯淪落,天涯淪落,
爲了生存,血肉相拚,
出賣靈魂!
貧者受苦,富者荒淫,
茫茫人海,正義何處尋!」
小翠的歌剛終,阿福在地板上已經鼾聲大作。
「他睡着了,可憐的傻孩子!」
小翠輕輕地下床來,拿了一條毯子,給阿福蓋上,走囘床來,又嘆了一口氣。她睡下去,看着阿福,含笑地去尋她的好夢去了。
七
小翠居然學會跳舞了,她以爲這一下子可以跳上天堂。雖然鴇母怎麽阻難,都不能阻住她下海的决心。
她决然地投入了「紅星舞廳」當舞女了。
花燈初開,樂台上的洋琴狂奏着,舞池的舞影翩躚,小翠也被人擁着輕擺慢翔。……
在舞場的一角,朱養輔,朱姨太,任如貴正坐在一塊觀舞。任如貴手裏拿着一瓶藥水,向朱養輔說:
「我們這種藥水,論裝璜比美國貨好!」
「推銷計劃你有把握嗎?」朱養輔說。
「我的計劃是老方法,可是用新花樣,你放心,我們的貨出來,馬上登報招推銷員。」
「會有人來嗎?」
「現在失業人多,你怕沒有人來嗎?」
「人多,貨也頂不上呀!」
「每一位堆銷員要預收一百萬保証金,一個一百,十個一千,百個一億,千個十億。我的朱經理,你算算折息是多少錢一個月,他們不賣葯我們就賺了二億。」
「這麼說這生意倒不壞呀?」
「不發財,誰幹這種買賣!」
朱養輔和任如貴在一鑼一鈸的談着,朱姨太則從旁打邊鼓。樂聲響了,朱養輔站起來對姨太太說:
「我們跳一次吧?」
「任先生是客,你一點禮貌也不懂!」
朱姨太這一拒絕,朱養輔却呌大班找個舞女來給任如貴。大班把小翠介紹過來,任如貴打量了小翠一下,頗表滿意,請她坐下。朱姨太念着妒意的扭過身去,暗地裡踢了任如貴一脚,任如貴馬上假裝正經地說:
「朱經理先跳吧!」
「太太,」朱養輔對姨太太說:「我可以跳嗎?」
「你跳黃浦我也不管。」
朱姨太瞟了他一眼,朱養輔就扶着小翠跳入舞池。任如貴想請朱姨太跳舞,朱姨太却低低的說:
「我不跳,我把房門的鑰匙交給你,老猪玀毎逢二四六不會來的,你只管放心來。」
「好!」任如貴如奉玉音地,朱姨太打了他一下說:
「別迷住這個小舞女,聽見了沒有?我走了!」
說着離座而去。朱養輔舞罷歸座,看不見太太,問着任如貴:
「太太呢?」
「太大吃了點醋,先走了。」
「走了也好,」朱養輔乾笑着:「我們方便點,今天不是她當班。」
於是兩人拉小翠輪流狂舞,又嬲着她上台歌唱。
八
阿福經連生的介紹,居然得到一份擦玻璃窗的工作,明天就要上工了。乘夜,連生帶他到那大樓試一遍,並且吿訴他,不能跳進人家房間的規矩。
連生領着阿福沿着窗台向右面移動。阿福站在高樓的窗外,俯視馬路上的夜景,車輛燈光閃閃,他有些發慌。連生忙向他說:
「當心轉灣,你用手抓住牆,把臉向裡面,慢慢地搽着窗。」
阿福戰戰兢兢地抓住了窗子,他不知這個窗子是滾式的,用力過猛,窗子突然翻動,他就給滾進去了。連生看見,嚇得毛髮森豎,知道阿福這囘跌下去,一定壞了,他急得朿手無策,只得懊喪地囘去再作打算。
但是,阿福不曾跌死,他從高處跌下來,恰好跌在一張大沙發上□巳經暈過去了。等到他醒來,不禁嚇了一跳,忙起來開窗,但是開不動,他輕步走到門口竊視。
外室有一男一女的笑聲。
任如貴和朱姨太擁抱在沙發上,狂吻大笑。朱姨太撒嬌地說:
「討厭,討厭!」
「好,我抱你進去!」
任如貴抱起朱姨太向臥室走,又是一陣狂笑。阿福看見一個小門,連忙逃過去,偷開了門鑽進一個小房間。任如貴把朱姨太抱進房來。
「好,好容易才能輪到二四六,你可得好好應酬我,不然我會一三五到二姨太家去。」
「你想得好,二姨太要你這壞東西?」朱姨太妖媚地瞟了任如貴一眼。任如貴說:
「你會要,她也會要,你信不信?」
「我信,我信!」
朱姨太情急地摟着任如貴,任如貴輕輕地把她丟在床上。
這一對狗男女正在胡天胡地,欲罷不能的時候,朱養輔忽然怒氣冲冲地走進外室來,大聲的叫駡。任如貴和朱姨太嚇得從床上跳起來!
「糟糕!老東西囘來了,怎麽他又囘來?」
「哎呀!快,你快藏起來!」
朱姨太慌忙地把任如貴推進小房間之後,花容失色地出來迎接朱養輔,心虛地問他爲什麽生這樣的大氣。
朱養輔吿訴她,他剛才在二姨太那裡碰到了姦夫。給逃了,如果捉着,一定在那小子身上扎一百下刀子。朱姨太聽說,才把心上的石放下來,於是換上了一副媚態,把朱養輔逗上床了。
任如貴逃進了小房問,在黑暗中摸索,忽然摸到一個人的耳朶,他不禁一驚,這個人正是阿福。任如貴低聲地問:
「你是人是鬼?」
「我是人,你不要怕!」阿福也低聲地說。
「你說什麼話,當心外面人聽見,噓!」
任如貴嚇得發抖,阿福也抖得痛苦不堪。任如貴求着阿福:
「你把衣服給我換好不好?」
「爲什麽?」
「我寧可叫他們認我是個小偷。」
「我可不是小偷!」阿福說:「我是搽玻璃窗的,一交跌進屋子來,我出不去啦,所以只有躱在這兒。」
「唉!」任如貴懇求着:「把衣服脫了,我用這套西裝給你換。」
「那,那何必呢?」阿福覺得奇怪地推辭着,任如貴則心如熱鍋的螞蟻,催着:
「我還有錢,都給你。」
「好,好!」
阿福只得答應下來,任如貴換了阿福的衣服,像喪家犬似的溜走了。阿福却呆然地不敢動。
朱姨太乘朱養輔睡了,偷偷到了小房間,開了門,把阿福拉出來,慌忙中吻了阿福一下,但一定睛,才發現不是任如貴,大驚失色。阿福這才慌忙逃出去了。
九
阿福囘到連生的住處來。連生看見阿福穿着西裝革履,不禁大驚:
「你沒有死?」
「這是什麽話?連生,我轉運了,你瞧!」
阿福說着掏出了一捲鈔票出來:
「人家送給我的,衣裳,鈔票——分給你一份。」
阿福把鈔票給連生,連生呆住了,打了一耳光說:「我在做夢吧!」阿福說:
「我明天還要分給小翠一份,這孩子她待我很好!」
阿福果然到小翠家,鴇母正在打牌。小翠看見阿福,問他:
「你是來拿你的帽子嗎?」
「不是,我是來看你的!」
阿福要邀小翠出來有話說,小翠得了鴇母的允諾,跟着阿福出來。他們走到復興島橋上,一邊走一邊談着話,阿福問着小翠:
「天堂究竟是什麽樣子?」
「天堂原來也得花錢,跳一跳給一張舞票,舞票也是錢買來的。——」小翠向着阿福說:
「你有什麽話給我說?」她揉着手巾,瞟了阿福一眼,阿福說:
「我有一票錢!」
「有了錢不要亂用,錢是不容易掙來的。」
「這錢來得方便,是人送給我的,所以我要分一份給你。」
「何必呢?」小翠說:「你自已留着用不好嗎?」
「我現在只有兩個人才是朋友,一個是你,一個是連生!」
「噢!」小翠幡然地說:「是那個和你帮着我打倒那個流氓的那個人?」
阿福把錢放入小翠的手袋裡,小翠感動地說:
「我怎麽能無原無故收你的錢!」
「有錢大家用,我們是好朋友!」
「不過,」小翠說:「你應該找一個正當職業,那生活才會安定,你這樣閒着不是辦法。」
「什麼是正常職業?」
「職業有正當的,也有不正當的,一個人有了正當職業,就可養活自已,養活老婆和孩子。」
「養活我自已我倒滿意,可是我還沒有老婆和孩子。」
「難道你不想有一個安定的家,有一個眞正愛你的老婆嗎?」
小翠說着就發羞,低下頭來,阿福這才恍然大悟,忙說:
「想,想,我想,我想!」
說着情急地拉了小翠的手,小翠羞得滿面通紅,把手拉開說:
「時間不早了,我該囘去了,要不然我的過房娘又該打死我了,再見阿福!」
「再見小翠!」
阿福目送着小翠去後,自言自語地說:「找一個正當職業,養活自己和養活老婆!」
十
阿福從此在大街小巷找尋正當職業。
他經過「大德葯廠」門前,看到懸着一張佈吿,寫着:「招請推銷員一百名,正當職業,歡迎參加」,當他注意到「正當職業」四字時,萬分高興,不禁高呼一聲,馬上鑽入葯廠的大門去。
這葯廠正是朱養輔和任如貴設的騙局,應徵推銷員的要繳一百萬元的保証金,阿福只有七十萬元,但懇求結果也錄取了。葯廠的職員吿訴他,推銷的是「大德補腦汁」,能賣一萬瓶,就有一萬萬元佣金。並且敎了他一套推銷葯品的口訣。
「謝謝你,謝謝你,正當職業,我可以發財了。」
阿福喜出望外,捧着藥品,奔門而出。
阿褔囘到連生住處,把這事吿訴連生,連生說他上了人家的當,阿福急辯着:
「這是正當職業,那里是上當?」
說罷,送了連生一瓶補腦汁,連生打開一飮而盡,馬上就吐了出來。
阿福跑到小翠家,想把這好消息吿訴她。恰巧碰到鴇母在鞭打她,說她偷偷藏着錢。小翠哭泣申辯着:
「這,這不是跳舞掙來的錢,是一個朋友存在這裡的。」
「我撕你的嘴!」
鴇母想再打她,但阿福已走進來,她只好住手,讓小翠到房裡去。小翠見了阿福,啜泣地說:
「阿福,你又來幹什麽?」
「我有了正當職業了。」阿福義。
「很好!」
小翠吿訴阿福,鴇母要以三干萬元的身價,把她賣給一個大麻子,但是她不願。說罷又號陶大哭。阿福撫着她的傷痕,悲酸地安慰着她:
「小翠,你等着我,我去賣藥,我一定拿三千萬把你贖出來,你千萬千等着我,不要呌她把你賣掉」
小翠淚光瑩然,阿福憐憫地走了。
阿福在人羣中大聲地呌着:
「諸位,我來介紹一種名貴的科學,吃了以後,保管精神衰弱,性情暴燥,失眠健忘,只收成本十萬元。」
但行人不顧而去,他仍在高聲大叫。
一個警察走過來,他看見阿福,問着:
「你在幹什麼?」
「這是正當職業。」阿福說:「推銷補腦汁,警爺你也來一瓶怎麽樣?」
「大德藥廠的藥!」
警察看了標頭,忙把阿福抓了:
「好,大德藥廠已叫衛生局查封了,你還賣他的藥。」
阿福終給抓進局裏去了。
連生在街上的牆壁上的貼報處,看見報上刊載阿福販賣假藥被捕的消息,不禁驚異,馬上撕下報紙,飛也似的跑到小翠家,瞞着鴇母說舞女要開請願大會,拉了小翠出來,吿訴她阿福被捕的事。小翠很傷心地說:
「他爲了我,他爲了我!」
說罷忙和連生到警局去看他。警方以阿福「案情不大,姑念愚昧無知,准予交保」,結果由小翠當了一隻金鐲,把阿福交保出來。
阿福感激得要流下淚來,他向小翠說:
「我一定去努力,做苦力也好,拉洋車也好,我要去找到一個眞正的正當職業,賺到錢把你的金鐲子贖出來,也把你從的你乾媽那裏贖出來!」
「只盼望你有一天能够把我救出火坑!」
小翠滿含眼淚,目送着阿福和連生遠去,不覺從身上掏出當票來,看看當票,「唉」的一聲嘆了一口氣走了。
十一
阿福爲了要使小翠跳出火坑,他踏遍碼頭工廠,想找一份工作,都是碰壁。他的臉上浮出一層憂鬱的氣息,兩脚無力地在馬路上移動。
連生爲了幫助阿福,居然替他介紹找到一份工作了。他馬上吿訴阿福,帶他去見僱主。
僱主不是別人,就是搞「大德藥廠」的朱養輔和任如貴,他們計劃開了一個空頭公司,先把股份收得差不多,弄上幾票定貨,馬上就關門溜走。但這公司要有一個外表像樣的傻瓜,來作吃官司的替死鬼。他們本來想請連生,因爲連生的頭腦較清楚,不合用。所以找到了忠厚愚直的阿福身上了。
朱養輔和任如貴認爲阿福土頭土腦,很合條件,立刻用了他,答應給他一月一百塊底薪。
「一百塊底薪有多少鈔票呢?」阿福懵然的問着。朱養輔說:
「差不多一千多萬!不過要絕對服從我們的話,叫你幹你就幹!」
「一千多萬,我可以買一個金鐲子,我幹我幹!」
一言爲定,這樣阿福就任了空頭公司的經理了。
「XX企業公司」成立了,阿福衣着煥然一新,每日裏坐在經理室簽名和打圖章。
連生在下午來探阿福,偷偷遞給他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阿福關着門,和連生說:
「唉!我爲了叫小翠自由,可是害得我關在這裏,連馬路跑跑都不自由了。」
「喝一點吧!連生把酒倒下了。
「究竟這些有錢的人,是想幹些什麼,養着我們可有什麽意思?」
「我也不明白!」連生說:「搽窗戶是爲了要叫房子亮一點,現在你幹的事,我就莫明其妙了。」
「連生,我借到一千萬,趕明天就可以把金鐲子贖出來還給小翠了!」
阿福說着,端起酒杯,就朝着連生,說聲「請」!連生也舉杯向他相敬。兩人已經喝得差不多了,很高興地合唱着「搽玻璃歌」。
掛鐘正打着六時,阿福馬上站起來:
「連生,我該下辦公室了,我要去找小翠,把這一千萬元給她贖囘金鐲子囘來,你在這裡等我。」
阿福走了,連生一個人仍繼續喝酒,醉了就倒在沙發上睡。
市上對於「XX企業公司」的風聲不好了,有人說它是滑頭公司,托他們運載的貨物,很久還沒有起運。警察局也開始注意了。任如貴聽到這風聲,早已把公司所收現款全部提出來,他夾着皮包,馬上去找朱姨太。朱姨太見了他忙說:
「剛才有人來這裡調査你,飛機票拿到了嗎?」
「已經拿到了,」任如貴匆忙地說:「明晨五點半起飛,趁老頭不在這兒的時候,我們先逃到別的地方去住一夜。」
「現在?」
「馬上!」
朱姨太和任如貴連忙由客廳奔入臥室,把門關了,急促中收拾細軟放入箱內,兩個人把室內弄得亂七八糟。一會,朱姨太提着皮箱出來,吩咐娘姨,有要事要出去,今晚不囘來,娘姨唯唯而退。
他們兩人倉惶地開門而出,突然看見朱養輔匆匆上來,不禁大吃一驚。
朱養輔走入門來,把門關上,叱問着:
「你們要到那裡去?」
「沒有,沒有,」朱姨太掩飾着說:「我們正要來迎接你的。」
朱養輔把皮箱打開,裡面盡是金條和首飾。任如貴心虛,恐慌地拔脚就跑,却被養輔攔住,他破口大駡:
「可惡的東西,原來你想拐我的錢和我的女人!」
「養輔,養輔,他實在是來找你,要你一起走的。」
朱姨太拉着朱養輔,却被他一巴掌打去,打得蒙面大哭。
「我今天非要你這個狗命不可!」
朱養輔兇惡地迫上任如貴,如貴慌張地拿了一把椅子向朱擲去,於是兩人展開格鬥,娘姨站在一旁,束手無策。朱姨太慌張中從抽斗內取出一把小刀,向朱剌去。朱把她手裏的小刀奪過來,順手一刺而過,任如貴應聲倒地,娘姨驚慌失色,開門狂呼奔出,嚷着救命。警察聞聲,抽出警笛狂鳴。
朱養輔慌亂中把散在地上的皮箱拿起,一手拖着朱姨太,喊着:「跟我走!」
他打開窗戶,想走出去,警察已在狂烈地敲門。朱養輔滿頭大汗,朱姨太花容失色。水緊了,他拼命拉着姨太走,但脚一滑,跟朱姨太由窗口向馬路掉下去,跌死了。
十二
小翠在舞廳跳舞,以爲是上了天堂了,可是因爲先前得罪過幾個流氓,他們特地到舞廳去跟她搗亂,舞女大班不滿意她,終給開除出來。
小翠又跌落到地獄裡來,鴇母夜夜迫着她出去接客。因爲小翠的不聽話,愈使鴇母要緊緊把她賣給大麻子老爺。價錢已經講妥了,人販子六爺派了車子來接她去。
小翠正在化裝,聞聲不禁驚駭。鴇母匆匆走入房來:
「小翠恭喜你了,大麻子老爺派人來接你了,快快把你的東西收拾收拾,外面有一輛三輪車等着哪!」
「過房娘!」小翠哀怨地求着:「我求你不要賣給大麻子老爺吧,我寧可做你的牛馬,不願意去嫁給那樣的一個人。」
「少說廢話,快點去,你把金鐲子取了下來!」
「金鐲子………」
小翠驚愕地說不出聲來。鴇母拉開她的手,手上空無一物,怒火不禁上升起來:
「怎麼?金鐲子那裡去了?」
「當了!」
小翠取出當票來,鴇母立刻給她一個耳光,又拿起棍子,向她沒頭沒腦亂打,小翠倒在地上,像殺猪一樣地哀叫着。鴇母如兇神惡煞地迫問着:
「說,說,你把我的金鐲子拿到那裡去了?」
「金鐲子的錢在這裡,不許你打她!」
阿福手裡拿着鈔票,忽然出現在他們面前。鴇母見了錢,臉上馬上換了冷冷的笑容來:
「喔,原來錢在大少爺這裡,大少爺你眞眞好!」
鴇母把錢接過了手。阿福忙上前扶住小翠,小翠張開眼來,叫了一聲「阿福」,又哇地一聲哭出來。
「小翠!」阿福也哭了:「可憐的小翠,爲了我你吃苦了,我把鐲子的錢已經賠了她,以後該不受苦了吧!」
「他們現在就要把我賣掉,我命裡注定要苦一輩子!」
小翠語不成聲,和阿福相擁而泣。
六爺催着鴇母打定主意,讓小翠給他帶去。阿福毅然地出來阻止:
「不,你不能賣她,三千萬,兩個鐘頭裏,我一定借來還給你,」阿福轉向小翠說:「你就可自由了,你千萬等我!」說罷,奔門而出。
六爺不相信阿福有錢,鴇母也迫着小翠跟六爺去。小翠哀求着:
「過房娘,我求你,請你再等兩個鐘頭,如果阿福拿不到錢來,我祇有認命苦,我就跟六爺去,祇要求你再等兩個鐘頭。」
鴇母偏偏不肯,小翠苦苦哀求,鴇母狠狠地向她痛打。小翠涙痕滿面地哭着:
「過房娘,請你不要打了!」
「非打死你不可!」
鴇母仍是木棍橫飛地打着她,小翠從心底爆出了反抗的聲音,她咬緊牙根斬釘截鐵地說:
「不要打吧,過房娘,我請求你祇等兩個鐘頭,我這樣的哀求你,難道你沒有聽見嗎?過房娘,你再打我是要反抗的。」
「哼!」鴇母怪叫起來:「你敢!我看你怎麽反抗,你反抗?你反抗!」
小翠突然挺起胸,咬牙切齒地搶過木棍,猛然向鴇母臉上一擊:
「過房娘,我是個猪,我也不能叫你隨便宰了!」
鴇母不禁愕然,小翠憤然奪門奔出,鴇母恍然大驚:
「這,這不得了,六爺你趕快把她追囘來!」
小翠走下樓,在街上飛也似地狂奔,六爺和鴇母在後面拚命追趕。
小翠走到了「XX企業公司」門口,衝了入去,只見室內人聲鼎沸,阿褔連生和幾位警察在爭論,她不禁驚異。她聽知這是一宗大騙案,阿福是經理,警長要抓他。小翠的心冰冷下來了。
阿褔轉頭看見了小翠,失望地說:
「小翠!你!」
「這是怎麼了?」小翠的淚又掉下來了。
「不懂,又呌他們抓去了!」
「大騙案鬧得人人知,你們會不知道!」
警察說着,推了阿福和連生出門,小翠嗟嘆地說:
「阿福,你又上了人家的當了!」
警察把阿福和連生押上警車,小翠流着淚,情不自禁地追上去拉阿福的手:
「阿福!」
「小翠,你不要害怕,」阿福哭喪着臉說:「我是好人,我馬上就囘來,你千萬要等我!」
警車開動遠去,小翠瘋狂地哭喊着:
「阿福!阿福!」
鴇母和六爺從牆角走上來,一邊一個挾起小翠。小翠木然地被兩人挾着向馬路中心遠去。
凄涼的「天涯淪落」的歌聲,伴送着昏喑的太陽落下西山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