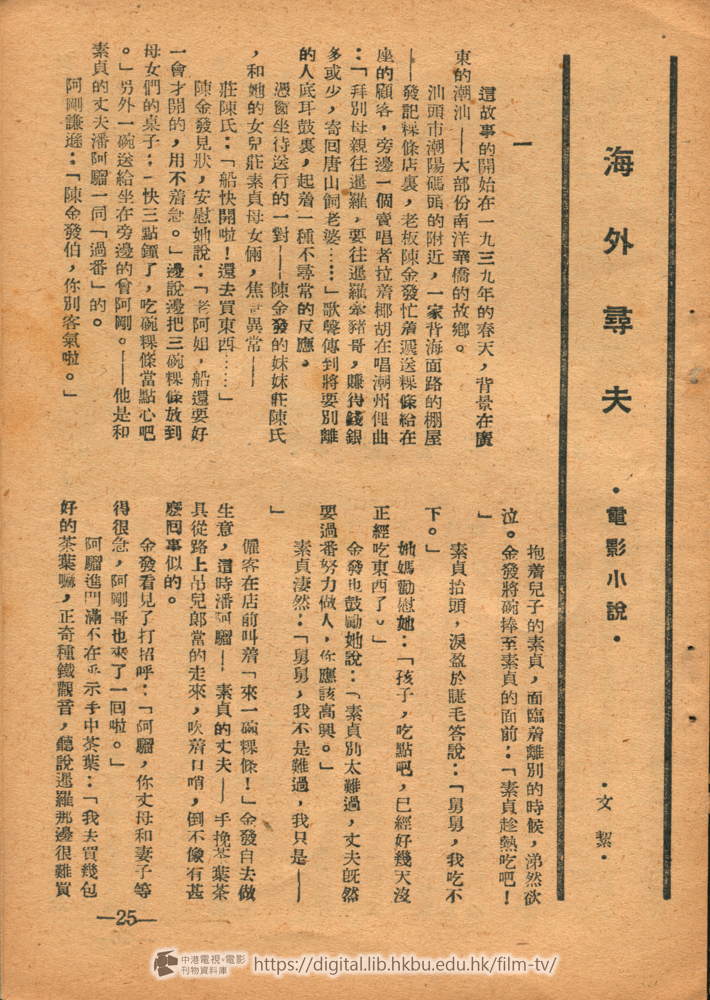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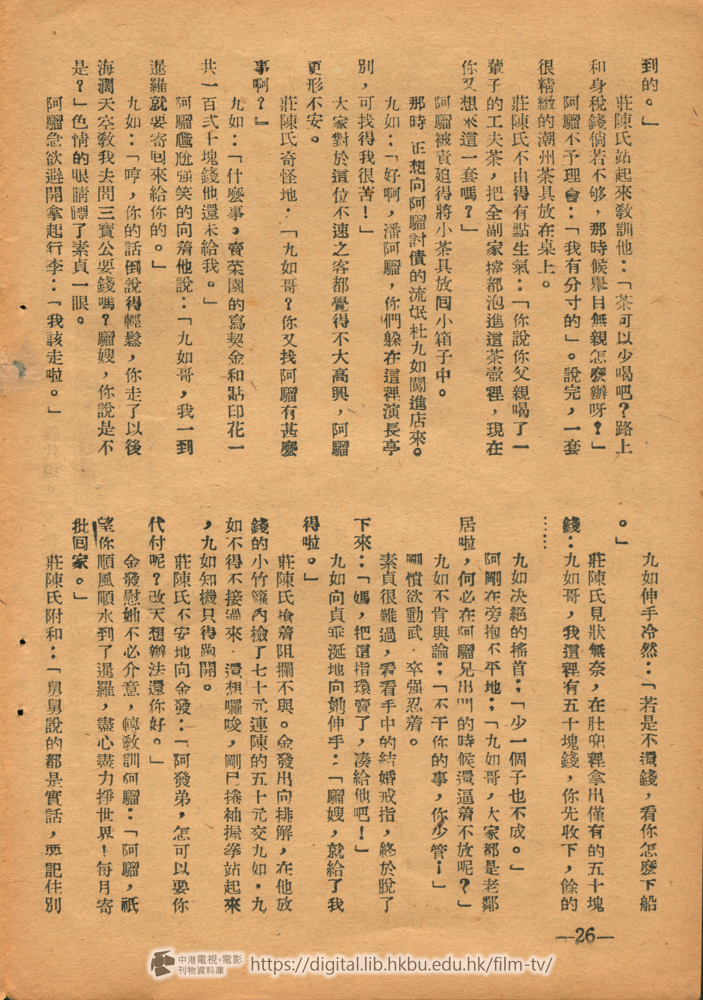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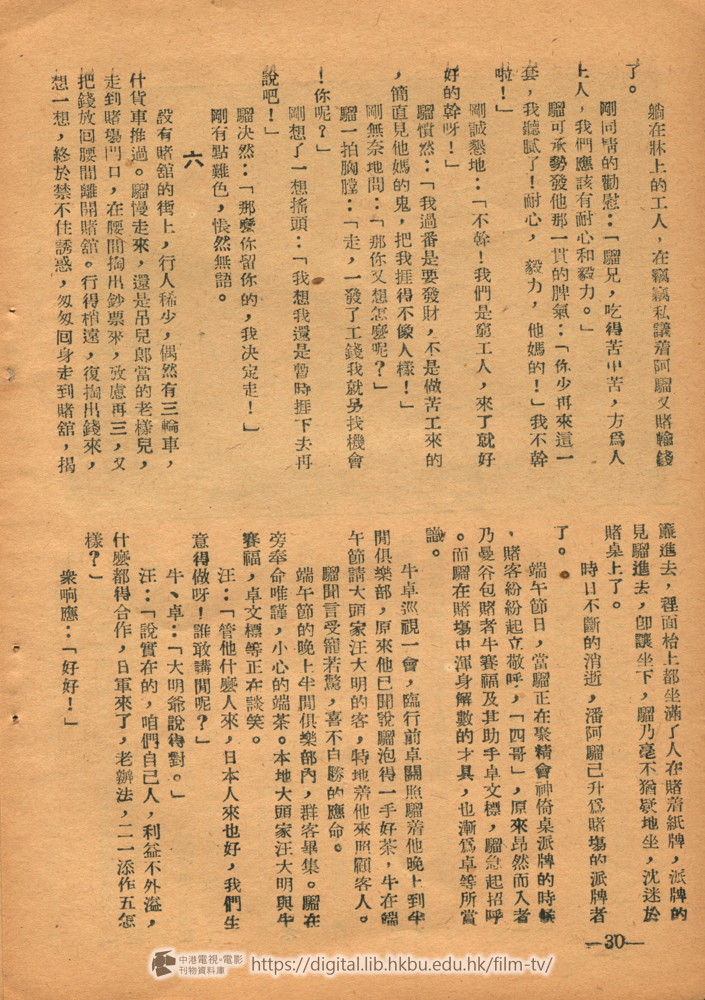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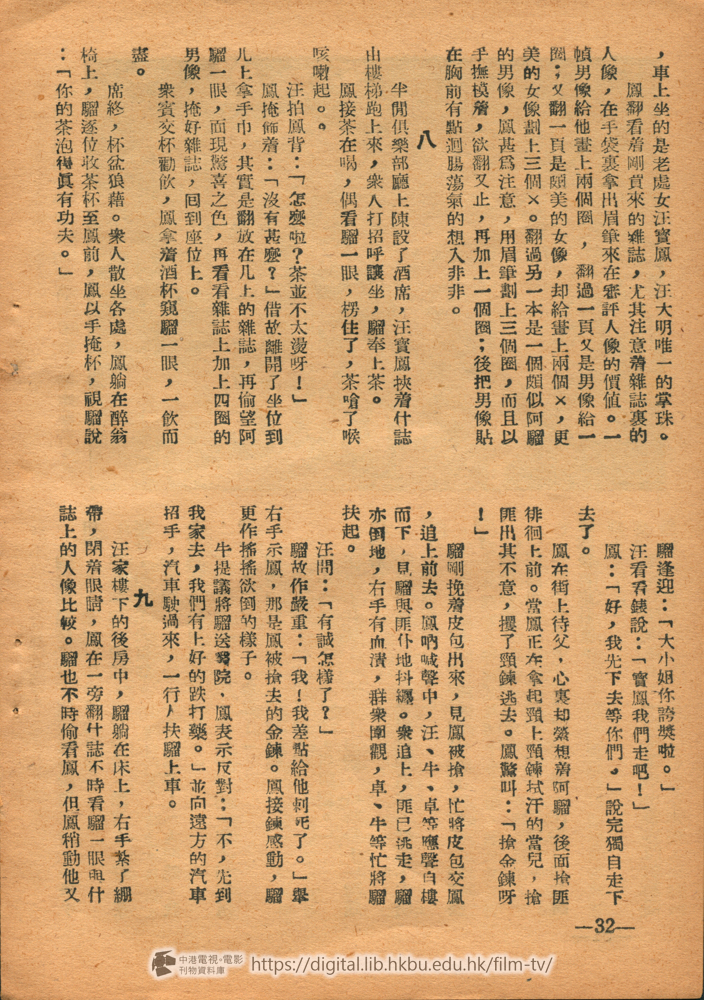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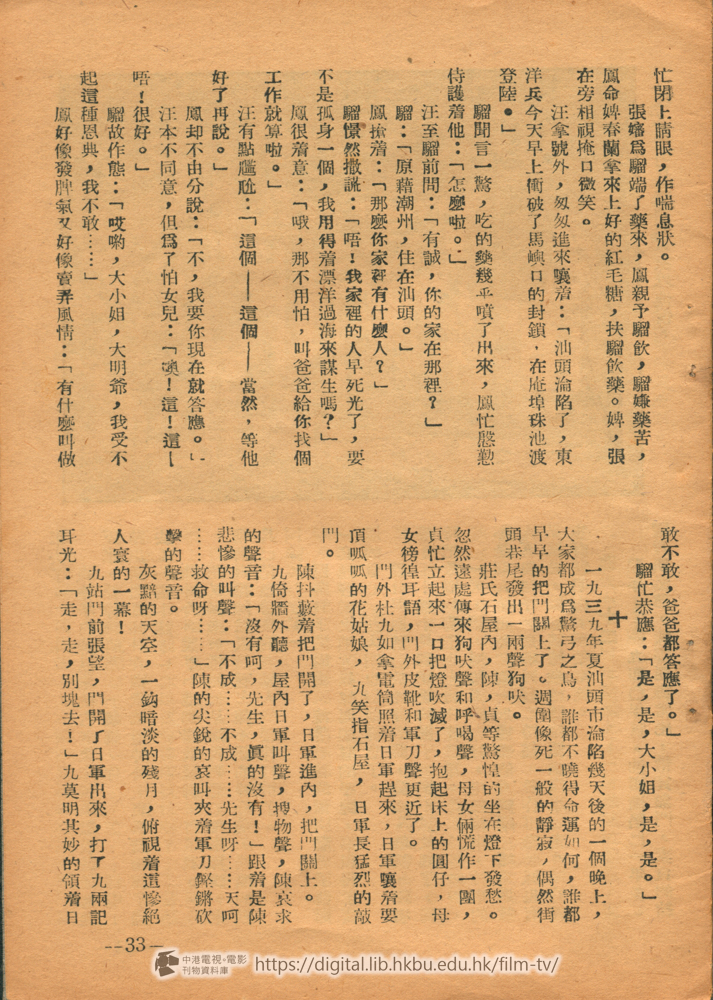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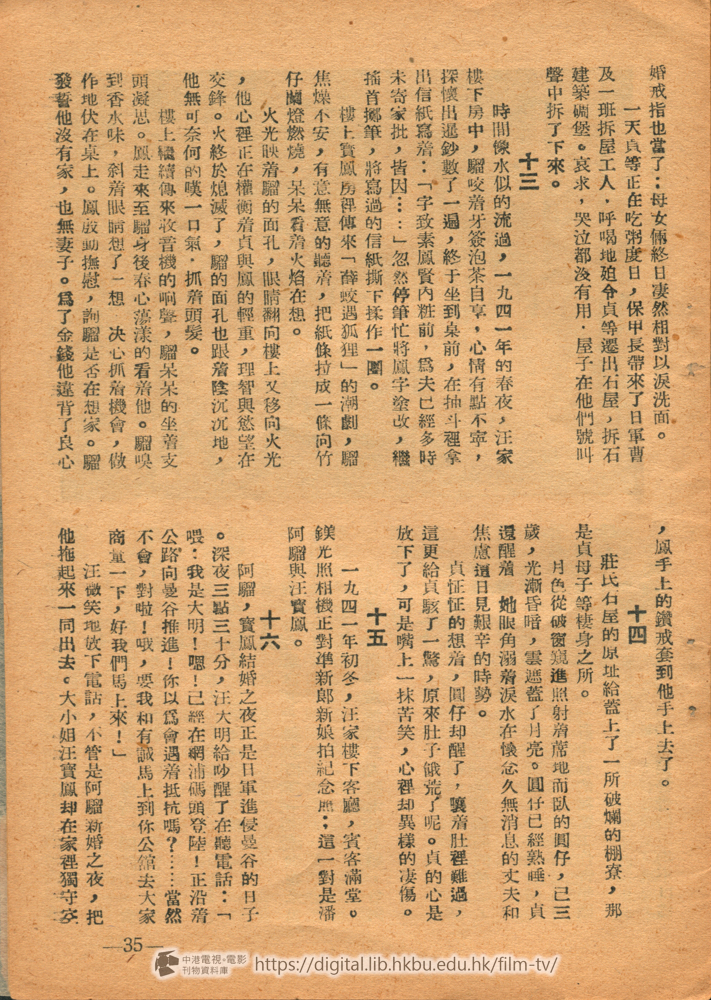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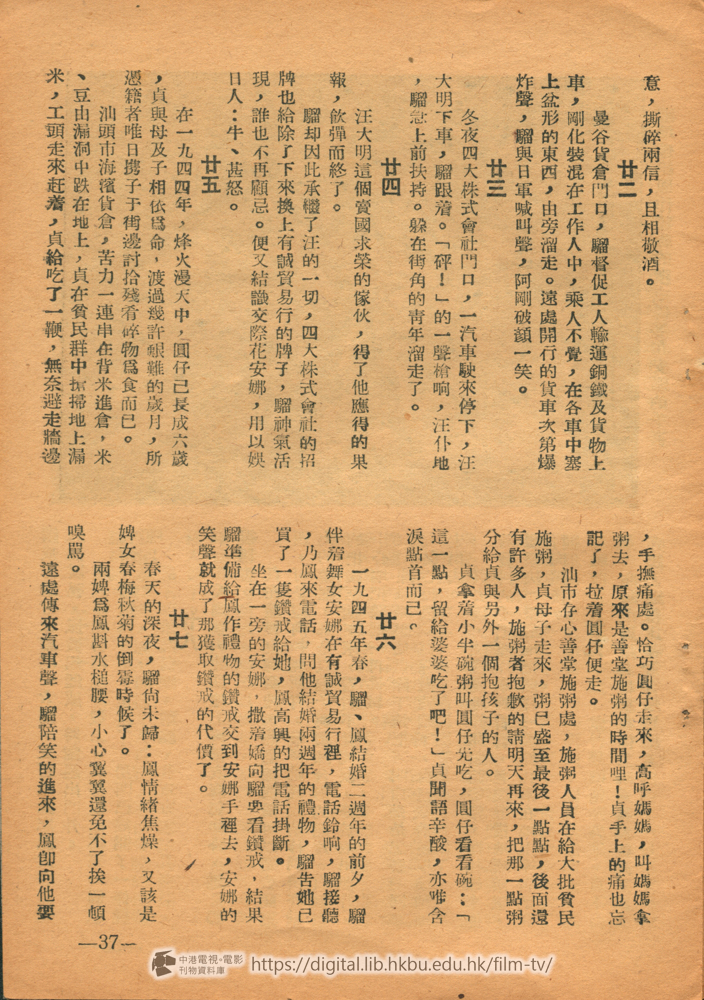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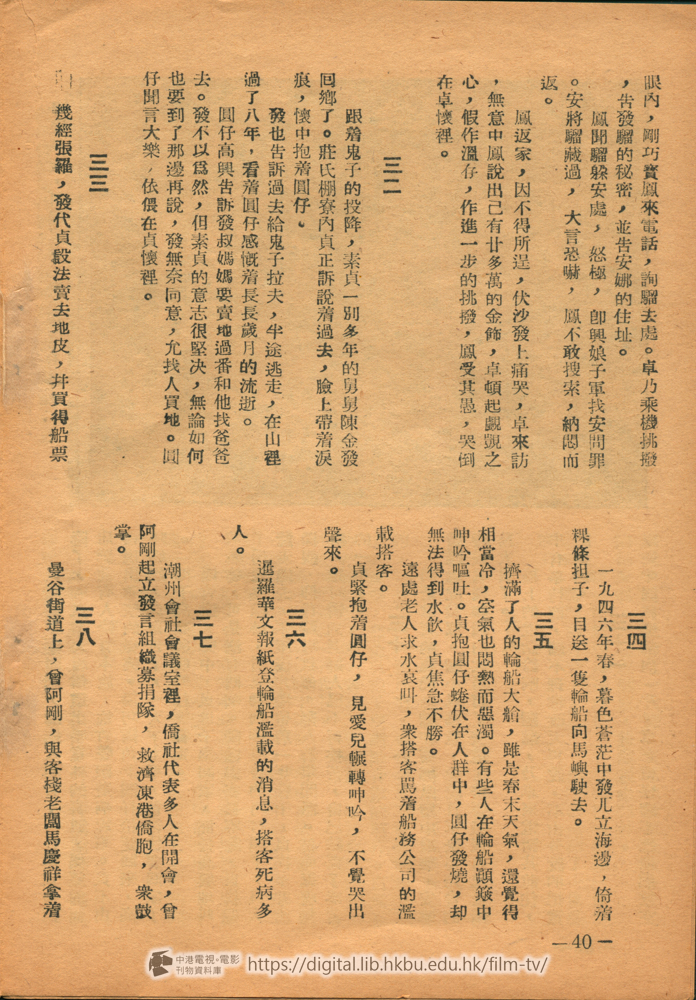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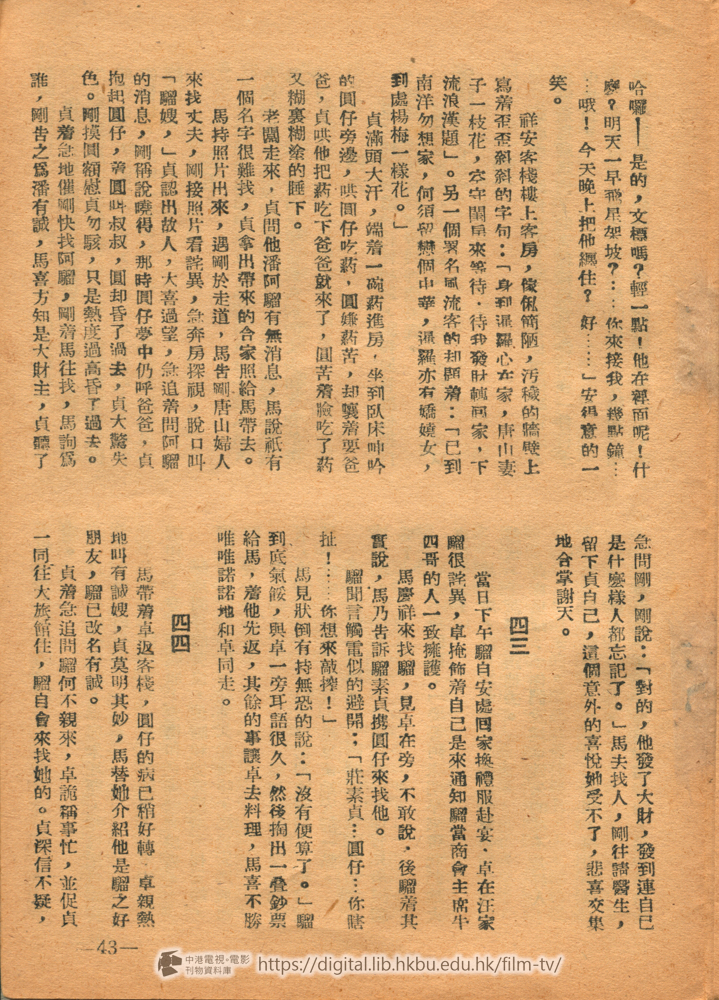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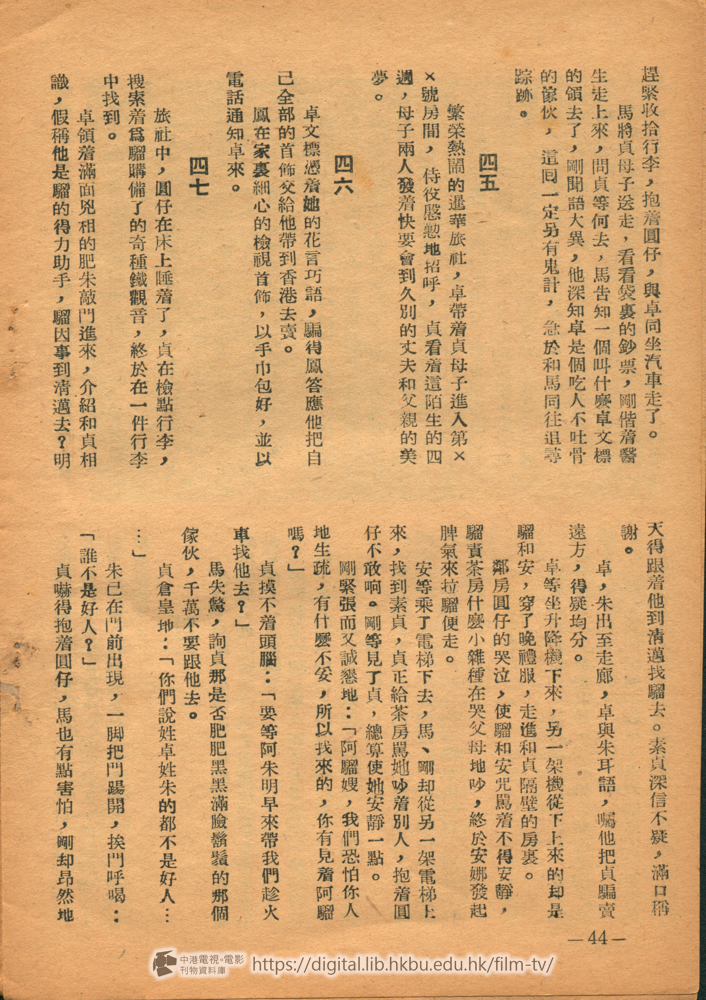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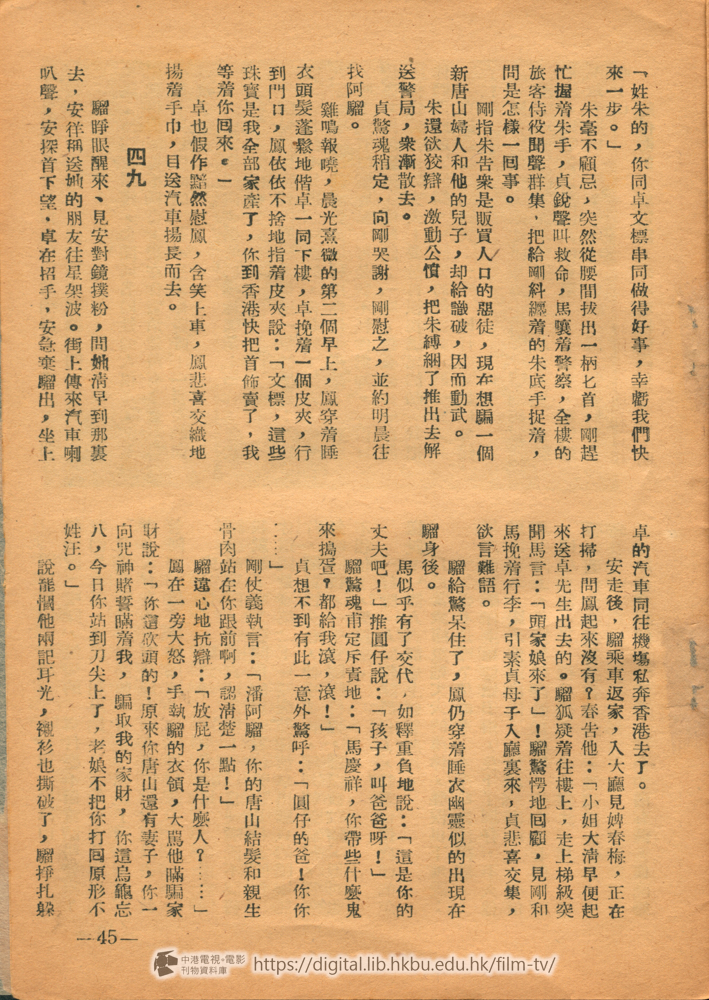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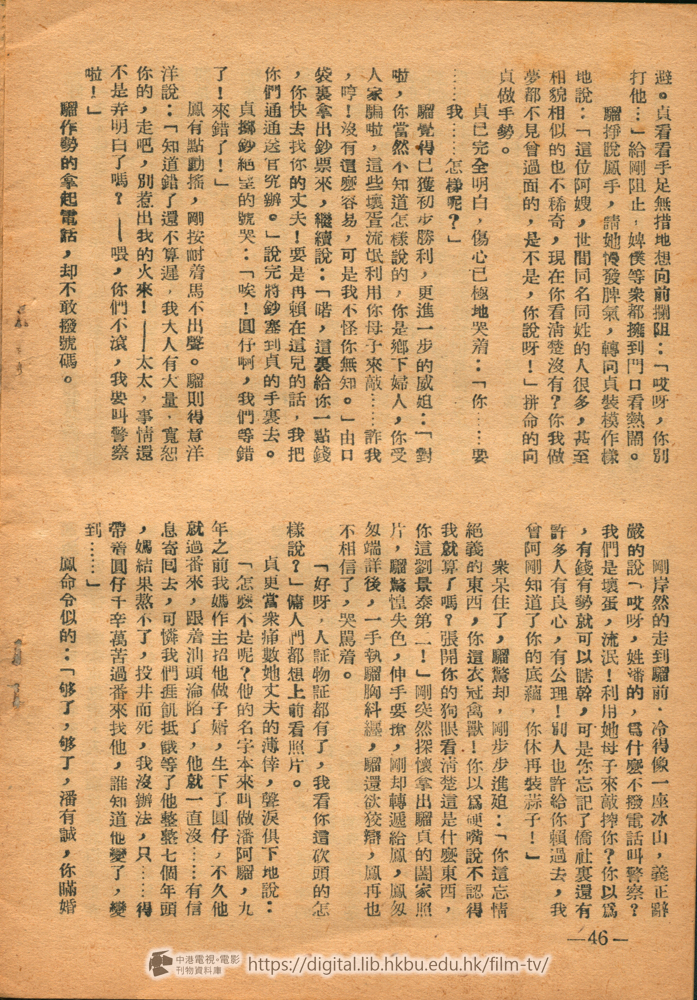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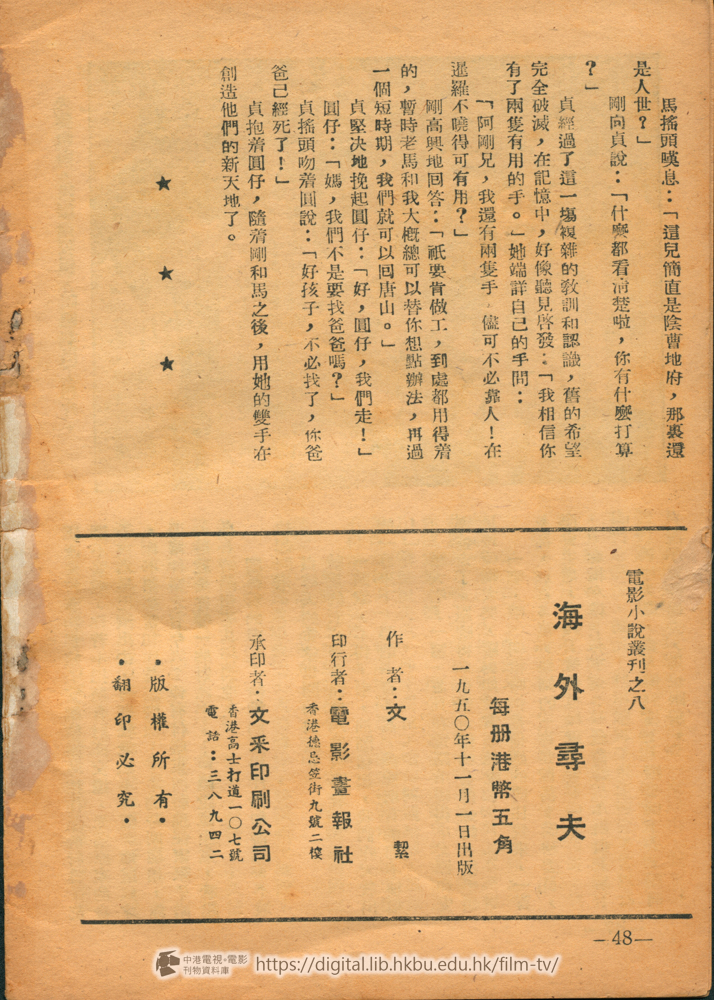
海外尋夫
・電影小說・
・文絜・
一
這故事的開始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背景在廣東的潮汕——大部份南洋華僑的故鄕。
汕頭市潮陽碼頭的附近,一家背海面路的棚屋——發記粿條店裏,老板陳金發忙着遞送棵條給在座的顧客,旁邊一個賣唱者拉着椰胡在唱潮州俚曲:「拜別母親往暹羅,要往暹羅牽豬哥,賺得錢銀多或少,寄囘唐山飼老婆……」歌聲傳到將要別離的人底耳鼓裏,起着一種不尋常的反應。
憑窗坐待送行的一對——陳金發的妹妹莊陳氏,和她的女兒莊素貞母女倆,焦急異常——
莊陳氏:「船快開啦!還去買東西……」
陳金發見狀,安慰她說:「老阿姐,船還要好一會才開的,用不着急。」邊說邊把三碗粿條放到母女們的桌子;一快三點鐘了,吃碗粿條當點心吧。」叧外一碗送給坐在旁邊的曾阿剛。——他是和素貞的丈夫潘阿騮一同「過番」的。
阿剛謙遜:「陳金發伯,你別客氣啦。」
抱着兒子的素貞,面臨着離別的時候,涕然欲泣。金發將碗捧至素貞的面前:「素貞趁熱吃吧!」
素貞抬頭,淚盈於睫毛答說:「舅舅,我吃不下。」
她媽勸慰她:「孩子,吃點吧,巳經好幾天沒正經吃東西了。」
金發也鼓勵她說:「素貞別太難過,丈夫旣然要過番努力做人,你應該高興。」
素貞淒然:「舅舅,我不是難過,我只是——」
僱客在店前叫着「來一碗粿條!」金發自去做生意,這時潘阿騮——素貞的丈夫——手挽茶葉茶具從路上吊兒郞當的走來,吹着口哨,倒不像有甚麽囘車似的。
金發看見了打招呼:「阿驟,你丈母和妻子等得很急,阿剛哥也來了一囘啦。」
阿騮進門滿不在乎示手中茶葉:「我去買幾包好的茶葉嘛,正奇種鐵觀音,聽說暹羅那邊很難買到的。」
莊陳氏站起來敎訓他:「茶可以少喝吧?路上和身稅錢倘若不够,那時候舉目無親怎麼辦呀?」
阿騮不予理會:「我有分寸的」。說完,一套很精緻的潮州茶具放在桌上。
莊陳氏不由得有點生氣:「你說你父親喝了一輩子的工夫茶,把全副家擋都泡進這茶壺裡,現在你又想來這一套嗎?」
阿騮被責廹得將小茶具放囘小箱子中。
那時,正想向阿騮討債的流氓杜九如關進店來。
九如:「好啊,潘阿騮,你們躱在這裡演長亭別,可找得我很苦!」
大家對於這位不速之客都覺得不大高興,阿騮更形不安。
莊陳氏奇怪地:「九如哥?你又找阿騮有甚麼事啊?』
九如:「什麼事。賣菜園的寫契金和貼印花一共一百弍千塊錢他還未給我。」
阿騮尷尬强笑的向着他說:「九如哥,我一到暹羅就要寄囘來給你的。」
九如:「哼,你的話倒說得輕鬆,你走了以後海濶天空敎我去問三寶公要錢嗎?騷嫂,你說是不是?」色情的眼睛瞟了素貞一眼。
阿騮急欲避開拿起行李:「我該走啦。」
九如伸手冷然:「若是不還錢,看你怎麽下船。」
莊陳氏見狀無奈,在肚兜裡拿出僅有的五十塊錢:九如哥,我這裡有五十塊錢,你先收下,餘的……
九如决絕的搖首;「少一個子也不成。」
阿剛在旁抱不平地:「九如哥,大家都是老鄰居啦,何必在阿騮兄出門的時候還逼着不放呢?」
九如不肯與論;「不干你的事,你少管!」
剛憤欲動武,卒强忍着。
素貞很難過,看看手中的結婚戒指,終於脫了下來:「媽,把這指環賣了,凑給他吧!」
九如向貞垂涎地向她伸手:「驟嫂,就給了我得啦。」
莊陳氏搶着阻攔不與。金發出向排解,在他放錢的小竹籮內檢了七十元連陳的五十元交九如。九如不得不接過來,還想囉唆,剛已捲袖握拳站起來,九如知機只得跑開。
莊陳氏不安地問金發:「阿發弟,怎可以要你代付呢?改天想辦法還你好。」
金發慰她不必介意,轉敎訓阿騮:「阿騮,祇望你順風順水到了暹羅,盡心盡力掙世界!每月寄批囘家。」
莊陳氏附和:「舅舅說的都是實話,要記住別敎素貞和我失了倚靠呵!」說完不禁老淚縱横了。
素貞竭力忍着哭不成聲,阿騮只唯唯。
遠處碼頭隱隱傳來押客招呼過番男女的聲音,一押客正從那邊走來。
金發對押客李福招呼,並爲阿騮介紹:「這位是押客李福叔。」轉向押客:「他們初出門,船上,山上都托你多多照顧。」
阿騮、莊陳氏阿剛等正拿起了行李起行,素貞抱着圓仔跟着,金發隨後,一行人走出了店門向碼頭送船去了。
二
汕頭海濱石碼頭,一隻準備開往暹羅的輪船放着汽笛,升火待發。阿福照料着過番男女沿石碼頭的石級下木艇,陳金發,莊陳氏和抱着兒子的素貞站在岸上向着阿騮叮嚀囑咐,騮頗不耐。
發等帮騮挽行李下艇,貞不由得跟上兩步,
陳招手說:「孩子,天后聖母保祐你,多給家中來信。」
騮在艇上揮手示別,貞再也忍不住哭倒在陳懷裡,發也默然神傷。
暮色蒼茫中,輪船向馬嶼口駛去,陳,貞,發等兀立江頭目送。在貞懷中的圓仔,忽然呱呱大哭,也像曉得這悲涼的別離!
三
汕頭某村莊的石屋門前,悄然無人,雙門緊閉。
素貞歡喜的寫寄阿騮的囘信,她的母親在旁囑吿她怎樣措詞,並忙着去燒香拜神。
莊陳氏取信去寄,杜九如從門隙中偷入,竊窺素貞的信。爲素貞所發現,忙說:「啊,恭喜,阿騮哥有平安信囘來啦。」
九如只是笑吟吟的看着素貞,素貞覺得不安。
九如計上心來說:「哦,什麽?祇寄十塊錢囘來!我說驟這個人太豈有此理,一點點錢就够養活家小嗎?」
貞冷淡地問:「九如叔,你來……?」
九如:「哦,哦,進來進來探望你們。」
貞更冷淡地:「不敢當!不敢當」。九拿起兩包老婆餅和一些錢遞到貞前,嘻皮笑臉,貞感到突然:「這是什麽意思?」
九如色然:「嬉嬉,我知道你們要靠阿騮寄家用是很渺茫的,暫時先拿這一百塊錢去周轉周轉吧。」 貞婉拒:「我們用不着你躭心事,我做抽紗的工錢也還够家用……」
九如涎臉:「那麼就當做我送給你買花粉吧!」
貞有怒意:「這是什麽話?」
九更放肄的摸着素貞的手:「這難道還用我說嗎?」
貞再也忍不住了:「滾出去!你這個流泯!」
九如羞怒地:「不識抬舉,等着瞧吧!」說罷失意的溜走了。
貞趕快把門關上,倚門悲憤,懊惱的眼淚滴在衣襟上。
四
一九三九年的暮春,暹羅的首府曼谷河邊,米倉林立,剛和騮雜在苦力叢中扛米。
曼谷的街頭、賭舘、和商業店舖甚麼都有。行人來往,情形熱鬧。
一羣苦力經過賭舘,有不顧而去的,也有就什食攤購食者。騮和剛在注視這初來的城市底熱鬧,騮對賭舘的興致很濃,徘徊探視不忍遽去。
五
簡陋的工人宿舍。操作了一整天疲倦不勘的工人續漸的囘來了,拭汗的,拿水布去洗澡的,抽烟的,亂糟糟地不一而足。
騮一進來把工具丟下就往牀處躺,剛脫了衣服拿起衫衭水布想去洗澡,望騮一眼發現他的神氣不對,上前撫着他的額說:「怎樣,是不是病啦?」
騮不耐煩的囘答。
躺在牀上的工人,在竊竊私議着阿騮又賭輸錢了。
剛同晴的勸慰:「騮兄,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們應該有耐心和毅力。」
騮可承勢發他那一貫的脾氣:「你少再來這一套,我聽膩了!耐心,毅力,他媽的!」我不幹啦!」
剛誠懇地:「不幹!我們是窮工人,來了就好好的幹呀!」
騮憤然:「我過番是要發財,不是做苦工來的,簡直見他媽的鬼,把我捱得不像人樣!」
剛無奈地問:「那你又想怎麽呢?」
騮一拍胸膛:「走,一發了工錢我就另找機會!你呢?」
剛想了一想搖頭:「我想我還是暫時捱下去再說吧!」
騮决然:「那麽你留你的,我决定走!」
剛有點難色,悵然無語。
六
設有賭舘的街上,行人稀少,偶然有三輪車,什貨車推過。騮慢走来,還是吊兒郞當的老樣兒,走到賭塲門口,在腰間掏出鈔票來,攷慮再三,又把錢放囘腰間離開賭舘。行得稍遠,復掏出錢來,想一想,終於禁不住誘惑,匆匆囘身走到賭舘,揭簾進去,裡面枱上都坐滿了人在賭著紙牌,派牌的見騮進去,卽讓坐下,騮乃亳不猶疑地坐,沈迷於賭桌上了。
時日不斷的消逝,潘阿騮已升爲賭場的派牌者了。
端午節日,當騮正在聚精會神倚桌派牌的時候,賭客紛紛起立敬呼,「四哥」,原來昂然而入者乃曼谷包賭者牛賽福及其助手卓文標,騮急起招呼。而騮在賭塲中渾身解數的才具,也漸爲卓等所賞識。
牛卓巡視一會,臨行前卓關照騮着他晚上到半閒俱樂部,原來他已聞說騮泡得一手好茶,牛在端午節請大頭家汪大明的客,特地着他來照顧客人。
騮聞言受寵若驚,喜不白勝的應命。
端午節的晚上半閒俱樂部內,群客畢集。騮在旁奉命唯謹,小心的端茶。本地大頭家汪大明與牛賽福,卓文標等正在談笑。
汪:「管他什麽人來,日本人來也好,我們生意得做呀!誰敢講閒呢?」
牛、卓:「大明爺說得對。」
汪:「說實在的,咱個自己人,利益不外溢,什麼都得合作,日軍來了,老辦法,一二添作五怎樣?」
衆响應:「好好!」
騮己經泡好了茶,慇懃地奉献到汪前,牛舉手相讓,各人拿起一杯慢慢的喝着。
汪舉杯淺嘗辨味,舐唇唧舌,點首:「好,茶葉好,泡的工夫更好。」
騮受讚十分高興,牛亦以爲榮:「大明爺,我今天特地去找他來侍候你的。」
汪意外好地道:「哦,年紀靑靑的,想不到有這麽一手?不容易!不容易!」
騮逢迎地:「承大明爺誇獎。」
汪放下杯:「你叫甚麼名字?」
騮小心翼翼:「小姓潘,叫阿騮。」
汪忍不住笑:「哈哈!阿騮,哈哈哈!」
騮尷尬陪着笑。
牛附和地:「我也覺得這個名字不好聽,大明爺,你給他起個名字。」
汪:「靑年人最要緊的是老實,改名有誠怎麽樣?」
騮逢迎地:「謝謝大明爺!」
汪露得意之色,並着騮再泡茶,騮應諾。
牛詢汪其千金汪寶鳳何以不來,汪答以其女購雜誌後再來赴宴。
七
曼谷石龍車路上,一輛敞蓬車由書店門前駛開,車上坐的是老處女汪寶鳳,汪大明唯一的掌珠。
鳳翻看着剛買來的雜誌,尤其注意着雜誌裏的人像,在手袋裏拿出眉筆來在審評人像的價値。一幀男像給他畫上兩個圈,翻過一頁又是男像給一圈;又翻一頁是頗美的女像,却給畫上兩個X,更美的女像劃上三個X。翻過另一本是一個頗似阿騮的男像,鳳甚爲注意,用眉筆劃上三個圈,而且以手撫模着,欲翻又止,再加上一個圈;後把男像貼在胸前有點迴腸蕩氣的想入非非。
八
半閒俱樂部廳上陳設了酒席,汪寳鳳挾着什誌由樓梯跑上來,衆人打招呼讓坐,騮奉上茶。
鳳接茶在喝,偶看騮一眼,楞住了,茶嗆了喉咳嗽。。
汪拍鳳背:「怎麽啦?茶並不太燙呀!」
鳳掩飾着:「沒有甚麽?」借故離開了坐位到儿上拿手巾,其實是翻放在几上的雜誌,再偷望阿騮一眼,面現驚喜之色,再看看雜誌上加上四圈的男像,掩好雜誌,囘到座位上。
衆賓交杯勸飲,鳳拿着酒杯窺騮一眼,一飮而盡。
席終,杯盆狼藉。衆人散坐各處,鳳躺在醉翁椅上,騮逐位收茶杯至鳳前,鳳以手掩杯,視騮說:「你的茶泡得眞有功夫。」
騮逢迎:「大小姐你誇獎啦。」
汪看看錶說:「寶鳳我們走吧!」
鳳:「好,我先下去等你們。」說完獨自走下去了。
鳳在街上待父,心裏却縈想着阿騮,後面搶匪徘徊上前。常鳳正在拿起頸上頸鍊拭汗的當兒,搶匪出其不意,攫了頸鍊逃去。鳳驚叫:「搶金鍊呀!」
騮剛挽着皮包出來,見鳳被搶,忙將皮包交鳳,追上前去。鳳吶喊聲中,汪、牛、卓等應聲自樓而下,見騮與匪仆地抖纏。衆追上,匪已逃走,騮亦倒地,右手有血漬,群衆圍觀,卓、牛等忙將騮扶起。
汪問:「有誠怎樣了?」
騮故作嚴重:「我!我差站給他刺死了。」舉右手示鳳,那是鳳被搶去的金鍊。鳳接鍊感動,騮更作搖搖欲倒的樣子。
牛提議將騮送醫院,鳳表示反對:「不,先到我家去,我們有上好的跌打藥。」並向遠方的汽車招手,汽車駛過來,一行人扶騮上車。
九
汪家樓下的後房中,騮躺在床上,右手紮了綳帶,閉着眼睛,鳳在一旁翻什誌不時看騮一眼與什誌上的人像比較。騮也不時偷看鳳,但鳳稍動他又忙閉上睛眼,作喘息狀。
張嬸爲騮端了藥來,鳳親予騮飮,騮嫌藥苦,鳳命婢春蘭拿來上好的紅毛糖,扶騮飲藥。婢,張在旁相視掩口微笑。
汪拿號外,匆匆進來嚷着:「汕頭淪陷了,東洋兵今天早上衝破了馬嶼口的封鎖,在庵埠珠池渡登陸。」
騮聞言一驚,吃的藥幾乎噴了用來,鳳慇懃侍護着他:「怎麼啦。」
汪至騮前問:「有誠,你的家在那裡?」
騮:「原藉潮州,住在汕頭。」
鳳搶着:「那麽你家裡有什麽人?」
騮憬然撒謊:「唔,我家裡的人早死光了,要不是孤身一個,我用得着漂洋過海來謀生嗎?」
鳳很着意:「哦,那不用怕,叫爸爸給你找個工作就算啦。」
汪有點尷尬:「這個——這個——當然,等他好了再說。」
鳳却不由分說:「不,我要你現在就答應。」
汪本不同意,但爲了怕女兒:「噢!這!這—唔!很好。」
騮故作態:「哎喲,大小姐,大明爺,我受不起這種恩典,我不敢……」
鳳好像發脾氣又好像賣弄風情:「有什麽叫做敢不敢,爸爸都答應了。」
騮忙恭應:「是,是,大小姐,是,是。」
十
一九三九年夏汕頭市淪陷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大家都成爲驚弓之鳥,誰都不曉得命運如何,誰都早早的把門關上了。週圍像死一般的靜寂,偶然街頭巷尾發出一兩聲狗吠。
莊氏石屋內,陳,貞等驚惶的坐在燈下發愁。忽然遠處傳來狗吠聲和呼喝聲,母女倆慌作一團,貞忙立起來一口把燈吹滅了,抱起床上的圓仔,母女彷徨耳語,門外皮靴和軍刀聲更近了。
門外杜九如拿電筒照着日軍趕來,日軍嚷着要頂呱呱的花姑娘,九笑指石屋,日軍長猛烈的敲門。
陳抖藪着把門開了,日軍進內,把門關上。
九倚牆外聽,屋內日軍叫聲,搜物聲,陳哀求的聲音:「沒有呵,先生,眞的沒有!」跟着是陳悲慘的叫聲:「不成……不成……先生呀……天呵……救命呀……」陳的尖銳的哀叫夾着軍刀鏗鏘砍擊的聲音。
灰黯的天空,一鈎暗淡的殘月,俯視着這慘絕人寰的一幕!
九站門前張望,門開了日軍出來,打了九兩記耳光:「走,走,別塊去!」九莫明其妙的領着日軍去了。
貞抱子自陳臥室的古老大床頂上戰戰兢兢地爬下來,悖悸地叫着:「媽媽,你……怎……樣啦!踏出房門見陳仆在廳堂牆邊呻吟,貞震驚地撲了過去:「媽!媽!」
陳呻吟訴說:「他們踢我幾脚,打了我。」
門又漸漸被推開,是鄰人們瑟縮地來探視。衆帮着貞把陳抬入房裡,陳不斷的呻吟着,残酷的獸兵已把這善良的老婦人的腰骨打折了。
十一
跟着日子的過去,流落曼谷的潘阿騮憑了他那一套逢迎,吹拍,奴隸底馴服的手腕,不但得了寳鳳的歡心,汪大明也對他滿意了。
騮日與鳳偕遊於曼谷名勝,公園、戲院、舞場等……無不見到雙雙的影子,樂不思故鄉了,同時把故鄕的妻子也忘得一乾二净。
一天,驟,鳳遊玉怫寺歸,坐三輪車,拉車的不是別人,正是和騮一同過番的曾阿剛,剛重遇故人喜與招呼,那曉得騮竟愕然,詐作不識,鳳也有點疑惑,騮恐被她識破轉拉鳳坐汽車急走。剛心裡也有點明白,不禁冷笑。
十二
翌年——一九四〇年秋,汕頭淪陷已一年多。騮音訊渺然,陳等窮盡當絕,借貸無門,素貞的結婚戒指也當了:母女倆終日凄然相對以淚洗面。
一天貞等正在吃粥度日,保甲長帶來了日軍曹及一班拆屋工人,呼喝地廹令貞等遷出石屋,拆石建築碉堡。哀求,哭泣都没有用,屋子在他們號叫聲中拆了下來。
十三
時間像水似的流過,一九四一年的春夜,汪家樓下房中,騮咬着牙簽泡茶自享,心情有點不寧,探懷出暹鈔數了一遍,終于坐到桌前,在抽斗裡拿出信紙寫着:「字致素鳳賢內粧前,爲夫已經多時未寄家批,皆因……」忽然停筆忙將鳳字塗改,繼搖首擲筆,將寫過的信紙撕下揉作一團。
樓上寶鳳房裡傳來「薛蛟遇孤狸」的潮劇,騮焦燥小安,有意無意的聽著,把紙條拉成一條向竹仔闌燈燃燒,呆呆看著火焰在想。
火光映着騮的面孔,眼睛翻向樓上又移向火光,他心裡正在權衡着貞與鳳的輕重,理智與慾望在交鋒。火終於熄滅了,騮的面孔也跟着陰沉沉地,他無可奈何的嘆一口氣,抓著頭髮。
樓上繼續傳來收音機的响聲,騮呆呆的坐着支頭凝思。鳳走來至騮身後春心蕩漾的看着他。騮嗅到香水味,斜着眼睛想了一想,决心抓着機會,做作地伏在桌上。鳳殷勤撫慰,詢騮是否在想家。驟發誓他沒有家,也無妻子。爲了金錢他違背了良心,鳳手上的鑽戒套到他手上去了。
十四
莊氏石屋的原址給蓋上了一所破爛的棚寮,那是貞母子等棲身之所。
月色從破窗窺進照射着蓆地而臥的圓仔,已三歲,光漸昏暗,雲遮蓋了月亮。圓仔已經熟睡,貞還醒着,她眼角溺着淚水在懷念久無消息的丈夫和焦慮這日見艱辛的時勢。
貞怔怔的想着,圓仔却醒了,嚷着肚裡難過,這更給貞駭了一驚,原來肚子餓荒了呢。貞的心是放下了,可是嘴上一抹苦笑,心裡却異樣的凄傷。
十五
一九四一年初冬,汪家樓下客廳,賓客滿堂。鎂光照相機正對準新郞新娘拍紀念照;這一對是潘阿騮與汪寶鳳。
十六
阿騮,寳鳳結婚之夜正是日軍進侵曼谷的日子。深夜三點三十分,汪大明給吵醒了在聽電話:「喂:我是大明!嗯!己經在網浦碼頭登陸!正沿着公路向曼谷推進!你以為會遇着抵抗嗎?……當然不會,對啦!哦,要我和有福馬上到你公舘去大家商量一下,好我們馬上來!」
汪微笑地放下電話,不管是阿騮新婚之夜,把他拖起來一同出去。大小姐汪寳鳳却在家裡獨守空房,大發脾氣怨罵爸爸的不懂事。
十七
汪大明的四大株式會社是「應時」開設了。會議桌上放着「徵集米粮計劃」「集中五金辦法」…一大堆,汪、卓、牛,騮正陪着日人野、川會議,川、野分拍汪,牛的肩,汪牛詔笑點首,取計劃書分授騮,卓,兩人足恭收下,諾諾答應。」
十八
堆積如山的米倉中,騮在指揮一班流氓在米包上用墨油擦上日本字。
十九
曼谷碼頭騮指揮著流氓三人運木材上船,曾阿剛在旁窺伺。
二十
曼谷淪陷已一年,熱愛祖國的靑年己組成了堅强的團體,來打擊敵人的野心,懲戒無恥的流氓,這個團體的領導者是曾阿剛。
秘密工作室中,桌上擺着致汪及牛的警吿信,署名的是中暹反軸心執行委員會。剛堅决的立桌前,慷慨激昂的在致詞,一群中暹的秘密工作靑年圍聽,大家都動容鼓掌。
廿一
四大株式社內,汪,牛同接警吿信,均不以爲意,撕碎兩信,且相敬酒。
廿二
曼谷貨倉門口,騮督促工人輸運銅鐵及貨物上車,剛化裝混在工作人中,乘人不覺,在各車中塞上盆形的東西,由旁溜走。遠處開行的貨車次第爆炸聲,騮與日軍喊叫聲,阿剛破顏一笑。
廿三
冬夜四大株式會社門口,一汽車駛來停下,汪大明下車,騮跟着。「砰!」的一聲槍响,汪仆地,騮急上前扶持。躱在街角的靑年溜走了。
廿四
汪大明這個賣國求榮的傢伙,得了他應得的果報,飮彈而終了。
騮却因此承繼了汪的一切,四大株式會社的招牌也給除了下來換上有誠貿易行的牌子,騮神氣活現,誰也不再顧忌。便又結識交際花安娜,用以娛日人:牛、甚怒。
廿五
在一九四四年,烽火漫天中,圓仔己長成六歲,貞與母及子相依爲命,渡過幾許艱難的歲月,所憑籍者唯日携子于街邊討拾殘肴碎物爲食而已。
汕頭市海濱貨倉,苦力一連串在背米進倉,米、豆由漏洞中跌在地上,貞在貧民群中搶掃地上漏米,工頭走來赶着,貞給吃了一鞭,無奈避走牆邊,手撫痛處。恰巧圓仔走來,高呼媽媽,叫媽媽拿粥去,原來是善堂施粥的時間哩!貞手上的痛也忘記了,拉着圓仔便走。
汕市存心善堂施粥處,施粥人員在給大批貧民施粥,貞母子走來,粥巳盛至最後一點點,後面還有許多人,施粥者抱歉的請明天再來,把那一點粥分給貞與另外一個抱孩子的人。
貞拿着小半碗粥叫圓仔先吃,圓仔看看碗:「這一點,留給婆婆吃了吧!」貞聞語辛酸,亦唯合淚點首而己。
廿六
一九四五年春,騮、鳳結婚二週年的前夕,騮伴着舞女安娜在有誠貿易行裡,電話鈴晌,騮接聽,乃鳳來電話,問他結婚兩週年的禮物,騮吿她已買了一隻鑽戒給她,鳳高興的把電話掛斷。
坐在一旁的安娜,撒着嬌向騮要看鑽戒,結果騮準備給鳳作禮物的鑽戒交到安娜手裡去,安娜的笑聲就成了那獲取鑽戒的代價了。
廿七
春天的深夜,騮尙未歸:鳳情緖焦燥,又該是婢女春梅秋菊的倒霉時候了。
兩婢爲鳳斟水槌腰,小心翼翼還免不了挨一頓嗅駡。
遠處傳來汽車聲,騮陪笑的進來,鳳卽向他要鑽戒,這可使騮吃一大驚,支吾地說忘記放在公司的抽屜裡,鳳發起雌威,將騮趕出門外。
騮被逐無聊地坐沙發上,突然後面擲來一個軟枕頭,騮驚囘首望,失笑,房門己經開了一條縫哩!
廿八
莊氏棚寮,陳臥地上擁破衣麻包呻吟,她痛得很利害。
貞在屋裡東翻西搜,焦急地找着可以變賣的東西,可是屋內一無所有,最後她底眼睛移到掛在壁上的鏡框,那是貞抱子與騮陳合影的照片。貞無奈的把鏡框摘下來,看看不覺流淚,終於取出照片,小心地把鏡框一再拂拭。
陳睜開眼見貞除下鏡框,明白那是怎麼一囘事,傷心得很。貞强慰陳躺下,自己拿着鏡框悄悄地走出去。
貞去後,陳慢慢地睜開眼睛望望,掙扎起來伸着發抖的手把照片拿到看看,老淚縱橫地嘆着氣,繼堅决而憤怒地把照片一丟掙扎着在地上辛苦的爬行向屋後。
廿九
汕頭市馬路上報童在街上叫着特別號外,路人奔起,顯得比尋常有點異樣。
貞剛買了藥囘來,聽途人相吿:「日軍宣佈投降了,」貞不大相信這出乎意外的喜訊,偶望前面店舖前有人降日本旗,炮竹聲跟着响起來。貞不由得現出希望的微笑。凑巧街角上圓仔拾荒囘來,髙呼媽媽,貞喜吿子,「天下太平,爸爸快要囘家了。」母子高高興興的往家裡走。
爆竹連大聲中,貞母子跑囘家,圓仔高興地叫着婆婆,可是沒有囘响。陳臥處衣衫零亂,貞找遍了房也沒踪跡,看見通到棚寮後的門打開了,貞大驚走過去,茅屋後井邊留着一隻鞋子,貞撲至井沿探視,仰首驚叫救命。鄰人群集問訊。然而返魂無術,這可憐的老婦人己不再挨苦,自己結束了凄苦的一生了。
三十
同是秋天的夜晚,騮在安娜臥室中取樂,安娜妨雌老虎發威。騮不以爲意,並說日軍快要垮台的時候,便和國內大員打了交道,快要發表自己當僑務大員了。
檯上的電話鈴响,騮聽,乃卓來電請其前往,牛有事待商,騮不理推改天再說,不由分說的把電話掛斷。
三十一
半間俱樂部内,牛、卓正憤恨騮不把他們放在眼內,剛巧寶鳳來電話,詢騮去處。卓乃乘機挑撥,吿發騮的秘密,並吿安娜的住址。
鳳聞騮躱安處,怒極;卽興娘子軍找安問罪。安將騮蔵過,大言恐嚇,鳳不敢搜索,納悶而返。
鳳返家,因不得所逞,伏沙發上痛哭,卓來訪,無意中鳳說出己有廿多萬的金飾,卓頓起覷覬之心,假作溫存,作進一步的挑撥,鳳受其懸,哭倒在卓懷裡。
三二
跟着鬼子的投降,素貞一別多年的舅舅陳金發囘鄉了。莊氏棚寮内貞正訴說着過去,臉上帶着淚痕,懷中抱着圓仔。
發也吿訴過去給鬼子拉夫,半途逃走,在山裡過了八年,看着圓仔感慨着長長歲月的流逝。
圓仔高興吿訴發叔媽媽要賣地過番和他找爸爸去。發不以爲然,但素貞的意志很堅决,無論如何也要到了那邊再說,發無奈同意,允找人買地。圓仔聞言大樂,依偎在貞懷裡。
三三
幾經張羅,發代貞設法賣去地皮,幷買得船票
三四
一九四六年春,暮色蒼茫中發兀立海邊,倚着粿條担子,目送一隻輪船向馬嶼駛去。
三五
擠滿了人的輪船大艙,雖是春末天氣,還覺得相當冷,空氣也悶熱而惡濁。有些人在輪船顚簸中呻吟嘔吐。貞抱圓仔蜷伏在人群中,圓仔發燒,却無法得到水飮,貞焦急不勝。
遠處老人求水哀叫,衆搭客罵着船務公司的濫載搭客。
貞緊抱着圓仔,見愛兒輾轉呻吟,不覺哭出聲來。
三六
暹羅華文報紙登輪船濫載的消息,搭客死病多人。
三七
潮州會社會議室裡,僑社代表多人在開會,曾阿剛起立發言組織募捐隊,救濟凍港僑胞,衆鼓掌。
三八
曼谷街道上,曾阿剛,與客棧老闆馬慶祥拿着捐册向行人募捐,人多解囊。
三九
暹華大旅社中騮和安娜坐房中,侍者來報,「救濟怡利南凍港僑胞請其捐助,」騮怒斥侍者,並駡此舉爲假公濟私。剛在房外聽了,踢門進來,責騮「幾年來為日人走狗,尙詆人假公濟私。」騮見剛駭極轉圓,願捐款十元。剛憤睜怒目,不要其髒錢,聲言後必有淸算他的一天,偕衆走了。
四十
暹華文報載衞生廳准許怡利南輪船乘客登岸暫住XX米倉檢疾。
暫作被凍港旅客收容處的XX米倉,外面空地上豎了竹竿圍了繩子,一些難胞男女孩童在空地上徘徊,門前插着報德善堂旗幟。
汽車聲响廣肇醫院救濟車停善堂門前,剛與僑社代表多人下車,代表們各處巡視,剛與多人則從貨車上搬下救濟品來預備分發,馬慶祥和客棧夥伴前來和剛招呼。
這時貞氣喘喘的由倉內跑出來,哀叫着:「有醫生嗎?有醫生嗎?」繼抬首見看護車與女護士,急撲上去拉着護士:「姑娘,救命啊,我的孩子病得很利害啊!」急不及待的匆匆往倉裏走。
剛在一旁憤駡輪船公司之貪污,不顧同胞死活,馬也搖首嘆息不已。
貞領護士入米倉內,男女搭客均蓆地坐臥,枯瘠疲乏不堪。圓仔臥地已染熱病,輾轉呻吟,護士加以診視,知熱度甚高,替他注射退熱針,圓仔在昏迷中頻呼「爸爸」,貞伏圓旁,憂急不己。
剛和馬等拿着救濟品前來逐人分派,剛派的是另一邊,與貞相左。
馬派至貞前問他有無人來相接,貞吿馬來找人,吿夫名潘阿騮,馬覺此君並不陌生,允她代找,貞喜謝之。
四一
有誠貿易行經理室中,騮接牛來電話吿國內內戰將起,黃金一定看漲。騮興高采烈地向坐在一旁的卓文標說:「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决定儘量拋空汕匯,大量吸進黃金雙管齊下,事不宜遲。」卓也像替他高興,心裡却是陰謀的笑着。
四二
安娜臥室內,騮與安正在厮戀,騮吿安自己的投機,三天內家財要加個壹倍,安假意戰懃。
婢來叩門請安接聽電話,安至甬道接電話:「哈曬——是的,文標嗎?輕一點!他在裡面呢!什麽?明天一早飛星架坡?……你來接我,幾點鐘……哦!今天晚上把他纏住?好……」安得意的一笑。
祥安客棧樓上客房,傢俬簡陋,污穢的牆壁上寫着歪歪斜斜的字句:「身到暹羅心在家,唐山妻子一枝花,空守閨房來等待,待我發財轉囘家,下流浪漢題」。另一個署名風流客的却題着:「已到南洋勿想家,何須留戀個中華,暹羅亦有嬌姨女,到處楊梅一樣花。」
貞滿頭大汗,端着一碗药進房,坐到臥床呻吟的圓仔旁邊,哄圓仔吃葯,圓嫌葯苦,却嚷着要爸爸,貞哄他把葯吃下爸爸就來了,圓苦着臉吃了葯又糊裏糊塗的睡下。
老闆走來,貞問他潘阿騮有無消息,馬說祇有一個名字很難找,貞拿出帶来的合家照給馬帶去。
馬持照片出來,遇剛於走道,馬吿剛唐山婦人來找丈夫,剛接照片看詫異,急奔房探視,脫口叫「騮嫂,」貞認出故人,大喜過望,急追着問阿騮的消息,剛稱說曉得,那時圓仔夢中仍呼爸爸,貞抱起圓仔,着圓叫叔叔,圓却昏了過去,貞大驚失色。剛摸圓額慰貞勿駭,只是熱度過高昏了過去。
貞着急地催剛快找阿騮,剛着馬往找,馬詢爲誰,剛吿之為潘有誠,馬喜方知是大財主,貞聽了急問剛,剛說:「對的,他發了大財,發到連自已是什麼樣人都忘記了。」馬去找人,剛往請醫生,留下貞自己,這個意外的喜悅她受不了,悲喜交集地合掌謝天。
四三
當日下午騮自安處囘家換禮服赴宴,卓在汪家騮很詫異,卓掩飾着自己是來通知騮當商會主席牛四哥的人一致擁護。
馬慶祥來找騮,見卓在旁,不敢說,後騮着其實說,馬乃告訴騮素貞携圓仔來找他。
騮聞言觸電似的避開:「莊素貞…圓仔…你瞎扯!……你想來敲搾!」
馬見狀倒有持無恐的說:「沒有便算了。」騮到底氣餒,與卓一旁耳語很久,然後掏出一叠鈔票給馬,着他先返,其餘的事讓卓去料理,馬喜不勝唯唯諾諾地和卓同走。
四四
馬帶着卓返客棧,圓仔的病已稍好轉,卓親熱地叫有誠嫂,貞莫明其妙,馬替她介紹他是驟之好朋友,驟已改名有誠。
貞着急追問騮何不親來,卓詭稱事忙,並促貞一同一往大旅館住,騮自會來找她的。貞深信不疑,趕緊收拾行李,抱着圓仔,與卓同坐汽車走了。
馬將貞母子送走,看看袋裏的鈔票,剛偕着醫生走上來,問貞等何去,馬吿知一個叫什麽卓文標的領去了,剛聞語大異,他深知卓是個吃人不吐骨的傢伙,這囘一定另有鬼計,急於和馬同往追尋踪跡。
四五
繁榮熱鬧的暹華旅社,卓帶着貞母子進入第XX號房間,侍役慇熱地招呼,貞看着這陌生的四週,母子兩人發着快要會到久別的丈夫和父親的美夢。
四六
卓文標憑着她的花言巧語,騙得鳳答應他把自己全部的首飾交給他帶到香港去賣。
鳳在家裏細心的檢視首飾,以手巾包好,並以電話通知卓來。
四七
旅社中,圓仔在床上睡着了,貞在檢點行李,搜索着爲騮購備了的奇種鐵觀音,終於在一件行李中找到。
卓領着滿面兇相的肥朱敲門進來,介紹和貞相識,假稱他是騮的得力助手,騮因事到清邁去?明天得跟着他到清邁找騮去。素貞深信不疑,滿口稱謝。
卓,朱出至走廊,卓與朱耳語,囑他把貞騙賣遠方,得疑均分。
卓等坐升降機下來,另一架機從下上來的却是騮和安,穿了晚禮服,走進和貞隔壁的房裏。
鄰房圓仔的哭泣,使騮和安咒駡着不得安靜,騮責茶房什麽小雜種在哭父母地吵,終於安娜發起脾氣來拉騮便走。
安等乘了電梯下去,馬、剛却從另一架電梯上來,找到素貞,貞正給茶房駡她吵着別人,抱着圓仔不敢响。剛等見了貞,總算使她安靜一點。
剛緊張而又誠懇地:「阿騮嫂,我們恐怕你人地生疏,有什麽不妥,所以我來的,你有見着阿騮嗎?」
貞摸不着頭腦:「要等阿朱明早來帶我們趁火車找他去?」
馬失驚,詢貞那是否肥肥黑黑滿瞼鬍鬚的那個傢伙,千萬不要跟他去。
貞倉皇地:「你們說姓卓姓朱的都不是好人……」
朱已在門前出現,一脚把門踢開,挨門呼喝:「誰不是好人?」
貞嚇得抱着圓仔,馬也有點害怕,剛却昂然地「姓朱的,你同卓文標串同做得好事,幸虧我們快來一歩。」
朱毫不顧忌,突然從腰間拔出一柄匕首,剛趕忙握着朱手,貞銳聲叫救命,馬嚷着警察,全樓的旅客侍役聞聲群集,把給剛紏纏着的朱底手捉着,問是怎樣一囘事。
剛指朱吿衆是販買人口的惡徒,現在想騙一個新唐山婦人和他的兒子,却給識破,因而動武。
朱還欲狡辯,激動公憤,把朱縛綑了推出去解送警局,衆漸散去。
貞驚魂稍定,向剛哭謝,剛慰之,並約明晨往找阿騮。
雞鳴報曉,晨光熹微的第二個早上,鳳穿着睡衣頭髮蓬鬆地偕卓一同下樓,卓挽着一個皮夾,行到門口,鳳依依不捨地指着皮夾說:「文標,這些珠寳是我全部家產了,你到香港快把首飾賣了,我等着你囘來。」
卓也假作黯然慰鳳,含笑上車,鳳悲喜交織地揚着手巾,目送汽車揚長而去。
四九
騮睜眼醒來、見安對鏡撲粉,問她淸早到那裏去,安徉稱送她的朋友往星架波。街上傳來汽車喇叭聲,安探首下望,卓在招手,安急棄騮出,坐上卓的汽車同往機塲私奔香港去了。
安走後,騮乘車返家,入大廳見婢春梅,正在打掃,問鳳起來沒有?春吿他:「小姐大淸早便起來送卓先生出去的。騮狐疑着往樓上,走上梯級突聞馬言:「頭家娘來了」!騮驚愕地囘顧,見剛和馬挽着行李,引素貞母子入廳裏來,貞悲喜交集,欲言難語。
騮給驚呆住了,鳳仍穿著睡衣幽靈似的出現在騮身後。
馬似乎有了交代,如釋重負地說:「這是你的丈夫吧!」推圓仔說:「孩子,叫爸爸呀!」
騷驚魂甫定斥責地:「馬慶祥,你帶些什麼鬼來搗疍?都給我滾,滾!」
貞想不到有此一意外驚呼:「圓仔的爸!你你……」
剛仗義執言:「潘阿騮,你的唐山結髮和親生骨肉站在你跟前啊,認淸楚一點!」
騮違心地抗辯:「放屁,你是什麽人?……」
鳳在一旁大怒,手執騮的衣領,大罵他瞞騙家財說:「你這砍頭的!原來你唐山還有妻子,你一向咒神賭誓瞞着我,騙取我的家財,你這烏龜忘八,今日你站到刀尖上了,老娘不把你打囘原形不姓汪。」
說罷慖他兩記耳光,襯衫也撕破了,騮掙扎躲避。貞看看手足無措地想向前攔阻:「哎呀,你別打他…」給剛阻止,婢僕等衆都擁到門口看熱鬧。
騮掙脫鳳手,請她慢發脾氣,轉向貞裝模作樣地說:「這位阿嫂,世間同名同姓的人很多,甚至相貌相似的也不稀奇,現在你看淸楚沒有?你我做夢都不見曾過面的,是不是,你說呀!」拼命的向貞做手勢。
貞已完全明白,傷心已極地哭着:「你……要……我……怎样呢?」
騮覺得已獲初步勝利,更進一步的威廹:「對啦,你當然不知道怎樣說的,你是鄕下婦人,你受人家騙啦,這些壞疍流氓利用你母子來敲.……詐我,哼!沒有這麽容易,可是我不怪你無知。」由口袋裏拿出鈔票來,繼續說:「喏,這裏給你一點錢,你快去找你的丈夫!要是再賴在這兒的話,我把你們通通送官究辦。」說完將鈔塞到貞的手裏去。
貞擲鈔絶望的號哭:「唉!圓仔啊,我們等錯了!來錯了!」
鳳有點動搖,剛按耐着馬不出聲。騮則得意洋洋說:「知道錯了還不算遲,我大人有大量,寬恕你的,走吧,別惹出我的火來!——太太,事情還不是弄明白了嗎?——喂,你們不滾,我要叫警察啦!」
騮作勢的拿起電話,却不敢撥號碼。
剛岸然的走到騮前,冷得像一座冰山,義正辭嚴的說「哎呀,姓潘的,為什麼不撥電話叫警察?我們是壞蛋,流泯!利用她母子來敲搾你?你以爲,有錢有勢就可以瞎幹,可是你忘記了僑社裏還有許多人有良心,有公理!別人也許給你賴過去,我曾阿剛知道了你的底蘊,你休再裝蒜子!」
衆呆住了,騮驚却,剛步步進廹:「你這忘情絕義的東西,你這衣冠禽獸!你以爲硬嘴說不認得我就算了嗎?張開你的狗眼看清楚這是什麼東西,你這劉景泰第一!」剛突然探懷拿出騮貞的闔家照片,騮驚惶失色,伸手要搶,剛却轉遞給鳳,鳳匆匆端詳後,一手執騮胸紏纏,騮還欲狡辯,鳳再也不相信了,哭駡着。
「好呀,人証物証都有了,我看你這砍頭的怎樣說?」傭人門都想上前看照片。
貞更當衆痛數她丈夫的薄倖,聲淚俱下地說:
「怎麼不是呢?他的名字本來叫做潘阿騮,九年之前我媽作主招他做子婿,生下了圓仔,不久他就過番來,跟着汕頭淪陷了,他就一直沒……有信息寄囘去,可憐我們捱飢抵餓等了他整整七個年頭,媽結果熬不了,投井而死,我沒辦法,只……得帶着圓仔千辛萬苦過番來找他,誰知道他變了,變到……」
鳳命令似的:「够了,够了,潘有誠,你瞞婚騙産又打算和那婊子安娜結婚種種作惡的行為,都綳不緊啦,你若不把所有財產交還,光着原來的身子夾着尾巴滾出去,可別怪老娘不客氣,你這奴才,你不想想當初你是怎麽樣……的一副窮相,你憑藉什麼才有今天?你有什麽東西帶進汪家來?喏,這就是你唯一的財產……」越說越生氣,拿起桌上的潮州茶具捽到地上。
騮難看的面孔,給她們罵得汗出如瀋地,不敢抬起頭來。
貞尋夫的希望也開始破滅。
誠記的石心賢倉惶地跑進來嚷着:
「頭家,不得了啦,汕滙猛起,我們昨天放出的一算來下,要蝕一百多萬,誠記所有的都不够啦!」
騮大吃了一驚,並且在電話中曉得卓文標和安娜逃走了。鳳曉得卓也帶走她的全部金飾,拍手頓足地嚎啕大哭,騮更如受雷殛地說:
「哦,哦,明槍暗箭都他媽的向住我來,一百多萬,三百多萬,他媽的一共五百萬!僑務委員,商會主席,金錢!難道這様就完疍!」
春梅六樓上奔下來:「救命呀,小姐啦上吊!」
秩序大亂,衆人擁到樓上,騮也倒下去,剛向貞說示意外面去,馬也跟着。
馬搖頭嘆息:「這兒簡直是陰曹地府,那裏還是人世?」
剛向貞說:「什麼都看清楚啦,你有什麼打算?」
貞經過了這一場復雜的敎訓和認識,舊的希望完全破滅,在記憶中,好像聽見啓發:「我相信你有了兩隻有用的手。」她端詳自己的手問:
「阿剛兄,我還有兩隻手,儘可不必靠人!在暹羅不曉得可有用?」
剛高興地囘答:「祇要肯做工,到處都用得着的,暫時老馬和我大槪總可以替你想點辦法,再過一個短時期,我們就可以囘唐山。」
貞堅决地挽起圓仔:「好,圓仔,我們走!」
圓仔:「媽,我們不是要找爸爸嗎?」
貞搖頭吻着圓說:「好孩子,不必找了,你爸爸已經死了!」
貞抱着圓仔,隨著剛和馬之後,用她的雙手在創造他們的新天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