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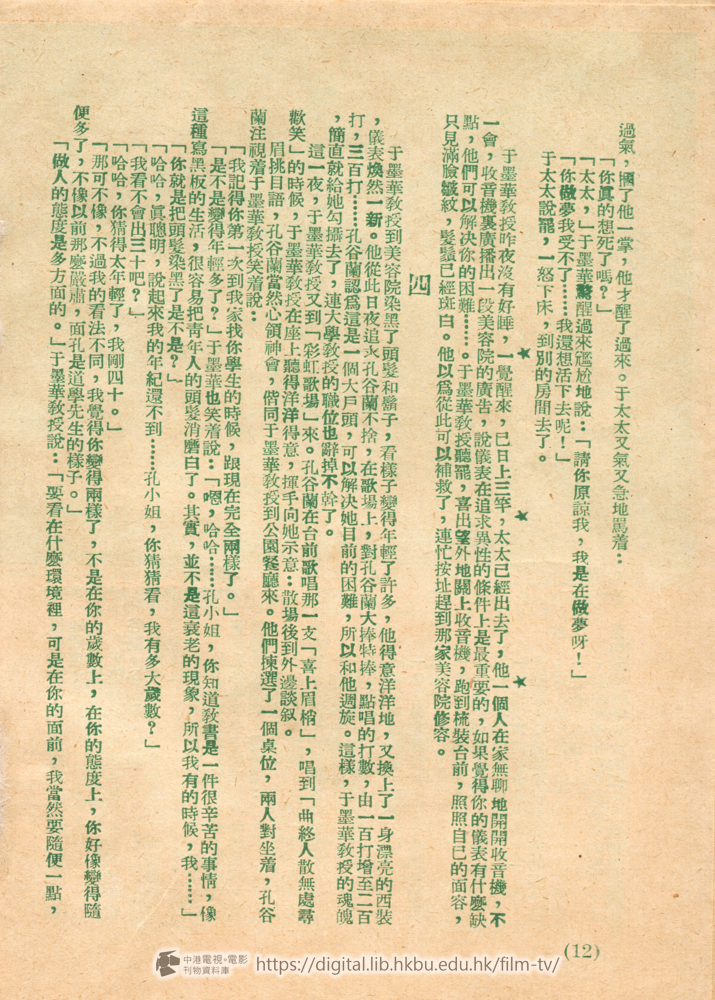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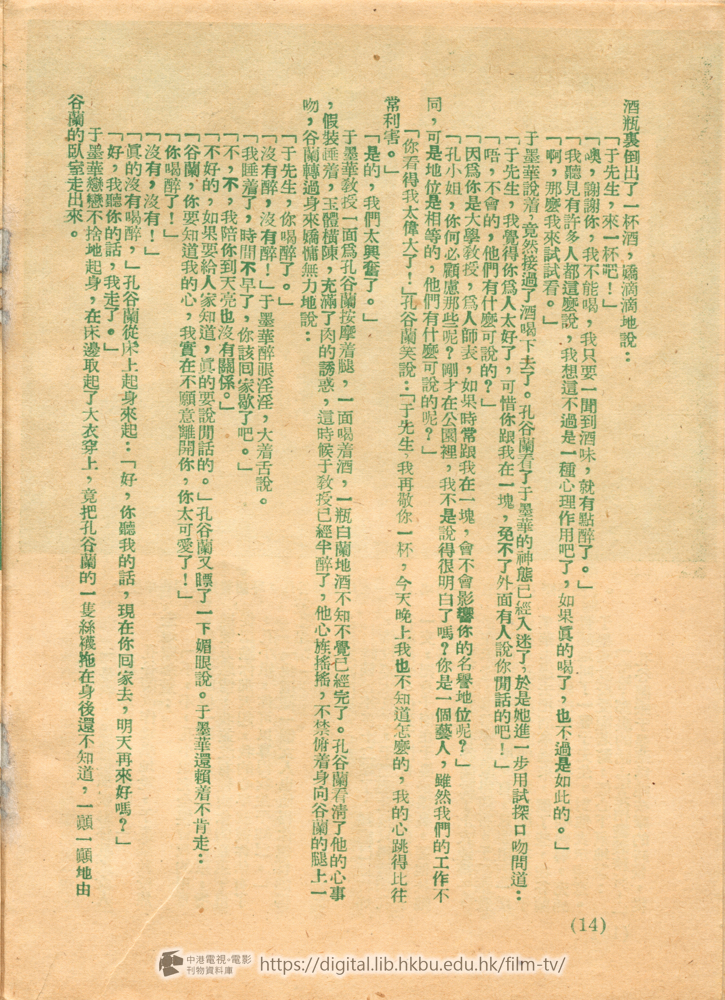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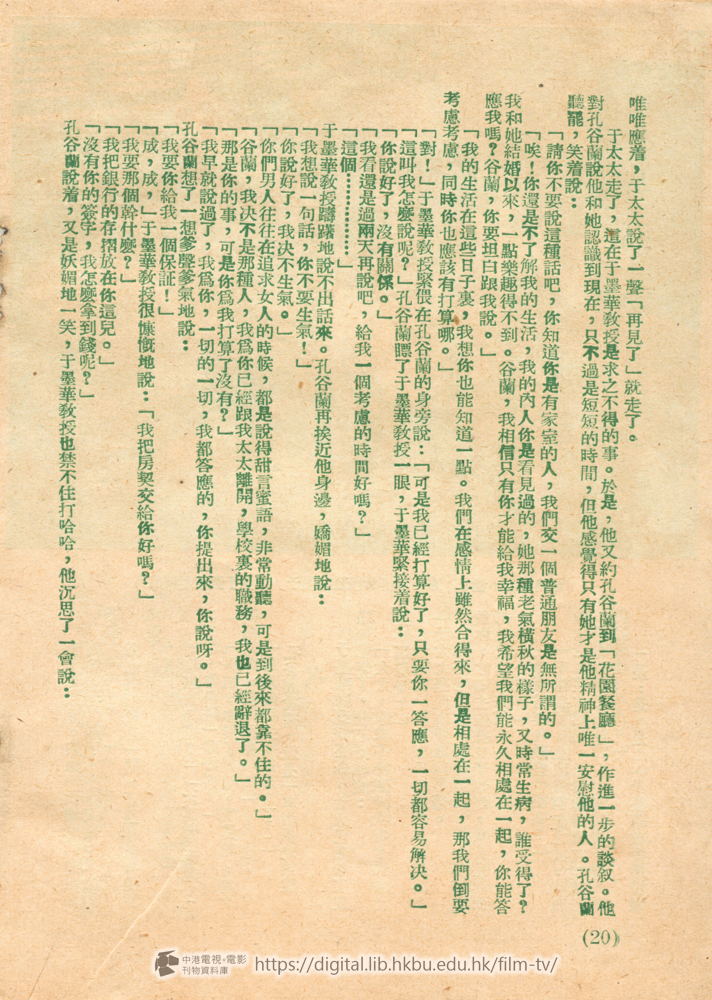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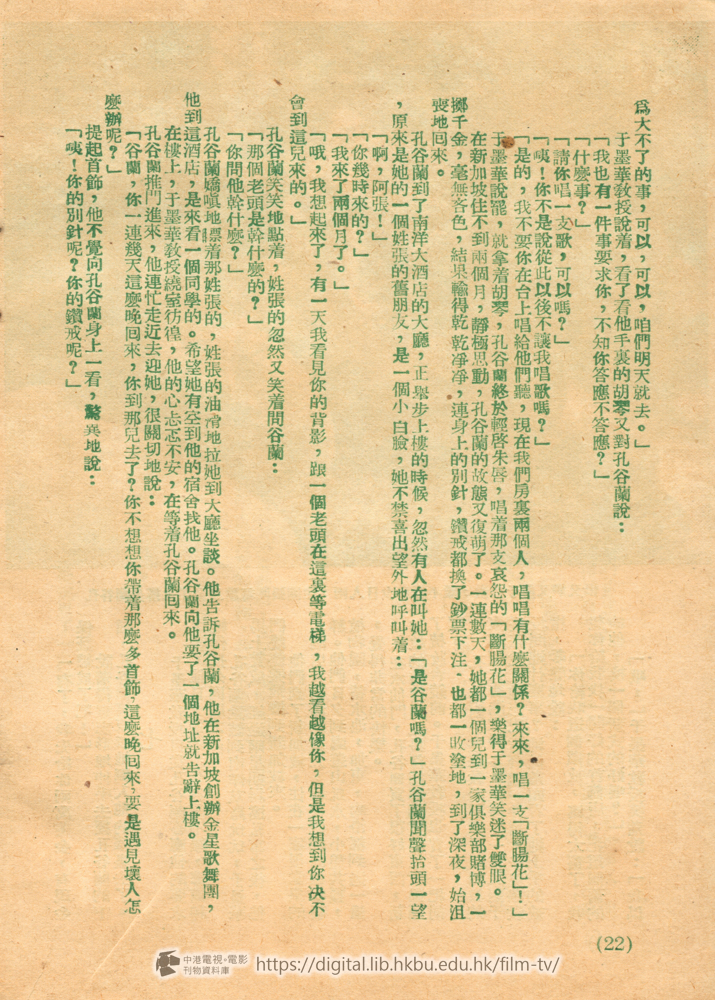





勾魂艶曲
電影小説
田家瑾改作
一
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大都市。
私立培東大學的校舍巍然矗立着。
時候剛是早晨,還沒有上課,于墨華敎授正在敎務室裡休息,忽然聽見窗外有學生的喊聲:
「孔小姐……喂……Miss孔……哈…… Good Morning!」
敎室窗口處,正有許多學生向對面公寓樓上大喊特喊。于墨華敎授奇怪地走到窗口張望,只見對面公寓樓上,一個女人啓門,走到洋台上,向學生們招手,那個女人妖聲怪氣地說:
「你們太不客氣了,一淸早就來開我的玩笑啊!」
在這邊是一陣騷動。
「噯,我們不是存心跟你開玩笑,我們以爲你早起來了。」這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學生叫黃喬奇的聲音。
「我們特地向你問早安呢!」這是那個流氓型十足叫李彼得的聲音。另一個身軀臃腫得像肥猪一般叫呂可松的從人叢中擠出前面來嚷着:
「喂,Miss孔,你的那張像片到底送給誰呀?」
「送給誰的?你還不知道嗎?」對面那女人飄着媚眼,妖媚地說。呂可松一聽,樂得迷着雙眼向同學們說:
「聽見沒有,她是送給我的!」
「得了吧,她送給你?」
同學們譏笑着呂可松,對面那個女人已舉手向他們示意,說聲再見就走入房了。學生們又一哄地走入了敎室,爭看着呂可松手裡拿着的女人相片。那像片上的女人一,腰下圍了一黑裙,輕輕一吹,紗裙飄動,玉腿就若隱若現,神秘惑人。學生們覺得好玩,互相搶着吹動,鬧得團團轉,不料這時于墨華敎授剛踱進敎室來上課,一見他們手裏的相片,立刻搶了過來,道貌岸然地說:
「這是那來的?」
下課後,于墨華敎授把黃喬奇,呂可松,李彼得叫進敎務室來,大聲地申斥着:
「你們想想,諸位的家長培養你們到今天,能够送你們到這兒來求學,眞不知道費去多少心血,對你們抱着若大的期望,現在你們這個樣子胡鬧,對得起你們的父母嗎?再說,現在的社會裏,那些妖形怪狀的舞女,歌女,更不是你們應該接近的。你們看——」說着拿出那張女人的相片指着說:「這是一個規矩女子拍的照嗎?這簡直是一個妖精!」
于墨華敎授一本正經地,說完了話就把相片放在辦公桌抽斗内。黃喬奇李彼得呂可松三人滿臉現出了失望的神色。于教授又囘身問他們說:
「她叫孔……孔什麽?」
「她叫孔谷蘭。」黃喬奇尷尬地囘着。
「奇怪,以前我怎麼沒有看見她呢?」
「搬到這對面,也只不過有三天。」
「好,你們囘去吧!」
黃喬奇三人聞聲,如獲大赦地唯唯走了出去。于墨華敎授看見左右無人,連忙拿出那相片來看看,躊躇了一下,也輕輕吹動着紗裙,覺得實在太香艶,太神秘,太可愛了,竟把相片偷偷帶囘家去。
到了夜裏,于太太已經睡着了,于墨華敎授好像有什麽心事,躺在床上沉思,日間所見的事,就一一浮現在他的腦際,他偷偷起床,走到櫉邊開門,在衣袋裡拿出那張孔谷蘭的相片,又囘到床上,躺下來輕輕地吹着,老懷興起,春心微動,嘴角浮着一抹淫褻的笑影。
二
于墨華敎授自從看了孔谷蘭那張相片後,神態有點失常,他的腦袋給那雙艶膩的玉腿所征服。過了幾天,也許忍耐不住了,他决定去訪問她,他走到了公寓附近,抬頭向樓上望着。
在孔谷蘭的房裡,這時候樂聲飄揚。黃喬奇,呂可松,李彼得正和孔谷蘭在歌唱作樂,李彼得彈着鋼琴,孔谷蘭唱出一支「香車美人」的歌——
他在街頭徜徉,
看見了香車一輛,
車上有個姑娘
她是實實在在漂亮。
他在後面追上,
穿過了紅燈阻擋,
不管警察叫嚷,
望着那遠去了的車輛。
啊呀呀,這個姑娘, 沒有字形容她漂亮。
啊好呀,這個姑娘,怎不叫人遐想
…………………………………..
…………………………………..
黃喬奇和呂可松,得意忘形,隨着歌聲,手舞足蹈,怪狀百出,不料剛唱完歌,忽然聽見門鈴響,大家立卽靜下來。孔谷蘭走邊到門邊問是誰,外面的應聲使喬奇三人怔住,輕聲叫孔谷蘭不要開門,原來于敎授到來。孔谷蘭把三人藏進浴室之後,再出來開門。
房門開了,門口出現的是于墨華敎授,他向孔谷蘭打量一下說:
「你就是孔小姐嗎?」
「不敢當,不敢當…………」孔谷蘭問着:「你是?…………」
「我是對面培東大學的敎授于墨華。」
「哦,于先生,你有什麼事嗎?」
「我有一點小事情想來請敎你!」
「那麽,請裏邊談吧!」
孔谷蘭把于墨華敎授請進房裏來,剛要坐下,電話鈴就響了。她忙的去聽電話,大聲說小聲笑一陣之後,她放下聽筒對于敎授說:
「于先生,眞對不起,我沒好好的招待你,因爲我還有個約會,爲了時間關係,我要換件衣服。」
「那麼我明天來。」
「不,不,你有什麽事,儘管說好了,不會妨碍你的談話的。請你坐呀,我就在那邊換衣服。」
「是是!」
于墨華敎授坐下來,孔谷蘭到衣橱那邊拿了一件旗袍,又移步到化粧鏡台前,拉開了尼龍的屛幕,在屏幕內更衣,粧台燈光把她那苗條的腰肢,曲線玲瓏的影子,映照在幕上,看得于墨華敎授心動神飛。
孔谷蘭在幕內一邊換衣一邊向于墨華敎授說,有什麽事要指敎儘管說好了,她在裡面是聽得見的。于墨華敎授恍然省悟,故作矜持地說:
「我是負責敎育的人,今天我到你這兒來麻煩你不是爲了別的是,聽說本校有幾個學生,時常到這兒打攪你,不知是不是有這囘事?如果眞的有這囘事,我認爲他們這種行爲是不對的。」他說着又向屏幕偷窺。孔谷蘭在幕內接應着:
「是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不過我這兒來往的男朋友很多,不知道那幾位是貴校的學生,最好姓什麽,叫什麽,你吿訴我好不好?」
「可以,可以,一個叫黃喬奇,一個叫李彼得,還有一個叫呂可松。」
「對不起,在我的男朋友中,還沒有這幾位的名字!」
「哦,那麼也許是我的誤會了。」
「是啊,往往有許多事情,會容易發生誤會的。」
孔谷蘭在幕內妖聲怪氣地說,于墨華敎授又饞眼地偷窺,垂涎三尺,怪形怪狀,那躱在浴室裏的黃喬奇等,在鎖匙眼中,看見這個假道學者的怪模樣,也不覺失笑。
孔谷蘭換好了衣,拉開了屛幕出來, 艷光四射地在于墨華敎授眼前一幌:
「于先生,我這樣招待你,未免太不禮貌了吧?」
「客氣,客氣!」
于墨華終於向孔谷蘭吿辭了,孔谷蘭送他到門口說:
「再見,有空請過來坐呀,于先生, 我不送了!」
★ ★ ★
于墨華敎授囘到家裡來,心裡有點飄飄然,孔谷蘭那妖艶的影子,無時無刻不在他腦子裡幌來幌去。
上燈的時候,他下樓來吃飯,剛拿起飯碗來,又呆想着,彷彿孔谷蘭的聲音又在他耳邊響着:
「再見,有空過來坐呀,于先生,我不送了!」
他微微一笑,自言自語地說:「客氣!客氣!」
「你跟誰說客氣呀?」
坐在他對面的于太太。覺得奇怪地詰問着他。于墨華失魂落魄地說:
「我,我說什麽?」
「我說你剛才說客氣,你跟誰客氣呀 ?」
「我沒有說呀!」
「墨華,我看你這兩天來又有點失常了!」
「唉,你又在那兒瞎懷疑了!」
三
「彩虹歌場」門口的電燈璀璨四射,樂聲梟梟地輕飄着。
在後台的化裝室,孔谷蘭正坐在鏡前化裝。有幾個債主在向她討債,一個是傢私店的夥計,一個是成衣店的小裁縫,她都約定日期把他們打發走了。獨有一個頭髮灰白叫王老板的站在一角落不去。孔谷蘭站起來冷冷地說:
「哎,王老板你從那兒來啊?有什麼事嗎?」
「還不是找你孔小姐幾個錢花花嗎?」
「幹麼那麽客氣呀?」孔谷蘭說:「 王老板,聽說最近你在外面說我很多閒話 ,很不滿意我是麽?」
「誰說的?」王老板着急地說:「我們除了錢財上的關係之外,我對你有什麼閒話可說的?」 ,
「對呀,我也是這樣想呀,我一共欠了五千塊錢,單單是利錢,你就拿了七千塊錢了,可是最近我手頭不方便,欠你兩個月利錢,我想你不至於在外面說我壞話吧?」
「孔小姐,你不要聽別人的閒話,我這麽大歲數了,還能在外面胡說嗎?」
王老板焦急地辯解着,歌台的管事人莊先生來催孔谷蘭上場,孔谷蘭乘機敷衍着王老板,說一星期後還他利錢,他只得怏怏地走了。
王老板走後,莊先生數說着孔谷蘭,怎麼會跟這老東西借錢,那是有名閻王債。孔谷蘭不禁慨嘆了一聲說:
「想不到會拖他這麼多日子,當初我在賭場裡向他借的時候,我預算最多一個月就可以還他了,誰知道我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壞呢?」
「你現在究竟有多少債呢?」
「債呀?嗯,得一萬美金才可以了淸我這一身債。」
「債債…………」莊先生嚴正地說:「谷蘭,我勸你不要再去賭了,久賭無勝家,不管是賭場,馬場,跑狗塲,一進門,你的錢就打了一個七折八扣,你想贏他,他想贏你,赢來贏去,都贏不着,結果是給賭場的老板贏去了。你不要見怪,再說,你近來生意不好,也是你好賭的關係。」
「唉,我知道,就因爲我好賭,有許多朋友都不敢接近我,可是我現在有什麼辦法呢?我希望能够再找一個朋友還淸了債,我就不賭了。」
孔谷蘭說着坐下來對鏡梳頭,接着又慢慢的塗着口紅,這時候,黃喬奇和李彼得吹着口哨走了進來,孔谷蘭問他們爲什麽不到前邊去坐?黃喬奇笑道:
「前邊風大,我們到這裡避風的。」
「什麼,今天台前沒有開電風扇啊!」莊先生聽了黃喬奇的話,不勝奇怪。李彼得笑笑地說:
「此風不是電風扇,是落帽風,哈哈……」
「你們在搗什麼鬼呀?」
孔谷蘭不禁揷着問,喬奇嘻皮笑臉地說:
「老實告訴你吧,我們那位于敎授從今天起要到這裏査我們了。」
孔谷蘭聽說也不禁奇怪,莊先生出去之後,她問喬奇,是誰吿訴他們,于敎授要來?喬奇說是今天上課的時候,于敎授這樣警吿他們。孔谷蘭正覺得好笑,那個大胖子呂可松忽然匆匆走進來,裝腔作勢地嚷着:
「大事壞了,大事壞了,于鬍子眞的來了,他沒有看我就溜進來了,莊先生正在請他點歌呢!」
喬奇和彼得聽說都覺得好笑,孔谷蘭也很納罕。莊先生走了進來,吿訴大家,于墨華敎授點孔谷蘭的歌,一點就是一百打。孔谷蘭詫異謂喬奇,于敎授敎書能掙多少錢?喬奇吿訴她,敎書的錢,有限得很,可是他家裡有錢,他祖上傳給他不少遺產。孔谷蘭聽說,若有所感地低下頭沉思。
★ ★ ★
歌場壁上懸着點唱的燈牌,上面寫着,「于墨華先生點孔谷蘭小姐一百打」。于墨華敎授已坐在場中前座的一張桌前。另一個座位上,有兩個聽客在交頭接語,批評孔谷蘭,說孔谷蘭講人品講歌唱,可以說最近沒有一個歌女比得上她,可是近來生意不好,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爲誰捧她就倒霉,剩個十頭二十萬,捧不過她,擋不住她一年半載花在賭場上面。
後台的出入口處,孔谷蘭盛裝出來,走向台前來了,她媚眼輕輕向台下一飄,台下就響起了一陣掌聲。樂聲悠揚地交奏着,她輕啓朱唇,唱着「一把扇子」的歌……
于墨華敎授在台下聽得非常入神,孔谷蘭有意無意地向他投着媚眼,使他不禁魂飛魄散。
★ ★ ★
于墨華敎授從歌場囘來,一心念念着孔谷蘭,他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漸漸地入夢。
他懷了一枚鑽戒,到公寓來訪孔谷蘭。孔谷蘭笑臉迎人地說:
「怎麽,我唱完,就找不着你啦!」
「我囘去拿一樣東西。」
于墨華敎授說着握着孔谷蘭的手,很親暱地和她並肩坐在沙發上。孔谷蘭妖媚地問道:
「你囘去拿什麽去了?」
于墨華敎授由袋裡取出一枚鑽戒送給谷蘭,谷關驚異地說:
「哎喲…………你給我的,那怎麼好意思呢?」
「哈哈,不要客氣,戴上,戴上!」
他癡迷地挨近孔谷蘭身邊,要吻孔谷蘭,孔谷蘭半推半就地投在他的懷裡,忽然她抬起頭來,驚叫着:
「有人來了!」
于墨華敎授聞聲,抬頭一望,看見黃喬奇進來,不禁憤然作色地叱着:
「你來幹什麽?」
「你能來,我就不能來嗎?」黄喬奇也憤然地說。
「你給我滾出去,混蛋!」
「你才是老混蛋,…………你這個假道學,僞君子!」
「你說誰是僞君子?」
于墨華敎授怒火上升,他跑過來動手要打喬奇,喬奇也不甘示弱囘手來打他。
「你這狗東西,你想打我!」
于華墨敎授兇狠地扼着喬奇的頸子嚷着……
「墨華,墨華!」
于墨華在夢中所扼着喬奇的頸子,正是和他同睡的太太的頸子,地被扼得透不過氣,摑了他一掌,他才醒了過來。于太太又氣又急地駡着:
「你眞的想死了嗎?」
「太太,」于墨華醒過來尷尬地說:「請你原諒我,我是在做夢呀!」
「你做夢我受不了……我還想活下去呢!」
于太太說罷,一怒下床,到別的房間去了。
★ ★ ★
于墨華敎授昨夜沒有好睡,一覺醒來,已日上三竿,太太已經出去了,他一個人在家無聊地開開收音機,不一會,收音機裏廣播出一段美容院的廣吿,說儀表在追求異性的條件上是最重要的,如果覺得你的儀表有什麼缺點,他們可以解决你的困難……。于墨華敎授聽罷,喜出望外地關上收音機,跑到梳裝台前,照照自已的面容,只見滿臉皺紋,髪鬚已經斑白。他以爲從此可以補救了,連忙按址趕到那家美容院修容。
四
于墨華敎授到美容院染黑了頭髮和鬍子,看樣子變得年輕了許多,他得意洋洋地,又換上了一身漂亮的西裝,儀表煥然一新。他從此日夜追求孔谷蘭不捨,在歌場上,對孔谷蘭大捧特捧,點唱的打數,由一百打增至二百打,三百打……孔谷蘭認爲這是一個大戶頭,可以解决她目前的困難,所以和他週旋。這樣,于墨華敎授的魂魄,簡直就給她勾攝去了,連大學敎授的職位也辭掉不幹了。
這一夜,于墨華敎授又到「彩虹歌場」來。孔谷蘭在台前歌唱那一支「喜上眉梢」,唱到「曲終人散無處尋歡笑」的時候,于墨華敎授在座上聽得洋洋得意,揮手向她示意:散場後到外邊談叙。
眉挑目語,孔谷蘭當然心領神會,偕同于墨華敎授到公園餐廳來。他們揀選了一個桌位,兩人對坐着,孔谷蘭注視着于墨華敎授笑着說:
「我記得你第一次到我家找你學生的時候,跟現在完全兩樣了。」
「是不是變得年輕多了?」于墨華也笑着說:「嗯,哈哈……孔小姐,你知道敎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像這種寫黑板的生活,很容易把靑年人的頭髮消磨白了。其實,並不是這衰老的現象,所以我有的時候,我……」
「你就是把頭髮染黑了是不是?」
「哈哈,眞聰明,說起來我的年紀還不到……孔小姐,你猜猜看,我有多大歲數?」
「我看不會出三十吧?」
「哈哈,你猜得太年輕了,我剛四十。」
「那可不像,不過我的看法不同,我覺得你變得兩樣了,不是在你的歲數上,在你的態度上,你好像變得隨便多了,不像以前那麽嚴肅,面孔是道學先生的樣子。」
「做人的態度是多方面的。」于墨華敎授說:「要看在什麽環境裡,可是在你的面前,我當然要隨便一點,不必那麼嚴肅了。」
「是啊,像我這種妖形怪狀的女人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對待我的。」
孔谷蘭故作嬌嗔地說,于墨華敎授焦急地辯解着:
「不,不,孔小姐完全誤會我的用意。我對你隨便一點,是彼此不愛拘束,增進雙方感情,我並沒有輕視你的意思,自從認識你那天起,我的心早就被你佔有了,孔小姐,你可以算得我生平知己。」
「我這樣一個女人也値得你這樣瞧得起嗎?」
孔谷蘭囘嗔作喜,閃着眸子一笑,于墨華敎授的靈魂已經出竅了。
時候差不多十二點了,餐廳已經打烊,侍役要休息了,于墨華敎授只得偕同孔谷蘭出來。但到了門口,孔谷蘭故意捧了一交,把身子倚在于墨華懷裏,要他扶她囘公寓去。
到了公寓,孔谷蘭脫了上衣連襪子,扱在床邊,嚷着雙足酸得利害。于墨華敎授問她這裏有白蘭地沒有,只要用酒一搓就好。孔谷蘭吿訴他,那邊櫃裏有酒。于墨華走過去把酒拿過來,倒了些,在谷蘭的腿上爲她按摩。孔谷蘭珠喉婉囀,充滿性感地叫了一聲于先生,對他表示謝意。于墨華敎授受寵若驚,低心下氣地說:
「哈哈,那裏的話,這是稍盡義務呀!」
孔谷蘭乘于墨華爲她按摩的時候,從酒瓶裏倒出了一杯酒,嬌滴滴地說:
「于先生,來一杯吧!」
「噢,謝謝你,我不能喝,我只要一聞到酒味,就有點醉了。」
「我聽見有許多人都這麽說,我想這不過是一種心理作用吧了,如果眞的喝了,也不過是如此的。」
「啊,那麽我來試試看。」
于墨華說着,竟然接過了酒喝下去了。孔谷蘭看了于墨華的神態已經入迷了,於是她進一步用試探口吻問道:
「于先生,我覺得你爲人太好了,可惜你跟我在一塊,免不了外面有人說你閒話的吧!」
「唔,不會的,他們有什麽可說的?」
「因爲你是大學敎授,爲人師表,如果時常跟我在一塊,會不會影響你的名譽地位呢?」
「孔小姐,你何必顧慮那些呢?剛才在公園裡,我不是說得很明白了嗎?你是一個藝人,雖然我們的工作不同,可是地位是相等的,他們有什麼可說的呢?」
「你看得我太偉大了!」孔谷蘭笑說:「于先生,我再敬你一杯,今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麽的,我的心跳得比往常利害。」
「是的,我們太興奮了。」・
于墨華敎授一面爲孔谷蘭按摩着腿,一面喝着酒,一瓶白蘭地酒不知不覺已經完了。孔谷蘭看淸了他的心事,假裝睡着,玉體横陳,充滿了肉的誘惑,這時候于敎授已經半醉了,他心旌搖搖,不禁俯着身向谷蘭的腿上一吻,谷蘭轉過身來嬌慵無力地說:
「于先生,你喝醉了。」
「沒有醉,沒有醉!」于墨華醉眼淫淫,大着舌說。
「我睡着了,時間不早了,你該囘家歇了吧。」
「不,不,我陪你到天亮也沒有關係。」
「不好的,如果要給人家知道,真的要說閒話的。」孔谷蘭又瞟了一下媚眼說。于墨華還賴着不肯走:
「谷蘭,你要知道我的心,我實在不願意離開你,你太可愛了!」
「你喝醉了!」
「沒有,沒有!」
「眞的沒有喝醉,」孔谷蘭從床上起身來起:「好,你聽我的話,現在你囘家去,明天再來好嗎?」
「好,我聽你的話,我走了。」
于墨華戀戀不捨好起身,在床邊取起了大衣穿上,竟把孔谷蘭的一隻絲襪拖在身後還不知道,一顚一顚地由谷蘭的臥室走出來。
五
于墨華敎授醉醺醺地走進了自家的門首,于太太穿着睡衣出來開門,他醉態朦朧的誤認她是傭人趙媽,吩咐她去睡,說完就叩着扶牆,脫去皮鞋,用手拿着,衣領上還拖着那隻絲襪,輕輕地向樓上走去,走了幾步,酒醉無力的身體,又倒退下來,踉踉蹌蹌,又勉强再走上去,到了床邊,就倒身地躺下去了。于太太不悅地跟在他後面,伸手從他背後拿出那隻絲襪,握在手裏,低首沉思。
于墨華敎授胡里胡塗睡了一覺,當他醒來的時候,太太己經出門了,女傭趙媽吿訴他,太太出去散步,留下一包東西,囑她交給他,叫他別忘記送還人家。于墨華敎授把紙包打開,竟是一隻絲襪,覺得很是奇怪,他向趙媽要了帽子和皮包之後,匆匆出門去了。
他到八國飯店孔谷蘭的房間,孔谷蘭穿着晨衣,正在聽電話,有一位叫趙太太的,在電話裏向她索討賭債。她看見于墨華脫帽進來,忙把電話掛上,和他打招呼:
「于先生,你早,你怎麼沒去上課?」
「哈哈……」于墨華敎授乾笑着:「 昨天晚上太失禮了,請你原諒!」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很好呀,很聽話。」
孔谷蘭媚笑着,陣陣的粉香,透進了于墨華敎授的鼻官,他望着她說:
「我喝醉了……你知道我今天這麽早來,有什麽事嗎?」
于墨華敎授一面說,一面從袋裏取出那隻絲襪。孔谷蘭一見,故作驚訝地說:
「啊呀!你太太知道了吧?」
「她知道也無所謂,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她等於是一個活死人了,哈哈……我想請你出去吃飯,你能賞臉嗎?」
「上那兒去吃啊?」
「廬山飯店,我們還可以順便看看風景。」
「好,讓我去收拾收拾。」
孔谷蘭話剛說完,忽聞門鈴聲響,兩人不禁詫異着。孔谷蘭走近門邊問是誰,對方囘說是姓于,于墨華的心一動,知道是他太太到來,忙阻着谷蘭不要開門,自己跑進浴室去躱避。
孔谷蘭把門開了,于太太站在門口問着:
「你貴姓?」
「我姓孔。」
孔谷蘭冷冷地答,于太太走了進來,很委宛地說:
「孔小姐,我非常的冒眛,我到這兒來是找我丈夫于墨華的,于墨華就是對面培東大學的敎授。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對,我說得太模糊了,我簡單一點跟你說吧,我到這兒是找于墨華的,于墨華就是我的丈夫。」 「奇怪了,你的丈夫怎麼會到我這兒來呢?」
「因爲我看見他來的。」
「哦,是嗎?好,于太太你儘管找,不過,如果你在這兒找不着你的丈夫,那麼我的名譽你要負責的。」
孔谷蘭扳起了臉說,于太太却謙遜地囘着:
「孔小姐,我並沒有侮辱你的意思,請你原諒!」
說罷,她就在房裏東張西望,但都不見于墨華的踪影,忽然她發覺了浴室的門是緊閉着,猜度于墨華一定躱在裏面,她要求孔谷蘭把打開給她看看,孔谷蘭說裏面禁着一隻惡狗。于太太冷冷的一笑,表示不相信。孔小谷蘭說:
「你不信嗎?」接着她朝浴室門喊了一聲:「Lucky」
孔谷蘭喊出了這一聲,浴室裏面就囘應了一陣狗叫聲。于太太一聽,心裏明白,她向孔谷蘭說:「你用不着拿狗來嚇唬我,我不是到這兒爭風吃醋的,現在我明白了,裏邊那條狗叫的聲音,我聽得很熟的,希望你好好的養着那條狗吧,再見!」
于太太說罷,頭也不囘地奪門而出。
孔谷蘭把門關了,不禁笑着,又朝向浴室大喊「Lucky」。
浴室的門砰然一開,于墨華敎授狼狽地走了出來:
「糟了糟了,她怎麽會來呢?」
「我怎麽知道?」孔谷蘭笑着說「Lucky,你再叫一聲好嗎?」
「小姐,你饒了我吧。說真的,剛才我學狗叫,學得還像嗎?」
「那要你囘去問你太太了!」
孔谷蘭說罷,就是一串銀鈴的笑聲。
六
于墨華囘到家裏來,太太已收拾了皮箱預備走了。他不安地說:
「太太,你真不能原諒我嗎?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難道我囘去看看母親都不可以嗎?」于太太毫無表情地囘答着。
「好吧,你一定要囘去,我也不能勉强你,你囘去住些日子也好,我希望你到那兒就給我來信!」
「一定。」
「你還需要我做些什麽嗎?」
「不需要了。在我沒有走之前,我有兩句話希望你記住,希望你時常照照鏡子,看看你自己的尊容,不要枉費心機,弄得將來後悔不及。」
「是,是,是!」于墨華敎授慚愧地唯唯應着,于太太說了一聲「再見了」就走了。
于太太走了,這在于墨華敎授是求之不得的事。於是,他又約孔谷蘭到「花園餐廳」,作進一步的談叙。他對孔谷蘭說他和她認識到現在,只不過是短短的時間,但他感覺得只有她才是他精神上唯一安慰他的人。孔谷蘭聽罷,笑着說:
「請你不要說這種話吧,你知道你是有家室的人,我們交一個普通朋友是無所謂的。」
「唉!你還是不了解我的生活,我的內人你是看見過的,她那種老氣橫秋的樣子,又時常生病,誰受得了?我和她結婚以來,一點樂趣得不到。谷蘭,我相信只有你才能給我幸福,我希望我們能永久相處在一起,你能答應我嗎?谷蘭,你要坦白跟我說。」
「我的生活在這些日子裏,我想你也能知道一點。我們在感情上雖然合得來,但是相處在一起,那我們倒要考慮考慮,同時你也應該有打算哪。」
「對!」于墨華敎授緊偎在孔谷蘭的身旁說:「可是我已經打算好了,只要你一答應,一切都容易解决。」
「這叫我怎麽說呢?」孔谷蘭瞟了于墨華敎授一眼,于墨華緊接着說:
「你說好了,沒有關係。」
「我看還是過兩天再說吧,給我一個考慮的時間好嗎?」
「這個…………」
于墨華敎授躊躇地說不出話來。孔谷蘭再挨近他身邊,嬌媚地說:
「我想說一句話,你不耍生氣!」
「你說好了,我决不生氣。」
「你們男人往往在追求女人的時候,都是說得甜言蜜語,非常動聽,可是到後來都靠不住的。」
「谷蘭,我决不是那種人,我爲你已經跟我太太離開,學校裏的職務,我也已經辭退了。」
「那是你的事,可是你爲我打算了沒有?」
「我早就說過了,我爲你,一切的一切,我都答應的,你提出來,你說呀。」
孔谷蘭想了一想爹聲爹氣地說:
「我要你給我一個保証!」
「成,成,」于墨華敎授很慷慨地說:「我把房契交給你好嗎?」
「我要那個幹什麼?」
「我把銀行的存摺放在你這兒。」
「沒有你的簽字,我怎麼拿到錢呢?」
孔谷蘭說着?又是妖媚地一笑,于墨華敎授也禁不住打哈哈,他沉思了一會說:「有了,我先給你兩萬美金,有現金保証總成了吧!」
說着得意忘形地伸手去摸孔谷蘭的下頦,孔谷蘭笑吱吱地倒入他的懷裏去了。
七
于墨華敎授自從孔谷蘭答應他的要求之後,他日夕追隨着孔谷蘭不離,籌備和她作長久同居之計。
孔谷蘭說該到南洋羣島玩玩,于墨華馬上贊成,經過兩星期摒擋私事之後,他們雙雙乘飛機到新加坡來。
他們到了新加坡,住在一家很堂皇的大酒店。南洋的風光,給他們的印象很新鮮。他們日夕到處遊山玩水,小憩共餐,植物園,蓄水池,加東,吻洛都到過一趟,覺得非常的快樂。
在水仙門,孔谷蘭買了很好東西,新加坡的特產和衣料首飾等都買囘來,擺滿了梳妝台鏡前。于墨華敎授也買了一把胡琴。
孔谷蘭對于墨華教授稱讚了新加坡的東西便比香港宜得多。她停了一會又對于墨華說,她忘記吿訴他一件事。于墨華教授問她什麽事?她低着頭看了她上手的戒指,爹聲地說:
「你給我這個鑽戒,鑲得太舊了,我想你給我找一間好的首飾店,把這個舊的給他,換一個新式的好嗎?」
「哦,」于墨華敎授笑着說:「我以爲大不了的事,可以,可以,咱們明天就去。」
于墨華敎授說着,看了看他手裏的胡琴又對孔谷蘭說:
「我也有一件事要求你,不知你答應不答應?」
「什麼事?」
「請你唱一支歌,可以嗎?」
「咦!你不是說從此以後不讓我唱歌嗎?」
「是的,我不要你在台上唱給他們聽,現在我們房裏兩個人,唱唱有什麽關係?來來,唱一支「斷陽花」!」
于墨華說罷,就拿着胡琴,孔谷蘭終於輕啓朱唇,唱着那支哀怨的「斷腸花」,樂得于墨華笑迷了雙眼。
在新加坡住不到兩個月,靜極思動,孔谷蘭的故態又復萌了。一連數天,她都一個兒到一家俱樂部賭博,一擲千金,毫無吝色,結果輸得乾乾淨淨,連身上的別針,鑽戒都換了鈔票下注,也都一敗塗地,到了深夜,始沮喪地囘來。
孔谷蘭到了南洋大酒店的大廳,正舉步上樓的時候,忽然有人在叫她:「是谷蘭嗎?」孔谷蘭聞聲抬頭一望,原來是她的一個姓張的舊朋友,是一個小白臉,她不禁喜出望外地呼叫着:
「啊,阿張!」
「你幾時來的?」
「我來了兩個月了。」
「哦,我想起來了,有一天我看見你的背影,跟一個老頭在這裏等電梯,我越看越像你,但是我想到你决不會到這兒來的。」
孔谷蘭笑笑地點着,姓張的忽然又笑着問谷蘭:
「那個老頭是幹什麼的?」
「你問他幹什麽?」
孔谷蘭嬌嗔地瞟着那姓張的,姓張的油滑地拉她到大廳坐談。他吿訴孔谷蘭,他在新加坡創辦金星歌舞團,他到這酒店,是來看一個同學的。希望她有空到他的宿舍找他。孔谷蘭向他要了一個地址就吿辭上樓。
在樓上,于墨華敎授繞室彷徨,他的心忐忑不安,在等着孔谷蘭囘來。
孔谷蘭推門進來,他連忙走近去迎她,很關切地說:
「谷蘭,你一連幾天這麽晚囘來,你到那兒去了?你不想想你帶着那麽多首飾,這麽晚囘來,要是遇見壞人怎麽辦呢?」
提起首飾,他不覺向孔谷蘭身上一看,驚異地說:
「咦!你的別針呢?你的鑽戒呢?」
「輸了!」孔谷蘭漠然地囘着,但于墨華敎授却着急地追問下去:
「輸了,我給你那許多錢呢?」
「錢,早就輸了。」
孔谷蘭冷冷地換了睡衣,倒在床上抽煙,于墨華急得跺着脚:
「照這樣下去,我怎麽能維持得?」
「我怎麼能知道呢?」
「谷蘭,美金,還有那許多首飾,你竟然通通都輸光了,你不是說不賭了嗎?」
「輸已經輸了,還說那些廢話做什麼?」
孔谷蘭不悅的說。于墨華敎授不覺大氣起來:
「谷蘭,你這麽好賭,你太荒唐了。」
孔谷蘭看了于墨華生氣。她忽然坐了起來,變着臉頂着嘴說:
「我愛賭不止一天了,誰不知道我孔谷蘭是個賭鬼。要是我不好賭,我也不至於今天跟着一個像我爸爸的人在一塊了。」
「我沒有勸錯你呀,」于墨華敎授痛苦地說:「你何必挖苦我呢?」
「如果你不滿意我,那末我們可以分開的。」
「啊,分開?」于墨華意外地:「你眞狠心說出來,難道我勸錯了你嗎?谷蘭,我帶了多少錢來,你是知道的,我現在只剩了三千美金了。」
「總比沒有强呀!」孔谷蘭靈機一動地說:「我還有一句話,你再給我兩千!」
「啊,你還要去賭?」
「我總得首飾贖囘來呀,你答應不答應?」
「好,」于墨華敎授壓住了怒火說:「可是我也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我想我們換一個地方住可以簡省一點,妳願意嗎?」
「可以,你先把錢給我!」
「好,我就給你拿來。」
孔谷蘭不悅地看着他。
過了幾天,于墨華敎授和孔谷蘭搬到一家小公寓來。那天,于墨華正在親自打掃,一面在埋怨着: 「唉,那兩千美金,要不給你,你不痛快,給了你,你又全把它輸光了,要是放到我這兒,今天我們還不至於搬到這兒來。」
「說這些廢話幹什麼,我不喜歡聽,我就是爲了愛賭,需要錢才跟你的。你趕快想辦法,像這種地方,我只能暫時住一住,要是你沒有力量供給我,還是那句話,各人走各人的路。」
孔谷蘭刁蠻地說罷就丟棄了香煙,走到小几上坐下來玩紙牌,到了這地步,于墨華錢已經沒有了,氣也沒法子出,他很傷心地求着孔谷蘭:
「谷蘭,你不要再說這些話好嗎?你真的離開我,我只好死給你看,我現在是在找事啊,我的一切都爲了你,請你不要再刺激我好嗎?」
孔谷蘭睬也不睬地在玩她的紙牌,那一張妖艷的臉,灑滿了冷冷的霜花。
八
孔谷蘭看淸于墨華敎授已經沒有錢供她揮霍了,她轉了念頭去找,她那位姓張的朋友。她跟那姓張的在餐舘進餐,談着未來的大計,有說有笑,早已把于墨華敎授丢在一邊。
于墨華敎授在公寓裏苦悶地踱着。這時,孔谷蘭正和那姓張的在舞廳歡談狂舞。
于墨華敎授孤單的等候着孔谷蘭囘來,將近凌晨的時候,街上忽傳來汽車的喇叭聲,他連忙跑到洋台向下一望,看見有人送谷蘭囘來。
孔谷蘭推開門進來,看見于墨華不悅的在等着她,她冷冷地問了一聲:「你還沒有睡?」于墨華敎授憤怒地詰問着她:
「剛才底下汽車送你囘來的是誰?是誰呀?」
「朋友!」孔谷蘭愛理不理地囘他。
「什麽朋友,什麽朋友?你陪人家一宵到現在才囘來?我于墨華不能受這種侮辱,我花錢,你陪人家玩,你對得起我嗎?」
「什麽,你花過什麽錢?」孔谷蘭張大着眼說。
「我兩萬美金不是都讓你花完了嗎?」
「兩萬美金就心痛了,你不是老是說一切都是爲了我嗎?」
「是啊,我都是爲了你,你也應該爲我想一想呀!」
「為你想想,」孔谷蘭冷笑地:「你就是再花十倍兩萬美金,我孔谷蘭也未必是屬於你的。」
「真想不到你這個人這樣沒有感情!」
于墨華很傷心地說。孔谷蘭却哈哈的大笑:
「墨華,你是一個大學敎授,憑你的學問想一想,我們之間會有感情的存在嗎?事實擺在眼前,拆穿了說你愛的是我的肉體,我愛的是你的金錢,這不過等於一票交易吧了。我看你的情形,你也沒有辦法維持我了,今天我已經跟金星歌舞團簽過合同,再過四天,我就要去登台了。」
「啊,你要登台?」于墨華大吃一驚的說,這一下實在太出他意外了。
「嗯,剛才送我囘來的就是金星歌舞的團主,我現在再吿訴你,趁着我們愛情還沒有太破裂的時候,彼此好來好散,免得將來大家都痛苦!」
孔谷蘭說着,轉身走進了浴室。于墨華敎授苦悶的低着頭在沉思,等谷蘭穿好了晨衣出來的候,他痛苦地問道:
「谷蘭,你眞的要離開我嗎?」
「怎麽?」孔谷蘭冷笑着:「你又要死給我看?」
「不,不,我一切都爲了你,你就忍心不要我了嗎?我在那兒找事,我並沒有放棄我的責任。」
「責任?就算你找着了事?你有這力量供給我一切的享受嗎?我看算了吧。」
「谷蘭怎麽你一定要離開我了!」
孔谷蘭笑了一聲。于墨華暴怒地嚷着要跳樓,孔谷蘭冷笑的慫恿他跳,他絕望的走到了窗外一看,猶豫的又囘到她的身邊來懇求着:
「谷蘭。我實在捨不得你呀,你離開我不要緊,我怎麼囘去?我有什麽臉見人?」
「那麽你打算怎麽樣呢?」
「我求你可憐我。過去對你的一番情意,你讓我在你身邊,像傭人一樣的服侍你,我也情願。可是你不要抛棄我!」
于墨華敎授邊說邊跪下來。孔谷蘭的心這時不禁軟下來,忙扶他起來:
「嗯,你這是幹什麽呀?起來,起來。可以,你要跟我在一起,你要是干涉我的行動是辦不到的。」
「好好,從今天起决不干涉你的自由,剛才你說得很對,我是沒有力量供給你的享受的。」
「我還有一句話希望你答應我,爲了我事業上的起見,暫時我們不能住在一個房間裏,你答應嗎?」
「好的,只要你說,什麼地方都能住的。」
這樣,于墨華敎授不久就搬到厨房去住,房間讓給孔谷蘭自已派用場。那位所謂金星歌舞團的張團主,時時來和孔谷蘭鬼混,形影不離。于墨華敎授偷偷地看着他們的情形,又妒又恨,有說不出的苦衷。他巳被遺忘了,在家裏只像傭僕一樣,操作雜務。
孔谷蘭正式在「金星歌舞團」登台了,于墨華敎授就跟隨在她左右,給她扇扇,送茶,取東西。
有一夜,孔谷蘭排演化裝演唱「天涯歌女」,戲剛開幕了,那個拉胡琴的老者,臨時因病不來,孔谷蘭和那個姓張的,强迫于墨華敎授化裝登台,他無法反抗,只得拉着胡琴伴孔谷蘭出場。
戲散場了,孔谷蘭和那個姓張的出去宵夜,撇下于墨華敎授一個人在替她收拾東西。他滿腹憤妒地回到公寓來。
夜深沉了,孔谷蘭和那個姓張的囘來,兩個人餘興未盡,還關着門在房裏鬼混,漏出了一片淫褻的笑聲。
于墨華敎授在厨房裏不能睡,幾次去敲孔谷蘭的門,都給拒絕囘來,他傷心的坐着,左思右想,悲憤填胸。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已經三點多鐘了,于墨華敎授忽然聽見走廊有人走着,他連忙到門縫偷看,只見走廊上,孔谷蘭正跟那個姓張的送別,到了樓梯口,兩人又暗暗地接吻着。他窺看得很淸楚,痛恨得不得了,在厨房裏考慮了大半天,猛然發現牆上掛着一把切肉的尖刀,不覺起了殺機…………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于墨華敎授下了决心,他毅然拿了尖刀,直到孔谷蘭的房裏去。
孔谷蘭已經睡着,慵倦的面容,仍很迷人,于墨華敎授走近前去,一看又捨不得下手。忽然孔谷蘭輾轉嬌軀,他一見忙把刀子藏入袖內,呆立在床前。
孔谷蘭在床上的心一動,睜眼一瞧,不禁吃了一驚:
「怎麽,你還沒有睡啊?墨華,有什麼事嗎?」
「嗯,」于墨滿頭大汗地說:「我……我睡不着。」
孔谷蘭看見于墨華敎授的神色不對,心裏已感到不安,驀然又見他的袖口露出刀柄,已經明白他此來的動機,她按下了跳動的心,不動聲色,假意和氣親切的說:
「呃,不知怎麼着,我也睡不着,墨華,你坐下,我們很久沒有好好談過了」
她拉着他的手坐在床沿着,這一下,于墨華敎授的心已軟了大半了。接着,她裝着虛情假愛,噓寒問暖,把他的殺機吹到爪哇國去了,反覺得剛才的舉動太過鹵莽。他無話可說的,安靜地躺在床上休憩了。 第二天,孔谷蘭趕去找那位姓張的,把昨晚的事吿訴他,她的心還有餘怖。姓張的慫恿她,立刻跟他逃到外地去,避免了太多的麻煩。孔谷蘭同意了。姓張的於是偷偷把金星歌舞團頂了出去。
于墨華敎授誤認孔谷蘭囘心轉意,依然愛他,他四出找職業。終於在「大昌洋行」找到一個書記職。但當他興冲冲跑囘公寓的時候,他的希望破滅了。他一進臥房,已是人去樓空,沒有孔谷蘭的踪影。他四處張望,只見滿室凌亂,妝台上留有一把胡琴和一封信,他忙把信拆開,那信上寫着:
「墨華,千言萬語,只有一句話,我們不能再相處下去了,從前你說我太荒唐,不錯,我承認自己荒唐,可是,你也太胡塗了,到了今天,我們誰也不要責備誰,誰也不要原諒誰,因爲我們都是被挨駡的人,你說是嗎?現在我决定走了,你也該走了,我知道你的情形不好,特地留下一筆錢,給你作盤費,早一點囘去,祝你前途光明!孔谷蘭留上」
于墨華敎授看完了信,悔恨交集,他把鈔票擲在地上,又把信件撕得粉碎,突然拿起胡琴,猛力地擊碎妝台。他神氣激揚,彷佛聽見他太太的聲音……
「墨華,在我沒有走之前,我有兩句話希望你記住,希望你要時常照照鏡子,看看你自己的尊容,不要枉費心機,弄得將來後悔無及。」
于墨華到了這時,深深感到絕望,他萬念俱灰,突如發瘋似的狂笑不己….…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