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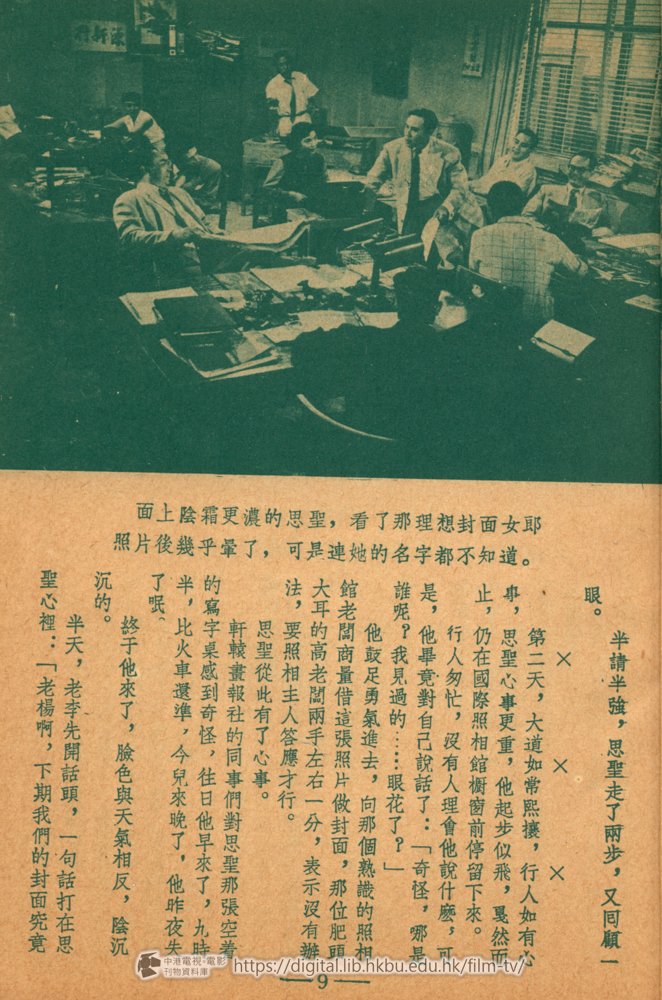























有口難言 電影小說
黄昏,大道上的百年古樹看起來高大得寂寞,紫金色的陽光嬌慵無力,疲乏地穿過大樹葉際的每一空隙,懶懶散散落到一家照相館的玻璃橱窗上,橱窗上嵌着玻璃膠的紅字,横排一行——國際照相館,行人們每爲這幾個鮮紅的字投以一瞥,也有佇足下來看的,那是兩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此中較高的一個,兩眼看住橱窗裡那張少女照片,幾乎出了神。他是一個畫報的編輯,有名的畫報編輯楊思聖,他常常注意一些女人的相片,也就是注意他那畫報的封面;但今天可不尋常,他簡直像中了邪,半天了,還不移動。
與他一起看的是會計小趙,他巳經看得眼前金星直冒了,看看思聖,思聖像個神道。
「你怎樣看個沒完了?明天它還擺在這兒的,走吧!」
半請半強,思聖走了雨步,又囘顧一眼。
第二天,大道如常熙攘,行人如有心事,思聖心事更重,他起步似飛,戛然而止,仍在國際照相館橱窗前停留下來。
行人匆忙,沒有人理會他說什麽,可是,他畢竟對白己說話了:「奇怪,哪是誰呢?我見過的……眼花了?」
他鼓足勇氣進去,向那個熟識的照相館老闆商量借這張照片做封面,那位肥頭大耳的高老闆兩手左右一分,表示沒有辦法,要照相主人答應才行。
思聖從此有了心事。
軒轅畫報社的同事們對思聖那張空着的寫字桌感到奇怪,往日他早來了,九時半,比火車還準,今兒來晚了,他昨夜失了眠。
終于他來了,臉色與天氣相反,陰沉沉的。
半天,老李先開話頭,一句話打在思聖心裡︰「老楊啊,下期我們的封面究竟是誰?」
思聖心更煩,臉上陰霜更濃。
「我不早吿訴你了?思聖這幾天暈了斗,他看那張國際櫥窗裡擺着的女人相片看得快發瘋了,天天去看,可是到現在姓什麽叫什麽都無法打聽出來。」小趙看思聖一眼。
「老楊的獨身主義快搖動了吧?」楊也看思聖。
思聖冷若冰霜,電話鈴響,思聖冷冷道:「喂!」
隨手把聽筒遞紿老李:「你太太。」
老李慌不迭對着電話:「喂,呀……唔……是。」
如接聖旨,把小趙笑得先仰後倒,老李有點窘,但心有不服:「你不用笑我,等你太太打電話來時,嘿……!」
思聖這時也耐不住笑了:「本來,我可能對我的主義搖動,可是爲了這事,又堅定起來。」
電話鈴續响,思聖沒接聽,一弩嘴向小趙道:「八成這是你太太。」
小趙去接,又隨手交給思聖:「這是給你的。」
「誰?」
「是你的太上老闆。」
思聖聽了作無可奈何的自怨自艾道:「又是打英文信,畫報的事還忙不過來呢!」
「打什麽信?又是推銷他那種百靈丸?」
思聖不作表示,一派怨憤的默認表情。
廣吿主任黄德興一進門,也許是平時有恩賞,Boy叫得很晌,頗有軍閥時代遺風,不過把立正改爲「黃先生早!」
思聖在百忙中想到一件事:「德興兄,上囘你經手的一筆廣吿費,今兒月底了,可以交來了吧?」
「才過一個禮拜,忙什麽?我那一囘辦事有錯?催這未緊幹什麽?走,咱們喝茶去!」
「誰有工夫跟你喝茶呀!」
小趙又釘上一句:「請喝茶也打不了馬虎賬,八成給你花掉了。」
「瞎扯,單據還在這裡呢!」一急,黃德興打開公文包,亂找一通,有一張照片跌出,思聖眼前一亮,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就是她,他站起來拉了黃德興就走。
「走,我請你喝茶去!」
「看見了照片,老楊又有工夫去喝茶了。」
「什麽照片?」德興指着桌上那一 張:「這是我太太的妹妹呀!」
「不管,我跟你喝茶去!」德興踉踉蹌蹌地跟着走了。
相片的主人原來是個啞巴,三姊妹她長得最俏,杜珊瑚、珍珠、琥珀,珍珠長得最漂亮。難怪楊思聖要爲她顛倒,但是該多少可惜有多少可惜,珍珠却是一個啞巴。
董德興以東床女婿之尊,去見岳丈,拿出一張相片,是思聖的,有意荐賢,杜子健老太爺看他方面大耳,心裡願意,却袒心珍珠的啞巴。
杜老太太與德興的意思,應該先瞞着珍珠是個啞巴,先讓他們會面。子健雖講究商業信用,但杜太太有錦囊妙計,耳邊一陣絮絮細語,杜老太爺也笑了,杜太太於是叫珊瑚過來,如此這般,吩咐一番。
德興受託於杜子健,親往邀請思聖,思聖心花怒放,打扮整齊,一路走,一路心跳。
杜老一家也按陣以侍,他自己坐在沙發上,珊瑚與珍珠坐在椅上,背向窗外,短髮輕衫,襯上一對大眼睛,漂亮極了。
德興打頭裡走,直達內堂,杜老假意的看思聖一眼,然後笑,德興急爲之介紹:「健伯,這位就是……。」
杜老站起身來,趨前一步,展開文明禮,伸出右手,猛的握住了對方的手道:「是楊先生吧?久仰,久仰!」
「不敢,不敢。」他的視線由老頭的黃鬚移到那角裡坐着玩手絹的珍珠,珍珠旁邊那個黃太太琥珀却並未進鏡。
他笑笑,她也似笑非笑。
德興道:「這是我太太!」
他一愕,繼而看到琥珀,這才釋下一口氣道︰「大嫂!」
杜老指着珍珠道:「這是我的二女兒珍珠!」
思聖不自覺忘形的道:「是的,我們在那兒見過?」
珍珠用手絹掩住了口,珊瑚躲在沙發椅後說:「見過面?什麽地方見過面?」
杜老爲之大吃大驚,珊瑚怎麽亂添字彙?吹鬚碌眼對她儆戒一番。
思聖被這一問,却很尲尬,他訥訥然道:「想……想不起了。」
德興解圍,說道:「是在國際照相館吧?」
杜老也慌忙挿口:「楊先生眞是年青有爲。」
「那裡那裡,請多指教。」
小小風波旣平,杜太太來了,一進門就自我介紹:「呀,是楊先生吧?我是珍珠的媽,聽說您來,我頭也來不及梳,好在都是自己人……」
還有發表下去的意思,杜老一急,搶先說話:「楊先生,貴公司最近營業狀况怎麽樣?」
思聖不知如何囘答才好,幸虧琥珀說明,他幹的是文化事業。
但老頭兒不懂,亂說一通,看看不是話頭,轉問年庚八字,杜老太趕緊為他算:「子鼠、丑牛、寅虎……也該三十了,還沒有成婚?」
「人家楊先生眼界高嘛,要像我馬虎點,早就……」不好,太太在旁白眼,於是噤若寒蟬。
珊瑚亂說話,珍珠背手制止,擰了她 一把,不料珊瑚却哇的叫起來,思聖心裡一慌,就想過去,杜子健出盡平生之力拉住,小狗從椅後出現,珊瑚情急智生,忙道:「小狗眞頑皮,儘咬人!」
珍珠急忙作撫小狗狀,一塲驚險,█才吿消除。
這一次「談話」,使思聖更感意亂情迷,由此也常到杜家,由於杜太的急行政策,幾番密談,珍珠的小弟弟居然叫思聖爲姐夫,而彼此不以爲怪了,珊瑚與珍珠的雙簧,思聖居然全不知曉。
雜誌的封面印成了,杜珍珠的美艷,人人讚賞不已,那位百靈丸的專家錢永明,俗不可耐的傢伙,就憑他登了幾千元的廣吿,就常常擺出一臉子的太上老闆面孔,也常到畫報寫字間來。
他看到封面,匆匆而至,一見思聖,就指着封面問道:「老楊,那小姐姓什麽?」
「姓杜!」
「幹什麽的?」
「還是小姐嘛,幹什麽?」思聖有點光火,可不敢發作。
「開麥拉反司不錯,她那兒人?」
「不清楚,反正說國語的。」
「可以捧她做電影明星呀!」他接着說出計劃,要她爲他出品的藥丸做廣告。
寫字樓的同人反對,思聖尤其反對,但是那個錢永明,使了撒手鐧,他以停登廣吿作威脅,而雜誌目前經費,却是靠那份廣告才補足的。
思聖想去看珍珠,探探意思,太上老闆的問題其一,他本人的相思其二,他借着送雜誌爲名,親白送去。
客廳裡 正好珊瑚的男朋友在,失了發言人,珍珠就無法辦理「外交」,躱在樓上。
珊瑚萬不防思聖突然而至,只得與他們介紹,小王自我介紹道:「王,亞歷山大王,我是杜珊瑚的同學。」
思聖見珊瑚進去弄茶,忽然想起,就向小王說:「她們姐妹倆的聲音眞像。」
「什麽?聲音像?這就奇怪了。」小王抓抓頭。
「這沒有什麽奇怪的,凡是兄弟姐妹,聲音常常是很像的,嘿嘿。」
小王愕住了:「哦,鬧了半天,你還不知道?」
「是呀,因爲上次來,沒看見杜小姐的妹妹。」
「不,珍珠是不講話的。」
「是呀!她很少講話的。那眞好,女孩子也該文靜一點,吿訴你,女人要是成天嘩啦嘩啦才討厭呢!」
珊瑚弄出茶來,同時又說:「楊先生,二姐看到封面了,她謝謝你,因爲嗓子痛不下來了。」
小王更覺奇怪,他問道:「她嗓子痛?」
珊瑚猛踩他一脚,也虧這一脚,免得露了馬脚。
思聖買了許多治嗓子的藥丸,同時又繫去ー封慰問的信,珍珠生平第一次接得這樣的信,高興極了,於是急於覆信,此去彼來,簡直毎天寫信了。
情感由信上漸漸加厚,正同兩人的積信一樣自然的增高,但杜老太爺認爲老寫信也不是辦法。
他徵求珍珠意見,想把珍珠的毛病,坦白吿訴思聖,但杜老太因德興約了去打牌,拉杜老走,珊瑚又被小王拉去跳舞,家裡於是只剩珍珠與僕人阿金。
思聖却在此時來訪,珍珠忸怩不安。
在思聖看來,更覺可愛,他提出最後一封信,要求結婚的問題,珍珠只寫了四個字給他:「我說不出。」
完全誤解,他以爲她是難以啓齒呢!他說:「我也是這樣,見了面,反而說不出了。」
珍珠姗姗的走到鋼琴前,奏了一曲“Fantasie Impromp Tu”,琴聲悠揚,使思聖益感神往,他與她互擁無言,珍珠上了樓,思聖高興地走了,一路走,在夜風中吹起那只曲子。
可是使思聖頹然傷神的,乃是第二天珍珠的來信,那信上寫着寥寥數十字:「你走了以後,我想了半夜,覺得我們還是不來往的好,這樣下去,只有使彼此更痛苦,我的隱衷一直沒法吿訴你,我眞是有口難言。」
思聖不明白這倒底是爲什麽,但同事們却紛紛說這一定是杜老頭在作梗。
衆議旣决,思聖約了杜子健出來晤談。
喜臨門飱室中一談,杜子健坦白說出來 珍珠是個啞巴。
原以爲他會發脾氣的,不料得到相反的效果,思聖毫不以爲是問題,他欣然知道珍珠的「有口難言」並非她有其他困難,他向杜老頭說:「我要立刻結婚。」
婚後歲月,眞是郎情妾意,但是,爲了她本人的啞疾,在無意間聽來許多傷心話。譬如有一次,錢永明這太上老闆邀思聖赴宴會,思聖邀了珍珠,但珍珠在樓上化粧時,永明却對思聖道:
「你太太去,有點兒不大方便吧?今天有很多生客人,她是個啞巴,要是他老不開口,不是把人家都該得罪了?」
儘管思聖叫他輕聲,樓上的珍珠已經聽見了,她哭了整整幾小時。
又有一晚,思聖囘來得較晚,樓上人家正在打牌,珍珠是「有口難言」,吿訴了思聖,思聖一看錶,已經是十二時一刻了,這是「法定睡眠時間」,他們還沒有「收工」,於是他一鼓作氣的上去干涉。
干涉的結果,是勝利了,但是有一句話,使思聖悔此一行,那鄰居最後說了一句話:
「早不來干涉的?」
另一個却說:「樓下是啞巴,當然不會干涉囉。」
珍珠的眼淚因此似珍珠。
她拼命的跟着無綫電說話,想迸出聲來,但迸不出,思聖也帶了她去看過他的醫生朋友,醫生說她的啞,是後天的不能出聲,不單是生理上有了毛病,心理上的病更重。言下就表示無能爲力。
要避免珍珠因啞巴的奚落而難過,他想搬得遠遠的,正巧老王——思聖的一個老同學——到了日本去了,他有一個別墅,思聖决定搬過去住,珍珠對這事,也非常高興,一方面環境清靜些,另一方面說氣腦也可以減少些。
搬進半山的第一夜 這一對小夫婦享受了神仙生活,遠處燈光一閃一閃,天上的星却這麽近。
珍珠在舒適中感到恐怖。
這一夜,他們依舊保持了分床而眠的習慣,珍珠看看窗外,月亮很明,思聖正面向着牆,八成巳睡着了,珍珠看着水銀似瀉進來的月光,一時難以闔眼,虫聲四起,並無其他聲晌。
將朦朧睡去,忽然驚覺,那是爲一種細碎輕微的脚步所驚醒,她看到窗口有一個黑影,珍珠驚得張大了眼睛,那黑影進了屋,珍珠無法叫醒思聖,但黑影已近,她用盡她所有的力氣,高聲喊出:「啊,賊,有賊!」
賊給趕走了,思聖也驚醒了,順手開燈,忙問:「在那兒,在那兒!」
「……跑出去了。」
思聖拿了一個花瓶趕出去,一不留神,連人帶花瓶跳倒在樓梯間,珍珠急忙趕過去扶住問:「怎麽樣?別跌壊了吧? 痛不痛?」
「不……痛,」他頓有所悟,狂喜喊道:「珍珠,你……你會說話了!」
珍珠也到這時才發覺,她顫抖着嗓子道:「我會說話了!」她以手指指自己的口,同時又再高聲道:「我會說話了,我會說話了!」終於喜極而流下眼淚來。
一家人都知珍珠開了口,迎小夫婦囘家,一到家裡,把珍珠給弄傻了,拿着相機的記者探得了消息,正等着探訪呢?
各報記者滿意而去,珍珠用四種方言答覆了他們的問題,關於她恢復發音,而且比本來能說話的人說得更好的原因,她說:「這都是我的耳朵平時教給我嗓子的。」
報上特寫她的消息,她成爲了新聞人物,那個賣假藥的錢永明,這時却來登門拜候。
他要珍珠說假話,說她那嗓子所以會恢復發聲,都是爲了吃百靈丸。
「好,我撒銷廣告,你們有辦法,自己去幹好了!」老羞成怒的錢永明,生氣離去,門口正値思聖。
「錢先生,爲什麽不坐坐?」
「你囘來了正好,告訴你,從今天起,咱們斷絶一切外交關係,不,斷絶ー切商業往來。」說罷,氣冲冲上了車。
又有一家電影公司的王老闆來接,洽請她拍電影,她也拒絶。結果,却選擇了一個廣吿公司的播音節目,有一個祕密的交換條件。
她講的是婦女家庭問題,主持聽衆來信答覆一切有關家庭的問題。
思聖爲了錢永明撒去廣吿事,煩惱已極,他那軒轅畫報,朝夕難保,又因珍珠能說話了,杜太與琥珀就每夜來聊天,而思聖想跟太太談談,太太又爲了公事,上電台去播音了。
「她爲人家家庭謀幸福,自己家裡的幸福却置之不顧。」思聖就有這種想法。
他們兩口子吵起架來了,一個說:「你知不知道我的畫報沒有廣吿就幹不下去?」
「那你就再去找幾個廣告好了。」她冷冷地。
「你知不知道市面不好?」
「市面不好,我有什麽辦法?」她心種對他失却了錢永明廣吿如此緊張,深不以爲然。
吵架無結果,珍珠终於在播音室開始播音,介紹員介紹杜珍珠小姐不僅懂各種方言,而且是個家庭問題的專家。
在家失望與憤懣的楊思聖這時也在收音機畔聽,他聽到報告員說:「杜小姐自從會講話之後,自己的家庭就幸福了。」他ー聽就氣,擰熄了那具收音機。
珍珠在電台上受人歡迎,聲譽一天比一天爲高,但思聖的苦悶,也一天比一天爲深。他常獨自一人「悶」在咖啡室中,而咖啡室裡的收音機,常常又播放珍珠的幸福家庭節目,不但如此,爲了聽眾的歡迎,珍珠又加多了一小時的節目,思聖覺得這真已忍無可忍,他趕到她播音的電台裡去,那個節目是許多聽衆到電台提出問題的,思聖就在那些爲聽衆們排着的一張空位上坐下來,珍珠正在整理來信,偶然抬頭,見思聖也在,爲之愕然。
思聖的領帶沒有打好,珍珠在内示意,但他不懂,依舊左顧右盼,聽眾甲推推他道:
「請你把領帶打好,尊重點!」
思聖沒好氣,就打打正,音樂此刻剛剛停止。
珍珠微笑向聽衆道:「因爲時間關係,請大家說得簡明一些,現在請舉手。」
思聖與另一個聽衆同時舉起手來。珍珠點了另一個聽衆,他站起來說:「我有個很嚴重的問題,」他頓了一頓 又說:「我的太太整天不管家,天天不在家裡,儘在外頭打麻將,簡直不像話。」
杜老夫婦在家正聽着收音機呢!老太太一聽到那話,不免有點窘,杜子健掀髯道:「聽見沒有,簡直不像話。」
杜太白了他一眼,但來不及置答,收音機又說話了:
「這個,你也有不對的地方,你不管家,太太也不管家,事情就糟了,我想你太太總喜歡打麻將,這或者是因爲她沒有其他消遣之故,你如果常常陪她,也許就好一點。」
這句話講完,杜太太哈哈大笑,子健關上收音機道:「沒想到珍珠倒把我們教訓了。」
杜太太聽不見什麽了,一看,收音機已關,急道:「別關上呀,開開!」
這時正聽到思聖也提問題了:「我也有個問題,假如太太使丈夫失業了,自己出來做事,怎麽辦?」
「對不起,我們這節目不囘答『假如』的家庭問題。」
思聖更氣了,他說:「那更好,剛才我說的那位太太就是我的太太。」
「我爲你高興,你有這末一個好太太,肯在你失業以後,出來做事,你還有什麽問題?」
思聖愈問愈光火,竟忘記了這是播音室,大肆咆哮起來,觀衆大起反感,幾乎打作一團,連珍珠也無法繼續說下去,離座勸架。
杜老夫婦愈聽愈不對,杜太太急道:「他們怎末鬧到播音室裡去了?」
「我得去看看去!」說罷,老人也不顧忘了戴帽,一股氣兒的奔出去。
思聖被電台上的管理員、報吿員及聽衆們攆了出來,領帶不正了,頭髮亂了,面色也鐵青的了。
珍珠也趕着出來,但思聖巳走遠去了,她才囘進播音室,杜老也趕到了。
「這……這是怎麽一囘事?」他喘息着道:「怎麽家庭問題專家,自己也出了家庭問題了?」
珍珠哭笑不得,把事情吿訴了他,正說時,廣吿公司的經理也來了,氣急敗壊的道︰
「杜小姐,我正要找你。」
「我也正有事要問你,軒轅畫報的廣吿,您……」
「這個不成問題,明天我就派人去接頭,剛才電器公司已經派人把電器樣品都給你送了一份去,請代設計廣吿圖樣。」
「謝謝您!」
「至於妳的節目……」
「决定不繼續下去。」
「杜小姐,請妳再考慮考慮,明天再說,我先走一步啦!」廣吿經理站了起來,與杜老一頷首,走了。
杜子健莫名其妙,忙問究竟。
珍珠拿出一張合同給父親看:「爸爸,你看看這張合同!」
杜老恍然大悟,葫蘆裡還有藥,原來珍珠播音,全是爲軒轅畫報的廣告,她是與廣告主任談好了條件的。
囘到家,一邊是催討印刷費的,爲了軒轅畫報,一方面是電影公司老闆、唱片公司幹事來接洽珍珠上銀幕及灌音的事,兩種完全不同的嘴臉,思聖忍不得半分鐘,他想立刻離去,於是寫了一張紙條,留在家中,寫的是:「珍珠,都是你多嘴惹出來的禍,還是原來不說話的好,我走了,大丈夫一言旣出駟馬難追!」
他又走到杜家客廳,杜老正打電話找他呢!他對着電話道:「思聖,我要你到我這兒來一趟。」
思聖在後邊答應了,杜老囘過頭來,正是驚喜交集。
「咳,你真是個糊塗虫。」一邊說,一邊往胸前掏合同。
「是,我是糊塗虫,誰想到她說話以後,鬧了個天翻地覆,連好好的家都快拆了。」
「她要不是啞巴,準不嫁給你吶,現在她會說話了,還不便宜了你。」
「謝謝,我倒情願她是個啞巴,女人的嘴最好光吃飯,不講話。」
一老一少又拌上嘴了,思聖要他到他家去看看,家鬧成什麽樣了?
家裡已佈置得井井有條,阿金倒出冰水,開上風扇,思聖冷笑道:「是她發了財還是怎麽的?」
「你還不知道這些電器都是那兒來的?」
「那兒來的?」
杜老把合同拿出來,思聖大喜過望・「他們登多少廣吿呀?怎麽珍珠事先不吿訴我?」這時又想起來了:
「珍珠呢?」
阿金說:「小姐囘來,看了你留的紙條,大哭一場,出去了。」
這時雨很大,急得思聖團團亂轉。
珍珠囘來了,杜太也來了,她罵思聖:「我的女兒犯了什麽七出之條,你說你走呀,你爲什麽不走呀?」
思聖打拱作揖賠不是,但,杜太說:「珍珠舊病復發了,嗓子又給你氣啞了。」
這對思聖,無異是晴天霹靂,他走到珍珠身邊,哭似的道:「珍珠,你眞的又說不出話來啦?」
珍珠沒有理他。「珍珠,你還生我的氣嗎?我都認錯了,你還不理我,我恨不得你罵我一頓都好。噯,你眞的又不能講話啦?你試試看。」
珍珠不出聲,裝着非常難過的表情,思聖更難過了,他懊喪地道:「我眞該死,倒霉,現在一切都好了,你又啞了,都怪我糊塗,現在可怎麽辦呢?」
他團團亂轉,走來走去,不小心,把那小狗踩了一脚,小狗被踩,哇的直叫,奔向門外去,珍珠這時一急,忘了自己還在裝啞,竟說出話來了,她怒冲冲的指着思聖。
「你怎麽連我們家的小狗都欺負?」
這真是一陣春雷,使他破涕爲笑,一時間萬物囘春,他高興得直跳起來道:
「呀,你這個壞東西,誠心裝啞來嚇我!」
珍珠也笑了,思聖把她抱起,一連轉了幾個圈,倒在沙發椅上,珍珠掙扎着道:「思聖,思聖,你……唔,眞討厭,一會兒阿金來了,多不好意思呢!」
天氣很高爽,窗外枝上的鳴蟬唱出「知了」歌,這一對年青人,在互相瞭解下,尋得了他們更幸福的生活,一條小狗往門裡張望一下,不好意思似的默默退出門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