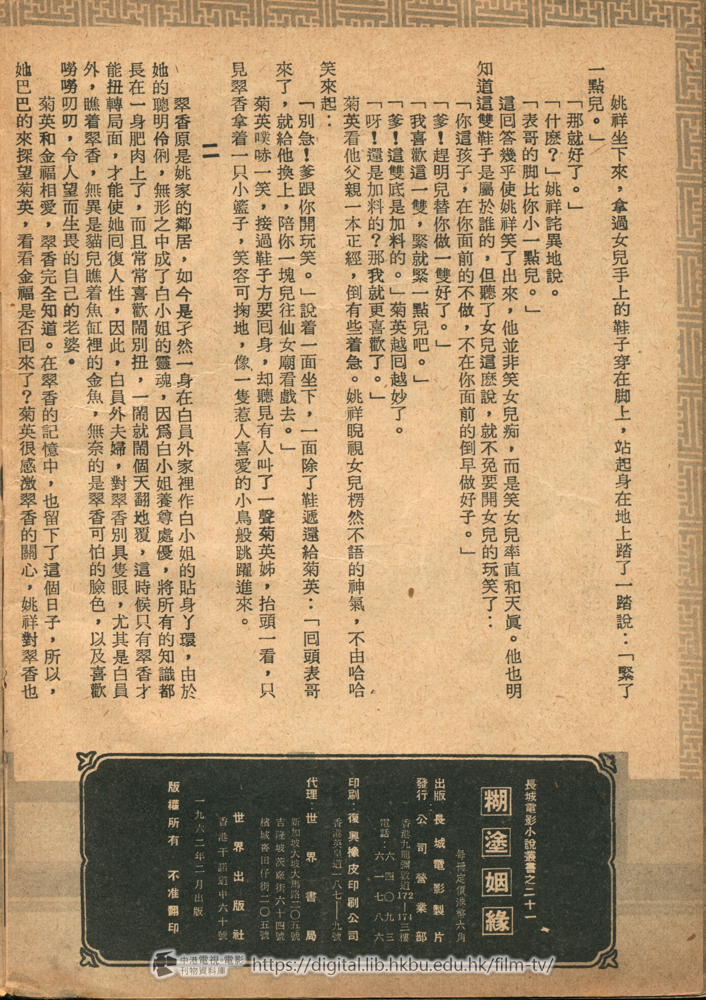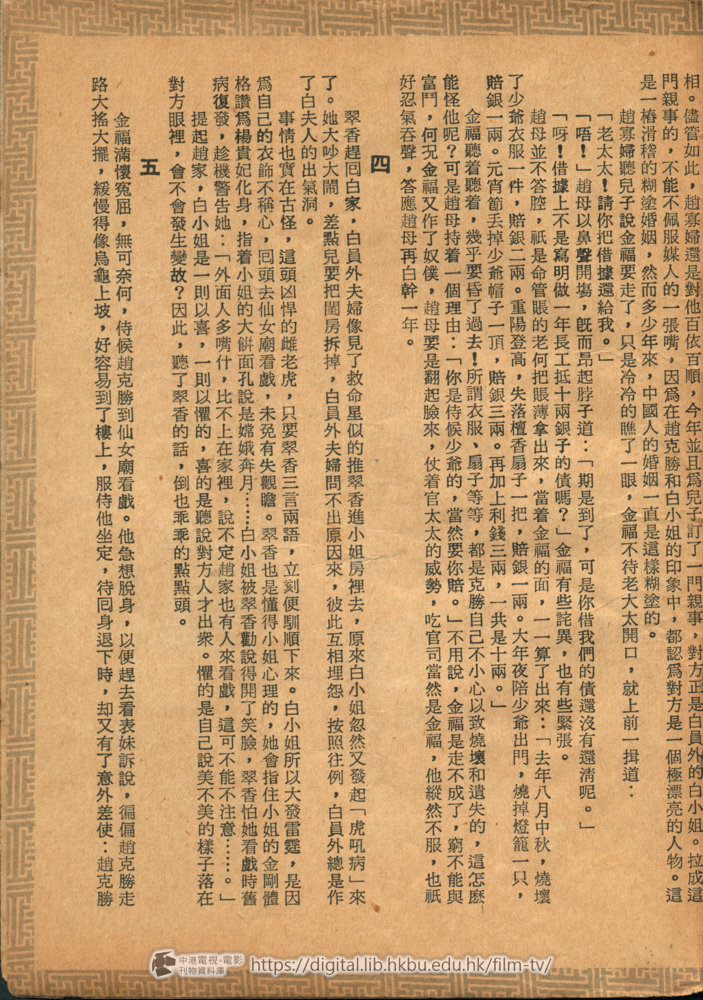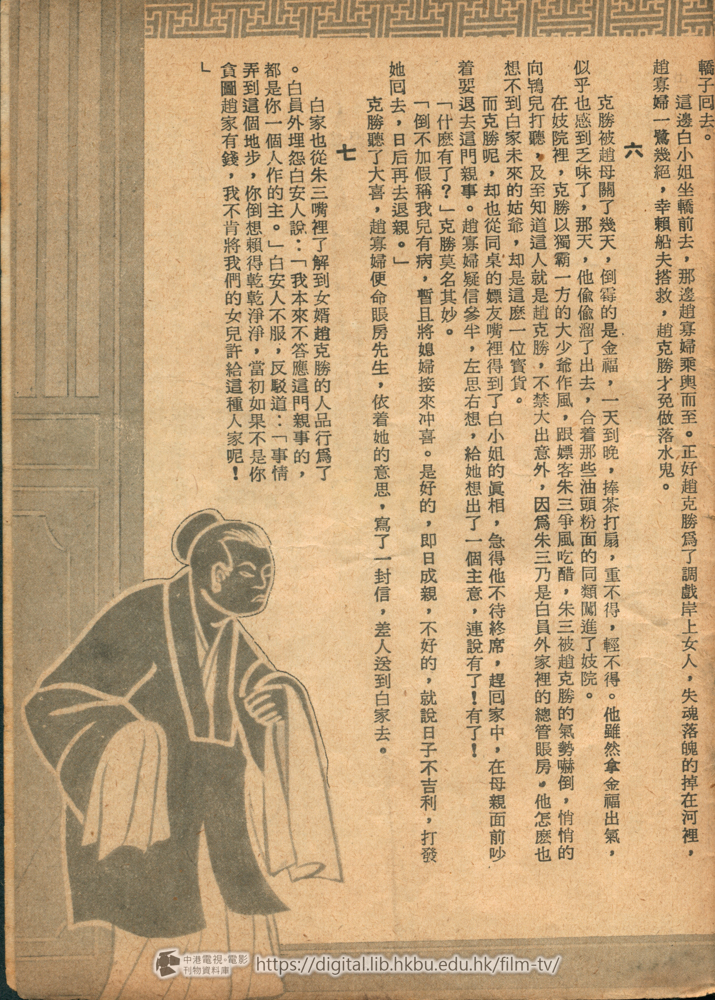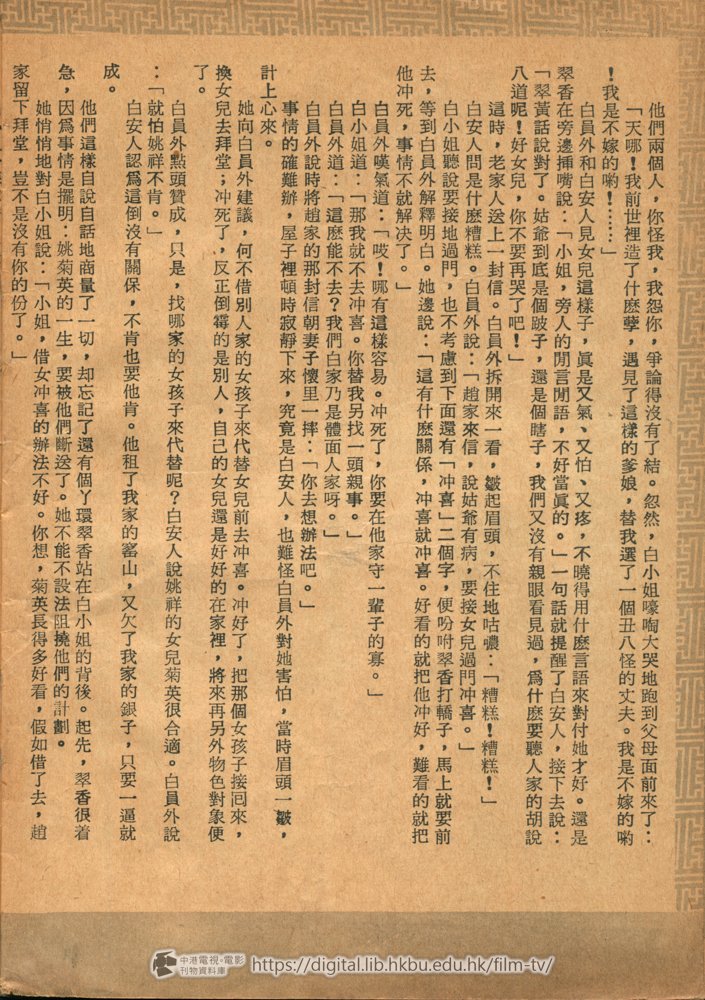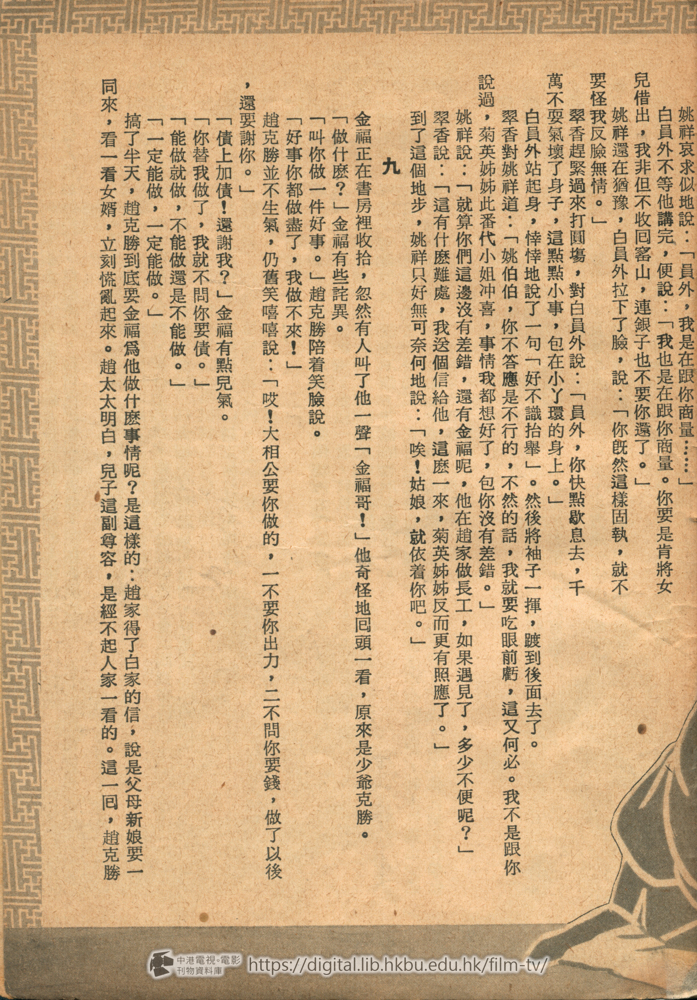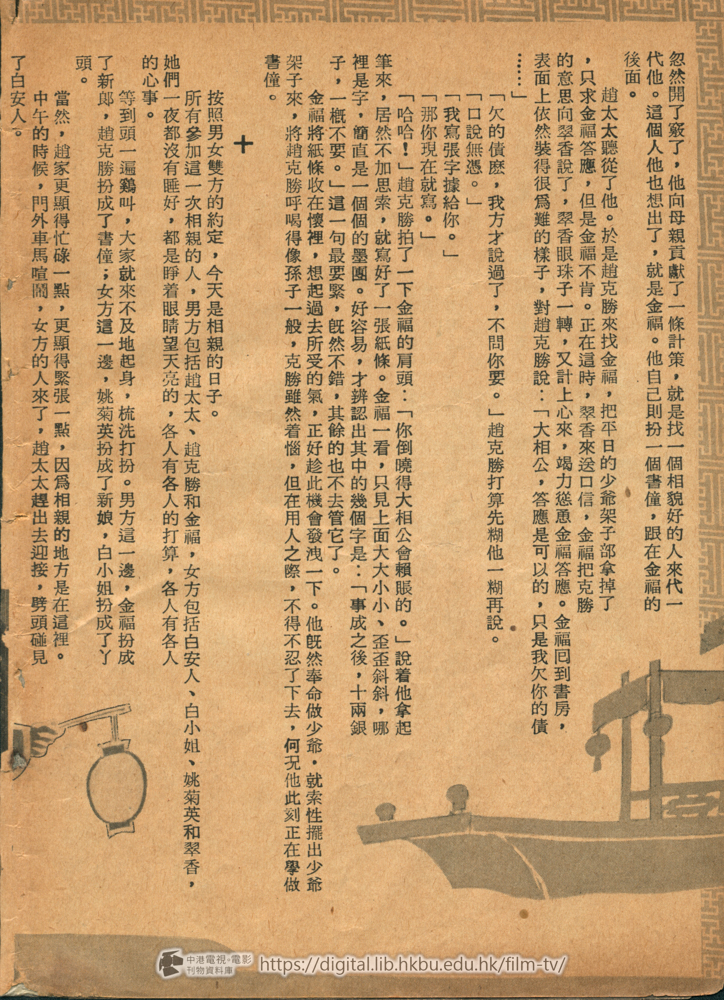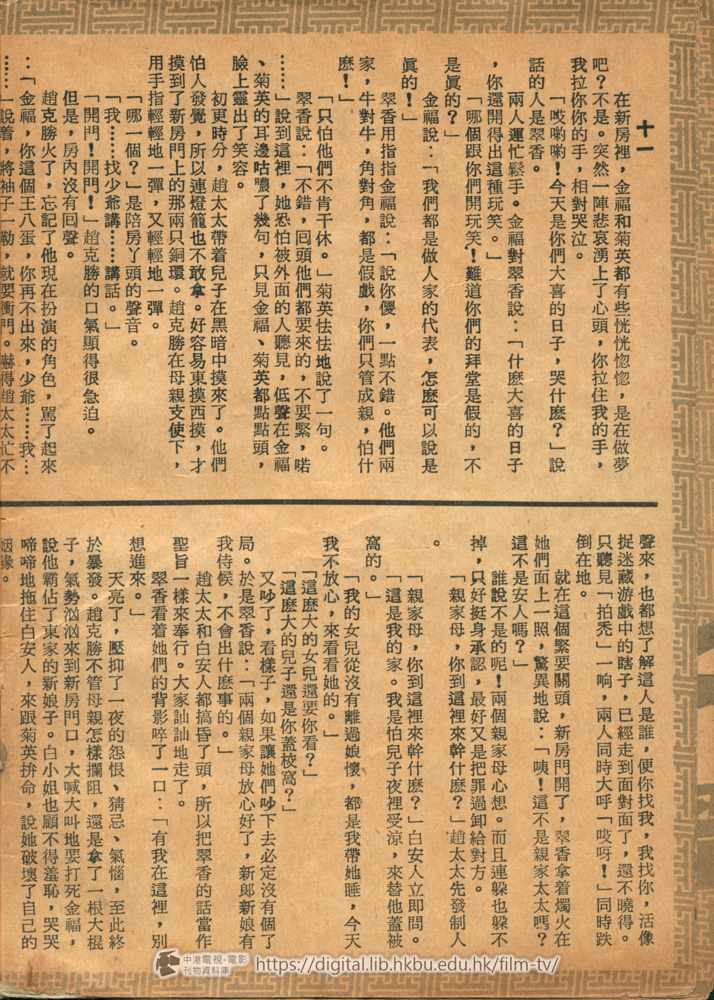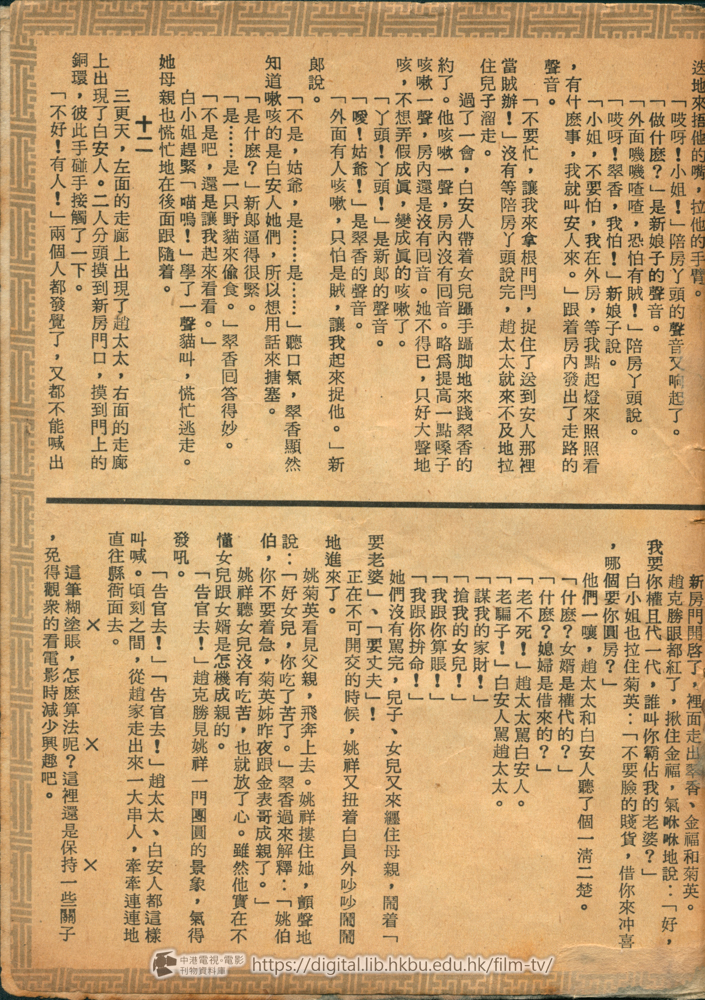電影小説
糊塗姻緣
ー
落日餘暉,映紅山頭,遍野的稻穗,迎風搖晃,宛若橙色的波浪,莊稼漢沿了阡陌囘家,童子伏在牛背上,拉着牛鼻繩慢步而行。
在一家簡陋的庭園內,長着一株挺拔的石榴樹,榴花吐紅,夾着在繁茂的綠葉中間,彷彿美人臉上的胭脂。樹下坐着一個粗壯的中年男子,彎着身體,正伸手到脚盆裡洗濯他的雙足,忽然,一陣淸脆悅耳的歌聲,從屋子裡傳出來,他不由側耳凝聽:
「春風吹過夏雨來,靑山翠谷眞可愛,花兒香,蝶徘徊,蜂兒飛舞將蜜採,一雙去呀一對來,哥呀哥!小妹妹眼望榴花開啊!七不龍冬得兒呀嗨,哥呀哥!小妹妹眼望榴花開。」
這個風霜滿面的中年人,跟着那陣歌聲,流靈出欣慰之色。他感慨地㸃了一㸃頭,一眼瞥見門檻內人影晃動,使立即囘過頭來,裝着不曾聽見似的繼續洗濯他的雙足,然而猶不免偸偸地用眼角注意。
門前出現了一個捧着盤子的少女,她生得眉靑目秀,嬌艷動人,白嫩的臉蛋兒上,充滿着無可遏制的喜悅,一面輕盈的向庭園中走去,一面繼續唱道:
「榴花開來紅似火,牛郞織女到銀河,銀河上,萬丈波,咫尺天涯可奈何,謝喜鵲呀把橋做,哥呀哥!我二人相會笑呵呵喲,七不龍冬得兒呀嗨,哥呀哥,我二人相會笑呵呵!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比織女會牛郞,月也圓,花也好,月圓花好人成雙,你盼望呀我盼望,哥呀哥!從今後可把心願償喲,七不龍冬得兒呀嗨,哥呀哥!從今後可把心願償。」
她唱時將盤子裡的盃筷移放到桌子上,端起那樽特備的酒瓶,深情蜜意地看了一眼,輕輕放下,却沒有提防一陣瞭亮的笑聲起自背後。
「哈……今日裡共把心願償。對!好!」
「爹!」少女羞澀地叫了一聲,丢下盤子,反身過去端起脚桶,往牆角走去。
他們是父女倆——姚祥和菊英。這屋子裡沒有第三個人。姚祥租了白員外家的窰山作工爲活,只能勉强過日子,因此自從死了老婆之後,也就無力再娶。菊英在父親辛勞哺育下逐漸成長,當她知事之初,便以她小小的力氣幫助父親料理家務了。她愛父親,父親疼她,在貧苦的環境中,倒洋溢着極富人情味的骨肉之愛。
這一天,恰是乞巧節日,姚祥已知道女兒的心事,但不便直說,他趁女兒替他去傾倒洗脚水時,拿着旱煙桿走到桌子前,指一指桌上的酒說:
「菊英!你買了酒啦?」
「買了。」
「還是你想得週到,今日應該有酒。」
「爹!」菊英笑了起來:「瞧你看見酒就樂!」
「不!我問你,今日是什麽日子?」
「什麽日子?」菊英有些領悟,但她佯作不知地搖搖頭:「我不知道啊。」
「孩子!別裝傻了,你金福表哥在趙家總算熬滿了這一年,今日是你們兩個——。」
「爹!你又來了。」菊英含羞地一扭身,朝屋子裡進去。姚祥滿懷高興的看着女兒的背影在門前消失,囘身拿起酒瓶,注視有頃,喟然地說了一句:「該給他們辦喜事了。」
「爹!」姚祥一聽女兒的聲音,便將酒瓶放下,側轉了身體,只見菊英拿着一雙新做的布底鞋跑到他面前:
「爹!你穿穿看,不知大小怎麽樣?」
姚祥坐下來,拿過女兒手上的鞋子穿在脚上,站起身在地上踏了一踏說:「緊了 一㸃兒。」
「那就好了。」
「什麽?」姚祥詫異地說。
「表哥的脚比你小一㸃兒。」
這囘答幾乎使姚祥笑了出來,他並非笑女兒痴,而是笑女兒率直和天眞。他也明知道這雙鞋子是屬於誰的,但聽了女兒這麽說,就不免要開女兒的玩笑了:「你這孩子,在你面前的不做,不在你面前的倒早做好子。」
「爹!趕明兒替你做一雙好了。」
「我喜歡這一雙,緊就緊一㸃兒吧。」
「爹!這雙底是加料的。」菊英越囘越妙了。
「呀!還是加料的?那我就更喜歡了。」
菊英看他父親一本正經,倒有些着急。姚祥睨視女兒楞然不語的神氣,不由哈哈笑來起:
「別急!爹跟你開玩笑。」說着一面坐下,一面除了鞋遞還給菊英:「囘頭表哥來了,就給他換上,陪你一塊兒往仙女廟看戲去。」
菊英噗哧一笑,接過鞋子方要囘身,却聽見有人叫了一聲菊英姊,抬頭一看,只見翠香拿着一只小籃子,笑容可掬地,像一隻惹人喜愛的小鳥般跳躍進來。
二
翠香原是姚家的鄰居,如今是孑然一身在白員外家裡作白小姐的貼身丫環,由於她的聰明伶俐,無形之中成了白小姐的靈魂,因爲白小姐養尊處優,將所有的知識都長在一身肥肉上了,而且常常喜歡閙別扭,一閙就閙個天翻地覆,這時候只有翠香才能扭轉局面,才能使她囘復人性,因此,白員外夫婦,對翠香別具隻眼,尤其是白員外,瞧着翠香,無異是貓兒瞧着魚缸裡的金魚,無奈的是翠香可怕的臉色,以及喜歡嘮嘮叨叨,令人望而生畏的自己的老婆。
菊英和金福相愛,翠香完全知道。在翠香的記憶中,也留下了這個日子,所以,她巴巴的來探望菊英,看看金福是否囘來了?菊英很感激翠香的關心,姚祥對翠香也像自己女兒一樣。父女想留翠香吃飯,但翠香要趕囘去侍候白小姐到仙女廟去看戯,因此婉謝了,她問姚祥,什麽時候可以喝菊英的喜酒?
姚祥聽了,含笑一指桌上的酒說:「你瞧!這不是喜酒?」
「哦!這麽快?」翠香別轉道向菊英道:「金福哥囘來了?」
「沒有呢,爹在說笑話。」
翠香上前一步,舉着籃子向菊英笑咪咪說:「今天當然囘來了,恭喜你。這是七巧果,祝你們表兄妹甜甜蜜蜜,團團圓圓。」翠香頓了一頓,又帶着探問的口氣:「哎!你們的好日了定了沒有?」
金福的歸期,在菊英心中自然忘記不了,但這時眼看太陽就快落山,猶未見金福到來,她心裡的焦急,正感無處可訴之苦,一聽翠香動問,不由雙黛微蹙,抱怨地說了一句:「人還沒有囘來呢!」頑皮的翠香,馬上依樣葫蘆的學着說:「人還沒有囘來呢!瞧你這副急相。」
菊英紅暈雙頰,啐了翠香一口,翠香轉身對姚祥說:「姚伯伯,以後別疼她了,她現在已經一心一意的在表哥身上了。」
「可不是?」姚祥指一指桌上那雙鞋子道:「你看,人沒來,鞋都巳經做好了,還是雙料底的呢。」
「不害臊!」翠香嗤然一笑。菊英扭身欲避,却給翠香拉住。姚祥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如果不是翠香急着要趕囘去,這個難得展眉的辛苦人,也許有更多的笑話要說呢。
三
在趙家,金福懷着菊英一樣的心情,忙着收拾行囊。他想起去年七月,親娘去世時的慘苦情形,要不是表妹殷殷相勸,爲他奔走,挽人向趙寡婦那裡吿貸了十兩銀子,那悲慘的局面將不知如何收拾?雖說趙寡婦拿出十兩銀子,是要用自己的身體作抵押的,而且因此也使表妹傷心落淚,然而表妹待他的一番恩情,是叫他刻骨難忘的。如今,一年的期限滿了,他欠趙家的債也還淸了,囘頭見了表妹,彼此該多麽快樂啊!想到這裡,不由格外的喜形於色。
忽然,趙家小丫環奔來吿訴金福,說少爺囘家,正在發脾氣,叫金福快去。金福暗忖,從現在起,我再不是趙家的奴僕了,趙克勝還發什麽脾氣?可是轉念一想,趙家母子都是鬼靈精怪,在尙未跨出這一條惡門檻之前,還是小心一㸃好,何况那張借據仍在他們手裡,於是放下手裡的東西,跟着去見趙克勝。
克勝一見金福,擺着少爺架子大駡混賬。金福蹩着一肚子冤氣朝肚裡嚥,客客氣氣向克勝辭行。這一來,倒頗使克勝尷尬,怎麽?金福這小子要離開這裡了?那麽叫我大少爺呼喝誰去?他有些惱恨,也有些着急,怔怔的注視金福半晌,一股勁兒去找娘說話。
趙寡婦依靠丈夫遺下來的產業,盤盤剝剝過日子,宅肥屋潤,並不比丈夫在世做官時遜色,這就顯出她的能幹以及天生的一種善於計算的性格。在她認爲美中不足的,是自己肚子裡落下的却是這麽一塊寳貝材料——趙克勝﹔他除了吃喝、賭錢之外,見了美貌子子還能裝出種種醜態。而事實上,他確乎生成一副與衆不同的醜相。儘管如此,趙寡婦還是對他百依百順,今年並且爲兒子訂了一門親事,對方正是白員外的白小姐。拉成這門親事的,不能不佩服媒人的一張嘴,因爲在趙克勝和白小姐的印象中,都認爲對方是一個極漂亮的人物。這是一樁滑稽的糊塗婚姻,然而多少年來,中國人的婚姻一直是這樣糊塗的。
趙寡婦聽兒子說金福要走了,只是冷冷的瞧了一眼,金福不待老大太開口,就上前一揖道:
「老太太!請你把借據還給我。」
「唔!」趙母以鼻聲開塲,旣而昂起脖子道:「期是到了,可是你借我們的債還沒有還淸呢。」
「呀!借據上不是寫明做一年長工抵十兩銀子的債嗎?」金福有些詫異,也有些緊張。
趙母並不答腔,祇是命管賬的老何把賬薄拿出來,當着金福的面,一一算了出來:「去年八月中秋,燒壞了少爺衣服一件,賠銀二兩。重陽登高,失落檀香扇子一把,賠銀一兩。大年夜陪少爺出門,燒掉燈籠一只,賠銀一兩。元宵節丟掉少爺帽子一頂,賠銀三兩。再加上利錢三兩,一共是十兩。」
金福聽着聽着,幾乎要昏了過去!所謂衣服、扇子等等,都是克勝自己不小心以致燒壞和遺失的,這怎麽能怪他呢?可是趙母持着一個理由:「你是侍候少爺的,當然要你賠。」不用說,金福是走不成了,窮不能與富鬥,何况金福又作了奴僕,趙母要是翻起臉來,仗着官太太的威勢,吃官司當然是金福,他縱然不服,也祇好忍氣吞聲,答應趙母再白幹一年。
四
翠香趕囘白家,白員外夫婦像見了救命星似的推翠香進小姐房裡去,原來白小姐忽然又發起「虎吼病」來了。她大吵大鬧,差㸃兒要把閨房拆掉,白員外夫婦問不出原因來,彼此互相埋怨,按照往例,白員外總是作了白夫人的出氣洞。
事情也實在古怪,這頭凶悍的雌老虎,只要翠香三言兩語,立刻便馴順下來。白小姐所以大發雷霆,是因爲自己的衣飾不稱心,囘頭去仙女廟看戲,未免有失觀瞻。翠香也是懂得小姐心理的,她會指住小姐的金剛體格讚爲楊貴妃化身,指着小姐的大餅面孔說是嫦娥奔月……白小姐被翠香勸說得開了笑臉,翠香怕她看戲時舊病復發,趁機警吿她:「外面人多嘴什,比不上在家裡,說不定趙家也有人來看戲,這可不能不注意……。」
提起趙家,白小姐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喜的是聽說對方人才出衆。懼的是自己說美不美的樣子落在對方眼裡,會不會發生變故?因此,聽了翠香的話,倒也乖乖的㸃㸃頭。
五
金福滿懷寃屈,無可奈何,侍候趙克勝到仙女廟看戲。他急想脫身,以便趕去看表妹訴說,徧偏趙克勝走路大搖大擺,緩慢得像烏龜上坡,好容易到了樓上,服侍他坐定,待囘身退下時,却又有了意外差使:趙克勝順手拿起一隻桃子,指着對面座位上一個艷麗少婦,命金福送過去。
「少爺!你又來了。」金福直立不動。
「怕甚麽?她是少爺的老相好,去!就說我趙克勝送的。」
金福明知克勝胡鬧,頗感疇躇,但轉念一想,自己急着要去見表妹,管他識與不識,送去了事。於是,移動脚步,循着那艷婦坐的方向走去。趙克勝賊忒嬉嬉,突出一對色眼,遙遙的直盯着那個婦人,靜觀反應。他見婦人笑容滿面立起來招手,心花爲之怒放,自己也趕緊站起來把手一揚,算是答禮,正想撩袍端帶離座時,却見婦人身旁來了一個赳赳武夫,和婦人親熱相見,趙克勝大吃一驚,立即意識到自己闖下大禍了,欲待叫住金福,不想金福已拿着桃子到了婦人面前,趙克勝暗叫壞了,慌忙縮短身體,躱到椅子背後去。
他眼見武夫橫眉怒目,殺氣騰騰的拔出刀來,幾乎把胆嚇破,顧不得面子不面子,像狗一樣的在看客 脚下爬了出去,至於墮樓丟了鞋子都不理,只是捧着腦袋朝外逃。武夫是給婦人勸住了。金福找不到少爺,却拾到了少爺的一只鞋,他害怕這筆損失又會算在他的頭上,不由又恨又氣地去找尋趙克勝。而克勝呢,逃到外面,便給豬朋狗友拉到畫舫上去賭錢了。
金福沒有找到少爺,却遇見翠香,就把自己的寃屈向翠香訴了一訴,並且求翠香去叫菊英到仙女廟來。翠香知道主人都在看戲,這時候未必會使喚,便答應了金福之請,可是半路上就碰着了菊英。
菊英正是來找金福的。她獲悉了金福受趙家欺侮,心裡也着實氣憤,但爲了避免金福激動,却相反的 加以勸慰。二人並肩相依,對着耿耿星河,都覺得黯然神傷,正在沉默無言時,却聽見廟外人聲鼎沸,笑 聲喧天,相偕着上前一望,却見白小姐就地打滾,涕淚交流,原來她不自檢㸃,和看客發生衝突,竟然打 起出手來了,看客怕她如狼如虎,相與逃遁,白小姐餘怒未息,追着追着,失了對手,素性拉開嗓門,當 衆表演潑相,慌得白員外夫婦手足無措,幸虧翠香在白小姐耳邊提出警吿;這才偃旗息鼓,拉拉扯扯坐上轎子囘去。
這邊白小姐坐轎前去,那邊趙寡婦乘輿而至。正好趙克勝爲了調戲岸上女人,失魂落魄的掉在河裡,趙寡婦一鷺幾絕,幸賴船夫搭救,趙克勝才免做落水鬼。
六
克勝被趙母關了幾天,倒霉的是金福,一天到晚,捧茶打扇,重不得,輕不得。他雖然拿金福出氣,似乎也感到乏味了,那天,他偸偸溜了出去,合着那些油頭粉面的同類闖進了妓院。
在妓院裡,克勝以獨霸一方的大少爺作風,跟嫖客朱三爭風吃醋,朱三被趙克勝的氣勢嚇倒,悄悄的向鴇兒打聽,及至知道這人就是趙克勝,不禁大出意外,因爲朱三乃是白員外家裡的總管賬房。他怎麽也想不到白家未來的姑爺,却是這麽一位寳貨。
而克勝呢,却也從同桌的嫖友嘴裡得到了白小姐的眞相,急得他不待終席,趕囘家中,在母親面前吵着要退去這門親事。趙寡婦疑信參半,左思右想,給她想出了一個主意,連說有了!有了!
「什麽有了?」克勝莫名其妙。
「倒不加假稱我兒有病,暫且將媳婦接來冲喜。是好的,即日成親,不好的,就說日子不吉利,打發 她囘去,日后再去退親。」
克勝聽了大喜,趙寡婦便命賬房先生,依着她的意思,寫了一封信,差人送到白家去。
七
白家也從朱三嘴裡了解到女婿趙克勝的人品行爲了。白員外埋怨白安人說:「我本來不答應這門親事的,都是你一個人作的主。」白安人不服,反駁道:「事情弄到這個地步,你倒想賴得乾乾淨淨,當初如果不是你貪圖趙家有錢,我不肯將我們的女兒許給這種人家呢!」
他們兩個人,你怪我,我怨你,爭論得沒有了結。忽然,白小姐嚎啕大哭地跑到父母面前來了:
「天哪!我前世裡造了什麽孽,遇見了這樣的爹娘,替我選了一個丑八怪的丈夫。我是不嫁的喲!我是不嫁的喲!」
白員外和白安人見女兒這樣子,眞是又氣、又怕、又疼,不曉得用什麽言語來對付她才好。還是翠香在旁邊揷嘴說:「小姐,旁人的閒言閒語,不好當眞的。」一句話就提醒了白安人,接下去說:「翠黃話說對了。姑爺到底是個跛子,還是個瞎子,我們又沒有親眼看見過,爲什麽要聽人家的胡說八道呢!好女兒,你不要再哭了吧!」
這時,老家人送上一封信。白員外拆開來一看,皺起眉頭,不住地咕噥:「糟糕!糟糕!」
白安人問是什麽糟糕。白員外說:「趙家來信,說姑爺有病,要接女兒過門冲喜。」
白小姐聽說要接地過門,也不考慮到下面還有「冲喜」二個字,便吩咐翠香打轎子,馬上就要前去,等到白員外解釋明白。她邊說:「這有什麽關係,冲喜就冲喜。好看的就把他冲好,難看的就把他冲死,事情不就解决了。」
白員外嘆氣道:「哎!哪有這樣容易。冲死了,你要在他家守一輩子的寡。」
白小姐道:「那我就不去冲喜。你替我另找一頭親事。」
白員外道:「這麽能不去?我們白家乃是體面人家呀。」
白員外說時將趙家的那封信朝妻子懷里一摔:「你去想辦法吧。」
事情的確難辦,屋子裡頓時寂靜下來,究竟是白安人,也難怪白員外對她害怕,當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她向白員外建議,何不借別人家的女孩子來代替女兒前去冲喜。冲好了,把那個女孩子接囘來,換女兒去拜堂﹔冲死了,反正倒霉的是別人,自己的女兒還是好好的在家裡,將來再另外物色對象便了。
白員外㸃頭贊成,只是,找哪家的女孩子來代替呢?白安人說姚祥的女兒菊英很合適。白員外說 :「就怕姚祥不肯。」
白安人認爲這倒沒有關保,不肯也要他肯。他租了我家的窰山,又欠了我家的銀子,只要一逼就成。
他們這樣自說自話地商量了一切,却忘記了還有個丫環翠香站在白小姐的背後。起先,翠香很着急,因爲事情是擺明:姚菊英的一生,要被他們斷送了。她不能不設法阻撓他們的計劃。
她悄悄地對白小姐說:「小姐,借女冲喜的辦法不好。你想,菊英長得多好看,假如借了去,趙家留下拜堂,豈不是沒有你的份了。」
白小姐一聽不錯,連忙將翠香的這番話對母親說了。
白安人想了一想,又想出了一個「兩全之計」。叫白小姐扮做丫頭,跟了假新娘同去。到了那邊,見機行事。不拜堂便罷,要是拜堂,先且不動,等到進洞房的時候,再將白小姐換囘姚菊英,不是什麽問題也沒有了!
白小姐快活得拍手跳脚。翠香却早就料到白安人有這一着,於是又悄悄對白小姐說:「小姐,這還是使不得。白家只有你一位小姐,那個不曉得,要是在趙家拜了堂,人家當你已經出嫁,再沒有人上門求親,你不是做一輩子的老處女?」
白小姐的一團高興,被這一句冷水澆滅了。愁眉苦臉地問翠香:「那怎麽辦呢?」
翠香笑笑,說:「這有什麽難處,反正安人也去的,你叫她跟趙家說,要相相姑爺,相得好,就換你拜堂;相得醜,你們當天就囘來,囘來了就退了這門親。」
這一囘,白安人走到了翠香算好的這條路上去。他們一面囘復趙家,一面差人去叫姚祥,翠香乘機討了這差使。
八
翠香找到姚祥,將白家打的主意吿訴了他,幷再三地安慰他說:「姚伯伯,你只管答應好了,一切都有我,包你不讓菊英姊姊吃虧。」
姚祥起先一聽,自然很着急,後來 翠香拍胸担保,才稍爲好一㸃,不過終究有些不放心。他遲疑地隨着翠香去白家,一邊走,一邊想:「能夠不答應,還是不答應的好。」
往常,白員外的眼裡那裡會有姚祥這樣的人。可是今天,他的態度大爲兩樣。姚祥向他請安,他不但拱手還禮,而且請姚祥在一旁坐下。
寒喧了幾句,白員外就將借女冲喜的事情說出。
姚祥忙陪笑臉,說:「員外,小女已經許了人家,這個……請員外原談,收囘成命吧。」
白員外眉頭一皺,沉吟一會,便說:「也好,那你租的窰山,欠的銀子,我也要一起收囘。」
姚祥聽見這句話,坐不住了,向白員外打恭作揖地說:「員外,你老人家開開恩吧,這是萬萬不能收囘的啊!」
白員外說:「要我不收囘也可以,只要你答應借女冲喜。」
姚祥說:「你……你這不是在逼我麽?」
白員外冷笑一聲,說:「借不借在你,收不收在我,哪個逼你!
姚祥哀求似地說:「員外,我是在跟你商量……」
白員外不等他講完,便說:「我也是在跟你商量。你要是肯將女兒借出,我非但不收囘窰山,連銀子也不要你還了。」
姚祥還在猶豫,白員外拉下了臉,說:「你旣然這樣固執,就不要怪我反臉無情。」
翠香趕緊過來打圓塲,對白員外說:「員外,你快㸃歇息去,千萬不耍氣壞了身子,這㸃㸃小事,包在小丫環的身上。」
白員外站起身,悻悻地說了一句「好不識抬舉」。然後將袖子一揮,踱到後面去了。
翠香對姚祥道:「姚伯伯,你不答應是不行的,不然的話,我就要吃眼前虧,這又何必。我不是跟你說過,菊英姊姊此番代小姐冲喜,事情我都想好了,包你沒有差錯。」
姚祥說:「就算你們這邊沒有差錯,還有金福呢,他在趙家做長工,如果遇見了,多少不便呢?」
翠香說:「這有什麽難處,我送個信給他,這麽一來,菊英姊姊反而更有照應了。」
到了這個地步,姚祥只好無可奈何地說:「唉!姑娘,就依着你吧。」
九
金福正在書房裡收拾,忽然有人叫了他一聲「金福哥!」他奇怪地囘頭一看,原來是少爺克勝。
「做什麽?」金福有些詫異。
「叫你做一件好事。」趙克勝陪着笑臉說。
「好事你都做盡了,我做不來!」
趙克勝並不生氣,仍舊笑嘻嘻說:「哎!大相公要你做的,一不要你出力,二不問你要錢,做了以後,還要謝你。」
「債上加債!還謝我?」金福有㸃兒氣。
「你替我做了,我就不問你要債。」
「能做就做,不能做還是不能做。」
「一定能做,一定能做。」
搞了半天,趙克勝到底要金福爲他做什麽事情呢?是這樣的:趙家得了白家的信,說是父母新娘要一同來,看一看女婿,立刻慌亂起來。趙太太明白,兒子這副尊容,是經不起人家一看的。這一囘,趙克勝忽然開了竅了,他向母親貢獻了一條計策,就是找一個相貌好的人來代一代他。這個人他也想出了,就是金福。他自己則扮一個書僮,跟在金福的後面。
趙太太聽從了他。於是趙克勝來找金福,把平日的少爺架子部拿掉了,只求金福答應,但是金福不肯。正在這時,翠香來送口信,金福把克勝的意思向翠香說了,翠香眼珠子一轉,又計上心來,竭力慫恿金福答應。金福囘到書房,表面上依然裝得很爲難的樣子,對趙克勝說:「大相公,答應是可以的,只是我欠你的債 ……」
「欠的債麽,我方才說過了,不問你要。」趙克勝打算先糊他一糊再說。
「口說無憑。」
「我寫張字據給你。」
「那你現在就寫。」
「哈哈!」趙克勝拍了一下金福的肩頭:「你倒曉得大相公會賴賬的。」說着他拿起筆來,居然不加思索,就寫好了一張紙條。金福一看,只見上面大大小小、歪歪斜斜,哪裡是字,簡直是一個個的墨團。好容易,才辨認出其中的幾個字是:「事成之後,十兩銀子,一槪不要。」這一句最要緊,旣然不錯,其餘的也不去管它了。
金福將紙條收在懷裡,想起過去所受的氣,正好趁此機會發洩一下。他旣然奉命做少爺,就索性擺出少爺子來,將趙克勝呼喝得像孫子一般,克勝雖然着惱,但在用人之際,不得不忍了下去,何况他此刻正在學做書僮。
十
按照男女雙方的約定,今天是相親的日子。
所有參加這一次相親的人,男方包括趙太太、趙克勝和金福,女方包括白安人、白小姐、姚菊英和翠香,她們一夜都沒有睡好,都是睜着眼睛望天亮的,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各人有各人的心事。
等到頭一遍鷄叫,大家就來不及地起身,梳洗打扮。男方這一邊,金福扮成了新郞,趙克勝扮成了書僮;女方這一邊,姚菊英扮成了新娘,白小姐扮成了丫頭。
當然,趙家更顯得忙碌一㸃,更顯得緊張一㸃,因爲相親的地方是在這裡。
中午的時候,門外車馬喧鬧,女方的人來了,趙太太趕出去迎接,劈頭碰見了白安人。
「哎呀!這不是白家親母嗎?」
「哎呀!這不是趙家親母嗎?」
「今天是什麽好風,還煩勞親家母親自送小姐來。」
「親家母,我早就想來看看你了,無奈家裡事情忙,走不脱身。」
「不敢當。親家母,小姐想必來了?」
「來了。」
趙太太一聽,急忙冲過去望,只聽得「啊」的一聲,原來她把白安人的脚踩了。她連忙打招呼,白安人囘說不要緊,幷反過來問她:「女婿的病好了沒有?」
趙太太說:「好了,我已叫他出來了。」
白安人一聽,也急忙伸過脖子去望,只聽得「啊」的一聲,原來她也把趙太太的頭撞了。她也連聲地打招呼,趙太太也囘說不要緊。
這樣踩來撞去,不能解决問題。最後雙方同意,先到客廳中坐好,再分別將自己的兒女送到對方的面前來,聽憑鑑定。
一會兒,假新郞來拜見岳母,假新娘來拜見婆婆了。
趙太太,白安人同時都暗吃一驚,都感覺奇怪:「人人都說是個丑的,今天一看,怎麽是個美的!」
一對假新人,都知對方是誰,所以幷不奇怪。不明白的是趙克勝和白小姐。他們只當自己的對象眞的是這樣好看,喜歡得手脚沒有放處,各人將母親拉到一旁去,同時提出:要讓他們立刻成親。
趙太太、白安人也不明白,可是她們產生了疑慮。由於自己這邊弄了個假貸,因此也担心對方的貨色不是眞的。
「你不要急,等我詐她一詐,她要是敢拜堂,就是眞的,她要是不敢拜堂,就是假的。」她們安慰兒女的話幷沒有讓對方聽見,但內容是完全一樣的。
兩個親家母重新在賓主的位子上坐下,你瞄瞄我,我瞄瞄你,然後開口了。先發動攻擊的是趙太太:「親家母,不瞞你說,這一囘我家雖是接姑娘來冲喜,不過樣樣都不敢馬虎,還不是跟成親一樣。我家兒子,看相早就說道,他是個官相壽相。不過年輕的時候要命犯小人星,所以惹得人家閒言閒語,造謠生事。自然囉,隨便人家怎麽說,相是天生的,有憑有證。而且只要一成親,魔星退,福星來,將來做官做府,大富大貴。親家母,小人的話是聽不得的,聽了是要爛耳朶的。」
白安人可也不是個好說話的,她的囘答是:「親家母,你說對了。這一囘我家雖是送女來冲喜,頭頭面面,辦的可是跟陪嫁一樣。我家姑娘也算不得金枝玉葉,但是算命的說過,她是夫人命,將來相夫敎子,兒孫滿堂。姑爺的八字軟一㸃,只要姑娘的夫人命帶一帶,三災八難都帶得過。你看,今天一冲喜,不就把姑爺冲好了?親家母,八字是天生成的,眞金不怕火。有一班凝心鬼,喜歡搬弄口舌,不管他們怎樣顚倒是非,小鬼搬不倒閻王的座!」
趙太太的鼻子一哼,說:「親家母,話可不要講過了頭。常言說得好:『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們娶媳婦是眞心眞意的。喜事辦得停停當當,只等新人來拜堂!」
白安人肩頭一聳,說:「親家母,我們養女兒的人家,好有一比,好比做買賣的人,有貨也不愁貧!」
趙太太抓住對方未了這句話,接着說:「好好好,親家母,我們明人不說暗話,今天難得你也來了,我兒子也是好好的,媳婦呢,我看也不用囘去了,不如就住在這裡,揀個日子成婚。」
白安人先聽對方要她們住在這裡,倒是一急,後來聽下面還有「揀個日子」四個字,便找到了托辭:「要揀個日子?那也好,我們先囘去,你幾時揀好日子,我女兒幾時過門。」
趙太太見對方找機會下台了,决定再逼她一句:「住在這裡,還怕怠慢了你?」
白安人略爲一楞,便說:「那揀日子曉得你揀到幾時?」
「我就不揀!」好比下棋,趙太太一心要把對方「將」死。
「我就不走!」白安人是寧死也不肯投降。
「我眞錢不買假貨!」趙太太索性揭穿了對方。
「我眞貨不賣賒賬!」白安人也勸手揭對方的底。
「哪個是假的?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這一出活劇,幾乎樂壞了翠香。她想:時候到了,於是站出來講話:
「哎呀呀!兩個親家母不要吵了。」翠香將身子朝趙太太和白安人中間一攔,說:「吵了半天,也不曉得哪個是眞的,哪個是假的的。要曉得誰眞誰假,除非是現買現賣。」說着便問趙太太:「你敢現買?」
趙太太賭氣說:「現買就現買。」
翠香又問白安人:「你敢現賣?」
白安人也賭氣說:「我就現賣。」
翠香雙手一拍,說:「好哇!一個現買,一個現賣,可見是眞不是假。我看,揀日不如撞日,就是今天拜堂。」說着,用眼晴一掃趙太太和白安人,又問她們:「不拜就是假的,是嗎?」
趙太太和白安人同聲地囘答:「好,就是今天拜堂。」
此話一出,一班僕役們等于得到了命令,當下七手八脚,一陣忙亂,只一會兒功夫,一對假新郞和新娘,就在吹吹打打的鼓樂聲中,被送到洞房裡去了。
別人不要緊,可急死了趙克勝和白小姐,各人拉住母親問:「這怎麽辦?」
怎麽辦呢?兩個母親想了 一想,分別安慰她們的兒女說:「不碍事,倒了晚上把你換進去就是。」
晚上?對了!翠香也想到這ー層,萬一雙方都來調包,那可是白費心機。她眼珠子一轉,悄悄對白安人說:「安人,新人都進了洞房,你還不想個法子!」白安人將剛才對女兒說的話又吿訴了翠香。翠香聽了,雙手,直搖說:「不行,不行,倘若被新郞曉得了,半夜裡鬧起來豈不壞事!」這一說,白安人也着了急。翠香將手裡的那方手絹揉成一團,裝作竭力思索的樣子,稍停,若有所悟地說:「哦!有了,有了!」白安人催她快說。
翠香說:「你就說我是陪房的丫頭,今天晚上讓我睡在新房的外屋,夜裡,便帶小姐來調人,只要輕輕咳嗽一聲,我就知道了,偸偸地將房門一開,放小姐進去,人不知鬼不覺,到明天,生米已成熟飯,還怕他們不認賬?」
白安人連聲稱贊:「好,我帶你跟親家母說去,讓你睡在新房的外屋。」
十一
在新房裡,金福和菊英都有些恍恍惚惚,是在做夢吧?不是。突然一陣悲哀湧上了心頭,你拉住我的手,我拉你你的手,相對哭泣。
「哎喲喲!今天是你們大喜的日子,哭什麽?」說話的人是翠香。
兩人連忙鬆手。金福對翠香說:「什麽大喜的日子,你還開得出這種玩笑。」
「哪個跟你們開玩笑!難道你們的拜堂是假的,不是眞的?」
金福說:「我們都是做人家的代表,怎麽可以說是眞的!」
翠香用指指金福說:「說你傻,一㸃不錯。他們兩家,牛對牛,角對角,都是假戲,你們只管成親,怕什麽!」
「只怕他們不肯干休。」菊英怯怯地說了一句。
翠香說:「不錯,囘頭他們都要來的,不要緊,喏 ……」說到這裡,她恐怕被外面的人聽見,低聲在金福、菊英的耳邊咕噥了幾句,只見金福、菊英都㸃㸃頭,臉上靈出了笑容。
初更時分,趙太太帶着兒子在黑暗中摸來了。他們怕人發覺,所以連燈籠也不敢拿。好容易東摸西摸,才摸到了新房門上的那兩只銅環。趙克勝在母親支使下,用手指輕輕地一彈,又輕輕地一彈。
「哪一個?」是陪房丫頭的聲音。
「我……找少爺講……講話。」
「開門!開門!」趙克勝的口氣顯得很急迫。
但是,房內沒有囘聲。
趙克勝火了,忘記了他現在扮演的角色,駡了起來 :「金福,你這個王八蛋,你再不出來,少爺……我……說着,將袖子一勒,就要衝門。嚇得趙太太忙不迭地來捂他的嘴,拉他的手臂。
「哎呀!小姐!」陪房丫頭的聲音又响起了。
「做什麽?」是新娘子的聲音。
「外面嘰嘰喳喳,恐怕有賊!」陪房丫頭說。
「哎呀!翠香,我怕!」新娘子說。
「小姐,不要怕,我在外房,等我㸃起燈來照照看,有什麽事,我就叫安人來。」跟着房內發出了走路的聲音。
「不要忙,讓我來拿根門閂,捉住了送到安人那裡當賊辦!」沒有等陪房丫頭說完,趙太太就來不及地拉住兒子溜走。
過了一會,白安人帶着女兒躡手躡脚地來踐翠香的約了。他咳嗽一聲,房內沒有囘音。略爲提高一㸃嗓子咳嗽一聲,房內還是沒有囘音。她不得已,只好大聲地咳,不想弄假成眞,變成眞的咳嗽了。
「丫頭!丫頭!」是新郞的聲音。
「噯!姑爺!」是翠香的聲音。
「外面有人咳嗽,只怕是賊,讓我起來捉他。」新郞說。
「不是,姑爺,是……是……」聽口氣,翠香顯然知道嗽咳的是白安人她們,所以想用話來搪塞。
「是什麽?」新郞逼得很緊。
「是……是一只野貓來偸食。」翠香囘答得妙。
「不是吧,還是讓我起來看看。」
白小姐趕緊「喵嗚!」學了一聲貓叫,慌忙逃走。她母親也慌忙地在後面跟隨着。
十二
三更天,左面的走廊上出現了趙太太,右面的走廊上出現了白安人。二人分頭摸到新房門口,摸到門上的 銅環,彼此手碰手接觸了一下。
「不好!有人!」兩個人都發覺了,又都不能喊出聲來,也都想了解這人是誰,便你找我,我找你,活像捉迷藏游戲中的瞎子,已經走到面對面了,還不曉得。只聽見「拍禿」一响,兩人同時大呼「哎呀!」同時跌倒在地。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新房門開了,翠香拿着燭火在她們面上一照,驚異地說:「咦!這不是親家太太嗎?這不是安人嗎?」
誰說不是的呢!兩個親家母心想。而且連躱也躱不掉,只好挺身承認,最好又是把罪過卸給對方。
「親家母,你到這裡來幹什麽?」趙太太先發制人。
「親家母,你到這裡來幹什麽?」白安人立即問。
「這是我的家。我是怕兒子夜裡受涼,來替他蓋被窩的。」
「我的女兒從沒有離過娘懷,都是我帶她睡,今天我不放心,來看看她的。」
「這麽大的女兒還要你看?」
「這麽大的兒子還是你蓋校窩?」
又吵了,看樣子,如果讓她們吵下去必定沒有個了局。於是翠香說:「兩個親家母放心好了,新郞新娘有我侍候,不會出什麽事的。」
趙太太和白安人都搞昏了頭,所以把翠香的話當作聖旨一樣來奉行。大家訕訕地走了。
翠香看着她們的背影咋了一口:「有我在這裡,別想進來。」
天亮了,壓抑了一夜的怨恨、猜忌、氣惱,至此終於暴發。趙克勝不管母親怎樣攔阻,還是拿了一根大棍子,氣勢汹汹來到新房門口,大喊大叫地要打死金福,說他霸佔了東家的新娘子。白小姐也顧不得羞恥,哭哭啼啼地拖住白安人,來跟菊英拚命,說她破壞了自己的姻緣。
新房門開啓了,裡面走出翠香、金福和菊英。
趙克勝眼都紅了,揪住金福,氣咻咻地說:「好,我要你權且代一代,誰叫你霸佔我的老婆?」
白小姐也拉住菊英:「不要臉的賤貨,借你來冲喜,哪個要你圓房?」
他們一嚷,趙太太和白安人聽了個一淸二楚。
「什麽?女婿是權代的?」
「什麽?媳婦是借來的?」
「老不死!」趙太太駡白安人。
「老騙子!」白安人駡趙太太。
「謀我的家財!」
「搶我的女兒!」
「我跟你算賬!」
「我跟你拚命!」
她們沒有駡完,兒子、女兒又來纏住母親,鬧着「 要老婆」、「要丈夫」!
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姚祥又扭着白員外吵吵鬧鬧地進來了。
姚菊英看見父親,飛奔上去。姚祥摟住她,顫聲地說:「好女兒,你吃了苦了。」翠香過來解釋:「姚伯伯,你不要着急,菊英姊昨夜跟金表哥成親了。」
姚祥聽女兒沒有吃苦,也就放了心。雖然他實在不懂女兒跟女婿是怎機成親的。
「告官去!」趙克勝見姚祥一門團圓的景象,氣得發吼。
「告官去!」「吿官去!」趙太太、白安人都這樣叫喊。頃刻之間,從趙家走出來一大串人,牽牽連連地直往縣衙面去。
這筆糊塗賬,怎麽算法呢?這裡還是保持一些關子,免得觀衆的看電影時減少興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