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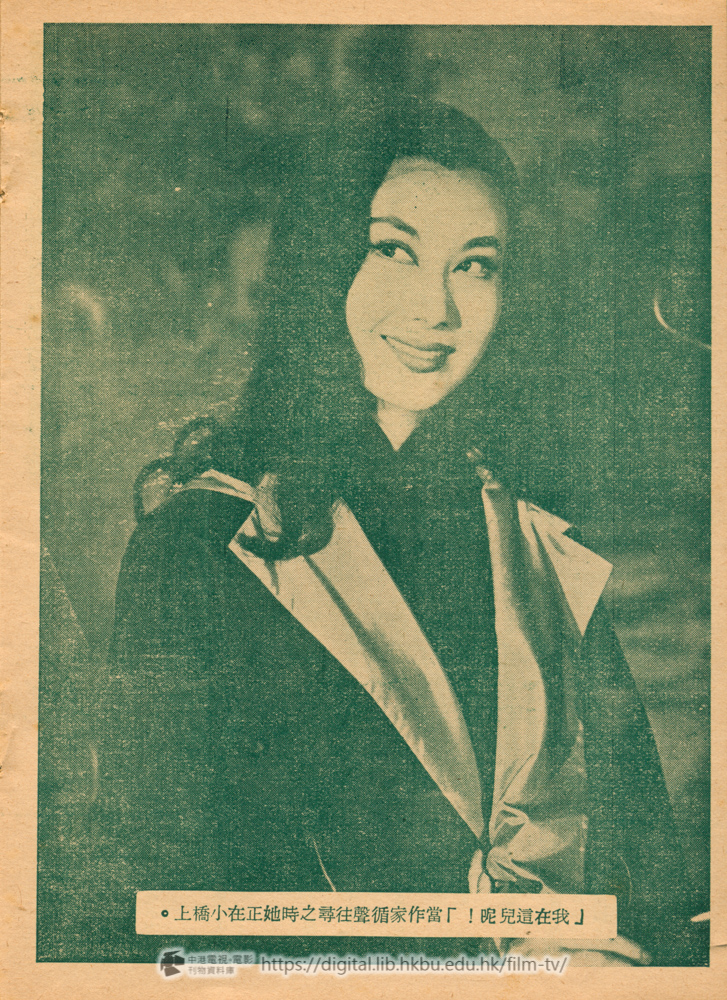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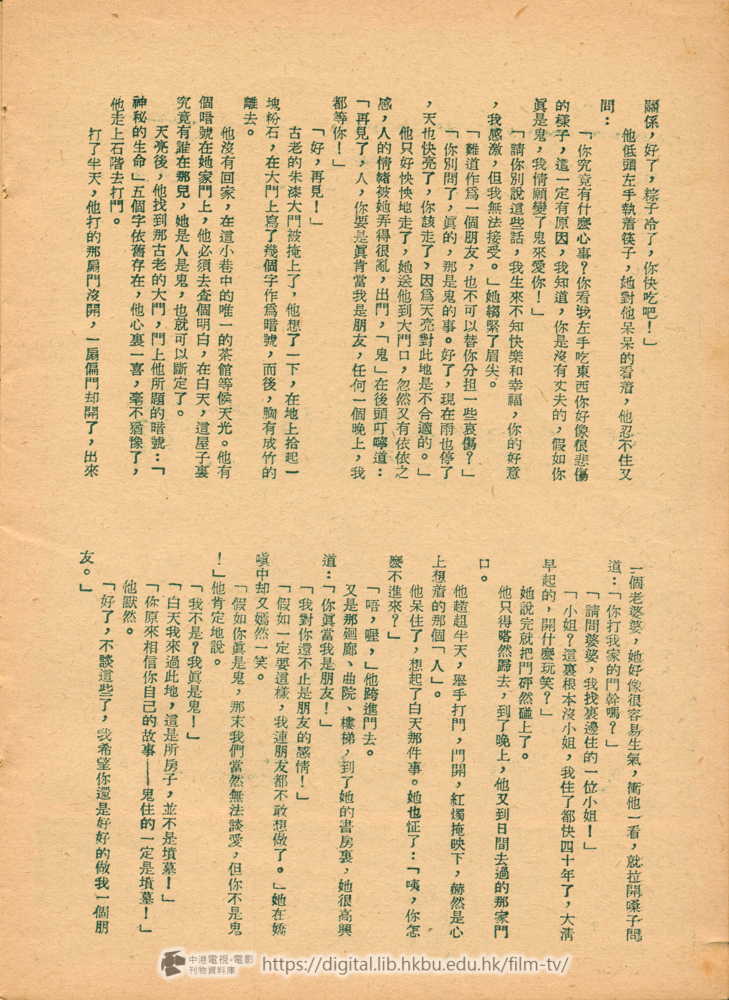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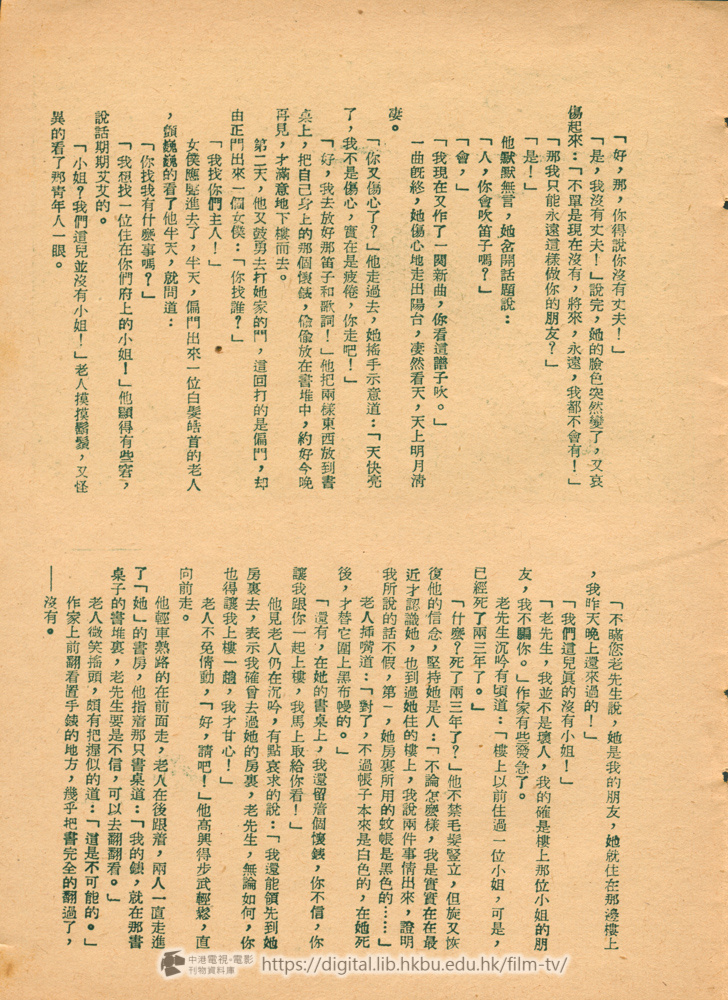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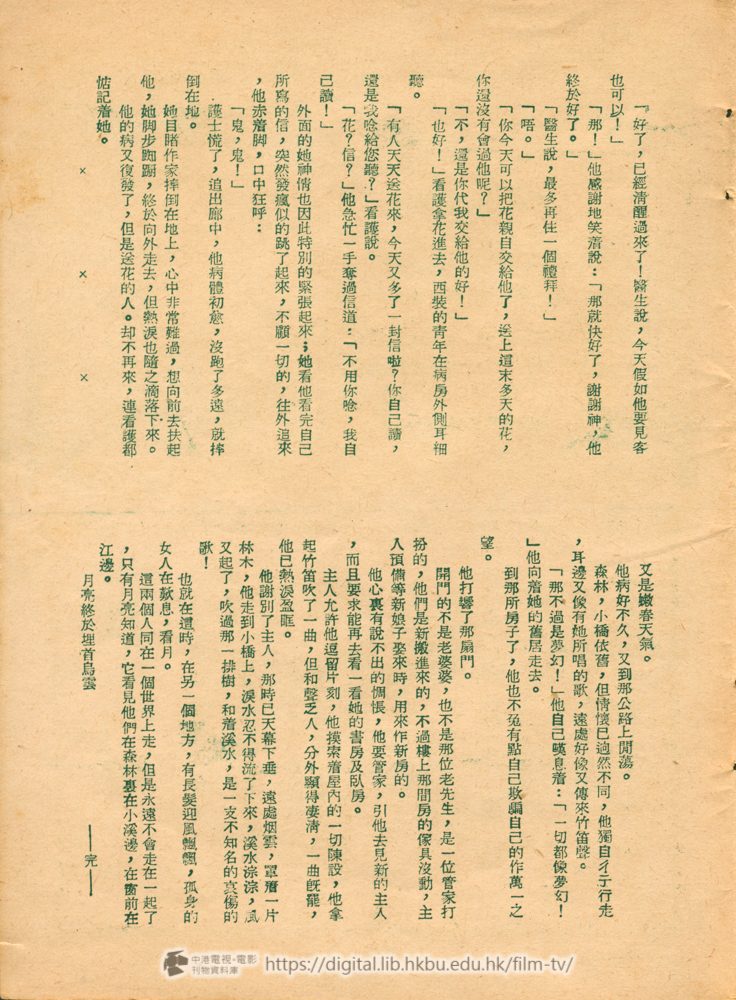
電影小說
鬼戀
那時是嫩春天氣。
上海近郊有一座森林,毗連森林的公路上分支着一條小巷,深而狹,像是一條垂死的長蛇,昏黃的街燈在冷風下閃爍着。店家差不多全閂上門了,只有一家店舖的門隙透出一些微弱的光亮,然而那已是全街、全森林與公路最具溫暖的地方了。
在這寂靜的小巷裏,隱約傳來陣陣紆緩、有節奏的足聲,漸漸一個高大的影子踱了過來,他是一位年靑作家,他幾乎每天都到這一帶散步,他對這小巷、公路都非常熟悉,他停步於那小穴前,買了一包香烟,取火燃吸。
「對不起,借個火!」作家下意識地燃上火,火光耀着自己的眼睛,又映到對方臉上,女人,一個女人!這麽晚?作家詫異地想。
「請問,斜土路往那走?」
作家仍在思慮中,一個較高的聲音:「人,你別老呆着,回答我呀!」
「你叫我是人?」作家驚奇地問。
「你不是人難道是鬼?」女人輕俏的笑了。
「不,我覺得你叫我人很奇怪,這種稱呼很少人用。」
「這有什麽可怪?人,你能吿訴我斜土路往那兒走?」
作家覺得對方很奇怪,爲了滿足他的窺探心理,他堅持要送她回斜土路。
他們一路說笑,女的老說到鬼,到了黑暗的森林裏,作家不禁覺得有些胆怯。
他問倒底在那裏,女的笑了:「怎麽,你有點怕?」
「我才不怕呢,」作家鼓着勇氣,「我說個鬼故事給你聽你怕不怕?」
「你講講看!」她的話總是那麽沉着而平穩。
他說了一個他認爲很可怕的鬼故事。他以爲她會驚叫,但出乎意外的,她非但沒叫,而且若無其事,少頃,她哈哈笑起來。
「你笑什麽?」
「你說我怕,其實該怕的倒是你,你在這兒說了半天的鬼,你知你身旁站着的是什麽?」
「什麽?」
「我是鬼!」
她說完,人本能的往後退了一兩步。
「你看看我!」
在淡月淸輝之下,他看到一張標緻而微帶憂鬱的臉,美麗極了。
「有這麽美麗的鬼?」
「你以爲鬼一定很難看?」
「要是你眞的是鬼,那我一定認爲鬼比人美,可惜你是人,不是鬼!」
「你一定相信我是人?」
「當然!」
「那麽,你要不要我變個鬼相,給你看看?」
他點頭,心着實有點駭怕,她變了,變得更漂亮,秀髮隨風,飄然似仙。
在森林中兩人談得很融洽,這時,天已微白,女的說要回去,人問她爲什麽如此急於歸去?她說鬼是怕白天的,人要送她回去,她拒絕了。他問:「以後我們還會見面嗎?」
「假如你不害怕,可以!」
「幾時呢?」
「下星期月亮圓時。」她說着轉身要走。
「慢點,我還沒請敎過貴姓呢?」
「叫我鬼好了。」
「叫你是鬼?……」他的話沒完,她已倏然而去,漸漸沒入曉霧之中。
x x x
月圓之夜,他在森林之中呆等,但人影全無,他正急躁的四外望着,遠處忽有竹笛聲起,隱約聽到淸脆的歌聲,他循着歌聲尋去。
一座小橋映入他的眼簾,橋上人是她,他急忙跑過去,歌聲戞然而止。
「怎麽,果然來了?一點不怕?」她的白牙在月下閃着明光,微笑着問。
「不怕,倒沒想着你會唱小曲吹笛子,不過那歌實在太悲涼了些!」
「鬼唱的曲子總不免凄惻一點,你想聽興奮的曲子?」
「怎麽,你也能唱興奮的?」
「我不會唱,但,我能帶你去個地方聽。」
「到你們鬼的世界去?」他猶豫的眼色向她看去,她笑道:
「你現在信我是鬼了?」
「不是,因爲你老愛說鬼,所以我也順口說了出來,不過你說上那兒去呢?」
「鬼區沒有興奮的音樂,只有愁之慘霧,我現在陪你到人間去。」
「到人間?你能去?」他又怔着看她。
「你眞是大儍瓜,鬼到處都有,就是你不能辨別那個是人,那個是鬼?」
「眞的?」他對面前那個漂亮的影子,眞無法分辨她是人還是鬼。
她帶他到一家夜總會,那是個燈光幽暗,但人多,音樂很興奮的地方,她要他寫個曲名送給樂隊,那曲子叫「死亡曲」。
他拿出筆寫時,她忽然問:
「爲什麽你不用眼鏡?」
「用眼鏡?我用不着眼鏡,奇怪,你怎麽會叫我用眼鏡?」
「嗯……」她愕了一愕,旋卽故作鎭靜:「我……沒什麽!」
樂隊奏出死亡曲,她叫他去跳舞。
他們跳得很高興,回到座上,倏然,全院的燈黑了,算是黑燈舞,音樂變得快促,而鼓聲更催得緊,彷彿室内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了。
他請她跳這隻舞,但是,她却催着道:「走,走,快走,我不想跳舞了,走吧!」
他忽忙付賬,不知她急於要走究竟是爲了什麽?走到門外,他詫異地問道:
「爲什麽忽然不高興了?」
「你別問,我們快叫車走!」
他們終於又到了森林,就在溪邊石上坐下。
「你不是很高興的在跳舞嗎?幹嗎又不開心了?」
「我也說不上理由來,大槪是人去的地方,究竟不大適宜鬼去的!」
「我總覺原因不這末簡單!」
「你不要問,請你不要再問再想,反正我不高興了!」
他們談着,棺材後忽然有人走出來,他們趕緊一躱,却是一個鄕下人挑過一担粽子。
「已經快吃粽子了?幾時啦?」她問。
「還有二十天左右,就是端午啦!你也喜歡粽子,賽龍舟?」
「我喜歡,到時你陪我去看龍舟好不好?」
「你白天也能往人堆裏去?」
「賽龍舟端午節是紀念屈死寃鬼的,我是鬼,當然也能去,端午那天你在這兒等我,現在我要走了!」
「好,那天在此地見面!」
他們就這樣分了手,他懷着一肚子的疑慮歸去。
x x x
二十多天不算長,但對作家來說,相當於二十年,他已愛上了那美麗的影子一樣的她。
端午,天氣晴明,江邊擠滿了人,那個美麗的自稱鬼的,正與作家依偎着同看,江心中的龍舟鼓聲震天,正如箭一般,划破江水,向前駛去。過了淺灘,就是終點,淺灘上有幾個人站着,她的目光一接觸到他們,立刻像脫兎似的,向着後面跑去,作家急忙也趕上去,她跑得很快,他追了半天才追上。
「怎麽好好的又不高興了呢?」
「我自己也說不上來,總覺得在人堆裏站久了就不舒服。」
「眞奇怪……」
「…………」
他們又回到了森林,突然一條閃電直射下來,雷聲繼之鼓隆隆的暴響起來。
「哎呀?要下雨了,這裏也無處避雨……」
「上我家!」
「你家?……我去?……」他幾乎不敢相信。
「你別怕,快走,不遠!」她拉着他的手急走,雨點已經灑了下來,兩人冒雨飛奔,衣服都淋濕了,她推門入去,一個人也沒有,直到她樓上的書房,她先進去臥房換上睡衣,又叫他也去換衣服。
「我沒有帶衣服呀!」
「我替你預備好了,快去吧!全濕了當心招涼!」
他遲疑而終於進了房,男用睡衣及睡鞋就放在櫃子裏,他穿上試試,却十分合適,好像是爲他定做的一樣。他越發覺得莫名其妙。
「噯,你怎麽會有這些男用的東西?」
「這些是我丈夫的東西!」
「你的什麽?」
「我的丈夫,」她的臉色更哀傷憂鬱了。
「那,深更半夜的,帶個陌生男人到家裏來,你丈夫要是知道了,難道……」
「這是你們人爲的把戲,我們鬼是不在乎旳。」
她又苦笑了一下,繼又走了出去,回來時,竟端來了一盤粽子。
「你也有粽子?」
「我不早說過,今天端午,你們人拿粽子祀祭鬼,我們當然就有粽子了!」
他用左手拿起筷子夾粽子吃。在寫字桌上有一張白紙,他不經心的取來看。
「是我做的歌詞,就是上回你聽到那一支,做的不好,你可別笑我!」
「不,詞是好極了,不過爲什麽充滿了痴怨與悲苦,你不說有丈夫的?」
「鬼的感情,你們人是無法了解的,別談這些了,你還是吃粽子吧!」
他們在桌前互相呆望着,默默無言。
「你眞有丈夫?」
「這些事,你都可以不必管。」
「我怎麽能不管?」
「爲什麽?」她驚奇於這話。
「因爲我愛你!」
他誠懇眞摯的態度,使她震動,但又努力壓抑下去,半晌,她冷冷的說:
「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往來已經很反常了,至於愛,那是太荒唐了」。
「那你怎麽結婚有丈夫呢?」
「那些都是生前的事,在鬼的世界裏,並沒有這些嚕囌關係,好了,粽子冷了,你快吃吧!」
他低頭左手執着筷子,她對他呆呆的看着,他忍不住又問:
「你究竟有什麽心事?你看我左手吃東西你好像很悲傷的樣子,這一定有原因,我知道,你是沒有丈夫的,假如你眞是鬼,我情願變了鬼來愛你!」
「請你別說這些話,我生來不知快樂和幸福,你的好意,我感激,但我無法接受。」她縐緊了眉尖。
「難道作爲一個朋友,也不可以替你分担一些哀傷?」
「你別問了,眞的,那是鬼的事。好了,現在雨也停了,天也快亮了,你該走了,因爲天亮對此地是不合適的。」
他只好怏怏地走了,她送他到大門口,忽然又有依依之感,人的情緖被她弄得很亂,出門,「鬼」在後頭叮嚀道:「再見了,人,你要是眞肯當我是朋友,任何一個晚上,我都等你!」
「好,再見!」
古老的朱漆大門被掩上了,他想了一下,在地上拾起一塊粉石,在大門上寫了幾個字作爲暗號,而後,胸有成竹的離去。
他沒有回家,在這小巷中的唯一的茶館等候天光。他有個暗號在她家門上,他必須去査個明白,在白天,這屋子裏究竟有誰在那兒,她是人是鬼,也就可以斷定了。
天亮後,他找到那古老的大門,門上他所題的暗號:「神秘的生命」五個字依舊存在,他心裏一喜,毫不猶豫了,他走上石階去打門。
打了半天,他打的那扇門沒開,一扇偏門却開了,出來一個老婆婆,她好像很容易生氣,衝他一看,就拉開嗓子問道:「你打我家的門幹嗎?」
「請問婆婆,我找裏邊住的一位小姐!」
「小姐?這裏根本沒小姐,我住了都快四十年了,大淸早起的,開什麽玩笑?」
她說完就把門砰然碰上了。
他只得嗒然歸去,到了晚上,他又到日間去過的那家門口。
他趦趄半天,舉手打門,門開,紅燭掩映下,赫然是心上想着的那個「人」。
他呆住了,想起了白天那件事。她也怔了:「咦,你怎麽不進來?」
「唔,喔,」他跨進門去。
又是那廻廊、曲院、樓梯,到了她的書房裏,她很高興道:「你眞當我是朋友!」
「我對你還不止是朋友的感情!」
「假如一定要這樣,我連朋友都不敢想做了。」她在嬌嗔中却又嫣然一笑。
「假如你眞是鬼,那末我們當然無法談愛,但你不是鬼!」他肯定地說。
「我不是?我眞是鬼!」
「白天我來過此地,這是所房子,並不是墳墓!」
「你原來相信你自己的故事——鬼住的一定是墳墓!」
他默然。
「好了,不談這些了,我希望你還是好好的做我一個朋友。」
「好,那,你得說你沒有丈夫!」
「是,我沒有丈夫!」說完,她的臉色突然變了,又哀傷起來:「不單是現在沒有,將來,永遠,我都不會有!」
「那我只能永遠這樣做你的朋友?」
「是!」
他默默無言,她岔開話題說:
「人,你會吹笛子嗎?」
「會,」
「我現在又作了一関新曲,你看這譜子吹。」
一曲旣終,她傷心地走出陽台,凄然看天,天上明月淸凄。
「你又傷心了?」他走過去,她搖手示意道:「天快亮了,我不是傷心,實在是疲倦,你走吧!」
「好,我去放好那笛子和歌詞!」他把兩樣東西放到書桌上,把自己身上的那個懷錶,偸偸放在書堆中,約好今晚再見,才滿意地下樓而去。
第二天,他又鼓勇去打她家的門,這回打的是偏門,却由正門出來一個女僕:「你找誰?」
「我找你們主人!」
女僕應聲進去了,半天,偏門出來一位白髪皓首的老人,顫巍巍的看了他半天,就問道:
「你找我有什麽事嗎?」
「我想找一位住在你們府上的小姐!」他顯得有些窘,說話期期艾艾的。
「小姐?我們這兒並沒有小姐!」老人摸摸鬍鬚,又怪異的看了那靑年人一眼。
「不瞞您老先生說,她是我的朋友,她就住在那邊樓上,我昨天晚上還來過的!」
「我們這兒眞的沒有小姐!」
「老先生,我並不是壞人,我的確是樓上那位小姐的朋友,我不騙你。」作家有些發急了。
老先生沉吟有頃道:「樓上以前住過一位小姐,可是,已經死了兩三年了。」
「什麽?死了兩三年了?」他不禁毛髪豎立,但旋又恢復他的信念,堅持她是人:「不論怎麽樣,我是實實在在最近才認識她,也到過她住的樓上,我說兩件事情出來,證明我所說的話不假,第一,她房裏所用的蚊帳是黑色的……」
老人揷嘴道:「對了,不過帳子本來是白色的,在她死後,才替它圍上黑布幔的。」
「還有,在她的書桌上,我還留着個懷錶,你不信,你讓我跟你一起上樓,我馬上取給你看!」
他見老人仍在沉吟,有點哀求的說:「我還能領先到她房裏去,表示我確曾去過她的房裏,老先生,無論如何,你也得讓我上樓一趟,我才甘心!」
老人不免倩動,「好,請吧!」他高興得步武輕鬆,直向前走。
他輕車熟路的在前面走,老人在後跟着,兩人一直走進了「她」的書房,他指着那只書桌道:「我的錶,就在那書桌子的書堆裏,老先生要是不信,可以去翻翻看。」
老人微笑搖頭,頗有把握似的道:「這是不可能的。」
作家上前翻看置手錶的地方,幾乎把書完全的翻過了,——沒有。
明明自己放的東西,怎麽會?……
他抬頭又看到一張照相,畫中人微笑似昨,風緻娟好,他指向老人:「喏,就是她,一點兒也不假旳就是她!」
話還未完,老人忽然狂笑,而後又涕隨淚下,聲音哽咽:「先生,你別說笑話了,這是我死去了兩三年的女兒,可憐,她是生肺病死的。」
「死了兩三年?」
「嗯,我不願再獃在這裏了,先生,請您也走吧,你要看房子也巳經看過了。」
他無可奈何的下了樓,怏怏與老人道别。
他沒再到她家去看她,但她是人是鬼的問題,却使他非常煩悶,他上她帶他去的那家夜總會,叫了一瓶酒,獨自狂飮,又點了一支曲子——死亡曲。
「高興得很麽?一個人到這兒來飮酒?」那個美麗的影子來到桌邊。
「我?……我是來找尋過去的。」
「過去什麽?」
「你聽音樂!」他指指樂隊,「來,你喝一杯。」他的舌根在打捲。
她阻止他再喝,然後說:「你什麽時候學會喝酒的?」
「離開你之後。」他雙眼似火。
「是你自己不來找我嘛!」她笑得還是那麽甜。
「我病了!」
「那不如早點回去!」
「不,我還要喝酒,病,怕什麽?」他倔强地去取酒瓶,她央求了:「那末,到我家中去喝好不好?」
「上你那兒?」
「是。」
他叫侍者付賬,踉蹌地隨着一個美麗的身影走了出去。
x x x
到了房裏,他環目四顧,景色和他白天來時一樣。
她帶點埋怨的口吻道:「我想不到你那麽儍,那麽認眞!」
「因爲,我愛你!」
「你又說錯了,人怎能同鬼談戀愛。」
說完,她走進後間屋去,取出酒來,注入玻璃杯內。
他們互飮了一口,窗外野風撼着玉梨花,各有心事,相對無言。
他緘默半天,忽問:「現在幾點鐘了?」
「總該兩三點了吧!噢,你還有個錶,上回放在書桌上的,我替你藏着,天天開錬,現在還走着呢!」
她說完進臥房取錶,他又猛飮了一口酒。
錶取岀來了,他的橫梗在胸前的問題,始終無答案,而且愈來愈糊塗難决了:「人?鬼?鬼?人?」
他緩緩的說:「我眞不知怎麽好,上次白天到這兒來,跟一位老先生談過,證明你是鬼!」
「嗯,可是你放心,這裏决不會搬演聊齋故事,我這個鬼是決不肯害你的。」
「不會,我也知你不會。」他忽有所感觸,站起來道:「我走了,我們也不再見了,我不想再來麻煩你了。」
他雖然站起想往外走,可是頭重脚輕,他竟然量倒在地上。
x x x
次日到近午才醒,頭還在痛,他不知自己是怎麽回來的,按電鈴召來公寓的侍役,問他:「誰送我回來的?」
茶房用手比着說:「是一個矮小的靑年人,送你回來的,他還有封信留給您呢!」
「信?快拿來我看!」
信的大意是她怕惹煩惱,所以决意飄然他去,從茲訣別,願他自己珍重。
他看完信又暈了過去,等他醒來,已躺在醫院的床上,他恨自己爲什麽不死,死了,如果無鬼可以渾忘一切,有鬼就可與她比翼雙飛於殘草流螢之間了。
他病了幾個月,待病稍好,已近新年。在舊曆新年的初一,他才搬回公寓。一天他信步又走到了那森林旁的小巷,小巷中人正在慶賀新年,有的舞獅,有的放炮,到處擠滿了人,他正想離去,忽然一個熟悉的人影投進他眼裏。
「是她!」他幾乎叫了出來,她也發現了他,於是反身急走,他也趕快追上去。她還是循着舊路向她的故居奔跑。
就在到達那所古屋時,他緊趕了幾步,追上了她,氣喘吁吁的叫:「鬼」!
他誠懇的態度使她非常感動,但她還是抑制着說道:
「人,我們到裏面去談談吧」!
他又進入了那熟悉的書房,他的第一句話,就說:「你別再叫我人!你得在今天承認,你是人,你絕對不能撤謊了!」
「可是我的確是鬼!」
「我們雖然分開許多日子,可是,你的影子一直在我腦子裏縈繞着,我曾仔細想過,你沒有半點理由是鬼,你一定是人,你不必再跟我來故弄玄虛!」
她沒說話,他又說下去:「你是人,你不是鬼,但你一定有一段傷心事,使你不得不承認自己是鬼,不承認你是人!」他說話時情緖很激動。
她默坐無言,眼淚終於流了下來,她泣語:「爲什麽你終不能原諒我?一定要說我是人?一定要把埋在土裏的人拾到世上去,一定要我在這鬼怪離奇的世上做人?」
「因爲我是人,而我又愛你!」
「可是,我的的確確不想做人!」她哭出聲來了,但他更堅强的說道:「今天,不是再說那些話的時候了,請你不要難過,吿訴我,倒底爲什麽你要把自己當作鬼?爲什麽又要與我做朋友?又不許我親近你?你今天也該說說明白了吧?」
她止住哭聲,抬起頭,眼睛裏充滿了光芒,頓了一頓,向他說:「你一定要我說?那我就吿訴你,你可別生氣,我現在先答覆你一個問題,爲什麽我答應你做朋友,而又不肯叫你親近!」
「爲什麽?」
「因爲你很像我一個朋友,一個共生死,同患難,叫我永難忘記的朋友!」
「那人呢?」
「死了!」她又說:「是光榮地爲國而死,我們本來都是來作秘密工作的,開始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很順利,我們倆就以一對假夫妻的身份,在這兒活動,不料,有一天,我們正在夜總會……」
她另外挿入一句閒文:「那夜總會是我們的集中地,就是上次我跟你去的地方。」
他怔着聽她說下去:「有一天,我們仍在聚會,突然,音樂改了節奏,那音樂是我們報訊的記號,也就是上次我點奏的那個死亡曲……
「……我們當時賴黑燈舞逃走,一同逃到這個森林,我想先讓我的愛人逃走,因爲他比我們重要……
「……於是揀了端午節,扮了競渡人,想到一淺灘由小舟接應逃走,可是……」說到這裏,她泣不成聲:「他竟被發現而中槍死在江裏,所以,上次你問我看龍舟爲什麽逃走,你現在該明白那是爲什麽了……
「我親眼看見,我最心愛的人被槍打死,從此,我改變了整個的生活,我的生命彷彿已隨他同去,我立刻搬來此地,我愛人之家,與他父母說定,當我是鬼,情願過一輩子孤寂的生活。
「……但,自那天遇到你,我看你身材,面貌,一切舉止,與他完全一樣,甚至習慣用左手。
「因此我跟你交朋友,希望找回他的影子,我跟你跳舞,看龍舟,森林裏夜談。」
「可是你爲什麽不讓我親近你」?
「你們雖然像,可是你决不是他,我的愛,已隨他而去。我的事已全吿訴了你,我覺得非常對不起你,而且我很慚愧,我太自私!」
「不,我並不覺得你自私,只覺你太儍,我希望你把事情看開一點,我知道你是愛我的,那末請你答應我,忘記過去,從新做人!」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搖頭太息。
「那末至少你得承認你愛我!」他苦苦不放。
「也許是,不過……你現在去吧!我累了。」
「那麽以後呢?」
「以後麽?明兒晚上你來,讓我有一點精神,跟你再詳談一晚!」
他大喜過望,站起來,步履輕鬆,他不再是個新病初痊的人了,他與她道別,在公路上,輕快的走着,他彷彿突然年靑了幾歲。
x x x
第二天,他快樂地等候日落,不由自主地吹起口哨來了,這是他十年來未有的快樂神情,他覺得他該感謝神!
這時公寓的茶房敲門進來,遞給他一封信。
「這次眞的永別了,我們再也不會相逢,房子我已退掉,你摯誠的熱愛,我將永記在心頭……」
他的心臟病發於一刹那,他又暈倒在地上。
x x x
醫院的醫生,盡力挽救他的生命。他不但天天說囈語,而且沒有一切感覺。
在他昏迷時期,看護士天天接到一位年靑俊朗的西裝少年所獻來的花。
看護問他姓名,他不肯說,只說:「他知道的,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x x x
「你倒是準時間!」看護又接了他一次花。
「今天,他怎麽樣了?」
「好了,已經淸醒過來了!醫生說,今天假如他要見客也可以!」
「那!」他感謝地笑着說:「那就快好了,謝謝神,他終於好了。」
「醫生說,最多再住一個禮拜!」
「唔。」
「你今天可以把花親自交給他了,送上這末多天的花,你還沒有會過他呢?」
「不,還是你代我交給他的好!」
「也好!」看護拿花進去,西裝的靑年在病房外側耳細聽。
「有人天天送花來,今天又多了一封信啦?你自己讀,還是我唸給您聽?」看護說。
「花?信?」他急忙一手奪過信道:「不用你唸,我自己讀!」
外面的她神情也因此特別的緊張起來;她看他看完自己所寫的信,突然發瘋似的跳了起來,不顧一切的,往外追來,他赤着脚,口中狂呼:
「鬼,鬼!」
護士慌了,追出廊中,他病體初愈,沒跑了多遠,就摔倒在地。
她目睹作家摔倒在地上,心中非常難過,想向前去扶起他,她脚步踟蹰,終於向外走去,但熱淚也隨之滴落下來。
他的病又復發了,但是送花的人。却不再來,連看護都惦記着她。
x x x
又是嫩春天氣。
他病好不久,又到那公路上閒蕩。
森林,小橋依舊,但情懷已逈然不同,他獨自彳亍行走,耳邊又像有她所唱的歌,遠處好像又傳來竹笛聲。
「那不過是夢幻!」他自己嘆息着:「一切都像夢幻!」他向着她的舊居走去。
到那所房子了,他也不免有點自己欺騙自己的作萬一之望。
他打響了那扇門。
開門的不是老婆婆,也不是那位老先生,是一位管家打扮的,他們是新搬進來的,不過樓上那間房的傢具沒動,主人預備等新娘子娶來時,用來作新房的。
他心裏有說不出的惆悵,他要管家,引他去見新的主人,而且要求能再去看一看她的書房及臥房。
主人允許他逗留片刻,他摸索着屋內的一切陳設,他拿起竹笛吹了一曲,但和聲乏人,分外顯得凄淸,一曲旣罷,他已熱淚盈眶。
他謝別了主人,那時已天幕下垂,遠處烟雲,罩着一片林木,他走到小橋上,淚水忍不得流了下來,溪水淙淙,風又起了,吹過那一排樹,和着溪水,是一支不知名的哀傷的歌!
也就在這時,在另一個地方,有長髮迎風飄飄,孤身的女人在歎息,看月。
這兩個人同在一個世界上走,但是永遠不會走在一起了,只有月亮知道,它看見他們在森林裏在小溪邊,在窗前在江邊。
月亮終於埋首烏雲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