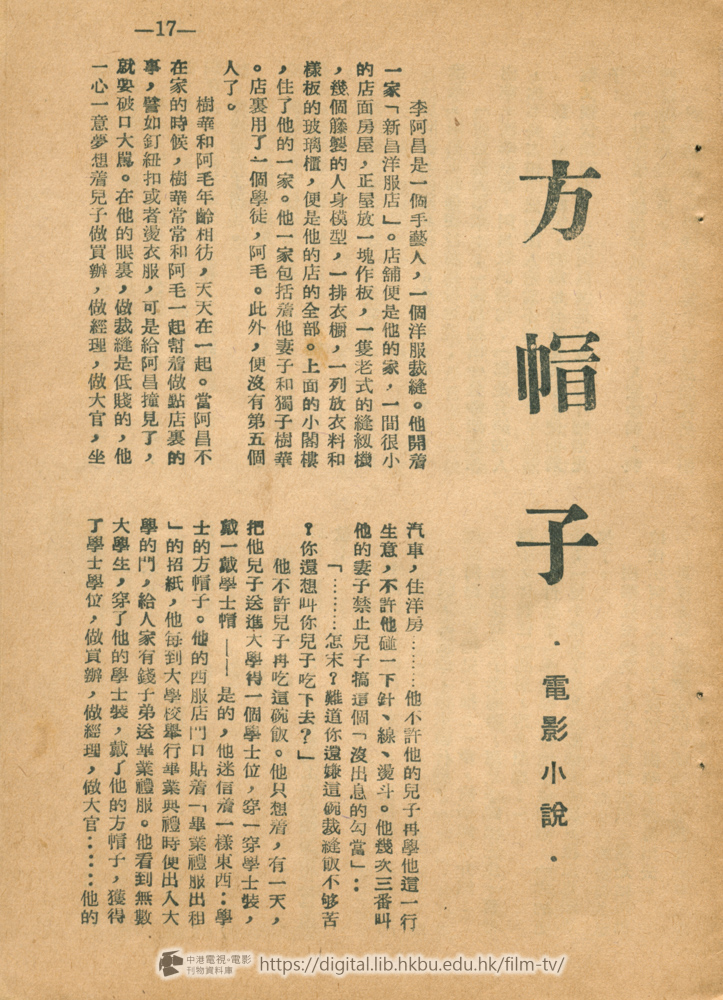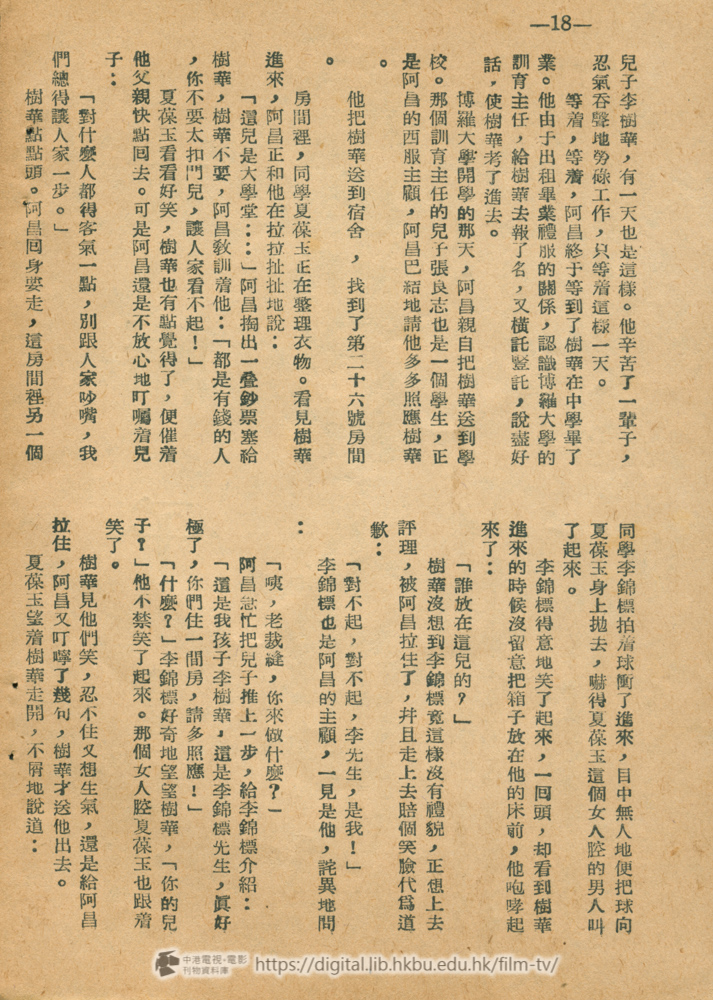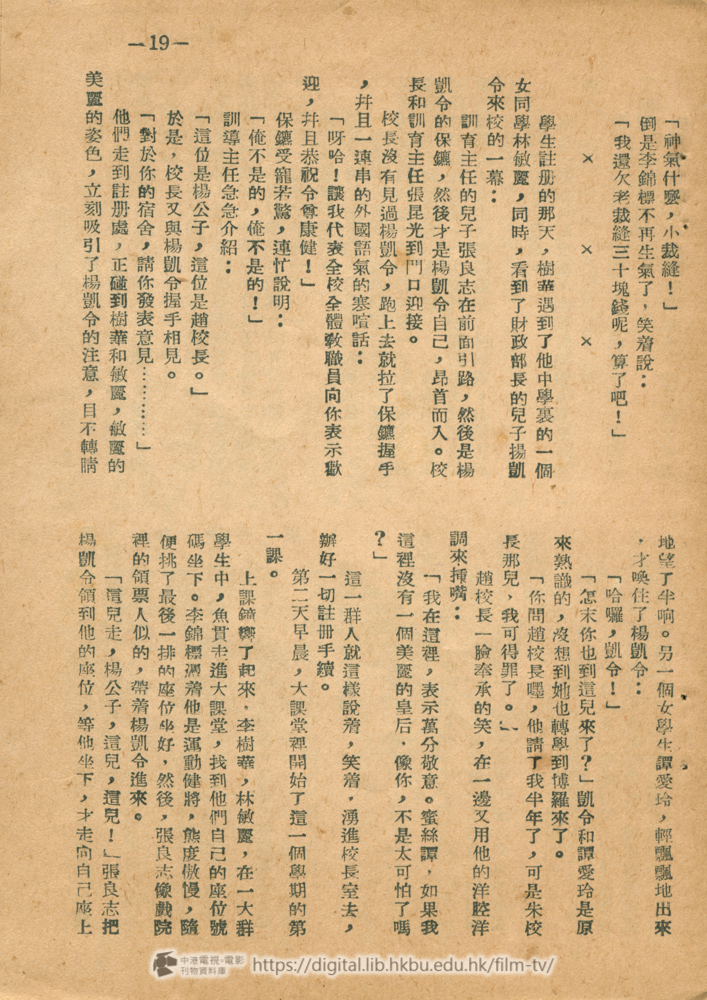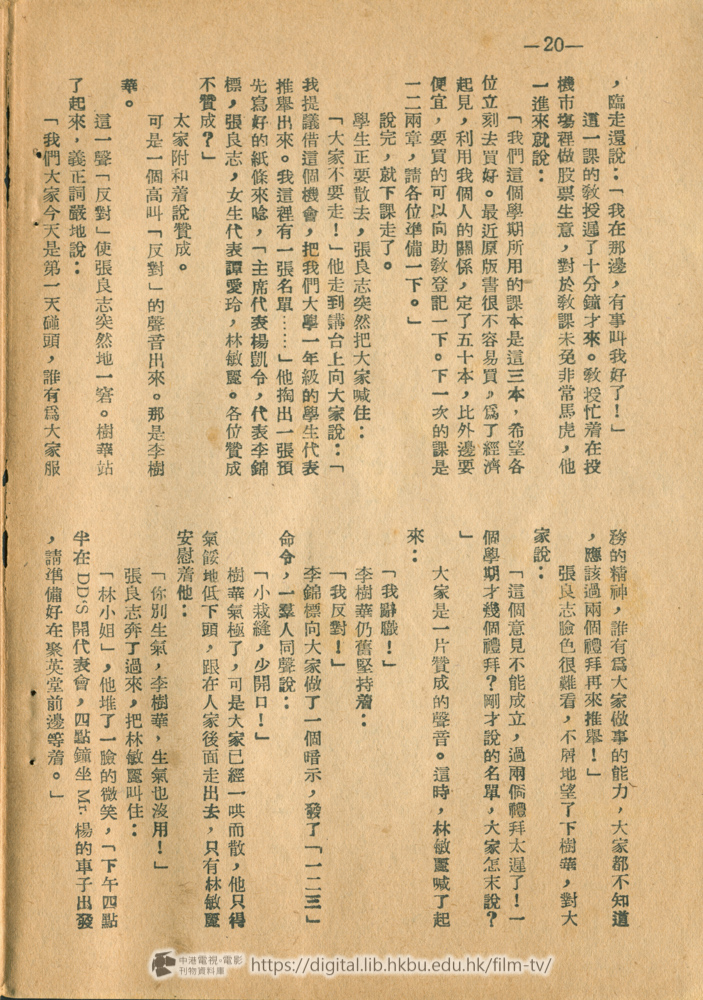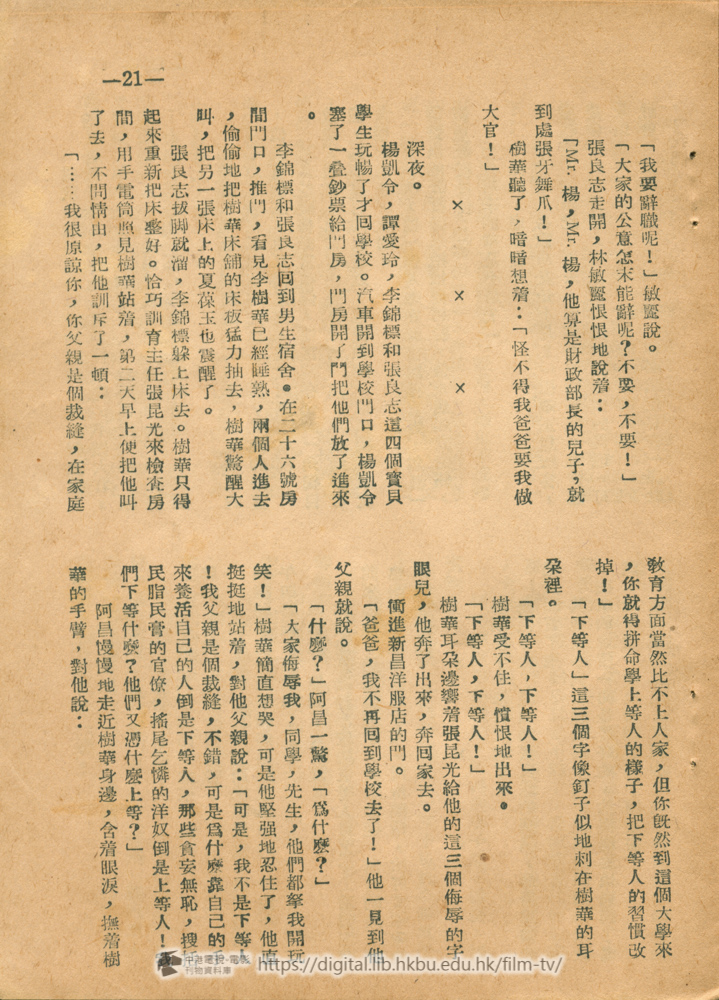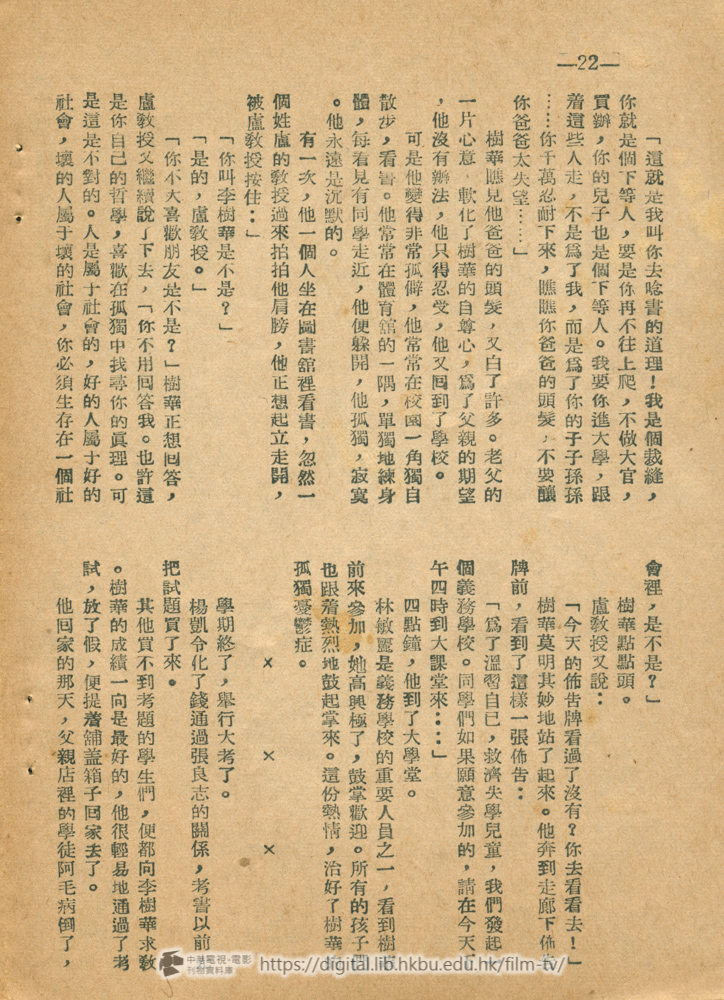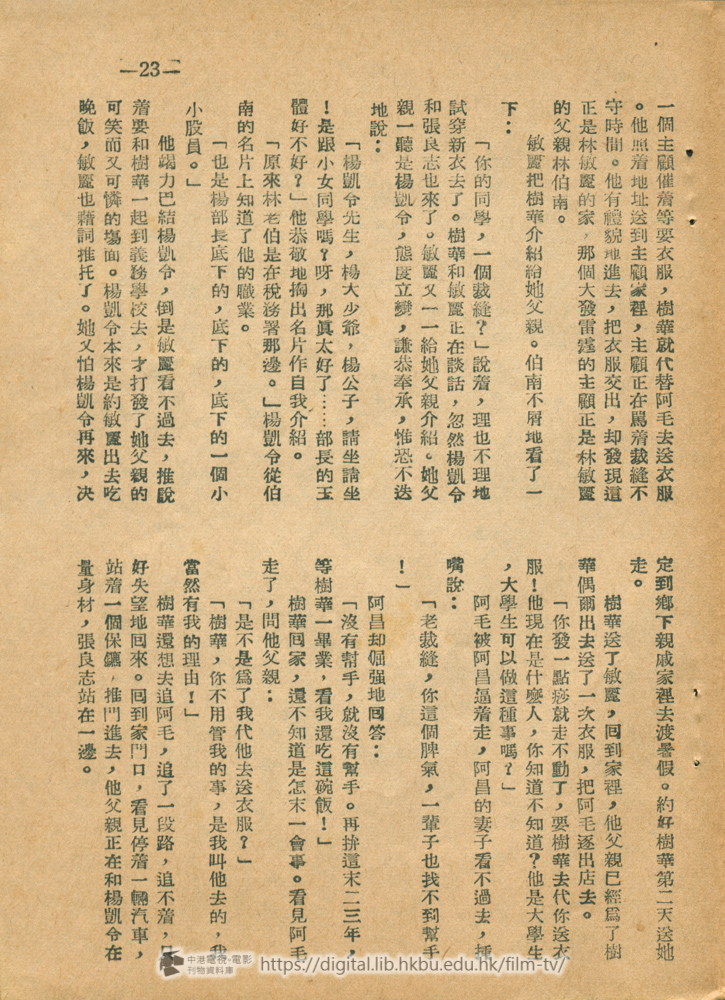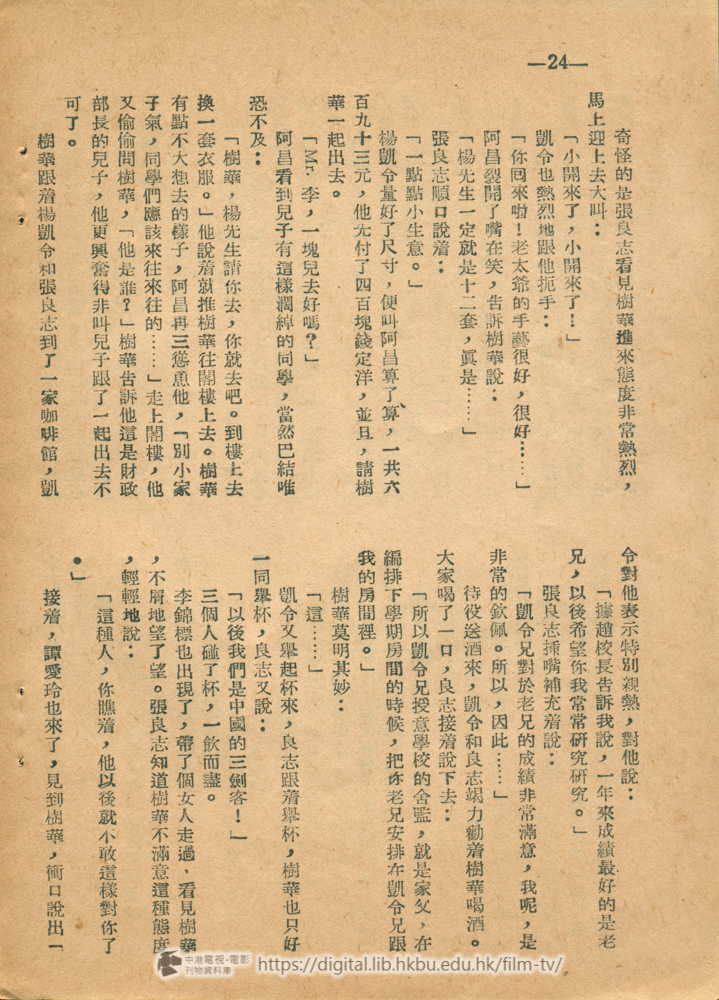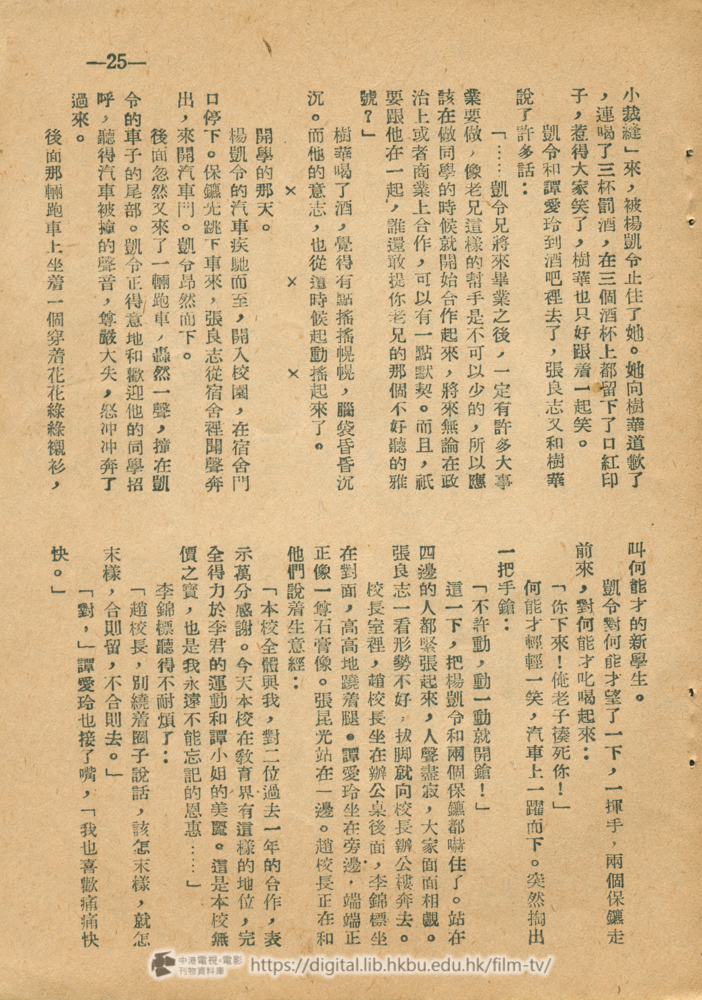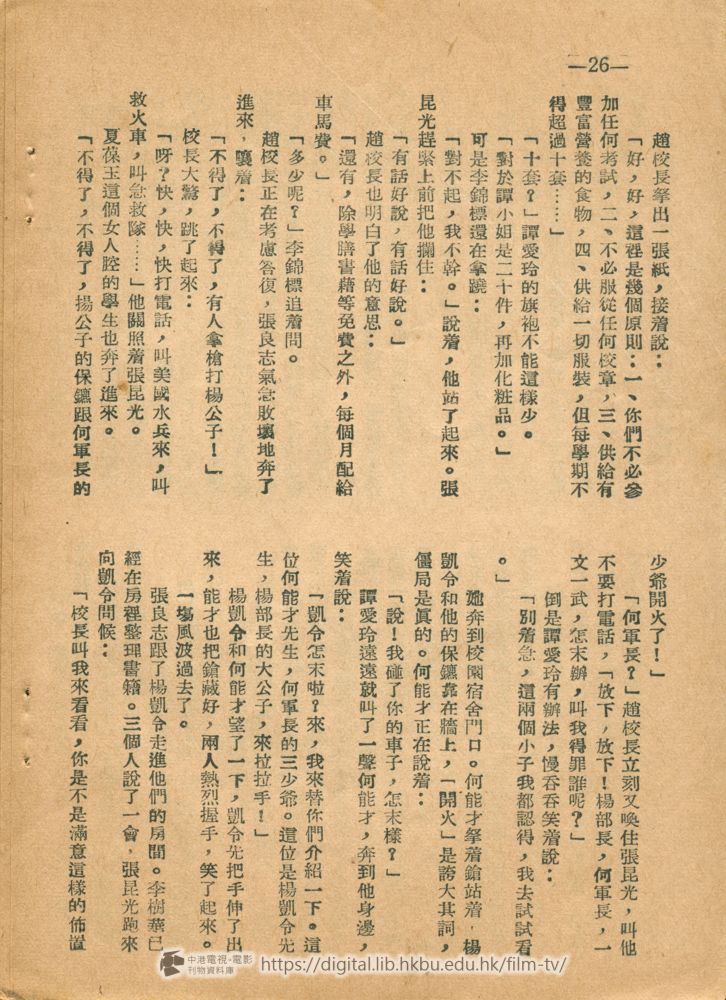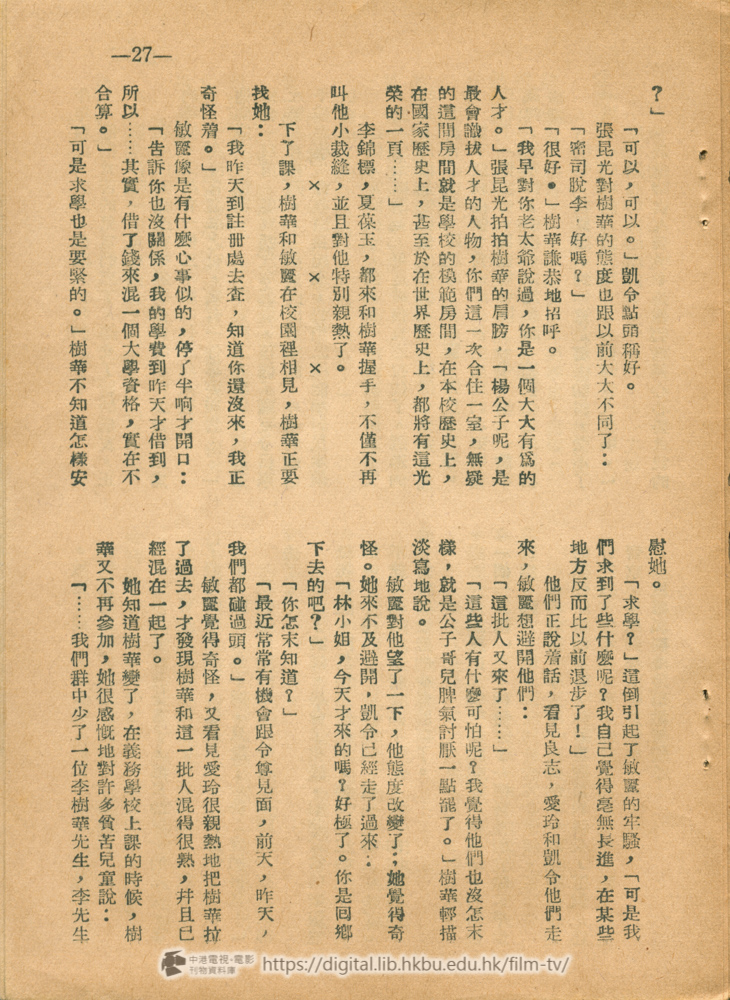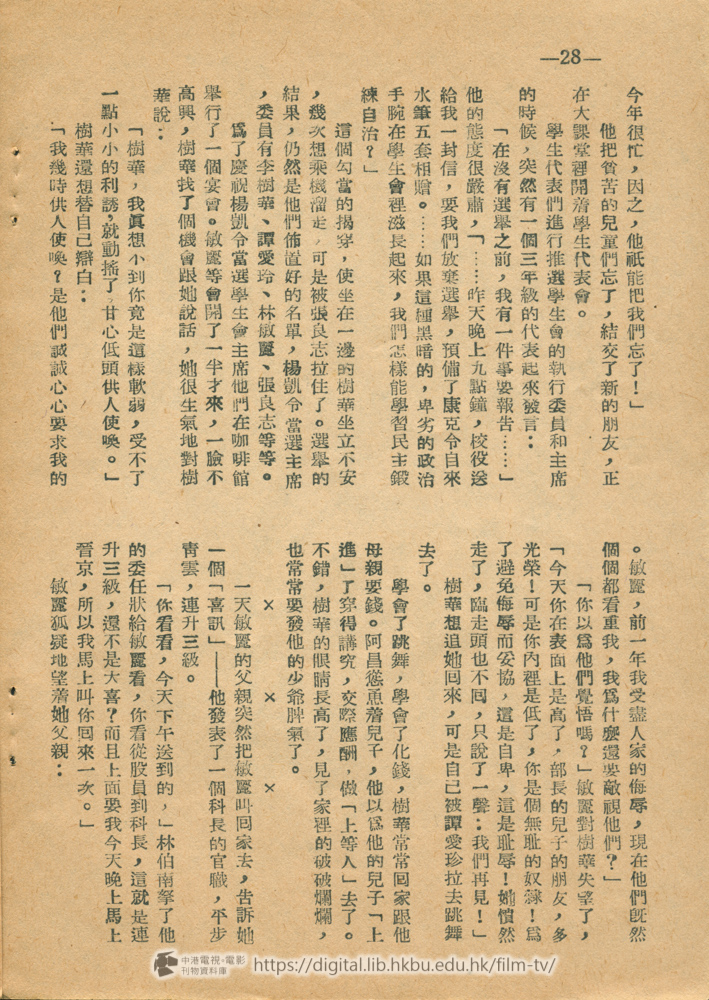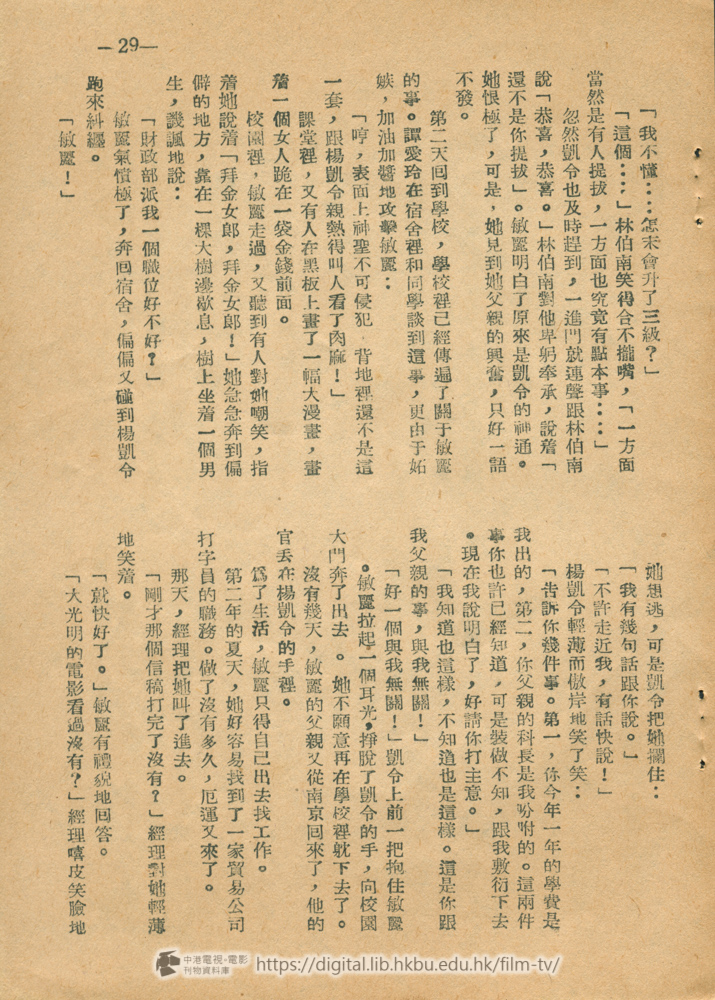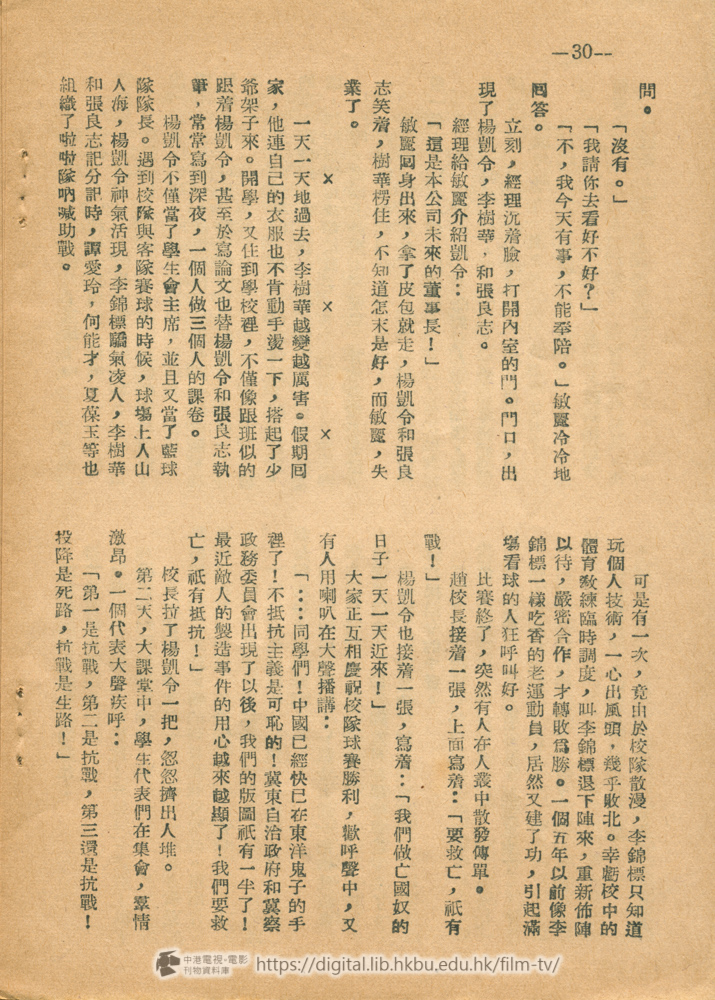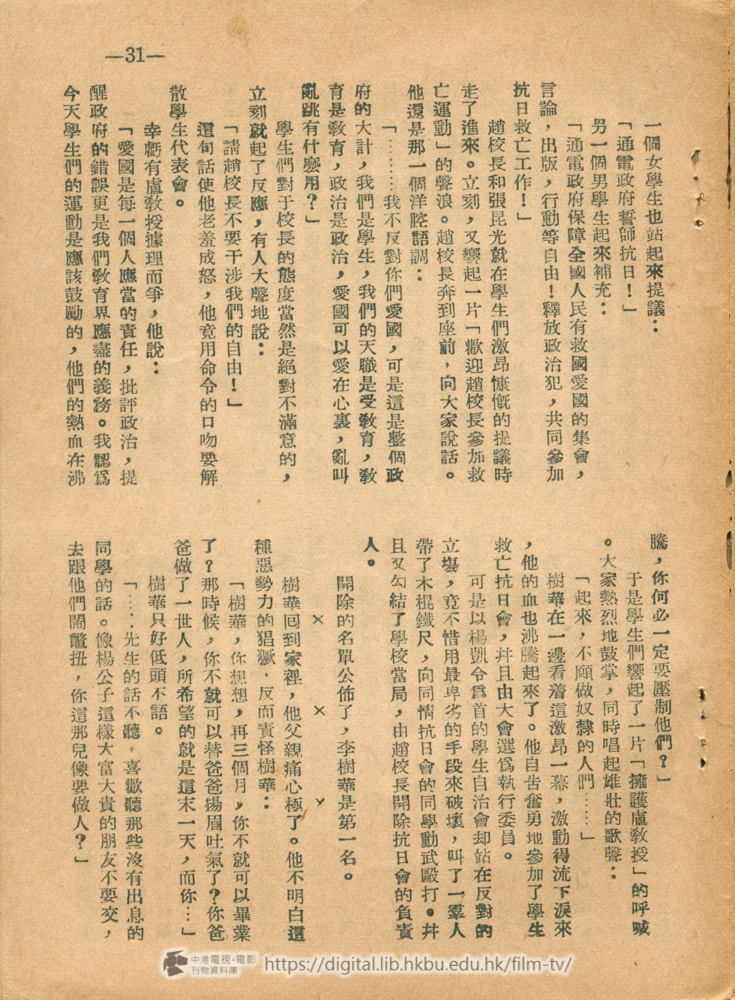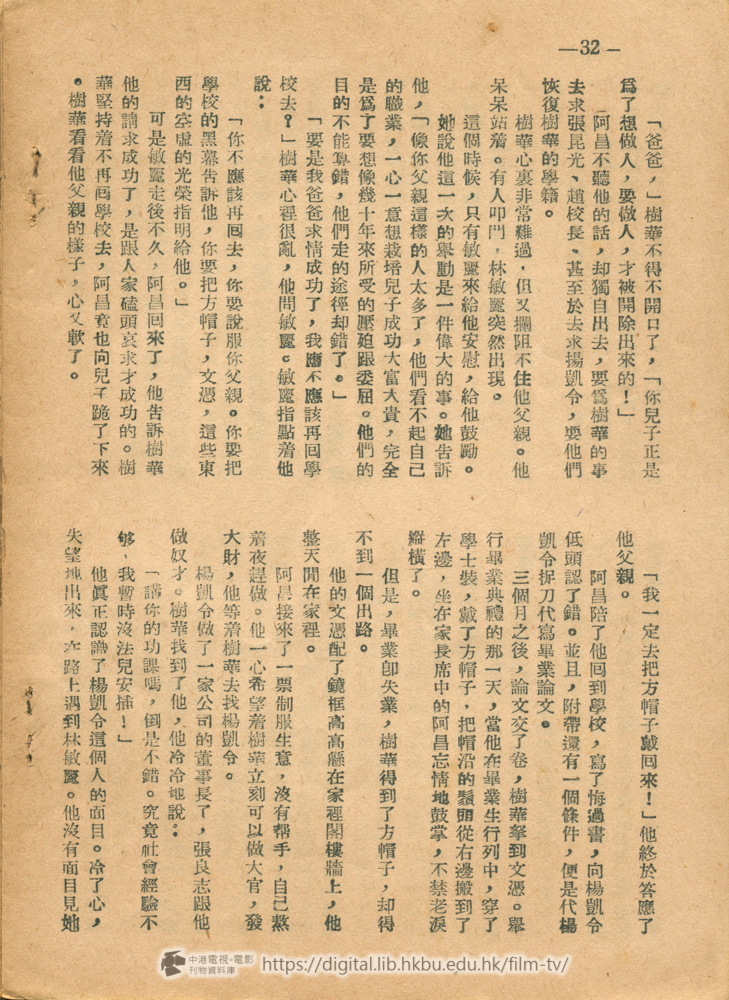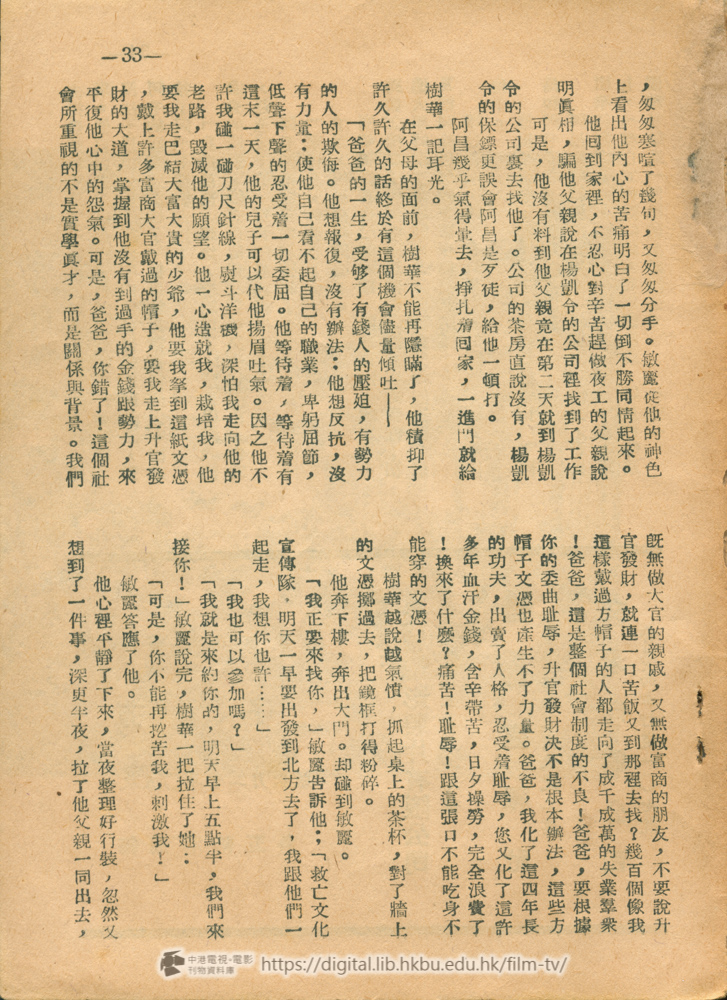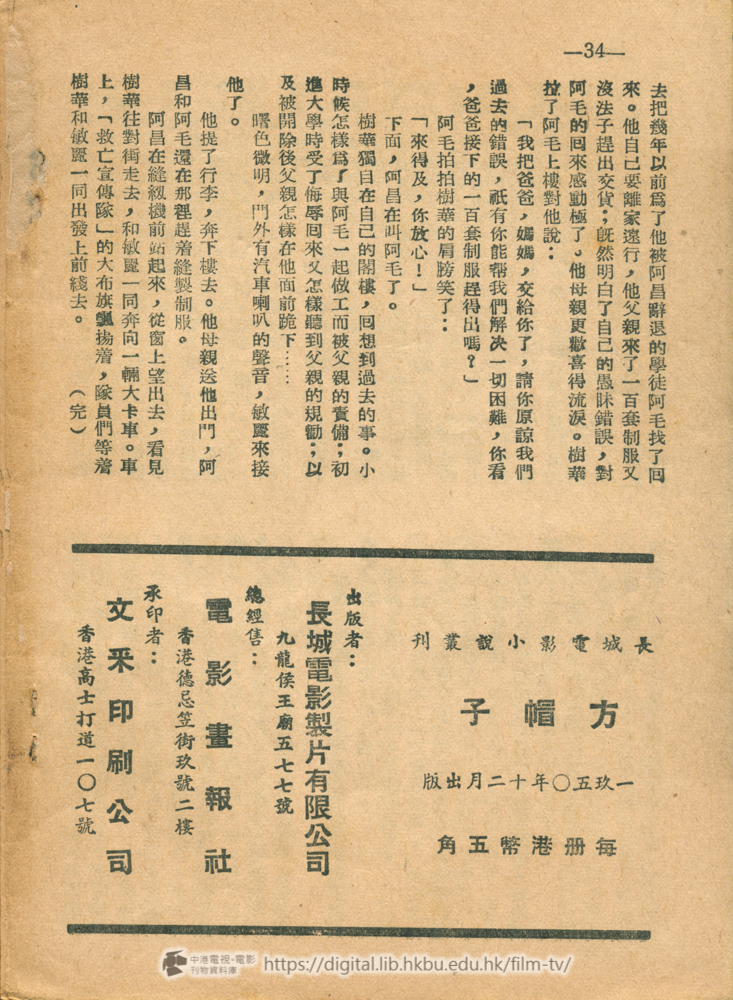方帽子
.電影小說.
李阿昌是一個手藝人,一個洋服裁縫。他開着一家「新昌洋服店」。店舖便是他的家,一間很小的店面房屋,正屋放一塊作板,一隻老式的縫紉機,幾個籐製的人身模型,一排衣櫉,一列放衣料和樣板的玻璃櫃,便是他的店的全部。上面的小閣樓,住了他的一家。他一家包括着他妻子和獨子樹華。店裏用了一個學徒,阿毛。此外,便沒有第五個人了。
樹華和阿毛年齡相彷,天天在一起。當阿昌不在家的時候,樹華常常和阿毛一起幇着做點店裏的事,譬如釘紐扣或者燙衣服,可是給阿昌撞見了,就要破口大駡。在他的眼裏,做裁縫是低賤的,他一心一意夢想着兒子做買辦,做經理,做大官,坐汽車,住洋房………他不許他的兒子再學他這一行生意,不許他碰一下針、線、燙斗。他幾次三番叫他的妻子禁止兒子搞這個「沒出息的勾當」:
「………怎末?難道你還嫌這碗裁縫飯不够苦?你還想叫你兒子吃下去?」
他不許兒子再吃這碗飯。他只想着,有一天,把他兒子送進大學得一個學士位,穿一穿學士裝,戴一戴學士帽——是的,他迷信着一樣東西:學士的方帽子。他的西服店門口貼着「畢業禮服出租」的招紙,他每到大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時便出入大學的門,給人家有錢子弟送畢業禮服。他看到無數大學生,穿了他的學士裝,戴了他的方帽子,獲得了學士學位,做買辦,做經埋,做大官………他的兒子李樹華,有一天也是這樣。他辛苦了一輩子,忍氣呑聲地勞碌工作,只等着這樣一天。
等着,等着,阿昌終于等到了樹華在中學畢了業。他由于出租畢業禮服的關係,認識博羅大學的訓育主任,給樹華去報了名,又橫託豎託,說盡好話,使樹華考了進去。
博羅大學開學的那天,阿昌親自把樹華送到學校。那個訓育主任的兒子張良志也是一個學生,正是阿昌的西服主顧,阿昌巴結地請他多多照應樹華。
他把樹華送到宿舍,找到了第二十六號房間。
房間裡,同學夏葆玉正在整理衣物。看見樹華進來,阿昌正和他在拉拉扯扯地說:
「這兒是大學堂……」阿昌掏出一叠鈔票塞給樹華,樹華不要,阿昌敎訓着他:「都是有錢的人,你不要太扣門兒,讓人家看不起!」
夏葆玉看看好笑,樹華也有點覺得了,便催着他父親快點囘去。可是阿昌還是不放心地叮囑着兒子:
「對什麽人都得客氣一點,別跟人家吵嘴,我們總得讓人家一歩。」
樹華點點頭。阿昌囘身要走,這房間裡另一個同學李錦標拍着球衝了進來,目中無人地便把球向夏葆玉身上拋去,嚇得夏葆玉這個女人腔的男人叫了起來。
李錦標得意地笑了起來,一囘頭,却看到樹華進來的時候沒留意把箱子放在他的床前,他咆哮起來了:
「誰放在這兒的?」
樹華沒想到李錦標竟這樣沒有禮貌,正想上去評理,被阿昌拉住了,幷且走上去賠個笑臉代爲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李先生,是我!」
李錦標也是阿昌的主顧,一見是他,詫異地問:
「咦,老裁縫,你來做什麽?」
阿昌急忙把兒子推上一步,給李錦標介紹:
「這是我孩子李樹華,這是李錦標先生,眞好極了,你們住一間房,請多照應!」
「什麽?」李錦標好奇地望望樹華,「你的兒子?」他不禁笑了起來。那個女人腔夏葆玉也跟着笑了。
樹華見他們笑,忍不住又想生氣,還是給阿昌拉住,阿昌又叮嚀了幾句,樹華才送他出去。
夏葆玉望着樹華走開,不屑地說道:
「神氣什麽,小裁縫!」
倒是李錦標不再生氣了,笑着說:
「我還欠老裁縫三十塊錢呢,算了吧!」
x x x
學生註册的那天,樹華遇到了他中學裏的一個女同學林敏麗,同時,看到了財政部長的兒子揚凱令來校的一幕:
訓育主任的兒子張良志在前面引路,然後是楊凱令的保鑣,然後才是楊凱令自己,昂首而入。校長和訓育主任張昆光到門口迎接。
校長沒有見過楊凱令,跑上去就拉了保鑣握手,幷且一連串的外國語氣的寒喧話:
「呀哈!讓我代表全校全體敎職員向你表示歡迎,幷且恭祝令尊康健!」
保鑣受寵若驚,連忙說明:
「俺不是的,俺不是的!」
訓導主任急急介紹:
「這位是楊公子,這位是趙校長。」
於是,校長又與楊凱令握手相見。
「對於你的宿舍,請你發表意見…………」
他們走到註册處,正碰到樹華和敏麗,敏麗的美麗的姿色,立刻吸引了楊凱令的注意,目不轉睛地望了半响。另一個女學生譚愛玲,輕飄飄地出來,才喚住了楊凱令:
「哈囉,凱令!」
「怎末你也到這兒來了?」凱令和譚愛玲是原來熟識的,沒想到她也轉學到博羅來了。
「你問趙校長嚜,他請了我半年了,可是朱校長那兒,我可得罪了。」
趙校長一臉奉承的笑,在一邊又用他的洋腔洋調來揷嘴:
「我在這裡,表示萬分敬意。蜜絲譚,如果我這裡沒有一個美麗的皇后,像你,不是太可怕了嗎?」
這一群人就這樣說着,笑着,湧進校長室去,辦好一切註册手續。
第二天早晨,大課堂裡開始了這一個學期的第一課。
上課鐘響了起來,李樹華,林敏麗,在一大群學生中,魚貫走進大課堂,找到他們自己的座位號碼坐下。李錦標憑着他是運動健將,態度傲慢,隨便挑了最後一排的座位坐好,然後,張良志像戲院裡的領票人似的,帶着楊凱令進來。
「這兒走,楊公子,這兒,這兒!」張良志把楊凱令領到他的座位,等他坐下,才走向自己座上,臨走還說:「我在那邊,有事叫我好了!」
這一課的敎授遲了十分鐘才來。敎授忙着在投機市塲裡做股票生意,對於敎課未免非常馬虎,他一進來就說:
「我們這個學期所用的課本是這三本,希望各位立刻去買好。最近原版書很不容易買,爲了經濟起見,利用我個人的關係,定了五十本,比外邊要便宜,要買的可以向助敎登記一下。下一次的課是一二兩章,請各位凖備一下。」
說完,就下課走了。
學生正要散去,張良志突然把大家喊住:
「大家不要走!」他走到講台上向大家說:「我提議借這個機會,把我們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代表推舉出來。我這裡有一張名單……」他掏出一張預先寫好的紙條來唸,「主席代表楊凱令,代表李錦標,張良志,女生代表譚愛玲,林敏麗。各位贊成不贊成?」
太家附和着說贊成。
可是一個高叫「反對」的聲音出來。那是李樹華。
這一聲「反對」使張良志突然地一窘。樹華站了起來,義正詞嚴地說:
「我們大家今天是第一天碰頭,誰有爲大家服務的精神,誰有爲大家做事的能力,大家都不知道,應該過兩個禮拜再來推舉!」
張良志臉色很難看,不屑地望了下樹華,對大家說:
「這個意見不能成立,過兩個禮拜太遲了!一個學期才幾個禮拜?剛才說的名單,大家怎末說?」
大家是一片贊成的聲音。這時,林敏麗喊了起來:
「我辭職!」
李樹華仍舊堅持着:
「我反對!」
李錦標向大家做了一個暗示,發了「一二三」命令,一羣人同聲說:
「小栽縫,少開口!」
樹華氣極了,可是大家已經一哄而散,他只得氣餒地低下頭,跟在人家後面走出去,只有林敏麗安慰着他:
「你別生氣,李樹華,生氣也沒用!」
張良志奔了過來,把林敏麗叫住:
「林小姐」,他堆了一臉的微笑,「下午四點半在DD’S開代表會,四點鐘坐Mr.楊的車子出發,請凖備好在聚英堂前邊等着。」
「我要辭職呢!」敏麗說。
「大家的公意怎末能辭呢?不要,不要!」
張良志走開,林敏麗恨恨地說着:
「Mr.楊,Mr.楊,他算是財政部長的兒子,就到處張牙舞爪!」
樹華聽了,暗暗想着:「怪不得我爸爸要我做大官!」
x x x
深夜。
楊凱令,譚愛玲,李錦標和張良志這四個寳貝學生玩暢了才囘學校。汽車開到學校門口,楊凱令塞了一叠鈔票給門房,門房開了門把他們放了進來。
李錦標和張良志囘到男生宿舍。在二十六號房間門口,推門,看見李樹華已經睡熟,兩個人進去,偷偷地把樹華床舖的床板猛力抽去,樹華驚醒大叫,把叧一張床上的夏葆玉也震醒了。
張良志拔脚就溜,李錦標躱上床去。樹華只得起來重新把床整好。恰巧訓育主任張昆光來檢査房間,用手電筒照見樹華站着,第二天早上便把他叫了去,不問情由,把他訓斥了一頓:
「……我很原諒你,你父親是個裁縫,在家庭敎育方面當然比不上人家,但你旣然到這個大學來,你就得拼命學上等人的樣子,把下等人的習慣改掉!」
「下等人」這三個字像釘子似地刺在樹華的耳朶裡。
「下等人,下等人!」
樹華受不住,憤恨地出來。
「下等人,下等人!」
樹華耳朶邊響着張昆光給他的這三個侮辱的字眼兒,他奔了出來,奔囘家去。
衝進新昌洋服店的門。
「爸爸,我不再囘到學校去了!」他一見到他父親就說。
「什麽?」阿昌一驚,「爲什麽?」
「大家侮辱我,同學,先生,他們都拏我開玩笑!」樹華簡直想哭,可是他堅强地忍住了,他直挺挺地站着,對他父親說:「可是,我不是下等人!我父親是個裁縫,不錯,可是爲什麽靠自己的手來養活自己的人倒是下等人,那些貪妄無恥,搜括民脂民膏的官僚,搖尾乞憐的洋奴倒是上等人!我們下等什麽?他們又憑什麽上等?」
阿昌慢慢地走近樹華身邊,含著眼淚,撫着樹華的手臂,對他說:
「這就是我叫你去唸書的道理!我是個裁縫,你就是個下等人,要是你再不往上爬,不做大官,買辦,你的兒子也是個下等人。我要你進大學,跟着這些人走,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你的子子孫孫……你千萬忍耐下來,瞧瞧你爸爸的頭髮,不要釀你爸爸太失望……」
樹華瞧見他爸爸的頭髮,又白了許多。老父的一片心意,軟化了樹華的自尊心,爲了父親的期望,他沒有辦法,他只得忍受,他又囘到了學校。
可是他變得非常孤僻,他常常在校園一角獨自散步,看書。他常常在體育舘的一隅,單獨地練身體,每看見有同學走近,他便躱開,他孤獨,寂寞。他永遠是沉默的。
有一次,他一個人坐在圖書舘裡看書,忽然一個姓盧的敎授過來拍拍他肩膀,他正想起立走開,被盧敎授按住:」
「你叫李樹華是不是?」
「是的,盧敎授。」
「你不大喜歡朋友是不是?」樹華正想囘答,盧敎授又繼續說了下去,「你不用囘答我。也許這是你自己的哲學,喜歡在孤獨中找尋你的眞理。可是這是不對的。人是屬于社會的,好的人屬于好的社會,壞的人屬于壞的社會,你必須生存在一個社會裡,是不是?」
樹華點點頭。
盧敎授又說:
「今天的佈吿牌看過了沒有?你去看看去!」
樹華莫明其妙地站了起來。他奔到走廊下佈吿牌前,看到了這樣一張佈吿:
「爲了溫習自已,救濟失學兒童,我們發起一個義務學校。同學們如果願意參加的,請在今天下午四時到大課堂來……」
四點鐘,他到了大學堂。
林敏麗是義務學校的重要人員之一,看到樹華前來參加,她高興極了,鼓掌歡迎。所有的孩子們也跟着熱烈地鼓起掌來。這份熱情,治好了樹華的孤獨憂鬱症。
x x x
學期終了,舉行大考了。
楊凱令化了錢通過張良志的關係,考書以前先把試題買了來。
其他買不到考題的學生們,便都向李樹華求敎。樹華的成績一向是最好的,他很輕易地通過了考試,放了假,便提着舖盖箱子囘家去了。
他囘家的那天,父親店裡的學徒阿毛病倒了,一個主顧催着等要衣服,樹華就代替阿毛去送衣服。他照着地址送到主顧家裡,主顧正在駡着裁縫不守時間。他有禮貌地進去,把衣服交出,却發現這正是林敏麗的家,那個大發雷霆的主顧正是林敏麗的父親林伯南。
敏麗把樹華介紹給她父親。伯南不屑地看了一下:
「你的同學,一個裁縫?」說着,理也不理地試穿新衣去了。樹華和敏麗正在談話,忽然楊凱令和張良志也來了。敏麗又一一給她父親介紹。她父親一聽是楊凱令,態度立變,謙恭奉承,惟恐不迭地說:
「楊凱令先生,楊大少爺,楊公子,請坐請坐!是跟小女同學嗎?呀,那眞太好了……部長的玉體好不好?」他恭敬地掏出名片作自我介紹。
「原來林老伯是在稅務署那邊。」楊凱令從伯南的名片上知道了他的職業。
「也是楊部長底下的,底下的,底下的一個小小股員。」
他竭力巴結楊凱令,倒是敏麗看不過去,推說着要和樹華一起到義務學校去,才打發了她父親的可笑而又可憐的塲面。楊凱令本來是約敏麗出去吃晚飯,敏麗也藉詞推托了。她又怕楊凱令再來,决定到鄕下親戚家裡去渡暑假。約好樹華第二天送她走。
樹華送了敏麗,囘到家裡,他父親已經爲了樹華偶爾出去送了一次衣服,把阿毛逐出店去。
「你發一點痧就走不動了,要樹華去代你送衣服!他現在是什麽人,你知道不知道?他是大學生,大學生可以做這種事嗎?」
阿毛被阿昌逼着走,阿昌的妻子看不過去,揰嘴說:
「老裁縫,你這個脾氣,一輩子也找不到幫手!」
阿昌却倔强地囘答:
「沒有幇手,就沒有幫手。再拚這末二三年,等樹華一畢業,看我還吃這碗飯!」
樹華囘家,還不知道是怎末一會事。看見阿毛走了,問他父親:
「是不是爲了我代他去送衣服?」
「樹華,你不用管我的事,是我叫他去的,我當然有我的理由!」
樹華還想去追阿毛,追了一段路,追不着,只好失望地囘來。囘到家門口,看見停着一輛汽車,站着一個保鑣,推門進去,他父親正在和楊凱令在量身材,張良志站在一邊。
奇怪的是張良志看見樹華進來態度非常熱烈,馬上迎上去大叫:
「小開來了,小開來了!」
凱令也熱烈地跟他扼手:
「你囘來啦!老太爺的手藝很好,很好……」
阿昌裂開了嘴在笑,吿訴樹華說:
「楊先生一定就是十二套,眞是……」
張良志順口說着:
「一點點小生意。」
楊凱令量好了尺寸,便叫阿昌算了算,一共六百九十三元,他先付了四百塊錢定洋,並且,請樹華一起出去。
「Mr.李,一塊兒去好嗎?」
阿昌看到兒子有這樣濶綽的同學,當然巴結唯恐不及:
「樹華,楊先生請你去,你就去吧。到樓上去換一套衣服。」他說着就推樹華往閣樓上去。樹華有點不大想去的樣子,阿昌再三慫恿他,「別小家子氣,同學們應該來往來往的……」走上閣樓,他又偷偷問樹華,「他是誰?」樹華吿訴他這是財政部長的兒子,他更興奮得非叫兒子跟了一起出去不可了。
樹華跟著楊凱令和張良志到了一家咖啡館,凱令對他表示特別親熱,對他說:
「據趙校長吿訴我說,一年來成績最好的是老兄,以後希望你我常常硏究硏究。」
張良志挿嘴補充着說:
「凱令兄對於老兄的成績非常滿意,我呢,是非常的欽佩。所以,因此……」
待役送酒來,凱令和良志竭力勸着樹華喝酒。大家喝了一口,良志接着說下去:
「所以凱令兄授意學校的舍監,就是家父,在編排下學期房間的時候,把你老兄安排在凱令兄跟我的房間裡。」
樹華莫明其妙:
「這……」
凱令又舉起杯來,良志跟着舉杯,樹華也只好一同舉杯,良志又說:
「以後我們是中國的三劍客!」
三個人碰了杯,一飮而盡。
李錦標也出現了,帶了個女人走過,看見樹華,不屑地望了望。張良志知道樹華不滿意這種態度,輕輕地說:
「這種人,你瞧着,他以後就不敢這樣對你了。」
接着,譚愛玲也來了,見到樹華,衝口說出「小裁縫」來,被楊凱令止住了她。她向樹華道歉了,連喝了三杯罰酒,在三個酒杯上都留下了口紅印子,惹得大家笑了,樹華也只好跟着一起笑。
凱令和譚愛玲到酒吧裡去了,張良志又和樹華說了許多話:
「……凱令兄將來畢業之後,一定有許多大事業要做,像老兄這樣的幇手是不可以少的,所以應該在做同學的時候就開始合作起來,將來無論在政治上或者商業上合作,可以有一點默契。而且,祇要跟他在一起。誰還敢捉你老兄的那個不好聽的雅號?」
樹華喝了酒,覺得有點搖搖幌幌,腦袋昏昏沉沉。而他的意志,也從這時候起動搖起來了。
x x x
開學的那天。
楊凱令的汽車疾馳而至,開入校園,在宿舍門口停下。保鑣先跳下車來,張良志從宿舍裡聞聲奔出,來開汽車門。凱令昂然而下。
後面忽然又來了一輛跑車,轟然一聲,撞在凱令的車子的尾部。凱令正得意地和歡迎他的同學招呼,聽得汽車被撞的聲音,尊嚴大失,怒冲冲奔了過來。
後面那輛跑車上坐着一個穿着花花綠綠襯衫,叫何能才的新學生。
凱令對何能才望了一下,一揮手,兩個保鑣走前來,對何能才叱喝起來:
「你下來!俺老子揍死你!」
何能才輕輕一笑,汽車上一躍而下。突然掏出一把手鎗:
「不許動,動一動就開鎗!」
這一下,把楊凱令和兩個保鑣都嚇住了。站在四邊的人都緊張起來,人聲盡寂,大家面面相覷。張良志一看形勢不好,拔脚就向校長辦公樓奔去。
校長室裡,趙校長坐在辦公桌後面,李錦標坐在對面,高高地蹺着腿。譚愛玲坐在旁邊,端端正正像一尊石膏像。張昆光站在一邊。趙校長正在和他們說着生意經:
「本校全體與我,對二位過去一年的合作,表示萬分感謝。今天本校在敎育界有這樣的地位,完全得力於李君的運動和譚小姐的美麗。這是本校無價之寳,也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恩惠……」
李錦標聽得不耐煩了:
「趙校長,別繞著圈子說話,該怎末樣,就怎末樣,合則留,不合則去。」
「對,」譚愛玲也接了嘴,「我也喜歡痛痛快快。」
趙校長拏出一張紙,接着說:
「好,好,這裡是幾個原則:一、你們不必參加任何考試,二、不必服從任何校章,三、供給有豐富營養的食物,四、供給一切服裝,但每學期不得超過十套……」
「十套?」譚愛玲的旗袍不能這樣少。
「對於譚小姐是二十件,再加化粧品。」
可是李錦標還在拿蹺:
「對不起,我不幹。」說着,他站了起來。張昆光趕緊上前把他攔住: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趙校長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還有,除學膳書藉等免費之外,每個月配給車馬費。」
「多少呢?」李錦標追著問。
趙校長正在考慮答復,張良志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嚷着:
「不得了,不得了,有人拿槍打楊公子!」
校長大驚,跳了起來:
「呀?快,快,快打電話,叫美國水兵來,叫救火車,叫急救隊……」他關照着張昆光。
夏葆玉這個女人腔的學生也奔了進來。
「不得了,不得了,揚公子的保鑣跟何軍長的少爺開火了!」
「何軍長?」趙校長立刻又喚住張昆光,叫他不要打電話,「放下,放下!楊部長,何軍長,一文一武,怎末辦,叫我得罪誰呢?」
倒是譚愛玲有辦法,慢呑呑笑着說:
「別着急,這兩個小子我都認得,我去試試看。」
她奔到校園宿舍門口。何能才拏着鎗站着,楊凱令和他的保鑣靠在牆上,「開火」是誇大其詞,僵局是眞的。何能才正在說着:
「說!我碰了你的車子,怎末樣?」
譚愛玲遠遠就叫了一聲何能才,奔到他身邊,笑着說:
「凱令怎末啦?來,我來替你們介紹一下。這位何能才先生,何軍長的三少爺。這位是楊凱令先生,楊部長的大公子,來拉拉手!」
楊凱令和何能才望了一下,凱令先把手伸了出來,能才也把鎗藏好,兩人熱烈握手,笑了起來。
一塲風波過去了。
張良志跟了楊凱令走進他們的房間。李樹華已經在房裡整理書籍。三個人說了一會,張昆光跑來向凱令問候:
「校長叫我來看看,你是不是滿意這樣的佈置?」
「可以,可以。」凱令點頭稱好。
張昆光對樹華的態度也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密司脫李,好嗎?」
「很好。」樹華謙恭地招呼。
「我早對你老太爺說過,你是一個大大有爲的人才。」張昆光拍拍樹華的肩膀,「楊公子呢,是最會識拔人才的人物,你們這一次合住一室,無疑的這間房間就是學校的模範房間,在本校歷史上,在國家歷史上,甚至於在世界歷史上,都將有這光榮的一頁……」
李錦標,夏葆玉,都來和樹華握手,不僅不再叫他小裁縫,並且對他特別親熱了。
x x x
下了課,樹華和敏麗在校園裡相見,樹華正要找她:
「我昨天到註册處去査,知道你還沒來,我正奇怪着。」
敏麗像是有什麽心事似的,停了半响才開口:
「吿訴你也沒關係,我的學費到昨天才借到,所以……其實,借了錢來混一個大學資格,實在不合算。」
「可是求學也是要緊的。」樹華不知道怎樣安慰她。
「求學?」這倒引起了敏麗的牢騷,「可是我們求到了些什麽呢?我自己覺得亳無長進,在某些地方反而比以前退歩了!」
他們正說着話,看見良志,愛玲和凱令他們走來,敏麗想避開他們:
「這批人又來了……」
「這些人有什麽可怕呢?我覺得他們也沒怎末樣,就是公子哥兒脾氣討厭一點罷了。」樹華輕描淡寫地說。
敏麗對他望了一下,他態度改變了;她覺得奇怪。她來不及避開,凱令已經走了過來:
「林小姐,今天才來的嗎?好極了。你是囘鄕下去的吧?」
「你怎末知道?」
「最近常常有機會跟令尊見面,前天,昨天,我們都碰過頭。」
敏麗覺得奇怪,又看見愛玲很親熱地把樹華拉了過去,才發現樹華和這一批人混得很熟,幷且已經混在一起了。
她知道樹華變了,在義務學校上課的時候,樹華又不再參加,她很感慨地對許多貧苦兒童說:
「……我們群中少了一位李樹華先生,李先生今年很忙,因之,他祇能把我們忘了!」
他把貧苦的兒童們忘了,結交了新的朋友,正在大課堂裡開着學生代表會。
學生代表們進行推選學生會的執行委員和主席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三年級的代表起來發言:
「在沒有選舉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報吿……」他的態度很嚴肅,「……昨天晚上九點鐘,校役送給我一封信,要我們放棄選舉,預備了康克令自來水筆五套相贈。……如果這種黑暗的,卑劣的政治手腕在學生會裡滋長起來,我們怎樣能學習民主鍛練自治?」
這個勾當的揭穿,使坐在一邊的樹華坐立不安,幾次想乘機溜走,可是被張良志拉住了。選舉的結果,仍然是他們佈置好的名單,楊凱令當選主席,委員有李樹華、譚愛玲、林敏麗、張良志等等。
爲了慶祝楊凱令當選學生會主席他門在咖啡館舉行了一個宴會。敏麗等會開了一半才來,一臉不高興,樹華找了個機會跟她說話,她很生氣地對樹華說:
「樹華,我眞想不到你竟是這樣軟弱,受不了一點小小的利誘,就動搖了,甘心低頭供人使喚。」
樹華還想替自己辯白:
「我幾時供人使喚?是他們誠誠心心要求我的。敏麗,前一年我受盡人家的侮辱,現在他們旣然個個都看重我,我爲什麽還要敵視他們?」
「你以爲他們覺悟嗎?」敏麗對樹華失望了,「今天你在表面上是高了,部長的兒子的朋友,多光榮!可是你內裡是低了,你是個無耻的奴隸!爲了避免侮辱而妥協,這是自卑,這是耻辱!她憤然走了,臨走頭也不囘,只說了一聲:我們再見!」
樹華想追她囘來,可是自己被譚愛珍拉去跳舞去了。
學會了跳舞,學會了化錢,樹華常常囘家跟他母親要錢。阿昌慫恿着兒子,他以爲他的兒子「上進」了穿得講究,交際應酬,做「上等人」去了。不錯,樹華的眼睛長高了,見了家裡的破破爛爛,也常常要發他的少爺脾氣了。
x x x
一天敏麗的父親突然把敏麗叫囘家去,吿訴她一個「喜訊」——他發表了一個科長的官職,平步靑雲,連升三級。
「你看看,今天下午送到的,」林伯南拏了他的委任狀給敏麗看,你看從股員到科長,這就是連升三級,還不是大喜?而且上面要我今天晚上馬上晉京,所以我馬上叫你囘來一次。」
敏麗孤疑地望着她父親:
「我不懂……怎未會升了三級?」
「這個……」林伯南笑得合不攏嘴,「一方面當然是有人提拔,一方面也究竟有點本事……」
忽然凱令也及時趕到,一進門就連聲跟林伯南說「恭喜,恭喜。」林伯南對他卑躬奉承,說着「還不是你提拔」。敏麗明白了原來是凱令的神通。她恨極了,可是,她見到她父親的興奮,只好一語不發。
第二天囘到學校,學校裡己經傳遍了關于敏麗的事。譚愛玲在宿舍裡和同學談到這事,更由于妬嫉,加油加醬地攻擊敏麗:
「哼,表面上神聖不可侵犯,背地理還不是這一套,跟楊凱令親熱得叫人看了肉麻!」
課堂裡,又有人在黑板上畫了一幅大漫畫,畫着一個女人跪在一袋金錢前面。
校園裡,敏麗走過,又聽到有人對她嘲笑,指着她說着「拜金女郞,拜金女郞!」她急急奔到偏僻的地方,靠在一棵大樹邊歇息,樹上坐着一個男生,譏諷地說:
「財政部派我一個職位好不好?」
敏麗氣憤極了,奔囘宿舍,偏偏又碰到楊凱令跑來糾纒。
「敏麗!」
她想逃,可是凱令把她攔住:
「我有幾句話跟你說。」
「不許走近我,有話快說!」
楊凱令輕薄而傲岸地笑了笑:
「吿訴你幾件事。第一,你今年一年的學費是我出的,第二,你父親的科長是我吩咐的。這兩件事你也許已經知道,可是裝做不知,跟我敷衍下去。現在我說明白了,好請你打主意。」
「我知道也這樣,不知道也是這樣。這是你跟我父親的事,與我無關!」
「好一個與我無關!」凱令上前一把抱住敏麗
。敏麗拉起一個耳光,掙脫了凱令的手,向校園大門奔了出去。她不願意再在學校裡躭下去了。
沒有幾天,敏麗的父親又從南京囘來了,他的官丟在楊凱令的手裡。
爲了生活,敏麗只得自己出去找工作。
第二年的夏天,她好容易找到了一家貿易公司打字員的職務。做了沒有多久,厄運又來了。
那天,經理把她叫了進去。
「剛才那個信稿打完了沒有?」經理對她輕薄地笑着。
「就快好了。」敏麗有禮貌地囘答。
「大光明的電影看過沒有?」經理嘻皮笑臉地問。
「沒有。」
「我請你去看好不好?」
「不,我今天有事,不能奉陪。」敏麗冷冷地囘答。
立刻,經理沉著臉,打開內室的門。門口,出現了楊凱令,李樹華,和張良志。
經理給敏麗介紹凱令:
「這是本公司未來的董事長!」
敏麗囘身出來,拿了皮包就走,楊凱令和張良志笑着,樹華楞住,不知道怎末是好,而敏麗,失業了。
x x x
一天一天地過去,李樹華越變越厲害。假期囘家,他連自己的衣服也不肯動手燙一下,搭起了少爺架子來。開學,又住到學校裡,不僅像跟班似的跟着楊凱令,甚至於寫論文也替楊凱令和張良志執筆,常常寫到深夜,一個人做三個人的課卷。
楊凱令不僅當了學生會主席,並且又當了藍球隊隊長。遇到校隊與客隊賽球的時候,球塲上人山人海,楊凱令神氣活現,李錦標驕氣凌人,李樹華和張良志記分記時,譚愛玲,何能才,夏葆玉等也組織了啦啦隊吶喊助戰。
可是有一次,竟由於校隊散漫,李錦標只知道玩個人技術,一心出風頭,幾乎敗北。幸虧校中的體育敎練臨時調度,叫李錦標退下陣來,重新佈陣以待,嚴密合作,才轉敗爲勝。一個五年以前像李錦標一樣吃香的老運動員,居然又建了功,引起滿塲看球的人狂呼叫好。
比賽終了,突然有人在人叢中散發傳單。
趙校長接着一張,上面寫着:「要救亡,祇有戰!」
楊凱令也接着一張,寫着:「我們做亡國奴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來!」
大家正互相慶祝校隊球賽勝利,歡呼聲中,又有人用喇叭在大聲播講:
「……同學們!中國已經快已在東洋鬼子的手裡了!不抵抗主義是可恥的!冀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出現了以後,我們的版圖祇有一半了!最近敵人的製造事件的用心越來越顯了!我們要救亡,祇有抵抗!」
校長拉了楊凱令一把,怱怱擠出人堆。
第二天,大課堂中,學生代表們在集會,羣情激昂。一個代表大聲疾呼:
「第一是抗戰,第二是抗戰,第三還是抗戰!投降是死路,抗戰是生路!」
一個女學生也站起來提議:
「通電政府誓師抗日!」
叧一個男學生起來補充:
「通電政府保障全國人民有救國愛國的集會,言論,出版,行動等自由!釋放政治犯,共同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趙校長和張昆光就在學生們激昂慷慨的提議時走了進來。立刻,又響起一片「歡迎趙校長參加救亡運動」的聲浪。趙校長奔到座前,向大家說話。他還是那一個洋腔語調:
「………我不反對你們愛國,可是這是整個政府的大計,我們是學生,我們的天職是受教育,敎育是敎育,政治是政治,愛國可以愛在心裏,亂叫亂跳有什麽用?」
學生們對于校長的態度當然是絕對不滿意的,立刻就起了反應,有人大聲地說:
「請趙校長不要干涉我們的自由!」
這句話使他老羞成怒,他竟用命令的口吻要解散學生代表會。
幸虧有盧敎授據理而爭,他說:
「愛國是每一個人應當的責任,批評政治,提醒政府的錯誤更是我們敎育界應盡的義務。我認爲今天學生們的運動是應該鼓勵的,他們的熱血在沸騰,你何必一定要壓制他們?」
于是學生們響起了一片「擁護盧敎授」的呼喊。大家熱烈地鼓掌,同時唱起雄壯的歌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樹華在一邊看着這激昂一幕,激動得流下淚來,他的血也沸騰起來了。他自吿奮勇地參加了學生救亡抗日會,幷且由大會選爲執行委員。
可是以楊凱令為首的學生自治會却站在反對的立塲,竟不惜用最卑劣的手段來破壞,叫了一羣人帶了木棍鐵尺,向同情抗日會的同學動武毆打。并且又勾結了學校當局,由趙校長開除抗日會的負責人。
開除的名單公佈了,李樹華是第一名。
x x x
樹華囘到家裡,他父親痛心極了。他不明白這種惡勢力的猖獗,反而責怪樹華:
「樹華,你想想,再三個月,你不就可以畢業了?那時候,你不就可以替爸爸揚眉吐氣了?你爸爸做了一世人,所希望的就是這末一天,而你…」
樹華只好低頭不語。
「……先生的話不聽,喜歡聽那些沒有出息的同學的話。像楊公子這樣大富大貴的朋友不要交,去跟他們鬧鼈扭,你這那兒像要做人?」
「爸爸,」樹華不得不開口了,「你兒子正是爲了想做人,要做人,才被開除出來的!」
阿昌不聽他的話,却獨自出去,要爲樹華的事去求張昆光、趙校長、甚至於去求揚凱令,要他們恢復樹華的學籍。
樹華心裏非常難過,但又攔阻不住他父親。他呆呆站着。有人叩門,林敏麗突然出現。
這個時候,只有敏麗來給他安慰,給他鼓勵。
她說他這一次的舉動是一件偉大的事。她吿訴他,「像你父親這樣的人太多了,他們看不起自己的職業,一心一意想栽培兒子成功大富大貴,完全是爲了要想像幾十年來所受的壓廹跟委屈。他們的目的不能算錯,他們走的途徑却錯了。」
「要是我爸爸求情成功了,我應不應該再囘學校去?」樹華心裡很亂,他問敏麗。敏麗指點着他說:
「你不應該再囘去,你要說服你父親。你要把學校的黑幕告訴他,你要把方帽子,文憑,這些東西的空虛的光榮指明給他。」
可是敏麗走後不久,阿昌囘來了,他吿訴樹華他的請求成功了,是跟人家磕頭哀求才成功的。樹華堅持着不再囘學校去,阿昌竟也向兒子跪了下來。樹華看看他父親的樣子,心又軟了。
「我一定去把方帽子戴囘來!」他終於答應了他父親。
阿昌陪了他囘到學校,寫了悔過書,向楊凱令低頭認了錯。並且,附帶還有一個條件,便是代楊凱令捉刀代寫畢業論文。
三個月之後,論文交了卷,樹華拏到文憑。舉行畢業典禮的那一天,當他在畢業生行列中,穿了學士裝,戴了方帽子,把帽沿的鬚頭從右邊搬到了左邊,坐在家長席中的阿昌忘情地鼓掌,不禁老淚縱橫了。
但是,畢業卽失業,樹華得到了方帽子,却得不到一個出路。
他的文憑配了鏡框高高懸在家裡閣樓牆上,他整天閒在家裡。
阿昌接來了一票制服生意,沒有帮手,自己熬着夜趕做。他一心希望着樹華立刻可以做大官,發大財,他等着樹華去找楊凱令。
楊凱令做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長了,張良志跟他做奴才。樹華找到了他,他冷冷地說:
「講你的功課嗎,倒是不錯。究竟社會經驗不够,我暫時沒法兒安插!」
他眞正認識了楊凱令這個人的面目。冷了心,失望地出來,在路上遇到林敏麗。他沒有面目見她,匆匆寒喧了幾句,又匆匆分手。敏麗從他的神色上看出他內心的苦痛明白了一切倒不勝同情起來。
他囘到家裡,不忍心對辛苦趕做夜工的父親說明眞相,騙他父親說在楊凱令的公司裡找到了工作
可是,他沒有料到他父親竟在第二天就到楊凱令的公司裏去找他了。公司的茶房直說沒有,楊凱令的保鏢更誤會阿昌是歹徒,給他一頓打。
阿昌幾乎氣得暈去,掙扎着囘家,一進門就給樹華一記耳光。
在父母的面前,樹華不能再隱瞞了,他積抑了許久許久的話終於有這個機會儘量傾吐——
「爸爸的一生,受够了有錢人的壓廹,有勢力的人的欺侮。他想報復,沒有辦法;他想反抗,沒有力量;使他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職業,卑躬屈節,低聲下聲的忍受着一切委屈。他等待着,等待着有這末一天,他的兒子可以代他揚眉吐氣。因之他不許我碰一碰刀尺針線,熨斗洋機,深怕我走向他的老路,毀滅他的願望。他一心造就我,栽培我,他要我走巴結大富大貴的少爺,他要我拏到這紙文憑,戴上許多富商大官戴過的帽子,要我走上升官發財的大道,掌握到他沒有到過手的金錢跟勢力,來平復他心中的怨氣。可是,爸爸,你錯了!這個社會所重視的不是實學眞才,而是關係與背景。我們旣無做大官的親戚,又無做富商的朋友,不要說升官發財,就連一口苦飯又到那裡去找?幾百個像我這樣戴過方帽子的人都走向了成千成萬的失業羣衆!爸爸,這是整個社會制度的不良!爸爸,要根據你的委曲耻辱,升官發財决不是根本辦法,這些方帽子文憑也產生不了力量。爸爸,我化了這四年長的功夫,出賣了人格,忍受着耻辱,您又化了這許多年血汗金錢,含辛帶苦,日夕操勞,完全浪費了!換來了什麽?痛苦!耻辱!跟這張口不能吃身不能穿的文憑!
樹華越說越氣憤,抓起桌上的茶杯,對了牆上的文憑擲過去,把鏡框打得粉碎。
他奔下樓,奔出大門。却碰到敏麗。
「我正要來找你,」敏麗吿訴他;「救亡文化宣傳隊,明天一早要出發到北方去了,我跟他們一起走,我想你也許……」
「我也可以參加嗎?」
「我就是來約你的,明天早上五點半,我們來接你!」敏麗說完,樹華一把拉住了她:
「可是,你不能再挖苦我,剌激我!」
敏麗答應了他。
他心裡平靜了下來,當夜整理好行裝,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深更半夜,拉了他父親一同出去,
去把幾年以前爲了他被阿昌辭退的學徒阿毛找了囘來。他自己要離家遠行,他父親來了一百套制服又沒法子趕出交貨;旣然明白了自己的愚眛錯誤,對阿毛的囘來感動極了。他母親更歡喜得流淚。樹華拉了阿毛上樓對他說:
「我把爸爸,媽媽,交給你了,請你原諒我們過去的錯誤,祇有你能帮我們解决一切困難,你看,爸爸接下的一百套制服趕得出嗎?」
阿毛拍拍樹華的肩膀笑了:
「來得及,你放心!」
下面,阿昌在叫阿毛了。
樹華獨自在自己的閣樓,囘想到過去的事。小時候怎樣爲了與阿毛一起做工而被父親的責備;初進大學時受了侮辱囘來又怎樣聽到父親的規勸;以及被開除後父親怎樣在他面前跪下……
曙色微明,門外有汽車喇叭的聲音,敏麗來接他了。
他提了行李,奔下樓去。他母親送他出門,阿昌和阿毛還在那裡趕着縫製制服。
阿昌在縫紉機前站起來,從窗上望出去,看見樹華往對街走去,和敏麗一同奔向一輛大卡車。車上,「救亡宣傳隊」的大布旗飄揚着,隊員們等着樹華和敏麗一同出發上前綫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