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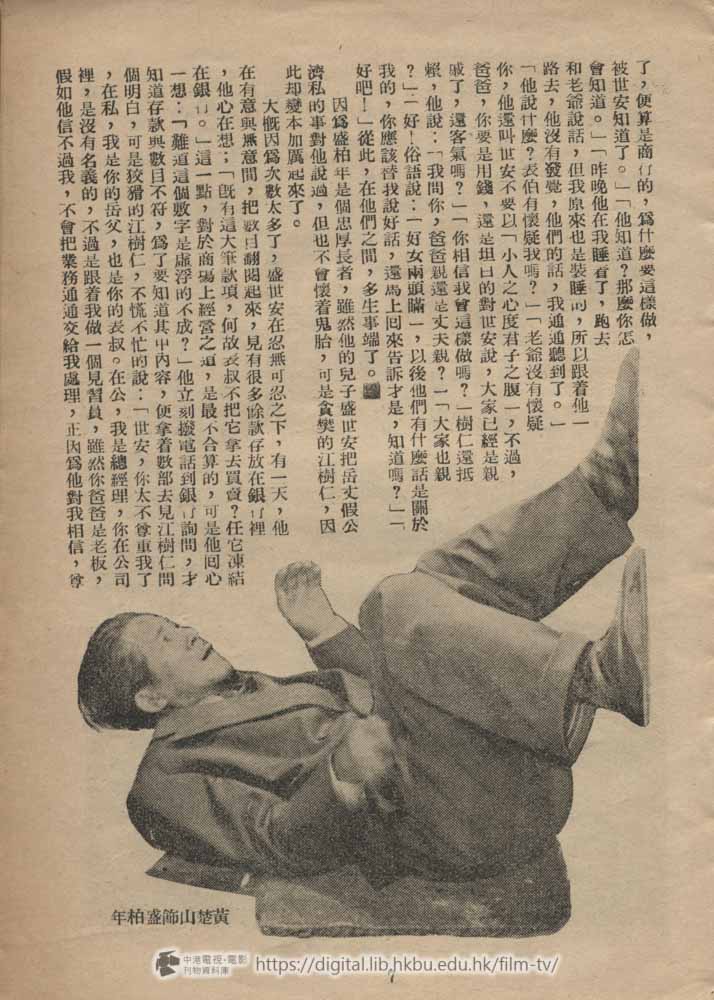

























冷桃源・電影小說・
一天的中午,正在火傘高張的當兒,華都中區近北的一個碼頭裡,有許多男男女女,不畏烈日逞兇,一樣的站着,引領瞻眺。
「爲什麽這麽久還不來!」其中的一位女郞不耐煩地叫。
原來這一羣人都是等候着一艘大洋船抵步。
「來了!來了!你們看!」其中一個靑年發現了洋船的踪跡,他高興地叫。
大家的目光跟着這靑年的指示去看,在悠悠的綠水中,忽然滾滾揚波,這艘大洋船「海神號」冉冉而來,原來這艘「海神號」是剛從美國囘來的。不久,它泊岸了,船上的乘客們接踵而出,在碼頭迎接的人,瞧見了自己的人,紛紛握手,表露出很愉快的情緒。
最後,乘客們差不多通通登岸完畢,迎接的人們,也漸漸地星散,祇剩下一個妙齡女郞,和她的父親一個五十來歳的男子,遠站在碼頭上等候着。
「爸爸,還不見他們呢?我們走吧!」
「等一會兒,别心急!」
不到半响,果然在船上出現了一個靑年男子,個子英俊不凡,穿一套最時髦的筆挺西服,他還拖着一個老人的臂膀,這老人也是五十來歳的人,慢慢地從船上下來。
「表伯!表伯!我們在這裡。」女郞如獲異寶地說:「爸爸,你看!」
原來這靑年姓盛名世安,他的爸爸盛柏年,在十幾年前去了美國。在這十幾年的過程裡,辛勤所得,現在算是鳥倦知返了。他父子兩人幷沒有什麽親友,有的就是目前在碼頭迎接他們的兩父女,那位女郞姓江叫做綺薇,她的父親江樹仁,就是盛柏年的表弟,所以江綺薇和盛世安也是表兄妹的名份。
「啊!樹仁,不見久了,為什麽綺薇也認識我?」
「表伯,我持着你寄來的相片來認人的。」綺薇搶着說。
「世安,這是你的表妹,隔別了十幾年,你們一定不認識了。」
世安和綺薇交換了一個眼光,然後熱烈握手為見面禮。
「表兄,你一定很疲勞了,囘去歇息吧!你的行李哩?樹仁說。
「己交給旅行社,囘頭會替我弄好的。」柏年答。
他們一行四衆,很欣悅地同到江家,這裡可說是一所華麗的大廈。江樹人是華都的商人,雖然是客居性,可是差不多算是在這裡「落籍」了。
江樹仁以主人家的身份,把盛柏年父子介紹給傭婦們相識,並且下令把東廂房打掃淸潔,用來招呼他們。兩個老人家互談往事,不勝感槪,江樹仁早在盛柏年出國後的第二年由鄕來華都經營了。
「樹仁,你不是還有一個女兒比綺薇幼一年的嗎?現在那裡?」
「哦!當我還沒有來華都前一年,郷中大亂,幼女已經失散了。」
「十年人事幾翻新,這是不錯的,記得我出國時世安才五歳,現在囘國後,他已經二十一歳了,在這十幾年裡,在外雖有些小成就,但不能永遠客居異地的,所以還是囘國。在這裡有什麽生意可做呢?現在我把你當做指引了。」
「出入口買賣是最好不過,我也是做這一類的生意」。
「我祇顧談,忘記了,表嫂在那裡?」
「她?早就去世了,我决定不再娶,所以買了一個兒子來撫養,那麽將來江家也有個承繼人呢!今年十九歳了,比綺薇幼一年。」
「他呢!我也未見,叫做什麽名字」。
「叫做浪生,他在學校寄宿的,我己着人到學校叫他囘來了」。
正在詳談的當兒,忽然一個靑年剛從外來,是個典型都市少爺的樣子,却原來就是江樹仁的兒子——江浪生。
「表伯,這所華麗的房子,我們接到你囘國的消息才遷來的,因爲從前住的地方,那麽………」樹仁在扯兒子的衣角,意思是叫他不要說,但浪生好像不知覺似的,繼續說:
「那麽狹窄,祇有兩個房間,一定招呼不起表伯,所以特地遷來這裡。還有。這些傢具的佈置,也是我設計的,爸爸,傢私店來收………」樹仁用力把一扯,這時候,浪生才醒覺便不再說了。
本來這所房子是租囘來,所有的傢具也是租賃,所以樹仁不讓浪生說出來,免在表兄面前出醜。幷誇張地說,這房子以四十八萬的價値購囘來,江樹仁是個老華都,所以早就習染了那種虛榮和愛撑塲面的陋習,但敦厚的盛柏年父子,那裡知道其中內幕,以爲這是表弟對他的厚待。
第二天,江樹仁又勸盛柏年做出入口生意,並談及買房子的事。
「我的意見,還是買一間現成的,最好能在三蛇洞附近。」盛柏年說。
「好,三蛇洞是富人住宅區,這地方最好。」
「你的房子我也很合意,照這款式買間也好,你買的時候多少錢?」
「我這間嗎?唔……幾十萬哩!」江樹仁支吾地說:「那點我替你留意留意,各方面的人仕我也熟識,要是我替你買總不會吃虧的。」
「好吧!」
X X X X
在三蛇洞三蛇道三號的那間洋房,門前掛着一個小牌,上書「盛苑」兩個字,從此,便是盛柏年的新居了。新居遷入的那天,三蛇道特別熱鬧,車水馬龍,本來柏年剛從外國囘來,戚友不多,爲什麽遷入那天,會有這多的賀客。原來江樹仁以冒牌屋主的身份,發出請帖去請客,他是老華都,朋友自然多,幷且,華都的人是「附旺不附衰」的,聽說江樹仁請吃喜酒,馬上趕來,所以在賀客中大半數是他的朋友。
熱熱鬧鬧的高興了一整天,新居典禮過去,自然變成了舊居,在這個過程中,世安和綺薇的情感與日俱增。
新居遷入的這天晚上江樹仁和浪生綺薇,也在這裏留宿,在談話中,江樹仁轉入正題說:「表兄,今晚我介紹你相識的汪先生,他就是民盛洋行的總經理,因爲近來棉花疏滯,假如有資本便大量購入,囤積起來,將來等待到市面最喝市的時候便抛出。其次,同時在可能内,收買那些舊爛棉胎,經過漂洗工作,自然雪白如新,這種工作我是很熟悉的,假使採用後者辦法,獲利更大,這種經營,我想讓給你幹,大概資本需要二百萬元,便可以和汪先生合股組織一間貿易行。」
盛武年囘國後,不能坐食的。他本想要做些生意,現在聽江樹仁說有這樣好的經營,不能不為所心動,他並且希望能夠獨資去幹,他着江樹仁先擬一份計劃,大家來商量商量。「樹仁,你不參加股本,那麽將來你瞧着我贃錢嗎?你也應該有點利益才好。」「啊!大家是親戚,談這些幹嗎?」「不!有義務,有權利,我分三成紅股給你。」「表伯,那麽我不讀書了,假如這貿易行成立,我就在這裡當副經理,好嗎?我可勝任的。」浪生突如其來地說。「你懂得什麽?」樹仁斥責說,「爸爸,你還沒有知道你的兒子那種本領,表伯,你說是嗎?」浪生跨耀着說。「是的,將來你畢業後,我把總經理的職位給你。」栢年說:「眞的嗎?那麽我便一心一意的等候你了。」
「好!你們三人先去睡覺吧!」柏年把他們命令進去,然後再說:「表弟!世安和綺薇的婚事,你以爲怎樣?」「我以爲等待貿易行籌備成熟,便舉行訂婚,邀請社會名流來,大家聯絡聯絡感情,使大家認識你,然後開辦貿易行,這樣旳步驟,你以爲對嗎?」「好極了,你是老華都,比我明白許多,我有了你指引,安心得多。」「那裏話,我也想表兄提拔我,現在時間不早了,早點睡覺吧!」「也好,晚安!」
X X X X
時光荏苒,世安和綺薇的愛情日進,在兩老的慫恿之下,他倆已經由訂婚而結婚了。婚前的張羅,固忙了這兩老子,結婚那天,更盡鋪張華麗,華僑之子——盛世安結婚,轟動了整個華都。
從此,世安和綺薇同走向戀愛的墳墓——結婚,大家是有家室的人,世安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囘來,深得妻子施與的温暖,也感到家的幸福,更領略到婚前爸爸那番話的眞意。
時光不留人的過去,快到除夕了,世安和綺薇出去趁趁花市,購備年宵品,在擠擁的花市中,遇見了江浪生和一個少女把臂同行,浪生是個不畏羞的人,他替世安和綺薇介紹這少女——游漫萍。
游漫萍和江綺薇在世安一看之下,果然很相像,為什麽這般巧。「好!浪生,我們到那邊去,不阻碍了你。」浪生和漫萍,世安和綺薇也就各各分道而去了。
農曆元旦,中國人互相拜年的習俗,江樹仁和盛柏年兩親家也不可免。元旦期內,各商店是休業的,盛柏年開設旳茂盛貿易商行也不能例外,想不到在這三天裏,弄出了許多不如意的事來。
江樹仁早就暗中掌管了大權,現在乘這三天假期中,盛世安沒有出來料理,他便勾通外界人做出對不起良心的事來。
假期已滿,世安再出商行辦事,他雖是年靑人,但有老成練達之風,在他細心審査之下,發覺數目不符,他立刻向江樹仁詢問,但江樹仁却說。
「這是經營生意必然現象,當然是利用這筆款塡那筆款,那筆款又塡這筆款,不會不對的。」
世安暗想,也許這是生意上普通的現象吧!他决不會懷疑岳父——江樹仁作弊,也不敢對父親洩露這事,祇是在心裏思索着。
那天,星期六中午下班的時候,世安無意中走過甬道,正欲往毛厠,恰巧路經總經理室的窗戶,突然聽到江仁樹和別人在談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站立着偷聽,隱隱可以聽到裏面的談話。
「現在這批貨我以爲是可以獲利的,所以拿了公家的錢作爲我的私人買賣,將來賺了錢,我把本錢還給了商行,」不是一樣嗎?要是不幸虧本了,便作爲是商行的買賣,這是最上算的,所以這批貨的單據,不要入商行的賬。」「好啦!」這個朋友說。「以後你來的時候,先給一個電話給我,另外約一塊地方見面,因為我不想給我的女婿知道。」「那麽星期一約在什麽地方?」「也在那老地方吧!」世安聽到這裡,那朋友要告辭,世安急得從後門走去。
囘家帶着沒精打彩的神色,表叔為什麽會這樣做,也許他已經早已準備的了,難怪發覺了賬目不符。吃晚飯的時候,世安還是一樣的呆着了臉,因為他還未做到喜怒不形於色,柏年以為兒子有病,向他詢問,撫摸一下他的額,幷沒有病容。
世安不想把這件事給綺薇知道,因為江樹仁是她的父親,知道了總是有許多不便的,同時他不想為了這事破壞了夫婦間的感情,所以寧在妻子面前不坦白。晚上,世安等待綺薇睡着了,他才起來,放輕了步,把房開了,跑到柏年的房間裡。「什麽事?還不睡覺。」「爸爸,我有件事,要告訴你的,但我不想被綺薇知道。」「什麽事?」
世安便把賬目糊塗和偷聽了江樹仁的詭計,通通盡說了出來。「世安,你要知道,表叔是你的岳父,决不會這樣做,或者他暫借商行的錢,將來一定歸還的,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做事也不要太認眞,知道嗎?」柏年是個忠厚長者,他以為所有的人也像他一樣的。「爸爸,我知道。」「沒有什麽事便去睡吧!」第二天是禮拜天,世安習慣了要郊外遊玩,但綺薇說是精神不好,需要休息,不能同去了。世安看見妻子不去,他也想把遊玩的念頭打消,但綺薇說:「你和老爺去吧!不要為我。」柏年父子兩個人出去了,綺薇沒有半點不舒服,趕快起來,整裝,塗脂抹粉,囘娘家去。
江樹仁恰巧在看報,綺薇把他拉到房間裏一去才說爸爸,為什麽你幹出這些事來?」「什麽事?」」你拿了商行的錢去經營私人生意,瞣了錢算是你的,虧本了便算是商行的,爲什麽要這樣做,被世安知道了。」「他知道?那麽你怎會知道。」「昨晚他在我睡着了,跑去和老爺說話,但我原來也是裝睡的,所以跟着他一路去,他沒有發覺,他們的話,我通通聽到了。」「他說什麽?表伯有懷疑我嗎?」「老爺沒有懷疑你,他還叫世安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爸爸,你要是用錢,還是坦白的對世安說,大家已經是親戚了,還客氣嗎?」「你相信我會這樣做嗎?。」樹仁還抵賴,他說:「我問你,爸爸親還是丈夫親?」「大家也親?」「好!俗語說:「好女兩頭瞞」,以後他們有什麽話是關於我的,你應該替我說好話,還馬上囘來告訴才是,知道嗎?」「好吧!」從此,在他們之間,多生事端了。
因為盛柏年是個忠厚長者,雖然他的兒子盛世安把岳丈假公濟私的事對他說過,但也不會懷着鬼胎,可是貪樊的江樹仁,因此却變本加厲起來了。
大概因爲次數太多了,盛世安在忍無可忍之下,有一天,他在有意與無意間,把數目翻閱起來,見有很多餘款存放在銀行裡,他心在想;「旣有這大筆款項,何故表叔不把它拿去買賣?任它凍結在銀行。」這一點,對於商塲上經營之道,是最不合算的,可是他囘心一想:「難道這個敷字是虛浮的不成?」他立刻撥電話到銀行詢問,才知道存款與數目不符,爲了要知道其中內容,便拿着數部去見江樹仁問個明白,可是狡猾旳江樹仁,不慌不忙的說:「世安,你太不尊重我了,在私,我是你的岳父,也是你的表叔。在公,我是總經埋,你在公司裡,是沒有名義的,不過是跟着我做一個見習員,雖然你爸爸是老板,假如他信不過我,不會把業務通通交給我處理,正因爲他對我相信,尊重,也不理會我,反而你竟干涉我的商政措施嗎?」
世安聽他這番話,大不舒服,還謙恭地說:「這不是不尊重你老人家,但我知道數目與存款不符,所以我便要求向你請敎請敎,正因爲我剛才撥電話詢問銀行呢!」
江樹仁一聽,便大發牢騷地說:「你得不到我的同意,竟敢詢問銀行,是你的大大不對。不過,我也明白,你是很聰明的,但你這次是聰明笨了,我現在敎你,假如你要査數,要技巧一點,運用別種方法才好。比方説:前數月那天星期六卜干,你所幹的事,偷聽我和朋友談話之後,你又在爸爸跟前播弄是非,這就是你太不技巧,所以你爸爸也不相信你的說話,你以爲我不知道嗎?笑話,我什麽也知的,不過我是大量的人,便不爲已甚吧。我現在雖然暫借公款去經營我的私人事業,可是我絕對不會對公司不起的。反正,這是公司裡的餘款,難道我受了公司百份三十紅股,便把私務不理嗎?老實說,假如你看不過眼,可以叫你爸爸取囘我的經理大權。」
世安因他是自己岳丈,表叔,祇好啞然而退
在下辦公的歸途中,心裏暗想:前次的事,我半夜和爸爸談話的時候,再沒有第三者在內,難道自己的妻子綺薇偷聽了之後,又去對她父親說知不成?他愈想愈有可能,於是决定向妻子偵察。
晚飯的時候,世安作悶悶不樂之狀,像前次表情一樣,綺薇問他是否生病,他也祇答一句「不是」,飯後也不外出,沐浴後,便到房裏去睡覺,綺薇眼看丈夫的情緒,知道他一定又像前次想向他爸爸談話前的徵象了。便詐作熟睡,等候丈夫到家翁房間去。
盛世安也明知妻子詐睡的,也不作聲,半响,他偷偷地跑到父親的房間去,進了房後,把房門虛掩,餘下一條小縫,慢條斯理地坐下來,故意坐近房門,便一一地把今天的情形對爸爸報告,說完了,冷不提防地順手把房門一拉,爸爸也不知他弄什麽玄虛,原來門外正立着一個人,正想囘身跑走,說時遲,那時快,世安把那人拉囘來,在燈光下一看,原來正是世安的妻子江綺薇,蓬鬆的頭髪,靑白的臉孔,戰競不敢內進,像待罪之囚一般的竚立門前,本來世安十分盛怒了,但,畢竟是自己的妻子,見她慌張的態度,心有不忍,便倒了一杯熱茶給她,温柔地扶她進來,使他坐下,過了片刻,他的張徨神色漸漸消失了,才對她說:
「綺薇,你是我的妻子,我的事如你的事,我首先向你道歉,前次我瞞着你,半夜裡和爸爸談話,但你該原諒我,何以我要瞞騙你?正因為這是關乎你爸爸的事,假如你知道了,偶然對他說知,便會影响親戚間的情感,所以我便不想給你知道,但你不明白我,以爲我有什麽私心,便在門外偷聽,更在你爸爸前說知,這樣幹你以爲對嗎?幷不,在我們親戚間發生裂痕,所受的惡果是誰?不在話都是你個人,因爲你是他的女兒,又是我的妻子,岳婿間不和,對你是絕無益處的,幷且,你更應明白,你爸爸這樣幹,是對不起公司的,而我們尙不責備他,完全為了尊重他老人家,我很希望你今後不要再把我們的事宣露給你爸爸。」世安和柏年也不爲己甚,便把這件事情淡然過去了。
X X X X
過了若干時期,世安暗中遍査賬目,比從前淸楚了,樹仁動用了的公款,也塡囘來了。有一天,樹仁和世安談話,幷說要辭退總經理的職位,幷把商行內的五十六萬九千二百七十四塊錢的存款賬目移交給世安。
世安經他突然的辭職,也感到奇怪,幾經世安挽留,樹仁仍然堅持已意。馬上撥電話囘去稟知柏年,柏年急命世安速歸家,囘到家裡,柏年當然不願意樹仁辭職,不免向世安敎訓一番,又命綺薇撥電話邀請樹仁來喫晚飯,但適樹仁外出未歸,綺薇祇好把說話留下。
將到晚飯的時候,樹仁眞的來了。「表弟,你來得巧了。」「我也是專誠來的,因爲我辭退商行的職位,特地來向你說聲!」「表弟,你賞面給我,也要替我再幹下去,世安少不更事,怎能負起這大的責任?」柏年說:「世安,你快向表叔道歉。」「爸爸!世安是你的女婿,你原諒他吧!」綺薇說。
「表叔,從前的事眞對不起,請你原諒我!」世安說。「不!一切是我不對,我祇會動用公款,你正當的査數和質問我,是很應該的。我辭職了,你一定担當得起,我想,一定是「靑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嗎?表兄,你不必操心的,還有我的百份三十的紅股,你給我也算,不給我也算吧!」「我言出必行的。」栢年說:
這次樹仁的來,是帶點意氣的,說完了正話,飯也不吃便走了。
「世安,萬事要忍耐才好,現在弄成這樣子!」「忍耐總有限度的,表叔不幹,難道商行眞的要倒閉不成!」世安說話時很有把握。
自從江樹仁辭職後,本來盛世安可以担當總經理的職務的,可是他的父親——盛柏年恐怕他少不更事,便要親自料理,可是麻煩又來了。
江樹仁退職後的第二個月,洗棉工塲裡發生了絕大的變化,因爲工場裡的主要命脉——配藥師與洗棉師相繼辭職,雖經多次挽留,甚或加倍支薪,也一樣無濟於事,因此,那兩要缺便繼後無人了,迫得不已便把工塲關閉。
這天的下午,盛柏年正在公司裡料理業務,聽差進來報道:「有客求見」原來正是多時不見的表弟——江樹仁,他臉上表現着一片虛僞的笑容,彬彬有禮的和他握手,本來盛柏年一見了他便老大不高興了,但人家旣然謙恭求見,幷且他們之間幷沒有發生過正面衝突,便虛與委蛇。
江樹仁表明來意,並叙述這次來見的原因有三,「第一,特地來道歉,因爲他本來不願辭職的,因爲經過兩次被世安太不尊重,不能不這樣做,以表明自己並非存心虧空公款,明知對表兄不住,也要這樣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第二,也要請原諒的,自從自己辭職後,洗棉工塲的兩個主要人員相繼辭職,原因是爲了他兩人是自己的左右手一般,也是自己的學徒,我在茂盛公司辭職後,爲了生活,一定要另謀生計,所以便和朋友合股經營同樣業務,便不能不要他倆帮忙自己。第三,我今日特來拜訪,完全希望將功贖罪,更希望我們之間的感情恢復,因近日各行商業不景當中,有一種生意是一技獨秀的,便是棉紗,現在市價日高一日,以我眼光看來,在一個月以後,定會漲至兩倍三倍之多,假如存這種貨的話,一定獲利不菲。現在外來貨日少一日,祇有少數商戶放出,所以我們不妨大量吸收,在多方的搜購下,得悉目前有一大戶,急需現款,願將其本人存貯大量棉紗拋售,這人的名字我暫不宣佈,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本地的殷商,不願給人知道他有棉紗脫售的消息。所以着我給他走盤,照目前市價賣給我,我明知這帮貨會賺錢的,所以我已盡了最大能力大量吸進,但存貨仍然甚豐,且又不願公開求售,我爲了這朋友設想與肥水不流別人田的原則下,請你大量吸進,不到一月光景,當可溢利數倍。那時,世安知道是我替你幹的,定會把前嫌冰釋,不會把我當作壞人看待了,那時我們豈不是可以再度合作嗎?」
盛柏年聽後,還打不定主意,訂明三天內答覆他,歸家作愼重的攷慮,先寫一封信給兒子盛世安,他自己感覺世安的見解常常會勝一籌的,更攷慮這次買賣不知是眞是幻,他打定主意,明天請樹仁帶自己去看看他的存貨和買貨的單據,如果屬實,自己也不妨買入,希望在一個月後,可獲大利哩!
翌日,他約樹仁相見,叫他引看他自已的存貨和貨單,江樹仁聽了,立卽跑去自己的公司裡去和汪某商議,準備以僞亂眞的計劃來把盛柏年欺騙。
江樹仁幷沒有買入棉紗,爲了盛老要看他的存貨,他便和另一家公司商量,借別人的存貨和僞造貨單給柏年看,果然把盛柏年騙過了。柏年爲了要履行諾言,在三天內答覆江樹仁,現在已是第二天的下午,他企盼兒子盛世安的囘信,希望得到一點投資棉紗的意見,可是待至信來了,却沒有提到棉紗的事,祇報平安而已,也許世安尙未收到他的信罷。
爲了集思廣益起見,他老人家便和公司裡的心腹職員商議,一致公認「寧買當頭起,莫買當頭跌」,於是盛柏年决定把棉紗買入。交易之日,江樹仁對盛柏年說:「現在是上午,但你不必現在交款給我,該貨等待下午入倉後,你才給我便是,幷且先訂明條件,須把全部貨物盡量購入,約計洋紗一萬五千條至二萬條左右,但你可先交五千條的貨値。餘俟貨物全部收訖,才淸找貨款。
盛柏年認爲最便宜的事,就是這筆交易了,就在這天的下午,江樹仁把五千條洋紗搬遷入茂盛公司的貨倉後,便和盛柏年一起去看貨,經過一番視察後,算是交易妥當了。但江樹仁沒有萬多條洋紗,他便决定以土紗夾雜作一起,實行以僞亂眞,這樣一來,他的腰包也漸漸漲大起來。
三天之期旣至,共計一萬五千多條棉紗,運進茂盛公司貨倉,因事先訂明貨款兩訖的,不能稍有半點稽延。但盛柏年因現款不足,便由江樹仁代他設計,叫他把現居的房子按給銀行去,幷且把茂盛公司所存下來的其他貨物盡量放出,於是便把這批洋紗交易了。
這天的下午,盛世安的信由綠衣使者交到栢年手上,信內說:「洋紗市道當盛,可買入,但表叔的來路,我以爲愼予考慮爲佳………」盛柏年看後祇一笑置之,他還以爲這是自己的兒子和江樹仁心病未消罷。
又過了兩星期,盛世安和妻子江綺薇囘來了,才知道父親和表叔買入萬多條洋紗,價錢太便宜了。他心裡有點懷疑。盛世安很懷疑這批棉紗其中或會夾雜土紗,於是在翌晨邀請父親一道去貨倉看貨,經細心審視後,也認爲無甚可疑,因爲江樹仁早已鈎通看倉的人,把眞貨堆在上面和前排的當眼地方,所有僞貨都放貯在內裡,所以世安偵査不到破錠來。
那時候的盛栢年,還敎訓兒子一番,叫他不要以小人之心來度君子之腹,他還認爲這批貨,再過一月後,大可獲利數倍。世安問起他那有這麽大的現款?才知道父親已把房子按給銀行,他主張現在立刻把洋紗大量放出,得囘巨款,經營別項買賣,更恐怕洋紗市道盛極必衰,到紗價一下暴跌時,便損失不貲了,但盛老認爲自己的眼光遠大,不以兒子說話見信,所以决定等待一月後,希望貨價起至兩三倍,那時,豈不勝於浮沉海外半生經營嗎!
X X X X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棉紗的市價,由高漲而至牛皮價,但盛柏年還主張等候再度漲價的時候才放出。
等了一天又一天,在這個月底,突然市道急轉直下,紗價大跌,盛柏年父子兩人立卽商量,趁在還可獲薄利的時候,應該急把棉紗放出。
找到了顧主,帶到貨倉看貨,這時候,在顧主審査之下,才發覺大部份的棉紗是雜夾着土紗的。這樣,誰願意買?盛世安决定要去找江樹仁,縱使是親家變寃家也算了。立卽囘公館去,撥電話到必成行找不着他,再撥電話到江樹仁家裏也不在家,世安决定和盛柏年到他家裏附近,站在暗處窺伺他的進去。
盛柏年在這時候已經氣憤到極,頹喪的站在牆角,等了兩小時,果然瞧見江樹仁在外返,世安上前呌他一聲:「表叔。」
江樹仁看見的是盛柏年兩父子,怔了一陣,但他還極力地鎭定自己,請他們入內,傭婦還沒有看淸楚後面還跟世安和柏年,她說:「老爺,剛才親家老爺剛來過,我遵你的吩咐告訴他,你不在家………」
「我們已經來了!」世安打斷了她的話,從傭婦的話中,世安淸楚江樹仁的詭計。「你們先出去,沒有叫喚,不可進來,」世安把傭婦們打發出去。「樹仁,你也對得起我了,前月介紹我大量購入這大批棉砂,說是價錢便宜,可是完全是夾雜土紗的,你這樣做,有良心沒有?」柏年氣憤憤地說。
「表兄,這些要怪我嗎?笑話,你已經驗看過了,現在距離一個多月才來和我說?也許是你們的管理不當,看倉人作弊也未可料。」樹仁還作强辯。「表叔,憑你的良心說,你是不是故意這樣做,不然,爲什麽我到處找你也不見我?」「笑話,你是我的女婿,難道我要等候你,我應酬大,常常在家裏的嗎?關於這些貨你們太大意了,還在來怪責我!」「樹仁,你不要抵賴,我提拔你,但反為得到的是這樣惡果,哼!」「什麽?什麽?你提拔我?你沒有我,你能在華都經營生意,結識上流人物。表兄,我忠告你,趕快把這批紗放出,得囘多少錢也好,不然,你的生意要崩潰了,現在我不大舒服,遵醫生吩咐我需要休息!」江樹仁說完了走進房間裏去,眼也不瞧一瞧。盛柏年氣壞了,終於在怒極之餘,暈倒了,世安和傭婦帮着急救,好一會,才把柏年救醒,但忍心的江樹仁還沒有理會他。
柏年經過這次的打擊,病倒了,柏年主張把棉紗快放出,但當時市面已有洋紗大量入口,充積市塲,在供過於求的情形下,棉紗價大跌,土紗更甚,世安眼看着這批棉紗的價値一天比一天低,立卽遵照父親的話,把它賣出□但交易的那天,在點數之下,發覺短欠棉紗二千多條,眞糟糕了,終而祇得囘是百份一十的本錢,本擬利用這筆錢去銀行把房子贖囘,但已和理想距離太遠了。房子按期是三個月,逾期便要損失,世安眼看着父親在病,那敢把這眞實情形詳告,沒精打彩的囘房間裡去,這也盡向綺薇吐露,幷强調說,今後因此便宣告破產了,這都是江樹仁一人做成的。
X X X X
第二天,僕人們星散,從前是婢僕如雲的,現在靜寂寂的,傢私也賣掉了,得不到多少錢,但也沒有辦法哩。經過了幾天旳光景,新房子找着了,僱了伕力把餘剩的殘舊的傢私搬去,自用車也沒有了,世安僱了一輛街車送柏年到新居去。當柏年瀕去之時,他用貪婪的眼光凝視着舊居,這就是用血汗□取囘來的東西,從此後已屬他人了!他不覺老懷悲痛起來「世安,這房子賣了多少錢?我按給銀行也按到十二萬塊,現在算應該有十五萬才對呀!」「爸爸,賣了十八萬塊哩!」「好了,把公司的舊債淸還了,還剩下來有幾萬塊錢,足夠經營小生意,以後要努力才是」「這房子,明天已更換業主了,唉!」「爸爸,街車在外面等候了,我們去吧!」「這房子姓什麽的人買了。」「姓………張的。」世安又把爸爸瞞過。柏年幾翻的囘頭凝視,才離開這裏。抵達了新居,和舊居相比,眞是天壤之別,這裡狹小得很,又使盛柏年撩起重重心事。
一天一天地過去,世安再不能隱瞞着父親了,在他追問等候,索性把眞實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訴他。「爸爸,你不要傷感,雖然我們連這所僅有的房子也沒有了,但我還有這雙手,我要創造一番事業,目前是艱苦一點,但我總能抵受,爸爸,你安心!」「那麽………這房子我們是沒有了嗎?唉!不過,你還有大志,我也很安心,」「老爺,這都是我爸爸不好,才有今天。」綺薇帶淚地說。「嫂嫂,你沒有錯過,祇是你爸爸沒有良心,別哭!」
可是,盛柏年果然是這樣的達觀嗎?他辛辛苦苦的流浪異域,十多年來才贃到這些血汗錢,現在一旦損失了,那有不傷感哩!但柏年把辛酸淚向肚子流,他也不想兒媳太傷心,實在,他現在已經悲愴到極點。世安在想,長此下去不是辦法,應該要找職業,不然,每天的兩頓飯也要發生恐慌了。
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世安天天在街上跑,爲了甚麽?是找尋職業,恰巧在第二天,救星到了,他偶然經過一間『發展俱樂部』,看見了招請工人的字條,他連忙跑上樓去,見了老板,老板瞧見世安進來,連忙從床上坐起來,問過了他的姓名和學歷,知道世安是個飽學的人,不但懂英文,還懂國語,在複雜的俱樂部中,最需要懂得幾種語言的人來招呼,於是世安便被錄用了。雖然薪金訂明每月五十塊錢,但還有小賬,毎月收入幾百塊錢也有的,每天工作時間,由上午七時至晚上十二時,但這裏是供膳的。所做的工作是打掃地方和招呼來客,這顯然是一個聽差,世安爲了解决生活,還顧慮這許多嗎?
翌晨,世安七點鐘便到發展俱樂部裏,但靜寂得很。老板還沒有起牀,祇有一個聽差阿勝在打掃地方,世安向他說明來意,阿勝知道多來一個助手,十分歡喜,把工作大家劃分來幹,在合力之下,很容易弄到好了,漸漸地,人客來了,阿勝指點世安招呼,這時候毛小姐也來,雖然她是徐娘半老,但打扮得很時髦,阿勝恰巧下樓去買東西,世安是不認識她的,看她直向老板的房間裏去,忙上前向她詢問,但毛小姐看見這個英俊不凡的靑年,投以奇異的眼光,她反問世安是什麽人,世安把身份說明。「你剛來的嗎?你今年有多大?」奇怪!爲什麽她這樣問我?說大一點好啦,世安便說:「我………二十八歳。」「沒有吧!」「毛小姐,老板囑咐請你進去坐坐,但鎖匙在阿勝手裏。」世安正說到這裡,阿勝恰巧囘來,世安連忙叫阿勝開門給她入去,他自己乘機溜到別號去,因爲他感到毛小姐有點奇怪。
一會兒,阿勝吿訴世安,毛小姐請他入去,世安不能不去,當他進去房間的時候,毛小姐不以聽差來看待他,瞧見他呆立着,連忙把他推在椅子上坐下。毛小姐態度超乎良家婦女的所爲,她隨手在烟具上取出了一枝香烟,放在咀角,用眼光掃射着世安,意思是叫他點火,但世安是幹不慣的,那裡知道她的意思,世安見她望着自己,忙說:「毛小姐,我出去好嗎?」「不!替我點火。」盛世安暗忌,旣然是做聽差,老板旳朋友叫點火,豈怠慢?連忙燃着了燐火,但繼績燃着了一枝兩枝,被毛小姐吹熄了。不知她弄什麽把戲?世安在想,好!四枝燐火一同燃着,看她還吹熄不?毛小姐燃着了香烟,還綯綯不休的問世安的年齡及姓名,又問他的學歷,世安想,對這些人是不能不說謊,告訴她是目不識丁,但毛小姐看他一表人材,那裡相信。
世安被她瞎纏,正想找脫身之計,幸而阿勝匆匆忙忙進來說:「阿安,現在外面忙得很,快來!快來!」「對不起,毛小姐我要出去工作。」世安乘機溜了出去。
今天晚上,毛小姐沒有例外旳不停地呼喚世安,幹這個,幹那個。突然,老板又呼喚他招呼他的朋友。這位朋友正在玩撲克,兩個手指夾着雪茄烟,老板示意世安給他燃火。「先生,抽烟!」世安燃着了火在說,豈料那人轉過臉來,和世安四顆眼睛的視線交接,在世安眼睛裡看見這個人,唇上長着兩攝稀疏的鬍子,年紀在五十歳以上,穿着筆挺的西服,世安暗叫不好,原來是樹仁,寃家相遇,還要侍奉他?世安掉頭不顧地說:「江先生,請隨便休息!」「世安,我看見了你現在幹這工作,我很不忍心。」「江先生,你也說這些話嗎?」「爲甚麽叫我做江先生?我愛我的女兒而及於你,你不要再在這裏工作了,囘去我那必成行吧!」「江先生,現在不比從前,我是聽差,你是必成洋行經理,我不想影响了你的名譽,所以應以江先生稱呼。」「江先生,原來你也有良心的嗎?我寧願餓死也不在你間洋行工作,你的錢從甚麽地方來?
世安的話,總是句句不離江先生,弄到江樹仁啼笑皆非。「你總是不尊重我,致有今天,我的女兒怎樣?」「你要我尊重,你先尊重我,再說到你的女兒,卽是我的妻子,她嗎?還好,沒有挨過餓!」「哼!」江樹仁氣極了。
他對老板說:「阿安這個人雖然是有才學,但太自負,才有今天,說起來,他的爸爸是我相識的,你知道是誰?」「是誰?」
「就是那個歸國華僑盛柏年哩!阿安是他的兒子,他擁有巨資囘國,但兒子經營不力,把所有錢付諸東流了,直到現在,阿安還是這般驕傲,好像看不起你的客人,僱請了他,恐怕有碍了你的生意。」江樹仁在大庭廣衆中把世安的世身揭露,幷且更向老板的挑撥。
世安再不能忍耐了,高聲地說:「江樹仁,你別在老板面前挑撥,我窮得硬漢,我可以不幹,你說得我,我也說你,沒有錯,我是你的女婿,我的爸爸盛栢年是你的表兄,但你利用詭計,呑沒了我爸爸的產業,你便優悠自在的貴爲經理,你的錢從那裏來?沒良心的東西!」世安愈說愈氣。「老板,我不幹了。」說畢,匆匆的跑出門去。
世安囘到家裏,妻子向他問長問短,他大發牢騷,把父親驚醒了,他在憤怒的時候,索性把今晚的事詳細告訴給他,盛柏年聽了氣得眼睛向上翻。
正因為是綺薇的父親做成今天的艱苦,在最窮困的時候,世安對於綺薇總有不悅的心理,但綺薇華都長大的,從來過慣着奢華的生活,現在辛辛苦苦地挨着,還要看他的臉?
在這兩人的心理下,大家便有了一度鴻溝,尤其是世安,因爲生活的打擊,脾氣愈來愈壞。
在沒辦法中,綺薇說要娘家去,向爸爸借錢,世安是個剛强的人,到底不贊同妻子的要求。
「我告訴你,別囘去!現在我出去想辦法,你好好地侍奉爸爸不要離開他!」世安命令似的說。
然而,她終於借故囘娘家去,向江樹仁借了一百塊錢買了柴,米,油,菜囘家,又恰巧被世安囘家看見了,追問他錢從那裏來?
綺薇想要說謊,但被世安厲言疾聲地說:「你是做壞得到的嗎?」
「不………我向爸爸借的。」綺薇迫得說實話。
世安一氣,又叫她把所有東西送囘給江樹仁。
「世安,算了吧,吵甚麽,下次她再不這樣的。」柏年說。
「下次我不再向爸爸借錢好了」
世安看在父親的面子,又饒恕她一次。
盛世安的心裏總是很不愉快,便在吃飯的時候,想到這是岳父的臭錢,認爲是奇恥大辱,他最後忠告妻子,最困難的時候,也不能再向江樹仁借一毛錢。
借來的一百塊錢,除了解决每天的兩頓飯外,還要醫理父親的病,漸漸地又苦不堪言。
世安每天也躑躅街頭,想要碰碰運氣,但不過是失望吧了。
X X X
一夜,火油燈的火油用乾了,燈火熄滅,世安囑咐綺薇擦亮了燐火看看爸爸怎麽樣,豈料綺薇看見他的形狀是翻了白眼,呼吸緊促,胸部起伏不定,綺薇高呼世安,世安也起上前,急搖柏年的背膊呼叫:「爸爸…………」
盛柏年這時候已不能說話,祇是手搖搖。
綺薇要獨自去請醫生,但她是轉向娘家的路走,因爲萬事非錢不行。
沒有雨傘,更沒有雨衣,綺薇一路冒雨前去,抵達的時候,宛似水人一般。
樹仁在家裏,綺薇把來意說明,幷要求爸爸走一躺。
「我不想去,因爲世安是個壞脾氣的人,難道我要送去給他怒駡不成?」樹仁說。
「爸爸,你看在我面上去救救老爺,難道見死不救嗎?爸爸,去吧!去吧。綺薇像梨花帶雨般跪在樹仁跟前說。」到底是父女情深,樹仁心軟了,終於乘自用車同去。
「怎麽黑漆一片的,燈也不亮!」樹仁抵達了綺薇家說:
「是,火油也沒錢買了,你當心走路。」
世安聽到他們說話,猜想這是醫生,不知道就是他的岳父,還說:「綺薇,你帶他上來!」
當擦着了燐火,盛世安看淸楚這不是醫生,原來是江樹仁,不禁愕然,忙向綺薇詢問,但被樹仁搶着說:「世安,我特意來探望你的父親。綺薇,快去買些火油囘來!」樹仁在口袋裏掏出些鈔票給綺薇。
綺薇去後,樹仁撫摸著柏年的手,感覺冰凍凍的。
「表兄,你覺得怎樣?」
柏年已經不能說話了,祇是搖搖頭。
半响,綺薇買了火油囘來,火油燈才光亮了。
「表兄,你們和我鬧意見是鬧不過的,常常說我怎樣的欺騙你,但有甚麽証據?不過,從前的事,不要再說了,世安肯低頭到我公司當職員,這還可以養妻子,不然,令到我的女兒衣食無着,這完全是爲了我女兒着想。」
柏年聽了,憤恨到極,握着老拳用力搥在床上。
「爸爸,你別生氣。」世安趕忙倒了一杯茶給他喝了一口,他說:「表叔,你現在說甚麽話?我可以趕你走!」
「混賬!」
「爸爸,世安,大家別再鬧下去了,寃家宜解不宜結,爸爸,我現在去請醫生!」
「去吧!」江樹仁說:「表兄,你們現在還口口聲聲說我對不起你,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兒子沒用…」
「表叔,你不是呑併我們的財產嗎?還在抵賴!現在你來是問病還是取命!」
「你………樹…仁……忘……忘恩……負義。」柏年勉强支撑起來,很辛苦擠出這句話來。
「好吧!你的病,反正是看醫生也是不會好的,人總是要死,你也老了,不死待何時?趁我也在,送你去吧!」江樹仁的話,句句也是剌心的。
盛柏年聽了,一雙脚狠命地亂扎,表示極度憤恨的樣子,口裡祇說出一個「你」字外,連續的咳漱,接着喘氣不定,終於從急促而至緩慢,再由緩慢而呼吸停止了,突然雷聲一響,好像送着盛柏年魂歸天國去似的。
這時候恰巧綺薇帶了醫生囘來,但已經來遲了,樹仁打發他走。
「爸爸」………
「老爺」………
世安和綺薇的哭聲,呼聲不絕於耳,但江樹仁慢慢地說:「好了,他死了更好,不用挨苦,世安,你囘去我處工作吧!不然,你會餓死了。」
「世安,你聽爸爸的話!」綺薇苦苦的央求。
「不!表叔是我殺父之仇,爸爸完全是他迫死的,我低頭接受你的恩惠,便是沒廉恥的東西!」世安咬牙切齒地說。
雨愈下愈大,時間已經是十二點鐘了,江樹仁在口袋裏掏出一叠鈔票說:「窮是敵不過鈔票的,我作為施捨似的代你收葬你的父親,這些錢拿去吧!江樹仁把鈔票一擲,馬上下來,走出外去。
「錢!錢!這是孽錢,我不要!我不要!」世安發瘋似的拿着鈔票追出去,正想交囘給江樹仁,但是他乘着自用車恰巧走開了。
「安哥,幹嗎?」
世安跑囘來,矛盾的心情又展開了,他想,這些錢是江樹仁從爸爸手裏奪來的,爲甚麽不可要它。
「爸爸,我沒有用!我沒有能力收葬你,你在九泉有知應該原諒我!」
剎那間,世安又把意見轉移了,用力地把鈔票擲在地上,要綺薇馬上送囘給江樹仁。
「世安,你想淸楚,我們完全是沒有錢的,難道令老爺的屍骸暴露嗎?他死了也不暝目哩。
「人死如燈滅,有甚麽關係,快快送囘去。」
「安哥……………」
「不要說,去!去!」世安這時痛苦到極,雙手亂扯頭髪。他向綺薇說:「你一認為我沒出息的,你可以同去,別理我!想不到你是個都市小姐之流,祇會同甘,不知共苦!」
綺薇忍耐性總有一個限度,現在她不能再忍了,圓睜了眼睛,怒說:
「世安,我這樣做是爲了家庭,但你還時常駡我,好!我就囘爸爸家裏,你迴心轉意的時候便來找我」!綺薇說完了,氣憤憤出門去。
世安的個性是倔强的,眼巴巴看着她去,也不呌她囘來,這樣,局勢就弄僵了。
X X X
綺薇囘到父家,自然是向爸爸哭訴,江樹仁勸她趁在這時候和世安辦離婚手續。但綺薇是因一時氣憤才離開世安,到底和她還有感情存在□綺薇的意思是等待世安來道歉她便囘去了。
盛世安離別了妻子後,生活一樣是很潦倒,但心情比從前更煩悶,每天早出晚歸,進食無定,有時竟整日餓着肚子,他希望妻子終有天會自動囘來的。
相反的,綺薇在父家中的生活,過得很舒適,很寫意,雖然,她也希望世安終有一天找她,她的心常是這樣想,但敵不過江樹仁終日勸她早日和世安離婚的說話,更被她的弟弟江浪生常常邀去跳舞,看戲,在這環境下,江綺薇已不復記憶着世安了。
天天的生活也沈醉在繁華中,綺薇的都市小姐氣漸漸地復甦。
那天,是一個平凡的下午,他們正在吃晚飯,從門外傳來汽車响笛聲,江浪生辨別出這是他的朋友——曹槐靑來探訪他了,連忙喝令女傭開門,進來的是一個不過廿來歳的靑年,但他唇上故意長着一撮稀疏小鬍子,身穿筆挺的西服,手持士的,裝着紳士風度,神態十足的樣子,浪生替他們介紹,曹槐靑此來,當然是約浪生去遊玩,浪生也一併邀請綺薇同去。
飯後,浪生和綺薇同進房間去,也許是更衣吧。客廳上祗有江樹仁和曹槐靑談着,曹槐靑是個輕佻的靑年,都市少爺氣很重,在他和江樹仁談話中,他便極力誇張他的父親是在美洲經商,家中怎樣的富有,這些話正合江樹仁的口胃,他是個拜金的人物,他認爲兒子有這朋友是很榮幸的。
「爸爸,姐姐不去。」浪生在房間出來說。
「爲甚麽不去?反正是坐在家裡沒事幹,去吧!綺薇。」江樹仁說。
曹槐靑當然也說:「江小姐,賞面一同去吧!」
綺薇在人情難却下,果然盛裝同去。綺薇本來是長得不錯的,加上了人工的修飾,漂亮極了,令到曹槐靑目不轉睛。
三人同乘汽車而去,浪生故意讓綺薇坐近槐靑身邊。整晚的節目,便是看電影,跳舞,曹槐靑像是個情塲聖手,對綺薇大獻殷勤,終於興盡而返。但當此時,也有一段挿曲:
「你是誰?」世安在岳父家門口被女傭喝問。
「我找江樹仁。」
「老爺不在家。」
「不在家也開門給我進來!」
「你是誰?我要關門!你走!你想偷東西嗎?」
「我是什麽人,你知道沒有?」
他們正吵嘴中被其他女傭聽到走出來,其中的阿娟認識這是姑少爺,立刻開門讓他進來。
世安見到了江樹仁,誤會爲了屈服他而來;但世安連忙解釋道:
「我是來找綺薇,她在那裏?」
「今天是什麽日子,他和弟弟及朋友們去玩耍了。」
「我看見了她和一個靑年走進南雀舞廳,浪生是沒有去。」
「那麽你比我更淸楚,倒來問我。你的妻子我替你養着不是好嗎?呌她囘去,你要餓死她不成?」
世安怒不可遏,他忍耐着等候綺薇囘來算賬。
江樹仁不屑理會世安,他獨自囘房休息,祇剩下世安坐着等候綺薇,等了不知若干時候,他坐在沙發上打瞌睡了,才聞到一種女人稔熟的聲音。
「請坐!」
「我還是送你囘去你的蘭閨吧!」
世安睜開了眼晴一看,原來這就是江綺薇,他立卽跑過一把拖着綺薇,喝問:「你到那裏去?」
「什………麽,是你?」
「是我,這是誰?」世安指着綺薇旁邊站着的靑年——曹槐靑說:
「小弟姓曹名槐靑。」曹槐靑裝模作樣地說:
「我不和你說,綺薇,你答覆我!」
江樹仁聞聲走出來了,他裝着很嚴肅的樣子說:
綺薇懷着恐懼的心情跟着他們走出客廳。
「表叔,綺薇囘娘家我也不管,但和這些壞人接近是不可以的,他還是我的妻子。」世安問。
「笑話!現在社交公開,她和男朋友接近也有罪嗎?你養不起妻子還說什麽?」
「我不管這許多,綺薇馬上跟我囘家去!」
「我的女兒是嬌生慣養的,你呌她囘去要餓死她不成?你看你的衣裳,千瘡百孔,饔餐不繼,有什麽能力養妻子,還是離婚好了!」
「對了,對了,老伯說得對,江小姐和他離了婚幸福得多了。不然,正像一朵鮮花挿在牛糞上!」槐靑諷剌地說:
「你說什麽?你有資格說話嗎?」世安怒極,接着給槐靑一記耳光。
槐靑幾乎和他火併起來,但被江樹仁勸着,他慢條斯理地說。
「盛世安,你蠻不講理,綺薇,你還是和他離婚,別牽累了你一生。」
「綺薇,你說,你是不是願意和我離婚?祇要你說,我馬上離開這裏!
綺薇不知怎樣是好,說嗎?「祇要你說?共渡困苦的生活」,但她除了哭,便不知所措了,只有匆匆地跑進房間裏去。
「朋友,江小姐不喜歡你了,你難道要賴死嗎?」槐靑說。
「本來夫婦離婚,是由男方補償瞻養費給女方的,但現在我可以倒給瞻養費給你,這裏有一百塊錢,拿了去吧!」江樹仁掏取了鈔票放在桌上。
這是侮辱,爲什麽要接受他的錢?世安沒有接受。
江樹仁還寫好了一張離婚書,迫令世安署名,世安這時的心情,悲恨交集,他想,妻子己懷去志,勉强奪囘來也不是幸福的,咬緊牙根,痛快地寫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取過了鈔票也撕開三段,才悻悻然離開。
盛世安這時候,腦海裏充滿着自殺的念頭,死了倒乾净,不覺走到海邊,正想跳下去,剛巧阿勝走來,他是要搭船囘鄕的,看見世安一把拉往一家凉茶店,正想喝茶止渴,突然聽到涼茶店裏的收音機,發出了聲音「現在請XXX先生主講:「人類是不應該自殺的」。
世安被這題目吸引了,他靜耳細聽。
「生存,是人類的義務,人類是社會的公民,法律是絕對保護人類的,假如你自殺,便是殺了一個社會的公民,是有罪的,應要受到法律的裁判。幷且,自殺是弱者的措施,大凡自殺者,祇要你用自己的力量去換取代價,就能夠解决生活了,此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如果每一個人能夠這樣想,便不應該自殺了,我們要知道,生存是人類的義務,如果把自殺的勇氣,拿去向惡劣社會鬥爭,結果,最後勝利必屬於你的。」
盛世安聽完了這番說話後,他的心境果然開朗了,把自殺的念頭,拋去九霄雲外,他自己也認為如果不畏艱難,就算去當伕力,也可以解决生活呢!他便咬緊牙根,拿自殺勇氣,去向惡劣社會鬥爭!
他緩步而行,路經海傍,遙見一個少女,憂鬱地徘徊感歎,他心裏想,「莫非她想自殺」?於是靜靜行近她的身傍,見她正在縱身欲躍,他一手把他攔阻着,這少女囘過頭一看,啊!原來是相識的。
這個少女年紀在十八歳至二十歳,面貌和江綺薇很相像,原來這就是游漫萍,在江浪生的學校中收洗衣服的女郞,幷且曾經是江浪生的戀人。
「盛先生,你別救我了,我死了還好。」游漫萍說。
「不!游小姐,為了失戀而自殺是最愚蠢的,江浪生旣然不愛妳,妳為什麽為他而死?妳應該拿出死的勇氣去創造事業,獻身社會,凡事强求是不可能的,他不愛你,妳可以再去找尋新的對象,在雙方情投意合之下而相愛的,才是眞摯的情感,江浪生這個人是極度拜金主義的人,他的父親也是一樣,所以才做成他這慕虛榮的壞習慣,就算他現在還愛妳,對妳的前途也不會幸福的,游小姐,別為他而作沒價値的犠牲,拿出妳的勇氣生存下去,你是國家的公民,妳不保存自己的生命反而自殺,這是有罪的,妳會受到處分的,游小姐,聽的我話,快囘家裏去吧!」
游漫萍聽了這段話,心境突然開朗了許多,自己也太愚蠢,也太衝動,為這無情鬼來自殺?不!决不!凡自殺的人,他的自殺勇氣是一剎那間存在的,現在旣經盛世安的感動,她的理智漸漸恢復了。
「盛先生,聽你一席話,使我明白了,我實在不應該自殺,那麽,你是江浪生的姐夫,為什麽現在………」
「我現在很頹喪是嗎?一言難盡了,總是江浪生這家人累了我,我也曾經像妳一樣想去自殺。」
「為什麽?可以告訴我嗎?」
盛世安感覺他和游漫萍同是天涯淪落人,不妨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她。
「哦!為什麽江浪生這一家人,每個都是這麽無情無義的呢?唔!盛先生!幸虧你救了我,不然,我枉死了。」漫萍懊悔地說。
盛世安瞧見天空漸漸被黑幕籠罩了,恐怕和游漫萍站在這裏不便,本來他自己要走,但更恐怕游漫萍再萌死念,最後還是親自送她囘家去。
第二天,世安一樣在街頭走着,一間茶樓門前,發覺一個老年人在賣報,他想,上了年紀的人也可以維持生活,難道我坐着待斃嗎?馬上走前和這老人家搭訕,才知道他把每天賣報所得的利錢來養活自己。
「老伯,我也想跟你一樣賣報紙,可是我不懂手續和規矩,你能引領我嗎?」
盛世安並把自己的困苦吿訴了他,老伯原是窮人,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便說:
「可以的,我看你年靑有爲,一定敎導你的,每天我也在這裏,明天來找吧!」
盛世安好不歡喜,向他道謝了,立卽囘家找賣報紙的資本,最後,把一被袋一賣掉了,得到三塊錢的資本,又過了一天,却見江浪生從茶樓下來,雖然盛世安正要避開,但被江浪生瞧見了,除了奚落他一番外,還在袋角裏摸出一毫錢,把他當作呌化子一樣的施捨,盛安世怒極走開了。
大淸早,祥伯帶世安到各報館兩去取報紙,手持着一大叠報紙,祥伯吩咐世安走動兩條腿到處去,世安日裏不斷地呌,腿不斷地跑,終於在他勤懇之下,獲利兩塊多錢。
午報生意做完了,祥伯帶世安到茶樓裏去喝杯茶,休息一下疲勞,世安這時候才感到「生」的興趣。
這天晚上結賬,世安整日獲利五塊多錢。
那一天在微弱的傍晚,世安持着一叠報紙正想走過馬路,但看見一個人不留神幾乎捽倒在地,他眼明手快把那個人一把拉起,兩人的目光接觸着,原來是游漫萍。
「盛先生,眞巧了,我到你居住的地方找你不着,媽想見你,現住你和我囘去好嗎?」
「什麽事?我要賣報紙哩。今天下雨生意不好」。
「今天是媽的生口,你到我家裏吃飯好嗎?」
世安是漫萍家裏唯一的客人,正在舉杯欲飲的時候,大門被猛力地推開,進來兩個人,一個是江浪生,另一個是他的朋友,大家不禁愕然,他來這裏幹嗎?漫萍正想向他質間,但被江浪生先說:「盛世安,你來這裏幹嗎?游漫萍是我的什麽人?」
「我不知道,我祇是知道他就是游漫萍。」世安說:
「游漫萍就是我的愛人,知道嗎?」
「哼!我不是你的愛人,你快滾,這是我的家。」漫萍怒駡。
「我不走又怎麽樣?可是盛世安你不應該播弄是非,偏說我們父子,姐弟的壞話,哼!」
「你們是這樣的人,我不怕說,我的爸爸被你們害了,我的家被你們毀了,你們有今天,也是我爸爸帮助你,原來你江家的人通通是没良心的………………」
「你還在說什麽?我們有錢是你幫助的嗎?姐姐被你累了,幸虧現在嫁了,才過着幸福的日子,跟着你嗎?」
「沒有良心的東西,快滾!」
「我不滾!」江浪生一邊說,一邊給世安一記耳光。
「什麽?你打人!」漫萍說。
「拍」的一聲,浪生把漫萍也照樣子給她一記耳光。浪生正欲帶着勝利的微笑走出門外,但盛世安這時候不能再忍耐了,搶步上前一把抓着浪生,連忙向他的面頰餉以一拳。
「你快帮我打他,打他!」浪生手足無措地呌同來的那位朋友帮助,但這朋友是個瘦削的個子,他那裏敢替浪生還抗,祇管拖着浪生出去,浪生的面頰被打後,從嘴角流出了牙血來,他忍着痛還駡:「哼……打我,你小心,盛世安!」
「還說什麽?快滾!」
浪生被他一喝,兩步當作一步走了。
漫萍爲了避免江浪生的不斷騷擾,凑巧在世安住的屋子裏,尾房的住客爲了和二房東三嬸鬧意見,突然搬走了。世安靈機一觸,漫萍正好遷來這裏,於是和三嬸接洽,三嬸祇要有人租房子便可以了,尤其是世安的朋友,她更樂於租出,這樣她們搬家了。
X X X
好容易過了幾個月的時光,這是春末初夏的時候,在一個週末的晚上,本來江綺薇是個過慣繁華的人,爲甚麽在這好時光裏會閨幃獨守?
毛毛的細雨不斷地下着,江綺薇站立窗前,凝視着雨景,這是夜深兩點鐘了,曹槐靑還沒有囘來,致令她寂寞地守候空房,眼光偶然瞧見案上的日曆,原來是接近淸明時節,這樣觸起她紊亂的心情,好幾年前,她和世安在這淸明時節的時候,不是携手囘鄕去掃墓嗎?那種熱切情景還隱現在眼簾,哼!為甚麽要再嫁?曹槐靑有甚麽好處?不務正業,終日在外花天酒地,江綺薇想起來,吊下了兩點淚,半倚在沙發上,眼倦了,正當矇朧入睡的時候,時鐘敲响了三吓,她突然聽到有汽車的停止聲,綺薇霍然起立跑到窗前,眼光投下去,在車廂裏走出來的是一個穿西服靑年,這正是自己的丈夫——曹槐靑,跟着有一個女郞探頭出來。
「謝謝你,再見!」槐靑和這女郞握手說:
「明天再見!」女郞說畢,汽車風馳電擊般駛去了。
綺薇一切也看得淸楚,她等槐靑走進房中,怒不可遏,便問:
「你今晚到那裏去?」
「………………………」
「送你囘來的女人是誰?你以爲我全不知道嗎?你對得起我嗎?現在爸爸把全盤生意交給了你,提拔你,你應該心滿意足,循規蹈距,爲甚麽還這樣,你想想,你沒有我爸爸,你有今天嗎?」
「甚麽!甚麽,你爸爸不是笨人,爲甚麽把生意交给我,不交給你的好弟弟,他甚麽也不懂,只會花錢,我是個忠實能幹的人,所以你爸爸才把生意交給我管理!再說到你,假如你爸爸沒有錢,我會愛你嗎?你是有過丈夫的女人,我現在也不嫌棄你,你還要管我?我出去交際應酬,當然有女朋友的,這一點也看不開?」
「從前你說過不計較婚前的一切,婚後我有甚麽對你不起?」綺薇哭起來。
曹槐靑和江綺薇鬧翻了,便和江浪生到一處細談:
「浪生,現在你這樣要錢也不是辦法,你爸爸對你也不大好」。
「是的,他十分吝嗇,總不讓我用多一文錢」。
「因爲你不是他的親生子,總是這樣的。」
「這個我也知道的,」
「你假如要掌握大權,一定要等待你爸爸死了,他不死你一定不能暢所欲爲,」
「難道希望他死嗎?」
「不!你能和我同一陣線的話,不特大權可以掌握,並且可以有無窮盡的錢用。」
「怎樣?你說!」
槐靑附耳和他說了好一會,浪生點點頭。
X X X
一天,兩天,槐靑不但不囘家,公司也不到,第三天才發現他挾款潛逃,經常在生意上有來往的各商號也紛紛來追債,原來槐靑在幾月前已蓄意逃走,把一切款項抽出來,欠下各商號的錢也不淸還。
當江樹仁和綺薇跑出公司的時候,許多人圍攏着要討債,可憐江樹仁實在不如他的去向,還被人駡他蛇鼠一窩。
江綺薇跑到學校找尋浪生,才知道他退學兩個月了,浪生也失踪,當然和槐靑同一道的。
江樹仁不德掙來的錢,就這樣沒有了,這是天理循環,理應要他受這公道的裁判。
江樹仁不但是生意倒閉,並且債主臨門,他實在無法應付,因此被牽涉到訴訟公堂,這樣一來,傾他所有來解决才漸漸踏過難關。
房子賣掉了,產業也化整為零,現金用光了。現居住在平民區裏,江樹仁爲了這終日憂抑,漸漸地走上了昔日盛柏年的路,——貧病交迫,現在相依爲命的祇有女兒——綺薇一個人。
過了幾天,九嬸替綺薇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做女傭的,綺薇爲求解决生活,什麽也願幹。
九嬸帶她到主人家裡面議,這間房子雖小,但住了好幾伙人,住尾房的大少奶便是綺薇的女主人。工資講好每月祇有二十五塊錢,照顧五個孩子和大少奶夫婦,一共七個人,另外還有零碎工作。
第二天早上,綺薇去上工,一見到主婦,嚇了一跳,原來她正是以前綺薇家裏的丫頭,從前自己使喚的人,現在自己要受她使喚,綺薇感到了侮辱,頭也不囘逕自走了。
第二天淸晨,從鄰居傳來一個消息,外面有人施粥。江樹仁拿着漱口盅走在窮人隊伍裏,按次序分派。
「老伯請等一下,粥派完了,我們的老板就送來了。」輪到了樹仁,分派的人說:
「你們的老板是誰?這樣熱心。」樹仁問。
「哪,他來了」。一個伙計說:
原來這施粥是他做的善舉。
樹仁看到世安,粥也不領,丟頭便跑。世安也看到了他,跟着趕去。
「表叔,是你!」「啊………………」江樹仁慌忙驚訝地說。
就是我哩!表叔,你們爲甚麽弄成這樣?在這裏居住?」世安追問着。
「世安,我還有甚麽面目再見你?」樹仁說。
過去的讓它過去,別再提了。」世安很不介意地說。「綺薇,現在怎樣生活?」
樹仁聽他這一問,還沒有說話,她的酸淚便不斷地流下,略歇一會兒才說:「世安,你看這房子還成一個家嗎?簡直是乞丐窩一樣,不過,能不露宿街頭已經甘願了。」
「表叔,我看到報紙,槐靑和浪生分賍,浪生給槐靑打死,槐靑也被警察拘捕。你的財產一部份追囘,等着你去認領呢。」世安拿出報紙說着。
「那也是你的錢,我領了囘來,一定還你,好給你多做一點善事。」樹仁看了報紙,對世安說。
「萍媽,漫萍,祥伯他們都來了,世安一一介紹。大家寒喧一番,樹仁發現漫萍和自己旳女兒長得一模一樣,便問萍媽故鄕在那裡,因爲廿多年前因水災失散的次女,算起來正和漫萍一樣大呵。
「江老爺,我老實告訴你,漫萍不是我親生………」「媽,爲甚麽我不是你親生的?」漫萍急問。「阿萍,我一向沒有告訴你吧了,江老爺,你的故鄕在那裡?」「是大髻鄉西村的。」
「啊!是了,我也給大髻鄕的,不過是北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守淸在夫家,夫家就是大髻鄕,那年間水災後我看見一個剛會行的女孩在哭,我便抱回來撫養,一直到現在,漫萍已長大成人了,也許她就是你的女兒。一「不錯,就是在水災那年我的次女失散,當我和游小姐相見的時候,我就聯想到次女的樣子和她一樣…」「媽,這是事實嗎?」漫萍驚奇地問。
盛世安張大了嘴巴不會說話,因為他感到事情太凑巧和離奇了。「我現在不敢斷定她是不是我的女兒,但我記得在兩個女兒之中,一個是左脚腫有一痣痕,一個是右脚腫有一個痣痕的,你看看是左脚還是右脚。」
綺薇連忙脫下了木屐瞧瞧,原來是右脚腫,漫萍也脫去了鞋襪一看,却是在左脚腫,這樣的証明下,漫萍果然是江樹仁的次女了。
「那麽……你是爸爸,你是我的姐姐,」漫萍驚訝的聲音中有些沙啞,她像高興,但也像帶哭地說。
是呀!老爺就是你的爸爸,快過去呌一聲。萍媽說。「唉。爸爸太沒用了,也許世安已經告訴過你。」
「爸爸,你究竟是我的爸爸哩!」漫萍說。
好孩子,現在我們能夠骨肉重逢,這也該感謝游老太養育你的深恩。「妹妹你和表哥甚麽時候結婚,好讓爸爸也可看到。」綺薇說,「媽,姐姐,我不結婚了,我不結婚了。」漫萍突然帶哭地說,弄得各人也莫明其妙,尤其是盛世安。「甚麽事,你說,漫萍」萍媽問。「世安本來是姐姐的丈夫,我不應該奪她的愛,我希望讓囘給姐姐。」
原來她是爲了這樣,可是綺薇聽了,心內更苦,她說:「妹妹,我和表哥已經沒有半點恩情了,我們不能覆水重收,假使他還是我的丈夫,我不致有今日,妹妹,我不想破壞你的幸福,祇希望你們組織快樂的家庭,你別這樣說,再說不過是挖苦我吧了!」綺薇的話很眞誠。「不錯,阿薇應該這樣做,」江樹仁說。
盛世安這時候說話了,「我和漫萍是眞誠的相愛,綺薇當然不會和我復合,漫萍你何必說這些話,現在我們都是親人,表叔將來也是我的岳父,我必盡我的力量去供養他。」(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