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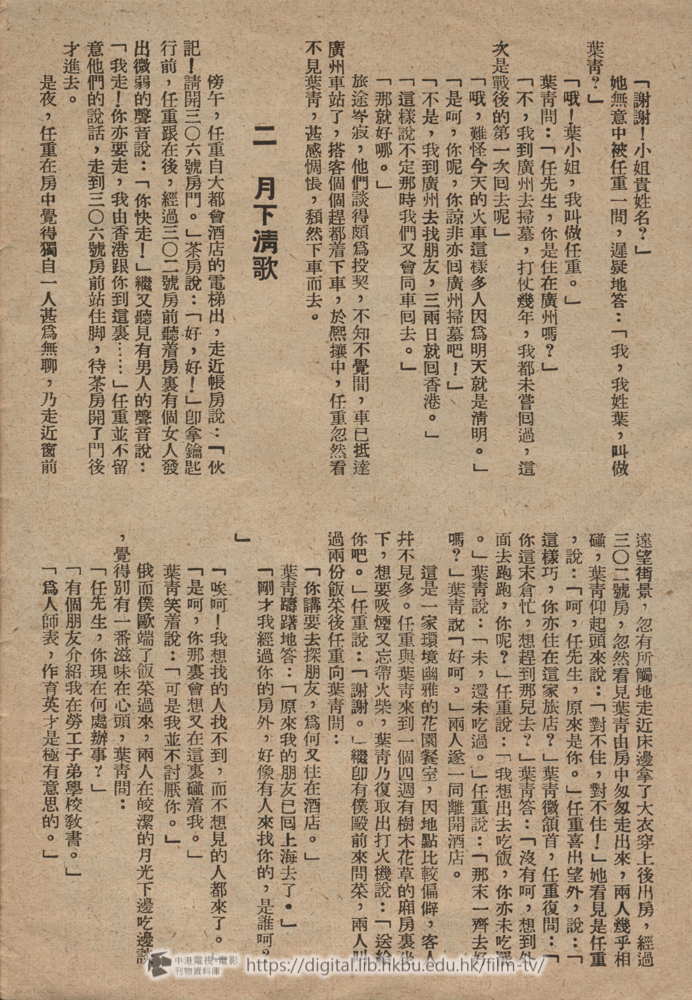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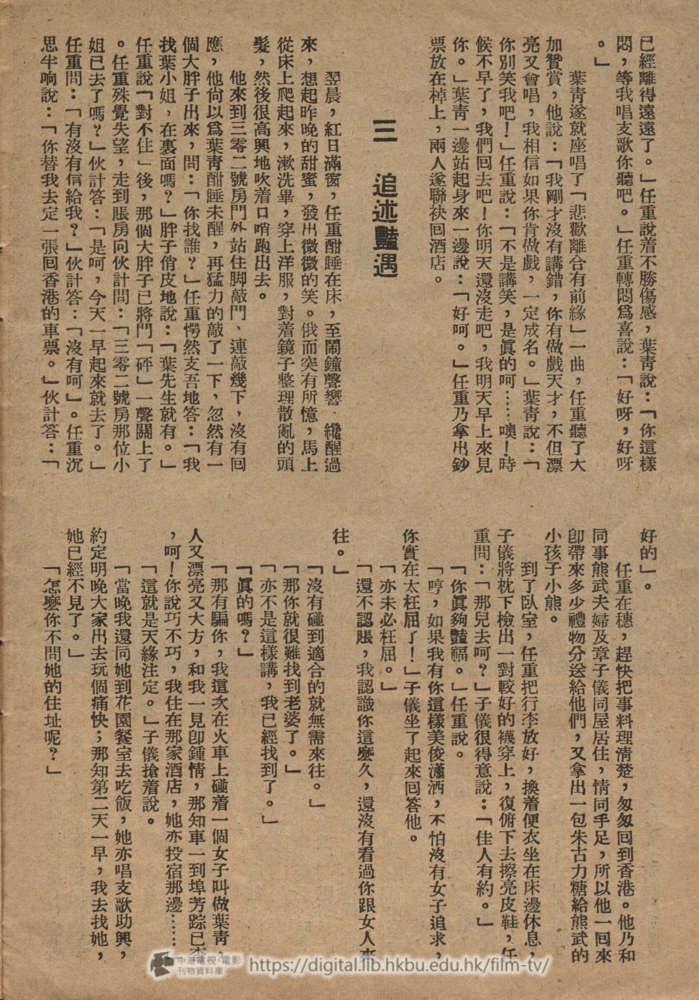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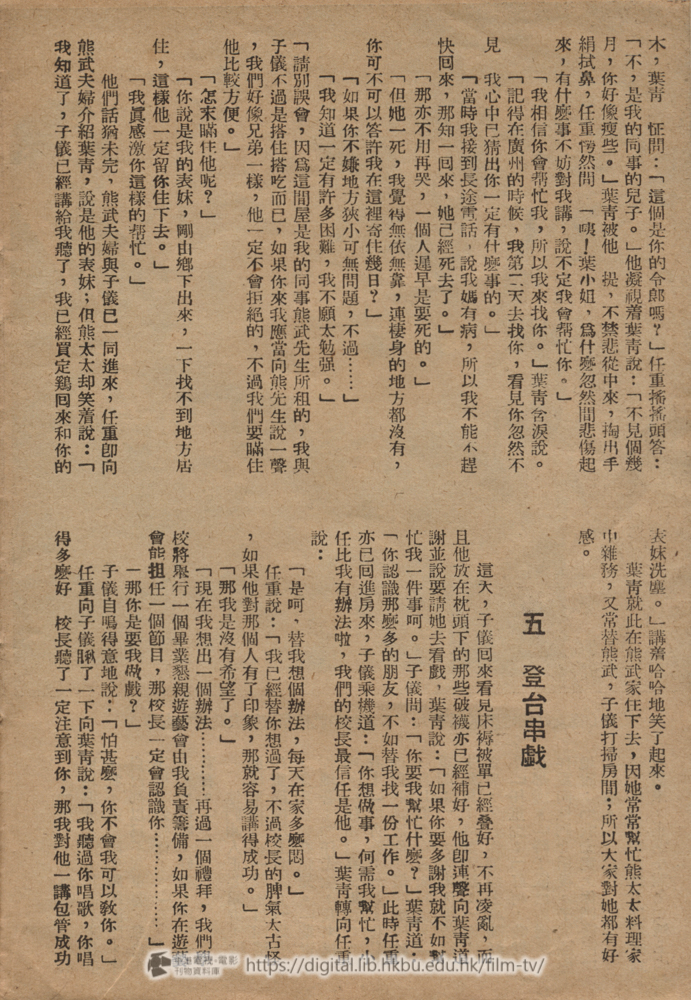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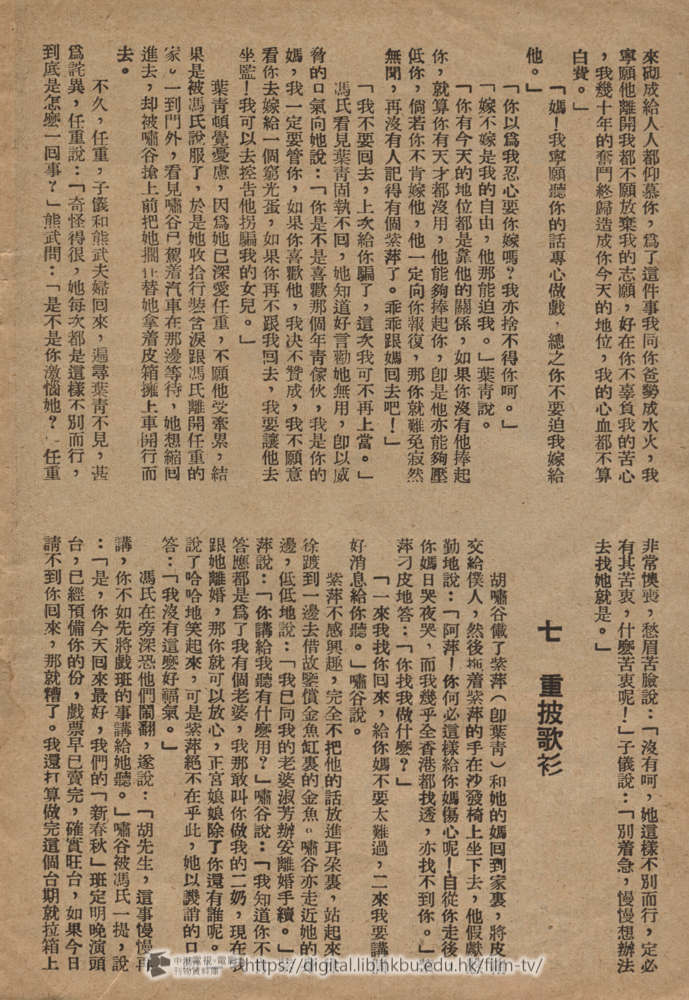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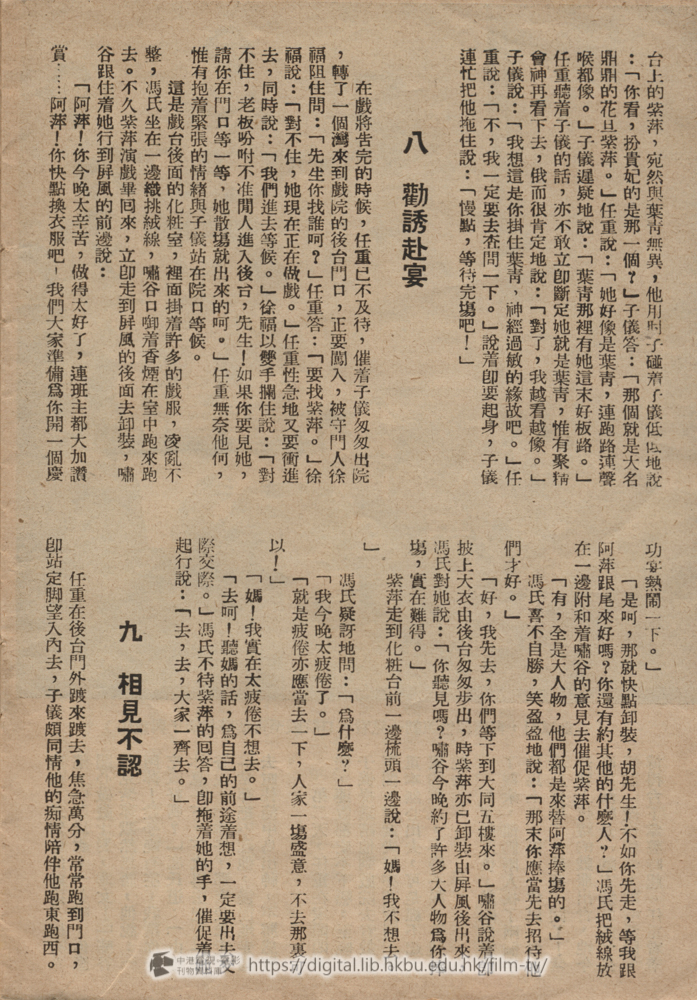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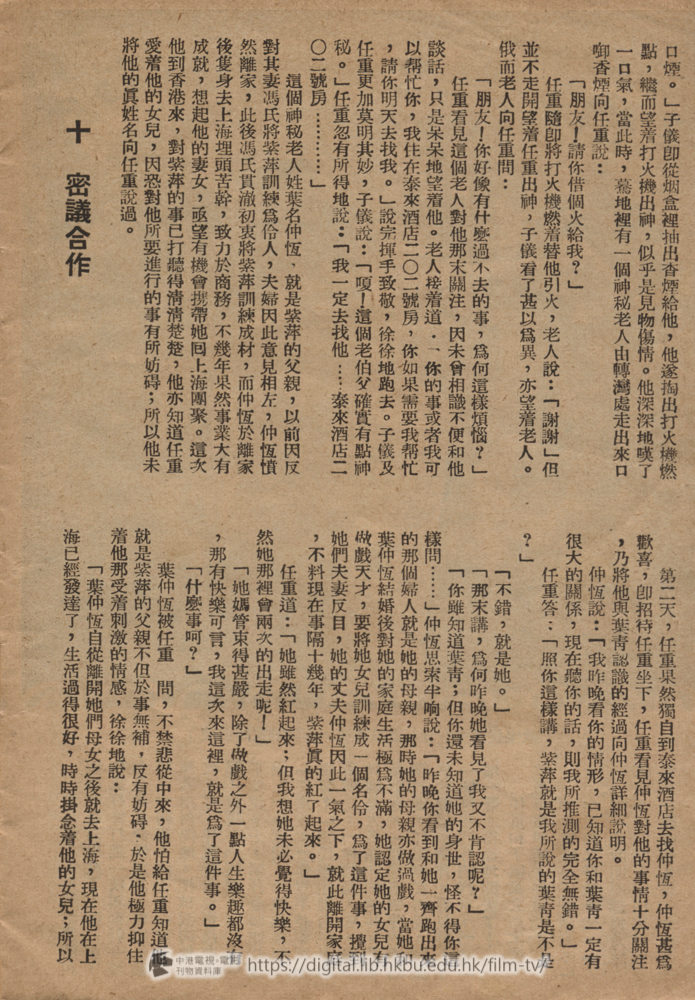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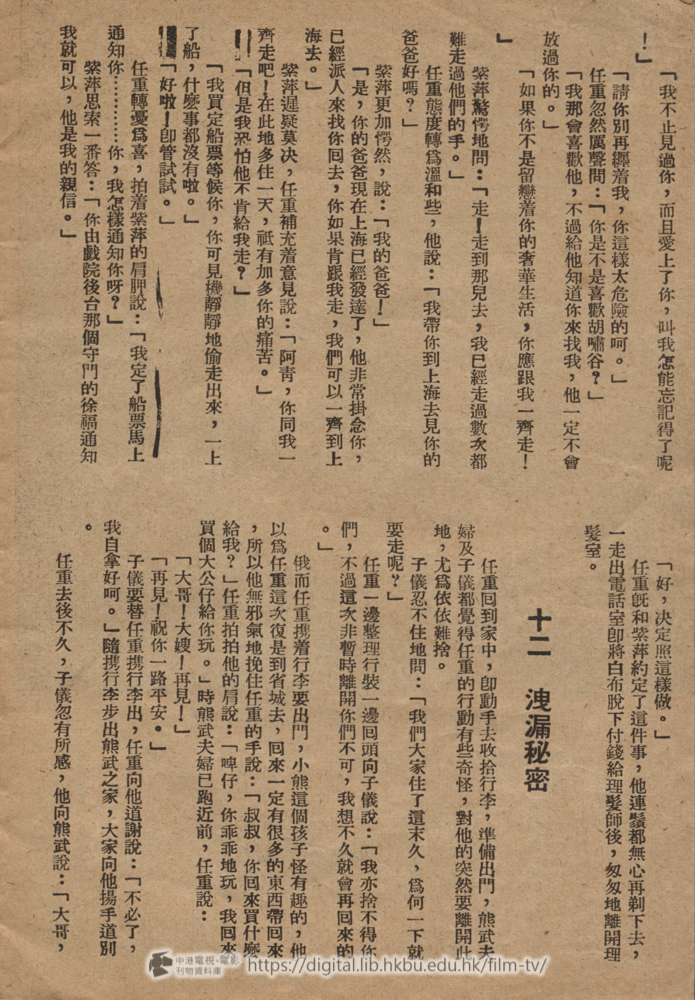





電影小説 長恨歌
原著編劇:俊人
小説改作:湘子
一 車中邂逅
一列卽將開往廣州的火車停在車站,男女搭客紛紛上車把座位已經佔滿。臨行時,有一個女子手携皮箱匆匆地上車張目四望,但找不到一個空位,乃暫時坐在座格外的椅上,把皮箱放在身邊。
靑年敎師任重,他這天亦搭這列火車,正坐在這個女子旁邊的座位,披閱報紙。他看見這個女子所坐的地方極不舒適。私自替她不安,眼睛耿耿地注視她,徒使她更加侷促。在另一邊的座格裡坐着甲乙兩個中年婦人,甲婦向任重說:
「先生,請你借張報紙給我看。」
任重給她一叫,打斷思潮,答:「哦!好,好!」將報紙交給甲婦。甲婦一看報紙,忽然驚異起來向她的同伴說:
「唉呵!紫萍失踪了!」
乙婦說:「眞的嗎?爲什麽緣故,會不會又是宣傳作用!」
「不會的,紫萍現在正紅,有那個花旦能夠跟得她上,那怕不會旺台,何必以此宣傳。」
「不然爲何會失踪?」
「我想一定又是鬧出什麽桃色糾紛」
「是麼?聽見她媽管得甚嚴,那裏有這件事?」
「就是因爲這樣,迫得她非走不可:聽說她媽要她嫁給一個姓胡的,她不肯所以走了。」
「你怎末知道,是不是你認識她?」
甲婦答:「我看過小報的。」
「這末看,她媽亦太不應該了。」
「這個姓胡的聽說很有錢。」
「有錢什麼用,現在她走了,怎末辦?」
這兩個婦人的說話,句句入了她的耳朶,覺得甚爲不安。時適任重旁邊的一個搭客正離座他去,任重卽向她說:「請來這裏坐吧!」她說聲「謝謝」卽把行李拿過來,任重替它放在上面,她然後坐下去。
俄而甲婦將報紙還給任重,任重拿出香煙,燃上火柴,那知不着,而火柴只有一根,任重正要呼喚侍役,坐在鄰座的她立卽由她的手袋裡掏出一個打火機給任重,任重接過來將香煙引着火後,取出香煙說「你抽煙麼?」她答:「我不抽煙。」任重說:「不抽煙,怎末會有打火機呢?」她微笑答:「嗄,我不過當它玩玩。」
火車向前疾馳,搭客受了車身的震動,個個都好像很疲倦似地靜坐着,只有任重他此時被這個女子的魔力所吸引,亟想要和她攀談,將打火機還給她,說:
「謝謝!小姐貴姓名?」
她無意中被任重一問,遲疑地答:「我,我姓葉,叫做葉靑?」
「哦!葉小姐,我叫做任重。」
葉靑問:「任先生,你是住在廣州嗎?」
「不,我到廣州去掃墓,打仗幾年,我都未嘗囘過,這次是戰後的第一次囘去呢」
「哦,難怪今天的火車這樣多人因爲明天就是淸明。」
「是呵,你呢,你諒非亦囘廣州掃墓吧!」
「不是,我到廣州去找朋友,三兩日就囘香港。」
「這樣說不定那時我們又會同車囘去。」
「那就好哪。」
旅途岑寂,他們談得頗爲投契,不知不覺間,車已抵達廣州車站了,搭客個個趕着下車,於熙攘中,任重忽然看不見葉靑,甚感惆悵,頹然下車而去。
二 月下演歌
傍午,任重自大都會酒店的電梯出,走近帳房說:「伙記!請開三〇六號房門。」茶房說:「好,好!」卽拿鑰匙行前,任重跟在後,經過三〇二號房前聽着房裏有個女人發出微弱的聲音說:「你快走!」繼又聽見有男人的聲音說:「我走!你亦要走,我由香港跟你到這裏……」任重並不留意他們的說話,走到三〇六號房前站住脚,待茶房開了門後才進去。
是夜,任重在房中覺得獨自一人甚爲無聊,乃走近窗前遠望街景,忽有所觸地走近床拿了大衣穿上後出房,經過三〇二號房,忽然看見葉靑由房中匆匆走出來,兩人幾乎相碰,葉靑仰起頭來說:「對不住,對不住!」她看見是任重,說:「呵,任先生,原來是你。」任重喜出望外,說:「這樣巧,你亦住在這家旅店?」葉靑微頷首,任重復問:「你這末倉忙,想趕到那兒去?」葉靑答:「沒有呵,想到外面去跑跑,你呢?」任重說:「我想出去吃飯,你亦未吃罷。」葉靑說:「未,還未吃過。」任重說:「那末一齊去好嗎?」葉靑說「好呵。」兩人遂一同離開酒店。
這是一家環境幽雅的花園餐室,因地點比較偏僻,客人幷不見多。任重與葉靑來到一個四週有樹木花草的廂房裏坐下,想要吸煙又忘帶火柴,葉靑乃復取出打火機說:「送給你吧。」任重說:「謝謝。」繼卽有僕毆前來問菜,兩人叫過兩份飯菜後任重向葉靑問:
「你講要去探朋友,爲何又住在酒店。」
葉靑躊躇地答:「原來我的朋友已囘上海去了。」
「剛才我經過你的房外,好像有人來找你的,是誰呵?」
「唉呵!我想找的人找不到,而不想見的人都來了。」
「是呵,你那裏會想又在這裏碰着我。」
葉靑笑着說:「可是我並不討厭你。」
俄而僕歐端了飯菜過來,兩人在皎潔的月光下邊吃邊談,覺得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葉靑問:
「任先生,你現在何處辦事?」
「有個朋友介紹我在勞工子弟學校敎書。」
「爲人師表,作育英才是極有意思的。」
「意思雖不能講有什麽意思,不過一班學生和同事們對我都算不錯。」
「我覺得敎書工作甚爲有趣。」葉靑說。
「但這對你是不適合的。」
「你以爲我應做什麽工作才適合呢?」
「你最好是去做戲,因爲你生得這末漂亮。」
葉靑聽了為之愕然,暗想他爲何會講做戲呢,默然無語,時僕毆已走來收拾碗碟,打斷他們的話柄。
一會兒,任重舉首向空一望,看着一輪明月似有所感,微嘆着氣,葉靑頗爲詫異問:「任先生,爲甚麽忽然嘆氣?」任重說:「我想到人生確實奇妙,好像我們一離開火車,我以爲從此不會再見到你,那知現在又碰着,今晚月色這樣美麗,我們又能在此傾談,好像多年的相識,但不知第二次月圓之夜,我們能不能再有聚談的機會嗎?算不定我們那時已經離得遠遠了。」任重說着不勝傷感,葉靑說:「你這樣悶,等我唱支歌你聽吧。」任重轉悶爲喜說:「好呀,好呀。」
葉靑遂就座唱了「悲歡離合有前緣」一曲,任重聽了大加贊賞,他說:「我剛才沒有講錯,你有做戲天才,不但漂亮又會唱,我相信如果你肯做戲,一定成名。」葉靑說:「你別笑我吧!」任重說:「不是講笑,是眞的呵……噢!時候不早了,我們囘去吧!你明天還沒走吧,我明天早上來見你。」葉靑一邊站起身來一邊說:「好呵。」任重乃拿出鈔票放在棹上,兩人遂聯袂囘酒店。
三 追述豔遇
翌晨,紅日滿窗,任重酣睡在床,至鬧鐘聲響,纔醒過來,想起昨晚的甜蜜,發用微微的笑。俄而突有所憶,馬上從床上爬起來,漱洗畢,穿上洋服,對着鏡子整理散亂的頭髮,然後很高興地吹着口哨跑出去。
他來到三零二號房門外站住脚敲門、連敲幾下,沒有囘應,他尚以爲葉靑酣睡未醒,再猛力的敲了一下,忽然有一個大胖子出來,問:「你找誰?」任重愕然支吾地答:「我找葉小姐,在裏面嗎?」胖子俏皮地說:「葉先生就有。」任重說「對不住」後,那個大胖子已將門「砰」一聲關上了。任重殊覺失望,走到賬房向伙計問:「三零二號房那位小姐已去了嗎?」伙計答:「是呵,今天一早起來就去了。」任重問:「有沒有信給我?」伙計答:「沒有呵」。任重沉思半响說:「你替我去定一張囘香港的車票。」伙計答:「好的」。
任重在穗,趕快把事料理淸楚,匆匆囘到香港。他乃和同事熊武夫婦及章子儀同屋居住,情同手足,所以他一囘來卽帶來多少禮物分送給他們,又拿出一包朱古力糖給熊武的小孩子小熊。
到了臥室,任重把行李放好,換着便衣坐在床邊休息,子儀將枕下檢出一對較好的襪穿上,復俯下去擦亮皮鞋,任重問.:「那兒去呵?」子儀很得意說:「佳人有約。」
「你眞夠豔福。」任重說。
「哼,如果我有你這樣美俊瀟洒,不怕沒有女子追求,你實在太枉屈了!」子儀坐了起來囘答他。
「亦未必枉屈。」
「還不認賬,我認識你這麼久,還沒有看過你跟女人來往。」
「沒有碰到適合的就無需來往。」
「那你就很難找到老婆了。」
「亦不是這樣講,我已經找到了。」
「眞的嗎?」
「那有騙你,我這次在火車上碰着一個女子叫做葉靑,人又漂亮又大方,和我一見卽鍾情,那知車一到埠芳踪已杳,呵!你說巧不巧,我住在那家酒店,她亦投宿那邊……」
「這就是天緣注定。」子儀搶着說。
「當晚我還同她到花園餐室去吃飯,她亦唱支歌助興,約定明晚大家出去玩個痛快;那知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她,她已經不見了。」
「怎麽你不問她的住址呢?」
「我知道她是住在香港的;但香港這麽大如何去找她呢?」
子儀自作聰明地說:「我有辦法,在報紙上登載一尋人廣吿,包你找得着她。」
「我同她只見面數次,那未免太唐突。」
「那惟有天天到街上去碰,想不定會給你碰到」
「怕沒有這麽容易。」
任重聽着子儀的建議,若有所感,將烟盒取出一根香煙啣上口,復由褲袋裏掏出葉靑送給他的打火機,呆呆地發怔一下,然後打火吸烟。
四 玉人復來
自此以後,任重與子儀兩人每天於學校放課後,卽到各處去散步,希望能夠碰到葉靑,可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芳踪依然渺茫。
有一天,他們兩人來到一間戯院的門前大廳,子儀瞪睛看着掛在大廳正面的一張大劇照,戀戀不捨說:」你看,這個花旦多麽漂亮。」任重拖着他的手說:「走吧,在這裏那能碰到她呢!」子儀說:「我今晚請你看戲好嗎?」任重說:「聽說一張票要十幾塊,別太花費。」子儀說:「不怕,我節省了幾個月,現在已籌備夠錢我今晚請你看,這個花旦紫萍曾停演了一個時期,現在剛重披歌衫,這個機會不可錯過。」任重說:「好啦,好啦,囘去再談。於是兩人乃踏出戲院,到各處去跑了一趟才囘家去。」
一個多月後,在勞工子弟學校的門前,任重與子儀站在那邊說話:
「今天我不想再去找了。」
「爲什麼?」
「我們跑了一個多月,皮鞋亦踏破了幾對,連個影子都看不見,這樣找,好像大海撈針,那能找得到呢!」
「你未免太無耐性,怎末可以追求女性,其實不關我事,我不過是陪你跑跑而已,你自己都以爲不關重要那我亦不要太勉强你了。」
「好哪,好哪,再跑一天看看。」
他們倆人正要開步,猛發現葉靑站在一邊張目四望,任重趕快跑上前問:「葉小姐,怎末你會在這兒。」葉靑忸怩地答:「任先生,我來找你呵。」任重驚喜交集說:「找我!」葉靑答:「是,我記得你對我講過你在這間學校敎書,所以我現在專來拜訪。」任重問:「咦,怎末你提着行李去那兒?」葉靑說:「你住在那裏,先到你那邊去再談好嗎?」任重說:「好呵,我就住在那邊。」時子儀已跑過來,任重向他們介紹後,子儀識趣地說:「我先走,你們慢慢地談好啦。」
任重替葉靑携着皮箱囘到家裏來,正遇小熊坐在地上砌木,葉靑怔問:「這個是你的令郞嗎?」任重搖搖頭答:「不,是我的同事的兒子。」他凝視着葉靑說:「不見個幾月,你好像瘦些。」葉靑被他一提,不禁悲從中來,掏出手絹拭鼻,任重愕然問「咦!葉小姐,爲什麼忽然間悲傷起來,有什麼事不妨對我講,說不定我會帮忙你。」
「我相信你會帮忙我,所以我來找你。」葉靑含淚說。
「記得在廣州的時候,我第二天去找你,看見你忽然不見我心中已猜出你一定有什麽事的。」
「當時我接到長途電話,說我媽有病,所以我不能不趕快囘來,那知一囘來,她已經死去了。」
「那亦不用再哭,一個人遲早是要死的。」
「但她一死,我覺得無依無靠,連棲身的地方都沒有,你可不可以答許我在這裡寄住幾日?」
「如果你不嫌地方狹小可無問題,不過……」
「我知道一定有許多困難,我不願太勉强。」
「請別誤會,因爲這間屋是我的同事熊武先生所租的,我與子儀不過是搭住搭吃而已,如果你來我應當向熊先生說一聲,我們好像兄弟一樣,他一定不會拒絕的,不過我們要瞞住他比較方便。」
「怎末瞞住他呢?」
「你說是我的表妹,剛由鄕下出來,一下找不到地方居住,這樣他一定留你住下去。」
「我眞感激你這樣的帮忙。」
他們話猶未完,熊武夫婦與子儀已一同進來,任重卽向熊武夫婦介紹葉靑,說是他的表妹,但熊太太却笑着說:「我知道了,子儀已經講給我聽了,我已經買定鷄囘來和你的表妹洗塵。」講着哈哈地笑了起來。
葉靑就此在熊武家住下去,因她常常帮忙熊太太料理家中雜務,又常替能武,子儀打掃房間;所以大家對她都有好感。
五 登台串戯
這天,子儀囘來看見床褥被單已經叠好,不再凌亂,而且他放在枕頭下的那些破襪亦已經補好,他卽連聲向葉靑道謝並說要請她去看戲,葉靑說:「如果你要多謝我就不如幫忙我一件事呵。」子儀問:「你要我幫忙什麽?」葉靑道:「你認識那麽多的朋友,不如替我找一份工作。」此時任重亦已囘進房來,子儀乘機道:「你想做事,何需我幫忙,小任比我有辦法啦,我們的校長最信任是他。」葉靑轉向任重說:
「是呵,替我想個辨法,每天在家多麼悶。」
任重說:「我已經替你想過了,不過校長的脾氣太古怪,如果他對那個人有了印象,那就容易講得成功。」「那我是沒有希望了。」
「現在我想出一個辦法……再過一個禮拜,我們學校將舉行一個畢業懇親遊藝會由我負責籌備,如果你在遊藝會能担任一個節目,那校長一定會認識你……」
「那你是要我做戲?」
子儀自鳴得意地說:「怕甚麽,你不會我可以敎你。」
任重向子儀瞅了一下向葉靑說:「我聽過你唱歌,你唱得多麽好校長聽了一定注意到你,那我對他一講包管成功的。」
「但是我怕不會成功。」
子儀隨卽擺弄姿勢,敎葉靑行踏花旦的台步,還說葉靑的樣子像似紫萍,如果學到紫萍那樣,不怕沒有事做。他們的吵鬧聲已引起熊武的注意,走進來問:「你們在幹什麽呵?」子儀答:「做戲咯!」熊武以譏誚的口吻說:「你做戲,請借個鎚子給我打低我的毛管。」引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一星期後,勞工子弟學校的禮堂掛着「第十屆畢業聯歡遊藝會」的花牌,中間搭着一個低低的戲台,台下已經坐滿了觀衆,校長亦在座參觀,在衆人的拍掌間,任重登台向衆宣佈:「下一個節目由葉靑小姐,章子儀先生,熊武先生三人合演諧劇。」
台上的布幕開了,葉靑,子儀,熊武相繼登場,演得甚爲精采,博得全塲的喊采,傅校長亦笑容滿面的坐在一邊,任重已看出校長已有反應,向葉靑抛個眼色表示已有希望,葉靑亦微頷首,繼續演下去。待到這幕戲的完塲,任重走入後台向他們三人稱讚不已,遂向葉靑道:「等下我們跟校長去聚餐時我立卽向校長提出這件事,你先囘去等我的消息。」葉靑非常歡喜,頻向任重道謝。
六 被母尋囘
葉靑囘到家中,遇着小熊走出來,卽給他一塊錢叫女傭桂香帶他去買東西吃,然後入房去收拾衣服,正想要將任重與子儀的衣服早出去洗滌的時候,忽然聽見門鈴聲響,她即放下衣服出房,走過冷巷去開門,那知把門一開,現在她臉前的就是她的媽媽馮氏,嚇得她心爲之一跳。馮氏一看見葉靑亦不做聲,卽跟着她走進房。葉靑招待馮氏坐下,馮氏然後徐徐地說
「阿萍!我這次來找你,你一定覺得好奇怪。」
「其實你無謂來找我,你找到我,我亦不願囘去。」葉靑答。
「你幾次靜悄悄地離家,完全不當我是你的媽一樣看,你應知道我這樣做無非爲着你好。」
「爲我好,哼!胡嘯谷這個人我那能嫁給他呢!我同他亳無愛情,嫁給他,我一世就完哪。」葉靑怨嘆地說。
「阿萍!你以爲我壓迫你,其實我的苦心你還未了解。」
「如果你不强迫我嫁給胡嘯谷,我什麽事都可以答應。」
「阿萍!你所知你八歲的時候,我就覺得你有做戲的天才,希望你成爲一個名伶,不要學我這樣爲要做一個賢妻良母就犧牲自己的前途,我覺得嫁給你爸爸後就好像結束了我的性命,我不想你同我一樣的命運,我要你的名字用電光管來砌成給人人都仰慕你,爲了這件事我同你爸勢成水火,我寧願他離開我都不願放棄我的志願,好在你不辜負我的苦心,我幾十年的奮鬥終歸造成你今天的地位,我的心血都不算白費。」
「媽!我寧願聽你的話專心做戲,總之你不要迫我嫁給他。」
「你以爲我忍心要你嫁嗎?我亦捨不得你呵。」
「嫁不嫁是我自己,他那能迫我。」葉靑說。
「你有今天的地位都是靠他的關係,如果你沒有捧起你,就算你有天才都沒用,他能夠捧起你,卽是他亦能夠壓低你,倘若你不肯嫁他,他一定向你報復,那你就難免寂然無聞,再沒有人記得有個紫萍了。乖乖跟媽囘去吧!」
「我不要囘去,上次給你騙了,這次我可不再上當。」
馮氏看見葉靑固執不囘,她知道好言勸她無用,卽以威脅的口氣向她說:「你是不是喜歡那個年靑傢伙,我是你的媽,我一定要管你,如果你喜歡他,我决不贊成,我不願意看你去嫁給一個窮光蛋,如果你再不跟我囘去我要讓他去坐監!我可以去控吿他拐騙我的女兒。」
葉靑頓覺憂慮,因爲她已深愛任重,不願他受牽累,結果是被馮氏說服了,於是她收拾行裝含淚跟馮氏離開任重的家。一到門外,看見嘯谷已駕着汽車在那邊等待,她想縮囘進去,却被嘯谷搶上前把她擱住替她拿着皮箱擁上車開行而去。
不久,任重,子儀和熊武夫婦囘來,遍尋葉靑不見,甚為詫異,任重說:「奇怪得很,她每次都是這樣不別而行,到底是怎麽一囘事?」熊武問:「是不是你激惱她?」任重非常懊喪,愁眉苦臉說:「沒有呵,她這樣不別而行,定必有其苦衷,什麼苦衷呢!」子儀說:「別着急,慢慢想辨法去找她就是。」
七 重披歌衫
胡嘯谷儎了紫萍(卽葉靑)和她的媽囘到家裏,將皮箱交給僕人,然後拖着紫萍的手在沙發椅上坐下去,他假獻憨勤地說:「阿萍!你何必這樣給你媽傷心呢!自從你走後,你媽日哭夜哭,而我幾乎全香港都找透,亦找不到你。」紫萍刁皮地答:「你找我做什麽?」
「一來我找你囘來,給你媽不要太難過,二來我要講個好消息給你聽。」嘯谷說。
紫萍不感興趣,完全不把他的話放進耳朶裏,站起來徐徐踱到一邊去借故鑒償金魚缸裏的金魚。嘯谷亦走近她的身邊,低低地說:「我已同我的老婆淑芳辦妥離婚手續。」紫萍說:「你講給我聽有什麽用?」嘯谷說:「我知道你不肯答應都是爲了我有個老婆,我那敢叫你做我的二奶,現在我跟她離婚,那你就可以放心,正宮娘娘除了你還有誰呢。」說了哈哈地笑起來,可是紫萍絕不在乎此,她以譏誚的口吻答:「我沒有這麼好福氣。」
馮氏在旁深恐他們鬧翻,遂說:「胡先生,這事慢慢再講,你不如先將戲班的事講給她聽。」嘯谷被馮氏一提,說:「是,你今天囘來最好,我們的「新春秋」班定明晚演頭台,已經預備你的份,戲票早已賣完,確實旺台,如果今日請不到你囘來,那就糟了。我還打算做完這個台期就拉箱上廣州,這對你的前途是極有希望。」馮氏說:「是呵,你應關心做戲才對,乖女!」嘯谷看見紫萍默然無語,他說:「阿萍!趁今晚有空,我請你去吃飯好嗎?」馮氏道:「由她休息一下,下次再去吧!」嘯谷說:「亦好,那末我先走。」紫萍絕不理他,慢慢地走過去瞪住籠中鳥出神,不勝感慨。
第二天,任重在家悶悶不樂,連飯都吃不下嚥,至晚,子儀提議請他到戲院去看戲散下悶,熊武夫婦亦甚讚同,任重本無心出去,可是經不起大家的慫恿,不得不跟子儀到戲院去。
到了戲院後,戯院已擠滿了觀衆,他們兩人找了兩個空位馬上坐下去。一會兒,台上鑼鼓聲響了,綉幕亦開了!紫萍上炫耀的戲服出台,她今晚所演的是一齣古裝歌劇「長恨歌」做作穩煉,歌喉淸脆,博得台下掌聲時起。任重看着台上的紫萍,宛然與葉靑無異,他用肘子碰着子儀低低地說:「你看,扮貴妃的是那一個?」子儀答:「那個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旦紫萍。」任重說:「她好像是葉靑,連跑路連聲喉都像。」子儀遲疑地說:「葉靑那裡有她這末好板路。」任重聽着子儀的話,亦不敢立卽斷定她就是葉靑,惟有聚精會神再看下去,俄而很肯定地說:「對了,我越看越像。」子儀說:「我想這是你掛住葉靑,神經過敏的緣故吧。」任重說:「不,我一定要去査問一下。」說着卽要起身,子儀連忙把他拖住說:「慢點,等待完場吧!」
八 勸誘赴宴
在戲將吿完的時候,任重已不及待,催着子儀匆匆出院,轉了一個灣來到戲院的後台門口,正要闖入,被守門人徐福阻住問:「先生你找誰呵?」任重答:「要找紫萍。」徐福說:「對不住,她現在正在做戲。」任重性急地又要衝進去,同時說:「我們進去等候。」徐福以雙手攔住說:「對不住,老板吩咐不准閒人進入後口,先生!如果你要見她,請你在門口等一等,她散場就出來的呵。」任重無奈他何,惟有抱着緊張的情緖與子儀站在院口等候。
這是戲台後面的化粧室,裡面掛着許多的戲服,凌亂不整,馮氏坐在一邊織挑絨線,嘯谷口啣着香煙在室中跑來跑去。不久紫萍演戲畢囘來,立卽走到屛風的後面去卸裝,嘯谷跟住着她行到屛風的前邊說:
「阿萍!你今晚太辛苦,做得太好了,連班主都大加讚賞……阿萍!你快點換衣服吧!我們大家準備爲你開一個慶功宴熱鬧一下。」
「是呵,那就快點卸裝,胡先生!不如你先走,等我跟阿萍跟尾來好嗎?你還有約其他的什麽人?」馮氏把絨線放在一邊附和着嘯谷的意見去催促紫萍。
「有,全是大人物,他們都是來替阿萍捧塲的。」
馮氏喜不自勝,笑盈盈地說:「那末你應當先去招待他們才好。」
「好,我先去,你們等下到大同五樓來。」嘯谷說着卽披上大衣由後台匆匆步出,時紫萍亦已卸裝由屛風後出來,馮氏對她說:「你聽見嗎?嘯谷今晚約了許多大人物爲你捧塲,實在難得。」
紫萍走到化粧台前一梳頭一邊說:「媽!我不想去。」
馮氏疑訝地問:「爲什麼?」
「我今晚太疲倦了。」
「就是疲倦亦應當去一下,人家一塲盛意,不去那裏可以!」
「媽!我實在太疲倦不想去。」
「去呵!聽媽的話,爲自己的前途着想,一定要出去交際交際。」馮氏不待紫萍的囘答,卽拖着她的手,催促着她起行說:「去,去,大家一齊去。」
九 相見不認
任重在後台門外踱來踱去,焦急萬分,常常跑到門口,卽站定脚望入內去,子儀頗同情他的痴情陪伴他跑東跑西。
沒有幾久,果然紫萍隨在她媽的後面出來了!這一來,任重好像打進一枝興奮針一樣,全身都舒暢起來,忙趨上前叫:「阿靑!阿靑!」可是紫萍若無所聞地,把秋波向他輕輕一掃,任重看着葉慶沒有出聲,復叫:「阿靑,你……」正要說下去,紫萍急囘頭以極鎭定的態度問:「你找誰呵?」任重說:「你豈不是葉靑小姐嗎?」馮氏停住脚向任重努着嘴說:「你認錯人哪,誰不知她是大名鼎鼎的紫萍。甚末是葉靑。」卽携着紫萍的手繼續前進,任重無從再說,兩眼耿耿地望着紫萍,看見她上了一輛停在門外的汽車,「嗡」地一聲,徐徐地開去了!
任重和子儀呆立如木雞,望着車塵興嘆,任重問:
「你看她是不是阿靑?」
「又像又好像不像。」
「可是我明明認得是她,怎末不理我呢!」任重很失望地靠在牆邊發呆說:「給我一口煙。」子儀卽從烟盒裡抽出香煙給他,他遂掏出打火機燃點,繼而望着打火機出神,似乎是見物傷情。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當此時,驀地裡有一個神秘老人由轉灣處走出來口啣香煙向任重說:
「朋友!請你借個火給我?」
任重隨卽將打火機燃着替他引火,老人說:「謝謝」但並不走開望着任重出神,子儀看了甚以爲異,亦望着老人。俄而老人向任重問:
「朋友!你好像有什麽過不去的事,爲何這樣煩惱?」
任重看見這個老人對他那末關注,因未曾相識不便和他談話,只是呆呆地望着他。老人接着道:「你的事或者我可以帮忙你,我住在泰來酒店二〇二號房,你如果需要我帮忙,請你明天去找我。」說完揮手致敬,徐徐地跑去。子儀及任重更加莫明其妙,子儀說:「嗄!這個老伯父確實有點神秘。」任重忽有所得地說:「我一定去找他……泰來酒店二〇二號房……」
這個神秘老人姓葉名仲恆,就是紫萍的父親,以前因反對其妻馮氏將紫萍訓練爲伶人,夫婦因此意見相左,仲恆憤然離家,此後馮氏貫澈初衷將紫萍訓練成材,而仲恆於離家後隻身去上海埋頭苦幹,致力於商務,不幾年果然事業大有成就,想起他的妻女,亟望有機會携帶她囘上海團聚。這次他到香港來,對紫萍的事已打聽得淸淸楚楚,他亦知道任重愛着他的女兒,因恐對他所要進行的事有所妨碍;所以他未將他的眞姓名向任重說過。
十 密議合作
第二天,任重果然獨自到泰來酒店去找仲恆,仲恆甚爲歡喜,卽招待任重坐下,任重看見仲恆對他的事情十分關注,乃將他與葉靑認識的經過向仲恆詳細說明。
仲恆說:「我昨晚看你的情形,已知道你和葉靑一定有很大的關係,現在聽你的話,則我所推測的完全無錯。」
任重答:「照你這樣講,紫萍就是我所說的葉靑是不是?」
「不錯,就是她。」
「那末講,爲何昨晚她看見了我又不肯認呢?」
「你雖知道葉靑;但你還未知道她的身世,怪不得你這樣問……」仲恆思索半响說:「昨晚你看到和她一齊跑出來的那個婦人就是她的母親,那時她的母親亦做過戲,當她和葉仲恆結婚後對她的家庭生活極爲不滿,她認定她的女兒有做戲天才,要將她女兒訓練成一個名伶,爲了這件事,攪到她們夫妻反目,她的丈夫仲恆因此一氣之下,就此離開家庭,不料現在事隔十幾年,紫萍眞的紅了起來。」
任重道:「她雖然紅起來,但我想她未必覺得快樂,不然她那裡會兩次的出走呢!」
「她媽管束得甚嚴,除了做戲之外一點人生樂趣都沒有,那有快樂可言,我這次來這裡,就是爲了這件事。」
「什麼事呵?」
葉仲恆被任重問,不禁悲從中來,他怕給任重知道他就是紫萍的父親不但於事無補,反有妨碍,於是他極力抑住着他那受着刺激的情感,徐徐地說:
「葉仲恆自從離開她們母女之後就去上海,現在他在上海已經發達了,生活過得很好,時時掛念着他的女兒;所以托我到這裏來找她,仲恆曾向我講過,希望他的女兒趕快結婚,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仲恆還說:「如果能找到一個好像你這樣的好女婿,他老人家一定很滿意的,我想。」
任重很失望地答:「她竟然看見我好像不相識的,這叫我有什麽辦法?」
仲恆道:「我叫你來找我,就是想要同你合作,設法叫紫萍出來。」
「合作!怎樣合作?」
「我受了老友之托要設法帶他的女兒囘上海,你則想要與情人會面,我們彼此的目的相同,這樣我們最好是來合作,比較容易成功。不過我想,我們如果貿然去帶紫萍走,她的媽一定不肯,那個姓胡的又不是好人,一失手就要蝕大虧,所以我想只有靜靜地去帶她一同逃走。」
任重問:「可是我們那能見得到她?」
仲恆答「有辦法,我已査明她每天下午五點左右,一定去大都會理髮室梳頭,你到那邊去見她就不怕會碰到她的媽和那個姓胡的。
「她不肯認我有什麽辨法?」
「不會的,你卽管去試一試,我看她有心愛你,如果你和她約定,立刻來講給我聽,我馬上去買船票,一離開香港她就可自由了。」
任重聽着這個神秘老人的話覺得大有其理,遂决定照他的計劃去進行。
十一 同意偕逃
是日下午,未到五時,任重卽到大都會理髮室去,他坐在理髮椅上,讓理髮師替他剃鬚,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目的不在乎剃鬚,兩眼頻頻向前面的大鏡注視到門口去。
果然,給他有所發現了。胡嘯谷此時偕紫萍來到理髮室門外,嘯谷說:「六點我來接你好嗎?」紫萍答:「好呵。」隨由門口進入。任重一眼望見,如拾得珍寶一樣,喜而忘形,立即推開理髮師要站起身,理髮師愕然:「喂!先生,還未剃好。」可是任重置諸不理,披着白布直行到門前去迎接紫萍,笑微微地叫:「阿靑,阿靑!」紫萍他瞟了一眼說:「跟你講過我不是葉靑略!」任重下意識地說:「是,是你,我跟你講幾句話。」說着卽强拖紫萍進入電話室,把門關上,面對紫萍說:
「你不必再否認,我已經知道你的一切,亦已經明白你的身世。你爲什麼不肯見我,爲什麽不認自己是葉靑,我都曉得。」
「你旣然知道又何必來糾纏我呢?」
「自從你離開後,我非常的難過。」
「你可當此世未曾見過我就得了!」
「我不止見過你,而且愛上了你,叫我怎能忘記得了呢!」
「請你別再纏着我,你這樣太危險的呵。」
任重忽然厲聲問:「你是不是喜歡胡嘯谷?」
「我那會喜歡他,不過給他知道你來找我,他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如果你不是留戀着你的奢華生活,你應跟我一齊走!」
紫萍驚愕地問:「走!走到那兒去,我已經走過數次都難走過他們的手。」
任重態度轉爲溫和些,他說:「我帶你到上海去見你的爸爸好嗎?」
紫萍更加愕然,說:「我的爸爸!」
「是,你的爸爸現在上海已經發達了,他非常掛念你,已經派人來找你回去,你如果肯跟我走,我們可以一齊到上海去。」
紫萍遲疑莫决,任重補充着意見說:「阿靑,你同我一齊走吧!並此地多住一天,祗有加多你的痛苦。」
「但是我恐怕他不肯給我走?」
「我買定船票等候你,你可見機靜靜地偷走出來,一上了船,什麽事都沒有啦。」
「好啦!卽管試試。」
任重轉憂爲喜,拍着紫萍的肩胛說:「我定了船票馬上通知你……你,我怎樣通知你呀?」
紫萍思索一番答:「你由戲院後台那個守門的徐福通知我就可以,他是我的親信。」
「好,决定照這樣做。」
任重旣和紫萍約定了這件事,他連鬚都無心再剃下去,一走出電話室卽將白布脫下付錢給理髮師後,匆匆地離開理髮室。
十二 洩漏秘密
任重囘到家中,卽動手去收拾行李,準備出門,熊武夫婦及子儀都覺得任重的行動有些奇怪,對他的突然要離開此地,尤爲依依難捨。
子儀忍不住地問:「我們大家住了這末久,爲何一下就要走呢?」
任重一邊整理行裝一邊囘頭向子儀說:「我亦捨不得你們,不過這次非暫時離開你們不可,我想不久就會再囘來的。」
俄而任重携着行李要出門,小熊這個孩子怪有趣的,他以爲任重這次復是到省城去,囘來一定有很多的東西帶囘來,所以他無邪氣地挽住任重的手說:「叔叔,你囘來買什麼給我?」任重拍拍他的肩說:「啤仔,你乖乖地玩,我囘來買個大公仔給你玩。」時熊武夫婦已跑近前,任重說:
「大哥!大嫂!再見!」
「再見!祝你一路平安。」
子儀要替任重携行李出,任重向他道謝說:「不必了,我自拿好呵。」隨携行李步出熊武之家,大家向他揚手道別。
任重去後不久,子儀忽有所感,他向熊武說:「大哥,我想小任不是去上海。」
「爲怎麽你疑他不是去上海?」
「這幾個月來,他總是鬼鬼祟祟地那樣,我想他一定同表姑娘有什麽關係?」
「這亦算不定,葉靑這個女孩子不要講小任,就是我亦都中意……」熊武講了一半忽然想起他的太太在旁邊,知道失言趕快掩住口。
子儀說:「如果他眞的同葉靑走,那就太危險……」
熊武怔忡地說:「危險!」
「是呵,危險!胡嘯谷這個人不是好惹的,如果小任去撬他的牆脚,哼!要他的命都算不定!」
「那怎末好呵?」
「我們大家好像兄弟一般樣,應該帮助他才對。」
「怎末帮助法呢?」熊太太亦着急起來問。
子儀說:「我們暗中跟住小任,如果碰着他有什麽意外的事情發生我們就去帮他。」
熊武夫婦都同意子儀的建議,於是熊武與子儀遂興奮地跑出門去。
任重離開熊武的家後,立卽到泰來酒店去找葉仲恆,仲恆喜甚,遂將船票兩張交給任重叫他設法去通知紫萍,任重問:「幾時可以動身?」仲恆說:「最好是明天中午下船,你來得及通知她嗎?」任重答:「我今晚寫信交給人去通知她是不好。」仲恆說:「亦好,在碼頭的附近有間璇宮酒店,你明早去開間房,約她到那邊去和你見面,然後一齊落船就得了。」任重問:「那末你呢?」仲恆說:「我可以自su 下船去等你們。」
任重休息片時,卽取出信紙預備寫信通知紫萍。
是晚,約在戲院散場以前,任重來到後台門口,看見徐福在那邊守門,任重囘頭四望,當四週無人的時候慌慌張張地走近徐福的身邊叫:「福哥!請你替我交這張字條給紫萍。」徐福仰首一望,看見一個生面的人突然將一張紙交給他,甚爲詫異,不予之理,還是任重比較聰明,拿出一張鈔票遞給他,他才轉落笑容說:「可以,可以,我替你交給紫萍。」任重說:「千祈別給他人看見!」徐福笑着說:「可以,可以!」遂將字條拿進去,任重以爲大功吿成,抱着無限的欣慰囘到酒店去。
徐福冒冒失失地闖入後台化粧室,看着一個人正在對鏡梳頭,他以爲是紫萍,將字條揸在手中叫:「萍姑娘!」那個人回頭過來,嚇得徐福縮頭縮腦地想要走出去,原來那個人就是胡嘯谷。
嘯谷看見徐福鬼鬼祟祟的樣子,問:「你手中揸的是什麼?」徐福支吾答:「沒有,沒有。」嘯谷大聲喊:「行過來,給我看!」徐福不敢違命,惟有將字條交給嘯谷。嘯谷看過字後露着奸險的笑容,頓頓頭,將字條交還給徐福說:「你去門口等候她進來給她!但不可給她知道我已經看過。」徐福連聲應諾,待到紫萍拿戲服進入化粧室,才趕快將字條遞給她,紫萍以爲無人知道,偷偷地走入屛風後面去看字條所寫的是什麽?
十三 痛遭襲撃
一夜好容易過去了,任重這天的情緖特別緊張,他一早起來就到璇宮旅店去租房,時時刻刻地注意着鐘點,眞是坐臥不安,及至看到手錶已是十一點三十分的時候,他更加焦急起來,他担心紫會不萍會依約到來,頻頻向外望去。
同時在另一方面的紫萍,她想如何去掩飾這次的外出呢?經過一番的忖量,纔索性換了一襲旅行裝,手携籐籃從樓梯下來,時,馮氏正坐在沙發椅上織絨線,一見紫萍下來卽停住手問:
「阿萍!這樣早去那兒?」
紫萍芳心忐忑,佯作無事地答:「胡先生約我到沙田去旅行。」
「你已經睡夠了嗎?」
「是,睡夠了。」
「不要去得太晚,早點囘來。」
「你放心哪,同胡先生去我不會失場的。」
「是咯!你現在乖乖的聽媽的話,眞是好極。」
「媽!我現在去咯!」
現在再來說任重吧!任重看見中午已到而佳人芳踪仍杳,不勝焦急,正在房中踱着方步,忽聞敲門聲,他以爲是玉人如約而至,那知一開門却是一個好像僕毆的人進來,他問:「你是任先生嗎?」任重答:「是,有何要事?」僕毆說:「有位小姐找你,請你下樓去看她。」任重問:「在那兒?」僕毆說:「我帶你去吧!」
任重不知有詐,卽跟隨僕毆出了旅店,來到一條橫巷的路口,驀然跳出幾個彪形大漢,將任重痛毆一場,任重猛力掙扎企圖走避,當此時,熊武與子儀突然出現,如生龍活虎般將幾個流氓擊退,乃將他們幾日來暗中偷伺他的行踪,以防不測的事吿訴任重,並扶着他一同囘去。
這幾個流氓當然是受胡嘯谷所嗾使,嘯谷因偷看了那張字條,不出聲息,於任重約着紫萍的時間內分頭進行他的毒計,一方面嗾使流氓截擊任重,一方面自己駕車停在紫萍家的門外。他一看見紫萍出來,卽叫:「阿萍!你到那兒去?」紫萍大感驚駭,但力持鎮定微笑說:「我約幾個朋友去旅行咧。」嘯谷佯作不知地說:「來,我送你去。」紫萍說:「不必呵,沒有幾遠我行路去好啦。」說着卽大踏着步想要走去,可是嘯谷已有成竹在胸,他不管紫萍的肯與不肯,强拉着她的手擁入車門開車前進。
十四 駕車墮崖
胡嘯谷把車一直開到他的別墅去,强迫着紫萍入內,女傭阿四連忙把茶煙送出來,紫萍站在一邊說:
「我已約好了姊妹去旅行,你帶我來這裡幹嗎?」
「有事商量,請你坐低再講。」
紫萍無法可想,惟有坐落在沙發椅上,嘯谷遂笑着問:
「我問你,你喜歡這間屋嗎?」
「關我什麽事?」
「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可以送給你。」
「可是我沒有那末福氣。」
「眞的,這間屋是我預備跟你好結婚的,我帶你去裡面參觀參觀。」嘯谷復吩咐女傭說:「阿四!你去冲壺咖啡,預備一點東西來吃。」
嘯谷拖着紫萍的手進入一間書房,靜悄悄地將房門關起來,說:「這裡環境很好,我知道你好靜;所以選擇了這個地方,你歡喜嗎?」紫萍心急如箭,對嘯谷的話完全聽不入耳,嘯谷繼續說:「爲何這樣問,是不是掛住你的朋友,他是不會等你的,如果你要去旅行,我儘可以同你去。」紫萍厲聲說:「不可以,我要囘去!」說着卽翻身要走,却被嘯谷拉住說:「你囘去幹嗎?你今世不能夠再見到他了,而且現在已經過了鐘點。」
「怎末,你說我今世不能再見他!」紫萍大驚追問。
「他對我們太大胆,我眞不明白,你爲何愛着那個窮鬼。」
「你害死他,你這樣狠心!」
「這種人不給他一個利害那兒可以。」
紫萍頹然俯下沙發椅,登時大哭起來,嘯谷假慈悲地趨上前說:「阿萍,你何必這末傷心,你須知道我這樣做完全是爲着你呵,我愛你,就不能夠容許第二人亦愛你……」同時將紫萍擁抱起來,紫萍猛力掙扎,嘯谷如餓虎撲羊似地强要親她的吻,紫萍大聲呼喊,可是到底她是一個弱質女,子那能抵抗得住這個粗漢的强暴呢!結局是被他壓倒下去,當此千鈞一髮之際,突然聽見阿四敲門的聲音,嘯谷把手稍爲放鬆一下,紫萍乘機掙扎起來奪門而出,走到大門外,看見有輛汽車停在那邊,立卽登車開掣,嘯谷慌忙追出,恰巧與阿四撞個滿懷,跌下去,待到他爬起來追出時,紫萍的汽車已經飛馳而去了。
紫萍駕着車開足速度,不料因心慌意亂,兼駕駛術太過生硬,以致無法控制車身的向前猛進,由懸崖隨車墮下去,幸被附近的人救出;但她已負重傷不省人事了。
任重被熊武,子儀兩人扶到家裡,精神已漸漸恢復,子儀以綳帶與藥水替他縛住傷口,叫他休息一下,不久,葉仲恆帶徐福進來將紫萍開車墮崖,現在醫院的事向任重說過,任重悲傷不已,卽與仲恆趕到醫院去探視,仲恆的本來面目纔被馮氏拆穿,任重方纔知道這個神秘老人原來就是紫萍的父親。
紫萍受傷躺在病床上,據醫生云恐有殘廢之虞;雖任重愛之始終不渝,然收音機中正播出「長恨歌」一曲,使人不勝悲悼呢!
馮氏覺悟前非,欲與仲恆重修舊好,然仲恆於悲痛之餘,不顧而去。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