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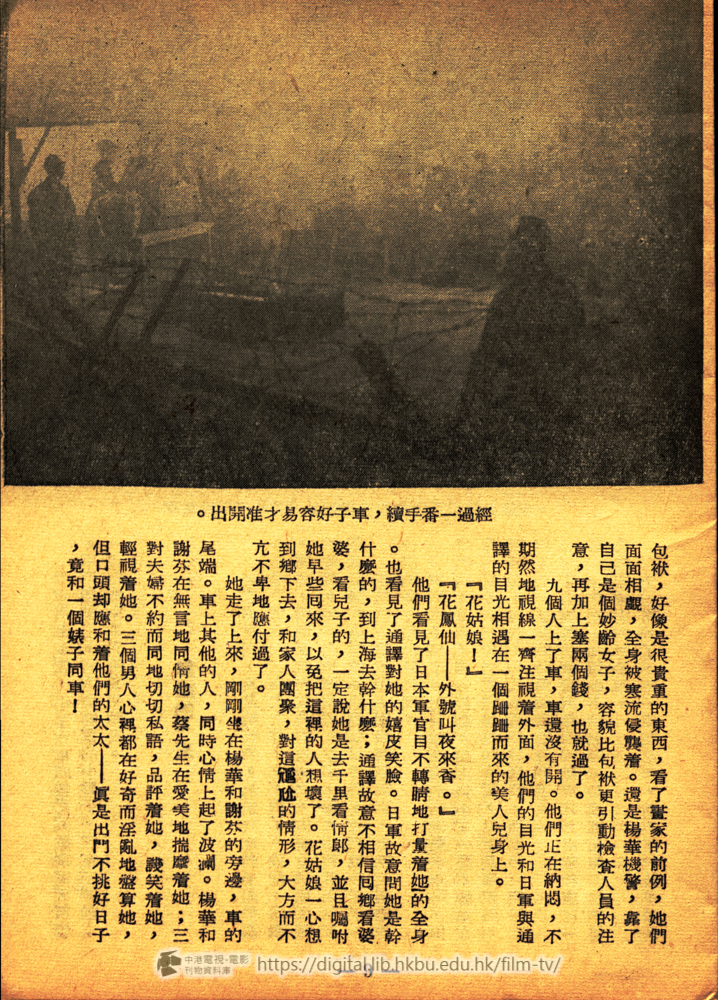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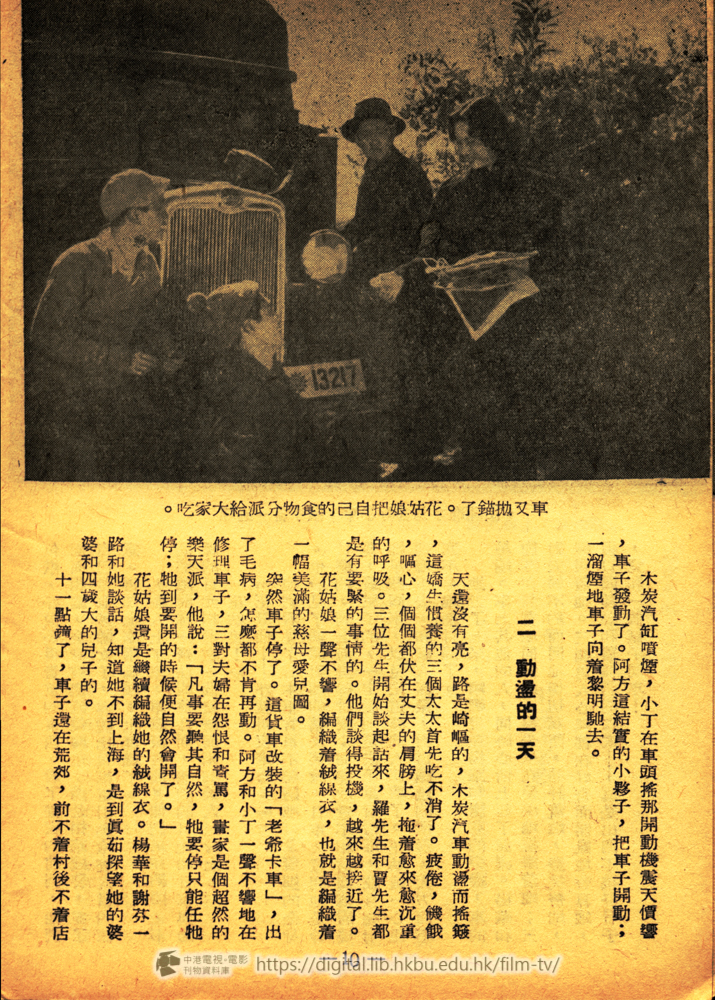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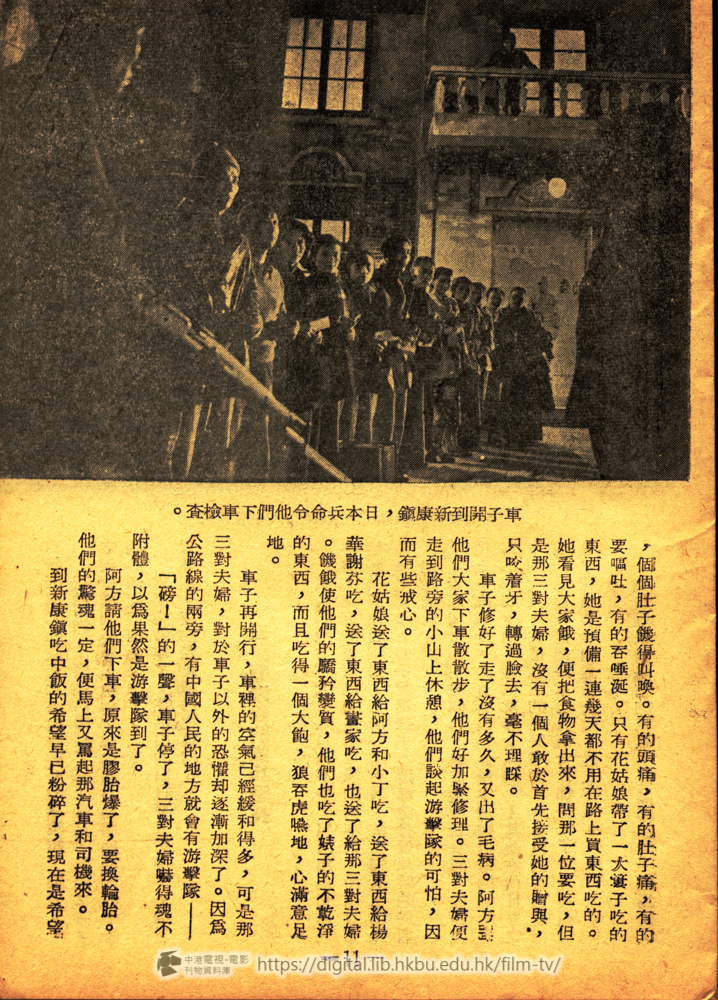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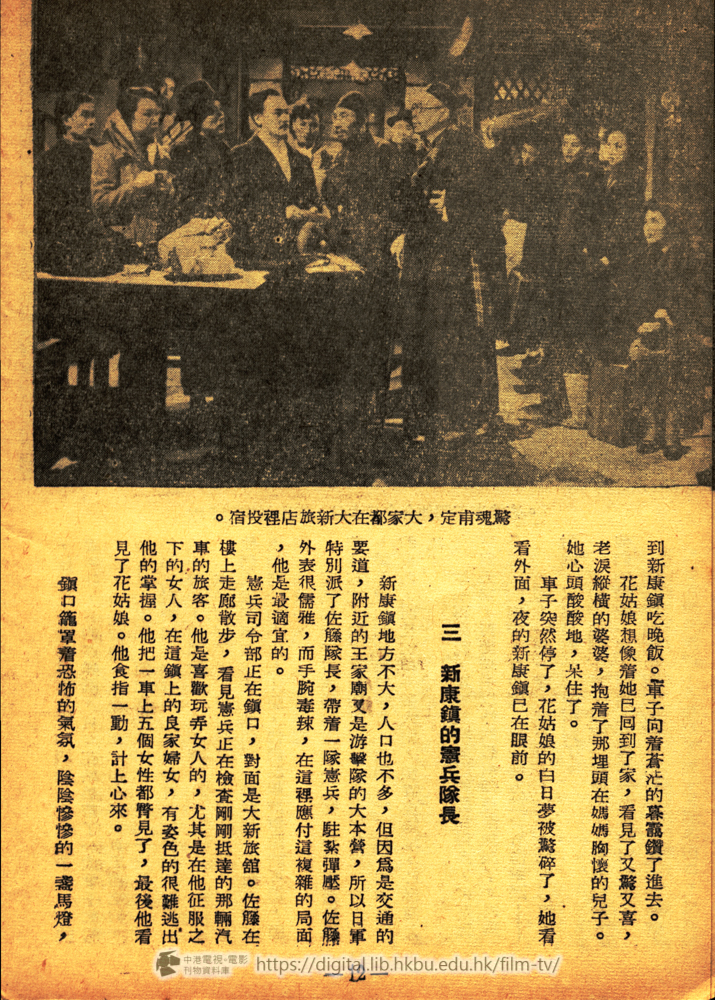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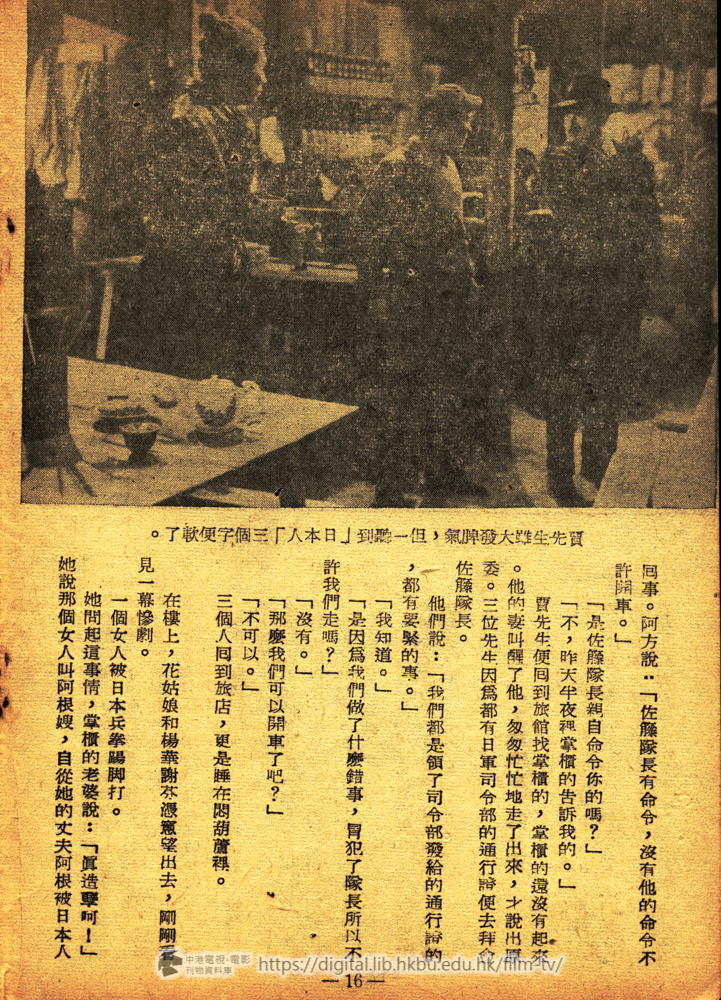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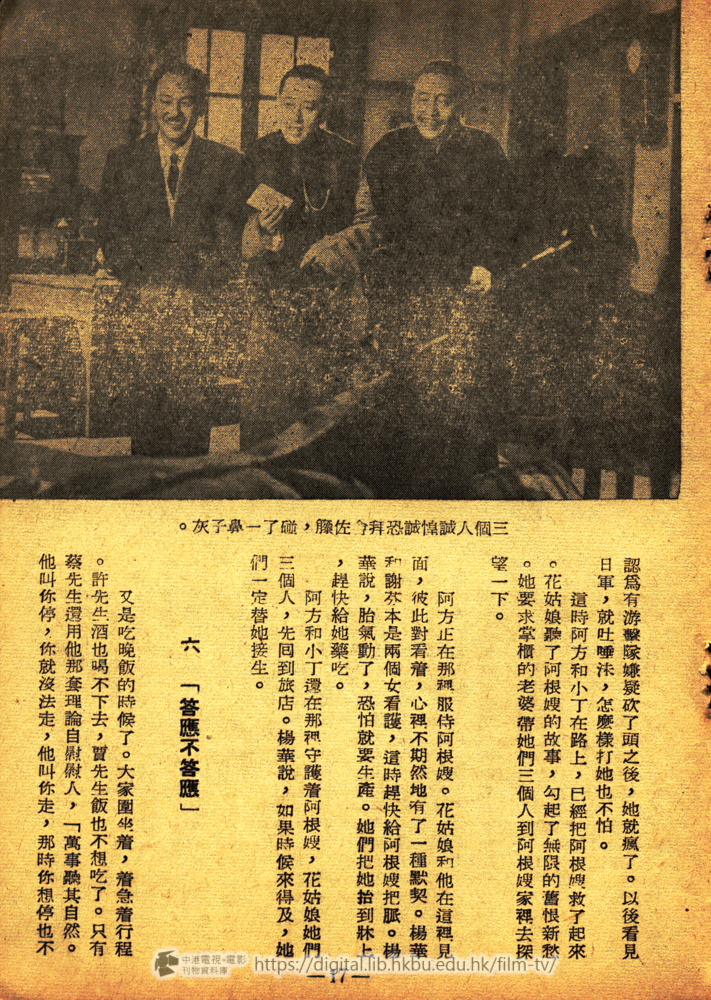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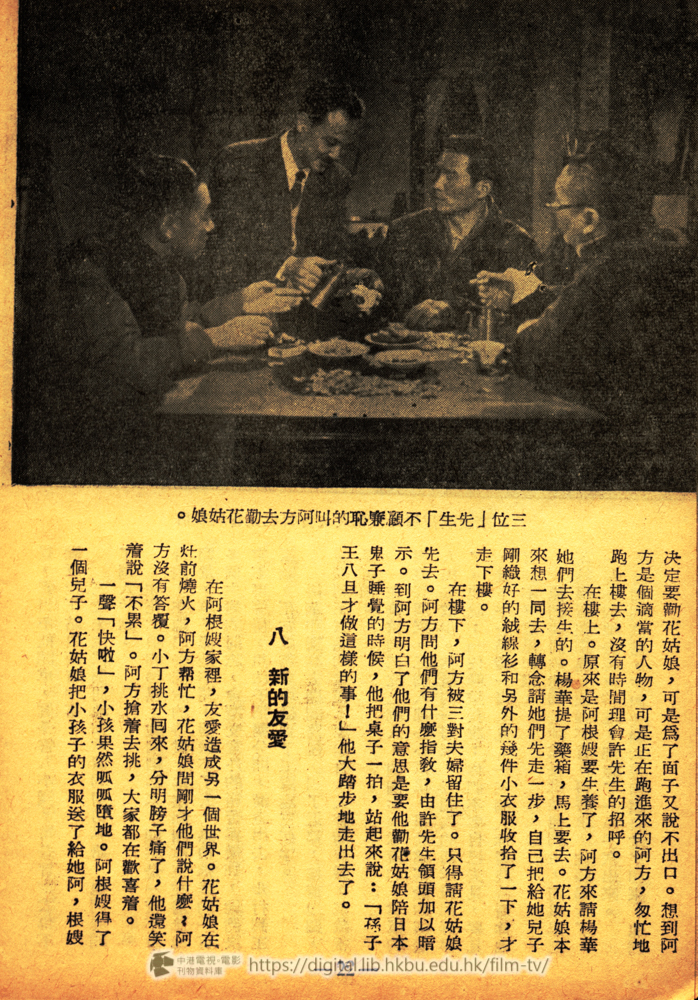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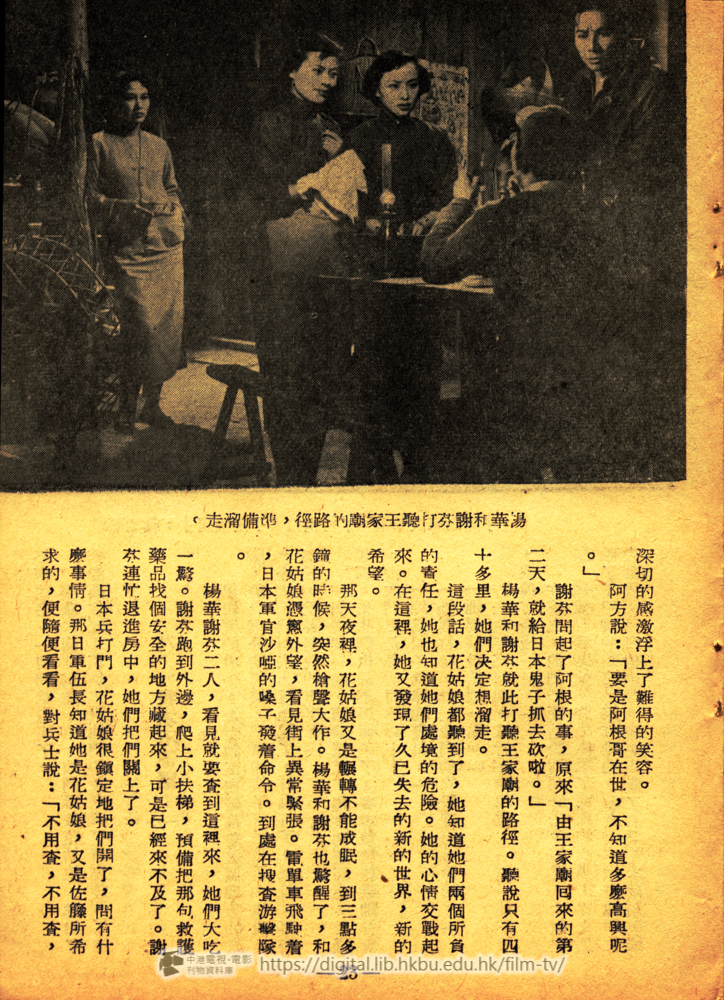








花姑娘 喬治.唐丹
一 黎明之前
深沉的夜,濃雲的後面慢慢地有了薄薄的光亮,,把遠山勾了一個淡淡的輪廓。
雄鷄開始了牠的啼聲。
W鎭的飽經戰爭剝蝕的破瓦殘垣,始終暴露着牠的愁眉苦臉,和那戰勝者的日軍的剌刀的光亮與馬靴的響聲相對,牠是一個襯托,一個諷剌,一個挑戰。
這破瓦殘垣間開始有了生氣,一個一個的黑影子走過,沙沙的脚步聲敲破着死樣的靜寂。男男女女的走到鎭口的汽車站來。在寧滬火車因為游擊隊的困擾和破壞以致於停頓了的時候,公共汽車是交通的主要工具:在汽油全由日軍分配用途的時候,木炭汽車是公共交通中的最現代的方法。這裡的一架木炭汽車,便是預備一直開到上海去的。司機阿方和他的助手小丁正在忙着燃燒木炭,攪動那機器。
一張小桌子擺在那裡,坐着的是日本軍官,檢査行旅的,站着的是一個通譯。他們依次地檢査旅客的証件和他們的行李。第一對夫婦是羅先生和羅太太,是殷實的米商,一方面呈騐了証件,一方面塞了錢給通譯,他們於是乎上了車。第二對是許先生和許太太,是本地的大地主。通譯也知道他是去找禇民誼參加「和平救國」的,對他很是客氣。第三對是賈先生和賈太太,是三井洋行的買辦。他們一方面說自己人,一方面塞了錢,人和行李便也安然通過。這三對上等人,都一團和氣地對着坐在那裡的日本軍官鞠了九十度角的躬。日本人動也沒有動。活動的是那個通譯,可是通譯和本軍官是一個東西的兩面,這是大都家心裡明白的一件事。
接着走過來的是蔡先生,他是一個畫家。他沒有那三對夫婦有錢,沒有他們有地位,可是他有點骨氣,對於日軍,他沒有謟笑,有意識地保留着大國國民的風度。他是畫西洋畫的,畫的是西洋裸體畫,除去了感官的直覺和美的意識以外,他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理。這次的行李檢査,是第一次使他脚踏實地來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日本人當他的傑作是商品,是玩意,是應該奉獻給征服者的玩意,於是把牠無條件地留下,畫家的囁嚅的抗議,禁不住日本軍官的呱喝和通譯的推聳,畫家只得凄然地和他的心血結晶——那裸體美女相別,結果,他必定多喝些酒。
跟着是兩個小姑娘,楊華和謝芬,都帶了小小的包袱,好像是很貴重的東西,看了畫家的前例,她們面面相覷,全身被寒流侵襲着。還是楊華機警,靠了自己是個妙齡女子,容貌比包袱更引動檢査人員的注意,再加上塞兩個餞,也就過了。
九個人上了車,車還沒有開。他們正在納悶,不期然地視線一齊注視着外面,他們的目光和日軍與通譯的目光相遇在一個跚跚而來的美人兒身上。
「花姑娘!」
「花鳳仙——外號叫夜來香。」
他們看見了日本軍官目不轉睛地打量着她的全身。也看見了通譯對她的嬉皮笑臉。日軍故意問她是幹什麼的,到上海去幹什麼;通譯故意不相信囘鄕看婆婆,看兒子的,一定說她是去千里看情郎,並且囑咐她早些冋來,以免把這裡的人想壞了。花姑娘一心想到鄕下去,和家人團聚,對這尷尬的情形,大方而不亢不卑地應付過了。
她走了上來,剛剛坐在楊華和謝芬的旁邊,車的尾端。車上其他的人,同時心情上起了波瀾。楊華和謝芬在無言地同情她,蔡先生在愛美地揣摩着她;三對夫婦不約而同地切切私語,品評着地,譏笑着她,輕視着她。三個男人心裡都在好奇而淫亂地盤算她,但口頭却應和着他們的太太——眞是出門不挑好日子,竟和一個婊子同車!
木炭汽缸噴煙,小丁在車頭搖那開動機震天價響,車子發動了。阿方這結實的小夥子,把車子開動;一溜煙地車子向着黎明馳去。
二 動盪的一天
天還沒有亮,路是崎嶇的,木炭汽車動盪而搖簸,這嬌生慣養的三個太太首先吃不消了。疲倦,饑餓,嘔心,個個都伏在丈夫的肩膀上,拖着愈來愈沉重的呼吸。三位先生開始談起話來,羅先生和賈先生都是有要緊的事情的。他們談得投機,越來越接近了。
花姑娘一聲不響,編織着絨線衣,也就是編織着一幅美滿附慈母愛兒圖。
突然車子停了。這貨車改裝的「老爺卡車」,出了毛病,怎麼都不肯再動。阿方和小丁一聲不響地在修理車子,三對夫婦在怨恨和責罵,畫家是個超然的樂天派,他說:「凡事要聽其自然,牠要停只能任牠停;牠到要開的時候便自然會開了。」
花姑娘還是繼續編織她的絨線衣。楊華和謝芬一路和她談話,知道她不到上海,是到眞茹探望她的婆婆和四歲大的兒子的。
十一點鐘了,車子還在荒郊,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個個肚子饑得叫喚。有的頭痛,有的肚子痛,有的要嘔吐,有的吞唾涎。只有花姑娘帶了一大簍子吃的東西,她是預備一連幾天都不用在路上買東西吃的。她看見大家餓,便把食物拿出來,問那一位要吃,但是那三對夫婦,沒有一個人敢於首先接受她的贈與,只咬着牙,轉過臉去,毫不理睬。
車子修好了走了沒有多久,又出了毛病。阿方請他們大家下車散散步,他們好加緊修理。三對夫婦便走到路旁的小山上休憩,他們談起游擊隊的可怕,因而有些戒心。
花姑娘送了東西給阿方和小丁吃,送了東西給楊華謝芬吃,送了東西給畫家吃,也送了給那三對夫婦。饑餓使他們的驕矜變質,他們也吃了婊子的不乾淨的東西,而且吃得一個大飽,狠吞虎嚥地,心滿意足地。
車子再開行,車裡的空氣已經緩和得多,可是那三對夫婦,對於車子以外的恐懼却逐漸加深了。因爲公路線的兩旁,有中國人民的地方就會有游擊隊——
「磅!」的一聲,車子停了,三對夫婦嚇得魂不附體,以爲果然是游擊隊到了。
阿方請他們下車,原來是膠胎爆了,要換輪胎。他們的驚魂一定,便馬上又罵起那汽車和司機來。
到新康鎭吃中飯的希望早已粉碎了,現在是希望到新康鎭吃晚飯。車子向着蒼茫的暮靄鑽了進去。
花姑娘想像着她已囘到了家,看見了又驚又喜,老淚縱横的婆婆,抱着了那埋頭在媽媽胸懷的兒子。她心頭酸酸地,呆住了。
車子突然停了,花姑娘的白日夢被驚碎了,她看看外面,夜的新康鎭已在眼前。
三 新康鎮的憲兵隊長
新康鎮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因爲是交通的要道,附近的王家廟又是游擊隊的大本營,所以日軍特別派了佐滕隊長,帶着一隊憲兵,駐紮彈壓。佐籐外表很儒雅,而手腕毒辣,在這裡應付這複雜的局面,他是最適宜的。
憲兵司令部正在鎮口,對面是大新旅舘。佐籐在樓上走廊散步,看見憲兵正在檢査剛剛抵達的那輛汽車的旅客。他是喜歡玩弄女人的,尤其是在他征服之下的女人,在這鎮上的良家婦女,有姿色的很難逃出他的掌握。他把一車上五個女性都瞥見了,最後他看見了花姑娘。他食指一動,計上心來。
鎮口籠罩着恐怖的氣氛,陰陰慘慘的一盞馬燈,凄凄厲厲的幾聲尖叫,日本兵命令他們下車排隊,以便檢査。隊長下了樓,逐一的看過了他們的身份。那三對上流夫婦,當然還是一樣地謟笑,而花姑娘則莊嚴得像一尊女神的石像。
檢査完了之後,由大新旅店的掌櫃歡迎他們進去。旅店雖小,可是在一天的饑餓與勞頓之後,特別是驚魂甫定之頃,總算是天堂了。那三對夫婦又把上流的氣派拿了出來。他們大方地說,大家同車共濟,總算患離之交,還是同桌吃飯,可以舉杯相慶。對於這個邀請,只有畫家蔡先生拒絶了,他要單獨吃飯喝酒,可以無束無拘。
旅館樓上只有四間客房。三對夫婦毎對一間,賸下的一間,楊華謝芬和花姑娘三位女客同住。蔡先生自願住在樓下,一個人可以無拘無束。
四 「請花姑娘去問話」
正在九個人坐下吃飯的時候,掌櫃的由外面跑囘來,問那一位是花姑娘,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掌櫃的說,佐籐隊長請過去問句話。
花姑娘本能地打了一個寒戰,她旋卽鎭定地說:「我不去。」
這一來可把同車來的人嚇壞了。掌櫃戰戰競競的說:「東洋人的事常常說不出道理,可是,不是鬧着玩的呀!」
賈先生誇張着皇軍命令的尊嚴,許先生說如果不去一定連累大家,羅先生更驚慌,勸她爲大家走一趟。太太們覺得那日本隊長,英俊而文雅,差不多以沒有叫到自己去爲可惜;有的以爲女客會依次叫去問話,自己好像在準備着什麼。她們異口同聲地勸花姑娘前往一行。楊華和謝芬面面相覷,沒有說什麼話,花姑娘看見大家的情形,只得隨掌櫃的前往一行。
蔡先生在提出爲什麼佐籐隊長叫花姑娘前去的疑問。
——因爲她生得漂亮吧?
——說不定有什麼嫌疑呢!
說到這裡,太太們不寒而慄,想起那種情形,把方才想被叫去問話的好奇心和熱情,大大地降低了。楊華和謝芬也緊張着,不過她們所盤算着的和那幾個太太不同而巳。
到了憲兵司令部,一直是冷酷和兇殺之氣,花姑娘莊嚴地走了上樓,掌櫃的報吿了之後便退了出來。花姑娘進了隊長室之後,那門便由一雙穿了馬靴的腿給帶上了。
同桌的八個人,猜測和疑慮使他們不安。蔡先生的酒也喝不下了。他們互相在推測,疑神疑鬼。正在這時候,花姑娘氣冲冲地囘來了,她一口氣走上樓梯想囘自己的房裡去。那三對夫婦追問着到底爲了什麽?
「反正不關你們的事。」花姑娘說着,扭轉身快速地走上樓去。
掌櫃的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囘事。他因爲夜晚十二點鐘戒嚴,所以勸大家早睡。三對夫婦但求不要影響自己,也就不再追問,便吩咐司機,明天早晨八點鐘開車,他們各自囘房休息了。
在花姑娘的房裡,楊華和謝芬安慰着她,她氣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充滿了眼淚和憤恨。
五 『不許開車』的一天
第二天早晨七點五十分。大家一齊走到車站,等着八點鐘開車,看見只有小丁一個人在車上打盹,阿方連影子都不見了。
賈先生好容易在小酒店找到了阿方,問他是怎麼囘事。阿方說:「佐籐隊長有命令,沒有他的命令不許開車。」
「是佐籐隊長親自命令你的嗎?」
「不,昨天半夜裡掌櫃的吿訴我的。」
賈先生便囘到旅館找掌櫃的,掌櫃的還沒有起來。他的妻叫醒了他,匆匆忙忙地走了出來,才說出原委。三位先生因爲都有日軍司令部的通行證便去拜會佐籐隊長。
他們說:「我們都是領了司令部發給的通行證的,都有要緊的事。」
「我知道。」
「是因爲我們做了什麽錯事,冒犯了隊長所以不許我們走嗎?」
「沒有。」
「那麽我們可以開車了吧?」
「不可以。」
三個人囘到放店,更是睡在悶胡蘆裡。
在樓上,花姑娘和楊華謝芬憑窻望出去,剛剛看見一幕慘劇。
一個女人被日本兵拳踢脚打。
她問起這事情,掌櫃的老婆說:「真造孽呵!」她說那個女人叫阿根嫂,自從她的丈夫阿根被日本人認爲有游擊隊嫌疑砍了頭之後,她就瘋了。以後看見日軍,就吐唾沬,怎麼樣打她也不怕。
這時阿方和小丁在路上,已經把阿根嫂救了起來。花姑娘聽了阿根嫂的故事,勾起了無限的舊恨新愁。她要求掌櫃的老婆帶她們三個人到阿根嫂家裡去探望一下。
阿方正在那裡服侍阿根嫂。花姑娘和他在這裡見面,彼此對看着,心裡不期然地有了一種默契。楊華和謝芬本是兩個女看護,這時趕快給阿根嫂把脈。楊華說,胎氣動了,恐怕就要生產。她們把她抬到牀上,趕快給她藥吃。
阿方和小丁還在那裡守護着阿根嫂,花姑娘她們三個人,先囘到旅店。楊華說,如果時候來得及,她們一定替她接生。
六 「答應不答應」
又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大家圍坐着,着急着行程。許先生酒也喝不下去,賈先生飯也不想吃了。只有蔡先生還用他那套理論自慰慰人,「萬事聽其自然。他叫你停,你就沒法走,他叫你走,那時你想停也不能停了。」
掌櫃的又來了。他說:「花小姐,佐籐隊長問你答應不答應?」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她的身上,花姑娘初初沒有作聲。掌櫃的說等着囘話,催她說句話,她才說:「我不答應!」
掌櫃的出去囘話了。這三對夫婦好奇和着急的情緖又沸騰了起來。
「到底要你答應什麼呀?」
「日本人的命令是不能違抗的呀!」
七嘴八舌地喋喋不休,幾個太太更是輪番進迫。花姑娘忍不住了,她說:「他要我答應什麼呀?他要我答應陪他睡覺!」
「AH!」的一聲,大家都驚訝着。太太們嘩然,連幾位崇拜日本的先生也談起愛國來了。許先生慷慨激昂地說了一套愛國的理論,結論是他要有個表示,他的表示是:他不滿意,他很不滿意!
羅先生也說這未免氣人。賈先生也斷定佐籐先生太不禮貌。
忽聽日軍皮鞋響,這幾位「愛國人士」便肅然站立,鞠着九十度角的躬,對着進來的日軍伍長,恭恭敬敬地等候他吩咐。
日軍找掌櫃的要囘話,掌櫃的再問花姑娘。「我不答應!」花姑娘說完便逕自上樓去了。
在樓上,花姑娘憑欄對着遠天,她點着了一枝香烟,噴出了縷縷幽怨。她腦子裡有着許多模糊的影子,風馳雲捲地飄忽過去,在她一用力思想的時候,那些影子都消失了——整個腦子成了一個空白。
楊華和謝芬深切地同情她的遭遇和她的態度,她們批評那些上等人的醜悪。她們說:不能受這欺負,這樣拒絕是對的。勸她不要難過。
「我不是難過」,花姑娘搖了搖頭。她說:「我恨,我恨日本鬼子,他是我們的仇人。今天那位阿根嫂你們看見了,可是我呢?⋯⋯」
她囘憶着她的過去,沉重地說:「我的家燒了光,爺爺死在火裡,妹妹被鬼子兵蹧踏以後發了瘋跳河死了。我丈夫也是因爲參加抗戰被他們砍了。剩下我跟奶奶,抱着沒滿月的孩子出來。四年了,從關外逃到關内,從北方走到南方,爲了養活我的孩子跟我奶奶,我⋯⋯我做了最下賤的事情。今天要讓我的仇人來蹧踏我,我寧死也不願意!」
她堅強的意志,發射出殉道者的光輝。在這人獸關頭,她是寧死不辱的。
茫茫的長夜,她反覆地想,往事如煙,一縷一縷地飄過,她恨!她恨透了!兇殘的敵人,懦弱的統治者,被宰割的老百姓,辛酸的日與夜,四年了,她這樣地度過了四年悠長的歲月,而這四年血淚的歲月便結成了恨,仇恨,對侵畧者的日本鬼子的仇恨。在目前,她沒有法子報這仇恨,她想死,用死來洗雪她的恥辱,並且控訴這仇恨。
七 各人的心事
第三天了。
許先生每天早晨一定打坐,打完坐,參湯也煑好了,這是他的功課,也是他那「太太」的公事。他着急了,恐怕去上海到得太遲,禇民誼答應他的那個稅務局長的肥缺落到別人手裡。他恨恨地說道:「這個女人真是害人精!」他想叫「太太」和花姑娘去談談,她說:「我才不高興去呢!要不,叫羅太太去說吧。」
在羅先生的房裡,羅先生正爲他答應山本的五百包米着急。要是交不出來,影響可真太大了。羅太太也在奇怪,這種女人爲什麼想不通,其實睡睡覺有什麼關係?何况她又本來是賣的!羅先生叫她去勸花姑娘,她說:「我才不高興去哪,要不,叫賈太太去」
賈先生的房間,正討論着那批軍火原料交易的驚人利潤。他們夫婦深恨花姑娘爲什麼不肯陪日本人睡覺,弄得不能開車,眞是害人不淺。可是賈太太也不願意找花姑娘談這件事。
三位先生都個別地和掌櫃的切切私語。他們展開了個人活動。
在花姑娘的房裡,她剛剛起來,顯然是一夜不曾合眼,在她出去洗臉的時候,楊華和謝芬正在着急地商量,車子總是不開,藥送不了去,恐怕那裡的一百多個生病的同志,會遭受意外的痛苦與犧牲,她們决定不再等待,想法子把藥分開,溜走出去,步行到王家廟。花姑娘無意中聽到了王家廟三個字。
楊華和謝芬去探問路徑,到了近郊,按着地圖,看通到王家廟的途徑。周圍日本人警衛森嚴,氣象很是可怕。
在旅館的三位上流人,個個在問掌櫃的。掌櫃的還沒有囘來。三個人都心心重重,很希望其餘的兩個人出去散步。掌櫃的一囘來,三個人的西洋鏡都拆穿了。他說:「佐籐隊長說:你們不要自己去見,要見,就下午一點鐘一齊去見。」三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他們共同的建議是請隊長批准他們走,而單單把花姑娘留在那裡。佐籐不肯。再要求,佐籐喝斥了。一個一個地去要求特准,都碰了一鼻子灰出來。
囘到旅館,三對夫婦六張嘴頓時忙了起來,他們决定要勸花姑娘,可是爲了面子又說不出口。想到阿方是個適當的人物,可是正在跑進來的阿方,匆忙地跑上樓去,沒有時間理會許先生的招呼。
在樓上。原來是阿根嫂要生養了,阿方來請楊華她們去接生的。楊華提了藥箱,馬上要去。花姑娘本來想一同去,轉念請她們先走一步,自己把給她兒子剛織好的絨線衫和另外的幾件小衣服收拾了一下,才走下樓。
在樓下,阿方被三對夫婦留住了。只得請花姑娘先去。阿方問他們有什麼指敎,由許先生領頭加以暗示。到阿方明白了他們的意思是要他勸花姑娘陪日本鬼子睡覺的時候,他把桌子一拍,站起來說:「孫子王八旦才做這樣的事!」他大踏步地走岀去了。
八 新的友愛
在阿根嫂家裡,友愛造成另一個世界。花姑娘在灶前燒火,阿方帮忙,花姑娘問剛才他們說什麽,阿方沒有答覆。小丁挑水囘來,分明膀子痛了,他還笑着說「不累」。阿方搶着去挑,大家都在歡喜着。
一聲「快啦」,小孩果然呱呱墮地。阿根嫂得了一個兒子。花姑娘把小孩子的衣服送了給她阿,根嫂深切的感激浮上了難得的笑容。
阿方說:「要是阿根哥在世,不知道多麽高興呢。」
謝芬問起了阿根的事,原來「由王家廟囘來的第二天,就給日本鬼子抓去砍啦。」
楊華和謝芬就此打聽王家廟的路徑。聽說只有四十多里,她們决定想溜走。
這段話,花姑娘都聽到了,她知道她們兩個所負的責任,她也知道她們處境的危險。她的心情交戰起來。在這裡,她又發現了久已失去的新的世界,新的希望。
那天夜裡,花姑娘又是輾轉不能成眠,到三點多鐘的時候,突然槍聲大作。楊華和謝芬也驚醒了,和花姑娘憑窻外望,看見街上異常緊張。電單車飛駛着,日本軍官沙啞的嗓子發着命令。到處在搜査游擊隊。
楊華謝芬二人,看見就要査到這裡來,她們大吃一驚。謝芬跑到外邊,爬上小扶梯,預備把那包救護藥品找個安全的地方藏起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謝芬連忙退進房中,她們把們關上了。
日本兵打門,花姑娘很鎭定地把們開了,問有什麼事情。那日軍伍長知道她是花姑娘,又是佐籐所希求的,便隨便看看,對兵士說:「不用査,不用査,好來西格。」他們就退走了。
楊華和謝芬驚魂才定,她們看着花姑娘,露出了感激與欽佩;花姑娘對她們的敬意與了解也加深了。
九 「我決不答應!」
第四天的中午,太太們正在談論着這個地方的危險,着急萬分的時候,掌櫃的挨了打囘來了。他說:「今天把我叫去,罵也罵了,打也打了。還說,再辦不好,就要封我的店了。」
三對夫婦一聽,事態嚴重,趕快圍着圓桌,計議起來。先生們也顧不得面子了,要乾乾脆脆勸她答應,太太們更是急切而熱心——
「她愛面子就捧她幾句。」
「她要打扮,就把我們的衣服首飾借給她。」
「她要錢就給她一點。」
許先生年高徳劭,成竹在胸地說:「萬一都不成,我還有最後一計。」
在樓上,他們把花姑娘請到許先生房裡,大獻慇懃,然後說教開始。許先生說了西施的故事,賈先生說了王昭君的故事,來打動她。羅太太不願意她的丈夫落後,示意他也說。羅先生說了名妓花木蘭陪美國軍宫大西瓜睡覺的故事。後來經過許賈兩先生的修正,花木蘭應做賽金花,大西瓜應做瓦徳西。至於美國軍官應做德國軍宫一點,羅先生提出了抗議。他說:
「美國軍宫和德國軍官還不是一樣的?」
這些愛國女傑的提出,目的無非是要花姑娘去陪日本鬼子睡覺,而花姑娘就偏不肯。
聽他們每個人都說了一套之後,花姑娘莊嚴地站了起來,她說:「對不住,我還有事,少陪了。」她要走出去,許先生把別人都送了出去,只留下她,做知心的談話。他首先聲明他之看花姑娘,和對自己女兒一樣,所以說的話出自至誠。他說,捨己爲人就是善。「你本來是幹這個的,就是睡不睡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是這麽一來,就把我們救了,這是行好事呵。」他馬上拿出錢來說:「這一點兒小意思,你收下吧,給小孩子買一點東西!」
正在這時候,掌櫃的又來問了:「佐藤隊長問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花小姐己經答應了」,許先生搶着囘答,也許他以爲花姑娘不好意思說出口所以由他代達,也許明知道花姑娘還沒有决定,他先說出來,希望花姑娘不好意思駁他,就此可以成功。
可是花姑娘却連忙站起來,鄭重地說:「慢着,我决不答應!」她頭也不囘,走囘她自己的房。
那三對夫婦可嘩然了,他們怪她去幫一個卑賤的瘋女人去接生,而不爲這些上流人打算打算,賣點面子。他們紛紛地嘲罵着,一個聲音比一個高。
「她不要弄得敬酒不吃吃罰酒!」
「她本來是賣的,有什麼了不起?」
「下流坯子,天生的賤骨頭!」
花姑娘在房裡聽着這些剌耳的話,她突然把門打開,他們倒都弄得瞠目結舌了。她一氣下了樓,走出去了。
賈先生目送着她,狠狠地說,「我恨不得把她連手帶脚用繩子綁了,送到隊長那裡去!」
十 新的顯示、新的决定
花姑娘到了阿根嫂家裡,不期然她在窻戶外邊聽到了楊華謝芬和阿根嫂的談話。
楊華和謝芬向阿根嫂要兩套舊衣服,她們想乘黑夜跑到王家廟。阿根嫂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你們也——」楊華把這次重大的任務吿訴了她,「帶了特效藥去救一百多個同志的命,在這裡已經躭誤了三天,不能不冒險地趕去。」
阿根嫂感動得流淚,她說:「日本鬼子査得很緊,你們路上可要小心呵!」
花姑娘聽到這裡,便自己走開了。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河邊,憑樹遐思,對水感懷,想起了恩和怨,記起了愛和恨,想到破碎的河山,念着苦難的健旅,想着楊華和謝芬的可能危險,想着那一百多英勇的戰士可能的犧牲,她的心劇烈地跳着,她的血沸騰着。
「彭!」一塊石子抛到了河中,激起無數的漣漪。爲了祖國的得救,爲了無數好漢的生命,個人榮辱的生死算得什麼!花姑娘作了一個决定。
這時楊華和謝芬已經結束停當,一個人帶一半藥,由兩條路線分別前去。萬一有一個犧牲了,還有一半的藥品可以到達。
她們和阿根嫂吿別。阿根嫂只是說:「你們要快點囘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呀!」
花姑娘在路上碰見阿方,問阿方「爲了許多的好人,犧牲自己,是不是對的?」阿方摸不淸頭腦,他說「那些上流人並不是好人。」
「我說的不是他們,是眞正的好人。」
「那麼爲他們犧牲是値得的。」
花姑娘的假設得了一個肯定。她毅然地走到阿根嫂家,想阻止場華謝芬冒險的行動。使她失望和焦急的,是她們已經走了,阿根嫂也不肯說她們是到那裡去。
花姑娘追到了鎮口,希望把她們追囘來。楊華和謝芬已經溜到叢林深處,預備向王家廟進發。可是鬼子兵守衞森嚴,接連開槍,她們無法前進,只得退了囘來。
花姑娘聽到了槍聲,非常着急。後來看見兩個飛奔的影子進了阿根嫂的家裡,她才放了心,經過戒了嚴的街道,囘到了旅館。
十一 「花姑娘答應了!」
旅館裡充滿了怨天怨地的聲音和對於花姑娘的詛咒。花姑娘更不答話,昂着頭一直走上樓去。
日本伍長又來討囘話,同時準備封店。
三對夫婦個個愁眉苦臉,掌櫃的更是進退兩難。他明知再問也沒有用,但他的老婆無論如何,勸他對花姑娘再去求情。
在樓上,掌櫃的並沒有求情,他只報吿了伍長來聽囘話的事。他沒有聽見什麼聲音,但是他臉上的表情有了激劇的變化。他岀其不意地微笑了,連蹦帶跳地下了樓。他吿訴他們大家說:「花姑娘答應了!」
對這些上流人,這是一個大的喜訊。於是先生們在樓下喝酒,太太們送了衣服首飾到花姑娘房裡替她打扮。
本來漂亮的花姑娘,經過了艷裝濃抹,更能勾魂奪魄。但是她木然地由她們擺佈,一點表情也沒有。他挺直着胸脯,走下樓來。先生們作揖打恭地歡送她。她們目送着她走出了旅館門口,畧一振作,鎭靜而莊嚴地走上日本憲兵司令部的樓梯。
又是那樣地進了隊長室,又是一隻穿着馬靴的腿把門關上了。
花姑娘凛然地說:必須等到她的朋友都走了,她才肯從。這本來出乎佐籐的意外,而且他本可以用强,但是佐籐手腕向來漂亮,他又相信已經到了手的小鳥是不怕她飛去的。他很大方地答應了她,明天早晨八點准他們開車。他和花姑娘的好事,也只有再延一日。
在旅館裡,三對夫婦因爲爭功發生了內閧。太太們更是各不相下,彼此攻訐陰私。正在要打起來的時候,花姑娘之出其不意的囘來給她們解了圍。
三對夫妻以爲花姑娘又變了卦,紛紛質問。花姑娘更不則聲,看着他們。直到掌櫃的前來宣佈明天早晨八點鐘開車,大家才又恢復興高釆烈的狀態。
阿方聽說開車,想必花姑娘已經屈服,他上樓去質問她,不該爲了這些王八旦,蹧踏自己。
花姑娘平靜得和止水一樣,她說:「你不用問。我請你相信,我决不做對不起我自己的事情。以後你自然會明白。最要緊的就是你們明天早晨快些通過最後一個閘口,而且你要照料楊小姐和謝小姐,把她們送到王家廟。」
阿方有些明白了,一方面是欽敬她,一方面爲她可惜。花姑娘說:「我會處理我自己。這行李請你照址交給我的老奶奶和兒子,並且請你照應他們。」
三位太太曉得不會再變卦了,便來討囘她們方才自己送來衣服和首飾。花姑娘不動聲色地一一還給了她們,她沒有一點表示,這三個太太彼此相覷,倒不免有些不安之感了。
十二 花姑娘一個人倒了下去——
第五天一大早,車子早已預備好了。他們都坐的是老位子。只是花姑娘的位子却空在那裡。楊華和謝芬問花姑娘爲什麼不上車,她們很爲她難過,而且依依不捨。
「你們先走吧,我過幾天就來。」花姑娘英勇地微笑着安慰着,鎭定着她們。
日本兵的剌刀把她們分開,車子風馳雲捲地開出了鎮口。花姑娘看着車子越來越遠,她莞爾地感到高度的快慰。她堅毅地轉過身來,向着日本憲兵司令部走去。那些日軍爲她的崇高的精神所震懾,好像無可如何地隨着她走去。
到了樓上,佐籐還沒有囘來。花姑娘寧靜地坐在那裡,看見掛鐘,預算卡車已經通過了最後的關閘。
車子過了最後的關閘,阿方小丁和楊華謝芬很高興,他們打算看以後的事。那三對夫婦也很高興,他們批評着花姑娘假正經,這樣顯得他們是上流人,是要人了。
佐籐囘來了,他發現的是一個滿腔仇恨,滿眼敵意的花姑娘,不向敵人低頭,永遠不被征服的花姑娘。她乘他不備,抽出了剌刀,剌傷佐籐。
並且當這時候,阿方和小丁騙說車子抛錨,把三對夫婦和畫家拋在路上,他們加高速度地把楊華謝芬送去王家廟。
這裡花姑娘已經倒在血泊中,她瞑目了,那索取敵人鮮血的那把刀還緊握在她手中。
這裡,楊華和謝芬已經上了山,向王家廟進發。阿方揮着手說,「我們也快來了。」
花姑娘一個人倒下去了,王家廟多數的好人站了起來。他們是有着共同的靈魂的,不朽的不敗的中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