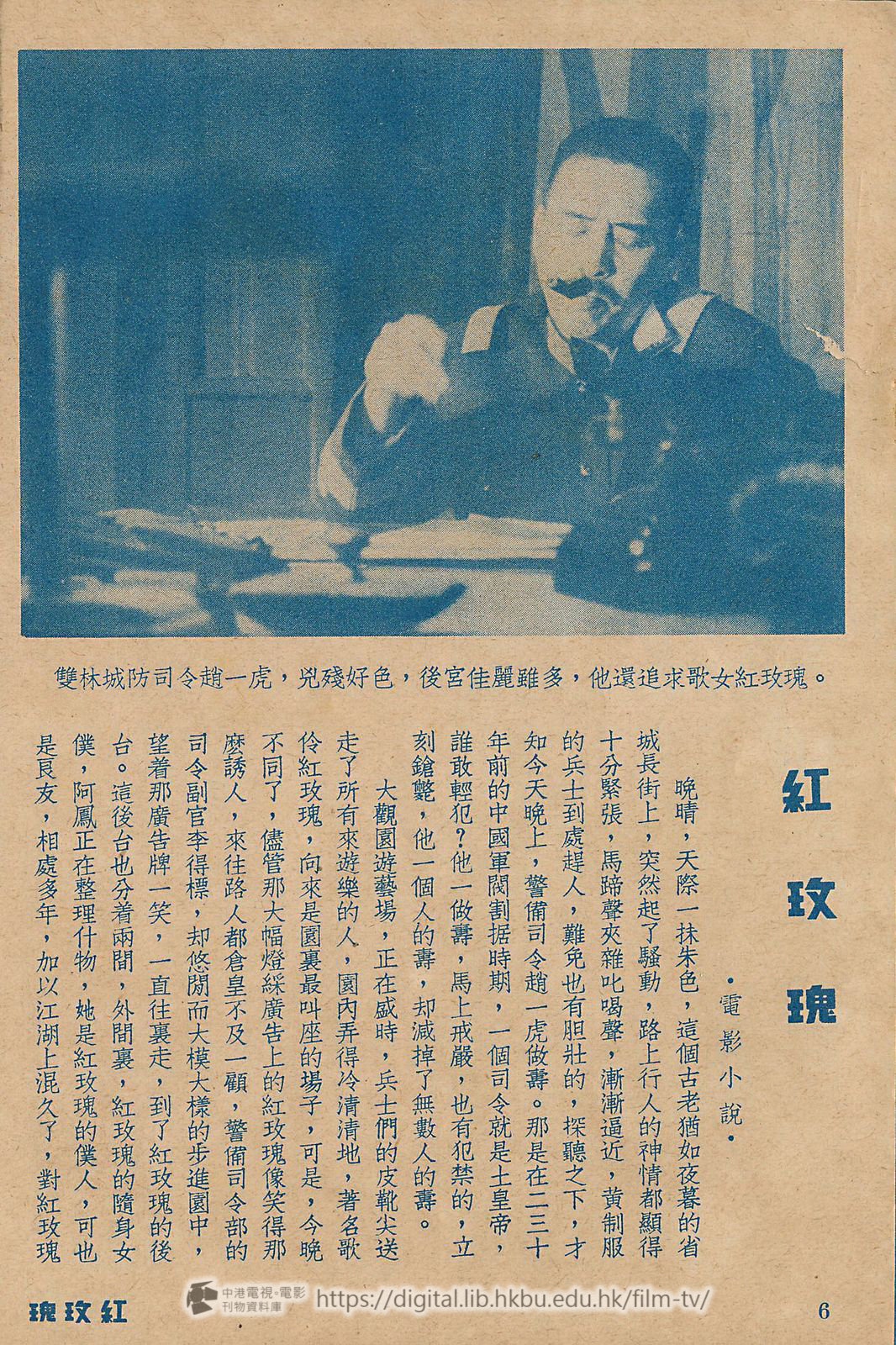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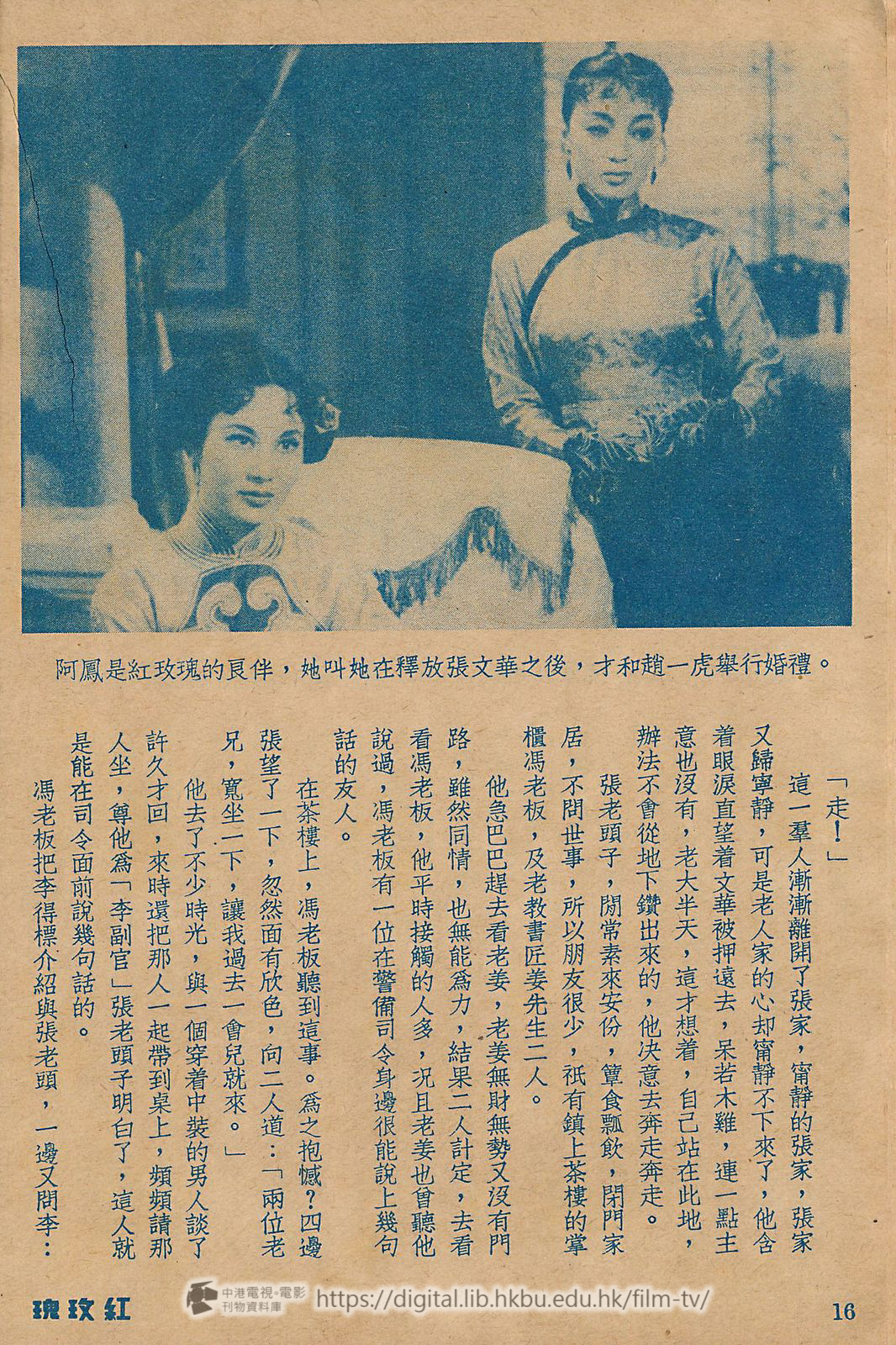
















紅玫瑰
.電影小說.
晚晴,天際一抹朱色,這個古老猶如夜暮的省城長 街上,突然起了騷動,路上行人的神情都顯得十分緊張,馬蹄聲夾雜叱喝聲,漸漸逼近,黄制服的兵士到處趕人,難免也有胆壯的,探聽之下,才知今天晚上,警備司令趙一虎做壽。那是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國軍閥割据時期,一個司令就是土皇帝,誰敢輕犯?他一做壽,馬上戒嚴,也有犯禁的,立刻鎗斃,他一個人的壽,却減掉了無數人的壽。
大觀園遊藝場,正在盛時,兵士們的皮靴尖送走了所有來 遊樂的人,園內弄得冷清清地,著名歌伶紅玫瑰,向來是園裏最叫座的場子,可是,今晚不同了,儘管那大幅燈綵廣告上的紅玫瑰像笑得那麽誘人,來往路人都倉皇不及一顧,警備司令部的司令副官李得標,却悠閒而大模大樣的步進園中,望着那廣告牌一笑,一直往裏走,到了紅玫瑰的後台。這後台也分着兩間,外間裏,紅玫瑰的隨身女僕,阿鳳正在整理什物,她是紅玫瑰的僕人,可也是良友,相處多年,加以江湖上混久了,對紅玫瑰旣如家人,又如導師,一向紅玫瑰把她當作靈魂。
李得標對那個俏傭人,一向存心不良,見阿鳳就 難以自制的色迷迷一笑,阿鳳不理,李得標這才說到正題:
「你們老板呢?」
「在裏邊呢!」阿鳳淡淡地回了一句,李得標把皮靴踏得鎮天價響,大踏步的走進紅玫瑰的化粧室。
紅玫瑰正悵然坐着,李得標諂媚的一笑:
「紅姑娘你準備好沒有?司令讓我接你啦!」
「你坐會兒,讓我換件衣服,咱們就走。小秃子,給李副官倒茶!」紅玫瑰映在窗外透進的落霞餘輝中, 更覺如麗釆春葩,李副官跌入綺思中,那伺候紅玫瑰的小廝叫小秃,土裏土氣的,戰兢兢替「李老爺」送上了茶。
紅玫瑰把衣服 換好,想起了剛才趕客人的事,正想問,恰值李得標敷衍討好,問起上座情形,紅玫瑰嘆口氣道:
「座兒?别提了,剛上座,就 來了幫弟兄,把客人都趕走了,司令做生日,何必要這末緊張?爲什麽不讓老百姓也痛快痛快玩一宵呢?」
李得標心想:「這姑 娘也真是,什麽叫官?什麽叫百姓?她怎麽連這點都不懂?」可是她是司令的寵室,不敢頂撞,祗說:「車在門口呢,咱們走罷。」
司令部的門口掛滿了燈綵,汽車停成了一條長龍,男男女女錦衣金飾相擁魚貫而入,李得標先下了車,扶住紅玫瑰,衞兵們站得畢恭 畢正,把李得標與紅玫瑰迎了進去,門口有看見紅玫瑰的,投以驚羨的一瞥,又爲她的美麗迷惑。
趙一虎,那形似虎霸心比狐詐 的城防司令,這時正在內室陪同十餘位他目中的貴賓,打牌消遺,也有横榻供貴賓們吞雲吐霧吸食大煙,那一羣剝榨百姓的傢伙,個個都露着笑容,趙一虎呢?雖然笑着,可是心裏的心事難把笑容掩沒,他惦念着一個人——紅玫瑰——千方百計弄不上手的小綿羊。
丁祕書進來了,一虎的神情立現緊張之色,在丁祕書附耳告訴他「紅玫瑰已來了」時,緊張神色又變成興奮。
紅玫瑰真的來了, 她在那個大廳的衆貴賓注目下款款步入,竟然也有拍手叫好得意忘形的,丁祕書傳達了趙司令的主意:「紅姑娘請到東邊屋裏去坐。」
紅玫瑰沒好氣,她向李得標裝作那麽一笑道:
「李副官,讓我們在這兒看一會戲,成嗎?」
「行,行。」那有不行 的道理?李得標趕忙叫僕人們取椅子給紅玫瑰擺下那最好的座位。
趙一虎終于見着了紅玫瑰,他帶她到小屋子裏去,貴賓們也跟 着來瞧她,一虎與紅玫瑰的事,早已在那省城中傳騰衆口。
在小屋裏,趙司令像個小丑了,他堅要紅玫瑰喝酒,可是紅玫瑰却心 不在焉的加以拒絶了,她的話說得可真動聽,她說:「司令!我不能喝,以前有過這種經驗,喝了酒就難受,你能不能原諒我,今天剛有點不舒服呢?」
這晚,紅玫瑰雖給鬧到很晚才回去,可是,也給趙一虎看出了她神情不安,急于要回去的樣子,狡詐的一虎,心 裏明白了幾分,他之所以拿不到她的心,拿不到她的人,中間有個第三者横梗着,她的一切都被那第三者拿走了。
他在紅玫瑰走 了以後,就召進李副官得標,叫他留意紅玫瑰的行蹤,李得標卑鄙的笑了笑道:
「說起來也真巧,剛才從東門外坐洋車回來,聽 那車夫說起,他今天做了一筆好生意。我一聽,就注意他的話,我拿話去探聽他,問是什麽生意呢?他說他拉着了紅玫瑰,到鐵佛寺去進香,拿着了十塊錢,我就問他有什麽人同紅玫瑰在一起呢?他就說了說……」
「說什麽?一虎跳起來。」
「他說是一個年青的小夥子,看去好像是一個學生,也坐着一輛洋車,可是那拉車的不認識那個年青的是誰,看他們的樣子,已經很親嫟,一路上有說有笑的。」
趙一虎抓抓頭摸摸耳朵,半响才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
「李得標!」
「是!」
「你着意的打聽那小子是誰,愈快愈好,知道嗎?」
「是!」
李得標鞠躬敬禮唯唯而退。
趙一虎的心裏可就起了個大疙瘩, 心想:「也有這吃了熊心豹胆的敢來太歲頭上動土?」
李得標急于完成使命,一路趕到大觀園,坐在歌場一隅,暗中注意各在座 聽歌的人,眼鋒飛來飛去,飛到了正從後台走出來的小秃子臉上。
小秃子鬼鬼祟祟的,得標看準他走的方向,好像是要到自己那 邊,可又不敢,乃佯作假寐,留着半個眼睛看住他的行蹤,果然,小秃子偷偷地走過李的身邊,交給離李座三四位遠的一個青年,那人看完,就揑作一團丟在地上,得標把鞋尖兒踢過紙團,而後乘那人看戲緊張時拾起來,離了座,抬頭見趙司令已在包廂裏了。
李得 標把那張紙條給了趙一虎,他打開看時,又注意李得標所注意的那個人,眉目清秀,大方端壯,才三十上下年紀,他更妒了,紙條上寫的是:「文華,明八時,原處會晤,至盼勿誤 紅」。
他眉頭一縐,立刻改了笑容,走進後台去。
紅玫瑰一見就站起來讓座道:「嗄,五爺,這末晚打那兒來?」
「開緊急會議,開完了會,我看時候還早,所以上這兒看戲來,看看你,玫瑰啊,方才 那戲可編得真好!」
「瞧你,又在捧我啦,五爺你這兒坐!」
趙一虎假作想起了什麽事:「玫瑰,我想起來啦,明兒上午我請客,咱們上鳳凰林吃素齋去,換換口味好嗎?」
「上午?幾點哪?」紅玫瑰的心有點不正常的跳動。
「八點,到那邊得九點多,咱們玩到個下午四時回來怎麽樣?」一虎若無其事的偷窺她表情。
「這……五爺,你得原諒我,我起不來呀,下午成 不成?」
「下午我沒空,旣這末着,過兩天再說吧!」
「好的,你真可憐我?」
「我不可憐你,我還能可憐誰麽 ?」一虎口中這麽說,心裏却想:「你那個人却真該可憐的日子近了。」
乖覺的阿鳳,漸覺趙一虎這幾天的神色不如往昔,於是 向紅玫瑰提出一點警告,要她小心,别把她與張文華的事被那魔鬼發現,紅玫瑰與張文華的戀愛進行,是賊一樣的,祕密得連張文華的父親都不知道,她安慰阿鳳:
「這個你放心,除了你跟小秃子兩個,連張先生的爸爸都不曉得我們的事。反正日子也沒有多久了, 我這一期合同一滿,我們就跟張先生離開這裏了。」
阿鳳的猜疑一點沒錯,趙一虎一回家就反覆硏究這紙條,那些狐羣狗黨李得 標,丁祕書,都在。
趙一虎思慮有頃,喃喃自言道:
「這個字跡我認識是紅玫瑰寫的,奇怪,他們怎末會認識的,照這字條上看,好像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這末着,李得標!」
「是!」
「明天你得把這件事弄清楚啦,他們到底是什麽關係?」趙一虎眉頭的結更深了。
李得標諾諾連聲退了出去,一虎與丁祕書,在雪茄的煙霧中,想出了搶過紅玫瑰心來的計劃。
李得標在清晨七時多已埋伏在鐵佛寺前的隱伏處,梵音鐘聲,和尙們已開始上早課了,李得標見紅玫瑰從遠處而來,在又一角,張文華也與她對面而至,正好,停留在李得標躲藏處,見他們兩人並肩走着,呢喃而語,紅玫瑰的聲音非常輕,但生成兔子似耳朵,也被他聽了去,約隱聽到紅玫瑰向張文華道:
「文華,我希望你,還是趁這幾天,跟你爸爸說明了我們倆的事吧!因爲我的職業地位不怎麽好 聽,要是臨時再跟老人家說,萬一他要是不贊成,不是麻煩嗎?」
「玫瑰,你不要担心這個問題,我相信我父親不會反對的,我 不願意預先告訴他,是爲了我們的環境關係,我怕他老人家,有時候喝了幾杯,太過興奮,會不留神說了出去,倒不如等你合同期滿以後,我再告訴他老人家去。」
兩人當然不會知道這樹,這石山,會張上了眼睛鼻子,在興奮時,情不自禁的互相擁吻起來,李得標 暗暗妒忌張文華,心裏也跟着一陣冷笑。
這一天,張文華有了滔天大禍。
那是張文華在小學中教完書後回來批閲學生們的卷子的時候,張老太爺悠閒地一手執卷,看來津津入味,突然像晴空中起了雷,皮靴與擂門的聲音立時大發。
文華向來不作壞事 ,坦然把門開了,進來的却是一小隊的兵士,一見文華就喝止他「不許動!」又斜睨他一眼道:
「幹什麽的?」
「我姓張叫張文華,在此地小學裏教書的。」
文華正正直直的告訴了他,那人又指着張老太爺道:「他呢?」
「他是我父親,噯究竟有什麽事嗎?」
「有人報密,說你們私販軍火!」來人臉色一沉又復唸一遍「私販軍火!」
老太爺急了,他吶呐的道:「這簡直是胡說,我們住了這許多年,誰都知道我們是老老實實的人家。」
「這不能憑你自己說,那一個人不說自己是好人?來 啊,搜査!」一羣兵士分了三四處搜査,有一個乘着衆人不備把懷裏一個小包拿出放在櫃中,然後當文華等注意的時候,把它拿了出來,那個隊長親自査看,這是兩把盒子鎗,這才使文華父子着急起來,一時都呆住了。
那個隊長身份的就哼了一聲道:「這看你們還 有什麽話說啊!」就走上前一連打了文華幾個耳刮子,又命令爪牙:
「把他們帶走。」
文華莫明其妙的挨了打,心中是憤火中燒,可是爲了自己,爲了玫瑰,也爲了年老的父親,他不敢發作,要求的口吻,請他們祇帶自己,别把父親也帶進去。
來人 說了聲「這個……」好像思索甚苦,半天才道:「也好,看他這末大的一把年紀了,就把他一個人帶走,那老頭兒别帶進去了。」
一羣人簇擁着手無寸鐵的良民張文華走出了大門,滿頭霜白的老人不免老淚縱横,他拉着那隊長身份的道:
「你…你們是什麽衙門的?」
那人不耐煩地摔開他的手,隨口答了一聲「警備司令部」說畢就推文華道:
「走!」
這一羣人漸漸離開 了張家,甯靜的張家,張家又歸寧靜,可是老人家的心却甯靜不下來了,他含着眼涙直望着文華被押遠去,呆若木雞,連一點主意也沒有,老大半天,這才想着,自己站在此地,辦法不會從地下鑽出來的,他决意去奔走奔走。
張老頭子,閒常素來安份,簟食瓢飲, 閉門家居,不問世事,所以朋友很少,祇有鎮上茶樓的掌櫃馮老板,及老教書匠姜先生二人。
他急巴巴趕去看老姜,老姜無財無 勢又沒有門路,雖然同情,也無能爲力,結果二人計定,去看看馮老板,他平時接觸的人多,况且老姜也曾聽他說過,馮老板有一位在警備司令身邊很能說上幾句話的友人。
在茶樓上,馮老板聽到這事。爲之抱憾?四邊張望了一下,忽然面有欣色,向二人道:「兩 位老兄,寬坐一下,讓我過去一會兒就來。」
他去了不少時光,與一個穿着中裝的男人談了許久才回,來時還把那人一起帶到桌 上,頻頻請那人坐,尊他爲「李副官」張老頭子明白了,這人就是能在司令面前說幾句話的。
馮老板把李得標介紹與張老頭,一 邊又問李:
「李副官,方才我跟你談起的事?……」
「你不知道司令的脾氣,他最恨的是人家跟他說情,不說也罷了,一說反而不好,而且脏證已搜到,這事情就麻煩啦,不過……路倒是有一條。」他飲了一口茶,張老頭却急得汗都出來了。
「你們 有人認識紅玫瑰嗎?」
「紅玫瑰?」馮老板想了想:「是大觀歌場那個歌女?」
「噯!就是她,要是她肯幫忙,就有了八成的希望,我們司令,很看得起她,可是千萬不可提到我,否則這事更壞更僵。
「張先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剛才李副官的 話,是好話,還是上紅玫瑰家裏去,求求她,也許死馬可當活馬醫!」老姜拍拍張老頭的肩膀。
「也好,就讓我去看看,姜先生 !」他說完又使個眼色,老姜把方才張老頭交給他的一包鈔票交給馮掌櫃,那裏面有文華的心血,可是救子心切,老頭兒再也顧不得了。
老姜幫張老頭打聽紅玫瑰住處,好幾天才探悉到。
老頭兒的心急,紅玫瑰的心更急。
一連三天,鐵佛寺前沒見到 張文華,在愛河中的紅玫瑰爲了愛人之不來,寢食俱廢,儘是在室中徘徊沉思,阿鳳爲她的健康担心,第三天了,紅玫瑰沒有好好吃過一餐飯。
「奇怪,他怎麽會連着三天不來呢?」
「小姐,你先别急,一會兒小秃子回來,終會有消息,你先吃點兒東西罷。」
「我不餓!」
阿鳳無可奈何的站在一邊,勸又不是,說又不合,正在這空氣沉重時,來了一陣打門聲,阿鳳急急的去開了門。
「你找誰?」
「請問紅玫瑰紅小姐是住在這裏嗎?」
「你貴姓找我們小姐有什麽事嗎?」阿鳳看來人,旣 縐且黄的臉上,一臉憂慮之色。
「我姓張,有點小事要求你們小姐幫忙。」
紅玫瑰也聽到張老頭聲音了,就着阿鳳請他進去。
張老頭子見紅玫瑰,看了看那大廳的華麗的佈置,輕聲訴述了來意。
「那人叫什麽名字?」
「是我兒子,他 是當小學教員的叫張文華!」
紅玫瑰陡然色變,阿鳳雖然平時做事鎮靜利落,到此也呆住了,半响才問:
「你就是張先生的爸爸?」
「是啊,我們雖然不相識,我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求你,祗當是做好事吧。」老人說到傷心處,淚盈睇睫,幾 將失聲痛哭,紅玫瑰叫他先回去,後來再說。
老人走後。紅玫瑰心緒大劣,粉頰掛滿了涙,半响才對阿鳳道:
你去接個電話給五爺,請他來一趟。
「小姐,你聽我一句話,忍一忍,先别告訴五爺,我想今天晚上他也許會來,你不妨探探他的口氣。」
「探他什麽?」
「咦!」阿鳳奇怪了:「你平常很機靈的?」紅玫瑰這才恍然,更恨趙一虎了。
趙一虎晚上却並沒有到紅玫瑰那裏去,這是那批混賬的同他設計好了,李得標知道張文華父親去求紅玫瑰,紅玫瑰一定得找司令幫忙,所以要一虎沉住氣别往她那兒。
可是趙一虎終忍不住氣了,他乘車趕到紅玫瑰家,紅玫瑰故意的盛粧出迎,請他進房。
話入正題,紅玫瑰單刀直入的:「五爺我要問你一件事,警備處有什麽公事一定得經過你手裏批過的罷?」
「你問這幹什麽?」
紅玫瑰望他一眼道:「你先别急,聽我說啊,有一天我發生了什麽事,找你不是容易了嗎?」
「小紅!你有什麽事儘管說,有人麻煩你?」
紅玫瑰有心和盤托出,推說張文華是她表哥,一虎心下明白,可表面也裝着代她婉惜,打電話到警備處去。假意關示不要難爲了文華,又說這是大帥命令,非常嚴重,故意說要到警備處去一趟,辭了紅玫瑰就走。
趙一虎真的上警備處了,處長姓馮,報告他張文華 非常屈強不肯吐實。關于紅玫瑰的事,他叫人假扮與他同監犯人與他並監,勾出他的話,已把錄音機收妥。
收者機放出來的聲音 ,使一虎心更煩亂了,冷笑道:「紅姐兒,你真有一手,還要與他遠走高飛呢?我看你是走不成了,寶貝,我得乖乖的叫你送入我懷抱裏來!」
又吩咐李得標假以找一虎爲名,到紅玫瑰家探探消息。
李得標到紅玫瑰家裏,聽說司令不在,回身要去,紅玫瑰却把他喊住了!
「李副官。」
「紅老板。」
「五爺上警備處去了。」
「奇怪,司令從來不上警備處的,今兒幹嗎去了?」
「你常去嗎?」
「一天我得去三趟!」
「那麽我請教你,假如有人被他們抓了進去……,譬如私藏 軍火一類案子,會受苦嗎?」
「不用說别的進去就得嚐三小件。」「什麽叫作三小件哪?」「第一灌水,第二老虎櫈,第三上電 ,不管你是銅打鉄澆,也受不了。」
紅玫瑰聽了慘然色變,強自抑制,紅玫瑰拿出一叠鈔票,遞給李,請他無論如何照應張文華 ,得標客氣一回,這才問明了姓名走了。
紅玫瑰心裏懷疑了,難道自己與張文華在鉄佛寺會面給他們査到了?心中忐忑不定,阿 鳳斷定李得標與趙一虎是串同連謀,她證明道:「他一會說是找五爺來的,臨走却又說「司令等着呢?」這不是漏了風了嗎?」
紅玫瑰到此更確信自己與文華的事,被趙一虎偵得,文華之被誣也是爲了自己,問小秃,小秃却絶口否認曾說過這件事。
第三天 ,心急似焚的張老頭去訪紅玫瑰,正值紅玫瑰約好了趙司令,於是吩咐張老頭,充他的姑丈,叫她小紅。
司令來了,張老頭叩頭 連連望他開恩,並拿了司令片子去會兒子,
告辭之後,父親惦掛兒子,含涙直奔牢獄,見兒子鉄索叮噹並形容憔悴,心胆皆碎, 倒是文華先開的口:
「爸爸你好?」
「還好!」
「你是怎麽進來的?」文華奇怪的望了老父一眼,老頭子沒說是 紅玫瑰,文華偷偷塞過一張小紙條。輕聲向父親說:「你回去罷,别掉了那張紙,千萬帶給紅玫瑰去。」
他以爲紅玫瑰還矇在鼓 裏呢?其實紅玫瑰她早已知道,不單知道,她已爲這事,痩却許多,流乾淚了,說得唇焦舌蔽,當趙五爺同她說:「回文一到,卽將處决」的話時,她忍不住放聲大哭,向趙一虎叩頭,要他想辦法,陰險的一虎把責任推在大帥頭上,可是有一句問話:「小紅,要是我放他出來,你要怎樣酬謝我。」
「祗要你說,我能辦的都行!」人在情急時,什麽都顧忌不得了,可是一虎沒說,祗是笑道:
「小紅,你還不知道嗎?」又斜阿鳳一眼道:「别忙,我喜歡什麽,你慢慢兒的想,哈哈,我走了。」
一虎走了之後,紅玫瑰跟阿 鳳商量,阿鳳的意思是:「犧牲張文華,或是犧牲紅玫瑰自己的幸福兩條路。」
紅玫瑰真的沒了主意,張老頭恰在這時趕來,他 把信交給她,紅玫瑰的手却抖了。阿鳳與小秃都偷窺紅玫瑰的神情,祗見她才讀一二行,已流下無數珠淚。
那信很簡單,祗寥寥 數行,還怕人眼目,寫的與她十分冷淡,稱她爲玫瑰小姐,文爲「素仰仁俠好義,拯人于水火,文華不幸遭厄,將瀕絶境,如有可能,尙乞賜以援手,匆此勿罪是幸,此請粧安」下署難中人張文華頓首百拜。
接着小秃子又在路上聽李得標說批文已到。
紅玫瑰向大觀園請了假,幾夜沒交睫,她决定了,决定毁了自己一生,去拯救比自己生命更值得重視的張文華,一個有前途的青年,她的愛人!
她絶不猶豫的去看趙一虎,一虎讓丁祕書跟她談,紅玫瑰坦率的告訴這狐狸養着的走狗,她願意嫁給趙一虎,祗有一項條件,「 放張文華,把他放走,由阿鳳看他走出這管轄區之内就嫁。」
丁祕書把一切情形告訴了一虎,他怕斬草不除根,逢春再復生,可 是一虎却答應了,可要叫紅玫瑰寫一份志願書。
比做壽更熱鬧,趙司令納妾了,在洞房花燭之夜,如餓虎撲羊,一個興高采烈, 一個含涙飲泣。
趙五爺已好幾天沒出門了,這天出去,回來時見阿鳳與紅玫瑰對泣,心想:「阿鳳留在此地,决非自己的福氣。 」
過不了幾天,阿鳳給辭退了,分别之際,阿鳳哽咽着說:
「太太,我走了,你自己保重,司令我去了。」可是紅玫瑰喚住了他:
「鳳姐,你等一等。」說罷去取了錢,她一滴眼涙也沒有,要流的涙都流完了,却是親親熱熱的道:
「我們相處了整整十五年了,像親姊妹一樣,今天分别,你要知道我的苦衷,這一點錢你拿去,是我送給你的,我還希望你别忘了我,能夠常常來看看我,噢!」她又回身向趙一虎道:
「能允許她常來看我嗎?」
「可以!」
阿鳳含涙而别,就靠了這點錢,她設 了個裁缝舖,生意還不錯,一年容易,阿鳳手上多了幾文,也偶而到趙一虎家去看看紅玫瑰,小秃也有了吃,住的地方,那一晚北風天,有涼月,阿鳳自外面回來,走入小巷子裏,發現有人跟踪她,江湖上老來的,半點都不怕的站定了,喝問那人:
「你老是跟着我 幹嗎?」
「鳳姐,别怕是我!」
一聽口音駭得退了幾步,這不是張文華嗎?她指着他道:
「你!你怎樣?你怎麽 又跑來了?來。」
她把他帶回自己的衣舖。
坐定之後,張文華才說出他來了已經七天了,每晚都在司令部門口,希望能默默無聲中見紅玫瑰一眼,今天看見鳳姐出來,才跟踪她。
阿鳳力勸他快離此地,告訴他,小姐的犧牲全爲他,要不是爲他,她怎 肯嫁給趙一虎?但文華也有他的說法,就是很簡單的一句話「人非草木,今日但願見一面,死也甘心了。」
阿鳳想了半天,願代 他遞個條子進去。
這消息讓紅玫瑰知道了,紙條也看見了,可是她長嘆一聲,叫阿鳳叫他趕快回去,再兩天此地就戒嚴了,要走 也走不了,叫他不要再找麻煩,她的犧牲,否則成毫無價值了。
阿鳳把消息帶給張文華。文華癡癡呆呆的,時局很不靖,阿鳳收 拾收拾隨時要棄家他逃,把一點貴重的東西準備送到紅玫瑰處寄存,有一個大木箱帶給文華一絲笑容,阿鳳口中却還唧唧咕咕叫他快走:「你是個有學問的人,應該知道小姐的苦心,她的困難。」
小秃也插上嘴了:「張先生,别那末固執啦,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 你一年多都等了下來,趙一虎說不定那一天完蛋啦,小姐自然會來找你的。
張文華一句都聽不進,突然他抓住阿鳳道:「這木箱 值多少錢?」
「也許得兩萬罷。」
「鳳姑娘我給你兩萬元,你把我裝進這隻箱子裏,送進趙家好嗎?」
阿鳳那裏 肯送,這一送弄個不巧送了文華的命不算,還得賠上自己那條命,但文華苦苦哀求,含涙下跪,阿鳳慌了,答應了他。
在天黑時 ,阿鳳及扛夫兩名,把箱扛到趙寓,在司令部中,門口逢到檢査,但聽說是阿鳳寄存皮貨,也不疑有他放了她進去,把個地方將木箱安排好了,阿鳳離去,紅玫瑰在阿鳳去後片刻卽自汽車上跳下,李得標亦步亦趨,跟入内廳。
箱子裏的張文華,也正悶得要死了,偷 開箱蓋潛出,透了一口長氣,遠處有兵士敬禮聲,他急忙再避回箱子,紅玫瑰與李得標到了客廳,得標道了明天見,紅玫瑰上了樓,這一年多來,物質享受夠好,精神上却無盡痛苦,早晚受人監視,但也感麻痺了,她回進房,李媽却又跟了進來:
「太太這末早就回 來了,用飯了沒有?」
「吃過了,喝多酒了,你先去睡罷,我也要睡了。」
「司令呢?」
「他還有八圈牌沒有打 完呢?」
李媽一出去,醉裏帶愁,看着窗外的月,心想同在一個月亮之下,却已分成兩個世界,偷偷取出一張照片,呆了半天, 忽覺床前有人,一看却是文華,以爲幻夢,急睜眼再看,果是,她幾乎號喊:
「是你,文……」
文華急忙把他的嘴掩住了。
「你這樣會讓外面聽見的,紅妹,難道你不想看到我嗎?」
「讓我把門鎖了再說。」
「我已經鎖上了。」
「你怎末進來的?」
文華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她,紅玫瑰却正色的問道:「難道阿鳳沒把我的話告訴你嗎?」
「告訴我的可是……」
「可是什麽,文華,你知道我今天到了這地步是爲了誰?可是我沒想到你把自己生命看得如同兒戲,你沒有想到,你 看到了我又能怎末樣呢?你能把我帶走嗎?當初阿鳳送你走的時候,我要她把我的話,都跟你說了嗎?你不是也答應了我嗎?今天你冒了這個險到這裏來,我覺得太沒有意義了,我早知道你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末輕。我也决不會把我的身體犧牲給他了。」紅玫瑰邊說邊淌淚,抽噎不止,再說也說不下去,祗是指着文華說:「你…」
「紅,你也得原諒我,我們究竟是人啊,我當時答應你,也就是希望 能有機會,我們再見面啊,可是這一年來,我日夜的想你,使我無可忍受下去了,所以……」
「你太儍了,我何嘗不想你:我不 是早就托阿鳳告訴你了嗎?他雖然得到我的人,可得不着我的心,希望你忍耐些,我會來找你的,今天你走進這個魔窟來,怎麽再出得去?」
「你放心,阿鳳在天一亮就會來拿箱子的。」
紅玫瑰緊緊抱住了文華,眼涙歡笑,驚怖,快樂說不出是什麽滋味。
好景難長,趙一虎他回來了,文華避入箱中,玫瑰把鎖開了,司令一踏進門就笑着問道:
「太太什麽時候回來的?」
「你不是知道嗎?」
忽然趙一虎注意起那大木箱來,知道是阿鳳送來的,一定要撬開它,紅玫瑰着了慌,半天也撬不開箱內的人正把小刀死頂住了那箱蓋。
正在這時,忽報丁祕書來,馮處長被刺了,一虎急忙披衣下樓,紅玫瑰輕輕叩箱道:
「文華出來吧?…」
一刻千金,訴不完的相思流不盡的淚,在天剛曙時,阿鳳派了小秃跟兩扛夫來扛箱,扛出了司令部,紅玫瑰看箱子被 抬走,心也跟着一起飛走了,天還沒有大亮,一路走到山坡之上,扛夫們累了,要歇歇脚,把箱子給倒翻了,箱中人頭地脚天,半响實在受不了,高喊起來:「快把箱倒過來!」
這時天還初曙,扛夫們一聽見,沒命就逃,大喊有鬼,小秃攔阻已來不及,恰巧趙一虎 由警備處打聽馮處長被刺消息回來,見人奔跑,卽予喝住。
李得標先上去問道:「什麽事?」
扛夫把情形說了,還叫有鬼。
趙一虎聽說箱是自己家搬出來的,「有鬼」,真的有鬼,立刻吩咐査看箱子,但,由箱內人的掙扎,箱已滾下山坡去了,趙一 虎立卽吩咐關城搜查戒嚴。
文華吃盡千辛萬苦,混身是傷,到處聽到車輛警鈴聲,張文華筋疲力盡,被李得標帶着的警犬發現遭 逮。
趙一虎回到公館中,他要紅玫瑰承認這事,並追問文華往事,紅玫瑰心一横都說了出來,被三四女僕軟禁了。
一虎特意在花園裏擺上一席酒,這天月色依舊那麽清明,他據桌獨飲,紅玫瑰由幾個女僕說伴送也可,說押送也可,送到一虎身邊。
趙 一虎高翹了雙腿,看紅玫瑰入座,就笑着向月指道:
「小紅,你看今兒晚上的月亮,多好?多美?所以特地請你下來賞月,像這 樣的月亮,祗有你這樣的美人兒,方配得上,真所謂花好月圓人長壽,來來來,坐下喝一杯,一會兒還有好戲可看哪!」
紅玫瑰 正等待着不可抗拒的刼運,一聲不發。
「月亮圓圓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小紅我的好太太,咱們應該是屬於歡喜的幾人的, 來,喝一杯,我的好太太。」
紅玫瑰猛的把杯中酒向口裏一送,在月光下的她的臉白得帶青。
一會,兵士押了個人上來,紅玫瑰一看,是小秃,心下更明白了,趙一虎却向小秃道:
「小秃子,這回你受了委屈了。」說着拿出錢來道:「喏這是一百塊 錢你拿去,是太太賞你的,你回去罷。」
小秃子凄然望了紅玫瑰一眼道:「太太謝謝你的賞,多謝司令的恩典。」
紅玫瑰咬緊牙道:「小秃子,你快回去罷!」
小秃子接過賞錢走了,紅玫瑰道:
「就是指這齣戲?」
「嘿,好太太,小 秃子祗能算是個龍套,算得了什麽?好戲,名角兒還在後頭哪,來呀!」
花園後面皮靴聲響,進來了四個衞兵,押着一個人犯, 黑巾蒙住了臉,趙一虎對兵示意,紅玫瑰的神情緊張,心幾乎要跳出口腔來了,
黑巾除下,紅玫瑰看清這正是文華,她差點暈過 去,却聽趙一虎道:
「太太,這才是那齣真赃實犯的正本好戲!」說罷冷笑,紅玫瑰抱了必死勇氣,可是還想救愛人的生命,她 霍的站起來道:
「你打算把他怎樣?你不用對付他,我承認一切都是我的主意,你鎗斃我好了。」
「嘿,太太,似乎晚了點兒了。」
趙一虎也站起來手一揮,一陣鎗聲,張文華倒下了,血在他身上似激湍进發,紅玫瑰至此哀痛欲狂,又聽得一虎笑聲 ,正仰天得意,那支鎗正掛在腰上,紅玫瑰一把搶過來,對準趙一虎亂發,一虎痛極狂呼!
「拿住她打死她!」
亂鎗聲又起,紅玫瑰在彈雨中落紅紛紛,倒在地上,許多人都去扶一虎,一虎的眼睛却看着紅玫瑰,紅玫瑰掙扎着一步又一步的爬行過去,在文華身側,手與手相挽,血與血交融,一對青年男女的臉上却有着安詳滿足的笑容,月亮不忍再看這個世界,他披起了烏紗,流下淚,細雨下來,垂死的趙一虎眼中臉上,不知是雨是淚?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