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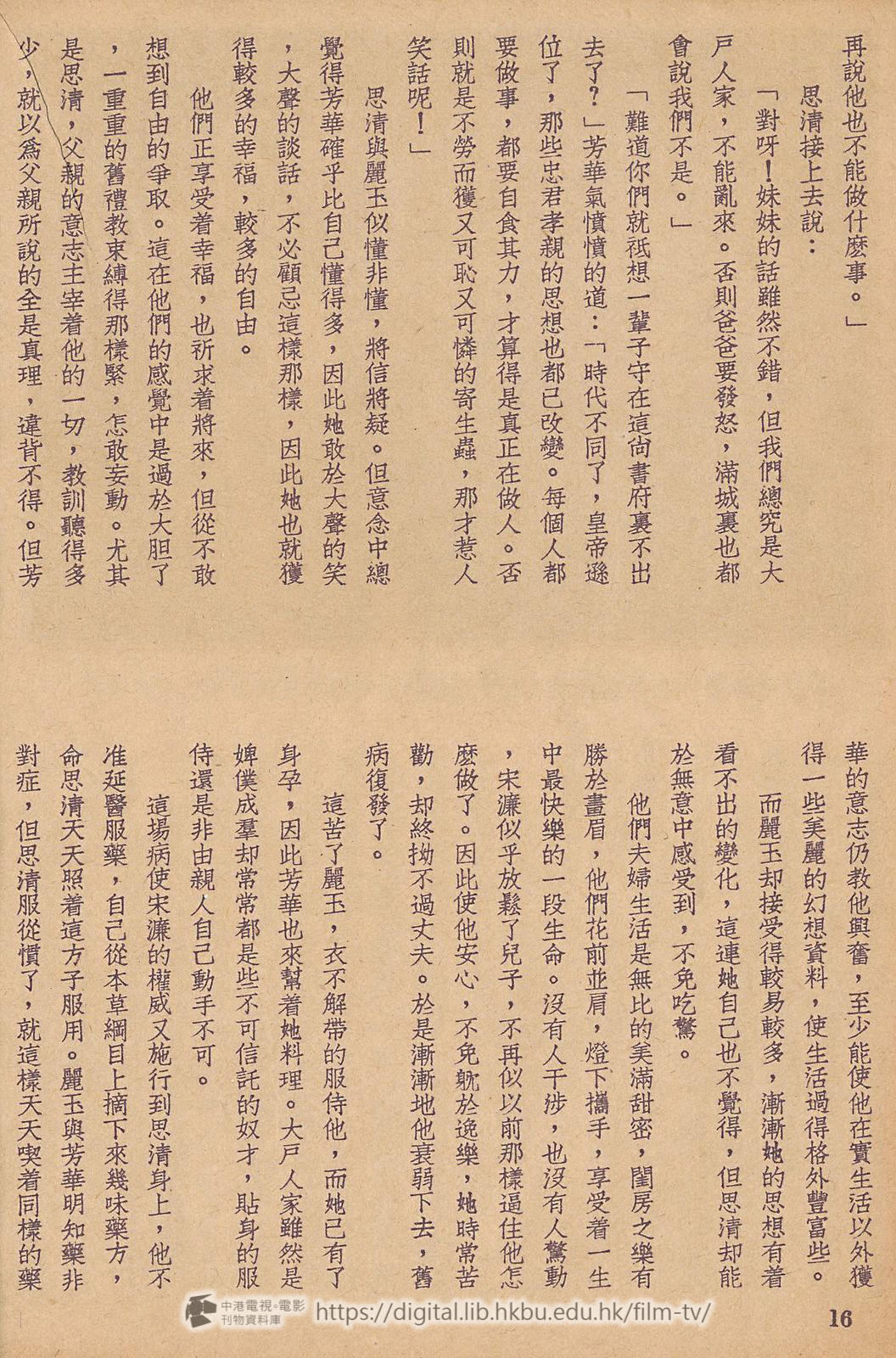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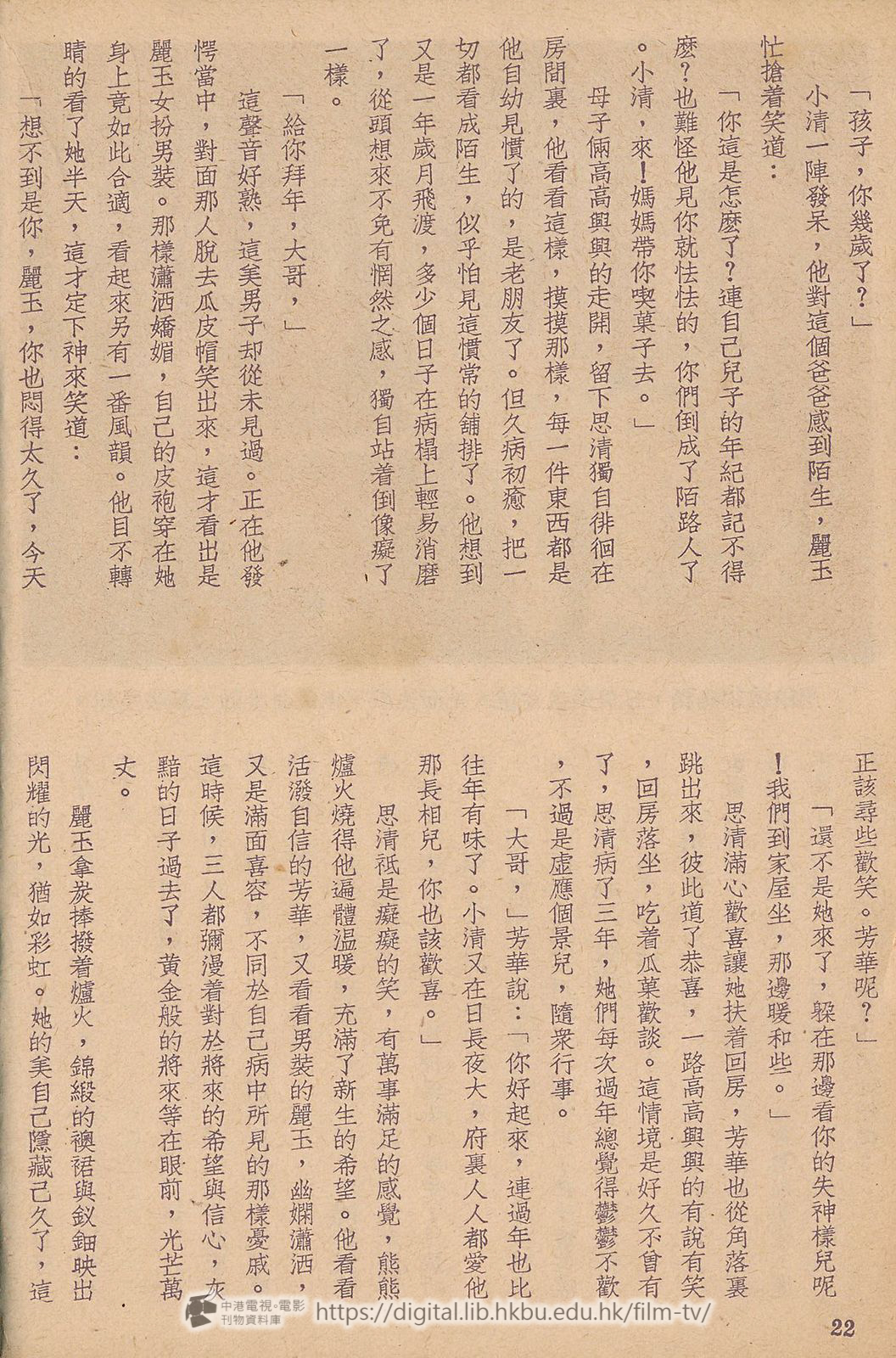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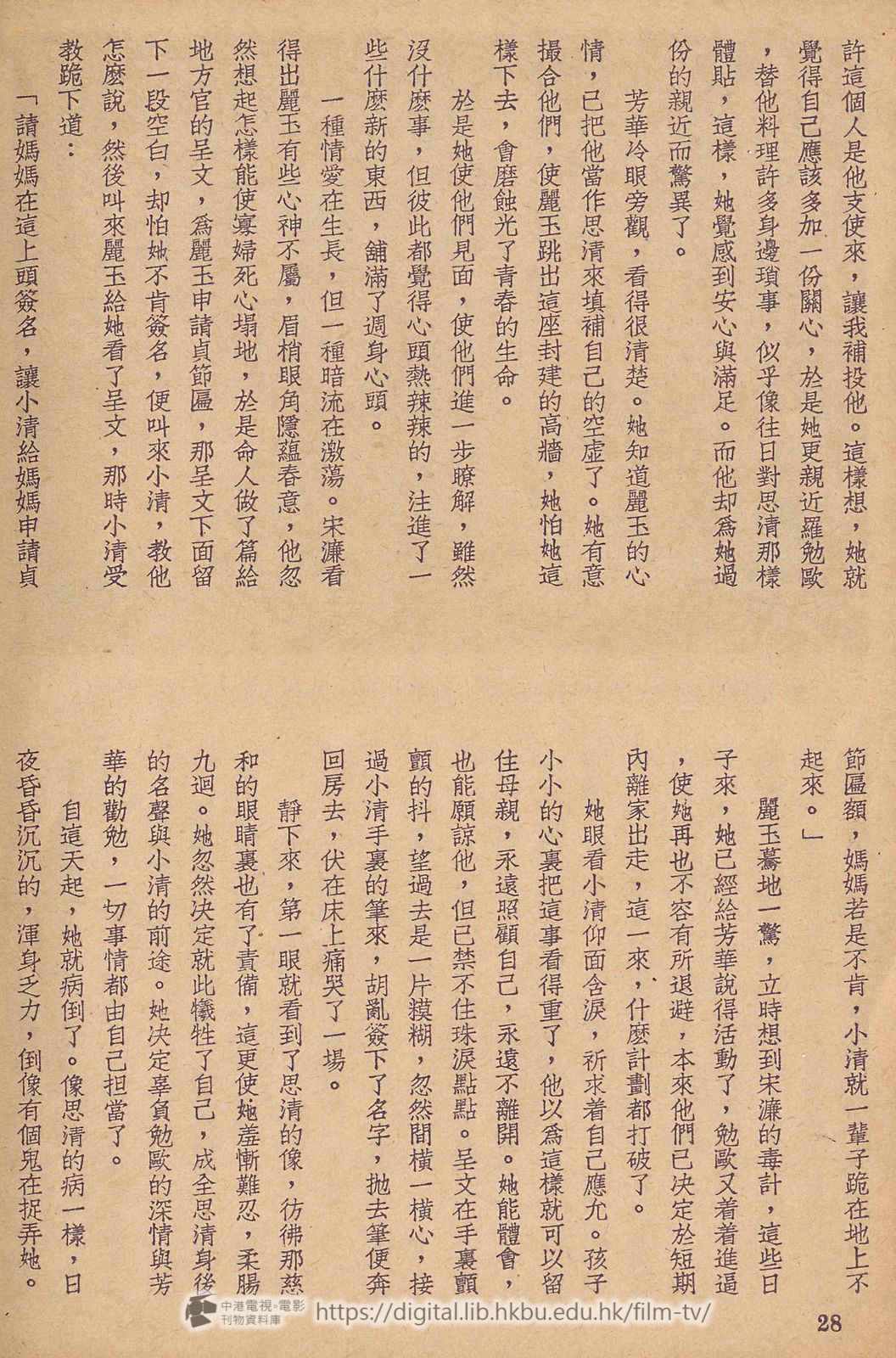




孽海情天
.電影小說.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男女之情在每一個時代總要受到外來環境的壓力,而抱恨終天。
這個故事發生在民初北京城裏,正是新舊思想衝突最尖銳的時間與地點。在這個夾缝裏產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讓後人唏噓嘆息,一掬同情之淚。
清室遜位不久, 北京城依舊是首善之區,遺老們緬懷着舊日的風光,幻想那好日子仍將回來。幾年過去了,新的思潮不斷灌入這個古老的都城,殘存的封建餘孽仍在作垂死的掙扎,力量還是大得驚人。多少青年男女身受煎逼,毁滅在無形的魔掌之下,可憐他們有些還不明白因何如此,而慨嘆於命運的坎坷。
禮部尙書宋濂,自從失去了權位,他的脾氣益發變得暴燥了。於是他沒奈何把統治的對象放在家人兒女身上, 不許他們有一些反抗的表示與行動。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他的喜怒决定一切,他以統治别人,干涉别人,以滿足自己的權位慾,全不顧人家的死活。
他代表着舊的時代,滿腦子的忠孝節義,澈頭澈尾的封建餘孽。兒子宋思清對他唯命是從,久處在積威之下,已不知 建立自由的思想了。女兒宋芳華却正相反,她曾偷偷的瞞了父親進過學校,接受過新思潮的洗禮,懂得自由的可貴。她勸思清振作,把眼光投得遠一些,但他旣生成因循的性格,又從未接觸過甚至想到過新的事物,對於芳華的鼓勵雖有了躍躍欲試的心情,到頭來却還是因循莫决,自誤誤人。
真的是自誤誤人,宋濂很早就替他訂下婚約,現在又定下迎娶佳期。他有宿疾,照說有病不能娶親,但宋濂以 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娶親是名正言順的事,那裏容得思清置喙?
迎娶之日,轟動了整個北京城。儀仗隊排滿了整條大街,一 切都照舊式行事,鼓樂喧天,賀客盈門,尙書府很久沒有這樣熱鬧了,因此更顯得熱鬧的可愛。凡是北京城裏甚至外省外縣的宋家戚友全都來了,他們向老尙書道賀,他拈鬚微笑,表現滿足的喜悅。他們也向思清道賀,思清的心上却吊着一塊石頭,他從來沒見過新娘朱麗玉,只知道也是名門世家的女兒。他不知道她生性如何容貌怎樣?也不知道可與自己合得來?
彩輿臨門,爆竹連天,人聲如潮,樂 聲也如潮。廳堂上早已陳設得燈彩輝煌,滿眼錦繡。新娘由喜娘扶到堂上,贊禮的一聲吆喝,樂戸們細吹細打。他們這一對從來不曾晤面的青年男女便在幾百個親友注視之下行那交拜天地的大禮。燈彩輝煌,紅燭高燒,香煙繚繞,喜氣洋洋,思清也感受了那種喜氣,頓覺精神好了許多。他原本宿疾未癒,但一時還看不出來,袍冠齊整,居然精神奕奕。但時間久了,嘈什與起伏頻仍使他疲倦,且險些窒息。但他居然一直撑持下去,拜完天地祖先,又向宋濂及長輩們見禮,鬧到天晚下來,內外燈火通明,將要開席了,才獲得片時的休息。
敬酒,取笑,吵鬧,一陣陣難關都闖過,在送入洞房的笑語聲中,他們雙雙被搬弄着。八個男女小孩,一式的高矮打扮,手棒花燭,在前分兩排行進。思清在前,手拖綢帶,後面雨個喜娘扶着新娘朱麗玉,算是握着綢帶前進。大羣年輕的親友與思清的妹妹芳華,嘻嘻哈哈的圍隨在旁,穿過廳堂迴廊重門繡戸,來到宋濂爲兒子佈置下的新房裏。
飲過交杯酒,行過合衾禮,婚儀算是已到了繁複的盡頭 ,也可以說是完成了。麗玉坐在床前,喜娘請思清替她挑去蓋面巾,思清自覺像做夢一樣的昏昏沉沉,身不由己,一伸手去掀去了她的面巾。這一下,整個房間裏的輝煌燈火都黯然無光了,滿地下的男女都爲新娘的絶世容光所攝,哦了一聲之後便寂然不聞人語,又過了半响,才聽見竊竊私議,驚異於新娘的美麗。
思清的感覺更深切,他萬萬料不到麗玉有這樣好看,甚至於他一生之中從未看到過這樣 美麗的女人,除非是在夢裏,啊!真的是在夢裏見過的,否則那裏會感到這樣親切,這樣似曾相識。
她坐在那裏屏息底頭,但不 忍是矯喘微微,也許是禁不住那鳳冠的重壓,也許是陌生的環境使她害怕了。她的雙頰染滿嫩紅,在大花燭底下更顯得容光照人,揚眉垂簾,也不知是愁是喜?
他坐在桌邊,還不敢細細向她打量,因爲怕人取笑。那些年輕人照例鬧房,但幸而宋濂早有嚴命,所以不 致放肆到無法無天的地步。但這樣已夠教他們受用了。幸有喜娘百般敷衍打扯,芳華又幫着哥哥,總算在更深夜靜後把這些人請出了門外。
現在新房中祗賸下他們兩人了。花燭高燒,爐火熊熊,那樣的安靜温暖,那樣的春光欲醉。兩人從沒見面,更沒有說過話,怎 麽開口?她不動,他也不動,她感到疲倦而焦急,他也何嘗不是一樣,也許還更甚些。
跟過去千年來大多數夫妻一般,總之他們 曾經說過話,彼此獲得對方初步的印象與體貼。從此天長地久,便注定了永遠在一起了。
思清對於以後這一段日子感到從未有過 的快樂,才開始領會了世間原有刻骨銘心的情愛。父親對他也放鬆了,除了晨昏定省外,也不大教訓他了。妻子又是那樣美慧,情愛上固然獲得了滿足,心理上生活上也有了安慰與照顧。他再不感到孤獨或悲觀,第一次想起自己還有將來,虚擬了一些奇怪的念頭。
麗玉是一個好女子,祗是一樣生長在純然保守的家庭中,信守着三從四德。當然,思清的儀表風度學問性格都是使她滿意的,因此她格外的待他好,盲目的仰望終身於良人,其他不問。
有時兩人談起來,誰也想不出將來究竟該怎樣?難道結婚生子就算盡了一個人的 責任?抱殘守闕就是難得的好子孫?他們都知道凡是人都應該做一些事業,但是誰也想不出應該怎樣做?做什麽?
尙書府的門牆 對於他們是一重攔柵,不能任意去窺探外面的天地。更不准有所謀劃了。所以芳華的見解每每使他們折服,願意天天傾聽她的勸勉與鼓動。她曾在姨母家裏住過一個時期,瞞着父親進過學校,接觸到了新的自由思潮。她每每勸他們把眼光放得遠些,不要困守在這高大深遠的府第裏。麗玉比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但她仍無胆實行,怯怯的問:
「芳華,那怎麽成?爸爸怎肯讓我們出去呢?再說他也不能 做什麽事。」
思清接上去說:
「對呀!妹妹的話雖然不錯,但我們總究是大戸人家,不能亂來。否則爸爸要發怒,滿城裏也都會說我們不是。」
「難道你們就祗想一輩子守在這尙書府裏不出去了?」芳華氣憤憤的道:「時代不同了,皇帝遜位了,那 些忠君孝親的思想也都已改變。每個人都要做事,都要自食其力,才算得是真正在做人。否則就是不勞而獲又可恥又可憐的寄生蟲,那才惹人笑話呢!」
思清與麗玉似懂非懂,將信將疑。但意念中總覺得芳華確乎比自己懂得多,因此她敢於大聲的笑,大聲的談話, 不必顧忌這樣那樣,因此她也就獲得較多的幸福,較多的自由。
他們正享受着幸福,也祈求着將來,但從不敢想到自由的爭取。 這在他們的感覺中是過於大胆了,一重重的舊禮教束縛得那樣緊,怎敢妄動。尤其是思清,父親的意志主宰着他的一切,教訓聽得多少,就以爲父親所說的全是真理,違背不得。但芳華的意志仍教他興奮,至少能使他在實生活以外獲得一些美麗的幻想資料,使生活過得格外豐富些。
而麗玉却接受得較易較多,漸漸她的思想有着看不出的變化,這連她自己也不覺得,但思清却能於無意中感受到,不免 吃驚。
他們夫婦生活是無比的美滿甜密,閨房之樂有勝於畫眉,他們花前並肩,燈下攜手,享受着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生命。沒 有人干涉,也沒有人驚動,宋濂似乎放鬆了兒子,不再似以前那樣逼住他怎麽做了。因此使他安心,不免躭於逸樂,她時常苦勸,却終拗不過丈夫。於是漸漸地他衰弱下去,舊病復發了。
這苦了麗玉,衣不解帶的服侍他,而她已有了身孕,因此芳華也來幫着她料理 。大戸人家雖然是婢僕成羣却常常都是些不可信託的奴才,貼身的服侍還是非由親人自己動手不可。
這場大病使宋濂的權威又施 行到思清身上,他不准延醫服藥,自己從本草綱目上摘下來幾味藥方,命思清天天照着這方子服用。麗玉與芳華明知藥非對症,但思清服從慣了,就這樣天天喫着同樣的藥汁,病情也不好也不壞,從春天拖到秋天。
歲序的更換折磨着舊的生命,也孕育了新的生命。 麗玉懷孕足月,平安生產,是個白白胖胖的男孩子。宋濂的喜歡是難以形容的,他忘記了兒子的病,却忙於爲孫子的一切,他替小孩命名爲小清,以表示承繼兒子思清,現在他有了第三代,他自覺權威已更昇一級,歸他主宰的生命又多了一個了。
思清的病同時也恰 有起色,其是雙喜臨門,麗玉雖然產後虚弱,却也滿懷喜悅。現在祗有芳華一個人常常陪伴榻前,爲她消解寂寞。她確然是寂寞的,祗爲不能看到思清的面,但有小清豐富的小生命在日長夜大,也是夠使她歡喜了。何况芳華又能善言善語,不時搜羅些外面的奇事異聞說與她聽,因此一個月的日子很容易打發過去,轉眼就是湯餅宴開的時候了。
宋濂對於這些事是最講究的,下令盡量舖張,務求熱鬧。 到日他親自招待賓客,賭酒猜拳。思清體稍健,也隨着父親敷衍,麗玉與芳華則在内堂招待女眷,直鬧了兩三天,方算過去。
歡 娛的節目方過去,不幸的事接踵而來,思清的病又發了。他祗覺得昏昏沉沉的渾身無力,宋濂命他喫藥他就喫藥,麗玉芳華教他休息,他就睡下。人瘦了,面色也枯槁了,精神萎頓,意志頹喪,再也不像以前的他了,惹起一家憂急。
宋濂除了命他繼續喫藥,也來看 過他幾次,總是拈鬚搖頭說:
「年輕人不懂得養生之道,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我累次耳提面命,怎樣教你,你却我行我素,全無 領會。我看這病固然不妨事,可也得好好將養,别再胡思亂想的,再者,我開的藥方全有來歷,非這些江湖醫生可比,多喫了自然就好。」
思清祗在枕上不住點頭,沒口子稱是,好容易等父親離開,這才放下心來,但已累得滿身冷汗,溼透重衾,喘息不止。
麗玉與芳華忙上來扶他睡平,又爲他拭汗撫摩,這才見他漸漸平靜下去。然後再餵他喫藥,藥汁倒下去,他皺眉吞飲,喝完長嘆一聲道:
「我看我是不行了。這藥喫了許多天,全不見效,我也怕喫它了。」
麗玉聽了祗覺心裏一陣難受,那兩行珠淚便忍不住撲籟籟的落將下來,祗在喉間哽咽。芳華見情境不好,忙向前強笑道:
「嫂嫂這是怎麽了?哥哥原祗是小病,眼看就好,那裏值得 傷心了?」
麗玉猛然警覺,自己不該忘形,忙着拭去了頰上淚痕,那哽咽却還未止。思清從枕上回過頭來,看了麗玉半响,強笑 道:
「你也癡了,我不過是那麽說,想來一時也不見得就死,再說有了你,又有了小清,卽使我要死,恐怕天也不容我雜開你們 。」
麗玉聽了,話是好話,却句句都是不祥之兆,不由得悲從中來,泣不可仰,任她強自抑制,也止不住那淚如泉湧。
芳華原是想勸,却不知怎的也覺滿懷蕭瑟,愁然無歡。女孩兒家心軟,見嫂嫂哭得那樣傷心,也忍不佳陪着流跟淚。
思清耳聞目賭 ,不由寒了半截,自思她們這等傷心,想是看出自己病入膏肓,業已不可救藥了。雖然人孰無死,但是矯妻情重,孺子幼弱,又教自己怎樣放得下這條心,於心酸中便感到一陣陣的絶望,勉強抬頭相看,她們也正凝眸涕,不覺一陣惘然。
思清的病便在纏綿床褥時好 時壞中打發日子,麗玉的憂愁自不必說,眼看着小清漸漸長大,漸漸會說話會走路了,思清却還脫不掉病魔的纏繞,而且日漸衰弱下去,像油燈般愈見暗淡了。
尙書府裏的歲月就這樣打發過去,外面的世界正是天翻地覆的時候,却一些也影响不到府裏的人。祗有芳 華能時刻嗅到那新鮮的氣息,但她知而不能行,更沒法影响别人的行爲。
思清的病,對於麗玉當然是一種磨折,日久以後,這種 磨折也就成爲習慣了。在夫婦生活中,現在她祗有義務而沒有權利,享受不到愛情却要支付無窮的代價。有時她會懷疑自己的命宮多難,否則何以刹那的歡樂便成空?有時她也想着思清終究會好起來,那時家庭生活又是何等美滿!因爲兒子也大了。
歲序又將更新, 尙書府中還照舊例過年,到處都顯得熱鬧。祗是在麗玉眼中那熱鬧也是悽悽切切的,全沒一些顏色。人在忙亂在笑,但不知是爲什麽,好像全無目標,似乎活着祗是爲了打發日子,爲了打發日子所以才過年。那樣的年,真是不過也罷!
幸得小清點綴了這個新年,他 已懂得逗大人歡喜了。而且思清人逢喜事精神爽,居然也能起床行動了,他總算過了三年來等一個健康的除夕,也感到人間居然還有温暖的希望。
爆竹除舊,桃符迎新,元旦一早,思清穿戴整齊,等着麗玉梳粧齊全,這才一同到上房向宋濂拜賀新年。宋濂袍掛齊全 ,精神奕奕,接受了兒媳的叩拜,和顏悅色的問了幾句話,就說:
「你病體剛好,也不要過於操勞了,早些休息去罷!外面各處 都不用去了,咱們也不在乎這些虚文,我這裏也不必全按規矩,祗要大槪不錯就好了,安心養病才是正經。去罷!」
思清麗玉都 想不到老人家今天這樣和易近人,歡歎喜喜的叩謝了回到自己房裏。思清站在供桌前徘徊摸索,倒不覺得怎樣乏力,正在思前想後,麗玉帶了小清過來給父親叩頭賀年。他便覺一陣滿足的喜悅,拉起小清來撫着他的臉頓道:
「孩子,你幾歲了?」
小清一陣發呆,他對這個爸爸感到陌生,麗玉忙搶着笑道:
「你這是怎麽了?連自己兒子的年紀都記不得麽?也難怪他見你就怯怯的,你們 倒成了陌路人了。小清,來!媽媽帶你喫菓子去。」
母子倆高高興興的走開,留下思清獨自徘徊在房間裏,他看看這樣,摸摸那 樣,每一件東西都是他自幼見慣了的,是老朋友了。但久病初癒,把一切都看成陌生,似乎怕見這慣常的舖排了。他想到又是一年歲月飛渡,多少個日子在病榻上輕易消磨了,從頭想來不免有惘然之感,獨自站着倒像癡了一樣。
「給你拜年,大哥,」
這聲音好熟,這美男子却從未見過。正在他發愕當中,對面那人脫去瓜皮帽笑出來,這才看出是麗玉女扮男裝。那樣瀟洒嬌媚,自己的皮袍穿在她身上竟如此合適,看起來另有一番風韻。他目不轉睛的看了她半天,這才定下神來笑道:
「想不到是你,麗玉,你也悶得太久 了,今天正該尋些歡笑。芳華呢?」
「還不是她來了,躱在那邊看你的失神樣兒呢!我們到家屋坐,那邊暖和些。」
思清滿心歡喜讓她扶着回房,芳華也從角落裏跳出來,彼此道了恭喜,一路高高興興的有說有笑,回房落坐,吃着瓜菓歡談。這情境是好久不曾有了,思清病了三年,她們每次過年總覺得鬱鬱不歡,不過是虚應個景兒,隨衆行事。
「大哥,」芳華說:「你好起來,連過 年也比往年有味了。小清又在日長夜大,府裏人人都愛他那長相兒,你也該歡喜。」
思清祗是癡癡的笑,有萬事滿足的感覺,熊 熊爐火燒得他遍體温暖,充滿了新生的希望。他看看活潑自信的芳華,又看看男裝的麗玉,幽嫻瀟洒,又是滿面喜容,不同於自己病中所見的那樣憂戚。這時候,三人都彌漫着對於將來的希望與信心,灰黯的日子過去了,黄金般的將來等在眼前,光芒萬丈。
麗玉拿 炭捧撥着爐火,錦緞的襖裙與釵鈿映出閃耀的光,猶如彩虹。她的美自己隱藏己久了,這次重又容光煥發,這是自然的現象,並不爲了給人看,而是她從自己的心裏發將出來。
他咳嗽了一聲,她抬頭道:
「怎麽樣?思清,你坐得太近火爐了,這火氣會使你乾咳。坐到我這邊來。」
說着自己站起,在椅子上舖好虎皮,墊了軟枕,然後扶思清坐過來,自己坐到他原來的座位上去,仍然撥 旺了炭火,然後安上一壺水。
現在房子裏的炭火氣少了,他們歡樂地渡過整個上午和下午,直談到上燈。
思清感到疲乏,麗玉和芳華扶他睡下,然後兩人對燈烤火,談着談着,越來越遠了。兩人差不多年紀,而思想與生活却隔得那麽遠,彷彿是兩個世紀裏的人,芳華竭力要使麗玉懂得多一些,不斷向她灌輸外面的情况。她懂得好多,但習慣與傳統使她遲疑。她聽她說,不住點頭,有時會說:
「芳華,這太過份了,這怎麽可以呢?」
實則她心裏正在激動,想像着外面廣大的世界裏,所發生的新鮮事,不禁神往。她的臉頰緋紅,胸前起伏,嬌喘微微,雙眸裏閃動着火般的光,然而,她不肯說更不敢做,有一些無形的東西縛住了她。
思清仰 躺在床上聽她們輕聲細語,房間裏是那麽的靜寂,卽使她們說得那樣低聲,也讓他聽到了。他也感覺到非常興奮,但這興奮祗是虚幻的,他並沒有想望到可以成爲事實,祗是想想也就夠温暖了。
第二天,思清就不曾起來,他又病倒了。元旦以後的新年就成爲一片灰 色的空白。麗玉的希望打算全都落了空,她又恢復了伺候病榻的老本行,再也不敢聽芳華談起美麗的廣大世界了。
她天天眼看着 思清衰弱下去,似乎是上蒼又加重了對朱麗玉的懲罰,看來這次一定要失去他了。
「但願他好起來,」她時常獨自默祝:「寧願 我自己折壽,也不要讓他離開,我不能沒有他,小清也不能沒有他,願他平安。」
但她的祝禱,終究祗是虚幻的想望,思清的病 祇有重起來,父親的藥方,不能挽救他油盡燈枯的殘生,麗玉的挽留哭泣也不能使他駐足,他靜悄悄的死了,彷彿全無留戀,實則帶着一肚子的牽掛去了。
麗玉的悲痛可以想像,她要以身殉節,但被芳華的義詞所折,又看到孤零零的小清,更使她不忍了,她勉強生 活下去。鉛華盡洗,素裝布衣,在萬念俱灰中打發着日子。
也許時間果真是治療悲痛的良方,日久她心頭的創痕漸漸平復了。和 小清在一起時,也能在她清淡的臉上找到甜蜜的笑容,她把整個生命都寄託在小清身上,爲他而面對現實。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正是爲她寫照,於是日月輪轉,小清長大了。
宋濂旣痛失明,望孫成人,聘得一位表親來充當小清的教師。麗玉原本日常就在 教着小清認字唸書,一旦少了這項功課,倒覺得十分寂寞,有時和芳華說說笑笑,也不過解得少許寂寞。因此花園裏常常能見到她的蹤跡,在樹蔭之下徘徊,花前凝神靜思。
這一天,她獨自在園裏癡想了半天,看花開花落,生生不已,不禁自念身世,威慨萬端。時 久脚酸,渾身的不自在,獨自懶洋洋地穿花拂柳,繞過曲曲的迴廊,低頭行來。忽然聽得耳邊有兒子唸書的聲音,不禁心裏一動,打量是在那一排廂屋裏,便繞將過去,正從窗下行過。看見小清正在伏案勤讀,心無旁鶩,也不去喊他。忽然瞥見對面書案上坐着思清,這一驚真是不小,定睛看時,不是思清還有誰呢?世間上决沒有這樣相似的人,卽有也不會連年歲神情,全都一樣。她明知這是請來的教師,一向總以爲是個老先生,那裏想得到是這樣年輕瀟洒。
她看得呆了,幸喜屋子裏師生教讀興濃,不曾瞥見。她猛然驚覺不該多看, 祗感到面紅心跳,足有千斤重,一步一移的回到房裏。一抬頭就看見思清遺像含笑而視,她不禁站在像前抬頭默祝道:
「思清, 你嚇着我了。莫不是因爲你怕我寂寞,才教個像你的人來安慰我?再不然,便是你不放心,支使他來折磨我?」
他的像依舊微笑 而視,不變不動。她拭眼再看,還是這樣,禁不住心亂如蔴,徬徨無主。倘若說婦人的心理有一個最複什的高潮,那末這便是她此時的心境了,她低迴如癡。
一串微細的脚步聲驚醒了她,猛抬頭,是笑嘻嘻的芳華。微微吃驚道:
「怎麽了?大嫂。你的臉色不好,怕是在園裏受了風寒了。」
說着伸手撫她的臉頰,祗覺熱得燙手。她閃避着推開芳華的關切說:
「我沒有病,我是嚇着了。」
「怎麽?」芳華越發驚異。
「小清的教師太像思清了,簡直一摸一樣,連神情都酷肖,他是誰?」
「哦 ,我忘記告訴你了。他叫羅勉歐,是我們家的表親,學問很好,父親特别請他來教小清,就住在我們家裏,早晚教學方便些,說起來,倒是實在像。」
「實在像,」她喃喃道:「我還以爲是思清特意來使我受驚的,天下事真有那麽巧。」
天下事真有那麽巧,從此她的心就有意無意的掛在羅勉歐身上了。沒事會時常向書房裏走一遭,看他一眼也覺得有種安慰。夜靜更深,她想起來會覺得抱愧,但她想,怎見得這不是思清的意思,也許這個人是他支使來,讓我補投他。這樣想,她就覺得自己應該多加一份關心,於是她更親近羅勉歐,替他料理許多身邊瑣辜,似乎像往日對思清那樣體貼,這樣,她覺感到安心與滿足。而他却爲她過份的親近而驚異了。
芳華 冷眼旁觀,看得很清楚。她知道麗玉的心情,已把他當作思清來填補自己的空虚了。她有意撮合他們,使麗玉跳出這座封建的高牆,她怕她這樣下去,會磨蝕光了青春的生命。
於是她使他們見面,使他們進一步瞭解,雖然沒什麽事,但彼此都覺得心頭熱辣辣的,注 進了一些什麽新的東西,舖滿了週身心頭。
一種情愛在生長,但一種暗流在激蕩。宋濂看得出麗玉有些心神不屬,眉梢眼角隱蘊 春意,他忽然想起怎樣能使寡婦死心塌地,於是命人做了篇給地方官的呈文,爲麗玉申請貞節匾,那呈文下面留下一段空白,却怕她不肯簽名,便叫來小清,教他怎麽說,然後叫來麗玉給她看了呈文,那時小清受教跪下道:
「請媽媽在這上頭簽名,讓小清給媽媽申 請貞節匾額,媽媽若是不肯,小清就一輩子跪在地上不起來。」
麗玉驀地一驚,立時想到宋濂的毒計,這些日子來,她已經給芳 華說得活動了,勉歐又着着進逼,使她再也不容有所退避,本來他們已决定於短期內離家出走,這一來,什麽計劃都打破了。
她 眼看小清仰面含涙,祈求着自己應允。孩子小小的心裏把這事看得重了,他以爲這樣就可以留住母親,永遠照顧自己,永遠不離開。她能體會,也能願諒他,但已禁不住珠淚點點。呈文在手裏顫顫的抖,望過去是一片糢糊,忽然間横一横心,接過小清手裏的筆來胡亂簽下了名字,抛去筆便奔回房去,伏在床上痛哭了一場。
靜下來,第一眼就看到了思清的像,彷彿那慈和的眼睛裏也有了責備,這更使 她羞慚難忍,柔腸九迴。她忽然决定就此犧牲了自己,成全思清身後的名聲與小清的前途。她决定辜負勉歐的深情與芳華的勸勉,一切事情都由自己担當了。
自這天起,她就病倒了。像思清的病一樣,日夜昏昏沉沉的,渾身乏力,倒像有個鬼在捉弄她。
幾年來憂急辛勞的磨折使她虧下去,這一病就不可收拾了。
芳華問知了這一段事,還勸她堅強地站起來抗議,但她祗有搖頭了。她已 真的如死灰一樣,再也想不到奮飛了,芳華一而再,再而三勸她尋取自由,她却說:
「不必了,芳華,謝謝你的好意,我懂得, 但我覺得疲倦了,再也不想享受什麽自由與幸福。祗要對得起思清,對得起孩子,我就心安了。小清的話不錯,我該爲他着想才是啊!」
「但是這話不是小清自己想出來的,這是爸爸教他說的。」
「我知道,」她在床上苦笑道:「但是和他自己說出來的有什麽兩樣?原是我錯了,我太自私,從沒想到過我要是離開他,他會怎樣痛苦,以後的日子又怎麽過?人人都會恥笑他。」
「不會 的,大嫂,你想錯了。現在時世不同,再也沒有人會笑一個再嫁的女人,更不會譏笑無知孩子。你何苦丟掉這後半生的幸福?」
她沒有回答,祗在嘴角邊露出一線苦笑,便默然向着裏床睡了。
芳華沒法,又去找了小清來,教他向母親認錯賠不是,但再也不 能挽回她鐵石般的心腸了。她拉着小清的手說:
「孩子,不是你的錯,是媽媽自己不好,你以後要聽姑姑的話,聽先生的教訓, 媽媽不能一輩子守着你,媽,要陪伴爸爸去的。」
孩子被這凄涼欲絶的語調所打動,跪在床前痛哭起來,她摩着他的頭頂,默默 流涙。芳華也陪着,於是滿屋子裏都是凄凄切切的哭聲,倒像生離死别的日子已在眼前,倒像她病重如山了。
真的病重如山,年 盡歲逼,臘月寒冬,她的病豈但沒有起色,反而越發的重了。芳華知道不好,告訴了宋濂替她預備後事,宋濂很安心,他不怕她再有什麽異動了。他願意看到死亡,因爲死亡能替他帶來榮耀,與這尙書府的名聲。
大除夕,尙書府裏準備過年也準備喪事,他們兩樣都 不曾落空,她真的是懨懨一息了。
芳華和小清在床前陪伴着她,勉歐沒法進去看她,祗在書房裏急得搓手頓足。一場春夢已瀕醒 ,他也傷了心了,他還來不及可憐自己,祗替麗玉難過。
大門口一捧鑼响,人聲喧鬧,宋濂聽說是貞節匾發下來了,高興得親自 出門去迎接,一面命人去通知麗玉,叫她也來接匾。麗玉聽說,不由得苦笑道:
「好了,我在宋家門中的責任算是盡了。總算還 我清白之軀,不曾沾辱了尙書府的名聲,芳華,請你扶我出去看看。」
「不能,大嫂,」芳華急忙攔住她,「你怎能下床?養病 還來不及,又何苦出去觸景傷情,别理他們,讓他們鬧去。」
說着打發了來人,回頭看麗玉氣喘得越來越急促,人已不對了。回 過頭來,屋子裏冷靜得異常,連小清也被宋濂差人來喚去了,祗賸下幾個不甚懂事的僕婢,連個幫手也沒有,不禁着急起來,又聽麗玉顫聲道:
「芳華,告訴勉歐,我對不起他,害他白喜歡了一場。若是他真愛我,就不要在我死後破壞我清白的名聲,我就十分感激 了。再請他多多照顧小清,這比待我好還令我感激。小清就全託你們兩人照顧了。勉歐人很好,芳華,你爲什麽不爲自己打算呢?」
芳華也覺一陣臉紅心跳,她知道這件事勢必要由自己出來收拾,却說:
「大嫂,你不要胡思亂想,你就會好起來的,酷冷的冬天已經過去,現在已經是暖和的春天了。我們陪你一同出去玩,自然的陽光與空氣會使你好得更快,你安心些。」
她苦心道:
「芳華,你不要騙我了,我並不怕死,我祗是放心不下小清,祗要你和勉歐答應照顧他,我就安心了。告訴他,我對他一輩子負責。」
芳華但覺淚眼糢糊,再看時,麗玉已暝目不視,伸手探胸,連氣息了停了。
外面鑼鼓的聲音喧閙不休,屋子裏却陰沉沉的可怕。這個人是被封建所折磨死的,以後也許還有不斷的受害者,衝破封建樊籬的責任就落在後一輩子身上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