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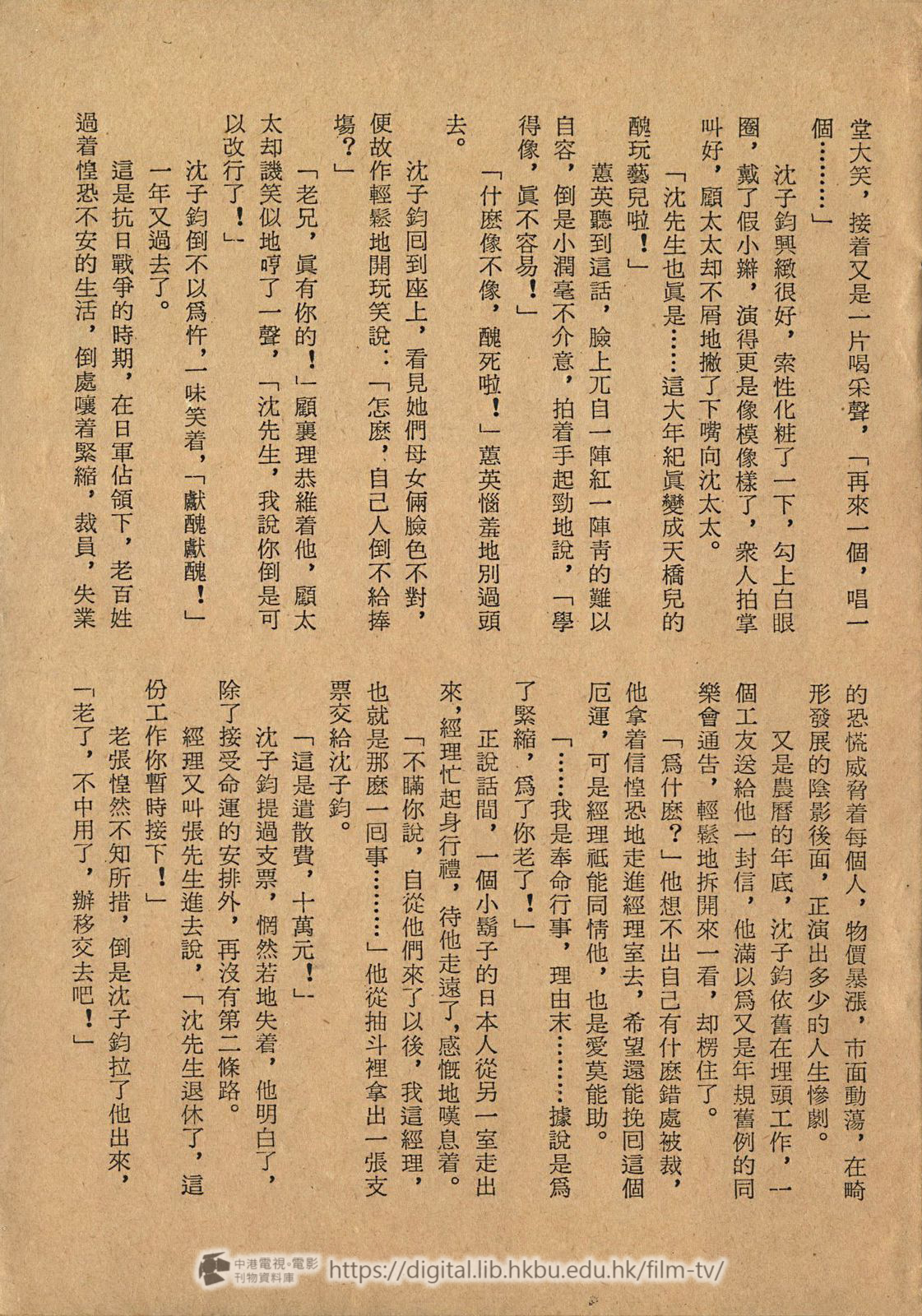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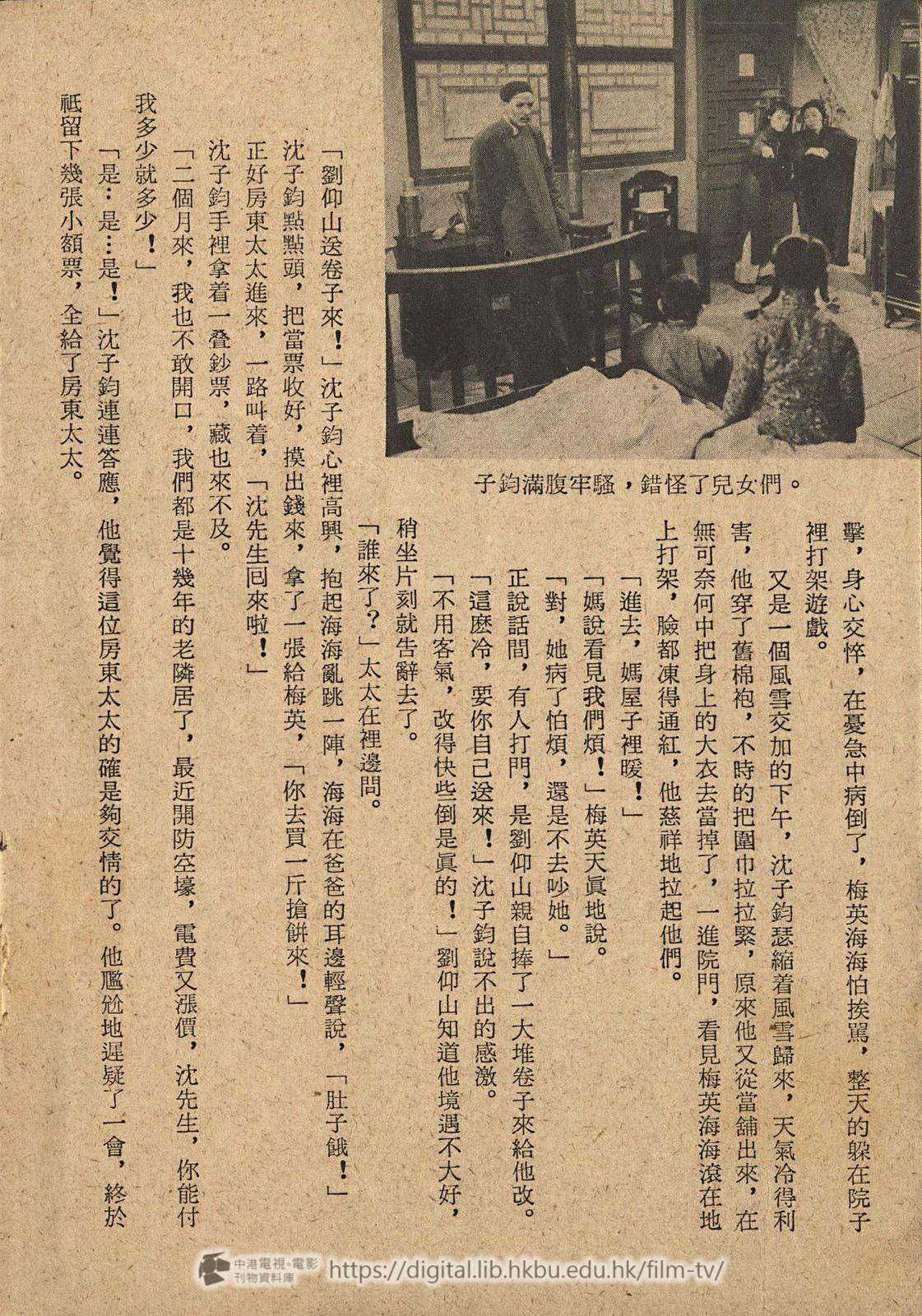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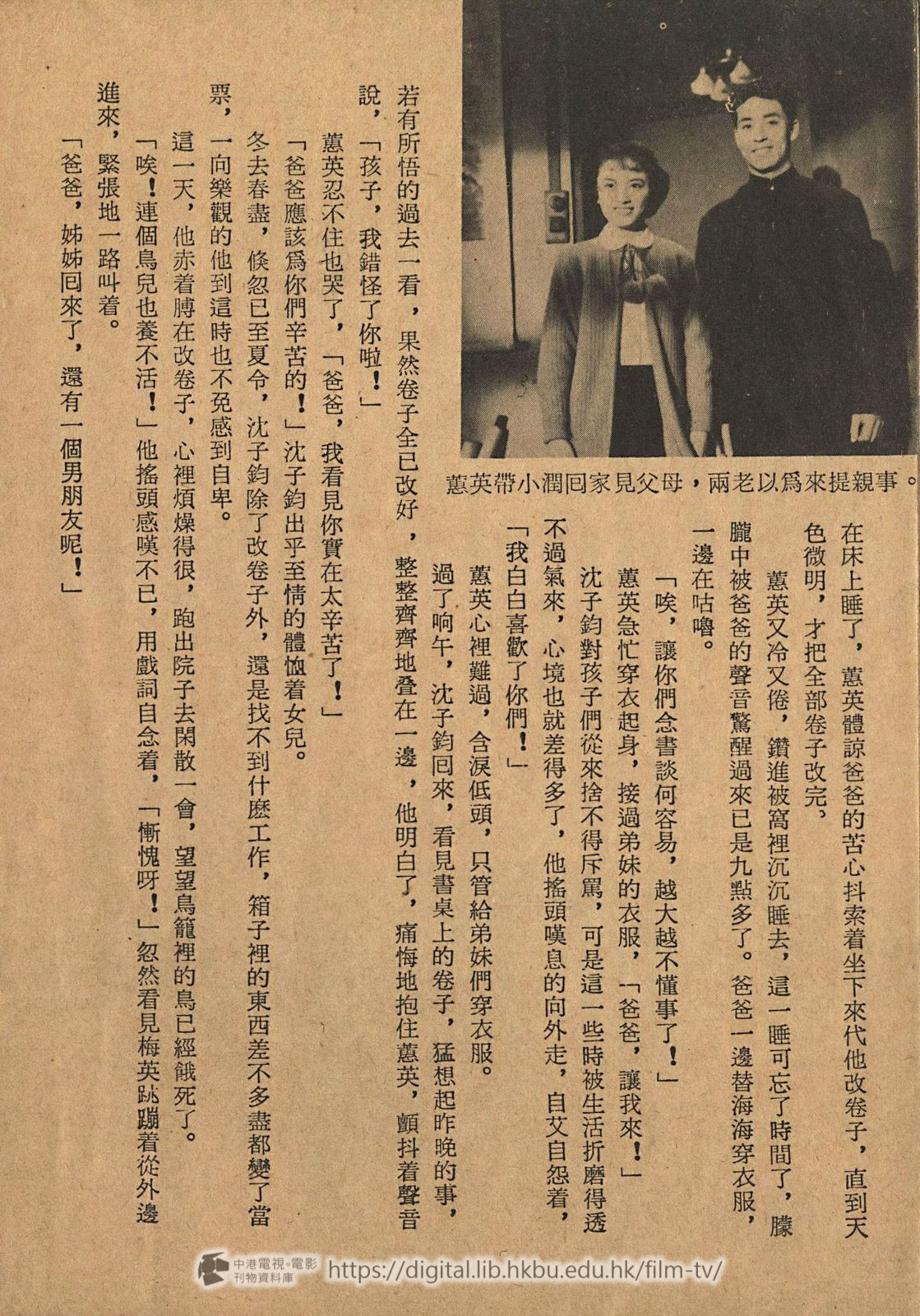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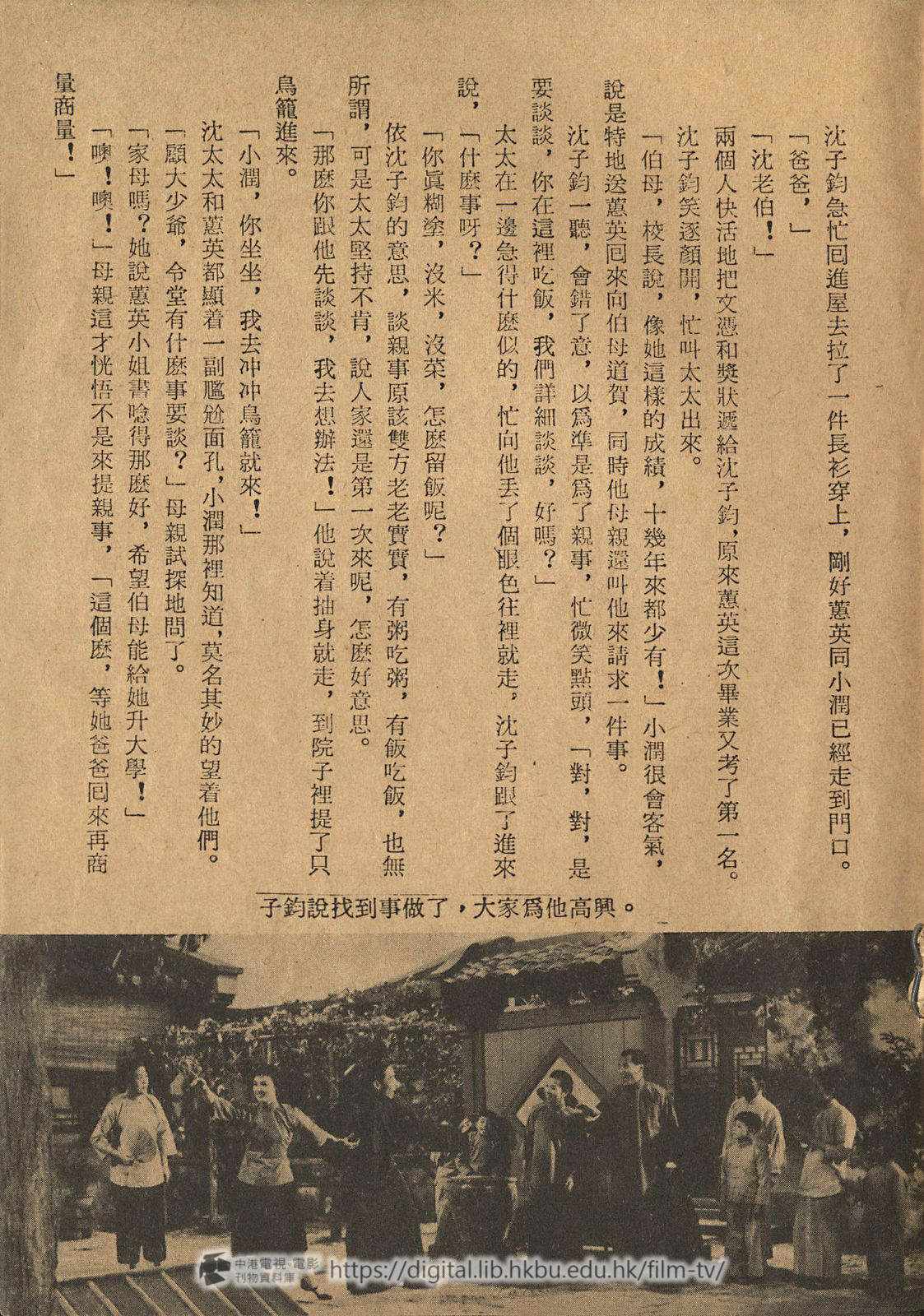







笑笑笑
.電影小說.
沈子鈞是天津集成銀行的稽核主任,他過着這刻板 的銀行生活,已經整整的二十年了,他爲人和善,平時總喜歡說說笑笑的,同事們都說他是個風趣人物。
這是一九四二年的除夕 ,銀行辦公室裡,大家正忙忙碌碌地趕工作,工友拿了一叠信過來,依次分發,沈子鈞拆開信封裡邊是行裡擧行的除夕晚會的通吿和入塲券,欣喜地笑向對座的同事張先生說。
「老張,轉眼又是一年了!」
「是啊,今兒晚上您得闔第光臨囉!」
「那 還有說的!」
是下班的時候了,同事們一個個的離去,沈子鈞也收拾好了桌上的東西,脫下陳舊的袖罩,塞入抽斗裡鎖好,拿起 兩本舊書走到出納科關頌平的桌子邊,原來他們兩個人興趣相同,是硏究相聲的同志。
「頌平兄,二本相聲的書帶囘去吧!」
「你留着不一樣?」
「不,明兒起放假,拿囘去研究研究!」
「謝謝你,那末晚上見!」
他們出了銀行,分 道而走,沈子鈞自得其樂的一路哼着天津落子,信步歸來,轉進一條冷淸淸的老胡同,便到了他的家,同住的林大娘已給他開好了門。
「聽見胡同口兒哼呀的哼,準知道是你囘來了!」
鄰居對他的感情都很好,一路說笑着走進院子來,走過林大娘的房,唱戲的林振庭正掀簾出來,在找他的兒子「小狗子」。
「林老板還沒有出去?」沈子鈞客氣地招呼。
「出去不出去,還不是一樣!」林大娘嘆了口氣。
「大嫂,愁,解决不了事情,祗有幹!」沈子鈞老喜歡說輕鬆的話兒,可也帶着十分的同情與感慨。
「是啊,沈先生,你就是這麽看得開!」林振庭點頭苦笑。
庭院裡,小狗子和沈子鈞的兩個孩子,梅英海海,正在串演虹霓 關,小狗子扮王伯黨,梅英扮東方氏,海海做觀衆,在一旁拍手助興,沈子鈞遠遠的站住了,望着他們大爲欣賞。
小狗子被林大 娘喊走了,梅英海海見了爸爸也都跳着囘房去,大姊蕙英氣咻咻的瞪着梅英,母親從裡邊出來駡着︰「叫你們不要跟唱戲的孩子玩,你們偏偏………」
「出了什麽岔子啦?」沈子鈞在後邊進來,愕然問太太。
「不一定出岔子!跟唱戲的孩子玩,也會變成沒出息!」
「噓,快別這麽說,大家同住不好意思,再說唱戲的也是憑本領吃飯!」
「噢,你也幇着說,叫我怎麽管敎孩子!」
沈子鈞對太太的成見很不以爲然,可是見她沉着險,也就不敢多說了,囘頭笑對蕙英說,「你媽眞搞不通!」
那知蕙英跟媽媽一般見解,她也最愛面子,也瞧不起人家唱戲的,「說眞的,提起唱戲的誰都瞧不起,我的同學………」
「好,好,好。 別說了!」沈子鈞忙轉變話題,從公事包裡拿出入塲券,高高舉起,「看,今兒晚上行裡開同樂會,有飯吃,有戲看!」
梅英和 海海狂喜,都嚷着要去。
「大家都去,快換衣服。」他又柔聲對太太說,「你也打扮打扮!」
他見她們都進房去了,一時戲癮又作,拉起袍子,擺好身段,冷不防太太走了出來,他立刻停止。
「差點兒又讓你說沒出息了!」
太太又氣又好笑的咕嚕着囘進房去,「我說你呀,越老越瘋癲!」
沈子鈞伸伸舌頭,自念自唱,「說說笑笑,長生不老!」
他就是這麽一個樂觀的人,雖然生活很淸苦,家裡却也養了一只鳥兒,種了幾盆玫瑰花,這時趁閒去澆了花,餵了鳥,囘進屋子,祗聽得裡邊叫叫嚷嚷忙做一團,海海躲在一角裡不知在搞什麽,走去一看那才笑壞人呢,原來他用鞋刷在擦牙齒,弄得滿臉都是鞋油。
母親和蕙英在翻 箱子找衣服,從蕙英的大衣裡跌下了一支小辮子,那是蕙英小時候的,沈子鈞拾起來把玩着,满有意味的。
「看你,又要搞這東 西,還不快來幇手!」
他連忙放下辮子,手舞足蹈的過去幇太太托起箱子,不料一舉手腋下的鈕扣給拉破了,太太又得百忙中替 他縫補。「別輕骨頭啦,快五十歲啦,還像個淘氣孩子!」
「媽,爸爸自己也說是老天眞呢!」蕙英在一邊笑着插嘴。
「什麽老天眞,簡直是小寃家!」母親的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終于大家都打扮好了,走出門來,蕙英忽然發覺大衣襟上有個 小蛀洞,母女兩人最講面子,這又難住了。不穿吧,不像樣,穿上吧,多難爲情,沈子鈞靈機一動,急匆匆跑囘去折了朶玫瑰花兒,給插在破洞裡。
「怎麽樣?洞給遮了,派頭也夠新的了!」
蕙英笑了,一家五人,這才滿意地出發。
同樂會的會塲上 很是熱閙,經理襄理職員外,還有家屬和孩子們滿滿地擠了一堂,沈太太正坐在顧襄理太太的旁邊,不免有些拘束,她囘頭見梅英海海吵做一圑。
「蕙英呢?」
顧太太聽見了,笑着說,「她跟我家小潤,不曉得在談些什麽,海海,去叫哥哥姊姊來看戲吧!」
梅英海海跳躍着出去了,顧太太微笑着向沈太太說,「看樣子,我們快成兩親家囉!」
沈太太聽了心裡一喜,祗是謙虛說。「襄理太太,只怕高攀不上!」
「那裡話!」她們正在客氣,已見梅英海海拖了小潤和蕙英進來了,各人在座位上坐下,臉上 還露着神秘的甜蜜的微笑,顧太太向沈太太做了個眼色,彼此會意含笑。
忽然有位同事提議請沈子鈞關頌平來一段滑稽相聲,衆 人鼓掌,沈子鈞心裡早就躍躍欲試,只是碍於太太在旁不敢答應,只好抱拳起立,向大家拱拱手,衆人那肯罷休,而且關頌平已經擠了過來,在他耳邊低聲催促。
「凑合凑合,助個興吧!」
「怎麽樣?」沈子鈞問太太,沈太太的臉色顯然不贊成,勉强笑着說,「隨你!」
「看樣子,不上去也不行,好,請吧!」他自己找了個下塲便匆匆離座去了,沈太太很不高興,又奈何他不得,祗 得按耐下了,還對顧太太說:「我們子鈞就是什麽都不在乎!」
一段滑稽倒眞是說得有聲有色,引起了台下哄堂大笑,接着又是 一片喝采聲,「再來一個,唱一個………」
沈子鈞興緻很好,索性化粧了一下,勾上白眼圈,戴了假小辮,演得更是像模像樣了 ,衆人拍掌叫好,顧太太却不屑地撇了下嘴向沈太太。
「沈先生也眞是……這大年紀眞變成天橋兒的醜玩藝兒啦!」
蕙英聽到這話,臉上兀自一陣紅一陣靑的難以自容,倒是小潤毫不介意,拍着手起勁地說,「學得像,眞不容易!」
「什麽像不像, 醜死啦!」蕙英惱羞地別過頭去。
沈子鈞囘到座上,看見她們母女倆臉色不對,便故作輕鬆地開玩笑說:「怎麽,自己人倒不給 捧塲?」
「老兄,眞有你的!」顧襄理恭維着他,顧太太却譏笑似地哼了一聲,「沈先生,我說你倒是可以改行了!」
沈子鈞倒不以爲忤,一味笑着,「獻醜獻醜!」
一年又過去了。
這是抗日戰爭的時期,在日軍佔領下,老百姓過着惶恐不安的生活,倒處嚷着緊縮,裁員,失業的恐慌威脅着每個人,物價暴漲,市面動蕩,在畸形發展的陰影後面,正演出多少的人生慘劇。
又是農曆的年底,沈子鈞依舊在埋頭工作,一個工友送給他一封信,他滿以爲又是年規舊例的同樂會通吿,輕鬆地拆開來一看,却楞 住了。
「爲什麽?」他想不出自己有什麽錯處被裁,他拿着信惶恐地走進經理室去,希望還能挽囘這個厄運,可是經理祗能同情 他,也是愛莫能助。
「……我是奉命行事,理由末………據說是爲了緊縮,爲了你老了!」
正說話間,一個小鬍子的日本人從另一室走出來,經理忙起身行禮,待他走遠了,感槪地嘆息着。
「不瞞你說,自從他們來了以後,我這經理,也就是那麽一 囘事………」他從抽斗裡拿出一張支票交給沈子鈞。
「這是遣散費,十萬元!」
沈子鈞提過支票,惘然若地失着,他明白了,除了接受命運的安排外,再沒有第二條路。
經理又叫張先生進去說,「沈先生退休了,這份工作你暫時接下!」
老張惶然不知所措,倒是沈子鈞拉了他出來,「老了,不中用了,辦移交去吧!」
同事們聽到沈子鈞被裁的消息,都萬分同情,有的 替他難過,有的代他不平,可是這年頭,誰也不敢說什麽,老張接過沈子鈞的帳册和鑰匙,臉上顯得很難過。
「老弟,你也是奉 命行事,別過意不去!」沈子鈞邊說邊理自己的零物,全室的空氣很是沉重。
忽然電話鈴响,沈子鈞拾起來聽,正是蕙英打來的 ,說是要他買些年貨,早點囘家吃年飯,他一只手還拿着支票,感慨系之的說着。
「……好,好,記得住,你也當我老糊塗啦! 哈……哈,一樣都忘不了,錢?有的是……對,分了花紅了,十萬元,好……我這就囘來啦!」他擱下電話,只覺得一陣徬徨。
出納科的關頌平親自捧了十萬元現鈔過來,同情地勸慰了一番,沈子鈞收了錢,除下袖罩,吶吶自語地。
「跟了我多年,可不能 隨便丢了!」他把袖罩塞進了公事包。
辦公室裡一片沉寂,沈子鈞悵然離座,向同事們拱手作別:「各位,彼此心照不宣,大家 心裡的話,我領情了,謝謝。」
他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故作輕鬆地哼起天津落子,向大家揮手吿別,衆人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悲哀 。
沈子鈞提了大包小包的年貨囘家,一路上的行人都投以羡慕的目光,有個叫六叔的鄰居,排了整天隊才輪到了一小袋麵粉,看 見他,「唉!沈老先生,你眞發財呢!」
「托福,托福六叔!」沈子鈞苦笑着低頭前走。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對他好似一個晴天霹靂,他失魂落魄地只是在想:「怎麽辦呢,被裁之事吿不吿訴家裡呀!吿訴了,無補於事,徒然害得一家大小不安寧……」
一路行來一路想,最後他决定暫時不說,讓大家快快活活的過了個新年再作計較,於是他振起精神來又哼着落子,將到家門,門又呀 的開了,林大娘笑着說。
「聽着哼呀哼的,就知道是你囘來了!」
沈子鈞忙拿出一包南貨送給她,「有勞大嫂開了一年的門,這一點不成敬意!」
林大娘歡喜得什麽似的受下了。
梅英海海見爸爸捧着大包小包囘來,都擁上去投在他懷裡,各人接了年貨狂奔進去。
「爸爸!」蕙英忙着搬菜,臉上浮起欣喜的笑容,「媽在厨房裡吶!」
沈子鈞怕露出心事,故意作興奮的神氣走到厨房去,拿起一把扇子就扇暖鍋,一邊說笑着。
「夫人,在下來幇忙了!」話沒完,飛起了一陣炭灰。
沈太太連忙奪下扇子,「不用了,快去點燭,好祭祖了。」
「噢!」他嘻笑着退出。
年飯桌上,一家人團團坐着,蕙英拿起酒杯,祝爸爸稱心如意,沈子鈞含笑乾杯,只是無限愁苦在心頭,不禁下意識地嘆了口氣。
「爸爸幹嗎嘆氣?」蕙英驚覺。
「不,我嘆氣了嗎?我是太高興了!」
席間,他把遣散費交給太太,說這是分到的花紅,沈太太直樂得嘻開口笑,看見他的舊袖 罩跌落地下,忙拾起來。
「蕙英呀,囘頭替爸爸縫一付新的!」
「不用……」他說出後頓覺失言,忙含糊地應着,「好……過了年再說吧!」
「換一副新的,明年更有勁,花紅也更多!」太太討着口好彩。
「對,更有勁!」沈子鈞苦笑點頭。
沈太太高興極了,一會兒叫梅英敬蛋給爸爸,說爸爸明年多賺銀元寶,一會兒又叫海海敬蛋,說爸爸多賺金元寶,沈子鈞聽着, 心裡祗是陣陣刺痛,可是他一一接着,還提起酒杯向太太,「你辛苦一年,明年如意!」
他一杯杯地飲着,太太只以爲他今天特 別高興,也不阻止,却不知道他心裡有苦說不出,終于支撑不住了,伏在桌上沉沉睡去。
太太在房裡孩子們拿新衣服,理紅封包 ,蕙英在剪窗花,梅英海海幇着貼,大家喜洋洋的準備過新年。
院子裡放起爆竹,沈子鈞被高升震醒過來,他來到庭院,看見梅 英海海在點爆竹,便也跟他們一起玩,鑼鼓咚咚,送財神的叫化子來了,大家爭先恐後的跑出去迎接財神爺,沈子鈞也不落後,買了個紙財神,把梅英海海抱一個肩一個的,高高興興地囘進屋子去。
沈太太見他醒了,忙笑嘻嘻地叫蕙英。「蕙英呀,替弟弟妹妹換衣 服,來向爸爸辭歲!」
孩子跳下來們亂做一團,爸爸媽媽並肩坐了,孩子們正在叩首,忽然空襲警報聲大作,大家一時忙着下燈 罩熄腊燭,屋子裡一片漆黑,院子裡也肅靜了,驚恐與不安替了代替團聚的歡樂。
四天假期倏忽過了去,沈子鈞可總沒有勇氣向 太太吐露被栽的事
年初五的早晨,沈子鈞照例很早起身,他一邊洗臉一邊心裡想不出主意,不說穿吧,上那兒去呢!他想過來想 過去,决定還是向太太講個明白吧,主意已定,一路走出房來。
「噯……噯……」他的話還沒說,祗見太太高興地從厨房裡捧了 一盆年糕出來,放在桌上︰「什麽呀………今年第一天上班,讓你吃年糕,好高高興興!」
這一下,沈子鈞的勇氣頓時消失了, 想說的話無從出口,祗好吱唔着坐下來,可是心裡一亂,怎麽也吃不下了。
太太見他坐着,「是不是不喜歡呀?」
「不,胃不舒服,不想吃!」
「要請假一天吧!」太太體恤地問。
沈子鈞心裡想這倒是個辦法,何不將計就計,便點了點頭,「也好!」那知太太想得周到。
「蕙英呀,去打個電話替爸爸請個假!」
「不不不!」沈子鈞嚇得連忙忙起來,取大衣圍巾一邊穿一邊說,「不用了,我還是去上班!」
他提了公事包匆匆走去,蕙英從後邊追上來,把一付新縫的袖罩遞給爸爸,「新年 用新的!」
沈子鈞見了袖罩只得苦笑着點點頭,「該換新的了!」
他茫然地走到胡同口,不禁躊躇起來,仰望天空,不知道該上天?還是入地!他嘆了口氣。「唉,走吧!」
沈子鈞滿腹心事,茫無頭緒的一路走着,走了很久,腿也開始酸了,可是一 看錶還只有十點半,今天的時間眞是過得何其慢呀,好容易才挨到了一點鐘,他疲憊地走進一家小館子去,坐下來透了口氣,抹抹汗,隨便地吃了一碗大鹵麵,竟不自制的伏在桌上朦朧睡去了。待他一覺醒來已是下午三時,心裡暗自好笑,見跑堂遞上手巾,他有點不好意思了。「怎麽不叫我?」
「您好睡吆,打了通宵麻將啦?」
「是……是!帳單來!」
却不知他睡了二個鐘頭,麵價 已從五百廿元漲到八百五十了。
「先生,您先付了再養神,就便宜多了!」
「對,對!」沈子鈞付了錢出來,又不得不在路上兜幾個圈子。
當他囘到裡家,好像長途拔涉歸來似的,倒在搖椅中,只感到一陣解脫的舒服,他閉目養神,幾乎連話也不想 說了。
「爸爸,你好像很累,沒什麽吧!」蕙英正在火爐邊讀書,看見他頹喪的神情,想起爸爸早晨要請假的事情,忙倒了杯茶 走過來。
「沒什麽,就是忙得累,連腿都酸痛,你媽呢?」
「在厨房燒飯,我你捶捶腿好嗎?」
蕙英拖過一張小 櫈子在他腿邊坐下,開始捶腿,沈子鈞闔上了眼,露着笑容,姑且享受着這片刻的安寧,父女倆一邊談着。
「蕙英,你跟顧小潤 很好吧!你們可曾談過什麽……」
蕙英羞澀地低着頭。
「這有什麽難爲情,吿訴爸爸聽聽!」
「沒有……」她停 了又說,「我們只談過一些將來的計劃。」
「將來的計劃?」爸爸含笑坐起。
「不是呀,他在大學裡念的是工程,叫我升大學之後,念經濟,他說顧伯伯將來要辦工業,好分工合作!」
「噢!還不是談過了,分工合作吆……就是分工合作!哈哈…… 哈!」爸爸神秘的笑聲倒使蕙英不好意思起來,撒嬌地一轉身,「我不來了,你總是開玩笑!」
蕙英今年暑假要畢業了,她的升 學問題早就想跟爸爸商量,可是見爸爸工作辛苦,負担重,弟妹們又小,遲遲的總覺不忍開口,現在看見爸爸興緻很好,又正在談起將來的問題,心想不如乘機探探爸爸的意思。
「說眞的,爸爸,我升大學,你答應不答應?」
沈子鈞聽了一楞,但立刻鎭靜下來,點點頭,
「你書念得這麽好,我總得想辦法給你升學!」
「經濟不成問題嗎?」蕙英不大放心。
「這不是你 的事!」
正談到這裡,母親從厨房裡出來了,她像需要付什麽帳似的,一出來就問沈子鈞,「你身邊有錢嗎?」
沈子鈞又是一愣。「今天才初五,十萬塊錢已經,——」
「哎啊,我的老太爺!物價一天三變……」沈太太半發牢騷似的報了一大筆帳, 沈子鈞嚇得連連點頭。
「哦……哦,那是應該的,應該的!」
還有,學校的學費單也等着要付呢,原來太太把錢都買了柴米日用品,心想丈夫在銀行裡稍爲變通一下,家裡就要便利多了,沈子鈞臉上儘管毫不介意的應着,心裡却揑了把汗,逕自走到鳥籠前餵着鳥,只是出神。
「我看你一點都不愁!」太太說笑似的埋怨他道。
「船到橋頭自會過!有我!」
第二天,沈子 鈞拖着沉重的脚步又按時出門去了。這擺在眼前的問題怎麽解决?不由得不焦急起來,下午,他買了幾份報紙,坐在一家小茶舘裡,詳讀聘請欄的廣告,藉以消磨時間,忽聽得一個熟悉的名字。
「蕙英,那邊好!」
他抬頭一望,見小潤和蕙英正並肩進來,他慌忙地把報紙遮住了臉,待他們在廂座裡坐定後,便急匆匆付了帳溜走了。
這裡小潤和蕙英親熱地坐着談心,他們剛剛看了電影 出來,小潤問起她的升學問題。
「爸爸答應了,就看我媽媽怎樣,大槪沒有問題!」
「說起沈伯父找到事嗎?」小潤想起了這事。
「什麽?他不是在集成做得好好的?」
「他被裁了呀,你不曉得?」
「啊?那他昨天還去上班的!」
小潤聽了着實詫異,蕙英却立刻不安起來了,她知道小潤的消息决不會錯的。
蕙英別了小潤,囘到家裡,母親和弟妹們都不 在,她煩燥地在室中徘徊,要等爸爸問個底細,她爲爸爸的失業担憂,更爲自己的前途傍徨了,天色漸黑,寒風裡,雪花飄着,可是爸爸還沒有囘來。
原來沈子鈞離了茶館,一直在路上徘徊,囘家去怎麽交待呢,說好了今天向銀行借學費的,他左思右想,終于不得 已而走向一家當舖門口,他從來沒有這個經騐,一到門口,心就跳得厲害,祗怕碰見了熟人下不了面子,他向四週張望了一會,終于鼓足了勇氣,一竄而入,在當舖裡左右顧盼,見沒有熟人,便迅速地除去了大衣,脫下長袍,朝奉翻看估價,沈子鈞穿囘了大衣,那裡還想講價,拿了錢和當票往袋裡一竄,便急匆匆地奔竄出去,低下頭跑了一陣,這才放慢脚步,從容走去,在風雪中,他感到一陣寒慄,可是想到眼前問題總算已經解决,心頭一鬆,倒也就興冲冲的不覺得冷了。
他裹緊了身子,推門進來,看見蕙英正在隔窗探望,便裝得 若無其事的欣喜地叫着道,「啊,蕙英,下雪了,這朝雪正是時候,種田人可好了……怎麽你一個人?媽媽呢?弟弟妹妹呢?」
「都出去了!」蕙英見爸爸有說有笑的,倒有點兒摸不淸究竟是怎麽囘事,她上前去給他脫大衣,沈子鈞忙避到爐子邊去,「慢着,現在還冷呢!」
他從袋裡掏出錢來數了數,「蕙英!這是你的學費,這是梅英的,你看爸爸是不是有辦法!」
蕙英呆呆地望着錢,她滿腔的狐疑,决定要問個明白,「爸爸,我不念書了!」
「爲什麽?昨兒還說得好好的要升大學呢!」
蕙英一陣心酸,別過頭去流下淚來了,「爸爸,您爲什麽要騙我們,你給裁了,還要裝着去上班!」
沈子鈞一愕,「誰說的?」
「顧伯伯講給小潤聽的!」
他停了一停,計上心來,立刻有了主意,「哈哈!原來是一個誤會!」他一邊說一邊在轉念頭,喝了一口 茶,安祥地囘過身來。
「吿訴你吧,曾經有此一說,可是經我跟經理去說理,當時就收囘成命啦!」這本來是他的願望,所以很 順口的說了出來,蕙英見他態度從容,有些將信將疑。
「你想,我幹了二十多年,又沒有一個錯,裁我有理由嗎?」他走近去把 錢交給女兒,「儍孩子,錢都帶囘來了,還會假?」
蕙英這才轉悲爲喜的笑起來,忽然想起厨房裡的飯,「啊喲,不���了, 飯快焦了!」說着急匆匆地奔了進去,沈子鈞如釋重負的舒了口氣,抹去了頭上的汗,走進臥室去了。
他匆匆忙忙地翻着箱子, 找出了一件舊棉袍子,不意那條小辮又帶了出來落在地上,他正想要除大衣,忽聽得蕙英的脚步聲進來,忙把棉袍子塞在被頭底下,看見蕙英,故作滑稽的拾起小辮在在頭上搖幌,蕙英見了一怔,嬌嗔地,「爸爸,你在找什麽?怎麽啦?快藏起來,醜死了!」
「對 ,你跟媽最不喜歡我這樣,可是我最愛你這支小辮子!」說着,忙岔開話題,「飯焦了沒有?」
「一點點!」
「那更香,更有有味,媽不在你先去做菜好嗎?」
「好,瞧我的手法!」
蕙英高興地跳躍着去了,沈子鈞急忙脫下大衣,剛拿出棉袍,忽又聽得脚步聲,只好再把它塞囘被下,穿了短襖,手足無措地坐在床沿上。
沈太太推門進來,見他脫得薄薄的,「外邊下雪 ,你……」
「說也奇怪,我祗覺得熱,莫非返老囘童了……」儘管他裝着悠閒的樣子,可是一副窘相早給太太看出破綻,「你的 皮袍子呢?」
「喔,今天眞倒霉,給打了悶棍!」
他又編造了一篇謊話,說是那打刼的傢伙上了他的當,拿走了皮袍子留下了大衣,却不知他向銀行裡借的錢還藏在大衣袋裡呢。
爲了要証實他的話,他匆匆的從大衣袋裡去摸出一叠鈔票,慌忙中那當 票跌落地下,太太見他臉色慌張,搶着拾起來一看,凄然怔住。
「原來你把它當了!」
蕙英剛走到門口,聽住傾聽,祗聽得爸爸的聲音。
「噓!別響,當心給蕙英聽見!」
可是她已經聽到,她一進來摸出學費,放在桌上忍不住哭泣起來了。
「你何苦要弄成這樣子!」太太不知情由,生氣地埋怨他。
「媽媽,爸爸早給行裡辭掉了,一直瞞着我們。」
沈子 鈞想阻止也來不及,不知所措的楞着,蕙英堅持說不念書要去找事做了,母親口口聲聲地嘆着以後的日子怎麽過。
沈子鈞這時惱 羞成怒,煩燥地咆哮起來,「怎麽過!有我,我半輩子都過來了,剩下的半輩子會過不去?」
母女兩人給他喝住了,悲切地沉默 着。
「好了好了!」沈子鈞又鎭靜下來,「天無絕人之路,世界之大,那會容不下我這麽個勤懇老實的老好人?你們儘管放心, 我自有辦法!」他又拿錢塞給女兒。
「你儘管好好唸書,明天我陪你去繳學費!」
這個悶在心裡的問題,一旦給說穿了,沈子鈞反覺得輕鬆起來,他穿上舊棉袍,說說笑笑的又恢復平時那消遙自在的態度了。
第二天,沈子鈞陪着蕙英去學校繳費,意 外的遇見了老同學劉仰山,他在這裡當敎師已經二年了,沈子鈞忙拉他到一旁,「仰山兄,有沒有辦法,我也來當個國文敎員!」
劉仰山見他喜笑的神氣,以爲他在開玩笑,「你呀,還是老樣子,難得見面,見面就開玩笑!」
「不,給奉命吿老囉!」
「眞的?」劉仰山知道了實情,非常同情他,立刻答應代爲設法,可惜的是這學期寒假已過,敎員就請定了。
「這樣吧。」他想了一會,誠懇地說,「我先替你弄點卷子改改,不過不夠用呀!」
「拜托拜托,總比閒着好!」沈子鈞滿懷希望的吿別出來。
現在,他不用再裝着上班去了,祗是每天依着聘請廣吿的地址不斷地跑着應徵,一家復一家的,他的信心漸漸動搖了,事實那有理想那麽容易,心裡不禁惶急起來,世界雖大,眞會有無地容身之虞了。
沈太太受不起這打擊,身心交悴,在憂急中病倒了,梅英海 海怕挨駡,整天的躱在院子裡打架遊戲。
又是一個風雪交加的下午,沈子鈞瑟縮着風雪歸來,天氣冷得利害,他穿了舊棉袍,不 時的把圍巾拉拉緊,原來他又從當舖出來,在無可奈何中把身上的大衣去當掉了,一進院門,看見梅英海海滾在地上打架,臉都凍得通紅,他慈祥地拉起他們。
「進去,媽屋子裡暖!」
「媽說看見我們煩!」梅英天眞地說。
「對,她病了怕煩,還是 不去吵她。」
正說話間,有人打門,是劉仰山親自捧了一大堆卷子來給他改。
「這麽冷,要你自己送來!」沈子鈞說不出的感激。
「不用客氣,改得快些倒是眞的!」劉仰山知道他境遇不大好,稍坐片刻就吿辭去了。
「誰來了?」太太在裡邊問。
「劉仰山送卷子來!」沈子鈞心裡高興,抱起海海亂跳一陣,海海在爸爸的耳邊輕聲說,「肚子餓!」
沈子鈞點點頭,把當票收好,摸出錢來,拿了一張給梅英,「你去買一斤搶餅來!」
正好房東太太進來,一路叫着,「沈先生囘來啦!」
沈子鈞手裡拿着一叠鈔票,藏也來不及。
「二個月來,我也不敢開口,我們都是十幾年的老隣居了,最近開防空壕,電費又漲 價,沈先生,你能付我多少就多少!」
「是…是…是!」沈子鈞連連答應,他覺得這位房東太太的確是夠交情的了。他尶尬地遲 疑了一會,終於祗留下幾張小額票,全給了房東太太。
沈子鈞送走了房東,笑嘻嘻地囘進來,手裡還拿着餘下的另錢,交給太太 ,太太一望而知是他把大衣去當掉了,心裡一陣難道,淚也流下來了。
「凍出病來怎麽好!咳!」說着一咳嗽便倒了下去。
「你好好養病,別管這麽多!你看,我是金剛百鍊身,一點都不冷!」他一邊說,一邊假作打拳狀,偸偸地溜了出去。
沈子鈞 跑到院子裡去餵鳥澆花,嘴裡還哼着落子,看見林振庭正在掃雪,兩個人攀談了一會,很是投機,直到蕙英囘家,他這才收了話匣子同女兒笑着走進屋子。
「那麽晚,是不是又在討論你們的合作計劃?」
「爸爸,你!」蕙英嬌嗔地啫着嘴笑。
「進去 吧,去熬點小米兒粥,我叫梅英去買槍餅了!」
「好!」蕙英放下書,逕去厨房工作了。
桌上放了一大鍋小米粥,父女四人團團圍坐,一口餅一口粥,哈支哈支的吃得其味無窮。
晚上,屋子裡靜悄悄的,孩子們都已睡了,沈子鈞獨自在燈下改卷子, 窗外雪下得很大,他坐着直是哆嗦,只好站起來跑步跳躍,增加一點熱力,夜愈深愈冷,他忍不住到臥室裡去拿了一條棉被裹在身上,這才暖了一些。
已經是半夜二點鐘了,沈子鈞一心想把卷子一齊改完,唯恐再失掉了道唯一的生計來源,可是他的精神實在不濟了 ,伏在桌上不自覺的睡着了,一個轉身竟把身旁的茶杯打落地下。
蕙英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輕輕開門出來,看見爸爸可憐的樣子 ,心裡大爲不忍,把爸爸扶進房去,沈子鈞睡眼惺忪,糊裡糊塗的就倒在床上睡了,蕙英體諒爸爸的苦心抖索着坐下來代他改卷子,直到天色微明,才把全部卷子改完。
蕙英又冷又倦,鑽進被窩裡沉沉睡去,這一睡可忘了時間了,朦朧中被爸爸的聲音驚醒過來已是 九點多了。爸爸一邊替海海穿衣服,一邊在咕嚕。
「唉,讓你們念書談何容易,越大越不懂事了!」
蕙英急忙穿衣起身,接過弟妹的衣服,「爸爸,讓我來!」
沈子鈞對孩子們從來捨不得斥罵,可是這一些時被生活折磨得透不過氣來,心境也就差得 多了,他搖頭嘆息的向外走,自艾自怨着,「我白白喜歡了你們!」
蕙英心裡難過,含淚低頭,只管給弟妹們穿衣服。
過了响午,沈子鈞囘來,看見書桌上的卷子,猛想起昨晚的事,若有所悟的過去一看,果然卷子全已改好,整整齊齊地叠在一邊,他明白了,痛悔地抱住蕙英,顫抖着聲音說,「孩子,我錯怪了你啦!」
蕙英忍不住也哭了,「爸爸,我看見你實在太辛苦了!」
「爸爸應該爲你們辛苦的!」沈子鈞出乎至情的體恤着女兒。
冬去春盡,倏忽已至夏令,沈子鈞除了改卷子外,還是找不到什麽 工作,箱子裡的東西差不多盡都變了當票,一向樂觀的他到這時也不免感到自卑。
這一天,他赤着膊在改卷子,心裡煩燥得很, 跑出院子去閑散一會,望望鳥籠裡的鳥已經餓死了。
「唉!連個鳥兒也養不活!」他搖頭感嘆不已,用戲詞自念着,「慚愧呀! 」忽然看見梅英跳蹦着從外邊進來,緊張地一路叫着。
「爸爸,姊姊囘來了,還有一個男朋友呢!」
沈子鈞急忙囘進屋去拉了一件長衫穿上,剛好蕙英同小潤已經走到門口。
「爸爸,」
「沈老伯!」
兩個人快活地把文憑和獎狀遞給沈 子鈞,原來蕙英這次畢業又考了第一名。
沈子鈞笑逐顔開,忙叫太太出來。
「伯母,校長說,像她這樣的成績,十幾年來都少有!」小潤很會客氣,說是特地送蕙英囘來向伯母道賀,同時他母親還叫他來請求一件事。
沈子鈞一聽,會錯了意,以爲準 是爲了親事,忙微笑點頭,「對,對,是要談談,你在這裡吃飯,我們詳細談談,好嗎?」
太太在一邊急得什麽似的,忙向他丢 了個眼色往裡就走,沈子鈞跟了進來說,「什麽事呀?」
「你眞糊塗,沒米,沒菜,怎麽留飯呢?」
依沈子鈞的意思,談親事原該雙方老老實實,有粥吃粥,有飯吃飯,也無所謂,可是太太堅持不肯,說人家還是第一次來呢,怎麽好意思。
「那麽你 跟他先談談,我去想辦法!」他說着抽身就走,到院子裡提了只鳥籠進來。
「小潤,你坐坐,我去冲冲鳥籠就來!」
沈太太和蕙英都顯着一副尶尬面孔,小潤那裡知道,莫名其妙的望着他們。
「顧大少爺,令堂有什麽事要談?」母親試探地問了。
「家母嗎?她說蕙英小姐書唸得那麽好,希望伯母能給她升大學!」
「噢!噢!」母親這才恍悟不是來提親事,「這個麽, 等她爸爸囘來再商量商量!」
却說沈子鈞提了鳥籠,滿頭大汗的趕到關頌平家裡,把小潤來提親,現在還在家裡,不得不留飯的 苦衷向老關情商,關頌平跟他原是好朋友,立刻慷槪地答應了。
「沒有問題,是應該的:這個你留着好用!」
沈子鈞感繳面又慚愧地辭了出來,走不多路,聽得關頌平追了上來,他一次再次的勸沈子鈞跟他搭檔,一同去說相聲唱滑稽,「我被裁之後,起初也想不通,可是現在呀幹上了,收入可眞不錯!老兄,我們不搶不偸,有什麽關係呢,生活要緊呀!」
「好,我再考慮考慮!」沈 子鈞接受了他出於至誠的勸吿。
晚上,沈子鈞轉輾不能入眠,他覺得關頌平的建議一點不錯,他决定跟太太商量一下,好讓蕙英 去念大學,成全她的願望,那知一提這件事,太太又氣又惱,嘮嘮叨叨地罵個不停。
「得…得…得,我收囘,別嚷別嚷!」
「你這不是要蕙英好,簡直是要害她!以後叫我們還能出去見人嗎?」
「好了好了,我不過這麽說說,不做就不做!」
可是,爲了一家人的生活,他終於私下裡决定和關頌平去拍檔了。
這一天早晨,他把鬍子剃得光光的走出來,蕙英奇怪地叫起來 ,「爸爸,你怎麽啦?」
「看相的說我的鬍子擋好運,所以我把它剃光了!」
「哎,剃了倒精神一點!」蕙英順口說着,原來她這幾晚上也沒有好睡,她心想小潤希望她升大學,自己何嘗不想,可是爸爸的境遇這麽苦,升大學別說是不可能,而且太不應該的了,她也下了决心,去到學校向劉老師商量,要求給她一份小學敎員的位置,也可以分担一些爸爸的重累。」
劉仰山對他們父女 兩人本來非常同情,恰巧有個敎員空缺,他答應了。
「……可是,我以爲把這個機會讓給你爸爸更合式,你能升大學最好,要不 ,再想辦法!」
蕙英高興極了,喜孜孜地趕囘家,要把這好消息吿訴爸爸,那知剛走到胡同口,看見爸爸在前邊搖搖擺擺說的哼 着落子一路進去,樣子也是滿起勁似的。
「爸爸!」蕙英從後邊追了上去。
「蕙英呀,我找到事了!」
「呀!我 也給你找到事啦!小學敎員!」蕙英把劉仰山的話說了一遍,「那麽,我去敎書!」
「不,你念大學,一定給你念大學!」
「是嗎!」蕙英歡喜得緊緊拉住爸爸的手。
這個喜訊一路傳揚進來,梅英海海也跟在後邊嚷着「爸爸找到事了。」連院子的隣 居都出來道賀。
「找到了什麽事啊,看你瘋成這樣子!」太太從厨房裡奔出來,口裡佯惱着,心裡却早樂不可抑了。
「說眞的,爸爸,究竟是什麽事呀?」
「好差使,好差使,相面的說我鬍子壓住了好運,果然…」
「爸爸,你儘管講鬍子,快說啦!」
沈子鈞早就編好了一套謊話,他說有一個朋友的兒子,最近發了財,要在天津找個商行代理人,「今天運氣眞好,剛出 去碰到他,一說就成……哈……薪水佣金,說是每個月至少有十萬塊,比銀行裡强得多啦!」他說得高興,抱起海海轉了個圈子。
屋子裡充滿了幾個月從未有過的愉快的氣氛,孩子們這一時也嘗夠了窮苦的滋味,對爸爸重獲職業的喜訊眞是歡騰不已。
從此,沈子鈞每天早出晚歸,有時忙到夜深才囘家,做生意,當然得應酬,家裡又過着和平安靜生活,蕙英進了大學,太太因爲丈夫有了地位又有錢,在外邊遇上了熟人也覺得很有光彩。
小潤的母親顧太太原是個勢利人,她要蕙英唸大學,也無非是想較量一下沈家的境况 ,現在得知沈子鈞當了商行代表,地位很不錯,對沈家就更熱絡起來了。
一天星期日,她特地請沈氏夫婦去吃飯,可是沈子鈞說 行裡忙不過來,讓太太帶了孩子們去了。顧襄理和太太都殷勤招待,孩子們擁在客廳裡聽收音機,這一檔節目恰巧是著名潮流滑稽大家笑笑笑唱的夫妻相罵,有聲有色,客廳裡只是一片笑聲,蕙英小潤也親熱地坐在一起,梅英聽得忍不住奔進房去。
「媽媽,快來聽 ,笑笑笑唱的!」
說也奇怪,這新起的相聲家的名氣忽然紅遍了電台,連顧襄理也佩服他的玩藝。
「哎,他的玩藝可眞不錯!」
「我才不愛聽呢。」顧太太不屑地向他看了一眼,「你說好笑,我只覺得低級,下流,粗口!」
沈太太當然也附和着顧太太的見解,節目完了,小潤同蕙英一同囘學校去了,望着他們走後,顧太太一本正經笑咪咪地說了,「其實他們眞是一對,沈太太,你說怎麽樣?」
這一次她是誠誠心心的給兒子提親了,說是蕙英品人好,書讀得好,家裡又是世代書香,這門親事才眞是門當 戶對,沈太太聽了好不歡喜。
「你說得好,只要你們不嫌棄,我們還有什麽說的!」
「好,那就這麽說定了,」顧太太笑向顧襄理,「以後的事你去和沈先生當面細談吧!」
晚飯後,沈太太滿懷髙興的帶了梅英海海囘家,去到胡同裡,望見家門口擁 了一大堆居孩子們,歡呼騰騰,不知道什麽事,擠上前一看,不料沈子鈞挑着彩担在跑大補缸的圓塲,林振庭在一邊點撥他,沈太太一看怒不可抑。
「我以爲你眞的公司有事,還替你在顧家吿罪呢,原來你………」
沈子鈞一怔,忙裝着小丑似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學着玩兒麽!」說着把彩担交還林振庭道了謝,隨着太太進屋子去。
「快做岳父了,還這麽個樣子!」
「怎麽婚事談成啦!」
「以後少跟他打交道,多沒出息!」太太還在生氣。
沈子鈞不敢多說,抱起海海做了個鬼臉。
這一 天合該有事了。
學校的女生宿舍裡嘻嘻哈哈的一片嬌笑聲,幾個女同學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要去喝喜酒了。只有蕙英還在埋頭用功 。
「女博士,還不化粧,劉美娟的喜酒去不去喝了?」
「去,急什麽?又不是你當新娘!」蕙英笑着還是看書。
正在這時,小潤來了,說是爸爸媽媽也有請帖,所以特地來約蕙英一同去的,蕙英對這未來的婆婆不但拘謹而且還有幾分怕懼,一聽之下,連忙進去趕快化粧,剛才說她說笑的同學這時可翻本了。
「喔,沈蕙英,急什麽?也要做新娘了嗎?」
又是一陣嘻笑。
這席喜事排塲可不小,禮堂裡賓客滿座,台上正在唱大鼓,歡笑聲,猜拳聲,拍掌聲,鬧成一片,正中一席坐着顧襄理顧太太, 王太太趙太太,小潤蕙英,還有一班同學們。
大鼓唱完了,檢塲的擺出桌子,掛上「笑笑笑」三個繡花大字的桌圍,四周立刻响 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因爲這笑笑笑的滑稽,大家在電台裡聞名已久,今天可見個眞面目了。
鑼鼓聲起,笑笑笑挑了担子扮着王 大娘補缸登塲了,一個滑稽圓塲,博得了全塲彩聲。
忽然,顧太太和蕙英的臉色變了,台下幾個熟人已先認出,原來笑笑笑就是 沈子鈞的化名。
「想不到就是他!」顧襄理低聲對太太說了。
「你父親不是說是商行代表嗎?」顧太太沉下了臉問蕙英。
蕙英大窘,低頭不敢作聲,只聽得一邊的趙太太在嘆氣,「唉,人窮志短,也是沒有辦法!」
多事的王太太偏偏故意向顧太太微笑着問,「顧太太,聽說你跟沈子鈞已經結成親家了?」
「沒有啊!」顧太太連忙否認。倏的站起來就往外走,顧襄理尶 尬地望着蕙英,蕙英哭笑不得,她的神情引起了同學們的注意,忽然,一個同學發覺了。
「咦,蕙英,笑笑笑就是你爸爸?」
蕙英再也忍不住了,起身疾走,小潤在後邊叫着追出來,台下一陣騷動,台上的沈子鈞這時也看到出走的蕙英了,他心裡一楞,他還是勉强提神演唱,台下叫好聲不絕。
蕙英哭喪着臉奔囘家中,鎖上房門,倒在床上縱聲大哭,顧太太的鄙視的臉,否認婚事的聲 音,以及同學們的耻笑,一齊湧上心頭,她難過極了。
沈太太正在燈下給梅英海海補習,猛見蕙英神色蒼白的奔了囘來,以爲她 病了,連忙放下書跟進去,那知她把門鎖了,只在裡邊哭,沈太太驚慌異常,不知道出了什麽事了。
「姐姐,姐姐!」梅英海海 也拚命捶門叫喊。
正在這時,沈子鈞挾了公事包匆匆趕到了,沈太太一見他囘來,舒了口氣,「噢,你囘來了,蕙英不知道出了 什麽事,在房裡儘是哭,怎麽也不肯開門!」
沈子鈞一句話也不說,發狂似的把門撞開了,一直走到蕙英身邊,推她叫她,蕙英 只是不理他,反而哭得更慘了,太太在一邊見他臉色慘白,莫名其妙。
「到底什麽事?你怎麽啦?」
「唉,怎麽啦!我自己都不明白!」他感傷已極,涙和聲下,「我爲了愛你們,愛家裡每一個人,到頭來,還是我錯了,哈……這是從何說起……」
「我剃鬍子,唱滑稽,說相聲,全是爲了你們呀!」他毫無顧忌的大聲叫着。
「啊!」太太這才明白,生氣地一下子跳起來,「 原來你不是商行代表?你!你叫女兒怎去見人!」
沈子鈞的心裡像一陣刀刺,痛苦,悲憤,交織在他的心中,他受盡了委屈與苦 難,現在連自己的太太女兒都不能諒解他!那他辛辛苦苦的究竟是爲了什麽!
「蕙英,是我讓你當着大家難堪了,傷了你的心是 不是?……唉!」他嘆了口氣沉重地,「我受得住,你應該也受得住!」
蕙英的哭聲轉爲悲切的嗚咽了!
沈子鈞再也忍不住把滿腹的委屈向她們傾倒了。
「我活了這麽大年紀就不愛面子,不知自愛?你們難道不知道我爲什麽?爲什麽?我心裡也曾多 少次徬徨矛盾,我也知道終有一天會給人發覺,可是我終於對自己說,爲了孩子們的前途,犧牲你自己吧,別再講面子啦,我這才咬咬牙關登上了台,難道這是我自願的嗎?當我在台上裝着笑臉時,心裡老是提心吊胆的,怕給人認出了………可是爲了生活………」
這悲慘的感人肺腑的話說得太太和蕙英都悲泛起來了。
「爸爸,我知道你的苦楚!」蕙英哭着說。
他愈說愈激動,從公事包裡拿出一付袖罩一條辮子狠狠地向自己頭上亂打,「爲了要讓你念大學,我不做小學敎員,做了滑稽,我對不起你們了!」
蕙 英痛悔已極,抱住了爸爸。
「爸爸,是我們錯了,你爲我們受盡了委屈,你愛我們,你是我們的好爸爸!」
「要是小潤……他……」子鈞還在爲她的婚事不安。
「沈伯伯,我在這裡!」
原來小潤早己來到門口,他聽到了沈子鈞的痛心的話,爲他的偉大的父愛感動得流下淚來,他緊緊的拉住了蕙英的手,激動而誠懇地說。
「蕙英,沈伯父的話是對的,我愛你,我决不會 ………」
沈子鈞望着他們,淚眼中露出了安慰的微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