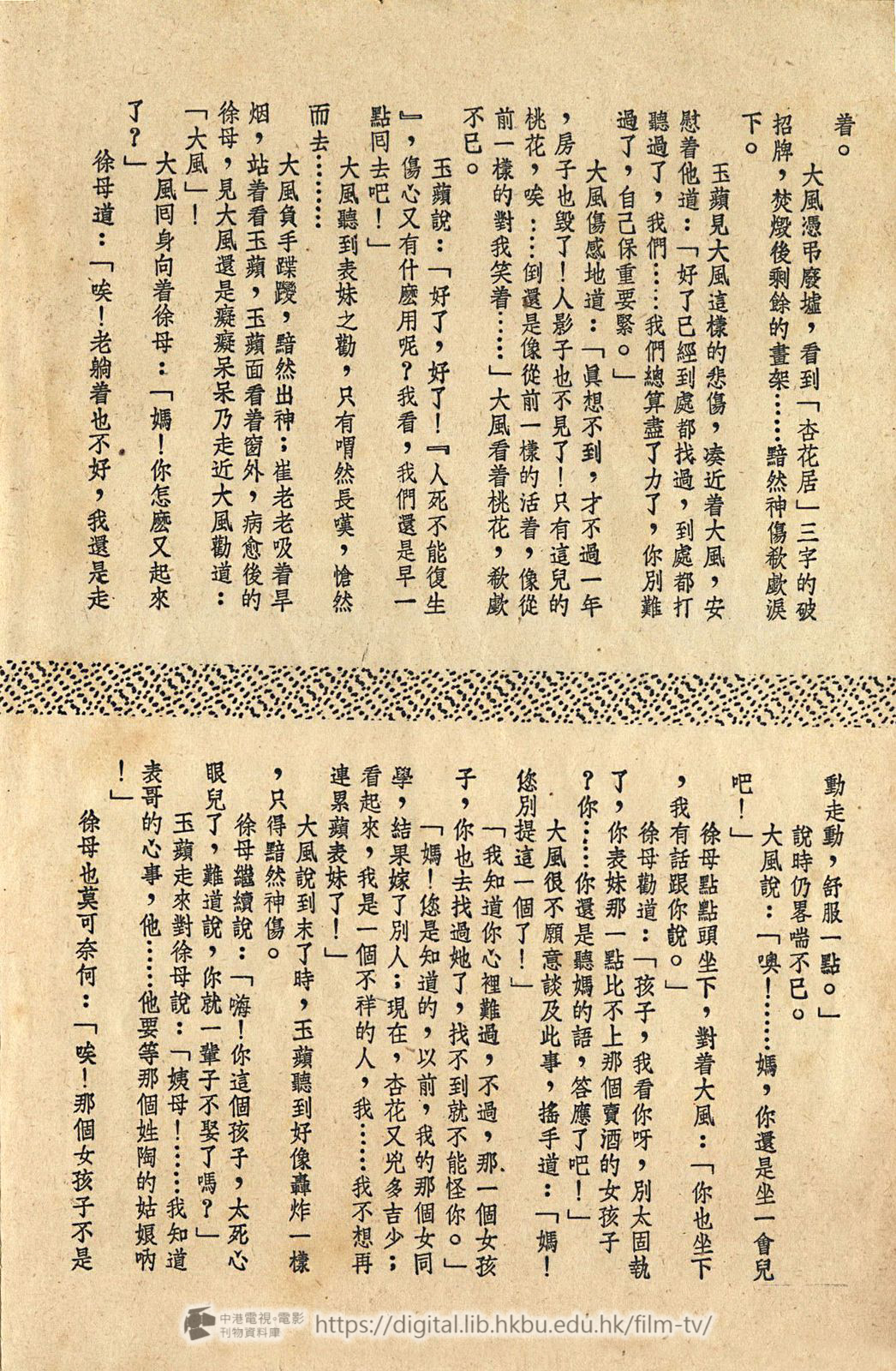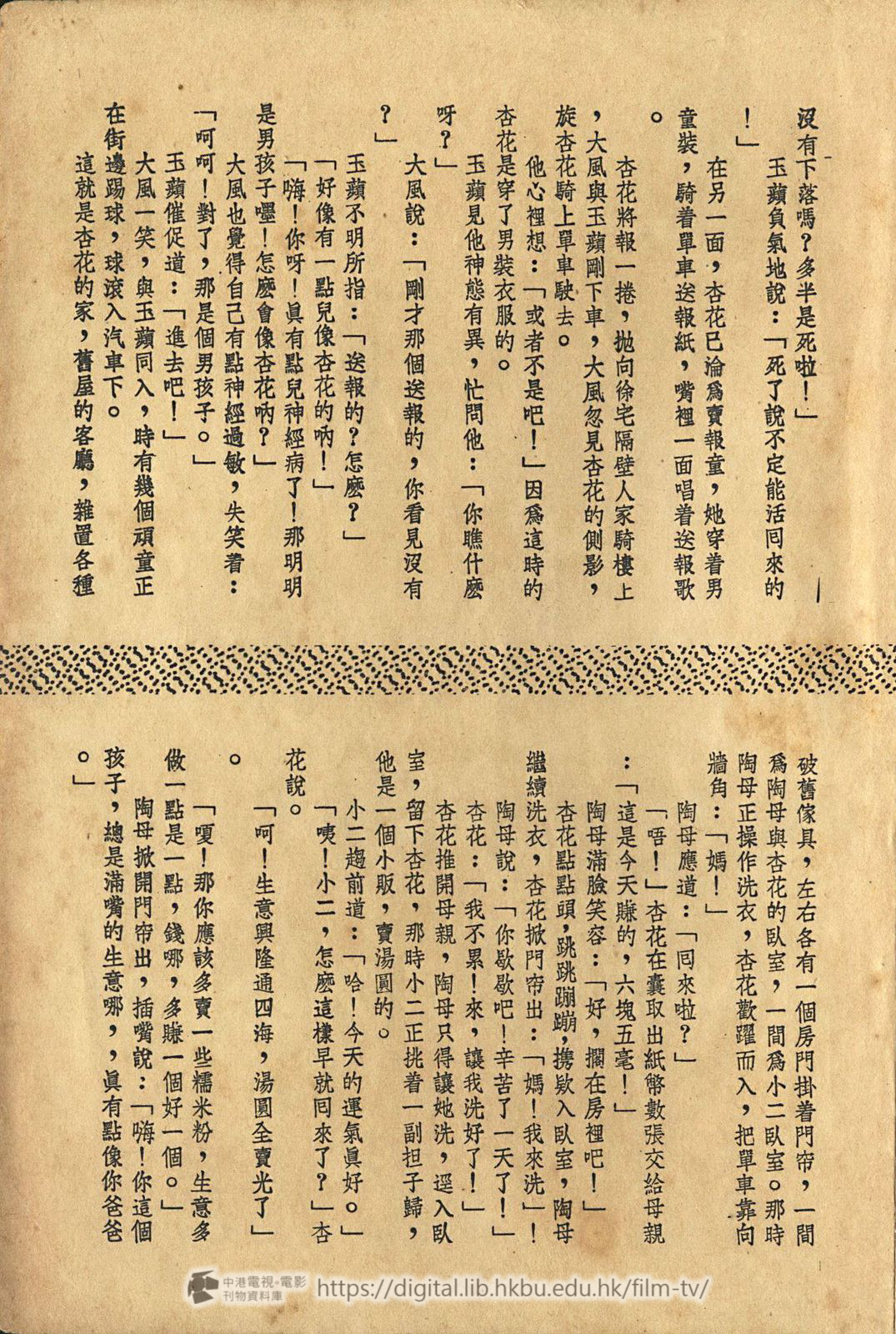風雨桃花村
.電影小說.
三月的桃花村,正是鮮艷的桃花盛開的季節, 遠遠的林裡傳來了陣陣的歌聲,金哥銀鳳在阡陌間騎牛吹笛,迤邐而來,途中適逢陶杏花手携筠藍送酒歸來,金哥憨怒着招呼她:
「嗨!杏花,妳又送酒去啦?」
「唔!」杏花一面走着。
「要不要我來幫妳?」金哥指筠藍向前討好。
「用不着,我自己會拿的。」杏花逕去。
「哼!拍馬屁拍到馬脚上去了!」銀鳳鄙夷地對金哥譏諷,然後他們跟着杏花而走。是時天空忽 然陰暗,杏花囘頭對他們說:
「明天是清明了呀!清明時節雨紛紛…」
金哥接着說:「對了!對了!清明時節雨………」
「不害臊!祇會學人家說話。」銀鳳又鄙夷地指金哥。
雨快要下了,他們急着而歸。
紛紛的雨花,飄下了鄕村, 花木叢中青年畫家徐大風在寫生,忽見兩越下越大,隨卽收拾畫具,急着找地方躲雨,在奔走中適遇金哥,便由金哥指路,扶大風騎上牛背,金哥牽牛向杏花村而去。
杏花居是陶杏花的家,裡面陶母開設的酒店,是村裡人們消遣醉酒的地方,那時在風雨中杏花跳躍 而入,裡面滿坐酒客,他們見杏花歸來,莫不高興地叫喊着,杏花隨卽拿酒壺斟送,一面天眞地唱歌,無數酒客們都沉醉在她的歌聲裡。
在歌聲中大風騎着牛,金哥牽着而至,大風一見杏花便呆住了,金哥摧促着:
「喂!到啦!」但大風仍出神地望着杏花。
「下來!下來!」金哥再摧促着大風。
「喔!喔!」大風如夢初醒地捧着畫具走下來。
那時杏花在內,起了一鬨 笑聲,然後杏花發現金哥。
「金哥!怎麽啦?」杏花大聲喊着,跑了出來。
「嗨!」金哥指着大風:「這位客人他要喝點兒酒檔檔寒氣,我就把他帶到這兒來了。」又轉向大風:「你不是要喝酒嗎?怎麽不進來呀?」然後大風逕入酒店。
進了酒店, 杏花吩咐工人小二將火盆端來,指點着放在大風座旁,對大風說:
「瞧!你的衣裳也淋濕了。」杏花又着小二送酒來。
那時杏花居門外,村女銀鳳發見金哥在內,披披嘴,惡作劇地將金哥的牛放走。
金哥發現牛逸去,大爲着急,連忙追上去,駡銀鳳 :
「死丫頭,我的牛!我的牛!」金哥追得很遠去了。
酒店內大風和杏花坐在一起喝酒,大風讚美道:
「唔!這 酒眞不錯!」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杏花忽然看到坐旁的畫具,好奇地問:
「這是什麽?」
「喔!這是畫。」
「畫得眞好,是你畫的?」
「是的,畫的是桃花,」大風嚥下一口酒:「你們這兒叫桃花村是不是?」
「一點兒不錯,你瞧!」杏花指着門口:「我們門口也有桃花樹。」
於是大風和杏花一起走至桃花樹下。
「那麽你們的招牌為什麽又叫杏花居呢?」大風問道。
「這名字不能叫嗎?」
「我猜一定有個道理!」
「或許有,可是我不能告訴你!」杏 花畧沉昑地囘答,一會兒,視線又向畫具投射了一下:「唔!告訴你也可以,不過我不能白白的告訴你。」
「嗄!難道有什樣條 件嗎?」
「對了!有一個條件!」杏花嬌嗔地道:「就是替我們店裡畫一幅畫,掛在牆上。」
「可以!可以!等天晴了我一定替你畫!」大風高興得跳起來。
過了幾天,大風和杏花相約到郊外去了,他們雙雙的在桃花林下作畫,杏花一面在唱歌,大 風一面在欣賞着三月裡的綺麗的村莊,加上了杏花那美麗的歌聲,大風就沉迷在這美景之下了。
杏花唱完了,接着是大風的一陣 掌聲,杏花嬌嗔地依在大風身邊,突然發現大風的畫幅上一片空白,大爲詫異:
「怎麽?你……你還沒有畫呀!」杏花着急地問 。
「你放心!我一定替妳畫……噯,坐下,「我問問妳,」於是杏花坐在草地上。
「你……可以把原因告訴我了吧!」
「其實也沒有什麽原因。」杏花笑着說:「不過因爲我是二月裡生下來的,二月是杏月,所以爸爸替我起了這名字。」
「噢!你爸爸呢?」
「過世了,就留下我們娘兒倆,還有那間酒店。」
「你們的酒是自己做的嗎?」
「唔……我爸爸 活着的時候,就是會做酒,所以開了這間酒店,開店那幾天恰巧就生了我,所以連招牌也題上了「杏花居」三個字。」杏花忽然道:「好!現在該輪到你告訴我了。」
「噢!」大風笑着:「我姓徐.名字叫大風。」
「大風?我猜你一定是刮大風的時候生下來的。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大風和杏花一陣大笑。然後杏花又問道:
「你是從那兒來的?怎麽從没有看過你!」
「我是從省城來的,現在躭在我姨夫家裡,就是後面虎岡村的崔家。」
「嗄!那麽你還要囘到省城裡去?」
「暫 時不囘去,」大風搖搖頭,指畫架;「我的畫還沒繳卷呢!」
「那麽你該動筆了。」
「唔!」大風點點頭。然後開始作畫,口中唔唔唔地,揑了筆,醮了一下顏色,又囘顧杏花。杏花含情脈脈地,低下了頭,輕輕地說:
「畫呀!……畫好了我再請你 喝酒。」大風一笑,開始作畫。……
到了黃昏,大風的畫已完成了,掛上了「杏花居」的牆上,杏花高興極了,並拿親自製作的 「女兒紅」酒欵待大風,而且杏花唱歌助興。
那時陶母觀見,覺得杏花興奮過度,又恐杏花對大風鍾情,不覺皺眉,於是呼喚杏 花:
「杏花!杏花!」
「媽!怎麽啦?」杏花聞喚而至。
「你怎麽啦?去了那麽半天,囘來了又哇拉哇拉地唱, 當着陌生人面前不害臊嗎?」陶母指責杏花。
「嗄!我當是什麽呢!……人家畫了一幅畫,送給我們,我們請他喝點兒酒,不是 應當的嗎?」
「喝酒就喝酒,為什麽還要唱歌?」
「噢!唱歌又不花本錢……。」
那時大風叫着杏花。杏花跑了 過去。
「怎麽?就要走了?」
「時候不早了,該走了。」取了畫具:「謝謝你的女兒紅。」
「謝謝你的畫!」
「再見!」大風又低聲說:「你媽好像不歡迎我。」
「沒有的事,」杏花輕輕地安慰大風。
陶母隨卽趕來,向杏花問道:
「那個姓徐的,住在虎岡村,是嗎?」
「是的,」杏花留戀着說:「虎岡村,………崔家!」
那一晚,大風 在崔家的客廳裡,呆呆地向着窗外思疑,姨夫之女玉蘋,尙未對大風甚感興趣,突見表哥神態不常,便向前問道:
「表哥!」
「噢!玉蘋。」大風一個驚聳,忙着囘應。
「你怎麽啦?心裡有事嗎?」
「沒什麽!……沒有什麽。」
「表 哥,你答應教我畫畫,現在就教教好嗎?」
「噢……這個,還是明天吧!」大風期期艾艾的。
次日清晨,大風又匆勿地從客廳溜出去了。玉蘋目見大風而去,心裡不禁起了懷疑,後與其父崔老老商議,並指大風行動有異,决同往「杏花居」探大風之行踪。
崔家工人高昇和玉蘋走至「杏花居」,見並無大風踪影,相顧愕然,兩人便匆匆離去。途中金哥牽牛而至,注視玉蘋和高昇,但在 他的心裡早已認識那兩位是崔家小姐和長工了。
金哥見此情景,知崔家找尋大風踪影,隨卽便四處尋找杏花和大風,直至樹林旁 邊,忽發現杏花和大風,在林下雙雙唱歌,那親切倩影,眞使金哥難受,因此便一肚子氣的跑到崔家,準備告密。
金哥將所遇對 玉蘋報告後,氣得玉蘋痛恨不已,知大風對己不誠,捧頭鳴咽一番。時適大風囘來,見金哥在内,不禁吃了一驚,又見玉蘋形態有異,已知此乃金哥之所幹,玉蘋隨卽奔近大風前痛斥一頓:
「怪不得你急着要走,原来你『另有貴幹』,忙得很吶!哼!」說完便離去 。
大風知金哥來此告密,便責斥金哥:
「嘿!一定是你,你眞有本領搗蛋!」金哥以笑掩飾,愴惶取鋤遁去。
次 日,大風領着高昇到「杏花居」喝酒,因爲高昇是個有名的酒徒,而大風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能使用高昇做敢死隊,替自己在陶母面前求親。不料事很凑巧,陶母一聽此言便搖首拒絶:
「我們是鄉下窮人,怎配得上城裡有錢的濶少爺呢?再說攀親總得講個門當戶對, 鄉下人跟城裡的人路差得太遠了,所以我們不敢高攀!」結果陶母又拒絶了。
「那……那麽,我們再商量商量好嗎?」高昇無奈 地說。
「没有什麽好商量,你知道嗎?我就祇有這麽個女兒,就是要嫁,也得招女婿,我不會讓她嫁到城裡去的!」
爲了愛情之逐使,大風又無條件的投降了。
「嗨!老太太,我們表少爺答應了,他願意做招女婿!」高昇又第三次地充任炮灰。但結 果陶母仍是搖首拒絶。
兩人失敗後,各有心情,高昇利用良機痛飲一塲,而大風爲了愛情波折,心緒如麻,也只得借酒消愁,於 是他們在那晚便醉倒在「杏花居」了。
陶母等急得直跳,又恐出事,那只得顧用四個鄉人,用板門兩塊,把大風和高昇躺在上面 ,鄉人把他們抬了囘去。當晚,崔老和玉蘋却吃了一驚。
第二天,大風忽接家信,謂母親病危,要大風馬上返家一趟。大風獲此 消息,急於尋見杏花,並告知其明天早上要乘船離此,一時杏花難分難捨,眼淚滿眶,而大風亦是苦悶到欲慰無語了。
次日早上 大風便乘船囘去了。
杏花自分別了大風,生活憂鬱不樂,於是在晨熹,在黃昏,她依舊孤零零地站在桃花林下;河水邊自唱自嘆 ,在她心堆裡依舊是惦念大風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了,大風仍無音訊,杏花更掛念,在徬徨之際,忽想一巧計,利用金哥到崔 家去找取消息,但並不明言,而採用「打賭」之方式,聲明如能一走,必定給金哥大醉一番。因此金哥果被蒙過。不料銀鳳走來隱約揭穿杏花之謀,銀鳳說:
「嘿,你呀,眞是個大儍瓜!」
「什麽?我是個大傻瓜?誰說的?」金哥勇以辯護。
「哼! 上了人家當還不知道,不是儍瓜是什麽?」
「我……我上了什麽當了?」
「你呀!眞是猪油蒙了心,糊塗透頂了!……這還不明白嗎?那鬼丫頭要你替他跑腿,什麽打賭不打賭!」銀鳳直折穿杏花之計。
「嗄!……跑腿?咄!你以我眞是大儍瓜?我 才不替他跑腿呢!」金哥始恍然大悟。
次日,金哥搖搖擺擺地走至杏花居,杏花一見金哥以爲好消息駕臨,便迎頭催向金哥:
「怎麽樣?去打聽過了嗎?」
「先請客,我再說。」金哥狡黠地說。
於是杏花對金哥大舉招待,吩咐盪酒切火腿,金哥大爲得意,挺胸昂首,以指擊桌,似乎成了個貴客一般,但金哥被「招待」了半天仍不說話,衹顧嘴之鮮味,故急煞了杏花:
「喂!怎麽樣?」杏花低低地說。
「嗄!….喔!徐先生……沒有信給崔家。」金哥也低低地囘答。
「沒有信?」
「昨天我去過了,沒有接到信。」但杏花巳起身離坐了。
「噯!我想徐先生總有一天會寫信的,假如一有信我就來報信,而且每天去一趟,以後再不要你請客了,完全盡義務,好嗎?」金哥自作聰明地安慰杏花。
「好!今天晚上我在小屋子等你消息!」
當晚,杏花獨自在小屋裡等金哥囘音,忽聞敲門三下,杏花以爲金哥踐約而至,連忙去開門,誰料門一拉開,一個大黑影撲了進來,原來是地方壞蛋而且垂涎杏花已久的馬德奎,這囘便撲進杏花身邊來了,杏花一叫,馬德奎用手帕塞進杏花口中,擁住杏花。
倆 人掙扎之際,馬德奎忽失足捽在酒罎堆裡,酒罎紛紛倒下,壓得馬德奎滿頭鮮血,卽時陶母聞呼救之聲,便急着拔門而入,一進裡面,不禁大吃一驚,而杏花連忙呼喚強盜!
那時金哥才至,聞言大訝;
「什麽,這兒有強盜?」
那時馬德奎掙扎而起, 流血滿面,拾起手巾拭額,忽大怒道:
「啍!這是怎麽着,你們……你們存心謀財害命!」
「什麽?你……你自己不安好心,闖進這屋子裡來欺負人,反而誣賴別人,你……你不害臊!」杏花指斥馬德奎。
「嘿!明明是你開門給我,你想賴呀!」馬 德奎仍兇兇地依賴着。
「爲什麽你跑到這屋子裡來呢!是你自己開門給他的嗎?」陶母很詫異地,金哥也莫名奇妙地站在那兒。
那時馬德奎雙目兇狠,聲言决往報警,以謀財害命之號,和杏花决打官司,陶母聞語大吃一驚,杏花因母着慌,也躭愛起來,衹得金哥向馬德奎講和。
「不打官司也可以,除非杏花嫁給我,咱們結了親,寃家變成親家,我……我就不告你們,限三天以內囘答 我,要不然!嘿!非打官司不可!」馬德奎以拳擊桌,兇兇囘答金哥。
陶母和杏花面面相覷,互抱啜泣不巳。
於是,杏花的心頭又加上了一個重担,加上了惦念大風的苦哀,她的心情就更如醉如麻了,她終日孤獨地在郊外悲歌自嘆,總想盼望着大風歸來。
馬德奎的三天期限,巳經是第二天將過去了,那晚狂風雨夜,杏花哭泣甚哀,祇得陶母慰之。共渡風雨苦夜。
第三天了,馬德奎果然帶兩個爪牙大搖大擺地走向杏花居,誰料一進酒店,却是一片哭聲,混亂連天,陶母號啕大哭;
「杏花呀!我的孩子, 你怎麽就那樣丢了我走啦?……」
那時王小二,馬上氣冲冲的走上德奎前面說:
「好!姓馬的,來得正好,我們大姑娘給你逼得投了湖,死了,」小二又轉向衆酒徒:「好!我們得逮住他,跟他打官司去!」衆酒客齊聲响應,嚷着擁上德奎,馬德奎見勢不隹,與兩爪牙亟亟逃退,衆人一面而追,馬德奎一面奔逃,一面朝天開槍而至脱險。
而戰事發生,彈烟硝雨,沖天而起,鄉人均紛 紛逃難去。
刦後的杏花居,只剩了斷垣殘,壁屋外大大的桃花樹,大風與王蘋,刦後餘生,衣衫襤褸,重臨舊地,不禁愴然淚下 ,皆搖首嘆息着,而「人面桃花」一曲也好像在他們耳邊响着。
大風憑弔廢墟,看到「杏花居」三字的破招牌,焚燬後剩餘的畫 架……黯然神傷欷歔淚下。
玉蘋見大風這樣的悲傷,凑近着大風,安慰着他道:「好了已經到處都找過,到處都打聽過了,我們 ……我們總算盡了力了,你別難過了,自己保重要緊。」
大風傷感地道:「眞想不到,才不過一年,房子也毁了!人影子也不見 了!只有這兒的桃花,唉……倒還是像從前一樣的活着,像從前一樣的對我笑着……」大風看着桃花,欷歔不巳。
玉蘋說:「好 了,好了!『人死不能復生』,傷心又有什麽用呢?我看,我們還是早一點囘去吧!」
大風聽到表妹之勸,只有喟然長嘆,愴然 而去………
大風負手蹀X,黯然出神;崔老老吸着旱烟,站着看玉蘋,玉蘋面看着窗外,病愈後的徐母,見大風還是癡癡呆呆乃 走近大風勸道:「大風」!
大風囘身向着徐母:「媽!你怎麽又起來了?」
徐母道:「唉!老躺着也不好,我還是走動走動,舒服一點。」
說時仍畧喘不巳。
大風說:「噢!……媽,你還是坐一會兒吧!」
徐母點點頭坐下,對着大風 :「你也坐下,我有話跟你說。」
徐母勸道:「孩子,我看你呀,別太固執了,你表妹那一點比不上那個賣酒的女孩子?你…… 你還是聽媽的語,答應了吧!」
大風很不願意談及此事,搖手道:「媽!您別提這一個了!」
「我知道你心裡難過,不過,那一個女孩子,你也去找過她了,找不到就不能怪你。」
「媽!您是知道的,以前,我的那個女同學,結果嫁了别人;現在, 杏花又兇多吉少;看起來,我是一個不祥的人,我……我不想再連累蘋表妹了!」
大風說到末了時,玉蘋聽到好像轟炸一樣,只 得黯然神傷。
徐母繼續說:「嗨!你這個孩子,太死心眼兒了,難道說,你就一輩子不娶了嗎?」
玉蘋走來對徐母說:「姨母!……我知道表哥的心事,他……他要等那個姓陶的姑娘吶!」
徐母也莫可奈何:「唉!那個女孩子不是没有下落嗎?多半 是死啦!」
玉蘋負氣地說:「死了說不定能活囘來的!」
在另一面,杏花巳淪爲賣報童,她穿着男童裝,騎着單車送報紙,嘴裡一面唱着送報歌。
杏花將報一捲,抛向徐宅隔壁人家騎樓上,大風與玉蘋剛下車,大風忽見杏花的側影,旋杏花騎上單車 駛去。
他心裡想:「或者不是吧!」因爲這時的杏花是穿了男裝衣服的。
玉蘋見他神態有異,忙問他:「你瞧什麽呀?」
大風說:「剛才那個送報的,你看見没有?」
玉蘋不明所指:「送報的?怎麽?」
「好像有一點兒像杏花的吶! 」
「嗨!你呀!眞有點兒神經病了!那明明是男孩子嚜!怎麽會像杏花吶?」
大風也覺得有點神經過敏,失笑着:「呵呵!對了,那是個男孩子。」
玉蘋催促道:「進去吧!」
大風一笑,與玉蘋同入,時有幾個頑童正在街邊踢球,球滾入汽車下。
這就是杏花的家,舊屋的客廳,雜置各種破舊傢具,左右各有一個房門掛着門帘,一間為陶母與杏花的臥室,一間爲小二臥 室。那時陶母正操作洗衣,杏花歡躍而入,把單車靠向牆角:「媽!」
陶母應道:「回來啦?」
「唔!」杏花在囊取出紙幣數張交給母親:「這是今天賺的,六塊五毫!」
陶母滿臉笑容:「好,擱在房裡吧!」
杏花點點頭,跳跳蹦蹦,携欵入臥室,陶母繼續洗衣,杏花掀門帘出:「媽!我來洗」!
陶母說:「你歇歇吧!辛苦了一天了!」
杏花:「我不累!來,讓我洗好了!」
杏花推開母親,陶母只得讓她洗,逕入臥室,留下杏花,那時小二正挑着一副担子歸,他是一個小販,賣湯圓的 。
小二趨前道:「哈!今天的運氣眞好。」
「咦!小二,怎麽這樣早就囘來了?」杏花說。
「呵!生意興隆通四 海,湯圓全賣光了」。
「嗄!那你應該多賣一些糯米粉,生意多做一點是一點,錢哪,多賺一個好一個。」
陶母掀開門帘出,插嘴說:「嗨!你這個孩子,總是滿嘴的生意哪,,眞有點像你爸爸。」
小二發表意見了:「杏花姑娘說得對,錢多賺一個 好一個,明天哪,我得多預備一點貨,反正明天賣不掉,後天還可以賣。」
「晚上我幫你多做一點」杏花說。
「好……噯,你說替我編一個賣湯圓歌,編好了没有?」
杏花點頭道:「編好了,晚上做湯圓的時候,我教你唱。」
小二聞言大樂:「好!」
到了晚上,陶母,杏花,小二,三人做着湯圓,杏花與小二合唱「賣湯圓」歌。
杏花越唱越興奮:「來,再來一遍。一!二!三!」
他們一起唱着賣湯圓歌,歌畢,小二大笑。
第二天,王小二又挑着湯圓担子停在一家住宅門外,唱着賣湯圓歌,婦人牽着孩子紛紛的來吃,小二一邊唱,一邊賣,杏花踏車而去,小二注視杏花而笑,杏花在車上對小二揮手而去。
徐宅門外,有彈鋼琴聲自窗外傳出,杏花帶着晚報成叠,推單車而過,聞琴聲,詫異,止步,聽着走近窗口,琴聲止,適有大漢自門內出,睜目注視杏花,杏花見大漢怒目而視,急急踏車而去。
囘到家裡,杏花把經過告訴母親,並說决定去問問,陶母勸她不要去問 。杏花疑竇未釋,次日下午,將一份報紙抛向徐宅隔壁的騎樓,然後走近徐宅窗口,傾聽着琴聲,不料頑童追逐蹴球,一球飛起,球飛到,打破了徐宅的玻璃窗,杏花驚惶囘顧,衆頑童見闖出了事,均速逃,杏花深恐受疑,亦拔脚逃開。大風白內追出,杏花剛欲踏上單車,大風一把將她抓住,杏花囘顧,見是大風,怔住:
「啊呀!……徐……徐……徐先生」
「呀!是你,杏花。」大風打量着杏花。
「是呀!我就是杏花。」杏花自覺自慚形穢。
「我們到裡面談吧!」大風說。
杏花叙述别後經過:「那個 姓馬的限三天給他囘音,她急得沒法子,只得裝死,後來又遇到打仗,只有急忙逃了出來。」大風聽了忽對杏花說:「給你一個喜訊,那個姓馬傢伙,給打仗打死了。」
仗己經打完了,陶母一定要囘去重振「杏花居」,雖然他們有點不捨分開,但陶母一定要去,只 得沒辦法。
陶母,杏花及王小二結伴囘鄉,在歸途中,忽然傳來汽車喇叭聲,杏花見是大風,大喜,他們一夥兒便從樂聲緩緩而 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