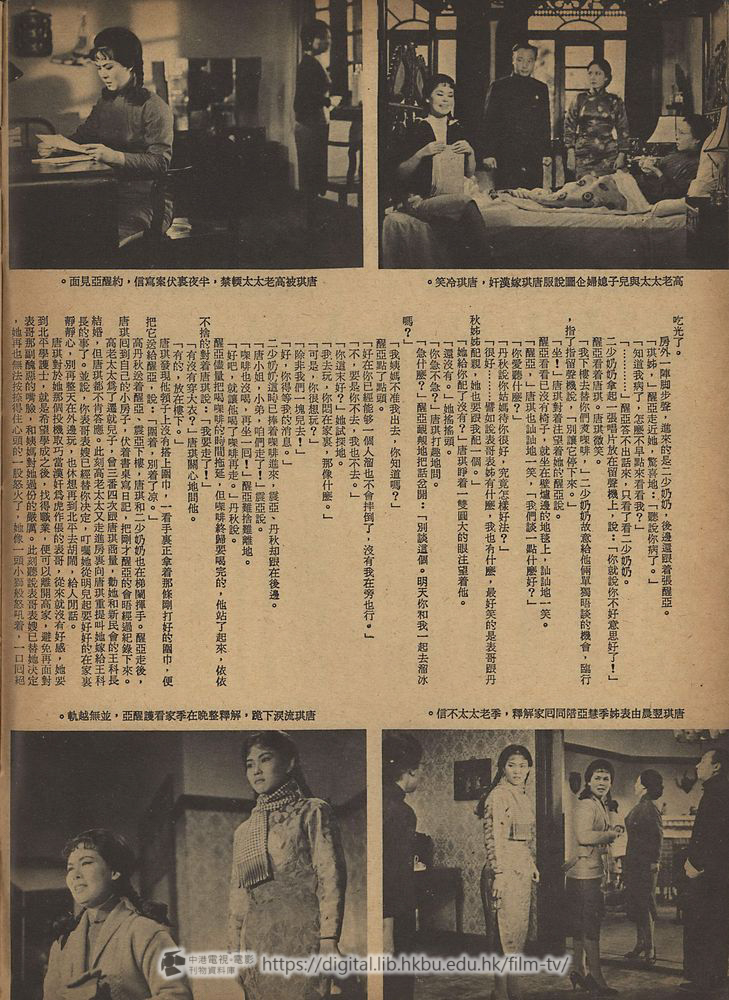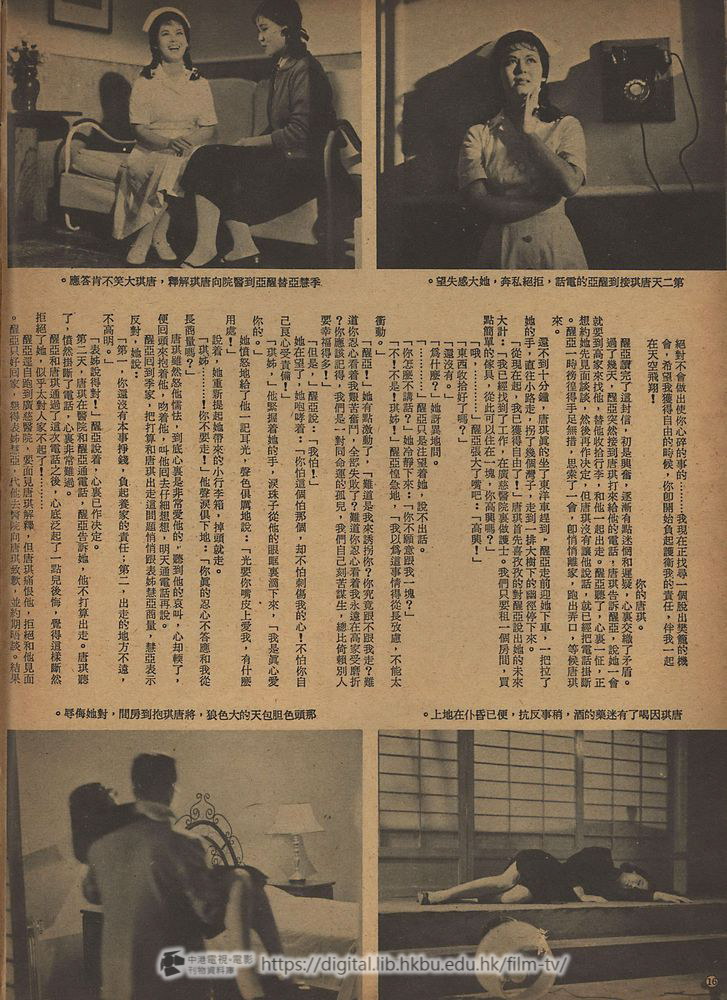藍與黑
電影小說
上集
一
藍色象徵光明,它代表了自由仁愛。
黑色象徵陰暗,它代表了陷阱深淵。
二
唐琪是一位外型美麗,内心爽朗的十九歲少女,當她幼小的時候,父母就已相繼去世,依靠着姨母高老太太撫養成人。高家世居天津市的英租界,是個守舊的禮敎家庭,高老太爺逝世已久,留下高老太太和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少爺和大少奶奶是一對夫唱婦隨的投機份子,熱中追求名利,利之所在,不擇手段,絲毫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二少爺留學英倫,讓年青的二少奶奶獨守空閨,侍奉老太太。二十歲的女兒高丹秋,已經和遠房親戚攀了親。高老太太對於唐琪這個姨甥女雖然疼愛,但管束很嚴。而唐琪與大表哥和大表嫂之間,由於彼此性情思想有很大的距離,相處得並不融洽,但她和二表嫂及表姊丹秋的感情却不錯。
唐琪天資聰慧而個性堅强,她認爲長此寄人籬下,决不是辦法,因此她在高中畢業之後,即單獨離開天津,到北平去,在一家徳國人開的醫院裏學習護士,準備學成之後,自食其力。
高丹秋的未婚夫是季震亞。季家也是世居天津的一個家庭,季老先生和季老太太除了廿一歲的兒子震亞,十八歲的女兒慧亞之外,還養着一個内侄兒張醒亞。醒亞是個十七歲的孤兒,他父親原是革命軍人,在民國十一年從廣州出發北伐,不幸在贛州戰死,醒亞這時才兩歲,接着,他母親也因憶夫成疾,不治謝世。醒亞孤苦伶仃,由季姑父姑母撫育,待如己出,表兄表姐,也對他像手足般看待,使他雖然失去父母之愛,却一樣享受到家庭的溫暖。
(圖)
唐琪與姨母、表哥、大表嫂、表姊高丹秋、二少奶奶。
張醒亞與表哥季震亞、季姑父、季姑母、表姊季慧亞。
孤女唐琪,在北平學護士,回天津高家和她姨母拜壽。
高老太太坐在大堂,接受兒媳親友向她祝賀快樂誕辰。
(第八頁圖:)
高老太太原很疼愛唐琪,因聽信讒言,對她有了偏見。
唐琪的表哥高大少爺,企圖利用唐琪不遂,說她壞話。
醒亞得唐琪教他溜冰,很感興趣,叫她以後常常教他。
醒亞與唐琪互談身世,說到傷心,醒亞勸她強忍悲憤。
三
那是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年,這個華北重鎭天津市,已經給侵華日軍佔領盤據,因爲高家的所在地是在英國租界,而且高大少爺和日本人又很有交往,所以沒有受到皇軍的搜刮,連干擾也沒有。
重陽節後的一個星期天,高大少爺要鋪張地替他母親高老太太做五十五歲大壽,事前分柬通知親友。張醒亞這天隨同表哥季震亞、表姊慧亞到高家道賀。意外地,醒亞第一次見到了唐琪,他平時已從表哥表姊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這位在北平學護士的唐琪的故事,包括了她的身世——父親是個北洋軍閥政府的幕僚,母親超過三個,父親死後,姨太太分携細軟私逃,她的生母不久也鬱鬱而死……關於她本身的評論,幾乎都一致說她長得很美麗,很活潑,但高老太太和高大少奶奶却說了她很多壞話,主要是說她在北平濫交男友,行爲浪漫,越來越不像樣。
當季慧亞悄悄指着那個梳了兩條辮子的少女告訴醒亞,說她就是唐琪之後,醒亞對她,非常注意,希望從她的外表來觀察一下大家對於她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批評的可靠性。他發現她和滿堂的那些太太小姐們有着不同的氣質,不同的丰度,和不同的神采。她談笑之間,十分活潑跳脫,却不流於浪漫,她的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淸澈靈活,絕不冶蕩妖媚,她的皮膚是白得那末柔美,淡淡的玫瑰色,呈現在她的雙頰,像朝霞染在潔白晶瑩的象牙塑像上,使她格外顯得鮮麗。她穿着一件淡綠色的長袖毛綫衣,一件花綢子的絲棉旗袍,長逾膝蓋,腿上穿着長長的淡咖啡色絲襪。在這個女人堆裏,她的儀態裝飾,只給人以淸麗、雅緻的感覺,一點不見得妖冶。
醒亞對唐琪的注意給慧亞看淸楚了,她連忙走近醒亞,拉了他的手,一同走到唐琪面前,替他和她介紹,於是,唐琪和醒亞熱烈地在握手。
四
一個月之後的一天,天氣很冷,馬路旁的老樹枯枝,隨風雪搖曳,積掛在樹X的雪花飄舞,路上一片冷寂。
冒着風雪在路上走的是四個青年男女,他們都背着溜冰鞋子,他們是要到溜冰場去玩的。
這四個男女一個是季震亞,一個是他未婚妻高丹秋,一個是他妹妹季慧亞,另一個是他的表弟張醒亞。
驀地,一陣子汽車的馬達聲和喇叭聲,逼使他們吃驚地退避到馬路邊,才站定了脚,三部插着太陽旗的大卡車已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
四人的眼睛同時射出憤怒的光芒。最年青的張醒亞更以快速的動作,從路邊拾起了一塊石頭,朝着絕塵而去的卡車,狠狠地抛過去。
季震亞發覺,要攔阻已來不及,只好作事後的警告說:
「幹嗎?小弟!」
「張牙舞爪,我看得不順眼!」醒亞餘怒未息地回答。
「那有什麽辦法?小心鬼子停下車來,把你拉出租界去,看你還有命!」震亞的語氣加重。
「一切都得忍耐,」高丹秋補充着說,「暴燥是於事無補的。」
「我眞不曉得要讓他們横行到什麽時候!」醒亞還是咬牙切齒的忿忿地說。
「終歸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侵略者倒下去的。」震亞說。
「別再談這個了,」季慧亞說,「趕快走吧,別讓唐琪玩膩了先走。」
她說完,拉着醒亞繼續走路。
五
大夥兒到了溜冰場,唐琪正在場裏像穿花蝴蝶般穿插在人叢裏,美麗的臉龐和苗條的身型加上優美的姿態,吸引了場上許多男女的視綫。
十九歲的唐琪是季震亞的未婚妻高丹秋的表妹,由於上月唐琪在他姨母高老太太的壽宴席上經慧亞的介紹,認識了張醒亞,所以她一看見醒亞偕同她表姊丹秋和震亞、慧亞兄妹一起來,連忙從場的那邊溜到這邊來,和他們打招呼,叫他們趕快同玩。
震亞和丹秋很快已換上冰鞋,溜到冰場裏去。慧亞因爲知道醒亞不懂得溜,所以陪着他扶欄看熱鬧。
唐琪在場子上和震亞、丹秋各顯身手,唐琪溜冰的技術特別出色,看得醒亞大感興趣。
「我不相信她是個學護士的小姐,」醒亞對慧亞說。
「爲什麽?」慧亞問。
「那兒有這麽活潑的看護小姐?她今天的樣子,比我們到高家拜壽那天更……」
「更什麼?更美麗,更可愛是不是?」
「我沒那末說,」醒亞有點害羞。
「我真不明白,唐琪有什麼不好,高老太太總是那樣說她壞話。」
「又有什麼壞話?」醒亞追問着。
「還不是老套?什麼不像個正經女孩子呀,什麼浪漫呀……難聽的話多着呢!」
「高老太太是她媽媽的姊姊是不是?」
「連姨媽都不會說!」慧亞說。
「你媽是我爹爹的妹妹!」
「應該叫姑媽!」
「姨媽跟姑媽應該差不多,」醒亞說:「高老太太待唐琪應該像姑媽待我一樣。」
「媽待你比我好,誰好跟你比!」慧亞說,「唐琪跟你都是孤兒,你在天堂,她却在地獄!」
「慧亞!」唐琪突像飛箭般溜過來:「怎麽不玩?」
「琪姊!」慧亞看看醒亞說:「他不會。」
「不會,他來幹嗎?」
「來看你!」
「胡說!」唐琪溜近醒亞面前,伸着手要跟他握手:「張弟弟!」
「嗨……」醒亞忙不迭的遞出手來。
「你是男人,得脫手套!」唐琪微笑着。
「是!」醒亞連忙脫下手套,再遞手和她互握。
「你表姊說你不會溜冰,是嗎?」唐琪說:「我敎你,但有個條件,得叫我做師父!」
「師……師父!」
「乖!來!」唐琪伸手拉着醒亞離開欄杆:「不要怕!來嘛!」又轉對慧亞:「你也一起來。」
這時,震亞與丹秋溜近來,丹秋對着慧亞說:「我的表妹,你的表弟,他倆倒是很好的一對。」
「你做媒人?」震亞笑着問她。
「咱們倆做媒人。」慧亞說。
他們的話,唐琪和醒亞都沒有聽到,因爲唐琪已拉了醒亞溜到場中間,她一會兒用手在做比劃,一會兒指腰,一會兒指脚的在小心敎導醒亞怎樣穩定重心去溜。
經過多次的跌仆,醒亞已漸漸無須唐琪的扶持,也能在冰場上單獨行動了。自此,醒亞對溜冰這玩意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次又一次的約她同玩,有時同去看電影,去散步,玩够了,他才送她回去。青年男女一經接近得頻密,自然容易投機,感情也增進得快。
(圖)
孤兒張醒亞,得表姊季慧亞的介紹,和唐琪初度結識。
赴溜冰場途中,醒亞痛恨日兵車橫衝直撞,慧亞勸阻。
唐琪與張醒亞溜冰歸來,各自回家,臨別時無限依依。
唐琪和醒亞得感情日漸增進,深宵遊倦,他送她回家。
六
夕陽西下,寒鴉歸巢,醒亞和唐琪玩了大半天,唐琪提議回家,醒亞伴送她,邊走邊談。
「聽說,你爸媽早去世了?」她問醒亞。
「是的。」醒亞說:「我兩歲的時候,爸就去世了。」
「我跟你一樣。」唐琪說。
「我早聽說過。」
「想起爸媽時,你會哭嗎?」
「會的。」
「我們同是苦命人,以後讓我們在一塊兒哭個痛快!」唐琪說:「我媽就葬在天津的,你願意找一天陪我去給她墓前送一點花嗎?」
「願意,」醒亞說,「我已長到這末大,還不曉得爸和媽葬在那兒,爸是死在戰場上,媽的墳聽說在湖南,終有一天,我得到湖南拜祭一次。」
「我陪你去,你願意嗎?」
「當然。」
唐琪偶然抬頭看見寒鴉紛紛飛回巢裏,不禁歎了口氣:「烏鴉也有個巢,就是咱倆沒個家!」
醒亞停了步,注望着她。
「不,」她連忙更正:「我說錯了,你姑媽待你好,你有家,就我一個人沒家。」
「琪姊……」他想了想才說:「我勸你別這樣說,高老太太待你也好的。」
「好什麽?」她有點激動:「我在北平學護士,還差半年就畢業,爲了到過前綫去救護第二十九軍,我那做漢奸的表哥就怕我牽累他,不許我再學;我一心到天津來拜壽,就硬說我在北平濫交男朋友,不許我出去,姨媽罵我,表哥表嫂還在旁邊推波助瀾,我提起箱子要回北平,他們却又把我關起來!姨媽一天到晩罵,什麽小狐狸精、小妖怪、爛桃貨、騷貨!……我究竟做錯了什麽,要這末挨罵!」
「不,不要……」他發見了她眼眶凝着涙珠,連忙掏出手帕來替她抹涙,把話題岔開:「我們還是談別的吧,明天溜冰嗎?」
「要是明天我出得來就去,現在很難說。」
兩人沉默着再走了一段路,唐琪停了步說:「咱們就這兒分手吧,要給那大表嫂看見你送我回來,閒話又多呢!」
「那麽,明兒見了!」醒亞的心情有着異樣的感覺。
七
唐琪回到高家,二少奶奶突然走進來,先把房門關上,才悄悄的告訴她說:「表哥已跟老太太商量好,要把你嫁給在新民會做事那個什麽王科長,你得小心啊!」
「他想吧!」唐琪輕藐地冷笑。
忽地,房門給推開,二少奶奶和唐琪連忙回頭看,進來的原來是高丹秋。
「是呀!」丹秋說:「媽剛才曾經叮囑我,從明兒起,不許我再叫你一起去溜冰呢!」
「唔,」唐琪像想起了什麽事,忙往房外走。
「你要上那兒?」丹秋追問她。
「我要去打個電話給醒亞,」唐琪說:「告訴他明天我不能和他一起去溜冰。」
「你別下去討罵了,讓丹秋替你去打,叫震亞轉知醒亞吧。」二少奶奶說。
(圖)
醒亞送唐琪回到門口,彼此難捨難離,殷殷訂期後會。
唐琪笑嘻嘻的問醒亞:為什麼來得這麼晚?你很忙嗎?
高二少奶奶悄悄告訴唐琪,高老太太想迫她嫁王科長。
醒亞訪唐琪,二少奶奶開留聲機,使談話聲不致外洩。
八
季震亞接聽着高丹秋替唐琪打來的電話。
餐桌上已擺好飯菜,季父、季母,和慧亞、醒亞圍坐着等候震亞。
季父對女兒慧亞說:「寒假裏邊,也得溫習溫習功課,不能天天只顧去溜冰。」
「我說過了,」疼愛兒女的季母說:「讓他們痛痛快快的玩一個星期。」
「那個學護士的小姐還住不住在高家?」季父問慧亞。
「……」慧亞只是望着父親,沒有回答。
「還在的。」季母替女兒回答。
「你們有跟她在一起玩嗎?」季父追問。
「有時有,有時沒有。」慧亞囁嚅地。
「最好是沒有,」季父注望着聽完電話回座的震亞續說:「男孩子跟她在一起不好聽,女孩子跟她在一起會學壞!震亞,你是大哥,得注意提點你妹妹和表弟!」
「唔……!」震亞說:「我會依着做的。」
季父吃完了飯,放下筷子,轉到客廳去。大家立時感到氣氛輕鬆了一點。
「媽,」慧亞望着母親:「我眞要替唐琪不平,大夥都聯合起來欺侮她這個孤單的女孩子。」
「你不懂!」季母說。
震亞忽地想起一件事情,忙對醒亞說:「剛才丹秋來的電話,叫我告訴你,從明天起,唐琪再不許出門一步了。」
醒亞聽了,心裏一怔!
「爲什麽要告訴醒亞?」季母警覺地問。
「媽聽錯了!」慧亞連忙掩飾說:「她不是告訴小弟,是告訴我,小弟的名字,跟我只差一個字,我是跟唐琪約好了,明天她敎我溜冰的。」
醒亞正在發呆,不知所措,得慧亞解圍,不禁報以感謝的目光。
大家吃完飯離席,醒亞的同班同學賀蒙來訪醒亞,說他在重慶的大哥賀力有信寄來給他。醒亞便領他上樓詳談。
賀蒙隨着醒亞上樓,走進他的小房間,從懷裏拿出一封信來遞給他,醒亞接過信,只擱在手裏,要跟賀蒙先談談別的事情。
「怎麽?醒亞,你像有心事?」賀蒙覺得他的神態有點異樣。
「賀蒙!你有沒有戀愛過?」
「你在搞戀愛了?」
「有那末一個女孩子,我跟他在一起就快樂,看不見她就苦悶,這是不是戀愛?」
「我不懂!」賀蒙說:「醒亞,談戀愛得看時機,我們還要到後方去!我們還要去打日本鬼子!」
「這不會有衝突。」
「怎麽沒有?你要再談戀愛下去,中央派專機來接你,你也不肯去啦!」
「這是過慮,」醒亞說:「我可以帶同她一起去從軍,她是個孤兒,我也是個孤兒,我們都沒有牽掛。」
「別做你的夢!」賀蒙說:「到底她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
「那末,看了大哥的信再說,別胡塗!」
醒亞如言把信看了,原來是賀力鼓勵醒亞和賀蒙加緊讀書,候機報國,並表示他將於短期内秘密到津,帶領他倆和一批愛國青年到大後方去,參加抗戰工作,叫他們早作準備。
這時,慧亞突登樓,悄悄告訴醒亞,說剛才打電話給唐琪,接聽的是高大少奶奶,叫我有話可告訴她,讓她轉告唐琪。照情形看,事情並不簡單,連電話也不許唐琪接聽了。
醒亞心煩意亂,送走了賀蒙後,即向慧亞請敎,該怎麽辦,慧亞建議他明天跟她哥哥一起去高家,看看情形再說。
(圖)
吃飯時,季震亞告訴表弟醒亞,說唐琪打過電話給他。
季姑父出門時,囑醒亞及女兒慧亞,勿再與唐琪同玩。
二少奶奶藉口煮咖啡避到樓下,讓唐琪醒亞細談心悃。
醒亞走了,唐琪凭着樓欄,目送他出門,心情極愉快。
九
唐琪因爲拒絕她的表哥高大少爺約到外邊去參加一個宴會,藉口有病,躱在樓上結絨綫。到了傍晩,二少奶奶悄悄走來告訴她說:「下邊有一個人等着你。」
唐琪對二少奶奶笑了笑說:「他不好上來?」
「他怎麽好意思?」二少奶奶說,「快到我房裏去,我已跟你泡了茶,我那兒有你二表哥從英國寄回來的一等餅乾,你已整天沒吃飯,吃幾塊,點點飢。趕快!我自己得先到飯廳吃晩飯。」
唐琪感激地點了點頭,讓二少奶奶先下樓,然後輕步穿過走廊,走進二少奶奶的房間。
房間裏的壁爐爐火熾盛,比她的小房間溫暖得多;她坐在沙發,看見小几上放了一壺熱茶,和一盤餅乾,她已經很餓,先拿起餅乾,一塊一塊的送到口裹,發現那邊放了一隻留聲機,旁邊還有一叠唱片。她拿起了一張唱片,看了看便隨手放下,仍舊一塊一塊的拿餅乾送進口裏,一會,她已把盤子上的餅乾吃光了。
房外一陣脚步聲,進來的是二少奶奶,後邊還跟着張醒亞。
「琪姊,」醒亞走近她,驚喜地:「聽說你病了。」
「知道我病了,怎麽不早點來看看我?」
「……」醒亞答不出話來,只看了看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拿起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說:「你就說你不好意思好了!」
醒亞看着唐琪。唐琪微笑。
「我下樓去替你們煮咖啡,」二少奶奶故意給他倆單獨晤談的機會,臨行,指了指留聲機說,「別讓它停下來。」
「坐!」唐琪對着注望着她的醒亞說。
醒亞看看已沒有椅子,就坐在壁爐邊的地毯上,訕訕地一笑。
「醒亞,」唐琪也訕訕地一笑,「我們談一點什麽好?」
「你愛聽什麽?」
「丹秋說你姑媽待你很好,究竟怎樣好法?」
「很好……譬如說表哥表姊有什麽,我也有什麽,最好笑的是表哥跟丹秋姊姊配親,她也要跟我配一個。」
「她給你配了沒有?」唐琪睜着一雙圓大的眼注望着他。
「還沒有。」她搖搖頭。
「你急不急?」唐琪打趣地問。
「急什麽?」醒亞腼腆地把話岔開:「別談這個。明天你和我一起去溜冰嗎?」
「我姨媽不准我出去,你知道嗎?」
醒亞點了點頭。
「好在你已經能够一個人溜也不會摔倒了,沒有我在旁也行。」
「不,要是你不去,我也不去。」
「你這末好?」她試探地。
「我去玩,你悶在家裏,那像什麽。」
「可是,你很想玩?」
「除非我們一塊兒去!」
「好,你得等我的消息。」
二少奶奶這時已捧着咖啡進來,震亞、丹秋却跟在後邊。
「唐小姐,小弟,咱們走了!」震亞說。
「咖啡也沒喝,再坐一回!」醒亞難捨難離地。
「好吧,就讓他喝了咖啡再走。」丹秋說。
醒亞盡量把喝咖啡的時間拖延,但咖啡終歸要唱完的,他站了起來,依依不捨的對着唐琪說:「我要走了!」
「有沒有穿大衣?」唐琪關心地問他。
「有的,放在樓下。」
唐琪發現他脖子上沒有搭上圍巾,一看手裏正拿着那條剛打好的圍巾,便把它送給醒亞,說:「圍着,別着了凉。」
高丹秋送着醒亞、震亞下樓,唐琪和二少奶奶也在梯闌揮手。醒亞走後,唐琪回到自己的小房子,伏着書桌寫日記,把剛才醒亞的會晤經過紀錄下來。
高老太太爲了遷就兒子,曾三番四次跟唐琪商量,勸她和新民會的王科長結婚,但唐琪都不肯答應。此刻高老太太又走進房裏向唐琪重提叫她嫁給王科長的事了。並說,你表哥表嫂已經替你决定,叮囑她從明兒起要好好的在家裏靜靜心,別再整天在外邊玩,也休想再到北平去胡鬧,給人閒話。
唐琪對於她那個投機取巧當漢奸爲虎作倀的表哥,從來就沒有好感,她要到北平學護士,就是希望學成之後,找得職業,便可以離開高家,避免再面對表哥那副醜惡的嘴臉,和姨媽對她過份的嚴厲。此刻聽說表哥表嫂已替她决定,她再也無法按捺得住心頭的一股怒火了,她像一頭小獅般怒吼着,一口回絕了高老太太,堅决表示她不嫁給漢奸。
高老太太給她氣得暴跳如雷,指她忘恩負義。
吵聲給二少奶奶和高丹秋聽到,趕忙來勸止,說好說歹的,總算把局面暫時安定下來。
唐琪這夜徹宵沒有睡覺,涙水染濕了衾枕。黎明前,她流着涙寫了一封給醒亞的信,約他第二天晩上八點鐘在溜冰場門外和她見面。天亮後,她托高丹秋把信送給醒亞。
(圖)
高老太太與兒子媳婦企圖說服唐琪嫁漢奸,唐琪冷笑。
唐琪被高老太太軟禁,半夜裏伏案寫信,約醒亞見面。
唐琪翌晨由表姊季慧亞陪同回家解釋,季老太太不信。
唐琪流淚下跪,解釋整晚在季家看護醒亞,並無越軌。
十
溜冰場在英租界倫敦道的盡頭,入夜後行人稀少,唐琪邊走邊有點害怕,她把步子加快,走到距離溜冰場約略還有五百碼的地方,她發覺背後有雜亂的步履聲,像是跟踪她,她下意識地回頭看看,在路燈的閃爍光綫下,看到兩個流氓,亦步亦趨的跟着她走,她暗裏吃驚,走得更快,但這兩個流氓也隨着走得一樣快,她慌亂了,不由拔脚飛跑,邊跑邊大聲叫:「醒亞!醒亞……」
醒亞果然早已等在溜冰場門外,聽到唐琪的叫聲,發現她奔跑而來,後邊跟了兩個流氓,意識到定有事故,立即迎前。
唐琪一見到醒亞,如獲救星,再加快兩步,撲伏在醒亞的懷裏喘息着,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兩個色胆包天的流氓,竟然也在醒亞的面前停下步,其中一個對着唐琪說出輕薄的話,一個却握拳透爪,裝腔作勢。
醒亞立即了解這是怎麽回事了,他雙手一扶唐琪,示意她避過一旁,然後他以快速動作,卸下大衣,抛給唐琪拿着,即對着作勢的那個流氓發拳打去,打在他的太陽穴,那流氓身子幌了幌,再也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另一個流氓爲了支援同伴,飛身撲前打醒亞,醒亞側身閃避,不料脚下一滑,身體失了重心,踉蹌兩步,勢將跌仆,但他跌仆前的一刹那間,乘勢伸手把對方一拉,和他一同倒地。
醒亞和這流氓滾地混戰,彼此頭部都受了傷,醒亞雖然負傷,仍拚力將對方也擊昏,才掙扎站起來,靠着電燈柱,唐琪替他穿回大衣後,好容易才召到了一部洋車子,扶醒亞登車,因爲流了不少血,醒亞登車後不久,就覺得眼前一陣昏黑,什麽事情也不曉得了。
(圖)
醒亞和流氓决鬥受傷,唐琪替他裹傷看護,徹宵無眠。
醒亞和唐琪擁抱着熱吻,彼此都陶醉在愛情的甜蜜中。
季姑父責備醒亞,囑他不要再和唐琪交遊,醒亞默然。
唐琪被高老太太禁止外出,躲在房裏,流着淚織毛綫。
十一
深宵的時候,醒亞已悠然淸醒,他還記得打架杓事,他睜眼看看,發現自己躺在自己的床上,伸手摸摸頭臉,已給紗布膠布裹得好好的,也不覺得劇痛了。他正在追憶自己在昏倒前的情形,突然見到唐琪走進房裏,拿了個熱水瓶,倒了一杯開水遞到他的唇邊。
「你醒來了,先喝一口開水再說話。」
醒亞喝了一口就問:「現在是什麽時候了?琪姊,你還沒有回家去?」
「我不放心。」唐琪說:「你昏迷了兩個多小時。傷口痛不痛?」
「不痛,」醒亞說:「我太感激你了!」
「我不要你感激,」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續說:「我只要你……」
「要我怎麽?」
「要你愛!」她雙手捧着他的臉,「聽見沒有?要你愛!」
「要我……」他臉上掛了一道喜悅的笑痕。
她俯了身,低着頭,把嘴唇吻在他的臉,說:「叫我!」
「琪姊,琪姊!」他的聲調愉快而興奮。
「告訴我,你愛我!」
「我是多麼愛尔,但我不會表達。」
「吻我,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她熱情奔放,像萬馬奔騰。
「琪姊!……」他興奮地緊緊地擁抱了她,在她的臉、唇不停地熱吻。
「……唔,」他向着懷抱裏的唐琪的耳邊問:「我們是不是在做夢?」
「不是,是比夢更美的月夜!」
一忽兒她的臉磨擦着他的臉,一忽兒她的嘴唇磨擦着他的嘴唇,一忽見她的眼睛和他的眼對看着,他和她都像在沉醉中。
「琪姊,我吻得對不對?」醒亞問:「我沒有這經驗。」
「傻孩子,我還不是跟你一樣!我何嘗跟任何人談着情,說過愛?」唐琪說:「不過,我曾幻想過有這末一天,我會碰上一個我愛的,也是愛我的男孩子;我又曾幻想過,我應該怎樣和他熱情地和他說話,怎樣熱情地接吻……今天,我的幻想實現了!」
「琪姊,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愛情……」
「是啊!你應該珍貴我這份愛情——一個女孩子奉献出她的最寳貴的愛情,也是最後的愛情。」
「我知道我應該怎樣做的。」醒亞撫摩着她的頭髪,她的臉,她的手。她是那末馴順地,像隻小綿羊似地蜷伏在他的床頭。
(圖)
張醒亞正在家裡溫習,突然接到唐琪打來找他的電話。
唐琪打了電話給張醒亞,自己也就趕了東陽車去會他。
唐琪告訴醒亞,說已得到護士職,叫他跟她一起私奔。
醒亞說要考慮,唐琪一怒而行,醒亞哀懇她回頭再談。
十二
唐琪因爲整夜看護着醒亞,沒有回家,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由慧亞陪伴她返高家。高老太太責她日以繼夜在外邊混,女孩子外宿,太不成話了!唐琪跪地解釋原因,慧亞也在旁作證,高大少奶奶却冷笑,表示不信她們的話,並說不贊成唐琪和醒亞常常在一起。唐琪只得坦白表示,她已愛上醒亞,而醒亞也愛上了她。在旁的高二少奶奶和慧亞,也替唐琪和醒亞說好話,懇求高老太太玉成好事。但高大少奶奶和她的丈夫高大少爺却另有計劃,力表反對。高大少爺更在母親耳邊說了些什麽話,高老太太便吩咐唐琪,從今天起,沒有得到她的同意,不許出街!
原來高大少爺的如意算盤是利用唐琪的美麗,去滿足新民會那個王科長,以加强自己和這僞組織的關係。對於唐琪不受利用,而且和醒亞熱戀,認爲嚴重地打擊了他的計劃。除了要求母親將她實施軟禁外,更親自到季家,向醒亞的季姑父季姑母遊說,謊說唐琪已答應了和王科長結婚,爲了大家的名譽,要求季姑父阻止醒亞再和唐琪往來。季姑父對唐琪本來就印象不佳,再經高大少爺的花言巧語,危詞聳聽,自是滿口答應。
就在這天晩上,醒亞的季姑父和姑母向他告誡,過去的不多說,囑他傷勢痊癒之後,要和唐琪疏遠,別招惹外邊的閒言閒語。醒亞極力替唐琪辯護,說唐琪是個有志氣的好女孩,不應對她持有偏見,並且堅信她不會和什麽王科長結婚,爲什麼不可以跟她來往呢?季姑父聽了大爲光火,責備醒亞無知,堅持要醒亞跟唐琪絕交。在旁的震亞和慧亞,不敢參加意見。醒亞知道再難轉回,只好默不作聲,等他們走開,才抱頭痛哭。
醒亞與唐琪已經好幾天沒有見面了。醒亞整天沒精打彩,坐臥不安。而唐琪在高老太太的看管下,形同軟禁,自然也是心情苦惱,整天躱在房間裏淌着眼涙織毛綫。
倒是高二少奶奶了解年青人心理,更了解唐琪與醒亞的愛情,她不惜冒了被高老太太斥罵的危險,暗地裏替唐琪和醒亞互遞信件,因此他倆雖是暫將不能見面,却可互寫情信,傾訴相思。
十三
唐琪不斷受到高大少爺的脅迫,要她與王科長結婚,面臨抉擇,必須當機立斷,於是她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醒亞——
醒亞:
目前我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自殺;二是出走;三是忍耐。爲了愛你,我不能死;離開高家,沒地方去。因之只有忍耐,等待……
雖然他們全力對我威迫利誘,要我嫁給姓王的,但,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做出使你心碎的事的……我現在正找尋一個脫出樊籠的機會,希望我獲得自由的時候,你即開始負起護衞我的責任,伴我一起在天空飛翔!
你的唐琪。
醒亞讀完了這封信,初是興奮,逐漸有點迷惘和遲疑,心裏交織了矛盾。
過了幾天,醒亞突然接到唐琪打來給他的電話,唐琪告訴醒亞,說她一會就要到高家來找他,替他收拾行李,和他一起出走。醒亞聽了,心裏一怔,正想約她先見面談談,然後再作决定,但唐琪沒有譲他說話,就已經把電話掛斷。醒亞一時彷徨得手足無措,思索了一會,即悄悄離家,跑出弄口,等候唐琪來。
還不到十分鐘,唐琪眞的坐了東洋車趕到,醒亞走前迎她下車,一把拉了她的手,直往小路走,拐了幾個彎灣子,走到一排大樹下的幽徑停下來。
「從現在起,我已獲得自由了!」唐琪首先喜孜孜的對醒亞說出她的未來大計:「我已經找到了工作,在廣慈醫院裏做護士。我們只要租一個房間,買點簡單的傢具,從此可以住在一塊,你高興嗎?」
「哦,……」醒亞張大了嘴巴:「高興!」
「東西收拾好了嗎?」
「還沒有。」
「爲什麽?」她訝異地問。
「……」醒亞只是注望着她,說不出話。
「你怎麽不講話?」她冷靜下來:「你不願意跟我一塊?」
「不!不是!琪姊!」醒亞惶急地,「我以爲這事情得從長考慮,不能太衝動。」
「醒亞!」她有點激動了,「難道是我來誘拐你?你究竟跟不跟我走?難道你忍心看着我艱苦奮鬥,全部失敗了?難道你忍心看着我永遠在高家受磨折?你應該記得,我們是一對同命運的孤兒,我們自己刻苦謀生,總比倚賴別人要幸福得多!」
「但是,」醒亞說:「我怕!」
她在望了,她咆哮着:「你怕這個怕那個,却不怕刺傷我的心!不怕你自己良心受責備!」
「琪姊,」他緊握着她的手,涙珠子從他的眼眶裏滴下來,「我是眞心愛你的。」
她憤怒地給了他一記耳光,聲色俱厲地說:「光要你嘴皮上愛我,有什麽用處!」
說着,她重新提起她帶來的小行李箱,掉頭就走。
「琪姊……!你不要走!」他聲涙俱下地:「你眞的忍心不答應和我從長商量嗎?」
唐琪雖然怒他懦怯,到底心裏是非常愛他的,聽到他的哀叫,心却軟了,便回頭來抱着他,吻着他,叫他回去仔細想想,明天通電話再說。
醒亞回到季家,把打算和唐琪出走這問題悄悄跟表姊慧亞商量,慧亞表示反對,她說:
「第一,你還沒有本事掙錢,負起養家的責任;第二,出走的地方不遠,不高明。」
「表姊說得對!」醒亞說着,心裏已作决定。
第二天,唐琪在醫院和醒亞通電話,醒亞告訴她,他不打算出走。唐琪聽了,憤然掛斷了電話,心裏非常難過。
醒亞和唐琪通過了這次電話之後,心底泛起了一點兒後悔,覺得這樣斷然拒絕了她,似乎太對人家不起了!……
醒亞逕自跑到廣慈醫院,要面見唐琪解釋,但唐琪痛恨他,拒絕和他見面。醒亞只好回家,懇得表姊慧亞,代他去醫院向唐琪致歉,並約期晤談。結果,醒亞還是失望,因爲慧亞見過了唐琪後回來告訴他,唐琪恨透了他,不想再跟他會面。
(第十六頁圖:)
第二天唐琪接到醒亞得電話,拒絕私奔,她大感失望。
季慧亞替醒亞到醫院向唐琪解釋,唐琪大笑不肯答應。
唐琪因喝了有迷藥的酒,稍事反抗,便已昏仆在地上。
那頭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將唐琪抱到房間,對她侮辱。
(第十七頁圖:)
唐琪正準備下班,醫院院長約她同吃晚飯,商談院務。
常院長人面獸心,下迷藥在酒裏給唐琪飲,將她迷姦。
唐琪被迷姦案擴大了,高老太太看見報紙,大罵活該!
醒亞看報知唐琪受辱,憤怒如狂,大罵高家害了唐琪。
十四
廣慈醫院是間私人經營的小型醫院,但病人很多,護士人手又少,唐琪雖是心情沉重,但對於這繁忙的工作,還是非常小心。
下班的時候,姓常的院長對唐琪表示,要跟她商談一些有關院裏的護士問題,約她同到他家裏吃晩飯。唐琪聽說是有關工作業務,答應了他。
晩飯的時候,常院長有計劃地不停要她喝酒,但唐琪淺嚐輒止,不肯多喝。詭計多端的常院長竟乘唐琪沒有注意,悄悄下了些東西在她那杯酒裏,要她喝了就吃飯,琪唐不便固執,一喝而盡。
漸漸,她感到自己的神志有點不對,同時也發現常院長的態度跟着不對,她想走,但她已無法支持,頹然倒地……
這一夜,唐琪遭受了無可補償的損害與侮辱。
第二天,唐琪回復了淸醒,她知道自己昨夜遭遇了什麽事情,她當然不甘心,就到警局告了常院長一狀。
所有天津的報紙都把這宗醫生迷姦女護士案大加渲染,作爲頭條新聞。
高大少奶奶和高大少爺立即把報紙遞給高老太太看,高老太太對於這個姨甥女兒的悲慘遭遇,不但未予同情,還附和着兒媳的意見,大罵唐琪下賤,好好的一個科長太太不去做,却跟風流醫生攪得一榻糊塗!
張醒亞雖然沒有答應唐琪偕她一塊出走同居,但他對唐琪仍舊深深的愛戀着。他看到報紙,知道就在自己不答應和她同一行動的當夜,她即遭受不幸,正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内心非常難過,瘋狂般嚷着要去見唐琪,季姑父怕他出意外,把他軟禁在房裏,他整天大叫大罵,指責高家和季家的人害了唐琪。姑母只好邀請了醒亞的同班同學賀蒙來居住,陪伴和勸解醒亞。
十五
唐琪自從遭受了遺憾畢生的打擊之後,思想和行爲都有了若干程度的改變。爲了生存,她毅然在天津有名的聖安娜舞廳下海,唱歌和伴舞。憑了她的青春、美麗,和過去她服務軍中時練得的歌喉,很快很快便艶名四播,成爲津門歡場的出色人物。
追逐在唐琪的旗袍下的,不少是僞朝新貴,和發了國難財的暴發戶,殷勤奉献,買她歡心,但他們買到的,只是她的敷衍式的虛僞笑容,不能買到她的身體,自然更不能買到她的芳心了。她的心,她好像認爲仍然是屬於醒亞的。她期待着他——雖然他的懦怯曾經使她憤怒。
十六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年秋初的一個風雨之夜,賀蒙的大哥賀力到季家來拍門訪賀蒙和張醒亞。賀力是重慶國民政府派到淪陷區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他一向跟季家從季姑父、姑母、震亞、到慧亞都很熟,故此闔家同表歡迎。賀力表示此次秘密回津,準備帶領一羣愛國青年和他弟弟賀蒙回到大後方,參加抗戰工作。季姑父爲了使醒亞轉換環境,隔離了他跟唐琪的關係,乘機力懇賀力也帶同醒亞回後方。賀力表示他早有此意,月前曾寫信給醒亞,叫他準備,只是不知他準備了沒有。季姑父忙說他已準備了,賀力便答應下來。
一切行期計劃都已商定了。
這夜,醒亞單獨向賀力懇求,准許他帶同他的愛人唐琪一起回大後方。賀力表示怕她受不了苦,醒亞保證她吃得消。
「她已經答應和你同行了?」賀力問。
「只要你答應我,」醒亞說,「我馬上去告訴她,她一定肯跟我們一起挨苦的。」
醒亞說完也不待賀力的答應,竟一溜烟的跑去找唐琪。
賀力望着他的背影,搖搖頭說:「痴情!」
醒亞一口氣跑到聖安娜舞廳,坐在臨近樂台的一隅。
唐琪正在樂台上,對着米高峯,曼聲唱着「痴痴地等」一曲,曲詞哀艷,聲調悽怨,醒亞邊聽着邊眼眶凝涙。
一會,唐琪一曲告終,姗姗走下音樂台,才走了幾步,聽到有人叫着她:「琪姊!」聲音是那末熟習。她回頭一看,發現叫她的人正是她痴痴地等的醒亞。
「是你?」她笑了笑,但笑容立即就消失。
「我特別來看你。」
「看我幹什麽?」她保持冰冷的態度。
「有……有話要跟你說。」
「這裏太嘈雜,你到對門的凱士林咖啡館等我。」
「別騙我……」
「我什麽時候騙過你?只有你才騙過我!」
醒亞在凱士林咖啡館裏見到了唐琪,即把自己要回大後方的計劃告訴她,並要求她一塊兒去。唐琪却表示要考慮一個時期。醒亞再三懇求,唐琪才答應把考慮的時間縮短,明天就答覆他。
離開凱士林咖啡館,已是深夜,醒亞送唐琪回她的住所,到了門口,他要求:
「我跟你進去看看!」
「這不方便的,」她故意地說:「有人跟我同住!」
「你跟什麽人同居?」他的神態顯得緊張。
「是我的愛人!」
醒亞楞住了。她跑上石階,取出鎖匙,開了門,再走下石階,拉了呆站着的醒亞進門。
唐琪順手亮了燈,醒亞忽地聽到女人的尖叫聲:「快把燈關了,讓我穿起睡衣來。」
醒亞一看,原來床上睡了個美麗的女子,正在狼狽地拉被往身上蓋。
唐琪拉了醒亞到床前,說:「方大姐,別客氣,這是我的大令張醒亞。」
「哦!就是你!」方小姐恍然地:「你把我的小白鴿琪姊想壞了啦!好吧,我睡我的,你門談談吧!」
唐琪點頭一笑,走到自己床邊坐下,抬頭望着醒亞。
「你現在就答覆我好不好?」醒亞低聲說。
唐琪不答,站起來走近窗前。
「你怎末不說話?」醒亞說:「你別考慮了!」
「對你沒有什麽好處。」她回過頭來。
「你說什麽?」他莫名其妙地。
「我說我跟着你走,那我就變成你的累贅,對你沒有什麽好處。」
「琪姊,」醒亞霍地跪在她跟前:「你對我的好處是說不完的,沒有你,我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有了!」
「……起來!」她感動得流涙:「我答應了!」
「好極了!」他快樂地站起來:「後天一早我們就走了,現在我跟你去看看我們的賀大哥。」
醒亞帶同唐琪見到賀力,說唐琪非常願意一起回大後方。賀力唯唯答應。
第二天,賀力却單獨去訪唐琪,力陳利害,說:「要是你眞的愛醒亞,應該讓他單獨回去,以免他爲了愛情,疏忽了責任。」
結果唐琪給賀力說服,决定不跟隨醒亞回大後方。關於明天怎樣應付醒亞,由賀力安排。
(圖)
唐琪受盡折磨,把心一橫,下海舞廳做歌手兼做舞伴。
唐琪在聖廳裏做歌手,也當舞伴,過着燈紅酒綠生活。
賀力由渝秘密抵津訪季家,準備帶醒亞、賀蒙到內地。
醒亞到舞廳訪唐琪,唐琪以他突如其來,對他很冷淡。
十七
這天淸晨,醒亞依照吩咐,化裝學徒,和學生打扮的賀蒙,另外兩個青年學生,隨同商人裝束的賀力,大家提着輕便行李箱,進入天津老龍頭火車站,搭京奉鐵路的南行火車。他們通過驗票處走向月台,火車機頭已升火待發,車廂裏已坐滿搭客。醒亞東張西望,找尋約好了在車站會面的唐琪,可是,月台上的人雖然不少,却沒有唐琪的影子。醒亞心裏焦急,和賀力、賀蒙等攀上了一節車廂,放好行李,對着賀力說:
「怎麽還不見唐琪呢?」
「她可能在別的車廂裏。」賀力說:「你去找找看。」
慧亞這時也匆匆趕來送行,她見醒亞張惶地到處找,問賀蒙,賀蒙告訴了她。
醒亞匆匆跑出這節車廂,進入另一節車廂,一連找了好幾節都不見唐琪的影子,再走下月台去找,仍是芳踪杳然。
火車頭的汽笛在嗚嗚的叫着,手裏拿着紅綠色小旗的站長已在月台出現,醒亞更加惶急,趕忙攀上車廂,對賀力說:「找不到她,怎麽辦呢?」
「慧亞剛才也來送行,你找她問問看。」
「我見到慧亞了,她說她沒有見過唐琪。」醍亞焦急得像燒紅了的鍋子上的螞蟻。
「噢!」賀力略一思索,「大槪她還在路上沒有趕到。你坐下來,別跑來跑去,引起人家注意。」
醒亞勉强坐下來,仍舊惶急地向窗外張望。火車已慢慢移動,突然,醒亞發現方大姐一個人跑進月台來,向每一節車廂探望。
「方大姐!」醒亞向她招手,方大姐已看見醒亞,追近窗口,醒亞大聲問她:「唐琪呢?叫她快上車!」
方大姐跟着蠕動着的火車跑,遞了一封信給他。醒亞接過信,火車移動轉快,說話已來不及,只好向方大姐招了招手。
醒亞急忙地坐下來拆開信看,上面寫道:
醒亞:
請原諒我,我再三考慮的結果,决定不跟你同行了。這不但爲我好,也爲你好。我寧願這次對你失信,叫你恨我一個短時期,不願隨你同行,連累你終生,而使你恨我一輩子了。醒亞:果眞緣份未盡,我們後會有期……醒亞,堅强點!珍重!努力!我爲你的偉大前程祝福!
琪寫於黎明前。
醒亞一字一字的讀完,憤怒地:「她騙我!她報復我!……」
「別太衝動!」賀力沉着臉:「想想我們此行的目的,出了事,你對得起大家?」
火車在原野朝着南方飛馳。
唐琪頭上蒙了白絲巾,遮住了一邊臉,讓人看不淸楚她的廬山眞面目。她站在火車站月台上一個角落,睜着涙眼,呆望着這列火車向南馳去……火車不見了,也還凝望着留在天空的一縷黑烟。
一會,她流着涙對身旁的方大姐和季慧亞說:「幚助我,幚助我祝福他一路平安!」
(圖)
唐琪美麗而歌喉好,很快便走紅,成為津市一流舞星。
被譽為舞海奇葩的唐琪,不少富商巨賈向她熱烈追求。
醒亞在咖啡館要求唐琪,放棄歡場生活,同到大後方。
醒亞偕同唐琪來訪賀力,由賀力的弟弟賀蒙接待入內。
(圖)
醒亞立即帶唐琪訪賀力,懇賀力許他偕同唐琪去重慶。
醒亞第二晚親訪唐琪,勸她為了醒亞前程,不要隨行。
醒亞、賀蒙據守陣地,瞄準來犯的日本兵,發射機槍。
醒亞那支隊伍被友軍襲擊,狼狽撤退,他肩部中了彈。
十八
從搭火車到走路,又從走路到坐船,醒亞等一行跟隨着賀力,安抵太行山,他們立即給安置到訓練機構裏,接受了一個時期的嚴格軍事訓練。受訓期滿後,醒亞和賀蒙,參加了青年軍,編進一個作戰部隊。不久,這個部隊奉令開到前綫和日本侵略軍作戰,負起保國衞民的神聖任務。
這天,他們這支隊伍仍由賀力指揮,奉命到陵川城附近的一個高地,掩護友軍。醒亞和賀蒙,在暮色蒼茫中和分散着的隊伍逐步向這高地推進,突然一陣機槍掃來,醒亞連忙伏地,等槍聲响過了幾陣,再匍匐前進,發現三名日兵正據守一個機槍陣地,醒亞示意賀蒙提防,自解下一枚手榴彈,咬開保險摯,看準了目標,奮力扔過去。只聽轟隆一聲,火光過後,瀰漫了硝磺烟霧。醒亞挺站起來察看,見機槍陣地已被炸毀,却見一個日本兵想爬起來,醒亞快打慢,一個箭步跳過去,人和刺刀一齊到,這個日本兵當堂穿背而起。
隊伍繼續捜索前進,醒亞保持着和賀蒙的聯繫。
忽地,成千的鄕民,扶老携幼,從山頭上的他們的隊伍衝過來,鄉民們並喊叫着:「放下武器!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隊伍的弟兄們,都感到惶惑失措,稍一躊躇,密集的槍彈從鄕民叢中的後邊射過來!曾經有過這樣經驗的賀力立即揮手發令:
「大家散開,脫離火網!自己人來消滅自己人了!」
弟兄們立即緊急分散。醒亞看見戰友們都得到掩蔽了,才最後衝出火網。
不料,嗤的一聲,一顆子彈鑽進他的肩膊,一陣疼痛,身體失了平衡,倒在地下,向山崖滾落,幸而滾到崖邊,身體給巨石阻擋,就此停住,不致直滾落崖下。這時,鮮血已從傷口流出,軍衣已濕了一大塊,陣陣劇痛難忍,陡覺眼前昏黑,就昏了過去。
十九
黎明的時候,一片碧藍的天空,給那些被炮火燃燒過的野草雜樹餘燼冒起來像朶朶黑雲般的黑烟掩蔽着。
田隴、壕溝、石山旁都躺着戰死者的屍體,從他們傷口淌出來的血液,在泥土上、在青草上,已凝結成瘀紅色的血塊。
躺在崖邊亂石上的張醒亞,悠悠復甦,睜開眼,向左右看,支撐坐起來。
斜斜的山邊上有人拿着燈籠在尋找、叫喚,像是叫着:「醒亞!醒亞!」
醒亞發現了,鼓足了氣,大聲的叫:「賀大哥!」
果然,他看見那點燈籠火光搖幌着,漸漸的,高高低低的向他幌近。
「——賀大哥!」他再大聲叫。
賀力辨明了方向,向山下邊滾,終於,他找到了醒亞。他放下燈籠,一把抱着醒亞,說:「給我看看!」
賀力看到醒亞只傷肩膀,忙說:「總算幸運!找個老百姓的家躱一躱。」
賀力說着,放下醒亞,自撕褲子,把布條替他裹紮傷口。
「咱們的隊伍呢?」醒亞邊走邊問賀力。
「部份垮了,部份突了圍到沁陽去集合。」
「賀蒙昵?」
「找了整晩都找不到他……也許陣亡了!」賀力的聲調帶點嗚咽。
「拿老百姓做擋箭牌,襲擊我們隊伍的這支軍隊呢?」
「也撤退了。今晩我們碰到的,就是他們的人海戰術,他們要把我們這支青年軍收編。他們避免跟日本鬼子兵接觸,天一亮,他們便撤走了。」
賀力摻扶了醒亞走了十來丈遠,見醒亞痛苦難支,索性把他背在肩膀上走,好容易在日出的時候,找到一家農舍,得到老農父子的答應,讓他倆暫時藏匿,等到傍晩,老農父子造了飯讓他吃飽,又找來兩套破衣給他倆改裝農民,然後親往嚮導,通過了日本兵的檢査崗位,抄小路横越晉德公路,指點着直到沁陽縣紫陵鎭的通路,然後和賀力、醒亞道別。
第二天的日落時候,賀力、醒亞已行抵紫陵鎭,鎭上設有中央正規部隊的前綫指揮部,賀力偕醒亞到部裏辦理報到的手續,却意外地,賀蒙和一羣較早時撤退的戰友都在裏邊。彼此無恙重逢,無不歡欣鼓舞。
不久,賀力告訴醒亞和賀蒙,他們明天就要開拔到中條山去,到了中條山以後,醒亞將會被送到重慶大學,賀蒙送入軍校,他自己則要即晩起程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賀力說完,便在「重慶再見」聲中,和醒亞、賀蒙握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