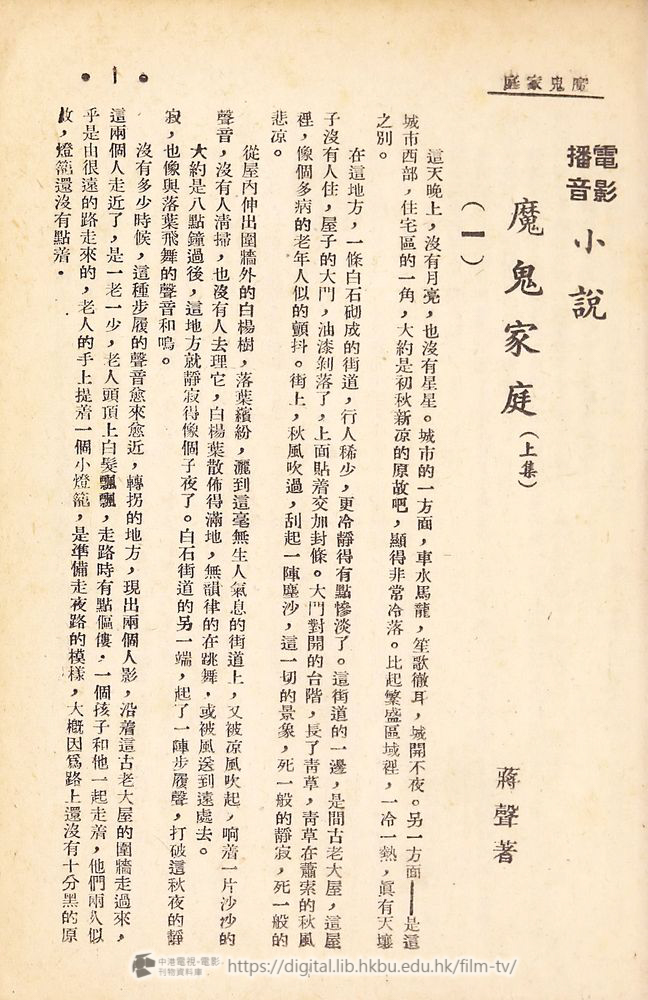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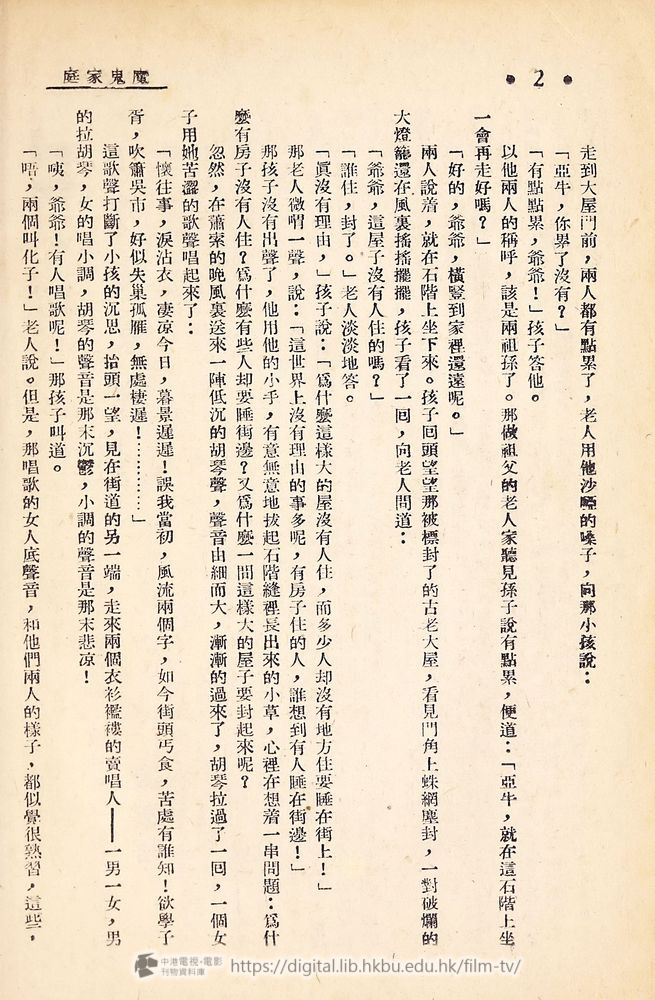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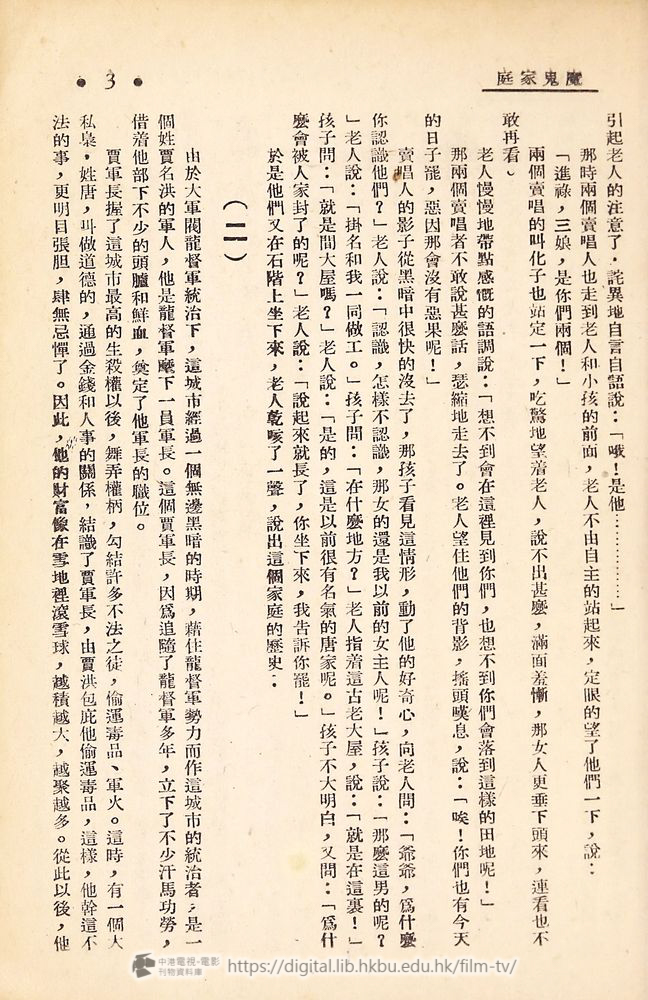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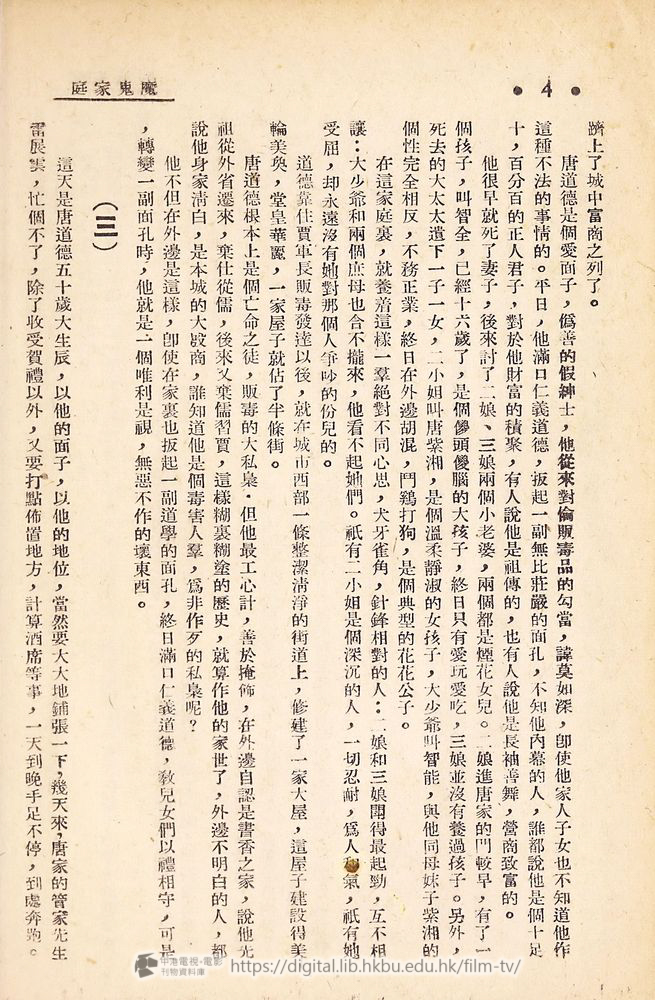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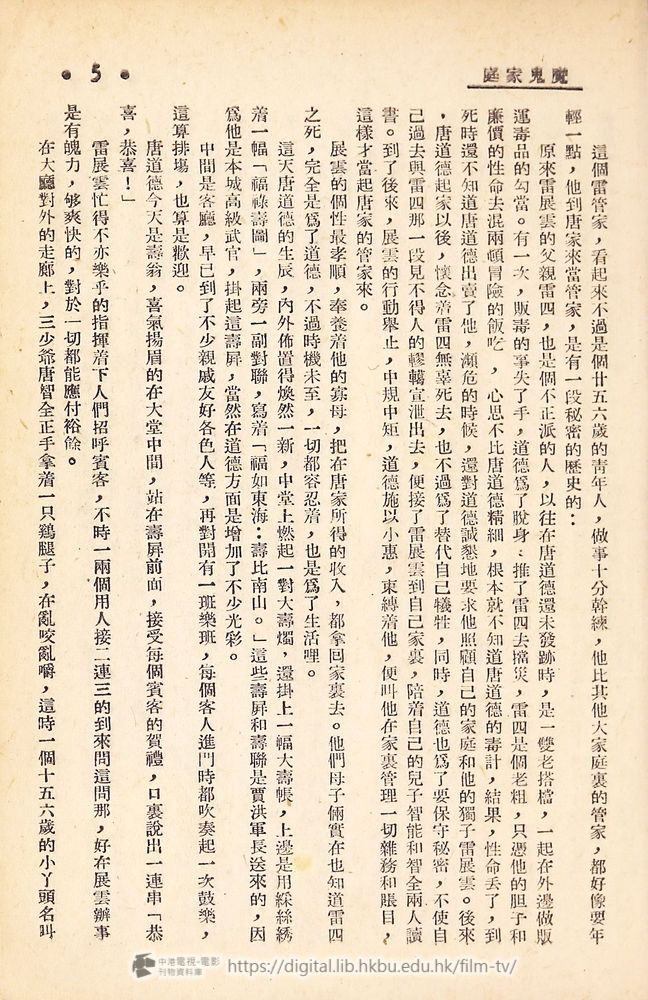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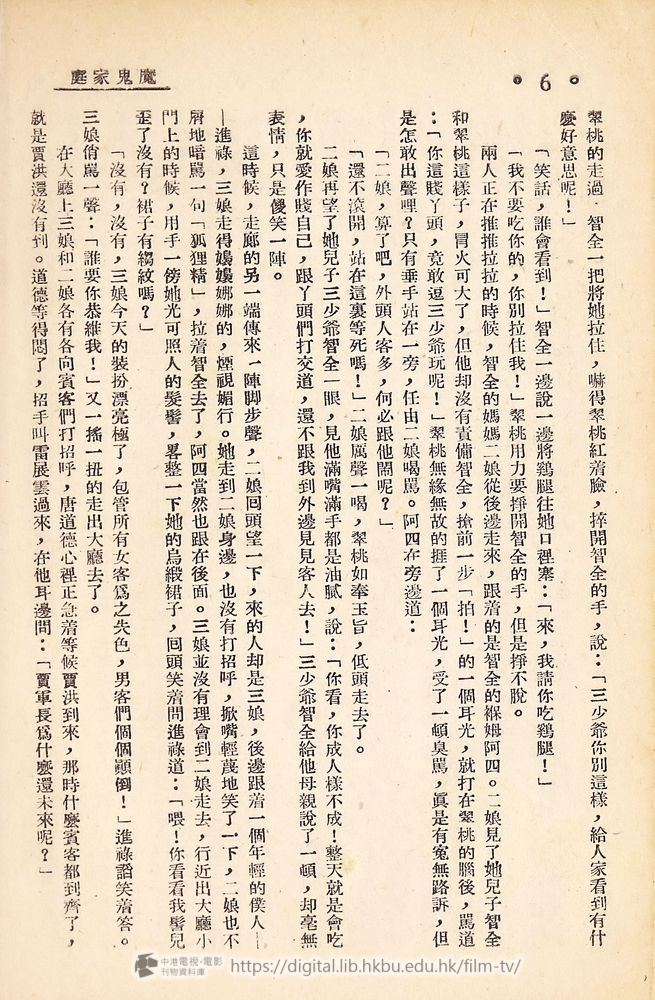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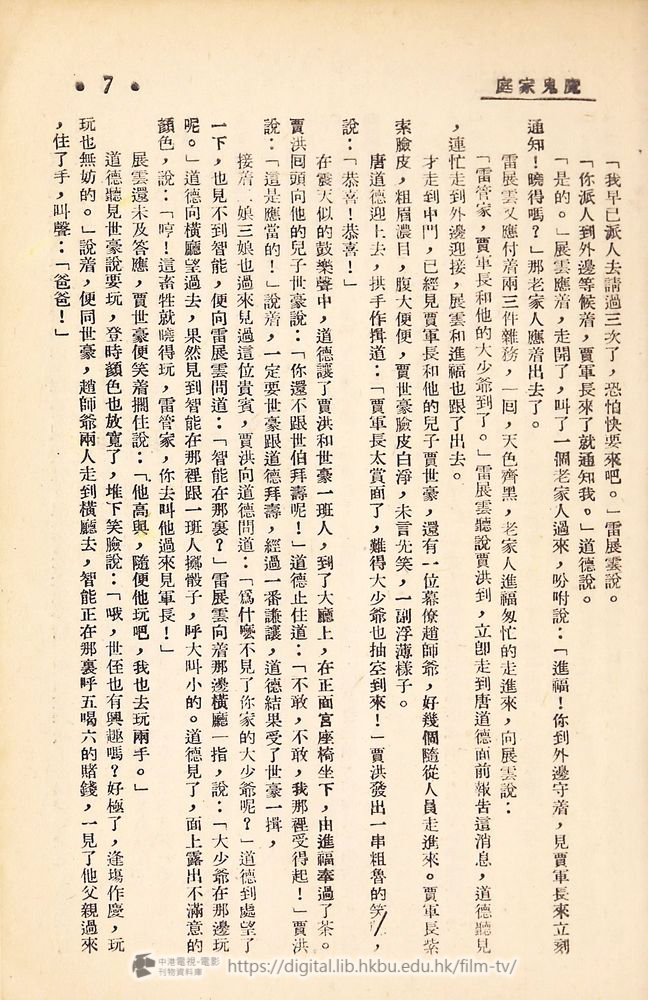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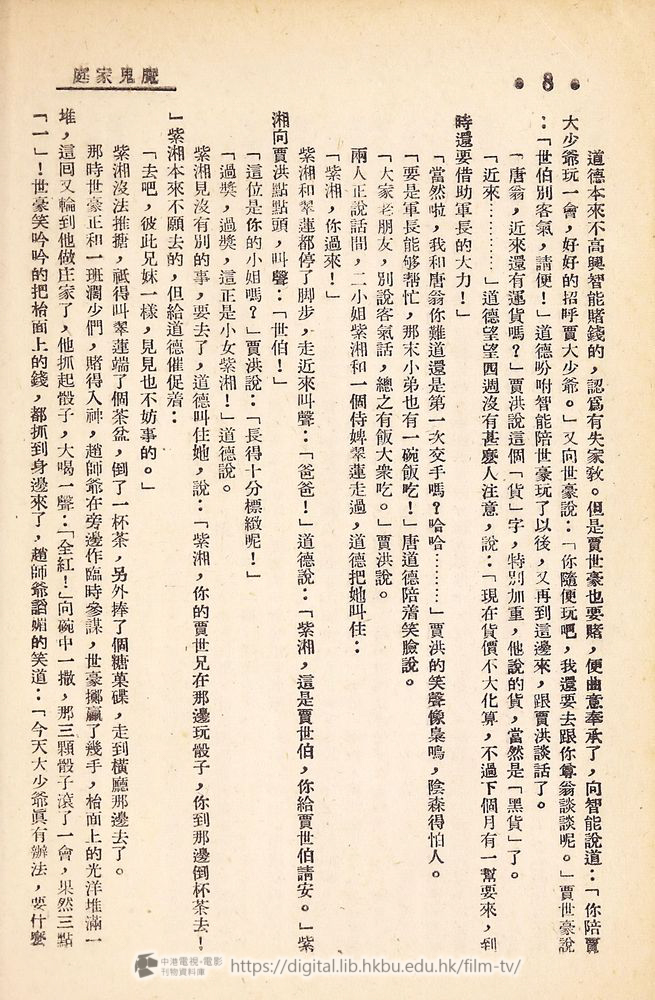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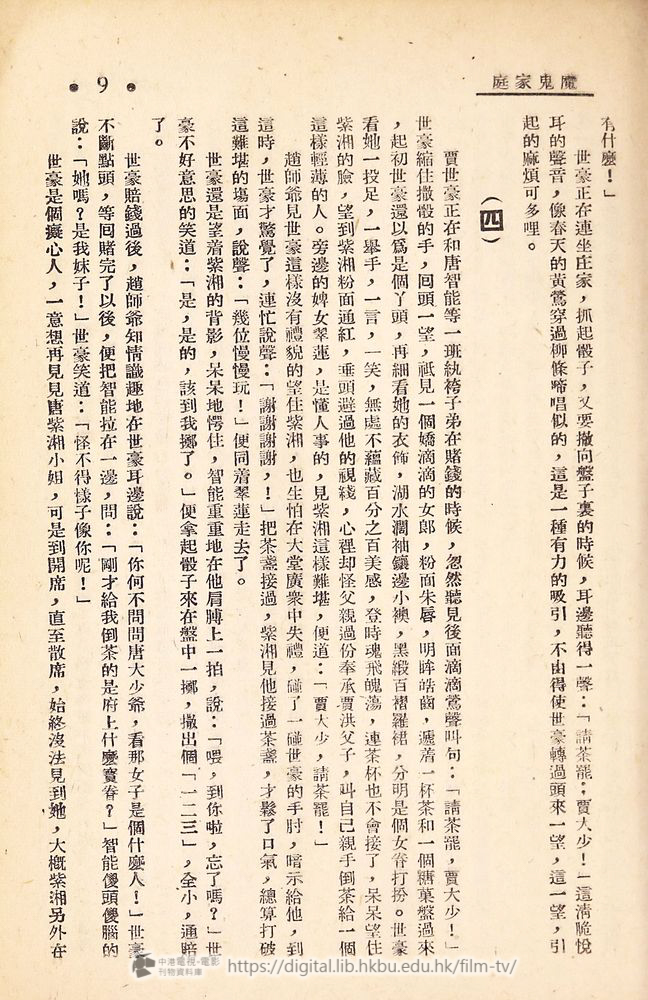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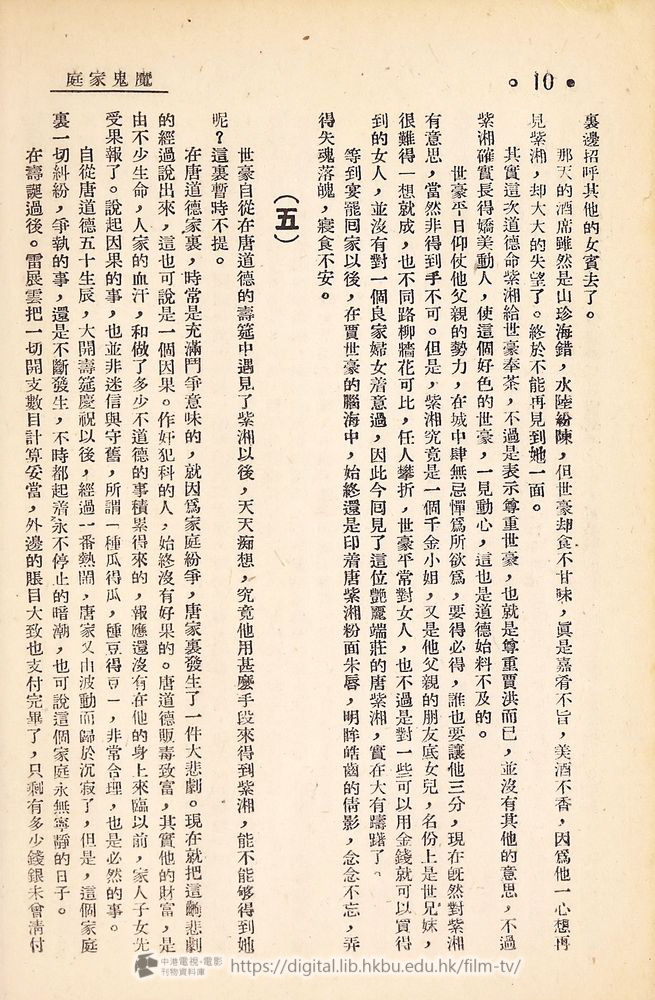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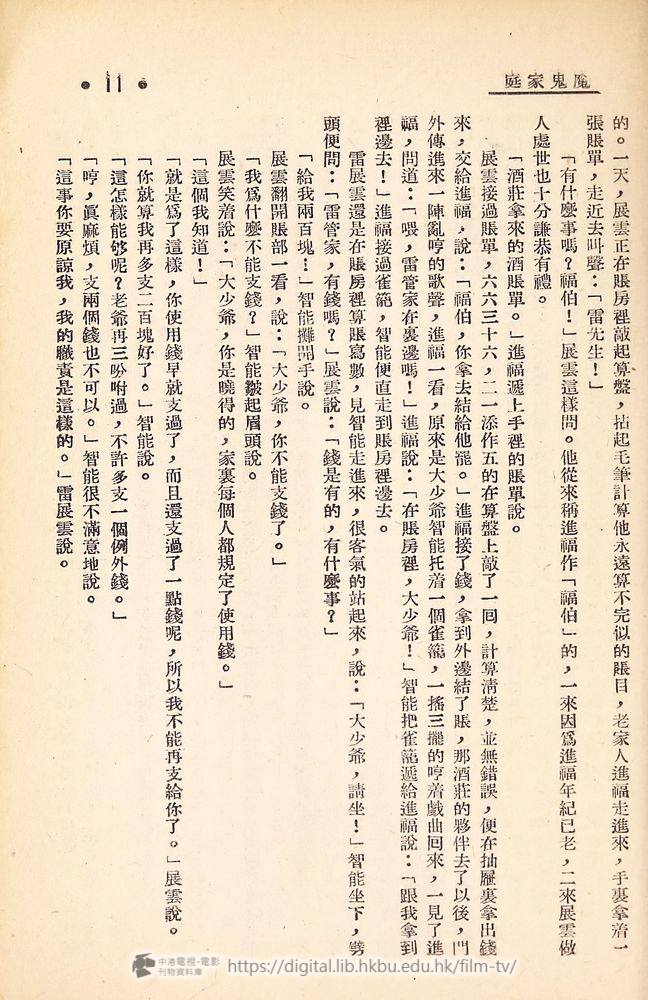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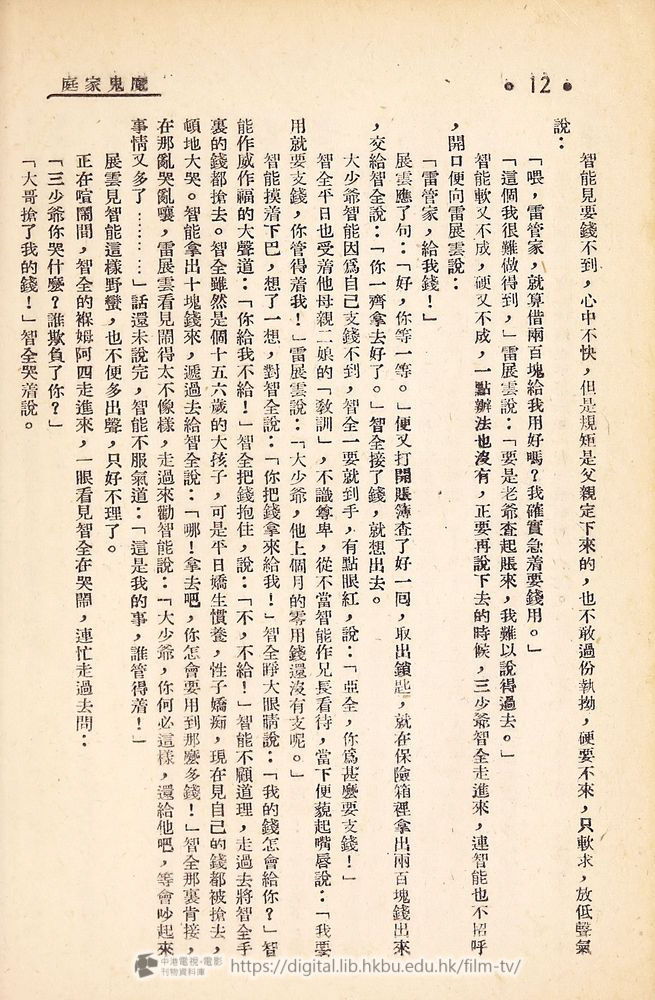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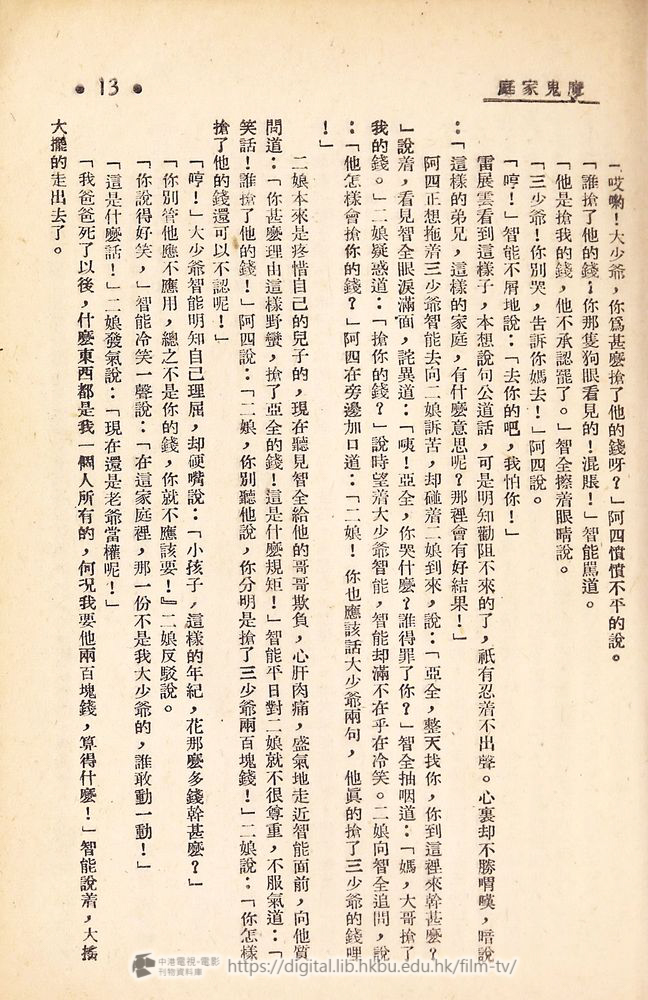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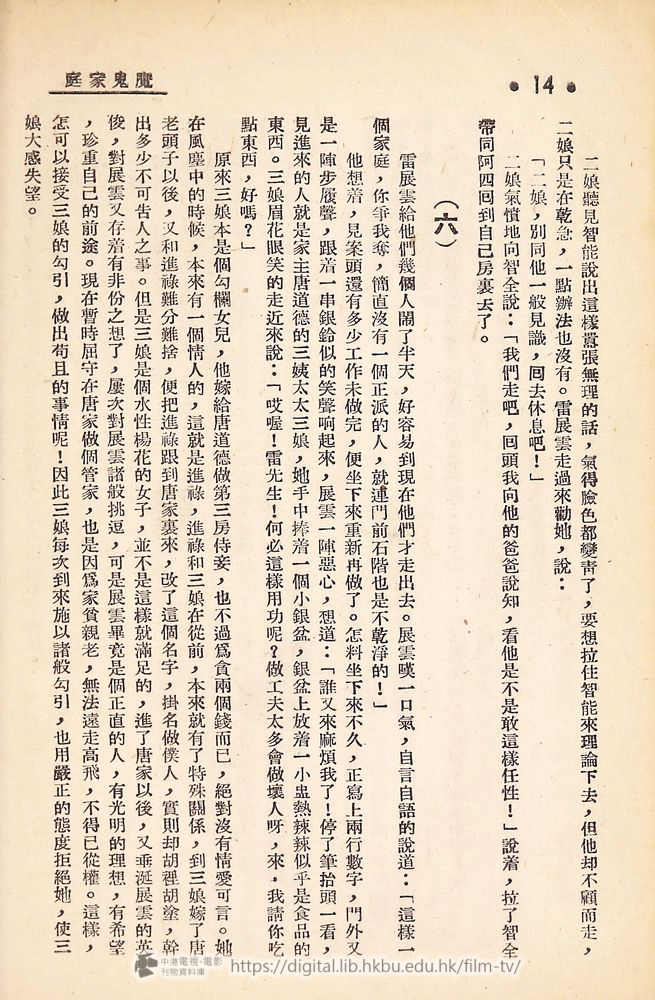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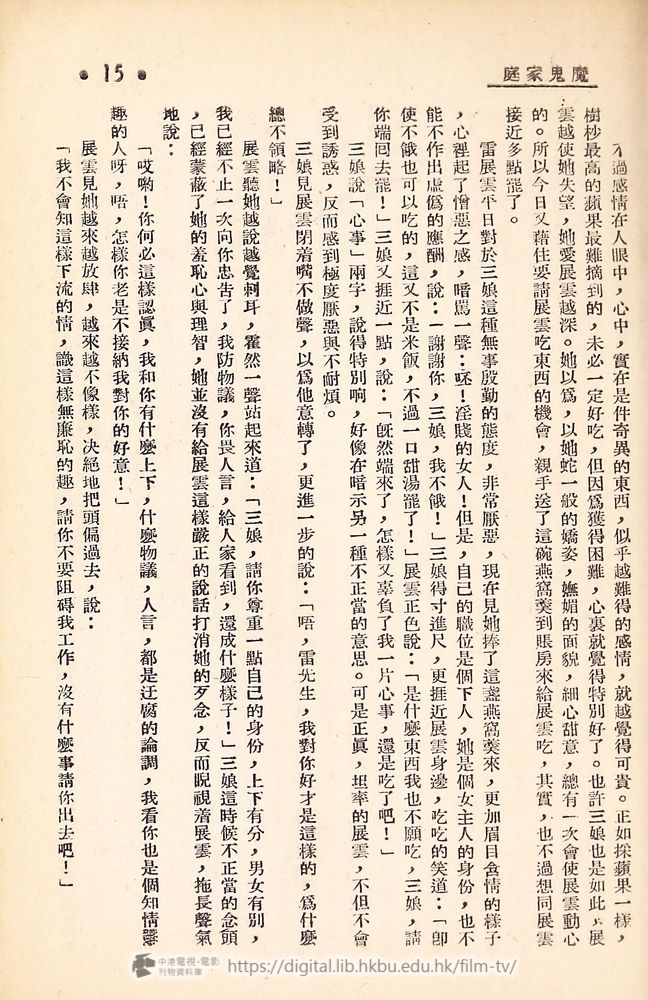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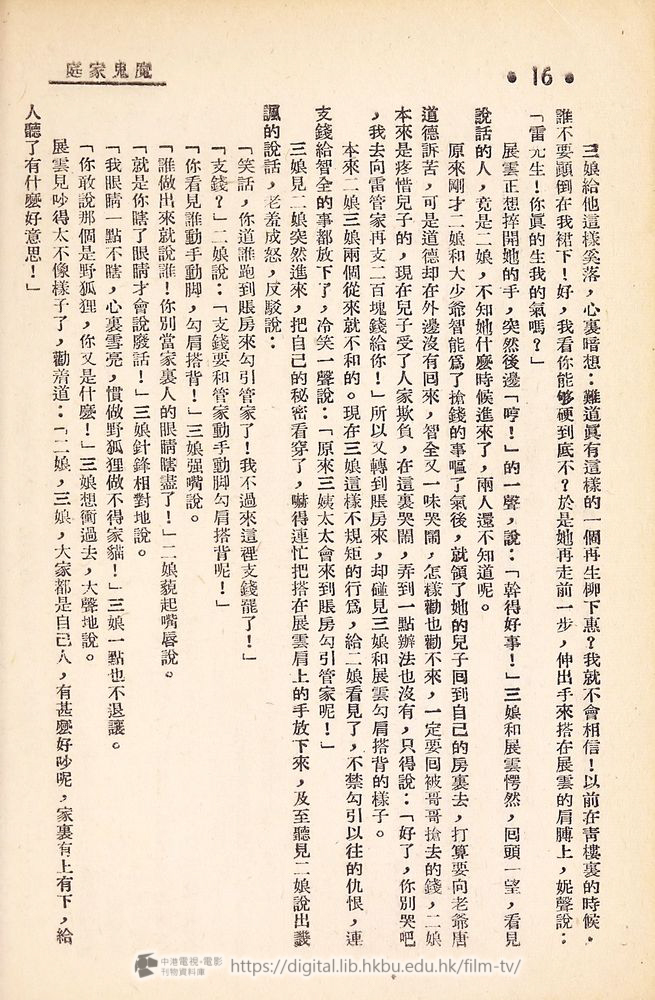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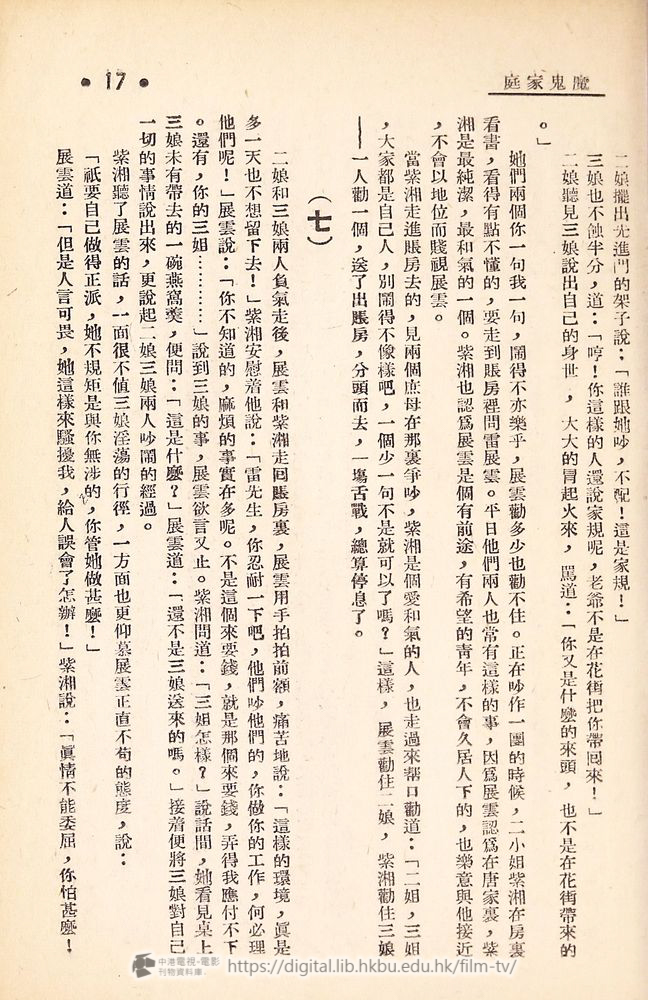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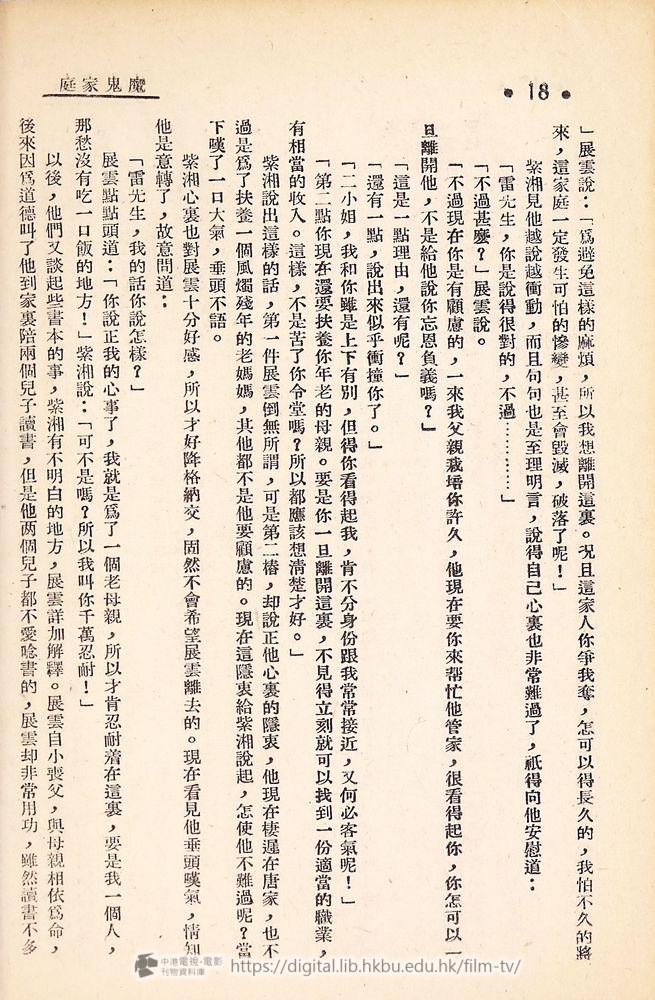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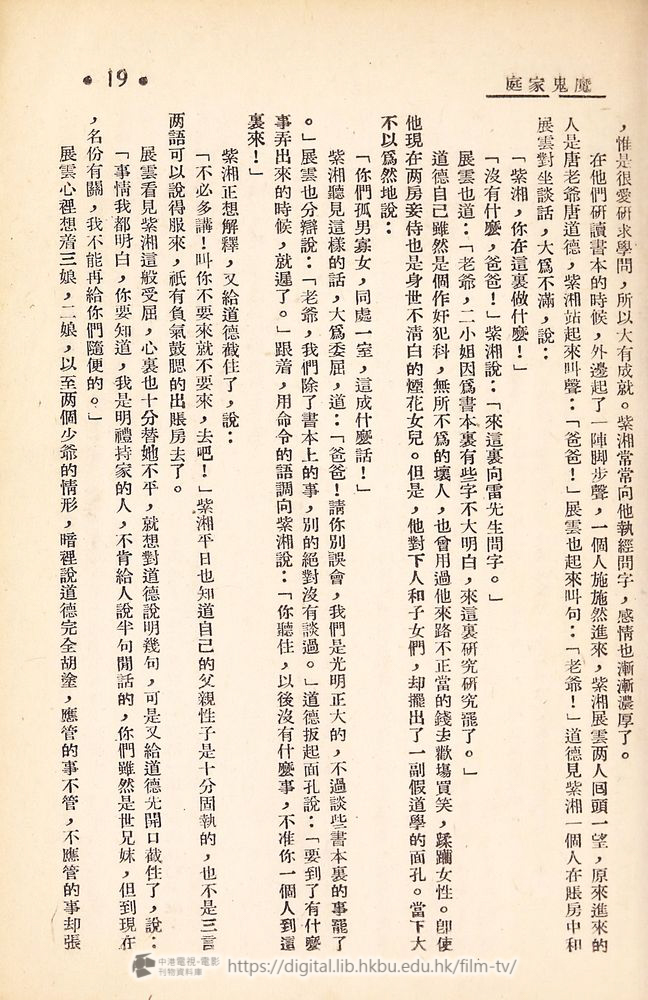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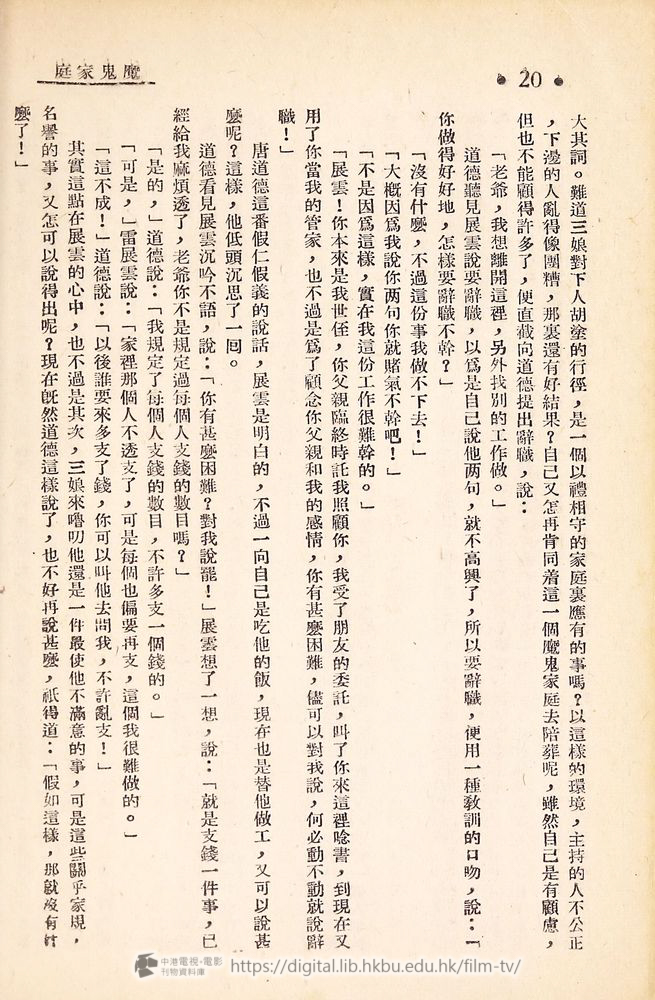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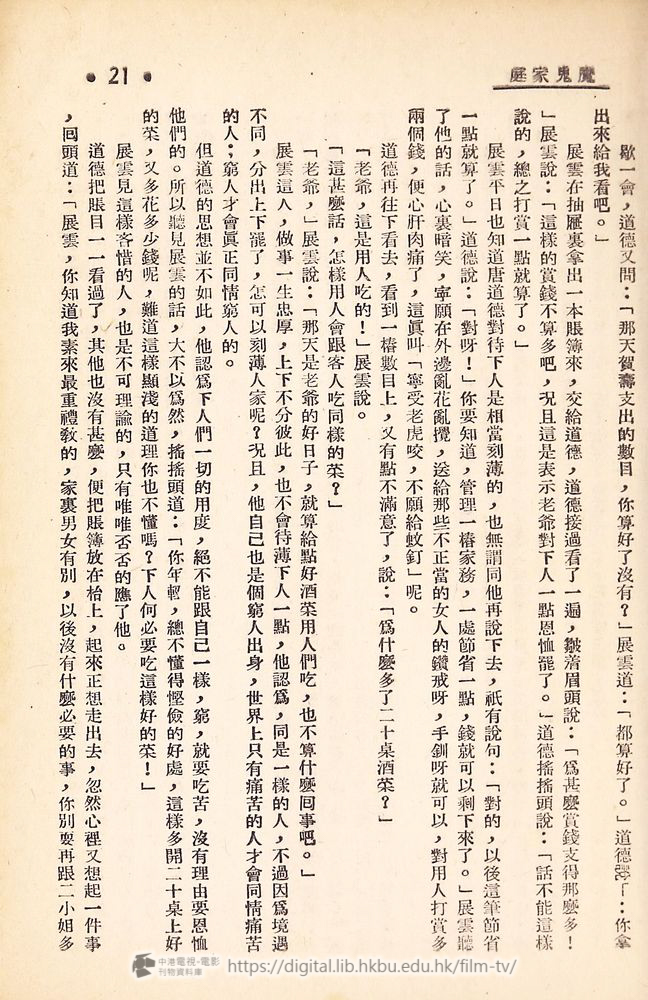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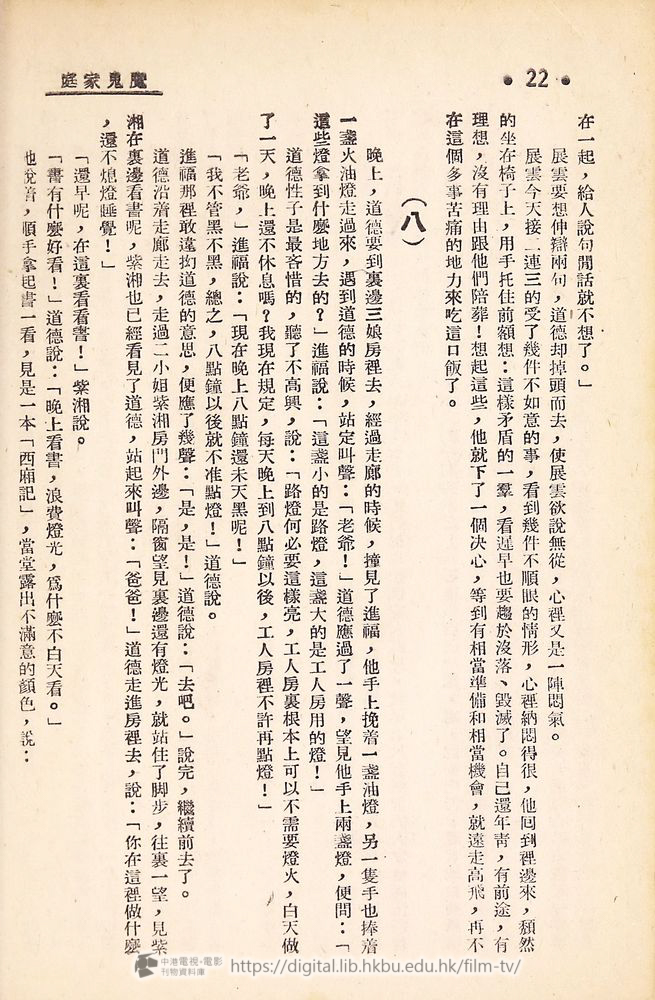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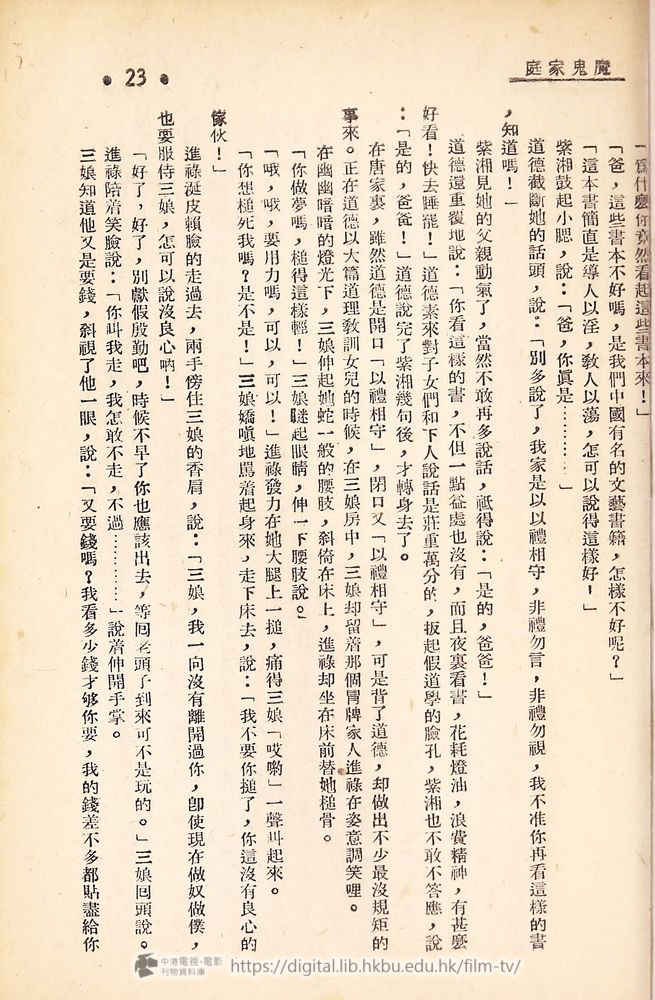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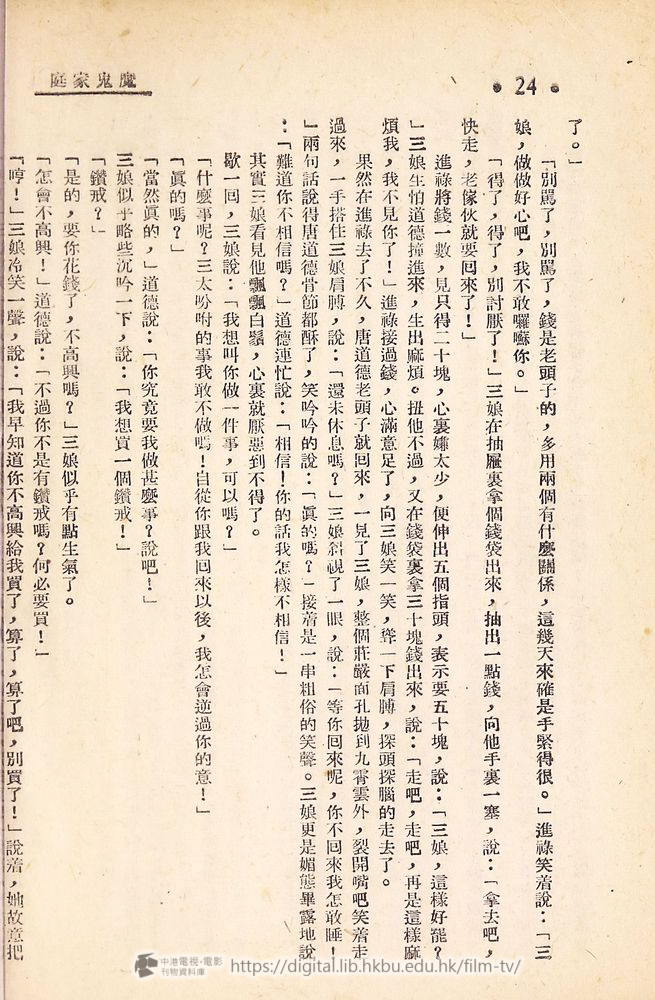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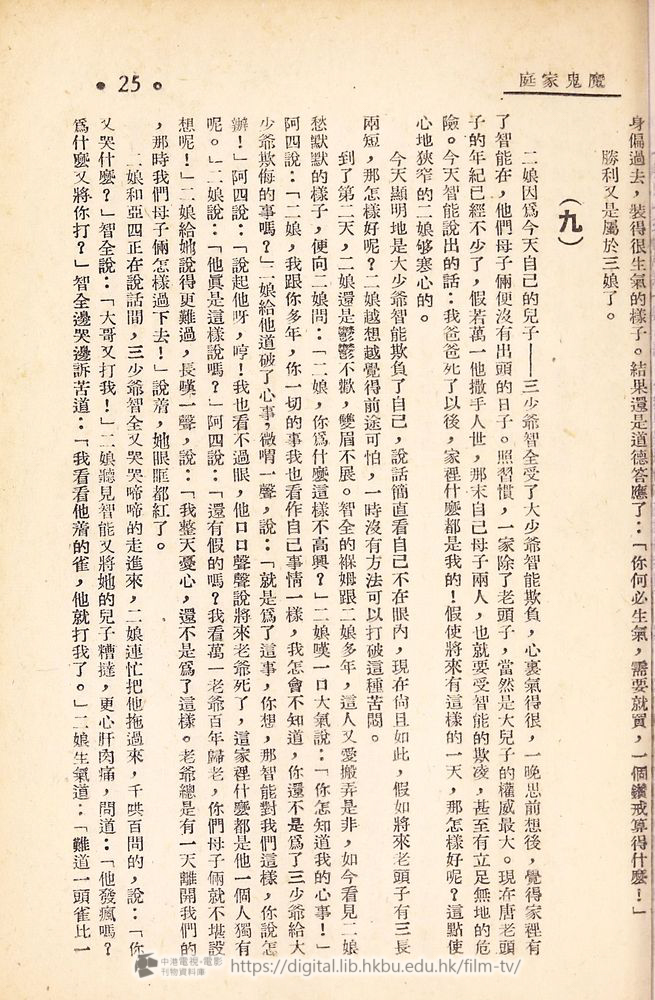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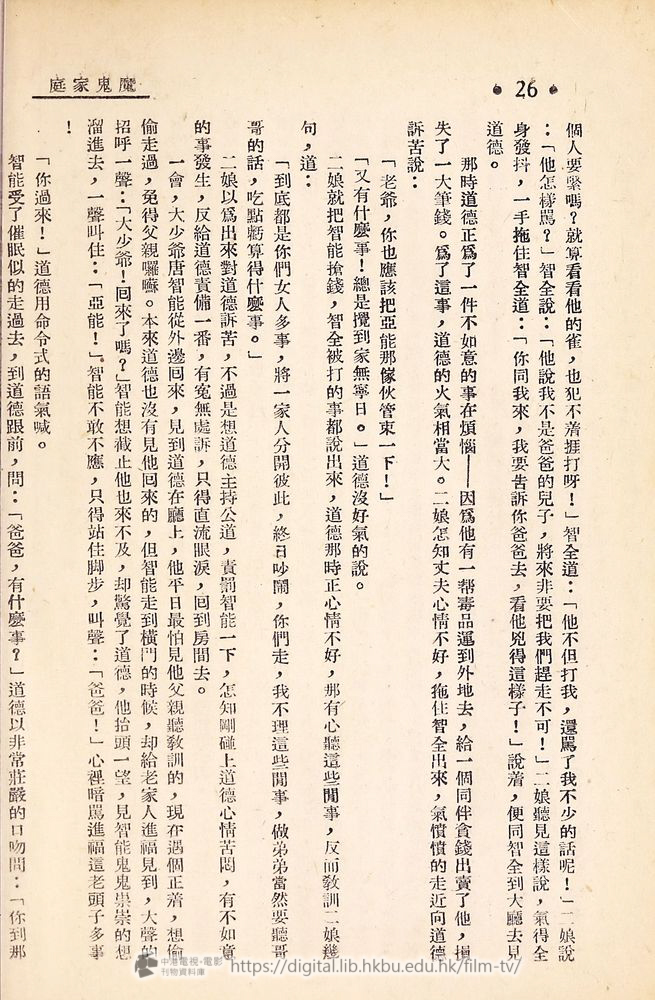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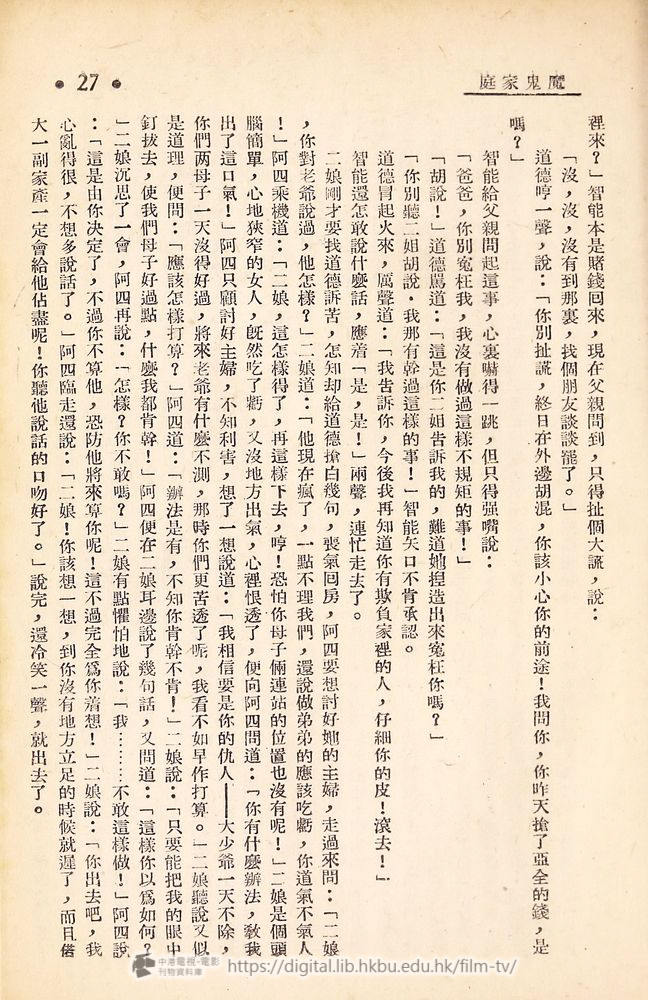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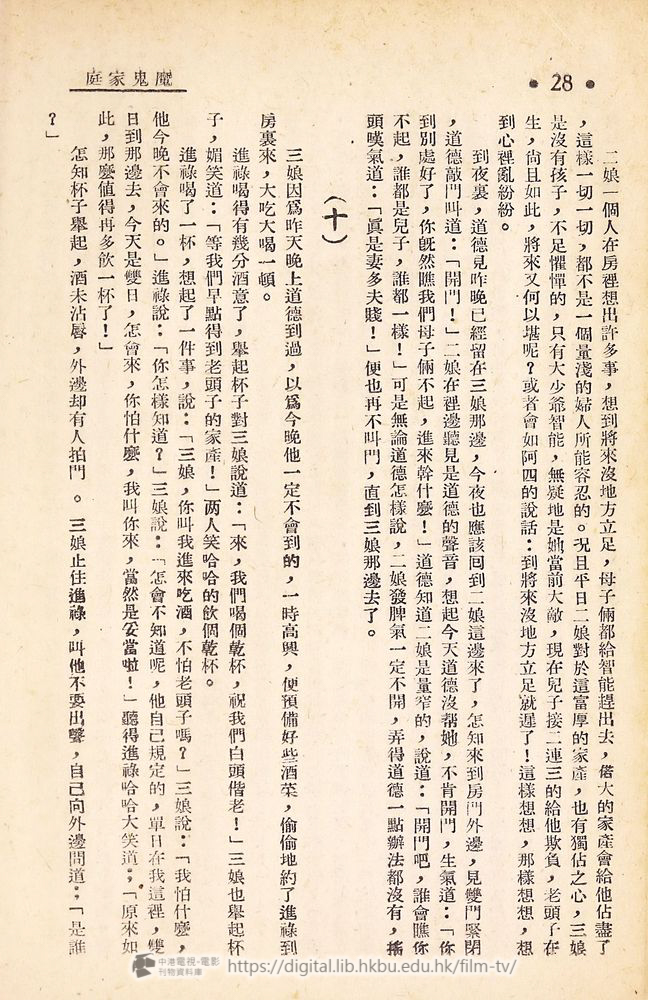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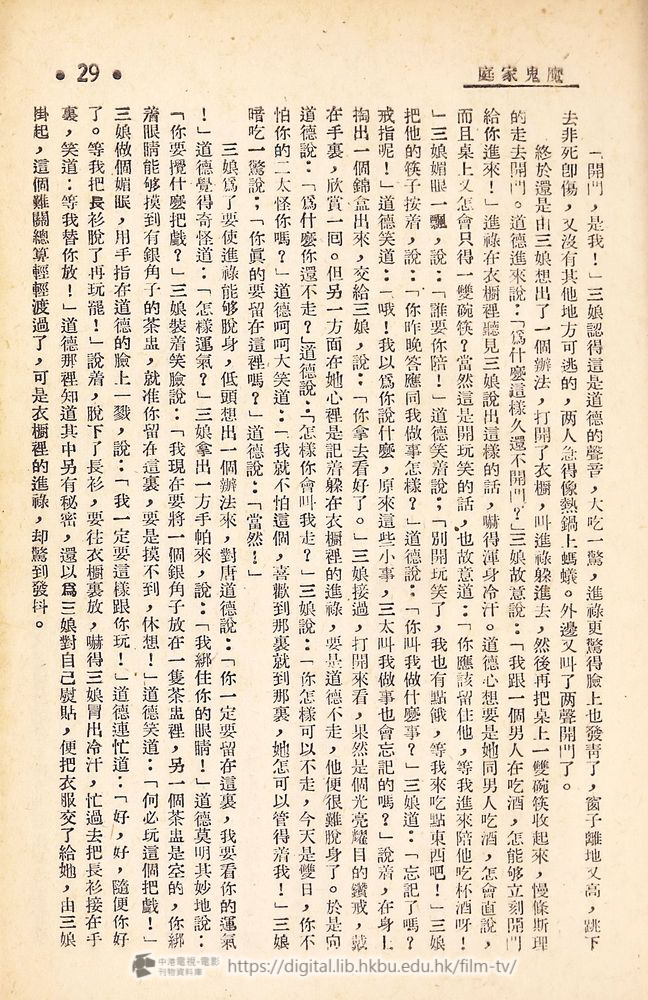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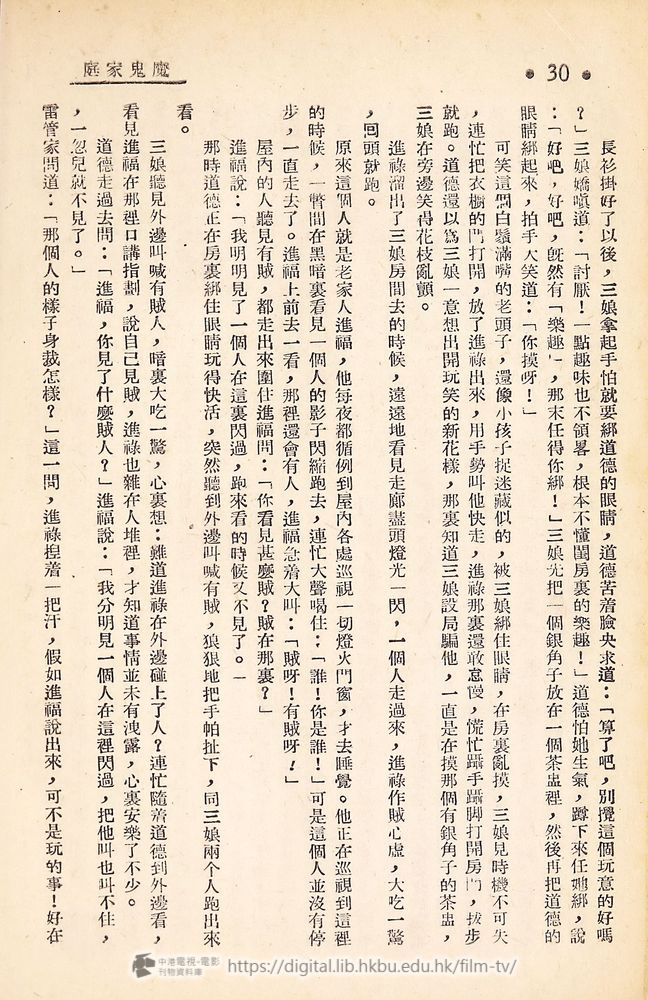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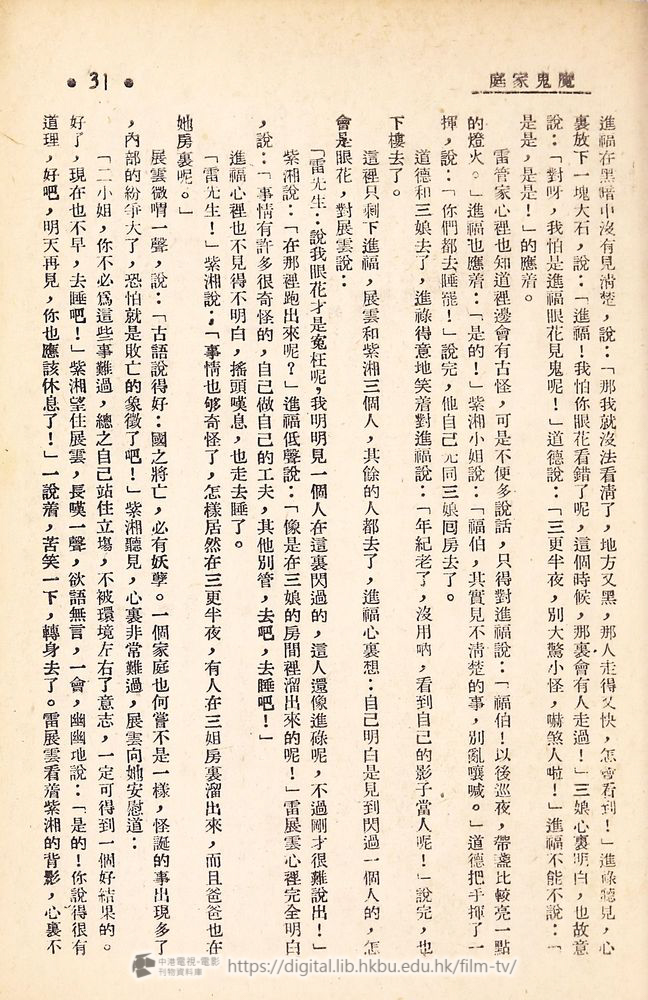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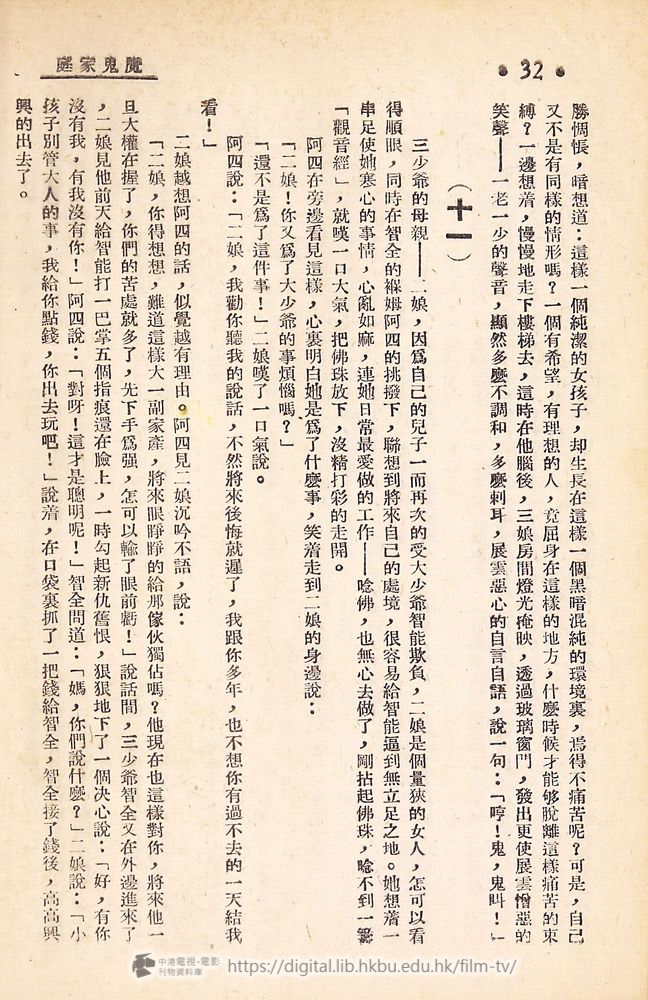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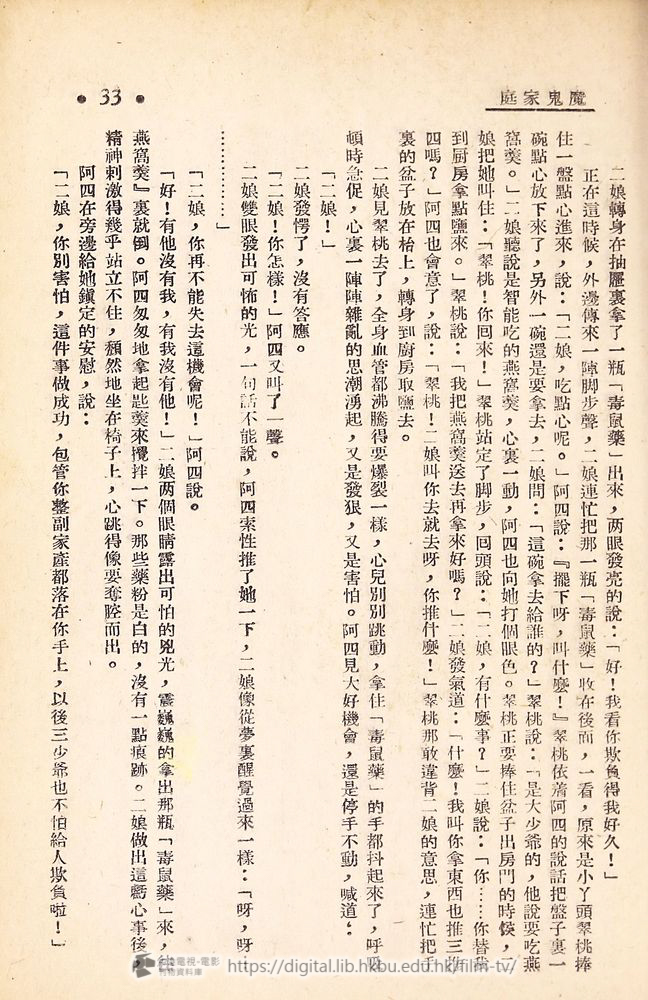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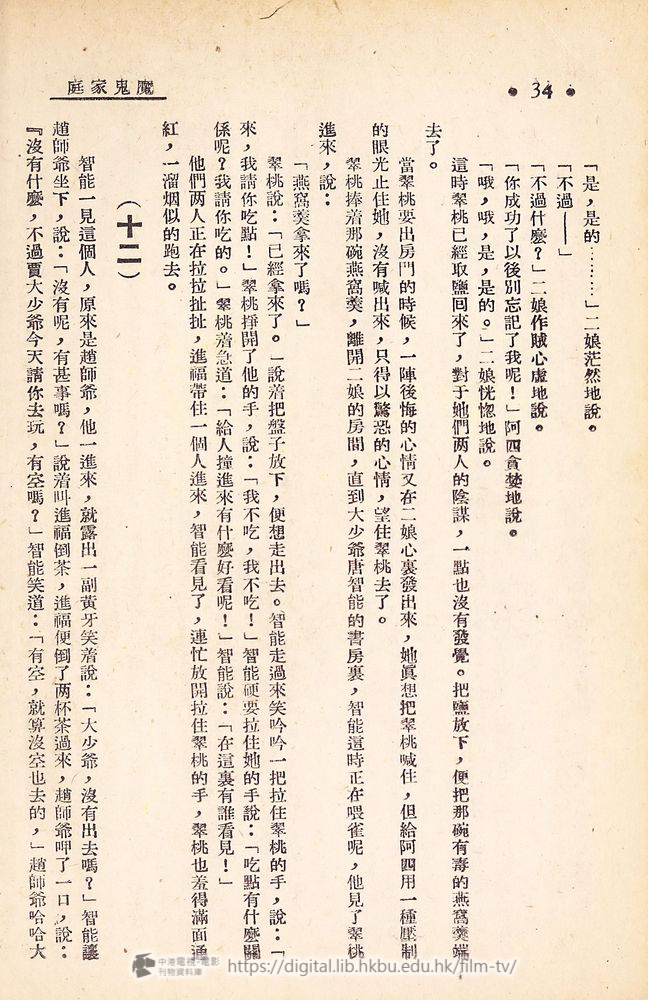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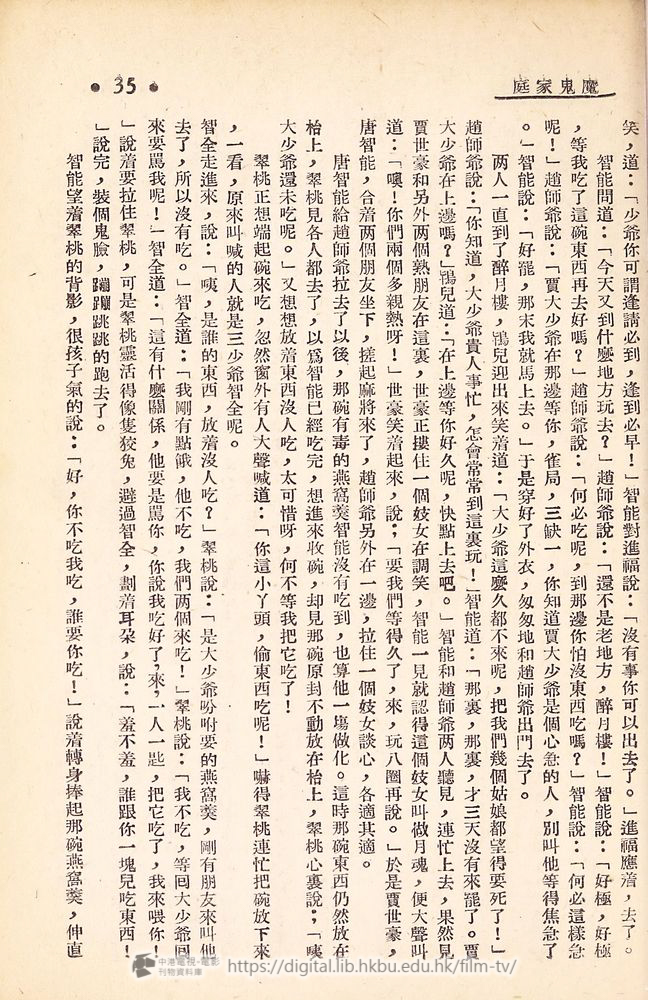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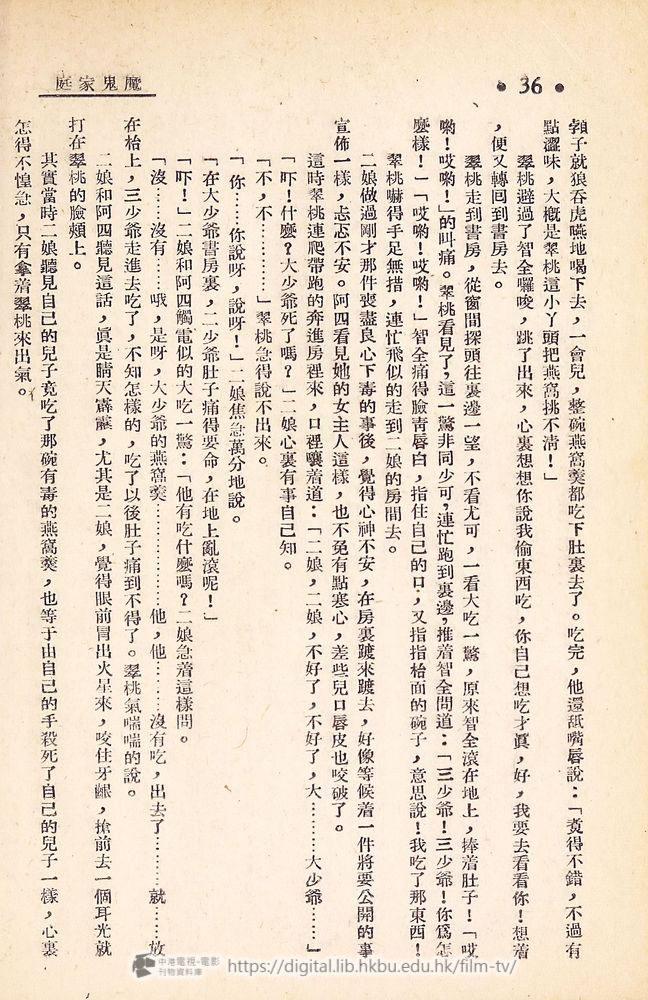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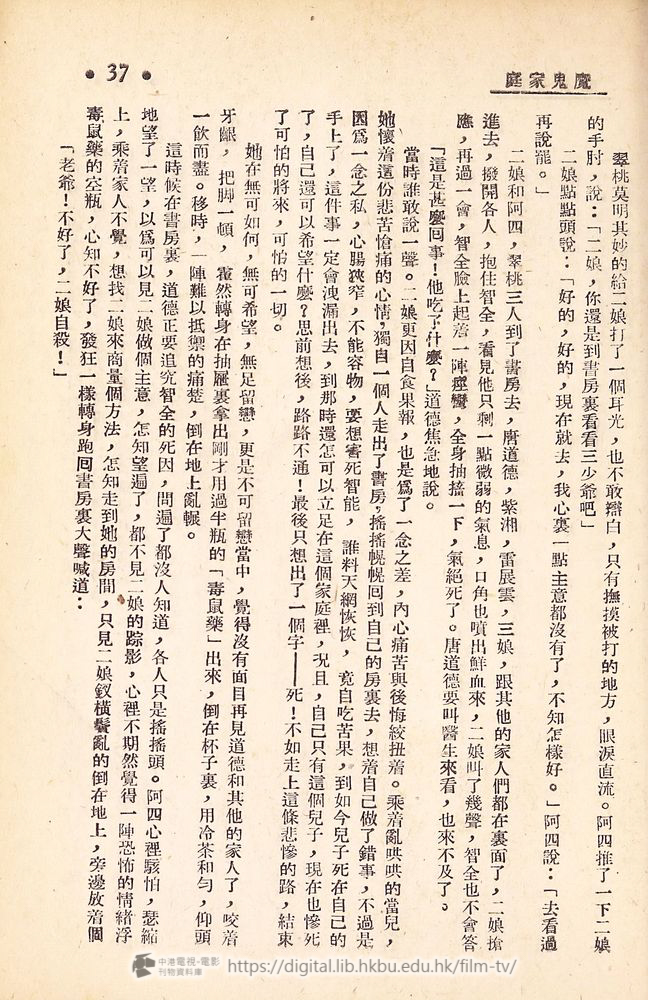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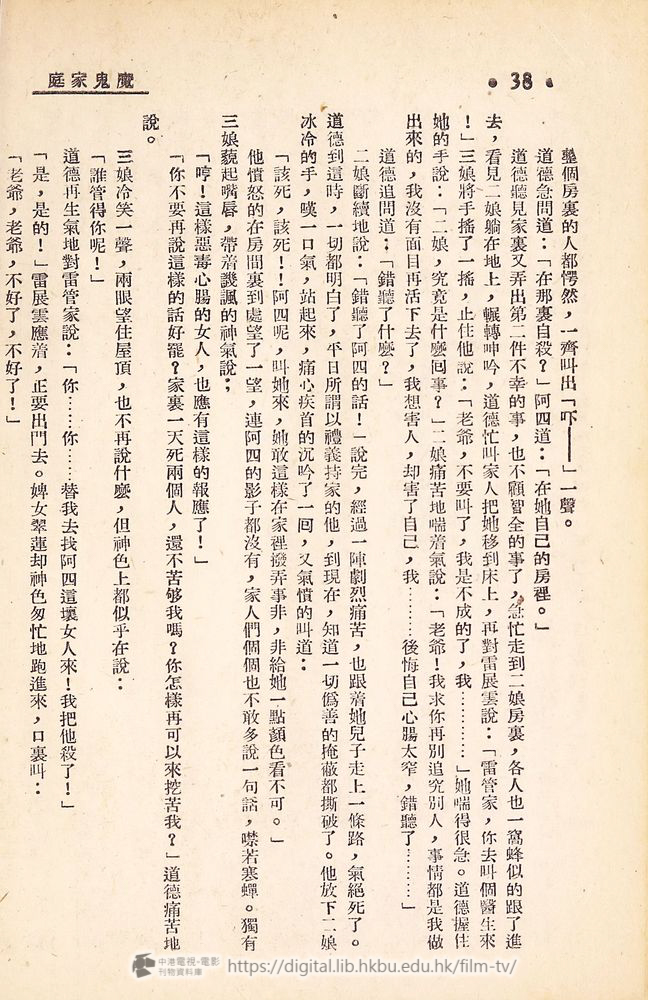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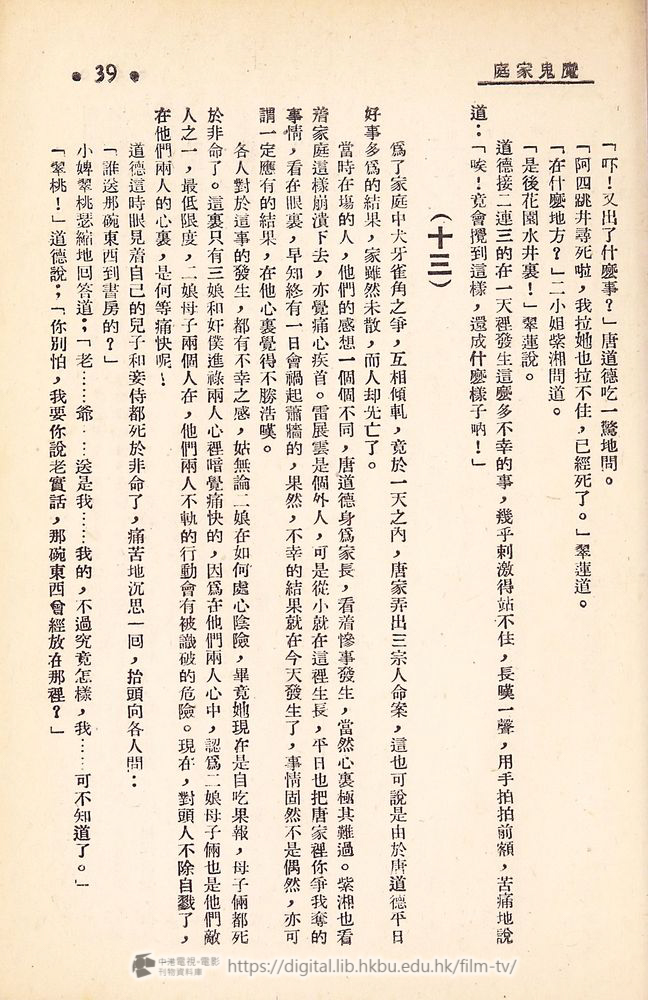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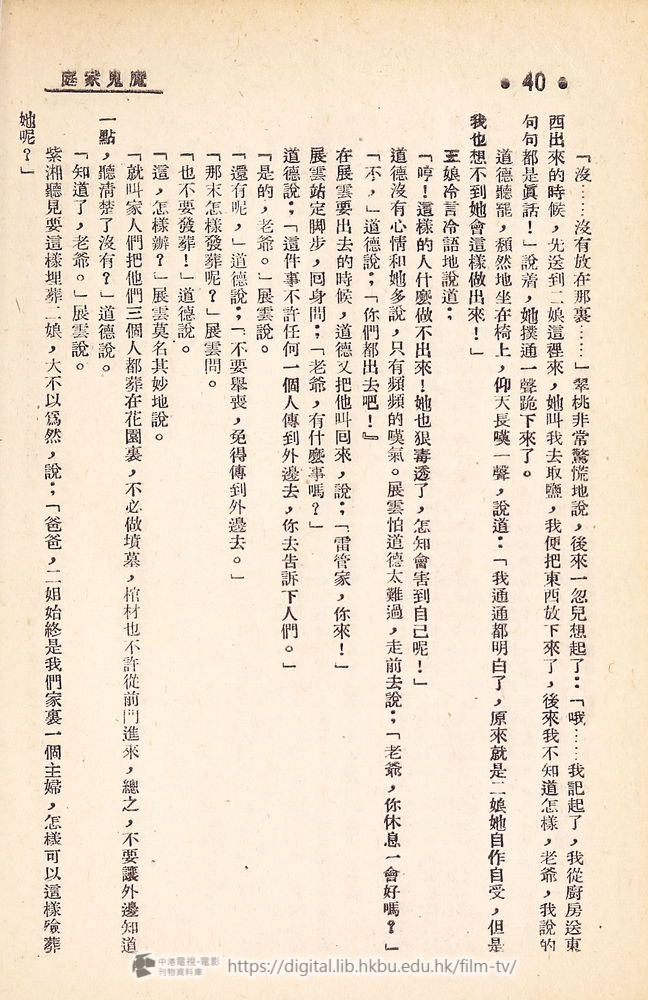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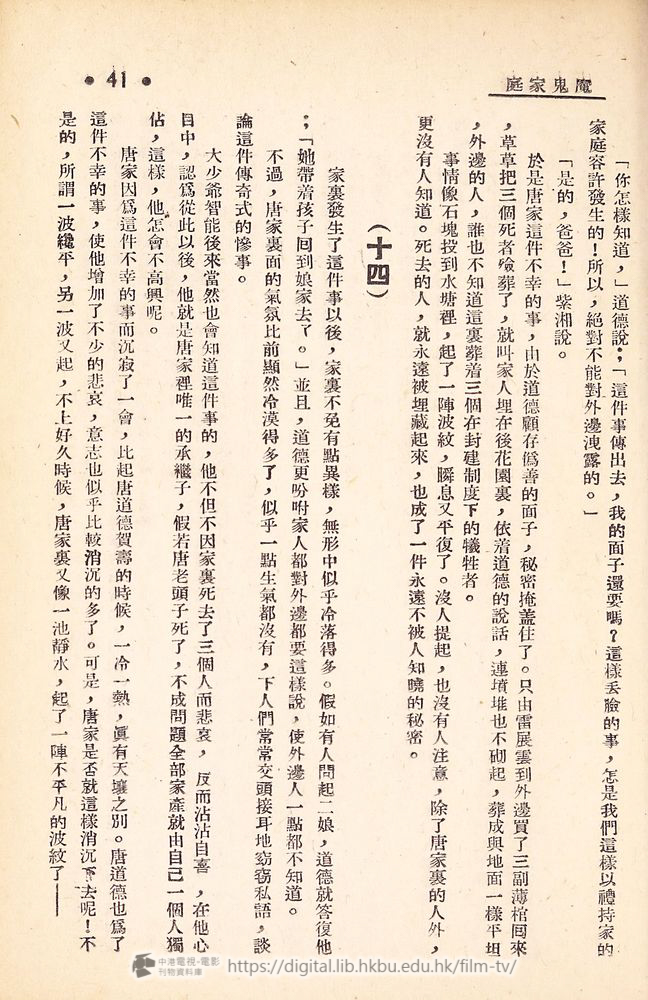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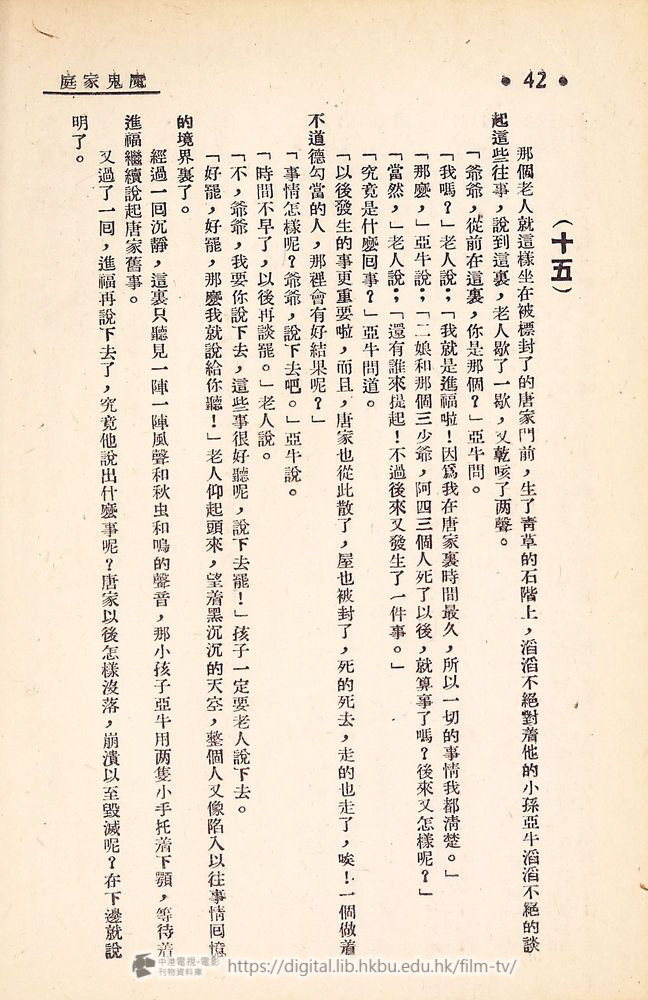
電影播音小説
魔鬼家庭(上集)蔣聲著
(一)
這天晚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城市的一方面,車水馬龍,笙歌徹耳,城開不夜。另一方面——是這城市西部,住宅區的一角,大約是初秋新凉的原故吧,顯得非常冷落。比起繁盛區域𥚃,一冷一熱,眞有天壤之別。
在這地方,一條白石砌成的街道,行人稀少,更冷靜得有點慘淡了。這街道的一邊,是間古老大屋,這屋子沒有人住,屋子的大門,油漆剝落了,上面貼着交加封條。大門對開的台階,長了青草,青草在蕭索的秋風裡,像個多病的老年人似的顫抖。街上,秋風吹過,刮起一陣塵沙,這一切的景象,死一般的靜寂,死一般的悲涼。
從屋內伸出圍牆外的白楊樹,落葉繽紛,灑到這毫無人氣息的街道上,又被凉風吹起,响着一片沙沙的聲音,沒有人清掃,也沒有人去理它,白楊葉散佈得滿地,無韻律的在跳舞,或被風送到遠處去。
大約是八點鐘過後,這地方就靜寂得像個子夜了。白石街道的另一端,起了一陣步履聲,打破這秋夜的靜寂,也像與落葉飛舞的聲音和鳴。
沒有多少時候,這種步履的聲音愈來愈近,轉拐的地方,現出兩個人影,沿着這古老大屋的圍牆走過來,這兩個人走近了,是一老一少,老人頭頂上白髮飄飄,走路時有點傴僂,一個孩子和他一起走着,他們兩人似乎是由很遠的路走來的,老人的手上提着一個小燈籠,是準備走夜路的模樣,大概因為路上還沒有十分黑的原故,燈籠還沒有點着。
走到大屋門前,兩人都有點累了,老人用他沙啞的嗓子,向那小孩説:
「亞牛,你累了沒有?」
「有點點累,爺爺!」孩子答他。
以他兩人的稱呼,該是兩祖孫了。那做祖父的老人家聽見孫子説有點累,便道:「亞牛,就在這石階上坐一會再走好嗎?」
「好的,爺爺,橫竪到家裡還遠呢。」
兩人説着,就在石階上坐下來。孩子囘頭望望那被標封了的古老大屋,看見門角上蛛網塵封,一對破爛的大燈籠還在風裏搖搖擺擺,在孩子看了一囘,向老人問道:
「爺爺,這屋子沒有人住的嗎?」
「誰住,封了。」老人淡淡地答。
「眞沒有理由,」孩子説:「為什麼這樣大的屋沒有人住,而多少人却沒有地方住要睡在街上!」
那老人微喟一聲,説:「這世界上沒有理由的事多呢,有房子住的人,誰想到有人睡在街邊!」
那孩子沒有出聲了,他用他的小手,有意無意地拔起石階縫𥚃長出來的小草,心𥚃在想着一串問題:為什麼有房子沒有人住?為什麼有些人却要睡街邊?又為什麼一間這樣大的屋子要封起來呢?
忽然,在蕭索的晚風裏送來一陣低沉的胡琴聲,聲音由細而大,漸漸的過來了,胡琴拉過了一囘,一個女子用她苦澀的歌聲唱起來:
「懷往事,淚沾衣,淒涼今日,暮景遲遲!誤我當初,風流兩個字,如今街頭丐食,苦處有誰知!欲學子胥,吹蕭吳市,好似失巢孤雁,無處棲遲!⋯⋯⋯⋯」
這歌聲打斷了小孩的沉思,胡琴的聲音是那末沉鬱⋯⋯小調的聲音是那末悲凉!
「咦,爺爺!有人唱歌呢!」那孩子叫道。
「唔,兩人叫化子!」老人說。但是,那唱歌的女人底聲音,和他們兩人的樣子,都似覺得很熟習,這些,
引起老人的注意了,詫異地自言自語説:「哦!是他⋯⋯⋯⋯」
那時兩個賣唱人也走到老人和小孩的前面,老人不由自主的站起來,定眼的望了他們一下,説:「進祿,三娘,是你們兩個!」
兩個賣唱的叫化子也站定一下,吃驚地望着老人,説不出甚麼,滿面羞慚,那女人更垂下頭來,連看也不敢再看。
老人慢慢地帶點感慨的語調説:「想不到會在這裡見到你們,也想不到你們會落到這樣的田地呢!」
那兩個賣唱者不敢說甚麼話,瑟縮地走去了。老人望住他們的背影,搖頭嘆息,説:「唉!你們也有今天的日子罷,惡因那會沒有惡果呢!」
賣唱人的影子從黑暗中很快的沒去了,那孩子看見這情形,動了他的好奇心,向老人問:「爺爺,為什麼你認識他們?」老人説:「認識,怎樣不認識,那女的還是我以前的女主人呢!」孩子説:「那麼這男的呢?」老人說:「掛名和我一同做工。」孩子問:「在什麼地方?」老人指着這古老大屋,說:「就是在這裏!」孩子問:「就是間大屋嗎?」老人説:「是的,這是以前很有名氣的唐家呢。」孩子不大明白,又問:「為什麼會被人家封了的呢?」老人説:「説起來就長了,你坐下來,我告訴你罷!」
於是他們又在石階上坐下來,老人乾咳了一聲,説出這個家庭的歷史:
(二)
由於大軍閥龍督軍統治下,這城市經過一個無邊黑暗的時期,藉住龍督軍勢力而作這城市的統治者,是一個姓賈名洪的軍人,他是龍督軍麾下一員軍長。這個賈軍長,因為追隨了龍督軍多年,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借着他部下不少的頭臚和鮮血,奠定了他軍長的職位。
賈軍長握下這城市最高的生殺權以後,舞弄權柄,勾結許多不法之徒,偷運毒品、軍火。這時,有一個大私梟,姓唐,叫做道德的,通過金錢和人事的關係,結識了賈軍長,由賈洪包庇他偷運毒品,這樣,他幹這不法的事,更明目張胆,肆無忌憚了。因此,他的財富像在雪地裡滾雪球,越積越大,越聚越多。從此以後,他
躋上了城中富商之列了。
唐道德是個愛面子,偽善的假紳士,他從來對偷販毒品的勾當,諱莫如深,即使他家人子女也不知道他作這種不法的事情的。平日,他滿口仁義道德,扳起一副無比莊嚴的面孔,不知他內幕的人,誰都説他是十足十,百分百的正人君子,對於他財富的積聚,有人説他是祖傳的,也有人説他是長袖善舞,營商致富的。
他很早就死了妻子,後來討了二娘、三娘兩個小老婆,兩個都是煙花女兒。二娘進唐家的門較早,有了一個孩子,叫智全,已經十六歲了,是個儍頭儍腦的大孩子,終日只有愛玩愛吃,三娘並沒有養過孩子。另外,死去的大太太遺下一子一女,二小姐叫唐紫湘,是個溫柔靜淑的女孩子,大少爺叫智能,與他同母妹子紫湘的個性完全相反,不務正業,終日在外邊胡混,鬥鷄打狗,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
在這家庭裏,就養着這樣一羣絕對不同心思,犬牙雀角,針鋒相對的人:二娘和三娘閗得最起勁,互不相讓:大少爺和兩個庶母也合不攏來,他看不起她們。祇有二小姐是個深沉的人,一切忍耐,為人和氣,祇有她受屈,却永遠沒有她對那個人爭吵的份兒的。
道德靠住賈軍長販毒發達以後,就在城市西部一條整潔清淨的街道上,修建了一家大屋,這屋子建設得美輪美奐,堂皇華麗,一家屋子就佔了半條街。
唐道德根本上是個亡命之徒,販毒的大私梟,但他最工心計,善於掩飾,在外邊自認是書香之家,説他先祖從外省遷來,棄仕從儒,後來又棄儒習賈,這樣糊裏糊塗的歷史,就算作他的家世了,外邊不明白的人,都説他身家清白,是本城的大殷商,誰知道他是個毒害人羣,為非作歹的私梟呢?
他不但在外邊是這樣,即使在家裏也扳起一副道學的面孔,終日滿口仁義道德,教兒女們以禮相守,可是,轉變一副面孔時,他就是一個唯利是視,無惡不作的壞東西。
(三)
這天是唐道德五十歲大生辰,以他的面子,以他的地位,當然要大大地鋪張一下,幾天來,唐家的管家先生雷展雲,忙個不了,除了收受賀禮以外,又要打點佈置地方,計算酒席等事,一天到晚手足不停,到處奔跑。
這個雷管家,看起來不過是個廿五六歲的青年人,做事十分幹練,他比其他大家庭裏的管家,都好像要年輕一點,他到唐家來當管家,是有一段秘密的歷史的:
原來雷展雲的父親雷四,也是個不正派的人,以往在唐道德還未發跡時,是一雙老搭檔,一起在外邊做販運毒品的勾當。有一次,販毒的事失了手,道德為了脱身,推了雷四去擋災,雷四是個老粗,只憑他的胆子和廉價的性命去混兩頓冒險的飯吃,心思不比唐道德精細,根本就不知道唐道德的毒計,結果,性命丟了,到死時還不知道唐道德出賣了他,瀕危的時候,還對道德誠懇地要求他照顧自己的家庭和他的獨子雷展雲。後來,唐道德起家以後,懷念着雷四無辜死去,也不過為了替代自己犧牲,同時,道德也為了要保守秘密,不使自己過去與雷四那段見不得人的轇轕宣泄出去,便接了雷展雲到自己家裏,陪着自己的兒子智能和智全兩人讀書。到了後來,展雲的行動舉止,中規中矩,道德施以小惠,束縛着他,便叫他在家裏管理一切雜務和賑目,這樣才當起唐家的管家來。
展雲的個性最孝順,奉養着他的寡母,把在唐家所得的收入,都拿囘家裏去。他們母子倆實在也知道雷四之死,完全是為了道德,不過時機未至,一切都容忍着,也是為了生活哩。
這天唐道德的生辰,內外佈置得煥然一新,中堂上燃起一對大壽燭,還掛上一幅大壽燭,上邊是用綵絲綉着一幅「福祿壽圖」,兩旁一副對聯,寫着「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這些壽屏和壽聯是賈洪軍長送來的,因為他是本城高級武官,掛起這壽屏,當然在道德方面是增加了不少光彩。
中間是客廳,早已到了不少親戚友好各色人等,再對開有一班樂班,每個客人進門時都吹奏起一次鼓樂,這算排塲,也算是歡迎。
唐道德今天是壽翁,喜氣揚眉的在大堂中間,站在壽屏前面,接受每個賓客的賀禮,口裏説出一連串「恭喜,恭喜!」
雷展雲忙得不亦樂乎的指揮着下人們招呼賓客,不時一兩個人接二連三的到來問那,好在展雲辦事是有魄力,够爽快的,對於一切都能應付裕餘。
在大廳對外的走廊上,三少爺唐智全正手拿着一只鷄腿子,在亂咬亂嚼,這時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丫頭名叫
翠桃的走過,智全一把將她拉住,嚇得翠桃紅着瞼,捽開智全的手,說:「三少爺你別這樣,給人家看到有什麽好意思呢!」
「笑話,誰會看到!」智全一邊說一邊將鷄腿往她口裡塞:「來,我請你吃鷄腿!」
「我不要吃你的,你別拉住我!」翠桃用力要掙開智全的手,但是掙不脫。
兩人正在推推拉拉的時候,智全的媽媽二娘從後邊走來,跟着的是智全的褓姆阿四。二娘見了她兒子智全和翠桃這樣子,冒火可大了,但他却沒有責備智全,搶前一步「拍!」的一個耳光,就打在翠桃的腦後,駡道:「你這賤丫頭,竟敢逗三少爺玩呢!」翠桃無緣無故的捱了一個耳光,受了一頓臭駡,眞是有寃無路訴,但是怎敢出聲哩?只有垂手站在一旁,任由二娘喝駡。阿四在旁邊道:
「二娘,算了吧,外頭人客多,何必跟他鬧呢?」
「還不滾開,站在這裏等死嗎!」二娘厲聲一喝,翠桃如奉玉旨,低頭走去了。
二娘再望了她兒子三少爺智全一眼,見他滿嘴滿手都是油膩,說:「你看,你成人樣不成!整天就是會吃,你就愛作賤自己,跟丫頭們打交道,還不跟我到外邊見見客人去!」三少爺智全給他母親說了一頓,却亳無表情,只是儍笑一陣。
這時候,走廊的另一端傳來一陣脚步聲,二娘囘頭望一下,來的人却是三娘,後邊跟着一個年輕的僕人——進祿,三娘走得嬝嬝娜娜的,煙視媚行。她走到二娘身邊,也沒有打招呼,掀嘴輕蔑地笑了一下,二娘也不屑地暗駡一句「狐狸精」,拉着智全去了,阿四當然也跟在後面。三娘並沒有理會到二娘走,去行近出大廳小門上的時候,用手一傍她光可照人的髮髻,畧整一下她的烏緞裙子,囘頭笑着問進祿道「喂!你看看我髻兒歪了沒有?裙子有縐紋嗎?」
「沒有,沒有,三娘今天的裝扮漂亮極了,包管所有女客爲之失色,男客們個個顚倒!」進祿諧笑着答。三娘俏罵一聲:「誰要你恭維我!」又一搖一扭的走出大廳去了。
在大廳上三娘和二娘各有各向賓客們打招呼,唐道德心裡正急着等候賈洪到來,那時什麽賓客都到齊了,就是賈洪還沒有到。道德等得悶了,招手叫雷展雲過來,在他耳邊問:「賈軍長爲什麼還未來呢?」
「我早已派人去請過三次了,恐怕快要來吧。」雷展雲説。
「你派人到外邊等候着,賈軍長來了就通知我。」道德説。
「是的。」展雲應着,走開了,叫了一個老家人過來,吩咐説:「進福!你到外邊守着,見賈軍長來立刻通知!曉得嗎?」那老家人應着出去了。
雷展雲又應付着兩三件雜務,一囘,天色齊黑,老家人進福匆忙的走進來,向展雲説:
「雷管家,賈軍長和他的大少爺到了。」雷展雲聽説賈洪到,立即走到唐道德面前報告這消息,道德聽見,連忙走到外邊迎接,展雲和進福也跟了出去。
才走到中門,已經見賈軍長和他的兒子賈世豪,還有都位幕僚趙師爺,好幾個隨從人員走進來。賈軍長紫索臉皮,粗眉濃目,腹大便便,賈世豪臉皮白淨,未言先笑,一副浮薄樣子。
唐道德迎上去,拱手作揖道:「賈軍長太賞面了,難得大少爺也抽空到來!」賈洪發出一串粗魯的笑聲,説:「恭喜!恭喜!」
在震天似的鼓樂聲中,道德讓了賈洪和世豪一班人,到了大廳上,在正面宮座椅坐下,由進福奉過了茶。賈洪囘頭向他的兒子世豪説:「你還不跟世伯拜壽呢!」道德止住道:「不敢,不敢,我那𥚃受得起!」賈洪説:「這是應當的!」説着,一定要世豪跟道德拜壽,經過一番謙讓,道德結果受了世豪一揖,
接着二娘三娘也過來見過這位貴賓,賈洪向道德問道:「為什麼不見了你家的大少爺呢?」道德到處望了一下,也見不到智能,便向雷展雲問道:「智能在那裏?」雷展雲向着那邊橫廳一指,説:「大少爺在那邊玩呢。」道德向橫廳望過去,果然見到智能在那𥚃跟一班人擲骰子,呼大叫小的。道德見了,面上露出不滿意的顏色,説:「哼!這畜牲就曉得玩,雷管家,你去叫他過來見軍長!」
展雲還未及答應,賈世豪便笑着擱住説:「他高興,隨便他玩吧,我也去玩兩手。」
道德聽見世豪説要玩,登時顏色也放寬了,堆下笑臉説:「哦,世侄也有興趣嗎?好極了,逢塲作慶,玩玩也無妨的。」説着,便同世豪,趙師爺兩人走到橫廳去,智能正在那裏呼五喝六的賭錢,一見了他父親過來,住了手,叫聲:「爸爸!」
道德本來不高興智能賭錢的,認爲有失家敎。但是賈世豪也要賭,便曲意奉承了,向智能說道:「你陪賈大少爺玩一會,好好的招呼賈大少爺。」又向世豪說:「你隨便玩吧,我還要去跟你尊翁談談呢。」賈世豪說:「世伯別客氣,請便!」道德吩咐智能陪世豪玩了以後,又再到這邊來,跟賈洪談話了。
「唐翁,近來還有運貨嗎?」賈洪說這個「貨」字,特別加重,他說的貨,當然是「黑貨」了。
「近來⋯⋯⋯⋯」道德望望四週沒有甚麽人注意,說:「現在貨價不大化算,不過下個月有一幫要來,到時還要借助軍長的大力!」
「當然啦,我和唐翁你難道還是第一次交手嗎?哈哈⋯⋯⋯」賈洪的笑聲像梟鳴,陰森得怕人。
「要是軍長能够帮忙,那末小弟也有一碗飯吃!」唐道德陪着笑臉說。
「大家老朋友,別說客氣話,總之有飯大衆吃。」賈洪說。
兩人正說話間,二小姐紫湘和一個侍婢翠蓮走過,道德把她叫住:
「紫湘,你過來!」
紫湘和翠蓮都停了脚步,走近來叫聲:「爸爸!」道德說:「紫湘,這是賈世伯,你給賈世伯請安。」紫湘向賈洪點點頭,叫聲:「世伯!」
「這位是你的小姐嗎?」賈洪說:「長得十分標緻呢!」
「過獎,過獎,這正是小女紫湘!」道德說。
紫湘見沒有別的事,要去了,道德叫住她,說:「紫湘,你的賈世兄在那邊玩骰子,你到那邊倒杯茶去!」紫湘本來不願去的,但給道德催促着:
「去吧,彼此兄妹一樣,見見也不妨事的。」
紫湘沒法推搪,祗得叫翠蓮端了個茶盆,倒了一杯茶,另外捧了個糖菓碟,走到橫廳那邊去了。
那時世豪正和一班濶少們,賭得入神,趙師爺在旁邊作臨時參謀,世豪擲羸了幾手,枱面上的光洋堆滿一堆,這囘又輪到他做庄家了,他抓起骰子,大喝一聲:「全紅!」向碗中一撒,那三顆骰子滾了一會,果然三點「一」!世豪笑吟吟的把枱面上的錢,都抓到身邊來了,趙師爺謟媚的笑道:「今天大少爺眞有辦法,要什麼
有什麼!」
世豪正在連坐庄家,抓起骰子,又要撤向盤子裏的時候,耳邊聽得一聲:「請茶罷;賈大少!」這淸脆悅耳的聲音,像春天的黃鶯穿過柳條啼唱似的,這是一種有力的吸引,不由得使世濛轉過頭來一望,這一望,引起的麻煩可多哩。
(四)
賈世豪正在和唐智能等一班紈袴子弟在賭錢的時候,忽然聽見後面滴滴鶯聲叫句:「請茶罷,賈大少!」世豪縮住撒骰的手,囘頭一望,祗見一個嬌滴滴的女郞,粉面朱唇,明眸皓齒,遞着一杯茶和一個糖菓盤過來,起初世豪還以爲是個丫頭,再細看她的衣飾,湖水濶袖鑲邊小襖,黑緞百褶羅裙,分明是個女眷打扮。世豪看她一投足,一舉手,一言,一笑,無處不蘊藏百分之百美感,登時魂飛魄蕩,連茶杯也不會接了,呆呆望住紫湘的瞼,望到紫湘粉面通紅,垂頭避過他的視綫,心裡却怪父親過份奉承賈洪父子,叫自己親手倒茶給一個這樣輕薄的人。旁邊的婢女翠蓮,是懂人事的,見紫湘這樣難堪,便道:「賈大少,請茶罷!」
趙師爺見世豪這様沒有禮貌的望住紫湘,也生怕在大堂廣衆中失禮,碰了一碰世豪的手肘,喑示給他,到這時,世豪才驚覺了,連忙說聲:「謝謝謝謝,!」把茶盞接過,紫湘見他接過茶盞,才鬆了口氣,總算打破這難堪的塲面,說聲:「幾位慢慢玩!」便同着翠蓮走去了。
世豪還是望着紫湘的背影,呆呆地愕住,智能重重地在他肩膊上一拍,說:「喂,到你啦,忘了嗎?」世豪不好意思的笑道:「是,是的,該到我擲了。」便拿起骰子來在盤中一擲,撒出個「一二三」全小,通賠了。
世豪賠錢過後,趙師爺知情識趣地在世豪耳邊說:「你何不問問唐大少爺,看那女子是個什麼人!」世豪不斷點頭,等囘賭完了以後,便把智能拉在一邊,問:「剛才給我倒茶的是府上什麽寳眷?」智能儍頭儍腦的說:「她嗎?是我妹子!」世豪笑道:「怪不得樣子像你呢!」
世豪是個癡心人,一意想再見見唐紫湘小姐,可是到開席,直至散席,始終沒法見到她,大槪紫湘另外在
裏邊招呼其他的女賓去了。
那天的酒席雖然是山珍海錯,水陸紛陳,但世豪却食不甘味;眞是嘉肴不旨,美酒不香,因爲他一心想再見紫湘,却大大的失望了。終於不能再見到她一面。
其實這次道德命紫湘給世豪奉茶,不過是表示尊重世豪,也就是尊重賈洪而已,並沒有其他的意思,不過紫湘確實長得嬌美動人,使這個好色的世豪,一見動心,這也是道德始料不及的。
世豪平日仰仗他父親的勢力,在城中肆無忌憚爲所欲爲,要得必得,誰也要讓他三分,現在旣然對紫湘有意思,當然非得到手不可。但是,紫湘究竟是一個千金小姐,又是他父親的朋友底女兒,名份上是世兄妹,很難得一想就成,也不同路柳牆花可比,任人攀折,世豪平常對女人,也不過是對一些可以用金錢就可以買得到的女人,並沒有對一個良家婦女着意過,因此今囘見了這位艶麗端莊的唐紫湘,實在大有躊躇了。
等到宴罷囘家以後,在賈世豪的腦海中,始終還是印着唐紫湘粉面朱唇,明眸皓齒的倩影,念念不忘,弄得失魂落魄,寢食不安。
(五)
世豪自從在唐道德的壽筵中遇見了紫湘以後,天天痴想,究竟他用甚麽手段來得到紫湘,能不能够得到她呢?這裏暫時不提。
在唐道德家裏,時常是充滿鬥爭意味的,就因爲家庭紛爭,唐家裏發生了一件大悲劇。現在就把這齣悲劇的經過說出來,這也可說是一個因果。作奸犯科的人,始終沒有好果的。唐道德販毒致富,其實他的財富,是由不少生命,人家的血汗,和做了多少不道德的事積累得來的,報應還沒有在他的身上來臨以前,家人子女先受果報了。說起因果的事,也並非迷信與守舊,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非常合理,也是必然的事。
自從唐道德五十生辰,大開壽筵慶祝以後,經過一番熱閙,唐家又由波動而歸於沉寂了,但是,這個家庭裏一切糾紛,爭執的事,還是不斷發生,不時都起着永不停比的暗潮,也可說這個家庭永無寧靜的日子。在壽誕過後。雷展雲把一切開支數目計算妥當,外邊的賬目大致也支付完畢了,只剩有多少錢銀去曾淸付
的。一天,展雲正在賬房裡敲起算盤,拈起毛筆計算他永遠算不完似的賬目,老家人進福走進來,手裹拿着一張賬單,走近去叫聲:「雷先生!」
「有什麼事嗎?福伯!」展雲這樣問。他從來稱進福作「福伯」的,一來因爲進福年紀已老,二來展雲做人處世也十分謙恭有禮。
「酒莊拿來的酒賬單。」進福遞上手裡的賬單說。
展雲接過賬單,六六三十六,二一添作五的在算盤上敲了一囘,計算淸楚,並無錯誤,便在抽屜裏拿出錢來,交給進福說:「福伯,你拿去結給他罷。」進福接了錢,拿到外邊結了賬,那酒莊的夥伴去了以後,門外傳進來一陣亂哼的歌聲,進福一看,原來是大少爺智能托着一個雀籠,一搖三擺的哼着戯曲囘來,一見了進福,問道:「喂,雷管家在裏邊嗎!」進福說:「在賬房裡,大少爺!」智能把雀籠遞給進福說:「跟我拿到裡邊去!」進福接過雀籠,智能便直走到賬房裡邊去。
雷展雲還是在賬房裡算賬寫數,見智能走進來,很客氣的站起來,說:「大少爺,請坐!」智能坐下,劈頭便問:「雷管家,有錢嗎?」展雲說:「錢是有的,有什麼事?」
「給我兩百塊…」智能攤開手說。
展雲翻開賬部一看,說:「大少爺,你不能支錢了。」
「我爲什麽不能支錢?」智能皺起眉頭說。
展雲笑着說:「大少爺,你是曉得的,家裏每個人都規定了使用錢。」
「這個我知道!」
「就是爲了這樣,你使用錢早就支過了,而且還支過了一點錢呢,所以我不能再支給你了。」展雲說。
「你就算我再多支二百塊好了。」智能說。
「這怎樣能够呢?老爺再三吩咐過,不許多支一個例外錢。」
「哼,眞麻煩,支兩個錢也不可以。」智能很不滿意地說。
「這事你要原諒我,我的職責是這樣的。」雷展雲說。
智能見要錢不到,心中不快,但是規矩是父親定下來的,也不敢過份執拗,硬要不來,只軟求,放低聲氣說:
「喂,雷管家,就算借兩百塊給我用好嗎?我確實急着要錢用。」
「這個我很難做得到,」雷展雲說:「要是老爺査起賬來,我難以說得過去。」
智能軟又不成,硬又不成,一點辦法也沒有,正要再說下去的時候,三少爺智全走進來,連智能也不招呼,開口便向雷展雲說:
「雷管家,給我錢!」
展雲應了句:「好,你等一等。」便又打開賬簿査了好一囘,取出鎖匙,就在保險箱裡拿出兩百塊錢出來,交給智全說:「你一齊拿去好了。」智全接了錢,就想出去。
大少爺智能因爲自己支錢不到,智全一要就到手,有點眼紅,說:「亞全,你爲甚麼要支錢!」
智全平日也受着他母親二娘的「敎訓」,不識尊卑,從不當智能作兄長看待,當下便藐起嘴唇說:「我要用就要支錢,你管得着我!」雷展雲說:「大少爺,他上個月的零用錢還沒有支呢。」
智能摸着下巴,想了一想,對智全說:「你把錢拿來給我!」智全睜大眼睛說:「我的錢怎會給你?」智能作威作福的大聲道:「你給我不給!」智全把錢抱住,說:「不,不給!」智能不顧道理,走過去將智全手裏的錢都搶去。智全雖然是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可是平日嬌生慣養,性子嬌痴,現在見自己的錢都被搶去,頓地大哭。智能拿出十塊錢來,遞過去給智全說:「哪!拿去吧,你怎會要用到那麼多錢!」智全那裏肯接,在那亂哭亂嚷,雷展雲看見鬧得太不像樣,走過來勸智能說:「大少爺,你何必這樣,還給他吧,等會吵起來事情又多了⋯⋯⋯」話還未說完,智能不服氣道:「這是我的事,誰管得着!」
展雲見智能這樣野蠻,也不便多出聲,只好不理了。
正在喧鬧間,智全的褓姆阿四走進來,一眼看見智全在哭鬧,連忙走過去問:
「三少爺你哭什麽?誰欺負了你?」
「大哥搶了我的錢!」智全哭着說。
「哎喲!大少爺,你爲甚麽搶了他的錢呀?」阿四憤憤不平的說。
「誰搶了他的錢!你那隻狗眼看見的!混賬!」智能罵道。
「他是搶我的錢,他不承認罷了。」智全擦着眼晴說。
「三少爺!你別哭,吿訴你媽去!」阿四說。
「哼!」智能不屑地說:「去你的吧,我怕你!」
雷展雲看到這樣子,本想說句公道話,可是明知勸阻不來的了,祇有忍着不出聲。心裏却不勝喟嘆,喑說:「這樣的弟兄,這樣的家庭,有什麽意思呢?那裡會有好結果!」
阿四正想拖着三少爺智能去向二娘訴苦,却碰着二娘到來,說:「亞全,整天找你,你到這裡來幹甚麽?」說着,看見智全眼淚滿徇,詫異道:「咦!亞全,你哭什麼?誰得罪了你?」智全抽咽道:「媽,大哥搶了我的錢。」二娘疑惑道:「搶你的錢?」說時望着大少爺智能,智能却滿不在乎在冷笑。二娘向智全追問,說:「他怎樣會搶你的錢?」阿四在旁邊加口道:「二娘!你也應該話大少爺兩句,他眞的搶了三少爺的錢哩!」
二娘本來是疼惜自己的兒子的,現在聽見智全給他的哥哥欺負,心肝肉痛,盛氣地走近智能面前,向他質問道:「你甚麽理由這樣野蠻,搶了亞全的錢!這是什麼規矩!」智能平日對二娘就不很尊重,不服氣道:「笑話!誰搶了他的錢!」阿四說:「二娘,你別聽他說,你分明是搶了三少爺兩百塊錢!」二娘說:「你怎樣搶了他的錢還可以不認呢!」
「哼!」大少爺智能明知自己理屈,却硬嘴說:「小孩子,這樣的年紀,花那麼多錢幹甚麼?」
「你別管他應不應用,總之不是你的錢,你就不應該要!』二娘反駁說。
「你說得好笑,」智能冷笑一聲說:「在這家庭裡,那一份不是我大少爺的,誰敢動一動!」
「這是什麽話!」二娘發氣說:「現在還是老爺當權呢!」-
「我爸爸死了以後,什麼東西都是我一個人所有的,何况我要他兩百塊錢,算得什麽!」智能說着,大搖大擺的走出去了。
二娘聽見智能說出這樣囂張無理的話,氣得臉色都變靑了,要想拉住智能來理論下去,但他却不顧而走,二娘只是在乾急,一點辦法也沒有。雷展雲走過來勸她,說:
「二娘,別同他一般見識,囘去休息吧!」
二娘氣憤地向智全說:「我們走吧,囘頭我向他的爸爸說知,看他是不是敢這樣任性!」說着,拉了智全帶同阿四囘到自己房裏去了。
(六)
雷展雲給他們幾個人鬧了半天,好容易到現在他們才走出去。展雲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樣一個家庭,你爭我奪,簡直沒有一個正派的人,就連門前石階也是不乾淨的!」
他想着,見案頭還有多少工作未做完,便坐下來重新再做了。怎料坐下來不久,正寫上兩行數字,門外又是一陣步履聲,跟着一串銀鈴似的笑聲响起來,展雲一陣惡心,想道:「誰又來麻煩我了!停了筆抬頭一看,見進來的人就是家主唐道德的三姨太太三娘,她手中捧着一個小銀盆,銀盆上放着一小盅熱辣辣似乎是食品的東西。三娘眉花眼笑的走近來說:「哎喔!雷先生!何必這樣用功呢?做工夫太多會做壞人呀,來,我請你吃點東西,好嗎?」
原來三娘本是個勾欄女兒,他嫁給唐道德做第三房侍妾,也不過爲貪兩個錢而已,絕對沒有情愛可言。她在風塵中的時候,本來有一個情人的,這就是進祿,進祿和三娘在從前,本來就有了特殊關係,到三娘嫁了唐老頭子以後,又和進祿難分難捨,便把進祿跟到唐家裏來,改了這個名字,掛名做僕人,實則却胡裡胡塗,幹出多少不可吿人之事。但是三娘是個水性楊花的女子,並不是這樣就滿足的,進了唐家以後,又垂涎展雲的英俊,對展雲又存着有非份之想了,屢次對展雲諸般挑逗,可是展雲畢竟是個正直的人,有光明的理想,有希望,珍重自己的前途。現在暫時屈守在唐家做個管家,也是因爲家貧親老,無法遠走高飛,不得已從權。這樣,怎可以接受三娘的勾引,做出苟且的事情呢!因此三娘每次到來施以諸般勾引,也用嚴正的態度拒絕她,使三娘大感失望。
不過感情在人眼中,心中,實在是件奇異的東西,似乎越難得的感情,就越覺得可貴。正如採蘋果一樣,樹杪最高的蘋果最難摘到的,未必一定好吃,但因爲獲得困難,心裏就覺得特別好了。也許三娘也是如此,展雲越使她失望,她愛展雲越深。她以爲,以她蛇一般的嬌姿,撫媚的面貌,細心甜意,總有一次會使展雲動心的。所以今日又藉住要請展雲吃東西的機會,親手送了這碗燕窩羹到賬房來給展雲吃,其實,也不過想同展雲接近多點罷了。
雷展雲平日對於三娘這種無事殷勤的態度,非常厭惡,現在見她捧了這盞燕窩羹來,更加眉目含情的樣子,心裡起了憎惡之感,暗罵一聲:呸!淫賤的女人!但是,自己的職位是個下人,她是個女主人的身份,也不能不作出虛僞的應酬,說:「謝謝你,三娘,我不餓!」三娘得寸進尺,更捱近展雲身邊,吃吃的笑道:「卽使不餓也可以吃的,這又不是米飯,不過一口甜湯罷了!」展雲正色說:「是什麼東西我也不願吃,三娘,請你端囘去罷!」三娘又捱近一點,說:「旣然端來了,怎樣又辜負了我一片心事,還是吃了吧!」
三娘說「心事」兩字,說得特別响,好像在暗示另一種不正當的意思。可是正眞,坦率的展雲,不但不會受到誘惑,反而感到極度厭惡與不耐煩。
三娘見展雲閉着嘴不做聲,以爲他意轉了,更進一步的說:「唔,雷先生,我對你好才是這樣的,爲什麽總不領略!」
展雲聽她越說越覺剌耳,霍然一聲站起來道:「三娘,請你尊重一點自己的身份,上下有分,男女有別,我已經不止一次向你忠吿了,我防物議,你畏人言,給人家看到,還成什麼樣子!」三娘這時候不正當的念頭,已經蒙蔽了她的羞恥心與理智,她並沒有給展雲這樣嚴正的說話打消她的歹念,反而睨視着展雲,拖長聲氣地說:
「哎喲!你何必這樣認眞,我和你有什麽上下,什麽物議,人言,都是迂腐的論調,我看你也是個知情識趣的人呀,唔,怎樣你老是不接納我對你的好意!」
展雲見她越來越放肆,越來越不像樣,决絕地把頭偏過去,說:
「我不會知這樣下流的情,識這樣無廉恥的趣,請你不要阻碍我工作,沒有什麼事請你出去吧!」
三娘給他這樣奚落,心裏暗想:難道眞有這樣的一個再生柳下惠?我就不會相信!以前在靑樓裏的時候,誰不要顚倒在我裙下!好,我看你能够硬到底不?於是她再走前一步,伸出手來搭在展雲的肩膊上,妮聲說;「雷先生!你眞的生我的氣嗎?」
展雲正想捽開她的手,突然後邊「哼!」的一聲,說:「幹得好事!」三娘和展雲愕然,囘頭一望,看見說話的人,竟是二娘,不知她什麽時候進來了,兩人還不知道呢。
原來剛才二娘和大少爺智能爲了搶錢的事嘔了氣後,就領了她的兒子囘到自己的房裏去,打算要向老爺唐道德訴苦,可是道德却在外邊沒有囘來,智全又一味哭鬧,怎樣勸也勸不來,一定要囘被哥哥搶去的錢,二娘本來是疼惜兒子的,現在兒子受了人家欺負,在這裏哭鬧,弄到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得說:「好了,你別哭吧,我去向雷管家再支二百塊錢給你!」所以又轉到賬房來,却碰見三娘和展雲勾肩搭背的樣子。
本來二娘三娘兩個從來就不和的。現在三娘這樣不規矩的行爲,給二娘看見了,不禁勾引以往的仇恨,連支錢給智全的事都放下了,冷笑一聲說:「原來三姨太太會來到賬房勾引管家呢!」
三娘見二娘突然進來,把自己的秘密看穿了,嚇得連忙把搭在展雲肩上的手放下來,及至聽見二娘說出譏諷的說話,老羞成怒,反駁說:
「笑話,你道誰跑到賬房來勾引管家了!我不過來這裡支錢罷了!」
「支錢?」二娘說:「支錢要和管家動手動脚勾肩搭背呢!」
「你看見誰動手動脚,勾肩搭背!」三娘强嘴說。
「誰做出來就說誰!你別當家裏人的眼睛瞎盡了!」二娘藐起嘴唇說。
「就是你瞎了眼睛才會說廢話!」三娘針鋒相對地說。
「我眼睛一點不瞎,心裏雪亮,慣做野狐狸做不得家貓!」三娘一點也不退讓。
「你敢說那個是野狐狸,你又是什麽!」三娘想衝過去,大聲地說。
展雲見吵得太不像樣子了,勸着道:「二娘,三娘,大家都是自己人,有甚麽好吵呢,家裏有上有下,給人聽了有什麽好意思!」
二娘擺出先進門的架子說:「誰跟她吵,不配,這是家規!」
三娘也不蝕半分,道:「哼!你這樣的人還説家規呢,老爺不是在花街把你帶囘來!」
二娘聽見三娘説出自己的身世,大大的冒起火來,罵道:「你又是什麼的來頭,也不是在花街帶來的。」
她們兩個你一句我一句,鬧得不亦樂乎,展雲勸多少也勸不住。正在吵作一團的時候,二小姐紫湘在房裏看書,看得有點不懂的,要走到賑房裡問雷展雲。平日他們兩人也常有這樣的事,因為展雲認為在唐家裏,紫湘是最純潔,最和氣的一個。紫湘也認為展雲是個前途,有希望的青年,不會久居人下的,也樂意與他接近,不會以地位而賤視展雲。
當紫湘走進賑房去的,見兩個庶母在那裏爭吵,紫湘是個愛和氣的人,也走過來幫口勸道:「二姐,三姐,大家都是自己人,別鬧得不像樣吧,一個少一句不是就可以了嗎?」這樣,展雲勸住二娘,紫湘勸住三娘——一人勸一個,送了出賑房,分頭而去,一塲舌戰,總算停息了。
(七)
二娘和三娘兩人負氣走後,展雲和紫湘走囘賬房裏,展雲用手拍拍前額,痛苦地説:「這樣的環境,眞是多一天也不想留下去!」紫湘安慰着他説:「雷先生,你忍耐一下吧,他們吵他們的,你做你的工作,何必理他們呢!」展雲説:「你不知道的,麻煩的事實在多呢。不是這個來要錢,就是那個來要錢,弄得我應付不下。還有,你的三姐⋯⋯⋯」説到三娘的事,展雲欲言又止。紫湘問道:「三姐怎樣?」説話間,她看見桌上三娘未有帶去的一碗燕窩羹,便問:「這是什麼?」展雲道:「還不是三娘送來的嗎。」接着便將三娘對自己一切的事情説出來,更説起二娘三娘兩人吵鬧的經過。
紫湘聽了展雲的話,一面很不值三娘淫蕩的行徑,一方面也更仰慕展雲正直不苟的態度,説:「祇要自己做得正派,她不規矩是與你無涉的,你管她做甚麼!」
展雲道:「但是人言可畏,她這樣來騷擾我,給人誤會了怎辦!」紫湘説:「眞情不能委屈,你怕甚麼!」
」展雲説:「為避免這樣的麻煩,所以我想離開這裏。况且這家人你爭我奪,怎可以得長久的,我怕不久的將來,這家庭一定發生可怕的慘變,甚至會毁滅,破落了呢!」
紫湘見他越説越衝動,而且句句也是至理明言,説得自己心裏也非常難過了,祇得向他安慰道:
「雷先生,你是説得很對的,不過⋯⋯⋯⋯」
「不過甚麼?」展雲説。
「不過現在你是有顧慮的,一來我父親栽培你許久,他現在要你來幫忙他管家,很看很起你,你怎可以一旦離開他,不是給他説你忘恩負義嗎?」
「這是一點理由,還有呢?」
「還有一點,説出來似乎衝撞你了。」
「二小姐,我和你雖是上下有別,但得你看得起我,肯不分身份跟我常常接近,又何必客氣呢!」
「第二點你現在還要扶養你年老的母親。要是你一旦離開這裏,不見得立刻就可以找到一份適當的職業,有相當的收入。這樣,不是苦了你令堂嗎?所以都應該想清楚才好。」
紫湘説出這樣的話,第一件展雲倒無所謂,可是第二樁,却説正他心裏的隱衷,他現在棲遲在唐家,也不過是為了扶養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媽媽,其他都不是他要顧慮的。現在這隱衷給紫湘説起,怎使他不難過呢?當下嘆了一口大氣,垂頭不語。
紫湘心裏也對展雲十分好感,所以才好降格納交,固然不會希望展雲離去的。現在看見他垂頭嘆氣,情知他是意轉了,故意問道:
「雷先生,我的話你説怎樣?」
展雲點點頭道:「你説正我的心事了,我就是為了一個老母親,所以才肯忍耐着在這裏,要是我一個人,那愁沒有吃一口飯的地方!」紫湘説:「可不是嗎?所以我叫你千萬忍耐!」
以後,他們又談起些書本的事,紫湘有不明白的地方,展雲詳加解釋。展雲自小喪父,與父母相依為命,後來因為道德叫了他到家裏陪兩個兒子讀書,但是他兩個兒子都不愛唸書的,展雲却非常用功,雖然讀書不多
,惟是很愛研求學問,所以大有成就。紫湘常常向他執經問字,感情也漸漸濃厚了。
在他們研讀書本的時候,外邊起了一陣脚步聲,一個人施施然進來,紫湘展雲兩人囘頭一望,原來進來的人是唐老爺唐道德,紫湘站起來叫聲:「爸爸!」展雲也起來叫句:「老爺!」道德見紫湘一個人在賬房中和展雲對坐談話,大為不滿,説:
「紫湘,你在這裏做什麼!」
「沒有什麼,爸爸!」紫湘説:「來這裏向雷先生問字。」
展雲也道:「老爺,二小姐因為書本裏有些字不大明白,來這裏研究研究罷了。」
道德自己雖然是個作奸犯科,無所不為的壞人,也曾用過他來路不正當的錢去歡塲買笑,蹂躪女性。即使他現在兩房妾侍也是身世不清白的煙花女兒。但是,他對下人和子女們,却擺出了一副假道學的面孔。當下大不以為然地説:
「你們孤男寡女,同處一室,這成什麼話!」
紫湘聽見這樣的話,大為委屈,道:「爸爸!請你別誤會,我們是光明正大的,不過談些書本裏的事罷了。」展雲也分辯説:「老爺,我們除了書本上的事,別的絕對沒有談過。」道德扳起面孔説:「要到了有什麼事弄出來的時候,就遲了。」跟着,用命令的語調向紫湘説:「你聽住,以後沒有什麼事,不准你一個人到這裏來!」
紫湘正想解釋,又給道德截住了,説:
「不必多講!叫你不要來就不要來,去吧!」紫湘平日也知道自己的父親性子是十分固執的,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服來,祇有負氣鼓腮的出賑房去了。
展雲看見紫湘這般受屈,心裏也十分替她不平,就想對道德説明幾句,可是又給道德先開口截住了,説:
「事情我都明白,你要知道,我是明禮持家的人,不肯給人説半句閒話的,你們雖然是世兄妹,但到現在,名份有關,我不能再給你們隨便的。」
展雲心𥚃想着三娘,二娘,以至两個少爺的情形,暗𥚃説道德完全胡塗,應管的事不管,不應管的事却張
大其詞。難道三娘對下人胡塗的行徑,是一個以禮相守的家庭裏應有的事嗎?以這樣的環境,主持的人不公正,下邊的人亂得像團糟,那裏還有好結果?自己又怎再肯同着這一個魔鬼家庭去陪葬呢,雖然自己是有顧慮,但也不能顧得許多了,便直截向道德提出辭職,説:
「老爺,我想離開這𥚃,另外找別的工作做。」
道德聽見展雲説要辭職,以為是自己説他两句,就不高興了,所以要辭職,便用一種教訓的口吻,説:「你做得好好地,怎樣要辭職不幹?」
「沒有什麼,不過這份事我做不下去!」
「大概因為我説你两句你就賭氣不幹吧!」
「不是因為這樣,實在我這份工作很難幹的。」
「展雲!你本來是我世侄,你父親臨終時托我照顧你,我受了朋友的委托,叫了你來這裏唸書,到現在又用了你當我的管家,也不過是為了觀念你父親和我的感情,你有什麼困難,盡可以對我說,何必動不動就說辭職!」
唐道德這番假仁假義的説話,展雲是明白的,不過一向自己是吃他的飯,現在也是替他做工,又可以説甚麼呢?這樣,他低頭沉思了一囘。
道德看見展雲沉吟不語,説:「你有甚麼困難?對我説罷!」展雲想了一想,説:「就是支錢一件事,已經給我麻煩透了,老爺你不是規定過每個人支錢的數目嗎?」
「是的,」道德説:「我規定了每個人支錢的數目,不許多支一個錢的。」
「可是,」雷展雲説:「家𥚃那個人不透支了,可是每個也偏要再支,這個我很難做的。」
「這不成!」道德説:「以後誰要來多支了錢,你可以叫他去問我,不許亂支!」
其實這一點在展雲的心中,也不過是其次,三娘來嚕叨他還是一件最使他不滿意的事,可是這些關乎家規,名譽的事,又怎可以説得出呢?現在即然道德這樣説了,也不好再説其甚麼,祇得道:「假如這樣,那就沒有什麼了!」
歇一會,道德又問:「那天賀壽支出的數目,你算好了沒有?」展雲道:「都算好了。」道德説「:你拿出來給我看吧。」
展雲在抽屜裏拿出一本賑簿來,交給道德,道德接過看了一遍,皺着眉頭説:「為甚麼賞錢支得那麼多!」展雲説:「這樣的賞錢不算多吧,况且這是表示老爺對下人一點恩恤罷了。」道德搖搖頭說:「話不能這樣說的,總之打賞一點就算了。」
展雲平日也知道唐道德對下人是相當刻薄的,也無謂同他再說下去,只有說句:「對的,以後這筆節省一點就算了。」道德說:「對呀!」你要知道,管理一樁家務,一處節省一點,錢就可以剩下來了。」展雲聽了他的話,心裏暗笑,寧願在外邊亂花亂攪,送給那些不正當的女人的鑽戒呀,手釧呀就可以,對用人打賞多兩個錢,便心肝肉痛了,這眞叫「寧受老虎咬,不願給蚊釘」呢。
道德再往下看去,看到一樁數目上,又有點不滿意了,説:「為什麼多了二十桌酒菜?」
「老爺,這是用人吃的!」展雲説。
「這甚麼話,怎樣用人會跟客人吃同樣的菜?」
「老爺,」展雲説:「那天是老爺的好日子,就算給點好酒菜用人們吃,也不算什麼囘事吧。」
展雲這人,做事一生忠厚,上下不分彼此,也不會待薄下人一點,他認為,同是一樣的人,不過因為境遇不同,分出上下罷了,怎可以刻薄人家呢?况且,他自己也是個窮人出身,世界上只有痛苦的人才會同情痛苦的人;窮人才會眞正同情窮人的。
但道德的思想並不如此,他認為下人們一切的用度,絕不能跟自己一樣,窮,就要吃苦,沒有理由要恩恤他們的。所以聽見展雲的話,大不以為然,搖搖頭道:「你年輕,總不懂得慳儉的好處,這樣多開二十桌上好的菜,又多花多少錢呢,難道這樣顯淺的道理你也不懂嗎?下人何必要吃這樣好的菜!」
展雲見這樣吝惜的人,也是不可理諭的,只有唯唯否否的應了他。
道德把賑目一一看過了,其他也沒有甚麼,便把賑簿放在枱上,起來正想走出去,忽然心又想起一件事,囘頭道:「展雲,你知道我素年來最重禮教的,家裏男女有別,以後沒有什麼必要的事,你別要再跟二小姐多
在一起,給人説句閒話就不想了。」
展雲要想伸辯兩句,道德却掉頭而去,使展雲欲説無從,心𥚃又是一陣悶氣。
展雲今天接二連三的受了幾件不如意的事,看到幾件不順眼的情形,心𥚃納悶得很,他囘到裡邊來,頹然的坐在椅子上,用手托住前額想:這樣矛盾的一羣,看遲早也要趨於沒落、毁滅了。自己還年青,有前途,有理想,沒有理由跟他們陪葬!想起這些,他就下了一個决心,等到有相當準備和相當機會,就遠走高飛,再不在這個多事苦痛的地力來吃這口飯了。
(八)
晚上,道德要到裏邊三娘房裡去,經過走廊的時候,撞見了進福,他手上挽着一盞油燈,另一隻手也捧着一盞火油燈走過來,遇到道德的時候,站定叫聲:「老爺!」道德應過了一聲,望見他手上兩盞燈,便問:「這些燈拿到甚麼地方去的?」進福説:「這盞小的是路燈,這盞大的是工人房用的燈!」
道德性子最吝惜的,聽了不高興,説:「路燈何必要這樣亮,工人房裏根本上可以不需要燈火,白天做了一天,晚上還不休息嗎?我現在規定,每天晚上到八點鐘以後,工人房裡不許再點燈!」
「老爺,」進福説:「現在晚上八點鐘還未天黑呢!」
「我不管黑不黑,總之,八點鐘以後就不准點燈!」道德説。
進福那𥚃敢違抝道德的意思,便應了幾聲:「是,是!」道德説:「去吧。」説完,繼續前去了。
道德沿着走廊走去,走過二小姐紫湘房門外邊,隔窗望見裏邊還有燈光,就站住了脚步,往裏一望,見紫湘在裏邊看書呢,紫湘也已經看見了道德,站起來叫聲:「爸爸!」道德走進房裡去,説:「你在這裡做什麼,還不熄燈睡覺!」
「還早呢,在這裏看看書!」紫湘説。
「書有什麼好看!」道德説:「晚上看書,浪費燈光,為什麼不白天看。」
他説着,順手拿起書一看,見是一本「西廂記」,當堂露出不滿意的顏色,説:
「為什麼你竟然看起這些書本來!」
「爸,這些書本不好嗎,是我們中國有名的文藝書籍,怎樣不好呢?」
「這本書簡直是導人以淫,教人以蕩,怎可以説得這樣好!」
紫湘鼓起小腮,説:「爸,你眞是⋯⋯⋯⋯」
道德截斷她的話頭,説:「別多説了,我家是以以禮相守,非禮相守,非禮勿言,非禮勿視,我不准你再看這樣的書,知道嗎!」
紫湘見她的父親動氣了,當然不敢再多説話,祇得説:「是的,爸爸!」
道德還重覆地説:「你看這樣的書,不但一點益處也沒有,而且夜裏看書,花耗燈油,浪費精神,有甚麼好看!快去睡罷!」道德素來對子女們和下人説話是莊重萬分的,扳起假道學的臉孔,紫湘也不敢不答應,説:「是的,爸爸!」道德説完了紫湘幾句後,才轉身去了。
在唐家裏,雖然道德是開口「以禮相守」,閉口又「以禮相守」,可是背了道德,却做出不少最沒規矩的事來。正在道德以大篇道理教訓女兒的時候,在三娘房中,三娘却留着那個冒牌家人進祿在姿意調笑哩。
在幽幽暗暗的燈光下,三娘伸起她蛇一般的腰肢,斜倚在床上,進祿却坐在床前替她槌骨。
「你做夢嗎?槌得這樣輕!」三娘瞇起眼睛,伸一下腰肢説。
「哦,哦,要用力嗎?可以,可以!」進祿發力在她大腿上一搥,痛得三娘「哎喲」一聲叫起來。
「你想槌死我嗎?是不是!」三娘嬌嗔地駡着起身來,走下床去,説:「我不要你搥了,你這沒有良心的傢伙!」
進祿涎皮賴臉的走過去,兩手傍住三娘的香肩,説:「三娘,我一向沒有離開過你,即使現在做奴做僕也要服侍三娘,怎可以説沒良心吶!」
「好了,好了,別獻假殷勤吧,時候不早了你也應該出去,等囘老頭子到來可不是玩的。」三娘囘頭説。
進祿陪着笑臉説:「你叫我走,我怎敢不走,不過⋯⋯⋯」説着伸開手掌。
三娘知道他又是要錢,斜視了他一眼,説:「又要錢嗎?我看多少錢才够你要,我的錢差不多都貼盡給你
了。」
「別駡了,別駡了,錢是老頭子的,多用兩個有什麼關係,這幾天來確是手緊得很。」進祿笑着説:「三娘,做做好心吧,我不敢囉囌你。」
「得了,得了,別討厭了!」三娘在抽屜裏拿個錢袋出來,抽出一點錢,向他手裏一塞,説:「拿去吧,快走,老傢伙就要囘來了!」
進祿將錢一數,見只得二十塊,心裏嫌太少,便伸出五個指頭,表示要五十塊,説:「三娘,這樣好罷?」三娘生怕道德撞進來,生出麻煩。扭他不過,又在錢袋裏拿三十塊錢出來,説:「走吧,走吧,再是這樣麻煩我,我不見你了!」進祿接過錢,心滿意足了,他三娘笑一笑,聳一下肩膊,探頭探腦的走去了。
果然在進祿去了不久,唐道德老頭子就囘來,一見了三娘,整個莊嚴面孔拋到九霄雲外,裂開嘴吧笑着走過來,一手搭住三娘肩膊,説:「還未休息嗎?」三娘斜視了一眼,説:「等你囘來呢,你不囘來我怎敢睡!」兩句話說得唐道德骨節都酥了,笑吟吟的説:「眞的嗎?」接着是一串粗俗的笑聲。三娘更是媚態畢露地説:「難道你不相信嗎?」道德連忙説:「相信!你的話我怎樣不相信!」
其實三娘看見他飄飄白鬚,心裏就厭惡到不得了。
歇一囘,三娘説:「我想叫你做一件事,可以嗎?」
「什麼事呢?三太吩咐的事我敢不做嗎!自從你跟我囘來以後,我怎會逆過你的意!」
「眞的嗎?」
「當然眞的,」道德説:「你究竟要我做甚麼事?説吧!」
三娘似乎略些沉吟一下,説:「我想買一個鑽戒!」
「鑽戒?」
「是的,要你花錢了,不高興嗎?」三娘似乎有點生氣了。
「怎會不高興!」道德説:「不過你不是有鑽戒嗎?何必要買!」
「哼!」三娘冷笑一聲,説:「我早知道你不高興給我買了,算了,算了吧,別買了!」説着,她故意把
身偏過去,裝得很生氣的樣子。結果還是道德答應了:「你何必生氣,需要就買,一個鑽戒算得什麼!」
勝利又是屬於三娘了。
(九)
二娘因為今天自己的兒子——三少爺智全受了大少爺智能欺負,心裏氣得很,一晚思前想後,覺得家裡有了智能在,他們母子倆便沒有出頭的日子。照習慣,一家除了老頭子,當然是大兒子的權威最大。現在唐老頭子的年紀已經不少了,假若萬一他撒手人世,那末自己母子兩人,也就要受智能的欺凌,甚至有立足無地的危險。今天智能説出的話:我爸爸死了以後,家裡什麼都是我的!假使將來有這樣的一天,那怎樣好呢?這點使心地狹窄的二娘够寒心的。
今天顯明地是大少爺智能欺負了自己,説話簡直看自己不在眼內,現在尚且如此,假如將來老頭子有三長兩短,那怎樣好呢?二娘越想越覺得前途可怕,一時沒有方法可以打破這種苦悶。
到了第二天,二娘還是鬱鬱不歡,雙眉不展。智全的褓姆跟二娘多年,這人又愛搬弄是非,如今看見二娘愁默默的樣子,便向二娘問:「二娘,你為什麼這樣不高興?」二娘嘆一口大氣説:「你怎知道我的心事!」阿四説:「二娘,我跟你多年,你一切的事我也看作自己事情一樣,我怎會不知道,你還不是為了三少爺給大少爺欺侮的事嗎?」二娘給他道破了心事,微喟一聲,説:「就是為了這事,你想,那智能對我們這樣,你説怎辦!」阿四説:「説起他呀,哼!我也看不過眼,他口口聲聲説將來老爺死了,這家裡什麼都是他一個獨有呢。」二娘説:「他眞是這樣説嗎?」阿四説:「還有假的嗎?我看萬一老爺百年歸老,你們母子倆就不堪設想呢!」二娘給她説得更難過,長嘆一聲,説:「我整天憂心,還不是為了這樣。老爺總是有一天離開我們的,那時我們母子倆怎樣過下去!」説着,她眼眶都紅了。
二娘和亞四正在説話間,三少爺智全又哭哭啼啼的走進來,二娘連忙把他拖過來,千哄百問的,説:「你又哭什麼?」智全説:「大哥又打我!」二娘聽見智能又將她的兒子糟撻,更心肝肉痛,問道:「他發瘋嗎?為什麼又將你打?」智全邊哭邊訴苦道:「我看看他着的雀,他就打我了。」二娘生氣道:「難道一頭雀比一
個人要緊嗎?就算看看他的雀,也犯不着捱打呀!」智全道:「他不但打我,還駡了我不少的話呢!」二娘説:「他怎樣罵?」智全説:「他説我不是爸爸的兒子,將來非要把我們趕走不可!」二娘聽見這樣説,氣得全身發抖,一手拖住智全道:「你同我來,我要告訴你爸爸去,看他兇得這樣子!」説着,便同智全到大廳去見道德。
那時道德正為了一件不如意的事在煩惱——因為他有一幫毒品運到外地去,給一個同伴貪錢出賣了他,損失了一大筆錢。為了這事,道德的火氣相當大。二娘怎知丈夫心情不如好,拖住智全出來,氣憤憤的走近向道德訴苦説:
「老爺,你也應該把亞能那傢伙管束一下!」
「又有什麼事!總是攪到家無寧日。」道德沒好氣的說。
二娘就把智能搶錢,智全被打的事都説出來,道德那時正心情不好,那有心聽這些閒事,反而教訓二娘幾句,道:
「到底都是你們女人多事,將一家人分開彼此,終日吵鬧,你們走,我不理這些閒事,做弟弟當然要聽哥哥的話,吃點虧算得什麼事。」
二娘以為出來對道德訴苦,不過是想道德主持公道,責罰智能一下,怎知剛碰上道德心情苦悶,有不如意的事發生,反給道德責備一番,有冤無處訴,只得直流眼淚,囘到房間去。
一會,大少爺唐智能從外邊囘來,見到道德在廳上,他平日最怕見他父親聽教訓的,現在遇個正着,想偷偷走過,免得父親囉囌,本來道德也沒有見他囘來的,但智能走到橫門的時候,却給老人家進福見到,大聲的招呼一聲:「大少爺!囘來了嗎?」智能想截止他也來不及,却驚覺了道德,他抬頭一望,見智能鬼鬼祟祟的想溜進去,一聲叫住:「亞能!」智能不敢不應,只得站住脚步,叫聲:「爸爸!」心𥚃暗罵進福這老頭子多事!
「你過來!」道德用命令式的語氣喊。
智能受了催眠似的走過去,到道德跟前,問:「爸爸,有什麼事?」道德以非常莊嚴的口吻問:「你到那
裡來?」智能本是賭錢囘來,現在父親問到,只得扯個大謊,説:
「沒,沒,沒有到那裏,找個朋友談談罷了。」
道德哼一聲,説:「你別扯謊,終日在外邊胡混,你該小心你的前途!我問你,你昨天搶了亞全的錢,是嗎?」
智能給父親問起這事,心裏嚇得一跳,但只得強嘴説:
「爸爸,你別寃枉我,我沒有做過這樣不規矩的事!」
「胡説!」道德罵道:「這是你二姐告訴我的,難道她揑造出來冤枉你嗎?」
「你別聽二姐胡説,我那有幹過這樣的事!」智能矢口不肯承認。
道德冒起火來,厲聲道:「我告訴你,今後我再知道你有欺負家裡的人,仔細你的皮!滾去!」
智能還怎敢説什麼話,應着「是,是!」兩聲,連忙走去了。
二娘剛才要找道德訴苦,怎知却給道德搶白幾句,喪氣囘房,阿四要想討好她的主婦,走過來問:「二娘,你對老爺説過,他怎樣?」二娘道:「他現在瘋了,一點不理我們,還說做弟弟的應該吃虧,他道氣不氣人!」阿四乘機道:「二娘,這怎樣得了,再這樣下去,哼!恐怕你母子倆連站的位置也沒有呢!」二娘是個頭腦簡單,心地狹窄的女人,即然吃了虧,又沒地方出氣,心𥚃恨透了,便向阿四問道:「你有什麼辦法,教我出了這口氣!」阿四只顧討好主婦,不知利害,想了一想説道:「我相信要是你的仇人——大少爺一天不除,你們兩母子一天沒得好過,將來老爺有什麼不測,那時你們更苦透了呢,我看不如早作打算。」二娘聽説又似是道理,便問:「應該怎樣打算?」阿四道:「辦法是有,不知你肯幹不肯!」二娘説:「只要能把我的眼中釘拔去,使我們母子好過點,什麼我都肯幹!」阿四便在二娘耳邊説了幾句話,又問道:「這樣你以為如何?」二娘沉思了一會,阿四再説:「怎樣?你不敢嗎?」二娘有點懼怕地説:「我⋯⋯不敢這樣做!」阿四説:「這是由你决定了,不過你不算他,恐防他將來算你呢!這不過完全為你着想!」二娘説:「你出去吧,我心亂得很,不想多説話了。」阿四臨走還説:「二娘!你該想一想,到你沒有地方立足的時候就遲了,而且偌大一副家產一定會給他佔盡呢!你聽他説話的口吻好了。」説完,還冷笑一聲,就出去了。
二娘一個人在房裡想出許多事,想到將來沒地方立足,母子倆都給智能趕出去,偌大的家產會給他佔盡了,這樣一切一切,都不是一個量淺的婦人所能容忍的。况且平日二娘對於這富厚的家產,也有獨佔之心,三娘是沒有孩子,不足懼憚的,只有大少爺智能,無疑地是她當前大敵,現在兒子接二連三的給他欺負,老頭子在生,尚且如此,將來又何以堪呢?或者會如阿四説話:到將來沒地方立足就遲了!這樣想想,那樣想想,想到心裡亂紛紛。
到夜裏,道德見昨晚已經留在三娘那邊,今夜也應該囘到二娘這邊來了,怎知來到房門外邊,見雙門緊閉,道德敲門叫道:「開門!」二娘在裡邊聽見是道德的聲音,想起今天道德沒幫她,不肯開門,生氣道:「你到別處好了,你既然瞧我們母子倆不起,進來幹什麼!」道德知道二娘是量窄的,説道:「開門吧,誰會瞧你不起,誰都是兒子,誰都一樣!」可是無論道德怎樣説,二娘發脾氣一定不開,弄得道德一點辦法都沒有,搖頭嘆氣道:「眞是妻多夫賤!」便也再不叫門,直到三娘那邊去了。
(十)
三娘因為昨天晚上道德到過,以為今晚他一定不會到的,一時高興,便預備好些酒菜,偷偷地約了進祿到房裏來,大吃大喝一頓。
進祿喝得有幾分酒意了,舉起杯子對三娘説道:「來,我們喝個乾杯,祝我們白頭偕老!」三娘也舉起杯子,媚笑道:「等我們早點得到老頭子的家產!」兩人笑哈哈的飲個乾杯。
進祿喝了一杯,想起了一件事,説:「三娘,你叫我進來吃酒,不怕老頭子嗎?」三娘説:「我怕什麼,他今晚不會來的。」進祿説:「你怎樣知道?」三娘説:「怎會不知道呢,他自己規定的,單日在我這裡,雙日到那邊去,今天是雙日,怎會來,你怕什麼,我叫你來,當然是妥當啦!」聽得進祿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那麼值得再多飲一杯了!」
怎知杯子舉起,酒未沾唇,外邊却有人拍門。三娘止住進祿,叫他不要出聲,自己向外邊問道:「是誰
「開門,是我!」三娘認得這是道德的聲音,大吃一驚,進祿更驚得臉上也發青了,窗子離地又高,跳下去非死即傷,又沒有其他地方可逃的,兩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外邊又叫了兩聲開門了。
終於還是由三娘想出了一個辦法,打開了衣櫉,叫進被躲進去,然後再把桌上一雙碗筷收起來,慢條斯理的走去開門。道德進來説:「為什麼這樣久還不開門?」三娘故意説:「我跟一個男人在吃酒,怎能够立刻開門給你進來!」進祿在衣櫥裡聽見三娘説出這樣的話,嚇得渾身冷汗。道德心想要是她同男人吃酒,怎會直説,而且桌上又怎會只得一雙碗筷?當然這是開玩笑的話,也故意道:「你應該留住他,等我進來陪他吃杯酒呀!」三娘媚媚眼一飄,説:「誰要你陪!」道德笑着説;「別開玩笑了,我也有點餓,等我來吃點東西吧!」三娘把他的筷子按着,説:「你昨晚答應同我做事怎樣?」道德説:「你叫我做什麼事?」三娘道:「忘記了嗎?戒指呢!」道德笑道:「哦!我以為你説什麼,原來這些小事,三太叫我做事也會忘記的嗎?」説着,在身上掏出一個錦盒出來,交給三娘,説:「你拿去看好了。」三娘接過,打開來看,果然是個光亮耀目的鑽戒,戴在手裏,欣賞一囘。但另一方面在她心𥚃是記着躲在衣櫉裡的進祿,要是道德不走,他便很難脱身了。於是向道德説:「為什麼你還不走?」道德説:「怎樣你會叫我走?」三娘説:「你怎樣可以不走,今天是雙日,你不怕你的二太怪你嗎?」道德呵呵大笑道:「我就不怕這個,喜歡到那裏就到那裏,她怎可以管得着我!」三娘暗吃一驚説;「你眞的要留在這𥚃嗎?」道德説:「當然!」
三娘為了要使進祿能够脱身,低頭想出一個辦法來,對唐道德説:「你一定要留在這裏,我要看你的運氣!」道德覺得奇怪道:「怎樣運氣?」三娘拿出一方手帕來,説:「我綁住你的眼睛!」道德連忙道:「好,好,隨便你好了。等我把長衫脱了再玩罷!」説着,脱了長衫,要往衣櫉裏放,嚇得三娘冒出冷汗,忙過去把長衫接在手裏,笑道:等我替你放!」道德那𥚃知道其中另有秘密,還以為三娘對自己熨貼,便把衣服交了給她,由三娘掛起,這個難關總算輕輕渡過了,可是衣櫥裡的進祿,却驚到發抖。
長衫掛好了以後,三娘拿起手怕道要綁道德的眼睛,道德苦着臉央求道:「算了吧,別攪這個玩意的好嗎?」三娘嬌嗔道:「討厭!一點趣味也不領畧,根本不懂閨房裏的樂趣!」道德怕她生氣,蹲下來任她綁,說:「好吧,好吧,卽然有「樂趣」,那末任得你綁!」三娘光把一個銀角子放在一個茶盅裡,然後再把道德的眼睛綁起來,拍手大笑道:「你摸呀!」
可笑這個白鬚滿嘴的老頭子,還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被三娘綁住眼睛,在房裏亂摸,三娘見時機不可失,連忙把衣櫥的門打開,放了進祿出來,用手勢叫他快走,進祿那裏還敢怠慢,慌忙躡手躡脚打開房門,拔步就跑。道德還以為三娘一意想出開玩笑的新花樣,那裏知道三娘設局騙他,一直是在摸那個有銀角子的茶盅,三娘在旁邊笑得花枝亂顫。
進祿溜出了三娘房間去的時候,遠遠地看見走廊盡頭燈光一閃,一個人走過來,進祿作賊心虛,大吃一驚,囘頭就跑。
原來這個人就是老家人進福,他每夜都循例到屋內各處巡視一切燈火門窗,才去睡覺。他正在巡視到這裡的時候,一瞥間在黑暗裏看見一個人的影子閃縮跑去,連忙十聲喝住:「誰!你是誰!」可是這個人並沒有停步,一直走去了。進福上前去一看,那裡還會有人,進福急着大叫:「賊呀!有賊呀!」
屋內的人聽見有賊,都走出來圍住進福問:「你看見甚麼賊?賊在那裏?」
進福說:「我明明見了一個人在這裏閃過,跑來看的時候又不見了。」
那時道德正在房裏綁住眼睛玩得個快活,突然聽到外邊叫喊有賊,狼狠地把手帕扯下,同三娘兩个人跑出來看。
三娘聽見外邊叫喊有賊人,暗裏大吃一驚,心裏想:難道進祿在外邊碰上了人?連忙隨着道德到外邊看,看見進福在那裡口講指劃,說自己見賊,進祿也雜在人堆裡,才知道事情並未有洩露,心裏安樂了不少。
道德走過去問:「進福,你見了什麼賊人?」進福說:「我分明見一個人在這裡閃過,把他叫也叫不住,,一忽兒就不見了。」
雷管家問道:「那個人的樣子身裁怎樣?」這一問,進祿揑着一把汗,假如進福說出來,可不是玩的事!好在
進福在黑暗中沒有見清楚,説:「那我就沒法看清了,地方又黑,那人走得又快,怎會看到!」進祿聽見,心裏放下一塊大石,説:「進福!我怕你眼花看錯了呢,這個時間,那裏會有人走過!」三娘心裏明白,也故意説:「對呀,我怕是進福眼花見鬼呢!」道德説:「三更半夜,別大驚小怪,嚇煞人啦!」進福不能不説:「是是,是是!」的應着。
雷管家心𥚃也知道裡邊會有古怪,可是不便多説話,只得對進福説:「福伯!以後巡夜,帶盞比較亮一點的燈火。」進福也應着:「是的!」紫湘小姐説:「福伯,其實見不清楚的事,別亂嚷喊。」道德把手揮了一揮,説:「你們都去睡罷!」説完,他自己X同三娘囘房去了。
道德和三娘去了,進祿得意地笑着對進福説:「年紀老了,沒用吶,看到自己的影子當人呢!」説完,也下樓去了。
這𥚃只剩下進福,展雲和紫湘三個人,其餘的人都去了,進福心裏想:自己明白是見到閃過一個人的,怎會是眼花,對展雲説:
「雷先生:説我眼花才是冤枉呢,我明明見一個人在這裏閃過的,這人還像進碌呢,不過剛才很難説出!」
紫湘説:「在那𥚃跑出來呢?」進福低聲説:「像是在三娘的房間𥚃溜出來的呢!」雷展雲心𥚃完全明白,説:「事情有許多很奇怪的,自己做自己的工夫,其他別管,去吧,去睡吧!」
進福心𥚃也不見得不明白,搖頭嘆息,也走去睡了。
「雷先生!」紫湘説:「事情也够奇怪了,怎樣居然在三更半夜,有人在三姐房裏溜出來,而且爸爸也在她房裏呢。」
展雲微喟一聲,説:「古語説得好: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一個家庭也何嘗不是一樣,怪誕的事出現多了,內部紛爭大了,恐怕就是敗亡的象徵了吧!」紫湘聽見,心裏非常難過,展雲向她安慰道:
「二小姐,你不必為這些事難過,總之自己站住立場,不被環境左右了意志,一定可得到一個好結果的。好了,現在也不早,去睡吧!」紫湘望住展雲,長嘆一聲,欲語無言,一會,幽幽地説:「是的!你説得很有道理,好吧,明天再見,你也應該休息了!」一説着,苦笑一下,轉身去了。雷展雲看着紫湘的背影,心裏不
勝惆悵,暗想道:這樣一個純潔的女孩子,却生長在這樣一個黑暗混純的環境裏,焉得不痛苦呢?可是,自己又不是有同樣的情形嗎?一個有希望,有理想的人,竟屈身在這樣的地方,什麼時候才能够脱離這樣痛苦的束縛?一邊想着,慢慢地走下樓梯去,這時在他腦後,三娘房間燈光掩映,透過玻璃窗門,發出更使展雲憎惡的笑聲——一老一少的聲音,顯然多麽不調和,多麼剌耳,展雲惡心的自言自語,説一句:「哼!鬼,鬼叫!」
(十一)
三少爺的母親——二娘,因為自己的兒子一而再次的受大少爺智能欺負,二娘是個量狹的女人,怎可以看得順眼,同時在智全的褓姆阿四的挑撥下,聯想到將來自己的處境,很容易給智能逼到無立足之地。她想着一串足使她寒心的事情,心亂如麻,連她日常最愛做的工作——唸佛,也無心去做了,剛拈起佛珠,唸不到一籌「觀音經」,就嘆一口大氣,把佛珠放下,沒精打彩的走開。
阿四在旁邊看見這樣,心裏明白她是為了什麼事,笑着走到二娘的身邊説:
「二娘!你又為了大少爺的事煩惱嗎?」
「還不是為了這件事!」二娘嘆了一口氣説。
阿四説:「二娘,我勸你聽我的説話,不然將來後悔就遲了,我跟你多年,也不想你有過不去的一天結我看!」
二娘越想阿四的話,似覺越有理由。阿四見二娘沉吟不語,説:
「二娘,你得想想,難道這樣大一副家產,將來眼睜的給那傢伙獨佔嗎?他現在也這樣對你,將來他一旦大權在握了,你們的苦處就多了,先下手為強,怎可以輸了眼前虧!」説話間,三少爺智全又在外邊進來了,二人見他前天給智能打一巴掌五個指痕還在臉上,一時勾起新仇舊恨,狠狠地下了一個决心説:「好,有你沒有我,有我沒有你!」阿四説:「對呀!這才是聰明呢!」智全問道:「媽,你們説什麼?」二娘説:「小孩子別管大人的事,我給你點錢,你出去玩吧!」説着,在口袋裏抓了一把錢給智全,智全接了錢後,高高興
二娘轉身在抽屜裏拿了一瓶「毒鼠藥」出來,两眼發亮的説:「好!我看你欺負得我好久!」
正在這時候,外邊傳來一陣脚步聲,二娘連忙把那一瓶「毒鼠藥」收在後面,一看,原來是小丫頭翠桃捧住一盤點心進來,説:「二娘,吃點心呢。」阿四説:「擺下呀,叫什麼!」翠桃依着阿四的説話把盤子裏一碗點心放下來了,另外一碗還是要拿去,二娘問:「這碗拿去給誰的!」翠桃説:「是大少爺的,他説要吃燕窩羮。,二娘聽説是智能吃的燕窩羹,心裏一動,阿四也向她打個眼色。翠桃正要捧住盆子出房門的時候,二娘把她叫住:「翠桃!你囘來!」翠桃站定了脚步,囘頭説:「二娘,有什麼事?」二娘説:「你⋯⋯你替我到廚房拿點鹽來。」翠桃説:「我把燕窩羹送去再拿來好嗎?」二娘發氣道,「什麼!我叫你拿東西也推三推四嗎?」阿四也會意了,説:「翠桃!二娘叫你去就去呀,你推什麼!」翠桃那敢違背二娘的意思,連忙把手裏的盆子放在枱上,轉身到廚房取鹽去。
二娘見翠桃去了,全身血管都沸騰得要爆裂一樣,心兒別別跳動,拿住「毒鼠藥」的手都抖起來了,呼吸頓時急促,心裏一陣陣雜亂的思潮湧起,又是發狠,又是害怕。阿四見大好機會,還是停手不動,喊道:
「二娘!」
二娘發愕了,沒有答應。
「二娘!你怎樣!」阿四又叫了一聲。
二娘雙眼發出可怖的光,一句話不能説,阿四索性推了她一下,二娘像從夢裏醒覺過來一樣:「呀,呀⋯⋯⋯⋯⋯」
「二娘,你再不能失去這機會呢!」阿四説。
「好!有他沒有我,有我沒有他!」二娘兩個眼睛露出可怕的兇光,震巍巍的拿出那瓶「毒鼠藥」來,往燕窩羹』裏就倒。阿四匆匆地拿起匙羹來攪拌一下。那些藥粉是白的,沒有一點痕跡。二娘做出這虧心事後,精神剌激得幾乎站立不住,頹然地坐在椅子上,心跳得像要奪腔而出。
阿四在旁邊給她鎮定的安慰,説:
「二娘,你別害怕,這件事做成功,包管你整副家產都落在手上,以後三少爺也不怕給人欺負啦!」
「是,是的⋯⋯⋯」二娘茫然地説。
「不過——」
「不過什麼?」二娘作賊心虛地説。
「你成功了以後別忘記了我呢!」阿四貪婪地説。
「哦,哦,是,是的。」二人恍惚地説。
這時翠桃已經取鹽囘來了,對于她們兩人的陰謀,一點也沒有發覺。把鹽放下,便把那碗有毒的燕窩羹端去了。
當翠桃要出房門的時候,一陣後悔的心情又在二娘心裏發出來,她眞想把翠桃喊住,但給阿四用一種壓制的眼光止住她,沒有喊出來,只得以驚恐的心情,望住翠桃去了。
翠桃捧着那碗燕窩羹,離開二娘的房間,直到大少爺唐智能的書房裏,智能這時正在喂雀呢,他見了翠桃進來,説:
「燕窩羹拿來了嗎?」
翠桃説:「已經拿來了。」説着把盤子放下,便想走出去。智能走過來笑吟吟一把拉住翠桃的手,説:「來,我請你吃點!」翠桃掙開了他的手,説:「我不吃,我不吃!」智能硬要拉住她的手説:「吃點有什麼關係呢?我請你吃的。」翠桃着急道:「給人撞進來有什麼好看呢!」智能説:「在這裏有誰看見!」
他們兩人正在拉拉扯扯,進福帶住一個人進來,智能看見了,連忙放開拉住翠桃的手,翠桃也羞得滿面通紅,一溜烟似的跑去。
(十二)
智能一見這個人,原來是趙師爺,他一進來,就露出一副黃牙笑着説:「大少爺,沒有出去嗎?」智能讓趙師爺坐下,説:「沒有呢,有甚麼事嗎?」説着叫進福倒茶,進福便倒了兩杯茶過來,趙師爺呷了一口,説:「沒有什麼,不過賈大少爺今天請你去玩,有空嗎?」智能笑道:「有空,就算沒空也去的,」趙師爺哈哈大
笑,道:「少爺你可謂逢請必到,逢到必早!」智能對進福説:「沒有事你可以出去了。」進福應着,去了。
智能問道:「今天又到什麼地方玩去?」趙師爺説:「還不是老地方,醉月樓!」智能説:「好極,好極,等我吃了這碗東西再去好嗎?」趙師爺説:「何必吃呢,到那邊你怕沒東西吃嗎?」智能説:「何必這樣急呢!」趙師爺説:「賈大少爺在那邊等你,雀局,三缺一,你知道賈大少爺是個心急的人,別叫他等得焦急了。」智能説:「好罷,那末我就馬上去。」于是穿好了外衣,匆匆地和趙師爺出門去了。
两人一直到了醉月樓,鴇兒迎出來笑着道:「大少爺這麼久都不來呢,把我們幾個姑娘都望得要死了!」趙師爺説:「你知道,大少爺貴人事忙,怎會常常到這裏玩!」智能道:「那裏,那裏,才三天沒有來罷了。賈大少爺在上邊嗎?」鴇兒道:「在上邊等你好久呢,快點上去吧。」智能和趙師爺兩人聽見,連忙上去,果然見賈世豪和另外兩個熟朋友在這裏,世豪正摟住一個妓女在調笑,智能一見就認得這個妓女叫做月魂,便大聲叫道:「噢!你們兩個多親熱呀!」世豪笑着起來,説:「要我們等得久了,來,玩八圈再説。」於是賈世豪,唐智能,合着兩個朋友坐下,搓起麻將來了,趙師爺另外在一邊,拉住一個妓女談心,各適其適。
唐智能給趙師爺拉去了以後,那碗有毒的燕窩羹智能沒有吃到,也算他一塲做化。這時那碗東西仍然放在枱上,翠桃見各人都去了,以為智能已經吃完,想進來收碗,却見那碗原封不動放在枱上,翠桃心裏説;「咦大少爺還未吃呢。」又想想放着東西沒人吃,太可惜呀,何不等我把它吃了!
翠桃正想端起碗來吃,忽然窗外有人大聲喊道:「你這小丫頭,偷東西吃呢!」嚇得翠桃連忙把碗放下來,一看,原來叫喊的人就是三少爺智全呢。智全走進來,説:「咦,是誰的東西,放着沒人吃?」翠桃説:「是大少爺吩咐要的燕窩羹,剛有朋友來叫他去了,所以沒有吃。」智全道:「我剛有點餓,他不吃,我們兩個來吃!」翠桃説:「我不吃,等囘大少爺囘來要罵我呢!」智全道:「這有什麼關係,他要是罵你,你説我吃好了,來,一人一匙,把它吃了,我來喂你!」説着要拉住翠桃,可是翠桃靈活得像隻狡兔,避過智全,劃着耳朶,説:「羞不羞,誰跟你一塊兒吃東西!」説完,裝個鬼臉,蹦蹦跳跳的跑去了。
智能望着翠桃的背影,很孩子氣的説:「好,你不吃我吃,誰要你吃!」説着轉身捧起那碗燕窩羹,伸直
𩓐子就狼吞虎嚥地喝下去,一會兒,整碗燕窩羹都吃下肚裏去了。吃完,他還䑛嘴唇説:「煮得不錯,不過有點澀味,大概是翠桃這小丫頭把燕窩挑不清!」
翠桃避過了智全囉唆,跳了出來,心裏想想你説我偷東西吃,你自己想吃才眞,好,我要去看看你!想着,便又轉囘到書房去。
翠桃走到書房,從窗間探頭往裏邊一望,不看尤可,一看大吃一驚,原來智全滾在地上,捧着肚子!「哎喲!哎喲!」的叫痛。翠桃看見了,這一驚非同少可,連忙跑到裏邊,推着智全問道:「三少爺!三少爺!你為怎麼樣!」「哎喲!哎喲!」智全痛得臉青唇白,指住自己的口,又指指枱面的碗子,意思説!我吃了那東西!
翠桃嚇得手足無措,連忙飛似的走到二娘的房間去。
二娘做過剛才那件喪盡良心下毒的事後,覺得心神不安,在房裏踱來踱去,好像等候着一件將要公開的事宣佈一樣,忐忑不安。阿四看見她的女主人這樣,也不免有點一寒心,差些兒口唇皮也咬破了。
這時翠桃連爬帶跑的奔進房裡來,口裡嚷着道:「二娘,二娘,不好了,不好了,大⋯⋯⋯大少爺⋯⋯」
「吓!什麼?大少爺死了嗎?」二娘心裏有事自己知。
「不,不⋯⋯⋯」翠桃急得説不出來。
「你⋯⋯你説呀,説呀!」二娘焦急萬分地説。
「在大少爺書房裏,二少爺肚子痛得要命,在地上亂滾呢!」
「吓!」二娘和阿四觸電似的大吃一驚:「他有吃什麼嗎?二娘急着這樣問。
「沒⋯⋯⋯沒有⋯⋯哦,是呀,大少爺的燕窩羹⋯⋯⋯他,他⋯⋯⋯沒有吃,出去了⋯⋯⋯⋯就⋯⋯放在枱上,三少爺走進去吃了,不知怎樣的,吃了以後肚子痛到不得了。翠桃氣喘喘的説。
二娘和阿四聽見這話,眞是晴天霹靂,尤其是二娘,覺得眼前冒出火星來,咬住牙齦,搶前去一個耳光就打在翠桃的臉頰上。
其實當時二娘聽見自己的兒子竟吃了那碗有毒的燕羹,也等于由自己的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子一樣,心裏怎得不惶急,只有拿着翠桃來出氣。
翠桃莫明其妙的給二娘打了一個耳光,也不敢辯白,只有撫摸被打的地方,眼睙直流。阿四推了一下二娘的手肘,説:「二娘,你還是到書房裏看看三少爺吧」
二娘點點頭説:「好的,好的,現在就去,我心裏一點主意都沒有了,不知怎樣好。」阿四説:「去看過再説罷。」
二娘和阿四,翠桃三人到了書房去,唐道德,紫湘,雷展雲,三娘,跟其他的家人們都在裏面了,二娘搶進去,撥開各人,抱住智全,看見他只剩一點微弱的氣息,口角也噴出鮮血來,二娘叫了幾聲,智全也不會答應,可過一會,智全臉上起着一陣痙攣,全身抽搐一下,氣絕死了。唐道德要叫醫生來看,也來不及了。
「這是甚麼囘事!他吃了什麼?」道德焦急地説。
當時誰敢説一聲。二娘更因自食果報,也為了一念之差,內心痛苦與後悔絞扭着。乘着亂哄哄的當兒,她懷着這份悲苦愴痛的心情,獨自一個人走出了書房,搖搖幌幌囘到自己的房裏去,想着自己做了錯事,不過是因為一念之私,心腸狹窄,不能容物,要想害死智能,誰料天網恢恢,竟自吃苦果,到如今兒子死在自己的手上了,這件事一定會洩漏出去,到那時還怎可以立足在這個家庭裡,况且,自己只有這個兒子,現在也慘死了,自己還可以希望什麼?思前想後,路路不通!最後只想出了一個字——死!不如走上這條悲慘的路,結束了可怕的將來,可怕的一切。
她在無可如何,無可希望,無足留戀,更是不可留戀當中,覺得沒有面目再見道德和其他的家人了,咬着牙齦,把脚一頓,霍然轉身在抽屜裏拿出剛才用過半瓶的「毒鼠藥」出來,倒在杯子裹,用冷茶和勻,仰頭一飲而盡。移時,一陣難以抵禦的痛楚,倒在地上亂輾。
這時候在書房裏,道德正要追究智全的死因,問遍了都沒人知道,各人只是搖搖頭,阿四心𥚃駭怕,瑟縮地望了一望,以為可以見二娘做個主意,怎知望遍了,都不見二娘的踪影,心裡不期然覺得一陣恐怖的情緒浮上,乘着家人不覺,想找二娘來商量個方法,怎知走到她的房間,只見二娘釵橫鬚亂的倒在地上,旁邊放着個毒鼠藥的空瓶,心知不好了,發狂一樣轉身跑囘書房裏大聲喊道:
「老爺!不好了,二娘自殺!」
整個房裏的人都愕然,一齊叫出「吓——」一聲。
道德急問道:「在那裏自殺?」阿四道:「在她自己的房裡。」
道德聽見家裏又弄出第二件不幸的事,也不顧智全的事了,急忙走到二娘房裏,各人也一窩蜂似的跟了進去,看見二娘躺在地上,輾轉呻吟,道德忙叫家人把她移到床上,再對雷展雲説:「雷管家,你去叫個醫生來!」三娘將手搖了一搖,止住他説:「老爺,不要叫了,我是不成的,我⋯⋯⋯」喘得很急。道德握住她的手説:「二娘,究竟是什麼囘事?」二娘痛苦地喘着氣説,「老爺!我求你再別追究別人,事情都是我做出來的,我沒有面目再活下去了,我想害人,却害了自己,我⋯⋯⋯後悔自己心腸太窄,錯聽了⋯⋯⋯」
道德追問道:「錯聽了什麼?」
二娘斷續地説:「錯聽了阿四的話!」説完,經過一陣劇烈痛苦,也跟着她兒子走上一條路,氣絕死了。道德到這時,一切都明白了,平日所謂以禮義持家的他,到現在,知道一切偽善的掩蔽都撕破了。他放下二娘冰冷的手,嘆一口氣,站起來,痛心疾首的沉吟了一囘,又氣憤的叫道:
「該死,該死!阿四呢,叫她來,她敢這樣在家𥚃撥弄事非,非給她一點顏色看不可。」
他憤怒的在房間裏到處望了一望,連阿四的影子都沒有,家人們個個也不敢多説一句話,噤若寒蟬。獨有三娘藐起嘴唇,帶着譏諷的神氣説;
「哼!這樣惡毒心腸的女人,也應有這樣的報應了!」
「你不要再説這樣的話好罷?家裏一天死兩個人,還不苦够我嗎?你怎樣再可以來挖苦我?」道德痛苦地説。
三娘冷笑一聲,兩眼望住屋頂,也不再説什麼,但神色上都似乎在説:
「誰管得你呢!」
道德再生氣地對雷管家説:「你⋯⋯你⋯⋯替我去找阿四這壞女人來!我把他殺了!」
「是,是的!」雷展雲應着,正要出門去。婢女翠蓮却神色匆忙地跑進來,口裏叫:
「老爺,老爺,不好了,不好了!」
「吓!又出了什麼事?」唐道德吃一驚地問。
「阿四跳井尋死啦,我拉她也拉不住,已經死了。」翠蓮道。
「在什麼地方?」二小姐紫湘問道。
「是後花園水井裏!」翠蓮説。
道德接二連三的在一天𥚃發生這麼多不幸的事,幾乎剌激得站不住,長嘆一聲,用手拍拍前額,苦痛地説道:「唉!竟會攪到這樣,還成什麼樣子吶!」
(十三)
為了家庭中犬牙雀角之爭,互相傾軋,竟於一天之內,唐家弄出三宗人命案,這也可説是由於唐道德平日好事多為的結果,家雖然未散,而人却先亡了。
當時在塲的人,他們的感想一個個不同,唐道德身為家長,看着慘事發生,當然心裏極其難過。紫湘也看着家庭這樣崩潰下去,亦覺痛心疾首。雷展雲是個外人,可是從小就在這裡生長,平日也把唐家裡你爭我奪的事情,看在眼裏,早知終有一日會禍起蕭牆的,果然,不幸的結果就在今天發生了,事情固然不是偶然,亦可謂一定應有的結果,在他心裏覺得不勝浩嘆。
各人對於這事的發生,都有不幸之感,姑無論二娘在如何處心陰險,畢竟她現在是自吃果報,母子倆都死於非命了。這裏只有三娘和奸僕進祿兩人心𥚃暗覺痛快的,因為在他們兩人心中,認為二娘母子倆也是他們敵人之一,最低限度,二娘母子兩個人在,他們兩人不軌的行動會有被識破的危險。現在,對頭人不除自戮了,在他們兩人的心裏,是何等痛快呢!
道德這時眼見着自己的兒子和妾侍都死於非命了,痛苦地沉思一囘,抬頭向各人問:
「誰送那碗東西到書房的?」
小婢翠桃瑟縮地囘答道:「老⋯⋯爺⋯⋯送是我⋯⋯我的,不過究竟怎樣,我⋯⋯⋯可不知道了。」
「翠桃!」道德説;「你別怕,我要你説老實話,那碗東西曾經放在那𥚃?」
「沒⋯⋯沒有放在那裏⋯⋯⋯」翠桃非常驚慌地説,後來一忽兒想起了:「哦⋯⋯我記起了,我從廚房送東西出來的時候,先送到二娘這𥚃來,她叫我去取鹽,我便把東西放下來了,後來我不知道怎樣,老爺,我説的句句都是眞話!」説着,她撲通一聲跪下來了。
道德聽罷,頹然地坐在椅上,仰天長嘆一聲,説道:「我通通都明白了,原來就是二娘她自作自受,但是我也想不到她會這樣做出來!」
三娘冷言冷語地説道:
「哼!這樣的人什麼做不出來!她也狠毒透了,怎知會害到自己呢!」
道德沒有心情和她多説,只有頻頻的嘆氣。展雲怕道德太難過,走前去説:「老爺,你休息一會好嗎?」
「不,」道德説;「你們都出去吧!』
在展雲要出去的時候,道德又把他叫囘來,説:「雷管家,你來!」
展雲站定脚步,囘身問;「老爺,有什麼事嗎?」
道德説;「這件事不許任何一個人傳到外邊去,你去告訴下人們。」
「是的,老爺。」展雲説。
「還有呢,」道德説;「不要舉喪,免得傳到外邊去。」
「那末怎樣發葬呢?」展雲問。
「也不要發葬!」道德説。
「這,怎樣辦?」展雲莫名其妙地説。
「就叫家人們把他們三個人都葬在花園裏,不必做墳墓,棺材也不許從前門進來,總之,不要讓外邊知道一點,聽清楚了沒有?」道德説。
「知道了,老爺。」展雲説。
紫湘聽見要這樣埋葬二娘,大不以為然,説:「爸爸,二姐始終是我們家裏一個主婦,怎樣可以這樣殮葬她呢?」
「你怎樣知道,」道德説;「這件事傳出去,我的面子還要嗎?這樣丟臉的事,怎是我們這樣以禮持家的家庭容許發生的!所以,絕對不能對外邊洩露的。」
「是的,爸爸!」紫湘説。
於是唐家這件不幸的事,由於道德顧存偽善的面子,秘密掩盖住了。只由雷展雲到外邊買了三副薄棺囘來,草草把三個死者殮葬了,就叫家人埋在後花園裏,依着道德的説話,連墳堆也不砌起,葬成與地面一樣平坦,外邊的人,誰也不知道這裏葬着三個在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
事情像石塊投到水塘裡,起了一陣波紋,瞬息又平復了。沒人提起,也沒有人注意,除了唐家裏的人外,更沒有人知道。死去的人,就永遠被埋藏起來,也成了一件永遠不被人知曉的秘密。
(十四)
家裏發生了這件事以後,家裏不免有點異樣,無形中似乎冷落得多。假如有人問起二娘,道德就答復他;「她帶着孩子囘到娘家去了。」並且,道德更吩咐家人都對外邊都要這樣説,使外邊人一點都不知道。
不過,唐家裏面的氣氛比前顯然冷漠得多了,似乎一點生氣都沒有,下人們常常交頭接耳地窈窃私語,談論這件傳奇式的慘事。
大少爺智能後來當然也會知道這件事的,他不但不因家裏死去了三個人而悲哀,反而沾沾自喜,在他心目中,認為從此以後,他就是唐家裡唯一的承繼子,假若唐老頭子死了,不成問題全部家產就由自己一個人獨佔,這樣,他怎會不高興呢。
唐家因為這件事不幸的事而沉寂了一會,比起唐道德賀壽的時候,一冷一熱,眞有天壤之別。唐道德也為了這件不幸的事,使他增加了不少的悲哀,意志也似乎比較消沉的多了。可是,唐家是否就這樣消沉下去呢!不是的,所謂一波纔平,另一波又起,不上好久時候,唐家裏又像一池靜水,起了一陣不平凡的波紋了———
(十五)
那個老人就這樣坐在被標封了的唐家門前,生了青草的石階上,滔滔不絕對着他的小孫亞牛滔滔不絕的談起這些往事,説到這裏,老人歇了一歇,又乾咳了两聲。
「爺爺,從前在這裏,你是那個?」亞牛問。
「我嗎?」老人説:「我就是進福啦!因為我在家裏時間最久,所以一切的事情我都清楚。」
「那麼,」亞牛説:「二娘和那個三少爺,阿四三個人死了以後,就算事了嗎?後來又怎樣呢?」
「當然,」老人説;「還有誰來提起!不過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
「究竟是什麼囘事?」亞牛問道。
「以後發生的事更重要啦,而且,唐家也從此散了,屋也被封了,死的死去,走的也走了,唉!一個做着不道德勾當的人,那裏會有好結果呢?」
「事情怎樣呢?爺爺,説下去吧。」亞牛説。
「時間不早了,以後再談罷。」老人説。
「不,爺爺,我要你説下去,這些事很好聽呢,説下去罷!」孩子一定要老人説下去。
「好罷,好罷,那麼我就説給你聽!」老人仰起頭來,望着黑沉沉的天空,整個人又像陷入以往事情囘憶的境界裏了。
經過一囘沉靜,這裏只聽見一陣一陣風聲和秋虫和鳴的聲音,那小孩子亞牛用两隻小手托着下顎,等待着進福繼續説起唐家舊事。
又過了一囘,進福再説下去了,究竟他説出什麼事呢?唐家以後怎樣沒落,崩潰以至毁滅呢?在下邊就説明了。
